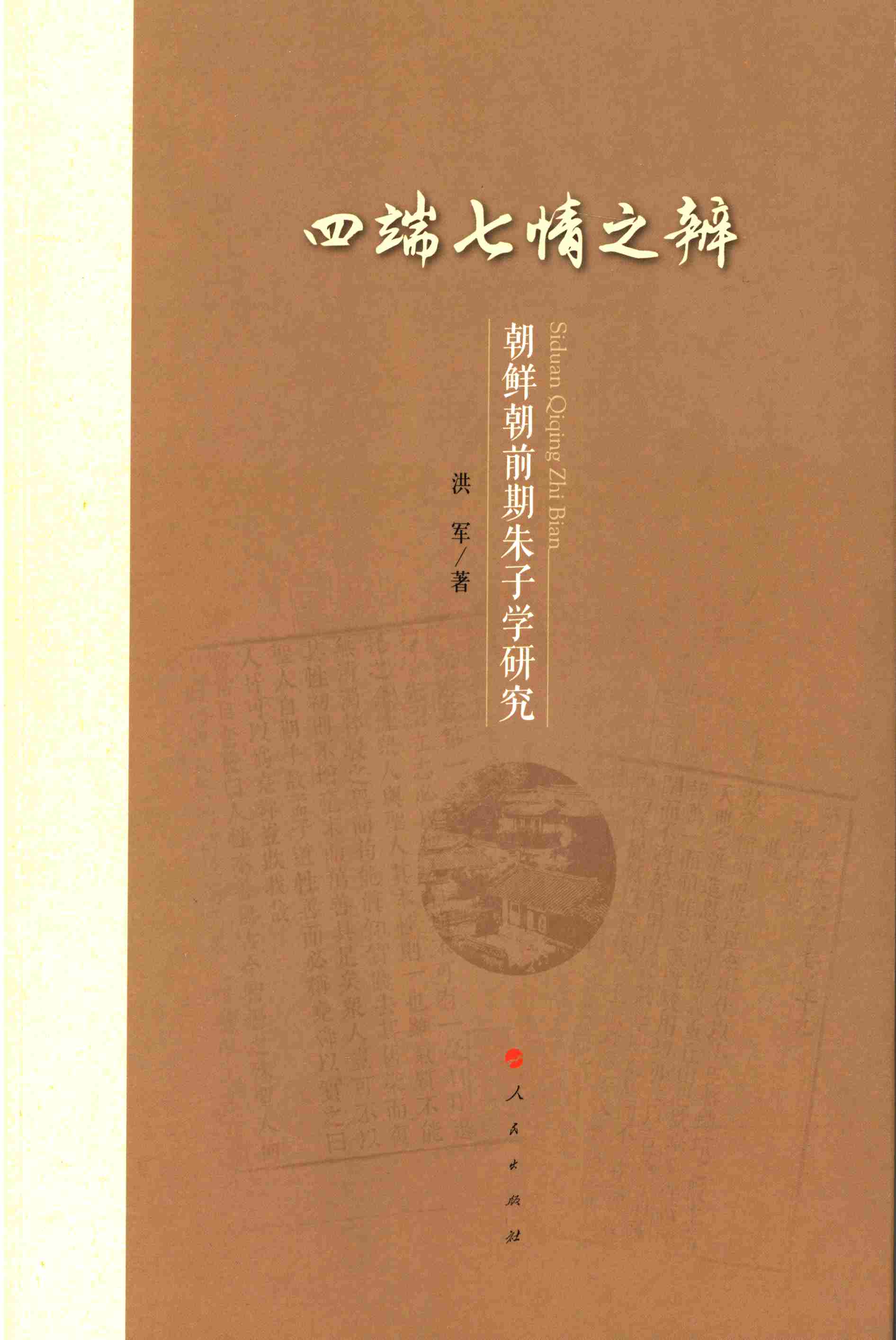内容
奇大升与李滉皆为李朝一代儒宗,二人的学说亦各具其理论特色。由上所述可知,奇大升的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理气观和性情论等方面。
首先,在理气观上奇大升主张理气的“混沦一体”性,但是亦不否认二者区别——所谓“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①奇氏说过: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
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③
他主张在二者的“不离”义上应持“合看”和“离看”的立场。“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④,因此要求学者于此当特别“精以察之”。依其“理无朕而气有迹”等观点来看,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奇大升论曰:“盖理无朕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⑤“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以及“非以理气为一物”等观点皆是奇氏理气论的重点所在,必须仔细玩味方能体会出其性理学说之特点。
他与李滉虽然在强调“理”的主宰性和理气不杂性方面取得了共识(二人皆承认理的“实在性”),但是在对理的作用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与奇氏不同,李滉十分重视“理”的能动性和发用性。李滉说过“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①。他还提出“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②的“理帅气卒”论。这是李滉在理气论方面的创见,也是其思想的特色所在。论者将此称为朱学的“死理向活理的转化”③。
在理气观方面奇氏的理论呈现的是“一元论”的倾向,而李滉的学说则体现了鲜明的“二元论”特色。
其次,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问题上,奇大升认为二者是“一本”和“万殊”的关系。奇氏论曰: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愚谓:天地之性,是就天地上总说;气质之性,是从人物禀受上说。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无碍”者乎?④
从援引的朱子语录中可以看出,奇氏实际上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理”与“分殊用之理”的关系。他以“天命之性”为本,而以“气质之性”为末。奇氏还曾引用朱子《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⑤可见,奇大升还将“天命之性”(理)视作“道之体”和“天下之大本”,而且认为天下之道理皆由此出。
但他又说:
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者……若就性上论,则所谓“气质之性”者,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然则论性,而曰“本性”、曰“气禀”云者,非如就天地及人物上,分理、气而各自为一物也,乃以一性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耳。至若论其情,则缘本性堕在气质,然后发而为情,故谓之“兼理气,有善恶”。而其发见之际,自有发于理者,亦有发于气者,虽分别言之,无所不可,而仔细秤停,则亦有似不能无碍。①依奇氏之见,“气质之性”(“万殊”之性)与“天命之性”(“一本”之性)实际上同为一性。之所以有“本性”、“气禀”之说乃因以“一性”之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换句话说,“气质之性”即指此“理”(“天命之性”)堕在气质之中者。“天命之性”要通过“气质之性”来得到具体呈现和实现,所以说在“气质之性”之外“非别有一性也”。
对“天命之性”与“四端”、“七情”的关系,奇大升认为“‘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②。在他看来,“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为“天命之性”、“本然之体”,与“四端”是同实而异名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是气禀物欲之所为,并非是性之本然。
与奇氏不同,李滉却以程朱的“二性说”为理论依据,提出自己的“性”论。“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在李滉看来,思、孟所言“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根据(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李滉主要是基于“四端”与“七情”在“所指”及“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的差别,提出“性”有本性、气禀之异。他坚持“二性论”的立场,强调“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的观点。进而又认为“性”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以分理气而言之。
简言之,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及“一本万殊”的理念主张“一性论”。他重视人的现实之性也就是所谓“气质之性”;与之不同,李滉依据理气二分及理气互发的思想,坚持其“二性论”的观点。
再次,在“四端”与“七情”关系方面,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以及“一性说”之立场,坚持独到的“七包四”(“因说”)的思想。在奇氏性理学的逻辑结构中,“四端”与“七情”是同构性的(“一情”)。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同实而异名”,所以在其看来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并无差异。
奇大升说过:
盖七情亦本善也,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恶矣……盖七情中善者,乃理之发,而与四端同实而异名者也。②
盖性虽本善,而堕于气质,则不无偏胜,故谓之“气质之性”。七情虽兼理、气,而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而易流于恶,故谓之“气之发”也。然其发而中节者,乃发于理,而无不善,则与四端初不异也。但四端只是理之发,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扩而充之,则学者于四端之发,可不体认以扩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气之发,而理之所发,或不能以宰乎气,气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则学者于七情之发,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义各有所以然者,学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则亦可以思过半矣。③
依其之见,七情亦本善,只因兼摄理气加之理弱气强,故易流于恶。但是,奇大升认为七情中善者(发而中节者),与发于理的四端是同实而异名。这里奇氏所提到的“发于理”一词常被视为经与李滉多次辩论后对李氏立场的妥协。其实不然,此处奇大升只是顺着孟子的四端说扩展开来讲而已①,并非向“四七理气互发”说的回归。在其理气论中,理之本体被规定为“气之自然发见”,故其所言“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②。若奇氏“四七”说带有理发论的意味,肯定会遭到后来李珥等人的批判。但是李珥只对李滉的理发论展开批驳,而对奇氏之说则每持接续之姿态。
因此,“四端”与“七情”为“一情”还是“二情”的问题上,奇氏始终坚定地抱持二者为“一情”的立场。奇大升说过:
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③
大升前者妄以鄙见撰说一篇。当时以为子思就情上,以兼理气、有善恶者,而浑沦言之,故谓之“道其全”;孟子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言之,故谓之“剔拨出来”。然则均是情也,而曰“四端”、曰“七情”者,岂非以所就而言之者不同,而实则非有二情也。④
如前所述,奇氏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和四端无别,因而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同具价值之善。在他看来,四端、七情之别就在于“所就而言”之者的不同之故。孟子所谓四端是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剔拨言之,子思所谓七情则是就情上“兼理气、有善恶者(道其全)”浑沦言之——其实人之情是“一”而已矣。“剔拨论”是奇大升在“四七”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理论观点。
李滉则基于其“理气二分”和“二性论”的立场,主张将四端与七情“对举互言”——奇氏将其理气互发说称为“对说”。
李滉在答奇氏对于其“四端七情”论的质疑时,从“所就而言”的视角写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他也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但同时又认为以理气分言“四七”之发的说法前所未见。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来探讨的研究范式始自韩国儒者。依李滉之见,尽管理与气在具体生成事物的过程中“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具有不可分离性,但是不能将四端和七情“滚合为一说”。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应分别以言之。
李滉进而又从“所指”的视角论述道:
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①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认为情之有“四七”之分犹如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他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微妙的关系,以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源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主于理,一主于气。之所以有此分别乃因“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李滉说过:“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②二者各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他主张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这一观点虽经几次修正,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概而言之,在持续8年之久的往复论辩中,因所持的立场角度及所仰重的诠释文本上的差异,③双方始终无法在见解上达成一致。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主张“一性论”和“一情说”,而李滉则依止“理气二分”的思想强调“二性论”和“二情说”。
奇氏以为四端与七情皆可视为情的一种善恶性质,不能将二者看作性质有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情,也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更为贴近朱学原论。但是李滉却从“理气二分”和“尊理”的立场出发,强调二者的异质性亦即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不同。退溪十分关注道德行为的源起,而奇氏则更留意流行层面已发之情的中节问题,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等篇中就多有对中节问题的论述。奇大升和李滉皆为一代儒学名宿,二人的论辩虽未达成共识,却给后人提供了广阔的哲学思辨的空间。
他们所开启的“四七理气”之辨,后为李珥、成浑等人进一步扩展为“四七人心道心”之辨。
李珥曾这样评价奇氏的“四七”理论:“余在江陵,览奇明彦与退溪论四端七情书。退溪则以为‘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明彦则以为四端七情元非二情,七情中之发于理者为四端耳。往复万余言,终不相合。余曰,明彦之论,正合我意。盖性中有仁义礼智信,情中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如斯而已。五常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七情中之不杂人欲,粹然出于天理者,是四端也。”①这表明李珥的思想与奇大升一脉相承,亦持“四端七情非二”之立场。他又提道:“退溪与奇明彦论四七之说,无虑万余言。明彦之论,则分明直截,势如破竹。退溪则辨说虽详,而义理不明,反复咀嚼,卒无的实之滋味。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乎,只是有个才智,偶于此处见得到耳。窃详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为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做出许多葛藤。每读之,未尝不慨叹,以为正见之一累也。”②李珥对“四端七情”之辨中双方的学说皆有透彻之领悟。像“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的说法确为李滉四七论的要害所在。但他却支持奇氏的主张,盖因其追求的“明德之实效,新民之实迹”③的务实精神与高峰之学更为合拍。
由此可见,奇大升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退溪李滉在与其辩论中逐步确立了其“四七理气互发”说的立场,由此奠定了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栗谷李珥则在奇氏与李滉辩论中同情前者之立场,并将之发扬光大以为“气发理乘一途”说,从而奠定了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
首先,在理气观上奇大升主张理气的“混沦一体”性,但是亦不否认二者区别——所谓“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①奇氏说过: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
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③
他主张在二者的“不离”义上应持“合看”和“离看”的立场。“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④,因此要求学者于此当特别“精以察之”。依其“理无朕而气有迹”等观点来看,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奇大升论曰:“盖理无朕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⑤“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以及“非以理气为一物”等观点皆是奇氏理气论的重点所在,必须仔细玩味方能体会出其性理学说之特点。
他与李滉虽然在强调“理”的主宰性和理气不杂性方面取得了共识(二人皆承认理的“实在性”),但是在对理的作用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与奇氏不同,李滉十分重视“理”的能动性和发用性。李滉说过“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①。他还提出“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②的“理帅气卒”论。这是李滉在理气论方面的创见,也是其思想的特色所在。论者将此称为朱学的“死理向活理的转化”③。
在理气观方面奇氏的理论呈现的是“一元论”的倾向,而李滉的学说则体现了鲜明的“二元论”特色。
其次,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问题上,奇大升认为二者是“一本”和“万殊”的关系。奇氏论曰: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愚谓:天地之性,是就天地上总说;气质之性,是从人物禀受上说。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无碍”者乎?④
从援引的朱子语录中可以看出,奇氏实际上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理”与“分殊用之理”的关系。他以“天命之性”为本,而以“气质之性”为末。奇氏还曾引用朱子《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⑤可见,奇大升还将“天命之性”(理)视作“道之体”和“天下之大本”,而且认为天下之道理皆由此出。
但他又说:
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者……若就性上论,则所谓“气质之性”者,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然则论性,而曰“本性”、曰“气禀”云者,非如就天地及人物上,分理、气而各自为一物也,乃以一性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耳。至若论其情,则缘本性堕在气质,然后发而为情,故谓之“兼理气,有善恶”。而其发见之际,自有发于理者,亦有发于气者,虽分别言之,无所不可,而仔细秤停,则亦有似不能无碍。①依奇氏之见,“气质之性”(“万殊”之性)与“天命之性”(“一本”之性)实际上同为一性。之所以有“本性”、“气禀”之说乃因以“一性”之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换句话说,“气质之性”即指此“理”(“天命之性”)堕在气质之中者。“天命之性”要通过“气质之性”来得到具体呈现和实现,所以说在“气质之性”之外“非别有一性也”。
对“天命之性”与“四端”、“七情”的关系,奇大升认为“‘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②。在他看来,“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为“天命之性”、“本然之体”,与“四端”是同实而异名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是气禀物欲之所为,并非是性之本然。
与奇氏不同,李滉却以程朱的“二性说”为理论依据,提出自己的“性”论。“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在李滉看来,思、孟所言“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根据(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李滉主要是基于“四端”与“七情”在“所指”及“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的差别,提出“性”有本性、气禀之异。他坚持“二性论”的立场,强调“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的观点。进而又认为“性”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以分理气而言之。
简言之,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及“一本万殊”的理念主张“一性论”。他重视人的现实之性也就是所谓“气质之性”;与之不同,李滉依据理气二分及理气互发的思想,坚持其“二性论”的观点。
再次,在“四端”与“七情”关系方面,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以及“一性说”之立场,坚持独到的“七包四”(“因说”)的思想。在奇氏性理学的逻辑结构中,“四端”与“七情”是同构性的(“一情”)。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同实而异名”,所以在其看来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并无差异。
奇大升说过:
盖七情亦本善也,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恶矣……盖七情中善者,乃理之发,而与四端同实而异名者也。②
盖性虽本善,而堕于气质,则不无偏胜,故谓之“气质之性”。七情虽兼理、气,而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而易流于恶,故谓之“气之发”也。然其发而中节者,乃发于理,而无不善,则与四端初不异也。但四端只是理之发,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扩而充之,则学者于四端之发,可不体认以扩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气之发,而理之所发,或不能以宰乎气,气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则学者于七情之发,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义各有所以然者,学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则亦可以思过半矣。③
依其之见,七情亦本善,只因兼摄理气加之理弱气强,故易流于恶。但是,奇大升认为七情中善者(发而中节者),与发于理的四端是同实而异名。这里奇氏所提到的“发于理”一词常被视为经与李滉多次辩论后对李氏立场的妥协。其实不然,此处奇大升只是顺着孟子的四端说扩展开来讲而已①,并非向“四七理气互发”说的回归。在其理气论中,理之本体被规定为“气之自然发见”,故其所言“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②。若奇氏“四七”说带有理发论的意味,肯定会遭到后来李珥等人的批判。但是李珥只对李滉的理发论展开批驳,而对奇氏之说则每持接续之姿态。
因此,“四端”与“七情”为“一情”还是“二情”的问题上,奇氏始终坚定地抱持二者为“一情”的立场。奇大升说过:
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③
大升前者妄以鄙见撰说一篇。当时以为子思就情上,以兼理气、有善恶者,而浑沦言之,故谓之“道其全”;孟子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言之,故谓之“剔拨出来”。然则均是情也,而曰“四端”、曰“七情”者,岂非以所就而言之者不同,而实则非有二情也。④
如前所述,奇氏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和四端无别,因而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同具价值之善。在他看来,四端、七情之别就在于“所就而言”之者的不同之故。孟子所谓四端是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剔拨言之,子思所谓七情则是就情上“兼理气、有善恶者(道其全)”浑沦言之——其实人之情是“一”而已矣。“剔拨论”是奇大升在“四七”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理论观点。
李滉则基于其“理气二分”和“二性论”的立场,主张将四端与七情“对举互言”——奇氏将其理气互发说称为“对说”。
李滉在答奇氏对于其“四端七情”论的质疑时,从“所就而言”的视角写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他也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但同时又认为以理气分言“四七”之发的说法前所未见。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来探讨的研究范式始自韩国儒者。依李滉之见,尽管理与气在具体生成事物的过程中“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具有不可分离性,但是不能将四端和七情“滚合为一说”。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应分别以言之。
李滉进而又从“所指”的视角论述道:
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①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认为情之有“四七”之分犹如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他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微妙的关系,以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源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主于理,一主于气。之所以有此分别乃因“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李滉说过:“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②二者各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他主张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这一观点虽经几次修正,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概而言之,在持续8年之久的往复论辩中,因所持的立场角度及所仰重的诠释文本上的差异,③双方始终无法在见解上达成一致。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主张“一性论”和“一情说”,而李滉则依止“理气二分”的思想强调“二性论”和“二情说”。
奇氏以为四端与七情皆可视为情的一种善恶性质,不能将二者看作性质有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情,也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更为贴近朱学原论。但是李滉却从“理气二分”和“尊理”的立场出发,强调二者的异质性亦即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不同。退溪十分关注道德行为的源起,而奇氏则更留意流行层面已发之情的中节问题,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等篇中就多有对中节问题的论述。奇大升和李滉皆为一代儒学名宿,二人的论辩虽未达成共识,却给后人提供了广阔的哲学思辨的空间。
他们所开启的“四七理气”之辨,后为李珥、成浑等人进一步扩展为“四七人心道心”之辨。
李珥曾这样评价奇氏的“四七”理论:“余在江陵,览奇明彦与退溪论四端七情书。退溪则以为‘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明彦则以为四端七情元非二情,七情中之发于理者为四端耳。往复万余言,终不相合。余曰,明彦之论,正合我意。盖性中有仁义礼智信,情中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如斯而已。五常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七情中之不杂人欲,粹然出于天理者,是四端也。”①这表明李珥的思想与奇大升一脉相承,亦持“四端七情非二”之立场。他又提道:“退溪与奇明彦论四七之说,无虑万余言。明彦之论,则分明直截,势如破竹。退溪则辨说虽详,而义理不明,反复咀嚼,卒无的实之滋味。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乎,只是有个才智,偶于此处见得到耳。窃详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为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做出许多葛藤。每读之,未尝不慨叹,以为正见之一累也。”②李珥对“四端七情”之辨中双方的学说皆有透彻之领悟。像“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的说法确为李滉四七论的要害所在。但他却支持奇氏的主张,盖因其追求的“明德之实效,新民之实迹”③的务实精神与高峰之学更为合拍。
由此可见,奇大升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退溪李滉在与其辩论中逐步确立了其“四七理气互发”说的立场,由此奠定了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栗谷李珥则在奇氏与李滉辩论中同情前者之立场,并将之发扬光大以为“气发理乘一途”说,从而奠定了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