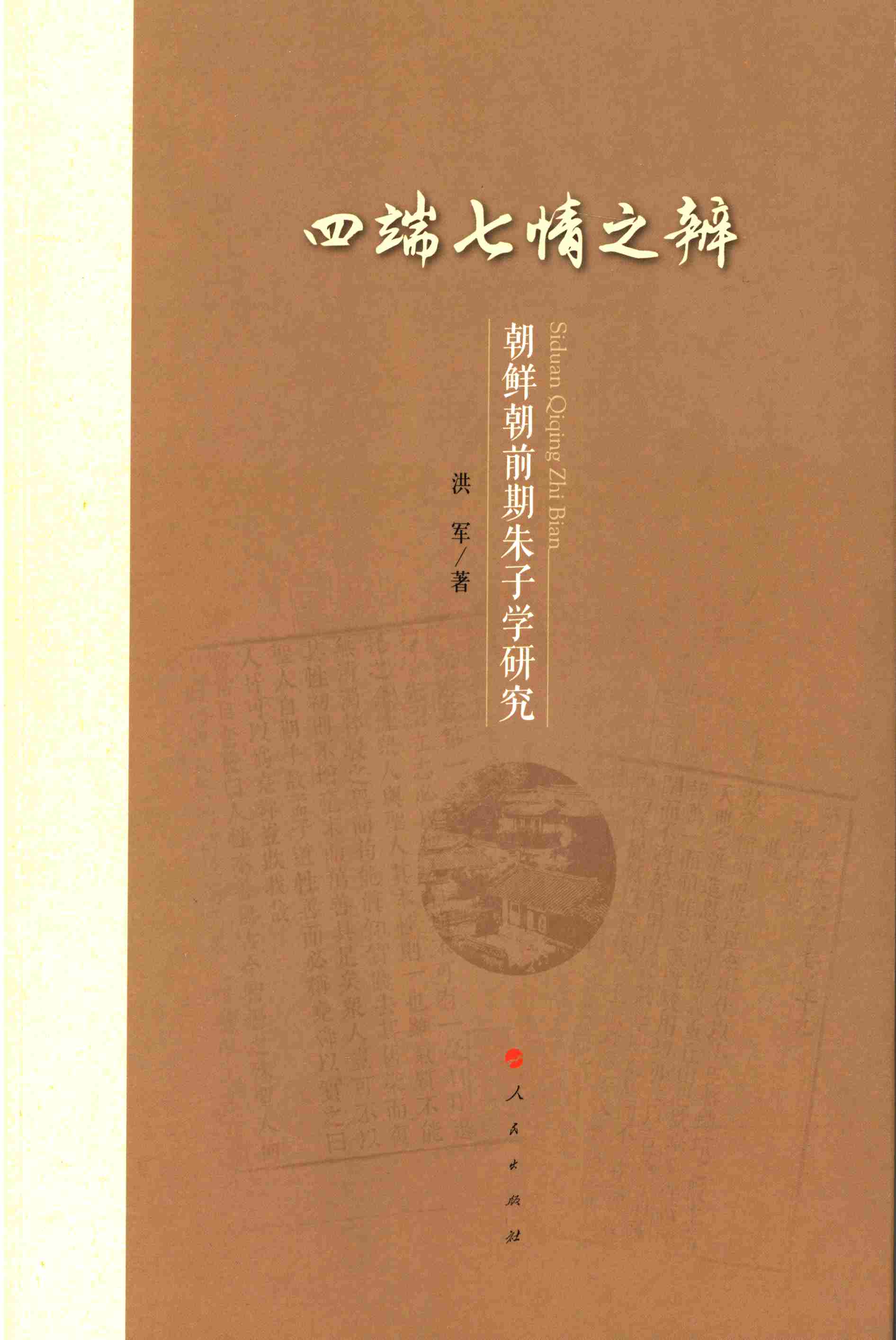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与李滉“四七”论之比较为中心
| 内容出处: | 《四端七情之辨》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9049 |
| 颗粒名称: | 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与李滉“四七”论之比较为中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4 |
| 页码: | 143-15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奇大升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持批判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剔拨论”主张。他认为“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但二者并非不同性质的情,而是在情所指及所偏重方面有所不同。奇大升强调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的观点,主张将“四端”和“七情”分别言之。李滉提出了对奇氏的回应,认为二者可以分理气而言,因“四端”和“七情”在来源和所主所重方面存在差异。 |
| 关键词: | 奇大升 李滉 四七理气 |
内容
在四端七情①以及理气问题上,奇氏基于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
明宗十四年(1559年)一月,李滉曾致书奇大升,提到“又因士友间传闻所论四端七情之说,鄙意亦尝自病其下语之未稳。逮得砭驳,益知疏缪,即改之云:‘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未知如此下语,无病否?”②就自己对“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所做的表述征求了奇氏的意见。
是年三月,奇大升撰《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他将书寄赠李滉,此书即为奇大升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其中写道:“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说也,而先儒发明尽矣。然窃尝致之,子思之言,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论,所谓剔拨出来者也。盖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而性无不善,情则有善恶,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③奇大升以为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别乃因子思、孟子等先圣“所就以言之者”不同之故,也就是二者在情之所指及所偏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情”只有一种,而“四端”和“七情”所指的对象却有所不同——一指全体,一指其中之部分,二者并不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情。已发之情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心是否依性理而为主宰。性是形上之理,情则是形下之气。理气不离——理不能独自发用,必因气之发而显理之意义。奇氏以为若依李滉之说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两边,则会使人认为理发时无气之作用,而气发时无理作根据。这是不合于程朱学理气“不离”之义。①奇大升指出,子思所说的“情”是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所论的“情”则是所谓“剔拨”②出来者。故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若谓“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便如同将理与气判而为两物,也就无异于认为“七情”不发于性、“四端”不乘于气。这就是奇氏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所持的“剔拨论”主张。
在奇大升而言,将“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一句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③,虽似稍胜于前说但终究在语意上仍有所未安。
盖性之乍发,气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谓“四端”者也。此固纯是天理所发,然非能出于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也。然则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兼气”,可乎?论人心、道心,则或可如此说;若四端、七情,则恐不得如此说,盖七情不可专以人心观也。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④
奇氏所言“四端”为本然之善(“良知”)得以直遂者即指“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因此他以为,“人心”、“道心”或可以理气分言,但是“四端”、“七情”却不宜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或“兼气”。奇大升进而指出所谓“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而所谓“恶”者则为“气禀之过不及”。于此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奇氏的基本见解可概括为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因此七情之发或善或恶,“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者。而且,他还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初非有二义,二者只是不同性质的(如“善”的或“恶”的)“情”而已。奇氏又进一步论道曰:“近来学者,不察孟子就善一边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别而论之,愚窃病焉。朱子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及论性情之际,则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盖恐人之不晓,而以气言性也。然学者须知理之不外于气,而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乃理之本体然也,而用其力焉,则庶乎其不差矣。”①奇大升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主张被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论。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其“理气兼发”或“理气共发”说中的“理”是否具“发用义”?依奇氏之见,“理之本体”为“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若以此推之自然得出“四端”为“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的结论。而且因其力主“理”的“不外于气”之特性,故其“四七理气”论可以表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说。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其“四七理气”之发论中发之者是“气”而不是“理”,“理”只具“主宰义”。这也正是奇大升和罗钦顺虽皆主理气二者“混沦一体”,前者却极力批判后者“认气为理”的主要原因。在罗钦顺的理气论中,理因不具“主宰义”弱化了自身的“实体性”——这对于谨遵传统程朱之旨的奇大升而言无异于离经叛道。
以上便是奇大升就“四七理气”问题致李滉的第一封书信中的主要内容。奇氏在信中着重阐述了其对“四端”和“七情”的理解以及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见解。
对于奇氏来函中的问难,李滉撰写了《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文章从以下几个角度作了认真的回应。首先,他肯定了奇大升对于“四端”和“七情”的区别。“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故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③在李滉看来,理与气是“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这表明他虽然承认理气二者不可分离,但是基于“四端”和“七情”“所就而言之”的差异而有种种分别。这是李滉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其次,李滉从程朱“二性论”的角度对“四七”说进行了阐发。“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子思、孟子所讲的“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与“气质之性”不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性(天之所与我者),即非由外铄的“我固有之”者。在此李滉则基于“四端”与“七情”各自的“所从来”之异(在源起上存在的差异),主张因“性”有本性、气禀之异,故“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性”可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分理气而言之。
再次,李滉又从四端七情的“所主”与“所重”之不同,力主二者皆可以分理气来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四端,皆善也。故曰:‘无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七情,善恶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则心已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谓之‘和’。由是观之,二者虽曰皆不外乎理、气,而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则谓之某为理,某为气,何不可之有乎。”①李滉也以为虽然“四端”与“七情”皆来自于理气,但是因其在“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之义上各有“所主”与“所重”,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四端”为发于内者,即仁义礼智之性的直接发用;“七情”则为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者,即人之形气感官因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四端”所主的是“理”,“七情”所重的是“气”。因此李滉主张“四端”和“七情”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换句话说,他力辩二者之区别的目的在于强调其在善恶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职是之故,李滉认为奇氏为学之失在于“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他在信中写道:“今之所辩则异于是,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从来,概以为兼理气,有善恶,深以分别言之为不可;中间虽有‘理弱气强’、‘理无朕,气有迹’之云,至于其末,则乃以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是则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滉寻常未达其指,不谓来喻之意亦似之也。”②在他看来,奇氏在倡言“四端”是从“七情”中剔拨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说“四端、七情为无异”——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李滉进而直言“讲学而恶分析,务合为一说”乃古人所谓囫囵吞枣,其病不少——为学者若如此不已的话,就会不知不觉之间骎骎然入于以气论性之弊,而堕于认人欲作天理之患。
在此信的结尾处,他还援引朱熹之论为其主张申辩。“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李明辉先生认为朱子这句话在其义理系统中有明确的意涵,而其中两个“发”字的涵义并不相同:“理之发”的“发”意谓“理是四端的存有依据”;“气之发”的“发”则意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引发”,谓七情是由气之活动所引生。但是在朱子的系统中,既然理本身不活动,自不能说:四端是由理之活动所引发。故对朱子而言,理之“发”是虚说,气之“发”为实说。②这一论述对解读李滉、奇大升等人的“理发”、“气发”之说很有启发意义。“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③一语的确见于《朱子语类》,但朱子并未对之做进一步的阐发。
接到李滉复函后,奇大升随即撰写了第二封信也就是《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信中对李滉在文中的答复一一作了回应。于是,两人之间就有了第二次往复论辩。奇氏第二封信的内容分为12节,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奇大升还是强调自己的“情”观,认为人只有一种“情”。“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然而所谓‘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其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是故愚之前说,以为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者,正谓此也。又以为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者,亦谓此也。由是言之,以‘四端主于理,七情主于气’而云云者,其大纲虽同,而曲折亦有所不同者也。”①依其之见,情兼理气故有善恶。四端和七情之异源于“所就以言之不同”——七情之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与孟子所谓四端皆同实而异名;至于发而不中节者则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因此并非七情之外又有所谓四端者。
其次,奇氏以为不仅四端是性之所发,而且七情亦是性之所发。“来辩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此言甚当,正与朱子之言互相发明,愚意亦未尝不以为然也。然而朱子有曰:‘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以是观之,所谓‘四端是理之发’者,专指理言;所谓‘七情是气之发’者,以理与气杂而言之者也。而‘是理之发’云者,固不可易;‘是气之发’云者,非专指气也。”②他进而写道:“四端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七情亦发于仁义礼智之性也。不然,朱子何以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乎?又何以曰‘情是性之发’乎?”③理学先辈即主情为性之所发。奇大升肯定情有四端、七情之分,而四端和七情皆由性所发。
再次,奇氏又据理学人性论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原则,进一步指出不仅七情是理乘气而发,而且四端也是理乘气而发。他还直言“四端亦气”。“后来伏奉示喻,改之以‘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云云,则视前语尤分晓。而鄙意亦以为未安者,盖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揭之于图,或谓之‘无不善’,或谓之‘有善恶’,则人之见之也,疑若有两情,且虽不疑于两情,而亦疑其情中有二善,一发于理,一发于气者,为未当也。”④奇大升认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情中有“发于理”和“发于气”的两种善的说法难免令人困惑。这在奇大升看来显然是不妥的。依其之见,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便是“情”。故“情”皆出于心,并非仅源于外物触其形。“心”是理气之合,当其感于物而动之际发之者只能是“气”——四端和七情也不例外。“愚按:‘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句,出《好学论》。然考本文曰:‘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其曰‘动于中’,又曰‘其中动’云者,即心之感也。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焉,乃所谓‘情’也。然则情见乎外,虽似缘境而出,实则由中以出也。辩(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引者注)曰:‘四端之发,其端绪也。’愚谓:四端、七情,无非出于心者,而心乃理、气之合,则情固兼理、气也,非别有一情,但出于理,而不兼乎气也。此处正要人分别得真与妄尔。辩曰:‘七情之发,其苗脉也。’愚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朱子曰:‘性之欲,即所谓情也。’然则情之感物而动者,自然之理也。盖由其中间实有是理,故外边所感,便相契合;非其中间本无是理,而外物之来,偶相凑著而感动也。然则‘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一语,恐道七情不著也。若以感物而动言之,则四端亦然。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其感物者,与七情不异也。辩曰:‘安有在中,为理之本体耶?’愚谓:在中之时,固纯是天理,然此时只可谓之‘性’,不可谓之‘情’也。若才发,则便是情,而有和不和之异矣。盖未发,则专是理;既发,则便乘气以行也。朱子《元亨利贞说》曰:‘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又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①可见,奇大升在谈论四端和七情时特别强调心的感知与主宰作用。心为理气之合,故出于心的四端和七情必兼理气。他还说过若以生长收藏为情,便见乘气以行之实,而“四端亦气”也。
最后,奇氏还从价值论意义上就四端和七情的善恶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愚按程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然则四端固皆善也,而七情亦皆善也。惟其发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而为恶矣。岂有善恶未定者哉?今乃谓之‘善恶未定’,又谓之‘一有而不能察,则心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乃谓之和’,则是七情者,其为冗长无用,甚矣!而况发而未中节之前,亦将以何者而名之耶?且‘一有之而不能察’云者,乃《大学》第七章《章句》中语,其意盖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者,只要从无处发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也。《或问》所谓‘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蚩俯仰,因物赋形’者,乃是心之用也,岂遽有不得其正者哉?惟其事物之来,有所不察,应之既或不能无失,且又不能不与俱往,则其喜怒忧惧,必有动乎中,而始有不得其正耳。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证七情,殊不相似也。夫以来辩之说,反复剖析,不啻详矣,而质以圣贤之旨,其不同有如此者,则所谓‘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者,虽若可以拟议,而其实恐皆未当也。然则谓‘四端为理’、谓‘七情为气’云者,亦安得遽谓之无所不可哉?况此所辩,非但名言之际有所不可,抑恐其于性情之实、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也。”①他又说道:“夫以四端之情为发于理而无不善者,本因孟子所指而言之也。若泛就情上细论之,则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固不可皆谓之善也。有如寻常人,或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亦有是非其所不当是非者。盖理在气中,乘气以发见,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其流行之际,固宜有如此者,乌可以为情无有不善?又乌可以为四端无不善耶?此正学者精察之地,若不分真妄,而但以为无不善,则其认人欲而作天理者,必有不可胜言者矣。”②在奇大升看来,“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恶”者则是“气禀之过不及”。③但因理具有“不外于气”之特性,故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即为“理之本体”。而“理之本体”乃“天命之本然”亦即天赋之“善”者。于是,他认为四端和七情初非有此二义,皆仅是“情”的一种善恶性质而已。因此不能以理气来分言四端和七情。二者的区别只在性发为情之际,所发是否中节——其发而中节者,则无往而不善;其发而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者而为恶。基于此,奇氏以为不仅“七情亦皆善”,而且“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可见,他强调的是二者作为人类感情的同质性和同构性。依奇氏之见,二者的关系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而是七情包含四端(可简称为“七包四”)的关系。
李滉受到奇大升的进一步质疑。他在即接到奇氏《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之后就对其之前不够严谨的表述作了修正,并撰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信中李滉首先对奇氏四端亦是感物而动、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等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不过,对其将四端和七情视为“同实异名”的观点则给予了坚决反对。“公意以为:四端、七情皆兼理、气,同实异名,不可以分属理、气。滉意以为:就异中见其有同,故二者固多有浑沦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则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气之不同,分属何不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虽或有疵,而其宗旨则实有所从来。盛辩一皆诋斥,无片言只字之得完。今虽更有论说,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无益于取信,而徒得哓哓之过也。”①李滉主张对于二者既要异中见其有同,又要同中而知其有异。他还指出以“所就而言”,二者本自有主理、主气之“所主”的区别。由此,李滉提出了“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其详细内容摘录如下:
盖浑沦而言,则七情兼理、气,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著而感动也。且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但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②
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李滉坚守的是对二者各自不同的“所从来”与“所主”的“主理/主气”立场,如其所言“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至此,李滉大体已确立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可视为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最终定论。在此后与奇氏的往复论辩中,李滉对这一基本观点则再未作修正。
对于李滉的答复,奇大升提出了再质疑——遂有《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此信即为其《论四端七情》之第三书,作于1561年(明宗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年)。信中开头奇氏先对《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第一书》的《改本》作了评论,之后又对李滉的答复给予了逐条回应,最后还对《后论以虚为理之说》、《四端不中节之说》、《俚俗相传之语,非出于胡氏》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奇大升以其“因说”和“对说”①之理论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信中写道:
大升以为朱子谓“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者,非对说也,乃因说也。盖对说者,如说左右,是对待底;因说者,如说上下,便是因仍底。圣贤言语,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不可不察也。②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朱夫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③
朱子的“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是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的重要立论依据,所以奇氏特意对朱子的这一说法作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朱子此句是“因说”而非“对说”,是“纵说”而非“横说”。故不能以左右对待来理解。依其之见,圣贤之言“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所以后之学者对之需加以详察。
基于其“因说”之立场,奇大升又援引朱子对理气特性的论述并以此为据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异议。奇氏指出:
如第二条所谓“人之一身,理与气合而生,故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也。互发,则各有所主可知;相须,则互在其中可知”云云者,实乃受病之原,不可不深察也。夫理、气之际,知之固难,而言之亦难。前贤尚以为患,况后学乎?今欲粗述鄙见,仰其镌晓,而辞不契意,难于正说出来,姑以一事譬之。譬如日之在空也,其光景万古常新,虽云雾滃浡,而其光景非有所损,固自若也;但为云雾所蔽,故其阴晴之候,有难齐者尔。及其云消雾卷,则便得偏照下土,而其光景非有所加,亦自若也。理之在气,亦犹是焉。喜、怒、哀、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理,浑然在中者,乃其本体之真;而或为气禀物欲之所拘蔽,则理之本体,虽固自若,而其发见者,便有昏明、真妄之分焉。若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岂不犹日之偏照下土乎?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分据一心之内,迭出用事,而互为首从也。此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①
这是奇氏就李滉在《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之第二书中作答的内容提出的反驳意见。李滉以为,人之一身是由理与气和合而生,因理与气互在其中,故浑沦言之者固有之;又因各有所主,故分别言之亦无不可。对此奇大升以日照大地为喻指出,日光照射大地虽受云雾之影响,但是在空之日“其光景则万古常新”,无所加损。他认为,理之在气亦是如此,故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犹如日之偏照大地。若曰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的话,等于是“理”却具有了情意、计度、造作等特性——这显然有违于朱学之根本原理。依他之见,这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可见,奇氏同样忠于朱子之学,且以朱学为其立学之据的。
基于此,奇大升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委婉地提出己之修正意见,并主张对于“此等议论”不可草草下定论。
“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为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只有理发一边尔。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又未知于先生意如何?子思道其全时,固不用所从来之说,则孟子剔拨而说四端时,虽可谓之指理发一边,而若七情者,子思固已兼理、气言之矣。岂以孟子之言,而遽变为气一边乎?此等议论,恐未可遽以为定也。①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所理解的“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对之他极为自信,认为若在此之外更求“理之发”之义“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②。由此可见,奇大升和李滉皆以朱子学说为据展开思想的攻防。
接到奇氏的《论四端七情》第三书后,李滉只是在来书中节录数段加以批示,并未再作答复——只向奇氏致以含有欲结束二人论辩之意的书函。或许在李滉看来,通过奇氏的三次来书和自己的两次答复已令双方充分了解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感到二人相互间很难说服对方,遂欲结束这场论辩。接到李滉来函后,奇大升又撰写了《四端七情后说》和《四端七情总论》寄赠李滉,此时已是1566年(明宗二十一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收到奇氏寄来的两书后,李滉只是简单作了回复,而对来书中的具体问题并未详加解答。他写道:“四端七情《总说》(应为《总论》——引者注)、《后说》两篇,议论极明快,无惹缠纷挐之病。眼目尽正当,能独观昭旷之原,亦能辨旧见之差于毫忽之微,顿改以从新意,此尤人所难者。甚善!甚善!所论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复致思于其间乎?兼前示人心道心等说,皆当反隅以求教。今兹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谨当一一。”③如引文所见,信中李滉仅就奇氏对“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的解释提出些异议,对来书之内容未作具体回复。这表明李滉已无意继续与奇氏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
这场开始于明宗十四年(1559年)1月的李滉《与奇明彦》一书的论辩,以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10月李滉作《答奇明彦》一书而告终。但是,双方的主要论点大都集中于奇大升上退溪的前三次书和李滉的前两次作答的书函中。尽管二人围绕四七理气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他们相互间的问学并未就此中断。宣祖昭敬王元年(1568年)7月奇氏就拜谒了奉王命入京的李滉,是年12月还与其一同讨论《圣学十图》。而且,次年(1569年)3月还将欲回安东陶山的李滉送至东湖,并同宿江墅。在东湖舟上,奇大升先寄一绝奉别李滉,朴和叔等继之。席上诸公,咸各赠言饯别李滉。奇氏诗曰:“江汉滔滔万古流,先生此去若为留。沙边拽缆迟徊处,不尽离肠万斛愁。”①李滉和韵:“列坐方舟尽胜流,归心终日为牵留。愿将汉水添行砚,写出临分无限愁。”②李滉临行,不能尽酬,谨用前二绝韵奉谢了诸公相送之厚意。不料,于东湖作别后的第二年,1570年(宣祖三年)12月李滉辞世。奇氏惊闻退溪李滉先生讣音,设位痛哭。翌年正月送吊祭于陶山,2月撰《退溪先生墓碣铭先生自铭并书》,赞其曰:“先生盛德大业,卓冠吾东者,当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后之学者,观于先生所论著,将必有感发默契焉者。而铭中所叙,尤足以想见其微意也。”③可见,奇大升和李滉虽然在为学和致思倾向上分歧明显,但是作为同道益友和直谅诤友,二人感情甚笃,在相互问学中共同推动了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明宗十四年(1559年)一月,李滉曾致书奇大升,提到“又因士友间传闻所论四端七情之说,鄙意亦尝自病其下语之未稳。逮得砭驳,益知疏缪,即改之云:‘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未知如此下语,无病否?”②就自己对“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所做的表述征求了奇氏的意见。
是年三月,奇大升撰《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他将书寄赠李滉,此书即为奇大升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其中写道:“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说也,而先儒发明尽矣。然窃尝致之,子思之言,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论,所谓剔拨出来者也。盖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而性无不善,情则有善恶,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③奇大升以为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别乃因子思、孟子等先圣“所就以言之者”不同之故,也就是二者在情之所指及所偏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情”只有一种,而“四端”和“七情”所指的对象却有所不同——一指全体,一指其中之部分,二者并不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情。已发之情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心是否依性理而为主宰。性是形上之理,情则是形下之气。理气不离——理不能独自发用,必因气之发而显理之意义。奇氏以为若依李滉之说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两边,则会使人认为理发时无气之作用,而气发时无理作根据。这是不合于程朱学理气“不离”之义。①奇大升指出,子思所说的“情”是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所论的“情”则是所谓“剔拨”②出来者。故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若谓“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便如同将理与气判而为两物,也就无异于认为“七情”不发于性、“四端”不乘于气。这就是奇氏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所持的“剔拨论”主张。
在奇大升而言,将“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一句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③,虽似稍胜于前说但终究在语意上仍有所未安。
盖性之乍发,气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谓“四端”者也。此固纯是天理所发,然非能出于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也。然则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兼气”,可乎?论人心、道心,则或可如此说;若四端、七情,则恐不得如此说,盖七情不可专以人心观也。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④
奇氏所言“四端”为本然之善(“良知”)得以直遂者即指“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因此他以为,“人心”、“道心”或可以理气分言,但是“四端”、“七情”却不宜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或“兼气”。奇大升进而指出所谓“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而所谓“恶”者则为“气禀之过不及”。于此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奇氏的基本见解可概括为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因此七情之发或善或恶,“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者。而且,他还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初非有二义,二者只是不同性质的(如“善”的或“恶”的)“情”而已。奇氏又进一步论道曰:“近来学者,不察孟子就善一边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别而论之,愚窃病焉。朱子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及论性情之际,则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盖恐人之不晓,而以气言性也。然学者须知理之不外于气,而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乃理之本体然也,而用其力焉,则庶乎其不差矣。”①奇大升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主张被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论。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其“理气兼发”或“理气共发”说中的“理”是否具“发用义”?依奇氏之见,“理之本体”为“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若以此推之自然得出“四端”为“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的结论。而且因其力主“理”的“不外于气”之特性,故其“四七理气”论可以表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说。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其“四七理气”之发论中发之者是“气”而不是“理”,“理”只具“主宰义”。这也正是奇大升和罗钦顺虽皆主理气二者“混沦一体”,前者却极力批判后者“认气为理”的主要原因。在罗钦顺的理气论中,理因不具“主宰义”弱化了自身的“实体性”——这对于谨遵传统程朱之旨的奇大升而言无异于离经叛道。
以上便是奇大升就“四七理气”问题致李滉的第一封书信中的主要内容。奇氏在信中着重阐述了其对“四端”和“七情”的理解以及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见解。
对于奇氏来函中的问难,李滉撰写了《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文章从以下几个角度作了认真的回应。首先,他肯定了奇大升对于“四端”和“七情”的区别。“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故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③在李滉看来,理与气是“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这表明他虽然承认理气二者不可分离,但是基于“四端”和“七情”“所就而言之”的差异而有种种分别。这是李滉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其次,李滉从程朱“二性论”的角度对“四七”说进行了阐发。“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子思、孟子所讲的“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与“气质之性”不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性(天之所与我者),即非由外铄的“我固有之”者。在此李滉则基于“四端”与“七情”各自的“所从来”之异(在源起上存在的差异),主张因“性”有本性、气禀之异,故“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性”可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分理气而言之。
再次,李滉又从四端七情的“所主”与“所重”之不同,力主二者皆可以分理气来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四端,皆善也。故曰:‘无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七情,善恶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则心已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谓之‘和’。由是观之,二者虽曰皆不外乎理、气,而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则谓之某为理,某为气,何不可之有乎。”①李滉也以为虽然“四端”与“七情”皆来自于理气,但是因其在“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之义上各有“所主”与“所重”,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四端”为发于内者,即仁义礼智之性的直接发用;“七情”则为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者,即人之形气感官因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四端”所主的是“理”,“七情”所重的是“气”。因此李滉主张“四端”和“七情”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换句话说,他力辩二者之区别的目的在于强调其在善恶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职是之故,李滉认为奇氏为学之失在于“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他在信中写道:“今之所辩则异于是,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从来,概以为兼理气,有善恶,深以分别言之为不可;中间虽有‘理弱气强’、‘理无朕,气有迹’之云,至于其末,则乃以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是则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滉寻常未达其指,不谓来喻之意亦似之也。”②在他看来,奇氏在倡言“四端”是从“七情”中剔拨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说“四端、七情为无异”——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李滉进而直言“讲学而恶分析,务合为一说”乃古人所谓囫囵吞枣,其病不少——为学者若如此不已的话,就会不知不觉之间骎骎然入于以气论性之弊,而堕于认人欲作天理之患。
在此信的结尾处,他还援引朱熹之论为其主张申辩。“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李明辉先生认为朱子这句话在其义理系统中有明确的意涵,而其中两个“发”字的涵义并不相同:“理之发”的“发”意谓“理是四端的存有依据”;“气之发”的“发”则意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引发”,谓七情是由气之活动所引生。但是在朱子的系统中,既然理本身不活动,自不能说:四端是由理之活动所引发。故对朱子而言,理之“发”是虚说,气之“发”为实说。②这一论述对解读李滉、奇大升等人的“理发”、“气发”之说很有启发意义。“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③一语的确见于《朱子语类》,但朱子并未对之做进一步的阐发。
接到李滉复函后,奇大升随即撰写了第二封信也就是《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信中对李滉在文中的答复一一作了回应。于是,两人之间就有了第二次往复论辩。奇氏第二封信的内容分为12节,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奇大升还是强调自己的“情”观,认为人只有一种“情”。“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然而所谓‘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其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是故愚之前说,以为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者,正谓此也。又以为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者,亦谓此也。由是言之,以‘四端主于理,七情主于气’而云云者,其大纲虽同,而曲折亦有所不同者也。”①依其之见,情兼理气故有善恶。四端和七情之异源于“所就以言之不同”——七情之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与孟子所谓四端皆同实而异名;至于发而不中节者则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因此并非七情之外又有所谓四端者。
其次,奇氏以为不仅四端是性之所发,而且七情亦是性之所发。“来辩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此言甚当,正与朱子之言互相发明,愚意亦未尝不以为然也。然而朱子有曰:‘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以是观之,所谓‘四端是理之发’者,专指理言;所谓‘七情是气之发’者,以理与气杂而言之者也。而‘是理之发’云者,固不可易;‘是气之发’云者,非专指气也。”②他进而写道:“四端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七情亦发于仁义礼智之性也。不然,朱子何以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乎?又何以曰‘情是性之发’乎?”③理学先辈即主情为性之所发。奇大升肯定情有四端、七情之分,而四端和七情皆由性所发。
再次,奇氏又据理学人性论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原则,进一步指出不仅七情是理乘气而发,而且四端也是理乘气而发。他还直言“四端亦气”。“后来伏奉示喻,改之以‘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云云,则视前语尤分晓。而鄙意亦以为未安者,盖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揭之于图,或谓之‘无不善’,或谓之‘有善恶’,则人之见之也,疑若有两情,且虽不疑于两情,而亦疑其情中有二善,一发于理,一发于气者,为未当也。”④奇大升认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情中有“发于理”和“发于气”的两种善的说法难免令人困惑。这在奇大升看来显然是不妥的。依其之见,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便是“情”。故“情”皆出于心,并非仅源于外物触其形。“心”是理气之合,当其感于物而动之际发之者只能是“气”——四端和七情也不例外。“愚按:‘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句,出《好学论》。然考本文曰:‘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其曰‘动于中’,又曰‘其中动’云者,即心之感也。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焉,乃所谓‘情’也。然则情见乎外,虽似缘境而出,实则由中以出也。辩(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引者注)曰:‘四端之发,其端绪也。’愚谓:四端、七情,无非出于心者,而心乃理、气之合,则情固兼理、气也,非别有一情,但出于理,而不兼乎气也。此处正要人分别得真与妄尔。辩曰:‘七情之发,其苗脉也。’愚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朱子曰:‘性之欲,即所谓情也。’然则情之感物而动者,自然之理也。盖由其中间实有是理,故外边所感,便相契合;非其中间本无是理,而外物之来,偶相凑著而感动也。然则‘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一语,恐道七情不著也。若以感物而动言之,则四端亦然。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其感物者,与七情不异也。辩曰:‘安有在中,为理之本体耶?’愚谓:在中之时,固纯是天理,然此时只可谓之‘性’,不可谓之‘情’也。若才发,则便是情,而有和不和之异矣。盖未发,则专是理;既发,则便乘气以行也。朱子《元亨利贞说》曰:‘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又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①可见,奇大升在谈论四端和七情时特别强调心的感知与主宰作用。心为理气之合,故出于心的四端和七情必兼理气。他还说过若以生长收藏为情,便见乘气以行之实,而“四端亦气”也。
最后,奇氏还从价值论意义上就四端和七情的善恶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愚按程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然则四端固皆善也,而七情亦皆善也。惟其发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而为恶矣。岂有善恶未定者哉?今乃谓之‘善恶未定’,又谓之‘一有而不能察,则心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乃谓之和’,则是七情者,其为冗长无用,甚矣!而况发而未中节之前,亦将以何者而名之耶?且‘一有之而不能察’云者,乃《大学》第七章《章句》中语,其意盖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者,只要从无处发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也。《或问》所谓‘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蚩俯仰,因物赋形’者,乃是心之用也,岂遽有不得其正者哉?惟其事物之来,有所不察,应之既或不能无失,且又不能不与俱往,则其喜怒忧惧,必有动乎中,而始有不得其正耳。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证七情,殊不相似也。夫以来辩之说,反复剖析,不啻详矣,而质以圣贤之旨,其不同有如此者,则所谓‘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者,虽若可以拟议,而其实恐皆未当也。然则谓‘四端为理’、谓‘七情为气’云者,亦安得遽谓之无所不可哉?况此所辩,非但名言之际有所不可,抑恐其于性情之实、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也。”①他又说道:“夫以四端之情为发于理而无不善者,本因孟子所指而言之也。若泛就情上细论之,则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固不可皆谓之善也。有如寻常人,或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亦有是非其所不当是非者。盖理在气中,乘气以发见,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其流行之际,固宜有如此者,乌可以为情无有不善?又乌可以为四端无不善耶?此正学者精察之地,若不分真妄,而但以为无不善,则其认人欲而作天理者,必有不可胜言者矣。”②在奇大升看来,“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恶”者则是“气禀之过不及”。③但因理具有“不外于气”之特性,故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即为“理之本体”。而“理之本体”乃“天命之本然”亦即天赋之“善”者。于是,他认为四端和七情初非有此二义,皆仅是“情”的一种善恶性质而已。因此不能以理气来分言四端和七情。二者的区别只在性发为情之际,所发是否中节——其发而中节者,则无往而不善;其发而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者而为恶。基于此,奇氏以为不仅“七情亦皆善”,而且“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可见,他强调的是二者作为人类感情的同质性和同构性。依奇氏之见,二者的关系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而是七情包含四端(可简称为“七包四”)的关系。
李滉受到奇大升的进一步质疑。他在即接到奇氏《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之后就对其之前不够严谨的表述作了修正,并撰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信中李滉首先对奇氏四端亦是感物而动、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等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不过,对其将四端和七情视为“同实异名”的观点则给予了坚决反对。“公意以为:四端、七情皆兼理、气,同实异名,不可以分属理、气。滉意以为:就异中见其有同,故二者固多有浑沦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则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气之不同,分属何不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虽或有疵,而其宗旨则实有所从来。盛辩一皆诋斥,无片言只字之得完。今虽更有论说,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无益于取信,而徒得哓哓之过也。”①李滉主张对于二者既要异中见其有同,又要同中而知其有异。他还指出以“所就而言”,二者本自有主理、主气之“所主”的区别。由此,李滉提出了“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其详细内容摘录如下:
盖浑沦而言,则七情兼理、气,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著而感动也。且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但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②
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李滉坚守的是对二者各自不同的“所从来”与“所主”的“主理/主气”立场,如其所言“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至此,李滉大体已确立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可视为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最终定论。在此后与奇氏的往复论辩中,李滉对这一基本观点则再未作修正。
对于李滉的答复,奇大升提出了再质疑——遂有《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此信即为其《论四端七情》之第三书,作于1561年(明宗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年)。信中开头奇氏先对《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第一书》的《改本》作了评论,之后又对李滉的答复给予了逐条回应,最后还对《后论以虚为理之说》、《四端不中节之说》、《俚俗相传之语,非出于胡氏》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奇大升以其“因说”和“对说”①之理论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信中写道:
大升以为朱子谓“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者,非对说也,乃因说也。盖对说者,如说左右,是对待底;因说者,如说上下,便是因仍底。圣贤言语,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不可不察也。②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朱夫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③
朱子的“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是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的重要立论依据,所以奇氏特意对朱子的这一说法作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朱子此句是“因说”而非“对说”,是“纵说”而非“横说”。故不能以左右对待来理解。依其之见,圣贤之言“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所以后之学者对之需加以详察。
基于其“因说”之立场,奇大升又援引朱子对理气特性的论述并以此为据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异议。奇氏指出:
如第二条所谓“人之一身,理与气合而生,故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也。互发,则各有所主可知;相须,则互在其中可知”云云者,实乃受病之原,不可不深察也。夫理、气之际,知之固难,而言之亦难。前贤尚以为患,况后学乎?今欲粗述鄙见,仰其镌晓,而辞不契意,难于正说出来,姑以一事譬之。譬如日之在空也,其光景万古常新,虽云雾滃浡,而其光景非有所损,固自若也;但为云雾所蔽,故其阴晴之候,有难齐者尔。及其云消雾卷,则便得偏照下土,而其光景非有所加,亦自若也。理之在气,亦犹是焉。喜、怒、哀、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理,浑然在中者,乃其本体之真;而或为气禀物欲之所拘蔽,则理之本体,虽固自若,而其发见者,便有昏明、真妄之分焉。若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岂不犹日之偏照下土乎?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分据一心之内,迭出用事,而互为首从也。此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①
这是奇氏就李滉在《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之第二书中作答的内容提出的反驳意见。李滉以为,人之一身是由理与气和合而生,因理与气互在其中,故浑沦言之者固有之;又因各有所主,故分别言之亦无不可。对此奇大升以日照大地为喻指出,日光照射大地虽受云雾之影响,但是在空之日“其光景则万古常新”,无所加损。他认为,理之在气亦是如此,故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犹如日之偏照大地。若曰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的话,等于是“理”却具有了情意、计度、造作等特性——这显然有违于朱学之根本原理。依他之见,这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可见,奇氏同样忠于朱子之学,且以朱学为其立学之据的。
基于此,奇大升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委婉地提出己之修正意见,并主张对于“此等议论”不可草草下定论。
“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为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只有理发一边尔。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又未知于先生意如何?子思道其全时,固不用所从来之说,则孟子剔拨而说四端时,虽可谓之指理发一边,而若七情者,子思固已兼理、气言之矣。岂以孟子之言,而遽变为气一边乎?此等议论,恐未可遽以为定也。①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所理解的“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对之他极为自信,认为若在此之外更求“理之发”之义“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②。由此可见,奇大升和李滉皆以朱子学说为据展开思想的攻防。
接到奇氏的《论四端七情》第三书后,李滉只是在来书中节录数段加以批示,并未再作答复——只向奇氏致以含有欲结束二人论辩之意的书函。或许在李滉看来,通过奇氏的三次来书和自己的两次答复已令双方充分了解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感到二人相互间很难说服对方,遂欲结束这场论辩。接到李滉来函后,奇大升又撰写了《四端七情后说》和《四端七情总论》寄赠李滉,此时已是1566年(明宗二十一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收到奇氏寄来的两书后,李滉只是简单作了回复,而对来书中的具体问题并未详加解答。他写道:“四端七情《总说》(应为《总论》——引者注)、《后说》两篇,议论极明快,无惹缠纷挐之病。眼目尽正当,能独观昭旷之原,亦能辨旧见之差于毫忽之微,顿改以从新意,此尤人所难者。甚善!甚善!所论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复致思于其间乎?兼前示人心道心等说,皆当反隅以求教。今兹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谨当一一。”③如引文所见,信中李滉仅就奇氏对“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的解释提出些异议,对来书之内容未作具体回复。这表明李滉已无意继续与奇氏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
这场开始于明宗十四年(1559年)1月的李滉《与奇明彦》一书的论辩,以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10月李滉作《答奇明彦》一书而告终。但是,双方的主要论点大都集中于奇大升上退溪的前三次书和李滉的前两次作答的书函中。尽管二人围绕四七理气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他们相互间的问学并未就此中断。宣祖昭敬王元年(1568年)7月奇氏就拜谒了奉王命入京的李滉,是年12月还与其一同讨论《圣学十图》。而且,次年(1569年)3月还将欲回安东陶山的李滉送至东湖,并同宿江墅。在东湖舟上,奇大升先寄一绝奉别李滉,朴和叔等继之。席上诸公,咸各赠言饯别李滉。奇氏诗曰:“江汉滔滔万古流,先生此去若为留。沙边拽缆迟徊处,不尽离肠万斛愁。”①李滉和韵:“列坐方舟尽胜流,归心终日为牵留。愿将汉水添行砚,写出临分无限愁。”②李滉临行,不能尽酬,谨用前二绝韵奉谢了诸公相送之厚意。不料,于东湖作别后的第二年,1570年(宣祖三年)12月李滉辞世。奇氏惊闻退溪李滉先生讣音,设位痛哭。翌年正月送吊祭于陶山,2月撰《退溪先生墓碣铭先生自铭并书》,赞其曰:“先生盛德大业,卓冠吾东者,当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后之学者,观于先生所论著,将必有感发默契焉者。而铭中所叙,尤足以想见其微意也。”③可见,奇大升和李滉虽然在为学和致思倾向上分歧明显,但是作为同道益友和直谅诤友,二人感情甚笃,在相互问学中共同推动了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