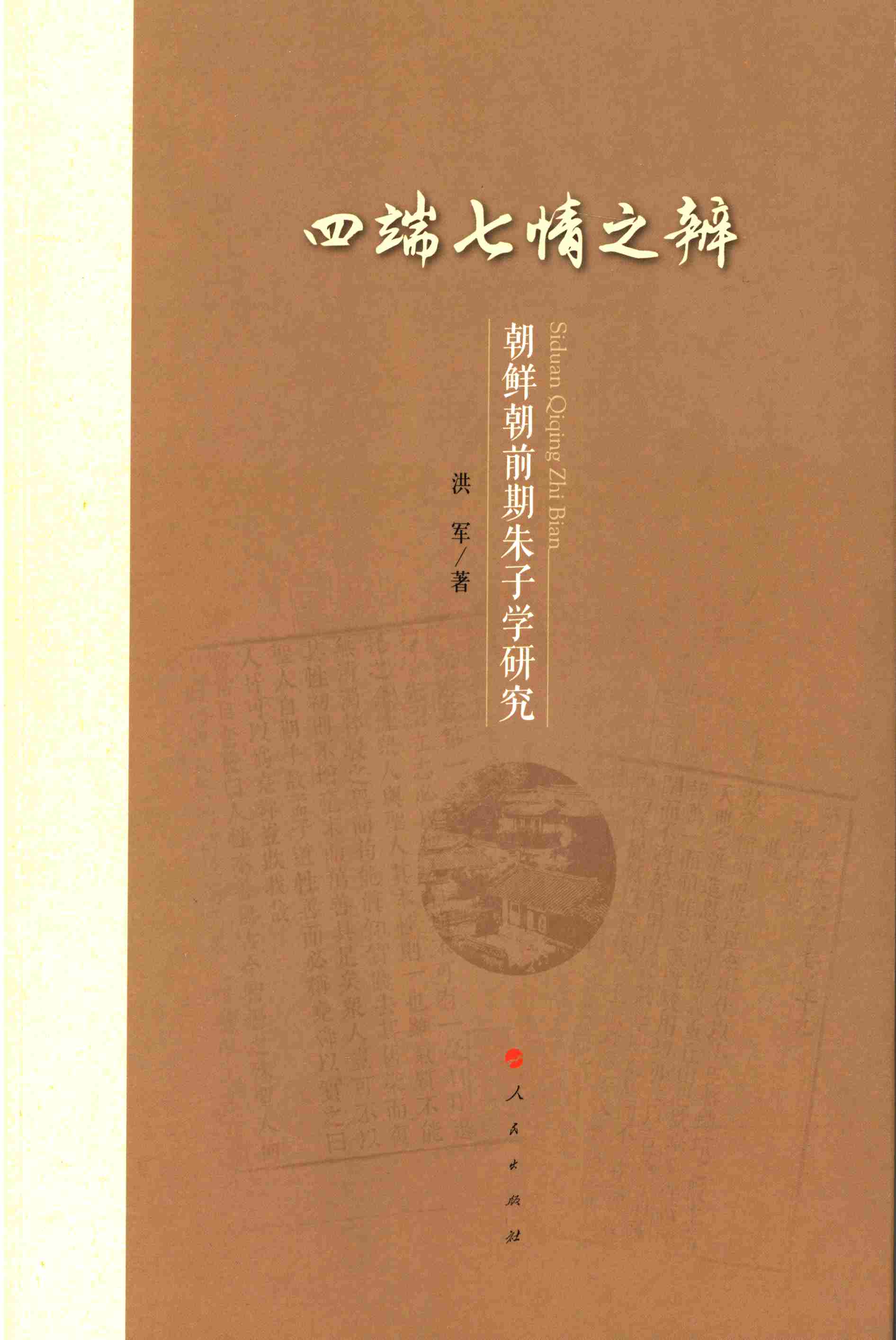第三节 奇大升与其“四端七情”论
内容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最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之特色。但是,他的四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与奇大升之间展开的相互问难。在与奇大升论辩过程中,不仅李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其立场也变得更加鲜明。本节将对奇大升“四七理气”论思想作一论述。
一、奇大升的理气论——兼述《论困知记》
奇大升(字名彦,号高峰、存斋)亦是朝鲜朝重要性理学家,生于中宗二十二年(1527年),卒于宣祖五年(1572年),谥号为文宪。他出生于全罗南道光州召古龙里松岘洞。③32岁中文科乙科第一人,后官至大司谏。奇氏天资聪敏,博览强记,长于论辩。33岁时便与李滉围绕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进行了长达8年的相互问难,由此拉开了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四七理气”论辩之帷幕。
理气问题是性理学的首要问题,奇大升亦十分重视此问题。他在信中写道:“然鄙意以为当于理气上,看得分明,然后心性情意,皆有着落,而四端七情,不难辩矣。后来诸先生之论,非不详且明矣。然质以思孟程朱之言,皆若异趣似于理气上未剖判也。”①依奇氏之见,若于理气问题上看得分明则心、性、情、意及四端七情诸说皆不难辩,故可将其理气说视为他的“四端七情”说的立论基础。于此也可以看出,他是追求理气说(存在论)与心性论相一致的性理学家。奇氏这一致思倾向与李珥有相似之处。下面将分析他的理气概念以及在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他用太极阴阳说规定了理气概念。“至于天地上分理气,则太极理也,阴阳气也。”②他以太极阴阳论定义理气的同时,将此贯彻到人和物上进一步指出:“就人物上分理气,则健顺五常理也,魂魄五脏气也。”③这表明奇氏以传统性理学形上、形下之理论来理解理气。
其次,在理气关系上,奇大升以理为气之主宰,以气为理之材料——强调理对气的主宰性乃其思想之特色。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④
理为气之主宰就意味着理对气之运动的主导作用。但他在强调理的主宰性的同时又指出理的脆弱性,即理无眹而气有迹。“理弱气强”似与理的主宰性相矛盾。其实这也是朱学理气论的困境所在,因为在朱子哲学中“理”就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⑤之“三无”特性。奇氏有言:“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①这是他在信中质疑李滉“理发”说的一段文字。如何化解本体义上理的主宰性与流行义上理的脆弱性矛盾以使气顺利而发?这是每位理学家都要面临的重要理论课题。欲分析奇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要从其理气关系的解读上着手。
再次,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奇氏强调二者的不离义,此即理气“混沦一体”说。但是在此问题上他又力主既要“合看”又要“离看”。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在奇大升看来,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③,因此学者于此应特别要“精以察之”。依其对理气的规定,理无眹而气有迹,故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他评论说:“盖理无眹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④非以理气为一物,而却“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奇氏的这一观点与明儒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47年)的理气为一物,“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的主张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罗整庵的《困知记》传入韩国后引起较大反响,有尊奉之者,也有批判之者。李滉和奇大升即属后者,二人皆撰文予以批判。李滉写了篇《非理气为一物辩证》,奇大升则写了篇《论困知记》。
《高峰集》中记载:“明学者罗钦顺,号整庵,作《困知记》以理气为一物,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为不然。若著‘所以’字,则便成二物云,又以‘道心为体,人心为用’。此书新出,而世之学者莫能辨其是非,或有深悦而笃信者。戊辰五月,大升以大司成,诣阙至玉堂与副提学臣卢守慎,共论《困知记》。守慎以整庵之言为至当,而无以议为。大升力辨其非曰,朱子以为道心源于性命之正,人心生于形气之私,固以理气分而言之矣。整庵认理为气,以理气为一物,故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种种新奇之说,皆从此出。何可背圣贤相传不可易之说,而从罗整庵之新奇乎?遂著困知记论以辨之。盖其正见,不眩于似是之非,而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反复纡余,光明俊伟粹然一出于正,此李滉所以敛袵者特深也。”①“戊辰五月”,即为宣祖元年(1568年)5月,时奇氏42岁。不过据其《年谱》记载,奇大升在明宗二十年(1565年)12月往见卢守慎(字寡悔,号苏斋,1515—1590年)于镇国院,并与之讨论了人心道心问题。②卢氏以罗整庵《困知记》的理论为依据论述了其对人道说的看法。可见,他的《论困知记》一书是在与卢守慎展开论辩过程中完成,也是其思想成熟期的著作。③此书对了解奇大升的理气性情学说特点以及《困知记》一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此文的开头奇氏写道:
罗整庵《困知记》,世多尊尚。余尝观其书,闳博精邃,顿挫变化,殆不可测其涯涘。试提大概则推尊孔孟程朱,为之宗主。援据《易》、《诗》、《书》、《礼》,以张其说,而又能躬探禅学而深斥之。其驰骋上下,抑扬予夺之际,可谓不遗余力矣。世俗悦其新奇,而不究其实,宜乎尊尚之也。然愚之浅见,窃尝以为,罗氏之学,实出于禅学,而改头换面,文以圣贤之语,乃诐淫邪遁之尤者。使孟子而复生,必当声罪致讨,以正人心,固不悠悠而已也。④
从引文中可以概见,《困知记》传入韩国之初作为“新奇”之说颇受世儒的尊尚。这与《困知记》在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罗钦顺为江西泰和人,生于宪宗成化元年,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父死服阙后起原官,嘉靖六年坚辞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之召,致仕居家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致之学。他与其时的名儒王阳明、湛若水及欧阳德等人皆有往复辩论①,是在朱学阵营中为数不多的能与心学分庭抗礼的大儒。他的著作有《整庵存稿》二十卷和《困知记》六卷,而其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困知记》一书中。但《困知记》问世后并未受到中国学界关注,而却在韩国引起不小的波澜。如引文内容所见,有尊尚者亦有排斥者。奇氏则直斥罗氏之学“实出于禅学”,即便是孟子复生亦必当声罪致讨以正人心。
他指出虽然罗氏的个别观点和圣贤之道也有相符之处,但是其大纲领大根本却与之相去不啻百千万里之远。他还举了罗氏《困知记》中的具体论点以说明其主张皆与圣贤本旨相违,舛错谬戾不须更辨。
《记》凡四卷,益以附录,无虑数万言。其间,岂无一二之几乎道,而其大纲领大根本,与圣贤相肯,不啻百千万里之远。则其学之邪正,为如何哉。其书所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及“理气为一物”及“良知非天理”云云者,皆与圣贤本旨,舛错谬戾此,不须更辨,而其出于禅学之实,则不可以不辨也。②
尽管奇大升也主张理气“混沦一体”说,但是与罗氏的“理气为一物”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看来,罗氏之学“其出于禅学之实,则不可以不辨”。罗钦顺的《困知记》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已难以确知,但是从奇氏这段文字中可推知,起初传至韩国的《困知记》并非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六卷《困知记》,而是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年)五月完成的4卷本——是年罗氏69岁。在《困知记》序中,他写道:“余才微而质鲁,志复凡近。早尝从事章句,不过为利禄谋尔。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虽已晚,然自谓苟能粗见大意,亦庶几无负此生。而官守拘牵,加之多病,工夫难得专一,间尝若有所见矣,既旬月或逾时,又疑而未定,如此者盖二十余年,其于钻研体究之功,亦可谓尽心焉耳矣。”①罗氏这部著作的写作前后历时二十多年。当完成“四续”时已是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五月,其时他年已82岁。全书由卷上、卷下、续卷上、续卷下、三续、四续共六卷和附录构成。奇氏文中所提及的“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理气为一物”及“良知非天理”等的确是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所阐述的理论主旨。罗氏在《困知记》开篇即讲:“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然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②又说:“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③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渐趋衰落,而陆王心学声势日隆。罗氏对此深以为忧,于是将辨明“心性之别”以批驳陆王的“良知即天理”说作为其历史使命。职是之故,罗氏立学极重“心性之辨”。他以为心性的关系是既不相离又不能相混的,二者之别甚是微妙。若于心性的分际区别上,稍不清晰,便真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由此他将“道心”与“人心”关系定义为体用关系,这就是其独特的“人心道心体用”说。
那么,被称为“朱学后劲”的罗氏学说为什么会受到同样遵奉朱学的韩儒李滉、奇大升等性理学家的批判呢?这主要是因于其“理气为一物”的思想和由此引申出的“人心道心体用”说。于此可见,至16世纪中韩两国朱子学的发展已各呈不同的义理旨趣,此与韩国性理学者与中国朱子学者所处的不同人文语境与各自所倚重的不同核心话题相关。对于这一问题,讨论李珥理气说时再做进一步分析。
奇大升以为,罗氏之所以提出“理气为一物”、“人心道心体用”说等主张是因其学源自禅学之故。故在《论困知记》一文中,他力图揭露罗氏学说“实出于禅学”的“真相”。于是,奇氏在文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与此相关的内容:
整庵自言“官京师,逢一老僧,闻‘庭前柏树’之话,精思达朝,揽衣将起,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云云,此则悟禅之证也。后官南雍,“潜玩圣贤之书,研磨体认,日复一日,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云云”,此则改头换面,文以圣贤之语之实也。此之分明招认,固不可掩。而又有其论道理处,尤显然而不可掩者焉。《记》上第五章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一,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用也,精微纯性之真也。释氏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故其为教,始则欲人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空即虚也。既则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觉即知觉也。觉性既得,则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神即灵也。凡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使其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识矣。顾乃自以为无上妙道,曾不知其终身,尚有寻不到处,乃敢驾其说,以误天下后世之人云云。”
以此一章观之,其学之出于禅学者,益无所遁矣。夫心之虚灵知觉,乃理气妙合,自然之妙,而其或有不能然者,特以气禀物欲之蔽,而失其正耳。人苟能操而存之,不为气禀物欲之所累,则其虚灵知觉之妙。固自若也,非如释氏之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然后心始虚也。又非如释子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然后心有知觉也。又非如释子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然后心可谓之神也。此与圣贤所论虚灵知觉者,同耶异耶?其亦不待辨而可知其非也。
且既曰:“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而继之曰:“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然则圣贤之论心,亦与释子无异致耶。“离诸相,契虚觉,而洞彻无方者”,乃释子之作弄精神,灭绝天理者也。今乃欲与圣贤之论心者,比而同之,其可乎,其不可乎。
又曰:“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可识。”夫欲适越而北其辕,终莫能幸而至焉。今乃欲据释子所见之及,而向上寻之,以识夫帝降之衷,吾恐其如北辕而适越,终身伥伥,竟无可至之日也。
整庵之学,初既悮禅,而后观圣贤之书以文之。故其言如此,殊不知儒释,道既不同,而立心亦异有如阴阳昼夜之相反,乌可据彼之见,而能为此之道乎。①
罗钦顺自述其一生孜孜求道,用心甚苦。先由禅学悟心之灵妙,后识吾儒性命之旨。年垂六十,才自认为有见于性命之真。②其学思历程中确有一个出入佛道的经历(早年由禅学而入),《明史》亦记载道:“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③罗氏从“佛在庭前拍树子”话头得悟后,始知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虽相似而实不同——释氏大抵有见于心而无见于性。他指出今之世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在罗氏看来,道之不明正由于此。由此而论,奇氏批驳钦顺之学“实出于禅学”一说似难成立。在《困知记》一书中罗氏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禅宗经典《楞伽经》以及达摩、宗杲等重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批判。连《明儒学案》也提到“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④其实,钦顺之学是建立于程朱的“理一分殊”说之上,罗氏曾说过:“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简而尽,约而无所不通,初不假于牵合安排,自确乎其不可易也。”⑤又说:“一旦于理一分殊四字有个悟处,反而验之身心,推而验之人人,又验之阴阳五行,又验之鸟兽草木,头头皆合。于是始涣然自信,而知二君子之言,断乎不我欺也。愚言及此,非以自多,盖尝屡见吾党所著书,有以‘性即理’为不然者,只为理字难明,往往为气字之所妨碍,才见得不合,便以先儒言说为不足信,殊不知工夫到后,虽欲添一个字,自是添不得也。”①可见罗氏之学大体是接续程朱而来,但是在理气观方面已与程朱有了较大不同。那么,为什么同尊朱子的奇大升与罗钦顺间会有如此大的理论分歧呢?这主要源于二人对“理”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并对其“理”的特性有不同的界定。奇氏力辩罗氏之学的“禅学之实”乃因二人的理气观差异甚大,所以他紧接着就对罗氏理气说与心性说不一致提出批评。奇大升对钦顺的理气观极为不满,批评亦较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内容。学者于此不可不察。
前面已论及,奇大升是追求理气论与心性论相合一的性理学家。于是,他对罗氏思想中的两论不一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佛氏“作用是性”之说,固认气为理,而以心论性也。整庵实见之差,实由于此。故理气一物之说,道心人心性情之云,亦皆因此而误焉。盖既以理气为一物,则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属理气。故其为说,必至于如是,而整庵之所自以为向上寻到者,亦不过于佛氏所见之外,知有理字。而其所谓理字者,亦不过于气上认其有节度处耳。整庵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者,正是此病也。虽其为说,张皇焜耀,开阖万端,而要其指归,终亦不出于此矣。
且整庵每自谓至当归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夫既以理气为一物矣,而又以体用为二物焉,并引“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以证体用之为二物。若曰:道是体神是用,而道与神为二物,则理气果一物乎?理气果一物,则道与神,又何以为二物乎?整庵又以心与性,为体用之二物,心与性,既是二物,与理气为一物之说,不亦矛盾之甚乎?②
奇氏认为钦顺之学有“认气为理”以及由此引生的“以心论性”之病。他进而指出,罗氏自以为向上寻到者,亦不过于佛氏所见之外知有一个“理”字。而其所谓“理”字者,亦不过于气上认其有节度处耳。所以奇大升直言,“整庵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者,正是此病也”。又指责说整庵每自谓至当归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既以理气为一物,则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属理气。”奇氏所要强调的是理学“体用一源”之原则,故指责罗钦顺“以心与性,为体用之二物,心与性,既是二物,与理气为一物之说,不亦矛盾之甚乎?”既然理气为一物,体用就不能析为二物。
在东亚儒学史上奇大升是最早具体指出罗氏学说之内在矛盾的学者。对于此不能“归一”性,被称为宋明理学殿军的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年)和《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1610—1695年)师生亦有评述。刘宗周指出:“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谓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不免抛自身之藏。”①黄宗羲则更直接指出:“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①当然,这是刘宗周与黄宗羲师弟基于心学之立场对罗氏之学作出的评判。但是,谨遵朱子之学的奇大升和秉持心学立场的刘、黄等人先后都对罗氏学说的自相矛盾提出批评。此一现象表明作为儒者他们皆以体用一源为共法,而其理论也因之具有相近的思想倾向。这无关各自的具体学术主张。就哲学体系的完整性而言,一个思想家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后者应为前者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有些当代学者因此十分肯定刘、黄二人对罗钦顺的批评。②当然也有人对刘、黄师弟对于罗氏学说的批评不以为然。③分歧的产生与朱子哲学特殊的义理架构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朱子哲学在存在论(理气论)意义上倾向理气二分(“不离不杂”)和以理为主的理本论;而在心性论意义上则偏于以性、情、心三分结构为义理间架的“心统性情”论。④陈来先生曾指出,以“心统性情”为代表的朱子心性论结构的表达并非“理/气”二分模式,而是“易/道/神”的模式。盖因心性系统乃一功能系统,而不是存在系统。因此黄宗羲等人以“天人未能合一”来批评朱子的理气论未能贯通到心性论,似与事实有悖。实际上在朱学中理气观念并非没有应用到“人”。朱子使用“性理/气质”来分析人的问题即与其理气观一脉相承。①陈来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对朱子“心”论的理解有帮助,而且对罗氏学说的不一致性以及韩国儒学“四七理气”之发问题的理解亦大有助益。
在论述权近、郑之云等人的性理学时已言及,韩国性理学者在探讨性理问题时皆热衷于追求“天人心性合一”——摄理气于心乃韩国性理学之特色。因此相较于中国朱子学的理气说,韩国性理学的理气说更多带有性情论色彩。韩国儒者借此以说明性情之辨以及性情之发等问题。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奇大升的“理气共发”说以及李珥的“气发理乘”说皆可从这一角度得到深入的理解。否则很难解释倡言“理发理动”②以及“太极自动静”③的李滉何以能被称为“东方之朱夫子”。
在《论困知记》文末,奇氏还批评了罗氏的“良知非天理”说。曰:
整庵又论良知非天理,而云“知能是人心之妙用,爱敬乃人心之天理”,然则天理在妙用之外,而妙用者无与于天理乎。夫天理之在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此心之所以统性情。而其未发者,寂也体也;其已发者,感也用也。然则爱敬者,为未发耶,已发耶。知能,虽皆心之用,而有真妄邪正之分,固不可皆指以为天理矣。若加一良字,则乃本然之善,岂非天理之发乎。今以爱敬为天理,而以良知为非天理,爱敬与良知果若是其不同耶。且以知能为心之妙用,而不察乎真妄邪正之实,则尤不可。佛氏之神通妙用,运水般柴之说,正坐不分其真妄,而皆以为妙用之失也。昔有问于胡文定公曰:“禅者,以枯槌竖拂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为用,用而不妙。须是动容周旋中礼,方始是妙用处。”以此而揆诸整庵之言,其是非得失亦可见矣。整庵尝论宗果,以为“直是会说,左来右去,神出鬼没,所以能耸动一世。”余以为整庵之状宗杲者,乃所以自状也。
噫,道丧学绝,世俗何尝知此意思。见余之论,必以为笑,不谓之狂,则谓之妄也。然余亦岂欲必信于世俗,而与哓哓者相竞。将以俟后来之君子尔,同志之士,幸相与谅之。①
从奇氏对罗整庵的批评中可见,他对罗氏的“良知非天理”说的理解上有些偏差。前面已论及,明中叶以后程朱之学渐显颓势,王学日渐兴盛。在此情形之下,罗氏愤而扛起朱学大旗,欲明“心性之辨”以批驳“良知非天理”说。他将此作为理论活动的首要任务。罗氏曰:“夫孔孟之绝学,至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尝认良知为天理也。以谓有物必有则,故学必先于格物。今以良知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此语见《传习录》。来书亦云:‘致其良知于日履之间,以达之天下。’),则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无乃不得于言乎(《雍语》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本体,岂可于事物上寻讨?’总是此见。)!”②可见罗氏倾向程朱的“性即理”,而非“心即理”。因此他认为“有物必有则,故学必先于格物”——“格物”即为克己之私的过程。依罗整庵之见,“良知为天理”的说法过分强调个体之慧悟,极易将艰苦的修养工夫化为简易的禅悟,这是学人需警惕的非常危险的理论动向。显而易见,罗氏所批“良知”是指阳明的“致良知”。而奇氏所理解之“良知”则为基于伊洛渊源的良知、良能,也就是本然之善。于此也可以窥出奇氏的心性说仍以程朱的心、性、情三分义理间架为基础。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并不同意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那么,应如何理解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呢?对此奇氏有如下表述:
喜同恶离,乐浑全厌剖析,乃末学之常累。然鄙意固未尝以是自安也,亦欲其一一剖析尔……又或问: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朱子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然,则气之自然发见,过不及者,岂非理之本体乎……至于极论其所以然,则乃以七情之发,为理之本体,又以气之自然发见者,亦非理之本体,则所谓发于理者于何而见之,而所谓发于气者,在理之外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失,不可不察也。罗整庵所论不曾见得,不知如何。若据此一句,则其误甚矣。若大升则固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也。①可见,奇大升主张的是基于“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的理气“混沦一体”说。他以为理气虽不可谓二物,但也不能视为一物,“若以为一物,则又无道器之分矣”②。因此在奇氏看来,罗整庵以理气为一物,“其见甚乖”③。其实,奇大升的“理气混沦”说与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理”作为“所以然”者的地位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牵涉到对“理”的主宰义的不同认识。奇氏强调理的主宰作用,所以不满“理气一物”论。“整庵则以理气为一物,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为不然。谓若着‘所以’字,则便成二物云云。”④但上一段引文中奇氏所言“罗整庵所论不曾见得,不知如何”一句则需做进一步商榷。此言出自奇大升回复李滉的“高峰第二书”中。据研究,奇氏大约是在戊午年(32岁)或己未年(33岁)已读到《困知记》,故与李滉开始“四七理气”论争之前很有可能已受《困知记》思想的影响。①而且,李滉将奇氏己未年“高峰第一书”中的“七情中四端”以及“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等观点,评为与整庵的“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②。由此可见其时李滉也认为奇氏思想受到罗氏学说的影响。而奇氏在第二封回信中自辩道“整庵所论不曾见得”,则不能不令后学对之生疑。奇氏的理气“混沦一体”说后被李珥继承发展,确立为极富主气论特色的“理气之妙”说。
李滉对罗钦顺亦有评价,曾说过“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③。他则谨依朱子在《答刘书文书》中所阐“理与气决是二物”说,对主气论学者的“理气非异物”之说进行了批评。
最后附上李滉的《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供学者参考。此文对理解李滉、罗钦顺以及奇大升三人理气论之间的差异有较大帮助。该文内容如下:
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又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今按:孔子、周子明言阴阳是太极所生,若曰理气本一物,则太极即是两仪,安有能生者乎?曰真曰精,以其二物,故曰妙合而凝。如其一物,宁有妙合而凝者乎?
明道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
今按,若理气果是一物,孔子何必以形而上下分道器,明道何必曰“须著如此说”乎?明道又以其不可离器而索道,故曰“器亦道”,非谓器即是道也;以其不能外道而有器,故曰“道亦器”,非谓道即是器也。(道器之分即理气之分,故引以为证。)
朱子《答刘书文书》曰:“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又曰:“须知未有此气,先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夹论。至论其偏体于物,无处不在,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莫不有是理焉。”(今按:理不囿于物,故能无物不在。)不当以气之精者为性,性之粗者为气也。(性即理也,故引以为证。)
今按: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又曰:“性虽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相夹杂。”不当以气之精者为性,性之粗者为气。夫以孔、周之旨即如彼,程、朱之说又如此,不知此与说同耶?异耶?滉愚陋滞见,但知笃信圣贤,依本分平铺说话,不能觑到花潭奇乎奇,妙乎妙处。然尝试以花潭说揆诸贤说,无一符合处。每谓花潭一生用力于此事,自谓穷深极妙,而终见得理字不透。所以虽拼死力谈奇说妙,未免落在形气粗浅一边了,为可惜也。而其门下诸人,坚守其误,诚所未谕,故今也未暇为来说一一订评。然窥见朱子谓叔文说:“精而又精,不可名状,所以得不已,而强名之曰太极。”又曰:“气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气为性之误。”愚谓此非为叔文说,正是花潭说也。又谓叔文“若未会得,且虑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张,久之自有见处,不费许多闲说话也。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说。别看他处,道理尚多,或恐别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胶漆之盆,枉费心力也。”愚又谓,此亦非为叔文说,恰似为莲老针破顶门上一穴也。且罗整庵于此学非无一斑之窥,而误入处,正在于理气非二之说。后之学者,又岂可踵谬袭误,相率而入于迷昧之域耶?①
依李滉之见,罗钦顺和奇大升等皆“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②,只强调理气之“不离”义而忽视二者的“不杂”义。于是,他特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纠正罗、奇等人“理气非二”说及气本论者徐花潭“指气为性”说的错误。
由是观之,强调理气“非一物”是李滉的根本立场。正是基于此种理气“不杂”义,李滉和奇大升围绕“四端”和“七情”的“所从来(根源或来源)”及“所指(所就以言)”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辩。
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与李滉“四七”论之比较为中心
在四端七情①以及理气问题上,奇氏基于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
明宗十四年(1559年)一月,李滉曾致书奇大升,提到“又因士友间传闻所论四端七情之说,鄙意亦尝自病其下语之未稳。逮得砭驳,益知疏缪,即改之云:‘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未知如此下语,无病否?”②就自己对“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所做的表述征求了奇氏的意见。
是年三月,奇大升撰《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他将书寄赠李滉,此书即为奇大升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其中写道:“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说也,而先儒发明尽矣。然窃尝致之,子思之言,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论,所谓剔拨出来者也。盖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而性无不善,情则有善恶,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③奇大升以为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别乃因子思、孟子等先圣“所就以言之者”不同之故,也就是二者在情之所指及所偏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情”只有一种,而“四端”和“七情”所指的对象却有所不同——一指全体,一指其中之部分,二者并不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情。已发之情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心是否依性理而为主宰。性是形上之理,情则是形下之气。理气不离——理不能独自发用,必因气之发而显理之意义。奇氏以为若依李滉之说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两边,则会使人认为理发时无气之作用,而气发时无理作根据。这是不合于程朱学理气“不离”之义。①奇大升指出,子思所说的“情”是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所论的“情”则是所谓“剔拨”②出来者。故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若谓“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便如同将理与气判而为两物,也就无异于认为“七情”不发于性、“四端”不乘于气。这就是奇氏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所持的“剔拨论”主张。
在奇大升而言,将“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一句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③,虽似稍胜于前说但终究在语意上仍有所未安。
盖性之乍发,气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谓“四端”者也。此固纯是天理所发,然非能出于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也。然则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兼气”,可乎?论人心、道心,则或可如此说;若四端、七情,则恐不得如此说,盖七情不可专以人心观也。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④
奇氏所言“四端”为本然之善(“良知”)得以直遂者即指“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因此他以为,“人心”、“道心”或可以理气分言,但是“四端”、“七情”却不宜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或“兼气”。奇大升进而指出所谓“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而所谓“恶”者则为“气禀之过不及”。于此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奇氏的基本见解可概括为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因此七情之发或善或恶,“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者。而且,他还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初非有二义,二者只是不同性质的(如“善”的或“恶”的)“情”而已。奇氏又进一步论道曰:“近来学者,不察孟子就善一边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别而论之,愚窃病焉。朱子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及论性情之际,则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盖恐人之不晓,而以气言性也。然学者须知理之不外于气,而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乃理之本体然也,而用其力焉,则庶乎其不差矣。”①奇大升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主张被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论。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其“理气兼发”或“理气共发”说中的“理”是否具“发用义”?依奇氏之见,“理之本体”为“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若以此推之自然得出“四端”为“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的结论。而且因其力主“理”的“不外于气”之特性,故其“四七理气”论可以表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说。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其“四七理气”之发论中发之者是“气”而不是“理”,“理”只具“主宰义”。这也正是奇大升和罗钦顺虽皆主理气二者“混沦一体”,前者却极力批判后者“认气为理”的主要原因。在罗钦顺的理气论中,理因不具“主宰义”弱化了自身的“实体性”——这对于谨遵传统程朱之旨的奇大升而言无异于离经叛道。
以上便是奇大升就“四七理气”问题致李滉的第一封书信中的主要内容。奇氏在信中着重阐述了其对“四端”和“七情”的理解以及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见解。
对于奇氏来函中的问难,李滉撰写了《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文章从以下几个角度作了认真的回应。首先,他肯定了奇大升对于“四端”和“七情”的区别。“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故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③在李滉看来,理与气是“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这表明他虽然承认理气二者不可分离,但是基于“四端”和“七情”“所就而言之”的差异而有种种分别。这是李滉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其次,李滉从程朱“二性论”的角度对“四七”说进行了阐发。“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子思、孟子所讲的“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与“气质之性”不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性(天之所与我者),即非由外铄的“我固有之”者。在此李滉则基于“四端”与“七情”各自的“所从来”之异(在源起上存在的差异),主张因“性”有本性、气禀之异,故“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性”可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分理气而言之。
再次,李滉又从四端七情的“所主”与“所重”之不同,力主二者皆可以分理气来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四端,皆善也。故曰:‘无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七情,善恶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则心已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谓之‘和’。由是观之,二者虽曰皆不外乎理、气,而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则谓之某为理,某为气,何不可之有乎。”①李滉也以为虽然“四端”与“七情”皆来自于理气,但是因其在“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之义上各有“所主”与“所重”,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四端”为发于内者,即仁义礼智之性的直接发用;“七情”则为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者,即人之形气感官因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四端”所主的是“理”,“七情”所重的是“气”。因此李滉主张“四端”和“七情”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换句话说,他力辩二者之区别的目的在于强调其在善恶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职是之故,李滉认为奇氏为学之失在于“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他在信中写道:“今之所辩则异于是,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从来,概以为兼理气,有善恶,深以分别言之为不可;中间虽有‘理弱气强’、‘理无朕,气有迹’之云,至于其末,则乃以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是则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滉寻常未达其指,不谓来喻之意亦似之也。”②在他看来,奇氏在倡言“四端”是从“七情”中剔拨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说“四端、七情为无异”——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李滉进而直言“讲学而恶分析,务合为一说”乃古人所谓囫囵吞枣,其病不少——为学者若如此不已的话,就会不知不觉之间骎骎然入于以气论性之弊,而堕于认人欲作天理之患。
在此信的结尾处,他还援引朱熹之论为其主张申辩。“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李明辉先生认为朱子这句话在其义理系统中有明确的意涵,而其中两个“发”字的涵义并不相同:“理之发”的“发”意谓“理是四端的存有依据”;“气之发”的“发”则意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引发”,谓七情是由气之活动所引生。但是在朱子的系统中,既然理本身不活动,自不能说:四端是由理之活动所引发。故对朱子而言,理之“发”是虚说,气之“发”为实说。②这一论述对解读李滉、奇大升等人的“理发”、“气发”之说很有启发意义。“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③一语的确见于《朱子语类》,但朱子并未对之做进一步的阐发。
接到李滉复函后,奇大升随即撰写了第二封信也就是《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信中对李滉在文中的答复一一作了回应。于是,两人之间就有了第二次往复论辩。奇氏第二封信的内容分为12节,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奇大升还是强调自己的“情”观,认为人只有一种“情”。“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然而所谓‘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其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是故愚之前说,以为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者,正谓此也。又以为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者,亦谓此也。由是言之,以‘四端主于理,七情主于气’而云云者,其大纲虽同,而曲折亦有所不同者也。”①依其之见,情兼理气故有善恶。四端和七情之异源于“所就以言之不同”——七情之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与孟子所谓四端皆同实而异名;至于发而不中节者则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因此并非七情之外又有所谓四端者。
其次,奇氏以为不仅四端是性之所发,而且七情亦是性之所发。“来辩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此言甚当,正与朱子之言互相发明,愚意亦未尝不以为然也。然而朱子有曰:‘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以是观之,所谓‘四端是理之发’者,专指理言;所谓‘七情是气之发’者,以理与气杂而言之者也。而‘是理之发’云者,固不可易;‘是气之发’云者,非专指气也。”②他进而写道:“四端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七情亦发于仁义礼智之性也。不然,朱子何以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乎?又何以曰‘情是性之发’乎?”③理学先辈即主情为性之所发。奇大升肯定情有四端、七情之分,而四端和七情皆由性所发。
再次,奇氏又据理学人性论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原则,进一步指出不仅七情是理乘气而发,而且四端也是理乘气而发。他还直言“四端亦气”。“后来伏奉示喻,改之以‘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云云,则视前语尤分晓。而鄙意亦以为未安者,盖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揭之于图,或谓之‘无不善’,或谓之‘有善恶’,则人之见之也,疑若有两情,且虽不疑于两情,而亦疑其情中有二善,一发于理,一发于气者,为未当也。”④奇大升认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情中有“发于理”和“发于气”的两种善的说法难免令人困惑。这在奇大升看来显然是不妥的。依其之见,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便是“情”。故“情”皆出于心,并非仅源于外物触其形。“心”是理气之合,当其感于物而动之际发之者只能是“气”——四端和七情也不例外。“愚按:‘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句,出《好学论》。然考本文曰:‘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其曰‘动于中’,又曰‘其中动’云者,即心之感也。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焉,乃所谓‘情’也。然则情见乎外,虽似缘境而出,实则由中以出也。辩(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引者注)曰:‘四端之发,其端绪也。’愚谓:四端、七情,无非出于心者,而心乃理、气之合,则情固兼理、气也,非别有一情,但出于理,而不兼乎气也。此处正要人分别得真与妄尔。辩曰:‘七情之发,其苗脉也。’愚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朱子曰:‘性之欲,即所谓情也。’然则情之感物而动者,自然之理也。盖由其中间实有是理,故外边所感,便相契合;非其中间本无是理,而外物之来,偶相凑著而感动也。然则‘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一语,恐道七情不著也。若以感物而动言之,则四端亦然。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其感物者,与七情不异也。辩曰:‘安有在中,为理之本体耶?’愚谓:在中之时,固纯是天理,然此时只可谓之‘性’,不可谓之‘情’也。若才发,则便是情,而有和不和之异矣。盖未发,则专是理;既发,则便乘气以行也。朱子《元亨利贞说》曰:‘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又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①可见,奇大升在谈论四端和七情时特别强调心的感知与主宰作用。心为理气之合,故出于心的四端和七情必兼理气。他还说过若以生长收藏为情,便见乘气以行之实,而“四端亦气”也。
最后,奇氏还从价值论意义上就四端和七情的善恶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愚按程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然则四端固皆善也,而七情亦皆善也。惟其发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而为恶矣。岂有善恶未定者哉?今乃谓之‘善恶未定’,又谓之‘一有而不能察,则心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乃谓之和’,则是七情者,其为冗长无用,甚矣!而况发而未中节之前,亦将以何者而名之耶?且‘一有之而不能察’云者,乃《大学》第七章《章句》中语,其意盖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者,只要从无处发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也。《或问》所谓‘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蚩俯仰,因物赋形’者,乃是心之用也,岂遽有不得其正者哉?惟其事物之来,有所不察,应之既或不能无失,且又不能不与俱往,则其喜怒忧惧,必有动乎中,而始有不得其正耳。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证七情,殊不相似也。夫以来辩之说,反复剖析,不啻详矣,而质以圣贤之旨,其不同有如此者,则所谓‘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者,虽若可以拟议,而其实恐皆未当也。然则谓‘四端为理’、谓‘七情为气’云者,亦安得遽谓之无所不可哉?况此所辩,非但名言之际有所不可,抑恐其于性情之实、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也。”①他又说道:“夫以四端之情为发于理而无不善者,本因孟子所指而言之也。若泛就情上细论之,则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固不可皆谓之善也。有如寻常人,或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亦有是非其所不当是非者。盖理在气中,乘气以发见,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其流行之际,固宜有如此者,乌可以为情无有不善?又乌可以为四端无不善耶?此正学者精察之地,若不分真妄,而但以为无不善,则其认人欲而作天理者,必有不可胜言者矣。”②在奇大升看来,“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恶”者则是“气禀之过不及”。③但因理具有“不外于气”之特性,故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即为“理之本体”。而“理之本体”乃“天命之本然”亦即天赋之“善”者。于是,他认为四端和七情初非有此二义,皆仅是“情”的一种善恶性质而已。因此不能以理气来分言四端和七情。二者的区别只在性发为情之际,所发是否中节——其发而中节者,则无往而不善;其发而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者而为恶。基于此,奇氏以为不仅“七情亦皆善”,而且“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可见,他强调的是二者作为人类感情的同质性和同构性。依奇氏之见,二者的关系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而是七情包含四端(可简称为“七包四”)的关系。
李滉受到奇大升的进一步质疑。他在即接到奇氏《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之后就对其之前不够严谨的表述作了修正,并撰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信中李滉首先对奇氏四端亦是感物而动、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等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不过,对其将四端和七情视为“同实异名”的观点则给予了坚决反对。“公意以为:四端、七情皆兼理、气,同实异名,不可以分属理、气。滉意以为:就异中见其有同,故二者固多有浑沦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则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气之不同,分属何不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虽或有疵,而其宗旨则实有所从来。盛辩一皆诋斥,无片言只字之得完。今虽更有论说,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无益于取信,而徒得哓哓之过也。”①李滉主张对于二者既要异中见其有同,又要同中而知其有异。他还指出以“所就而言”,二者本自有主理、主气之“所主”的区别。由此,李滉提出了“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其详细内容摘录如下:
盖浑沦而言,则七情兼理、气,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著而感动也。且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但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②
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李滉坚守的是对二者各自不同的“所从来”与“所主”的“主理/主气”立场,如其所言“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至此,李滉大体已确立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可视为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最终定论。在此后与奇氏的往复论辩中,李滉对这一基本观点则再未作修正。
对于李滉的答复,奇大升提出了再质疑——遂有《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此信即为其《论四端七情》之第三书,作于1561年(明宗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年)。信中开头奇氏先对《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第一书》的《改本》作了评论,之后又对李滉的答复给予了逐条回应,最后还对《后论以虚为理之说》、《四端不中节之说》、《俚俗相传之语,非出于胡氏》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奇大升以其“因说”和“对说”①之理论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信中写道:
大升以为朱子谓“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者,非对说也,乃因说也。盖对说者,如说左右,是对待底;因说者,如说上下,便是因仍底。圣贤言语,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不可不察也。②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朱夫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③
朱子的“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是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的重要立论依据,所以奇氏特意对朱子的这一说法作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朱子此句是“因说”而非“对说”,是“纵说”而非“横说”。故不能以左右对待来理解。依其之见,圣贤之言“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所以后之学者对之需加以详察。
基于其“因说”之立场,奇大升又援引朱子对理气特性的论述并以此为据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异议。奇氏指出:
如第二条所谓“人之一身,理与气合而生,故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也。互发,则各有所主可知;相须,则互在其中可知”云云者,实乃受病之原,不可不深察也。夫理、气之际,知之固难,而言之亦难。前贤尚以为患,况后学乎?今欲粗述鄙见,仰其镌晓,而辞不契意,难于正说出来,姑以一事譬之。譬如日之在空也,其光景万古常新,虽云雾滃浡,而其光景非有所损,固自若也;但为云雾所蔽,故其阴晴之候,有难齐者尔。及其云消雾卷,则便得偏照下土,而其光景非有所加,亦自若也。理之在气,亦犹是焉。喜、怒、哀、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理,浑然在中者,乃其本体之真;而或为气禀物欲之所拘蔽,则理之本体,虽固自若,而其发见者,便有昏明、真妄之分焉。若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岂不犹日之偏照下土乎?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分据一心之内,迭出用事,而互为首从也。此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①
这是奇氏就李滉在《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之第二书中作答的内容提出的反驳意见。李滉以为,人之一身是由理与气和合而生,因理与气互在其中,故浑沦言之者固有之;又因各有所主,故分别言之亦无不可。对此奇大升以日照大地为喻指出,日光照射大地虽受云雾之影响,但是在空之日“其光景则万古常新”,无所加损。他认为,理之在气亦是如此,故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犹如日之偏照大地。若曰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的话,等于是“理”却具有了情意、计度、造作等特性——这显然有违于朱学之根本原理。依他之见,这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可见,奇氏同样忠于朱子之学,且以朱学为其立学之据的。
基于此,奇大升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委婉地提出己之修正意见,并主张对于“此等议论”不可草草下定论。
“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为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只有理发一边尔。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又未知于先生意如何?子思道其全时,固不用所从来之说,则孟子剔拨而说四端时,虽可谓之指理发一边,而若七情者,子思固已兼理、气言之矣。岂以孟子之言,而遽变为气一边乎?此等议论,恐未可遽以为定也。①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所理解的“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对之他极为自信,认为若在此之外更求“理之发”之义“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②。由此可见,奇大升和李滉皆以朱子学说为据展开思想的攻防。
接到奇氏的《论四端七情》第三书后,李滉只是在来书中节录数段加以批示,并未再作答复——只向奇氏致以含有欲结束二人论辩之意的书函。或许在李滉看来,通过奇氏的三次来书和自己的两次答复已令双方充分了解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感到二人相互间很难说服对方,遂欲结束这场论辩。接到李滉来函后,奇大升又撰写了《四端七情后说》和《四端七情总论》寄赠李滉,此时已是1566年(明宗二十一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收到奇氏寄来的两书后,李滉只是简单作了回复,而对来书中的具体问题并未详加解答。他写道:“四端七情《总说》(应为《总论》——引者注)、《后说》两篇,议论极明快,无惹缠纷挐之病。眼目尽正当,能独观昭旷之原,亦能辨旧见之差于毫忽之微,顿改以从新意,此尤人所难者。甚善!甚善!所论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复致思于其间乎?兼前示人心道心等说,皆当反隅以求教。今兹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谨当一一。”③如引文所见,信中李滉仅就奇氏对“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的解释提出些异议,对来书之内容未作具体回复。这表明李滉已无意继续与奇氏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
这场开始于明宗十四年(1559年)1月的李滉《与奇明彦》一书的论辩,以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10月李滉作《答奇明彦》一书而告终。但是,双方的主要论点大都集中于奇大升上退溪的前三次书和李滉的前两次作答的书函中。尽管二人围绕四七理气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他们相互间的问学并未就此中断。宣祖昭敬王元年(1568年)7月奇氏就拜谒了奉王命入京的李滉,是年12月还与其一同讨论《圣学十图》。而且,次年(1569年)3月还将欲回安东陶山的李滉送至东湖,并同宿江墅。在东湖舟上,奇大升先寄一绝奉别李滉,朴和叔等继之。席上诸公,咸各赠言饯别李滉。奇氏诗曰:“江汉滔滔万古流,先生此去若为留。沙边拽缆迟徊处,不尽离肠万斛愁。”①李滉和韵:“列坐方舟尽胜流,归心终日为牵留。愿将汉水添行砚,写出临分无限愁。”②李滉临行,不能尽酬,谨用前二绝韵奉谢了诸公相送之厚意。不料,于东湖作别后的第二年,1570年(宣祖三年)12月李滉辞世。奇氏惊闻退溪李滉先生讣音,设位痛哭。翌年正月送吊祭于陶山,2月撰《退溪先生墓碣铭先生自铭并书》,赞其曰:“先生盛德大业,卓冠吾东者,当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后之学者,观于先生所论著,将必有感发默契焉者。而铭中所叙,尤足以想见其微意也。”③可见,奇大升和李滉虽然在为学和致思倾向上分歧明显,但是作为同道益友和直谅诤友,二人感情甚笃,在相互问学中共同推动了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三、奇大升“四端七情”论的特色
奇大升与李滉皆为李朝一代儒宗,二人的学说亦各具其理论特色。由上所述可知,奇大升的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理气观和性情论等方面。
首先,在理气观上奇大升主张理气的“混沦一体”性,但是亦不否认二者区别——所谓“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①奇氏说过: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
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③
他主张在二者的“不离”义上应持“合看”和“离看”的立场。“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④,因此要求学者于此当特别“精以察之”。依其“理无朕而气有迹”等观点来看,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奇大升论曰:“盖理无朕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⑤“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以及“非以理气为一物”等观点皆是奇氏理气论的重点所在,必须仔细玩味方能体会出其性理学说之特点。
他与李滉虽然在强调“理”的主宰性和理气不杂性方面取得了共识(二人皆承认理的“实在性”),但是在对理的作用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与奇氏不同,李滉十分重视“理”的能动性和发用性。李滉说过“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①。他还提出“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②的“理帅气卒”论。这是李滉在理气论方面的创见,也是其思想的特色所在。论者将此称为朱学的“死理向活理的转化”③。
在理气观方面奇氏的理论呈现的是“一元论”的倾向,而李滉的学说则体现了鲜明的“二元论”特色。
其次,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问题上,奇大升认为二者是“一本”和“万殊”的关系。奇氏论曰: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愚谓:天地之性,是就天地上总说;气质之性,是从人物禀受上说。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无碍”者乎?④
从援引的朱子语录中可以看出,奇氏实际上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理”与“分殊用之理”的关系。他以“天命之性”为本,而以“气质之性”为末。奇氏还曾引用朱子《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⑤可见,奇大升还将“天命之性”(理)视作“道之体”和“天下之大本”,而且认为天下之道理皆由此出。
但他又说:
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者……若就性上论,则所谓“气质之性”者,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然则论性,而曰“本性”、曰“气禀”云者,非如就天地及人物上,分理、气而各自为一物也,乃以一性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耳。至若论其情,则缘本性堕在气质,然后发而为情,故谓之“兼理气,有善恶”。而其发见之际,自有发于理者,亦有发于气者,虽分别言之,无所不可,而仔细秤停,则亦有似不能无碍。①依奇氏之见,“气质之性”(“万殊”之性)与“天命之性”(“一本”之性)实际上同为一性。之所以有“本性”、“气禀”之说乃因以“一性”之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换句话说,“气质之性”即指此“理”(“天命之性”)堕在气质之中者。“天命之性”要通过“气质之性”来得到具体呈现和实现,所以说在“气质之性”之外“非别有一性也”。
对“天命之性”与“四端”、“七情”的关系,奇大升认为“‘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②。在他看来,“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为“天命之性”、“本然之体”,与“四端”是同实而异名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是气禀物欲之所为,并非是性之本然。
与奇氏不同,李滉却以程朱的“二性说”为理论依据,提出自己的“性”论。“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在李滉看来,思、孟所言“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根据(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李滉主要是基于“四端”与“七情”在“所指”及“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的差别,提出“性”有本性、气禀之异。他坚持“二性论”的立场,强调“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的观点。进而又认为“性”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以分理气而言之。
简言之,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及“一本万殊”的理念主张“一性论”。他重视人的现实之性也就是所谓“气质之性”;与之不同,李滉依据理气二分及理气互发的思想,坚持其“二性论”的观点。
再次,在“四端”与“七情”关系方面,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以及“一性说”之立场,坚持独到的“七包四”(“因说”)的思想。在奇氏性理学的逻辑结构中,“四端”与“七情”是同构性的(“一情”)。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同实而异名”,所以在其看来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并无差异。
奇大升说过:
盖七情亦本善也,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恶矣……盖七情中善者,乃理之发,而与四端同实而异名者也。②
盖性虽本善,而堕于气质,则不无偏胜,故谓之“气质之性”。七情虽兼理、气,而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而易流于恶,故谓之“气之发”也。然其发而中节者,乃发于理,而无不善,则与四端初不异也。但四端只是理之发,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扩而充之,则学者于四端之发,可不体认以扩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气之发,而理之所发,或不能以宰乎气,气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则学者于七情之发,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义各有所以然者,学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则亦可以思过半矣。③
依其之见,七情亦本善,只因兼摄理气加之理弱气强,故易流于恶。但是,奇大升认为七情中善者(发而中节者),与发于理的四端是同实而异名。这里奇氏所提到的“发于理”一词常被视为经与李滉多次辩论后对李氏立场的妥协。其实不然,此处奇大升只是顺着孟子的四端说扩展开来讲而已①,并非向“四七理气互发”说的回归。在其理气论中,理之本体被规定为“气之自然发见”,故其所言“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②。若奇氏“四七”说带有理发论的意味,肯定会遭到后来李珥等人的批判。但是李珥只对李滉的理发论展开批驳,而对奇氏之说则每持接续之姿态。
因此,“四端”与“七情”为“一情”还是“二情”的问题上,奇氏始终坚定地抱持二者为“一情”的立场。奇大升说过:
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③
大升前者妄以鄙见撰说一篇。当时以为子思就情上,以兼理气、有善恶者,而浑沦言之,故谓之“道其全”;孟子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言之,故谓之“剔拨出来”。然则均是情也,而曰“四端”、曰“七情”者,岂非以所就而言之者不同,而实则非有二情也。④
如前所述,奇氏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和四端无别,因而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同具价值之善。在他看来,四端、七情之别就在于“所就而言”之者的不同之故。孟子所谓四端是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剔拨言之,子思所谓七情则是就情上“兼理气、有善恶者(道其全)”浑沦言之——其实人之情是“一”而已矣。“剔拨论”是奇大升在“四七”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理论观点。
李滉则基于其“理气二分”和“二性论”的立场,主张将四端与七情“对举互言”——奇氏将其理气互发说称为“对说”。
李滉在答奇氏对于其“四端七情”论的质疑时,从“所就而言”的视角写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他也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但同时又认为以理气分言“四七”之发的说法前所未见。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来探讨的研究范式始自韩国儒者。依李滉之见,尽管理与气在具体生成事物的过程中“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具有不可分离性,但是不能将四端和七情“滚合为一说”。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应分别以言之。
李滉进而又从“所指”的视角论述道:
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①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认为情之有“四七”之分犹如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他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微妙的关系,以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源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主于理,一主于气。之所以有此分别乃因“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李滉说过:“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②二者各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他主张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这一观点虽经几次修正,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概而言之,在持续8年之久的往复论辩中,因所持的立场角度及所仰重的诠释文本上的差异,③双方始终无法在见解上达成一致。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主张“一性论”和“一情说”,而李滉则依止“理气二分”的思想强调“二性论”和“二情说”。
奇氏以为四端与七情皆可视为情的一种善恶性质,不能将二者看作性质有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情,也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更为贴近朱学原论。但是李滉却从“理气二分”和“尊理”的立场出发,强调二者的异质性亦即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不同。退溪十分关注道德行为的源起,而奇氏则更留意流行层面已发之情的中节问题,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等篇中就多有对中节问题的论述。奇大升和李滉皆为一代儒学名宿,二人的论辩虽未达成共识,却给后人提供了广阔的哲学思辨的空间。
他们所开启的“四七理气”之辨,后为李珥、成浑等人进一步扩展为“四七人心道心”之辨。
李珥曾这样评价奇氏的“四七”理论:“余在江陵,览奇明彦与退溪论四端七情书。退溪则以为‘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明彦则以为四端七情元非二情,七情中之发于理者为四端耳。往复万余言,终不相合。余曰,明彦之论,正合我意。盖性中有仁义礼智信,情中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如斯而已。五常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七情中之不杂人欲,粹然出于天理者,是四端也。”①这表明李珥的思想与奇大升一脉相承,亦持“四端七情非二”之立场。他又提道:“退溪与奇明彦论四七之说,无虑万余言。明彦之论,则分明直截,势如破竹。退溪则辨说虽详,而义理不明,反复咀嚼,卒无的实之滋味。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乎,只是有个才智,偶于此处见得到耳。窃详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为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做出许多葛藤。每读之,未尝不慨叹,以为正见之一累也。”②李珥对“四端七情”之辨中双方的学说皆有透彻之领悟。像“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的说法确为李滉四七论的要害所在。但他却支持奇氏的主张,盖因其追求的“明德之实效,新民之实迹”③的务实精神与高峰之学更为合拍。
由此可见,奇大升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退溪李滉在与其辩论中逐步确立了其“四七理气互发”说的立场,由此奠定了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栗谷李珥则在奇氏与李滉辩论中同情前者之立场,并将之发扬光大以为“气发理乘一途”说,从而奠定了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
一、奇大升的理气论——兼述《论困知记》
奇大升(字名彦,号高峰、存斋)亦是朝鲜朝重要性理学家,生于中宗二十二年(1527年),卒于宣祖五年(1572年),谥号为文宪。他出生于全罗南道光州召古龙里松岘洞。③32岁中文科乙科第一人,后官至大司谏。奇氏天资聪敏,博览强记,长于论辩。33岁时便与李滉围绕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进行了长达8年的相互问难,由此拉开了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四七理气”论辩之帷幕。
理气问题是性理学的首要问题,奇大升亦十分重视此问题。他在信中写道:“然鄙意以为当于理气上,看得分明,然后心性情意,皆有着落,而四端七情,不难辩矣。后来诸先生之论,非不详且明矣。然质以思孟程朱之言,皆若异趣似于理气上未剖判也。”①依奇氏之见,若于理气问题上看得分明则心、性、情、意及四端七情诸说皆不难辩,故可将其理气说视为他的“四端七情”说的立论基础。于此也可以看出,他是追求理气说(存在论)与心性论相一致的性理学家。奇氏这一致思倾向与李珥有相似之处。下面将分析他的理气概念以及在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他用太极阴阳说规定了理气概念。“至于天地上分理气,则太极理也,阴阳气也。”②他以太极阴阳论定义理气的同时,将此贯彻到人和物上进一步指出:“就人物上分理气,则健顺五常理也,魂魄五脏气也。”③这表明奇氏以传统性理学形上、形下之理论来理解理气。
其次,在理气关系上,奇大升以理为气之主宰,以气为理之材料——强调理对气的主宰性乃其思想之特色。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④
理为气之主宰就意味着理对气之运动的主导作用。但他在强调理的主宰性的同时又指出理的脆弱性,即理无眹而气有迹。“理弱气强”似与理的主宰性相矛盾。其实这也是朱学理气论的困境所在,因为在朱子哲学中“理”就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⑤之“三无”特性。奇氏有言:“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①这是他在信中质疑李滉“理发”说的一段文字。如何化解本体义上理的主宰性与流行义上理的脆弱性矛盾以使气顺利而发?这是每位理学家都要面临的重要理论课题。欲分析奇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要从其理气关系的解读上着手。
再次,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奇氏强调二者的不离义,此即理气“混沦一体”说。但是在此问题上他又力主既要“合看”又要“离看”。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在奇大升看来,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③,因此学者于此应特别要“精以察之”。依其对理气的规定,理无眹而气有迹,故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他评论说:“盖理无眹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④非以理气为一物,而却“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奇氏的这一观点与明儒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47年)的理气为一物,“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的主张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罗整庵的《困知记》传入韩国后引起较大反响,有尊奉之者,也有批判之者。李滉和奇大升即属后者,二人皆撰文予以批判。李滉写了篇《非理气为一物辩证》,奇大升则写了篇《论困知记》。
《高峰集》中记载:“明学者罗钦顺,号整庵,作《困知记》以理气为一物,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为不然。若著‘所以’字,则便成二物云,又以‘道心为体,人心为用’。此书新出,而世之学者莫能辨其是非,或有深悦而笃信者。戊辰五月,大升以大司成,诣阙至玉堂与副提学臣卢守慎,共论《困知记》。守慎以整庵之言为至当,而无以议为。大升力辨其非曰,朱子以为道心源于性命之正,人心生于形气之私,固以理气分而言之矣。整庵认理为气,以理气为一物,故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种种新奇之说,皆从此出。何可背圣贤相传不可易之说,而从罗整庵之新奇乎?遂著困知记论以辨之。盖其正见,不眩于似是之非,而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反复纡余,光明俊伟粹然一出于正,此李滉所以敛袵者特深也。”①“戊辰五月”,即为宣祖元年(1568年)5月,时奇氏42岁。不过据其《年谱》记载,奇大升在明宗二十年(1565年)12月往见卢守慎(字寡悔,号苏斋,1515—1590年)于镇国院,并与之讨论了人心道心问题。②卢氏以罗整庵《困知记》的理论为依据论述了其对人道说的看法。可见,他的《论困知记》一书是在与卢守慎展开论辩过程中完成,也是其思想成熟期的著作。③此书对了解奇大升的理气性情学说特点以及《困知记》一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此文的开头奇氏写道:
罗整庵《困知记》,世多尊尚。余尝观其书,闳博精邃,顿挫变化,殆不可测其涯涘。试提大概则推尊孔孟程朱,为之宗主。援据《易》、《诗》、《书》、《礼》,以张其说,而又能躬探禅学而深斥之。其驰骋上下,抑扬予夺之际,可谓不遗余力矣。世俗悦其新奇,而不究其实,宜乎尊尚之也。然愚之浅见,窃尝以为,罗氏之学,实出于禅学,而改头换面,文以圣贤之语,乃诐淫邪遁之尤者。使孟子而复生,必当声罪致讨,以正人心,固不悠悠而已也。④
从引文中可以概见,《困知记》传入韩国之初作为“新奇”之说颇受世儒的尊尚。这与《困知记》在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罗钦顺为江西泰和人,生于宪宗成化元年,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父死服阙后起原官,嘉靖六年坚辞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之召,致仕居家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致之学。他与其时的名儒王阳明、湛若水及欧阳德等人皆有往复辩论①,是在朱学阵营中为数不多的能与心学分庭抗礼的大儒。他的著作有《整庵存稿》二十卷和《困知记》六卷,而其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困知记》一书中。但《困知记》问世后并未受到中国学界关注,而却在韩国引起不小的波澜。如引文内容所见,有尊尚者亦有排斥者。奇氏则直斥罗氏之学“实出于禅学”,即便是孟子复生亦必当声罪致讨以正人心。
他指出虽然罗氏的个别观点和圣贤之道也有相符之处,但是其大纲领大根本却与之相去不啻百千万里之远。他还举了罗氏《困知记》中的具体论点以说明其主张皆与圣贤本旨相违,舛错谬戾不须更辨。
《记》凡四卷,益以附录,无虑数万言。其间,岂无一二之几乎道,而其大纲领大根本,与圣贤相肯,不啻百千万里之远。则其学之邪正,为如何哉。其书所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及“理气为一物”及“良知非天理”云云者,皆与圣贤本旨,舛错谬戾此,不须更辨,而其出于禅学之实,则不可以不辨也。②
尽管奇大升也主张理气“混沦一体”说,但是与罗氏的“理气为一物”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看来,罗氏之学“其出于禅学之实,则不可以不辨”。罗钦顺的《困知记》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已难以确知,但是从奇氏这段文字中可推知,起初传至韩国的《困知记》并非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六卷《困知记》,而是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年)五月完成的4卷本——是年罗氏69岁。在《困知记》序中,他写道:“余才微而质鲁,志复凡近。早尝从事章句,不过为利禄谋尔。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虽已晚,然自谓苟能粗见大意,亦庶几无负此生。而官守拘牵,加之多病,工夫难得专一,间尝若有所见矣,既旬月或逾时,又疑而未定,如此者盖二十余年,其于钻研体究之功,亦可谓尽心焉耳矣。”①罗氏这部著作的写作前后历时二十多年。当完成“四续”时已是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五月,其时他年已82岁。全书由卷上、卷下、续卷上、续卷下、三续、四续共六卷和附录构成。奇氏文中所提及的“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理气为一物”及“良知非天理”等的确是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所阐述的理论主旨。罗氏在《困知记》开篇即讲:“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然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②又说:“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③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渐趋衰落,而陆王心学声势日隆。罗氏对此深以为忧,于是将辨明“心性之别”以批驳陆王的“良知即天理”说作为其历史使命。职是之故,罗氏立学极重“心性之辨”。他以为心性的关系是既不相离又不能相混的,二者之别甚是微妙。若于心性的分际区别上,稍不清晰,便真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由此他将“道心”与“人心”关系定义为体用关系,这就是其独特的“人心道心体用”说。
那么,被称为“朱学后劲”的罗氏学说为什么会受到同样遵奉朱学的韩儒李滉、奇大升等性理学家的批判呢?这主要是因于其“理气为一物”的思想和由此引申出的“人心道心体用”说。于此可见,至16世纪中韩两国朱子学的发展已各呈不同的义理旨趣,此与韩国性理学者与中国朱子学者所处的不同人文语境与各自所倚重的不同核心话题相关。对于这一问题,讨论李珥理气说时再做进一步分析。
奇大升以为,罗氏之所以提出“理气为一物”、“人心道心体用”说等主张是因其学源自禅学之故。故在《论困知记》一文中,他力图揭露罗氏学说“实出于禅学”的“真相”。于是,奇氏在文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与此相关的内容:
整庵自言“官京师,逢一老僧,闻‘庭前柏树’之话,精思达朝,揽衣将起,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云云,此则悟禅之证也。后官南雍,“潜玩圣贤之书,研磨体认,日复一日,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云云”,此则改头换面,文以圣贤之语之实也。此之分明招认,固不可掩。而又有其论道理处,尤显然而不可掩者焉。《记》上第五章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一,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用也,精微纯性之真也。释氏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故其为教,始则欲人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空即虚也。既则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觉即知觉也。觉性既得,则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神即灵也。凡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使其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识矣。顾乃自以为无上妙道,曾不知其终身,尚有寻不到处,乃敢驾其说,以误天下后世之人云云。”
以此一章观之,其学之出于禅学者,益无所遁矣。夫心之虚灵知觉,乃理气妙合,自然之妙,而其或有不能然者,特以气禀物欲之蔽,而失其正耳。人苟能操而存之,不为气禀物欲之所累,则其虚灵知觉之妙。固自若也,非如释氏之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然后心始虚也。又非如释子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然后心有知觉也。又非如释子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然后心可谓之神也。此与圣贤所论虚灵知觉者,同耶异耶?其亦不待辨而可知其非也。
且既曰:“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而继之曰:“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然则圣贤之论心,亦与释子无异致耶。“离诸相,契虚觉,而洞彻无方者”,乃释子之作弄精神,灭绝天理者也。今乃欲与圣贤之论心者,比而同之,其可乎,其不可乎。
又曰:“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可识。”夫欲适越而北其辕,终莫能幸而至焉。今乃欲据释子所见之及,而向上寻之,以识夫帝降之衷,吾恐其如北辕而适越,终身伥伥,竟无可至之日也。
整庵之学,初既悮禅,而后观圣贤之书以文之。故其言如此,殊不知儒释,道既不同,而立心亦异有如阴阳昼夜之相反,乌可据彼之见,而能为此之道乎。①
罗钦顺自述其一生孜孜求道,用心甚苦。先由禅学悟心之灵妙,后识吾儒性命之旨。年垂六十,才自认为有见于性命之真。②其学思历程中确有一个出入佛道的经历(早年由禅学而入),《明史》亦记载道:“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③罗氏从“佛在庭前拍树子”话头得悟后,始知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虽相似而实不同——释氏大抵有见于心而无见于性。他指出今之世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在罗氏看来,道之不明正由于此。由此而论,奇氏批驳钦顺之学“实出于禅学”一说似难成立。在《困知记》一书中罗氏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禅宗经典《楞伽经》以及达摩、宗杲等重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批判。连《明儒学案》也提到“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④其实,钦顺之学是建立于程朱的“理一分殊”说之上,罗氏曾说过:“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简而尽,约而无所不通,初不假于牵合安排,自确乎其不可易也。”⑤又说:“一旦于理一分殊四字有个悟处,反而验之身心,推而验之人人,又验之阴阳五行,又验之鸟兽草木,头头皆合。于是始涣然自信,而知二君子之言,断乎不我欺也。愚言及此,非以自多,盖尝屡见吾党所著书,有以‘性即理’为不然者,只为理字难明,往往为气字之所妨碍,才见得不合,便以先儒言说为不足信,殊不知工夫到后,虽欲添一个字,自是添不得也。”①可见罗氏之学大体是接续程朱而来,但是在理气观方面已与程朱有了较大不同。那么,为什么同尊朱子的奇大升与罗钦顺间会有如此大的理论分歧呢?这主要源于二人对“理”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并对其“理”的特性有不同的界定。奇氏力辩罗氏之学的“禅学之实”乃因二人的理气观差异甚大,所以他紧接着就对罗氏理气说与心性说不一致提出批评。奇大升对钦顺的理气观极为不满,批评亦较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内容。学者于此不可不察。
前面已论及,奇大升是追求理气论与心性论相合一的性理学家。于是,他对罗氏思想中的两论不一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佛氏“作用是性”之说,固认气为理,而以心论性也。整庵实见之差,实由于此。故理气一物之说,道心人心性情之云,亦皆因此而误焉。盖既以理气为一物,则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属理气。故其为说,必至于如是,而整庵之所自以为向上寻到者,亦不过于佛氏所见之外,知有理字。而其所谓理字者,亦不过于气上认其有节度处耳。整庵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者,正是此病也。虽其为说,张皇焜耀,开阖万端,而要其指归,终亦不出于此矣。
且整庵每自谓至当归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夫既以理气为一物矣,而又以体用为二物焉,并引“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以证体用之为二物。若曰:道是体神是用,而道与神为二物,则理气果一物乎?理气果一物,则道与神,又何以为二物乎?整庵又以心与性,为体用之二物,心与性,既是二物,与理气为一物之说,不亦矛盾之甚乎?②
奇氏认为钦顺之学有“认气为理”以及由此引生的“以心论性”之病。他进而指出,罗氏自以为向上寻到者,亦不过于佛氏所见之外知有一个“理”字。而其所谓“理”字者,亦不过于气上认其有节度处耳。所以奇大升直言,“整庵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者,正是此病也”。又指责说整庵每自谓至当归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既以理气为一物,则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属理气。”奇氏所要强调的是理学“体用一源”之原则,故指责罗钦顺“以心与性,为体用之二物,心与性,既是二物,与理气为一物之说,不亦矛盾之甚乎?”既然理气为一物,体用就不能析为二物。
在东亚儒学史上奇大升是最早具体指出罗氏学说之内在矛盾的学者。对于此不能“归一”性,被称为宋明理学殿军的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年)和《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1610—1695年)师生亦有评述。刘宗周指出:“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谓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不免抛自身之藏。”①黄宗羲则更直接指出:“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①当然,这是刘宗周与黄宗羲师弟基于心学之立场对罗氏之学作出的评判。但是,谨遵朱子之学的奇大升和秉持心学立场的刘、黄等人先后都对罗氏学说的自相矛盾提出批评。此一现象表明作为儒者他们皆以体用一源为共法,而其理论也因之具有相近的思想倾向。这无关各自的具体学术主张。就哲学体系的完整性而言,一个思想家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后者应为前者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有些当代学者因此十分肯定刘、黄二人对罗钦顺的批评。②当然也有人对刘、黄师弟对于罗氏学说的批评不以为然。③分歧的产生与朱子哲学特殊的义理架构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朱子哲学在存在论(理气论)意义上倾向理气二分(“不离不杂”)和以理为主的理本论;而在心性论意义上则偏于以性、情、心三分结构为义理间架的“心统性情”论。④陈来先生曾指出,以“心统性情”为代表的朱子心性论结构的表达并非“理/气”二分模式,而是“易/道/神”的模式。盖因心性系统乃一功能系统,而不是存在系统。因此黄宗羲等人以“天人未能合一”来批评朱子的理气论未能贯通到心性论,似与事实有悖。实际上在朱学中理气观念并非没有应用到“人”。朱子使用“性理/气质”来分析人的问题即与其理气观一脉相承。①陈来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对朱子“心”论的理解有帮助,而且对罗氏学说的不一致性以及韩国儒学“四七理气”之发问题的理解亦大有助益。
在论述权近、郑之云等人的性理学时已言及,韩国性理学者在探讨性理问题时皆热衷于追求“天人心性合一”——摄理气于心乃韩国性理学之特色。因此相较于中国朱子学的理气说,韩国性理学的理气说更多带有性情论色彩。韩国儒者借此以说明性情之辨以及性情之发等问题。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奇大升的“理气共发”说以及李珥的“气发理乘”说皆可从这一角度得到深入的理解。否则很难解释倡言“理发理动”②以及“太极自动静”③的李滉何以能被称为“东方之朱夫子”。
在《论困知记》文末,奇氏还批评了罗氏的“良知非天理”说。曰:
整庵又论良知非天理,而云“知能是人心之妙用,爱敬乃人心之天理”,然则天理在妙用之外,而妙用者无与于天理乎。夫天理之在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此心之所以统性情。而其未发者,寂也体也;其已发者,感也用也。然则爱敬者,为未发耶,已发耶。知能,虽皆心之用,而有真妄邪正之分,固不可皆指以为天理矣。若加一良字,则乃本然之善,岂非天理之发乎。今以爱敬为天理,而以良知为非天理,爱敬与良知果若是其不同耶。且以知能为心之妙用,而不察乎真妄邪正之实,则尤不可。佛氏之神通妙用,运水般柴之说,正坐不分其真妄,而皆以为妙用之失也。昔有问于胡文定公曰:“禅者,以枯槌竖拂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为用,用而不妙。须是动容周旋中礼,方始是妙用处。”以此而揆诸整庵之言,其是非得失亦可见矣。整庵尝论宗果,以为“直是会说,左来右去,神出鬼没,所以能耸动一世。”余以为整庵之状宗杲者,乃所以自状也。
噫,道丧学绝,世俗何尝知此意思。见余之论,必以为笑,不谓之狂,则谓之妄也。然余亦岂欲必信于世俗,而与哓哓者相竞。将以俟后来之君子尔,同志之士,幸相与谅之。①
从奇氏对罗整庵的批评中可见,他对罗氏的“良知非天理”说的理解上有些偏差。前面已论及,明中叶以后程朱之学渐显颓势,王学日渐兴盛。在此情形之下,罗氏愤而扛起朱学大旗,欲明“心性之辨”以批驳“良知非天理”说。他将此作为理论活动的首要任务。罗氏曰:“夫孔孟之绝学,至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尝认良知为天理也。以谓有物必有则,故学必先于格物。今以良知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此语见《传习录》。来书亦云:‘致其良知于日履之间,以达之天下。’),则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无乃不得于言乎(《雍语》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本体,岂可于事物上寻讨?’总是此见。)!”②可见罗氏倾向程朱的“性即理”,而非“心即理”。因此他认为“有物必有则,故学必先于格物”——“格物”即为克己之私的过程。依罗整庵之见,“良知为天理”的说法过分强调个体之慧悟,极易将艰苦的修养工夫化为简易的禅悟,这是学人需警惕的非常危险的理论动向。显而易见,罗氏所批“良知”是指阳明的“致良知”。而奇氏所理解之“良知”则为基于伊洛渊源的良知、良能,也就是本然之善。于此也可以窥出奇氏的心性说仍以程朱的心、性、情三分义理间架为基础。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并不同意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那么,应如何理解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呢?对此奇氏有如下表述:
喜同恶离,乐浑全厌剖析,乃末学之常累。然鄙意固未尝以是自安也,亦欲其一一剖析尔……又或问: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朱子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然,则气之自然发见,过不及者,岂非理之本体乎……至于极论其所以然,则乃以七情之发,为理之本体,又以气之自然发见者,亦非理之本体,则所谓发于理者于何而见之,而所谓发于气者,在理之外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失,不可不察也。罗整庵所论不曾见得,不知如何。若据此一句,则其误甚矣。若大升则固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也。①可见,奇大升主张的是基于“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的理气“混沦一体”说。他以为理气虽不可谓二物,但也不能视为一物,“若以为一物,则又无道器之分矣”②。因此在奇氏看来,罗整庵以理气为一物,“其见甚乖”③。其实,奇大升的“理气混沦”说与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理”作为“所以然”者的地位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牵涉到对“理”的主宰义的不同认识。奇氏强调理的主宰作用,所以不满“理气一物”论。“整庵则以理气为一物,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为不然。谓若着‘所以’字,则便成二物云云。”④但上一段引文中奇氏所言“罗整庵所论不曾见得,不知如何”一句则需做进一步商榷。此言出自奇大升回复李滉的“高峰第二书”中。据研究,奇氏大约是在戊午年(32岁)或己未年(33岁)已读到《困知记》,故与李滉开始“四七理气”论争之前很有可能已受《困知记》思想的影响。①而且,李滉将奇氏己未年“高峰第一书”中的“七情中四端”以及“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等观点,评为与整庵的“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②。由此可见其时李滉也认为奇氏思想受到罗氏学说的影响。而奇氏在第二封回信中自辩道“整庵所论不曾见得”,则不能不令后学对之生疑。奇氏的理气“混沦一体”说后被李珥继承发展,确立为极富主气论特色的“理气之妙”说。
李滉对罗钦顺亦有评价,曾说过“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③。他则谨依朱子在《答刘书文书》中所阐“理与气决是二物”说,对主气论学者的“理气非异物”之说进行了批评。
最后附上李滉的《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供学者参考。此文对理解李滉、罗钦顺以及奇大升三人理气论之间的差异有较大帮助。该文内容如下:
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又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今按:孔子、周子明言阴阳是太极所生,若曰理气本一物,则太极即是两仪,安有能生者乎?曰真曰精,以其二物,故曰妙合而凝。如其一物,宁有妙合而凝者乎?
明道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
今按,若理气果是一物,孔子何必以形而上下分道器,明道何必曰“须著如此说”乎?明道又以其不可离器而索道,故曰“器亦道”,非谓器即是道也;以其不能外道而有器,故曰“道亦器”,非谓道即是器也。(道器之分即理气之分,故引以为证。)
朱子《答刘书文书》曰:“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又曰:“须知未有此气,先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夹论。至论其偏体于物,无处不在,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莫不有是理焉。”(今按:理不囿于物,故能无物不在。)不当以气之精者为性,性之粗者为气也。(性即理也,故引以为证。)
今按: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又曰:“性虽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相夹杂。”不当以气之精者为性,性之粗者为气。夫以孔、周之旨即如彼,程、朱之说又如此,不知此与说同耶?异耶?滉愚陋滞见,但知笃信圣贤,依本分平铺说话,不能觑到花潭奇乎奇,妙乎妙处。然尝试以花潭说揆诸贤说,无一符合处。每谓花潭一生用力于此事,自谓穷深极妙,而终见得理字不透。所以虽拼死力谈奇说妙,未免落在形气粗浅一边了,为可惜也。而其门下诸人,坚守其误,诚所未谕,故今也未暇为来说一一订评。然窥见朱子谓叔文说:“精而又精,不可名状,所以得不已,而强名之曰太极。”又曰:“气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气为性之误。”愚谓此非为叔文说,正是花潭说也。又谓叔文“若未会得,且虑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张,久之自有见处,不费许多闲说话也。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说。别看他处,道理尚多,或恐别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胶漆之盆,枉费心力也。”愚又谓,此亦非为叔文说,恰似为莲老针破顶门上一穴也。且罗整庵于此学非无一斑之窥,而误入处,正在于理气非二之说。后之学者,又岂可踵谬袭误,相率而入于迷昧之域耶?①
依李滉之见,罗钦顺和奇大升等皆“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②,只强调理气之“不离”义而忽视二者的“不杂”义。于是,他特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纠正罗、奇等人“理气非二”说及气本论者徐花潭“指气为性”说的错误。
由是观之,强调理气“非一物”是李滉的根本立场。正是基于此种理气“不杂”义,李滉和奇大升围绕“四端”和“七情”的“所从来(根源或来源)”及“所指(所就以言)”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辩。
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与李滉“四七”论之比较为中心
在四端七情①以及理气问题上,奇氏基于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
明宗十四年(1559年)一月,李滉曾致书奇大升,提到“又因士友间传闻所论四端七情之说,鄙意亦尝自病其下语之未稳。逮得砭驳,益知疏缪,即改之云:‘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未知如此下语,无病否?”②就自己对“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所做的表述征求了奇氏的意见。
是年三月,奇大升撰《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他将书寄赠李滉,此书即为奇大升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其中写道:“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说也,而先儒发明尽矣。然窃尝致之,子思之言,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论,所谓剔拨出来者也。盖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而性无不善,情则有善恶,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③奇大升以为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别乃因子思、孟子等先圣“所就以言之者”不同之故,也就是二者在情之所指及所偏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情”只有一种,而“四端”和“七情”所指的对象却有所不同——一指全体,一指其中之部分,二者并不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情。已发之情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心是否依性理而为主宰。性是形上之理,情则是形下之气。理气不离——理不能独自发用,必因气之发而显理之意义。奇氏以为若依李滉之说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两边,则会使人认为理发时无气之作用,而气发时无理作根据。这是不合于程朱学理气“不离”之义。①奇大升指出,子思所说的“情”是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所论的“情”则是所谓“剔拨”②出来者。故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若谓“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便如同将理与气判而为两物,也就无异于认为“七情”不发于性、“四端”不乘于气。这就是奇氏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所持的“剔拨论”主张。
在奇大升而言,将“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一句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③,虽似稍胜于前说但终究在语意上仍有所未安。
盖性之乍发,气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谓“四端”者也。此固纯是天理所发,然非能出于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也。然则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兼气”,可乎?论人心、道心,则或可如此说;若四端、七情,则恐不得如此说,盖七情不可专以人心观也。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④
奇氏所言“四端”为本然之善(“良知”)得以直遂者即指“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因此他以为,“人心”、“道心”或可以理气分言,但是“四端”、“七情”却不宜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或“兼气”。奇大升进而指出所谓“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而所谓“恶”者则为“气禀之过不及”。于此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奇氏的基本见解可概括为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因此七情之发或善或恶,“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者。而且,他还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初非有二义,二者只是不同性质的(如“善”的或“恶”的)“情”而已。奇氏又进一步论道曰:“近来学者,不察孟子就善一边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别而论之,愚窃病焉。朱子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及论性情之际,则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盖恐人之不晓,而以气言性也。然学者须知理之不外于气,而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乃理之本体然也,而用其力焉,则庶乎其不差矣。”①奇大升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主张被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论。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其“理气兼发”或“理气共发”说中的“理”是否具“发用义”?依奇氏之见,“理之本体”为“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若以此推之自然得出“四端”为“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的结论。而且因其力主“理”的“不外于气”之特性,故其“四七理气”论可以表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说。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其“四七理气”之发论中发之者是“气”而不是“理”,“理”只具“主宰义”。这也正是奇大升和罗钦顺虽皆主理气二者“混沦一体”,前者却极力批判后者“认气为理”的主要原因。在罗钦顺的理气论中,理因不具“主宰义”弱化了自身的“实体性”——这对于谨遵传统程朱之旨的奇大升而言无异于离经叛道。
以上便是奇大升就“四七理气”问题致李滉的第一封书信中的主要内容。奇氏在信中着重阐述了其对“四端”和“七情”的理解以及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见解。
对于奇氏来函中的问难,李滉撰写了《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文章从以下几个角度作了认真的回应。首先,他肯定了奇大升对于“四端”和“七情”的区别。“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故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③在李滉看来,理与气是“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这表明他虽然承认理气二者不可分离,但是基于“四端”和“七情”“所就而言之”的差异而有种种分别。这是李滉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其次,李滉从程朱“二性论”的角度对“四七”说进行了阐发。“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子思、孟子所讲的“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与“气质之性”不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性(天之所与我者),即非由外铄的“我固有之”者。在此李滉则基于“四端”与“七情”各自的“所从来”之异(在源起上存在的差异),主张因“性”有本性、气禀之异,故“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性”可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分理气而言之。
再次,李滉又从四端七情的“所主”与“所重”之不同,力主二者皆可以分理气来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四端,皆善也。故曰:‘无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七情,善恶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则心已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谓之‘和’。由是观之,二者虽曰皆不外乎理、气,而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则谓之某为理,某为气,何不可之有乎。”①李滉也以为虽然“四端”与“七情”皆来自于理气,但是因其在“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之义上各有“所主”与“所重”,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四端”为发于内者,即仁义礼智之性的直接发用;“七情”则为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者,即人之形气感官因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四端”所主的是“理”,“七情”所重的是“气”。因此李滉主张“四端”和“七情”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换句话说,他力辩二者之区别的目的在于强调其在善恶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职是之故,李滉认为奇氏为学之失在于“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他在信中写道:“今之所辩则异于是,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从来,概以为兼理气,有善恶,深以分别言之为不可;中间虽有‘理弱气强’、‘理无朕,气有迹’之云,至于其末,则乃以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是则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滉寻常未达其指,不谓来喻之意亦似之也。”②在他看来,奇氏在倡言“四端”是从“七情”中剔拨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说“四端、七情为无异”——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李滉进而直言“讲学而恶分析,务合为一说”乃古人所谓囫囵吞枣,其病不少——为学者若如此不已的话,就会不知不觉之间骎骎然入于以气论性之弊,而堕于认人欲作天理之患。
在此信的结尾处,他还援引朱熹之论为其主张申辩。“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李明辉先生认为朱子这句话在其义理系统中有明确的意涵,而其中两个“发”字的涵义并不相同:“理之发”的“发”意谓“理是四端的存有依据”;“气之发”的“发”则意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引发”,谓七情是由气之活动所引生。但是在朱子的系统中,既然理本身不活动,自不能说:四端是由理之活动所引发。故对朱子而言,理之“发”是虚说,气之“发”为实说。②这一论述对解读李滉、奇大升等人的“理发”、“气发”之说很有启发意义。“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③一语的确见于《朱子语类》,但朱子并未对之做进一步的阐发。
接到李滉复函后,奇大升随即撰写了第二封信也就是《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信中对李滉在文中的答复一一作了回应。于是,两人之间就有了第二次往复论辩。奇氏第二封信的内容分为12节,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奇大升还是强调自己的“情”观,认为人只有一种“情”。“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然而所谓‘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其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是故愚之前说,以为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者,正谓此也。又以为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者,亦谓此也。由是言之,以‘四端主于理,七情主于气’而云云者,其大纲虽同,而曲折亦有所不同者也。”①依其之见,情兼理气故有善恶。四端和七情之异源于“所就以言之不同”——七情之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与孟子所谓四端皆同实而异名;至于发而不中节者则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因此并非七情之外又有所谓四端者。
其次,奇氏以为不仅四端是性之所发,而且七情亦是性之所发。“来辩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此言甚当,正与朱子之言互相发明,愚意亦未尝不以为然也。然而朱子有曰:‘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以是观之,所谓‘四端是理之发’者,专指理言;所谓‘七情是气之发’者,以理与气杂而言之者也。而‘是理之发’云者,固不可易;‘是气之发’云者,非专指气也。”②他进而写道:“四端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七情亦发于仁义礼智之性也。不然,朱子何以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乎?又何以曰‘情是性之发’乎?”③理学先辈即主情为性之所发。奇大升肯定情有四端、七情之分,而四端和七情皆由性所发。
再次,奇氏又据理学人性论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原则,进一步指出不仅七情是理乘气而发,而且四端也是理乘气而发。他还直言“四端亦气”。“后来伏奉示喻,改之以‘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云云,则视前语尤分晓。而鄙意亦以为未安者,盖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揭之于图,或谓之‘无不善’,或谓之‘有善恶’,则人之见之也,疑若有两情,且虽不疑于两情,而亦疑其情中有二善,一发于理,一发于气者,为未当也。”④奇大升认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情中有“发于理”和“发于气”的两种善的说法难免令人困惑。这在奇大升看来显然是不妥的。依其之见,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便是“情”。故“情”皆出于心,并非仅源于外物触其形。“心”是理气之合,当其感于物而动之际发之者只能是“气”——四端和七情也不例外。“愚按:‘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句,出《好学论》。然考本文曰:‘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其曰‘动于中’,又曰‘其中动’云者,即心之感也。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焉,乃所谓‘情’也。然则情见乎外,虽似缘境而出,实则由中以出也。辩(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引者注)曰:‘四端之发,其端绪也。’愚谓:四端、七情,无非出于心者,而心乃理、气之合,则情固兼理、气也,非别有一情,但出于理,而不兼乎气也。此处正要人分别得真与妄尔。辩曰:‘七情之发,其苗脉也。’愚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朱子曰:‘性之欲,即所谓情也。’然则情之感物而动者,自然之理也。盖由其中间实有是理,故外边所感,便相契合;非其中间本无是理,而外物之来,偶相凑著而感动也。然则‘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一语,恐道七情不著也。若以感物而动言之,则四端亦然。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其感物者,与七情不异也。辩曰:‘安有在中,为理之本体耶?’愚谓:在中之时,固纯是天理,然此时只可谓之‘性’,不可谓之‘情’也。若才发,则便是情,而有和不和之异矣。盖未发,则专是理;既发,则便乘气以行也。朱子《元亨利贞说》曰:‘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又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①可见,奇大升在谈论四端和七情时特别强调心的感知与主宰作用。心为理气之合,故出于心的四端和七情必兼理气。他还说过若以生长收藏为情,便见乘气以行之实,而“四端亦气”也。
最后,奇氏还从价值论意义上就四端和七情的善恶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愚按程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然则四端固皆善也,而七情亦皆善也。惟其发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而为恶矣。岂有善恶未定者哉?今乃谓之‘善恶未定’,又谓之‘一有而不能察,则心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乃谓之和’,则是七情者,其为冗长无用,甚矣!而况发而未中节之前,亦将以何者而名之耶?且‘一有之而不能察’云者,乃《大学》第七章《章句》中语,其意盖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者,只要从无处发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也。《或问》所谓‘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蚩俯仰,因物赋形’者,乃是心之用也,岂遽有不得其正者哉?惟其事物之来,有所不察,应之既或不能无失,且又不能不与俱往,则其喜怒忧惧,必有动乎中,而始有不得其正耳。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证七情,殊不相似也。夫以来辩之说,反复剖析,不啻详矣,而质以圣贤之旨,其不同有如此者,则所谓‘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者,虽若可以拟议,而其实恐皆未当也。然则谓‘四端为理’、谓‘七情为气’云者,亦安得遽谓之无所不可哉?况此所辩,非但名言之际有所不可,抑恐其于性情之实、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也。”①他又说道:“夫以四端之情为发于理而无不善者,本因孟子所指而言之也。若泛就情上细论之,则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固不可皆谓之善也。有如寻常人,或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亦有是非其所不当是非者。盖理在气中,乘气以发见,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其流行之际,固宜有如此者,乌可以为情无有不善?又乌可以为四端无不善耶?此正学者精察之地,若不分真妄,而但以为无不善,则其认人欲而作天理者,必有不可胜言者矣。”②在奇大升看来,“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恶”者则是“气禀之过不及”。③但因理具有“不外于气”之特性,故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即为“理之本体”。而“理之本体”乃“天命之本然”亦即天赋之“善”者。于是,他认为四端和七情初非有此二义,皆仅是“情”的一种善恶性质而已。因此不能以理气来分言四端和七情。二者的区别只在性发为情之际,所发是否中节——其发而中节者,则无往而不善;其发而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者而为恶。基于此,奇氏以为不仅“七情亦皆善”,而且“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可见,他强调的是二者作为人类感情的同质性和同构性。依奇氏之见,二者的关系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而是七情包含四端(可简称为“七包四”)的关系。
李滉受到奇大升的进一步质疑。他在即接到奇氏《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之后就对其之前不够严谨的表述作了修正,并撰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信中李滉首先对奇氏四端亦是感物而动、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等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不过,对其将四端和七情视为“同实异名”的观点则给予了坚决反对。“公意以为:四端、七情皆兼理、气,同实异名,不可以分属理、气。滉意以为:就异中见其有同,故二者固多有浑沦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则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气之不同,分属何不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虽或有疵,而其宗旨则实有所从来。盛辩一皆诋斥,无片言只字之得完。今虽更有论说,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无益于取信,而徒得哓哓之过也。”①李滉主张对于二者既要异中见其有同,又要同中而知其有异。他还指出以“所就而言”,二者本自有主理、主气之“所主”的区别。由此,李滉提出了“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其详细内容摘录如下:
盖浑沦而言,则七情兼理、气,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著而感动也。且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但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②
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李滉坚守的是对二者各自不同的“所从来”与“所主”的“主理/主气”立场,如其所言“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至此,李滉大体已确立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可视为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最终定论。在此后与奇氏的往复论辩中,李滉对这一基本观点则再未作修正。
对于李滉的答复,奇大升提出了再质疑——遂有《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此信即为其《论四端七情》之第三书,作于1561年(明宗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年)。信中开头奇氏先对《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第一书》的《改本》作了评论,之后又对李滉的答复给予了逐条回应,最后还对《后论以虚为理之说》、《四端不中节之说》、《俚俗相传之语,非出于胡氏》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奇大升以其“因说”和“对说”①之理论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信中写道:
大升以为朱子谓“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者,非对说也,乃因说也。盖对说者,如说左右,是对待底;因说者,如说上下,便是因仍底。圣贤言语,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不可不察也。②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朱夫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③
朱子的“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是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的重要立论依据,所以奇氏特意对朱子的这一说法作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朱子此句是“因说”而非“对说”,是“纵说”而非“横说”。故不能以左右对待来理解。依其之见,圣贤之言“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所以后之学者对之需加以详察。
基于其“因说”之立场,奇大升又援引朱子对理气特性的论述并以此为据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异议。奇氏指出:
如第二条所谓“人之一身,理与气合而生,故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也。互发,则各有所主可知;相须,则互在其中可知”云云者,实乃受病之原,不可不深察也。夫理、气之际,知之固难,而言之亦难。前贤尚以为患,况后学乎?今欲粗述鄙见,仰其镌晓,而辞不契意,难于正说出来,姑以一事譬之。譬如日之在空也,其光景万古常新,虽云雾滃浡,而其光景非有所损,固自若也;但为云雾所蔽,故其阴晴之候,有难齐者尔。及其云消雾卷,则便得偏照下土,而其光景非有所加,亦自若也。理之在气,亦犹是焉。喜、怒、哀、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理,浑然在中者,乃其本体之真;而或为气禀物欲之所拘蔽,则理之本体,虽固自若,而其发见者,便有昏明、真妄之分焉。若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岂不犹日之偏照下土乎?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分据一心之内,迭出用事,而互为首从也。此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①
这是奇氏就李滉在《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之第二书中作答的内容提出的反驳意见。李滉以为,人之一身是由理与气和合而生,因理与气互在其中,故浑沦言之者固有之;又因各有所主,故分别言之亦无不可。对此奇大升以日照大地为喻指出,日光照射大地虽受云雾之影响,但是在空之日“其光景则万古常新”,无所加损。他认为,理之在气亦是如此,故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犹如日之偏照大地。若曰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的话,等于是“理”却具有了情意、计度、造作等特性——这显然有违于朱学之根本原理。依他之见,这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可见,奇氏同样忠于朱子之学,且以朱学为其立学之据的。
基于此,奇大升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委婉地提出己之修正意见,并主张对于“此等议论”不可草草下定论。
“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为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只有理发一边尔。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又未知于先生意如何?子思道其全时,固不用所从来之说,则孟子剔拨而说四端时,虽可谓之指理发一边,而若七情者,子思固已兼理、气言之矣。岂以孟子之言,而遽变为气一边乎?此等议论,恐未可遽以为定也。①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所理解的“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对之他极为自信,认为若在此之外更求“理之发”之义“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②。由此可见,奇大升和李滉皆以朱子学说为据展开思想的攻防。
接到奇氏的《论四端七情》第三书后,李滉只是在来书中节录数段加以批示,并未再作答复——只向奇氏致以含有欲结束二人论辩之意的书函。或许在李滉看来,通过奇氏的三次来书和自己的两次答复已令双方充分了解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感到二人相互间很难说服对方,遂欲结束这场论辩。接到李滉来函后,奇大升又撰写了《四端七情后说》和《四端七情总论》寄赠李滉,此时已是1566年(明宗二十一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收到奇氏寄来的两书后,李滉只是简单作了回复,而对来书中的具体问题并未详加解答。他写道:“四端七情《总说》(应为《总论》——引者注)、《后说》两篇,议论极明快,无惹缠纷挐之病。眼目尽正当,能独观昭旷之原,亦能辨旧见之差于毫忽之微,顿改以从新意,此尤人所难者。甚善!甚善!所论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复致思于其间乎?兼前示人心道心等说,皆当反隅以求教。今兹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谨当一一。”③如引文所见,信中李滉仅就奇氏对“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的解释提出些异议,对来书之内容未作具体回复。这表明李滉已无意继续与奇氏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
这场开始于明宗十四年(1559年)1月的李滉《与奇明彦》一书的论辩,以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10月李滉作《答奇明彦》一书而告终。但是,双方的主要论点大都集中于奇大升上退溪的前三次书和李滉的前两次作答的书函中。尽管二人围绕四七理气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他们相互间的问学并未就此中断。宣祖昭敬王元年(1568年)7月奇氏就拜谒了奉王命入京的李滉,是年12月还与其一同讨论《圣学十图》。而且,次年(1569年)3月还将欲回安东陶山的李滉送至东湖,并同宿江墅。在东湖舟上,奇大升先寄一绝奉别李滉,朴和叔等继之。席上诸公,咸各赠言饯别李滉。奇氏诗曰:“江汉滔滔万古流,先生此去若为留。沙边拽缆迟徊处,不尽离肠万斛愁。”①李滉和韵:“列坐方舟尽胜流,归心终日为牵留。愿将汉水添行砚,写出临分无限愁。”②李滉临行,不能尽酬,谨用前二绝韵奉谢了诸公相送之厚意。不料,于东湖作别后的第二年,1570年(宣祖三年)12月李滉辞世。奇氏惊闻退溪李滉先生讣音,设位痛哭。翌年正月送吊祭于陶山,2月撰《退溪先生墓碣铭先生自铭并书》,赞其曰:“先生盛德大业,卓冠吾东者,当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后之学者,观于先生所论著,将必有感发默契焉者。而铭中所叙,尤足以想见其微意也。”③可见,奇大升和李滉虽然在为学和致思倾向上分歧明显,但是作为同道益友和直谅诤友,二人感情甚笃,在相互问学中共同推动了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三、奇大升“四端七情”论的特色
奇大升与李滉皆为李朝一代儒宗,二人的学说亦各具其理论特色。由上所述可知,奇大升的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理气观和性情论等方面。
首先,在理气观上奇大升主张理气的“混沦一体”性,但是亦不否认二者区别——所谓“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①奇氏说过: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
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③
他主张在二者的“不离”义上应持“合看”和“离看”的立场。“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④,因此要求学者于此当特别“精以察之”。依其“理无朕而气有迹”等观点来看,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奇大升论曰:“盖理无朕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⑤“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以及“非以理气为一物”等观点皆是奇氏理气论的重点所在,必须仔细玩味方能体会出其性理学说之特点。
他与李滉虽然在强调“理”的主宰性和理气不杂性方面取得了共识(二人皆承认理的“实在性”),但是在对理的作用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与奇氏不同,李滉十分重视“理”的能动性和发用性。李滉说过“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①。他还提出“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②的“理帅气卒”论。这是李滉在理气论方面的创见,也是其思想的特色所在。论者将此称为朱学的“死理向活理的转化”③。
在理气观方面奇氏的理论呈现的是“一元论”的倾向,而李滉的学说则体现了鲜明的“二元论”特色。
其次,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问题上,奇大升认为二者是“一本”和“万殊”的关系。奇氏论曰: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愚谓:天地之性,是就天地上总说;气质之性,是从人物禀受上说。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无碍”者乎?④
从援引的朱子语录中可以看出,奇氏实际上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理”与“分殊用之理”的关系。他以“天命之性”为本,而以“气质之性”为末。奇氏还曾引用朱子《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⑤可见,奇大升还将“天命之性”(理)视作“道之体”和“天下之大本”,而且认为天下之道理皆由此出。
但他又说:
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者……若就性上论,则所谓“气质之性”者,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然则论性,而曰“本性”、曰“气禀”云者,非如就天地及人物上,分理、气而各自为一物也,乃以一性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耳。至若论其情,则缘本性堕在气质,然后发而为情,故谓之“兼理气,有善恶”。而其发见之际,自有发于理者,亦有发于气者,虽分别言之,无所不可,而仔细秤停,则亦有似不能无碍。①依奇氏之见,“气质之性”(“万殊”之性)与“天命之性”(“一本”之性)实际上同为一性。之所以有“本性”、“气禀”之说乃因以“一性”之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换句话说,“气质之性”即指此“理”(“天命之性”)堕在气质之中者。“天命之性”要通过“气质之性”来得到具体呈现和实现,所以说在“气质之性”之外“非别有一性也”。
对“天命之性”与“四端”、“七情”的关系,奇大升认为“‘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②。在他看来,“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为“天命之性”、“本然之体”,与“四端”是同实而异名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是气禀物欲之所为,并非是性之本然。
与奇氏不同,李滉却以程朱的“二性说”为理论依据,提出自己的“性”论。“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在李滉看来,思、孟所言“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根据(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李滉主要是基于“四端”与“七情”在“所指”及“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的差别,提出“性”有本性、气禀之异。他坚持“二性论”的立场,强调“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的观点。进而又认为“性”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以分理气而言之。
简言之,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及“一本万殊”的理念主张“一性论”。他重视人的现实之性也就是所谓“气质之性”;与之不同,李滉依据理气二分及理气互发的思想,坚持其“二性论”的观点。
再次,在“四端”与“七情”关系方面,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以及“一性说”之立场,坚持独到的“七包四”(“因说”)的思想。在奇氏性理学的逻辑结构中,“四端”与“七情”是同构性的(“一情”)。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同实而异名”,所以在其看来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并无差异。
奇大升说过:
盖七情亦本善也,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恶矣……盖七情中善者,乃理之发,而与四端同实而异名者也。②
盖性虽本善,而堕于气质,则不无偏胜,故谓之“气质之性”。七情虽兼理、气,而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而易流于恶,故谓之“气之发”也。然其发而中节者,乃发于理,而无不善,则与四端初不异也。但四端只是理之发,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扩而充之,则学者于四端之发,可不体认以扩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气之发,而理之所发,或不能以宰乎气,气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则学者于七情之发,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义各有所以然者,学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则亦可以思过半矣。③
依其之见,七情亦本善,只因兼摄理气加之理弱气强,故易流于恶。但是,奇大升认为七情中善者(发而中节者),与发于理的四端是同实而异名。这里奇氏所提到的“发于理”一词常被视为经与李滉多次辩论后对李氏立场的妥协。其实不然,此处奇大升只是顺着孟子的四端说扩展开来讲而已①,并非向“四七理气互发”说的回归。在其理气论中,理之本体被规定为“气之自然发见”,故其所言“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②。若奇氏“四七”说带有理发论的意味,肯定会遭到后来李珥等人的批判。但是李珥只对李滉的理发论展开批驳,而对奇氏之说则每持接续之姿态。
因此,“四端”与“七情”为“一情”还是“二情”的问题上,奇氏始终坚定地抱持二者为“一情”的立场。奇大升说过:
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③
大升前者妄以鄙见撰说一篇。当时以为子思就情上,以兼理气、有善恶者,而浑沦言之,故谓之“道其全”;孟子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言之,故谓之“剔拨出来”。然则均是情也,而曰“四端”、曰“七情”者,岂非以所就而言之者不同,而实则非有二情也。④
如前所述,奇氏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和四端无别,因而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同具价值之善。在他看来,四端、七情之别就在于“所就而言”之者的不同之故。孟子所谓四端是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剔拨言之,子思所谓七情则是就情上“兼理气、有善恶者(道其全)”浑沦言之——其实人之情是“一”而已矣。“剔拨论”是奇大升在“四七”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理论观点。
李滉则基于其“理气二分”和“二性论”的立场,主张将四端与七情“对举互言”——奇氏将其理气互发说称为“对说”。
李滉在答奇氏对于其“四端七情”论的质疑时,从“所就而言”的视角写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他也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但同时又认为以理气分言“四七”之发的说法前所未见。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来探讨的研究范式始自韩国儒者。依李滉之见,尽管理与气在具体生成事物的过程中“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具有不可分离性,但是不能将四端和七情“滚合为一说”。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应分别以言之。
李滉进而又从“所指”的视角论述道:
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①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认为情之有“四七”之分犹如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他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微妙的关系,以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源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主于理,一主于气。之所以有此分别乃因“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李滉说过:“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②二者各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他主张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这一观点虽经几次修正,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概而言之,在持续8年之久的往复论辩中,因所持的立场角度及所仰重的诠释文本上的差异,③双方始终无法在见解上达成一致。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主张“一性论”和“一情说”,而李滉则依止“理气二分”的思想强调“二性论”和“二情说”。
奇氏以为四端与七情皆可视为情的一种善恶性质,不能将二者看作性质有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情,也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更为贴近朱学原论。但是李滉却从“理气二分”和“尊理”的立场出发,强调二者的异质性亦即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不同。退溪十分关注道德行为的源起,而奇氏则更留意流行层面已发之情的中节问题,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等篇中就多有对中节问题的论述。奇大升和李滉皆为一代儒学名宿,二人的论辩虽未达成共识,却给后人提供了广阔的哲学思辨的空间。
他们所开启的“四七理气”之辨,后为李珥、成浑等人进一步扩展为“四七人心道心”之辨。
李珥曾这样评价奇氏的“四七”理论:“余在江陵,览奇明彦与退溪论四端七情书。退溪则以为‘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明彦则以为四端七情元非二情,七情中之发于理者为四端耳。往复万余言,终不相合。余曰,明彦之论,正合我意。盖性中有仁义礼智信,情中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如斯而已。五常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七情中之不杂人欲,粹然出于天理者,是四端也。”①这表明李珥的思想与奇大升一脉相承,亦持“四端七情非二”之立场。他又提道:“退溪与奇明彦论四七之说,无虑万余言。明彦之论,则分明直截,势如破竹。退溪则辨说虽详,而义理不明,反复咀嚼,卒无的实之滋味。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乎,只是有个才智,偶于此处见得到耳。窃详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为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做出许多葛藤。每读之,未尝不慨叹,以为正见之一累也。”②李珥对“四端七情”之辨中双方的学说皆有透彻之领悟。像“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的说法确为李滉四七论的要害所在。但他却支持奇氏的主张,盖因其追求的“明德之实效,新民之实迹”③的务实精神与高峰之学更为合拍。
由此可见,奇大升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退溪李滉在与其辩论中逐步确立了其“四七理气互发”说的立场,由此奠定了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栗谷李珥则在奇氏与李滉辩论中同情前者之立场,并将之发扬光大以为“气发理乘一途”说,从而奠定了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