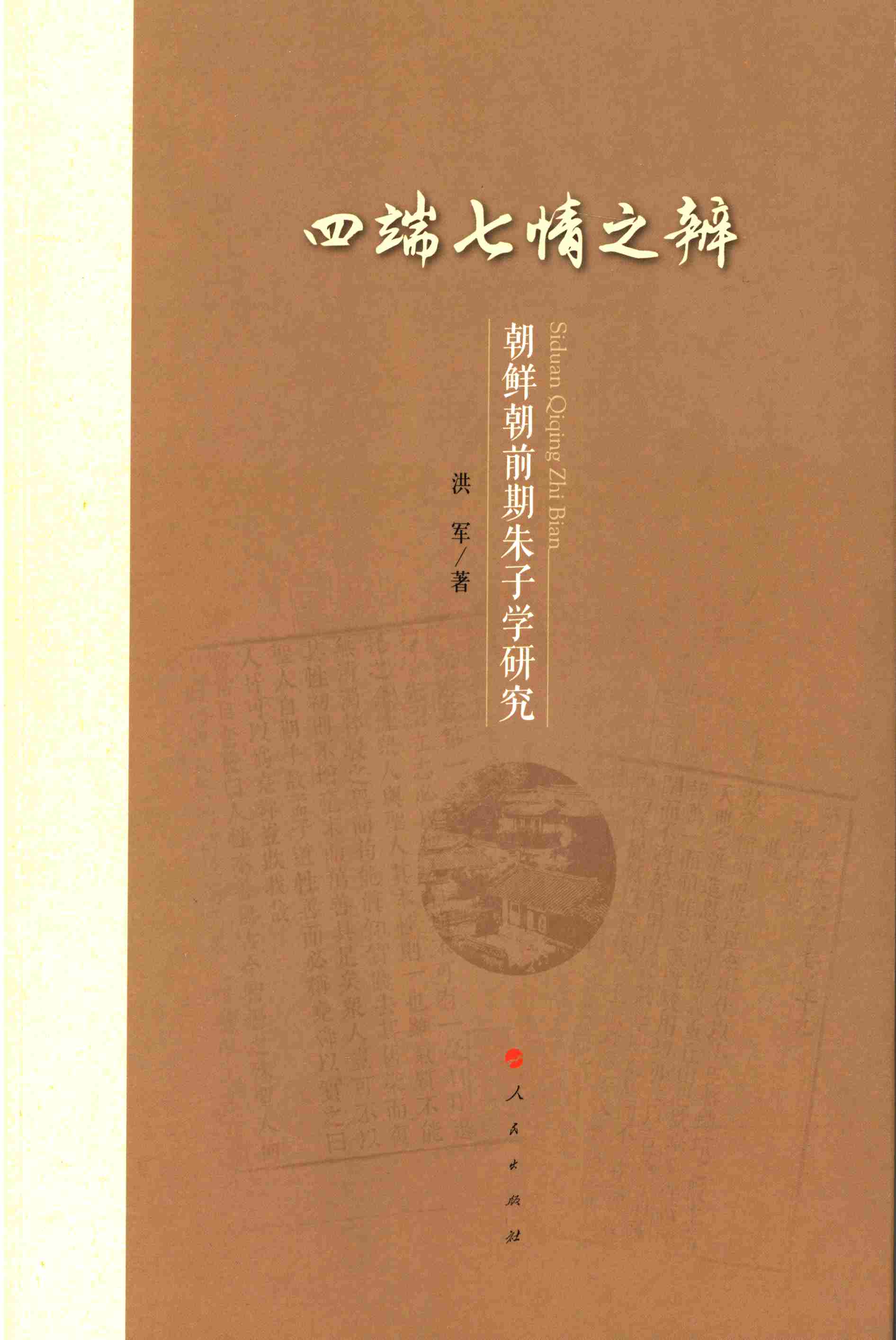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兼论郑之云的《天命图》与“四端七情”论
| 内容出处: | 《四端七情之辨》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9045 |
| 颗粒名称: |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兼论郑之云的《天命图》与“四端七情”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4 |
| 页码: | 103-11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郑之云的《天命图》在李滉的论述之前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郑氏提出的“四端七情”理论开启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性理学研究,并引发了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学术辨论。郑之云认为情由理发,情感纯善,而七情由气发,兼具善恶。而李滉在辩论中对郑氏的说法进行修订,主张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并解释了其中的非理非气的差异。李滉的“四七理气”理论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
| 关键词: | 李滉 四端七情 |
内容
在论述李滉的“四七理气”论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郑之云与其《天命图》。因为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郑氏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引致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李滉曾对郑之云称赞道:“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我妄以结状其难……有契有违,往返弗置,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④
郑氏是继权近、柳崇祖之后又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韩国性理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不仅为此后李滉和李珥等人的“四七理气”之辨提供了理论端绪,而且还开启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四端七情理论研究之先河。
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稼翁,1509—1561年)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曾受教于为金安国和金正国。郑氏世居高阳,本贯则为庆州。他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之辨发端于郑氏之《天命图》。对于自己的作图过程,他在《天命图序》中写道:
正德己卯(中宗十四年,1519年——引者注)思斋金先生被微谴而退卜居于高峰之芒洞,洞实之云所居里也,尝游其门受学焉。嘉靖戊戌(中宗三十三年,1538年——引者注)先生被召还朝,之云失其依归,与舍弟之霖学于家。论及天人之道,则之霖以幼学患其无据,莫能窥测。余于是试取朱子之说(见《性理大全》论人物之性),参以诸说设为一图,而又为问答名曰《天命图说》日与舍弟讲之。此非欲示诸人而作也,然图说既草,则亦不可不见正于长者,遂取质于慕斋思斋两先生,两先生不深责之,且曰:“未可轻议,姑俟后日。”不幸,两先生相继以没,呜呼,痛哉。由是此图之草,无所见正,而余之学问日就荒芜,几不能自振。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误闻不肖之名,躬行者再三之,云感其殷勤,斋木以进。退溪欣然出见,因语及《天命图》,之云以直告知,因请证之意,退溪稍假肯色。余退而私自贺曰:“吾丧两先生后,意谓更不得贤师友而求进,今得退溪,吾无忧矣。”常往来质问是图,退溪证以古说,参用己意,补其所欠,删其所剩,卒成完图。其赐己以厚,又从而为之说,附其后而教之,其幸孰大焉。非徒余之幸也,在昔日两先生姑竢后日之志,今始副焉,是尤幸之大也。余故首记作图之由次及定图之事,以藏于家。如有同志者出,其亦有以知退溪考证之意也。①
文中郑氏较完整地记述了此图的写作过程。他采先儒之论并以图解以明之,目的在于启子弟之蒙。此图取名为《天命图》——“天命”二字典出《中庸》首句,可见其以《中庸》为性理学之基础。为了说明天人相与之道,郑之云在《天命图解》①中使用了诸如理气、心性、太极、道等性理学概念,并用这些概念对天人之际进行了理气论的说明,旨在揭示了天人合一之根据。他还从理气论的角度对人的心性以及善恶问题进行了说明,此即所谓“四端七情”论。尽管郑之云并未将“四七”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来论述,而只视作探究天人合一的根据之一,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四七”论在其性理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②因为前者只是从其性理学整体构成之维度而言的。
此文写于嘉靖甲寅(明宗九年,1554年)之正月,此时退溪李滉已是年过五十的一代儒学名宿,思想也已渐趋成熟。他获得此图后,将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并在语气上作了改动。李滉的这一订正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尤其是奇大升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发展成为左右韩国性理学发展走向的学术论争。
郑之云在阐发其性理学说时,也意识到单纯凭借“气”论是很难对“恶”的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的。于是,他对阴阳之气赋予了善恶的价值含义。如把气分为清、浊、明、暗等。主张阳气清明,故可跻于善;阴气浊暗,故可流为恶。他断言“恶”的现象是由阴气所致,由此维护了“理”的纯善性。而且,还提出阴阳之气只是与心动之后的发用相关,并非各自独自发用的观点。这就消除了人的恶行的先天可能性。郑氏还认为,若心之发“意”根于性且其气属阳的话,天理会如实呈显;相反,如“意”与物相杂而其气属阴,则天理就会失去其真实性,终流于恶。依他之见,人的善恶行为取决于自由意志,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郑氏性理学追求“天人心性合一”,这表明他是韩国性理学史上的主流派学者。与中国的朱子学相比,韩国性理学以“图说类”诠释模式见长。从《天命图》在韩国性理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窥见郑之云在此一传统中的独特地位。①其“四七”理论的首要意义就是肯定人的道德行为(“人性善”)的先天可能性,此为性理学最根本的哲学观念。《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乃其天理观的来源和根据。实际上,性理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探讨的目的则是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寻找一个本体论的根据,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根据。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万物有机体观”正是性理学家们这一思想的反映。理与气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是为了证明这一思想。性理学家们以理气概念探讨道德行为之根源,尤其注重主宰人的行为的“心”的研讨,这也是心性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心性论中,与对心性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有关修养工夫的问题,即如何使心性向“善”的问题。欲解决之,首先要探讨“恶”的根源及来源。所以从理气论维度对“恶”之根源进行探讨也是心性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其中,“四端七情”之探讨是对人的本性的深层剖析,目的在于扩充良知所彰显的内心之善以上合天理。②实际上,他的这一思想根于孟子的性善说,欲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把握性与天道的关系。
可见,郑之云是韩国儒学史上继阳村权近、真一斋柳崇祖之后又一位坚持“天人心性合一”这一韩国性理学传统的学者。在韩国儒学史上,他还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性理学相关理论的学者。③尽管其理论仍显得较为简单缺乏系统性,但在《天命图解》及《天命图说》中所见的理论探索还是对性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了一定的概括和整理。所以李滉“君曾测海”的评价对他而言还是较为中肯的。郑之云的主要著作有《天命图解》以及《天命图说》。
李滉将其《天命图解》改订之后,首先遭到奇大升的发难。奇氏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又说过“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混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②。 在奇大升看来,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举,谓之纯理或兼气就有些不妥。奇氏主张四端虽由纯粹的天理所发,但只是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奇大升进一步评论说: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③
他认为四端与七情作为情感皆性状相似,而非有截然相反之特质。因此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学原论的。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回答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盖欲相资以讲明,非谓其言之无疵也。今者,蒙示辩说,摘抉差谬,开晓谆悉,警益深矣。然犹有所不能无惑者,请试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首先说明了其将郑氏之“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进行改动的缘由,他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认为先儒未有将“四端七情”分置于理与气的范畴来讨论的先例。李滉还是认可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在这一问题上他有过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首度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进行修订时的说法。李滉将郑氏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这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其实此两句从内涵到语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请参见新、旧天命图(图7、图8)。
起初他认为此说“本晦庵说,其理晓然矣”③,其时还未与奇大升展开论辩。二是在与奇氏进行论辩过程中有了第二种表述,即“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④。这是己未年李滉59岁(1559年)时的观点。当此之际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理气”之辨。加之李滉又恰好读到朱子的“四端是发于理,七情是发于气”一句,于是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与奇大升的信中提到:“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三是经奇大升之诘难后便有了新的说法——“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②。此后李滉对这一说法再未作改动,可视为其最终定论。对最后一说,他在其晚年代表作《圣学十图》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③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正是李滉性理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
他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本上的差异,这源于其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①
由此可知,在心性情的关系上李滉倾向张载的“心统性情”说。他将“心”理解为“理气之合”——与朱子“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的观念相比,心的含义以及与理、气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以此说为理论前提,可以分属理气的方式准确表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以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
四端七情之辨实质是性情之辨。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作为李滉晚年思想结晶的《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则为李滉所作。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概念。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此为性理学的主题。性理学的道德主体论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①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如此则性为体而情为用。朱熹认为“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②。与之不同,李滉进一步发挥朱熹的理气心性说并将性情与理气之发相结合,从而将朱子学的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端七情理气”论。此图的中、下两图乃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③对于“七情”的善恶,李滉起初以为“七情,善恶未定也”④。经与奇大升往复论辩之后改为“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故其发而中节者乃谓之和”⑤。这一改动容易造成七情之“善”和四端之“善”之混同,所以对之需作仔细辨析。四端之情是人的道德感情亦即良心。四端之“善”是纯粹的且还带有道德色彩。但是七情则与此不同,原是与道德情感无关之情。作为自然情感,七情在“性发为情”之后才能以发用是否为“中节”衡量其善恶。因此如李滉早年所言,它还是“善恶之未定”。那么,应如何理解其修订后的说法呢?我们可以从其“本善”一语中去寻找。“善”被赋予道德含义之前,“好”是其概念的核心内容。易言之,善是规定事物之好的状态,道德性的善也是如此。“七情”作为原始的自然的感情本是好的感情,只因具有“过或不及”的性质,容易“流于恶”。①其修订后的说法可以按此思路去解读。
对于下图李滉解释说:“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②
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和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遵循程朱“情根于性,性发为情”之原则,依此解读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和无不善之情。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我们也可以一窥李滉试图融合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正是两种权威文本相互冲突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引发韩国儒者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③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说,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还是气发皆可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甚至放而为恶,原因就在理发未遂或者气发不中。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显或气发而皆中节遂成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述引文中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子学的传统——李滉继承这一传统,也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也是情,而“情”必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遂成人性善恶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①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也就是说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自我反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多次对此图进行修改。“盖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中所载本也。”②此图在李滉《圣学十图》中具有的重要性实在是无需赘言。
李滉还以“七情”与“四端”分论“人心”与“道心”,指出“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也。”③这既是对朱子心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学术上的立异。在李滉看来,道心是义理之心即最高的道德原则,所以他在强调四端七情之差异的同时还特别重视道心人心之分别。虽然其中图未言及“气”,但他论性情仍以理气分言之。“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④这也表明李滉心说承继朱子之传统——倾向以“理气心”论性情,而且主张持教工夫。
在论辩的最后,李滉以《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三书》总结二人观点之异:
既曰“浑沦言之”,安有主理、主气之分?由对举分别言时,有此分耳。亦如朱子谓:“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又云:“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
前书引性言者,只为在性犹可兼理气说,以明情岂可不分理气之意耳,非为论性而言也。“理堕气质以后事”以下,固然,当就此而论。
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碍者乎?而况所谓四端七情者,乃理堕气质以后事,恰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则有明有暗,四端则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固因水之清浊而四端之不中节者,则光虽明而未免有波浪之动者也。伏乞将此道理更入思议,如何?
“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说,尝见先儒有论其不可,今不记得……敢问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者,为发于理耶?为发于气耶?而发而中节,无往不善之善,与四端之善,同欤?异欤?虽发于气,而理乘之为主,故其善同也。且“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谓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则只有理发一边。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未知于先生意如何?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发矣。若欲外此而更求理之发,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弊。前书亦以为禀,而犹复云云。苟曰未然,则朱子所谓“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者,亦不可从也。
道即器,器即道。冲漠之中,万象已具,非实以道为器;即物而理不外是,非实以物为理也。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用朱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也。
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此信写就之后李滉或觉没有必要继续与奇氏论辩,故而未将信寄给他,只是针对奇氏来信中的质问撰文阐述自己的主张。李滉的基本观点是四端七情混沦而言时则无需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但是若将二者对举而言则应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他还以“因说”和“对说”来解释了此问题。直至结束辩论二人仍各持己见,并未达成一致。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以为不仅“性”可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若说奇大升注重于对问题的客观性、逻辑性的阐明,李滉则更着力于对道德性的提高以及修养工夫论域中的主体的省察和践履的意义。
“四端七情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赓续朱子的理气心说,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无怪乎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此种理解,李滉进一步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他对七情的看法始终落在气的一边。他说:“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不能无理,所以“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四端”需要扩充,而易“流于恶”的“七情”则要受检束。因为二者各具相异的性质,如何理解其异中之同便值得认真思考。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说:“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若从客观的视角对情之结构做静态分析的话,便可以得出“四端”为“七情”之一部分的结论。但是在道德践履的意义上,二者又具有相反的性质。比较而言,奇大升关注前者,李滉则更倾向于后者。当然此种差异是相对的。两人真正的分歧源于各自在为学旨趣及问学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的问题意识。
要言之,“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中的核心内容。基于理气二分的立场李滉肯定情的“四七”之分,以为恻隐、善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是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而发,即缘境而出。不过依其理气心,“心气”之性质及所为,如气之清浊、偏杂、粹驳之状态,直接决定四端之呈显以及七情之善恶性质。李滉以为,“气”之状态影响理之显否,故在修养论上他特别主张施以主敬涵养工夫治“心气”之患,使气皆能循理而发以保证理发直遂而不被气所掩。
郑氏是继权近、柳崇祖之后又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韩国性理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不仅为此后李滉和李珥等人的“四七理气”之辨提供了理论端绪,而且还开启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四端七情理论研究之先河。
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稼翁,1509—1561年)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曾受教于为金安国和金正国。郑氏世居高阳,本贯则为庆州。他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之辨发端于郑氏之《天命图》。对于自己的作图过程,他在《天命图序》中写道:
正德己卯(中宗十四年,1519年——引者注)思斋金先生被微谴而退卜居于高峰之芒洞,洞实之云所居里也,尝游其门受学焉。嘉靖戊戌(中宗三十三年,1538年——引者注)先生被召还朝,之云失其依归,与舍弟之霖学于家。论及天人之道,则之霖以幼学患其无据,莫能窥测。余于是试取朱子之说(见《性理大全》论人物之性),参以诸说设为一图,而又为问答名曰《天命图说》日与舍弟讲之。此非欲示诸人而作也,然图说既草,则亦不可不见正于长者,遂取质于慕斋思斋两先生,两先生不深责之,且曰:“未可轻议,姑俟后日。”不幸,两先生相继以没,呜呼,痛哉。由是此图之草,无所见正,而余之学问日就荒芜,几不能自振。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误闻不肖之名,躬行者再三之,云感其殷勤,斋木以进。退溪欣然出见,因语及《天命图》,之云以直告知,因请证之意,退溪稍假肯色。余退而私自贺曰:“吾丧两先生后,意谓更不得贤师友而求进,今得退溪,吾无忧矣。”常往来质问是图,退溪证以古说,参用己意,补其所欠,删其所剩,卒成完图。其赐己以厚,又从而为之说,附其后而教之,其幸孰大焉。非徒余之幸也,在昔日两先生姑竢后日之志,今始副焉,是尤幸之大也。余故首记作图之由次及定图之事,以藏于家。如有同志者出,其亦有以知退溪考证之意也。①
文中郑氏较完整地记述了此图的写作过程。他采先儒之论并以图解以明之,目的在于启子弟之蒙。此图取名为《天命图》——“天命”二字典出《中庸》首句,可见其以《中庸》为性理学之基础。为了说明天人相与之道,郑之云在《天命图解》①中使用了诸如理气、心性、太极、道等性理学概念,并用这些概念对天人之际进行了理气论的说明,旨在揭示了天人合一之根据。他还从理气论的角度对人的心性以及善恶问题进行了说明,此即所谓“四端七情”论。尽管郑之云并未将“四七”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来论述,而只视作探究天人合一的根据之一,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四七”论在其性理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②因为前者只是从其性理学整体构成之维度而言的。
此文写于嘉靖甲寅(明宗九年,1554年)之正月,此时退溪李滉已是年过五十的一代儒学名宿,思想也已渐趋成熟。他获得此图后,将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并在语气上作了改动。李滉的这一订正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尤其是奇大升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发展成为左右韩国性理学发展走向的学术论争。
郑之云在阐发其性理学说时,也意识到单纯凭借“气”论是很难对“恶”的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的。于是,他对阴阳之气赋予了善恶的价值含义。如把气分为清、浊、明、暗等。主张阳气清明,故可跻于善;阴气浊暗,故可流为恶。他断言“恶”的现象是由阴气所致,由此维护了“理”的纯善性。而且,还提出阴阳之气只是与心动之后的发用相关,并非各自独自发用的观点。这就消除了人的恶行的先天可能性。郑氏还认为,若心之发“意”根于性且其气属阳的话,天理会如实呈显;相反,如“意”与物相杂而其气属阴,则天理就会失去其真实性,终流于恶。依他之见,人的善恶行为取决于自由意志,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郑氏性理学追求“天人心性合一”,这表明他是韩国性理学史上的主流派学者。与中国的朱子学相比,韩国性理学以“图说类”诠释模式见长。从《天命图》在韩国性理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窥见郑之云在此一传统中的独特地位。①其“四七”理论的首要意义就是肯定人的道德行为(“人性善”)的先天可能性,此为性理学最根本的哲学观念。《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乃其天理观的来源和根据。实际上,性理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探讨的目的则是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寻找一个本体论的根据,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根据。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万物有机体观”正是性理学家们这一思想的反映。理与气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是为了证明这一思想。性理学家们以理气概念探讨道德行为之根源,尤其注重主宰人的行为的“心”的研讨,这也是心性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心性论中,与对心性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有关修养工夫的问题,即如何使心性向“善”的问题。欲解决之,首先要探讨“恶”的根源及来源。所以从理气论维度对“恶”之根源进行探讨也是心性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其中,“四端七情”之探讨是对人的本性的深层剖析,目的在于扩充良知所彰显的内心之善以上合天理。②实际上,他的这一思想根于孟子的性善说,欲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把握性与天道的关系。
可见,郑之云是韩国儒学史上继阳村权近、真一斋柳崇祖之后又一位坚持“天人心性合一”这一韩国性理学传统的学者。在韩国儒学史上,他还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性理学相关理论的学者。③尽管其理论仍显得较为简单缺乏系统性,但在《天命图解》及《天命图说》中所见的理论探索还是对性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了一定的概括和整理。所以李滉“君曾测海”的评价对他而言还是较为中肯的。郑之云的主要著作有《天命图解》以及《天命图说》。
李滉将其《天命图解》改订之后,首先遭到奇大升的发难。奇氏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又说过“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混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②。 在奇大升看来,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举,谓之纯理或兼气就有些不妥。奇氏主张四端虽由纯粹的天理所发,但只是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奇大升进一步评论说: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③
他认为四端与七情作为情感皆性状相似,而非有截然相反之特质。因此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学原论的。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回答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盖欲相资以讲明,非谓其言之无疵也。今者,蒙示辩说,摘抉差谬,开晓谆悉,警益深矣。然犹有所不能无惑者,请试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首先说明了其将郑氏之“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进行改动的缘由,他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认为先儒未有将“四端七情”分置于理与气的范畴来讨论的先例。李滉还是认可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在这一问题上他有过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首度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进行修订时的说法。李滉将郑氏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这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其实此两句从内涵到语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请参见新、旧天命图(图7、图8)。
起初他认为此说“本晦庵说,其理晓然矣”③,其时还未与奇大升展开论辩。二是在与奇氏进行论辩过程中有了第二种表述,即“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④。这是己未年李滉59岁(1559年)时的观点。当此之际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理气”之辨。加之李滉又恰好读到朱子的“四端是发于理,七情是发于气”一句,于是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与奇大升的信中提到:“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三是经奇大升之诘难后便有了新的说法——“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②。此后李滉对这一说法再未作改动,可视为其最终定论。对最后一说,他在其晚年代表作《圣学十图》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③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正是李滉性理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
他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本上的差异,这源于其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①
由此可知,在心性情的关系上李滉倾向张载的“心统性情”说。他将“心”理解为“理气之合”——与朱子“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的观念相比,心的含义以及与理、气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以此说为理论前提,可以分属理气的方式准确表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以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
四端七情之辨实质是性情之辨。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作为李滉晚年思想结晶的《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则为李滉所作。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概念。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此为性理学的主题。性理学的道德主体论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①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如此则性为体而情为用。朱熹认为“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②。与之不同,李滉进一步发挥朱熹的理气心性说并将性情与理气之发相结合,从而将朱子学的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端七情理气”论。此图的中、下两图乃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③对于“七情”的善恶,李滉起初以为“七情,善恶未定也”④。经与奇大升往复论辩之后改为“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故其发而中节者乃谓之和”⑤。这一改动容易造成七情之“善”和四端之“善”之混同,所以对之需作仔细辨析。四端之情是人的道德感情亦即良心。四端之“善”是纯粹的且还带有道德色彩。但是七情则与此不同,原是与道德情感无关之情。作为自然情感,七情在“性发为情”之后才能以发用是否为“中节”衡量其善恶。因此如李滉早年所言,它还是“善恶之未定”。那么,应如何理解其修订后的说法呢?我们可以从其“本善”一语中去寻找。“善”被赋予道德含义之前,“好”是其概念的核心内容。易言之,善是规定事物之好的状态,道德性的善也是如此。“七情”作为原始的自然的感情本是好的感情,只因具有“过或不及”的性质,容易“流于恶”。①其修订后的说法可以按此思路去解读。
对于下图李滉解释说:“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②
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和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遵循程朱“情根于性,性发为情”之原则,依此解读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和无不善之情。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我们也可以一窥李滉试图融合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正是两种权威文本相互冲突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引发韩国儒者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③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说,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还是气发皆可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甚至放而为恶,原因就在理发未遂或者气发不中。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显或气发而皆中节遂成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述引文中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子学的传统——李滉继承这一传统,也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也是情,而“情”必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遂成人性善恶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①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也就是说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自我反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多次对此图进行修改。“盖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中所载本也。”②此图在李滉《圣学十图》中具有的重要性实在是无需赘言。
李滉还以“七情”与“四端”分论“人心”与“道心”,指出“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也。”③这既是对朱子心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学术上的立异。在李滉看来,道心是义理之心即最高的道德原则,所以他在强调四端七情之差异的同时还特别重视道心人心之分别。虽然其中图未言及“气”,但他论性情仍以理气分言之。“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④这也表明李滉心说承继朱子之传统——倾向以“理气心”论性情,而且主张持教工夫。
在论辩的最后,李滉以《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三书》总结二人观点之异:
既曰“浑沦言之”,安有主理、主气之分?由对举分别言时,有此分耳。亦如朱子谓:“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又云:“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
前书引性言者,只为在性犹可兼理气说,以明情岂可不分理气之意耳,非为论性而言也。“理堕气质以后事”以下,固然,当就此而论。
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碍者乎?而况所谓四端七情者,乃理堕气质以后事,恰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则有明有暗,四端则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固因水之清浊而四端之不中节者,则光虽明而未免有波浪之动者也。伏乞将此道理更入思议,如何?
“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说,尝见先儒有论其不可,今不记得……敢问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者,为发于理耶?为发于气耶?而发而中节,无往不善之善,与四端之善,同欤?异欤?虽发于气,而理乘之为主,故其善同也。且“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谓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则只有理发一边。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未知于先生意如何?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发矣。若欲外此而更求理之发,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弊。前书亦以为禀,而犹复云云。苟曰未然,则朱子所谓“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者,亦不可从也。
道即器,器即道。冲漠之中,万象已具,非实以道为器;即物而理不外是,非实以物为理也。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用朱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也。
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此信写就之后李滉或觉没有必要继续与奇氏论辩,故而未将信寄给他,只是针对奇氏来信中的质问撰文阐述自己的主张。李滉的基本观点是四端七情混沦而言时则无需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但是若将二者对举而言则应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他还以“因说”和“对说”来解释了此问题。直至结束辩论二人仍各持己见,并未达成一致。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以为不仅“性”可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若说奇大升注重于对问题的客观性、逻辑性的阐明,李滉则更着力于对道德性的提高以及修养工夫论域中的主体的省察和践履的意义。
“四端七情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赓续朱子的理气心说,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无怪乎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此种理解,李滉进一步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他对七情的看法始终落在气的一边。他说:“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不能无理,所以“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四端”需要扩充,而易“流于恶”的“七情”则要受检束。因为二者各具相异的性质,如何理解其异中之同便值得认真思考。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说:“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若从客观的视角对情之结构做静态分析的话,便可以得出“四端”为“七情”之一部分的结论。但是在道德践履的意义上,二者又具有相反的性质。比较而言,奇大升关注前者,李滉则更倾向于后者。当然此种差异是相对的。两人真正的分歧源于各自在为学旨趣及问学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的问题意识。
要言之,“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中的核心内容。基于理气二分的立场李滉肯定情的“四七”之分,以为恻隐、善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是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而发,即缘境而出。不过依其理气心,“心气”之性质及所为,如气之清浊、偏杂、粹驳之状态,直接决定四端之呈显以及七情之善恶性质。李滉以为,“气”之状态影响理之显否,故在修养论上他特别主张施以主敬涵养工夫治“心气”之患,使气皆能循理而发以保证理发直遂而不被气所掩。
相关人物
李滉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