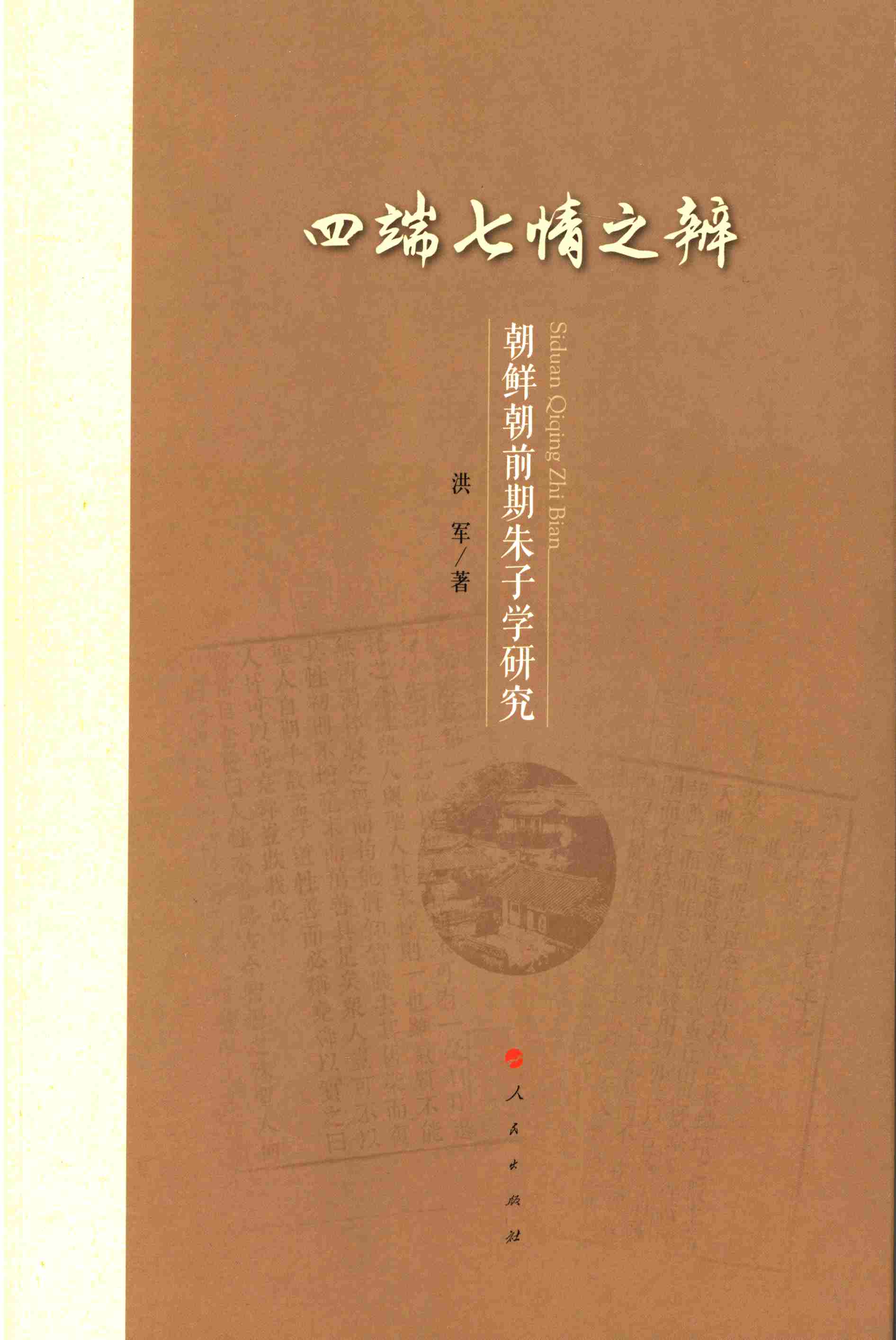内容
高丽末开始传入到朝鲜半岛的朱子学经过14—15世纪的传播与普及,至16世纪已基本发展成熟,开始形成了以主理、主气为理论特色的韩国化的性理学派,即以李滉(1501—1570年)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珥(1536—1584年)为宗的畿湖学派。两派围绕四端七情问题而展开的四七论辩使韩鲜朝性理学的发展走上了以性情论探讨为主的发展轨道。本节和下一节将主要对李滉与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进行论述。
一、李滉的理气论
李滉(字景浩,号退溪、退陶、陶叟)生于燕山君七年(1501年),卒于宣祖三年(1570年),谥号文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东方之朱夫子”。出生于礼安县温溪里(今安东郡陶山面温惠洞)。中宗时文科及第,官至大提学、右赞成。后辞官退隐乡里,闭门静居,钻研学术,以著书立说和授徒讲学为业度过了其一生。曾在家乡礼安选一景色宜人处卜筑“陶山书堂”,作为了其著述和讲学之场所。
李滉年轻时曾写过一首诗,诗中吟道:
露草夭夭绕碧坡,
小塘清活净无沙。
云飞鸟过元相管,
只恐时时燕蹴波。①
从这首哲理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峻别天理人欲之思想倾向早已有之。因此在之后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李滉提出以主理为特色的性理学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于其学问,弟子郑惟一(字子中,号文峰,1533—1576年)曾写道:“先生学问一以程朱为准,敬义夹持,知行并进,表里如一,本末兼举,洞见大原,植立大本,若论其至吾东方一人而已。”①李滉的学说被其后学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岭南退溪学派,影响了此后韩国儒学的发展进路。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首要问题。②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理气“不离不杂”③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鲜朝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说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④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韩儒丁时翰亦曾言道:“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⑤不过,李滉、李珥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之发及理气体用问题而展开。
李滉在接续朱熹“理气二分”说的基础上,依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尊无对”、“理帅气卒”、“理贵气贱”的主张。他说:
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故也。⑥
天即理也,而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是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才有理,便有气眹焉。才有气,便有理从焉。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所谓理者,四德是也;所谓气者,五行是也。①
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然理无为而气有欲。故主于践理者,养气在其中,圣贤是也;偏于养气者,必至于贼性,老庄是也。卫生之道,苟欲充其极致,则匪懈匪躬之职,皆当顿废而后,可庶几。其斁理害正如此,本不可以为训者也。若以为养气亦不可全无,而姑存其书为可,则其中尤近怪无稽者,亦当去之。②从引文中可见,对二者“不杂”之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论的重要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李滉重视其“不杂”之义的目的在于,主要是为了强调理的主宰性、主动性、优位性。由是在二者关系上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如其所言,“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等等。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他把朱熹的理气“先后”⑤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同时也为其“四七理气”论打下理论基础。
在东亚儒学史上,李滉性理学的“理”论极富特色,不过“理”亦是其性理学说中最为难解处。李滉本人也曾言道“理”字最为难知,对于缘由他写道:
凡人言理,孰不曰无形体、无分段、无内外、无大小、无精粗、无物我、虚而实、无而有哉。但真知其实无形体、实无分段、实无内外、实无大小、实无精粗、实无物我、实为虚而实、实为无而有为难。此某所以平日每云理字难知也。①
李滉为学一向主张学贵穷理,因为在他看来若对理有所未明,则或读书,或遇事都不能做到无碍。所谓“理有未明”,即是指学者还未做到对理字之义的“真知”。那么,何谓其所言之“真知妙解到十分处”呢?李滉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盖尝深思古今人学问道术之所以差者,只为理字难知故耳。所谓理字难知者,非略知之为难,真知妙解到十分处为难耳。若能穷究众理到得十分透彻,洞见得此个物事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洁洁净净地,一毫添不得,一毫减不得,能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而不囿于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中,安有杂气而认为一体,看作一物耶。其于道义,只见其无穷,在彼在我,何有于町畦,其听人言,惟是之从,如冻解春融,何容私意之坚执。任重道悠,终身事业,安有欲速之为患哉。假有初间误入,一闻人规,便能自改而图新,安忍护前而无意于回头乎。诚恐循此不变,处而论道,则惑于后生,出而用世,则害于政事,非细故也。其以博览群书为非,而欲人默思自得,其意之落在一边,可知。公之报书,所以正其偏而砭其病者得矣。②
这是李滉答奇大升信中的一段话,也集中反映了在其哲学中“理”概念所具有的基本义涵。由以上引文内容所见,在其学说中“理”既是一个具无形、无质、无为之特性的形上之存有,又是一个指代实理的“天理”。而且,“理”又兼体用,既有无声、无臭、无方体之“体”,又有至神至用之“用”。③对于这样的“理”,李滉在文中进行了多角度的阐发,认为古今人学问道术之所以差者,只是因为“理”字难知之故。所谓“理”字难知,不是指略知之为难,而是将之真知妙解到十分处为难的意思。认为,只有“穷究众理到得十分透彻,洞见得此个物事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处,才能算是真正知“理”。
从“虚实”、“有无”等角度论述“理”本体的同时,李滉在答复奇大升问难的信中还提出理有体用说,曰:“无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体也。其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见于本体之无为,而不知妙用之能显行,殆若认理为死物,其去道不亦远甚矣乎。”①实际上,理有体用说是为其“四七理气互发”说作了理论铺垫。
进而,李滉还提出“理非静有而动无,气亦非静无而动有”的理(太极)自有动静的思想,明确地肯定了理的发用性。李滉曰:
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但就无极二五妙合而凝,化生万物处看,若有主宰者运用而使其如此者。即书所谓惟皇上帝将衷于下民,程子所谓以主宰谓之帝是也。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②
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勉斋说,亦不必如此也。何者,理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阳生阴也。③由此,在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便有了理气互发之论。他对理本体所作的这一解释,不仅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④的朱学内在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可能,而且还积极回应了以“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原,理何足尚”⑤为由对朱学理气说提出质疑的明初朱子学者们的诘难。但是,对其理发说需做进一步的解释。李滉亲身经历朝鲜朝多起“士祸”,统治阶级内部血腥的权力斗争致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社会道义及生命的尊严荡然无存。作为生活于此一时代的大哲学家李滉势必将重塑社会纲纪,提高伦理意识以及加强道德教化视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对李滉来讲,如何保存和扩充源于天理的人性本然之纯粹性就成为其首先要思考的哲学课题。故他所追求的是此种性理的自然呈现或良知之心的自我坎陷。李滉的这一主张看似与陆王心学的良知说有些相近之处,但其根本立场是基于人的道德心理和伦理行为意义上的性理发用,并非为王学意义上的“致良知”,更不是本体论(宇宙论)向度上的“太极”之自动静。理发论在其学说中之所以能够得到成立,还与其对“理”特殊规定相关。前文已言及在其“理”论中,理具有“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之特性,“理”具有绝对性。而且,在“气”论中他亦对之作了相应之规定。要言之,强调道德心理和伦理行为意义上的理(性)之发用性、主宰性、优位性,是李滉理气论区别于朱子理气论的紧要处,学者于此处应仔细玩味和体会。
那么,相较于“理”,“气”在李滉哲学中具有何种特性呢?李滉认为,因为“气”是有形之物,故气有限量而理无限量,气有生死而理无生死之说①。
盖理本无有无,而犹有以有无言者。若气则至而伸,聚而形为有,反而归,散而灭为无,安得谓无有无耶。或别有所据,某未记耶,气之散也,自然消尽而泯灭。②
然滉前以为气散即无。近来细思,此亦偏而未尽。凡阴阳往来消息,莫不有渐,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然则既伸而反于屈,其伸之余者,不应顿尽,当以渐也。既屈而至于无,其屈之余者,亦不应顿无,岂不以渐乎。故凡人死之鬼,其初不至遽亡,其亡有渐。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非谓无其理,而姑设此以慰孝子之心,理正如此故也。由是观之,孔子答宰我之问,亦无可疑矣。以眼前事物言之,火既灭,炉中犹有熏热,久而方尽。夏月,日既落,余炎犹在,至夜阴盛而方歇,皆一理也。但无久而恒存,亦无将已屈之气为方伸之气耳。①可见,“气”在李滉哲学中具有生死、聚散之特性。他以为,没有恒久不变之气,气的聚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举炉中火苗渐渐熄灭和夏日白天之暑热至夜缓解为例详加阐述。
李滉进而还提出气之原初无不善的主张,曰:
气之始无不善,乃气生源头处,非禀受之初也。然气有一日之始,有一月之始,有一时之始,有一岁之始,有一元之始,然此亦概举而言之耳。推来推去,其变无穷,当随处活看,不可执定为某气之始。苟指认一处为定则不通,不足以语造化之妙。②
那么,其无不善之“气”是否与李珥“湛一清虚”之气泯然无别呢?对此,李滉解释说:“程子心本善之说,朱子以为微有未稳者。盖既谓之心,已是兼理气,气便不能无夹杂在这里。则人固有不待发于思虑动作,而不善之根株已在方寸中者,安得谓之善,故谓之未稳。然本于初而言,则心之未发,气未用事,本体虚明之时,则固无不善。故他日论此,又谓指心之本体,以发明程子之意,则非终以为未稳,可知矣。”③可知,其所言“气之始无不善”是指心之未发而本体虚明之时。这与徐敬德、李珥哲学中的“气”概念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李滉对此进一步解释道:“湛一气之本。当此时,未可谓之恶,然气何能纯善?惟是气未用事时,理为主故纯善耳。”④这一解释对理解其“四七”论极为重要。因为依李滉之见,“气”只有听命于理或顺理而发的时候才能呈现为善。但是,又不能将“气顺理而发”称之为“理之发”。“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于此可见,其“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之说实乃根于其特殊的“气”论思想。
李滉还从价值论维度对理气概念作了“理纯善而气兼善恶”的价值规定。“理纯善而气兼善恶”之说其实承自程颐、朱熹的理学思想。气有清浊,由其清浊而言,气有或循理或不循理之可能。因此,要施以主敬工夫“以理驭气”。理是纯善,而气兼善恶,故以纯善之理帅“气”则“气”能循理而直遂。这便是所谓“理帅气卒”的思想。李滉的尊理贬气(理贵气贱)的观念,与其“理纯善而气兼善恶”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他进而又从伦理道德的意义上,作出“理极尊而无对”、“理贵而气贱”的理优位论之规定。既保持了传统理学所崇尚的等级价值观,又体现了其独创性的一面。理既“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②,那么理气关系即为主宰与被主宰的上下位关系。上者尊贵而下者卑贱,所以李滉指出:“理贵气贱,然理无为气有欲。”③在存养省察的工夫上,他特别强调主敬,惟其如此才能达到“以理驭气”使“气”顺理而发的目的。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兼论郑之云的《天命图》与“四端七情”论
在论述李滉的“四七理气”论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郑之云与其《天命图》。因为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郑氏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引致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李滉曾对郑之云称赞道:“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我妄以结状其难……有契有违,往返弗置,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④
郑氏是继权近、柳崇祖之后又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韩国性理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不仅为此后李滉和李珥等人的“四七理气”之辨提供了理论端绪,而且还开启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四端七情理论研究之先河。
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稼翁,1509—1561年)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曾受教于为金安国和金正国。郑氏世居高阳,本贯则为庆州。他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之辨发端于郑氏之《天命图》。对于自己的作图过程,他在《天命图序》中写道:
正德己卯(中宗十四年,1519年——引者注)思斋金先生被微谴而退卜居于高峰之芒洞,洞实之云所居里也,尝游其门受学焉。嘉靖戊戌(中宗三十三年,1538年——引者注)先生被召还朝,之云失其依归,与舍弟之霖学于家。论及天人之道,则之霖以幼学患其无据,莫能窥测。余于是试取朱子之说(见《性理大全》论人物之性),参以诸说设为一图,而又为问答名曰《天命图说》日与舍弟讲之。此非欲示诸人而作也,然图说既草,则亦不可不见正于长者,遂取质于慕斋思斋两先生,两先生不深责之,且曰:“未可轻议,姑俟后日。”不幸,两先生相继以没,呜呼,痛哉。由是此图之草,无所见正,而余之学问日就荒芜,几不能自振。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误闻不肖之名,躬行者再三之,云感其殷勤,斋木以进。退溪欣然出见,因语及《天命图》,之云以直告知,因请证之意,退溪稍假肯色。余退而私自贺曰:“吾丧两先生后,意谓更不得贤师友而求进,今得退溪,吾无忧矣。”常往来质问是图,退溪证以古说,参用己意,补其所欠,删其所剩,卒成完图。其赐己以厚,又从而为之说,附其后而教之,其幸孰大焉。非徒余之幸也,在昔日两先生姑竢后日之志,今始副焉,是尤幸之大也。余故首记作图之由次及定图之事,以藏于家。如有同志者出,其亦有以知退溪考证之意也。①
文中郑氏较完整地记述了此图的写作过程。他采先儒之论并以图解以明之,目的在于启子弟之蒙。此图取名为《天命图》——“天命”二字典出《中庸》首句,可见其以《中庸》为性理学之基础。为了说明天人相与之道,郑之云在《天命图解》①中使用了诸如理气、心性、太极、道等性理学概念,并用这些概念对天人之际进行了理气论的说明,旨在揭示了天人合一之根据。他还从理气论的角度对人的心性以及善恶问题进行了说明,此即所谓“四端七情”论。尽管郑之云并未将“四七”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来论述,而只视作探究天人合一的根据之一,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四七”论在其性理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②因为前者只是从其性理学整体构成之维度而言的。
此文写于嘉靖甲寅(明宗九年,1554年)之正月,此时退溪李滉已是年过五十的一代儒学名宿,思想也已渐趋成熟。他获得此图后,将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并在语气上作了改动。李滉的这一订正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尤其是奇大升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发展成为左右韩国性理学发展走向的学术论争。
郑之云在阐发其性理学说时,也意识到单纯凭借“气”论是很难对“恶”的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的。于是,他对阴阳之气赋予了善恶的价值含义。如把气分为清、浊、明、暗等。主张阳气清明,故可跻于善;阴气浊暗,故可流为恶。他断言“恶”的现象是由阴气所致,由此维护了“理”的纯善性。而且,还提出阴阳之气只是与心动之后的发用相关,并非各自独自发用的观点。这就消除了人的恶行的先天可能性。郑氏还认为,若心之发“意”根于性且其气属阳的话,天理会如实呈显;相反,如“意”与物相杂而其气属阴,则天理就会失去其真实性,终流于恶。依他之见,人的善恶行为取决于自由意志,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郑氏性理学追求“天人心性合一”,这表明他是韩国性理学史上的主流派学者。与中国的朱子学相比,韩国性理学以“图说类”诠释模式见长。从《天命图》在韩国性理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窥见郑之云在此一传统中的独特地位。①其“四七”理论的首要意义就是肯定人的道德行为(“人性善”)的先天可能性,此为性理学最根本的哲学观念。《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乃其天理观的来源和根据。实际上,性理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探讨的目的则是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寻找一个本体论的根据,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根据。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万物有机体观”正是性理学家们这一思想的反映。理与气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是为了证明这一思想。性理学家们以理气概念探讨道德行为之根源,尤其注重主宰人的行为的“心”的研讨,这也是心性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心性论中,与对心性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有关修养工夫的问题,即如何使心性向“善”的问题。欲解决之,首先要探讨“恶”的根源及来源。所以从理气论维度对“恶”之根源进行探讨也是心性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其中,“四端七情”之探讨是对人的本性的深层剖析,目的在于扩充良知所彰显的内心之善以上合天理。②实际上,他的这一思想根于孟子的性善说,欲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把握性与天道的关系。
可见,郑之云是韩国儒学史上继阳村权近、真一斋柳崇祖之后又一位坚持“天人心性合一”这一韩国性理学传统的学者。在韩国儒学史上,他还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性理学相关理论的学者。③尽管其理论仍显得较为简单缺乏系统性,但在《天命图解》及《天命图说》中所见的理论探索还是对性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了一定的概括和整理。所以李滉“君曾测海”的评价对他而言还是较为中肯的。郑之云的主要著作有《天命图解》以及《天命图说》。
李滉将其《天命图解》改订之后,首先遭到奇大升的发难。奇氏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又说过“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混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②。 在奇大升看来,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举,谓之纯理或兼气就有些不妥。奇氏主张四端虽由纯粹的天理所发,但只是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奇大升进一步评论说: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③
他认为四端与七情作为情感皆性状相似,而非有截然相反之特质。因此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学原论的。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回答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盖欲相资以讲明,非谓其言之无疵也。今者,蒙示辩说,摘抉差谬,开晓谆悉,警益深矣。然犹有所不能无惑者,请试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首先说明了其将郑氏之“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进行改动的缘由,他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认为先儒未有将“四端七情”分置于理与气的范畴来讨论的先例。李滉还是认可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在这一问题上他有过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首度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进行修订时的说法。李滉将郑氏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这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其实此两句从内涵到语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请参见新、旧天命图(图7、图8)。
起初他认为此说“本晦庵说,其理晓然矣”③,其时还未与奇大升展开论辩。二是在与奇氏进行论辩过程中有了第二种表述,即“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④。这是己未年李滉59岁(1559年)时的观点。当此之际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理气”之辨。加之李滉又恰好读到朱子的“四端是发于理,七情是发于气”一句,于是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与奇大升的信中提到:“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三是经奇大升之诘难后便有了新的说法——“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②。此后李滉对这一说法再未作改动,可视为其最终定论。对最后一说,他在其晚年代表作《圣学十图》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③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正是李滉性理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
他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本上的差异,这源于其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①
由此可知,在心性情的关系上李滉倾向张载的“心统性情”说。他将“心”理解为“理气之合”——与朱子“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的观念相比,心的含义以及与理、气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以此说为理论前提,可以分属理气的方式准确表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以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
四端七情之辨实质是性情之辨。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作为李滉晚年思想结晶的《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则为李滉所作。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概念。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此为性理学的主题。性理学的道德主体论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①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如此则性为体而情为用。朱熹认为“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②。与之不同,李滉进一步发挥朱熹的理气心性说并将性情与理气之发相结合,从而将朱子学的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端七情理气”论。此图的中、下两图乃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③对于“七情”的善恶,李滉起初以为“七情,善恶未定也”④。经与奇大升往复论辩之后改为“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故其发而中节者乃谓之和”⑤。这一改动容易造成七情之“善”和四端之“善”之混同,所以对之需作仔细辨析。四端之情是人的道德感情亦即良心。四端之“善”是纯粹的且还带有道德色彩。但是七情则与此不同,原是与道德情感无关之情。作为自然情感,七情在“性发为情”之后才能以发用是否为“中节”衡量其善恶。因此如李滉早年所言,它还是“善恶之未定”。那么,应如何理解其修订后的说法呢?我们可以从其“本善”一语中去寻找。“善”被赋予道德含义之前,“好”是其概念的核心内容。易言之,善是规定事物之好的状态,道德性的善也是如此。“七情”作为原始的自然的感情本是好的感情,只因具有“过或不及”的性质,容易“流于恶”。①其修订后的说法可以按此思路去解读。
对于下图李滉解释说:“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②
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和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遵循程朱“情根于性,性发为情”之原则,依此解读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和无不善之情。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我们也可以一窥李滉试图融合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正是两种权威文本相互冲突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引发韩国儒者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③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说,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还是气发皆可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甚至放而为恶,原因就在理发未遂或者气发不中。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显或气发而皆中节遂成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述引文中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子学的传统——李滉继承这一传统,也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也是情,而“情”必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遂成人性善恶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①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也就是说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自我反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多次对此图进行修改。“盖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中所载本也。”②此图在李滉《圣学十图》中具有的重要性实在是无需赘言。
李滉还以“七情”与“四端”分论“人心”与“道心”,指出“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也。”③这既是对朱子心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学术上的立异。在李滉看来,道心是义理之心即最高的道德原则,所以他在强调四端七情之差异的同时还特别重视道心人心之分别。虽然其中图未言及“气”,但他论性情仍以理气分言之。“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④这也表明李滉心说承继朱子之传统——倾向以“理气心”论性情,而且主张持教工夫。
在论辩的最后,李滉以《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三书》总结二人观点之异:
既曰“浑沦言之”,安有主理、主气之分?由对举分别言时,有此分耳。亦如朱子谓:“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又云:“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
前书引性言者,只为在性犹可兼理气说,以明情岂可不分理气之意耳,非为论性而言也。“理堕气质以后事”以下,固然,当就此而论。
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碍者乎?而况所谓四端七情者,乃理堕气质以后事,恰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则有明有暗,四端则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固因水之清浊而四端之不中节者,则光虽明而未免有波浪之动者也。伏乞将此道理更入思议,如何?
“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说,尝见先儒有论其不可,今不记得……敢问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者,为发于理耶?为发于气耶?而发而中节,无往不善之善,与四端之善,同欤?异欤?虽发于气,而理乘之为主,故其善同也。且“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谓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则只有理发一边。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未知于先生意如何?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发矣。若欲外此而更求理之发,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弊。前书亦以为禀,而犹复云云。苟曰未然,则朱子所谓“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者,亦不可从也。
道即器,器即道。冲漠之中,万象已具,非实以道为器;即物而理不外是,非实以物为理也。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用朱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也。
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此信写就之后李滉或觉没有必要继续与奇氏论辩,故而未将信寄给他,只是针对奇氏来信中的质问撰文阐述自己的主张。李滉的基本观点是四端七情混沦而言时则无需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但是若将二者对举而言则应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他还以“因说”和“对说”来解释了此问题。直至结束辩论二人仍各持己见,并未达成一致。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以为不仅“性”可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若说奇大升注重于对问题的客观性、逻辑性的阐明,李滉则更着力于对道德性的提高以及修养工夫论域中的主体的省察和践履的意义。
“四端七情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赓续朱子的理气心说,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无怪乎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此种理解,李滉进一步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他对七情的看法始终落在气的一边。他说:“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不能无理,所以“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四端”需要扩充,而易“流于恶”的“七情”则要受检束。因为二者各具相异的性质,如何理解其异中之同便值得认真思考。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说:“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若从客观的视角对情之结构做静态分析的话,便可以得出“四端”为“七情”之一部分的结论。但是在道德践履的意义上,二者又具有相反的性质。比较而言,奇大升关注前者,李滉则更倾向于后者。当然此种差异是相对的。两人真正的分歧源于各自在为学旨趣及问学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的问题意识。
要言之,“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中的核心内容。基于理气二分的立场李滉肯定情的“四七”之分,以为恻隐、善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是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而发,即缘境而出。不过依其理气心,“心气”之性质及所为,如气之清浊、偏杂、粹驳之状态,直接决定四端之呈显以及七情之善恶性质。李滉以为,“气”之状态影响理之显否,故在修养论上他特别主张施以主敬涵养工夫治“心气”之患,使气皆能循理而发以保证理发直遂而不被气所掩。
三、李滉的主敬论——以《圣学十图》为中心
李滉之学亦被称为主敬之学。因此下面将通过对《圣学十图》的分析来探讨其以主敬说为特色的性理哲学思想。
《退溪全书》“言行录”中记载,其门人金诚一将其学问概括为“试举其学大概,则主敬之工,贯始终兼动静,而尤严于幽独肆之地,穷理之功,一体用该本末,而深造于真知实得之境,用功于日用语默之常”。①主敬思想的基本论纲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敬以直内,涵养本心;义以方外,省察行事。尽管李滉所依傍的是程朱的主敬之说,但是其主敬之说知行并重,贯始终兼动静。其学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又比程朱更强调“心”之作用和效用,也因之更加明确地揭示了“敬”之为学工夫与进入圣贤域以达至圣人的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
作为“东方之朱夫子”,李滉为学服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对朱子学的理气心性诸说多有发明。李氏68岁(宣祖元年,1568年)时进呈宣祖的《圣学十图》更是其学问宏纲大目的集中反映,也是其一生学问的思想结晶。可谓“晚年深思熟虑,提纲挈领的结晶,也是他体认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心得。李滉独以图的形式,既示人以圣学入道之门,亦给人以简明易懂的启迪。《圣学十图》,融铸宋明理学之精髓,构成他的思想逻辑结构,其规模之宏大,操履之功用,在李朝理学史上均属罕见”②。《圣学十图》由《进圣学十图札》和《圣学十图》组成。所谓十图包括:第一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第二图为程复心(字子见,号林隐,1279—1368年)绘的张载的《西铭图》;第三图为李退溪绘的朱子的《小学图》;第四图为阳村权近绘的朱子的《大学图》;第五图为李滉绘的朱子的《白鹿洞规图》;第六图为《心统性情图》(上图由程复心作,中、下二图由李滉作);第七图为朱子的《仁说图》;第八图为程复心绘的《心学图》;第九图为王柏(字会之,号鲁斋,1197—1274年)绘的朱子的《敬斋箴图》;第十图为李退溪绘的陈柏(字茂卿,号南塘,元儒)的《夙兴夜寐箴图》。对于上述十图,李滉还做了相应的引述和说明,指出前五图是“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③,后五图则是“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④。综观十图,“敬”①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纲目。
《圣学十图》的排列次序不仅体现了李滉哲学的逻辑结构,而且还反映了其对儒学(圣学)的全部理解。第一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李滉对此解释说:
朱子谓此是道理大头脑处。又以为百世道术渊源。今兹首揭此图,亦犹《近思录》以此说为首之意。盖学圣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于小学大学之类,及其收功之日,而溯极一源,则所谓实理尽性而至于命,所谓穷神知化,德之盛者也。②
朱熹立学极重周敦颐之《太极图》,此图可说奠定了“濂溪先生”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开山之祖的地位。李滉认为太极即是宇宙本体(天道),故将《太极图》视为百世道术之渊源亦即一切思想学说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强调学圣人者要“求端自此”。李滉将周敦颐的《太极图》理解为对《周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义的阐发。依李滉之见,圣人是“与天合德,而人极以立”,因此圣人之学便是继天立极之学。他认为此图的目的在于阐明圣学的理论根据,而且还揭示如何以抵达圣域的修养工夫。李滉进而引用朱子的《太极图说解》以作说明:“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间而已矣。敬则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静虚动直,而圣可学矣。”③《太极图》表明了以“敬”为核心的为学路数,具有将天道、地道和人道加以融合以作整体观照之特性。而其他九图皆为此图(“立太极”和“立人极”)的进一步展开。此其所以《近思录》、《性理大全》等开篇即设有《太极图》——李滉可以说继承了这一理学传统。
第二图为《西铭图》,旨在揭示天道的进一步展开。该图试图从对“求仁”的深刻体悟中阐明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道理。李滉以为“圣学在于求仁,须深体此意,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一体,真实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味,免于莽荡无交涉之患,又无认物为已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体也。又曰:充得尽时,圣人也。”①这是李滉体仁的最高境界,于此彻悟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强调物我一体论与事亲事天之实践,他在《西铭图》图说中写道:“朱子曰……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②天道以仁为本质。人只有懂得其所具之仁便是天地生生之理(太极),才能扩而充之与天地生生之理的合而为一,从而达到民胞物与的境界。这就需要通过心性修养、涵养工夫以提高人的素质,方能使其内心之德臻于完满。李滉将《太极图》与《西铭图》视为理学形而上学理论和修养工夫的根据,即小学大学的标准本原。“上二图,是求端扩充,体天尽道,极致之处,为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下六图,是明善诚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③
正是基于此种考量,李滉分别以《小学图》、《大学图》和《白鹿洞规图》为第三、四、五图。《小学》是朱熹所编的一个以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本。朱子极重小学,将其与大学并列。朱子学传入之初,朝鲜朝儒者便对《小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阳村权近曾写道:“小学之书,切于人伦世道为甚大,今之学者皆莫之习,甚不可也。自今京外教授官,须令生徒先读此书,然后方许他经。其赴生员之试,欲入大学者,令成均馆正录所先考此书通否,乃许赴试,永为恒试。”④李滉在《小学图》中,援引朱子的《大学或问》写道:“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涵养本原,而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⑤从中亦可看出李滉对小学的重视。他在继承和发展朱子思想的基础上,以敬身明伦为旨归将小学教育的组织、内容、目的、宗旨提纲挈领。《小学图》反映了李滉强调实践、注重践履的为学性格。李滉根据朱熹的《小学》一书的目录制作此图,以与《大学图》对举。在他看来小学和大学相反相成,是“一而二、二而一”①的关系。前文已言及《大学图》乃朝鲜朝初期的阳村权近所造。“大抵《大学》一书,一举目,一投踵,而精进本末,都在此。”②《大学》是被朱熹视作学者入德“行程节次”③的一本书,亦是其平生用力最久、最甚的一部儒家经典。朱子曾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全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④李滉认为为学者只要按此“行程节次”认真践履、勇猛精进便可达至圣域。《大学图》的特色在于引述朱子《大学或问》的论“敬”之说以为圣学的始终之要。“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尝以主一无适言之,尝以整齐严肃言之;门人谢氏之说,则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有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小学之赖此以始,则夫大学不能无赖于此以为终者,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盖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则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是诚意正心以修身,则所谓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乎天下,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离乎敬也,然则,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⑤本段引文对李滉《圣学十图》的主敬思想影响甚大。尊德性而道问学、居敬而穷理是理学的基本立场,朱熹曾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⑥认为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存养,不过朱熹实际上以“穷理”、“致知”为先。李滉指出:“非但二说(即《小学图》与《大学图》所引朱子论教之说)当通看,并与上下八图,皆当通此二图而看……下六图是明善诚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而敬又彻上彻下,着功收效,皆当从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之说如彼,而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①由此可见,“敬”在李滉哲学中并不仅仅是彻上彻下、贯穿动静始终之修养工夫,而且还是可以统摄存心养性与格物致知的圣学第一要义。《圣学十图》即是其主敬思想的集中体现。第五图《白鹿洞规图》是李滉依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而作,旨在阐明人伦之道。“盖唐虞之教在五品,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故规之穷理力行,皆本于五伦。”②李滉认为大学是小学阶段的延续,而两阶段的教育有着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穷理、力行)、在止于至善,而小学之宗旨则为在明人伦(五伦),所以说“此两图可以兼收相备”③。《白鹿洞规图》意在综合小学、大学的为学之方,着重突出五伦作为圣学内容的重要地位。另外,从《白鹿洞规图》中亦可看出李滉的书院教育思想。李滉以为以上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④。
心、性、情是理学人性论的核心范畴,第六图即为《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此图在上一节已有论及,这里只做简要介绍。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下图为李滉所作。在朝鲜朝儒学史上,主要论辩皆围绕“心”这一哲学范畴而展开。16世纪后半期的“四端七情”之辨、“人心道心”之辨、18世纪初叶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以及19世纪后半期的本心明德之“主理主气”论辩等均是对“心”之发用及相关问题的深入辨析。此为韩国性理学的特色所在。
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理学的主题。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就是通过“心性情”等范畴全面展开。⑤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一言蔽之即性为体情为用。朱熹认为“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①。李滉则与之不同。他进一步发挥程朱理气心性说,将性情之说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并将朱学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七理气”之辨。《心统性情图》之中图和下图将李滉理气心性诸说表述得最为简单明了。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秉承之,亦主“合理气,统性情”。但是,李滉比朱熹更专注于对“情”的探讨。重“情”乃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理气心”。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此心具心气之患)的“情”皆能中节便成为心性修养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气之患,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故其曰:“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②其持敬之目的就是要由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之际反观内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对此图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第一图的结构原是智上礼下仁左义右,先是对其中礼智上下结构进行改动,后来又对原图中的仁义左右次序做了修改。最后还是以第二次改动的为定本,收录十图之中。③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第七图为朱熹自作的《仁说图》。李滉曾将此图放于《心学图》之后,后接受李珥的建议移至《心学图》之前。他在给李珥的复信中写道:“《仁说图》当在《心学图》之前,此说甚好,此见解甚超诣。滉去年归来,始审得当如此,及得来说而益信之,即已依此说互易矣。”①由此亦可窥出《圣学十图》中各图的排列次序是经过了反复斟酌与思考。该图进一步说明了四德相互之间以及其与四端之间的关系。“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未发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则包乎四者。”②“仁”作为统摄“四德”与“四端”的道德理性,在理学中不仅与太极、诚以及中和等概念同等重要,而且还指代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人和天地生物皆以之为心。李滉将朱子学的仁说视为上承天道下启存养之途,亦即贯通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节点。这应该是李滉最终把此图置于《心学图》之前的重要原因。由其“圣学在于求仁”之见以及此图“发明仁道,无复余蕴”之说可以推知,在李滉的心目中人君者欲施仁政亦应于此图求其义。故《仁说图》在《圣学十图》中亦居重要地位。
第八图为程复心所绘《心学图》。李滉将此图目为天地生物之心(仁)的着足处。李滉性理学“求仁”之目的在于使人不断完善其人格,以优入于圣域。“此仁者,所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足以普四海弥六合也。”③《心学图》把“心”分为赤子心与大人心、人心与道心,也是为了给人提供实现理想人格的修养工夫。学者只有“惟精择善,惟一固执”,才能克去己私以存天理。所以必须施以“持敬”工夫使人心变为道心。唯有以“敬”抑欲才能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加之“敬”又是一心之主宰,存理遏欲的工夫大可统一到“敬”字上来。就此而言,“存天理遏人欲”是主敬工夫之实质内容。对《圣学十图》中的后五图,李滉认为“五图原于心性,而要在免日用崇敬畏”④。他在第六、第七图中着力探究主体之性情问题后,便将“天地生物之心”作为仁之根据。李滉在第八图中又论述了与“心”相关之问题,并指出了治心之工夫以及“敬”作为一心之主宰在涵养省察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第九图为金华王鲁斋柏就朱熹《敬斋箴》绘制的《敬斋箴图》,此箴乃朱熹有感于张敬夫的“主一箴”所作。若说第八图示“圣学心法”,那么此图则“为圣学之始终”。此图承《心学图》之旨,继续以“敬”为工夫之要以示具体的用工地头。在图说中,李滉引真西山之言曰:“敬之为义,至是无复余蕴,有志于圣学者,宜熟复之。”①这表明李滉不仅将“敬”视为其存养工夫的关键,而且还视为其性理学体系之核心。他在答李叔献(李珥)的信中写道:“惟十分勉力于穷理居敬之工。而二者之方,则《大学》见之矣,《章句》明之矣,《或问》尽之矣。足下方读此书,而犹患夫未有所得者,得非有见于文义,而未见于身心性情之间耶。虽见于身心性情,而或不能真切体验,实味膏腴耶。二者虽相首尾,而实是两段工夫,切勿以分段为忧,惟必以互进为法,勿为等待。即今便可下工,勿为迟疑。”②《敬斋箴》内容如下:“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参以三,惟心惟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弗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论,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灵台。”③这些可视为“敬”的具体细目,可以此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李滉还依据陈柏的《夙兴夜寐箴》绘制《夙兴夜寐箴图》④以为第十图。他认为“敬斋箴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其地头而排列为图。此箴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其时分而排列为图。”⑤第九图《敬斋箴图》与第十图《夙兴夜寐箴图》一是以地头言,一是以时刻言。①即,前者按行事罗列,是以心为核心展开的主敬工夫;后者是依时间编排,是以行为核心演绎的持敬规范。②李滉曰:“盖敬斋箴,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时其地头而配列为图。此箴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时分而配列为图。”③但道之流行于日用之间,无所适而不在,亦无顷刻之或停,因此李滉强调不分时分与地头的主敬工夫。两者在李滉性理学中相互发明、相互补充均为相当紧要,因之李滉言二者须并进。
《圣学十图》前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体现了《太极图》融自然本体、社会教育、人格培养为一体的思想;后五图则“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与前五图恰好构成不即不离的体用关系。前五图以无极太极为第一图,后五图以心统性情为第一图。这个划分不以天道人心为二,而是将二者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形而上本体遂与人世间的心性冥冥相通,立人极也就可以进而立太极。④易言之,后五图则展示心体(天道)呈现之修养过程。“综观此十图,其核心是人。因此,李退溪的圣学,我们亦可称为人学,即学做圣人之学。《圣学十图》,就是学做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情感意志等等。全面、系统而又渐次深入地论述了为圣的目的、方法。”⑤依李滉之见,除了“心”之外再没有完成自我人格的原动力。关键在于如何克去除理气心所具有的心气之患,从而使心气循理而行、顺理而为。这就要求学者时刻以“敬”字治心、以“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⑥。显而易见,以持敬工夫统摄心知乃是李滉主敬论的主要意涵。
由上所述可知,李滉主敬思想根植于其对性理学理气心性诸说的理解。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七情之善与不善端视发而中节与否——一切都随“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其实此时四端与七情皆滑入气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皆为气之所为。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皆为气之所为。所以主敬以治心上之“气患”,使气顺理而发、循理而行,这就是以主敬说为特色的李滉思想的根本主旨。
简言之,李滉以“敬”贯动静、知行并重以及内外如一为其主敬思想的方法论,由此构筑了以主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绘制的《圣学十图》以图画的形式将程朱理学中繁杂的主敬思想做了言简意赅的表述。此图既是主敬工夫的形象说明,也是李滉思想的简明提要。
“敬”作为理学修养的重要方法受到程朱诸儒的重视。朱子以为“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程子亦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语最妙”②。但是程朱诸儒并未以此为纲领构筑其道德形上学体系。朱子去世三百年后,号为“海东朱子”的李滉却以“敬”为核心构筑了颇具理论与践履特色的“实践道德哲学”(后人亦将之称为退溪“圣学”或退溪“心学”),遂集朝鲜朝的朱子学思想之大成。李滉对“敬”的强调与对“敬”的意义的理解确有超过朱子处。③以此为特色,退溪学代表了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李滉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坚持二者是不同类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④李滉还制作“心统性情图”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工夫论方面,李滉极重主敬,以下学上达为其居敬穷理之出发点。“只将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以验夫统体操存不作两段者为何等意味,方始有实用功处,脚跟着地,可渐渐进步,至于用功之久,积熟昭融,而有会于一原之妙,则心性动静之说不待辩论而嘿喻于心矣。”①他主张由下学上达之持敬修养工夫优入圣贤之域,从而体验天理之极致。由此可知李滉的道德学问观以及其为学的根本宗旨。“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②,李滉在知与行方面忠实履行了儒家之为学宗旨,堪称朝鲜朝五百年间难得的为己之学之楷模。
他的思想不仅对韩国性理学界影响至深,而且还对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启蒙传疑》、《自省录》、《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圣学十图》、《论四端七情书辨》等,均收录在《增补退溪全书》(1—5册)之中。
一、李滉的理气论
李滉(字景浩,号退溪、退陶、陶叟)生于燕山君七年(1501年),卒于宣祖三年(1570年),谥号文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东方之朱夫子”。出生于礼安县温溪里(今安东郡陶山面温惠洞)。中宗时文科及第,官至大提学、右赞成。后辞官退隐乡里,闭门静居,钻研学术,以著书立说和授徒讲学为业度过了其一生。曾在家乡礼安选一景色宜人处卜筑“陶山书堂”,作为了其著述和讲学之场所。
李滉年轻时曾写过一首诗,诗中吟道:
露草夭夭绕碧坡,
小塘清活净无沙。
云飞鸟过元相管,
只恐时时燕蹴波。①
从这首哲理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峻别天理人欲之思想倾向早已有之。因此在之后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李滉提出以主理为特色的性理学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于其学问,弟子郑惟一(字子中,号文峰,1533—1576年)曾写道:“先生学问一以程朱为准,敬义夹持,知行并进,表里如一,本末兼举,洞见大原,植立大本,若论其至吾东方一人而已。”①李滉的学说被其后学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岭南退溪学派,影响了此后韩国儒学的发展进路。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首要问题。②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理气“不离不杂”③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鲜朝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说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④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韩儒丁时翰亦曾言道:“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⑤不过,李滉、李珥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之发及理气体用问题而展开。
李滉在接续朱熹“理气二分”说的基础上,依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尊无对”、“理帅气卒”、“理贵气贱”的主张。他说:
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故也。⑥
天即理也,而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是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才有理,便有气眹焉。才有气,便有理从焉。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所谓理者,四德是也;所谓气者,五行是也。①
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然理无为而气有欲。故主于践理者,养气在其中,圣贤是也;偏于养气者,必至于贼性,老庄是也。卫生之道,苟欲充其极致,则匪懈匪躬之职,皆当顿废而后,可庶几。其斁理害正如此,本不可以为训者也。若以为养气亦不可全无,而姑存其书为可,则其中尤近怪无稽者,亦当去之。②从引文中可见,对二者“不杂”之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论的重要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李滉重视其“不杂”之义的目的在于,主要是为了强调理的主宰性、主动性、优位性。由是在二者关系上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如其所言,“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等等。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他把朱熹的理气“先后”⑤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同时也为其“四七理气”论打下理论基础。
在东亚儒学史上,李滉性理学的“理”论极富特色,不过“理”亦是其性理学说中最为难解处。李滉本人也曾言道“理”字最为难知,对于缘由他写道:
凡人言理,孰不曰无形体、无分段、无内外、无大小、无精粗、无物我、虚而实、无而有哉。但真知其实无形体、实无分段、实无内外、实无大小、实无精粗、实无物我、实为虚而实、实为无而有为难。此某所以平日每云理字难知也。①
李滉为学一向主张学贵穷理,因为在他看来若对理有所未明,则或读书,或遇事都不能做到无碍。所谓“理有未明”,即是指学者还未做到对理字之义的“真知”。那么,何谓其所言之“真知妙解到十分处”呢?李滉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盖尝深思古今人学问道术之所以差者,只为理字难知故耳。所谓理字难知者,非略知之为难,真知妙解到十分处为难耳。若能穷究众理到得十分透彻,洞见得此个物事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洁洁净净地,一毫添不得,一毫减不得,能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而不囿于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中,安有杂气而认为一体,看作一物耶。其于道义,只见其无穷,在彼在我,何有于町畦,其听人言,惟是之从,如冻解春融,何容私意之坚执。任重道悠,终身事业,安有欲速之为患哉。假有初间误入,一闻人规,便能自改而图新,安忍护前而无意于回头乎。诚恐循此不变,处而论道,则惑于后生,出而用世,则害于政事,非细故也。其以博览群书为非,而欲人默思自得,其意之落在一边,可知。公之报书,所以正其偏而砭其病者得矣。②
这是李滉答奇大升信中的一段话,也集中反映了在其哲学中“理”概念所具有的基本义涵。由以上引文内容所见,在其学说中“理”既是一个具无形、无质、无为之特性的形上之存有,又是一个指代实理的“天理”。而且,“理”又兼体用,既有无声、无臭、无方体之“体”,又有至神至用之“用”。③对于这样的“理”,李滉在文中进行了多角度的阐发,认为古今人学问道术之所以差者,只是因为“理”字难知之故。所谓“理”字难知,不是指略知之为难,而是将之真知妙解到十分处为难的意思。认为,只有“穷究众理到得十分透彻,洞见得此个物事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处,才能算是真正知“理”。
从“虚实”、“有无”等角度论述“理”本体的同时,李滉在答复奇大升问难的信中还提出理有体用说,曰:“无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体也。其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见于本体之无为,而不知妙用之能显行,殆若认理为死物,其去道不亦远甚矣乎。”①实际上,理有体用说是为其“四七理气互发”说作了理论铺垫。
进而,李滉还提出“理非静有而动无,气亦非静无而动有”的理(太极)自有动静的思想,明确地肯定了理的发用性。李滉曰:
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但就无极二五妙合而凝,化生万物处看,若有主宰者运用而使其如此者。即书所谓惟皇上帝将衷于下民,程子所谓以主宰谓之帝是也。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②
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勉斋说,亦不必如此也。何者,理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阳生阴也。③由此,在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便有了理气互发之论。他对理本体所作的这一解释,不仅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④的朱学内在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可能,而且还积极回应了以“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原,理何足尚”⑤为由对朱学理气说提出质疑的明初朱子学者们的诘难。但是,对其理发说需做进一步的解释。李滉亲身经历朝鲜朝多起“士祸”,统治阶级内部血腥的权力斗争致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社会道义及生命的尊严荡然无存。作为生活于此一时代的大哲学家李滉势必将重塑社会纲纪,提高伦理意识以及加强道德教化视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对李滉来讲,如何保存和扩充源于天理的人性本然之纯粹性就成为其首先要思考的哲学课题。故他所追求的是此种性理的自然呈现或良知之心的自我坎陷。李滉的这一主张看似与陆王心学的良知说有些相近之处,但其根本立场是基于人的道德心理和伦理行为意义上的性理发用,并非为王学意义上的“致良知”,更不是本体论(宇宙论)向度上的“太极”之自动静。理发论在其学说中之所以能够得到成立,还与其对“理”特殊规定相关。前文已言及在其“理”论中,理具有“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之特性,“理”具有绝对性。而且,在“气”论中他亦对之作了相应之规定。要言之,强调道德心理和伦理行为意义上的理(性)之发用性、主宰性、优位性,是李滉理气论区别于朱子理气论的紧要处,学者于此处应仔细玩味和体会。
那么,相较于“理”,“气”在李滉哲学中具有何种特性呢?李滉认为,因为“气”是有形之物,故气有限量而理无限量,气有生死而理无生死之说①。
盖理本无有无,而犹有以有无言者。若气则至而伸,聚而形为有,反而归,散而灭为无,安得谓无有无耶。或别有所据,某未记耶,气之散也,自然消尽而泯灭。②
然滉前以为气散即无。近来细思,此亦偏而未尽。凡阴阳往来消息,莫不有渐,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然则既伸而反于屈,其伸之余者,不应顿尽,当以渐也。既屈而至于无,其屈之余者,亦不应顿无,岂不以渐乎。故凡人死之鬼,其初不至遽亡,其亡有渐。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非谓无其理,而姑设此以慰孝子之心,理正如此故也。由是观之,孔子答宰我之问,亦无可疑矣。以眼前事物言之,火既灭,炉中犹有熏热,久而方尽。夏月,日既落,余炎犹在,至夜阴盛而方歇,皆一理也。但无久而恒存,亦无将已屈之气为方伸之气耳。①可见,“气”在李滉哲学中具有生死、聚散之特性。他以为,没有恒久不变之气,气的聚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举炉中火苗渐渐熄灭和夏日白天之暑热至夜缓解为例详加阐述。
李滉进而还提出气之原初无不善的主张,曰:
气之始无不善,乃气生源头处,非禀受之初也。然气有一日之始,有一月之始,有一时之始,有一岁之始,有一元之始,然此亦概举而言之耳。推来推去,其变无穷,当随处活看,不可执定为某气之始。苟指认一处为定则不通,不足以语造化之妙。②
那么,其无不善之“气”是否与李珥“湛一清虚”之气泯然无别呢?对此,李滉解释说:“程子心本善之说,朱子以为微有未稳者。盖既谓之心,已是兼理气,气便不能无夹杂在这里。则人固有不待发于思虑动作,而不善之根株已在方寸中者,安得谓之善,故谓之未稳。然本于初而言,则心之未发,气未用事,本体虚明之时,则固无不善。故他日论此,又谓指心之本体,以发明程子之意,则非终以为未稳,可知矣。”③可知,其所言“气之始无不善”是指心之未发而本体虚明之时。这与徐敬德、李珥哲学中的“气”概念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李滉对此进一步解释道:“湛一气之本。当此时,未可谓之恶,然气何能纯善?惟是气未用事时,理为主故纯善耳。”④这一解释对理解其“四七”论极为重要。因为依李滉之见,“气”只有听命于理或顺理而发的时候才能呈现为善。但是,又不能将“气顺理而发”称之为“理之发”。“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于此可见,其“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之说实乃根于其特殊的“气”论思想。
李滉还从价值论维度对理气概念作了“理纯善而气兼善恶”的价值规定。“理纯善而气兼善恶”之说其实承自程颐、朱熹的理学思想。气有清浊,由其清浊而言,气有或循理或不循理之可能。因此,要施以主敬工夫“以理驭气”。理是纯善,而气兼善恶,故以纯善之理帅“气”则“气”能循理而直遂。这便是所谓“理帅气卒”的思想。李滉的尊理贬气(理贵气贱)的观念,与其“理纯善而气兼善恶”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他进而又从伦理道德的意义上,作出“理极尊而无对”、“理贵而气贱”的理优位论之规定。既保持了传统理学所崇尚的等级价值观,又体现了其独创性的一面。理既“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②,那么理气关系即为主宰与被主宰的上下位关系。上者尊贵而下者卑贱,所以李滉指出:“理贵气贱,然理无为气有欲。”③在存养省察的工夫上,他特别强调主敬,惟其如此才能达到“以理驭气”使“气”顺理而发的目的。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兼论郑之云的《天命图》与“四端七情”论
在论述李滉的“四七理气”论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郑之云与其《天命图》。因为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郑氏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引致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李滉曾对郑之云称赞道:“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我妄以结状其难……有契有违,往返弗置,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④
郑氏是继权近、柳崇祖之后又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韩国性理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不仅为此后李滉和李珥等人的“四七理气”之辨提供了理论端绪,而且还开启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四端七情理论研究之先河。
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稼翁,1509—1561年)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曾受教于为金安国和金正国。郑氏世居高阳,本贯则为庆州。他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之辨发端于郑氏之《天命图》。对于自己的作图过程,他在《天命图序》中写道:
正德己卯(中宗十四年,1519年——引者注)思斋金先生被微谴而退卜居于高峰之芒洞,洞实之云所居里也,尝游其门受学焉。嘉靖戊戌(中宗三十三年,1538年——引者注)先生被召还朝,之云失其依归,与舍弟之霖学于家。论及天人之道,则之霖以幼学患其无据,莫能窥测。余于是试取朱子之说(见《性理大全》论人物之性),参以诸说设为一图,而又为问答名曰《天命图说》日与舍弟讲之。此非欲示诸人而作也,然图说既草,则亦不可不见正于长者,遂取质于慕斋思斋两先生,两先生不深责之,且曰:“未可轻议,姑俟后日。”不幸,两先生相继以没,呜呼,痛哉。由是此图之草,无所见正,而余之学问日就荒芜,几不能自振。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误闻不肖之名,躬行者再三之,云感其殷勤,斋木以进。退溪欣然出见,因语及《天命图》,之云以直告知,因请证之意,退溪稍假肯色。余退而私自贺曰:“吾丧两先生后,意谓更不得贤师友而求进,今得退溪,吾无忧矣。”常往来质问是图,退溪证以古说,参用己意,补其所欠,删其所剩,卒成完图。其赐己以厚,又从而为之说,附其后而教之,其幸孰大焉。非徒余之幸也,在昔日两先生姑竢后日之志,今始副焉,是尤幸之大也。余故首记作图之由次及定图之事,以藏于家。如有同志者出,其亦有以知退溪考证之意也。①
文中郑氏较完整地记述了此图的写作过程。他采先儒之论并以图解以明之,目的在于启子弟之蒙。此图取名为《天命图》——“天命”二字典出《中庸》首句,可见其以《中庸》为性理学之基础。为了说明天人相与之道,郑之云在《天命图解》①中使用了诸如理气、心性、太极、道等性理学概念,并用这些概念对天人之际进行了理气论的说明,旨在揭示了天人合一之根据。他还从理气论的角度对人的心性以及善恶问题进行了说明,此即所谓“四端七情”论。尽管郑之云并未将“四七”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来论述,而只视作探究天人合一的根据之一,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四七”论在其性理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②因为前者只是从其性理学整体构成之维度而言的。
此文写于嘉靖甲寅(明宗九年,1554年)之正月,此时退溪李滉已是年过五十的一代儒学名宿,思想也已渐趋成熟。他获得此图后,将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并在语气上作了改动。李滉的这一订正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尤其是奇大升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发展成为左右韩国性理学发展走向的学术论争。
郑之云在阐发其性理学说时,也意识到单纯凭借“气”论是很难对“恶”的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的。于是,他对阴阳之气赋予了善恶的价值含义。如把气分为清、浊、明、暗等。主张阳气清明,故可跻于善;阴气浊暗,故可流为恶。他断言“恶”的现象是由阴气所致,由此维护了“理”的纯善性。而且,还提出阴阳之气只是与心动之后的发用相关,并非各自独自发用的观点。这就消除了人的恶行的先天可能性。郑氏还认为,若心之发“意”根于性且其气属阳的话,天理会如实呈显;相反,如“意”与物相杂而其气属阴,则天理就会失去其真实性,终流于恶。依他之见,人的善恶行为取决于自由意志,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郑氏性理学追求“天人心性合一”,这表明他是韩国性理学史上的主流派学者。与中国的朱子学相比,韩国性理学以“图说类”诠释模式见长。从《天命图》在韩国性理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窥见郑之云在此一传统中的独特地位。①其“四七”理论的首要意义就是肯定人的道德行为(“人性善”)的先天可能性,此为性理学最根本的哲学观念。《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乃其天理观的来源和根据。实际上,性理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探讨的目的则是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寻找一个本体论的根据,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根据。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万物有机体观”正是性理学家们这一思想的反映。理与气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是为了证明这一思想。性理学家们以理气概念探讨道德行为之根源,尤其注重主宰人的行为的“心”的研讨,这也是心性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心性论中,与对心性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有关修养工夫的问题,即如何使心性向“善”的问题。欲解决之,首先要探讨“恶”的根源及来源。所以从理气论维度对“恶”之根源进行探讨也是心性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其中,“四端七情”之探讨是对人的本性的深层剖析,目的在于扩充良知所彰显的内心之善以上合天理。②实际上,他的这一思想根于孟子的性善说,欲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把握性与天道的关系。
可见,郑之云是韩国儒学史上继阳村权近、真一斋柳崇祖之后又一位坚持“天人心性合一”这一韩国性理学传统的学者。在韩国儒学史上,他还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性理学相关理论的学者。③尽管其理论仍显得较为简单缺乏系统性,但在《天命图解》及《天命图说》中所见的理论探索还是对性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了一定的概括和整理。所以李滉“君曾测海”的评价对他而言还是较为中肯的。郑之云的主要著作有《天命图解》以及《天命图说》。
李滉将其《天命图解》改订之后,首先遭到奇大升的发难。奇氏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又说过“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混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②。 在奇大升看来,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举,谓之纯理或兼气就有些不妥。奇氏主张四端虽由纯粹的天理所发,但只是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奇大升进一步评论说: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③
他认为四端与七情作为情感皆性状相似,而非有截然相反之特质。因此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学原论的。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回答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盖欲相资以讲明,非谓其言之无疵也。今者,蒙示辩说,摘抉差谬,开晓谆悉,警益深矣。然犹有所不能无惑者,请试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首先说明了其将郑氏之“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进行改动的缘由,他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认为先儒未有将“四端七情”分置于理与气的范畴来讨论的先例。李滉还是认可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在这一问题上他有过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首度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进行修订时的说法。李滉将郑氏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这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其实此两句从内涵到语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请参见新、旧天命图(图7、图8)。
起初他认为此说“本晦庵说,其理晓然矣”③,其时还未与奇大升展开论辩。二是在与奇氏进行论辩过程中有了第二种表述,即“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④。这是己未年李滉59岁(1559年)时的观点。当此之际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理气”之辨。加之李滉又恰好读到朱子的“四端是发于理,七情是发于气”一句,于是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与奇大升的信中提到:“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三是经奇大升之诘难后便有了新的说法——“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②。此后李滉对这一说法再未作改动,可视为其最终定论。对最后一说,他在其晚年代表作《圣学十图》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③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正是李滉性理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
他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本上的差异,这源于其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①
由此可知,在心性情的关系上李滉倾向张载的“心统性情”说。他将“心”理解为“理气之合”——与朱子“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的观念相比,心的含义以及与理、气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以此说为理论前提,可以分属理气的方式准确表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以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
四端七情之辨实质是性情之辨。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作为李滉晚年思想结晶的《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则为李滉所作。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概念。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此为性理学的主题。性理学的道德主体论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①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如此则性为体而情为用。朱熹认为“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②。与之不同,李滉进一步发挥朱熹的理气心性说并将性情与理气之发相结合,从而将朱子学的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端七情理气”论。此图的中、下两图乃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③对于“七情”的善恶,李滉起初以为“七情,善恶未定也”④。经与奇大升往复论辩之后改为“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故其发而中节者乃谓之和”⑤。这一改动容易造成七情之“善”和四端之“善”之混同,所以对之需作仔细辨析。四端之情是人的道德感情亦即良心。四端之“善”是纯粹的且还带有道德色彩。但是七情则与此不同,原是与道德情感无关之情。作为自然情感,七情在“性发为情”之后才能以发用是否为“中节”衡量其善恶。因此如李滉早年所言,它还是“善恶之未定”。那么,应如何理解其修订后的说法呢?我们可以从其“本善”一语中去寻找。“善”被赋予道德含义之前,“好”是其概念的核心内容。易言之,善是规定事物之好的状态,道德性的善也是如此。“七情”作为原始的自然的感情本是好的感情,只因具有“过或不及”的性质,容易“流于恶”。①其修订后的说法可以按此思路去解读。
对于下图李滉解释说:“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②
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和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遵循程朱“情根于性,性发为情”之原则,依此解读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和无不善之情。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我们也可以一窥李滉试图融合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正是两种权威文本相互冲突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引发韩国儒者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③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说,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还是气发皆可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甚至放而为恶,原因就在理发未遂或者气发不中。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显或气发而皆中节遂成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述引文中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子学的传统——李滉继承这一传统,也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也是情,而“情”必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遂成人性善恶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①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也就是说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自我反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多次对此图进行修改。“盖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中所载本也。”②此图在李滉《圣学十图》中具有的重要性实在是无需赘言。
李滉还以“七情”与“四端”分论“人心”与“道心”,指出“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也。”③这既是对朱子心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学术上的立异。在李滉看来,道心是义理之心即最高的道德原则,所以他在强调四端七情之差异的同时还特别重视道心人心之分别。虽然其中图未言及“气”,但他论性情仍以理气分言之。“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④这也表明李滉心说承继朱子之传统——倾向以“理气心”论性情,而且主张持教工夫。
在论辩的最后,李滉以《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三书》总结二人观点之异:
既曰“浑沦言之”,安有主理、主气之分?由对举分别言时,有此分耳。亦如朱子谓:“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又云:“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
前书引性言者,只为在性犹可兼理气说,以明情岂可不分理气之意耳,非为论性而言也。“理堕气质以后事”以下,固然,当就此而论。
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碍者乎?而况所谓四端七情者,乃理堕气质以后事,恰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则有明有暗,四端则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固因水之清浊而四端之不中节者,则光虽明而未免有波浪之动者也。伏乞将此道理更入思议,如何?
“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说,尝见先儒有论其不可,今不记得……敢问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者,为发于理耶?为发于气耶?而发而中节,无往不善之善,与四端之善,同欤?异欤?虽发于气,而理乘之为主,故其善同也。且“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谓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则只有理发一边。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未知于先生意如何?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发矣。若欲外此而更求理之发,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弊。前书亦以为禀,而犹复云云。苟曰未然,则朱子所谓“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者,亦不可从也。
道即器,器即道。冲漠之中,万象已具,非实以道为器;即物而理不外是,非实以物为理也。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用朱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也。
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此信写就之后李滉或觉没有必要继续与奇氏论辩,故而未将信寄给他,只是针对奇氏来信中的质问撰文阐述自己的主张。李滉的基本观点是四端七情混沦而言时则无需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但是若将二者对举而言则应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他还以“因说”和“对说”来解释了此问题。直至结束辩论二人仍各持己见,并未达成一致。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以为不仅“性”可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若说奇大升注重于对问题的客观性、逻辑性的阐明,李滉则更着力于对道德性的提高以及修养工夫论域中的主体的省察和践履的意义。
“四端七情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赓续朱子的理气心说,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无怪乎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此种理解,李滉进一步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他对七情的看法始终落在气的一边。他说:“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不能无理,所以“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四端”需要扩充,而易“流于恶”的“七情”则要受检束。因为二者各具相异的性质,如何理解其异中之同便值得认真思考。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说:“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若从客观的视角对情之结构做静态分析的话,便可以得出“四端”为“七情”之一部分的结论。但是在道德践履的意义上,二者又具有相反的性质。比较而言,奇大升关注前者,李滉则更倾向于后者。当然此种差异是相对的。两人真正的分歧源于各自在为学旨趣及问学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的问题意识。
要言之,“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中的核心内容。基于理气二分的立场李滉肯定情的“四七”之分,以为恻隐、善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是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而发,即缘境而出。不过依其理气心,“心气”之性质及所为,如气之清浊、偏杂、粹驳之状态,直接决定四端之呈显以及七情之善恶性质。李滉以为,“气”之状态影响理之显否,故在修养论上他特别主张施以主敬涵养工夫治“心气”之患,使气皆能循理而发以保证理发直遂而不被气所掩。
三、李滉的主敬论——以《圣学十图》为中心
李滉之学亦被称为主敬之学。因此下面将通过对《圣学十图》的分析来探讨其以主敬说为特色的性理哲学思想。
《退溪全书》“言行录”中记载,其门人金诚一将其学问概括为“试举其学大概,则主敬之工,贯始终兼动静,而尤严于幽独肆之地,穷理之功,一体用该本末,而深造于真知实得之境,用功于日用语默之常”。①主敬思想的基本论纲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敬以直内,涵养本心;义以方外,省察行事。尽管李滉所依傍的是程朱的主敬之说,但是其主敬之说知行并重,贯始终兼动静。其学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又比程朱更强调“心”之作用和效用,也因之更加明确地揭示了“敬”之为学工夫与进入圣贤域以达至圣人的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
作为“东方之朱夫子”,李滉为学服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对朱子学的理气心性诸说多有发明。李氏68岁(宣祖元年,1568年)时进呈宣祖的《圣学十图》更是其学问宏纲大目的集中反映,也是其一生学问的思想结晶。可谓“晚年深思熟虑,提纲挈领的结晶,也是他体认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心得。李滉独以图的形式,既示人以圣学入道之门,亦给人以简明易懂的启迪。《圣学十图》,融铸宋明理学之精髓,构成他的思想逻辑结构,其规模之宏大,操履之功用,在李朝理学史上均属罕见”②。《圣学十图》由《进圣学十图札》和《圣学十图》组成。所谓十图包括:第一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第二图为程复心(字子见,号林隐,1279—1368年)绘的张载的《西铭图》;第三图为李退溪绘的朱子的《小学图》;第四图为阳村权近绘的朱子的《大学图》;第五图为李滉绘的朱子的《白鹿洞规图》;第六图为《心统性情图》(上图由程复心作,中、下二图由李滉作);第七图为朱子的《仁说图》;第八图为程复心绘的《心学图》;第九图为王柏(字会之,号鲁斋,1197—1274年)绘的朱子的《敬斋箴图》;第十图为李退溪绘的陈柏(字茂卿,号南塘,元儒)的《夙兴夜寐箴图》。对于上述十图,李滉还做了相应的引述和说明,指出前五图是“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③,后五图则是“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④。综观十图,“敬”①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纲目。
《圣学十图》的排列次序不仅体现了李滉哲学的逻辑结构,而且还反映了其对儒学(圣学)的全部理解。第一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李滉对此解释说:
朱子谓此是道理大头脑处。又以为百世道术渊源。今兹首揭此图,亦犹《近思录》以此说为首之意。盖学圣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于小学大学之类,及其收功之日,而溯极一源,则所谓实理尽性而至于命,所谓穷神知化,德之盛者也。②
朱熹立学极重周敦颐之《太极图》,此图可说奠定了“濂溪先生”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开山之祖的地位。李滉认为太极即是宇宙本体(天道),故将《太极图》视为百世道术之渊源亦即一切思想学说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强调学圣人者要“求端自此”。李滉将周敦颐的《太极图》理解为对《周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义的阐发。依李滉之见,圣人是“与天合德,而人极以立”,因此圣人之学便是继天立极之学。他认为此图的目的在于阐明圣学的理论根据,而且还揭示如何以抵达圣域的修养工夫。李滉进而引用朱子的《太极图说解》以作说明:“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间而已矣。敬则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静虚动直,而圣可学矣。”③《太极图》表明了以“敬”为核心的为学路数,具有将天道、地道和人道加以融合以作整体观照之特性。而其他九图皆为此图(“立太极”和“立人极”)的进一步展开。此其所以《近思录》、《性理大全》等开篇即设有《太极图》——李滉可以说继承了这一理学传统。
第二图为《西铭图》,旨在揭示天道的进一步展开。该图试图从对“求仁”的深刻体悟中阐明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道理。李滉以为“圣学在于求仁,须深体此意,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一体,真实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味,免于莽荡无交涉之患,又无认物为已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体也。又曰:充得尽时,圣人也。”①这是李滉体仁的最高境界,于此彻悟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强调物我一体论与事亲事天之实践,他在《西铭图》图说中写道:“朱子曰……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②天道以仁为本质。人只有懂得其所具之仁便是天地生生之理(太极),才能扩而充之与天地生生之理的合而为一,从而达到民胞物与的境界。这就需要通过心性修养、涵养工夫以提高人的素质,方能使其内心之德臻于完满。李滉将《太极图》与《西铭图》视为理学形而上学理论和修养工夫的根据,即小学大学的标准本原。“上二图,是求端扩充,体天尽道,极致之处,为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下六图,是明善诚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③
正是基于此种考量,李滉分别以《小学图》、《大学图》和《白鹿洞规图》为第三、四、五图。《小学》是朱熹所编的一个以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本。朱子极重小学,将其与大学并列。朱子学传入之初,朝鲜朝儒者便对《小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阳村权近曾写道:“小学之书,切于人伦世道为甚大,今之学者皆莫之习,甚不可也。自今京外教授官,须令生徒先读此书,然后方许他经。其赴生员之试,欲入大学者,令成均馆正录所先考此书通否,乃许赴试,永为恒试。”④李滉在《小学图》中,援引朱子的《大学或问》写道:“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涵养本原,而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⑤从中亦可看出李滉对小学的重视。他在继承和发展朱子思想的基础上,以敬身明伦为旨归将小学教育的组织、内容、目的、宗旨提纲挈领。《小学图》反映了李滉强调实践、注重践履的为学性格。李滉根据朱熹的《小学》一书的目录制作此图,以与《大学图》对举。在他看来小学和大学相反相成,是“一而二、二而一”①的关系。前文已言及《大学图》乃朝鲜朝初期的阳村权近所造。“大抵《大学》一书,一举目,一投踵,而精进本末,都在此。”②《大学》是被朱熹视作学者入德“行程节次”③的一本书,亦是其平生用力最久、最甚的一部儒家经典。朱子曾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全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④李滉认为为学者只要按此“行程节次”认真践履、勇猛精进便可达至圣域。《大学图》的特色在于引述朱子《大学或问》的论“敬”之说以为圣学的始终之要。“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尝以主一无适言之,尝以整齐严肃言之;门人谢氏之说,则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有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小学之赖此以始,则夫大学不能无赖于此以为终者,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盖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则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是诚意正心以修身,则所谓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乎天下,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离乎敬也,然则,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⑤本段引文对李滉《圣学十图》的主敬思想影响甚大。尊德性而道问学、居敬而穷理是理学的基本立场,朱熹曾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⑥认为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存养,不过朱熹实际上以“穷理”、“致知”为先。李滉指出:“非但二说(即《小学图》与《大学图》所引朱子论教之说)当通看,并与上下八图,皆当通此二图而看……下六图是明善诚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而敬又彻上彻下,着功收效,皆当从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之说如彼,而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①由此可见,“敬”在李滉哲学中并不仅仅是彻上彻下、贯穿动静始终之修养工夫,而且还是可以统摄存心养性与格物致知的圣学第一要义。《圣学十图》即是其主敬思想的集中体现。第五图《白鹿洞规图》是李滉依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而作,旨在阐明人伦之道。“盖唐虞之教在五品,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故规之穷理力行,皆本于五伦。”②李滉认为大学是小学阶段的延续,而两阶段的教育有着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穷理、力行)、在止于至善,而小学之宗旨则为在明人伦(五伦),所以说“此两图可以兼收相备”③。《白鹿洞规图》意在综合小学、大学的为学之方,着重突出五伦作为圣学内容的重要地位。另外,从《白鹿洞规图》中亦可看出李滉的书院教育思想。李滉以为以上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④。
心、性、情是理学人性论的核心范畴,第六图即为《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此图在上一节已有论及,这里只做简要介绍。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下图为李滉所作。在朝鲜朝儒学史上,主要论辩皆围绕“心”这一哲学范畴而展开。16世纪后半期的“四端七情”之辨、“人心道心”之辨、18世纪初叶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以及19世纪后半期的本心明德之“主理主气”论辩等均是对“心”之发用及相关问题的深入辨析。此为韩国性理学的特色所在。
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理学的主题。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就是通过“心性情”等范畴全面展开。⑤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一言蔽之即性为体情为用。朱熹认为“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①。李滉则与之不同。他进一步发挥程朱理气心性说,将性情之说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并将朱学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七理气”之辨。《心统性情图》之中图和下图将李滉理气心性诸说表述得最为简单明了。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秉承之,亦主“合理气,统性情”。但是,李滉比朱熹更专注于对“情”的探讨。重“情”乃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理气心”。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此心具心气之患)的“情”皆能中节便成为心性修养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气之患,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故其曰:“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②其持敬之目的就是要由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之际反观内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对此图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第一图的结构原是智上礼下仁左义右,先是对其中礼智上下结构进行改动,后来又对原图中的仁义左右次序做了修改。最后还是以第二次改动的为定本,收录十图之中。③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第七图为朱熹自作的《仁说图》。李滉曾将此图放于《心学图》之后,后接受李珥的建议移至《心学图》之前。他在给李珥的复信中写道:“《仁说图》当在《心学图》之前,此说甚好,此见解甚超诣。滉去年归来,始审得当如此,及得来说而益信之,即已依此说互易矣。”①由此亦可窥出《圣学十图》中各图的排列次序是经过了反复斟酌与思考。该图进一步说明了四德相互之间以及其与四端之间的关系。“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未发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则包乎四者。”②“仁”作为统摄“四德”与“四端”的道德理性,在理学中不仅与太极、诚以及中和等概念同等重要,而且还指代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人和天地生物皆以之为心。李滉将朱子学的仁说视为上承天道下启存养之途,亦即贯通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节点。这应该是李滉最终把此图置于《心学图》之前的重要原因。由其“圣学在于求仁”之见以及此图“发明仁道,无复余蕴”之说可以推知,在李滉的心目中人君者欲施仁政亦应于此图求其义。故《仁说图》在《圣学十图》中亦居重要地位。
第八图为程复心所绘《心学图》。李滉将此图目为天地生物之心(仁)的着足处。李滉性理学“求仁”之目的在于使人不断完善其人格,以优入于圣域。“此仁者,所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足以普四海弥六合也。”③《心学图》把“心”分为赤子心与大人心、人心与道心,也是为了给人提供实现理想人格的修养工夫。学者只有“惟精择善,惟一固执”,才能克去己私以存天理。所以必须施以“持敬”工夫使人心变为道心。唯有以“敬”抑欲才能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加之“敬”又是一心之主宰,存理遏欲的工夫大可统一到“敬”字上来。就此而言,“存天理遏人欲”是主敬工夫之实质内容。对《圣学十图》中的后五图,李滉认为“五图原于心性,而要在免日用崇敬畏”④。他在第六、第七图中着力探究主体之性情问题后,便将“天地生物之心”作为仁之根据。李滉在第八图中又论述了与“心”相关之问题,并指出了治心之工夫以及“敬”作为一心之主宰在涵养省察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第九图为金华王鲁斋柏就朱熹《敬斋箴》绘制的《敬斋箴图》,此箴乃朱熹有感于张敬夫的“主一箴”所作。若说第八图示“圣学心法”,那么此图则“为圣学之始终”。此图承《心学图》之旨,继续以“敬”为工夫之要以示具体的用工地头。在图说中,李滉引真西山之言曰:“敬之为义,至是无复余蕴,有志于圣学者,宜熟复之。”①这表明李滉不仅将“敬”视为其存养工夫的关键,而且还视为其性理学体系之核心。他在答李叔献(李珥)的信中写道:“惟十分勉力于穷理居敬之工。而二者之方,则《大学》见之矣,《章句》明之矣,《或问》尽之矣。足下方读此书,而犹患夫未有所得者,得非有见于文义,而未见于身心性情之间耶。虽见于身心性情,而或不能真切体验,实味膏腴耶。二者虽相首尾,而实是两段工夫,切勿以分段为忧,惟必以互进为法,勿为等待。即今便可下工,勿为迟疑。”②《敬斋箴》内容如下:“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参以三,惟心惟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弗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论,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灵台。”③这些可视为“敬”的具体细目,可以此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李滉还依据陈柏的《夙兴夜寐箴》绘制《夙兴夜寐箴图》④以为第十图。他认为“敬斋箴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其地头而排列为图。此箴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其时分而排列为图。”⑤第九图《敬斋箴图》与第十图《夙兴夜寐箴图》一是以地头言,一是以时刻言。①即,前者按行事罗列,是以心为核心展开的主敬工夫;后者是依时间编排,是以行为核心演绎的持敬规范。②李滉曰:“盖敬斋箴,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时其地头而配列为图。此箴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时分而配列为图。”③但道之流行于日用之间,无所适而不在,亦无顷刻之或停,因此李滉强调不分时分与地头的主敬工夫。两者在李滉性理学中相互发明、相互补充均为相当紧要,因之李滉言二者须并进。
《圣学十图》前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体现了《太极图》融自然本体、社会教育、人格培养为一体的思想;后五图则“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与前五图恰好构成不即不离的体用关系。前五图以无极太极为第一图,后五图以心统性情为第一图。这个划分不以天道人心为二,而是将二者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形而上本体遂与人世间的心性冥冥相通,立人极也就可以进而立太极。④易言之,后五图则展示心体(天道)呈现之修养过程。“综观此十图,其核心是人。因此,李退溪的圣学,我们亦可称为人学,即学做圣人之学。《圣学十图》,就是学做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情感意志等等。全面、系统而又渐次深入地论述了为圣的目的、方法。”⑤依李滉之见,除了“心”之外再没有完成自我人格的原动力。关键在于如何克去除理气心所具有的心气之患,从而使心气循理而行、顺理而为。这就要求学者时刻以“敬”字治心、以“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⑥。显而易见,以持敬工夫统摄心知乃是李滉主敬论的主要意涵。
由上所述可知,李滉主敬思想根植于其对性理学理气心性诸说的理解。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七情之善与不善端视发而中节与否——一切都随“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其实此时四端与七情皆滑入气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皆为气之所为。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皆为气之所为。所以主敬以治心上之“气患”,使气顺理而发、循理而行,这就是以主敬说为特色的李滉思想的根本主旨。
简言之,李滉以“敬”贯动静、知行并重以及内外如一为其主敬思想的方法论,由此构筑了以主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绘制的《圣学十图》以图画的形式将程朱理学中繁杂的主敬思想做了言简意赅的表述。此图既是主敬工夫的形象说明,也是李滉思想的简明提要。
“敬”作为理学修养的重要方法受到程朱诸儒的重视。朱子以为“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程子亦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语最妙”②。但是程朱诸儒并未以此为纲领构筑其道德形上学体系。朱子去世三百年后,号为“海东朱子”的李滉却以“敬”为核心构筑了颇具理论与践履特色的“实践道德哲学”(后人亦将之称为退溪“圣学”或退溪“心学”),遂集朝鲜朝的朱子学思想之大成。李滉对“敬”的强调与对“敬”的意义的理解确有超过朱子处。③以此为特色,退溪学代表了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李滉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坚持二者是不同类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④李滉还制作“心统性情图”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工夫论方面,李滉极重主敬,以下学上达为其居敬穷理之出发点。“只将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以验夫统体操存不作两段者为何等意味,方始有实用功处,脚跟着地,可渐渐进步,至于用功之久,积熟昭融,而有会于一原之妙,则心性动静之说不待辩论而嘿喻于心矣。”①他主张由下学上达之持敬修养工夫优入圣贤之域,从而体验天理之极致。由此可知李滉的道德学问观以及其为学的根本宗旨。“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②,李滉在知与行方面忠实履行了儒家之为学宗旨,堪称朝鲜朝五百年间难得的为己之学之楷模。
他的思想不仅对韩国性理学界影响至深,而且还对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启蒙传疑》、《自省录》、《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圣学十图》、《论四端七情书辨》等,均收录在《增补退溪全书》(1—5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