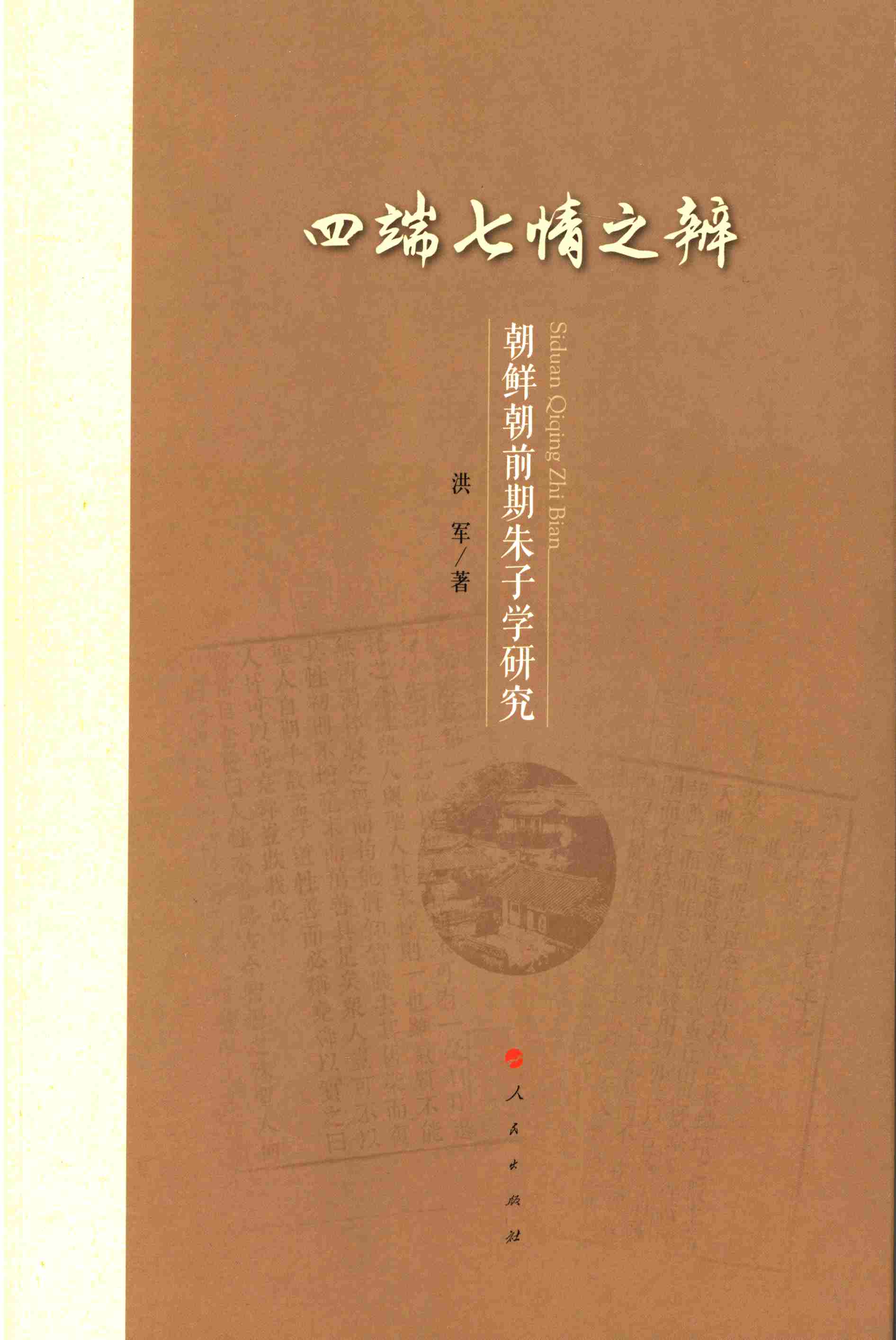第一节 四端七情论辩之发端
内容
权近、柳崇祖及郑之云等皆为朝鲜朝前期的著名朱子学者,其在四端七情问题上的论述和主张,遂成日后退溪李滉、高峰奇大升、栗谷李珥、牛溪成浑等人进行“四端七情理气”之辨的理论端绪。本节首先将权近和柳崇祖的思想合在一起加以讨论,目的在于能对四端七情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有个系统的了解。
一、权近与其“四端七情”论
活跃于丽末鲜初思想界的朱子学者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与郑道传一起并称为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双璧。权氏为安东人,曾受教于李穑和郑道传。他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前文所介绍的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
据年谱记载,权近步入仕途初期颇为顺当。他年17岁中成均试,年18岁(洪武二年己酉),三月中馆试第二名,五月樵隐李仁复、牧隐李穑同掌礼闱中第三名,六月擢殿试丙科第二名,七月直拜春秋检阅。历任中正大夫成均祭酒、艺文馆提学、成均馆的大提学、大司成等官职。但是,38岁(昌王元年)时他因“礼部咨文”事件中言事所牵连被贬到黄海道牛峰,后又贬至宁海。①在韩国儒学史上不管是“以图示说”的研究传统,还是四七论辩的理论萌芽皆可以追溯至权近,故后人赞其道:“丽朝以来,非无名人器士,而所尚者,文章勋业也。惟文忠公郑梦周,始传程朱之学,而遭时不幸,未有著述。文康公权近,有文章学识,而《入学图说》以四端七情,分左右书之。此所以理气之发于二歧也。后来学者传袭之论,无复异趣。”②
他一生致力于性理学理论之探究,为朱子学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泽堂李植曾说过:“我国先儒,皆无著述,权阳村说经论学,始有著述。”③其力作《五经浅见录》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了“五经”,而《入学图说》则是韩国最早一部理解朱子学思想的入门向导书籍,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近的《入学图说》是其为初学者讲授“四书五经”而作的一部“以图示说”的性理学入门书籍。全书分为前后集,前集中载有“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诸侯昭穆五庙都宫之图”等26种图说;后集中则收有“十二月卦之图”、“周天三辰之图”、“一朞生闰之图”、“天地竖看之图”、“天地横看之图”等14种图说,共计40种图说。卷首有权近的“自序”,卷末有郑道传和卞季良的跋文,书中权近将儒家经书中能够“图示”的内容尽己所能以图解的形式表现出来,极大方便了初学者的学习。
此图说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和李滉的《圣学十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滉的《圣学十图》中的“大学图”与权近的“大学指掌之图”可说是一脉相承。因此《入学图说》被后人称为韩国“图书学”的嚆矢。
尽管为初学者而作,《入学图说》还是集中反映了权近的心性论思想。其中又以“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和“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尤为根本。该书收录的40篇图说中,讲授“四书”的有6篇,讲授“五经”的有3篇,讲授“河图洛书”的有10篇,讲授礼的有4篇,讲授天文地理的有12篇等等。在这40篇图说中,较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的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中庸分节辨议”、“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五经体用分释之图”等篇,而“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五经体用分释之图”等图示正是权近对“四书五经”内容的系统解说图。权近思想除了此图说外,还散见于《阳村集》、《礼记浅见录》以及《三峰集》之注释内容。
下面,首先对其“天人心性合一之图”①(见图2)作出分析。
此图集中反映了权近的哲学思想。在该图解释的开头他便写道:“朱子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今本之作此图。”②表明此图的理论依据来自朱熹的宇宙论(理气论)。紧接着又写道:
右图谨依周子“太极图”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说,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故不及万物化生之象,然人物之生,其理则周,而气有通塞偏正之异,得其正则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即此图而观,则诚字一圈,得最精最通而为圣人;敬字一圈,得正且通者而为众人;欲字一圈,得偏且塞者而为物;其下禽兽横者得其尤偏塞而为草本者也。是则万物化生之象亦具于其中矣。夫天地之化,生生不穷,往者息而来者继。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①
可见,此图是权近谨依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的《中庸章句》之说制作而成。权近在图说中还附上其与弟子的有关天人心性问题的答问。此图不仅谈到了“太极”、“天命”、“理气”、“阴阳”、“五行”以及“四端七情”等性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还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图示形式清楚表示出来,使学者易于理解和把握其要领。
权近的性理学说非常重视“心”,以至于在其心性论中“性”是在论“心”时才附带成为讨论的对象。权近曰:“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①如图中所见,他对“心”这一概念作了详细辨析,并对像“性”、“情”、“意”、“诚”、“敬”、“欲”等概念皆从心性论到修养论多角度作了分析。从图中可见,他将“性”之德目规定为仁、义、礼、智、信;“情”则指代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喜怒哀惧爱恶欲;“意”为几善恶;“诚”乃真实无妄,纯亦不已,圣人性之;“敬”为存养省察,君子修之;“欲”为自暴自弃,众人害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心”大体上是相较于“身”而言。因为他认为,心是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者,是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故他写道:“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沫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虽曰应万事,而是非错乱,岂足为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其有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若从理学的心身关系的角度来看,因“心”有具众理而应万事之功能,故主宰个体肉身活动的只能是“心”。可见,性理学以为人的身体和神明的作用皆与“心”相关联。
另外,心之重要特征,即“虚灵洞彻”与“神明”问题在图中虽未标示,但是在论著中也有对此一问题的相关论述。他认为,心不仅仅是“神明之舍”,更是具有虚灵之妙之特性的认识器官。因心是“气之精爽”、“气之灵”,故此心具有虚灵之特性,可以应对万事。他将心比喻为“心之灵而镜之明也”,还说:“心之本体,寂然无朕,而其灵知不昧,譬则镜性本空,而明无不照。盖随缘者,心之灵而镜之明也。”③心之寂与镜之空是不变者,而心则以此感应万变而无穷尽。他还认为心所生发的行为可以为善为恶,而为善的行为必源于纯善无恶之性。
权近和郑道传皆为丽末鲜初的著名斥佛论者,权氏在展开其性理学“心”论的同时还对释氏所讲之“心”作了批判。“盖外边虽有应变之迹,而内则漠然无有一念之动,此释氏之学第一义也。”①佛教不承认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以为现实世界为虚幻的、不真实的存在。这种心说所隐含的是遁世绝俗、逃避现实的消极的人生态度,自然与主张积极入世、力求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人生观相去甚远。因此受到儒者的猛烈抨击。对此权近也批评道:“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沫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其有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可见,他所讲的“心”正是朱子学所言之天理论视域下的理气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权近绘制此图的目的在于“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③。将理气摄入心性域来讨论是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色,这一理论传统其实亦肇始于权近。韩儒的心性学说与其说是对人之性情问题的探究,不如说是从理气论的向度对人的性理问题的阐发。因人的行为皆与心理活动相关联,所以韩儒在思考如何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时重点考察了人的行为的根源,即试图立足于心性论以阐明人之道德行为的发生根源。于是,属于理学本体论范畴的理气概念被纳入心性论域,用于直接讲明人的道德行为的来源和根据。从“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可以看到,“心”分善恶,而整图则被代表理气的白色和黑色一分为二。心具众理,性源于理,理若如实呈现即为纯善。故圣人即是完全实现心中之理者。
如前所述,韩国性理学关注的首要课题是“人”,即具有道德良知的现实中的人。这一特点从《入学图说》开篇第一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亦能窥见。此图说首先要辨明的是人的心性问题,而非天地万物如何化生的本体论问题。
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善恶选择时如何抉择“善”,这是关乎修养论(工夫论)的问题,为此权近标出了“敬”。图中善恶被分在“心”之两侧,而“敬”又与二者相关联,意为人之为善为恶皆系于以“主敬”为主的存养省察工夫。
其次,讨论其“天人心性分释之图”的“天”之图(见图3)和其“人”之图①(见图4)。
从《入学图说》的排序中也可看到,权近是在第一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
中先论人之后,又在“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中次第论及“天”、“诚”、“敬”。“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天”之图显示“天为一大”:“一者”意为以理言则无对,以行言则无息,故为万殊之本;“大者”则意为以体言则无外,以化言则无穷,故为万化之源。其“以理言则无对”的观念与日后李滉“理极尊无对”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皆基于以理为本的理气论传统。“敬”是指主敬涵养下学工夫,“诚”是天人合一之媒介,故《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①
在“人”之图下,权近附言道:
人者,仁也。仁则天地所以生物之理,而人得以生而为心者也。故人为万物之灵,仁为众善之长,合而言之道也。圣人至诚,道与天同。君子能敬以修其道,众人以欲而迷,惟恶之从。故人者,其理一,而所禀之质,所行之事,有善恶之不同。故其为字,歧而二之,以示戒焉。人能体仁,以全心德,使其生理常存而不失,然后可无愧于为人之名。而其效必能得寿,不然则生理丧而非人矣。②
依权近之见,“仁”是天地所以生物之理,在人则为心。因此人是万物之灵,仁为众善之长,而将二者合而言之便是道。他进而指出惟君子能敬以修其道,而众人则迷于欲念、惟恶之从。权近将“仁”也就是文中所谓“生之理”视为人的本质。众所周知,儒家将“仁”视为人与万物共同的普遍原理,表现在人身上即为“人之性”。
再次,讨论其“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心”之图(见图5)。
对于此“心”之图,权近解释道:
心者,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理气妙舍、虚灵洞彻、以为神妙之舍而统性情,所谓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者也。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其用之发有时而昏。学者要当敬以直内,去其昏而复其明也。其字形方者,象居中方寸之地也。其中一点,象性理之源也。至圆至正,无所偏,象心之体也。其下凹者,象其中虚,惟虚故具象理也。其首之尖,自上而下者,象气之源,所以妙合而成心者也。其尾之锐,自下而上者,心于五行属火象,火之炎上也,故能光明发动以应万物也。其右一点象性发为情,心之用也;其左一点象心发为意,亦心之用也,其体则一而用则二。其发原于性命者,谓之道心而属乎情,其初无有不善,其端微而难见,故曰道心惟微,必当主敬以扩充之。其生于形气者谓之人心而属乎意,其几有善有恶,其势危而欲坠,故曰人心惟危,尤必当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然后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差谬而圣贤同归,参赞天地亦可以驯致矣。不然,则人欲日长,天理日消,此心之用不过情欲利害之事,虽有人形,其违禽兽不远矣。可不敬哉。①尽管此文篇幅不长,权近还是简明扼要地对心身关系、心之结构、心之机能、心之作用、心之体用等都作了必要的说明。在心身关系方面,主张心是“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亦即心为身之主宰;在心之结构方面,认为心是理气妙合而为神妙之舍;对于心之机能则主虚灵洞彻,由是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对于心之作用倾向心性关系中“心统性情”;至于心之体用则主心体至正无偏而为性理之源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即是用。①其体则一,而用则二。道心原于性命而属乎情,“其初无有不善,其端微而难见,故曰道心惟微”;人心则生于形气之私而属乎意,“其几有善有恶,其势危而欲坠,故曰人心惟危”。因此,以主敬工夫扩充天理之正,以遏人欲之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便可做到危者安而微者著。以上是权近心论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其基本见解皆来自朱熹理论。如对心之机能,朱熹曾有如下论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②在文中权近还探讨理欲之关系,以为二者此消彼长,必由主敬工夫方能扩充天理,所谓“人欲日长,天理日消”。
此图需注意的是,权近按心的字形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加以解释:其一为“理之源”;其二为“气之源”。他将道心和人心、情和意以性为中心分别列于“理之源”和“气之源”之下:道心属情,其初无有不善;人心属意,其几有善有恶。在权近看来,此时之“情”根于理,作为“四端”之情无有不善,人心是发于气之意,故其几有善有恶。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的思想行为或源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韩儒则更倾向于从理气之发的视角来探讨此一问题。权氏殆以作为心之二用的情意分别生于理与气——“其体则一而用则二”。“情”和“意”乃人心的两种发用方式,源于性命者为道心(情),生于形气者为人心(意)。因此“学者要当敬以直内”,防止生于私欲的行为的发生。
“人心道心”问题在韩国儒学史上极为重要。权近对此一问题基本立场是“人心惟危,尤必当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然后危者安,微者著。”依其之见,“情”的行为一般能呈现较为理想的状态,源于气的“意”则不然,后者之呈现或善或恶,不由“心”的作用即无以引之向理。
权近以“理之源”和“气之源”判分人心以作解释,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
最后,再讨论其有关“性”的论述(见图6)。
理学宇宙论(本体论)需借理气说才能得到阐发。从上文可见权近的思想大体不离伊洛渊源,是故在其学说中“性”总被赋予普遍宇宙之原理义,所谓“性即理”是也。
在《入学图说》中,权近彰示“性”之图并写道:
性者,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于吾心者也。故其为字,从心从生。人与万物其理则同,而气质之禀有不同者焉。告子曰生之谓性,韩子曰与生俱生,释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气言而遗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①
此图亦是为初学者而设。权近自言道,其训天人心性分释之意有些破碎,但是初学者则一见即可知其大意要旨。并标榜其解说皆本自程朱的格言,非为其臆说。初学之士的要务,则在于动处下功夫,而存养之事已包含在“敬”之中。
理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反躬实践,而在现实中如何如实地呈现“理”和实践“理”遂成首要课题。为此权氏欲将天人问题转化为心性问题,以图在心性层面上实现“天人合一”这一儒家最高价值理想。心作为理气之合既具形上之特性,又有形下之特性。而且心还以“虚灵洞彻”统摄性情,由是具众理以应万事者。因此,在心的层面上追求其与性理的合一便是“仁学”思想的主旨。
“心具众理”强调的是“理”常存于人心。理学家认为,人心之理即性理不能如实呈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②之故。权近重视“性”,亦因“理”只有通过“性”的发用才能呈现。那么,究竟由何呈现呢?无疑是要由“心”来呈现。从此意义上说,权近“心统性情”的思想可以视为对主体以其“实践性”能动地呈现天理的一种阐述。
如前文所述,他将“性”定义为“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于吾心者”。①这与程朱对“性”的论述大体相同,伊川曾言:“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②又说过:“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③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解释道:“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有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④相较于程朱,权近的性理概念更强调“生之理”之义。
“性”字“从心从生”,仅就字形便可了知其与人心、人生的密切关系。作为性理学家,权近对历史上出现的不同“性”说评价道:“告子曰,生之谓性;韩子曰,与生俱生;释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气言而遗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在他看来,告子、韩非子以及释氏之“性”论的主要理论缺陷是未意识到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即所谓“义理之性”。这也反映了性理学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安身立命,而且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道德水平的提升。于此可见,儒家的确比其他学派理论更具道德关怀。权氏的“性”论与其说对人之本性的阐发,不如说是对人的能动实践能力的揭示,故可将其拟于实践性理学。
权近在书中“天人心性分释之图”的“性”条里面还写道:
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於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又况程子之言,以为外物触而动于中,其中动而七情出,情既炽而其性鉴矣。则其不以为性发也,审矣。①
他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之善并无二致,皆为同质之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非为性之所发,故不能与“四端”并列。依权氏之见,“四端”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权近不仅依此区分“四端”和“七情”,还进而以理气分判道心与人心:“理本无为,其所以能灵而用之者,气也……道心为危,人心惟微,则固以理气分言之矣。夫心之发其几有善恶之殊,若纯乎理而不杂乎气,则其发安有不善哉。”②从权近“心”之图(图5)中可见,是以“理之源”和“气之源”的视角对心进行解读。依其思路,性之源是理,心之源是气。心为理气之合,故其发用呈现为道心和人心,前者属理,后者属气。同时心又统摄性情,理所当然“心之用”又可以显发为“情”和“意”。“情”发于“性理”,“意”发于“心气”。发于性理之善和发于心气之善者,虽同为至善之物,显发为“善”的过程却各有差异。这一过程乃攸关性理学存养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课题,对此权近未作具体阐发。直至16世纪,李滉、李珥等理学家群体们才对之进行深入而具体的讨论。
权近在书中对“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作出了解释。“‘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即仁义礼智之端,非有二也。今子既以四者列于情下,又书其端,于外别作一圈,何也?’曰:‘四者之性,浑然在中。而其用之行,随感而动。以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心则是心,即为四者之端,诚非二也。然发于中者,谓之心;现于外者,谓之端。故孟子于此几两言之,或言端,或不言端。而朱子于言端,以为犹物在中,其端绪见于外,则其义愈明而不容无辨矣。’”③对于学生就此问题的提问,权近回答说四者之性是浑然在中者,而四者之端则是犹物在中而其端绪见于外者。二者诚非二物。其实这是讲仁义礼智之性如何生发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情的问题。对于性情关系问题,朱子学的基本看法是“情根于性,性发为情”;权近在此亦持相同立场。但他之所以视二者为“诚非二物”,是因为四德与四端之情皆为纯善之物的缘故。
权近还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①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的基本问题。《入学图说》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论辩之先河。沙溪金长生(1548—1631年)说过:“退溪先生七情四端互发之说,其原出于权阳村《入学图说》。其图中,四端书于人之左边,七情书于人之右边。郑秋峦之云,因阳村而作图,李滉又因秋峦而作图,此互发之说所由起也。李滉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是阳村分书左右之意。”②不仅如此,权近还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对佛、道进行批判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认为“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③。权近这一思想后为李滉发展为“理尊无对”说和“理贵气贱”说,从而开启了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主理论传统。
权近有关四端七情问题的看法实为百余年后李滉、奇大升、李珥、成浑等诸家旷日持久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为代表的岭南学派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儒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伦理上的道德情感,典出《孟子·公孙丑上》;“七情”则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生理上的自然情感,典出《礼记·礼运篇》。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并未引起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儒学界引发了一场“四端七情,理发气发”的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使韩国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哲学轨道,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四端七情”这一问题的关注意味着韩国儒学已然开启本土化的进程。
权近与郑道传虽然同为朝鲜朝初期的理学大家,但是在接受和传播朱子学方面却各有特色。郑道传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注重朱子学理论本身的探究与思考。若就两人对韩国朱子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后世学者视为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主要代表。李滉也很服膺权近的学问,曾对其评价道:“阳村学术渊博,为此图说极有证据,后学安敢议其得失。”①权氏《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示类书籍,所以他被目为韩国儒学界“以图释说”研究范式的开创者。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传至日本,且在日本儒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曾多次翻刻权氏《入学图说》,现存宽永甲戌刻本和庆安元年刻本等。
权近的主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以及《三峰集》中的《佛氏杂辨》序,《心气理篇》注、序等。现有《阳村集》(40卷)。
二、柳崇祖与其“四端七情”论
中宗时期的真一斋柳崇祖(字宗孝,号真一斋、石轩,1452—1512年)是朝鲜朝前期继权近之后又一位论及四端七情理气问题的性理学家。柳氏本贯为全州,谥号为文穆。他成宗三年(1472年)中司马试进入太学,1489年文科及第,历任司谏院正言、弘文馆副校理、司宪府掌令、成均馆大司成等官职。他是“官学派”的代表,但是对“士林派”学者亦相当友好,在任大司成时还荐举了赵光祖、金锡弘、黄泽等“士林派”学者。燕山君十年(1504年)被发配至原州,中宗反正之后又官复原职。史书上对其为人有如下记载:“文穆公,天资高明,器宇峻洁,早有志于学。其为学也,本之以孝弟忠信,律之以刚方廉直,六经诸子与百家,靡不淹贯,妙年升庠,已有道义之所推服,既擢第入翰苑,儒臣启,以经明行修,可为师表,兼带成均掌教,教导后进,先正臣李滉所称师友堂堂经训皇皇者也。当燕山主九年,文穆在宪府,抗疏论十余事,皆切直不少讳,贬其官,甲子祸作,杖窜原州,靖国之初,首入经幄,旋升工曹参议,三公启,经幄不可无此人,命兼带经筵官。遂长国子,三公又启,性理之学,不可绝其传,请选年少文臣,就崇祖受业,崇祖承命,课授甚勤,作为四经、四书等谚解,以晓诸生,宣庙朝所纂集刊行者也。又命选诸生中可大用者以奏,崇祖,以文正公臣赵光祖首荐,六年辛未,上亲临太学,谒先圣,退御明伦堂,横经问难时,崇祖为大司成,以大学进讲,反复乎存心出治之要,上凝旒倾听,桥门观者皆耸然。”①柳氏在《书经》、《易经》、《礼记》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以口诀和悬吐的方式给“四书”、“三经”编了《七书彦解》②,作为韩国彦解类之嚆矢,对后世影响颇大。柳氏的著作还有《真一斋集》、《大学十箴》、《性理渊源撮要》等。
《性理渊源撮要》摘取先儒学说中的紧要段落加以编纂,从中可见其性理学思想。而《大学十箴》则以箴规人主之思想行为为目的。全书将《大学》内容分成明明德箴、作新民箴、止至善箴、使无讼箴、格物致知箴、谨独箴、正心箴、修身箴、齐家治国箴和絜矩箴十个条目,分门别类以述帝王学之要义。依柳氏之见,大学之道,是修齐治平之准绳,是方圆平直之至。为君者之所以不可不明此大学之道,是因为为政之规矩准绳之所出;为臣者之所以不可不讲此大学之道,是因为为臣者之规矩准绳之所由施;为民者之所以不可不知此大学之道,是因为规矩准绳之所当从。他进一步指出,二帝三皇之所以盛治者,乃正其规矩准绳之体,以成己而运之于上,故方圆平直之用自正而物成于下。
在理与气这一性理学基本问题上,柳崇祖认为:“气与理,气殊形禀理一天地,气不外理,理寓气里。理不离气,浑然一体,气不杂理,粲然不混。无先无后,无端无始。赋物之初理一气二,物禀之后气同理异。”③柳氏倾向理气“混沦一体”、“不离不杂”的传统朱子学立场。他认为理气二者在时间上无先后、无终始,赋物之初理一气二,物禀之后“气同理异”。柳崇祖正视分殊之理的差异性,认为既有天下公共之理,又有一物各具之理。柳氏思想较具特色,在人性论领域尤重“气质之性”。
在“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上,柳氏提出:
天下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有阴阳则有木火金水者气也,有健顺则有仁义礼智者理也。气非理则无所承,理非气则无所附,是故未有阴阳已有太极,未有此气已有此理。推所从来,固不无先后之别,然言太极则已不离乎阴阳,言性则已不离乎气质,有则具有,又岂别为一物而有先后之可言哉。合而言之,则太极无物不存,万物各具一太极,性即气、气即性,盖未始相离也。初岂有所谓本然之性而又岂有所谓气质之性哉。分而言之,则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性自性、气自气,又未始有相杂也。岂无所谓本然之性又岂无气质之性哉。①
此处涉及理(太极)的逻辑在先问题。理气之关系推所从来“固不无先后之别”,只能说“未有阴阳已有太极,未有此气已有此理”。但在现实生活中,言太极时则已不离乎阴阳,“言性则已不离乎气质”。柳崇祖在此着重说明“气质之性”的实在性和现实性。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性本于天,虽气之本而气存于人,实性之用。性如日月之明而气则如云雾之昏矣。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盖谓此也。夫形气未禀人物未生,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是人生而静以上也,可名之以理,不可名之以性,所谓在天曰命,是专以理言也。及降而在人则坠于形气,虽可谓之性,然已涉于有生,而不得超然于是理之本体矣。是才说性则便已不是性也,是所谓在人曰性也,是专以气质而言之。”②需要指出,尽管先儒在人性论方面已有本然之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之说,但是柳氏在性论上仍然坚持二程“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③的性气合一论。若综合上一段引文的内容来看,严格地讲他更倾向于明道的“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④的性气不离的思想。
柳崇祖曾对历史上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性”论做过评说,指出:“盖观古人之论‘性’,孟子专以本然言性,而不及于气,所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杨误以气质为性,而不识其本,所谓论气不论性不明;韩子之言性可谓备矣,五性之说固已见其理之同,三品之说乃不知其气之异。此廉溪张程所以不得不表彰而发明之也。然考之经传已有此意,但古人未尝明著其气质之名尔。”①儒家之人性论确有一个发展过程,曾产生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但是,张载“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这样性二元论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讨论推向了高潮。朱熹这样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②但朱熹之后人性论从性二元论逐渐转向性气合一的性一元论,开始强调现实性。从东亚儒学史的视角来看,人性论的此一转向在我国明代学者罗整庵(主理气一物论)、王廷相(主理气无性论)以及韩儒柳崇祖的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也反映了在理学传统中道德理想(理想性)与现世关怀(现实性)的尖锐冲突,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思想运动的演进,儒者的现实指向性在逐渐增强。此理论转向可视为17世纪东亚各国注重实践性与功利性的“实学”思潮兴起的前奏。
在权近提出以理气分言分四端七情的观点之后,柳崇祖也提出大体相同的主张。他在《大学十箴》中的“明明德箴”中写道:
一阴一阳,本一太极,继善成性,理气妙合,秉彝懿德,人所同得,精真之凝,灵妙虚寂,不吝于愚,不豊于智。内具众理,外应万事,统性与情,神明莹澈。情动于性,纯善无杂。意发于心,几善与恶。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③柳氏认为“四端”是理动所致,而“七情”则是气动所致。此一理动气动的解释模式说明他将二者视为基于不同发用过程的两种不同的情感。其“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的观点与日后的李滉“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思想颇为相似。柳崇祖在大作《性理渊源撮要》中将程迥(沙随程复心)理气说做了进一步阐发,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然之性,理也,仁义礼智信,五性皆天理,故本无不善。气质之性,气也,纯清者全其性,上智也。杂清浊者,善恶混,中人也。纯浊者,全是恶,下愚也。理发为四端,气发为七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者正情,无有不善。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中节则公而善,不中则私而恶。①
感通之谓情,则四端者理之发,七情者气之发。能为之谓才,则无不善者出乎性,而有不善者出乎气也。由是观之,理无不同也,所不同者气耳。理无不善也,所不善者才耳。②柳崇祖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主张,在以上言论中得到再次确认。他认为四端七情根源不同,坚持对之区别对待。
从柳氏在《性理渊源撮要》中对程迥“四端七情”说的整理可以窥见,其思想主张在先儒著述中也不无痕迹。像“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之说就与权近之“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之主旨大体相同。可见,“四七”对举、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传统早在郑之云之前的朝鲜朝性理学中即已存在。此为韩国性理学的又一特征。
柳崇祖对朝鲜朝性理学发展的贡献,在史书上也有记载:“窃稽中庙朝大司成赠谥文穆公臣柳崇祖,倡明道学,所撰进《大学十箴》、《性理渊源撮要》及经书《七书彦解》等书,启沃圣德,嘉惠后学,实为旷世之真儒,后生之师表,允合庑享之联跻而尚未彻旒,岁年侵寻,章甫之赍郁,不日不月,而朝家之令典,抑亦恐有未遑。臣等之责,愈久愈深,今当卫辟存闲之庆会,自不敢泯然,各道缝掖之徒,不谋而同,齐声而应,谨摭其平日实迹之有关于斯文者,以备乙览焉。”③
简言之,权近的《入学图说》和柳崇祖的《性理渊源撮要》所开创的“四七”对举之范式成为朝鲜朝“四端七情”之辨的理论端绪。明显可以看出,《入学图说》和《性理渊源撮要》中出现的“四七”对举的思想与郑之云、李滉的“四七互发”说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关联。
一、权近与其“四端七情”论
活跃于丽末鲜初思想界的朱子学者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与郑道传一起并称为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双璧。权氏为安东人,曾受教于李穑和郑道传。他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前文所介绍的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
据年谱记载,权近步入仕途初期颇为顺当。他年17岁中成均试,年18岁(洪武二年己酉),三月中馆试第二名,五月樵隐李仁复、牧隐李穑同掌礼闱中第三名,六月擢殿试丙科第二名,七月直拜春秋检阅。历任中正大夫成均祭酒、艺文馆提学、成均馆的大提学、大司成等官职。但是,38岁(昌王元年)时他因“礼部咨文”事件中言事所牵连被贬到黄海道牛峰,后又贬至宁海。①在韩国儒学史上不管是“以图示说”的研究传统,还是四七论辩的理论萌芽皆可以追溯至权近,故后人赞其道:“丽朝以来,非无名人器士,而所尚者,文章勋业也。惟文忠公郑梦周,始传程朱之学,而遭时不幸,未有著述。文康公权近,有文章学识,而《入学图说》以四端七情,分左右书之。此所以理气之发于二歧也。后来学者传袭之论,无复异趣。”②
他一生致力于性理学理论之探究,为朱子学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泽堂李植曾说过:“我国先儒,皆无著述,权阳村说经论学,始有著述。”③其力作《五经浅见录》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了“五经”,而《入学图说》则是韩国最早一部理解朱子学思想的入门向导书籍,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近的《入学图说》是其为初学者讲授“四书五经”而作的一部“以图示说”的性理学入门书籍。全书分为前后集,前集中载有“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诸侯昭穆五庙都宫之图”等26种图说;后集中则收有“十二月卦之图”、“周天三辰之图”、“一朞生闰之图”、“天地竖看之图”、“天地横看之图”等14种图说,共计40种图说。卷首有权近的“自序”,卷末有郑道传和卞季良的跋文,书中权近将儒家经书中能够“图示”的内容尽己所能以图解的形式表现出来,极大方便了初学者的学习。
此图说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和李滉的《圣学十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滉的《圣学十图》中的“大学图”与权近的“大学指掌之图”可说是一脉相承。因此《入学图说》被后人称为韩国“图书学”的嚆矢。
尽管为初学者而作,《入学图说》还是集中反映了权近的心性论思想。其中又以“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和“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尤为根本。该书收录的40篇图说中,讲授“四书”的有6篇,讲授“五经”的有3篇,讲授“河图洛书”的有10篇,讲授礼的有4篇,讲授天文地理的有12篇等等。在这40篇图说中,较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的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中庸分节辨议”、“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五经体用分释之图”等篇,而“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五经体用分释之图”等图示正是权近对“四书五经”内容的系统解说图。权近思想除了此图说外,还散见于《阳村集》、《礼记浅见录》以及《三峰集》之注释内容。
下面,首先对其“天人心性合一之图”①(见图2)作出分析。
此图集中反映了权近的哲学思想。在该图解释的开头他便写道:“朱子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今本之作此图。”②表明此图的理论依据来自朱熹的宇宙论(理气论)。紧接着又写道:
右图谨依周子“太极图”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说,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故不及万物化生之象,然人物之生,其理则周,而气有通塞偏正之异,得其正则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即此图而观,则诚字一圈,得最精最通而为圣人;敬字一圈,得正且通者而为众人;欲字一圈,得偏且塞者而为物;其下禽兽横者得其尤偏塞而为草本者也。是则万物化生之象亦具于其中矣。夫天地之化,生生不穷,往者息而来者继。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①
可见,此图是权近谨依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的《中庸章句》之说制作而成。权近在图说中还附上其与弟子的有关天人心性问题的答问。此图不仅谈到了“太极”、“天命”、“理气”、“阴阳”、“五行”以及“四端七情”等性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还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图示形式清楚表示出来,使学者易于理解和把握其要领。
权近的性理学说非常重视“心”,以至于在其心性论中“性”是在论“心”时才附带成为讨论的对象。权近曰:“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①如图中所见,他对“心”这一概念作了详细辨析,并对像“性”、“情”、“意”、“诚”、“敬”、“欲”等概念皆从心性论到修养论多角度作了分析。从图中可见,他将“性”之德目规定为仁、义、礼、智、信;“情”则指代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喜怒哀惧爱恶欲;“意”为几善恶;“诚”乃真实无妄,纯亦不已,圣人性之;“敬”为存养省察,君子修之;“欲”为自暴自弃,众人害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心”大体上是相较于“身”而言。因为他认为,心是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者,是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故他写道:“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沫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虽曰应万事,而是非错乱,岂足为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其有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若从理学的心身关系的角度来看,因“心”有具众理而应万事之功能,故主宰个体肉身活动的只能是“心”。可见,性理学以为人的身体和神明的作用皆与“心”相关联。
另外,心之重要特征,即“虚灵洞彻”与“神明”问题在图中虽未标示,但是在论著中也有对此一问题的相关论述。他认为,心不仅仅是“神明之舍”,更是具有虚灵之妙之特性的认识器官。因心是“气之精爽”、“气之灵”,故此心具有虚灵之特性,可以应对万事。他将心比喻为“心之灵而镜之明也”,还说:“心之本体,寂然无朕,而其灵知不昧,譬则镜性本空,而明无不照。盖随缘者,心之灵而镜之明也。”③心之寂与镜之空是不变者,而心则以此感应万变而无穷尽。他还认为心所生发的行为可以为善为恶,而为善的行为必源于纯善无恶之性。
权近和郑道传皆为丽末鲜初的著名斥佛论者,权氏在展开其性理学“心”论的同时还对释氏所讲之“心”作了批判。“盖外边虽有应变之迹,而内则漠然无有一念之动,此释氏之学第一义也。”①佛教不承认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以为现实世界为虚幻的、不真实的存在。这种心说所隐含的是遁世绝俗、逃避现实的消极的人生态度,自然与主张积极入世、力求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人生观相去甚远。因此受到儒者的猛烈抨击。对此权近也批评道:“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沫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其有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可见,他所讲的“心”正是朱子学所言之天理论视域下的理气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权近绘制此图的目的在于“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③。将理气摄入心性域来讨论是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色,这一理论传统其实亦肇始于权近。韩儒的心性学说与其说是对人之性情问题的探究,不如说是从理气论的向度对人的性理问题的阐发。因人的行为皆与心理活动相关联,所以韩儒在思考如何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时重点考察了人的行为的根源,即试图立足于心性论以阐明人之道德行为的发生根源。于是,属于理学本体论范畴的理气概念被纳入心性论域,用于直接讲明人的道德行为的来源和根据。从“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可以看到,“心”分善恶,而整图则被代表理气的白色和黑色一分为二。心具众理,性源于理,理若如实呈现即为纯善。故圣人即是完全实现心中之理者。
如前所述,韩国性理学关注的首要课题是“人”,即具有道德良知的现实中的人。这一特点从《入学图说》开篇第一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亦能窥见。此图说首先要辨明的是人的心性问题,而非天地万物如何化生的本体论问题。
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善恶选择时如何抉择“善”,这是关乎修养论(工夫论)的问题,为此权近标出了“敬”。图中善恶被分在“心”之两侧,而“敬”又与二者相关联,意为人之为善为恶皆系于以“主敬”为主的存养省察工夫。
其次,讨论其“天人心性分释之图”的“天”之图(见图3)和其“人”之图①(见图4)。
从《入学图说》的排序中也可看到,权近是在第一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
中先论人之后,又在“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中次第论及“天”、“诚”、“敬”。“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天”之图显示“天为一大”:“一者”意为以理言则无对,以行言则无息,故为万殊之本;“大者”则意为以体言则无外,以化言则无穷,故为万化之源。其“以理言则无对”的观念与日后李滉“理极尊无对”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皆基于以理为本的理气论传统。“敬”是指主敬涵养下学工夫,“诚”是天人合一之媒介,故《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①
在“人”之图下,权近附言道:
人者,仁也。仁则天地所以生物之理,而人得以生而为心者也。故人为万物之灵,仁为众善之长,合而言之道也。圣人至诚,道与天同。君子能敬以修其道,众人以欲而迷,惟恶之从。故人者,其理一,而所禀之质,所行之事,有善恶之不同。故其为字,歧而二之,以示戒焉。人能体仁,以全心德,使其生理常存而不失,然后可无愧于为人之名。而其效必能得寿,不然则生理丧而非人矣。②
依权近之见,“仁”是天地所以生物之理,在人则为心。因此人是万物之灵,仁为众善之长,而将二者合而言之便是道。他进而指出惟君子能敬以修其道,而众人则迷于欲念、惟恶之从。权近将“仁”也就是文中所谓“生之理”视为人的本质。众所周知,儒家将“仁”视为人与万物共同的普遍原理,表现在人身上即为“人之性”。
再次,讨论其“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心”之图(见图5)。
对于此“心”之图,权近解释道:
心者,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理气妙舍、虚灵洞彻、以为神妙之舍而统性情,所谓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者也。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其用之发有时而昏。学者要当敬以直内,去其昏而复其明也。其字形方者,象居中方寸之地也。其中一点,象性理之源也。至圆至正,无所偏,象心之体也。其下凹者,象其中虚,惟虚故具象理也。其首之尖,自上而下者,象气之源,所以妙合而成心者也。其尾之锐,自下而上者,心于五行属火象,火之炎上也,故能光明发动以应万物也。其右一点象性发为情,心之用也;其左一点象心发为意,亦心之用也,其体则一而用则二。其发原于性命者,谓之道心而属乎情,其初无有不善,其端微而难见,故曰道心惟微,必当主敬以扩充之。其生于形气者谓之人心而属乎意,其几有善有恶,其势危而欲坠,故曰人心惟危,尤必当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然后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差谬而圣贤同归,参赞天地亦可以驯致矣。不然,则人欲日长,天理日消,此心之用不过情欲利害之事,虽有人形,其违禽兽不远矣。可不敬哉。①尽管此文篇幅不长,权近还是简明扼要地对心身关系、心之结构、心之机能、心之作用、心之体用等都作了必要的说明。在心身关系方面,主张心是“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亦即心为身之主宰;在心之结构方面,认为心是理气妙合而为神妙之舍;对于心之机能则主虚灵洞彻,由是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对于心之作用倾向心性关系中“心统性情”;至于心之体用则主心体至正无偏而为性理之源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即是用。①其体则一,而用则二。道心原于性命而属乎情,“其初无有不善,其端微而难见,故曰道心惟微”;人心则生于形气之私而属乎意,“其几有善有恶,其势危而欲坠,故曰人心惟危”。因此,以主敬工夫扩充天理之正,以遏人欲之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便可做到危者安而微者著。以上是权近心论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其基本见解皆来自朱熹理论。如对心之机能,朱熹曾有如下论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②在文中权近还探讨理欲之关系,以为二者此消彼长,必由主敬工夫方能扩充天理,所谓“人欲日长,天理日消”。
此图需注意的是,权近按心的字形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加以解释:其一为“理之源”;其二为“气之源”。他将道心和人心、情和意以性为中心分别列于“理之源”和“气之源”之下:道心属情,其初无有不善;人心属意,其几有善有恶。在权近看来,此时之“情”根于理,作为“四端”之情无有不善,人心是发于气之意,故其几有善有恶。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的思想行为或源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韩儒则更倾向于从理气之发的视角来探讨此一问题。权氏殆以作为心之二用的情意分别生于理与气——“其体则一而用则二”。“情”和“意”乃人心的两种发用方式,源于性命者为道心(情),生于形气者为人心(意)。因此“学者要当敬以直内”,防止生于私欲的行为的发生。
“人心道心”问题在韩国儒学史上极为重要。权近对此一问题基本立场是“人心惟危,尤必当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然后危者安,微者著。”依其之见,“情”的行为一般能呈现较为理想的状态,源于气的“意”则不然,后者之呈现或善或恶,不由“心”的作用即无以引之向理。
权近以“理之源”和“气之源”判分人心以作解释,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
最后,再讨论其有关“性”的论述(见图6)。
理学宇宙论(本体论)需借理气说才能得到阐发。从上文可见权近的思想大体不离伊洛渊源,是故在其学说中“性”总被赋予普遍宇宙之原理义,所谓“性即理”是也。
在《入学图说》中,权近彰示“性”之图并写道:
性者,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于吾心者也。故其为字,从心从生。人与万物其理则同,而气质之禀有不同者焉。告子曰生之谓性,韩子曰与生俱生,释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气言而遗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①
此图亦是为初学者而设。权近自言道,其训天人心性分释之意有些破碎,但是初学者则一见即可知其大意要旨。并标榜其解说皆本自程朱的格言,非为其臆说。初学之士的要务,则在于动处下功夫,而存养之事已包含在“敬”之中。
理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反躬实践,而在现实中如何如实地呈现“理”和实践“理”遂成首要课题。为此权氏欲将天人问题转化为心性问题,以图在心性层面上实现“天人合一”这一儒家最高价值理想。心作为理气之合既具形上之特性,又有形下之特性。而且心还以“虚灵洞彻”统摄性情,由是具众理以应万事者。因此,在心的层面上追求其与性理的合一便是“仁学”思想的主旨。
“心具众理”强调的是“理”常存于人心。理学家认为,人心之理即性理不能如实呈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②之故。权近重视“性”,亦因“理”只有通过“性”的发用才能呈现。那么,究竟由何呈现呢?无疑是要由“心”来呈现。从此意义上说,权近“心统性情”的思想可以视为对主体以其“实践性”能动地呈现天理的一种阐述。
如前文所述,他将“性”定义为“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于吾心者”。①这与程朱对“性”的论述大体相同,伊川曾言:“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②又说过:“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③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解释道:“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有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④相较于程朱,权近的性理概念更强调“生之理”之义。
“性”字“从心从生”,仅就字形便可了知其与人心、人生的密切关系。作为性理学家,权近对历史上出现的不同“性”说评价道:“告子曰,生之谓性;韩子曰,与生俱生;释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气言而遗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在他看来,告子、韩非子以及释氏之“性”论的主要理论缺陷是未意识到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即所谓“义理之性”。这也反映了性理学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安身立命,而且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道德水平的提升。于此可见,儒家的确比其他学派理论更具道德关怀。权氏的“性”论与其说对人之本性的阐发,不如说是对人的能动实践能力的揭示,故可将其拟于实践性理学。
权近在书中“天人心性分释之图”的“性”条里面还写道:
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於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又况程子之言,以为外物触而动于中,其中动而七情出,情既炽而其性鉴矣。则其不以为性发也,审矣。①
他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之善并无二致,皆为同质之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非为性之所发,故不能与“四端”并列。依权氏之见,“四端”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权近不仅依此区分“四端”和“七情”,还进而以理气分判道心与人心:“理本无为,其所以能灵而用之者,气也……道心为危,人心惟微,则固以理气分言之矣。夫心之发其几有善恶之殊,若纯乎理而不杂乎气,则其发安有不善哉。”②从权近“心”之图(图5)中可见,是以“理之源”和“气之源”的视角对心进行解读。依其思路,性之源是理,心之源是气。心为理气之合,故其发用呈现为道心和人心,前者属理,后者属气。同时心又统摄性情,理所当然“心之用”又可以显发为“情”和“意”。“情”发于“性理”,“意”发于“心气”。发于性理之善和发于心气之善者,虽同为至善之物,显发为“善”的过程却各有差异。这一过程乃攸关性理学存养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课题,对此权近未作具体阐发。直至16世纪,李滉、李珥等理学家群体们才对之进行深入而具体的讨论。
权近在书中对“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作出了解释。“‘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即仁义礼智之端,非有二也。今子既以四者列于情下,又书其端,于外别作一圈,何也?’曰:‘四者之性,浑然在中。而其用之行,随感而动。以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心则是心,即为四者之端,诚非二也。然发于中者,谓之心;现于外者,谓之端。故孟子于此几两言之,或言端,或不言端。而朱子于言端,以为犹物在中,其端绪见于外,则其义愈明而不容无辨矣。’”③对于学生就此问题的提问,权近回答说四者之性是浑然在中者,而四者之端则是犹物在中而其端绪见于外者。二者诚非二物。其实这是讲仁义礼智之性如何生发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情的问题。对于性情关系问题,朱子学的基本看法是“情根于性,性发为情”;权近在此亦持相同立场。但他之所以视二者为“诚非二物”,是因为四德与四端之情皆为纯善之物的缘故。
权近还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①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的基本问题。《入学图说》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论辩之先河。沙溪金长生(1548—1631年)说过:“退溪先生七情四端互发之说,其原出于权阳村《入学图说》。其图中,四端书于人之左边,七情书于人之右边。郑秋峦之云,因阳村而作图,李滉又因秋峦而作图,此互发之说所由起也。李滉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是阳村分书左右之意。”②不仅如此,权近还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对佛、道进行批判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认为“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③。权近这一思想后为李滉发展为“理尊无对”说和“理贵气贱”说,从而开启了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主理论传统。
权近有关四端七情问题的看法实为百余年后李滉、奇大升、李珥、成浑等诸家旷日持久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为代表的岭南学派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儒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伦理上的道德情感,典出《孟子·公孙丑上》;“七情”则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生理上的自然情感,典出《礼记·礼运篇》。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并未引起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儒学界引发了一场“四端七情,理发气发”的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使韩国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哲学轨道,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四端七情”这一问题的关注意味着韩国儒学已然开启本土化的进程。
权近与郑道传虽然同为朝鲜朝初期的理学大家,但是在接受和传播朱子学方面却各有特色。郑道传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注重朱子学理论本身的探究与思考。若就两人对韩国朱子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后世学者视为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主要代表。李滉也很服膺权近的学问,曾对其评价道:“阳村学术渊博,为此图说极有证据,后学安敢议其得失。”①权氏《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示类书籍,所以他被目为韩国儒学界“以图释说”研究范式的开创者。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传至日本,且在日本儒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曾多次翻刻权氏《入学图说》,现存宽永甲戌刻本和庆安元年刻本等。
权近的主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以及《三峰集》中的《佛氏杂辨》序,《心气理篇》注、序等。现有《阳村集》(40卷)。
二、柳崇祖与其“四端七情”论
中宗时期的真一斋柳崇祖(字宗孝,号真一斋、石轩,1452—1512年)是朝鲜朝前期继权近之后又一位论及四端七情理气问题的性理学家。柳氏本贯为全州,谥号为文穆。他成宗三年(1472年)中司马试进入太学,1489年文科及第,历任司谏院正言、弘文馆副校理、司宪府掌令、成均馆大司成等官职。他是“官学派”的代表,但是对“士林派”学者亦相当友好,在任大司成时还荐举了赵光祖、金锡弘、黄泽等“士林派”学者。燕山君十年(1504年)被发配至原州,中宗反正之后又官复原职。史书上对其为人有如下记载:“文穆公,天资高明,器宇峻洁,早有志于学。其为学也,本之以孝弟忠信,律之以刚方廉直,六经诸子与百家,靡不淹贯,妙年升庠,已有道义之所推服,既擢第入翰苑,儒臣启,以经明行修,可为师表,兼带成均掌教,教导后进,先正臣李滉所称师友堂堂经训皇皇者也。当燕山主九年,文穆在宪府,抗疏论十余事,皆切直不少讳,贬其官,甲子祸作,杖窜原州,靖国之初,首入经幄,旋升工曹参议,三公启,经幄不可无此人,命兼带经筵官。遂长国子,三公又启,性理之学,不可绝其传,请选年少文臣,就崇祖受业,崇祖承命,课授甚勤,作为四经、四书等谚解,以晓诸生,宣庙朝所纂集刊行者也。又命选诸生中可大用者以奏,崇祖,以文正公臣赵光祖首荐,六年辛未,上亲临太学,谒先圣,退御明伦堂,横经问难时,崇祖为大司成,以大学进讲,反复乎存心出治之要,上凝旒倾听,桥门观者皆耸然。”①柳氏在《书经》、《易经》、《礼记》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以口诀和悬吐的方式给“四书”、“三经”编了《七书彦解》②,作为韩国彦解类之嚆矢,对后世影响颇大。柳氏的著作还有《真一斋集》、《大学十箴》、《性理渊源撮要》等。
《性理渊源撮要》摘取先儒学说中的紧要段落加以编纂,从中可见其性理学思想。而《大学十箴》则以箴规人主之思想行为为目的。全书将《大学》内容分成明明德箴、作新民箴、止至善箴、使无讼箴、格物致知箴、谨独箴、正心箴、修身箴、齐家治国箴和絜矩箴十个条目,分门别类以述帝王学之要义。依柳氏之见,大学之道,是修齐治平之准绳,是方圆平直之至。为君者之所以不可不明此大学之道,是因为为政之规矩准绳之所出;为臣者之所以不可不讲此大学之道,是因为为臣者之规矩准绳之所由施;为民者之所以不可不知此大学之道,是因为规矩准绳之所当从。他进一步指出,二帝三皇之所以盛治者,乃正其规矩准绳之体,以成己而运之于上,故方圆平直之用自正而物成于下。
在理与气这一性理学基本问题上,柳崇祖认为:“气与理,气殊形禀理一天地,气不外理,理寓气里。理不离气,浑然一体,气不杂理,粲然不混。无先无后,无端无始。赋物之初理一气二,物禀之后气同理异。”③柳氏倾向理气“混沦一体”、“不离不杂”的传统朱子学立场。他认为理气二者在时间上无先后、无终始,赋物之初理一气二,物禀之后“气同理异”。柳崇祖正视分殊之理的差异性,认为既有天下公共之理,又有一物各具之理。柳氏思想较具特色,在人性论领域尤重“气质之性”。
在“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上,柳氏提出:
天下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有阴阳则有木火金水者气也,有健顺则有仁义礼智者理也。气非理则无所承,理非气则无所附,是故未有阴阳已有太极,未有此气已有此理。推所从来,固不无先后之别,然言太极则已不离乎阴阳,言性则已不离乎气质,有则具有,又岂别为一物而有先后之可言哉。合而言之,则太极无物不存,万物各具一太极,性即气、气即性,盖未始相离也。初岂有所谓本然之性而又岂有所谓气质之性哉。分而言之,则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性自性、气自气,又未始有相杂也。岂无所谓本然之性又岂无气质之性哉。①
此处涉及理(太极)的逻辑在先问题。理气之关系推所从来“固不无先后之别”,只能说“未有阴阳已有太极,未有此气已有此理”。但在现实生活中,言太极时则已不离乎阴阳,“言性则已不离乎气质”。柳崇祖在此着重说明“气质之性”的实在性和现实性。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性本于天,虽气之本而气存于人,实性之用。性如日月之明而气则如云雾之昏矣。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盖谓此也。夫形气未禀人物未生,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是人生而静以上也,可名之以理,不可名之以性,所谓在天曰命,是专以理言也。及降而在人则坠于形气,虽可谓之性,然已涉于有生,而不得超然于是理之本体矣。是才说性则便已不是性也,是所谓在人曰性也,是专以气质而言之。”②需要指出,尽管先儒在人性论方面已有本然之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之说,但是柳氏在性论上仍然坚持二程“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③的性气合一论。若综合上一段引文的内容来看,严格地讲他更倾向于明道的“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④的性气不离的思想。
柳崇祖曾对历史上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性”论做过评说,指出:“盖观古人之论‘性’,孟子专以本然言性,而不及于气,所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杨误以气质为性,而不识其本,所谓论气不论性不明;韩子之言性可谓备矣,五性之说固已见其理之同,三品之说乃不知其气之异。此廉溪张程所以不得不表彰而发明之也。然考之经传已有此意,但古人未尝明著其气质之名尔。”①儒家之人性论确有一个发展过程,曾产生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但是,张载“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这样性二元论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讨论推向了高潮。朱熹这样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②但朱熹之后人性论从性二元论逐渐转向性气合一的性一元论,开始强调现实性。从东亚儒学史的视角来看,人性论的此一转向在我国明代学者罗整庵(主理气一物论)、王廷相(主理气无性论)以及韩儒柳崇祖的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也反映了在理学传统中道德理想(理想性)与现世关怀(现实性)的尖锐冲突,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思想运动的演进,儒者的现实指向性在逐渐增强。此理论转向可视为17世纪东亚各国注重实践性与功利性的“实学”思潮兴起的前奏。
在权近提出以理气分言分四端七情的观点之后,柳崇祖也提出大体相同的主张。他在《大学十箴》中的“明明德箴”中写道:
一阴一阳,本一太极,继善成性,理气妙合,秉彝懿德,人所同得,精真之凝,灵妙虚寂,不吝于愚,不豊于智。内具众理,外应万事,统性与情,神明莹澈。情动于性,纯善无杂。意发于心,几善与恶。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③柳氏认为“四端”是理动所致,而“七情”则是气动所致。此一理动气动的解释模式说明他将二者视为基于不同发用过程的两种不同的情感。其“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的观点与日后的李滉“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思想颇为相似。柳崇祖在大作《性理渊源撮要》中将程迥(沙随程复心)理气说做了进一步阐发,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然之性,理也,仁义礼智信,五性皆天理,故本无不善。气质之性,气也,纯清者全其性,上智也。杂清浊者,善恶混,中人也。纯浊者,全是恶,下愚也。理发为四端,气发为七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者正情,无有不善。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中节则公而善,不中则私而恶。①
感通之谓情,则四端者理之发,七情者气之发。能为之谓才,则无不善者出乎性,而有不善者出乎气也。由是观之,理无不同也,所不同者气耳。理无不善也,所不善者才耳。②柳崇祖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主张,在以上言论中得到再次确认。他认为四端七情根源不同,坚持对之区别对待。
从柳氏在《性理渊源撮要》中对程迥“四端七情”说的整理可以窥见,其思想主张在先儒著述中也不无痕迹。像“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之说就与权近之“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之主旨大体相同。可见,“四七”对举、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传统早在郑之云之前的朝鲜朝性理学中即已存在。此为韩国性理学的又一特征。
柳崇祖对朝鲜朝性理学发展的贡献,在史书上也有记载:“窃稽中庙朝大司成赠谥文穆公臣柳崇祖,倡明道学,所撰进《大学十箴》、《性理渊源撮要》及经书《七书彦解》等书,启沃圣德,嘉惠后学,实为旷世之真儒,后生之师表,允合庑享之联跻而尚未彻旒,岁年侵寻,章甫之赍郁,不日不月,而朝家之令典,抑亦恐有未遑。臣等之责,愈久愈深,今当卫辟存闲之庆会,自不敢泯然,各道缝掖之徒,不谋而同,齐声而应,谨摭其平日实迹之有关于斯文者,以备乙览焉。”③
简言之,权近的《入学图说》和柳崇祖的《性理渊源撮要》所开创的“四七”对举之范式成为朝鲜朝“四端七情”之辨的理论端绪。明显可以看出,《入学图说》和《性理渊源撮要》中出现的“四七”对举的思想与郑之云、李滉的“四七互发”说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