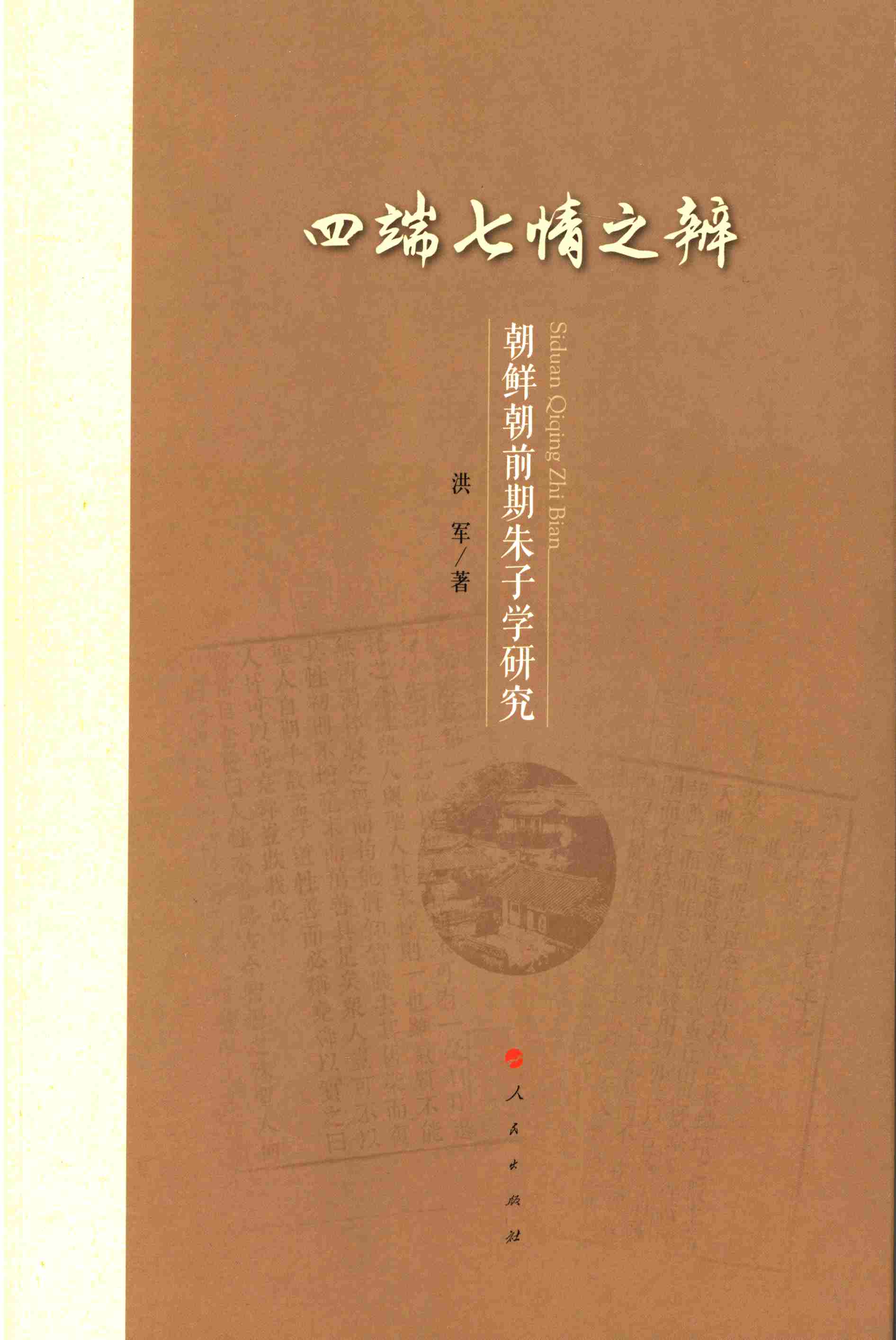内容
朝鲜朝开国之后,郑梦周一系的部分节义派学者即以岭南地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以义理研究为特色的“士林学派”。他们大兴私学教育,培养了众多新进士林。世宗(1419—1450年在位)朝时起“士林派”学者逐渐进驻中央朝政,与勋旧派形成了严重对立。于是,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60年代,两派之间曾发生了多次流血事件。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士祸”便发生于此一历史时期。经过多次血腥的“士祸”洗礼,“士林派”逐渐成为主导16世纪以后的韩国思想界和政界的政治势力,同时亦被定为韩国儒学史上的正统正脉。
第一节 四端七情论辩之发端
——以权近、柳崇祖的“四端七情”说为中心
权近、柳崇祖及郑之云等皆为朝鲜朝前期的著名朱子学者,其在四端七情问题上的论述和主张,遂成日后退溪李滉、高峰奇大升、栗谷李珥、牛溪成浑等人进行“四端七情理气”之辨的理论端绪。本节首先将权近和柳崇祖的思想合在一起加以讨论,目的在于能对四端七情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有个系统的了解。
一、权近与其“四端七情”论
活跃于丽末鲜初思想界的朱子学者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与郑道传一起并称为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双璧。权氏为安东人,曾受教于李穑和郑道传。他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前文所介绍的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
据年谱记载,权近步入仕途初期颇为顺当。他年17岁中成均试,年18岁(洪武二年己酉),三月中馆试第二名,五月樵隐李仁复、牧隐李穑同掌礼闱中第三名,六月擢殿试丙科第二名,七月直拜春秋检阅。历任中正大夫成均祭酒、艺文馆提学、成均馆的大提学、大司成等官职。但是,38岁(昌王元年)时他因“礼部咨文”事件中言事所牵连被贬到黄海道牛峰,后又贬至宁海。①在韩国儒学史上不管是“以图示说”的研究传统,还是四七论辩的理论萌芽皆可以追溯至权近,故后人赞其道:“丽朝以来,非无名人器士,而所尚者,文章勋业也。惟文忠公郑梦周,始传程朱之学,而遭时不幸,未有著述。文康公权近,有文章学识,而《入学图说》以四端七情,分左右书之。此所以理气之发于二歧也。后来学者传袭之论,无复异趣。”②
他一生致力于性理学理论之探究,为朱子学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泽堂李植曾说过:“我国先儒,皆无著述,权阳村说经论学,始有著述。”③其力作《五经浅见录》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了“五经”,而《入学图说》则是韩国最早一部理解朱子学思想的入门向导书籍,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近的《入学图说》是其为初学者讲授“四书五经”而作的一部“以图示说”的性理学入门书籍。全书分为前后集,前集中载有“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诸侯昭穆五庙都宫之图”等26种图说;后集中则收有“十二月卦之图”、“周天三辰之图”、“一朞生闰之图”、“天地竖看之图”、“天地横看之图”等14种图说,共计40种图说。卷首有权近的“自序”,卷末有郑道传和卞季良的跋文,书中权近将儒家经书中能够“图示”的内容尽己所能以图解的形式表现出来,极大方便了初学者的学习。
此图说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和李滉的《圣学十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滉的《圣学十图》中的“大学图”与权近的“大学指掌之图”可说是一脉相承。因此《入学图说》被后人称为韩国“图书学”的嚆矢。
尽管为初学者而作,《入学图说》还是集中反映了权近的心性论思想。其中又以“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和“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尤为根本。该书收录的40篇图说中,讲授“四书”的有6篇,讲授“五经”的有3篇,讲授“河图洛书”的有10篇,讲授礼的有4篇,讲授天文地理的有12篇等等。在这40篇图说中,较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的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中庸分节辨议”、“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五经体用分释之图”等篇,而“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五经体用分释之图”等图示正是权近对“四书五经”内容的系统解说图。权近思想除了此图说外,还散见于《阳村集》、《礼记浅见录》以及《三峰集》之注释内容。
下面,首先对其“天人心性合一之图”①(见图2)作出分析。
此图集中反映了权近的哲学思想。在该图解释的开头他便写道:“朱子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今本之作此图。”②表明此图的理论依据来自朱熹的宇宙论(理气论)。紧接着又写道:
右图谨依周子“太极图”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说,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故不及万物化生之象,然人物之生,其理则周,而气有通塞偏正之异,得其正则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即此图而观,则诚字一圈,得最精最通而为圣人;敬字一圈,得正且通者而为众人;欲字一圈,得偏且塞者而为物;其下禽兽横者得其尤偏塞而为草本者也。是则万物化生之象亦具于其中矣。夫天地之化,生生不穷,往者息而来者继。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①
可见,此图是权近谨依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的《中庸章句》之说制作而成。权近在图说中还附上其与弟子的有关天人心性问题的答问。此图不仅谈到了“太极”、“天命”、“理气”、“阴阳”、“五行”以及“四端七情”等性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还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图示形式清楚表示出来,使学者易于理解和把握其要领。
权近的性理学说非常重视“心”,以至于在其心性论中“性”是在论“心”时才附带成为讨论的对象。权近曰:“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①如图中所见,他对“心”这一概念作了详细辨析,并对像“性”、“情”、“意”、“诚”、“敬”、“欲”等概念皆从心性论到修养论多角度作了分析。从图中可见,他将“性”之德目规定为仁、义、礼、智、信;“情”则指代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喜怒哀惧爱恶欲;“意”为几善恶;“诚”乃真实无妄,纯亦不已,圣人性之;“敬”为存养省察,君子修之;“欲”为自暴自弃,众人害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心”大体上是相较于“身”而言。因为他认为,心是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者,是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故他写道:“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沫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虽曰应万事,而是非错乱,岂足为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其有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若从理学的心身关系的角度来看,因“心”有具众理而应万事之功能,故主宰个体肉身活动的只能是“心”。可见,性理学以为人的身体和神明的作用皆与“心”相关联。
另外,心之重要特征,即“虚灵洞彻”与“神明”问题在图中虽未标示,但是在论著中也有对此一问题的相关论述。他认为,心不仅仅是“神明之舍”,更是具有虚灵之妙之特性的认识器官。因心是“气之精爽”、“气之灵”,故此心具有虚灵之特性,可以应对万事。他将心比喻为“心之灵而镜之明也”,还说:“心之本体,寂然无朕,而其灵知不昧,譬则镜性本空,而明无不照。盖随缘者,心之灵而镜之明也。”③心之寂与镜之空是不变者,而心则以此感应万变而无穷尽。他还认为心所生发的行为可以为善为恶,而为善的行为必源于纯善无恶之性。
权近和郑道传皆为丽末鲜初的著名斥佛论者,权氏在展开其性理学“心”论的同时还对释氏所讲之“心”作了批判。“盖外边虽有应变之迹,而内则漠然无有一念之动,此释氏之学第一义也。”①佛教不承认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以为现实世界为虚幻的、不真实的存在。这种心说所隐含的是遁世绝俗、逃避现实的消极的人生态度,自然与主张积极入世、力求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人生观相去甚远。因此受到儒者的猛烈抨击。对此权近也批评道:“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沫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其有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可见,他所讲的“心”正是朱子学所言之天理论视域下的理气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权近绘制此图的目的在于“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③。将理气摄入心性域来讨论是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色,这一理论传统其实亦肇始于权近。韩儒的心性学说与其说是对人之性情问题的探究,不如说是从理气论的向度对人的性理问题的阐发。因人的行为皆与心理活动相关联,所以韩儒在思考如何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时重点考察了人的行为的根源,即试图立足于心性论以阐明人之道德行为的发生根源。于是,属于理学本体论范畴的理气概念被纳入心性论域,用于直接讲明人的道德行为的来源和根据。从“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可以看到,“心”分善恶,而整图则被代表理气的白色和黑色一分为二。心具众理,性源于理,理若如实呈现即为纯善。故圣人即是完全实现心中之理者。
如前所述,韩国性理学关注的首要课题是“人”,即具有道德良知的现实中的人。这一特点从《入学图说》开篇第一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亦能窥见。此图说首先要辨明的是人的心性问题,而非天地万物如何化生的本体论问题。
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善恶选择时如何抉择“善”,这是关乎修养论(工夫论)的问题,为此权近标出了“敬”。图中善恶被分在“心”之两侧,而“敬”又与二者相关联,意为人之为善为恶皆系于以“主敬”为主的存养省察工夫。
其次,讨论其“天人心性分释之图”的“天”之图(见图3)和其“人”之图①(见图4)。
从《入学图说》的排序中也可看到,权近是在第一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
中先论人之后,又在“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中次第论及“天”、“诚”、“敬”。“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天”之图显示“天为一大”:“一者”意为以理言则无对,以行言则无息,故为万殊之本;“大者”则意为以体言则无外,以化言则无穷,故为万化之源。其“以理言则无对”的观念与日后李滉“理极尊无对”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皆基于以理为本的理气论传统。“敬”是指主敬涵养下学工夫,“诚”是天人合一之媒介,故《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①
在“人”之图下,权近附言道:
人者,仁也。仁则天地所以生物之理,而人得以生而为心者也。故人为万物之灵,仁为众善之长,合而言之道也。圣人至诚,道与天同。君子能敬以修其道,众人以欲而迷,惟恶之从。故人者,其理一,而所禀之质,所行之事,有善恶之不同。故其为字,歧而二之,以示戒焉。人能体仁,以全心德,使其生理常存而不失,然后可无愧于为人之名。而其效必能得寿,不然则生理丧而非人矣。②
依权近之见,“仁”是天地所以生物之理,在人则为心。因此人是万物之灵,仁为众善之长,而将二者合而言之便是道。他进而指出惟君子能敬以修其道,而众人则迷于欲念、惟恶之从。权近将“仁”也就是文中所谓“生之理”视为人的本质。众所周知,儒家将“仁”视为人与万物共同的普遍原理,表现在人身上即为“人之性”。
再次,讨论其“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心”之图(见图5)。
对于此“心”之图,权近解释道:
心者,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理气妙舍、虚灵洞彻、以为神妙之舍而统性情,所谓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者也。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其用之发有时而昏。学者要当敬以直内,去其昏而复其明也。其字形方者,象居中方寸之地也。其中一点,象性理之源也。至圆至正,无所偏,象心之体也。其下凹者,象其中虚,惟虚故具象理也。其首之尖,自上而下者,象气之源,所以妙合而成心者也。其尾之锐,自下而上者,心于五行属火象,火之炎上也,故能光明发动以应万物也。其右一点象性发为情,心之用也;其左一点象心发为意,亦心之用也,其体则一而用则二。其发原于性命者,谓之道心而属乎情,其初无有不善,其端微而难见,故曰道心惟微,必当主敬以扩充之。其生于形气者谓之人心而属乎意,其几有善有恶,其势危而欲坠,故曰人心惟危,尤必当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然后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差谬而圣贤同归,参赞天地亦可以驯致矣。不然,则人欲日长,天理日消,此心之用不过情欲利害之事,虽有人形,其违禽兽不远矣。可不敬哉。①尽管此文篇幅不长,权近还是简明扼要地对心身关系、心之结构、心之机能、心之作用、心之体用等都作了必要的说明。在心身关系方面,主张心是“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亦即心为身之主宰;在心之结构方面,认为心是理气妙合而为神妙之舍;对于心之机能则主虚灵洞彻,由是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对于心之作用倾向心性关系中“心统性情”;至于心之体用则主心体至正无偏而为性理之源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即是用。①其体则一,而用则二。道心原于性命而属乎情,“其初无有不善,其端微而难见,故曰道心惟微”;人心则生于形气之私而属乎意,“其几有善有恶,其势危而欲坠,故曰人心惟危”。因此,以主敬工夫扩充天理之正,以遏人欲之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便可做到危者安而微者著。以上是权近心论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其基本见解皆来自朱熹理论。如对心之机能,朱熹曾有如下论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②在文中权近还探讨理欲之关系,以为二者此消彼长,必由主敬工夫方能扩充天理,所谓“人欲日长,天理日消”。
此图需注意的是,权近按心的字形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加以解释:其一为“理之源”;其二为“气之源”。他将道心和人心、情和意以性为中心分别列于“理之源”和“气之源”之下:道心属情,其初无有不善;人心属意,其几有善有恶。在权近看来,此时之“情”根于理,作为“四端”之情无有不善,人心是发于气之意,故其几有善有恶。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的思想行为或源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韩儒则更倾向于从理气之发的视角来探讨此一问题。权氏殆以作为心之二用的情意分别生于理与气——“其体则一而用则二”。“情”和“意”乃人心的两种发用方式,源于性命者为道心(情),生于形气者为人心(意)。因此“学者要当敬以直内”,防止生于私欲的行为的发生。
“人心道心”问题在韩国儒学史上极为重要。权近对此一问题基本立场是“人心惟危,尤必当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然后危者安,微者著。”依其之见,“情”的行为一般能呈现较为理想的状态,源于气的“意”则不然,后者之呈现或善或恶,不由“心”的作用即无以引之向理。
权近以“理之源”和“气之源”判分人心以作解释,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
最后,再讨论其有关“性”的论述(见图6)。
理学宇宙论(本体论)需借理气说才能得到阐发。从上文可见权近的思想大体不离伊洛渊源,是故在其学说中“性”总被赋予普遍宇宙之原理义,所谓“性即理”是也。
在《入学图说》中,权近彰示“性”之图并写道:
性者,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于吾心者也。故其为字,从心从生。人与万物其理则同,而气质之禀有不同者焉。告子曰生之谓性,韩子曰与生俱生,释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气言而遗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①
此图亦是为初学者而设。权近自言道,其训天人心性分释之意有些破碎,但是初学者则一见即可知其大意要旨。并标榜其解说皆本自程朱的格言,非为其臆说。初学之士的要务,则在于动处下功夫,而存养之事已包含在“敬”之中。
理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反躬实践,而在现实中如何如实地呈现“理”和实践“理”遂成首要课题。为此权氏欲将天人问题转化为心性问题,以图在心性层面上实现“天人合一”这一儒家最高价值理想。心作为理气之合既具形上之特性,又有形下之特性。而且心还以“虚灵洞彻”统摄性情,由是具众理以应万事者。因此,在心的层面上追求其与性理的合一便是“仁学”思想的主旨。
“心具众理”强调的是“理”常存于人心。理学家认为,人心之理即性理不能如实呈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②之故。权近重视“性”,亦因“理”只有通过“性”的发用才能呈现。那么,究竟由何呈现呢?无疑是要由“心”来呈现。从此意义上说,权近“心统性情”的思想可以视为对主体以其“实践性”能动地呈现天理的一种阐述。
如前文所述,他将“性”定义为“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于吾心者”。①这与程朱对“性”的论述大体相同,伊川曾言:“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②又说过:“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③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解释道:“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有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④相较于程朱,权近的性理概念更强调“生之理”之义。
“性”字“从心从生”,仅就字形便可了知其与人心、人生的密切关系。作为性理学家,权近对历史上出现的不同“性”说评价道:“告子曰,生之谓性;韩子曰,与生俱生;释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气言而遗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在他看来,告子、韩非子以及释氏之“性”论的主要理论缺陷是未意识到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即所谓“义理之性”。这也反映了性理学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安身立命,而且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道德水平的提升。于此可见,儒家的确比其他学派理论更具道德关怀。权氏的“性”论与其说对人之本性的阐发,不如说是对人的能动实践能力的揭示,故可将其拟于实践性理学。
权近在书中“天人心性分释之图”的“性”条里面还写道:
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於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又况程子之言,以为外物触而动于中,其中动而七情出,情既炽而其性鉴矣。则其不以为性发也,审矣。①
他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之善并无二致,皆为同质之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非为性之所发,故不能与“四端”并列。依权氏之见,“四端”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权近不仅依此区分“四端”和“七情”,还进而以理气分判道心与人心:“理本无为,其所以能灵而用之者,气也……道心为危,人心惟微,则固以理气分言之矣。夫心之发其几有善恶之殊,若纯乎理而不杂乎气,则其发安有不善哉。”②从权近“心”之图(图5)中可见,是以“理之源”和“气之源”的视角对心进行解读。依其思路,性之源是理,心之源是气。心为理气之合,故其发用呈现为道心和人心,前者属理,后者属气。同时心又统摄性情,理所当然“心之用”又可以显发为“情”和“意”。“情”发于“性理”,“意”发于“心气”。发于性理之善和发于心气之善者,虽同为至善之物,显发为“善”的过程却各有差异。这一过程乃攸关性理学存养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课题,对此权近未作具体阐发。直至16世纪,李滉、李珥等理学家群体们才对之进行深入而具体的讨论。
权近在书中对“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作出了解释。“‘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即仁义礼智之端,非有二也。今子既以四者列于情下,又书其端,于外别作一圈,何也?’曰:‘四者之性,浑然在中。而其用之行,随感而动。以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心则是心,即为四者之端,诚非二也。然发于中者,谓之心;现于外者,谓之端。故孟子于此几两言之,或言端,或不言端。而朱子于言端,以为犹物在中,其端绪见于外,则其义愈明而不容无辨矣。’”③对于学生就此问题的提问,权近回答说四者之性是浑然在中者,而四者之端则是犹物在中而其端绪见于外者。二者诚非二物。其实这是讲仁义礼智之性如何生发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情的问题。对于性情关系问题,朱子学的基本看法是“情根于性,性发为情”;权近在此亦持相同立场。但他之所以视二者为“诚非二物”,是因为四德与四端之情皆为纯善之物的缘故。
权近还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①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的基本问题。《入学图说》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论辩之先河。沙溪金长生(1548—1631年)说过:“退溪先生七情四端互发之说,其原出于权阳村《入学图说》。其图中,四端书于人之左边,七情书于人之右边。郑秋峦之云,因阳村而作图,李滉又因秋峦而作图,此互发之说所由起也。李滉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是阳村分书左右之意。”②不仅如此,权近还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对佛、道进行批判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认为“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③。权近这一思想后为李滉发展为“理尊无对”说和“理贵气贱”说,从而开启了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主理论传统。
权近有关四端七情问题的看法实为百余年后李滉、奇大升、李珥、成浑等诸家旷日持久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为代表的岭南学派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儒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伦理上的道德情感,典出《孟子·公孙丑上》;“七情”则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生理上的自然情感,典出《礼记·礼运篇》。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并未引起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儒学界引发了一场“四端七情,理发气发”的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使韩国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哲学轨道,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四端七情”这一问题的关注意味着韩国儒学已然开启本土化的进程。
权近与郑道传虽然同为朝鲜朝初期的理学大家,但是在接受和传播朱子学方面却各有特色。郑道传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注重朱子学理论本身的探究与思考。若就两人对韩国朱子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后世学者视为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主要代表。李滉也很服膺权近的学问,曾对其评价道:“阳村学术渊博,为此图说极有证据,后学安敢议其得失。”①权氏《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示类书籍,所以他被目为韩国儒学界“以图释说”研究范式的开创者。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传至日本,且在日本儒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曾多次翻刻权氏《入学图说》,现存宽永甲戌刻本和庆安元年刻本等。
权近的主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以及《三峰集》中的《佛氏杂辨》序,《心气理篇》注、序等。现有《阳村集》(40卷)。
二、柳崇祖与其“四端七情”论
中宗时期的真一斋柳崇祖(字宗孝,号真一斋、石轩,1452—1512年)是朝鲜朝前期继权近之后又一位论及四端七情理气问题的性理学家。柳氏本贯为全州,谥号为文穆。他成宗三年(1472年)中司马试进入太学,1489年文科及第,历任司谏院正言、弘文馆副校理、司宪府掌令、成均馆大司成等官职。他是“官学派”的代表,但是对“士林派”学者亦相当友好,在任大司成时还荐举了赵光祖、金锡弘、黄泽等“士林派”学者。燕山君十年(1504年)被发配至原州,中宗反正之后又官复原职。史书上对其为人有如下记载:“文穆公,天资高明,器宇峻洁,早有志于学。其为学也,本之以孝弟忠信,律之以刚方廉直,六经诸子与百家,靡不淹贯,妙年升庠,已有道义之所推服,既擢第入翰苑,儒臣启,以经明行修,可为师表,兼带成均掌教,教导后进,先正臣李滉所称师友堂堂经训皇皇者也。当燕山主九年,文穆在宪府,抗疏论十余事,皆切直不少讳,贬其官,甲子祸作,杖窜原州,靖国之初,首入经幄,旋升工曹参议,三公启,经幄不可无此人,命兼带经筵官。遂长国子,三公又启,性理之学,不可绝其传,请选年少文臣,就崇祖受业,崇祖承命,课授甚勤,作为四经、四书等谚解,以晓诸生,宣庙朝所纂集刊行者也。又命选诸生中可大用者以奏,崇祖,以文正公臣赵光祖首荐,六年辛未,上亲临太学,谒先圣,退御明伦堂,横经问难时,崇祖为大司成,以大学进讲,反复乎存心出治之要,上凝旒倾听,桥门观者皆耸然。”①柳氏在《书经》、《易经》、《礼记》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以口诀和悬吐的方式给“四书”、“三经”编了《七书彦解》②,作为韩国彦解类之嚆矢,对后世影响颇大。柳氏的著作还有《真一斋集》、《大学十箴》、《性理渊源撮要》等。
《性理渊源撮要》摘取先儒学说中的紧要段落加以编纂,从中可见其性理学思想。而《大学十箴》则以箴规人主之思想行为为目的。全书将《大学》内容分成明明德箴、作新民箴、止至善箴、使无讼箴、格物致知箴、谨独箴、正心箴、修身箴、齐家治国箴和絜矩箴十个条目,分门别类以述帝王学之要义。依柳氏之见,大学之道,是修齐治平之准绳,是方圆平直之至。为君者之所以不可不明此大学之道,是因为为政之规矩准绳之所出;为臣者之所以不可不讲此大学之道,是因为为臣者之规矩准绳之所由施;为民者之所以不可不知此大学之道,是因为规矩准绳之所当从。他进一步指出,二帝三皇之所以盛治者,乃正其规矩准绳之体,以成己而运之于上,故方圆平直之用自正而物成于下。
在理与气这一性理学基本问题上,柳崇祖认为:“气与理,气殊形禀理一天地,气不外理,理寓气里。理不离气,浑然一体,气不杂理,粲然不混。无先无后,无端无始。赋物之初理一气二,物禀之后气同理异。”③柳氏倾向理气“混沦一体”、“不离不杂”的传统朱子学立场。他认为理气二者在时间上无先后、无终始,赋物之初理一气二,物禀之后“气同理异”。柳崇祖正视分殊之理的差异性,认为既有天下公共之理,又有一物各具之理。柳氏思想较具特色,在人性论领域尤重“气质之性”。
在“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上,柳氏提出:
天下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有阴阳则有木火金水者气也,有健顺则有仁义礼智者理也。气非理则无所承,理非气则无所附,是故未有阴阳已有太极,未有此气已有此理。推所从来,固不无先后之别,然言太极则已不离乎阴阳,言性则已不离乎气质,有则具有,又岂别为一物而有先后之可言哉。合而言之,则太极无物不存,万物各具一太极,性即气、气即性,盖未始相离也。初岂有所谓本然之性而又岂有所谓气质之性哉。分而言之,则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性自性、气自气,又未始有相杂也。岂无所谓本然之性又岂无气质之性哉。①
此处涉及理(太极)的逻辑在先问题。理气之关系推所从来“固不无先后之别”,只能说“未有阴阳已有太极,未有此气已有此理”。但在现实生活中,言太极时则已不离乎阴阳,“言性则已不离乎气质”。柳崇祖在此着重说明“气质之性”的实在性和现实性。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性本于天,虽气之本而气存于人,实性之用。性如日月之明而气则如云雾之昏矣。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盖谓此也。夫形气未禀人物未生,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是人生而静以上也,可名之以理,不可名之以性,所谓在天曰命,是专以理言也。及降而在人则坠于形气,虽可谓之性,然已涉于有生,而不得超然于是理之本体矣。是才说性则便已不是性也,是所谓在人曰性也,是专以气质而言之。”②需要指出,尽管先儒在人性论方面已有本然之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之说,但是柳氏在性论上仍然坚持二程“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③的性气合一论。若综合上一段引文的内容来看,严格地讲他更倾向于明道的“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④的性气不离的思想。
柳崇祖曾对历史上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性”论做过评说,指出:“盖观古人之论‘性’,孟子专以本然言性,而不及于气,所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杨误以气质为性,而不识其本,所谓论气不论性不明;韩子之言性可谓备矣,五性之说固已见其理之同,三品之说乃不知其气之异。此廉溪张程所以不得不表彰而发明之也。然考之经传已有此意,但古人未尝明著其气质之名尔。”①儒家之人性论确有一个发展过程,曾产生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但是,张载“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这样性二元论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讨论推向了高潮。朱熹这样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②但朱熹之后人性论从性二元论逐渐转向性气合一的性一元论,开始强调现实性。从东亚儒学史的视角来看,人性论的此一转向在我国明代学者罗整庵(主理气一物论)、王廷相(主理气无性论)以及韩儒柳崇祖的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也反映了在理学传统中道德理想(理想性)与现世关怀(现实性)的尖锐冲突,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思想运动的演进,儒者的现实指向性在逐渐增强。此理论转向可视为17世纪东亚各国注重实践性与功利性的“实学”思潮兴起的前奏。
在权近提出以理气分言分四端七情的观点之后,柳崇祖也提出大体相同的主张。他在《大学十箴》中的“明明德箴”中写道:
一阴一阳,本一太极,继善成性,理气妙合,秉彝懿德,人所同得,精真之凝,灵妙虚寂,不吝于愚,不豊于智。内具众理,外应万事,统性与情,神明莹澈。情动于性,纯善无杂。意发于心,几善与恶。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③柳氏认为“四端”是理动所致,而“七情”则是气动所致。此一理动气动的解释模式说明他将二者视为基于不同发用过程的两种不同的情感。其“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的观点与日后的李滉“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思想颇为相似。柳崇祖在大作《性理渊源撮要》中将程迥(沙随程复心)理气说做了进一步阐发,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然之性,理也,仁义礼智信,五性皆天理,故本无不善。气质之性,气也,纯清者全其性,上智也。杂清浊者,善恶混,中人也。纯浊者,全是恶,下愚也。理发为四端,气发为七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者正情,无有不善。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中节则公而善,不中则私而恶。①
感通之谓情,则四端者理之发,七情者气之发。能为之谓才,则无不善者出乎性,而有不善者出乎气也。由是观之,理无不同也,所不同者气耳。理无不善也,所不善者才耳。②柳崇祖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主张,在以上言论中得到再次确认。他认为四端七情根源不同,坚持对之区别对待。
从柳氏在《性理渊源撮要》中对程迥“四端七情”说的整理可以窥见,其思想主张在先儒著述中也不无痕迹。像“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之说就与权近之“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之主旨大体相同。可见,“四七”对举、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传统早在郑之云之前的朝鲜朝性理学中即已存在。此为韩国性理学的又一特征。
柳崇祖对朝鲜朝性理学发展的贡献,在史书上也有记载:“窃稽中庙朝大司成赠谥文穆公臣柳崇祖,倡明道学,所撰进《大学十箴》、《性理渊源撮要》及经书《七书彦解》等书,启沃圣德,嘉惠后学,实为旷世之真儒,后生之师表,允合庑享之联跻而尚未彻旒,岁年侵寻,章甫之赍郁,不日不月,而朝家之令典,抑亦恐有未遑。臣等之责,愈久愈深,今当卫辟存闲之庆会,自不敢泯然,各道缝掖之徒,不谋而同,齐声而应,谨摭其平日实迹之有关于斯文者,以备乙览焉。”③
简言之,权近的《入学图说》和柳崇祖的《性理渊源撮要》所开创的“四七”对举之范式成为朝鲜朝“四端七情”之辨的理论端绪。明显可以看出,《入学图说》和《性理渊源撮要》中出现的“四七”对举的思想与郑之云、李滉的“四七互发”说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关联。
第二节 李滉与其“四端七情”论
高丽末开始传入到朝鲜半岛的朱子学经过14—15世纪的传播与普及,至16世纪已基本发展成熟,开始形成了以主理、主气为理论特色的韩国化的性理学派,即以李滉(1501—1570年)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珥(1536—1584年)为宗的畿湖学派。两派围绕四端七情问题而展开的四七论辩使韩鲜朝性理学的发展走上了以性情论探讨为主的发展轨道。本节和下一节将主要对李滉与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进行论述。
一、李滉的理气论
李滉(字景浩,号退溪、退陶、陶叟)生于燕山君七年(1501年),卒于宣祖三年(1570年),谥号文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东方之朱夫子”。出生于礼安县温溪里(今安东郡陶山面温惠洞)。中宗时文科及第,官至大提学、右赞成。后辞官退隐乡里,闭门静居,钻研学术,以著书立说和授徒讲学为业度过了其一生。曾在家乡礼安选一景色宜人处卜筑“陶山书堂”,作为了其著述和讲学之场所。
李滉年轻时曾写过一首诗,诗中吟道:
露草夭夭绕碧坡,
小塘清活净无沙。
云飞鸟过元相管,
只恐时时燕蹴波。①
从这首哲理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峻别天理人欲之思想倾向早已有之。因此在之后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李滉提出以主理为特色的性理学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于其学问,弟子郑惟一(字子中,号文峰,1533—1576年)曾写道:“先生学问一以程朱为准,敬义夹持,知行并进,表里如一,本末兼举,洞见大原,植立大本,若论其至吾东方一人而已。”①李滉的学说被其后学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岭南退溪学派,影响了此后韩国儒学的发展进路。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首要问题。②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理气“不离不杂”③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鲜朝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说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④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韩儒丁时翰亦曾言道:“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⑤不过,李滉、李珥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之发及理气体用问题而展开。
李滉在接续朱熹“理气二分”说的基础上,依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尊无对”、“理帅气卒”、“理贵气贱”的主张。他说:
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故也。⑥
天即理也,而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是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才有理,便有气眹焉。才有气,便有理从焉。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所谓理者,四德是也;所谓气者,五行是也。①
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然理无为而气有欲。故主于践理者,养气在其中,圣贤是也;偏于养气者,必至于贼性,老庄是也。卫生之道,苟欲充其极致,则匪懈匪躬之职,皆当顿废而后,可庶几。其斁理害正如此,本不可以为训者也。若以为养气亦不可全无,而姑存其书为可,则其中尤近怪无稽者,亦当去之。②从引文中可见,对二者“不杂”之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论的重要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李滉重视其“不杂”之义的目的在于,主要是为了强调理的主宰性、主动性、优位性。由是在二者关系上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如其所言,“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等等。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他把朱熹的理气“先后”⑤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同时也为其“四七理气”论打下理论基础。
在东亚儒学史上,李滉性理学的“理”论极富特色,不过“理”亦是其性理学说中最为难解处。李滉本人也曾言道“理”字最为难知,对于缘由他写道:
凡人言理,孰不曰无形体、无分段、无内外、无大小、无精粗、无物我、虚而实、无而有哉。但真知其实无形体、实无分段、实无内外、实无大小、实无精粗、实无物我、实为虚而实、实为无而有为难。此某所以平日每云理字难知也。①
李滉为学一向主张学贵穷理,因为在他看来若对理有所未明,则或读书,或遇事都不能做到无碍。所谓“理有未明”,即是指学者还未做到对理字之义的“真知”。那么,何谓其所言之“真知妙解到十分处”呢?李滉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盖尝深思古今人学问道术之所以差者,只为理字难知故耳。所谓理字难知者,非略知之为难,真知妙解到十分处为难耳。若能穷究众理到得十分透彻,洞见得此个物事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洁洁净净地,一毫添不得,一毫减不得,能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而不囿于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中,安有杂气而认为一体,看作一物耶。其于道义,只见其无穷,在彼在我,何有于町畦,其听人言,惟是之从,如冻解春融,何容私意之坚执。任重道悠,终身事业,安有欲速之为患哉。假有初间误入,一闻人规,便能自改而图新,安忍护前而无意于回头乎。诚恐循此不变,处而论道,则惑于后生,出而用世,则害于政事,非细故也。其以博览群书为非,而欲人默思自得,其意之落在一边,可知。公之报书,所以正其偏而砭其病者得矣。②
这是李滉答奇大升信中的一段话,也集中反映了在其哲学中“理”概念所具有的基本义涵。由以上引文内容所见,在其学说中“理”既是一个具无形、无质、无为之特性的形上之存有,又是一个指代实理的“天理”。而且,“理”又兼体用,既有无声、无臭、无方体之“体”,又有至神至用之“用”。③对于这样的“理”,李滉在文中进行了多角度的阐发,认为古今人学问道术之所以差者,只是因为“理”字难知之故。所谓“理”字难知,不是指略知之为难,而是将之真知妙解到十分处为难的意思。认为,只有“穷究众理到得十分透彻,洞见得此个物事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处,才能算是真正知“理”。
从“虚实”、“有无”等角度论述“理”本体的同时,李滉在答复奇大升问难的信中还提出理有体用说,曰:“无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体也。其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见于本体之无为,而不知妙用之能显行,殆若认理为死物,其去道不亦远甚矣乎。”①实际上,理有体用说是为其“四七理气互发”说作了理论铺垫。
进而,李滉还提出“理非静有而动无,气亦非静无而动有”的理(太极)自有动静的思想,明确地肯定了理的发用性。李滉曰:
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但就无极二五妙合而凝,化生万物处看,若有主宰者运用而使其如此者。即书所谓惟皇上帝将衷于下民,程子所谓以主宰谓之帝是也。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②
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勉斋说,亦不必如此也。何者,理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阳生阴也。③由此,在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便有了理气互发之论。他对理本体所作的这一解释,不仅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④的朱学内在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可能,而且还积极回应了以“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原,理何足尚”⑤为由对朱学理气说提出质疑的明初朱子学者们的诘难。但是,对其理发说需做进一步的解释。李滉亲身经历朝鲜朝多起“士祸”,统治阶级内部血腥的权力斗争致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社会道义及生命的尊严荡然无存。作为生活于此一时代的大哲学家李滉势必将重塑社会纲纪,提高伦理意识以及加强道德教化视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对李滉来讲,如何保存和扩充源于天理的人性本然之纯粹性就成为其首先要思考的哲学课题。故他所追求的是此种性理的自然呈现或良知之心的自我坎陷。李滉的这一主张看似与陆王心学的良知说有些相近之处,但其根本立场是基于人的道德心理和伦理行为意义上的性理发用,并非为王学意义上的“致良知”,更不是本体论(宇宙论)向度上的“太极”之自动静。理发论在其学说中之所以能够得到成立,还与其对“理”特殊规定相关。前文已言及在其“理”论中,理具有“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之特性,“理”具有绝对性。而且,在“气”论中他亦对之作了相应之规定。要言之,强调道德心理和伦理行为意义上的理(性)之发用性、主宰性、优位性,是李滉理气论区别于朱子理气论的紧要处,学者于此处应仔细玩味和体会。
那么,相较于“理”,“气”在李滉哲学中具有何种特性呢?李滉认为,因为“气”是有形之物,故气有限量而理无限量,气有生死而理无生死之说①。
盖理本无有无,而犹有以有无言者。若气则至而伸,聚而形为有,反而归,散而灭为无,安得谓无有无耶。或别有所据,某未记耶,气之散也,自然消尽而泯灭。②
然滉前以为气散即无。近来细思,此亦偏而未尽。凡阴阳往来消息,莫不有渐,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然则既伸而反于屈,其伸之余者,不应顿尽,当以渐也。既屈而至于无,其屈之余者,亦不应顿无,岂不以渐乎。故凡人死之鬼,其初不至遽亡,其亡有渐。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非谓无其理,而姑设此以慰孝子之心,理正如此故也。由是观之,孔子答宰我之问,亦无可疑矣。以眼前事物言之,火既灭,炉中犹有熏热,久而方尽。夏月,日既落,余炎犹在,至夜阴盛而方歇,皆一理也。但无久而恒存,亦无将已屈之气为方伸之气耳。①可见,“气”在李滉哲学中具有生死、聚散之特性。他以为,没有恒久不变之气,气的聚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举炉中火苗渐渐熄灭和夏日白天之暑热至夜缓解为例详加阐述。
李滉进而还提出气之原初无不善的主张,曰:
气之始无不善,乃气生源头处,非禀受之初也。然气有一日之始,有一月之始,有一时之始,有一岁之始,有一元之始,然此亦概举而言之耳。推来推去,其变无穷,当随处活看,不可执定为某气之始。苟指认一处为定则不通,不足以语造化之妙。②
那么,其无不善之“气”是否与李珥“湛一清虚”之气泯然无别呢?对此,李滉解释说:“程子心本善之说,朱子以为微有未稳者。盖既谓之心,已是兼理气,气便不能无夹杂在这里。则人固有不待发于思虑动作,而不善之根株已在方寸中者,安得谓之善,故谓之未稳。然本于初而言,则心之未发,气未用事,本体虚明之时,则固无不善。故他日论此,又谓指心之本体,以发明程子之意,则非终以为未稳,可知矣。”③可知,其所言“气之始无不善”是指心之未发而本体虚明之时。这与徐敬德、李珥哲学中的“气”概念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李滉对此进一步解释道:“湛一气之本。当此时,未可谓之恶,然气何能纯善?惟是气未用事时,理为主故纯善耳。”④这一解释对理解其“四七”论极为重要。因为依李滉之见,“气”只有听命于理或顺理而发的时候才能呈现为善。但是,又不能将“气顺理而发”称之为“理之发”。“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于此可见,其“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之说实乃根于其特殊的“气”论思想。
李滉还从价值论维度对理气概念作了“理纯善而气兼善恶”的价值规定。“理纯善而气兼善恶”之说其实承自程颐、朱熹的理学思想。气有清浊,由其清浊而言,气有或循理或不循理之可能。因此,要施以主敬工夫“以理驭气”。理是纯善,而气兼善恶,故以纯善之理帅“气”则“气”能循理而直遂。这便是所谓“理帅气卒”的思想。李滉的尊理贬气(理贵气贱)的观念,与其“理纯善而气兼善恶”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他进而又从伦理道德的意义上,作出“理极尊而无对”、“理贵而气贱”的理优位论之规定。既保持了传统理学所崇尚的等级价值观,又体现了其独创性的一面。理既“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②,那么理气关系即为主宰与被主宰的上下位关系。上者尊贵而下者卑贱,所以李滉指出:“理贵气贱,然理无为气有欲。”③在存养省察的工夫上,他特别强调主敬,惟其如此才能达到“以理驭气”使“气”顺理而发的目的。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兼论郑之云的《天命图》与“四端七情”论
在论述李滉的“四七理气”论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郑之云与其《天命图》。因为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郑氏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引致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李滉曾对郑之云称赞道:“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我妄以结状其难……有契有违,往返弗置,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④
郑氏是继权近、柳崇祖之后又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韩国性理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不仅为此后李滉和李珥等人的“四七理气”之辨提供了理论端绪,而且还开启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四端七情理论研究之先河。
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稼翁,1509—1561年)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曾受教于为金安国和金正国。郑氏世居高阳,本贯则为庆州。他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之辨发端于郑氏之《天命图》。对于自己的作图过程,他在《天命图序》中写道:
正德己卯(中宗十四年,1519年——引者注)思斋金先生被微谴而退卜居于高峰之芒洞,洞实之云所居里也,尝游其门受学焉。嘉靖戊戌(中宗三十三年,1538年——引者注)先生被召还朝,之云失其依归,与舍弟之霖学于家。论及天人之道,则之霖以幼学患其无据,莫能窥测。余于是试取朱子之说(见《性理大全》论人物之性),参以诸说设为一图,而又为问答名曰《天命图说》日与舍弟讲之。此非欲示诸人而作也,然图说既草,则亦不可不见正于长者,遂取质于慕斋思斋两先生,两先生不深责之,且曰:“未可轻议,姑俟后日。”不幸,两先生相继以没,呜呼,痛哉。由是此图之草,无所见正,而余之学问日就荒芜,几不能自振。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误闻不肖之名,躬行者再三之,云感其殷勤,斋木以进。退溪欣然出见,因语及《天命图》,之云以直告知,因请证之意,退溪稍假肯色。余退而私自贺曰:“吾丧两先生后,意谓更不得贤师友而求进,今得退溪,吾无忧矣。”常往来质问是图,退溪证以古说,参用己意,补其所欠,删其所剩,卒成完图。其赐己以厚,又从而为之说,附其后而教之,其幸孰大焉。非徒余之幸也,在昔日两先生姑竢后日之志,今始副焉,是尤幸之大也。余故首记作图之由次及定图之事,以藏于家。如有同志者出,其亦有以知退溪考证之意也。①
文中郑氏较完整地记述了此图的写作过程。他采先儒之论并以图解以明之,目的在于启子弟之蒙。此图取名为《天命图》——“天命”二字典出《中庸》首句,可见其以《中庸》为性理学之基础。为了说明天人相与之道,郑之云在《天命图解》①中使用了诸如理气、心性、太极、道等性理学概念,并用这些概念对天人之际进行了理气论的说明,旨在揭示了天人合一之根据。他还从理气论的角度对人的心性以及善恶问题进行了说明,此即所谓“四端七情”论。尽管郑之云并未将“四七”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来论述,而只视作探究天人合一的根据之一,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四七”论在其性理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②因为前者只是从其性理学整体构成之维度而言的。
此文写于嘉靖甲寅(明宗九年,1554年)之正月,此时退溪李滉已是年过五十的一代儒学名宿,思想也已渐趋成熟。他获得此图后,将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并在语气上作了改动。李滉的这一订正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尤其是奇大升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发展成为左右韩国性理学发展走向的学术论争。
郑之云在阐发其性理学说时,也意识到单纯凭借“气”论是很难对“恶”的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的。于是,他对阴阳之气赋予了善恶的价值含义。如把气分为清、浊、明、暗等。主张阳气清明,故可跻于善;阴气浊暗,故可流为恶。他断言“恶”的现象是由阴气所致,由此维护了“理”的纯善性。而且,还提出阴阳之气只是与心动之后的发用相关,并非各自独自发用的观点。这就消除了人的恶行的先天可能性。郑氏还认为,若心之发“意”根于性且其气属阳的话,天理会如实呈显;相反,如“意”与物相杂而其气属阴,则天理就会失去其真实性,终流于恶。依他之见,人的善恶行为取决于自由意志,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郑氏性理学追求“天人心性合一”,这表明他是韩国性理学史上的主流派学者。与中国的朱子学相比,韩国性理学以“图说类”诠释模式见长。从《天命图》在韩国性理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窥见郑之云在此一传统中的独特地位。①其“四七”理论的首要意义就是肯定人的道德行为(“人性善”)的先天可能性,此为性理学最根本的哲学观念。《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乃其天理观的来源和根据。实际上,性理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探讨的目的则是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寻找一个本体论的根据,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根据。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万物有机体观”正是性理学家们这一思想的反映。理与气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是为了证明这一思想。性理学家们以理气概念探讨道德行为之根源,尤其注重主宰人的行为的“心”的研讨,这也是心性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心性论中,与对心性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有关修养工夫的问题,即如何使心性向“善”的问题。欲解决之,首先要探讨“恶”的根源及来源。所以从理气论维度对“恶”之根源进行探讨也是心性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其中,“四端七情”之探讨是对人的本性的深层剖析,目的在于扩充良知所彰显的内心之善以上合天理。②实际上,他的这一思想根于孟子的性善说,欲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把握性与天道的关系。
可见,郑之云是韩国儒学史上继阳村权近、真一斋柳崇祖之后又一位坚持“天人心性合一”这一韩国性理学传统的学者。在韩国儒学史上,他还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性理学相关理论的学者。③尽管其理论仍显得较为简单缺乏系统性,但在《天命图解》及《天命图说》中所见的理论探索还是对性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了一定的概括和整理。所以李滉“君曾测海”的评价对他而言还是较为中肯的。郑之云的主要著作有《天命图解》以及《天命图说》。
李滉将其《天命图解》改订之后,首先遭到奇大升的发难。奇氏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又说过“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混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②。 在奇大升看来,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举,谓之纯理或兼气就有些不妥。奇氏主张四端虽由纯粹的天理所发,但只是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奇大升进一步评论说: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③
他认为四端与七情作为情感皆性状相似,而非有截然相反之特质。因此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学原论的。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回答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盖欲相资以讲明,非谓其言之无疵也。今者,蒙示辩说,摘抉差谬,开晓谆悉,警益深矣。然犹有所不能无惑者,请试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首先说明了其将郑氏之“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进行改动的缘由,他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认为先儒未有将“四端七情”分置于理与气的范畴来讨论的先例。李滉还是认可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在这一问题上他有过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首度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进行修订时的说法。李滉将郑氏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这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其实此两句从内涵到语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请参见新、旧天命图(图7、图8)。
起初他认为此说“本晦庵说,其理晓然矣”③,其时还未与奇大升展开论辩。二是在与奇氏进行论辩过程中有了第二种表述,即“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④。这是己未年李滉59岁(1559年)时的观点。当此之际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理气”之辨。加之李滉又恰好读到朱子的“四端是发于理,七情是发于气”一句,于是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与奇大升的信中提到:“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三是经奇大升之诘难后便有了新的说法——“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②。此后李滉对这一说法再未作改动,可视为其最终定论。对最后一说,他在其晚年代表作《圣学十图》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③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正是李滉性理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
他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本上的差异,这源于其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①
由此可知,在心性情的关系上李滉倾向张载的“心统性情”说。他将“心”理解为“理气之合”——与朱子“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的观念相比,心的含义以及与理、气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以此说为理论前提,可以分属理气的方式准确表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以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
四端七情之辨实质是性情之辨。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作为李滉晚年思想结晶的《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则为李滉所作。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概念。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此为性理学的主题。性理学的道德主体论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①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如此则性为体而情为用。朱熹认为“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②。与之不同,李滉进一步发挥朱熹的理气心性说并将性情与理气之发相结合,从而将朱子学的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端七情理气”论。此图的中、下两图乃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③对于“七情”的善恶,李滉起初以为“七情,善恶未定也”④。经与奇大升往复论辩之后改为“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故其发而中节者乃谓之和”⑤。这一改动容易造成七情之“善”和四端之“善”之混同,所以对之需作仔细辨析。四端之情是人的道德感情亦即良心。四端之“善”是纯粹的且还带有道德色彩。但是七情则与此不同,原是与道德情感无关之情。作为自然情感,七情在“性发为情”之后才能以发用是否为“中节”衡量其善恶。因此如李滉早年所言,它还是“善恶之未定”。那么,应如何理解其修订后的说法呢?我们可以从其“本善”一语中去寻找。“善”被赋予道德含义之前,“好”是其概念的核心内容。易言之,善是规定事物之好的状态,道德性的善也是如此。“七情”作为原始的自然的感情本是好的感情,只因具有“过或不及”的性质,容易“流于恶”。①其修订后的说法可以按此思路去解读。
对于下图李滉解释说:“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②
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和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遵循程朱“情根于性,性发为情”之原则,依此解读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和无不善之情。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我们也可以一窥李滉试图融合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正是两种权威文本相互冲突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引发韩国儒者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③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说,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还是气发皆可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甚至放而为恶,原因就在理发未遂或者气发不中。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显或气发而皆中节遂成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述引文中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子学的传统——李滉继承这一传统,也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也是情,而“情”必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遂成人性善恶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①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也就是说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自我反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多次对此图进行修改。“盖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中所载本也。”②此图在李滉《圣学十图》中具有的重要性实在是无需赘言。
李滉还以“七情”与“四端”分论“人心”与“道心”,指出“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也。”③这既是对朱子心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学术上的立异。在李滉看来,道心是义理之心即最高的道德原则,所以他在强调四端七情之差异的同时还特别重视道心人心之分别。虽然其中图未言及“气”,但他论性情仍以理气分言之。“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④这也表明李滉心说承继朱子之传统——倾向以“理气心”论性情,而且主张持教工夫。
在论辩的最后,李滉以《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三书》总结二人观点之异:
既曰“浑沦言之”,安有主理、主气之分?由对举分别言时,有此分耳。亦如朱子谓:“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又云:“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
前书引性言者,只为在性犹可兼理气说,以明情岂可不分理气之意耳,非为论性而言也。“理堕气质以后事”以下,固然,当就此而论。
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碍者乎?而况所谓四端七情者,乃理堕气质以后事,恰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则有明有暗,四端则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固因水之清浊而四端之不中节者,则光虽明而未免有波浪之动者也。伏乞将此道理更入思议,如何?
“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说,尝见先儒有论其不可,今不记得……敢问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者,为发于理耶?为发于气耶?而发而中节,无往不善之善,与四端之善,同欤?异欤?虽发于气,而理乘之为主,故其善同也。且“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谓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则只有理发一边。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未知于先生意如何?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发矣。若欲外此而更求理之发,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弊。前书亦以为禀,而犹复云云。苟曰未然,则朱子所谓“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者,亦不可从也。
道即器,器即道。冲漠之中,万象已具,非实以道为器;即物而理不外是,非实以物为理也。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用朱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也。
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此信写就之后李滉或觉没有必要继续与奇氏论辩,故而未将信寄给他,只是针对奇氏来信中的质问撰文阐述自己的主张。李滉的基本观点是四端七情混沦而言时则无需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但是若将二者对举而言则应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他还以“因说”和“对说”来解释了此问题。直至结束辩论二人仍各持己见,并未达成一致。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以为不仅“性”可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若说奇大升注重于对问题的客观性、逻辑性的阐明,李滉则更着力于对道德性的提高以及修养工夫论域中的主体的省察和践履的意义。
“四端七情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赓续朱子的理气心说,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无怪乎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此种理解,李滉进一步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他对七情的看法始终落在气的一边。他说:“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不能无理,所以“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四端”需要扩充,而易“流于恶”的“七情”则要受检束。因为二者各具相异的性质,如何理解其异中之同便值得认真思考。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说:“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若从客观的视角对情之结构做静态分析的话,便可以得出“四端”为“七情”之一部分的结论。但是在道德践履的意义上,二者又具有相反的性质。比较而言,奇大升关注前者,李滉则更倾向于后者。当然此种差异是相对的。两人真正的分歧源于各自在为学旨趣及问学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的问题意识。
要言之,“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中的核心内容。基于理气二分的立场李滉肯定情的“四七”之分,以为恻隐、善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是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而发,即缘境而出。不过依其理气心,“心气”之性质及所为,如气之清浊、偏杂、粹驳之状态,直接决定四端之呈显以及七情之善恶性质。李滉以为,“气”之状态影响理之显否,故在修养论上他特别主张施以主敬涵养工夫治“心气”之患,使气皆能循理而发以保证理发直遂而不被气所掩。
三、李滉的主敬论——以《圣学十图》为中心
李滉之学亦被称为主敬之学。因此下面将通过对《圣学十图》的分析来探讨其以主敬说为特色的性理哲学思想。
《退溪全书》“言行录”中记载,其门人金诚一将其学问概括为“试举其学大概,则主敬之工,贯始终兼动静,而尤严于幽独肆之地,穷理之功,一体用该本末,而深造于真知实得之境,用功于日用语默之常”。①主敬思想的基本论纲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敬以直内,涵养本心;义以方外,省察行事。尽管李滉所依傍的是程朱的主敬之说,但是其主敬之说知行并重,贯始终兼动静。其学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又比程朱更强调“心”之作用和效用,也因之更加明确地揭示了“敬”之为学工夫与进入圣贤域以达至圣人的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
作为“东方之朱夫子”,李滉为学服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对朱子学的理气心性诸说多有发明。李氏68岁(宣祖元年,1568年)时进呈宣祖的《圣学十图》更是其学问宏纲大目的集中反映,也是其一生学问的思想结晶。可谓“晚年深思熟虑,提纲挈领的结晶,也是他体认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心得。李滉独以图的形式,既示人以圣学入道之门,亦给人以简明易懂的启迪。《圣学十图》,融铸宋明理学之精髓,构成他的思想逻辑结构,其规模之宏大,操履之功用,在李朝理学史上均属罕见”②。《圣学十图》由《进圣学十图札》和《圣学十图》组成。所谓十图包括:第一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第二图为程复心(字子见,号林隐,1279—1368年)绘的张载的《西铭图》;第三图为李退溪绘的朱子的《小学图》;第四图为阳村权近绘的朱子的《大学图》;第五图为李滉绘的朱子的《白鹿洞规图》;第六图为《心统性情图》(上图由程复心作,中、下二图由李滉作);第七图为朱子的《仁说图》;第八图为程复心绘的《心学图》;第九图为王柏(字会之,号鲁斋,1197—1274年)绘的朱子的《敬斋箴图》;第十图为李退溪绘的陈柏(字茂卿,号南塘,元儒)的《夙兴夜寐箴图》。对于上述十图,李滉还做了相应的引述和说明,指出前五图是“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③,后五图则是“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④。综观十图,“敬”①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纲目。
《圣学十图》的排列次序不仅体现了李滉哲学的逻辑结构,而且还反映了其对儒学(圣学)的全部理解。第一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李滉对此解释说:
朱子谓此是道理大头脑处。又以为百世道术渊源。今兹首揭此图,亦犹《近思录》以此说为首之意。盖学圣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于小学大学之类,及其收功之日,而溯极一源,则所谓实理尽性而至于命,所谓穷神知化,德之盛者也。②
朱熹立学极重周敦颐之《太极图》,此图可说奠定了“濂溪先生”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开山之祖的地位。李滉认为太极即是宇宙本体(天道),故将《太极图》视为百世道术之渊源亦即一切思想学说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强调学圣人者要“求端自此”。李滉将周敦颐的《太极图》理解为对《周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义的阐发。依李滉之见,圣人是“与天合德,而人极以立”,因此圣人之学便是继天立极之学。他认为此图的目的在于阐明圣学的理论根据,而且还揭示如何以抵达圣域的修养工夫。李滉进而引用朱子的《太极图说解》以作说明:“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间而已矣。敬则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静虚动直,而圣可学矣。”③《太极图》表明了以“敬”为核心的为学路数,具有将天道、地道和人道加以融合以作整体观照之特性。而其他九图皆为此图(“立太极”和“立人极”)的进一步展开。此其所以《近思录》、《性理大全》等开篇即设有《太极图》——李滉可以说继承了这一理学传统。
第二图为《西铭图》,旨在揭示天道的进一步展开。该图试图从对“求仁”的深刻体悟中阐明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道理。李滉以为“圣学在于求仁,须深体此意,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一体,真实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味,免于莽荡无交涉之患,又无认物为已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体也。又曰:充得尽时,圣人也。”①这是李滉体仁的最高境界,于此彻悟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强调物我一体论与事亲事天之实践,他在《西铭图》图说中写道:“朱子曰……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②天道以仁为本质。人只有懂得其所具之仁便是天地生生之理(太极),才能扩而充之与天地生生之理的合而为一,从而达到民胞物与的境界。这就需要通过心性修养、涵养工夫以提高人的素质,方能使其内心之德臻于完满。李滉将《太极图》与《西铭图》视为理学形而上学理论和修养工夫的根据,即小学大学的标准本原。“上二图,是求端扩充,体天尽道,极致之处,为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下六图,是明善诚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③
正是基于此种考量,李滉分别以《小学图》、《大学图》和《白鹿洞规图》为第三、四、五图。《小学》是朱熹所编的一个以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本。朱子极重小学,将其与大学并列。朱子学传入之初,朝鲜朝儒者便对《小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阳村权近曾写道:“小学之书,切于人伦世道为甚大,今之学者皆莫之习,甚不可也。自今京外教授官,须令生徒先读此书,然后方许他经。其赴生员之试,欲入大学者,令成均馆正录所先考此书通否,乃许赴试,永为恒试。”④李滉在《小学图》中,援引朱子的《大学或问》写道:“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涵养本原,而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⑤从中亦可看出李滉对小学的重视。他在继承和发展朱子思想的基础上,以敬身明伦为旨归将小学教育的组织、内容、目的、宗旨提纲挈领。《小学图》反映了李滉强调实践、注重践履的为学性格。李滉根据朱熹的《小学》一书的目录制作此图,以与《大学图》对举。在他看来小学和大学相反相成,是“一而二、二而一”①的关系。前文已言及《大学图》乃朝鲜朝初期的阳村权近所造。“大抵《大学》一书,一举目,一投踵,而精进本末,都在此。”②《大学》是被朱熹视作学者入德“行程节次”③的一本书,亦是其平生用力最久、最甚的一部儒家经典。朱子曾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全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④李滉认为为学者只要按此“行程节次”认真践履、勇猛精进便可达至圣域。《大学图》的特色在于引述朱子《大学或问》的论“敬”之说以为圣学的始终之要。“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尝以主一无适言之,尝以整齐严肃言之;门人谢氏之说,则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有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小学之赖此以始,则夫大学不能无赖于此以为终者,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盖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则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是诚意正心以修身,则所谓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乎天下,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离乎敬也,然则,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⑤本段引文对李滉《圣学十图》的主敬思想影响甚大。尊德性而道问学、居敬而穷理是理学的基本立场,朱熹曾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⑥认为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存养,不过朱熹实际上以“穷理”、“致知”为先。李滉指出:“非但二说(即《小学图》与《大学图》所引朱子论教之说)当通看,并与上下八图,皆当通此二图而看……下六图是明善诚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而敬又彻上彻下,着功收效,皆当从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之说如彼,而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①由此可见,“敬”在李滉哲学中并不仅仅是彻上彻下、贯穿动静始终之修养工夫,而且还是可以统摄存心养性与格物致知的圣学第一要义。《圣学十图》即是其主敬思想的集中体现。第五图《白鹿洞规图》是李滉依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而作,旨在阐明人伦之道。“盖唐虞之教在五品,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故规之穷理力行,皆本于五伦。”②李滉认为大学是小学阶段的延续,而两阶段的教育有着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穷理、力行)、在止于至善,而小学之宗旨则为在明人伦(五伦),所以说“此两图可以兼收相备”③。《白鹿洞规图》意在综合小学、大学的为学之方,着重突出五伦作为圣学内容的重要地位。另外,从《白鹿洞规图》中亦可看出李滉的书院教育思想。李滉以为以上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④。
心、性、情是理学人性论的核心范畴,第六图即为《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此图在上一节已有论及,这里只做简要介绍。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下图为李滉所作。在朝鲜朝儒学史上,主要论辩皆围绕“心”这一哲学范畴而展开。16世纪后半期的“四端七情”之辨、“人心道心”之辨、18世纪初叶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以及19世纪后半期的本心明德之“主理主气”论辩等均是对“心”之发用及相关问题的深入辨析。此为韩国性理学的特色所在。
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理学的主题。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就是通过“心性情”等范畴全面展开。⑤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一言蔽之即性为体情为用。朱熹认为“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①。李滉则与之不同。他进一步发挥程朱理气心性说,将性情之说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并将朱学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七理气”之辨。《心统性情图》之中图和下图将李滉理气心性诸说表述得最为简单明了。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秉承之,亦主“合理气,统性情”。但是,李滉比朱熹更专注于对“情”的探讨。重“情”乃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理气心”。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此心具心气之患)的“情”皆能中节便成为心性修养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气之患,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故其曰:“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②其持敬之目的就是要由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之际反观内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对此图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第一图的结构原是智上礼下仁左义右,先是对其中礼智上下结构进行改动,后来又对原图中的仁义左右次序做了修改。最后还是以第二次改动的为定本,收录十图之中。③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第七图为朱熹自作的《仁说图》。李滉曾将此图放于《心学图》之后,后接受李珥的建议移至《心学图》之前。他在给李珥的复信中写道:“《仁说图》当在《心学图》之前,此说甚好,此见解甚超诣。滉去年归来,始审得当如此,及得来说而益信之,即已依此说互易矣。”①由此亦可窥出《圣学十图》中各图的排列次序是经过了反复斟酌与思考。该图进一步说明了四德相互之间以及其与四端之间的关系。“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未发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则包乎四者。”②“仁”作为统摄“四德”与“四端”的道德理性,在理学中不仅与太极、诚以及中和等概念同等重要,而且还指代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人和天地生物皆以之为心。李滉将朱子学的仁说视为上承天道下启存养之途,亦即贯通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节点。这应该是李滉最终把此图置于《心学图》之前的重要原因。由其“圣学在于求仁”之见以及此图“发明仁道,无复余蕴”之说可以推知,在李滉的心目中人君者欲施仁政亦应于此图求其义。故《仁说图》在《圣学十图》中亦居重要地位。
第八图为程复心所绘《心学图》。李滉将此图目为天地生物之心(仁)的着足处。李滉性理学“求仁”之目的在于使人不断完善其人格,以优入于圣域。“此仁者,所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足以普四海弥六合也。”③《心学图》把“心”分为赤子心与大人心、人心与道心,也是为了给人提供实现理想人格的修养工夫。学者只有“惟精择善,惟一固执”,才能克去己私以存天理。所以必须施以“持敬”工夫使人心变为道心。唯有以“敬”抑欲才能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加之“敬”又是一心之主宰,存理遏欲的工夫大可统一到“敬”字上来。就此而言,“存天理遏人欲”是主敬工夫之实质内容。对《圣学十图》中的后五图,李滉认为“五图原于心性,而要在免日用崇敬畏”④。他在第六、第七图中着力探究主体之性情问题后,便将“天地生物之心”作为仁之根据。李滉在第八图中又论述了与“心”相关之问题,并指出了治心之工夫以及“敬”作为一心之主宰在涵养省察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第九图为金华王鲁斋柏就朱熹《敬斋箴》绘制的《敬斋箴图》,此箴乃朱熹有感于张敬夫的“主一箴”所作。若说第八图示“圣学心法”,那么此图则“为圣学之始终”。此图承《心学图》之旨,继续以“敬”为工夫之要以示具体的用工地头。在图说中,李滉引真西山之言曰:“敬之为义,至是无复余蕴,有志于圣学者,宜熟复之。”①这表明李滉不仅将“敬”视为其存养工夫的关键,而且还视为其性理学体系之核心。他在答李叔献(李珥)的信中写道:“惟十分勉力于穷理居敬之工。而二者之方,则《大学》见之矣,《章句》明之矣,《或问》尽之矣。足下方读此书,而犹患夫未有所得者,得非有见于文义,而未见于身心性情之间耶。虽见于身心性情,而或不能真切体验,实味膏腴耶。二者虽相首尾,而实是两段工夫,切勿以分段为忧,惟必以互进为法,勿为等待。即今便可下工,勿为迟疑。”②《敬斋箴》内容如下:“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参以三,惟心惟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弗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论,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灵台。”③这些可视为“敬”的具体细目,可以此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李滉还依据陈柏的《夙兴夜寐箴》绘制《夙兴夜寐箴图》④以为第十图。他认为“敬斋箴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其地头而排列为图。此箴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其时分而排列为图。”⑤第九图《敬斋箴图》与第十图《夙兴夜寐箴图》一是以地头言,一是以时刻言。①即,前者按行事罗列,是以心为核心展开的主敬工夫;后者是依时间编排,是以行为核心演绎的持敬规范。②李滉曰:“盖敬斋箴,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时其地头而配列为图。此箴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时分而配列为图。”③但道之流行于日用之间,无所适而不在,亦无顷刻之或停,因此李滉强调不分时分与地头的主敬工夫。两者在李滉性理学中相互发明、相互补充均为相当紧要,因之李滉言二者须并进。
《圣学十图》前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体现了《太极图》融自然本体、社会教育、人格培养为一体的思想;后五图则“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与前五图恰好构成不即不离的体用关系。前五图以无极太极为第一图,后五图以心统性情为第一图。这个划分不以天道人心为二,而是将二者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形而上本体遂与人世间的心性冥冥相通,立人极也就可以进而立太极。④易言之,后五图则展示心体(天道)呈现之修养过程。“综观此十图,其核心是人。因此,李退溪的圣学,我们亦可称为人学,即学做圣人之学。《圣学十图》,就是学做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情感意志等等。全面、系统而又渐次深入地论述了为圣的目的、方法。”⑤依李滉之见,除了“心”之外再没有完成自我人格的原动力。关键在于如何克去除理气心所具有的心气之患,从而使心气循理而行、顺理而为。这就要求学者时刻以“敬”字治心、以“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⑥。显而易见,以持敬工夫统摄心知乃是李滉主敬论的主要意涵。
由上所述可知,李滉主敬思想根植于其对性理学理气心性诸说的理解。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七情之善与不善端视发而中节与否——一切都随“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其实此时四端与七情皆滑入气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皆为气之所为。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皆为气之所为。所以主敬以治心上之“气患”,使气顺理而发、循理而行,这就是以主敬说为特色的李滉思想的根本主旨。
简言之,李滉以“敬”贯动静、知行并重以及内外如一为其主敬思想的方法论,由此构筑了以主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绘制的《圣学十图》以图画的形式将程朱理学中繁杂的主敬思想做了言简意赅的表述。此图既是主敬工夫的形象说明,也是李滉思想的简明提要。
“敬”作为理学修养的重要方法受到程朱诸儒的重视。朱子以为“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程子亦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语最妙”②。但是程朱诸儒并未以此为纲领构筑其道德形上学体系。朱子去世三百年后,号为“海东朱子”的李滉却以“敬”为核心构筑了颇具理论与践履特色的“实践道德哲学”(后人亦将之称为退溪“圣学”或退溪“心学”),遂集朝鲜朝的朱子学思想之大成。李滉对“敬”的强调与对“敬”的意义的理解确有超过朱子处。③以此为特色,退溪学代表了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李滉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坚持二者是不同类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④李滉还制作“心统性情图”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工夫论方面,李滉极重主敬,以下学上达为其居敬穷理之出发点。“只将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以验夫统体操存不作两段者为何等意味,方始有实用功处,脚跟着地,可渐渐进步,至于用功之久,积熟昭融,而有会于一原之妙,则心性动静之说不待辩论而嘿喻于心矣。”①他主张由下学上达之持敬修养工夫优入圣贤之域,从而体验天理之极致。由此可知李滉的道德学问观以及其为学的根本宗旨。“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②,李滉在知与行方面忠实履行了儒家之为学宗旨,堪称朝鲜朝五百年间难得的为己之学之楷模。
他的思想不仅对韩国性理学界影响至深,而且还对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启蒙传疑》、《自省录》、《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圣学十图》、《论四端七情书辨》等,均收录在《增补退溪全书》(1—5册)之中。
第三节 奇大升与其“四端七情”论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最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之特色。但是,他的四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与奇大升之间展开的相互问难。在与奇大升论辩过程中,不仅李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其立场也变得更加鲜明。本节将对奇大升“四七理气”论思想作一论述。
一、奇大升的理气论——兼述《论困知记》
奇大升(字名彦,号高峰、存斋)亦是朝鲜朝重要性理学家,生于中宗二十二年(1527年),卒于宣祖五年(1572年),谥号为文宪。他出生于全罗南道光州召古龙里松岘洞。③32岁中文科乙科第一人,后官至大司谏。奇氏天资聪敏,博览强记,长于论辩。33岁时便与李滉围绕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进行了长达8年的相互问难,由此拉开了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四七理气”论辩之帷幕。
理气问题是性理学的首要问题,奇大升亦十分重视此问题。他在信中写道:“然鄙意以为当于理气上,看得分明,然后心性情意,皆有着落,而四端七情,不难辩矣。后来诸先生之论,非不详且明矣。然质以思孟程朱之言,皆若异趣似于理气上未剖判也。”①依奇氏之见,若于理气问题上看得分明则心、性、情、意及四端七情诸说皆不难辩,故可将其理气说视为他的“四端七情”说的立论基础。于此也可以看出,他是追求理气说(存在论)与心性论相一致的性理学家。奇氏这一致思倾向与李珥有相似之处。下面将分析他的理气概念以及在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他用太极阴阳说规定了理气概念。“至于天地上分理气,则太极理也,阴阳气也。”②他以太极阴阳论定义理气的同时,将此贯彻到人和物上进一步指出:“就人物上分理气,则健顺五常理也,魂魄五脏气也。”③这表明奇氏以传统性理学形上、形下之理论来理解理气。
其次,在理气关系上,奇大升以理为气之主宰,以气为理之材料——强调理对气的主宰性乃其思想之特色。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④
理为气之主宰就意味着理对气之运动的主导作用。但他在强调理的主宰性的同时又指出理的脆弱性,即理无眹而气有迹。“理弱气强”似与理的主宰性相矛盾。其实这也是朱学理气论的困境所在,因为在朱子哲学中“理”就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⑤之“三无”特性。奇氏有言:“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①这是他在信中质疑李滉“理发”说的一段文字。如何化解本体义上理的主宰性与流行义上理的脆弱性矛盾以使气顺利而发?这是每位理学家都要面临的重要理论课题。欲分析奇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要从其理气关系的解读上着手。
再次,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奇氏强调二者的不离义,此即理气“混沦一体”说。但是在此问题上他又力主既要“合看”又要“离看”。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在奇大升看来,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③,因此学者于此应特别要“精以察之”。依其对理气的规定,理无眹而气有迹,故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他评论说:“盖理无眹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④非以理气为一物,而却“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奇氏的这一观点与明儒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47年)的理气为一物,“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的主张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罗整庵的《困知记》传入韩国后引起较大反响,有尊奉之者,也有批判之者。李滉和奇大升即属后者,二人皆撰文予以批判。李滉写了篇《非理气为一物辩证》,奇大升则写了篇《论困知记》。
《高峰集》中记载:“明学者罗钦顺,号整庵,作《困知记》以理气为一物,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为不然。若著‘所以’字,则便成二物云,又以‘道心为体,人心为用’。此书新出,而世之学者莫能辨其是非,或有深悦而笃信者。戊辰五月,大升以大司成,诣阙至玉堂与副提学臣卢守慎,共论《困知记》。守慎以整庵之言为至当,而无以议为。大升力辨其非曰,朱子以为道心源于性命之正,人心生于形气之私,固以理气分而言之矣。整庵认理为气,以理气为一物,故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种种新奇之说,皆从此出。何可背圣贤相传不可易之说,而从罗整庵之新奇乎?遂著困知记论以辨之。盖其正见,不眩于似是之非,而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反复纡余,光明俊伟粹然一出于正,此李滉所以敛袵者特深也。”①“戊辰五月”,即为宣祖元年(1568年)5月,时奇氏42岁。不过据其《年谱》记载,奇大升在明宗二十年(1565年)12月往见卢守慎(字寡悔,号苏斋,1515—1590年)于镇国院,并与之讨论了人心道心问题。②卢氏以罗整庵《困知记》的理论为依据论述了其对人道说的看法。可见,他的《论困知记》一书是在与卢守慎展开论辩过程中完成,也是其思想成熟期的著作。③此书对了解奇大升的理气性情学说特点以及《困知记》一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此文的开头奇氏写道:
罗整庵《困知记》,世多尊尚。余尝观其书,闳博精邃,顿挫变化,殆不可测其涯涘。试提大概则推尊孔孟程朱,为之宗主。援据《易》、《诗》、《书》、《礼》,以张其说,而又能躬探禅学而深斥之。其驰骋上下,抑扬予夺之际,可谓不遗余力矣。世俗悦其新奇,而不究其实,宜乎尊尚之也。然愚之浅见,窃尝以为,罗氏之学,实出于禅学,而改头换面,文以圣贤之语,乃诐淫邪遁之尤者。使孟子而复生,必当声罪致讨,以正人心,固不悠悠而已也。④
从引文中可以概见,《困知记》传入韩国之初作为“新奇”之说颇受世儒的尊尚。这与《困知记》在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罗钦顺为江西泰和人,生于宪宗成化元年,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父死服阙后起原官,嘉靖六年坚辞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之召,致仕居家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致之学。他与其时的名儒王阳明、湛若水及欧阳德等人皆有往复辩论①,是在朱学阵营中为数不多的能与心学分庭抗礼的大儒。他的著作有《整庵存稿》二十卷和《困知记》六卷,而其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困知记》一书中。但《困知记》问世后并未受到中国学界关注,而却在韩国引起不小的波澜。如引文内容所见,有尊尚者亦有排斥者。奇氏则直斥罗氏之学“实出于禅学”,即便是孟子复生亦必当声罪致讨以正人心。
他指出虽然罗氏的个别观点和圣贤之道也有相符之处,但是其大纲领大根本却与之相去不啻百千万里之远。他还举了罗氏《困知记》中的具体论点以说明其主张皆与圣贤本旨相违,舛错谬戾不须更辨。
《记》凡四卷,益以附录,无虑数万言。其间,岂无一二之几乎道,而其大纲领大根本,与圣贤相肯,不啻百千万里之远。则其学之邪正,为如何哉。其书所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及“理气为一物”及“良知非天理”云云者,皆与圣贤本旨,舛错谬戾此,不须更辨,而其出于禅学之实,则不可以不辨也。②
尽管奇大升也主张理气“混沦一体”说,但是与罗氏的“理气为一物”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看来,罗氏之学“其出于禅学之实,则不可以不辨”。罗钦顺的《困知记》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已难以确知,但是从奇氏这段文字中可推知,起初传至韩国的《困知记》并非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六卷《困知记》,而是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年)五月完成的4卷本——是年罗氏69岁。在《困知记》序中,他写道:“余才微而质鲁,志复凡近。早尝从事章句,不过为利禄谋尔。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虽已晚,然自谓苟能粗见大意,亦庶几无负此生。而官守拘牵,加之多病,工夫难得专一,间尝若有所见矣,既旬月或逾时,又疑而未定,如此者盖二十余年,其于钻研体究之功,亦可谓尽心焉耳矣。”①罗氏这部著作的写作前后历时二十多年。当完成“四续”时已是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五月,其时他年已82岁。全书由卷上、卷下、续卷上、续卷下、三续、四续共六卷和附录构成。奇氏文中所提及的“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理气为一物”及“良知非天理”等的确是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所阐述的理论主旨。罗氏在《困知记》开篇即讲:“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然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②又说:“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③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渐趋衰落,而陆王心学声势日隆。罗氏对此深以为忧,于是将辨明“心性之别”以批驳陆王的“良知即天理”说作为其历史使命。职是之故,罗氏立学极重“心性之辨”。他以为心性的关系是既不相离又不能相混的,二者之别甚是微妙。若于心性的分际区别上,稍不清晰,便真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由此他将“道心”与“人心”关系定义为体用关系,这就是其独特的“人心道心体用”说。
那么,被称为“朱学后劲”的罗氏学说为什么会受到同样遵奉朱学的韩儒李滉、奇大升等性理学家的批判呢?这主要是因于其“理气为一物”的思想和由此引申出的“人心道心体用”说。于此可见,至16世纪中韩两国朱子学的发展已各呈不同的义理旨趣,此与韩国性理学者与中国朱子学者所处的不同人文语境与各自所倚重的不同核心话题相关。对于这一问题,讨论李珥理气说时再做进一步分析。
奇大升以为,罗氏之所以提出“理气为一物”、“人心道心体用”说等主张是因其学源自禅学之故。故在《论困知记》一文中,他力图揭露罗氏学说“实出于禅学”的“真相”。于是,奇氏在文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与此相关的内容:
整庵自言“官京师,逢一老僧,闻‘庭前柏树’之话,精思达朝,揽衣将起,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云云,此则悟禅之证也。后官南雍,“潜玩圣贤之书,研磨体认,日复一日,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云云”,此则改头换面,文以圣贤之语之实也。此之分明招认,固不可掩。而又有其论道理处,尤显然而不可掩者焉。《记》上第五章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一,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用也,精微纯性之真也。释氏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故其为教,始则欲人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空即虚也。既则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觉即知觉也。觉性既得,则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神即灵也。凡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使其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识矣。顾乃自以为无上妙道,曾不知其终身,尚有寻不到处,乃敢驾其说,以误天下后世之人云云。”
以此一章观之,其学之出于禅学者,益无所遁矣。夫心之虚灵知觉,乃理气妙合,自然之妙,而其或有不能然者,特以气禀物欲之蔽,而失其正耳。人苟能操而存之,不为气禀物欲之所累,则其虚灵知觉之妙。固自若也,非如释氏之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然后心始虚也。又非如释子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然后心有知觉也。又非如释子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然后心可谓之神也。此与圣贤所论虚灵知觉者,同耶异耶?其亦不待辨而可知其非也。
且既曰:“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而继之曰:“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然则圣贤之论心,亦与释子无异致耶。“离诸相,契虚觉,而洞彻无方者”,乃释子之作弄精神,灭绝天理者也。今乃欲与圣贤之论心者,比而同之,其可乎,其不可乎。
又曰:“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可识。”夫欲适越而北其辕,终莫能幸而至焉。今乃欲据释子所见之及,而向上寻之,以识夫帝降之衷,吾恐其如北辕而适越,终身伥伥,竟无可至之日也。
整庵之学,初既悮禅,而后观圣贤之书以文之。故其言如此,殊不知儒释,道既不同,而立心亦异有如阴阳昼夜之相反,乌可据彼之见,而能为此之道乎。①
罗钦顺自述其一生孜孜求道,用心甚苦。先由禅学悟心之灵妙,后识吾儒性命之旨。年垂六十,才自认为有见于性命之真。②其学思历程中确有一个出入佛道的经历(早年由禅学而入),《明史》亦记载道:“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③罗氏从“佛在庭前拍树子”话头得悟后,始知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虽相似而实不同——释氏大抵有见于心而无见于性。他指出今之世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在罗氏看来,道之不明正由于此。由此而论,奇氏批驳钦顺之学“实出于禅学”一说似难成立。在《困知记》一书中罗氏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禅宗经典《楞伽经》以及达摩、宗杲等重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批判。连《明儒学案》也提到“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④其实,钦顺之学是建立于程朱的“理一分殊”说之上,罗氏曾说过:“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简而尽,约而无所不通,初不假于牵合安排,自确乎其不可易也。”⑤又说:“一旦于理一分殊四字有个悟处,反而验之身心,推而验之人人,又验之阴阳五行,又验之鸟兽草木,头头皆合。于是始涣然自信,而知二君子之言,断乎不我欺也。愚言及此,非以自多,盖尝屡见吾党所著书,有以‘性即理’为不然者,只为理字难明,往往为气字之所妨碍,才见得不合,便以先儒言说为不足信,殊不知工夫到后,虽欲添一个字,自是添不得也。”①可见罗氏之学大体是接续程朱而来,但是在理气观方面已与程朱有了较大不同。那么,为什么同尊朱子的奇大升与罗钦顺间会有如此大的理论分歧呢?这主要源于二人对“理”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并对其“理”的特性有不同的界定。奇氏力辩罗氏之学的“禅学之实”乃因二人的理气观差异甚大,所以他紧接着就对罗氏理气说与心性说不一致提出批评。奇大升对钦顺的理气观极为不满,批评亦较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内容。学者于此不可不察。
前面已论及,奇大升是追求理气论与心性论相合一的性理学家。于是,他对罗氏思想中的两论不一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佛氏“作用是性”之说,固认气为理,而以心论性也。整庵实见之差,实由于此。故理气一物之说,道心人心性情之云,亦皆因此而误焉。盖既以理气为一物,则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属理气。故其为说,必至于如是,而整庵之所自以为向上寻到者,亦不过于佛氏所见之外,知有理字。而其所谓理字者,亦不过于气上认其有节度处耳。整庵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者,正是此病也。虽其为说,张皇焜耀,开阖万端,而要其指归,终亦不出于此矣。
且整庵每自谓至当归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夫既以理气为一物矣,而又以体用为二物焉,并引“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以证体用之为二物。若曰:道是体神是用,而道与神为二物,则理气果一物乎?理气果一物,则道与神,又何以为二物乎?整庵又以心与性,为体用之二物,心与性,既是二物,与理气为一物之说,不亦矛盾之甚乎?②
奇氏认为钦顺之学有“认气为理”以及由此引生的“以心论性”之病。他进而指出,罗氏自以为向上寻到者,亦不过于佛氏所见之外知有一个“理”字。而其所谓“理”字者,亦不过于气上认其有节度处耳。所以奇大升直言,“整庵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者,正是此病也”。又指责说整庵每自谓至当归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既以理气为一物,则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属理气。”奇氏所要强调的是理学“体用一源”之原则,故指责罗钦顺“以心与性,为体用之二物,心与性,既是二物,与理气为一物之说,不亦矛盾之甚乎?”既然理气为一物,体用就不能析为二物。
在东亚儒学史上奇大升是最早具体指出罗氏学说之内在矛盾的学者。对于此不能“归一”性,被称为宋明理学殿军的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年)和《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1610—1695年)师生亦有评述。刘宗周指出:“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谓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不免抛自身之藏。”①黄宗羲则更直接指出:“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①当然,这是刘宗周与黄宗羲师弟基于心学之立场对罗氏之学作出的评判。但是,谨遵朱子之学的奇大升和秉持心学立场的刘、黄等人先后都对罗氏学说的自相矛盾提出批评。此一现象表明作为儒者他们皆以体用一源为共法,而其理论也因之具有相近的思想倾向。这无关各自的具体学术主张。就哲学体系的完整性而言,一个思想家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后者应为前者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有些当代学者因此十分肯定刘、黄二人对罗钦顺的批评。②当然也有人对刘、黄师弟对于罗氏学说的批评不以为然。③分歧的产生与朱子哲学特殊的义理架构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朱子哲学在存在论(理气论)意义上倾向理气二分(“不离不杂”)和以理为主的理本论;而在心性论意义上则偏于以性、情、心三分结构为义理间架的“心统性情”论。④陈来先生曾指出,以“心统性情”为代表的朱子心性论结构的表达并非“理/气”二分模式,而是“易/道/神”的模式。盖因心性系统乃一功能系统,而不是存在系统。因此黄宗羲等人以“天人未能合一”来批评朱子的理气论未能贯通到心性论,似与事实有悖。实际上在朱学中理气观念并非没有应用到“人”。朱子使用“性理/气质”来分析人的问题即与其理气观一脉相承。①陈来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对朱子“心”论的理解有帮助,而且对罗氏学说的不一致性以及韩国儒学“四七理气”之发问题的理解亦大有助益。
在论述权近、郑之云等人的性理学时已言及,韩国性理学者在探讨性理问题时皆热衷于追求“天人心性合一”——摄理气于心乃韩国性理学之特色。因此相较于中国朱子学的理气说,韩国性理学的理气说更多带有性情论色彩。韩国儒者借此以说明性情之辨以及性情之发等问题。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奇大升的“理气共发”说以及李珥的“气发理乘”说皆可从这一角度得到深入的理解。否则很难解释倡言“理发理动”②以及“太极自动静”③的李滉何以能被称为“东方之朱夫子”。
在《论困知记》文末,奇氏还批评了罗氏的“良知非天理”说。曰:
整庵又论良知非天理,而云“知能是人心之妙用,爱敬乃人心之天理”,然则天理在妙用之外,而妙用者无与于天理乎。夫天理之在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此心之所以统性情。而其未发者,寂也体也;其已发者,感也用也。然则爱敬者,为未发耶,已发耶。知能,虽皆心之用,而有真妄邪正之分,固不可皆指以为天理矣。若加一良字,则乃本然之善,岂非天理之发乎。今以爱敬为天理,而以良知为非天理,爱敬与良知果若是其不同耶。且以知能为心之妙用,而不察乎真妄邪正之实,则尤不可。佛氏之神通妙用,运水般柴之说,正坐不分其真妄,而皆以为妙用之失也。昔有问于胡文定公曰:“禅者,以枯槌竖拂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为用,用而不妙。须是动容周旋中礼,方始是妙用处。”以此而揆诸整庵之言,其是非得失亦可见矣。整庵尝论宗果,以为“直是会说,左来右去,神出鬼没,所以能耸动一世。”余以为整庵之状宗杲者,乃所以自状也。
噫,道丧学绝,世俗何尝知此意思。见余之论,必以为笑,不谓之狂,则谓之妄也。然余亦岂欲必信于世俗,而与哓哓者相竞。将以俟后来之君子尔,同志之士,幸相与谅之。①
从奇氏对罗整庵的批评中可见,他对罗氏的“良知非天理”说的理解上有些偏差。前面已论及,明中叶以后程朱之学渐显颓势,王学日渐兴盛。在此情形之下,罗氏愤而扛起朱学大旗,欲明“心性之辨”以批驳“良知非天理”说。他将此作为理论活动的首要任务。罗氏曰:“夫孔孟之绝学,至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尝认良知为天理也。以谓有物必有则,故学必先于格物。今以良知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此语见《传习录》。来书亦云:‘致其良知于日履之间,以达之天下。’),则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无乃不得于言乎(《雍语》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本体,岂可于事物上寻讨?’总是此见。)!”②可见罗氏倾向程朱的“性即理”,而非“心即理”。因此他认为“有物必有则,故学必先于格物”——“格物”即为克己之私的过程。依罗整庵之见,“良知为天理”的说法过分强调个体之慧悟,极易将艰苦的修养工夫化为简易的禅悟,这是学人需警惕的非常危险的理论动向。显而易见,罗氏所批“良知”是指阳明的“致良知”。而奇氏所理解之“良知”则为基于伊洛渊源的良知、良能,也就是本然之善。于此也可以窥出奇氏的心性说仍以程朱的心、性、情三分义理间架为基础。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并不同意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那么,应如何理解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呢?对此奇氏有如下表述:
喜同恶离,乐浑全厌剖析,乃末学之常累。然鄙意固未尝以是自安也,亦欲其一一剖析尔……又或问: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朱子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然,则气之自然发见,过不及者,岂非理之本体乎……至于极论其所以然,则乃以七情之发,为理之本体,又以气之自然发见者,亦非理之本体,则所谓发于理者于何而见之,而所谓发于气者,在理之外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失,不可不察也。罗整庵所论不曾见得,不知如何。若据此一句,则其误甚矣。若大升则固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也。①可见,奇大升主张的是基于“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的理气“混沦一体”说。他以为理气虽不可谓二物,但也不能视为一物,“若以为一物,则又无道器之分矣”②。因此在奇氏看来,罗整庵以理气为一物,“其见甚乖”③。其实,奇大升的“理气混沦”说与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理”作为“所以然”者的地位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牵涉到对“理”的主宰义的不同认识。奇氏强调理的主宰作用,所以不满“理气一物”论。“整庵则以理气为一物,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为不然。谓若着‘所以’字,则便成二物云云。”④但上一段引文中奇氏所言“罗整庵所论不曾见得,不知如何”一句则需做进一步商榷。此言出自奇大升回复李滉的“高峰第二书”中。据研究,奇氏大约是在戊午年(32岁)或己未年(33岁)已读到《困知记》,故与李滉开始“四七理气”论争之前很有可能已受《困知记》思想的影响。①而且,李滉将奇氏己未年“高峰第一书”中的“七情中四端”以及“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等观点,评为与整庵的“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②。由此可见其时李滉也认为奇氏思想受到罗氏学说的影响。而奇氏在第二封回信中自辩道“整庵所论不曾见得”,则不能不令后学对之生疑。奇氏的理气“混沦一体”说后被李珥继承发展,确立为极富主气论特色的“理气之妙”说。
李滉对罗钦顺亦有评价,曾说过“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③。他则谨依朱子在《答刘书文书》中所阐“理与气决是二物”说,对主气论学者的“理气非异物”之说进行了批评。
最后附上李滉的《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供学者参考。此文对理解李滉、罗钦顺以及奇大升三人理气论之间的差异有较大帮助。该文内容如下:
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又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今按:孔子、周子明言阴阳是太极所生,若曰理气本一物,则太极即是两仪,安有能生者乎?曰真曰精,以其二物,故曰妙合而凝。如其一物,宁有妙合而凝者乎?
明道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
今按,若理气果是一物,孔子何必以形而上下分道器,明道何必曰“须著如此说”乎?明道又以其不可离器而索道,故曰“器亦道”,非谓器即是道也;以其不能外道而有器,故曰“道亦器”,非谓道即是器也。(道器之分即理气之分,故引以为证。)
朱子《答刘书文书》曰:“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又曰:“须知未有此气,先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夹论。至论其偏体于物,无处不在,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莫不有是理焉。”(今按:理不囿于物,故能无物不在。)不当以气之精者为性,性之粗者为气也。(性即理也,故引以为证。)
今按: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又曰:“性虽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相夹杂。”不当以气之精者为性,性之粗者为气。夫以孔、周之旨即如彼,程、朱之说又如此,不知此与说同耶?异耶?滉愚陋滞见,但知笃信圣贤,依本分平铺说话,不能觑到花潭奇乎奇,妙乎妙处。然尝试以花潭说揆诸贤说,无一符合处。每谓花潭一生用力于此事,自谓穷深极妙,而终见得理字不透。所以虽拼死力谈奇说妙,未免落在形气粗浅一边了,为可惜也。而其门下诸人,坚守其误,诚所未谕,故今也未暇为来说一一订评。然窥见朱子谓叔文说:“精而又精,不可名状,所以得不已,而强名之曰太极。”又曰:“气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气为性之误。”愚谓此非为叔文说,正是花潭说也。又谓叔文“若未会得,且虑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张,久之自有见处,不费许多闲说话也。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说。别看他处,道理尚多,或恐别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胶漆之盆,枉费心力也。”愚又谓,此亦非为叔文说,恰似为莲老针破顶门上一穴也。且罗整庵于此学非无一斑之窥,而误入处,正在于理气非二之说。后之学者,又岂可踵谬袭误,相率而入于迷昧之域耶?①
依李滉之见,罗钦顺和奇大升等皆“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②,只强调理气之“不离”义而忽视二者的“不杂”义。于是,他特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纠正罗、奇等人“理气非二”说及气本论者徐花潭“指气为性”说的错误。
由是观之,强调理气“非一物”是李滉的根本立场。正是基于此种理气“不杂”义,李滉和奇大升围绕“四端”和“七情”的“所从来(根源或来源)”及“所指(所就以言)”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辩。
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与李滉“四七”论之比较为中心
在四端七情①以及理气问题上,奇氏基于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
明宗十四年(1559年)一月,李滉曾致书奇大升,提到“又因士友间传闻所论四端七情之说,鄙意亦尝自病其下语之未稳。逮得砭驳,益知疏缪,即改之云:‘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未知如此下语,无病否?”②就自己对“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所做的表述征求了奇氏的意见。
是年三月,奇大升撰《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他将书寄赠李滉,此书即为奇大升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其中写道:“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说也,而先儒发明尽矣。然窃尝致之,子思之言,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论,所谓剔拨出来者也。盖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而性无不善,情则有善恶,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③奇大升以为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别乃因子思、孟子等先圣“所就以言之者”不同之故,也就是二者在情之所指及所偏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情”只有一种,而“四端”和“七情”所指的对象却有所不同——一指全体,一指其中之部分,二者并不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情。已发之情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心是否依性理而为主宰。性是形上之理,情则是形下之气。理气不离——理不能独自发用,必因气之发而显理之意义。奇氏以为若依李滉之说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两边,则会使人认为理发时无气之作用,而气发时无理作根据。这是不合于程朱学理气“不离”之义。①奇大升指出,子思所说的“情”是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所论的“情”则是所谓“剔拨”②出来者。故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若谓“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便如同将理与气判而为两物,也就无异于认为“七情”不发于性、“四端”不乘于气。这就是奇氏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所持的“剔拨论”主张。
在奇大升而言,将“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一句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③,虽似稍胜于前说但终究在语意上仍有所未安。
盖性之乍发,气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谓“四端”者也。此固纯是天理所发,然非能出于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也。然则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兼气”,可乎?论人心、道心,则或可如此说;若四端、七情,则恐不得如此说,盖七情不可专以人心观也。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④
奇氏所言“四端”为本然之善(“良知”)得以直遂者即指“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因此他以为,“人心”、“道心”或可以理气分言,但是“四端”、“七情”却不宜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或“兼气”。奇大升进而指出所谓“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而所谓“恶”者则为“气禀之过不及”。于此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奇氏的基本见解可概括为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因此七情之发或善或恶,“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者。而且,他还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初非有二义,二者只是不同性质的(如“善”的或“恶”的)“情”而已。奇氏又进一步论道曰:“近来学者,不察孟子就善一边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别而论之,愚窃病焉。朱子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及论性情之际,则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盖恐人之不晓,而以气言性也。然学者须知理之不外于气,而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乃理之本体然也,而用其力焉,则庶乎其不差矣。”①奇大升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主张被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论。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其“理气兼发”或“理气共发”说中的“理”是否具“发用义”?依奇氏之见,“理之本体”为“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若以此推之自然得出“四端”为“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的结论。而且因其力主“理”的“不外于气”之特性,故其“四七理气”论可以表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说。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其“四七理气”之发论中发之者是“气”而不是“理”,“理”只具“主宰义”。这也正是奇大升和罗钦顺虽皆主理气二者“混沦一体”,前者却极力批判后者“认气为理”的主要原因。在罗钦顺的理气论中,理因不具“主宰义”弱化了自身的“实体性”——这对于谨遵传统程朱之旨的奇大升而言无异于离经叛道。
以上便是奇大升就“四七理气”问题致李滉的第一封书信中的主要内容。奇氏在信中着重阐述了其对“四端”和“七情”的理解以及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见解。
对于奇氏来函中的问难,李滉撰写了《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文章从以下几个角度作了认真的回应。首先,他肯定了奇大升对于“四端”和“七情”的区别。“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故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③在李滉看来,理与气是“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这表明他虽然承认理气二者不可分离,但是基于“四端”和“七情”“所就而言之”的差异而有种种分别。这是李滉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其次,李滉从程朱“二性论”的角度对“四七”说进行了阐发。“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子思、孟子所讲的“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与“气质之性”不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性(天之所与我者),即非由外铄的“我固有之”者。在此李滉则基于“四端”与“七情”各自的“所从来”之异(在源起上存在的差异),主张因“性”有本性、气禀之异,故“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性”可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分理气而言之。
再次,李滉又从四端七情的“所主”与“所重”之不同,力主二者皆可以分理气来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四端,皆善也。故曰:‘无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七情,善恶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则心已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谓之‘和’。由是观之,二者虽曰皆不外乎理、气,而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则谓之某为理,某为气,何不可之有乎。”①李滉也以为虽然“四端”与“七情”皆来自于理气,但是因其在“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之义上各有“所主”与“所重”,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四端”为发于内者,即仁义礼智之性的直接发用;“七情”则为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者,即人之形气感官因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四端”所主的是“理”,“七情”所重的是“气”。因此李滉主张“四端”和“七情”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换句话说,他力辩二者之区别的目的在于强调其在善恶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职是之故,李滉认为奇氏为学之失在于“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他在信中写道:“今之所辩则异于是,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从来,概以为兼理气,有善恶,深以分别言之为不可;中间虽有‘理弱气强’、‘理无朕,气有迹’之云,至于其末,则乃以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是则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滉寻常未达其指,不谓来喻之意亦似之也。”②在他看来,奇氏在倡言“四端”是从“七情”中剔拨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说“四端、七情为无异”——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李滉进而直言“讲学而恶分析,务合为一说”乃古人所谓囫囵吞枣,其病不少——为学者若如此不已的话,就会不知不觉之间骎骎然入于以气论性之弊,而堕于认人欲作天理之患。
在此信的结尾处,他还援引朱熹之论为其主张申辩。“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李明辉先生认为朱子这句话在其义理系统中有明确的意涵,而其中两个“发”字的涵义并不相同:“理之发”的“发”意谓“理是四端的存有依据”;“气之发”的“发”则意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引发”,谓七情是由气之活动所引生。但是在朱子的系统中,既然理本身不活动,自不能说:四端是由理之活动所引发。故对朱子而言,理之“发”是虚说,气之“发”为实说。②这一论述对解读李滉、奇大升等人的“理发”、“气发”之说很有启发意义。“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③一语的确见于《朱子语类》,但朱子并未对之做进一步的阐发。
接到李滉复函后,奇大升随即撰写了第二封信也就是《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信中对李滉在文中的答复一一作了回应。于是,两人之间就有了第二次往复论辩。奇氏第二封信的内容分为12节,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奇大升还是强调自己的“情”观,认为人只有一种“情”。“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然而所谓‘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其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是故愚之前说,以为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者,正谓此也。又以为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者,亦谓此也。由是言之,以‘四端主于理,七情主于气’而云云者,其大纲虽同,而曲折亦有所不同者也。”①依其之见,情兼理气故有善恶。四端和七情之异源于“所就以言之不同”——七情之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与孟子所谓四端皆同实而异名;至于发而不中节者则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因此并非七情之外又有所谓四端者。
其次,奇氏以为不仅四端是性之所发,而且七情亦是性之所发。“来辩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此言甚当,正与朱子之言互相发明,愚意亦未尝不以为然也。然而朱子有曰:‘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以是观之,所谓‘四端是理之发’者,专指理言;所谓‘七情是气之发’者,以理与气杂而言之者也。而‘是理之发’云者,固不可易;‘是气之发’云者,非专指气也。”②他进而写道:“四端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七情亦发于仁义礼智之性也。不然,朱子何以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乎?又何以曰‘情是性之发’乎?”③理学先辈即主情为性之所发。奇大升肯定情有四端、七情之分,而四端和七情皆由性所发。
再次,奇氏又据理学人性论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原则,进一步指出不仅七情是理乘气而发,而且四端也是理乘气而发。他还直言“四端亦气”。“后来伏奉示喻,改之以‘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云云,则视前语尤分晓。而鄙意亦以为未安者,盖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揭之于图,或谓之‘无不善’,或谓之‘有善恶’,则人之见之也,疑若有两情,且虽不疑于两情,而亦疑其情中有二善,一发于理,一发于气者,为未当也。”④奇大升认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情中有“发于理”和“发于气”的两种善的说法难免令人困惑。这在奇大升看来显然是不妥的。依其之见,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便是“情”。故“情”皆出于心,并非仅源于外物触其形。“心”是理气之合,当其感于物而动之际发之者只能是“气”——四端和七情也不例外。“愚按:‘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句,出《好学论》。然考本文曰:‘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其曰‘动于中’,又曰‘其中动’云者,即心之感也。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焉,乃所谓‘情’也。然则情见乎外,虽似缘境而出,实则由中以出也。辩(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引者注)曰:‘四端之发,其端绪也。’愚谓:四端、七情,无非出于心者,而心乃理、气之合,则情固兼理、气也,非别有一情,但出于理,而不兼乎气也。此处正要人分别得真与妄尔。辩曰:‘七情之发,其苗脉也。’愚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朱子曰:‘性之欲,即所谓情也。’然则情之感物而动者,自然之理也。盖由其中间实有是理,故外边所感,便相契合;非其中间本无是理,而外物之来,偶相凑著而感动也。然则‘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一语,恐道七情不著也。若以感物而动言之,则四端亦然。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其感物者,与七情不异也。辩曰:‘安有在中,为理之本体耶?’愚谓:在中之时,固纯是天理,然此时只可谓之‘性’,不可谓之‘情’也。若才发,则便是情,而有和不和之异矣。盖未发,则专是理;既发,则便乘气以行也。朱子《元亨利贞说》曰:‘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又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①可见,奇大升在谈论四端和七情时特别强调心的感知与主宰作用。心为理气之合,故出于心的四端和七情必兼理气。他还说过若以生长收藏为情,便见乘气以行之实,而“四端亦气”也。
最后,奇氏还从价值论意义上就四端和七情的善恶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愚按程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然则四端固皆善也,而七情亦皆善也。惟其发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而为恶矣。岂有善恶未定者哉?今乃谓之‘善恶未定’,又谓之‘一有而不能察,则心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乃谓之和’,则是七情者,其为冗长无用,甚矣!而况发而未中节之前,亦将以何者而名之耶?且‘一有之而不能察’云者,乃《大学》第七章《章句》中语,其意盖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者,只要从无处发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也。《或问》所谓‘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蚩俯仰,因物赋形’者,乃是心之用也,岂遽有不得其正者哉?惟其事物之来,有所不察,应之既或不能无失,且又不能不与俱往,则其喜怒忧惧,必有动乎中,而始有不得其正耳。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证七情,殊不相似也。夫以来辩之说,反复剖析,不啻详矣,而质以圣贤之旨,其不同有如此者,则所谓‘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者,虽若可以拟议,而其实恐皆未当也。然则谓‘四端为理’、谓‘七情为气’云者,亦安得遽谓之无所不可哉?况此所辩,非但名言之际有所不可,抑恐其于性情之实、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也。”①他又说道:“夫以四端之情为发于理而无不善者,本因孟子所指而言之也。若泛就情上细论之,则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固不可皆谓之善也。有如寻常人,或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亦有是非其所不当是非者。盖理在气中,乘气以发见,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其流行之际,固宜有如此者,乌可以为情无有不善?又乌可以为四端无不善耶?此正学者精察之地,若不分真妄,而但以为无不善,则其认人欲而作天理者,必有不可胜言者矣。”②在奇大升看来,“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恶”者则是“气禀之过不及”。③但因理具有“不外于气”之特性,故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即为“理之本体”。而“理之本体”乃“天命之本然”亦即天赋之“善”者。于是,他认为四端和七情初非有此二义,皆仅是“情”的一种善恶性质而已。因此不能以理气来分言四端和七情。二者的区别只在性发为情之际,所发是否中节——其发而中节者,则无往而不善;其发而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者而为恶。基于此,奇氏以为不仅“七情亦皆善”,而且“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可见,他强调的是二者作为人类感情的同质性和同构性。依奇氏之见,二者的关系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而是七情包含四端(可简称为“七包四”)的关系。
李滉受到奇大升的进一步质疑。他在即接到奇氏《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之后就对其之前不够严谨的表述作了修正,并撰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信中李滉首先对奇氏四端亦是感物而动、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等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不过,对其将四端和七情视为“同实异名”的观点则给予了坚决反对。“公意以为:四端、七情皆兼理、气,同实异名,不可以分属理、气。滉意以为:就异中见其有同,故二者固多有浑沦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则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气之不同,分属何不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虽或有疵,而其宗旨则实有所从来。盛辩一皆诋斥,无片言只字之得完。今虽更有论说,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无益于取信,而徒得哓哓之过也。”①李滉主张对于二者既要异中见其有同,又要同中而知其有异。他还指出以“所就而言”,二者本自有主理、主气之“所主”的区别。由此,李滉提出了“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其详细内容摘录如下:
盖浑沦而言,则七情兼理、气,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著而感动也。且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但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②
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李滉坚守的是对二者各自不同的“所从来”与“所主”的“主理/主气”立场,如其所言“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至此,李滉大体已确立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可视为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最终定论。在此后与奇氏的往复论辩中,李滉对这一基本观点则再未作修正。
对于李滉的答复,奇大升提出了再质疑——遂有《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此信即为其《论四端七情》之第三书,作于1561年(明宗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年)。信中开头奇氏先对《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第一书》的《改本》作了评论,之后又对李滉的答复给予了逐条回应,最后还对《后论以虚为理之说》、《四端不中节之说》、《俚俗相传之语,非出于胡氏》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奇大升以其“因说”和“对说”①之理论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信中写道:
大升以为朱子谓“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者,非对说也,乃因说也。盖对说者,如说左右,是对待底;因说者,如说上下,便是因仍底。圣贤言语,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不可不察也。②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朱夫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③
朱子的“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是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的重要立论依据,所以奇氏特意对朱子的这一说法作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朱子此句是“因说”而非“对说”,是“纵说”而非“横说”。故不能以左右对待来理解。依其之见,圣贤之言“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所以后之学者对之需加以详察。
基于其“因说”之立场,奇大升又援引朱子对理气特性的论述并以此为据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异议。奇氏指出:
如第二条所谓“人之一身,理与气合而生,故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也。互发,则各有所主可知;相须,则互在其中可知”云云者,实乃受病之原,不可不深察也。夫理、气之际,知之固难,而言之亦难。前贤尚以为患,况后学乎?今欲粗述鄙见,仰其镌晓,而辞不契意,难于正说出来,姑以一事譬之。譬如日之在空也,其光景万古常新,虽云雾滃浡,而其光景非有所损,固自若也;但为云雾所蔽,故其阴晴之候,有难齐者尔。及其云消雾卷,则便得偏照下土,而其光景非有所加,亦自若也。理之在气,亦犹是焉。喜、怒、哀、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理,浑然在中者,乃其本体之真;而或为气禀物欲之所拘蔽,则理之本体,虽固自若,而其发见者,便有昏明、真妄之分焉。若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岂不犹日之偏照下土乎?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分据一心之内,迭出用事,而互为首从也。此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①
这是奇氏就李滉在《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之第二书中作答的内容提出的反驳意见。李滉以为,人之一身是由理与气和合而生,因理与气互在其中,故浑沦言之者固有之;又因各有所主,故分别言之亦无不可。对此奇大升以日照大地为喻指出,日光照射大地虽受云雾之影响,但是在空之日“其光景则万古常新”,无所加损。他认为,理之在气亦是如此,故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犹如日之偏照大地。若曰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的话,等于是“理”却具有了情意、计度、造作等特性——这显然有违于朱学之根本原理。依他之见,这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可见,奇氏同样忠于朱子之学,且以朱学为其立学之据的。
基于此,奇大升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委婉地提出己之修正意见,并主张对于“此等议论”不可草草下定论。
“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为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只有理发一边尔。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又未知于先生意如何?子思道其全时,固不用所从来之说,则孟子剔拨而说四端时,虽可谓之指理发一边,而若七情者,子思固已兼理、气言之矣。岂以孟子之言,而遽变为气一边乎?此等议论,恐未可遽以为定也。①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所理解的“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对之他极为自信,认为若在此之外更求“理之发”之义“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②。由此可见,奇大升和李滉皆以朱子学说为据展开思想的攻防。
接到奇氏的《论四端七情》第三书后,李滉只是在来书中节录数段加以批示,并未再作答复——只向奇氏致以含有欲结束二人论辩之意的书函。或许在李滉看来,通过奇氏的三次来书和自己的两次答复已令双方充分了解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感到二人相互间很难说服对方,遂欲结束这场论辩。接到李滉来函后,奇大升又撰写了《四端七情后说》和《四端七情总论》寄赠李滉,此时已是1566年(明宗二十一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收到奇氏寄来的两书后,李滉只是简单作了回复,而对来书中的具体问题并未详加解答。他写道:“四端七情《总说》(应为《总论》——引者注)、《后说》两篇,议论极明快,无惹缠纷挐之病。眼目尽正当,能独观昭旷之原,亦能辨旧见之差于毫忽之微,顿改以从新意,此尤人所难者。甚善!甚善!所论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复致思于其间乎?兼前示人心道心等说,皆当反隅以求教。今兹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谨当一一。”③如引文所见,信中李滉仅就奇氏对“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的解释提出些异议,对来书之内容未作具体回复。这表明李滉已无意继续与奇氏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
这场开始于明宗十四年(1559年)1月的李滉《与奇明彦》一书的论辩,以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10月李滉作《答奇明彦》一书而告终。但是,双方的主要论点大都集中于奇大升上退溪的前三次书和李滉的前两次作答的书函中。尽管二人围绕四七理气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他们相互间的问学并未就此中断。宣祖昭敬王元年(1568年)7月奇氏就拜谒了奉王命入京的李滉,是年12月还与其一同讨论《圣学十图》。而且,次年(1569年)3月还将欲回安东陶山的李滉送至东湖,并同宿江墅。在东湖舟上,奇大升先寄一绝奉别李滉,朴和叔等继之。席上诸公,咸各赠言饯别李滉。奇氏诗曰:“江汉滔滔万古流,先生此去若为留。沙边拽缆迟徊处,不尽离肠万斛愁。”①李滉和韵:“列坐方舟尽胜流,归心终日为牵留。愿将汉水添行砚,写出临分无限愁。”②李滉临行,不能尽酬,谨用前二绝韵奉谢了诸公相送之厚意。不料,于东湖作别后的第二年,1570年(宣祖三年)12月李滉辞世。奇氏惊闻退溪李滉先生讣音,设位痛哭。翌年正月送吊祭于陶山,2月撰《退溪先生墓碣铭先生自铭并书》,赞其曰:“先生盛德大业,卓冠吾东者,当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后之学者,观于先生所论著,将必有感发默契焉者。而铭中所叙,尤足以想见其微意也。”③可见,奇大升和李滉虽然在为学和致思倾向上分歧明显,但是作为同道益友和直谅诤友,二人感情甚笃,在相互问学中共同推动了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三、奇大升“四端七情”论的特色
奇大升与李滉皆为李朝一代儒宗,二人的学说亦各具其理论特色。由上所述可知,奇大升的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理气观和性情论等方面。
首先,在理气观上奇大升主张理气的“混沦一体”性,但是亦不否认二者区别——所谓“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①奇氏说过: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
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③
他主张在二者的“不离”义上应持“合看”和“离看”的立场。“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④,因此要求学者于此当特别“精以察之”。依其“理无朕而气有迹”等观点来看,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奇大升论曰:“盖理无朕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⑤“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以及“非以理气为一物”等观点皆是奇氏理气论的重点所在,必须仔细玩味方能体会出其性理学说之特点。
他与李滉虽然在强调“理”的主宰性和理气不杂性方面取得了共识(二人皆承认理的“实在性”),但是在对理的作用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与奇氏不同,李滉十分重视“理”的能动性和发用性。李滉说过“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①。他还提出“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②的“理帅气卒”论。这是李滉在理气论方面的创见,也是其思想的特色所在。论者将此称为朱学的“死理向活理的转化”③。
在理气观方面奇氏的理论呈现的是“一元论”的倾向,而李滉的学说则体现了鲜明的“二元论”特色。
其次,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问题上,奇大升认为二者是“一本”和“万殊”的关系。奇氏论曰: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愚谓:天地之性,是就天地上总说;气质之性,是从人物禀受上说。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无碍”者乎?④
从援引的朱子语录中可以看出,奇氏实际上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理”与“分殊用之理”的关系。他以“天命之性”为本,而以“气质之性”为末。奇氏还曾引用朱子《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⑤可见,奇大升还将“天命之性”(理)视作“道之体”和“天下之大本”,而且认为天下之道理皆由此出。
但他又说:
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者……若就性上论,则所谓“气质之性”者,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然则论性,而曰“本性”、曰“气禀”云者,非如就天地及人物上,分理、气而各自为一物也,乃以一性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耳。至若论其情,则缘本性堕在气质,然后发而为情,故谓之“兼理气,有善恶”。而其发见之际,自有发于理者,亦有发于气者,虽分别言之,无所不可,而仔细秤停,则亦有似不能无碍。①依奇氏之见,“气质之性”(“万殊”之性)与“天命之性”(“一本”之性)实际上同为一性。之所以有“本性”、“气禀”之说乃因以“一性”之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换句话说,“气质之性”即指此“理”(“天命之性”)堕在气质之中者。“天命之性”要通过“气质之性”来得到具体呈现和实现,所以说在“气质之性”之外“非别有一性也”。
对“天命之性”与“四端”、“七情”的关系,奇大升认为“‘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②。在他看来,“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为“天命之性”、“本然之体”,与“四端”是同实而异名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是气禀物欲之所为,并非是性之本然。
与奇氏不同,李滉却以程朱的“二性说”为理论依据,提出自己的“性”论。“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在李滉看来,思、孟所言“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根据(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李滉主要是基于“四端”与“七情”在“所指”及“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的差别,提出“性”有本性、气禀之异。他坚持“二性论”的立场,强调“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的观点。进而又认为“性”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以分理气而言之。
简言之,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及“一本万殊”的理念主张“一性论”。他重视人的现实之性也就是所谓“气质之性”;与之不同,李滉依据理气二分及理气互发的思想,坚持其“二性论”的观点。
再次,在“四端”与“七情”关系方面,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以及“一性说”之立场,坚持独到的“七包四”(“因说”)的思想。在奇氏性理学的逻辑结构中,“四端”与“七情”是同构性的(“一情”)。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同实而异名”,所以在其看来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并无差异。
奇大升说过:
盖七情亦本善也,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恶矣……盖七情中善者,乃理之发,而与四端同实而异名者也。②
盖性虽本善,而堕于气质,则不无偏胜,故谓之“气质之性”。七情虽兼理、气,而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而易流于恶,故谓之“气之发”也。然其发而中节者,乃发于理,而无不善,则与四端初不异也。但四端只是理之发,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扩而充之,则学者于四端之发,可不体认以扩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气之发,而理之所发,或不能以宰乎气,气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则学者于七情之发,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义各有所以然者,学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则亦可以思过半矣。③
依其之见,七情亦本善,只因兼摄理气加之理弱气强,故易流于恶。但是,奇大升认为七情中善者(发而中节者),与发于理的四端是同实而异名。这里奇氏所提到的“发于理”一词常被视为经与李滉多次辩论后对李氏立场的妥协。其实不然,此处奇大升只是顺着孟子的四端说扩展开来讲而已①,并非向“四七理气互发”说的回归。在其理气论中,理之本体被规定为“气之自然发见”,故其所言“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②。若奇氏“四七”说带有理发论的意味,肯定会遭到后来李珥等人的批判。但是李珥只对李滉的理发论展开批驳,而对奇氏之说则每持接续之姿态。
因此,“四端”与“七情”为“一情”还是“二情”的问题上,奇氏始终坚定地抱持二者为“一情”的立场。奇大升说过:
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③
大升前者妄以鄙见撰说一篇。当时以为子思就情上,以兼理气、有善恶者,而浑沦言之,故谓之“道其全”;孟子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言之,故谓之“剔拨出来”。然则均是情也,而曰“四端”、曰“七情”者,岂非以所就而言之者不同,而实则非有二情也。④
如前所述,奇氏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和四端无别,因而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同具价值之善。在他看来,四端、七情之别就在于“所就而言”之者的不同之故。孟子所谓四端是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剔拨言之,子思所谓七情则是就情上“兼理气、有善恶者(道其全)”浑沦言之——其实人之情是“一”而已矣。“剔拨论”是奇大升在“四七”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理论观点。
李滉则基于其“理气二分”和“二性论”的立场,主张将四端与七情“对举互言”——奇氏将其理气互发说称为“对说”。
李滉在答奇氏对于其“四端七情”论的质疑时,从“所就而言”的视角写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他也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但同时又认为以理气分言“四七”之发的说法前所未见。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来探讨的研究范式始自韩国儒者。依李滉之见,尽管理与气在具体生成事物的过程中“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具有不可分离性,但是不能将四端和七情“滚合为一说”。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应分别以言之。
李滉进而又从“所指”的视角论述道:
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①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认为情之有“四七”之分犹如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他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微妙的关系,以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源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主于理,一主于气。之所以有此分别乃因“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李滉说过:“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②二者各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他主张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这一观点虽经几次修正,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概而言之,在持续8年之久的往复论辩中,因所持的立场角度及所仰重的诠释文本上的差异,③双方始终无法在见解上达成一致。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主张“一性论”和“一情说”,而李滉则依止“理气二分”的思想强调“二性论”和“二情说”。
奇氏以为四端与七情皆可视为情的一种善恶性质,不能将二者看作性质有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情,也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更为贴近朱学原论。但是李滉却从“理气二分”和“尊理”的立场出发,强调二者的异质性亦即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不同。退溪十分关注道德行为的源起,而奇氏则更留意流行层面已发之情的中节问题,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等篇中就多有对中节问题的论述。奇大升和李滉皆为一代儒学名宿,二人的论辩虽未达成共识,却给后人提供了广阔的哲学思辨的空间。
他们所开启的“四七理气”之辨,后为李珥、成浑等人进一步扩展为“四七人心道心”之辨。
李珥曾这样评价奇氏的“四七”理论:“余在江陵,览奇明彦与退溪论四端七情书。退溪则以为‘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明彦则以为四端七情元非二情,七情中之发于理者为四端耳。往复万余言,终不相合。余曰,明彦之论,正合我意。盖性中有仁义礼智信,情中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如斯而已。五常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七情中之不杂人欲,粹然出于天理者,是四端也。”①这表明李珥的思想与奇大升一脉相承,亦持“四端七情非二”之立场。他又提道:“退溪与奇明彦论四七之说,无虑万余言。明彦之论,则分明直截,势如破竹。退溪则辨说虽详,而义理不明,反复咀嚼,卒无的实之滋味。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乎,只是有个才智,偶于此处见得到耳。窃详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为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做出许多葛藤。每读之,未尝不慨叹,以为正见之一累也。”②李珥对“四端七情”之辨中双方的学说皆有透彻之领悟。像“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的说法确为李滉四七论的要害所在。但他却支持奇氏的主张,盖因其追求的“明德之实效,新民之实迹”③的务实精神与高峰之学更为合拍。
由此可见,奇大升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退溪李滉在与其辩论中逐步确立了其“四七理气互发”说的立场,由此奠定了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栗谷李珥则在奇氏与李滉辩论中同情前者之立场,并将之发扬光大以为“气发理乘一途”说,从而奠定了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
第四节 李珥与其“四七人心道心”论
李珥(字叔献,号栗谷、石潭,1536—1584年)出生于江原道江陵北坪村(乌竹轩)外氏第,籍贯为德水,谥号文成,是韩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自幼受母亲师任堂之训导,很早便接触儒家经典。《年谱》中写道:“壬寅二十一年,先生七岁……先生始受学于母夫人,间就外傅,不劳而学日就,至是文理该贯,四书诸经,率皆自通。”①其母申氏,号师任堂,是己卯士祸(1519年)的名贤申命和之女,以诗、书、画三绝而闻名于世。在母亲的良好教育下,李珥从孩提时代起即表现出其超群天资。而其8岁时(在坡州栗谷里花石亭)写下的五言律诗《花石亭》,则至今令人惊叹不已。诗云:
林亭秋已晚,骚客意无穷。
远水连天碧,霜枫向日红。
山吐孤轮月,江含万里风。
塞鸿何处去,声断暮云中。②
这首诗不仅诗句对仗工整,而且其格调浑成,虽深谙诗律者亦有所不及。③尤其是诗中的“山吐孤轮月,江含万里风”一句,很难想象出自8岁孩童之笔。李珥从13岁始在进士初试中状元及第至29岁魁生员及文科前后止,应科举试9次,均已状元及第,故又被称为“九度状元公”。
李珥16岁时其母(师任堂申氏)遽尔逝世,与母亲感情极深的他此时深感人生无常,于是三年后(19岁)脱下孝服后入金刚山摩诃衍道场修行佛法。在一次与老僧的问答中他旋觉佛学之非而决心下山,正式弃佛学儒。次年(20岁)往江陵作了“自警文”11条,第一条即谓:“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则吾事末了。”①李珥年少李滉35岁,明宗十三年(23岁)春拜谒李滉于礼安陶山,并滞留两天向其主动请教了主一无适及应接事务之要,消释了平日积累之疑点,并给李滉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两位大儒的首次晤面,之后李滉在答门人月川赵穆的信中,曾大加赞赏李珥谓:“汉中李生珥自星山来访,关雨留三日乃去。其人明爽,多记览,颇有意于吾学,后生可畏,前圣真不我欺也。”②李珥的《行状》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写道:“二十三岁谒退溪先生于陶山,问主一无适、应接事物之要,厥后往来书札,辩论居敬穷理及庸学辑注,圣学十图等说。退溪多舍旧见而从之,尝致书曰:世间英才何限而不肯存心于古学,如君高才妙年,发轫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千万益以远大自期。”③可见,尽管这是二人初次晤对,但是对彼此的思想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他们通过书信还有过多次相互问学,由此共同开创出韩国性理学自主的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全盛时代。
在韩国哲学史上,李珥与李滉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畿湖地区的学者(指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一带的学者)大都从栗谷李珥之说,称栗谷为“东方之圣人”;岭南地区的学者(庆尚道一带的学者)则大都从退溪李滉之说,称退溪为“东方之朱夫子”。于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性理学派——栗谷学派和退溪学派,两个学派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李珥的“理气之妙”论——与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之比较为中心
以东亚儒学史的视角而观,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6世纪中后叶中韩儒学史上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理论建树和思想影响的鸿儒硕学。如这一时期的明代大儒有罗钦顺(1465—1547年)、湛若水(1466—1560年)、王守仁(1472—1528年)、王廷相(1474—1544年)等;朝鲜朝的名儒则有赵光祖(1482—1519年)、徐敬德(1489—1546年)、李彦迪(1491—1553年)、曹植(1501—1572年)、李滉(1501—1570年)、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珥(1536—1584年)、成浑(1535—1598年)等,皆为称誉于海内外的“杰然之儒”。可见,在东亚儒学史上这是一个名儒辈出、学说纷呈的学术至为兴盛时期。
其中,江右大儒罗钦顺则被称为“朱学后劲”、“宋学中坚”。他的学说中所呈现的新的理论动向不仅影响了其时的明代理学的演进,而且还传至域外影响了韩国性理学和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下面将通过罗钦顺与李珥理气说的比较,来探讨李珥理气论的特色。
李珥之学,正如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年)所言“不由师传,默契道体似濂溪”①。尽管李珥学无定师,但是其立学极重视统合诸流,汇纳各家。故宋时烈又赞其谓:“遂取诸家之说,分析其同异,论正其得失,务得至当之归……其有乐浑全而恶分析,则先生(指李珥——引者注)必辩其同异于毫厘之间,其有逐末流而昧本源,则先生必一其宗元于统会之极。”②
虽然李珥生活的年代是在“破邪显正”的幌子下,对除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学派均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的时代,但他并不盲从朱子,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和自主精神。针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之说,李珥曾言道:“若朱子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何以为朱子乎?”③这种为学上的自主和批判精神,使其能够对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各家学说加以吸收和借鉴,构筑以理气“不离”之义为特色的独特性理哲学体系。
在与其同时代的中韩诸儒中,李珥唯独对罗钦顺非常赞赏,曰:“罗整庵识见高明,近代杰然之儒也。有见于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见。此则虽不识朱子,而却于大本上有见矣。”④表明李珥认为罗钦顺对朱学之大本,即对朱学的要领是有真切之体会。于是,将整庵罗钦顺与退溪李滉、花潭徐敬德做比较时,亦将其推为最高。曰:“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①李滉和徐敬德是与李珥同朝的另外两位大儒,在韩国哲学史上均具有重要影响。而李珥最为称赞罗钦顺的原因在于,较之李滉和徐敬德,罗钦顺不仅有见于朱学之大本,且多有自得之味。
同时,他还将罗钦顺学说同薛瑄(1389—1465年)、王守仁(1472—1529年)之学亦做过比较,曰:“罗钦顺拔萃人物,自所见少差;薛瑄虽无自见处,自可谓贤者也;王守仁则以谓朱子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之祸,其学可知。”②此处李珥对薛瑄的评价同罗钦顺对薛氏的评价内容亦大体相似,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曾写道:“薛文清学识纯正,践履笃实,出处进退,惟义之安。其言虽间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见有能及之者,可谓君子儒矣。”③由此可见,《困知记》一书对李珥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困知记》何时传入韩国,学界尚无定论。④但是该书传入韩国后,在16世纪朝鲜朝儒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少学者撰文对之加以评说。⑤其中代表性论者有:卢守慎(字寡悔,号苏斋,1512—1590年)、李滉、奇大升、李珥等人。
不过,与罗钦顺相比李珥为学则更具开放性。比如对其时盛行于明代思想界的阳明心学李珥也并未一概排斥,而主张应“取其功而略其过”,认为这才是“忠厚之道”。⑥这显然与罗钦顺对待心学之立场差异较大。
前已言及,李珥的性理学是在对各家理论的批判、撷取中形成。其中,直接影响其理气学说形成的有三家理论——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李滉的“理气二元”论、徐敬德的“气一元”论。李珥曾对此三家学说做过详细的评论,曰:
整庵则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气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以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退溪则深信朱子,深求其意。而气质精详慎密,用功亦深。其于朱子之意,不可谓不契,其于全体,不可谓无见,而若豁然贯通处,则犹有所未至,故见有未莹,言或微差。理气互发,理发气随之说,反为知见之累耳。花潭则聪明过人,而厚重不足。其读书穷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聪明过人,故见之不难;厚重不足,故得少为足。其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了然目见,非他人读书依样之比,故便为至乐。以为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气局一节。继善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理无变而气有变,元气生生不息,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在。而花潭则以为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此花潭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虽然偏全闲,花潭是自得之见也。今之学者开口便说理无形而气有形,理气决非一物。此非自言也,传人之言也。何足以敌花潭之口而服花潭之心哉。惟退溪攻破之说,深中其病,可以救后学之误见也。盖退溪多依样之味,故其言拘而谨;花潭多自得之味,故其言乐而放。谨故少失,放故多失。①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尽管李珥为学极重“自得之味”,但是在为学性格上他仍坚守朱学的立场。故他强调,“宁为退溪之依样,不必效花潭之自得”②。二是,他认为罗钦顺气质英迈超卓故能望见朱学之全体,但是又因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故其言论确有“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李珥以为理气实际上“非为一物”,而是“一而二、二而一”妙合关系。三是,李滉能深信朱子,气质亦精详慎密,故对于朱子之意,不可谓不契。但是因于豁然贯通处有所未至,故其所见亦有未尽莹者。这里主要是指,他与李滉在理气之发问题上的分歧。在此一涉及朝鲜朝性理学的核心论题的见解上,李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而是主张颇有“主气”意味的“气发理乘一途说”。四是,李珥尽管对徐敬德“理不先于气”思想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于理气不相离之妙有了然目见”,但是同时指出徐敬德之说有“认气为理之病”。李珥以为,继善成性之“理”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故主张“一气长存”之上则更有“理通气局”一节。
由此亦可概见李珥在理气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即“一而二、二而一”的“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一途”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等。其实李珥正是用这些学说来试图解答,朱学的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基本理论问题。其中,“理气之妙”思想既是李珥性理学的根本立场,亦是理解其性理哲学的理论要害。
要之,从李珥对罗钦顺的肯定以及对其学说的重视中可以看出,罗钦顺理气说是影响李珥理气思想形成的主要理论之一。
朱子学演进至罗钦顺,较之原来的理论发生了明显改变。首先是在理气观方面与朱熹的学说产生了较大差异。从理学史角度来看,明中叶的朱学呈现出从“理本”向“气本”发展的趋向。无疑,罗钦顺是在这一理学发展转向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
理学从二程开始,在哲学的宇宙论上,把“理”作为宇宙的普遍原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是气的存在、运动的“所以然”。朱熹继承并发展这一思想,建构了以理气二分、理气“不离不杂”①为特色的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朱熹以为,“理”是不杂而又不离于气的形上实体,强调“理”作为气之所以然而具有的实体性和主宰性。这一思想在朱子后学中受到不少怀疑,罗钦顺便是对此提出异议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罗钦顺对朱熹理气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理气二分思想上。他在《困知记》一书中,写道: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①
周子《太极图说》篇首无极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释,可无疑矣。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愚也积数十年潜玩之功,至今未敢以为然也。尝考朱子之言有云“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若然,则所谓太极者,又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邪?惜乎,当时未有以此说叩之者。姑记于此,以俟后世之朱子云。②
此处所引两段引文是在其《困知记》中质疑朱熹理气二分说的主要段落。同时,从此段引文中亦可概见罗钦顺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首先在对于“气”的理解上,罗钦顺明确指出“气”才是宇宙的根本存在,故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虽然朱熹亦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的物质形态,但是罗钦顺的主张已明显呈现出由“理本”转向“气本”的趋向。其次在对于“理”的理解上,罗钦顺则明确反对“理”在朱熹学说中具有的“实体性”、“主宰性”。依罗钦顺之见,“理”即是所谓“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亦即事物自身中的“自然之机”和“不宰之宰”。
由此罗钦顺提出“理即气之理”的主张,他说:“吾夫子赞《易》,千言万语只是发明此理,始终未尝及气字,非遗之也,理即气之理也。”①
进而在理气为“一物”还是“二物”的问题上,他则断言“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②。以为,理是气之运动的内在根据和法则,并不像朱熹所说的是依附于气的另一实体(物)。尽管坚守“认理气为一物”的立场,但是他同时又明确表示学者亦不能将“气”认为“理”。他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③表明,罗钦顺是反对将理气视为二元对待的两个实体,实体只是气,而“理”只是这一实体的自身的规定。即,这一实体固有的属性或条理。
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以及“理须就气上认取”思想既是罗钦顺理气论的核心要义,亦是其理气说“最为难言”的地方。对此,他也曾坦言道:“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默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④
罗钦顺自谓其理气不二之说并非为“臆决”,而是由宗述明道而来。他说:“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明道尝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于‘原来只此是道’一语,则理气浑然,更无隙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晦翁先生……谓‘是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乃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良由将理气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终不能定于一也。”①可见,罗钦顺对程明道学说是极为推崇。尤其是,程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和“原来只此是道”思想是罗钦顺理气浑然一体说的立论根据。若以此来衡量伊川、朱子理气说,皆有析理气为二物之嫌。此外,二程的“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②和“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③等思想,亦是罗钦顺构筑其理气说的主要理论来源。
李珥对明道的思想亦极为重视,这一点与罗钦顺相似。而且,在李珥和罗钦顺著述中所引用的二程言论大都为明道之说。宣祖五年(李珥37岁),李珥与好友成浑(字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进行理气心性问题的论辩时,曾系统阐述自己的理气观。论辩中,他还对成浑言道:“兄若不信珥言,则更以近思录、定性书及生之谓性一段,反复详玩,则庶乎有以见之矣。”④表明《近思录》及明道的《定性书》、《生之谓性章》等是李珥性理学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尤其是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的思想亦是李珥理气说的立论根据。他说:“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此言理气之不能相离。”⑤李珥的理气观,正是以理气之不相离为其理论前提。
前已述及,李珥对罗钦顺十分赞赏,称其为“拔萃人物,自所见少差”。首先,在强调理气之不相离的意义上,李珥与罗钦顺持相同的立场。他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气不离理,理不离气,夫如是则理气一也。何处见其有异耶?所谓理自理,气自气,何处见其理自理,气自气耶?望吾兄精思著一转,欲验识见之所至也。”①这是李珥答成浑信中的一段话。李珥发挥明道之理气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告诫成浑理气不相离之妙须通过精思与证会方能真正体会。其次,在强调理气之不相杂的意义上,李珥与罗钦顺则明显有差异。在李珥的理气说中,理作为气之根柢及造化之根源在理气关系中被赋予主宰义,具有重要地位。如,李珥曰:“夫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②,“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③。可见,在理的规定上李珥与罗钦顺是有区别的。其实,这便是李珥称罗钦顺为“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及“气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李珥性理学说与朱学的传承关系。较之罗钦顺,李珥在强调理气之不相离的同时,亦强调二者之不相杂。他认为理气关系是“既非二物,又非一物”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他说:“一理浑成,二气流行,天地之大,事物之变,莫非理气之妙用也。”④这就是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也是其整个性理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那么,何谓“既非二物,又非一物”呢?李珥对此解释道:“非一物者,何谓也?理气虽相离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谓也?虽曰理自理,气自气,而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不见其为二物,故非二物也。”⑤理气一方面妙合之中互不相杂,理自理,气自气,故非为“一物”;另一方面二者又浑然无间,无先后,无离合,故亦非为“二物”。前者所强调的是理气二者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后者所强调的是在现实的意义上二者所具有的共时性、共存性。
接着李珥总结明道与朱子的理气关系论述,指出:
考诸前训,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气浑然无间,元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虽不相离而浑然之中实不相杂,不可指为一物。故朱子曰: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合二说而玩索,则理气之妙,庶乎见之矣。①
以上引文中,亦可概见李珥为学上的特点。即,注重对各家学说的融会贯通。因理与气是相互渗透、相互蕴涵的关系,故不可指为“二物”;但二者是妙合之中,又各自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性,故又不可指为“一物”。此种“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思维模式,正好反映了李珥独特的哲学思维方法。
李珥性理学中的最为紧要处,便是其“理气之妙”说。对此,他亦曾言道:“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②尽管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李珥却对此说颇为自信。他在给成浑的一封复信中,写道:“珥则十年前已窥此端,而厥后渐渐思绎,每读经传,辄取以相准,当初中有不合之时,厥后渐合,以至今日,则融会吻合,决然无疑。千百雄辩之口,终不可以回鄙见。”③表明,通过其多年努力而体贴到的理气之妙合关系,李珥已完全确信无疑。
于是,李珥从其“理气之妙”思想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理气动静说。他指出:“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④此即李珥所谓的“气发理乘”说。他对此二十三字所言之内容,极为肯定。简言之,所谓“气发理乘”是指,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气化流行)时理乘之而无所不在的存有形态。李珥此说,既是对李滉“理气互发”说的批判,亦是对朱子理气说的进一步继承与阐发。
理发气发问题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此论与“四端七情”之辨相关联,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理论特色。
李珥在与成浑(成浑基本上持李滉的立场)的四端七情论辩中,还系统阐发了其“气发理乘”思想。曰:
气发而理乘者,何谓也?阴静阳动,机自尔也,非有使之者也。阳之动则理乘于动,非理动也;阴之静则理乘于静,非理静也。故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阴静阳动,其机自尔,而其所以阴静阳动者,理也。故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夫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者,原其本然而言也;动静所乘之机者,见其已然而言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理气之流行皆已然而已,安有未然之时乎?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理乘之也。所谓气发理乘者,非气先于理也,气有为而理无为,则其言不得不尔也。①
李珥的“气发理乘”说是以理气“元不相离”为其立论前提,加之在其哲学中“气”具有形、有为之特性而“理”却无之,故“理”不能以动静言。依他之见,理之所以流行,是乘气之流行而流行,理之有“万殊”,亦因气之流行所致。不但天地之化是如此,而且人心之发亦不外乎此。发之者是其然,是表现者;所以发者是所以然,是使表现者得以实现的主宰者。
而且,同成浑的往复论辩中,李珥则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指出:“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②文中,李珥不仅指责李滉未能正确理会朱子之意,而且还主张不仅七情是气发而理乘,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
进而,他又以“理气之妙”论为基础推出自己在理气同异思想,即“理通气局”说。那么,何谓“理之通”、“气之局”呢?李珥解释曰:
理气元不相离,似是一物,而其所以异者,理无形也,气有形也;理无为也,气有为也。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理通者何谓也?理者,无本末也,无先后也。无本末、无先后,故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是故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而其本然之妙无乎不在。气之偏则理亦偏,而所偏非理也,气也。气之全则理亦全,而所全非理也,气也。至于清浊、粹驳、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中,理无所不在各为其性,而其本然之妙则不害其自若也。此之谓理之通。气局者何谓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气之本则湛一清虚而已曷。尝有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气哉?惟其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故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于是气之流行也,有不失其本然者,有失其本然者。既失其本然,则气之本然者已无所在,偏者偏气也,非全气也;清者清气也,非浊气也;糟粕煨烬,糟粕煨烬之气也;非湛一清虚之气也。非若理之于万物本然之妙,无乎不在也。此所谓气之局也。①此段引文集中反映了李珥理气说之基本要义。文中可以看出,他从理气关系和理气之特性着手,论述了“理通气局”、“气发理乘”及“理之偏全”等问题,阐明了其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要之,所谓“理通”,是指“理同(同一理)”;“气局”,则指“气异(各一气)”。②对于“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李珥自诩为“理通气局四字,自谓见得,而又恐读书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见之也”③。此说尽管亦受程朱的“理一分殊”、“理气同异”及佛教华严宗的“理事通局”说的影响,但是仅就以通局范畴表述理气之异而言确为李珥独见。而且,在他的性理哲学逻辑结构中“理通气局”与“气发理乘”说,作为说明人物性同异与性情善恶的重要命题互为对待、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了其“四七人道”说的立论基础。
概言之,通过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与李珥“理气之妙”说的比较,可以看出16世纪中韩朱子学的不同发展面向。罗钦顺从去“理”的实体化、主宰义入手,将“理”视为“气”所固有的属性或条理,反对将理气视为二元对待的两个实体,明显表现出由“理本”向“气本”的转向。而,李珥虽然与罗钦顺同尊明道,但是仍表现出坚守朱学之为学性格,提出理气“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颇具特色的“理气之妙”说,对明道和朱熹思想作了有益的阐发。李珥和罗钦顺的理气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朱熹的理气学说,而且也为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
二、李珥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与成浑“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
通过对李滉、奇大升等人的“四七”论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四端七情问题其实讨论的是“性”与“情”关系问题,因此顺四端七情理气问题便可以引出有关性情善恶及人心道心问题的论议。而栗谷李珥和牛溪成浑之间围绕人心道心问题展开的第二次“四七”之论争,便是四七理气问题在更深一层意义上的,即性情层面上的展开。在韩国哲学史上李珥和成浑之间发生的第二次“四七理气”之辨,既丰富了原有的四七理气理论之意涵,又开启了对性情善恶与人心道心关系问题的新的理论探索,将“四七”论引向了新的问题域。下面,将以李珥与成浑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探讨“四七”论进一步发展之状况。
成浑(字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昌宁人,谥号文简,朝鲜朝著名性理学家。成浑幼承庭训,学业大进,15岁便博通经史文辞,为人们所叹服。其父成守琛曾受学于赵光祖,成浑则尊幕李滉且多从其说。他与李珥交情甚笃,二人围绕“四七问题”进行了长达6年的书函往复,①继“退、高之辩”之后将此一论辩又推向了高潮。
成浑的“四七”论和“人心道心”说的主要理论观点,大都集中在与李珥的往复论辩第一书和第二书。在致李珥的信中,成浑写道:“今看十图《心性情图》,退翁立论,则中间一端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云。究此议论,以理、气之发,当初皆无不善,而气之不中,乃流于恶云矣。人心道心之说,既如彼其分理、气之发,而从古圣贤皆宗之,则退翁之论,自不为过耶?”①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成浑是大抵接受李滉的立场,也认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基于此,成浑以为理发则为道心,而气发则为人心。
进而,他又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二名,何欤?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理、气之发不同,而危、微之用各异,故名不能不二也。然则与所谓“四端、七情”者同耶?今以道心谓之四端,可矣;而以人心谓之七情,则不可矣。且夫四端、七情,以发于性者而言也;人心、道心,以发于心者而言也。其名目意味之间,有些不同焉。幸赐一言,发其直指,何如?人心、道心之发,其所从来,固有主气、主理之不同,在唐虞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说,圣贤宗旨,皆作两下说,则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然“气随之”、“理乘之”之说,正自拖引太长,似失于名理也。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为性情之图,则不当分开,但以四、七俱置情圈中,而曰“四端,指七情中理一边发者而言也:七情不中节,是气之过不及而流于恶”云云,则不混于理、气之发,而亦无分开二歧之患否耶?并乞详究示喻。②
文中成浑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具体看法。首先,援引朱子《中庸章句》中的或生、或原说法,主张人心、道心二者是理气之发不同、危微之用各异;其次,在四端七情与人心道心的关系上,以为道心可视为四端,但是人心不可视为七情。而且又从“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之向度,称“其名目意味之间,有些不同”;再次,他从二者的“所从来”意义上,主张人心、道心亦可以主理、主气言之。这是接续李滉的说法而来,李滉曾主张四端与道心是“理之发”,七情与人心为“气之发”。但是,成浑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中的“气随之”和“理乘之”说法却表示疑义。而且,在四七关系上也表现出对“七包四”逻辑(在未发意义上)的认可倾向。
简言之,成浑则主要是站在李滉的立场,对李珥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依他之见,理与气之互发是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并向李珥提出质疑道:自己也曾对退翁的“理气互发”说存疑,但细心玩味朱子关于“人心道心之异,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之说,觉得退溪的互发说亦未尝不可。他说:“顷日读朱子人心道心之说,有或生,或原之论,似与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为在虞舜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理气互发之说,则退翁之见不易论也。”①所谓“或生”与“或原”,指朱熹所说的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言。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纯善无恶;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故有善有恶。可见,成氏明显倾向于肯定“理气互发”说。
在与李珥的论辩中,成浑也试图以“理气互发”和人心、道心相互对待逻辑为基础,来阐释四端与七情、人心与道心的善恶问题,这是其性理学的特点。成浑的主要著作有《朱门旨诀》、《为学之方》、《牛溪集》(12卷)等。
下面一段文字是成浑对李珥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的质疑,曰:
吾兄(指李珥——引者注)前后勤喻,只曰:性情之间,有气发理乘一途而已,此外非有他事也。浑承是语,岂不欲受用,以为简便易晓之学?而参以圣贤前言,皆立两边说,无有如高诲者,故不敢从也。昨赐长书中有曰:“出门之时,或有马从人意而出者,或有人信马足而出者。马从人意而出者,属之人,乃道心也;人信马足而出者,属之马,乃人心也。”又曰:“圣人不能无人心,譬如马虽极驯,岂无或有人信马足而出门之时乎?”浑究此数段,皆下两边说,颇讶其与“只有一边,气发理乘”之语稍异,而渐近于古说也。又读今书,有曰:“发道心者,气也,而非性命,则道心不发。原人心者,性也,而非形气,则人心不发。以道心原于性命,以人心生于形气,岂不顺乎?”浑见此一段,与之意合,而叹其下语之精当也。虽然,于此亦有究极之未竟者焉。吾兄必曰:气发理乘,无他途也;浑则必曰:其未发也,虽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才发之际,意欲之动,当有主理、主气之可言也,非各出也,就一途而取其重而言也。此即退溪互发之意也,即吾兄“马随人意,人信马足”之说也,即“非性命则道心不发,非形气则人心不发”之言也。未知以为如何?如何?此处极可分辨,毫分缕析,以极其归趣而示之,千万至祝!于此终不合,则终不合矣。虽然,退溪互发之说,知道者见之,犹忧其错会;不知者读之,则其误人不少矣。况四七、理气之分位,两发、随乘之分段,言意不顺,名理未稳,此浑之所以不喜者也……情之发处,有主理、主气两个意思,分明是如此,则“马随人意,人信马足”之说也,非未发之前有两个意思也。于才发之际,有原于理、生于气者耳,非理发而气随其后,气发而理乘其第二也,乃理气一发,而人就其重处言之,谓之主理、主气也。①
文中成浑认为,衡之于圣贤前言,皆为立两边说,未曾有如李珥的一途论之说,并以人乘马之喻为其论说。这里他所指的圣贤应为,朱熹、陈淳等人。成浑的学说受朱、陈二人之影响也较大②,而且朱熹和陈淳的思想亦是其立论根据之一。具体而言,成浑的主张是心未发之时不能将四端与七情分别对待之,此时二者应为“混沦一体”之状态(可视为“七包四”)。已发之时才可以分别四端与七情,即发于理的为四端、道心;发于气的为七情、人心。这里亦可以看到他与李珥的细微差异,成浑不同意未发之时的“所从来”意义上的四七分别。依他之见,主理、主气是“才发之际”,即意欲动之时取其重而言之者。因此在这意义上,未发之时成浑对四七结构所持的立场又有与奇大升、李珥的“七包四”逻辑有相似的一面,表现出他的学说的折中性格。因此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他也提出折中李滉与奇大升等人主张的“理气一发”说。
针对成浑的质疑,李珥也以朱学理论为据,阐述了自己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他说:“‘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与‘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通贯。吾兄尚于此处未透,故犹于退溪‘理气互发、内出外感、先有两个意思’之说,未能尽舍,而反欲援退溪此说,附于珥说耳。别幅议论颇详,犹恐兄未能涣然释然也。盖‘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推本之论也;‘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沿流之论也。今兄曰‘其未发也,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此则合于鄙见矣。但谓‘性情之间,元有理、气两物,各自出来’,则此非但言语之失,实是所见差误也。”①李珥此处论述极为明快,他认为所谓“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或原或生”与“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以通贯。成浑对此有疑问,主要是对理气问题有所未透。于是李珥从理气论与性情说之间的相一致性出发,对“四七人心道心”论作了阐明。曰:“理气之说与人心道心之说,皆是一贯。若人心道心未透,则是与理气未透也。理气之不相离者若已灼见,则人心道心之无二原,可以推此而知之耳。”②由此可以看出,李珥的理气论(“理气之妙”说)是其心性论的立论根基,人道说是其理气论的直接生发。因理气之“不离”义是其理气论的主要理论倾向,因此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他也以二者的不可分和相联结为其主旨,强调人心道心的“无二原”性。这与李滉、成浑的基于二者不同价值意义上的人心道心相分思想是有明显区别的。
进而李珥阐发了自己的四七人道说。首先,从“主乎理”、“主乎气”的向度,对人心道心的含义作了论述。曰:“夫人也,禀天地之帅以为性,分天地之塞以为形,故吾心之用即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无二本,故吾心之发无二原矣。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复礼,欲穷理,欲忠信,欲孝于其亲……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因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掩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渴欲饮……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人心。其虽本于天性,而其发由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达,造次难见,故曰‘微’。人心之发,如鹰解鞲,如马脱羁,飞腾难制,故曰‘危’。”①依李珥之见,因外感者(感动者)是形气,故感动之际被何方为所主宰,显得十分紧要。“主乎理”的道心,是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又不为形气所掩蔽者;而“主乎气”的人心,则是出于耳目四肢之私,未直出于理之本然者。以“主乎理”、“主乎气”视角,探讨人心道心之含义,这一点颇能反映韩国儒学在讨论人间和存在的所以然根据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时,往往落实到性理层面上展开理气这个形上、形下问题的理论特性。②重视人间性理,是韩国儒学的根本特征。
其次,李珥从“心是气”的意义上,以知觉论的立场回答了“一心”何以有“二名”,即有人心道心之分的问题。
在李珥哲学中“心”属于气、属于已发,曰:“且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发而性不发之理,则岂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气之所重而言也,非当初有理、气二苗脉也。”③故不管人心还是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规定使其人心道心说具有了知觉论特色。对“一心”何以有“二名”,他有以下几段论述。他说:
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①
心一也,岂有二乎?特以所主而发者有二名。②
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一心。其发也或以理义或为食色,故随
其所发而异其名。③“心”只有一个,这与朱子的主张相同。但是在“一心”何以有“二名”的问题上,李珥所持的诠释立场与朱子不同。这源于李珥独特的性情论义理架构。众所周知,朱子的性理学说以“理气二分”、“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而李珥则以“理气之妙”,心、性、情、意四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因此朱子的性情论可以“心统性情”说来概称,而李珥的性情论则似以“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来指代更为恰当。此处,紧要处为二人对“意”概念的不同界定。在朱子性情论中,“意”和“情”都是从属于“心”的概念。“情”和“意”二者关系是,大抵“情”是性之动,“意”是心之所发;“情”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④因此在朱子心性论中,“意”的思量运用之意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在李珥哲学中,“意”和“情”是两个有明确规定的并列关系的哲学范畴,李珥曰:“意者,心有计较之谓也。情既发而商量运用者也……发出底是情,商量底是意。”⑤“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⑥“情”和“意”皆属于心之已发,而且还是心的两个不同境界。曰:“因所感而紬绎商量意境界”⑦,李珥提出其独特的“意境界”论。
故其人心、道心论是兼情、意而言,如其曰:“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⑧需注意的是,“意”其实是在其人心道心说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范畴。这既是李珥与朱子性情论之区别,亦是其对朱子心、性、情、意说的发展。相较而言,李珥的心性学说确实比朱子的理论更为细密和清晰。而且,强调“意”的商量计较作用是李珥知觉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基于“意之商量计较”意涵,李珥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终始”说。他说: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①不管根于性命之正的道心,还是源于形气的人心,皆属已发,此时气已用事。若欲不咈乎正理如实呈现,或知非制伏不从其欲,都要借“意”之计较、思虑、商量作用来实现。因此李珥认为,在人心之方寸之间,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可变状态。在已发层面上,二者是并无固定的、严格的分别。因此,李珥为学极重“诚意”,他以为“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时,“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②。指出,若能保证“意”之“诚”,则所发之“心”皆能呈现为道心。
再次,李珥还援引“四七”论、“理欲”论上的说法,进一步论述了其对人心道心问题及二者关系问题的认识。
前已论及,“四端七情”论是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重要学说,人心道心论争的发生其实就是“四七”论由“情”论层面向“心”论层面的进一步推进,即“四七”论在心性领域的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展开。
因为在李珥性理哲学中,“意”具有商量计较作用,故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相互转换之状态。这与其“四七”论中,七情兼四端的情形有所不同,对此差异李珥指出:“圣贤之说,或横或竖,各有所指,欲以竖准横,以横合竖,则或失其旨矣。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①可见,李珥对四端与七情的基本认识是,“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故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基于其“七包四”一元思维,他又对“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李珥谓:
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者,何谓也?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闲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也,乌可强就而相准耶?今欲两边说下,则当遵人心、道心之说;欲说善一边,则当遵四端之说:欲兼善恶说,则当遵七情之说,不必将柄就凿,纷纷立论也。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也;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故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朱子所谓“发于理”、“发于气”者,只是大纲说,岂料后人之分开太甚乎!学者活看可也。且退溪先生既以善归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若然,则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从何而发哉?孟子举其大概,故只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为四端,则学者当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于仁义礼智而为善者乎?此一段当深究精思。善情既有四端,而又于四端之外有善情,则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盛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矣。别纸之说,大概得之。但所谓“四、七发于性,人心、道心发于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则心中之理也,心则盛贮性之器也,安有发于性、发于心之别乎?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①
本段引文较长,但是此段内容则是李珥对四七人心道心问题的最为系统之论述。如其文中言的“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也”中可以看出,在李珥哲学中“情”不具商量计较之义,故性发为情之际,七情可以兼四端。因为依他之见,“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但是,人心、道心则已达比较、商量之地步,已具对比之意,故不能兼有,只能互为终始,这便是其“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
因为人心与道心是基于“意”之商量计较而存在的相对之物,李珥又由“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而提出“人心道心相对”说。他说:“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②
此论看似与其“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矛盾,但是这是李珥从天理人欲论角度对人道说的解读,可视为对人道终始说的另一种阐发。他说:“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③可见,李珥对道心、人心、人欲是有区分,而且也肯定人心亦有善。在此李珥所持的是朱子的立场。但是,人心之善与道心是否为同质之善呢?
对此,李珥在《人心道心图说》中写道:“孟子就七情中别出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①可见,他是把二者视为同质之善。在“理欲”论意义上,其人道说比朱子的人道说显得更为紧张和严峻,颇似“天理人欲相对”说。这也是二人人心道心之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李珥还从理欲之辨角度,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论辩的结束阶段,李珥写了首五言律诗(《理气咏》)致成浑,以阐明其理气哲学主旨。诗云:
元气何端始,无形在有形。
穷源知本合,沿派见群精。
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
二歧君莫惑,默验性为情。②这首理语诗中李珥又夹注,曰:“理、气本合也,非有始合之时。欲以理、气二之者,皆非知道者也……理、气原一,而分为二五之精……理之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者如此。空瓶之说,出于释氏,而其譬喻亲切,故用之。”③十分形象地从本体和流行的视角,再一次强调了其“理气之妙”和“气发理乘”思想。
成浑与李珥年龄相仿,李珥19岁时二人便定交。《年谱》记云:“成先生长于先生(指李珥——引者注)一岁,而初欲师事之,先生辞焉。遂定道义之交,相期以圣贤事业终始无替。”④李珥卒后,成浑曾评其道:“栗谷尽是五百年间气也。余少时讲论,自以为朋友相抗。到老思之,则真我师也,启我者甚多。”⑤李珥37岁(成浑时年38岁)时二人围绕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及理气之发问题展开了长达6年的辩论,尽管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但是成浑对李珥的崇敬之情从其评语中以见一斑。
在朝鲜朝儒学史上由李珥和成浑之间进行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是,继“四端七情”之辨之后发生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又一学术论争。
三、李珥“四七人心道心”论的特色
李珥的“四七人道”说特色主要表现在,其“四七理气”说和心性情意论方面。
李珥的“四七理气”论是在与成浑的相互论辩和与李滉的相互问学中形成。李滉在“四七理气”论方面的基本说法是,“四七理气互发”说。成浑大抵接受李滉此一立场。
李滉曾曰:“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此论便是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此一理论的性情论基础是,“二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二情”(四端/七情)论。由此自然可以推导出,对举分别而言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论,即主理、主气之说。
李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基于其理气“一而二、二而一”思路以为,子思、孟子所言的本然之性和程子、张子所言的气质之性,其实皆为“一性”,只是所主而言者不同而已。曰:
性者,理、气之合也。盖理在气中,然后为性。若不在形质之中,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也。但就形质中单指其理而言之,则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不可杂以气也。子思、孟子言其本然之性,程子、张子言其气质之性,其实一性,而所主而言者不同。今不知其所主之意,遂以为二性,则可谓知理乎?性既一,而乃以为情有理发、气发之殊,则可谓知性乎?①可见,李珥不仅主张性为理气之合,而且还明确区分“性”与“理”概念的不同用法。这既是李珥逻辑思维细密、精微之处,也是其“四七”论的独到之处。进而他指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其实是“一性”。这里还可以看出,他的“性”论又与奇大升的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依他之见,若不知其所主之意而视其为“二性”,可谓之味于“理”者。而在“性既一”之情形下,仍主情有理发、气发之殊的话,则又可谓之味于“性”者。
李珥也认为,理为形而上者也,气为形而下者也。不过,他特别强调二者的不能相离性。因此在他而观,二者既不能相离,则其发用也只能是“一”,不可谓互有发用。曰:
若曰互有发用,则是理发用时,气或有所不及;气发用时,理或有所不及也。如是,则理气有离合,有先后,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其错不小矣。但理无为,而气有为,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于形气者,属之理;当初虽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属之气,此亦不得已之论也。人性之本善者,理也,而非气则理不发。人心、道心,夫孰非原于理乎?非未发之时,亦有人心苗脉,与理相对于方寸中也。源一而流二,朱子岂不知之乎?特立言晓人,各有所主耳。程子曰:“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夫善、恶判然二物,而尚无相对各自出来之理,况理、气之混沦不离者,乃有相对互发之理乎?若朱子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何以为朱子乎?②
在李珥看来,承认“理气互发”说不仅等于承认理气有缝隙、有离合,而且还承认理气有先后、动静有终始。朱熹的“理气不杂”、“理气为二”思想,明初便遭到曹端、薛瑄、胡居仁等人的批评,他们依据程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理论,主张理在气中,坚持理气无间一体思想,反对把二者对立、割裂。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说,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理论。罗氏的《困知记》对朝鲜朝性理学及李珥“理气之妙”说的影响前文已多次论及,李珥也受此理论思潮之影响力主“理气非二”论。故他以为,四端与七情之说是朱子“特立言晓人,各有所主”而已。这与奇大升的所言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的思想并无二致。依李珥之见,若是朱子也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
于是,他进而指出:
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阴阳动静,而太极乘之,此则非有先后之可言也。②
在此李珥对朱子的“四七”论作了己之阐发的同时,指出李滉的错误在于只认同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他坚持,不仅四端是“气发而理乘”,七情亦是“气发而理乘”。对于李珥和李滉的“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陈来先生认为,二者并不相同。他指出:李滉所说的气发是发自于形气,而李珥所说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李珥进一步说的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这是气,就是气发,而理乘载其上。由于李珥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故把恻隐说成气,说成气发,这种说法与王阳明接近,容易引出“心即气”的主张,是与朱子和李滉不同的。李珥认为,气和理的这种动载关系是普遍的,不限于四端七情,整个天地之化都是如此。③陈先生的这一论述,对于二人的理气之发说的理解及理气论差异问题的探讨颇有裨益。
要之,“性”与“理”概念的区分,“一性”、“一情”论的强调以及“七包四”立场的坚守,是李珥“四七理气”论的主要特色。
那么,李珥和李滉的“气发而理乘”思想为什么会有理论差异呢?这源于李珥独特的心性情意论。
在李珥的心性情意论逻辑结构中,“心”处于十分重要之地位,他认为,就人之一身来说心“合性与气”,而有“主宰”于身之作用。他说:
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谓之心。心应事物而发于外者,谓之情。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未发已发之总名……性之目有五,曰仁义礼智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之发也,有为道义而发者。如欲孝其亲,欲忠其君,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非议而羞恶,过宗庙而恭敬之类是也,此则谓之道心。有为口体而发者,如饥欲食、寒欲衣、劳欲休、精盛思室之类是也,此则谓之人心。①
文中李珥对“性”、“情”、“心”、“道心”、“人心”等作了明确之界定。此说与朱子的“心为主宰”的思想和李滉的“心兼理气”、“理气合而为心”②说法皆也有所不同。因为在李滉的性理哲学体系中理具发用性和能动性,故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而在心、身的关系上,李珥也强调心的优位性,比朱子更加明确指出心对身的主宰作用,言道:“心为身主,身为心器,主正则器当正。”③而且,在李珥性理哲学中心属于气,属于已发,故“心”在其性情论中是被探讨的主要对象。
对于“心”、“性”、“情”概念及相互关系,李滉则界定为: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表明,李滉的心论结构大体延续的是朱熹的“心统性情”思路。但是,有别于朱熹的是,他的这一思想突出了理对于心之“灵”的作用,着重于解决心的知觉作用问题。
基于心之作用的独特认识,李珥又提出“心为性、情、意之主”的思想。他言道:
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盛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矣。别纸之说,大概得之。但所谓“四、七发于性,人心、道心发于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则心中之理也,心则盛贮性之器也,安有发于性、发于心之别乎?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①
李珥主张“心为性、情、意之主”,故以为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需注意的是,李珥对“性”概念的界定,曰:“性者,理、气之合也。盖理在气中,然后为性。”②其实,他所言之性为“气质之性”。“心是气”,因此性、情、意皆可谓之心。但是,性和情不具计较商量义,故“意”之作用又显得十分重要。“意”不仅在其“四七人道”说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其修养论亦具有重要意义,故其曰“自修莫先于诚意”。进而,李珥还提出“人心、道心皆发于性”的主张,此说与朱熹和李滉的思想相比区别较大。
李珥心性情论中最为独特的思想为,其“性心情意一路而各有境界”论。他说:
子固历见余谈话,从容语及心性情。余曰,公于此三字,将一一理会否。子固曰,未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云者,殊未晓得。余曰,公于此难晓,则庶几有见于心性情矣。先儒此说,意有所在,非直论心性。而今之学者为此说所误,分心性为有二用,情意为有二歧,余甚苦之。今公自谓于此有疑,则庶几有真知矣。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矣。岂不大差乎?须知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然后可谓不差矣。何谓一路?心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发后商量为意,此一路也。何谓各有境界?心之寂然不动时是性境界,感而遂通时是情境界,因所感而紬绎商量为意境界,只是一心各有境界。①
在心性情论方面,李珥一贯反对“分心性为有二用,情意为有二歧”。因为依他之见,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由此他提出“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思想。如前所述,李珥的性情论为心性情意四分逻辑结构,故性境界、情境界、意境界分别代表了“一心”之不同境界,犹如人之行走,一路走下去一路上各有不同的景致呈现一般。
总之,李珥心性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对“心”之主宰作用与“意”之计较商量作用的重视以及“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论。而“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论,的确为其在心性情论上的创见。
李珥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天道策》、《人心道心图说》、《圣学辑要》、《答成浩原》等。
自从29岁时任户曹左郎开始,他一生为宦,曾官至吏曹判书,49岁时卒于京城大寺洞寓所。李珥是朝鲜朝五百年间难得的道学家、通儒。政治上,他积极建言献策主张为了朝鲜朝的中兴“因时制宜”与“变法更张”,强调“事要务实”。在社会教育方面,他不仅亲自开展私学教育,而且还制定“海州相约”、“社会契约束”以及著《击蒙要诀》、《学校模范》等为朝鲜朝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故成浑赞其曰:“栗谷于道体,洞见大原。所谓天地之化无二本,人心之发无二原,理气不可互发,此等说话,真是吾师。其爱君忧国之忠,经世救民之志,求之古人,鲜有其俦。诚山河闲气,三代人物。”①他的学说被后人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韩国儒学史上颇具影响的畿湖性理学派。
第一节 四端七情论辩之发端
——以权近、柳崇祖的“四端七情”说为中心
权近、柳崇祖及郑之云等皆为朝鲜朝前期的著名朱子学者,其在四端七情问题上的论述和主张,遂成日后退溪李滉、高峰奇大升、栗谷李珥、牛溪成浑等人进行“四端七情理气”之辨的理论端绪。本节首先将权近和柳崇祖的思想合在一起加以讨论,目的在于能对四端七情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有个系统的了解。
一、权近与其“四端七情”论
活跃于丽末鲜初思想界的朱子学者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与郑道传一起并称为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双璧。权氏为安东人,曾受教于李穑和郑道传。他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前文所介绍的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
据年谱记载,权近步入仕途初期颇为顺当。他年17岁中成均试,年18岁(洪武二年己酉),三月中馆试第二名,五月樵隐李仁复、牧隐李穑同掌礼闱中第三名,六月擢殿试丙科第二名,七月直拜春秋检阅。历任中正大夫成均祭酒、艺文馆提学、成均馆的大提学、大司成等官职。但是,38岁(昌王元年)时他因“礼部咨文”事件中言事所牵连被贬到黄海道牛峰,后又贬至宁海。①在韩国儒学史上不管是“以图示说”的研究传统,还是四七论辩的理论萌芽皆可以追溯至权近,故后人赞其道:“丽朝以来,非无名人器士,而所尚者,文章勋业也。惟文忠公郑梦周,始传程朱之学,而遭时不幸,未有著述。文康公权近,有文章学识,而《入学图说》以四端七情,分左右书之。此所以理气之发于二歧也。后来学者传袭之论,无复异趣。”②
他一生致力于性理学理论之探究,为朱子学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泽堂李植曾说过:“我国先儒,皆无著述,权阳村说经论学,始有著述。”③其力作《五经浅见录》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了“五经”,而《入学图说》则是韩国最早一部理解朱子学思想的入门向导书籍,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近的《入学图说》是其为初学者讲授“四书五经”而作的一部“以图示说”的性理学入门书籍。全书分为前后集,前集中载有“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诸侯昭穆五庙都宫之图”等26种图说;后集中则收有“十二月卦之图”、“周天三辰之图”、“一朞生闰之图”、“天地竖看之图”、“天地横看之图”等14种图说,共计40种图说。卷首有权近的“自序”,卷末有郑道传和卞季良的跋文,书中权近将儒家经书中能够“图示”的内容尽己所能以图解的形式表现出来,极大方便了初学者的学习。
此图说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和李滉的《圣学十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滉的《圣学十图》中的“大学图”与权近的“大学指掌之图”可说是一脉相承。因此《入学图说》被后人称为韩国“图书学”的嚆矢。
尽管为初学者而作,《入学图说》还是集中反映了权近的心性论思想。其中又以“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和“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尤为根本。该书收录的40篇图说中,讲授“四书”的有6篇,讲授“五经”的有3篇,讲授“河图洛书”的有10篇,讲授礼的有4篇,讲授天文地理的有12篇等等。在这40篇图说中,较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的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中庸分节辨议”、“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五经体用分释之图”等篇,而“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五经体用分释之图”等图示正是权近对“四书五经”内容的系统解说图。权近思想除了此图说外,还散见于《阳村集》、《礼记浅见录》以及《三峰集》之注释内容。
下面,首先对其“天人心性合一之图”①(见图2)作出分析。
此图集中反映了权近的哲学思想。在该图解释的开头他便写道:“朱子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今本之作此图。”②表明此图的理论依据来自朱熹的宇宙论(理气论)。紧接着又写道:
右图谨依周子“太极图”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说,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故不及万物化生之象,然人物之生,其理则周,而气有通塞偏正之异,得其正则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即此图而观,则诚字一圈,得最精最通而为圣人;敬字一圈,得正且通者而为众人;欲字一圈,得偏且塞者而为物;其下禽兽横者得其尤偏塞而为草本者也。是则万物化生之象亦具于其中矣。夫天地之化,生生不穷,往者息而来者继。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①
可见,此图是权近谨依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的《中庸章句》之说制作而成。权近在图说中还附上其与弟子的有关天人心性问题的答问。此图不仅谈到了“太极”、“天命”、“理气”、“阴阳”、“五行”以及“四端七情”等性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还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图示形式清楚表示出来,使学者易于理解和把握其要领。
权近的性理学说非常重视“心”,以至于在其心性论中“性”是在论“心”时才附带成为讨论的对象。权近曰:“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①如图中所见,他对“心”这一概念作了详细辨析,并对像“性”、“情”、“意”、“诚”、“敬”、“欲”等概念皆从心性论到修养论多角度作了分析。从图中可见,他将“性”之德目规定为仁、义、礼、智、信;“情”则指代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喜怒哀惧爱恶欲;“意”为几善恶;“诚”乃真实无妄,纯亦不已,圣人性之;“敬”为存养省察,君子修之;“欲”为自暴自弃,众人害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心”大体上是相较于“身”而言。因为他认为,心是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者,是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故他写道:“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沫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虽曰应万事,而是非错乱,岂足为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其有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若从理学的心身关系的角度来看,因“心”有具众理而应万事之功能,故主宰个体肉身活动的只能是“心”。可见,性理学以为人的身体和神明的作用皆与“心”相关联。
另外,心之重要特征,即“虚灵洞彻”与“神明”问题在图中虽未标示,但是在论著中也有对此一问题的相关论述。他认为,心不仅仅是“神明之舍”,更是具有虚灵之妙之特性的认识器官。因心是“气之精爽”、“气之灵”,故此心具有虚灵之特性,可以应对万事。他将心比喻为“心之灵而镜之明也”,还说:“心之本体,寂然无朕,而其灵知不昧,譬则镜性本空,而明无不照。盖随缘者,心之灵而镜之明也。”③心之寂与镜之空是不变者,而心则以此感应万变而无穷尽。他还认为心所生发的行为可以为善为恶,而为善的行为必源于纯善无恶之性。
权近和郑道传皆为丽末鲜初的著名斥佛论者,权氏在展开其性理学“心”论的同时还对释氏所讲之“心”作了批判。“盖外边虽有应变之迹,而内则漠然无有一念之动,此释氏之学第一义也。”①佛教不承认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以为现实世界为虚幻的、不真实的存在。这种心说所隐含的是遁世绝俗、逃避现实的消极的人生态度,自然与主张积极入世、力求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人生观相去甚远。因此受到儒者的猛烈抨击。对此权近也批评道:“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沫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其有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可见,他所讲的“心”正是朱子学所言之天理论视域下的理气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权近绘制此图的目的在于“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③。将理气摄入心性域来讨论是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色,这一理论传统其实亦肇始于权近。韩儒的心性学说与其说是对人之性情问题的探究,不如说是从理气论的向度对人的性理问题的阐发。因人的行为皆与心理活动相关联,所以韩儒在思考如何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时重点考察了人的行为的根源,即试图立足于心性论以阐明人之道德行为的发生根源。于是,属于理学本体论范畴的理气概念被纳入心性论域,用于直接讲明人的道德行为的来源和根据。从“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可以看到,“心”分善恶,而整图则被代表理气的白色和黑色一分为二。心具众理,性源于理,理若如实呈现即为纯善。故圣人即是完全实现心中之理者。
如前所述,韩国性理学关注的首要课题是“人”,即具有道德良知的现实中的人。这一特点从《入学图说》开篇第一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亦能窥见。此图说首先要辨明的是人的心性问题,而非天地万物如何化生的本体论问题。
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善恶选择时如何抉择“善”,这是关乎修养论(工夫论)的问题,为此权近标出了“敬”。图中善恶被分在“心”之两侧,而“敬”又与二者相关联,意为人之为善为恶皆系于以“主敬”为主的存养省察工夫。
其次,讨论其“天人心性分释之图”的“天”之图(见图3)和其“人”之图①(见图4)。
从《入学图说》的排序中也可看到,权近是在第一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
中先论人之后,又在“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中次第论及“天”、“诚”、“敬”。“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天”之图显示“天为一大”:“一者”意为以理言则无对,以行言则无息,故为万殊之本;“大者”则意为以体言则无外,以化言则无穷,故为万化之源。其“以理言则无对”的观念与日后李滉“理极尊无对”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皆基于以理为本的理气论传统。“敬”是指主敬涵养下学工夫,“诚”是天人合一之媒介,故《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①
在“人”之图下,权近附言道:
人者,仁也。仁则天地所以生物之理,而人得以生而为心者也。故人为万物之灵,仁为众善之长,合而言之道也。圣人至诚,道与天同。君子能敬以修其道,众人以欲而迷,惟恶之从。故人者,其理一,而所禀之质,所行之事,有善恶之不同。故其为字,歧而二之,以示戒焉。人能体仁,以全心德,使其生理常存而不失,然后可无愧于为人之名。而其效必能得寿,不然则生理丧而非人矣。②
依权近之见,“仁”是天地所以生物之理,在人则为心。因此人是万物之灵,仁为众善之长,而将二者合而言之便是道。他进而指出惟君子能敬以修其道,而众人则迷于欲念、惟恶之从。权近将“仁”也就是文中所谓“生之理”视为人的本质。众所周知,儒家将“仁”视为人与万物共同的普遍原理,表现在人身上即为“人之性”。
再次,讨论其“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心”之图(见图5)。
对于此“心”之图,权近解释道:
心者,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理气妙舍、虚灵洞彻、以为神妙之舍而统性情,所谓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者也。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其用之发有时而昏。学者要当敬以直内,去其昏而复其明也。其字形方者,象居中方寸之地也。其中一点,象性理之源也。至圆至正,无所偏,象心之体也。其下凹者,象其中虚,惟虚故具象理也。其首之尖,自上而下者,象气之源,所以妙合而成心者也。其尾之锐,自下而上者,心于五行属火象,火之炎上也,故能光明发动以应万物也。其右一点象性发为情,心之用也;其左一点象心发为意,亦心之用也,其体则一而用则二。其发原于性命者,谓之道心而属乎情,其初无有不善,其端微而难见,故曰道心惟微,必当主敬以扩充之。其生于形气者谓之人心而属乎意,其几有善有恶,其势危而欲坠,故曰人心惟危,尤必当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然后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差谬而圣贤同归,参赞天地亦可以驯致矣。不然,则人欲日长,天理日消,此心之用不过情欲利害之事,虽有人形,其违禽兽不远矣。可不敬哉。①尽管此文篇幅不长,权近还是简明扼要地对心身关系、心之结构、心之机能、心之作用、心之体用等都作了必要的说明。在心身关系方面,主张心是“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亦即心为身之主宰;在心之结构方面,认为心是理气妙合而为神妙之舍;对于心之机能则主虚灵洞彻,由是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对于心之作用倾向心性关系中“心统性情”;至于心之体用则主心体至正无偏而为性理之源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即是用。①其体则一,而用则二。道心原于性命而属乎情,“其初无有不善,其端微而难见,故曰道心惟微”;人心则生于形气之私而属乎意,“其几有善有恶,其势危而欲坠,故曰人心惟危”。因此,以主敬工夫扩充天理之正,以遏人欲之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便可做到危者安而微者著。以上是权近心论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其基本见解皆来自朱熹理论。如对心之机能,朱熹曾有如下论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②在文中权近还探讨理欲之关系,以为二者此消彼长,必由主敬工夫方能扩充天理,所谓“人欲日长,天理日消”。
此图需注意的是,权近按心的字形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加以解释:其一为“理之源”;其二为“气之源”。他将道心和人心、情和意以性为中心分别列于“理之源”和“气之源”之下:道心属情,其初无有不善;人心属意,其几有善有恶。在权近看来,此时之“情”根于理,作为“四端”之情无有不善,人心是发于气之意,故其几有善有恶。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的思想行为或源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韩儒则更倾向于从理气之发的视角来探讨此一问题。权氏殆以作为心之二用的情意分别生于理与气——“其体则一而用则二”。“情”和“意”乃人心的两种发用方式,源于性命者为道心(情),生于形气者为人心(意)。因此“学者要当敬以直内”,防止生于私欲的行为的发生。
“人心道心”问题在韩国儒学史上极为重要。权近对此一问题基本立场是“人心惟危,尤必当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然后危者安,微者著。”依其之见,“情”的行为一般能呈现较为理想的状态,源于气的“意”则不然,后者之呈现或善或恶,不由“心”的作用即无以引之向理。
权近以“理之源”和“气之源”判分人心以作解释,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
最后,再讨论其有关“性”的论述(见图6)。
理学宇宙论(本体论)需借理气说才能得到阐发。从上文可见权近的思想大体不离伊洛渊源,是故在其学说中“性”总被赋予普遍宇宙之原理义,所谓“性即理”是也。
在《入学图说》中,权近彰示“性”之图并写道:
性者,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于吾心者也。故其为字,从心从生。人与万物其理则同,而气质之禀有不同者焉。告子曰生之谓性,韩子曰与生俱生,释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气言而遗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①
此图亦是为初学者而设。权近自言道,其训天人心性分释之意有些破碎,但是初学者则一见即可知其大意要旨。并标榜其解说皆本自程朱的格言,非为其臆说。初学之士的要务,则在于动处下功夫,而存养之事已包含在“敬”之中。
理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反躬实践,而在现实中如何如实地呈现“理”和实践“理”遂成首要课题。为此权氏欲将天人问题转化为心性问题,以图在心性层面上实现“天人合一”这一儒家最高价值理想。心作为理气之合既具形上之特性,又有形下之特性。而且心还以“虚灵洞彻”统摄性情,由是具众理以应万事者。因此,在心的层面上追求其与性理的合一便是“仁学”思想的主旨。
“心具众理”强调的是“理”常存于人心。理学家认为,人心之理即性理不能如实呈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②之故。权近重视“性”,亦因“理”只有通过“性”的发用才能呈现。那么,究竟由何呈现呢?无疑是要由“心”来呈现。从此意义上说,权近“心统性情”的思想可以视为对主体以其“实践性”能动地呈现天理的一种阐述。
如前文所述,他将“性”定义为“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于吾心者”。①这与程朱对“性”的论述大体相同,伊川曾言:“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②又说过:“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③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解释道:“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有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④相较于程朱,权近的性理概念更强调“生之理”之义。
“性”字“从心从生”,仅就字形便可了知其与人心、人生的密切关系。作为性理学家,权近对历史上出现的不同“性”说评价道:“告子曰,生之谓性;韩子曰,与生俱生;释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气言而遗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在他看来,告子、韩非子以及释氏之“性”论的主要理论缺陷是未意识到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即所谓“义理之性”。这也反映了性理学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安身立命,而且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道德水平的提升。于此可见,儒家的确比其他学派理论更具道德关怀。权氏的“性”论与其说对人之本性的阐发,不如说是对人的能动实践能力的揭示,故可将其拟于实践性理学。
权近在书中“天人心性分释之图”的“性”条里面还写道:
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於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又况程子之言,以为外物触而动于中,其中动而七情出,情既炽而其性鉴矣。则其不以为性发也,审矣。①
他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之善并无二致,皆为同质之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非为性之所发,故不能与“四端”并列。依权氏之见,“四端”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权近不仅依此区分“四端”和“七情”,还进而以理气分判道心与人心:“理本无为,其所以能灵而用之者,气也……道心为危,人心惟微,则固以理气分言之矣。夫心之发其几有善恶之殊,若纯乎理而不杂乎气,则其发安有不善哉。”②从权近“心”之图(图5)中可见,是以“理之源”和“气之源”的视角对心进行解读。依其思路,性之源是理,心之源是气。心为理气之合,故其发用呈现为道心和人心,前者属理,后者属气。同时心又统摄性情,理所当然“心之用”又可以显发为“情”和“意”。“情”发于“性理”,“意”发于“心气”。发于性理之善和发于心气之善者,虽同为至善之物,显发为“善”的过程却各有差异。这一过程乃攸关性理学存养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课题,对此权近未作具体阐发。直至16世纪,李滉、李珥等理学家群体们才对之进行深入而具体的讨论。
权近在书中对“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作出了解释。“‘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即仁义礼智之端,非有二也。今子既以四者列于情下,又书其端,于外别作一圈,何也?’曰:‘四者之性,浑然在中。而其用之行,随感而动。以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心则是心,即为四者之端,诚非二也。然发于中者,谓之心;现于外者,谓之端。故孟子于此几两言之,或言端,或不言端。而朱子于言端,以为犹物在中,其端绪见于外,则其义愈明而不容无辨矣。’”③对于学生就此问题的提问,权近回答说四者之性是浑然在中者,而四者之端则是犹物在中而其端绪见于外者。二者诚非二物。其实这是讲仁义礼智之性如何生发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情的问题。对于性情关系问题,朱子学的基本看法是“情根于性,性发为情”;权近在此亦持相同立场。但他之所以视二者为“诚非二物”,是因为四德与四端之情皆为纯善之物的缘故。
权近还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①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的基本问题。《入学图说》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论辩之先河。沙溪金长生(1548—1631年)说过:“退溪先生七情四端互发之说,其原出于权阳村《入学图说》。其图中,四端书于人之左边,七情书于人之右边。郑秋峦之云,因阳村而作图,李滉又因秋峦而作图,此互发之说所由起也。李滉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是阳村分书左右之意。”②不仅如此,权近还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对佛、道进行批判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认为“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③。权近这一思想后为李滉发展为“理尊无对”说和“理贵气贱”说,从而开启了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主理论传统。
权近有关四端七情问题的看法实为百余年后李滉、奇大升、李珥、成浑等诸家旷日持久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为代表的岭南学派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儒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伦理上的道德情感,典出《孟子·公孙丑上》;“七情”则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生理上的自然情感,典出《礼记·礼运篇》。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并未引起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儒学界引发了一场“四端七情,理发气发”的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使韩国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哲学轨道,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四端七情”这一问题的关注意味着韩国儒学已然开启本土化的进程。
权近与郑道传虽然同为朝鲜朝初期的理学大家,但是在接受和传播朱子学方面却各有特色。郑道传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注重朱子学理论本身的探究与思考。若就两人对韩国朱子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后世学者视为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主要代表。李滉也很服膺权近的学问,曾对其评价道:“阳村学术渊博,为此图说极有证据,后学安敢议其得失。”①权氏《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示类书籍,所以他被目为韩国儒学界“以图释说”研究范式的开创者。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传至日本,且在日本儒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曾多次翻刻权氏《入学图说》,现存宽永甲戌刻本和庆安元年刻本等。
权近的主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以及《三峰集》中的《佛氏杂辨》序,《心气理篇》注、序等。现有《阳村集》(40卷)。
二、柳崇祖与其“四端七情”论
中宗时期的真一斋柳崇祖(字宗孝,号真一斋、石轩,1452—1512年)是朝鲜朝前期继权近之后又一位论及四端七情理气问题的性理学家。柳氏本贯为全州,谥号为文穆。他成宗三年(1472年)中司马试进入太学,1489年文科及第,历任司谏院正言、弘文馆副校理、司宪府掌令、成均馆大司成等官职。他是“官学派”的代表,但是对“士林派”学者亦相当友好,在任大司成时还荐举了赵光祖、金锡弘、黄泽等“士林派”学者。燕山君十年(1504年)被发配至原州,中宗反正之后又官复原职。史书上对其为人有如下记载:“文穆公,天资高明,器宇峻洁,早有志于学。其为学也,本之以孝弟忠信,律之以刚方廉直,六经诸子与百家,靡不淹贯,妙年升庠,已有道义之所推服,既擢第入翰苑,儒臣启,以经明行修,可为师表,兼带成均掌教,教导后进,先正臣李滉所称师友堂堂经训皇皇者也。当燕山主九年,文穆在宪府,抗疏论十余事,皆切直不少讳,贬其官,甲子祸作,杖窜原州,靖国之初,首入经幄,旋升工曹参议,三公启,经幄不可无此人,命兼带经筵官。遂长国子,三公又启,性理之学,不可绝其传,请选年少文臣,就崇祖受业,崇祖承命,课授甚勤,作为四经、四书等谚解,以晓诸生,宣庙朝所纂集刊行者也。又命选诸生中可大用者以奏,崇祖,以文正公臣赵光祖首荐,六年辛未,上亲临太学,谒先圣,退御明伦堂,横经问难时,崇祖为大司成,以大学进讲,反复乎存心出治之要,上凝旒倾听,桥门观者皆耸然。”①柳氏在《书经》、《易经》、《礼记》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以口诀和悬吐的方式给“四书”、“三经”编了《七书彦解》②,作为韩国彦解类之嚆矢,对后世影响颇大。柳氏的著作还有《真一斋集》、《大学十箴》、《性理渊源撮要》等。
《性理渊源撮要》摘取先儒学说中的紧要段落加以编纂,从中可见其性理学思想。而《大学十箴》则以箴规人主之思想行为为目的。全书将《大学》内容分成明明德箴、作新民箴、止至善箴、使无讼箴、格物致知箴、谨独箴、正心箴、修身箴、齐家治国箴和絜矩箴十个条目,分门别类以述帝王学之要义。依柳氏之见,大学之道,是修齐治平之准绳,是方圆平直之至。为君者之所以不可不明此大学之道,是因为为政之规矩准绳之所出;为臣者之所以不可不讲此大学之道,是因为为臣者之规矩准绳之所由施;为民者之所以不可不知此大学之道,是因为规矩准绳之所当从。他进一步指出,二帝三皇之所以盛治者,乃正其规矩准绳之体,以成己而运之于上,故方圆平直之用自正而物成于下。
在理与气这一性理学基本问题上,柳崇祖认为:“气与理,气殊形禀理一天地,气不外理,理寓气里。理不离气,浑然一体,气不杂理,粲然不混。无先无后,无端无始。赋物之初理一气二,物禀之后气同理异。”③柳氏倾向理气“混沦一体”、“不离不杂”的传统朱子学立场。他认为理气二者在时间上无先后、无终始,赋物之初理一气二,物禀之后“气同理异”。柳崇祖正视分殊之理的差异性,认为既有天下公共之理,又有一物各具之理。柳氏思想较具特色,在人性论领域尤重“气质之性”。
在“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上,柳氏提出:
天下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有阴阳则有木火金水者气也,有健顺则有仁义礼智者理也。气非理则无所承,理非气则无所附,是故未有阴阳已有太极,未有此气已有此理。推所从来,固不无先后之别,然言太极则已不离乎阴阳,言性则已不离乎气质,有则具有,又岂别为一物而有先后之可言哉。合而言之,则太极无物不存,万物各具一太极,性即气、气即性,盖未始相离也。初岂有所谓本然之性而又岂有所谓气质之性哉。分而言之,则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性自性、气自气,又未始有相杂也。岂无所谓本然之性又岂无气质之性哉。①
此处涉及理(太极)的逻辑在先问题。理气之关系推所从来“固不无先后之别”,只能说“未有阴阳已有太极,未有此气已有此理”。但在现实生活中,言太极时则已不离乎阴阳,“言性则已不离乎气质”。柳崇祖在此着重说明“气质之性”的实在性和现实性。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性本于天,虽气之本而气存于人,实性之用。性如日月之明而气则如云雾之昏矣。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盖谓此也。夫形气未禀人物未生,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是人生而静以上也,可名之以理,不可名之以性,所谓在天曰命,是专以理言也。及降而在人则坠于形气,虽可谓之性,然已涉于有生,而不得超然于是理之本体矣。是才说性则便已不是性也,是所谓在人曰性也,是专以气质而言之。”②需要指出,尽管先儒在人性论方面已有本然之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之说,但是柳氏在性论上仍然坚持二程“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③的性气合一论。若综合上一段引文的内容来看,严格地讲他更倾向于明道的“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④的性气不离的思想。
柳崇祖曾对历史上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性”论做过评说,指出:“盖观古人之论‘性’,孟子专以本然言性,而不及于气,所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杨误以气质为性,而不识其本,所谓论气不论性不明;韩子之言性可谓备矣,五性之说固已见其理之同,三品之说乃不知其气之异。此廉溪张程所以不得不表彰而发明之也。然考之经传已有此意,但古人未尝明著其气质之名尔。”①儒家之人性论确有一个发展过程,曾产生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但是,张载“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这样性二元论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讨论推向了高潮。朱熹这样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②但朱熹之后人性论从性二元论逐渐转向性气合一的性一元论,开始强调现实性。从东亚儒学史的视角来看,人性论的此一转向在我国明代学者罗整庵(主理气一物论)、王廷相(主理气无性论)以及韩儒柳崇祖的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也反映了在理学传统中道德理想(理想性)与现世关怀(现实性)的尖锐冲突,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思想运动的演进,儒者的现实指向性在逐渐增强。此理论转向可视为17世纪东亚各国注重实践性与功利性的“实学”思潮兴起的前奏。
在权近提出以理气分言分四端七情的观点之后,柳崇祖也提出大体相同的主张。他在《大学十箴》中的“明明德箴”中写道:
一阴一阳,本一太极,继善成性,理气妙合,秉彝懿德,人所同得,精真之凝,灵妙虚寂,不吝于愚,不豊于智。内具众理,外应万事,统性与情,神明莹澈。情动于性,纯善无杂。意发于心,几善与恶。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③柳氏认为“四端”是理动所致,而“七情”则是气动所致。此一理动气动的解释模式说明他将二者视为基于不同发用过程的两种不同的情感。其“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的观点与日后的李滉“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思想颇为相似。柳崇祖在大作《性理渊源撮要》中将程迥(沙随程复心)理气说做了进一步阐发,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然之性,理也,仁义礼智信,五性皆天理,故本无不善。气质之性,气也,纯清者全其性,上智也。杂清浊者,善恶混,中人也。纯浊者,全是恶,下愚也。理发为四端,气发为七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者正情,无有不善。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中节则公而善,不中则私而恶。①
感通之谓情,则四端者理之发,七情者气之发。能为之谓才,则无不善者出乎性,而有不善者出乎气也。由是观之,理无不同也,所不同者气耳。理无不善也,所不善者才耳。②柳崇祖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主张,在以上言论中得到再次确认。他认为四端七情根源不同,坚持对之区别对待。
从柳氏在《性理渊源撮要》中对程迥“四端七情”说的整理可以窥见,其思想主张在先儒著述中也不无痕迹。像“理动气挟,四端之情,气动理随,七情之萌”之说就与权近之“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之主旨大体相同。可见,“四七”对举、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传统早在郑之云之前的朝鲜朝性理学中即已存在。此为韩国性理学的又一特征。
柳崇祖对朝鲜朝性理学发展的贡献,在史书上也有记载:“窃稽中庙朝大司成赠谥文穆公臣柳崇祖,倡明道学,所撰进《大学十箴》、《性理渊源撮要》及经书《七书彦解》等书,启沃圣德,嘉惠后学,实为旷世之真儒,后生之师表,允合庑享之联跻而尚未彻旒,岁年侵寻,章甫之赍郁,不日不月,而朝家之令典,抑亦恐有未遑。臣等之责,愈久愈深,今当卫辟存闲之庆会,自不敢泯然,各道缝掖之徒,不谋而同,齐声而应,谨摭其平日实迹之有关于斯文者,以备乙览焉。”③
简言之,权近的《入学图说》和柳崇祖的《性理渊源撮要》所开创的“四七”对举之范式成为朝鲜朝“四端七情”之辨的理论端绪。明显可以看出,《入学图说》和《性理渊源撮要》中出现的“四七”对举的思想与郑之云、李滉的“四七互发”说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关联。
第二节 李滉与其“四端七情”论
高丽末开始传入到朝鲜半岛的朱子学经过14—15世纪的传播与普及,至16世纪已基本发展成熟,开始形成了以主理、主气为理论特色的韩国化的性理学派,即以李滉(1501—1570年)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珥(1536—1584年)为宗的畿湖学派。两派围绕四端七情问题而展开的四七论辩使韩鲜朝性理学的发展走上了以性情论探讨为主的发展轨道。本节和下一节将主要对李滉与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进行论述。
一、李滉的理气论
李滉(字景浩,号退溪、退陶、陶叟)生于燕山君七年(1501年),卒于宣祖三年(1570年),谥号文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东方之朱夫子”。出生于礼安县温溪里(今安东郡陶山面温惠洞)。中宗时文科及第,官至大提学、右赞成。后辞官退隐乡里,闭门静居,钻研学术,以著书立说和授徒讲学为业度过了其一生。曾在家乡礼安选一景色宜人处卜筑“陶山书堂”,作为了其著述和讲学之场所。
李滉年轻时曾写过一首诗,诗中吟道:
露草夭夭绕碧坡,
小塘清活净无沙。
云飞鸟过元相管,
只恐时时燕蹴波。①
从这首哲理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峻别天理人欲之思想倾向早已有之。因此在之后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李滉提出以主理为特色的性理学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于其学问,弟子郑惟一(字子中,号文峰,1533—1576年)曾写道:“先生学问一以程朱为准,敬义夹持,知行并进,表里如一,本末兼举,洞见大原,植立大本,若论其至吾东方一人而已。”①李滉的学说被其后学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岭南退溪学派,影响了此后韩国儒学的发展进路。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首要问题。②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理气“不离不杂”③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鲜朝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说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④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韩儒丁时翰亦曾言道:“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⑤不过,李滉、李珥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之发及理气体用问题而展开。
李滉在接续朱熹“理气二分”说的基础上,依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尊无对”、“理帅气卒”、“理贵气贱”的主张。他说:
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故也。⑥
天即理也,而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是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才有理,便有气眹焉。才有气,便有理从焉。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所谓理者,四德是也;所谓气者,五行是也。①
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然理无为而气有欲。故主于践理者,养气在其中,圣贤是也;偏于养气者,必至于贼性,老庄是也。卫生之道,苟欲充其极致,则匪懈匪躬之职,皆当顿废而后,可庶几。其斁理害正如此,本不可以为训者也。若以为养气亦不可全无,而姑存其书为可,则其中尤近怪无稽者,亦当去之。②从引文中可见,对二者“不杂”之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论的重要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李滉重视其“不杂”之义的目的在于,主要是为了强调理的主宰性、主动性、优位性。由是在二者关系上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如其所言,“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等等。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他把朱熹的理气“先后”⑤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同时也为其“四七理气”论打下理论基础。
在东亚儒学史上,李滉性理学的“理”论极富特色,不过“理”亦是其性理学说中最为难解处。李滉本人也曾言道“理”字最为难知,对于缘由他写道:
凡人言理,孰不曰无形体、无分段、无内外、无大小、无精粗、无物我、虚而实、无而有哉。但真知其实无形体、实无分段、实无内外、实无大小、实无精粗、实无物我、实为虚而实、实为无而有为难。此某所以平日每云理字难知也。①
李滉为学一向主张学贵穷理,因为在他看来若对理有所未明,则或读书,或遇事都不能做到无碍。所谓“理有未明”,即是指学者还未做到对理字之义的“真知”。那么,何谓其所言之“真知妙解到十分处”呢?李滉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盖尝深思古今人学问道术之所以差者,只为理字难知故耳。所谓理字难知者,非略知之为难,真知妙解到十分处为难耳。若能穷究众理到得十分透彻,洞见得此个物事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洁洁净净地,一毫添不得,一毫减不得,能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而不囿于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中,安有杂气而认为一体,看作一物耶。其于道义,只见其无穷,在彼在我,何有于町畦,其听人言,惟是之从,如冻解春融,何容私意之坚执。任重道悠,终身事业,安有欲速之为患哉。假有初间误入,一闻人规,便能自改而图新,安忍护前而无意于回头乎。诚恐循此不变,处而论道,则惑于后生,出而用世,则害于政事,非细故也。其以博览群书为非,而欲人默思自得,其意之落在一边,可知。公之报书,所以正其偏而砭其病者得矣。②
这是李滉答奇大升信中的一段话,也集中反映了在其哲学中“理”概念所具有的基本义涵。由以上引文内容所见,在其学说中“理”既是一个具无形、无质、无为之特性的形上之存有,又是一个指代实理的“天理”。而且,“理”又兼体用,既有无声、无臭、无方体之“体”,又有至神至用之“用”。③对于这样的“理”,李滉在文中进行了多角度的阐发,认为古今人学问道术之所以差者,只是因为“理”字难知之故。所谓“理”字难知,不是指略知之为难,而是将之真知妙解到十分处为难的意思。认为,只有“穷究众理到得十分透彻,洞见得此个物事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处,才能算是真正知“理”。
从“虚实”、“有无”等角度论述“理”本体的同时,李滉在答复奇大升问难的信中还提出理有体用说,曰:“无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体也。其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见于本体之无为,而不知妙用之能显行,殆若认理为死物,其去道不亦远甚矣乎。”①实际上,理有体用说是为其“四七理气互发”说作了理论铺垫。
进而,李滉还提出“理非静有而动无,气亦非静无而动有”的理(太极)自有动静的思想,明确地肯定了理的发用性。李滉曰:
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但就无极二五妙合而凝,化生万物处看,若有主宰者运用而使其如此者。即书所谓惟皇上帝将衷于下民,程子所谓以主宰谓之帝是也。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②
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勉斋说,亦不必如此也。何者,理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阳生阴也。③由此,在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便有了理气互发之论。他对理本体所作的这一解释,不仅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④的朱学内在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可能,而且还积极回应了以“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原,理何足尚”⑤为由对朱学理气说提出质疑的明初朱子学者们的诘难。但是,对其理发说需做进一步的解释。李滉亲身经历朝鲜朝多起“士祸”,统治阶级内部血腥的权力斗争致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社会道义及生命的尊严荡然无存。作为生活于此一时代的大哲学家李滉势必将重塑社会纲纪,提高伦理意识以及加强道德教化视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对李滉来讲,如何保存和扩充源于天理的人性本然之纯粹性就成为其首先要思考的哲学课题。故他所追求的是此种性理的自然呈现或良知之心的自我坎陷。李滉的这一主张看似与陆王心学的良知说有些相近之处,但其根本立场是基于人的道德心理和伦理行为意义上的性理发用,并非为王学意义上的“致良知”,更不是本体论(宇宙论)向度上的“太极”之自动静。理发论在其学说中之所以能够得到成立,还与其对“理”特殊规定相关。前文已言及在其“理”论中,理具有“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之特性,“理”具有绝对性。而且,在“气”论中他亦对之作了相应之规定。要言之,强调道德心理和伦理行为意义上的理(性)之发用性、主宰性、优位性,是李滉理气论区别于朱子理气论的紧要处,学者于此处应仔细玩味和体会。
那么,相较于“理”,“气”在李滉哲学中具有何种特性呢?李滉认为,因为“气”是有形之物,故气有限量而理无限量,气有生死而理无生死之说①。
盖理本无有无,而犹有以有无言者。若气则至而伸,聚而形为有,反而归,散而灭为无,安得谓无有无耶。或别有所据,某未记耶,气之散也,自然消尽而泯灭。②
然滉前以为气散即无。近来细思,此亦偏而未尽。凡阴阳往来消息,莫不有渐,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然则既伸而反于屈,其伸之余者,不应顿尽,当以渐也。既屈而至于无,其屈之余者,亦不应顿无,岂不以渐乎。故凡人死之鬼,其初不至遽亡,其亡有渐。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非谓无其理,而姑设此以慰孝子之心,理正如此故也。由是观之,孔子答宰我之问,亦无可疑矣。以眼前事物言之,火既灭,炉中犹有熏热,久而方尽。夏月,日既落,余炎犹在,至夜阴盛而方歇,皆一理也。但无久而恒存,亦无将已屈之气为方伸之气耳。①可见,“气”在李滉哲学中具有生死、聚散之特性。他以为,没有恒久不变之气,气的聚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举炉中火苗渐渐熄灭和夏日白天之暑热至夜缓解为例详加阐述。
李滉进而还提出气之原初无不善的主张,曰:
气之始无不善,乃气生源头处,非禀受之初也。然气有一日之始,有一月之始,有一时之始,有一岁之始,有一元之始,然此亦概举而言之耳。推来推去,其变无穷,当随处活看,不可执定为某气之始。苟指认一处为定则不通,不足以语造化之妙。②
那么,其无不善之“气”是否与李珥“湛一清虚”之气泯然无别呢?对此,李滉解释说:“程子心本善之说,朱子以为微有未稳者。盖既谓之心,已是兼理气,气便不能无夹杂在这里。则人固有不待发于思虑动作,而不善之根株已在方寸中者,安得谓之善,故谓之未稳。然本于初而言,则心之未发,气未用事,本体虚明之时,则固无不善。故他日论此,又谓指心之本体,以发明程子之意,则非终以为未稳,可知矣。”③可知,其所言“气之始无不善”是指心之未发而本体虚明之时。这与徐敬德、李珥哲学中的“气”概念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李滉对此进一步解释道:“湛一气之本。当此时,未可谓之恶,然气何能纯善?惟是气未用事时,理为主故纯善耳。”④这一解释对理解其“四七”论极为重要。因为依李滉之见,“气”只有听命于理或顺理而发的时候才能呈现为善。但是,又不能将“气顺理而发”称之为“理之发”。“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于此可见,其“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之说实乃根于其特殊的“气”论思想。
李滉还从价值论维度对理气概念作了“理纯善而气兼善恶”的价值规定。“理纯善而气兼善恶”之说其实承自程颐、朱熹的理学思想。气有清浊,由其清浊而言,气有或循理或不循理之可能。因此,要施以主敬工夫“以理驭气”。理是纯善,而气兼善恶,故以纯善之理帅“气”则“气”能循理而直遂。这便是所谓“理帅气卒”的思想。李滉的尊理贬气(理贵气贱)的观念,与其“理纯善而气兼善恶”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他进而又从伦理道德的意义上,作出“理极尊而无对”、“理贵而气贱”的理优位论之规定。既保持了传统理学所崇尚的等级价值观,又体现了其独创性的一面。理既“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②,那么理气关系即为主宰与被主宰的上下位关系。上者尊贵而下者卑贱,所以李滉指出:“理贵气贱,然理无为气有欲。”③在存养省察的工夫上,他特别强调主敬,惟其如此才能达到“以理驭气”使“气”顺理而发的目的。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兼论郑之云的《天命图》与“四端七情”论
在论述李滉的“四七理气”论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郑之云与其《天命图》。因为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郑氏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引致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李滉曾对郑之云称赞道:“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我妄以结状其难……有契有违,往返弗置,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④
郑氏是继权近、柳崇祖之后又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七情”的韩国性理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不仅为此后李滉和李珥等人的“四七理气”之辨提供了理论端绪,而且还开启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四端七情理论研究之先河。
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稼翁,1509—1561年)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曾受教于为金安国和金正国。郑氏世居高阳,本贯则为庆州。他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之辨发端于郑氏之《天命图》。对于自己的作图过程,他在《天命图序》中写道:
正德己卯(中宗十四年,1519年——引者注)思斋金先生被微谴而退卜居于高峰之芒洞,洞实之云所居里也,尝游其门受学焉。嘉靖戊戌(中宗三十三年,1538年——引者注)先生被召还朝,之云失其依归,与舍弟之霖学于家。论及天人之道,则之霖以幼学患其无据,莫能窥测。余于是试取朱子之说(见《性理大全》论人物之性),参以诸说设为一图,而又为问答名曰《天命图说》日与舍弟讲之。此非欲示诸人而作也,然图说既草,则亦不可不见正于长者,遂取质于慕斋思斋两先生,两先生不深责之,且曰:“未可轻议,姑俟后日。”不幸,两先生相继以没,呜呼,痛哉。由是此图之草,无所见正,而余之学问日就荒芜,几不能自振。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误闻不肖之名,躬行者再三之,云感其殷勤,斋木以进。退溪欣然出见,因语及《天命图》,之云以直告知,因请证之意,退溪稍假肯色。余退而私自贺曰:“吾丧两先生后,意谓更不得贤师友而求进,今得退溪,吾无忧矣。”常往来质问是图,退溪证以古说,参用己意,补其所欠,删其所剩,卒成完图。其赐己以厚,又从而为之说,附其后而教之,其幸孰大焉。非徒余之幸也,在昔日两先生姑竢后日之志,今始副焉,是尤幸之大也。余故首记作图之由次及定图之事,以藏于家。如有同志者出,其亦有以知退溪考证之意也。①
文中郑氏较完整地记述了此图的写作过程。他采先儒之论并以图解以明之,目的在于启子弟之蒙。此图取名为《天命图》——“天命”二字典出《中庸》首句,可见其以《中庸》为性理学之基础。为了说明天人相与之道,郑之云在《天命图解》①中使用了诸如理气、心性、太极、道等性理学概念,并用这些概念对天人之际进行了理气论的说明,旨在揭示了天人合一之根据。他还从理气论的角度对人的心性以及善恶问题进行了说明,此即所谓“四端七情”论。尽管郑之云并未将“四七”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来论述,而只视作探究天人合一的根据之一,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四七”论在其性理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②因为前者只是从其性理学整体构成之维度而言的。
此文写于嘉靖甲寅(明宗九年,1554年)之正月,此时退溪李滉已是年过五十的一代儒学名宿,思想也已渐趋成熟。他获得此图后,将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并在语气上作了改动。李滉的这一订正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尤其是奇大升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辩。这一论辩最终发展成为左右韩国性理学发展走向的学术论争。
郑之云在阐发其性理学说时,也意识到单纯凭借“气”论是很难对“恶”的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的。于是,他对阴阳之气赋予了善恶的价值含义。如把气分为清、浊、明、暗等。主张阳气清明,故可跻于善;阴气浊暗,故可流为恶。他断言“恶”的现象是由阴气所致,由此维护了“理”的纯善性。而且,还提出阴阳之气只是与心动之后的发用相关,并非各自独自发用的观点。这就消除了人的恶行的先天可能性。郑氏还认为,若心之发“意”根于性且其气属阳的话,天理会如实呈显;相反,如“意”与物相杂而其气属阴,则天理就会失去其真实性,终流于恶。依他之见,人的善恶行为取决于自由意志,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郑氏性理学追求“天人心性合一”,这表明他是韩国性理学史上的主流派学者。与中国的朱子学相比,韩国性理学以“图说类”诠释模式见长。从《天命图》在韩国性理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窥见郑之云在此一传统中的独特地位。①其“四七”理论的首要意义就是肯定人的道德行为(“人性善”)的先天可能性,此为性理学最根本的哲学观念。《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乃其天理观的来源和根据。实际上,性理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探讨的目的则是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寻找一个本体论的根据,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根据。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万物有机体观”正是性理学家们这一思想的反映。理与气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是为了证明这一思想。性理学家们以理气概念探讨道德行为之根源,尤其注重主宰人的行为的“心”的研讨,这也是心性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心性论中,与对心性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有关修养工夫的问题,即如何使心性向“善”的问题。欲解决之,首先要探讨“恶”的根源及来源。所以从理气论维度对“恶”之根源进行探讨也是心性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其中,“四端七情”之探讨是对人的本性的深层剖析,目的在于扩充良知所彰显的内心之善以上合天理。②实际上,他的这一思想根于孟子的性善说,欲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把握性与天道的关系。
可见,郑之云是韩国儒学史上继阳村权近、真一斋柳崇祖之后又一位坚持“天人心性合一”这一韩国性理学传统的学者。在韩国儒学史上,他还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性理学相关理论的学者。③尽管其理论仍显得较为简单缺乏系统性,但在《天命图解》及《天命图说》中所见的理论探索还是对性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了一定的概括和整理。所以李滉“君曾测海”的评价对他而言还是较为中肯的。郑之云的主要著作有《天命图解》以及《天命图说》。
李滉将其《天命图解》改订之后,首先遭到奇大升的发难。奇氏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又说过“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混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②。 在奇大升看来,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举,谓之纯理或兼气就有些不妥。奇氏主张四端虽由纯粹的天理所发,但只是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奇大升进一步评论说: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③
他认为四端与七情作为情感皆性状相似,而非有截然相反之特质。因此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学原论的。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回答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盖欲相资以讲明,非谓其言之无疵也。今者,蒙示辩说,摘抉差谬,开晓谆悉,警益深矣。然犹有所不能无惑者,请试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首先说明了其将郑氏之“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进行改动的缘由,他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认为先儒未有将“四端七情”分置于理与气的范畴来讨论的先例。李滉还是认可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在这一问题上他有过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首度对郑之云的《天命图》进行修订时的说法。李滉将郑氏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这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其实此两句从内涵到语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请参见新、旧天命图(图7、图8)。
起初他认为此说“本晦庵说,其理晓然矣”③,其时还未与奇大升展开论辩。二是在与奇氏进行论辩过程中有了第二种表述,即“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④。这是己未年李滉59岁(1559年)时的观点。当此之际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理气”之辨。加之李滉又恰好读到朱子的“四端是发于理,七情是发于气”一句,于是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与奇大升的信中提到:“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三是经奇大升之诘难后便有了新的说法——“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②。此后李滉对这一说法再未作改动,可视为其最终定论。对最后一说,他在其晚年代表作《圣学十图》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③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正是李滉性理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
他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本上的差异,这源于其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①
由此可知,在心性情的关系上李滉倾向张载的“心统性情”说。他将“心”理解为“理气之合”——与朱子“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的观念相比,心的含义以及与理、气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以此说为理论前提,可以分属理气的方式准确表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以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
四端七情之辨实质是性情之辨。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作为李滉晚年思想结晶的《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则为李滉所作。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概念。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此为性理学的主题。性理学的道德主体论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①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如此则性为体而情为用。朱熹认为“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②。与之不同,李滉进一步发挥朱熹的理气心性说并将性情与理气之发相结合,从而将朱子学的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端七情理气”论。此图的中、下两图乃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③对于“七情”的善恶,李滉起初以为“七情,善恶未定也”④。经与奇大升往复论辩之后改为“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故其发而中节者乃谓之和”⑤。这一改动容易造成七情之“善”和四端之“善”之混同,所以对之需作仔细辨析。四端之情是人的道德感情亦即良心。四端之“善”是纯粹的且还带有道德色彩。但是七情则与此不同,原是与道德情感无关之情。作为自然情感,七情在“性发为情”之后才能以发用是否为“中节”衡量其善恶。因此如李滉早年所言,它还是“善恶之未定”。那么,应如何理解其修订后的说法呢?我们可以从其“本善”一语中去寻找。“善”被赋予道德含义之前,“好”是其概念的核心内容。易言之,善是规定事物之好的状态,道德性的善也是如此。“七情”作为原始的自然的感情本是好的感情,只因具有“过或不及”的性质,容易“流于恶”。①其修订后的说法可以按此思路去解读。
对于下图李滉解释说:“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②
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和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遵循程朱“情根于性,性发为情”之原则,依此解读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和无不善之情。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我们也可以一窥李滉试图融合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正是两种权威文本相互冲突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引发韩国儒者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③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说,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还是气发皆可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甚至放而为恶,原因就在理发未遂或者气发不中。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显或气发而皆中节遂成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述引文中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子学的传统——李滉继承这一传统,也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也是情,而“情”必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遂成人性善恶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①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也就是说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自我反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多次对此图进行修改。“盖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中所载本也。”②此图在李滉《圣学十图》中具有的重要性实在是无需赘言。
李滉还以“七情”与“四端”分论“人心”与“道心”,指出“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也。”③这既是对朱子心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学术上的立异。在李滉看来,道心是义理之心即最高的道德原则,所以他在强调四端七情之差异的同时还特别重视道心人心之分别。虽然其中图未言及“气”,但他论性情仍以理气分言之。“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④这也表明李滉心说承继朱子之传统——倾向以“理气心”论性情,而且主张持教工夫。
在论辩的最后,李滉以《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三书》总结二人观点之异:
既曰“浑沦言之”,安有主理、主气之分?由对举分别言时,有此分耳。亦如朱子谓:“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又云:“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
前书引性言者,只为在性犹可兼理气说,以明情岂可不分理气之意耳,非为论性而言也。“理堕气质以后事”以下,固然,当就此而论。
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碍者乎?而况所谓四端七情者,乃理堕气质以后事,恰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则有明有暗,四端则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固因水之清浊而四端之不中节者,则光虽明而未免有波浪之动者也。伏乞将此道理更入思议,如何?
“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说,尝见先儒有论其不可,今不记得……敢问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者,为发于理耶?为发于气耶?而发而中节,无往不善之善,与四端之善,同欤?异欤?虽发于气,而理乘之为主,故其善同也。且“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谓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则只有理发一边。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未知于先生意如何?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发矣。若欲外此而更求理之发,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弊。前书亦以为禀,而犹复云云。苟曰未然,则朱子所谓“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者,亦不可从也。
道即器,器即道。冲漠之中,万象已具,非实以道为器;即物而理不外是,非实以物为理也。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用朱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也。
以“气顺理而发”为理之发,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①此信写就之后李滉或觉没有必要继续与奇氏论辩,故而未将信寄给他,只是针对奇氏来信中的质问撰文阐述自己的主张。李滉的基本观点是四端七情混沦而言时则无需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但是若将二者对举而言则应以主理、主气来分言。他还以“因说”和“对说”来解释了此问题。直至结束辩论二人仍各持己见,并未达成一致。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以为不仅“性”可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若说奇大升注重于对问题的客观性、逻辑性的阐明,李滉则更着力于对道德性的提高以及修养工夫论域中的主体的省察和践履的意义。
“四端七情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赓续朱子的理气心说,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无怪乎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此种理解,李滉进一步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他对七情的看法始终落在气的一边。他说:“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不能无理,所以“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四端”需要扩充,而易“流于恶”的“七情”则要受检束。因为二者各具相异的性质,如何理解其异中之同便值得认真思考。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说:“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若从客观的视角对情之结构做静态分析的话,便可以得出“四端”为“七情”之一部分的结论。但是在道德践履的意义上,二者又具有相反的性质。比较而言,奇大升关注前者,李滉则更倾向于后者。当然此种差异是相对的。两人真正的分歧源于各自在为学旨趣及问学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的问题意识。
要言之,“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中的核心内容。基于理气二分的立场李滉肯定情的“四七”之分,以为恻隐、善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是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而发,即缘境而出。不过依其理气心,“心气”之性质及所为,如气之清浊、偏杂、粹驳之状态,直接决定四端之呈显以及七情之善恶性质。李滉以为,“气”之状态影响理之显否,故在修养论上他特别主张施以主敬涵养工夫治“心气”之患,使气皆能循理而发以保证理发直遂而不被气所掩。
三、李滉的主敬论——以《圣学十图》为中心
李滉之学亦被称为主敬之学。因此下面将通过对《圣学十图》的分析来探讨其以主敬说为特色的性理哲学思想。
《退溪全书》“言行录”中记载,其门人金诚一将其学问概括为“试举其学大概,则主敬之工,贯始终兼动静,而尤严于幽独肆之地,穷理之功,一体用该本末,而深造于真知实得之境,用功于日用语默之常”。①主敬思想的基本论纲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敬以直内,涵养本心;义以方外,省察行事。尽管李滉所依傍的是程朱的主敬之说,但是其主敬之说知行并重,贯始终兼动静。其学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又比程朱更强调“心”之作用和效用,也因之更加明确地揭示了“敬”之为学工夫与进入圣贤域以达至圣人的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
作为“东方之朱夫子”,李滉为学服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对朱子学的理气心性诸说多有发明。李氏68岁(宣祖元年,1568年)时进呈宣祖的《圣学十图》更是其学问宏纲大目的集中反映,也是其一生学问的思想结晶。可谓“晚年深思熟虑,提纲挈领的结晶,也是他体认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心得。李滉独以图的形式,既示人以圣学入道之门,亦给人以简明易懂的启迪。《圣学十图》,融铸宋明理学之精髓,构成他的思想逻辑结构,其规模之宏大,操履之功用,在李朝理学史上均属罕见”②。《圣学十图》由《进圣学十图札》和《圣学十图》组成。所谓十图包括:第一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第二图为程复心(字子见,号林隐,1279—1368年)绘的张载的《西铭图》;第三图为李退溪绘的朱子的《小学图》;第四图为阳村权近绘的朱子的《大学图》;第五图为李滉绘的朱子的《白鹿洞规图》;第六图为《心统性情图》(上图由程复心作,中、下二图由李滉作);第七图为朱子的《仁说图》;第八图为程复心绘的《心学图》;第九图为王柏(字会之,号鲁斋,1197—1274年)绘的朱子的《敬斋箴图》;第十图为李退溪绘的陈柏(字茂卿,号南塘,元儒)的《夙兴夜寐箴图》。对于上述十图,李滉还做了相应的引述和说明,指出前五图是“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③,后五图则是“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④。综观十图,“敬”①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纲目。
《圣学十图》的排列次序不仅体现了李滉哲学的逻辑结构,而且还反映了其对儒学(圣学)的全部理解。第一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李滉对此解释说:
朱子谓此是道理大头脑处。又以为百世道术渊源。今兹首揭此图,亦犹《近思录》以此说为首之意。盖学圣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于小学大学之类,及其收功之日,而溯极一源,则所谓实理尽性而至于命,所谓穷神知化,德之盛者也。②
朱熹立学极重周敦颐之《太极图》,此图可说奠定了“濂溪先生”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开山之祖的地位。李滉认为太极即是宇宙本体(天道),故将《太极图》视为百世道术之渊源亦即一切思想学说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强调学圣人者要“求端自此”。李滉将周敦颐的《太极图》理解为对《周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义的阐发。依李滉之见,圣人是“与天合德,而人极以立”,因此圣人之学便是继天立极之学。他认为此图的目的在于阐明圣学的理论根据,而且还揭示如何以抵达圣域的修养工夫。李滉进而引用朱子的《太极图说解》以作说明:“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间而已矣。敬则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静虚动直,而圣可学矣。”③《太极图》表明了以“敬”为核心的为学路数,具有将天道、地道和人道加以融合以作整体观照之特性。而其他九图皆为此图(“立太极”和“立人极”)的进一步展开。此其所以《近思录》、《性理大全》等开篇即设有《太极图》——李滉可以说继承了这一理学传统。
第二图为《西铭图》,旨在揭示天道的进一步展开。该图试图从对“求仁”的深刻体悟中阐明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道理。李滉以为“圣学在于求仁,须深体此意,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一体,真实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味,免于莽荡无交涉之患,又无认物为已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体也。又曰:充得尽时,圣人也。”①这是李滉体仁的最高境界,于此彻悟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强调物我一体论与事亲事天之实践,他在《西铭图》图说中写道:“朱子曰……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②天道以仁为本质。人只有懂得其所具之仁便是天地生生之理(太极),才能扩而充之与天地生生之理的合而为一,从而达到民胞物与的境界。这就需要通过心性修养、涵养工夫以提高人的素质,方能使其内心之德臻于完满。李滉将《太极图》与《西铭图》视为理学形而上学理论和修养工夫的根据,即小学大学的标准本原。“上二图,是求端扩充,体天尽道,极致之处,为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下六图,是明善诚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③
正是基于此种考量,李滉分别以《小学图》、《大学图》和《白鹿洞规图》为第三、四、五图。《小学》是朱熹所编的一个以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本。朱子极重小学,将其与大学并列。朱子学传入之初,朝鲜朝儒者便对《小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阳村权近曾写道:“小学之书,切于人伦世道为甚大,今之学者皆莫之习,甚不可也。自今京外教授官,须令生徒先读此书,然后方许他经。其赴生员之试,欲入大学者,令成均馆正录所先考此书通否,乃许赴试,永为恒试。”④李滉在《小学图》中,援引朱子的《大学或问》写道:“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涵养本原,而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⑤从中亦可看出李滉对小学的重视。他在继承和发展朱子思想的基础上,以敬身明伦为旨归将小学教育的组织、内容、目的、宗旨提纲挈领。《小学图》反映了李滉强调实践、注重践履的为学性格。李滉根据朱熹的《小学》一书的目录制作此图,以与《大学图》对举。在他看来小学和大学相反相成,是“一而二、二而一”①的关系。前文已言及《大学图》乃朝鲜朝初期的阳村权近所造。“大抵《大学》一书,一举目,一投踵,而精进本末,都在此。”②《大学》是被朱熹视作学者入德“行程节次”③的一本书,亦是其平生用力最久、最甚的一部儒家经典。朱子曾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全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④李滉认为为学者只要按此“行程节次”认真践履、勇猛精进便可达至圣域。《大学图》的特色在于引述朱子《大学或问》的论“敬”之说以为圣学的始终之要。“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尝以主一无适言之,尝以整齐严肃言之;门人谢氏之说,则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有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小学之赖此以始,则夫大学不能无赖于此以为终者,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盖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则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是诚意正心以修身,则所谓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乎天下,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离乎敬也,然则,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⑤本段引文对李滉《圣学十图》的主敬思想影响甚大。尊德性而道问学、居敬而穷理是理学的基本立场,朱熹曾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⑥认为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存养,不过朱熹实际上以“穷理”、“致知”为先。李滉指出:“非但二说(即《小学图》与《大学图》所引朱子论教之说)当通看,并与上下八图,皆当通此二图而看……下六图是明善诚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而敬又彻上彻下,着功收效,皆当从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之说如彼,而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①由此可见,“敬”在李滉哲学中并不仅仅是彻上彻下、贯穿动静始终之修养工夫,而且还是可以统摄存心养性与格物致知的圣学第一要义。《圣学十图》即是其主敬思想的集中体现。第五图《白鹿洞规图》是李滉依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而作,旨在阐明人伦之道。“盖唐虞之教在五品,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故规之穷理力行,皆本于五伦。”②李滉认为大学是小学阶段的延续,而两阶段的教育有着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穷理、力行)、在止于至善,而小学之宗旨则为在明人伦(五伦),所以说“此两图可以兼收相备”③。《白鹿洞规图》意在综合小学、大学的为学之方,着重突出五伦作为圣学内容的重要地位。另外,从《白鹿洞规图》中亦可看出李滉的书院教育思想。李滉以为以上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④。
心、性、情是理学人性论的核心范畴,第六图即为《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此图在上一节已有论及,这里只做简要介绍。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下图为李滉所作。在朝鲜朝儒学史上,主要论辩皆围绕“心”这一哲学范畴而展开。16世纪后半期的“四端七情”之辨、“人心道心”之辨、18世纪初叶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以及19世纪后半期的本心明德之“主理主气”论辩等均是对“心”之发用及相关问题的深入辨析。此为韩国性理学的特色所在。
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理学的主题。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就是通过“心性情”等范畴全面展开。⑤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一言蔽之即性为体情为用。朱熹认为“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①。李滉则与之不同。他进一步发挥程朱理气心性说,将性情之说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并将朱学心性论深化为以性情为中心的“四七理气”之辨。《心统性情图》之中图和下图将李滉理气心性诸说表述得最为简单明了。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秉承之,亦主“合理气,统性情”。但是,李滉比朱熹更专注于对“情”的探讨。重“情”乃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理气心”。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此心具心气之患)的“情”皆能中节便成为心性修养的关键所在。李滉主张以敬治心气之患,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的原因即在于此。故其曰:“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②其持敬之目的就是要由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之际反观内省以求致中和。至去世前为止,李滉曾对此图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第一图的结构原是智上礼下仁左义右,先是对其中礼智上下结构进行改动,后来又对原图中的仁义左右次序做了修改。最后还是以第二次改动的为定本,收录十图之中。③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第七图为朱熹自作的《仁说图》。李滉曾将此图放于《心学图》之后,后接受李珥的建议移至《心学图》之前。他在给李珥的复信中写道:“《仁说图》当在《心学图》之前,此说甚好,此见解甚超诣。滉去年归来,始审得当如此,及得来说而益信之,即已依此说互易矣。”①由此亦可窥出《圣学十图》中各图的排列次序是经过了反复斟酌与思考。该图进一步说明了四德相互之间以及其与四端之间的关系。“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未发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则包乎四者。”②“仁”作为统摄“四德”与“四端”的道德理性,在理学中不仅与太极、诚以及中和等概念同等重要,而且还指代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人和天地生物皆以之为心。李滉将朱子学的仁说视为上承天道下启存养之途,亦即贯通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节点。这应该是李滉最终把此图置于《心学图》之前的重要原因。由其“圣学在于求仁”之见以及此图“发明仁道,无复余蕴”之说可以推知,在李滉的心目中人君者欲施仁政亦应于此图求其义。故《仁说图》在《圣学十图》中亦居重要地位。
第八图为程复心所绘《心学图》。李滉将此图目为天地生物之心(仁)的着足处。李滉性理学“求仁”之目的在于使人不断完善其人格,以优入于圣域。“此仁者,所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足以普四海弥六合也。”③《心学图》把“心”分为赤子心与大人心、人心与道心,也是为了给人提供实现理想人格的修养工夫。学者只有“惟精择善,惟一固执”,才能克去己私以存天理。所以必须施以“持敬”工夫使人心变为道心。唯有以“敬”抑欲才能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加之“敬”又是一心之主宰,存理遏欲的工夫大可统一到“敬”字上来。就此而言,“存天理遏人欲”是主敬工夫之实质内容。对《圣学十图》中的后五图,李滉认为“五图原于心性,而要在免日用崇敬畏”④。他在第六、第七图中着力探究主体之性情问题后,便将“天地生物之心”作为仁之根据。李滉在第八图中又论述了与“心”相关之问题,并指出了治心之工夫以及“敬”作为一心之主宰在涵养省察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第九图为金华王鲁斋柏就朱熹《敬斋箴》绘制的《敬斋箴图》,此箴乃朱熹有感于张敬夫的“主一箴”所作。若说第八图示“圣学心法”,那么此图则“为圣学之始终”。此图承《心学图》之旨,继续以“敬”为工夫之要以示具体的用工地头。在图说中,李滉引真西山之言曰:“敬之为义,至是无复余蕴,有志于圣学者,宜熟复之。”①这表明李滉不仅将“敬”视为其存养工夫的关键,而且还视为其性理学体系之核心。他在答李叔献(李珥)的信中写道:“惟十分勉力于穷理居敬之工。而二者之方,则《大学》见之矣,《章句》明之矣,《或问》尽之矣。足下方读此书,而犹患夫未有所得者,得非有见于文义,而未见于身心性情之间耶。虽见于身心性情,而或不能真切体验,实味膏腴耶。二者虽相首尾,而实是两段工夫,切勿以分段为忧,惟必以互进为法,勿为等待。即今便可下工,勿为迟疑。”②《敬斋箴》内容如下:“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参以三,惟心惟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弗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论,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灵台。”③这些可视为“敬”的具体细目,可以此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李滉还依据陈柏的《夙兴夜寐箴》绘制《夙兴夜寐箴图》④以为第十图。他认为“敬斋箴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其地头而排列为图。此箴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其时分而排列为图。”⑤第九图《敬斋箴图》与第十图《夙兴夜寐箴图》一是以地头言,一是以时刻言。①即,前者按行事罗列,是以心为核心展开的主敬工夫;后者是依时间编排,是以行为核心演绎的持敬规范。②李滉曰:“盖敬斋箴,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时其地头而配列为图。此箴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时分而配列为图。”③但道之流行于日用之间,无所适而不在,亦无顷刻之或停,因此李滉强调不分时分与地头的主敬工夫。两者在李滉性理学中相互发明、相互补充均为相当紧要,因之李滉言二者须并进。
《圣学十图》前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体现了《太极图》融自然本体、社会教育、人格培养为一体的思想;后五图则“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与前五图恰好构成不即不离的体用关系。前五图以无极太极为第一图,后五图以心统性情为第一图。这个划分不以天道人心为二,而是将二者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形而上本体遂与人世间的心性冥冥相通,立人极也就可以进而立太极。④易言之,后五图则展示心体(天道)呈现之修养过程。“综观此十图,其核心是人。因此,李退溪的圣学,我们亦可称为人学,即学做圣人之学。《圣学十图》,就是学做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情感意志等等。全面、系统而又渐次深入地论述了为圣的目的、方法。”⑤依李滉之见,除了“心”之外再没有完成自我人格的原动力。关键在于如何克去除理气心所具有的心气之患,从而使心气循理而行、顺理而为。这就要求学者时刻以“敬”字治心、以“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⑥。显而易见,以持敬工夫统摄心知乃是李滉主敬论的主要意涵。
由上所述可知,李滉主敬思想根植于其对性理学理气心性诸说的理解。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七情之善与不善端视发而中节与否——一切都随“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其实此时四端与七情皆滑入气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皆为气之所为。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皆为气之所为。所以主敬以治心上之“气患”,使气顺理而发、循理而行,这就是以主敬说为特色的李滉思想的根本主旨。
简言之,李滉以“敬”贯动静、知行并重以及内外如一为其主敬思想的方法论,由此构筑了以主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绘制的《圣学十图》以图画的形式将程朱理学中繁杂的主敬思想做了言简意赅的表述。此图既是主敬工夫的形象说明,也是李滉思想的简明提要。
“敬”作为理学修养的重要方法受到程朱诸儒的重视。朱子以为“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程子亦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语最妙”②。但是程朱诸儒并未以此为纲领构筑其道德形上学体系。朱子去世三百年后,号为“海东朱子”的李滉却以“敬”为核心构筑了颇具理论与践履特色的“实践道德哲学”(后人亦将之称为退溪“圣学”或退溪“心学”),遂集朝鲜朝的朱子学思想之大成。李滉对“敬”的强调与对“敬”的意义的理解确有超过朱子处。③以此为特色,退溪学代表了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李滉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坚持二者是不同类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④李滉还制作“心统性情图”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工夫论方面,李滉极重主敬,以下学上达为其居敬穷理之出发点。“只将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以验夫统体操存不作两段者为何等意味,方始有实用功处,脚跟着地,可渐渐进步,至于用功之久,积熟昭融,而有会于一原之妙,则心性动静之说不待辩论而嘿喻于心矣。”①他主张由下学上达之持敬修养工夫优入圣贤之域,从而体验天理之极致。由此可知李滉的道德学问观以及其为学的根本宗旨。“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②,李滉在知与行方面忠实履行了儒家之为学宗旨,堪称朝鲜朝五百年间难得的为己之学之楷模。
他的思想不仅对韩国性理学界影响至深,而且还对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启蒙传疑》、《自省录》、《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圣学十图》、《论四端七情书辨》等,均收录在《增补退溪全书》(1—5册)之中。
第三节 奇大升与其“四端七情”论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最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之特色。但是,他的四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与奇大升之间展开的相互问难。在与奇大升论辩过程中,不仅李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其立场也变得更加鲜明。本节将对奇大升“四七理气”论思想作一论述。
一、奇大升的理气论——兼述《论困知记》
奇大升(字名彦,号高峰、存斋)亦是朝鲜朝重要性理学家,生于中宗二十二年(1527年),卒于宣祖五年(1572年),谥号为文宪。他出生于全罗南道光州召古龙里松岘洞。③32岁中文科乙科第一人,后官至大司谏。奇氏天资聪敏,博览强记,长于论辩。33岁时便与李滉围绕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进行了长达8年的相互问难,由此拉开了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四七理气”论辩之帷幕。
理气问题是性理学的首要问题,奇大升亦十分重视此问题。他在信中写道:“然鄙意以为当于理气上,看得分明,然后心性情意,皆有着落,而四端七情,不难辩矣。后来诸先生之论,非不详且明矣。然质以思孟程朱之言,皆若异趣似于理气上未剖判也。”①依奇氏之见,若于理气问题上看得分明则心、性、情、意及四端七情诸说皆不难辩,故可将其理气说视为他的“四端七情”说的立论基础。于此也可以看出,他是追求理气说(存在论)与心性论相一致的性理学家。奇氏这一致思倾向与李珥有相似之处。下面将分析他的理气概念以及在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他用太极阴阳说规定了理气概念。“至于天地上分理气,则太极理也,阴阳气也。”②他以太极阴阳论定义理气的同时,将此贯彻到人和物上进一步指出:“就人物上分理气,则健顺五常理也,魂魄五脏气也。”③这表明奇氏以传统性理学形上、形下之理论来理解理气。
其次,在理气关系上,奇大升以理为气之主宰,以气为理之材料——强调理对气的主宰性乃其思想之特色。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④
理为气之主宰就意味着理对气之运动的主导作用。但他在强调理的主宰性的同时又指出理的脆弱性,即理无眹而气有迹。“理弱气强”似与理的主宰性相矛盾。其实这也是朱学理气论的困境所在,因为在朱子哲学中“理”就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⑤之“三无”特性。奇氏有言:“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①这是他在信中质疑李滉“理发”说的一段文字。如何化解本体义上理的主宰性与流行义上理的脆弱性矛盾以使气顺利而发?这是每位理学家都要面临的重要理论课题。欲分析奇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要从其理气关系的解读上着手。
再次,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奇氏强调二者的不离义,此即理气“混沦一体”说。但是在此问题上他又力主既要“合看”又要“离看”。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在奇大升看来,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③,因此学者于此应特别要“精以察之”。依其对理气的规定,理无眹而气有迹,故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他评论说:“盖理无眹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④非以理气为一物,而却“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奇氏的这一观点与明儒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47年)的理气为一物,“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的主张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罗整庵的《困知记》传入韩国后引起较大反响,有尊奉之者,也有批判之者。李滉和奇大升即属后者,二人皆撰文予以批判。李滉写了篇《非理气为一物辩证》,奇大升则写了篇《论困知记》。
《高峰集》中记载:“明学者罗钦顺,号整庵,作《困知记》以理气为一物,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为不然。若著‘所以’字,则便成二物云,又以‘道心为体,人心为用’。此书新出,而世之学者莫能辨其是非,或有深悦而笃信者。戊辰五月,大升以大司成,诣阙至玉堂与副提学臣卢守慎,共论《困知记》。守慎以整庵之言为至当,而无以议为。大升力辨其非曰,朱子以为道心源于性命之正,人心生于形气之私,固以理气分而言之矣。整庵认理为气,以理气为一物,故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种种新奇之说,皆从此出。何可背圣贤相传不可易之说,而从罗整庵之新奇乎?遂著困知记论以辨之。盖其正见,不眩于似是之非,而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反复纡余,光明俊伟粹然一出于正,此李滉所以敛袵者特深也。”①“戊辰五月”,即为宣祖元年(1568年)5月,时奇氏42岁。不过据其《年谱》记载,奇大升在明宗二十年(1565年)12月往见卢守慎(字寡悔,号苏斋,1515—1590年)于镇国院,并与之讨论了人心道心问题。②卢氏以罗整庵《困知记》的理论为依据论述了其对人道说的看法。可见,他的《论困知记》一书是在与卢守慎展开论辩过程中完成,也是其思想成熟期的著作。③此书对了解奇大升的理气性情学说特点以及《困知记》一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此文的开头奇氏写道:
罗整庵《困知记》,世多尊尚。余尝观其书,闳博精邃,顿挫变化,殆不可测其涯涘。试提大概则推尊孔孟程朱,为之宗主。援据《易》、《诗》、《书》、《礼》,以张其说,而又能躬探禅学而深斥之。其驰骋上下,抑扬予夺之际,可谓不遗余力矣。世俗悦其新奇,而不究其实,宜乎尊尚之也。然愚之浅见,窃尝以为,罗氏之学,实出于禅学,而改头换面,文以圣贤之语,乃诐淫邪遁之尤者。使孟子而复生,必当声罪致讨,以正人心,固不悠悠而已也。④
从引文中可以概见,《困知记》传入韩国之初作为“新奇”之说颇受世儒的尊尚。这与《困知记》在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罗钦顺为江西泰和人,生于宪宗成化元年,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父死服阙后起原官,嘉靖六年坚辞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之召,致仕居家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致之学。他与其时的名儒王阳明、湛若水及欧阳德等人皆有往复辩论①,是在朱学阵营中为数不多的能与心学分庭抗礼的大儒。他的著作有《整庵存稿》二十卷和《困知记》六卷,而其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困知记》一书中。但《困知记》问世后并未受到中国学界关注,而却在韩国引起不小的波澜。如引文内容所见,有尊尚者亦有排斥者。奇氏则直斥罗氏之学“实出于禅学”,即便是孟子复生亦必当声罪致讨以正人心。
他指出虽然罗氏的个别观点和圣贤之道也有相符之处,但是其大纲领大根本却与之相去不啻百千万里之远。他还举了罗氏《困知记》中的具体论点以说明其主张皆与圣贤本旨相违,舛错谬戾不须更辨。
《记》凡四卷,益以附录,无虑数万言。其间,岂无一二之几乎道,而其大纲领大根本,与圣贤相肯,不啻百千万里之远。则其学之邪正,为如何哉。其书所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及“理气为一物”及“良知非天理”云云者,皆与圣贤本旨,舛错谬戾此,不须更辨,而其出于禅学之实,则不可以不辨也。②
尽管奇大升也主张理气“混沦一体”说,但是与罗氏的“理气为一物”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看来,罗氏之学“其出于禅学之实,则不可以不辨”。罗钦顺的《困知记》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已难以确知,但是从奇氏这段文字中可推知,起初传至韩国的《困知记》并非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六卷《困知记》,而是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年)五月完成的4卷本——是年罗氏69岁。在《困知记》序中,他写道:“余才微而质鲁,志复凡近。早尝从事章句,不过为利禄谋尔。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虽已晚,然自谓苟能粗见大意,亦庶几无负此生。而官守拘牵,加之多病,工夫难得专一,间尝若有所见矣,既旬月或逾时,又疑而未定,如此者盖二十余年,其于钻研体究之功,亦可谓尽心焉耳矣。”①罗氏这部著作的写作前后历时二十多年。当完成“四续”时已是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五月,其时他年已82岁。全书由卷上、卷下、续卷上、续卷下、三续、四续共六卷和附录构成。奇氏文中所提及的“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理气为一物”及“良知非天理”等的确是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所阐述的理论主旨。罗氏在《困知记》开篇即讲:“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然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②又说:“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③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渐趋衰落,而陆王心学声势日隆。罗氏对此深以为忧,于是将辨明“心性之别”以批驳陆王的“良知即天理”说作为其历史使命。职是之故,罗氏立学极重“心性之辨”。他以为心性的关系是既不相离又不能相混的,二者之别甚是微妙。若于心性的分际区别上,稍不清晰,便真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由此他将“道心”与“人心”关系定义为体用关系,这就是其独特的“人心道心体用”说。
那么,被称为“朱学后劲”的罗氏学说为什么会受到同样遵奉朱学的韩儒李滉、奇大升等性理学家的批判呢?这主要是因于其“理气为一物”的思想和由此引申出的“人心道心体用”说。于此可见,至16世纪中韩两国朱子学的发展已各呈不同的义理旨趣,此与韩国性理学者与中国朱子学者所处的不同人文语境与各自所倚重的不同核心话题相关。对于这一问题,讨论李珥理气说时再做进一步分析。
奇大升以为,罗氏之所以提出“理气为一物”、“人心道心体用”说等主张是因其学源自禅学之故。故在《论困知记》一文中,他力图揭露罗氏学说“实出于禅学”的“真相”。于是,奇氏在文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与此相关的内容:
整庵自言“官京师,逢一老僧,闻‘庭前柏树’之话,精思达朝,揽衣将起,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云云,此则悟禅之证也。后官南雍,“潜玩圣贤之书,研磨体认,日复一日,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云云”,此则改头换面,文以圣贤之语之实也。此之分明招认,固不可掩。而又有其论道理处,尤显然而不可掩者焉。《记》上第五章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一,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用也,精微纯性之真也。释氏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故其为教,始则欲人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空即虚也。既则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觉即知觉也。觉性既得,则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神即灵也。凡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使其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识矣。顾乃自以为无上妙道,曾不知其终身,尚有寻不到处,乃敢驾其说,以误天下后世之人云云。”
以此一章观之,其学之出于禅学者,益无所遁矣。夫心之虚灵知觉,乃理气妙合,自然之妙,而其或有不能然者,特以气禀物欲之蔽,而失其正耳。人苟能操而存之,不为气禀物欲之所累,则其虚灵知觉之妙。固自若也,非如释氏之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然后心始虚也。又非如释子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然后心有知觉也。又非如释子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然后心可谓之神也。此与圣贤所论虚灵知觉者,同耶异耶?其亦不待辨而可知其非也。
且既曰:“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而继之曰:“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然则圣贤之论心,亦与释子无异致耶。“离诸相,契虚觉,而洞彻无方者”,乃释子之作弄精神,灭绝天理者也。今乃欲与圣贤之论心者,比而同之,其可乎,其不可乎。
又曰:“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可识。”夫欲适越而北其辕,终莫能幸而至焉。今乃欲据释子所见之及,而向上寻之,以识夫帝降之衷,吾恐其如北辕而适越,终身伥伥,竟无可至之日也。
整庵之学,初既悮禅,而后观圣贤之书以文之。故其言如此,殊不知儒释,道既不同,而立心亦异有如阴阳昼夜之相反,乌可据彼之见,而能为此之道乎。①
罗钦顺自述其一生孜孜求道,用心甚苦。先由禅学悟心之灵妙,后识吾儒性命之旨。年垂六十,才自认为有见于性命之真。②其学思历程中确有一个出入佛道的经历(早年由禅学而入),《明史》亦记载道:“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③罗氏从“佛在庭前拍树子”话头得悟后,始知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虽相似而实不同——释氏大抵有见于心而无见于性。他指出今之世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在罗氏看来,道之不明正由于此。由此而论,奇氏批驳钦顺之学“实出于禅学”一说似难成立。在《困知记》一书中罗氏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禅宗经典《楞伽经》以及达摩、宗杲等重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批判。连《明儒学案》也提到“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④其实,钦顺之学是建立于程朱的“理一分殊”说之上,罗氏曾说过:“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简而尽,约而无所不通,初不假于牵合安排,自确乎其不可易也。”⑤又说:“一旦于理一分殊四字有个悟处,反而验之身心,推而验之人人,又验之阴阳五行,又验之鸟兽草木,头头皆合。于是始涣然自信,而知二君子之言,断乎不我欺也。愚言及此,非以自多,盖尝屡见吾党所著书,有以‘性即理’为不然者,只为理字难明,往往为气字之所妨碍,才见得不合,便以先儒言说为不足信,殊不知工夫到后,虽欲添一个字,自是添不得也。”①可见罗氏之学大体是接续程朱而来,但是在理气观方面已与程朱有了较大不同。那么,为什么同尊朱子的奇大升与罗钦顺间会有如此大的理论分歧呢?这主要源于二人对“理”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并对其“理”的特性有不同的界定。奇氏力辩罗氏之学的“禅学之实”乃因二人的理气观差异甚大,所以他紧接着就对罗氏理气说与心性说不一致提出批评。奇大升对钦顺的理气观极为不满,批评亦较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内容。学者于此不可不察。
前面已论及,奇大升是追求理气论与心性论相合一的性理学家。于是,他对罗氏思想中的两论不一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佛氏“作用是性”之说,固认气为理,而以心论性也。整庵实见之差,实由于此。故理气一物之说,道心人心性情之云,亦皆因此而误焉。盖既以理气为一物,则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属理气。故其为说,必至于如是,而整庵之所自以为向上寻到者,亦不过于佛氏所见之外,知有理字。而其所谓理字者,亦不过于气上认其有节度处耳。整庵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者,正是此病也。虽其为说,张皇焜耀,开阖万端,而要其指归,终亦不出于此矣。
且整庵每自谓至当归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夫既以理气为一物矣,而又以体用为二物焉,并引“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以证体用之为二物。若曰:道是体神是用,而道与神为二物,则理气果一物乎?理气果一物,则道与神,又何以为二物乎?整庵又以心与性,为体用之二物,心与性,既是二物,与理气为一物之说,不亦矛盾之甚乎?②
奇氏认为钦顺之学有“认气为理”以及由此引生的“以心论性”之病。他进而指出,罗氏自以为向上寻到者,亦不过于佛氏所见之外知有一个“理”字。而其所谓“理”字者,亦不过于气上认其有节度处耳。所以奇大升直言,“整庵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者,正是此病也”。又指责说整庵每自谓至当归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既以理气为一物,则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属理气。”奇氏所要强调的是理学“体用一源”之原则,故指责罗钦顺“以心与性,为体用之二物,心与性,既是二物,与理气为一物之说,不亦矛盾之甚乎?”既然理气为一物,体用就不能析为二物。
在东亚儒学史上奇大升是最早具体指出罗氏学说之内在矛盾的学者。对于此不能“归一”性,被称为宋明理学殿军的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年)和《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1610—1695年)师生亦有评述。刘宗周指出:“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谓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不免抛自身之藏。”①黄宗羲则更直接指出:“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①当然,这是刘宗周与黄宗羲师弟基于心学之立场对罗氏之学作出的评判。但是,谨遵朱子之学的奇大升和秉持心学立场的刘、黄等人先后都对罗氏学说的自相矛盾提出批评。此一现象表明作为儒者他们皆以体用一源为共法,而其理论也因之具有相近的思想倾向。这无关各自的具体学术主张。就哲学体系的完整性而言,一个思想家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后者应为前者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有些当代学者因此十分肯定刘、黄二人对罗钦顺的批评。②当然也有人对刘、黄师弟对于罗氏学说的批评不以为然。③分歧的产生与朱子哲学特殊的义理架构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朱子哲学在存在论(理气论)意义上倾向理气二分(“不离不杂”)和以理为主的理本论;而在心性论意义上则偏于以性、情、心三分结构为义理间架的“心统性情”论。④陈来先生曾指出,以“心统性情”为代表的朱子心性论结构的表达并非“理/气”二分模式,而是“易/道/神”的模式。盖因心性系统乃一功能系统,而不是存在系统。因此黄宗羲等人以“天人未能合一”来批评朱子的理气论未能贯通到心性论,似与事实有悖。实际上在朱学中理气观念并非没有应用到“人”。朱子使用“性理/气质”来分析人的问题即与其理气观一脉相承。①陈来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对朱子“心”论的理解有帮助,而且对罗氏学说的不一致性以及韩国儒学“四七理气”之发问题的理解亦大有助益。
在论述权近、郑之云等人的性理学时已言及,韩国性理学者在探讨性理问题时皆热衷于追求“天人心性合一”——摄理气于心乃韩国性理学之特色。因此相较于中国朱子学的理气说,韩国性理学的理气说更多带有性情论色彩。韩国儒者借此以说明性情之辨以及性情之发等问题。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奇大升的“理气共发”说以及李珥的“气发理乘”说皆可从这一角度得到深入的理解。否则很难解释倡言“理发理动”②以及“太极自动静”③的李滉何以能被称为“东方之朱夫子”。
在《论困知记》文末,奇氏还批评了罗氏的“良知非天理”说。曰:
整庵又论良知非天理,而云“知能是人心之妙用,爱敬乃人心之天理”,然则天理在妙用之外,而妙用者无与于天理乎。夫天理之在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此心之所以统性情。而其未发者,寂也体也;其已发者,感也用也。然则爱敬者,为未发耶,已发耶。知能,虽皆心之用,而有真妄邪正之分,固不可皆指以为天理矣。若加一良字,则乃本然之善,岂非天理之发乎。今以爱敬为天理,而以良知为非天理,爱敬与良知果若是其不同耶。且以知能为心之妙用,而不察乎真妄邪正之实,则尤不可。佛氏之神通妙用,运水般柴之说,正坐不分其真妄,而皆以为妙用之失也。昔有问于胡文定公曰:“禅者,以枯槌竖拂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为用,用而不妙。须是动容周旋中礼,方始是妙用处。”以此而揆诸整庵之言,其是非得失亦可见矣。整庵尝论宗果,以为“直是会说,左来右去,神出鬼没,所以能耸动一世。”余以为整庵之状宗杲者,乃所以自状也。
噫,道丧学绝,世俗何尝知此意思。见余之论,必以为笑,不谓之狂,则谓之妄也。然余亦岂欲必信于世俗,而与哓哓者相竞。将以俟后来之君子尔,同志之士,幸相与谅之。①
从奇氏对罗整庵的批评中可见,他对罗氏的“良知非天理”说的理解上有些偏差。前面已论及,明中叶以后程朱之学渐显颓势,王学日渐兴盛。在此情形之下,罗氏愤而扛起朱学大旗,欲明“心性之辨”以批驳“良知非天理”说。他将此作为理论活动的首要任务。罗氏曰:“夫孔孟之绝学,至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尝认良知为天理也。以谓有物必有则,故学必先于格物。今以良知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此语见《传习录》。来书亦云:‘致其良知于日履之间,以达之天下。’),则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无乃不得于言乎(《雍语》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本体,岂可于事物上寻讨?’总是此见。)!”②可见罗氏倾向程朱的“性即理”,而非“心即理”。因此他认为“有物必有则,故学必先于格物”——“格物”即为克己之私的过程。依罗整庵之见,“良知为天理”的说法过分强调个体之慧悟,极易将艰苦的修养工夫化为简易的禅悟,这是学人需警惕的非常危险的理论动向。显而易见,罗氏所批“良知”是指阳明的“致良知”。而奇氏所理解之“良知”则为基于伊洛渊源的良知、良能,也就是本然之善。于此也可以窥出奇氏的心性说仍以程朱的心、性、情三分义理间架为基础。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并不同意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那么,应如何理解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呢?对此奇氏有如下表述:
喜同恶离,乐浑全厌剖析,乃末学之常累。然鄙意固未尝以是自安也,亦欲其一一剖析尔……又或问: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朱子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端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然,则气之自然发见,过不及者,岂非理之本体乎……至于极论其所以然,则乃以七情之发,为理之本体,又以气之自然发见者,亦非理之本体,则所谓发于理者于何而见之,而所谓发于气者,在理之外矣。此正太以理气分说之失,不可不察也。罗整庵所论不曾见得,不知如何。若据此一句,则其误甚矣。若大升则固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也。①可见,奇大升主张的是基于“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的理气“混沦一体”说。他以为理气虽不可谓二物,但也不能视为一物,“若以为一物,则又无道器之分矣”②。因此在奇氏看来,罗整庵以理气为一物,“其见甚乖”③。其实,奇大升的“理气混沦”说与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理”作为“所以然”者的地位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牵涉到对“理”的主宰义的不同认识。奇氏强调理的主宰作用,所以不满“理气一物”论。“整庵则以理气为一物,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为不然。谓若着‘所以’字,则便成二物云云。”④但上一段引文中奇氏所言“罗整庵所论不曾见得,不知如何”一句则需做进一步商榷。此言出自奇大升回复李滉的“高峰第二书”中。据研究,奇氏大约是在戊午年(32岁)或己未年(33岁)已读到《困知记》,故与李滉开始“四七理气”论争之前很有可能已受《困知记》思想的影响。①而且,李滉将奇氏己未年“高峰第一书”中的“七情中四端”以及“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等观点,评为与整庵的“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②。由此可见其时李滉也认为奇氏思想受到罗氏学说的影响。而奇氏在第二封回信中自辩道“整庵所论不曾见得”,则不能不令后学对之生疑。奇氏的理气“混沦一体”说后被李珥继承发展,确立为极富主气论特色的“理气之妙”说。
李滉对罗钦顺亦有评价,曾说过“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③。他则谨依朱子在《答刘书文书》中所阐“理与气决是二物”说,对主气论学者的“理气非异物”之说进行了批评。
最后附上李滉的《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供学者参考。此文对理解李滉、罗钦顺以及奇大升三人理气论之间的差异有较大帮助。该文内容如下:
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又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今按:孔子、周子明言阴阳是太极所生,若曰理气本一物,则太极即是两仪,安有能生者乎?曰真曰精,以其二物,故曰妙合而凝。如其一物,宁有妙合而凝者乎?
明道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
今按,若理气果是一物,孔子何必以形而上下分道器,明道何必曰“须著如此说”乎?明道又以其不可离器而索道,故曰“器亦道”,非谓器即是道也;以其不能外道而有器,故曰“道亦器”,非谓道即是器也。(道器之分即理气之分,故引以为证。)
朱子《答刘书文书》曰:“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又曰:“须知未有此气,先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夹论。至论其偏体于物,无处不在,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莫不有是理焉。”(今按:理不囿于物,故能无物不在。)不当以气之精者为性,性之粗者为气也。(性即理也,故引以为证。)
今按: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又曰:“性虽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相夹杂。”不当以气之精者为性,性之粗者为气。夫以孔、周之旨即如彼,程、朱之说又如此,不知此与说同耶?异耶?滉愚陋滞见,但知笃信圣贤,依本分平铺说话,不能觑到花潭奇乎奇,妙乎妙处。然尝试以花潭说揆诸贤说,无一符合处。每谓花潭一生用力于此事,自谓穷深极妙,而终见得理字不透。所以虽拼死力谈奇说妙,未免落在形气粗浅一边了,为可惜也。而其门下诸人,坚守其误,诚所未谕,故今也未暇为来说一一订评。然窥见朱子谓叔文说:“精而又精,不可名状,所以得不已,而强名之曰太极。”又曰:“气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气为性之误。”愚谓此非为叔文说,正是花潭说也。又谓叔文“若未会得,且虑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张,久之自有见处,不费许多闲说话也。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说。别看他处,道理尚多,或恐别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胶漆之盆,枉费心力也。”愚又谓,此亦非为叔文说,恰似为莲老针破顶门上一穴也。且罗整庵于此学非无一斑之窥,而误入处,正在于理气非二之说。后之学者,又岂可踵谬袭误,相率而入于迷昧之域耶?①
依李滉之见,罗钦顺和奇大升等皆“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②,只强调理气之“不离”义而忽视二者的“不杂”义。于是,他特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纠正罗、奇等人“理气非二”说及气本论者徐花潭“指气为性”说的错误。
由是观之,强调理气“非一物”是李滉的根本立场。正是基于此种理气“不杂”义,李滉和奇大升围绕“四端”和“七情”的“所从来(根源或来源)”及“所指(所就以言)”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辩。
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与李滉“四七”论之比较为中心
在四端七情①以及理气问题上,奇氏基于其理气“混沦一体”的思想,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
明宗十四年(1559年)一月,李滉曾致书奇大升,提到“又因士友间传闻所论四端七情之说,鄙意亦尝自病其下语之未稳。逮得砭驳,益知疏缪,即改之云:‘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未知如此下语,无病否?”②就自己对“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所做的表述征求了奇氏的意见。
是年三月,奇大升撰《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他将书寄赠李滉,此书即为奇大升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其中写道:“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说也,而先儒发明尽矣。然窃尝致之,子思之言,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论,所谓剔拨出来者也。盖人心,未发则谓之性,已发则谓之情;而性无不善,情则有善恶,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耳,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③奇大升以为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别乃因子思、孟子等先圣“所就以言之者”不同之故,也就是二者在情之所指及所偏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情”只有一种,而“四端”和“七情”所指的对象却有所不同——一指全体,一指其中之部分,二者并不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情。已发之情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心是否依性理而为主宰。性是形上之理,情则是形下之气。理气不离——理不能独自发用,必因气之发而显理之意义。奇氏以为若依李滉之说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两边,则会使人认为理发时无气之作用,而气发时无理作根据。这是不合于程朱学理气“不离”之义。①奇大升指出,子思所说的“情”是所谓“道其全”者;而孟子所论的“情”则是所谓“剔拨”②出来者。故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若谓“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便如同将理与气判而为两物,也就无异于认为“七情”不发于性、“四端”不乘于气。这就是奇氏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所持的“剔拨论”主张。
在奇大升而言,将“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一句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③,虽似稍胜于前说但终究在语意上仍有所未安。
盖性之乍发,气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谓“四端”者也。此固纯是天理所发,然非能出于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也。然则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兼气”,可乎?论人心、道心,则或可如此说;若四端、七情,则恐不得如此说,盖七情不可专以人心观也。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朕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义也。④
奇氏所言“四端”为本然之善(“良知”)得以直遂者即指“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因此他以为,“人心”、“道心”或可以理气分言,但是“四端”、“七情”却不宜对举互言而谓之“纯理”或“兼气”。奇大升进而指出所谓“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而所谓“恶”者则为“气禀之过不及”。于此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奇氏的基本见解可概括为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因此七情之发或善或恶,“性之本体”或有不能全者。而且,他还以为所谓四端和七情初非有二义,二者只是不同性质的(如“善”的或“恶”的)“情”而已。奇氏又进一步论道曰:“近来学者,不察孟子就善一边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别而论之,愚窃病焉。朱子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及论性情之际,则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盖恐人之不晓,而以气言性也。然学者须知理之不外于气,而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乃理之本体然也,而用其力焉,则庶乎其不差矣。”①奇大升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主张被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论。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其“理气兼发”或“理气共发”说中的“理”是否具“发用义”?依奇氏之见,“理之本体”为“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若以此推之自然得出“四端”为“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的结论。而且因其力主“理”的“不外于气”之特性,故其“四七理气”论可以表述为“理气共发”或“理气兼发”说。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其“四七理气”之发论中发之者是“气”而不是“理”,“理”只具“主宰义”。这也正是奇大升和罗钦顺虽皆主理气二者“混沦一体”,前者却极力批判后者“认气为理”的主要原因。在罗钦顺的理气论中,理因不具“主宰义”弱化了自身的“实体性”——这对于谨遵传统程朱之旨的奇大升而言无异于离经叛道。
以上便是奇大升就“四七理气”问题致李滉的第一封书信中的主要内容。奇氏在信中着重阐述了其对“四端”和“七情”的理解以及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的见解。
对于奇氏来函中的问难,李滉撰写了《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文章从以下几个角度作了认真的回应。首先,他肯定了奇大升对于“四端”和“七情”的区别。“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故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③在李滉看来,理与气是“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这表明他虽然承认理气二者不可分离,但是基于“四端”和“七情”“所就而言之”的差异而有种种分别。这是李滉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其次,李滉从程朱“二性论”的角度对“四七”说进行了阐发。“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子思、孟子所讲的“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与“气质之性”不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性(天之所与我者),即非由外铄的“我固有之”者。在此李滉则基于“四端”与“七情”各自的“所从来”之异(在源起上存在的差异),主张因“性”有本性、气禀之异,故“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性”可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分理气而言之。
再次,李滉又从四端七情的“所主”与“所重”之不同,力主二者皆可以分理气来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四端,皆善也。故曰:‘无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七情,善恶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则心已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谓之‘和’。由是观之,二者虽曰皆不外乎理、气,而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则谓之某为理,某为气,何不可之有乎。”①李滉也以为虽然“四端”与“七情”皆来自于理气,但是因其在“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之义上各有“所主”与“所重”,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四端”为发于内者,即仁义礼智之性的直接发用;“七情”则为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者,即人之形气感官因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四端”所主的是“理”,“七情”所重的是“气”。因此李滉主张“四端”和“七情”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换句话说,他力辩二者之区别的目的在于强调其在善恶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职是之故,李滉认为奇氏为学之失在于“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他在信中写道:“今之所辩则异于是,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从来,概以为兼理气,有善恶,深以分别言之为不可;中间虽有‘理弱气强’、‘理无朕,气有迹’之云,至于其末,则乃以气之自然发见为理之本体然也,是则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别矣。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滉寻常未达其指,不谓来喻之意亦似之也。”②在他看来,奇氏在倡言“四端”是从“七情”中剔拨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说“四端、七情为无异”——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李滉进而直言“讲学而恶分析,务合为一说”乃古人所谓囫囵吞枣,其病不少——为学者若如此不已的话,就会不知不觉之间骎骎然入于以气论性之弊,而堕于认人欲作天理之患。
在此信的结尾处,他还援引朱熹之论为其主张申辩。“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而当初郑说亦自为无病,似不须改也。”①李明辉先生认为朱子这句话在其义理系统中有明确的意涵,而其中两个“发”字的涵义并不相同:“理之发”的“发”意谓“理是四端的存有依据”;“气之发”的“发”则意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引发”,谓七情是由气之活动所引生。但是在朱子的系统中,既然理本身不活动,自不能说:四端是由理之活动所引发。故对朱子而言,理之“发”是虚说,气之“发”为实说。②这一论述对解读李滉、奇大升等人的“理发”、“气发”之说很有启发意义。“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③一语的确见于《朱子语类》,但朱子并未对之做进一步的阐发。
接到李滉复函后,奇大升随即撰写了第二封信也就是《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信中对李滉在文中的答复一一作了回应。于是,两人之间就有了第二次往复论辩。奇氏第二封信的内容分为12节,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奇大升还是强调自己的“情”观,认为人只有一种“情”。“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然而所谓‘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其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是故愚之前说,以为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者,正谓此也。又以为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者,亦谓此也。由是言之,以‘四端主于理,七情主于气’而云云者,其大纲虽同,而曲折亦有所不同者也。”①依其之见,情兼理气故有善恶。四端和七情之异源于“所就以言之不同”——七情之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与孟子所谓四端皆同实而异名;至于发而不中节者则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因此并非七情之外又有所谓四端者。
其次,奇氏以为不仅四端是性之所发,而且七情亦是性之所发。“来辩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此言甚当,正与朱子之言互相发明,愚意亦未尝不以为然也。然而朱子有曰:‘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以是观之,所谓‘四端是理之发’者,专指理言;所谓‘七情是气之发’者,以理与气杂而言之者也。而‘是理之发’云者,固不可易;‘是气之发’云者,非专指气也。”②他进而写道:“四端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七情亦发于仁义礼智之性也。不然,朱子何以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乎?又何以曰‘情是性之发’乎?”③理学先辈即主情为性之所发。奇大升肯定情有四端、七情之分,而四端和七情皆由性所发。
再次,奇氏又据理学人性论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原则,进一步指出不仅七情是理乘气而发,而且四端也是理乘气而发。他还直言“四端亦气”。“后来伏奉示喻,改之以‘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云云,则视前语尤分晓。而鄙意亦以为未安者,盖以四端、七情对举互言,而揭之于图,或谓之‘无不善’,或谓之‘有善恶’,则人之见之也,疑若有两情,且虽不疑于两情,而亦疑其情中有二善,一发于理,一发于气者,为未当也。”④奇大升认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情中有“发于理”和“发于气”的两种善的说法难免令人困惑。这在奇大升看来显然是不妥的。依其之见,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便是“情”。故“情”皆出于心,并非仅源于外物触其形。“心”是理气之合,当其感于物而动之际发之者只能是“气”——四端和七情也不例外。“愚按:‘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句,出《好学论》。然考本文曰:‘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其曰‘动于中’,又曰‘其中动’云者,即心之感也。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焉,乃所谓‘情’也。然则情见乎外,虽似缘境而出,实则由中以出也。辩(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一文——引者注)曰:‘四端之发,其端绪也。’愚谓:四端、七情,无非出于心者,而心乃理、气之合,则情固兼理、气也,非别有一情,但出于理,而不兼乎气也。此处正要人分别得真与妄尔。辩曰:‘七情之发,其苗脉也。’愚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朱子曰:‘性之欲,即所谓情也。’然则情之感物而动者,自然之理也。盖由其中间实有是理,故外边所感,便相契合;非其中间本无是理,而外物之来,偶相凑著而感动也。然则‘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一语,恐道七情不著也。若以感物而动言之,则四端亦然。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其感物者,与七情不异也。辩曰:‘安有在中,为理之本体耶?’愚谓:在中之时,固纯是天理,然此时只可谓之‘性’,不可谓之‘情’也。若才发,则便是情,而有和不和之异矣。盖未发,则专是理;既发,则便乘气以行也。朱子《元亨利贞说》曰:‘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又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①可见,奇大升在谈论四端和七情时特别强调心的感知与主宰作用。心为理气之合,故出于心的四端和七情必兼理气。他还说过若以生长收藏为情,便见乘气以行之实,而“四端亦气”也。
最后,奇氏还从价值论意义上就四端和七情的善恶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愚按程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然则四端固皆善也,而七情亦皆善也。惟其发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而为恶矣。岂有善恶未定者哉?今乃谓之‘善恶未定’,又谓之‘一有而不能察,则心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乃谓之和’,则是七情者,其为冗长无用,甚矣!而况发而未中节之前,亦将以何者而名之耶?且‘一有之而不能察’云者,乃《大学》第七章《章句》中语,其意盖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者,只要从无处发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也。《或问》所谓‘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蚩俯仰,因物赋形’者,乃是心之用也,岂遽有不得其正者哉?惟其事物之来,有所不察,应之既或不能无失,且又不能不与俱往,则其喜怒忧惧,必有动乎中,而始有不得其正耳。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证七情,殊不相似也。夫以来辩之说,反复剖析,不啻详矣,而质以圣贤之旨,其不同有如此者,则所谓‘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者,虽若可以拟议,而其实恐皆未当也。然则谓‘四端为理’、谓‘七情为气’云者,亦安得遽谓之无所不可哉?况此所辩,非但名言之际有所不可,抑恐其于性情之实、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也。”①他又说道:“夫以四端之情为发于理而无不善者,本因孟子所指而言之也。若泛就情上细论之,则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固不可皆谓之善也。有如寻常人,或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亦有是非其所不当是非者。盖理在气中,乘气以发见,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其流行之际,固宜有如此者,乌可以为情无有不善?又乌可以为四端无不善耶?此正学者精察之地,若不分真妄,而但以为无不善,则其认人欲而作天理者,必有不可胜言者矣。”②在奇大升看来,“善”者乃是“天命之本然”,“恶”者则是“气禀之过不及”。③但因理具有“不外于气”之特性,故气之无过不及自然发见者即为“理之本体”。而“理之本体”乃“天命之本然”亦即天赋之“善”者。于是,他认为四端和七情初非有此二义,皆仅是“情”的一种善恶性质而已。因此不能以理气来分言四端和七情。二者的区别只在性发为情之际,所发是否中节——其发而中节者,则无往而不善;其发而不中节,则偏于一边者而为恶。基于此,奇氏以为不仅“七情亦皆善”,而且“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可见,他强调的是二者作为人类感情的同质性和同构性。依奇氏之见,二者的关系并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而是七情包含四端(可简称为“七包四”)的关系。
李滉受到奇大升的进一步质疑。他在即接到奇氏《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之后就对其之前不够严谨的表述作了修正,并撰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信中李滉首先对奇氏四端亦是感物而动、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等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不过,对其将四端和七情视为“同实异名”的观点则给予了坚决反对。“公意以为:四端、七情皆兼理、气,同实异名,不可以分属理、气。滉意以为:就异中见其有同,故二者固多有浑沦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则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气之不同,分属何不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虽或有疵,而其宗旨则实有所从来。盛辩一皆诋斥,无片言只字之得完。今虽更有论说,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无益于取信,而徒得哓哓之过也。”①李滉主张对于二者既要异中见其有同,又要同中而知其有异。他还指出以“所就而言”,二者本自有主理、主气之“所主”的区别。由此,李滉提出了“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其详细内容摘录如下:
盖浑沦而言,则七情兼理、气,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著而感动也。且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但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②
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李滉坚守的是对二者各自不同的“所从来”与“所主”的“主理/主气”立场,如其所言“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随其所主而分属之耳”。至此,李滉大体已确立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理论主张——“四七理气互发”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可视为其在四七理气问题上的最终定论。在此后与奇氏的往复论辩中,李滉对这一基本观点则再未作修正。
对于李滉的答复,奇大升提出了再质疑——遂有《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此信即为其《论四端七情》之第三书,作于1561年(明宗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年)。信中开头奇氏先对《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第一书》的《改本》作了评论,之后又对李滉的答复给予了逐条回应,最后还对《后论以虚为理之说》、《四端不中节之说》、《俚俗相传之语,非出于胡氏》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奇大升以其“因说”和“对说”①之理论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了质疑。信中写道:
大升以为朱子谓“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者,非对说也,乃因说也。盖对说者,如说左右,是对待底;因说者,如说上下,便是因仍底。圣贤言语,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不可不察也。②
大升谓“泛论则无不可”者,以其因说者而言之也。“著图则有未安”者,以其对说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对说者而言之,则虽朱夫子本说,恐未免错认之病。③
朱子的“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是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的重要立论依据,所以奇氏特意对朱子的这一说法作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朱子此句是“因说”而非“对说”,是“纵说”而非“横说”。故不能以左右对待来理解。依其之见,圣贤之言“固自有对说、因说之不同”,所以后之学者对之需加以详察。
基于其“因说”之立场,奇大升又援引朱子对理气特性的论述并以此为据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提出异议。奇氏指出:
如第二条所谓“人之一身,理与气合而生,故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也。互发,则各有所主可知;相须,则互在其中可知”云云者,实乃受病之原,不可不深察也。夫理、气之际,知之固难,而言之亦难。前贤尚以为患,况后学乎?今欲粗述鄙见,仰其镌晓,而辞不契意,难于正说出来,姑以一事譬之。譬如日之在空也,其光景万古常新,虽云雾滃浡,而其光景非有所损,固自若也;但为云雾所蔽,故其阴晴之候,有难齐者尔。及其云消雾卷,则便得偏照下土,而其光景非有所加,亦自若也。理之在气,亦犹是焉。喜、怒、哀、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理,浑然在中者,乃其本体之真;而或为气禀物欲之所拘蔽,则理之本体,虽固自若,而其发见者,便有昏明、真妄之分焉。若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岂不犹日之偏照下土乎?朱子曰:“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正谓此也。今曰“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则理却是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气二者,如两人然,分据一心之内,迭出用事,而互为首从也。此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①
这是奇氏就李滉在《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之第二书中作答的内容提出的反驳意见。李滉以为,人之一身是由理与气和合而生,因理与气互在其中,故浑沦言之者固有之;又因各有所主,故分别言之亦无不可。对此奇大升以日照大地为喻指出,日光照射大地虽受云雾之影响,但是在空之日“其光景则万古常新”,无所加损。他认为,理之在气亦是如此,故尽去气禀物欲之累则其本体之流行犹如日之偏照大地。若曰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的话,等于是“理”却具有了情意、计度、造作等特性——这显然有违于朱学之根本原理。依他之见,这是“道理筑底处,有不可以毫厘差者,于此有差,无所不差矣”。可见,奇氏同样忠于朱子之学,且以朱学为其立学之据的。
基于此,奇大升对李滉“四七理气互发”说委婉地提出己之修正意见,并主张对于“此等议论”不可草草下定论。
“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两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为此二个意思,七情则兼有,而四端只有理发一边尔。抑此两句,大升欲改之曰:“情之发也,或理动而气俱,或气感而理乘。”如此下语,又未知于先生意如何?子思道其全时,固不用所从来之说,则孟子剔拨而说四端时,虽可谓之指理发一边,而若七情者,子思固已兼理、气言之矣。岂以孟子之言,而遽变为气一边乎?此等议论,恐未可遽以为定也。①
前文已论及,奇大升所理解的“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对之他极为自信,认为若在此之外更求“理之发”之义“则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可得矣”②。由此可见,奇大升和李滉皆以朱子学说为据展开思想的攻防。
接到奇氏的《论四端七情》第三书后,李滉只是在来书中节录数段加以批示,并未再作答复——只向奇氏致以含有欲结束二人论辩之意的书函。或许在李滉看来,通过奇氏的三次来书和自己的两次答复已令双方充分了解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感到二人相互间很难说服对方,遂欲结束这场论辩。接到李滉来函后,奇大升又撰写了《四端七情后说》和《四端七情总论》寄赠李滉,此时已是1566年(明宗二十一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收到奇氏寄来的两书后,李滉只是简单作了回复,而对来书中的具体问题并未详加解答。他写道:“四端七情《总说》(应为《总论》——引者注)、《后说》两篇,议论极明快,无惹缠纷挐之病。眼目尽正当,能独观昭旷之原,亦能辨旧见之差于毫忽之微,顿改以从新意,此尤人所难者。甚善!甚善!所论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复致思于其间乎?兼前示人心道心等说,皆当反隅以求教。今兹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谨当一一。”③如引文所见,信中李滉仅就奇氏对“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的解释提出些异议,对来书之内容未作具体回复。这表明李滉已无意继续与奇氏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
这场开始于明宗十四年(1559年)1月的李滉《与奇明彦》一书的论辩,以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10月李滉作《答奇明彦》一书而告终。但是,双方的主要论点大都集中于奇大升上退溪的前三次书和李滉的前两次作答的书函中。尽管二人围绕四七理气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他们相互间的问学并未就此中断。宣祖昭敬王元年(1568年)7月奇氏就拜谒了奉王命入京的李滉,是年12月还与其一同讨论《圣学十图》。而且,次年(1569年)3月还将欲回安东陶山的李滉送至东湖,并同宿江墅。在东湖舟上,奇大升先寄一绝奉别李滉,朴和叔等继之。席上诸公,咸各赠言饯别李滉。奇氏诗曰:“江汉滔滔万古流,先生此去若为留。沙边拽缆迟徊处,不尽离肠万斛愁。”①李滉和韵:“列坐方舟尽胜流,归心终日为牵留。愿将汉水添行砚,写出临分无限愁。”②李滉临行,不能尽酬,谨用前二绝韵奉谢了诸公相送之厚意。不料,于东湖作别后的第二年,1570年(宣祖三年)12月李滉辞世。奇氏惊闻退溪李滉先生讣音,设位痛哭。翌年正月送吊祭于陶山,2月撰《退溪先生墓碣铭先生自铭并书》,赞其曰:“先生盛德大业,卓冠吾东者,当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后之学者,观于先生所论著,将必有感发默契焉者。而铭中所叙,尤足以想见其微意也。”③可见,奇大升和李滉虽然在为学和致思倾向上分歧明显,但是作为同道益友和直谅诤友,二人感情甚笃,在相互问学中共同推动了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三、奇大升“四端七情”论的特色
奇大升与李滉皆为李朝一代儒宗,二人的学说亦各具其理论特色。由上所述可知,奇大升的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理气观和性情论等方面。
首先,在理气观上奇大升主张理气的“混沦一体”性,但是亦不否认二者区别——所谓“非以理气为一物,而亦不谓理气非异物”。①奇氏说过:
理气在物,虽曰混沦不可分开,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与气,固不害一物之自为一物也。若就性上论,则正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及以一月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尔,非更别有一月也。②
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③
他主张在二者的“不离”义上应持“合看”和“离看”的立场。“古之圣贤论及理气性情之际,固有合而言之者,亦别而言之者,其意亦各有所主”④,因此要求学者于此当特别“精以察之”。依其“理无朕而气有迹”等观点来看,理之本体是漠然无形象可见的。奇大升论曰:“盖理无朕而气有迹,则理之本体,漠然无形象之可见,不过于气之流行处验得也。程子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此也。鄙说当初分别得理气,各有界限,不相混杂,至于所谓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然,则正是离合处,非以理气为一物也。”⑤“理”要在“气之流行处验得”、“气之自然发见,乃理之本体”以及“非以理气为一物”等观点皆是奇氏理气论的重点所在,必须仔细玩味方能体会出其性理学说之特点。
他与李滉虽然在强调“理”的主宰性和理气不杂性方面取得了共识(二人皆承认理的“实在性”),但是在对理的作用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与奇氏不同,李滉十分重视“理”的能动性和发用性。李滉说过“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有复使之者欲!……盖理气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谓天命流行处亦别有使之者也”①。他还提出“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②的“理帅气卒”论。这是李滉在理气论方面的创见,也是其思想的特色所在。论者将此称为朱学的“死理向活理的转化”③。
在理气观方面奇氏的理论呈现的是“一元论”的倾向,而李滉的学说则体现了鲜明的“二元论”特色。
其次,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问题上,奇大升认为二者是“一本”和“万殊”的关系。奇氏论曰: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愚谓:天地之性,是就天地上总说;气质之性,是从人物禀受上说。天地之性,譬则天上之月也;气质之性,譬则水中之月也。月虽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为月,则一而已矣。今乃以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则岂非所谓“不能无碍”者乎?④
从援引的朱子语录中可以看出,奇氏实际上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理”与“分殊用之理”的关系。他以“天命之性”为本,而以“气质之性”为末。奇氏还曾引用朱子《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⑤可见,奇大升还将“天命之性”(理)视作“道之体”和“天下之大本”,而且认为天下之道理皆由此出。
但他又说:
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者……若就性上论,则所谓“气质之性”者,即此理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然则论性,而曰“本性”、曰“气禀”云者,非如就天地及人物上,分理、气而各自为一物也,乃以一性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耳。至若论其情,则缘本性堕在气质,然后发而为情,故谓之“兼理气,有善恶”。而其发见之际,自有发于理者,亦有发于气者,虽分别言之,无所不可,而仔细秤停,则亦有似不能无碍。①依奇氏之见,“气质之性”(“万殊”之性)与“天命之性”(“一本”之性)实际上同为一性。之所以有“本性”、“气禀”之说乃因以“一性”之随其所在而分别言之。换句话说,“气质之性”即指此“理”(“天命之性”)堕在气质之中者。“天命之性”要通过“气质之性”来得到具体呈现和实现,所以说在“气质之性”之外“非别有一性也”。
对“天命之性”与“四端”、“七情”的关系,奇大升认为“‘七情’者,虽若涉乎气者,而理亦自在其中;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而与孟子所谓‘四端’者,同实而异名者也。至于发不中节,则乃气禀物欲之所为,而非复性之本然也”②。在他看来,“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为“天命之性”、“本然之体”,与“四端”是同实而异名的;而发而不中节者则是气禀物欲之所为,并非是性之本然。
与奇氏不同,李滉却以程朱的“二性说”为理论依据,提出自己的“性”论。“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将非就理气赋与之中,而指此理原头本然处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气,故可谓之‘纯善无恶’耳。若以理、气不相离之故,而欲兼气为说,则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见道体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诚以为杂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也。至于后世程、张诸子之出,然后不得已而有‘气质之性’之论,亦非求多而立异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禀生之后,则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称之也。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在李滉看来,思、孟所言“天命之性”和“性善之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道德根据(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李滉主要是基于“四端”与“七情”在“所指”及“所从来”(根源或来源)上的差别,提出“性”有本性、气禀之异。他坚持“二性论”的立场,强调“情”亦有四端、七情之别的观点。进而又认为“性”可以分理气而言之,“情”亦可以分理气而言之。
简言之,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及“一本万殊”的理念主张“一性论”。他重视人的现实之性也就是所谓“气质之性”;与之不同,李滉依据理气二分及理气互发的思想,坚持其“二性论”的观点。
再次,在“四端”与“七情”关系方面,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以及“一性说”之立场,坚持独到的“七包四”(“因说”)的思想。在奇氏性理学的逻辑结构中,“四端”与“七情”是同构性的(“一情”)。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同实而异名”,所以在其看来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并无差异。
奇大升说过:
盖七情亦本善也,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恶矣……盖七情中善者,乃理之发,而与四端同实而异名者也。②
盖性虽本善,而堕于气质,则不无偏胜,故谓之“气质之性”。七情虽兼理、气,而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而易流于恶,故谓之“气之发”也。然其发而中节者,乃发于理,而无不善,则与四端初不异也。但四端只是理之发,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扩而充之,则学者于四端之发,可不体认以扩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气之发,而理之所发,或不能以宰乎气,气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则学者于七情之发,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义各有所以然者,学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则亦可以思过半矣。③
依其之见,七情亦本善,只因兼摄理气加之理弱气强,故易流于恶。但是,奇大升认为七情中善者(发而中节者),与发于理的四端是同实而异名。这里奇氏所提到的“发于理”一词常被视为经与李滉多次辩论后对李氏立场的妥协。其实不然,此处奇大升只是顺着孟子的四端说扩展开来讲而已①,并非向“四七理气互发”说的回归。在其理气论中,理之本体被规定为“气之自然发见”,故其所言“理之发”即为“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者”②。若奇氏“四七”说带有理发论的意味,肯定会遭到后来李珥等人的批判。但是李珥只对李滉的理发论展开批驳,而对奇氏之说则每持接续之姿态。
因此,“四端”与“七情”为“一情”还是“二情”的问题上,奇氏始终坚定地抱持二者为“一情”的立场。奇大升说过:
盖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为情者,固兼理气,有善恶也;但孟子就理气妙合之中,专指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子思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同者也。③
大升前者妄以鄙见撰说一篇。当时以为子思就情上,以兼理气、有善恶者,而浑沦言之,故谓之“道其全”;孟子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言之,故谓之“剔拨出来”。然则均是情也,而曰“四端”、曰“七情”者,岂非以所就而言之者不同,而实则非有二情也。④
如前所述,奇氏认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和四端无别,因而七情之善与四端之善同具价值之善。在他看来,四端、七情之别就在于“所就而言”之者的不同之故。孟子所谓四端是就情中“只举其发于理而善者”剔拨言之,子思所谓七情则是就情上“兼理气、有善恶者(道其全)”浑沦言之——其实人之情是“一”而已矣。“剔拨论”是奇大升在“四七”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理论观点。
李滉则基于其“理气二分”和“二性论”的立场,主张将四端与七情“对举互言”——奇氏将其理气互发说称为“对说”。
李滉在答奇氏对于其“四端七情”论的质疑时,从“所就而言”的视角写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往年郑生之作图也,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愚意亦恐其分别太甚,或致争端,故改下纯善兼气等语……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他也承认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有详细论述。但同时又认为以理气分言“四七”之发的说法前所未见。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来探讨的研究范式始自韩国儒者。依李滉之见,尽管理与气在具体生成事物的过程中“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具有不可分离性,但是不能将四端和七情“滚合为一说”。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应分别以言之。
李滉进而又从“所指”的视角论述道:
故愚尝妄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四端之发,孟子既谓之心,则心固理气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主于理,何也?仁义礼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绪也。七情之发,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何也?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为杂气;外感则形气,而其发为理之本体耶?①
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认为情之有“四七”之分犹如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他阐述了四端(纯善)、七情(兼善恶)之间微妙的关系,以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源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一主于理,一主于气。之所以有此分别乃因“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李滉说过:“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②二者各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他主张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这一观点虽经几次修正,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概而言之,在持续8年之久的往复论辩中,因所持的立场角度及所仰重的诠释文本上的差异,③双方始终无法在见解上达成一致。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奇大升基于理气“混沦一体”的认识主张“一性论”和“一情说”,而李滉则依止“理气二分”的思想强调“二性论”和“二情说”。
奇氏以为四端与七情皆可视为情的一种善恶性质,不能将二者看作性质有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情,也不能将二者以理气来分而言之。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更为贴近朱学原论。但是李滉却从“理气二分”和“尊理”的立场出发,强调二者的异质性亦即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不同。退溪十分关注道德行为的源起,而奇氏则更留意流行层面已发之情的中节问题,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等篇中就多有对中节问题的论述。奇大升和李滉皆为一代儒学名宿,二人的论辩虽未达成共识,却给后人提供了广阔的哲学思辨的空间。
他们所开启的“四七理气”之辨,后为李珥、成浑等人进一步扩展为“四七人心道心”之辨。
李珥曾这样评价奇氏的“四七”理论:“余在江陵,览奇明彦与退溪论四端七情书。退溪则以为‘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明彦则以为四端七情元非二情,七情中之发于理者为四端耳。往复万余言,终不相合。余曰,明彦之论,正合我意。盖性中有仁义礼智信,情中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如斯而已。五常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七情中之不杂人欲,粹然出于天理者,是四端也。”①这表明李珥的思想与奇大升一脉相承,亦持“四端七情非二”之立场。他又提道:“退溪与奇明彦论四七之说,无虑万余言。明彦之论,则分明直截,势如破竹。退溪则辨说虽详,而义理不明,反复咀嚼,卒无的实之滋味。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乎,只是有个才智,偶于此处见得到耳。窃详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为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做出许多葛藤。每读之,未尝不慨叹,以为正见之一累也。”②李珥对“四端七情”之辨中双方的学说皆有透彻之领悟。像“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的说法确为李滉四七论的要害所在。但他却支持奇氏的主张,盖因其追求的“明德之实效,新民之实迹”③的务实精神与高峰之学更为合拍。
由此可见,奇大升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退溪李滉在与其辩论中逐步确立了其“四七理气互发”说的立场,由此奠定了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栗谷李珥则在奇氏与李滉辩论中同情前者之立场,并将之发扬光大以为“气发理乘一途”说,从而奠定了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
第四节 李珥与其“四七人心道心”论
李珥(字叔献,号栗谷、石潭,1536—1584年)出生于江原道江陵北坪村(乌竹轩)外氏第,籍贯为德水,谥号文成,是韩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自幼受母亲师任堂之训导,很早便接触儒家经典。《年谱》中写道:“壬寅二十一年,先生七岁……先生始受学于母夫人,间就外傅,不劳而学日就,至是文理该贯,四书诸经,率皆自通。”①其母申氏,号师任堂,是己卯士祸(1519年)的名贤申命和之女,以诗、书、画三绝而闻名于世。在母亲的良好教育下,李珥从孩提时代起即表现出其超群天资。而其8岁时(在坡州栗谷里花石亭)写下的五言律诗《花石亭》,则至今令人惊叹不已。诗云:
林亭秋已晚,骚客意无穷。
远水连天碧,霜枫向日红。
山吐孤轮月,江含万里风。
塞鸿何处去,声断暮云中。②
这首诗不仅诗句对仗工整,而且其格调浑成,虽深谙诗律者亦有所不及。③尤其是诗中的“山吐孤轮月,江含万里风”一句,很难想象出自8岁孩童之笔。李珥从13岁始在进士初试中状元及第至29岁魁生员及文科前后止,应科举试9次,均已状元及第,故又被称为“九度状元公”。
李珥16岁时其母(师任堂申氏)遽尔逝世,与母亲感情极深的他此时深感人生无常,于是三年后(19岁)脱下孝服后入金刚山摩诃衍道场修行佛法。在一次与老僧的问答中他旋觉佛学之非而决心下山,正式弃佛学儒。次年(20岁)往江陵作了“自警文”11条,第一条即谓:“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则吾事末了。”①李珥年少李滉35岁,明宗十三年(23岁)春拜谒李滉于礼安陶山,并滞留两天向其主动请教了主一无适及应接事务之要,消释了平日积累之疑点,并给李滉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两位大儒的首次晤面,之后李滉在答门人月川赵穆的信中,曾大加赞赏李珥谓:“汉中李生珥自星山来访,关雨留三日乃去。其人明爽,多记览,颇有意于吾学,后生可畏,前圣真不我欺也。”②李珥的《行状》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写道:“二十三岁谒退溪先生于陶山,问主一无适、应接事物之要,厥后往来书札,辩论居敬穷理及庸学辑注,圣学十图等说。退溪多舍旧见而从之,尝致书曰:世间英才何限而不肯存心于古学,如君高才妙年,发轫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千万益以远大自期。”③可见,尽管这是二人初次晤对,但是对彼此的思想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他们通过书信还有过多次相互问学,由此共同开创出韩国性理学自主的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全盛时代。
在韩国哲学史上,李珥与李滉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畿湖地区的学者(指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一带的学者)大都从栗谷李珥之说,称栗谷为“东方之圣人”;岭南地区的学者(庆尚道一带的学者)则大都从退溪李滉之说,称退溪为“东方之朱夫子”。于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性理学派——栗谷学派和退溪学派,两个学派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李珥的“理气之妙”论——与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之比较为中心
以东亚儒学史的视角而观,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6世纪中后叶中韩儒学史上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理论建树和思想影响的鸿儒硕学。如这一时期的明代大儒有罗钦顺(1465—1547年)、湛若水(1466—1560年)、王守仁(1472—1528年)、王廷相(1474—1544年)等;朝鲜朝的名儒则有赵光祖(1482—1519年)、徐敬德(1489—1546年)、李彦迪(1491—1553年)、曹植(1501—1572年)、李滉(1501—1570年)、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珥(1536—1584年)、成浑(1535—1598年)等,皆为称誉于海内外的“杰然之儒”。可见,在东亚儒学史上这是一个名儒辈出、学说纷呈的学术至为兴盛时期。
其中,江右大儒罗钦顺则被称为“朱学后劲”、“宋学中坚”。他的学说中所呈现的新的理论动向不仅影响了其时的明代理学的演进,而且还传至域外影响了韩国性理学和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下面将通过罗钦顺与李珥理气说的比较,来探讨李珥理气论的特色。
李珥之学,正如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年)所言“不由师传,默契道体似濂溪”①。尽管李珥学无定师,但是其立学极重视统合诸流,汇纳各家。故宋时烈又赞其谓:“遂取诸家之说,分析其同异,论正其得失,务得至当之归……其有乐浑全而恶分析,则先生(指李珥——引者注)必辩其同异于毫厘之间,其有逐末流而昧本源,则先生必一其宗元于统会之极。”②
虽然李珥生活的年代是在“破邪显正”的幌子下,对除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学派均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的时代,但他并不盲从朱子,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和自主精神。针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之说,李珥曾言道:“若朱子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何以为朱子乎?”③这种为学上的自主和批判精神,使其能够对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各家学说加以吸收和借鉴,构筑以理气“不离”之义为特色的独特性理哲学体系。
在与其同时代的中韩诸儒中,李珥唯独对罗钦顺非常赞赏,曰:“罗整庵识见高明,近代杰然之儒也。有见于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见。此则虽不识朱子,而却于大本上有见矣。”④表明李珥认为罗钦顺对朱学之大本,即对朱学的要领是有真切之体会。于是,将整庵罗钦顺与退溪李滉、花潭徐敬德做比较时,亦将其推为最高。曰:“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①李滉和徐敬德是与李珥同朝的另外两位大儒,在韩国哲学史上均具有重要影响。而李珥最为称赞罗钦顺的原因在于,较之李滉和徐敬德,罗钦顺不仅有见于朱学之大本,且多有自得之味。
同时,他还将罗钦顺学说同薛瑄(1389—1465年)、王守仁(1472—1529年)之学亦做过比较,曰:“罗钦顺拔萃人物,自所见少差;薛瑄虽无自见处,自可谓贤者也;王守仁则以谓朱子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之祸,其学可知。”②此处李珥对薛瑄的评价同罗钦顺对薛氏的评价内容亦大体相似,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曾写道:“薛文清学识纯正,践履笃实,出处进退,惟义之安。其言虽间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见有能及之者,可谓君子儒矣。”③由此可见,《困知记》一书对李珥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困知记》何时传入韩国,学界尚无定论。④但是该书传入韩国后,在16世纪朝鲜朝儒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少学者撰文对之加以评说。⑤其中代表性论者有:卢守慎(字寡悔,号苏斋,1512—1590年)、李滉、奇大升、李珥等人。
不过,与罗钦顺相比李珥为学则更具开放性。比如对其时盛行于明代思想界的阳明心学李珥也并未一概排斥,而主张应“取其功而略其过”,认为这才是“忠厚之道”。⑥这显然与罗钦顺对待心学之立场差异较大。
前已言及,李珥的性理学是在对各家理论的批判、撷取中形成。其中,直接影响其理气学说形成的有三家理论——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李滉的“理气二元”论、徐敬德的“气一元”论。李珥曾对此三家学说做过详细的评论,曰:
整庵则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气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以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退溪则深信朱子,深求其意。而气质精详慎密,用功亦深。其于朱子之意,不可谓不契,其于全体,不可谓无见,而若豁然贯通处,则犹有所未至,故见有未莹,言或微差。理气互发,理发气随之说,反为知见之累耳。花潭则聪明过人,而厚重不足。其读书穷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聪明过人,故见之不难;厚重不足,故得少为足。其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了然目见,非他人读书依样之比,故便为至乐。以为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气局一节。继善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理无变而气有变,元气生生不息,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在。而花潭则以为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此花潭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虽然偏全闲,花潭是自得之见也。今之学者开口便说理无形而气有形,理气决非一物。此非自言也,传人之言也。何足以敌花潭之口而服花潭之心哉。惟退溪攻破之说,深中其病,可以救后学之误见也。盖退溪多依样之味,故其言拘而谨;花潭多自得之味,故其言乐而放。谨故少失,放故多失。①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尽管李珥为学极重“自得之味”,但是在为学性格上他仍坚守朱学的立场。故他强调,“宁为退溪之依样,不必效花潭之自得”②。二是,他认为罗钦顺气质英迈超卓故能望见朱学之全体,但是又因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故其言论确有“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李珥以为理气实际上“非为一物”,而是“一而二、二而一”妙合关系。三是,李滉能深信朱子,气质亦精详慎密,故对于朱子之意,不可谓不契。但是因于豁然贯通处有所未至,故其所见亦有未尽莹者。这里主要是指,他与李滉在理气之发问题上的分歧。在此一涉及朝鲜朝性理学的核心论题的见解上,李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而是主张颇有“主气”意味的“气发理乘一途说”。四是,李珥尽管对徐敬德“理不先于气”思想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于理气不相离之妙有了然目见”,但是同时指出徐敬德之说有“认气为理之病”。李珥以为,继善成性之“理”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故主张“一气长存”之上则更有“理通气局”一节。
由此亦可概见李珥在理气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即“一而二、二而一”的“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一途”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等。其实李珥正是用这些学说来试图解答,朱学的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基本理论问题。其中,“理气之妙”思想既是李珥性理学的根本立场,亦是理解其性理哲学的理论要害。
要之,从李珥对罗钦顺的肯定以及对其学说的重视中可以看出,罗钦顺理气说是影响李珥理气思想形成的主要理论之一。
朱子学演进至罗钦顺,较之原来的理论发生了明显改变。首先是在理气观方面与朱熹的学说产生了较大差异。从理学史角度来看,明中叶的朱学呈现出从“理本”向“气本”发展的趋向。无疑,罗钦顺是在这一理学发展转向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
理学从二程开始,在哲学的宇宙论上,把“理”作为宇宙的普遍原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是气的存在、运动的“所以然”。朱熹继承并发展这一思想,建构了以理气二分、理气“不离不杂”①为特色的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朱熹以为,“理”是不杂而又不离于气的形上实体,强调“理”作为气之所以然而具有的实体性和主宰性。这一思想在朱子后学中受到不少怀疑,罗钦顺便是对此提出异议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罗钦顺对朱熹理气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理气二分思想上。他在《困知记》一书中,写道: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①
周子《太极图说》篇首无极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释,可无疑矣。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愚也积数十年潜玩之功,至今未敢以为然也。尝考朱子之言有云“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若然,则所谓太极者,又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邪?惜乎,当时未有以此说叩之者。姑记于此,以俟后世之朱子云。②
此处所引两段引文是在其《困知记》中质疑朱熹理气二分说的主要段落。同时,从此段引文中亦可概见罗钦顺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首先在对于“气”的理解上,罗钦顺明确指出“气”才是宇宙的根本存在,故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虽然朱熹亦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的物质形态,但是罗钦顺的主张已明显呈现出由“理本”转向“气本”的趋向。其次在对于“理”的理解上,罗钦顺则明确反对“理”在朱熹学说中具有的“实体性”、“主宰性”。依罗钦顺之见,“理”即是所谓“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亦即事物自身中的“自然之机”和“不宰之宰”。
由此罗钦顺提出“理即气之理”的主张,他说:“吾夫子赞《易》,千言万语只是发明此理,始终未尝及气字,非遗之也,理即气之理也。”①
进而在理气为“一物”还是“二物”的问题上,他则断言“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②。以为,理是气之运动的内在根据和法则,并不像朱熹所说的是依附于气的另一实体(物)。尽管坚守“认理气为一物”的立场,但是他同时又明确表示学者亦不能将“气”认为“理”。他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③表明,罗钦顺是反对将理气视为二元对待的两个实体,实体只是气,而“理”只是这一实体的自身的规定。即,这一实体固有的属性或条理。
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以及“理须就气上认取”思想既是罗钦顺理气论的核心要义,亦是其理气说“最为难言”的地方。对此,他也曾坦言道:“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默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④
罗钦顺自谓其理气不二之说并非为“臆决”,而是由宗述明道而来。他说:“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明道尝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于‘原来只此是道’一语,则理气浑然,更无隙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晦翁先生……谓‘是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乃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良由将理气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终不能定于一也。”①可见,罗钦顺对程明道学说是极为推崇。尤其是,程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和“原来只此是道”思想是罗钦顺理气浑然一体说的立论根据。若以此来衡量伊川、朱子理气说,皆有析理气为二物之嫌。此外,二程的“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②和“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③等思想,亦是罗钦顺构筑其理气说的主要理论来源。
李珥对明道的思想亦极为重视,这一点与罗钦顺相似。而且,在李珥和罗钦顺著述中所引用的二程言论大都为明道之说。宣祖五年(李珥37岁),李珥与好友成浑(字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进行理气心性问题的论辩时,曾系统阐述自己的理气观。论辩中,他还对成浑言道:“兄若不信珥言,则更以近思录、定性书及生之谓性一段,反复详玩,则庶乎有以见之矣。”④表明《近思录》及明道的《定性书》、《生之谓性章》等是李珥性理学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尤其是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的思想亦是李珥理气说的立论根据。他说:“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此言理气之不能相离。”⑤李珥的理气观,正是以理气之不相离为其理论前提。
前已述及,李珥对罗钦顺十分赞赏,称其为“拔萃人物,自所见少差”。首先,在强调理气之不相离的意义上,李珥与罗钦顺持相同的立场。他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气不离理,理不离气,夫如是则理气一也。何处见其有异耶?所谓理自理,气自气,何处见其理自理,气自气耶?望吾兄精思著一转,欲验识见之所至也。”①这是李珥答成浑信中的一段话。李珥发挥明道之理气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告诫成浑理气不相离之妙须通过精思与证会方能真正体会。其次,在强调理气之不相杂的意义上,李珥与罗钦顺则明显有差异。在李珥的理气说中,理作为气之根柢及造化之根源在理气关系中被赋予主宰义,具有重要地位。如,李珥曰:“夫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②,“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③。可见,在理的规定上李珥与罗钦顺是有区别的。其实,这便是李珥称罗钦顺为“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及“气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李珥性理学说与朱学的传承关系。较之罗钦顺,李珥在强调理气之不相离的同时,亦强调二者之不相杂。他认为理气关系是“既非二物,又非一物”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他说:“一理浑成,二气流行,天地之大,事物之变,莫非理气之妙用也。”④这就是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也是其整个性理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那么,何谓“既非二物,又非一物”呢?李珥对此解释道:“非一物者,何谓也?理气虽相离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谓也?虽曰理自理,气自气,而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不见其为二物,故非二物也。”⑤理气一方面妙合之中互不相杂,理自理,气自气,故非为“一物”;另一方面二者又浑然无间,无先后,无离合,故亦非为“二物”。前者所强调的是理气二者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后者所强调的是在现实的意义上二者所具有的共时性、共存性。
接着李珥总结明道与朱子的理气关系论述,指出:
考诸前训,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气浑然无间,元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虽不相离而浑然之中实不相杂,不可指为一物。故朱子曰: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合二说而玩索,则理气之妙,庶乎见之矣。①
以上引文中,亦可概见李珥为学上的特点。即,注重对各家学说的融会贯通。因理与气是相互渗透、相互蕴涵的关系,故不可指为“二物”;但二者是妙合之中,又各自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性,故又不可指为“一物”。此种“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思维模式,正好反映了李珥独特的哲学思维方法。
李珥性理学中的最为紧要处,便是其“理气之妙”说。对此,他亦曾言道:“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②尽管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李珥却对此说颇为自信。他在给成浑的一封复信中,写道:“珥则十年前已窥此端,而厥后渐渐思绎,每读经传,辄取以相准,当初中有不合之时,厥后渐合,以至今日,则融会吻合,决然无疑。千百雄辩之口,终不可以回鄙见。”③表明,通过其多年努力而体贴到的理气之妙合关系,李珥已完全确信无疑。
于是,李珥从其“理气之妙”思想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理气动静说。他指出:“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④此即李珥所谓的“气发理乘”说。他对此二十三字所言之内容,极为肯定。简言之,所谓“气发理乘”是指,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气化流行)时理乘之而无所不在的存有形态。李珥此说,既是对李滉“理气互发”说的批判,亦是对朱子理气说的进一步继承与阐发。
理发气发问题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此论与“四端七情”之辨相关联,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理论特色。
李珥在与成浑(成浑基本上持李滉的立场)的四端七情论辩中,还系统阐发了其“气发理乘”思想。曰:
气发而理乘者,何谓也?阴静阳动,机自尔也,非有使之者也。阳之动则理乘于动,非理动也;阴之静则理乘于静,非理静也。故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阴静阳动,其机自尔,而其所以阴静阳动者,理也。故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夫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者,原其本然而言也;动静所乘之机者,见其已然而言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理气之流行皆已然而已,安有未然之时乎?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理乘之也。所谓气发理乘者,非气先于理也,气有为而理无为,则其言不得不尔也。①
李珥的“气发理乘”说是以理气“元不相离”为其立论前提,加之在其哲学中“气”具有形、有为之特性而“理”却无之,故“理”不能以动静言。依他之见,理之所以流行,是乘气之流行而流行,理之有“万殊”,亦因气之流行所致。不但天地之化是如此,而且人心之发亦不外乎此。发之者是其然,是表现者;所以发者是所以然,是使表现者得以实现的主宰者。
而且,同成浑的往复论辩中,李珥则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指出:“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②文中,李珥不仅指责李滉未能正确理会朱子之意,而且还主张不仅七情是气发而理乘,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
进而,他又以“理气之妙”论为基础推出自己在理气同异思想,即“理通气局”说。那么,何谓“理之通”、“气之局”呢?李珥解释曰:
理气元不相离,似是一物,而其所以异者,理无形也,气有形也;理无为也,气有为也。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理通者何谓也?理者,无本末也,无先后也。无本末、无先后,故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是故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而其本然之妙无乎不在。气之偏则理亦偏,而所偏非理也,气也。气之全则理亦全,而所全非理也,气也。至于清浊、粹驳、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中,理无所不在各为其性,而其本然之妙则不害其自若也。此之谓理之通。气局者何谓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气之本则湛一清虚而已曷。尝有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气哉?惟其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故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于是气之流行也,有不失其本然者,有失其本然者。既失其本然,则气之本然者已无所在,偏者偏气也,非全气也;清者清气也,非浊气也;糟粕煨烬,糟粕煨烬之气也;非湛一清虚之气也。非若理之于万物本然之妙,无乎不在也。此所谓气之局也。①此段引文集中反映了李珥理气说之基本要义。文中可以看出,他从理气关系和理气之特性着手,论述了“理通气局”、“气发理乘”及“理之偏全”等问题,阐明了其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要之,所谓“理通”,是指“理同(同一理)”;“气局”,则指“气异(各一气)”。②对于“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李珥自诩为“理通气局四字,自谓见得,而又恐读书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见之也”③。此说尽管亦受程朱的“理一分殊”、“理气同异”及佛教华严宗的“理事通局”说的影响,但是仅就以通局范畴表述理气之异而言确为李珥独见。而且,在他的性理哲学逻辑结构中“理通气局”与“气发理乘”说,作为说明人物性同异与性情善恶的重要命题互为对待、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了其“四七人道”说的立论基础。
概言之,通过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与李珥“理气之妙”说的比较,可以看出16世纪中韩朱子学的不同发展面向。罗钦顺从去“理”的实体化、主宰义入手,将“理”视为“气”所固有的属性或条理,反对将理气视为二元对待的两个实体,明显表现出由“理本”向“气本”的转向。而,李珥虽然与罗钦顺同尊明道,但是仍表现出坚守朱学之为学性格,提出理气“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颇具特色的“理气之妙”说,对明道和朱熹思想作了有益的阐发。李珥和罗钦顺的理气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朱熹的理气学说,而且也为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
二、李珥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与成浑“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
通过对李滉、奇大升等人的“四七”论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四端七情问题其实讨论的是“性”与“情”关系问题,因此顺四端七情理气问题便可以引出有关性情善恶及人心道心问题的论议。而栗谷李珥和牛溪成浑之间围绕人心道心问题展开的第二次“四七”之论争,便是四七理气问题在更深一层意义上的,即性情层面上的展开。在韩国哲学史上李珥和成浑之间发生的第二次“四七理气”之辨,既丰富了原有的四七理气理论之意涵,又开启了对性情善恶与人心道心关系问题的新的理论探索,将“四七”论引向了新的问题域。下面,将以李珥与成浑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探讨“四七”论进一步发展之状况。
成浑(字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昌宁人,谥号文简,朝鲜朝著名性理学家。成浑幼承庭训,学业大进,15岁便博通经史文辞,为人们所叹服。其父成守琛曾受学于赵光祖,成浑则尊幕李滉且多从其说。他与李珥交情甚笃,二人围绕“四七问题”进行了长达6年的书函往复,①继“退、高之辩”之后将此一论辩又推向了高潮。
成浑的“四七”论和“人心道心”说的主要理论观点,大都集中在与李珥的往复论辩第一书和第二书。在致李珥的信中,成浑写道:“今看十图《心性情图》,退翁立论,则中间一端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云。究此议论,以理、气之发,当初皆无不善,而气之不中,乃流于恶云矣。人心道心之说,既如彼其分理、气之发,而从古圣贤皆宗之,则退翁之论,自不为过耶?”①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成浑是大抵接受李滉的立场,也认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基于此,成浑以为理发则为道心,而气发则为人心。
进而,他又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二名,何欤?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理、气之发不同,而危、微之用各异,故名不能不二也。然则与所谓“四端、七情”者同耶?今以道心谓之四端,可矣;而以人心谓之七情,则不可矣。且夫四端、七情,以发于性者而言也;人心、道心,以发于心者而言也。其名目意味之间,有些不同焉。幸赐一言,发其直指,何如?人心、道心之发,其所从来,固有主气、主理之不同,在唐虞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说,圣贤宗旨,皆作两下说,则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然“气随之”、“理乘之”之说,正自拖引太长,似失于名理也。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为性情之图,则不当分开,但以四、七俱置情圈中,而曰“四端,指七情中理一边发者而言也:七情不中节,是气之过不及而流于恶”云云,则不混于理、气之发,而亦无分开二歧之患否耶?并乞详究示喻。②
文中成浑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具体看法。首先,援引朱子《中庸章句》中的或生、或原说法,主张人心、道心二者是理气之发不同、危微之用各异;其次,在四端七情与人心道心的关系上,以为道心可视为四端,但是人心不可视为七情。而且又从“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之向度,称“其名目意味之间,有些不同”;再次,他从二者的“所从来”意义上,主张人心、道心亦可以主理、主气言之。这是接续李滉的说法而来,李滉曾主张四端与道心是“理之发”,七情与人心为“气之发”。但是,成浑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中的“气随之”和“理乘之”说法却表示疑义。而且,在四七关系上也表现出对“七包四”逻辑(在未发意义上)的认可倾向。
简言之,成浑则主要是站在李滉的立场,对李珥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依他之见,理与气之互发是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并向李珥提出质疑道:自己也曾对退翁的“理气互发”说存疑,但细心玩味朱子关于“人心道心之异,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之说,觉得退溪的互发说亦未尝不可。他说:“顷日读朱子人心道心之说,有或生,或原之论,似与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为在虞舜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理气互发之说,则退翁之见不易论也。”①所谓“或生”与“或原”,指朱熹所说的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言。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纯善无恶;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故有善有恶。可见,成氏明显倾向于肯定“理气互发”说。
在与李珥的论辩中,成浑也试图以“理气互发”和人心、道心相互对待逻辑为基础,来阐释四端与七情、人心与道心的善恶问题,这是其性理学的特点。成浑的主要著作有《朱门旨诀》、《为学之方》、《牛溪集》(12卷)等。
下面一段文字是成浑对李珥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的质疑,曰:
吾兄(指李珥——引者注)前后勤喻,只曰:性情之间,有气发理乘一途而已,此外非有他事也。浑承是语,岂不欲受用,以为简便易晓之学?而参以圣贤前言,皆立两边说,无有如高诲者,故不敢从也。昨赐长书中有曰:“出门之时,或有马从人意而出者,或有人信马足而出者。马从人意而出者,属之人,乃道心也;人信马足而出者,属之马,乃人心也。”又曰:“圣人不能无人心,譬如马虽极驯,岂无或有人信马足而出门之时乎?”浑究此数段,皆下两边说,颇讶其与“只有一边,气发理乘”之语稍异,而渐近于古说也。又读今书,有曰:“发道心者,气也,而非性命,则道心不发。原人心者,性也,而非形气,则人心不发。以道心原于性命,以人心生于形气,岂不顺乎?”浑见此一段,与之意合,而叹其下语之精当也。虽然,于此亦有究极之未竟者焉。吾兄必曰:气发理乘,无他途也;浑则必曰:其未发也,虽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才发之际,意欲之动,当有主理、主气之可言也,非各出也,就一途而取其重而言也。此即退溪互发之意也,即吾兄“马随人意,人信马足”之说也,即“非性命则道心不发,非形气则人心不发”之言也。未知以为如何?如何?此处极可分辨,毫分缕析,以极其归趣而示之,千万至祝!于此终不合,则终不合矣。虽然,退溪互发之说,知道者见之,犹忧其错会;不知者读之,则其误人不少矣。况四七、理气之分位,两发、随乘之分段,言意不顺,名理未稳,此浑之所以不喜者也……情之发处,有主理、主气两个意思,分明是如此,则“马随人意,人信马足”之说也,非未发之前有两个意思也。于才发之际,有原于理、生于气者耳,非理发而气随其后,气发而理乘其第二也,乃理气一发,而人就其重处言之,谓之主理、主气也。①
文中成浑认为,衡之于圣贤前言,皆为立两边说,未曾有如李珥的一途论之说,并以人乘马之喻为其论说。这里他所指的圣贤应为,朱熹、陈淳等人。成浑的学说受朱、陈二人之影响也较大②,而且朱熹和陈淳的思想亦是其立论根据之一。具体而言,成浑的主张是心未发之时不能将四端与七情分别对待之,此时二者应为“混沦一体”之状态(可视为“七包四”)。已发之时才可以分别四端与七情,即发于理的为四端、道心;发于气的为七情、人心。这里亦可以看到他与李珥的细微差异,成浑不同意未发之时的“所从来”意义上的四七分别。依他之见,主理、主气是“才发之际”,即意欲动之时取其重而言之者。因此在这意义上,未发之时成浑对四七结构所持的立场又有与奇大升、李珥的“七包四”逻辑有相似的一面,表现出他的学说的折中性格。因此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他也提出折中李滉与奇大升等人主张的“理气一发”说。
针对成浑的质疑,李珥也以朱学理论为据,阐述了自己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他说:“‘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与‘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通贯。吾兄尚于此处未透,故犹于退溪‘理气互发、内出外感、先有两个意思’之说,未能尽舍,而反欲援退溪此说,附于珥说耳。别幅议论颇详,犹恐兄未能涣然释然也。盖‘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推本之论也;‘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沿流之论也。今兄曰‘其未发也,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此则合于鄙见矣。但谓‘性情之间,元有理、气两物,各自出来’,则此非但言语之失,实是所见差误也。”①李珥此处论述极为明快,他认为所谓“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或原或生”与“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以通贯。成浑对此有疑问,主要是对理气问题有所未透。于是李珥从理气论与性情说之间的相一致性出发,对“四七人心道心”论作了阐明。曰:“理气之说与人心道心之说,皆是一贯。若人心道心未透,则是与理气未透也。理气之不相离者若已灼见,则人心道心之无二原,可以推此而知之耳。”②由此可以看出,李珥的理气论(“理气之妙”说)是其心性论的立论根基,人道说是其理气论的直接生发。因理气之“不离”义是其理气论的主要理论倾向,因此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他也以二者的不可分和相联结为其主旨,强调人心道心的“无二原”性。这与李滉、成浑的基于二者不同价值意义上的人心道心相分思想是有明显区别的。
进而李珥阐发了自己的四七人道说。首先,从“主乎理”、“主乎气”的向度,对人心道心的含义作了论述。曰:“夫人也,禀天地之帅以为性,分天地之塞以为形,故吾心之用即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无二本,故吾心之发无二原矣。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复礼,欲穷理,欲忠信,欲孝于其亲……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因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掩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渴欲饮……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人心。其虽本于天性,而其发由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达,造次难见,故曰‘微’。人心之发,如鹰解鞲,如马脱羁,飞腾难制,故曰‘危’。”①依李珥之见,因外感者(感动者)是形气,故感动之际被何方为所主宰,显得十分紧要。“主乎理”的道心,是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又不为形气所掩蔽者;而“主乎气”的人心,则是出于耳目四肢之私,未直出于理之本然者。以“主乎理”、“主乎气”视角,探讨人心道心之含义,这一点颇能反映韩国儒学在讨论人间和存在的所以然根据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时,往往落实到性理层面上展开理气这个形上、形下问题的理论特性。②重视人间性理,是韩国儒学的根本特征。
其次,李珥从“心是气”的意义上,以知觉论的立场回答了“一心”何以有“二名”,即有人心道心之分的问题。
在李珥哲学中“心”属于气、属于已发,曰:“且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发而性不发之理,则岂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气之所重而言也,非当初有理、气二苗脉也。”③故不管人心还是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规定使其人心道心说具有了知觉论特色。对“一心”何以有“二名”,他有以下几段论述。他说:
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①
心一也,岂有二乎?特以所主而发者有二名。②
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一心。其发也或以理义或为食色,故随
其所发而异其名。③“心”只有一个,这与朱子的主张相同。但是在“一心”何以有“二名”的问题上,李珥所持的诠释立场与朱子不同。这源于李珥独特的性情论义理架构。众所周知,朱子的性理学说以“理气二分”、“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而李珥则以“理气之妙”,心、性、情、意四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因此朱子的性情论可以“心统性情”说来概称,而李珥的性情论则似以“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来指代更为恰当。此处,紧要处为二人对“意”概念的不同界定。在朱子性情论中,“意”和“情”都是从属于“心”的概念。“情”和“意”二者关系是,大抵“情”是性之动,“意”是心之所发;“情”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④因此在朱子心性论中,“意”的思量运用之意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在李珥哲学中,“意”和“情”是两个有明确规定的并列关系的哲学范畴,李珥曰:“意者,心有计较之谓也。情既发而商量运用者也……发出底是情,商量底是意。”⑤“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⑥“情”和“意”皆属于心之已发,而且还是心的两个不同境界。曰:“因所感而紬绎商量意境界”⑦,李珥提出其独特的“意境界”论。
故其人心、道心论是兼情、意而言,如其曰:“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⑧需注意的是,“意”其实是在其人心道心说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范畴。这既是李珥与朱子性情论之区别,亦是其对朱子心、性、情、意说的发展。相较而言,李珥的心性学说确实比朱子的理论更为细密和清晰。而且,强调“意”的商量计较作用是李珥知觉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基于“意之商量计较”意涵,李珥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终始”说。他说: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①不管根于性命之正的道心,还是源于形气的人心,皆属已发,此时气已用事。若欲不咈乎正理如实呈现,或知非制伏不从其欲,都要借“意”之计较、思虑、商量作用来实现。因此李珥认为,在人心之方寸之间,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可变状态。在已发层面上,二者是并无固定的、严格的分别。因此,李珥为学极重“诚意”,他以为“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时,“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②。指出,若能保证“意”之“诚”,则所发之“心”皆能呈现为道心。
再次,李珥还援引“四七”论、“理欲”论上的说法,进一步论述了其对人心道心问题及二者关系问题的认识。
前已论及,“四端七情”论是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重要学说,人心道心论争的发生其实就是“四七”论由“情”论层面向“心”论层面的进一步推进,即“四七”论在心性领域的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展开。
因为在李珥性理哲学中,“意”具有商量计较作用,故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相互转换之状态。这与其“四七”论中,七情兼四端的情形有所不同,对此差异李珥指出:“圣贤之说,或横或竖,各有所指,欲以竖准横,以横合竖,则或失其旨矣。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①可见,李珥对四端与七情的基本认识是,“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故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基于其“七包四”一元思维,他又对“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李珥谓:
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者,何谓也?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闲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也,乌可强就而相准耶?今欲两边说下,则当遵人心、道心之说;欲说善一边,则当遵四端之说:欲兼善恶说,则当遵七情之说,不必将柄就凿,纷纷立论也。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也;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故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朱子所谓“发于理”、“发于气”者,只是大纲说,岂料后人之分开太甚乎!学者活看可也。且退溪先生既以善归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若然,则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从何而发哉?孟子举其大概,故只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为四端,则学者当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于仁义礼智而为善者乎?此一段当深究精思。善情既有四端,而又于四端之外有善情,则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盛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矣。别纸之说,大概得之。但所谓“四、七发于性,人心、道心发于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则心中之理也,心则盛贮性之器也,安有发于性、发于心之别乎?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①
本段引文较长,但是此段内容则是李珥对四七人心道心问题的最为系统之论述。如其文中言的“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也”中可以看出,在李珥哲学中“情”不具商量计较之义,故性发为情之际,七情可以兼四端。因为依他之见,“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但是,人心、道心则已达比较、商量之地步,已具对比之意,故不能兼有,只能互为终始,这便是其“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
因为人心与道心是基于“意”之商量计较而存在的相对之物,李珥又由“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而提出“人心道心相对”说。他说:“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②
此论看似与其“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矛盾,但是这是李珥从天理人欲论角度对人道说的解读,可视为对人道终始说的另一种阐发。他说:“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③可见,李珥对道心、人心、人欲是有区分,而且也肯定人心亦有善。在此李珥所持的是朱子的立场。但是,人心之善与道心是否为同质之善呢?
对此,李珥在《人心道心图说》中写道:“孟子就七情中别出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①可见,他是把二者视为同质之善。在“理欲”论意义上,其人道说比朱子的人道说显得更为紧张和严峻,颇似“天理人欲相对”说。这也是二人人心道心之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李珥还从理欲之辨角度,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论辩的结束阶段,李珥写了首五言律诗(《理气咏》)致成浑,以阐明其理气哲学主旨。诗云:
元气何端始,无形在有形。
穷源知本合,沿派见群精。
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
二歧君莫惑,默验性为情。②这首理语诗中李珥又夹注,曰:“理、气本合也,非有始合之时。欲以理、气二之者,皆非知道者也……理、气原一,而分为二五之精……理之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者如此。空瓶之说,出于释氏,而其譬喻亲切,故用之。”③十分形象地从本体和流行的视角,再一次强调了其“理气之妙”和“气发理乘”思想。
成浑与李珥年龄相仿,李珥19岁时二人便定交。《年谱》记云:“成先生长于先生(指李珥——引者注)一岁,而初欲师事之,先生辞焉。遂定道义之交,相期以圣贤事业终始无替。”④李珥卒后,成浑曾评其道:“栗谷尽是五百年间气也。余少时讲论,自以为朋友相抗。到老思之,则真我师也,启我者甚多。”⑤李珥37岁(成浑时年38岁)时二人围绕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及理气之发问题展开了长达6年的辩论,尽管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但是成浑对李珥的崇敬之情从其评语中以见一斑。
在朝鲜朝儒学史上由李珥和成浑之间进行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是,继“四端七情”之辨之后发生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又一学术论争。
三、李珥“四七人心道心”论的特色
李珥的“四七人道”说特色主要表现在,其“四七理气”说和心性情意论方面。
李珥的“四七理气”论是在与成浑的相互论辩和与李滉的相互问学中形成。李滉在“四七理气”论方面的基本说法是,“四七理气互发”说。成浑大抵接受李滉此一立场。
李滉曾曰:“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此论便是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此一理论的性情论基础是,“二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二情”(四端/七情)论。由此自然可以推导出,对举分别而言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论,即主理、主气之说。
李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基于其理气“一而二、二而一”思路以为,子思、孟子所言的本然之性和程子、张子所言的气质之性,其实皆为“一性”,只是所主而言者不同而已。曰:
性者,理、气之合也。盖理在气中,然后为性。若不在形质之中,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也。但就形质中单指其理而言之,则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不可杂以气也。子思、孟子言其本然之性,程子、张子言其气质之性,其实一性,而所主而言者不同。今不知其所主之意,遂以为二性,则可谓知理乎?性既一,而乃以为情有理发、气发之殊,则可谓知性乎?①可见,李珥不仅主张性为理气之合,而且还明确区分“性”与“理”概念的不同用法。这既是李珥逻辑思维细密、精微之处,也是其“四七”论的独到之处。进而他指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其实是“一性”。这里还可以看出,他的“性”论又与奇大升的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依他之见,若不知其所主之意而视其为“二性”,可谓之味于“理”者。而在“性既一”之情形下,仍主情有理发、气发之殊的话,则又可谓之味于“性”者。
李珥也认为,理为形而上者也,气为形而下者也。不过,他特别强调二者的不能相离性。因此在他而观,二者既不能相离,则其发用也只能是“一”,不可谓互有发用。曰:
若曰互有发用,则是理发用时,气或有所不及;气发用时,理或有所不及也。如是,则理气有离合,有先后,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其错不小矣。但理无为,而气有为,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于形气者,属之理;当初虽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属之气,此亦不得已之论也。人性之本善者,理也,而非气则理不发。人心、道心,夫孰非原于理乎?非未发之时,亦有人心苗脉,与理相对于方寸中也。源一而流二,朱子岂不知之乎?特立言晓人,各有所主耳。程子曰:“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夫善、恶判然二物,而尚无相对各自出来之理,况理、气之混沦不离者,乃有相对互发之理乎?若朱子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何以为朱子乎?②
在李珥看来,承认“理气互发”说不仅等于承认理气有缝隙、有离合,而且还承认理气有先后、动静有终始。朱熹的“理气不杂”、“理气为二”思想,明初便遭到曹端、薛瑄、胡居仁等人的批评,他们依据程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理论,主张理在气中,坚持理气无间一体思想,反对把二者对立、割裂。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说,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理论。罗氏的《困知记》对朝鲜朝性理学及李珥“理气之妙”说的影响前文已多次论及,李珥也受此理论思潮之影响力主“理气非二”论。故他以为,四端与七情之说是朱子“特立言晓人,各有所主”而已。这与奇大升的所言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的思想并无二致。依李珥之见,若是朱子也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
于是,他进而指出:
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阴阳动静,而太极乘之,此则非有先后之可言也。②
在此李珥对朱子的“四七”论作了己之阐发的同时,指出李滉的错误在于只认同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他坚持,不仅四端是“气发而理乘”,七情亦是“气发而理乘”。对于李珥和李滉的“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陈来先生认为,二者并不相同。他指出:李滉所说的气发是发自于形气,而李珥所说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李珥进一步说的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这是气,就是气发,而理乘载其上。由于李珥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故把恻隐说成气,说成气发,这种说法与王阳明接近,容易引出“心即气”的主张,是与朱子和李滉不同的。李珥认为,气和理的这种动载关系是普遍的,不限于四端七情,整个天地之化都是如此。③陈先生的这一论述,对于二人的理气之发说的理解及理气论差异问题的探讨颇有裨益。
要之,“性”与“理”概念的区分,“一性”、“一情”论的强调以及“七包四”立场的坚守,是李珥“四七理气”论的主要特色。
那么,李珥和李滉的“气发而理乘”思想为什么会有理论差异呢?这源于李珥独特的心性情意论。
在李珥的心性情意论逻辑结构中,“心”处于十分重要之地位,他认为,就人之一身来说心“合性与气”,而有“主宰”于身之作用。他说:
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谓之心。心应事物而发于外者,谓之情。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未发已发之总名……性之目有五,曰仁义礼智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之发也,有为道义而发者。如欲孝其亲,欲忠其君,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非议而羞恶,过宗庙而恭敬之类是也,此则谓之道心。有为口体而发者,如饥欲食、寒欲衣、劳欲休、精盛思室之类是也,此则谓之人心。①
文中李珥对“性”、“情”、“心”、“道心”、“人心”等作了明确之界定。此说与朱子的“心为主宰”的思想和李滉的“心兼理气”、“理气合而为心”②说法皆也有所不同。因为在李滉的性理哲学体系中理具发用性和能动性,故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而在心、身的关系上,李珥也强调心的优位性,比朱子更加明确指出心对身的主宰作用,言道:“心为身主,身为心器,主正则器当正。”③而且,在李珥性理哲学中心属于气,属于已发,故“心”在其性情论中是被探讨的主要对象。
对于“心”、“性”、“情”概念及相互关系,李滉则界定为: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表明,李滉的心论结构大体延续的是朱熹的“心统性情”思路。但是,有别于朱熹的是,他的这一思想突出了理对于心之“灵”的作用,着重于解决心的知觉作用问题。
基于心之作用的独特认识,李珥又提出“心为性、情、意之主”的思想。他言道:
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盛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矣。别纸之说,大概得之。但所谓“四、七发于性,人心、道心发于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则心中之理也,心则盛贮性之器也,安有发于性、发于心之别乎?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①
李珥主张“心为性、情、意之主”,故以为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需注意的是,李珥对“性”概念的界定,曰:“性者,理、气之合也。盖理在气中,然后为性。”②其实,他所言之性为“气质之性”。“心是气”,因此性、情、意皆可谓之心。但是,性和情不具计较商量义,故“意”之作用又显得十分重要。“意”不仅在其“四七人道”说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其修养论亦具有重要意义,故其曰“自修莫先于诚意”。进而,李珥还提出“人心、道心皆发于性”的主张,此说与朱熹和李滉的思想相比区别较大。
李珥心性情论中最为独特的思想为,其“性心情意一路而各有境界”论。他说:
子固历见余谈话,从容语及心性情。余曰,公于此三字,将一一理会否。子固曰,未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云者,殊未晓得。余曰,公于此难晓,则庶几有见于心性情矣。先儒此说,意有所在,非直论心性。而今之学者为此说所误,分心性为有二用,情意为有二歧,余甚苦之。今公自谓于此有疑,则庶几有真知矣。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矣。岂不大差乎?须知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然后可谓不差矣。何谓一路?心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发后商量为意,此一路也。何谓各有境界?心之寂然不动时是性境界,感而遂通时是情境界,因所感而紬绎商量为意境界,只是一心各有境界。①
在心性情论方面,李珥一贯反对“分心性为有二用,情意为有二歧”。因为依他之见,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由此他提出“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思想。如前所述,李珥的性情论为心性情意四分逻辑结构,故性境界、情境界、意境界分别代表了“一心”之不同境界,犹如人之行走,一路走下去一路上各有不同的景致呈现一般。
总之,李珥心性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对“心”之主宰作用与“意”之计较商量作用的重视以及“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论。而“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论,的确为其在心性情论上的创见。
李珥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天道策》、《人心道心图说》、《圣学辑要》、《答成浩原》等。
自从29岁时任户曹左郎开始,他一生为宦,曾官至吏曹判书,49岁时卒于京城大寺洞寓所。李珥是朝鲜朝五百年间难得的道学家、通儒。政治上,他积极建言献策主张为了朝鲜朝的中兴“因时制宜”与“变法更张”,强调“事要务实”。在社会教育方面,他不仅亲自开展私学教育,而且还制定“海州相约”、“社会契约束”以及著《击蒙要诀》、《学校模范》等为朝鲜朝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故成浑赞其曰:“栗谷于道体,洞见大原。所谓天地之化无二本,人心之发无二原,理气不可互发,此等说话,真是吾师。其爱君忧国之忠,经世救民之志,求之古人,鲜有其俦。诚山河闲气,三代人物。”①他的学说被后人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韩国儒学史上颇具影响的畿湖性理学派。
附注
①参见权近:《阳村先生年谱》,《阳村集》,《韩国文集丛刊》7,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9—10页。
②沈演:《请享疏》,《疏》,《高峰先生别集附录》卷2,《高峰集》第二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84页。
③李植:《追录》,《泽堂先生别集》卷15,《泽堂集》,《韩国文集丛刊》88,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版,第524页。
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上),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页。
②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上),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页。
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上),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页下、6页上。
①权近:《心气理篇》序,《三峰集》(下)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01页。
②权近:《心气理篇》序,《三峰集》(下)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01—202页。
③权近:《心气理篇》序,《三峰集》(下)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03页。
①权近:《心气理篇》序,《三峰集》(下)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03页。
②权近:《心气理篇》序,《三峰集》(下)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01—202页。
③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上),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页下。
①参见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上),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6页上。
①《中庸章句》第20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页。
②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上),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6页上。
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上),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6页下。
①李明辉先生指出,阳村坚守的是朱子的立场。因此他认为,这也可以解释阳村何以在引文中以“性发为情”为“心之用”,而非“性之用”。“性发为情”与“心发为意”的两个“发”字之意涵并不相同:前一“发”字是“静态地作为存有依据”之意,后一“发”字则是心理学意义的“引发”之意。这相当于康德所谓“动因”(Bewegungsgrund)与“动机”(Triebfeder)之别,或是朱子所谓“动底”与“动处”之别。阳村原先以“性发”与“心发”来区别“四端”与“七情”,但是他所说的“性发”并无实义,其实依然是“心发”(心之用),这便削弱了他欲区别二者之用心,而为后来的儒者留下极大的争论空间。(参见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172页)②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页。
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7页上。
②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页。
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7页上。
②程颐:《伊川先生语录》,《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4页。
③程颐:《伊川先生语录》,《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4页。
④陈淳:《性条》,《北溪字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页。
⑤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6页下、7页上。
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8页下;又见“天人心性分释之图”之“性”条,《入学图说》,首尔:乙酉文化社1974年版,第150页。
②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8页上。
③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8页下、9页上。
①权近:《心气理篇》注,《三峰集》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11页。
②金长生:《四端七情辨》,《辨》,《沙溪遗稿》卷5,《韩国文集丛刊》57,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版,第66页。
③权近:《心气理篇》注,《三峰集》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10页。
①李滉:《答金惇叙》,《退溪全书》(二)卷2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62页。
①《承政院日记》134册,高宗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电子版《承政院日记》,http://sjw.history.go.kr/search/inspectionDayList.do)另参见《承政院日记》影印本,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631页。
②柳希春(字仁仲,号眉岩,1513—1577年)曾对此书言道:“柳崇祖等所定吐诚善。然今讲尚书,亦往往有误处,未审当改否。”又曰:“东方自古未有咀嚼经训,沈潜反复乎朱子文语如李滉者也。臣谪居时,用十年之功研穷四书,有所论说。及见李滉之说,相合者十之七八。滉之经说,甚为精密,虽或千虑之一失,然不害其为得处之多也。又李珥有大学吐释。臣曾与珥在玉堂,说及大学,语多契合。”(《经筵日记》甲戌,《眉岩集》卷18,《韩国文集丛刊》3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495页)③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60页上。
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6页下。
②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7页上、57页下。
③程颢、程颐:《二先生语6》,《程氏遗书》卷6,《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1页。
④“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程颢、程颐:《二先生语1》,《程氏遗书》卷1,《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页),此文依其内容归在明道先生语似更恰当。(参见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8页上。
②《性理一·人物之性气质之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0页。
③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9页下。
①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3页下。
②裴宗镐编:《韩国儒学资料集成》,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版,第57页上。
③《承政院日记》134册,高宗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电子版《承政院日记》,http://sjw.history.go.kr/search/inspectionDayList.do)另参见《承政院日记》影印本,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631页。
①李滉:《野池》,《诗》,《退溪集》外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3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56页。
①李滉:《学问》,《言行录》卷1,《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170页。
②黄宗羲(1610—1695年)亦曾曰:“理气乃学之主脑。”(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0页)③朱子曰:“所谓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理离气杂不得。”“太极虽不离乎阴阳,而亦不杂乎阴阳。”(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72、1490页)④在朝鲜朝史上,理气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理论趋向和旨趣各不相同。初期以无极太极论辩为契机,更多以宇宙论层面探讨理气问题,中期和后期(即性理学确立和深化时期)则以“四端七情论辩”、“人心道心论辩”以及“人物性同异论辩”为契机,主要从心性论层面谈论理气问题。相关论述可参见尹丝淳:《朝鲜朝理气论的开展》,载《风流与和魂》,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54页;宋荣培等:《韩国儒学与理气哲学》,首尔:艺文书院2000年版;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⑤丁时翰:《与许太休曤,金士重》,《愚潭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257页。
⑥李滉:《答李达李天机》,《书》,《退溪集》卷13,《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56页。
①李滉:《天命图说》,《杂著》,《退溪集》卷8,《韩国文集丛刊》3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209—210页。
②李滉:《与朴泽之》,《书》,《退溪集》卷12,《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37页。
③此文是李滉为了辩驳罗钦顺等人的“理气一物”论思想而写。罗氏主张“理气一物”说,对此说李滉则认为,“整庵之学,自谓辟异端,而阳排而阴助,左遮右拦,实程朱之罪人也”。(李震相:《年谱》,《寒洲集》附录卷1,《韩国文集丛刊》318,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277页)④李滉:《非理气为一物辩证》,《退溪全书》(二)卷4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31页。
⑤对于“理气先后”论朱熹晚年也意识到此说可能会遭人质疑和批判,为此他也作过一些努力,但最终还是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只是模棱两可地说:“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理气上》,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此句反倒是在强调理的主动性与气的被动性。李滉则接续朱熹晚年的这一变化,把“先后”关系转换为“主仆”关系。
①李滉:《学问》,《言行录》卷1,《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179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后论·别纸》,《书》,《退溪集》卷16,《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26—427页。
③参见柳承国:《东洋哲学研究》,首尔:东方学术研究院1988年版,第220—221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别纸》,《书》,《退溪集》卷18,《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67页。
②李滉:《答李达李天机》,《退溪全书》(一)卷13,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54页。
③李滉:《答李公浩问目》,《书》,《退溪集》卷39,《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83—384页。
④李滉:《答郑子中别纸》,《书》,《退溪集》卷25,《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02页。
⑤黄宗羲:《诸儒学案上二》,《明儒学案》卷44,《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
①“气有生死,理无生死之说”。(李滉:《答郑子中别纸》,《书》,《退溪集》卷24,《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73页)②李滉:《答郑子中讲目》,《书》,《退溪集》卷25,《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95页。
①李滉:《答南时甫》,《书》,《退溪集》卷14,《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66—367页。
②李滉:《答郑子中别纸》,《书》,《退溪集》卷24,《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73页。
③李滉:《答郑子中别纸》,《书》,《退溪集》卷24,《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73页。
④“李公浩问于退溪先生曰:‘七情犹可谓之有善恶者,以其气未必纯善故也。但未知气本未纯善,则当其未发,谓之善恶未定可也,其谓之纯善无恶者何义?’答曰:‘湛一气之本。当此时,未可谓之恶,然气何能纯善?惟是气未用事时,理为主故纯善耳。’”(韩元震:《心纯善辨证》,《杂著》,《南塘集》卷29,《韩国文集丛刊》20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版,第129页)①李滉:《答奇明彦》,《书》,《退溪集》卷17,《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32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别纸》,《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24页。
③李滉:《与朴泽之》,《书》,《退溪集》卷12,《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37页。
④李滉:《祭亡友秋峦郑君之云文》,《退溪全书》(二)卷4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8页。
①奇大升:《郑秋峦天命图说序》,《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44页。
①研究郑之云性理学思想的基本资料有,《天命图解》和《天命图说》。《天命图解》为郑氏的原作,《天命图说》为经李滉修订后之作。《天命图解》和《天命图说》上都有郑之云的序文,李滉还为《天命图说》写了“后叙”。(参见丁大丸:《朝鲜朝性理学研究》,春川:江源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74页)②参见丁大丸:《朝鲜朝性理学研究》,春川:江源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76页。
①在韩国儒学史上以权近的《入学图说》为嚆矢,还出现过不少图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图解有金泮的《续入学图说》、权採的《作圣图》和《作圣图说》、郑之云的《天命图解》以及经李滉修订的《天命图说》、李滉的《圣学十图》等。其中,郑之云的《天命图解》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郑之云作《天命图解》后继续对此图加以修改以及与李滉相识后请教于李氏并与之一起修订《天命图解》等事例说明,起初郑、李二人对其修订的内容亦并未确信,即到此时为止李滉抑或是韩国性理学还未完全确立“四端七情”分属理气的理论主张。之后因受到奇大升的质疑,李滉一边接受其建议的同时,一边对其原有表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此过程中最终确立其“四七理气分属”理论。韩国性理学正是以此为起点,进入到极具细密性、精微性的独立发展阶段。(参见丁大丸:《郑之云与四七论争的发端》,载《四端七情论》,首尔:曙光社1992年版,第45、46页内容及当页注释)②参见丁大丸:《郑之云与四七论争的发端》,载《四端七情论》,首尔:曙光社1992年版,第44—47页。
③此点根据在于《天命图解》完成的时间,此图解完成于1543年。此时离徐敬德去世有3年、离李彦迪去世有10年时间。徐敬德还未完成其代表作《原理气》、《理气说》、《太虚说》、《鬼神死生论》等。李彦迪因当时还任官职,也未完成《大学章句补遗》、《奉选杂仪》、《求仁录》、《进修八规》、《中庸九经衍义》等性理学著述。(参见丁大丸:《郑之云与四七论争的发端》,载《四端七情论》,首尔:曙光社1992年版,第45页注释)①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②奇大升:《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6页。
③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5—406页。
②李滉:《天命图说后叙》,《退溪全书》(二)卷4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25—326页。
③李滉:《答李仲久》,《退溪集》卷11,《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04页。
④李滉:《与奇明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2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7页。
②李滉:《与奇明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7页。
③李滉:《心统性情图说》,《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别纸》,《退溪全书》(一)卷1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55—456页。
①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1—270页;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②《张子之书一》,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3页。
③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④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⑤李滉:《改本》,《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2页。
①参见金基铉:《退溪的四端七情论》,载《四端七情论》,首尔:曙光社1992年版,第56—57页。
②李滉:《心统性情图说》,《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③参见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①李滉:《心统性情图说》,《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206页。
②李震相:《答宋康叟》,《寒洲集》卷14,《韩国文集丛刊》317,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332—333页。
③《答李宏仲问目》,《退溪全书》(二)卷3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26页;另见宋时烈:《退溪四书质疑疑义二》,《杂著》,《宋子大全》卷133,《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65页。
④李滉:《心统性情图说》,《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三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29—430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③李滉:《后论》,《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22页。
④李滉:《改本》,《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9页。
⑤李滉:《改本》,《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9页。
⑥李滉:《改本》,《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9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①李滉:《附录·实记》,《言行录》卷6,《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46页。
②张立文:《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③李滉:《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4页。
④李滉:《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①退溪曰:“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李滉:《第四大学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3页)②李滉:《第一太极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199页。
③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①李滉:《第二西铭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1页。
②李滉:《第二西铭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0页。
③李滉:《第四大学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3页。
④权近:《论文科书》,《阳村集》卷31,《韩国文集丛刊》7,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281页。
⑤朱熹:《大学或问》,《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①李滉:《第三小学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2页。
②李滉:《答南时甫》,《退溪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65页。
③李滉:《答李平叔问目·大学》,《退溪全书》(二)卷3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58页。
④《大学一·纲领》,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8页。
⑤李滉:《第四大学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3页。
⑥《学三·论知行》,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0页。
①李滉:《第四大学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3页。
②李滉:《第五白鹿洞规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4页。
③李滉:《第三小学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2页。
④李滉:《第五白鹿洞规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4页。
⑤参见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2—243页;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①《张子之书一》,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3页。
②李滉:《第六心统性情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206页。
③“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所载本也。”(李震相:《答宋康叟》,《寒洲集》卷14,《韩国文集丛刊》317,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332—333页)①李滉:《答李叔献》,《退溪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80页。
②李滉:《第七仁说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6页。
③李滉:《答黄仲举》,《退溪集》卷19,《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87页。
④李滉:《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11页。
①李滉:《第九敬斋箴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9页。
②李滉:《答李叔献(珥)》,《书》,《退溪集》卷14,《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71页。
③李滉:《第九敬斋箴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9页。
④元儒程端礼曾在《读书分年日程》中,将程子的《四箴》、朱子的《敬斋箴》、真西山的《夜气说》、陈柏的《夙兴夜寐箴图》指定为学者当熟玩体察的文章。(参见程端礼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41页)⑤李滉:《第十夙兴夜寐箴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10页。
①参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48页。
②参见张立文:《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③李滉:《第九敬斋箴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10页。
④参见张立文:《李退溪思想世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⑤参见张立文:《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⑥《学六·持守》,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7页。
①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②《学六·持守》,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5页。
③参见张学智:《心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④李滉:《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4页。
①李滉:《答金而精》,《书》,《退溪全书》(二)卷29,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91页。
②陈澔注:《儒行第41》,《礼记集说》卷10,《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③学界对于奇大升的出生地、出生日期及亲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可参阅郑炳连:《关于奇高峰生平的几点问题》,《东洋哲学研究》1996年第15辑。
①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2页。
②奇大升:《首条第二条》,《第一书改本》,《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1页。
③奇大升:《首条第二条》,《第一书改本》,《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1页。
④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⑤“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理气上》,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①奇大升:《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8页。
②奇大升:《首条第二条》,《第一书改本》,《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1页。
③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第四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7页。
④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第十节,《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1页。
①沈演:《请享疏》,《疏》,《高峰先生别集附录》卷2,《高峰集》第二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88页。
②奇大升:《高峰先生年谱》,《高峰集》第一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6页。
③奇大升于宣祖五年(1572年)辞世,享年46岁。但是,其思想成熟较早,明宗十四年(1559年)李滉主动致书奇氏征求自己对“四端七情理气之发”的下语是否无病一事便是例证。可见,尽管二人年龄实际相差26岁之多,但是李滉对奇大升的学问和为人却十分推重,不以后辈待之。
④奇大升:《论困知记》,《高峰先生文集》卷1,《高峰集》第一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73页。
①罗钦顺与王阳明、湛若水及欧阳德等人的往复辩论书信现收录于《困知记》附录中。(参见罗钦顺:《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1—234页)②奇大升:《论困知记》,《高峰先生文集》卷1,《高峰集》第一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73页。
①罗钦顺:《困知记·序》,《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②罗钦顺:《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③罗钦顺:《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①奇大升:《论困知记》,《高峰先生文集》卷1,《高峰集》第一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73—74页。
②参见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③张廷玉等:《明史》24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237页。
④黄宗羲:《诸儒学案中一》,《明儒学案》卷47,《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⑤罗钦顺:《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页。
①罗钦顺:《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8页。
②奇大升:《论困知记》,《高峰先生文集》卷1,《高峰集》第一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74页。
①黄宗羲:《师说》,《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
①黄宗羲:《诸儒学案中一》,《明儒学案》卷47,《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409页。
②参见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323页;蒙培元:《理学的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③如林月惠教授指出:“现代学者似乎以为罗整庵的思想充满矛盾或不一致性。问题是,罗整庵的‘理气为一物’与其‘心性之辨’果真自相矛盾吗?这究竟不同学者根据不同判断得到的外在批评?还是不能善解罗整庵思想所下的判断?因为,在阅读哲学文本时,我们理解与诠释的起点,总是尽可能预设哲学家有一致性的观点。就以罗整庵为例,不论明代理学或朝鲜性理学,都将罗整庵归诸朱子学,则整庵之说,到底在哪个义理脉络下属于朱子学?这是必须探讨的问题。若以朱子为判准,字面上理解整庵的‘理气为一物’之说,似乎与朱子理气二元性的性的倾向不一致。但是,若罗整庵‘理气为一物’之意涵,在根本义理上不背离朱子理气‘不离不杂’的义理要旨,则罗整庵之理气论就不一定与朱子对立。如此一来,向来加诸整庵思想的‘矛盾’标签,亦可消解,罗整庵仍可复归于朱子学脉的传承系谱内。上述的设问,在朝鲜性理学者对整庵的评价中,可以得出线索。”由韩国儒者对罗钦顺的评价入手,探讨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特点是极好的研究视角,值得重视。林教授对此问题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参见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52—191页)④朱子极重张横渠之“心统性情”说及心、性、情三分结构说。朱子曰:“旧看五峰说,只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后来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有大功”;“横渠‘心统性情’语极好”;“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性、情、心,惟孟子、横渠说得好”。(《性理二》,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1、92、93页)①陈来先生认为,黄宗羲把“理/气”的二分分析看作一个绝对的、普遍的方法,认为无论主体、客体、实体、功能都应采取这种分析方法。朱子则与之不同,在人论方面,理气的方法只限于追溯意识情感的根源性分析和人身的结构分析。朱子从不把意识活动系统(即“心”本身)归结为“理”或者“气”。在朱子哲学中,知觉神明之心是作为以知觉为特色的功能总体,而不是存在实体,故不能把对存在实体的形上学分析(“理/气”)运用于对功能总体的了解。在功能系统中质料的概念找不到它适当的地位。另外,形上学的“理/气”分析把事物分解为形式、质料的要素,而“心”是统括性情的总体性范畴,并不是要素。这些都决定了存在论的形上学分析不能无条件地生搬硬套在朱子哲学中对“心”的把握上面。(参见陈来:《朱子哲学中的“心”的概念》,载《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26—128页)②李滉曰:“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盖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气生也。《易》言‘复其见天地之心’,是言气动而理显,故可见也(凡言心者,皆兼理气看)。二者皆属造化而非二致。故延平以复见天地之心,为动而生阳之理,其言约而尽矣。若朱子所引喜怒哀乐已发未发,虽亦合理气而言,只是就人心言动静,不可与说造化处牵合为说,故延平不以为然耳(此朱子初年所见,后来无此等说)。今曰‘朱子似以动而生阳,专作气看,故以为已发’,恐未必然也。又曰‘所谓一阳生者,专指气言,故以为已发’,恐未必然也。又曰‘所谓一阳生者,专指气言,其下系之以见天地之心,然后专是言理’,亦恐太分开看了。”(李滉:《答郑子中别纸》,《书》,《退溪集》卷24,《韩国文集丛刊》
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02页)③李滉:《答李达李天机》,《退溪全书》(一)卷13,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54页。
①奇大升:《论困知记》,《高峰先生文集》卷1,《高峰集》第一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74—75页。
②罗钦顺:《答欧阳少司成(甲午秋)》,《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7页。
①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第十节,《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1—112页。
②奇大升:《先生前上状》,《两先生往复书》,《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44页。
③奇大升:《答退溪先生问目》,《高峰先生文集》卷3,《高峰集》第一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29页。
④奇大升:《先生前上状》,《两先生往复书》,《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43页。
①参见刘明钟:《奇大升与<困知记>》,载《高峰学论丛》,韩国高峰学术院1993年版,第252页。
②奇大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4页。
③李滉:《答奇明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7页。
①李滉:《非理气为一物辩证》,《退溪全书》(二)卷4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30—332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7页。
①奇大升所言“七情”,多以《中庸》之喜、怒、哀、乐来指代。
②李滉:《与奇明彦·己未》,《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2页。
③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①参见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②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杨祖汉先生谓:“高峰此语,本于朱子。”《朱子语类》载:“又问:‘孟子言性,与伊川如何?’曰:‘不同。
孟子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气质而言,要之不可离也。’”(《性理一·人物之性气质之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页)③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④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①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②参见黄义东:《栗谷学的先驱与后学》,首尔:艺文书院1999年版,第211页。
③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3页。
①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3页。
②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3页。
①奇大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3页。对这段引文的部分内容退溪在《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
二书》中作了改动,如将本段引文中的“七情之发”以下“朱子谓‘本有当然之则’,则非无理”一句,改为“程子谓之‘动于中’,朱子谓之‘各有攸当’,则固亦兼理气”;“为理之本体”,改为“顾为理,不为气”;“七情”以下“善恶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则心已不得其正,而必发而中节,然后谓之‘和’”一段文字,改为“本善,而易流于恶,故其发而中节者,乃谓之‘和’”;“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一句中,则删掉“与所重”三字。(参见奇大升:《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第一书改本》,《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7页)结合李滉的《改本》阅读上引段落,有助于掌握其在论辩过程中的思想变化。
②奇大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4页。引文中的“似遂以”以下一段文字,退溪在《答奇明彦·论
四端七情第二书》中改为“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分矣。若真以为一物而无所分,则非滉之所敢知。不然,果亦以为非一物而有所别,故本体之下著‘然也’二字,则何苦于图,独以分别言之为不可乎?”(奇大升:《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第一书改本》,《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7页)①奇大升:《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4页。
②参见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③“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问:“看得来如喜怒爱恶欲,却似近仁义。”曰:“固有相似处。”(《孟子三·公孙丑上之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97页)①奇大升:《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6页。
②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5页。
③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9页。
④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6—107页。
①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9—110页。
①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0页。
②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4页。
③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①奇大升:《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第二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20页。
②奇大升:《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第二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21页。
①对于奇大升“因说”、“对说”问题的论述可参见李相殷:《四七论辩与对说、因说的意义》,载《高峰学论丛》,高峰学术院1993年版,第131—160页;黄义东:《高峰奇大升的哲学研究》,高峰学术院
2002年版,第126—132页。
②奇大升:《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1页。
③奇大升:《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3页。
①奇大升:《俚俗相传之语,非出于胡氏》,《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8页。
①奇大升:《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2页。
②奇大升:《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2页。
③李滉:《答奇明彦》,《退溪全书》(一)卷1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39页。
①奇大升:《奉别退溪先生》,《高峰续集》卷1,《高峰集》第二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9页。
②李滉:《京次韵奉赠》,《诗》,《退溪全书》(一)卷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154页;另见奇大升:《退溪先生次韵》,《高峰续集》卷1,《高峰集》第二辑,韩国东洋哲学会
1997年版,第19页。
③奇大升:《退溪先生墓碣铭先生自铭并书》,《高峰先生文集》卷3,《高峰集》第一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95页。
①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第十节,《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1—112页。
②奇大升:《首条第二条》,《第一书改本》,《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1页。
③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④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第四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7页。
⑤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第十节,《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1页。
①李滉:《答李达李天机》,《退溪全书》(一)卷13,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54页。
②李滉:《答李达李天机》,《书》,《退溪集》卷13,《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56页。
③参见张立文:《李退溪思想世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④奇大升:《第一书改本·首条第二条》,《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1页。
⑤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第六节,《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8页。
①奇大升:《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8页。
②奇大升:《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6页。
①奇大升:《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3页。
②奇大升:《高峰答郑秋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42页。
③奇大升:《四端七情总论》,《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40页。
①奇大升在《四端七情后说》中谓:“孟子论四端,以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夫有是四端,而欲其扩而充之,则‘四端是理之发’者,是固然矣。”(奇大升:《四端七情后说》,《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9页)②奇大升:《高峰答退溪再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下篇》卷2,《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32页。
③奇大升:《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6页。
④奇大升:《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12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5—406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7页上。
③李明辉先生指出,奇大升与李滉的主要分歧在于,高峰坚持四七的同质性,退溪主张四七的异质性。并认为高峰严守朱子的立场,将理本身视为“仅存有而不活动”;退溪则游移于孟子和朱子之间,而未清楚地意识到其间的矛盾。在以上基本前提下,双方各自引经据典,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参见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176页)张立文先生谓,高峰与退溪“四七理气”之辨的分歧处在于,高峰重视理气妙合之中的混沦性,而退溪忽视之。(参见张立文:《高峰奇大升》,载李甦平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此两种观点有助于学者对奇大升与李滉“四七理气”之辨理论特点的把握。
①李珥:《论心性情》,《栗谷全书》(一)卷14《杂著》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96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9页。
③李珥:《进札》,《圣学辑要》一,《栗谷全书》(一)卷19,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9页。
①李珥:《年谱》(上),《栗谷全书》(二)卷33《附录一》,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1—282页。
②李珥:《花石亭》,《诗》(上),《栗谷全书》(一)卷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1页。
③金长生亦谓:“尝题诗《花石亭》,格调浑成,虽老于诗律者,有能不及也。”(金长生:《栗谷先生行状》,《栗谷全书》(二)卷3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92年版,第342页)①李珥:《自警文》,《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300页。
②李滉:《答赵士敬·戊午》,《书》,《退溪集》卷23,《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6页。
③李珥:《行状》,《栗谷全书》(二)卷3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343页。
①宋时烈:《紫云书院庙庭碑》,《栗谷全书》(二)卷37《附录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02页。
②宋时烈:《紫云书院庙庭碑》,《栗谷全书》(二)卷37《附录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02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2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2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4页。
②李珥:《语录上》,《栗谷全书》(二)卷3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58页。
③罗钦顺:《困知记》卷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9—50页。
④关于此一问题可参考韩国学者尹南汉的研究。(参见尹南汉:《朝鲜时代的阳明学研究》,首尔:集文堂1982年版,第11页注6)尹氏认为《困知记》于1553年传入朝鲜半岛,大约于1560年在韩国刊行;相关论述还可参阅林月惠的研究。(参见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49—158页)⑤《困知记》传入朝鲜半岛后退溪便写《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驳斥了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说。
此外,奇大升著《论困知记》、李显益著《困知记辨》、韩元震著《罗整庵困知记辨》、李恒老著《困知记录疑》等,对罗氏的《困知记》进行评说。
⑥李珥:《学部通辨跋》,《栗谷全书》(一)卷13,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73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4—215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5页。
①朱子曰:“所谓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理离气杂不得。”“太极虽不离乎阴阳,而亦不杂乎阴阳。”(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72、1490页)①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7页。
②罗钦顺:《困知记》卷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7—38页。
①罗钦顺:《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4页。
②罗钦顺:《与林次崖佥宪》辛丑秋,《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6页。
③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9页。
④罗钦顺:《困知记》卷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页。
①罗钦顺:《答林次崖佥宪》壬寅冬,《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2—203页。
②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11,《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2页。
③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15,《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2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0页。
⑤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0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4—205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7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④李珥:《易数策》,《栗谷全书》(一)卷14《杂著》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304页。
⑤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7页。
①李珥:《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6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4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1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8—209页。
②李珥谓:“理通者,天地万物同一理也。气局者,天地万物各一气也。”(《圣学辑要》,《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7页)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
208页。
①成、李二人往复论辩期间,成浑致李珥的书函共为9封。但是现存的只有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5封,其余已佚。
①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②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194页。
①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0页。
①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1—212页。
②成浑曾质疑李珥谓:“只于才动之际,而便有主理、主气之不同,非元为互发,而各用事也。人之见理见气,各以其重而为言也。如是求之,与吾兄之诲不背焉矣!奈何朱子之说曰:‘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陈北溪之说曰:‘这知觉有从理而发者,有从气而发者。’正如退溪互发之说,何耶?”(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5页)①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
210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1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7—198页。
②参见张立文:《李退溪思想世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0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②李珥:《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6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④参见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页。
⑤李珥:《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6页。
⑥李珥:《杂记》,《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97页。
⑦李珥:《杂记》,《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97页。
⑧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193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9页。
③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2页。
①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3页。
②李珥:《理气咏呈牛溪道兄》,《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7页。
③李珥:《理气咏呈牛溪道兄》,《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7页。
④李珥:《年谱》(上),《栗谷全书》(二)卷33《《附录一》,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1页。
⑤李珥:《诸家记述杂录》,《栗谷全书》(二)卷38《附录》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29页。
①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①李珥:《理气咏呈牛溪道兄》,《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7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2页。
①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③参见陈来:《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①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2页。
②李滉:《李子粹语》卷1,《退溪全书》(五),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12页。
③李珥:《圣学辑要》三,《栗谷全书》(一)卷2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83页。
④李滉:《答奇明彦别纸》,《退溪全书》(一)卷1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55—456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193页。
②李珥:《理气咏呈牛溪道兄》,《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7页。
①李珥:《杂记》,《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97页。
①李珥:《诸家记述杂录》,《栗谷全书》(二)卷38《附录》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