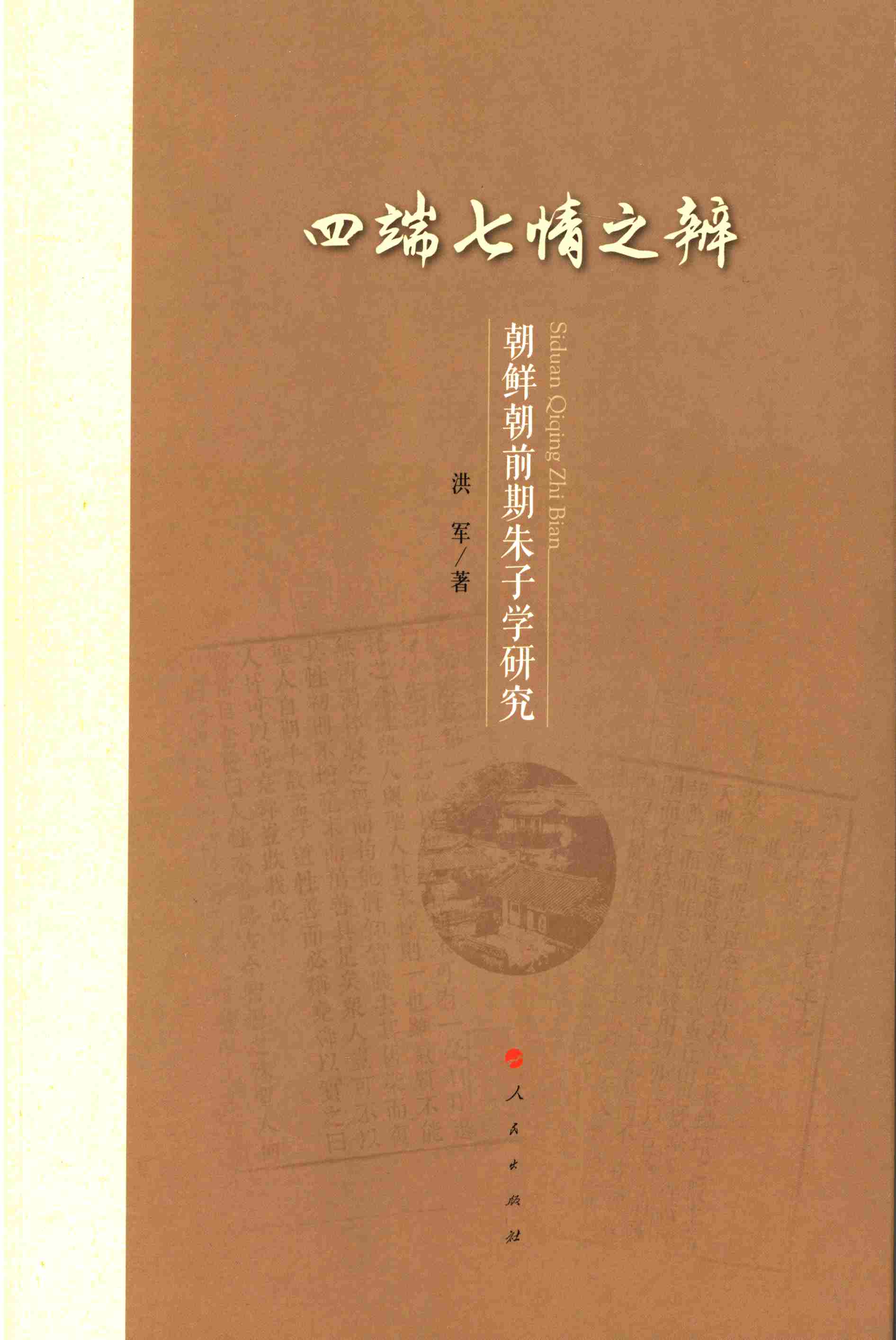第四节 李彦迪的理本论
| 内容出处: | 《四端七情之辨》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9034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李彦迪的理本论 |
| 其他题名: | 以“无极太极”之辨为中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2 |
| 页码: | 051-07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许多学术论辩,其中包括“无极太极”之辨,是对性理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李彦迪是朝鲜朝时期的学者,他与曹汉辅在《论无极太极书》一文中展开了论辩。李彦迪主张太极为万物之根本,而曹汉辅则认为太极即无极。李彦迪批评了曹汉辅的观点,并指出无极太极之理必须在至近而至实的实体中追求,否则会沦于空寂的异端。这场论辩对韩国性理学的发展和韩国儒学理论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
| 关键词: | 李彦迪 理本论 |
内容
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学术论辩有“无极太极”之辨、“四端七情理气”之辨、“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人物性同异(湖洛论争)”之辨以及“心说”论争等。其中,“无极太极”之辨是对性理学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其余皆为对性理学心、性、情等核心概念的深度辨析。这些论辩的依次展开不仅促进了韩国性理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韩国儒学独特理论风格的形成。从韩国儒学各个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争辩中,我们可以发现韩国性理学家们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本节要考察的是韩国儒学史上首次出现的学术论争——“无极太极”之辨。
一、论辩的发端
李彦迪(1491—1553年),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谥号文元,庆州府人。李氏出生于庆州良佐村,10岁丧父,12岁时短暂受学于其舅父愚斋孙仲暾(1463—1529年),而愚斋曾为佔毕斋金宗直门人。我们只知道李彦迪的思想与愚斋之弟亦为其舅父的忘斋孙叔暾①有所不同。李氏学无师承②,于中宗九年(1514年)登第,始入仕途,历任吏曹判书、刑曹判书、左赞成等官职。作为朝鲜朝前期士林学者的“五贤”③之一,他既是朝鲜朝主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先驱,又是朝鲜朝性理学鼎盛期的揭幕人。李彦迪一生从宦多年,旋进旋退,颇不平顺。在他8岁时发生“戊午士祸”,14岁时发生“甲子士祸”,29岁和55岁时又发生“己卯士祸”、“乙巳士祸”。韩国历史上的“四大士祸”皆曾亲历。但是,李彦迪始终将“养真”与“经世”④作为其平生之志,为后学树立了一个有担当、有追求的儒者形象。他23岁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生志业在穷经,不是区区为利名。
明善诚身希孔孟,治心存道慕朱程。
达而济世凭忠义,穷且还山养性灵。
岂料屈蟠多不快,夜深推枕倚前楹。⑤
此诗写于中宗九年,正是其中生员试之年。从“明善诚身”、“治心存道”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其强烈的希慕圣贤之情。诗中所抒发的正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的儒家理想情怀和入世精神。可见,李彦迪在步入仕途之初便立下修齐治平的人生志向。
他的学问和思想对韩国性理学的影响,从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滉之评价可以概见。李滉尝言:
谨受而伏读之,反复参究,质之以古圣贤之言,于是始知先生(指晦斋——引者注)之于道学,其求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正也。而凡先生之出处大节,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先生在谪所,作《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又修《中庸九经衍义》,《衍义》未及成书,而用力尤深。此三书者,可以见先生之学。而其精诣之见,独得之妙,最在于与曹忘机汉辅《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也。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呜呼,我东国古被仁贤之化,而其学无传焉。丽氏之末以及本朝,非无豪杰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归之者。然考之当时,则率未尽明诚之实,称之后世,则又罔有渊源之征,使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②
此段文字引自李滉为李彦迪所撰写的“行状”,文中他对李氏的生平和学问做了简明扼要之概括,称道其有精诣之见和独得之妙。文中李滉虽然举了《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成稿《中庸九经衍义》等李氏代表作,但是他认为李氏学问之理论精髓在于与曹忘机堂(名汉辅,庆州人)的《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中。其实,李滉提到的《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稿《中庸九经衍义》都是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所作。他在江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六年,最终在此地辞世,享年63岁。而与忘机堂的无极太极论辩书则作于李氏二十七八岁时,可见其思想成熟之早。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著作所表达的观点是早年与忘机堂曹汉辅论辩时确立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节也将以李彦迪与曹汉辅的《论无极太极书》为中心,来探讨其理本论哲学思想的特点。
这场论辩发生在1517年(中宗十二年)至1518年。最初是忘斋孙叔暾与忘机堂曹汉辅①之间通过书信对“无极太极”问题展开相互问难。李彦迪读到这些书信后,便撰写《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以下简称《说后》)一文对之加以评述。曹汉辅旋即对李彦迪的《说后》提出了异议。于是,李氏和曹汉辅之间开始有书信往来,现存《晦斋集》中有李彦迪答忘机堂书信四封。但曹汉辅致李彦迪的书信皆已失传,只能通过现存的李彦迪答曹汉辅书信一窥其思想梗概。
这里我们首先对《说后》的主要内容做些简要分析,以便对李彦迪、孙叔暾和曹汉辅的观点有个总体的了解。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说后》的内容按文意分为若干个段落,抄录如下:
第一段落:“谨按:忘斋无极太极辨,其说盖出于陆象山,而昔子朱子辨之详矣。愚不敢容赘。若忘机堂之答书,则犹本于濂溪之旨,而其论甚高,其见又甚远矣。其语《中庸》之理,亦颇深奥开广。得其领要,可谓甚似而几矣。然其间不能无过于高远而有悖于吾儒之说者。愚请言之:夫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柢也。是乃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来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哉!此理虽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实体之所以寓,则又至近而至实。若欲讲明此理而徒骛于窅冥虚远之地,不复求之至近至实之处,则未有不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矣。”②
本段引文的观点可视为李氏在“无极太极”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文中李彦迪首先对忘斋和忘机堂观点的理论来源作了说明,指出忘斋的主张出自陆子学说,而忘机堂的观点则本于濂溪之旨。他进而声言,陆子的无极太极之说因朱子已详辩无须赘言,而妄机堂的学说则因过于高远而似有背于吾儒之旨处。由此可见,宋代朱陆之辨是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之辨的理论先河。李彦迪在本段还阐述了自己对无极太极问题的基本理解,主张并非太极之上复有无极,此至高至妙之理只能在至近而至实处求之,不然就会有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的危险。由此可见,他对道体之根源、行为之应然等问题越有借由自己的理解。不过,从李氏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来看,其见似与朱子并无二致。此其所以李滉评论其学说时直言“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
第二段落:“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也则是矣。其曰岂有论有论无、分内分外,滞于名数之末则过矣。其曰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则是矣。其曰大本达道浑然为一则何处更论无极太极,有中无中之有间则过矣。此极之理虽曰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发差者。是岂漫无名数之可言乎?而其体之具于吾心者则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然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容不辨者。安有得其浑然则更无伦序之可论,而必至于灭无之地而后为此道之极致哉。今徒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极言之,而不知夫粲然者之未始相离也。是以其说喜合恶离、去实入虚,卒为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而后已。岂非穷高极远而无所止者欤?”①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援引朱子之说对忘机堂的不当言论进行了逐一反驳,指出其“太极即无极”、“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等见解可以成立,但不分有无、分内分外以及有中无中而论无极太极却明显不妥。李氏以为太极之理虽然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无有毫发之差。①而且,其“体”之具于吾心者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同。故不能只重其浑然而轻其伦序,“喜合恶离,去实入虚”。
第三段落:“先儒言周子吃紧为人特著道体之极致,而其所说用工夫处只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尝使人日用之间必求见此无极之真而固守之也。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若论工夫则只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今忘机之说则都遗却此等工夫,遽欲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万物朝宗于我而运用无滞,是乃欲登天而不虑其无阶,欲涉海而不量其无桥。其卒坠于虚远之域而无所得也必矣。大抵忘机堂平生学术之误病于空虚,而其病根之所在则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以灭字说太虚体,是断非吾儒之说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谓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谓于穆不已者存焉。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著灭字于寂字之下。试以心言之:喜怒哀乐未发、浑然在中者,此心本然之体而谓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则喜怒哀乐发皆中节,而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谓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灭则是枯木死灰而已,其得不至于灭天性乎?然忘机于本来寂灭之下便没灭字不说,而却云虚而灵、寂而妙。灵妙之体充满太虚、处处呈露,则可见忘机亦言其实理而说此灭字不去。故如是岂非有所穷而遁者乎?”②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直言不讳批评忘机堂,以为其平生之误在于“空虚”二字,而其病根则在“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他在指出错误根源的同时,还断言以“灭”字说太虚体“断非吾儒之说”。“寂灭”是佛教用语,《涅槃经》上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一句。而“诸行无常”则又是佛教三法印之一,因此《涅槃经》上的这一句又可视为佛家基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众所周知,大乘佛教不承认现实世界的实在性。以“四大”为假合,以寂灭为圆觉,遂将人伦道德视如赘疣。而儒家所说的“寂”则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寂”,与佛家之寂灭有着本质的区别。
李彦迪还批评忘机堂曹汉辅不仅在太极之上复设无极,而且漠视形而下之人伦日用之修养工夫。如果只关注形而上之“灵妙之体”,就无从体认至近至实处的太极之理。他认为上天无声无臭可谓“寂”,然至寂之中又有“于穆不已”,其化育流行遂生鸢飞鱼跃之景象,所以在“太极”之上绝不可添加一“灭”字。
“自汉以来圣道塞而邪说行,其祸至于划人伦、灭天理而至今未已者,无非此一灭字为之害也。而忘机堂一生学术言语及以上议论之误,皆自此灭字中来。愚也不得不辨。若其超然高会一理浑然之体而的无疑,则实非今世俗儒高释所可几及。亦可谓智而过者矣。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矣。而不幸世无孔孟周程也,悲夫!”①
在本文结尾处,李氏总结异端之弊害全在一“灭”字,而忘机堂为学论议之误亦皆源自此一“灭”字。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撰文辨析。“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
由此而论,李氏批评忘机堂曹汉辅的用意在于揭露其异端思想,像文章中隐约出现的佛家倾向。《说后》一文写于中宗十二年(1517年)正月,即李彦迪27岁之时。曹汉辅何时作复则已无从查考。从年谱上的记载看,李彦迪答忘机堂曹汉辅的第一封书信是在中宗十三年(戊寅年即1518年)写的。他时年28岁。
二、论辩的主要内容及理论特点
前已言及,“无极太极论辩”起因于李彦迪所撰的《说后》。该文写于中宗十二年,翌年曹汉辅对此提出异议。于是,便有了“答忘机堂”的四封书信。
在论辩的过程中,晦斋李彦迪和忘机堂曹汉辅围绕“无极”、“太极”概念以及儒家修养论等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发生于朝鲜朝初期的此一论辩中,李彦迪从朱子学理本论的立场出发,批驳了具有佛道思想色彩的曹汉辅的主张。此论辩在学理上可理解为“无极太极”问题的性理学式解读和非性理学式解读的立场对立。
因为《说后》主要是李彦迪对孙叔暾和曹汉辅的“无极太极”说的评论文章,故只能了解到他的思想概貌。不过,在“答忘机堂”的四封书信中却可以发现李氏较为系统的性理学观点。而且,从《说后》和《答忘机堂书》中还可以看出,曹汉辅的观点的确受到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故李彦迪在《答忘机堂书》中,指责其所持的是佛家之寂灭论而非儒家之寂感论。李氏和曹汉辅之间的论辩作为性理学本体论问题之探讨在韩国儒学史上意义重大,说明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已具备相当的理论水平。下面将对四封书信之内容做逐一分析。
在《答忘机堂第一书·戊寅》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伏蒙示无极寂灭之旨、存养上达之要,开释指教不一而足。亦见尊伯不鄙迪而收之,欲教以进之也。感戴欣悚,若无所容措。”①可知,曹汉辅在读了李氏所写的《说后》之后,就“无极寂灭”和“存养上达”等本体论、修养论问题给李氏回信,这应该是曹汉辅在致李彦迪信中谈的主要问题。
于是,李彦迪在复信中首先解释自己为何撰写《说后》,然后针对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又陈述了己见。他说:
来教所云寂灭存养之论有似未合于道者。小子亦有管见须尽露于左右者,敢避其僭越之罪而无所辨明耶。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风雷之所以变,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周子所以谓之无极者,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非若老氏之出无入有、释氏之所谓空也。①
从整个论辩过程中李氏自谦的语气和态度来看,曹汉辅应较彼时才二十七八岁的李彦迪年长许多。所以李氏在信中陈述己见时显得比较谨慎。对于曹氏的寂灭存养之论,李彦迪十分谦虚地讲到“小子亦有管见须尽露于左右”,然后谈了自己对“太极”与“无极”概念的理解。他指出“太极”作为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是实然而不可易者,周子所以又称之为“无极”乃因其具“无方所、无形状”之特性。究其实与佛道两家所言“空”、“无”等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接着他借“理”、“气”之概念阐发了己见,并对曹氏的本体论进行了批评:
今如来教所云,无则不无而灵源独立,有则不有而还归澌尽。是专以气化而语此理之有无,岂云知道哉?所谓灵源者气也,非可以语理也。至无之中至有存焉,故曰“无极而太极”。有理而后有气,故曰“太极生两仪”。然则理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而言。何必见灵源之独立然后始可以言此理之不无乎?鸢飞鱼跃昭著上下,亘古亘今充塞宇宙。无一毫之空阙,无一息之间断。岂可但见万化之澌尽而遂指此极之体为寂灭乎?②
从内容中可以推知,曹汉辅将“灵源”视为宇宙本体。而李彦迪则认为所谓“灵源”者其实是气,不能将形而下之“气”视为宇宙的终极本体。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其实是“至无之中至有存焉”之义。此处的“而”应指“所当然之中”的“所以然之理”——太极即是“理”。①李氏进而提出自己的理气观——“有理而后有气”,“理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理与气的关系问题是朱子学的基本问题,李氏对此所持的正是传统朱子学以理为本的理气二元论立场。
他还指出曹氏所云寂感、寂灭之分似同而实异的,先儒对此已有至论,后学者不可以此为浮议而独以异端之说为是:
盖太极之体虽极微妙,而其用之广亦无不在。然其寓于人而行于日用者,则又至近而至实。是以君子之体是道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有以全其本然之天而绝其外诱之私。不使须臾之顷、毫忽之微,有所间断而离去。其行之于身也,则必造端乎夫妇以至于和兄弟顺父母,而有以尽己之性。及其尽性之至也,则又有以尽人物之性。而其功化之妙极于参天地赞化育,而人极于是乎立矣。此君子之道所以至近而不远,至实而非虚,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此非愚生之言,实千古圣贤所相传授而极言至论者也。②
文中李彦迪借圣贤之言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表明己见合乎儒家正统。太极与理气的问题属于天道,李氏遂借探讨寂灭的问题将话题转入人道。他认为道不远人,若离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于空虚。李彦迪引用《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之句来说明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安得不先于下学之实务而驰神空荡之地?可以为上达乎?天理不离于人事。人事之尽而足目俱到以臻于贯通之极,则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浑全。酬酢万变、左右逢源,无非为我之实用矣。”③李氏依据朱子“统体一太极”的思想为依据,提出天理不离于人事,以此批判曹氏的“存养上达”修养方法的根本错误。李彦迪说: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又曰:“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讵不信欤?且如存养之云,只是敬以直内,存之于未发之前以全其本然之天而已。苦曰游心于无极之真。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使人不为近思之学而驰心空妙。其害可胜言哉?又况虚灵本是吾心之体也。无极之真,本是虚灵之中所具之物也。但加存之之功而不以人欲之私蔽之,以致其广大高明之体可也。张南轩曰:“太极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惟当本于敬以涵养之。”正谓此也。今曰“游心于无极”,曰“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似以无极太极为心外之物而别以心游之于其间,然后得以为之主也。此等议论似甚未安。①
李彦迪在文中先讲明虚灵、无极之真以及吾心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儒家修身的正确方法。由此可见二人为学工夫之差异。李彦迪强调洒扫应对当中的“下学而上达”,而曹氏则主张带有“顿悟”性质的“存养而上达”。后者的主张当然会受到正统儒者的批评。在结尾处李彦迪写道:
来教又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亦见尊伯立言之勇而自信之笃也。然前圣后圣其揆一也。今以已往圣贤之书考之,存养上达之论无所不备。其曰“存心养性”,其曰“戒慎恐惧”,其曰“主静曰主敬”者,无非存养之意。而曷尝闻有如是之说乎?吕氏虚心求中之说,朱子非之。况以游心无极为教乎?孔子生知之圣也,亦曰“我下学而上达”,又曰“吾尝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况下于孔子者乎?故程子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欲人收已放之心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以此观之,其言之可易与不可易直验于已往之圣人而可见矣。何必有待于后来复起之圣人乎?天下之祸,莫大于甚似而难辨。惟其甚似,故能惑人;惟其难辨,故弥乱真。伏详赐书,无非杂儒释以为一。至有何必分辨之说,此小子所甚惧而不敢不争者也。伏见尊伯年高德邵,其于道体之妙亦可谓有所见矣。但以滞于寂灭之说,于其本源之地已有所差。而至于存养上达之论,则又与圣门之教大异。学者于是非之原毫厘有差,则害流于生民,祸及于后世。况其所差不止于毫厘乎?伏惟尊伯勿以愚言为鄙,更加着眼平心玩理。黜去寂灭游心之见,粹然以往圣之轨范自律。吾道幸甚!善在刍荛,圣人择之。况听者非圣人,言者非刍荛。而遽指言者为狂见而不察乎?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古之君子改过不吝,故年弥高而德弥进也。小子所望于尊伯者止此。①
从曹汉辅“游心于无极之真”以及“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等见解中确实可以感受到其思想明显混杂于佛理。所以李彦迪在此信的末尾处称忘机堂“无非杂儒释以为一”,与圣门之教的理论旨趣相去甚远。尽管二人年龄相差较大,李彦迪仍以昂扬的卫道精神据理力争。
接到曹汉辅的回信后,李彦迪在《答忘机堂第二书》中写道:“伏睹来教于无极上去‘游心’二字,于其体至寂下去一‘灭’字。是不以愚言为鄙,有所许采。幸甚幸甚!”②这表明忘机堂接受李氏在第一封信中的批评,已去掉无极之上的“游心”二字和其体至寂下的一“灭”字。但是,彦迪仍然觉得曹汉辅尽管在字句上对之前的表述做了些调整,却并未尽弃其思想中的佛、道立场。于是,他继续提出委婉的批评:
书中所论一本之理及中庸之旨,亦颇明白少疵、妙得领要。圣人之道,固如斯而已,更无高远难穷之事。迪敢不承教。③
文中提到的“一本之理”和“中庸之旨”分别指的是第一封信中所讨论的无极太极、寂灭等本体论的问题和有关存养上达的工夫论问题。可见,在内容上此信殆可视为第一封信之继续。李彦迪提到:
至如寂灭之说,生于前书粗辨矣。未蒙察允,今又举虚灵无极之真,乃曰“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是未免于借儒言而文异端之说。小子之惑滋甚。先儒(指朱子——引者注)于此四字盖尝析之曰:“此之虚,虚而有;彼之虚,虚而无;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灭。”然则彼此之虚寂同,而其归绝异,固不容不辨。而至于无极之云,只是形容此理之妙无影响声臭云耳,非如彼之所谓无也。故朱子曰:“老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讵不信欤?①李彦迪认为曹氏的“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实际上是借吾儒之言文饰异端之说。他举朱子之言阐明儒家的虚寂观念与异端之虚寂说犹如南北水火之相反,在理论归趣上决然不同。彼此之虚寂名同而实异。
李彦迪进而指出:
来教又曰:“主敬存心而上达天理。”此语固善,然于上达天理上却欠“下学人事”四字,与圣门之教有异。天理不离于人事。下学人事,自然上达天理。若不存下学工夫,直欲上达,则是释氏觉之之说。乌可讳哉?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则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便是上达境界。从事于斯,积久贯通,可以达乎浑然之极矣。而至于穷神知化之妙,亦不过即是而驯致耳。②
李彦迪在为学次第上重视“下学人事”,体现心性工夫之切近日用人伦的一面。他引孔子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之语以证明己之看法。最后李彦迪写道:
夫穷理,非徒知之为贵。知此理又须体之于身而践其实,乃可以进德。若徒知而不能然,则乌贵其穷理?而其所知者终亦不得而有之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然则非知之难,行之难。此君子所以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必顾行、行必顾言,不敢容易大言者也。不知尊伯亦有如是体察之功乎?亦有如是践履之实乎?大抵道理,天下之公共。不可以私智臆见论之。要须平心徐玩,务求实是可也。③
依李彦迪之见,所谓“穷理”指的是由亲身体验知晓此理,必以进德为期才是理学家所谓德性之知。他委婉指出若无“体察之功”、“践履之实”,则所见往往流为异端。作为晚辈祈盼曹氏痛去寂灭之见,又能主敬存心以达于天理。诚如此,“则尊伯之于斯道,可谓醇乎醇矣。”①前已论及曹李二人年龄差距较大。但是从信的内容来看,曹汉辅并未轻视一位新锐学者对己见之质疑。于是,有了他们之间的第三封书信。
在《答忘机堂第三书》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伏睹来喻所陈,虽云不滞寂灭之说有年,而寂灭之习似依旧未除。是以其论说浮于道理幽妙之致,而未及反躬体道之要。不免为旷荡空虚之归,而非切近的当之训。此小子所以未敢承命者也。”②于是李氏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体道经验和感悟。
从此信的内容可以推知,曹汉辅复信中的主张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大本”与“达道”,即“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的存养之道问题。彦迪在信中提到:
迪闻子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古今论道体,至此而无余蕴矣。愚请因此而伸之。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散诸三极之间。凡天地之内,无适而非此道之流行,无物而非此道之所体……当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此心之真寂然不动。是则所谓无极之妙也,而天下之大本在于是也。固当常加存养之功以立大本,而为酬酢万变之主。而后可以发无不中而得时措之宜。然于此心之始动几微之际,天理人欲战于毫忽之间,而谬为千里之远。可不于是而益加敬慎乎?是故君子既常戒惧于不睹不闻之地,以存其本然之,而不使须臾之离有以全其无时不然之体……自其一心一身以至万事万物,处之无不当,而行之每不违焉。则达道之行于是乎广矣,而下学之功尽善全美矣。二者相须,体道工夫莫有切于此者。固不可阙其一矣。
来教有曰:“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则固存养之谓矣,而于静时工夫则有矣。若夫顿除下学之务,略无体验省察之为,则于动时工夫盖未之及焉。是以其于求道之功疏荡不实,而未免流为异端空虚之说。
伏睹日用酬酢之际,不能无人欲之累。而或失于喜怒之际,未能全其大虚灵之本体者有矣。岂非虽粗有敬以直内工夫,而无此义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体道不能精密而或至于此乎。昔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子继之曰:“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然则圣门工夫虽曰主于静以立其本,亦必于其动处深加省察。盖不如是则无以克己复礼,而保固其中心之所存矣。故曰“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未有不制其外而能安其中者也。愚前所云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顾行行顾言者,此之谓也。安有遗其心官、随声逐色,失其本源之弊哉?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盖地位已到圣人,则此等工夫皆为筌蹄矣。若未到从容中道之地而都遗却择善省察工夫,但执虚灵之识。①
李彦迪在信中对儒家的“大本”与“达道”作了简单明了的论述,这表明他对之已有了深切之体悟。李彦迪在工夫论问题上的立场是,“常加存养之功以立大本,而为酬酢万变之主”。他主张“存养”不能像曹汉辅那样只强调“敬以直内”,而忽视“义以方外”。在李彦迪看来,不假修为即可克己复礼、酬酢万变如同不出门而欲适千里,不举足而欲登泰山,结果肯定是“必不能矣”。
二是曹汉辅认为为破世人执幻为真,故言“寂灭”。对此有悖儒家宗旨的“异端”之见,李彦迪批评道:
来教又曰:“为破世人执幻形为坚实,故曰寂灭。”此语又甚害理。盖人之有此形体,莫非天之所赋而至理寓焉。是以圣门之教,每于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尽夫天之所以赋我之则,而保守其虚灵明德之本体。岂流于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岂可以此为幻妄?必使人断除外相,独守虚灵之体,而乃可以为道乎?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此寂灭之教所以陷于空虚诞谩之境,而无所逃其违天灭理之罪者。①众所周知佛教主张“四大皆空”,其耽空沦寂之弊对儒家之教危害甚深。李彦迪依性理学“道器不离”、“体用一源”之旨对之予以批驳。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肯定了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这一点在讨论“下学上达”时讲得更透彻。
三是在“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上,曹汉辅认为“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对此李彦迪不以为然。他说:
今曰“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愚请以孔子申之。自生民以来,生知之圣未有盛于孔子者,亦未尝不事于下学……然则孔子不得为豪杰之士,而其所为亦不足法欤?若曰孔子之言所以勉学者也,于其己则不必,然则愚请以孔子所亲为者白之。孔子问礼于老聃,问官于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是非下学之事乎?问官之时,实昭公十七年而孔子年二十七矣。入太庙则孔子始仕时也。古人三十而后仕,则是时孔子年亦不下三十。其非童蒙明矣。夫以生知之圣,年又非童蒙,而犹不能无下学之事。况不及孔子?而遽尔顿除下学不用力,而可以上达天理乎?是分明释氏顿悟之教,乌可尚哉?孟子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若使尊伯于此异说之诞终身迷没,不知其非则已矣。今曰不滞者有年,则是已觉其非而欲改之也。退之云“说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请自今痛去寂灭之见,反于吾道之正。②
曹汉辅与李彦迪二人在为学之方上的分歧与宋代朱陆之间“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颇有相似之处。陆氏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将朱子的“博学于文”视为“支离事业”。朱子则批评象山为学浮躁,只好发高论而不“道中庸”,造说遂与佛老相似。③在为学之方上李彦迪以圣贤为例批驳了曹氏的观点,强调不论童蒙初学还是豪杰之士皆不能无下学之事。
《答忘机堂第四书》是两人之间最后一次通信,在复信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今承赐教,辞旨谆谆,反复不置,且去‘寂灭’二字而存‘下学人事’之功。迪之蒙许深矣,受赐至矣,更复何言!”①从中可推知,经过几次书信往来曹汉辅对李彦迪的批评有所接受,对自己的立场也做了调整。而且李彦迪也认可曹汉辅态度之转变。他在信中指出:“然而窃详辱教之旨,虽若尽去异说之谬、入于圣门之学,然其辞意之间未免有些病。而至于物我无间之论,则依旧坠于虚空之教。小子惑焉。”②但在李彦迪看来,忘机堂仍未彻底摒弃其原有思想。第四封信的讨论焦点是有关“主敬存心”的工夫论问题。李彦迪写道:
圣门之教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齐其外以养其内。内则无贰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俨然肃然,深省密察,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动直、中一外融,则可以驯致乎不勉不思从容中道之极矣。两件工夫不可偏废明矣。安有姑舍其体而先学其用之云哉?③
李彦迪将理学工夫论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简言之,即践行居敬穷理。这是基于伊洛渊源的正统解释。李彦迪在信中十分强调“敬”之工夫,这一思想对后来李滉的主敬工夫论颇有影响。李彦迪援引程伊川从《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中提炼出来的道德戒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本体工夫固不可不先,而省察工夫又尤为体道之切要”。他认为颜子亦循此四箴之路径优入圣域,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李彦迪主张为人要谨守“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由此他对曹氏在第三封复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一一做了答复。
一是“主敬存心”的问题。李彦迪以“衣”、“网”为例答复说:“伏睹来教有曰‘主敬存心’,则于直内工夫有矣,而未见义以方外省察工夫。岂非但得衣之领而断其百裔,但得网之纲而绝其万目者哉?人之形体固当先有骨髓,而后肌肤赖以充肥。然若但得骨髓,一切削去皮肤,则安得为人之体?而其骨髓亦必至于枯槁而无所用矣。况既去皮肤而于骨髓亦未深得者哉?愚前所谓常加存养以立大本,为酬酢万变之主者,固尊伯主敬存心、先立其体之说。初非毁而弃之。未蒙照察,遽加罪责,不胜战汗。”①前已言及李氏并不反对“主敬存心”,只是向忘机堂强调了修养工夫不能缺失“义以方外”。在他看来,两段工夫同等重要,必须同时并举。
二是“先立其体和下学人事”的问题。李彦迪对此回复道:“来教又曰:‘先立其体,然后下学人事。’此语亦似未当。下学人事时,固当常常主敬存心。安有断除人事,独守其心?必立其体。然后始可事于下学乎。所谓体既立则运用万变,纯乎一理之正而纵横自得者。固无背于圣经贤传之旨。然其所谓纯乎一理、纵横自得者,乃圣人从容中道之极致。体既立后,有多少工夫?恐未易遽至于此。伏惟更加精察。”②此问题还是前一问题的延伸。李彦迪在存养省察的问题上立场鲜明,就是坚持下学与上达同时并进。
三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问题。李彦迪谈了自己的理解,指出:“且如万物生于一理。仁者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然其一体之中,亲疏远近是非好恶之分自不可乱。故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语》又曰:‘惟仁人为能好人,能恶人。’以此言之,仁者虽一体万物,而其是非好恶之公亦行乎其中而不能无也。舜大圣人也,固非有间而滞于所执者。然而取诸人为善,舍己从人则舜亦不能无取舍之别矣。安有心无间则茫然与物为一?更无彼此取舍好恶是非之可言,然后为一视之仁哉。”③追求“天人合一”是儒家修己的最高理想。但李彦迪强调的是“一体之中,亲疏远近是非好恶之分自不可乱”。他认为儒者同时还要具备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从而做到择善而从。
在信的最后李彦迪语词恳切,寄望曹汉辅平心察理,勿以其有是非取舍为罪。此后曹氏再未复信,而两人的论辩也就此而告终。从现存四封书信的内容来看,李氏最终也没能说服忘机堂尽弃其原有立场。读此书信可以感受到一位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士大夫①的卫道意识。两人温文尔雅之论辩既流露了少壮学者李彦迪的锐气和担当,又展现了学界名宿曹汉辅的平和与谦逊。
三、论辩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无极太极”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围绕与朱子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发生的首次论辩。此次论辩不论对李彦迪太极说的形成还是朱子学在韩国的发展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论辩的过程中,李彦迪基于朱熹之理气二元论对具有佛道思想倾向的曹汉辅“无极太极”说进行了批驳。与此同时,他还以性理学为正统捎带批判佛道两家的理论。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论辩不仅令性理学之本体论得以确立,而且使儒佛与儒道之义理分际得以明晰。尽管此后还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四七理气”之辨、“人心道心”之辨和“人物性同异”之辨等等,但是此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视。
“四七理气”之辨则与“人心道心”之辨密切相关。后者也是朱子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韩国儒学史上令“四七理气”之辨得以进一步深化。本书将在论述四端七情论辩时设专节详述“人心道心”之辨。
与前一节介绍的徐敬德相比较,李彦迪虽亦重视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思想之旨趣却与徐氏大相径庭。徐敬德基于气本论之立场,主张“太虚即气”;而李彦迪则依据理本论之立场,将“太极”视为天理。“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①李彦迪从主理论出发,阐述了其“太极说”。他认为这种“理”是“无形无质”之存有,“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但理先气后,“有理而后有气”。②李彦迪进一步指出:“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有日月之形则有所以为日月之理,有山川之形则有所以为山川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③他以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天地万物之理(太极),而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后依然作为事物之所以然与大千世界密切结合。李彦迪又说:“天下之理体用相须、动静交养,岂可专于内而不于外体察哉?”④由此可见李彦迪哲学思想的主理论特色。
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著有《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中庸九经衍义》——后者虽未完稿,但是较为详细地反映了他的道德经世观。《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则是申述朱子之学的著作。在《大学章句补遗》一书中李氏曾言及朱子所作《格物补传》之不当处。例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原文“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下朱熹写道:“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接着又写道:“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⑤于是依程子之意作了格致章的补传。对此李氏指出:“朱子得其结语一句,知其为释格物致知之义,而未得其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所以发明始学穷理之要,亦甚明备。然愚尝读至于此,每叹本文之未得见。近岁闻中朝有大儒得其阙文于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见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见。取经文中二节,以为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复参玩,辞足义明,无欠于经文而有补于传义,又与上下文义脉络贯通。虽晦庵复起,亦或有取于斯矣。”①可见,他对朱子之《格物补传》有失当处极为自信。李彦迪以为《大学章句补遗》开头经文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②二节原为格致章的原文,如今被错误纳入经文之中。为此他主张应将此两节,重新归入格致章之原文之中。而“此谓知之至也”一句是结上文两节之意的。《大学章句补遗》写于1549年,李氏时年59岁,早已是成名的儒学大家。此文对研究李彦迪理学思想大有助益。相较于朱子,李氏更强调格物致知之“止于至善”。依李彦迪之见,致知宜有缓急先后,由近及于远,由人伦及于庶物,必有以见其至善之所在而知所止,然后其所知所得皆切于身心。
从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程朱之学,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蕴育,至李彦迪才有较具体系的性理学说。李氏的理气论和无极太极论在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他的思想在韩国儒学本土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李彦迪的性理学说成为日后李滉和李珥等人集朝鲜朝朱子学之大成的理论基础。李氏第一次将有关心性修养和经世致用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整理,为韩国儒学界确立了理本论哲学体系,而与曹汉辅之论辩集中反映了他的心性论思想。正是李彦迪将修身之存养工夫引向了心性论的进路。
李彦迪理本论思想对李滉的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滉十分推崇李彦迪,不仅称赞他的“立言垂后”之功,还曾为其作行状极言学力之深湛。李滉评论道:“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③还说:“近代晦斋之学甚正,观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义正,浑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④他认为李彦迪的学问“所得之深殆近世为最也”①。李珥尽管对李彦迪在“乙巳士祸”中的作为颇有微词,但对其学问还是相当首肯,尝言:“李彦迪博学能文,事亲至孝,好玩性理之书,手不释卷。持身庄重,口无择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学者亦以道学推之。”②
光海君二年(1610年),李彦迪还与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混作为“士林五贤”配享文庙。他的哲学著作有《求仁录》、《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中庸九经衍义》、《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答忘机堂书》以及《奉先杂仪》等。
概而言之,发生于16世纪初期的这场论辩反映了朝鲜朝初期的韩国儒者对理学本体论的不同理解。尽管这一论辩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力不及16世纪发生的“四端七情”之辨和“人心道心”之辨,但在理学本土化的初期即由深度的哲学思考树立了正统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后来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两位老少学者间展开的“无极太极”之辨在成就韩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的同时,还正式拉开了16世纪韩国儒学一系列精彩的学术论辩的序幕。
一、论辩的发端
李彦迪(1491—1553年),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谥号文元,庆州府人。李氏出生于庆州良佐村,10岁丧父,12岁时短暂受学于其舅父愚斋孙仲暾(1463—1529年),而愚斋曾为佔毕斋金宗直门人。我们只知道李彦迪的思想与愚斋之弟亦为其舅父的忘斋孙叔暾①有所不同。李氏学无师承②,于中宗九年(1514年)登第,始入仕途,历任吏曹判书、刑曹判书、左赞成等官职。作为朝鲜朝前期士林学者的“五贤”③之一,他既是朝鲜朝主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先驱,又是朝鲜朝性理学鼎盛期的揭幕人。李彦迪一生从宦多年,旋进旋退,颇不平顺。在他8岁时发生“戊午士祸”,14岁时发生“甲子士祸”,29岁和55岁时又发生“己卯士祸”、“乙巳士祸”。韩国历史上的“四大士祸”皆曾亲历。但是,李彦迪始终将“养真”与“经世”④作为其平生之志,为后学树立了一个有担当、有追求的儒者形象。他23岁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生志业在穷经,不是区区为利名。
明善诚身希孔孟,治心存道慕朱程。
达而济世凭忠义,穷且还山养性灵。
岂料屈蟠多不快,夜深推枕倚前楹。⑤
此诗写于中宗九年,正是其中生员试之年。从“明善诚身”、“治心存道”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其强烈的希慕圣贤之情。诗中所抒发的正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的儒家理想情怀和入世精神。可见,李彦迪在步入仕途之初便立下修齐治平的人生志向。
他的学问和思想对韩国性理学的影响,从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滉之评价可以概见。李滉尝言:
谨受而伏读之,反复参究,质之以古圣贤之言,于是始知先生(指晦斋——引者注)之于道学,其求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正也。而凡先生之出处大节,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先生在谪所,作《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又修《中庸九经衍义》,《衍义》未及成书,而用力尤深。此三书者,可以见先生之学。而其精诣之见,独得之妙,最在于与曹忘机汉辅《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也。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呜呼,我东国古被仁贤之化,而其学无传焉。丽氏之末以及本朝,非无豪杰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归之者。然考之当时,则率未尽明诚之实,称之后世,则又罔有渊源之征,使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②
此段文字引自李滉为李彦迪所撰写的“行状”,文中他对李氏的生平和学问做了简明扼要之概括,称道其有精诣之见和独得之妙。文中李滉虽然举了《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成稿《中庸九经衍义》等李氏代表作,但是他认为李氏学问之理论精髓在于与曹忘机堂(名汉辅,庆州人)的《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中。其实,李滉提到的《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稿《中庸九经衍义》都是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所作。他在江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六年,最终在此地辞世,享年63岁。而与忘机堂的无极太极论辩书则作于李氏二十七八岁时,可见其思想成熟之早。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著作所表达的观点是早年与忘机堂曹汉辅论辩时确立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节也将以李彦迪与曹汉辅的《论无极太极书》为中心,来探讨其理本论哲学思想的特点。
这场论辩发生在1517年(中宗十二年)至1518年。最初是忘斋孙叔暾与忘机堂曹汉辅①之间通过书信对“无极太极”问题展开相互问难。李彦迪读到这些书信后,便撰写《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以下简称《说后》)一文对之加以评述。曹汉辅旋即对李彦迪的《说后》提出了异议。于是,李氏和曹汉辅之间开始有书信往来,现存《晦斋集》中有李彦迪答忘机堂书信四封。但曹汉辅致李彦迪的书信皆已失传,只能通过现存的李彦迪答曹汉辅书信一窥其思想梗概。
这里我们首先对《说后》的主要内容做些简要分析,以便对李彦迪、孙叔暾和曹汉辅的观点有个总体的了解。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说后》的内容按文意分为若干个段落,抄录如下:
第一段落:“谨按:忘斋无极太极辨,其说盖出于陆象山,而昔子朱子辨之详矣。愚不敢容赘。若忘机堂之答书,则犹本于濂溪之旨,而其论甚高,其见又甚远矣。其语《中庸》之理,亦颇深奥开广。得其领要,可谓甚似而几矣。然其间不能无过于高远而有悖于吾儒之说者。愚请言之:夫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柢也。是乃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来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哉!此理虽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实体之所以寓,则又至近而至实。若欲讲明此理而徒骛于窅冥虚远之地,不复求之至近至实之处,则未有不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矣。”②
本段引文的观点可视为李氏在“无极太极”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文中李彦迪首先对忘斋和忘机堂观点的理论来源作了说明,指出忘斋的主张出自陆子学说,而忘机堂的观点则本于濂溪之旨。他进而声言,陆子的无极太极之说因朱子已详辩无须赘言,而妄机堂的学说则因过于高远而似有背于吾儒之旨处。由此可见,宋代朱陆之辨是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之辨的理论先河。李彦迪在本段还阐述了自己对无极太极问题的基本理解,主张并非太极之上复有无极,此至高至妙之理只能在至近而至实处求之,不然就会有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的危险。由此可见,他对道体之根源、行为之应然等问题越有借由自己的理解。不过,从李氏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来看,其见似与朱子并无二致。此其所以李滉评论其学说时直言“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
第二段落:“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也则是矣。其曰岂有论有论无、分内分外,滞于名数之末则过矣。其曰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则是矣。其曰大本达道浑然为一则何处更论无极太极,有中无中之有间则过矣。此极之理虽曰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发差者。是岂漫无名数之可言乎?而其体之具于吾心者则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然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容不辨者。安有得其浑然则更无伦序之可论,而必至于灭无之地而后为此道之极致哉。今徒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极言之,而不知夫粲然者之未始相离也。是以其说喜合恶离、去实入虚,卒为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而后已。岂非穷高极远而无所止者欤?”①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援引朱子之说对忘机堂的不当言论进行了逐一反驳,指出其“太极即无极”、“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等见解可以成立,但不分有无、分内分外以及有中无中而论无极太极却明显不妥。李氏以为太极之理虽然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无有毫发之差。①而且,其“体”之具于吾心者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同。故不能只重其浑然而轻其伦序,“喜合恶离,去实入虚”。
第三段落:“先儒言周子吃紧为人特著道体之极致,而其所说用工夫处只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尝使人日用之间必求见此无极之真而固守之也。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若论工夫则只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今忘机之说则都遗却此等工夫,遽欲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万物朝宗于我而运用无滞,是乃欲登天而不虑其无阶,欲涉海而不量其无桥。其卒坠于虚远之域而无所得也必矣。大抵忘机堂平生学术之误病于空虚,而其病根之所在则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以灭字说太虚体,是断非吾儒之说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谓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谓于穆不已者存焉。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著灭字于寂字之下。试以心言之:喜怒哀乐未发、浑然在中者,此心本然之体而谓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则喜怒哀乐发皆中节,而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谓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灭则是枯木死灰而已,其得不至于灭天性乎?然忘机于本来寂灭之下便没灭字不说,而却云虚而灵、寂而妙。灵妙之体充满太虚、处处呈露,则可见忘机亦言其实理而说此灭字不去。故如是岂非有所穷而遁者乎?”②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直言不讳批评忘机堂,以为其平生之误在于“空虚”二字,而其病根则在“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他在指出错误根源的同时,还断言以“灭”字说太虚体“断非吾儒之说”。“寂灭”是佛教用语,《涅槃经》上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一句。而“诸行无常”则又是佛教三法印之一,因此《涅槃经》上的这一句又可视为佛家基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众所周知,大乘佛教不承认现实世界的实在性。以“四大”为假合,以寂灭为圆觉,遂将人伦道德视如赘疣。而儒家所说的“寂”则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寂”,与佛家之寂灭有着本质的区别。
李彦迪还批评忘机堂曹汉辅不仅在太极之上复设无极,而且漠视形而下之人伦日用之修养工夫。如果只关注形而上之“灵妙之体”,就无从体认至近至实处的太极之理。他认为上天无声无臭可谓“寂”,然至寂之中又有“于穆不已”,其化育流行遂生鸢飞鱼跃之景象,所以在“太极”之上绝不可添加一“灭”字。
“自汉以来圣道塞而邪说行,其祸至于划人伦、灭天理而至今未已者,无非此一灭字为之害也。而忘机堂一生学术言语及以上议论之误,皆自此灭字中来。愚也不得不辨。若其超然高会一理浑然之体而的无疑,则实非今世俗儒高释所可几及。亦可谓智而过者矣。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矣。而不幸世无孔孟周程也,悲夫!”①
在本文结尾处,李氏总结异端之弊害全在一“灭”字,而忘机堂为学论议之误亦皆源自此一“灭”字。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撰文辨析。“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
由此而论,李氏批评忘机堂曹汉辅的用意在于揭露其异端思想,像文章中隐约出现的佛家倾向。《说后》一文写于中宗十二年(1517年)正月,即李彦迪27岁之时。曹汉辅何时作复则已无从查考。从年谱上的记载看,李彦迪答忘机堂曹汉辅的第一封书信是在中宗十三年(戊寅年即1518年)写的。他时年28岁。
二、论辩的主要内容及理论特点
前已言及,“无极太极论辩”起因于李彦迪所撰的《说后》。该文写于中宗十二年,翌年曹汉辅对此提出异议。于是,便有了“答忘机堂”的四封书信。
在论辩的过程中,晦斋李彦迪和忘机堂曹汉辅围绕“无极”、“太极”概念以及儒家修养论等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发生于朝鲜朝初期的此一论辩中,李彦迪从朱子学理本论的立场出发,批驳了具有佛道思想色彩的曹汉辅的主张。此论辩在学理上可理解为“无极太极”问题的性理学式解读和非性理学式解读的立场对立。
因为《说后》主要是李彦迪对孙叔暾和曹汉辅的“无极太极”说的评论文章,故只能了解到他的思想概貌。不过,在“答忘机堂”的四封书信中却可以发现李氏较为系统的性理学观点。而且,从《说后》和《答忘机堂书》中还可以看出,曹汉辅的观点的确受到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故李彦迪在《答忘机堂书》中,指责其所持的是佛家之寂灭论而非儒家之寂感论。李氏和曹汉辅之间的论辩作为性理学本体论问题之探讨在韩国儒学史上意义重大,说明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已具备相当的理论水平。下面将对四封书信之内容做逐一分析。
在《答忘机堂第一书·戊寅》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伏蒙示无极寂灭之旨、存养上达之要,开释指教不一而足。亦见尊伯不鄙迪而收之,欲教以进之也。感戴欣悚,若无所容措。”①可知,曹汉辅在读了李氏所写的《说后》之后,就“无极寂灭”和“存养上达”等本体论、修养论问题给李氏回信,这应该是曹汉辅在致李彦迪信中谈的主要问题。
于是,李彦迪在复信中首先解释自己为何撰写《说后》,然后针对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又陈述了己见。他说:
来教所云寂灭存养之论有似未合于道者。小子亦有管见须尽露于左右者,敢避其僭越之罪而无所辨明耶。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风雷之所以变,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周子所以谓之无极者,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非若老氏之出无入有、释氏之所谓空也。①
从整个论辩过程中李氏自谦的语气和态度来看,曹汉辅应较彼时才二十七八岁的李彦迪年长许多。所以李氏在信中陈述己见时显得比较谨慎。对于曹氏的寂灭存养之论,李彦迪十分谦虚地讲到“小子亦有管见须尽露于左右”,然后谈了自己对“太极”与“无极”概念的理解。他指出“太极”作为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是实然而不可易者,周子所以又称之为“无极”乃因其具“无方所、无形状”之特性。究其实与佛道两家所言“空”、“无”等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接着他借“理”、“气”之概念阐发了己见,并对曹氏的本体论进行了批评:
今如来教所云,无则不无而灵源独立,有则不有而还归澌尽。是专以气化而语此理之有无,岂云知道哉?所谓灵源者气也,非可以语理也。至无之中至有存焉,故曰“无极而太极”。有理而后有气,故曰“太极生两仪”。然则理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而言。何必见灵源之独立然后始可以言此理之不无乎?鸢飞鱼跃昭著上下,亘古亘今充塞宇宙。无一毫之空阙,无一息之间断。岂可但见万化之澌尽而遂指此极之体为寂灭乎?②
从内容中可以推知,曹汉辅将“灵源”视为宇宙本体。而李彦迪则认为所谓“灵源”者其实是气,不能将形而下之“气”视为宇宙的终极本体。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其实是“至无之中至有存焉”之义。此处的“而”应指“所当然之中”的“所以然之理”——太极即是“理”。①李氏进而提出自己的理气观——“有理而后有气”,“理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理与气的关系问题是朱子学的基本问题,李氏对此所持的正是传统朱子学以理为本的理气二元论立场。
他还指出曹氏所云寂感、寂灭之分似同而实异的,先儒对此已有至论,后学者不可以此为浮议而独以异端之说为是:
盖太极之体虽极微妙,而其用之广亦无不在。然其寓于人而行于日用者,则又至近而至实。是以君子之体是道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有以全其本然之天而绝其外诱之私。不使须臾之顷、毫忽之微,有所间断而离去。其行之于身也,则必造端乎夫妇以至于和兄弟顺父母,而有以尽己之性。及其尽性之至也,则又有以尽人物之性。而其功化之妙极于参天地赞化育,而人极于是乎立矣。此君子之道所以至近而不远,至实而非虚,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此非愚生之言,实千古圣贤所相传授而极言至论者也。②
文中李彦迪借圣贤之言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表明己见合乎儒家正统。太极与理气的问题属于天道,李氏遂借探讨寂灭的问题将话题转入人道。他认为道不远人,若离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于空虚。李彦迪引用《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之句来说明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安得不先于下学之实务而驰神空荡之地?可以为上达乎?天理不离于人事。人事之尽而足目俱到以臻于贯通之极,则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浑全。酬酢万变、左右逢源,无非为我之实用矣。”③李氏依据朱子“统体一太极”的思想为依据,提出天理不离于人事,以此批判曹氏的“存养上达”修养方法的根本错误。李彦迪说: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又曰:“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讵不信欤?且如存养之云,只是敬以直内,存之于未发之前以全其本然之天而已。苦曰游心于无极之真。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使人不为近思之学而驰心空妙。其害可胜言哉?又况虚灵本是吾心之体也。无极之真,本是虚灵之中所具之物也。但加存之之功而不以人欲之私蔽之,以致其广大高明之体可也。张南轩曰:“太极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惟当本于敬以涵养之。”正谓此也。今曰“游心于无极”,曰“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似以无极太极为心外之物而别以心游之于其间,然后得以为之主也。此等议论似甚未安。①
李彦迪在文中先讲明虚灵、无极之真以及吾心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儒家修身的正确方法。由此可见二人为学工夫之差异。李彦迪强调洒扫应对当中的“下学而上达”,而曹氏则主张带有“顿悟”性质的“存养而上达”。后者的主张当然会受到正统儒者的批评。在结尾处李彦迪写道:
来教又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亦见尊伯立言之勇而自信之笃也。然前圣后圣其揆一也。今以已往圣贤之书考之,存养上达之论无所不备。其曰“存心养性”,其曰“戒慎恐惧”,其曰“主静曰主敬”者,无非存养之意。而曷尝闻有如是之说乎?吕氏虚心求中之说,朱子非之。况以游心无极为教乎?孔子生知之圣也,亦曰“我下学而上达”,又曰“吾尝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况下于孔子者乎?故程子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欲人收已放之心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以此观之,其言之可易与不可易直验于已往之圣人而可见矣。何必有待于后来复起之圣人乎?天下之祸,莫大于甚似而难辨。惟其甚似,故能惑人;惟其难辨,故弥乱真。伏详赐书,无非杂儒释以为一。至有何必分辨之说,此小子所甚惧而不敢不争者也。伏见尊伯年高德邵,其于道体之妙亦可谓有所见矣。但以滞于寂灭之说,于其本源之地已有所差。而至于存养上达之论,则又与圣门之教大异。学者于是非之原毫厘有差,则害流于生民,祸及于后世。况其所差不止于毫厘乎?伏惟尊伯勿以愚言为鄙,更加着眼平心玩理。黜去寂灭游心之见,粹然以往圣之轨范自律。吾道幸甚!善在刍荛,圣人择之。况听者非圣人,言者非刍荛。而遽指言者为狂见而不察乎?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古之君子改过不吝,故年弥高而德弥进也。小子所望于尊伯者止此。①
从曹汉辅“游心于无极之真”以及“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等见解中确实可以感受到其思想明显混杂于佛理。所以李彦迪在此信的末尾处称忘机堂“无非杂儒释以为一”,与圣门之教的理论旨趣相去甚远。尽管二人年龄相差较大,李彦迪仍以昂扬的卫道精神据理力争。
接到曹汉辅的回信后,李彦迪在《答忘机堂第二书》中写道:“伏睹来教于无极上去‘游心’二字,于其体至寂下去一‘灭’字。是不以愚言为鄙,有所许采。幸甚幸甚!”②这表明忘机堂接受李氏在第一封信中的批评,已去掉无极之上的“游心”二字和其体至寂下的一“灭”字。但是,彦迪仍然觉得曹汉辅尽管在字句上对之前的表述做了些调整,却并未尽弃其思想中的佛、道立场。于是,他继续提出委婉的批评:
书中所论一本之理及中庸之旨,亦颇明白少疵、妙得领要。圣人之道,固如斯而已,更无高远难穷之事。迪敢不承教。③
文中提到的“一本之理”和“中庸之旨”分别指的是第一封信中所讨论的无极太极、寂灭等本体论的问题和有关存养上达的工夫论问题。可见,在内容上此信殆可视为第一封信之继续。李彦迪提到:
至如寂灭之说,生于前书粗辨矣。未蒙察允,今又举虚灵无极之真,乃曰“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是未免于借儒言而文异端之说。小子之惑滋甚。先儒(指朱子——引者注)于此四字盖尝析之曰:“此之虚,虚而有;彼之虚,虚而无;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灭。”然则彼此之虚寂同,而其归绝异,固不容不辨。而至于无极之云,只是形容此理之妙无影响声臭云耳,非如彼之所谓无也。故朱子曰:“老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讵不信欤?①李彦迪认为曹氏的“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实际上是借吾儒之言文饰异端之说。他举朱子之言阐明儒家的虚寂观念与异端之虚寂说犹如南北水火之相反,在理论归趣上决然不同。彼此之虚寂名同而实异。
李彦迪进而指出:
来教又曰:“主敬存心而上达天理。”此语固善,然于上达天理上却欠“下学人事”四字,与圣门之教有异。天理不离于人事。下学人事,自然上达天理。若不存下学工夫,直欲上达,则是释氏觉之之说。乌可讳哉?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则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便是上达境界。从事于斯,积久贯通,可以达乎浑然之极矣。而至于穷神知化之妙,亦不过即是而驯致耳。②
李彦迪在为学次第上重视“下学人事”,体现心性工夫之切近日用人伦的一面。他引孔子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之语以证明己之看法。最后李彦迪写道:
夫穷理,非徒知之为贵。知此理又须体之于身而践其实,乃可以进德。若徒知而不能然,则乌贵其穷理?而其所知者终亦不得而有之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然则非知之难,行之难。此君子所以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必顾行、行必顾言,不敢容易大言者也。不知尊伯亦有如是体察之功乎?亦有如是践履之实乎?大抵道理,天下之公共。不可以私智臆见论之。要须平心徐玩,务求实是可也。③
依李彦迪之见,所谓“穷理”指的是由亲身体验知晓此理,必以进德为期才是理学家所谓德性之知。他委婉指出若无“体察之功”、“践履之实”,则所见往往流为异端。作为晚辈祈盼曹氏痛去寂灭之见,又能主敬存心以达于天理。诚如此,“则尊伯之于斯道,可谓醇乎醇矣。”①前已论及曹李二人年龄差距较大。但是从信的内容来看,曹汉辅并未轻视一位新锐学者对己见之质疑。于是,有了他们之间的第三封书信。
在《答忘机堂第三书》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伏睹来喻所陈,虽云不滞寂灭之说有年,而寂灭之习似依旧未除。是以其论说浮于道理幽妙之致,而未及反躬体道之要。不免为旷荡空虚之归,而非切近的当之训。此小子所以未敢承命者也。”②于是李氏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体道经验和感悟。
从此信的内容可以推知,曹汉辅复信中的主张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大本”与“达道”,即“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的存养之道问题。彦迪在信中提到:
迪闻子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古今论道体,至此而无余蕴矣。愚请因此而伸之。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散诸三极之间。凡天地之内,无适而非此道之流行,无物而非此道之所体……当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此心之真寂然不动。是则所谓无极之妙也,而天下之大本在于是也。固当常加存养之功以立大本,而为酬酢万变之主。而后可以发无不中而得时措之宜。然于此心之始动几微之际,天理人欲战于毫忽之间,而谬为千里之远。可不于是而益加敬慎乎?是故君子既常戒惧于不睹不闻之地,以存其本然之,而不使须臾之离有以全其无时不然之体……自其一心一身以至万事万物,处之无不当,而行之每不违焉。则达道之行于是乎广矣,而下学之功尽善全美矣。二者相须,体道工夫莫有切于此者。固不可阙其一矣。
来教有曰:“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则固存养之谓矣,而于静时工夫则有矣。若夫顿除下学之务,略无体验省察之为,则于动时工夫盖未之及焉。是以其于求道之功疏荡不实,而未免流为异端空虚之说。
伏睹日用酬酢之际,不能无人欲之累。而或失于喜怒之际,未能全其大虚灵之本体者有矣。岂非虽粗有敬以直内工夫,而无此义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体道不能精密而或至于此乎。昔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子继之曰:“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然则圣门工夫虽曰主于静以立其本,亦必于其动处深加省察。盖不如是则无以克己复礼,而保固其中心之所存矣。故曰“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未有不制其外而能安其中者也。愚前所云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顾行行顾言者,此之谓也。安有遗其心官、随声逐色,失其本源之弊哉?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盖地位已到圣人,则此等工夫皆为筌蹄矣。若未到从容中道之地而都遗却择善省察工夫,但执虚灵之识。①
李彦迪在信中对儒家的“大本”与“达道”作了简单明了的论述,这表明他对之已有了深切之体悟。李彦迪在工夫论问题上的立场是,“常加存养之功以立大本,而为酬酢万变之主”。他主张“存养”不能像曹汉辅那样只强调“敬以直内”,而忽视“义以方外”。在李彦迪看来,不假修为即可克己复礼、酬酢万变如同不出门而欲适千里,不举足而欲登泰山,结果肯定是“必不能矣”。
二是曹汉辅认为为破世人执幻为真,故言“寂灭”。对此有悖儒家宗旨的“异端”之见,李彦迪批评道:
来教又曰:“为破世人执幻形为坚实,故曰寂灭。”此语又甚害理。盖人之有此形体,莫非天之所赋而至理寓焉。是以圣门之教,每于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尽夫天之所以赋我之则,而保守其虚灵明德之本体。岂流于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岂可以此为幻妄?必使人断除外相,独守虚灵之体,而乃可以为道乎?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此寂灭之教所以陷于空虚诞谩之境,而无所逃其违天灭理之罪者。①众所周知佛教主张“四大皆空”,其耽空沦寂之弊对儒家之教危害甚深。李彦迪依性理学“道器不离”、“体用一源”之旨对之予以批驳。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肯定了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这一点在讨论“下学上达”时讲得更透彻。
三是在“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上,曹汉辅认为“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对此李彦迪不以为然。他说:
今曰“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愚请以孔子申之。自生民以来,生知之圣未有盛于孔子者,亦未尝不事于下学……然则孔子不得为豪杰之士,而其所为亦不足法欤?若曰孔子之言所以勉学者也,于其己则不必,然则愚请以孔子所亲为者白之。孔子问礼于老聃,问官于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是非下学之事乎?问官之时,实昭公十七年而孔子年二十七矣。入太庙则孔子始仕时也。古人三十而后仕,则是时孔子年亦不下三十。其非童蒙明矣。夫以生知之圣,年又非童蒙,而犹不能无下学之事。况不及孔子?而遽尔顿除下学不用力,而可以上达天理乎?是分明释氏顿悟之教,乌可尚哉?孟子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若使尊伯于此异说之诞终身迷没,不知其非则已矣。今曰不滞者有年,则是已觉其非而欲改之也。退之云“说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请自今痛去寂灭之见,反于吾道之正。②
曹汉辅与李彦迪二人在为学之方上的分歧与宋代朱陆之间“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颇有相似之处。陆氏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将朱子的“博学于文”视为“支离事业”。朱子则批评象山为学浮躁,只好发高论而不“道中庸”,造说遂与佛老相似。③在为学之方上李彦迪以圣贤为例批驳了曹氏的观点,强调不论童蒙初学还是豪杰之士皆不能无下学之事。
《答忘机堂第四书》是两人之间最后一次通信,在复信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今承赐教,辞旨谆谆,反复不置,且去‘寂灭’二字而存‘下学人事’之功。迪之蒙许深矣,受赐至矣,更复何言!”①从中可推知,经过几次书信往来曹汉辅对李彦迪的批评有所接受,对自己的立场也做了调整。而且李彦迪也认可曹汉辅态度之转变。他在信中指出:“然而窃详辱教之旨,虽若尽去异说之谬、入于圣门之学,然其辞意之间未免有些病。而至于物我无间之论,则依旧坠于虚空之教。小子惑焉。”②但在李彦迪看来,忘机堂仍未彻底摒弃其原有思想。第四封信的讨论焦点是有关“主敬存心”的工夫论问题。李彦迪写道:
圣门之教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齐其外以养其内。内则无贰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俨然肃然,深省密察,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动直、中一外融,则可以驯致乎不勉不思从容中道之极矣。两件工夫不可偏废明矣。安有姑舍其体而先学其用之云哉?③
李彦迪将理学工夫论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简言之,即践行居敬穷理。这是基于伊洛渊源的正统解释。李彦迪在信中十分强调“敬”之工夫,这一思想对后来李滉的主敬工夫论颇有影响。李彦迪援引程伊川从《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中提炼出来的道德戒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本体工夫固不可不先,而省察工夫又尤为体道之切要”。他认为颜子亦循此四箴之路径优入圣域,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李彦迪主张为人要谨守“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由此他对曹氏在第三封复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一一做了答复。
一是“主敬存心”的问题。李彦迪以“衣”、“网”为例答复说:“伏睹来教有曰‘主敬存心’,则于直内工夫有矣,而未见义以方外省察工夫。岂非但得衣之领而断其百裔,但得网之纲而绝其万目者哉?人之形体固当先有骨髓,而后肌肤赖以充肥。然若但得骨髓,一切削去皮肤,则安得为人之体?而其骨髓亦必至于枯槁而无所用矣。况既去皮肤而于骨髓亦未深得者哉?愚前所谓常加存养以立大本,为酬酢万变之主者,固尊伯主敬存心、先立其体之说。初非毁而弃之。未蒙照察,遽加罪责,不胜战汗。”①前已言及李氏并不反对“主敬存心”,只是向忘机堂强调了修养工夫不能缺失“义以方外”。在他看来,两段工夫同等重要,必须同时并举。
二是“先立其体和下学人事”的问题。李彦迪对此回复道:“来教又曰:‘先立其体,然后下学人事。’此语亦似未当。下学人事时,固当常常主敬存心。安有断除人事,独守其心?必立其体。然后始可事于下学乎。所谓体既立则运用万变,纯乎一理之正而纵横自得者。固无背于圣经贤传之旨。然其所谓纯乎一理、纵横自得者,乃圣人从容中道之极致。体既立后,有多少工夫?恐未易遽至于此。伏惟更加精察。”②此问题还是前一问题的延伸。李彦迪在存养省察的问题上立场鲜明,就是坚持下学与上达同时并进。
三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问题。李彦迪谈了自己的理解,指出:“且如万物生于一理。仁者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然其一体之中,亲疏远近是非好恶之分自不可乱。故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语》又曰:‘惟仁人为能好人,能恶人。’以此言之,仁者虽一体万物,而其是非好恶之公亦行乎其中而不能无也。舜大圣人也,固非有间而滞于所执者。然而取诸人为善,舍己从人则舜亦不能无取舍之别矣。安有心无间则茫然与物为一?更无彼此取舍好恶是非之可言,然后为一视之仁哉。”③追求“天人合一”是儒家修己的最高理想。但李彦迪强调的是“一体之中,亲疏远近是非好恶之分自不可乱”。他认为儒者同时还要具备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从而做到择善而从。
在信的最后李彦迪语词恳切,寄望曹汉辅平心察理,勿以其有是非取舍为罪。此后曹氏再未复信,而两人的论辩也就此而告终。从现存四封书信的内容来看,李氏最终也没能说服忘机堂尽弃其原有立场。读此书信可以感受到一位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士大夫①的卫道意识。两人温文尔雅之论辩既流露了少壮学者李彦迪的锐气和担当,又展现了学界名宿曹汉辅的平和与谦逊。
三、论辩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无极太极”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围绕与朱子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发生的首次论辩。此次论辩不论对李彦迪太极说的形成还是朱子学在韩国的发展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论辩的过程中,李彦迪基于朱熹之理气二元论对具有佛道思想倾向的曹汉辅“无极太极”说进行了批驳。与此同时,他还以性理学为正统捎带批判佛道两家的理论。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论辩不仅令性理学之本体论得以确立,而且使儒佛与儒道之义理分际得以明晰。尽管此后还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四七理气”之辨、“人心道心”之辨和“人物性同异”之辨等等,但是此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视。
“四七理气”之辨则与“人心道心”之辨密切相关。后者也是朱子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韩国儒学史上令“四七理气”之辨得以进一步深化。本书将在论述四端七情论辩时设专节详述“人心道心”之辨。
与前一节介绍的徐敬德相比较,李彦迪虽亦重视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思想之旨趣却与徐氏大相径庭。徐敬德基于气本论之立场,主张“太虚即气”;而李彦迪则依据理本论之立场,将“太极”视为天理。“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①李彦迪从主理论出发,阐述了其“太极说”。他认为这种“理”是“无形无质”之存有,“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但理先气后,“有理而后有气”。②李彦迪进一步指出:“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有日月之形则有所以为日月之理,有山川之形则有所以为山川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③他以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天地万物之理(太极),而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后依然作为事物之所以然与大千世界密切结合。李彦迪又说:“天下之理体用相须、动静交养,岂可专于内而不于外体察哉?”④由此可见李彦迪哲学思想的主理论特色。
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著有《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中庸九经衍义》——后者虽未完稿,但是较为详细地反映了他的道德经世观。《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则是申述朱子之学的著作。在《大学章句补遗》一书中李氏曾言及朱子所作《格物补传》之不当处。例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原文“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下朱熹写道:“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接着又写道:“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⑤于是依程子之意作了格致章的补传。对此李氏指出:“朱子得其结语一句,知其为释格物致知之义,而未得其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所以发明始学穷理之要,亦甚明备。然愚尝读至于此,每叹本文之未得见。近岁闻中朝有大儒得其阙文于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见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见。取经文中二节,以为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复参玩,辞足义明,无欠于经文而有补于传义,又与上下文义脉络贯通。虽晦庵复起,亦或有取于斯矣。”①可见,他对朱子之《格物补传》有失当处极为自信。李彦迪以为《大学章句补遗》开头经文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②二节原为格致章的原文,如今被错误纳入经文之中。为此他主张应将此两节,重新归入格致章之原文之中。而“此谓知之至也”一句是结上文两节之意的。《大学章句补遗》写于1549年,李氏时年59岁,早已是成名的儒学大家。此文对研究李彦迪理学思想大有助益。相较于朱子,李氏更强调格物致知之“止于至善”。依李彦迪之见,致知宜有缓急先后,由近及于远,由人伦及于庶物,必有以见其至善之所在而知所止,然后其所知所得皆切于身心。
从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程朱之学,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蕴育,至李彦迪才有较具体系的性理学说。李氏的理气论和无极太极论在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他的思想在韩国儒学本土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李彦迪的性理学说成为日后李滉和李珥等人集朝鲜朝朱子学之大成的理论基础。李氏第一次将有关心性修养和经世致用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整理,为韩国儒学界确立了理本论哲学体系,而与曹汉辅之论辩集中反映了他的心性论思想。正是李彦迪将修身之存养工夫引向了心性论的进路。
李彦迪理本论思想对李滉的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滉十分推崇李彦迪,不仅称赞他的“立言垂后”之功,还曾为其作行状极言学力之深湛。李滉评论道:“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③还说:“近代晦斋之学甚正,观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义正,浑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④他认为李彦迪的学问“所得之深殆近世为最也”①。李珥尽管对李彦迪在“乙巳士祸”中的作为颇有微词,但对其学问还是相当首肯,尝言:“李彦迪博学能文,事亲至孝,好玩性理之书,手不释卷。持身庄重,口无择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学者亦以道学推之。”②
光海君二年(1610年),李彦迪还与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混作为“士林五贤”配享文庙。他的哲学著作有《求仁录》、《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中庸九经衍义》、《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答忘机堂书》以及《奉先杂仪》等。
概而言之,发生于16世纪初期的这场论辩反映了朝鲜朝初期的韩国儒者对理学本体论的不同理解。尽管这一论辩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力不及16世纪发生的“四端七情”之辨和“人心道心”之辨,但在理学本土化的初期即由深度的哲学思考树立了正统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后来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两位老少学者间展开的“无极太极”之辨在成就韩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的同时,还正式拉开了16世纪韩国儒学一系列精彩的学术论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