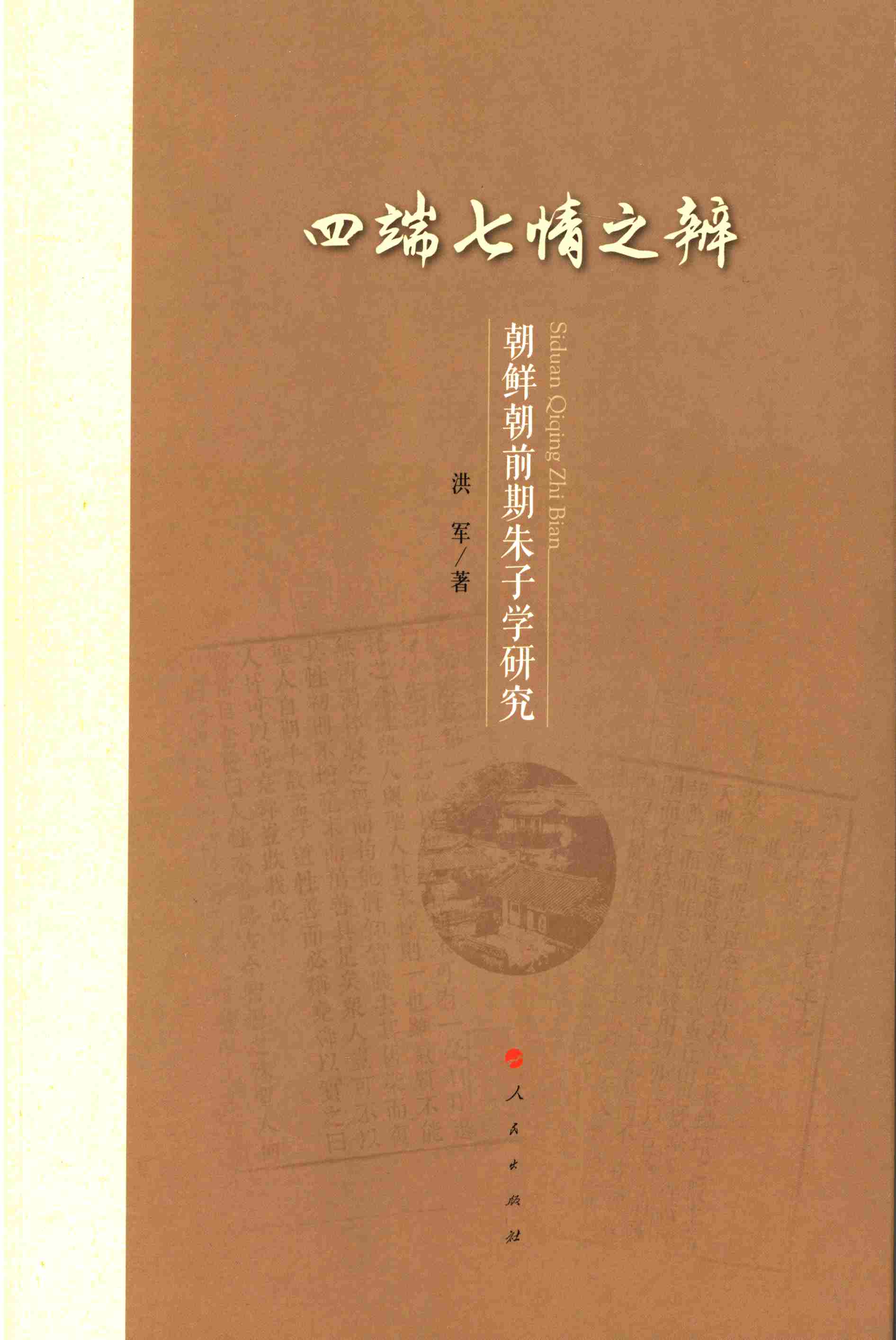内容
通过上一章的论述可以看出,新罗和高丽两朝的统治阶级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动用大批人力和物力支持弘法。高丽太祖王建(877—943年)在《十训要》第一条中便讲道:“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佛教的广泛传播不仅促进了韩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的进步。但是随着高丽王朝(918—1392年)的衰弱和作为国教之佛教的日益腐化堕落,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也随之逐渐丧失,“崇佛与排佛”成了高丽社会后期的矛盾焦点。在此种历史背景下,高丽朝的一些文人学者从13世纪末开始从元朝引进朱子学以对抗佛教。所以早期的韩国性理学也被称为高丽朱子学。朝鲜朝开国后,朱子学旋即被确定为官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第一节 金时习的太极论
金时习(1435—1493年)是朝鲜朝性理学家、文学家,在“生六臣”①中最为著名。他字悦卿,号梅月堂、东峰,生于江陵。金氏自幼聪慧,5岁便能读书缀文,13岁师事经学大家金泮、尹祥习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21岁皈依佛门出家,后还俗娶妻。其妻死后,复又还山,于成宗二十四年卒于鸿山无量寺。
一、太极说
太极说是金时习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太极”乃朱子学的核心概念,直接关系到对朱子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朱子曾说过:“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①太极只是理,未有天地,先有此理——“理”的在先并非时空意义上的先后,而是逻辑意义上的在先。
在韩国哲学史上,金时习是最早对“太极”问题进行论述的学者。他在《太极说》中写道:
太极者,无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谓之太极,别有极则非极也。极者,至极之要,理之至极,而不可加也。太者,包容之义,道之至大,而不可侔也。②
金氏以为并非“太极”之外另有“无极”。“太极”即是“理之至极”,乃事物存在的根据和最高原理。他进一步解释道:“阴阳外别有太极,则不能阴阳;太极里别有阴阳,则不可曰太极。阴而阳,阳而阴,动而静,静而动,其理之无极者,太极也。其气则动静辟阖而阴阳,其性则元亨而利贞也,其情则阴惨而阳舒也,其用则天地以之圆方。元气以之发育,万物以之遂性。其性之正者,太极之为阴阳也。”③可见,梅月堂将“太极”视为主宰“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之“理”。他在著作中对“理之主宰性”详细加以说明:
天地之间,生生不穷者道也,聚散往来者,理之气也。有聚故有散之名,有来故有往之名,有生故有死之名。名者,气之实事也。气之聚者,生而为人。人者,理之具而著者也。故有心焉。④
若夫寒暑往来,日月代明,昼夜之道,则此理之自然,气之所以为气,而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①
金时习将气之聚散、往来,即“生生不穷者道”视为理之主宰性所致。可见,他以“太极”为主宰气之运动的“所以然”之理。也有些学者主张,梅月堂是“唯气论者”或“气一元论者”。②有时他的言论确有类似倾向,比如说过“天地之间,惟一气橐籥耳”③等。
然此等言论是基于金时习“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④的思想。换言之,是基于金时习以气之聚散、往来来说明万物之生成的思想。这是仅将“理”视为气之运动法则的结果。不过,金时习同时也肯定理对气之主宰性,而且还强调理、气之区别。他曾讲过:“才有理,便有气。”⑤故其所言“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应理解为对“理气不离”的强调。梅月堂的理气二元论思想意在阐明理气之“造化”及其“相即不离”。
同时他还将“理”表述为“公共之理”。“天之生民,各与以性。性即理也,不谓之理,而谓之性者,理是泛言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在我之理,未尝不善。如父子有亲之理,以至朋友有信之理,便是人之性。如牛耕马驰,鸡司晨,犬护主,草木昆虫,各有形质,好恶不同,便是物之理,然而其源则一也。故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⑥此“公共之理”即为“理一”,所以万物皆与我为一体;同时“理”又是“分殊之理”,故天之生民必以性理,草木昆虫亦各有其物理。可见,金时习对“理”的认识大体接续朱子学说而来。
此外,梅月堂将人的“性理”阐发为“实理”。众所周知,“性即理”是程朱理学的基本命题,但是在具体的解释上每位理学家的视角各有不同。对于性理,梅月堂是这样认识的:
性与理,都无两般。先儒云,性即理也。天所命,人所受,而实理之具于吾心者也,盖初非有物。但是仁义礼智之在我,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尧舜,涂人,初无少异。惟气质有清浊粹驳之不齐,不能皆全,故汨于人欲而失之,谓之众人。无私欲之蔽而能尽其性,谓之圣人,其实未尝有殊也。子思之言天命,孟子之言性善者是也。彼告子之言生,荀子之言恶,杨子之言混,韩子之论三,释氏之作用,皆以气而遗其理也。①
道德与性理异乎?曰,无以异也。夫道者,性理之极处,初非有他歧可说。②
将“性理”理解为“实理”,即“天所命,人所受,而实理之具于吾心者”,此为朝鲜朝后期实学派的实心实理说的肇端。梅月堂之说既有助于防范性理的抽象化和空洞化,又有益于增强性理学家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在他看来,循此仁之性(实理)则可以自父子之亲以达至仁民爱物。
二、道佛观
梅月堂对佛、道也多持批判的态度。他曾以孟子“存心养性”之思想为依据批驳佛教“观心见性”说。“如浮屠氏观心则不可,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岂可以吾心观吾心。若云可观,心应有二。”③在此,他还阐述了自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理解,曰:“或问先圣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岂非二乎。曰,所谓人心者,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道心,源于性命之正,天理之公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遂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人欲卒无以胜夫天理之公矣。岂有但观而已乎。”④“道心为主,人心听命”,这是朱子人道说的主要观点。但是,将“人心”简单理解为“人欲之私”却有待斟酌。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韩国性理学尚处于理论建构阶段,仍需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金时习对道家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彼老氏者,体道而非率性之道。论德而非明命之德,则如之何其泽于世,垂于后也。”①老氏之学虽然也可称为已悟“道”本,但是其“道”并不是儒家所言“率性之道”,而其“德”亦非儒家所谓“明命之德”。因此,老氏之说就难以“泽于世,垂于后”。
在论述儒道两家之异时,梅月堂还提出“志为帅之气”的思想。他曾说过:“在圣人之道则不然。论养气,不论服气,盖在心为志,志发为气。志,气之帅也。”②这与郑道传、权近等人主张的“志帅气卒”的思想一脉相承。
由上所述,金时习是对儒释道的义理都有较深切体会的朝鲜朝初期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因而后人对其思想的学派属性也多有争论。退溪李滉即称其为“一种异人”。他评论道:“[篈]世人以金梅月之披缁,为不足观。在篈之意,以为梅月遯世一节,固未合于中庸之道。然而身中清,废中权,如此看则何如。[滉]梅月别是一种异人,近于索隐行怪之徒。而所值之世适然,遂成其高节耳。观其与柳襄阳(柳襄阳:本名,柳子汉,因曾任襄阳府使,故被称为“柳襄阳”——引者注)书,金鳌新话之类,恐不可太以高见远识许之也。”③而栗谷李珥则称梅月堂为“横谈竖论,多不失儒家宗旨。至如禅道二家,亦见大意”④。朝鲜朝中期著名性理学家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尤斋,谥号文正,1607—1689年)则在《梅月堂画像跋》中对其评论道:“其髭须虽在,而冠服则正缁流所著也。余尝按栗谷先生奉教所撰公传,公少为儒生,中为缁流,晚尝长发归正,临终时更为头陀像,盖三变其形矣,独乃留此缁像而自赞焉者,岂亦有意存乎其间耶。盖公出家放迹,实欲藏晦其身。然百世之下,见其气象精神于片幅之上者,犹知其为梅月公矣。”①但是,通过其性理说的分析可以看出,李珥在《金时习传》中“心儒迹佛”的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李珥写道:“自以声名早盛,而一朝逃世,心儒迹佛。取怪于时,乃故作狂易之态,以掩其实。士子有欲受学者,则逆击以木石,或弯弓将射,以试其诚。”②
概而言之,梅月堂的性理学思想肯定理对气的主宰性,但同时也强调二者之分别,所谓“才有理,便有气”。所以对其“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的思想应理解为对理气不离的重视。金时习的理气二元论思想强调理气之“造化”及其“相即不离”。梅月堂之学虽然在体系化方面有所不足,对朱子学的理解程度亦有欠缺,但是基本上还是笃守了朱子学的基本立场。金时习思想与李彦迪(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1491—1553年)对太极主理性的论述有所不同,却从“理气一体”、“理气造化”的角度解释“太极之理”的主宰性,由此开启了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无极太极论辩之先河。同时在他的学说中,还可以看到赵光祖道学思想的萌芽以及退溪李滉、栗谷李珥等人的性理学的端绪。
梅月堂金时习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说》、《生死说》、《神鬼说》、《易说》等,现均收录在《梅月堂集》(24卷)中。
第二节 赵光祖的道学论
朝鲜建国初期朝政由“事功派”(郑道传、权近等人)主导,他们以性理学(朱子学)为建国理念,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王朝建立后的短暂的繁荣期。但是随着李氏王朝的建立,退隐山林、远离政治争斗的“义理派”士人却并未完全退出社会政治的舞台。从世宗朝开始,他们逐渐重返朝政,对勋旧势力的腐败弊政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这一派继承圃隐郑梦周义理思想之衣钵,大体包括吉再、金叔滋、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人。与之同气相求的还有反对世祖篡位的“生六臣”、“死六臣”等节义派,他们都是继承圃隐郑梦周学脉的士林派学者。
中宗、明宗朝年间频发的“士祸”①,使大多数儒者逐渐远离现实政治,转而沉潜于对儒学义理问题之探究。于是,韩国士大夫们形成一股研究性理学义理的风潮。同时,这一时期性理学的“道学化”也得到加速发展。其实,15世纪中叶之前性理学的“道学化”现象已开始出现,掀起“道学化”思潮的正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林派学者。他们在至治主义思想的旗帜下试图彻底实现“大义(春秋大义)”,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道学思想正是支撑这些“士林派学者良心”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②本节将论述作为士林派学者翘楚的赵光祖的道学思想。
一、至治主义
赵光祖(1482—1519年),字孝直,号静庵,谥号文正,是朝鲜朝前期著名性理学家。他是士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金宏弼的高足。作为汉阳人,光祖出生于官僚两班世家。中宗五年(1510年)参加“春中进士会试”,中生员,入太学。中宗十年(1515年)又应谒圣别试以乙科状元及第,之后历任典籍监察、副提学、元子辅养官、大司宪等官职,从而确立了其朝鲜朝前期士林领袖之地位。后因遭勋旧势力的诬陷,在“己卯士祸”①中被中宗赐死。
赵光祖以“崇道学、正人心、法圣贤、兴至治”②为目标,热衷于“国是”之确立。他主张革弊扶新的社会改革,积极倡导至治主义,聚集了一批年轻士大夫反对勋旧派的专横。赵氏以为士大夫为学第一要务便是为生民而行道。他曾说过:“士生于世,业为学问者,冀得展其怀抱,有补于生民耳。孟子以亚圣,历聘齐、梁,岂有他意乎。但欲行其道而已。后世士子之事,自私而已。臣等面对六七度,徒以口舌,欲感君上,此特末耳。但君为君道,臣为臣道,则朝廷清而治道成矣。”③依其之见,君主若能“以道惟一”则德无不明,“治惟纯”则国无不理。但是,君主若不能“以道惟一”则德灭而国亡。他说:
伏以道惟一,而德无不明;治惟纯,而国无不理。不一乎道,不纯乎治,则二而暗,杂而乱。一纯二杂,罔不原乎是心,故正厥原,通微溥显,克一其居,而政化惟纯,德着而国昌。迷厥原,炽柱沈阘,二三其守,而政化乃杂,德灭而国亡。④
可见,“以道惟一”的“弘道”思想是赵氏道学的核心理念。他主张为了“弘道”,志士仁人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实现社会正义。那么其心目中的“道”又是何物呢?“夫道也者,本乎天,而依之于人,行之于事为之间,以为治国之方也。”①又曰:“夫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夫子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万物之多,莫不从此道而遂,天地之心,阴阳之感,亦莫不由此心而和。阴阳和,万物遂而后,无一物不成就于其间,而井井焉有别。”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③是孔子的主张,其要义是说人应有弘道的主观能动性。④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而仁又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所以说以人之理合于人之身才是道。赵光祖说:
天与人本乎一,而天未尝无其理于人。君与民本乎一,而君未尝无其道于民。故古之圣人以天地之大,兆民之众为一己,而观其理而处其道。观之以理,故负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处之以道,故凝精粗之体,领彝伦之节。是以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无所得逃于吾之心。而天下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万化之所以立,治道之所以成也。虽然道非心,无所依而立,心非诚,亦无所赖而行,为人主者,苟以观天理而处其道,由其诚而行其事,于为国乎何难。恭惟主上殿下,以干健坤顺之德,孜孜不息,出治之心既诚,为治之道已立。犹虑夫纪纲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其于尊礼先圣之余,进策臣等于泮宫,先之以先圣之事,遂及欲复隆古之治。⑤
对“天人一体”之道心的重视是赵光祖道学思想的根本精神。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是欲在李朝实现唐虞三代之治。因此,赵光祖要求学者为学当以圣贤自期,人主为政当以实现三代之治为期:“学者以圣贤为期,未必即至圣贤之域,人主以唐虞三代为期,未必即致唐虞三代之治。然立志如此,而用功于格致诚正,则渐至于圣贤之域,尧舜之治矣。若徒骛高远,而不下实功,则日趋浮虚之地而已……人君亦必以最贤者为师,次者为友,尊礼之,可也。”①在他看来,孔子之道只是与心相通之天理。学者只要“敬守此心”,对越上帝,就可以不背夫子之道。所谓“敬守此心”便是以诚心守道。
于是,赵光祖将心的“诚未诚”,视为天人离合、社会治乱之根据。他说:
然而所谓心、所谓道者,未尝不一于其间。而千万人事之虽殊,而其道心之所以为一者,天本一理而已。故以共天下之道,导与我为一之人,以共天下之心,感与我为一之心。感之而化其心,则天下之心化于吾心之正,莫敢不一于正。导之而导于吾道,则天下之人,善于吾道之大,莫敢不归于善。顾吾之道与心,诚未诚如何,而治乱分矣。②
他的至治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要求道德主体的自我省察和积极践履。而人主是否诚心守道最为关键。“所以治国者,道而已。所谓道者,率性之谓也。盖性无不有,故道无不在。大而礼乐刑政,小而制度文为,不假人力之为,而莫不各有当然之理,是乃古今帝王所共由为治;而充塞天地,贯彻古今,而实未尝外乎吾心之内;循之则国治,失之则国乱,不可须臾之可离也。是以使其此道之体,了然于心目之间,不敢有须臾之不明也。”③赵氏是朝鲜朝道学精神的确立者④。在他看来,治国即循道,若治国者离经叛道则国必乱。这就要求人君正心诚意、持敬慎独,先养己德,而后推之于行事。又说:
古云:至诚感神。又曰:不诚无物。君之遇臣,臣之事君,皆以诚实,则治化可期其成也。我国地方褊小,人君发一言,则八道之人,一朝皆得闻知。惟当于大臣则敬之,于群臣则体之,百工则来之,庶民则子之。患吾之所以遇臣爱民者有未诚耳,不患其难化也。后世治道渐下,不能复古者,盖以后世之君,无有真如古昔帝王故也。今之言者曰,欲复古之治道,徒为变乱旧章而已。此由知识庸下,直以所见为言也。近来士气稍稍振起,民之趋向,亦渐好矣。惟愿自上日加慎独诚实工夫,终始不渝,则治化可臻矣。若使世道,日渐污下,终不可变,则人道终归于禽兽矣。三代之治,今可复致者,虽不可易言,岂全无致之之道乎。自上先养己德,推之行事,则人皆诚服,不期化而自化矣。若吾德不修,而修饰于事为之间,则亦何益乎。须敦厚其德,使万化自明德中流出,则下民自然观瞻欣感,有不能已者矣。又非但拱手以守其德而已,必以礼乐刑政,提撕警觉,布置施设,如有可为之事,当振奋而力行也。①
赵光祖以为人主苟能遵道循理、以诚行事,则士气可振,治化可期,于为国亦无难事。作为当朝士林领袖,他将中宗朝(1506—1544年)视为实现理想政治的难得时机。在任副提学时,他曾向中宗进言道:“人主学问,非止澄明一心而已,当见诸施为之际。今者,圣学已至高明。若失此机,后不可图。”②赵光祖认为世宗朝(1419—1450年)是李氏王朝建立之后最为理想的时期,但“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使成宗朝(1470—1494年)刚刚培育起来的士气扫地以尽。他欲趁中宗即位之机重振士气,为朝鲜“立万世不拔之基”。赵氏言曰:“我国世宗朝,礼乐文物,制度施为,髣髴乎周时。而至于废朝初年,成宗梓宫,在殡未久,而宫中所为,已可寒心,惟其一身,不能善饬,故士大夫皆失恒心,终至迷乱而莫救。赖祖宗德泽深厚,浃于民心,故圣上即位之后,人心庶几向善,而然其旧染污俗,难可猝新也。当此机会,不正士习,不厚民生,不立万世不拔之基,则圣子神孙,将何所取法乎。自古欲治而不能善治者,必有小人喜为谗间生事故也。臣谓圣学,日进于高明,而又推诚以待大臣,则大臣不敢以杂语。陈于上前,而必尽心于国事矣。国事不出于大臣,则上下违咈不顺,而无以致治矣。”①朝鲜从15世纪末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勋旧派和士林派两大政治势力。二者围绕着土地和政权展开激烈的争斗,给朝鲜社会造成重大损失。士林派基于维护中小地主之利益的立场出发,极力谴责勋旧大臣土地兼并,他们传播程朱之学,宣扬事君以忠的节义精神。勋旧派则视士林派为“野生贵族”,每每伺机对其进行报复打压。从世祖(1455—1468年)时起,至16世纪60年代,大小“士祸”接连不断,其间多有流血事件。均以士林派的被害而告终,史称“士祸”。在“甲子士祸”中,赵光祖的恩师寒暄堂金宏弼(1454—1504年)亦遭到迫害。1545年(乙巳年)士林派又受尹元衡一派的打击,这就是“乙巳士祸”。1565年尹元衡一派被驱逐,士林派随之重回政治舞台,势力开始空前膨胀。中央政权遂为清一色的士林派所掌控。
二、性理说
15世纪的韩国因经历丽朝两朝更替和社会动荡,士林的士气有所受挫。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逐渐稳定,以冶隐吉再学统所代表的“义理”精神开始风靡半岛,继承其学统的士大夫试图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此一动向反映在15世纪末叶出现的“小学修身派”身上。此派以金宗直、金宏弼、金安国(号慕斋,1478—1543年)为代表,欲由高扬冶隐吉再以培育士林的“义理”精神。至16世纪初已成功在经延讲授“小学”。这表明他们的关注点已从个人修身之范围扩大至社会政治领域,在此过程中“心”的意义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以赵光祖为代表的至治主义则更是从“心”上寻找修身之依据。
赵光祖生活于朝鲜朝“士祸”期,所以强调为学应兼顾“学问”与“治道”,二者不可偏废。“虽曰存心于学问治道,而一有所嗜好,则所向不能专一矣。大抵心无二用,向善则背恶矣,夫文与书,可谓一事,而习文者,不暇于习书,理固然也,若意诚心正之功,到十分尽处,则可保无虞矣,不然则嗜好之害,不可不虑也。”②由此可见,他的道学思想所追求的是道德与政治、致知与践行的高度协调与统一,而重点则在于“实功”。
赵光祖的性理学说具有贵理贱气之“主理”论倾向。“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而“仁”则为理在人性上的显现。他曾说过:“理不为气所动……因论理气之分曰:理为主而气为理之所使,则可矣。”①又说:“春者,天之元也。四时自春而始,四端自仁而发。无春序不成,无仁不遂。”②光祖将“仁”比之于“春”,以为四季的流行自“春”而始,而人伦亦以“仁”为始端,这样便赋予“仁”以流行发育的功能,从而与天道合一。“虽天人之似殊兮,理在仁而靡爽,然则春于天,仁之于人,同一春也。”③他构筑了一个天人相贯、天人同理的“理一元”论性理哲学体系。在人性论上,主张人性是天理的体现,“性”与“理”同而不悖。静庵以为:“性无不善而气禀不齐,人之气不善,气之使然也。”④他又说过:“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义礼智之德。天理岂有恶哉,但为气禀所拘,故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厉猛,义之差也;谄谀过恭,礼之差也;奸谲诡诈,智之差也。理惟微而气易乘,故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⑤赵光祖对“心”非常重视,以为“心是活物,若有感而动”⑥,他的性理学说特别强调对“心”施以检束的修养工夫的必要性。“整齐严肃,则自然主一无适,而应物精当,言动中礼矣。常人之不能若此者,不能齐肃故也,此是圣学之始终,而形容之极难,必于心地惺惺,无昏杂懈弛之时,可见矣。故先儒以主一无适为言,夫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者,乃不昏惰之工夫也。”⑦他在继承朱子学的“诚”、“敬”工夫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持敬”、“去欲”修养方法。尽管士林学派学者很少论及认识论问题,赵光祖还是在强调“学以致用”的同时言及这些问题。他说:“大抵耳、目、鼻、声、色、臭味之欲,无非以气而出也。”①
作为道学政治的积极倡导者,静庵认为实践圣贤之学以复尧舜之治的关键就在于人主的正心诚意,所谓“道非心无所依而立,心非诚亦无所赖而行”。一生以行道为己任的赵光祖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阐发了“保民”、“泽民”等王道政治思想,还在执政期间提出诸多改革世弊的合理性方案。
简言之,赵光祖道学精神之主旨是由仁政实现儒家至治主义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严辨王霸义利,反对霸权政治,试图以存天理遏人欲来重塑社会纲常,从而构建一个充满正义的李朝社会。这正是儒家王道政治之理想。
静庵在其《戒心箴序》中写道:
人之于天地,禀刚柔以形,受健顺以性,气则四时,而心乃四德也,故气之大浩然无所不包,心之灵妙然无所不通。况人君一心,体天之大,天地之气,万物之理,皆包在吾心运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顺吾度,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谓灵妙者沈焉,梏于情私,不能流通。天理晦冥,气亦否屯,彝伦〓,而万物不遂。况人君声色臭味之诱,日凑于前,而势之高亢,又易骄欤。②
从以上引文可以一窥其诚实的人格和笃实的为学。这里需注意的是他对理气心性问题的阐释。静庵认为气之大浩然无所不包,心之灵妙然无所不通,天地之气、万物之理皆包在吾心运用之中。将理气摄于“心”来讨论不仅是静庵道学思想的特色,而且还是韩国重视人间性理之学术传统的发端。正是赵光祖理气论研究的路向转换成为日后李滉、李珥等人“四七理气”之辨的嚆矢。可见,肇始于圃隐郑梦周的义理派学术,传至静庵赵光祖已达新的理论高度。
后世学者对赵光祖多有称道,宋时烈即将其拟于宋代濂溪。时烈尝言:“余以为先生之生于我东者,实如濂溪之于宋朝也。岂必授受次第如贯珠,然后乃为道学之传哉。”①同为士林派学者的白仁杰(字士伟,号休菴,1497—1579年)则称美他说:“其丕阐绝学之功,优于郑梦周、金宏弼远矣。”②奇大升也赞道:“以东方学问相传之次而言之,则以梦周为东方理学之祖……金宗直学于叔滋,金宏弼学于宗直,而赵光祖学于宏弼,继其渊源之正,得其明诚之实,蔚然尤盛矣。”③号称朝鲜朝朱子学双璧之一的李滉同样对他推崇备至:“盖我东国先正之于道学,虽有不待文王而兴者,然其归终在于节义章句文词之间,求其专事为己,真实践履为学者惟寒暄为然。先生(指赵光祖——引者注)乃能当乱世冒险难而师事之,虽其当日讲论授受之旨,有不可得而闻者,观先生后来向道之诚,志业之卓如彼,其发端寔在于此矣。”④由此可见,至赵光祖朝鲜朝道学的义理思想已初具规模。
不过,最为推崇静庵赵光祖的还是李珥。李珥对静庵在李朝儒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作用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问:我朝学问,亦始于何代?曰:自前朝末始矣。权近入学图似龃龉,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视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至退陶先生,儒者模样已成矣。”⑤可见,尽管李珥承认朝鲜朝的理学传统由郑梦周始发其端,但是认为圃隐只是安社稷之臣,且其学又“规矩不精”,尚难称为儒者。只有赵光祖才是朝鲜朝性理学传统的真正始祖。李珥说过:“我国理学无传,前朝郑梦周始发其端,而规矩不精,我朝金宏弼接其绪,而犹未大著,及光祖倡道,学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学者,光祖之力也。”⑥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初,学者大多专注于功名和词章训诂,并未对道学的义理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直至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士林派学者出现后,道学研究才被引向义理探究之路。尤其是赵光祖以一己之力将道学研究推向了经世济国之实践性理学的轨道。①他的至治主义思想,后为李珥等人继承和发扬,不仅影响了朝鲜朝后期性理学的发展,而且还在韩国思想史上掀起了绵延几百年的实学思潮之狂飙。赵光祖的主要著作有《静庵集》(5卷)。
第三节 徐敬德的气本论
朝鲜朝开国百余年之后,朱子学发展终于迎来了鼎盛时期。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接连涌现出多位颇有理论建树的硕学鸿儒,如徐敬德、李彦迪、曹植(字楗仲,号南冥,1501—1572年)、李滉、奇大升、李珥、成浑等人。这一性理学家群体在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以及近世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节拟对徐敬德的哲学思想作些简要的论述。
一、太虚说
徐敬德(1489—1546年),字可久,号花潭、复斋,谥号文康。徐氏既是朝鲜朝前期代表性的性理学家之一,又是气本论哲学的理论先驱,世称“花潭先生”。他是开城府人,平生为学最得《大学》“格物致知”之旨。据《年谱》记载,徐氏18岁时当读《大学》至致知在格物一节,便慨然叹道:“为学而不先格物,读书安用?”②徐敬德志行甚高,不喜举业,曾卜筑精舍于开城五冠山下的花潭边,潜心道义,专以穷格为事,以此终其一生。他曾在一首《述怀》诗中吟道:
读书当日志经纶,晚岁还甘颜氏贫。
富贵有争难下手,林泉无禁可安身。
采山钓水堪充腹,咏月吟风足畅神。
学到不疑知快活,免教虚作百年人。①
隐居松都(开城)的花潭潜心治学,安贫乐道,其不拘形迹、狂放自适的形象由诗作跃然纸上。这首诗可视为其守道笃学之生平的真实写照。
徐敬德虽然其为学不尊朱子而多从邵雍和张载之说②,但是其所建构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在韩国儒学史上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李珥曾评论说:“敬德则深思远旨,多有自得之妙,非文字言语之学也。”③
关于“虚空与气”,张载论述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也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之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④他以为,气之本体乃无形的太虚,正是气的聚散形成万物与太虚。太虚、气和万物可谓同一实体的不同存在状态,这是张载气本论思想的立论基础。横渠的气一元学说不仅将中国古代哲学的气论思维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还促进了东亚儒家文化圈气论思想的深入发展。
作为韩国气学派的理论先驱,徐敬德确如李珥所言极重精思自得,其学说亦确有“自得之妙”。他不仅主张世界由“气”构成,而且还提出了独特的先后天理论。
首先,徐敬德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以为一切皆为“气之聚散而已”。他曾说过:“吾亦曰:‘死生人鬼,只是气之聚散而已’。”⑤还说过:“一气之分,为阴阳。阳极其鼓而为天,阴极其聚而为地,阳鼓之极,结其精者为日,阴聚之极,结其精者为月,余精之散为星辰,其在地为水火焉。”①在花潭看来,天地万物归根结底皆是先天之太虚。正是气的鼓、聚、凝、散之运动产生了千变万化的物质现象。因此,气的运动才是这包罗万象的世界的普遍本质,所以他以气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
其次,徐敬德将“气”之性质规定为“湛然虚静”,所谓“其湛然虚静,气之原也”②。他进而指出:“有聚散而无有无,气之本体然矣。气之湛一清虚者,弥漫无外之虚。聚之大者为天地,聚之小者为万物。聚散之势,有微著久速耳。大小之聚散于太虚,以大小有殊。虽一草一木之微者,其气终亦不散。况人之精神知觉,聚之大且久者哉!形魄见其有散,似归于尽没于无。”③依徐氏之见,气之本体“有聚散而无有无”。由此可知,其所言“湛一清虚”之气乃超时空之永恒存有物。他以气本论思想为基础对气之聚散运动给出自己的解释:即气之“聚”生成大千世界,“散”则还原为气;易言之,具体的事物只是“浮现一气中”而已。所以气虽看不见、摸不着,却作为实实在在的存有充塞着整个宇宙。徐敬德以为气“弥漫无外之远,逼塞充实,无有空阙、无一毫可容间也。然挹之则虚,执之则无,然而却实,不得谓之无也”④。
再次,在“太虚”与“气”的关系上,徐敬德相信因“虚静即气之体”,故太虚既无终始亦无穷尽。他说:“无外曰太虚,无始者曰气,虚即气也。虚本无穷,气亦无穷。气之源,其初一也。既曰气一,便涵二;太虚为一,其中涵二。既二也,斯不能无阖辟、无动静、无生克也。”⑤文中从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上对“太虚”与“气”作出了解释:太虚为“无外”,气为“无始”,二者皆无穷。花潭还指出二者初皆为“一”,但以其中涵“二”遂有事物的运动变化。“太虚,虚而不虚,虚则气。虚无穷无外,气亦无穷无外。既曰虚,安得谓之气?曰虚静,即气之体;聚散,其用也。知虚之不为虚,则不得谓之无。老氏曰:‘有生于无’,不知虚即气也。又曰:‘虚能生气。’非也。若曰:‘虚生气’,则方其末生,是无有气而虚为死也。既无有气,又何自而生?无始也,无生也。既无始,何所终?既无生,何所灭?老氏言虚无,佛氏言寂灭,是不识理气之源,又乌得知道。”①这里徐敬德对“太虚”和“气”的内涵、功用皆作了说明:太虚虚而不虚,虚即为“气”;“气”有体用,以虚静为体,而以聚散为用。引文中他在阐述其“太虚”说的同时,还指出了其与佛、老之寂灭虚无的本质区别。“有生于无”出自《老子》第四十章②,“虚能生气”亦与道家“有生于无”不无关系。对此,张横渠批判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③从徐敬德“虚静即气之体”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儒家气论与佛、老之学的本质区别。
二、先天说
徐敬德在论述“太虚”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先天说”:“太虚湛然无形,号之曰先天,其大无外,其先无始,其来不可究,其湛然虚静,气之原也。”④这就是其独特的“先天说”。从引文中可以概见,所谓“太虚”有三层含义:一太虚为世界的本原;二太虚(气)既无形迹亦无终始;三太虚即气。由此,徐敬德在韩国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气不灭”论。“虽一片香烛之气,见其有散于目前,其余气终亦不散,乌得谓之尽于无耶。”⑤举此实例的目的在于说明,气的存在形态虽从有变无也无损其根本属性,此为其“气不灭”论的基本主张。
接着,徐敬德进一步阐发气之“后天说”:
倏尔跃,忽尔辟,孰使之乎?自能尔也,亦自不得不尔,是谓理之时也。《易》所谓“感而遂通”,《庸》所谓“道自道”,周所谓“太极动而生阳”者也。不能无动静,无阖辟,其何故哉?机自尔也。既曰一气,一自含二;既曰太一,一便涵二。一不得不生二,二自能生克。生则克,克则生。气之自微以至鼓荡,其生克使之也。一生二。二者何谓也?阴阳也,动静也,亦曰坎离也。一者何谓也?阴阳之始,坎离之体,湛然为一者也。一气之分,为阴阳。阳极其鼓而为天,阴极其聚而为地。阳鼓之极,结其精者为日;阴聚之极,结其精者为月。余精之散为星辰,其在地为水火焉。是谓之后天,乃用事者也。①
徐敬德以先天、后天来说明本体界和现象界:气未用事时湛然虚静之状态谓之“先天”;气用事后变现之现象谓之“后天”。在太虚与气之聚散等问题的论述中,明显可见张载思想对他的影响。敬德门人朴淳(字和叔,号思庵,1523—1589年)就曾说过花潭所见得颇受张子《太和》等篇的影响。②同时,朴淳也充分肯定了徐敬德对张载气论的发展,指出:“张子所论‘清虚一大’,此穷源反本,前圣所未发也。花潭又推张子之未尽言者,极言竭论,可谓极高明也。”③朴淳虽为敬德的弟子,但与成浑、李珥等皆交好,故而学风较为开放。他讲“花潭又推张子之未尽言者,极言竭论”,可说是公允之言。
三、“二化一妙”论
如何解答“气”与“理”的关系,这是气论中十分重要的课题。为此,徐敬德特撰《理气说》一文,阐明其对理气问题的看法。在理学的首要问题理气先后上,徐氏基于“气为本”的思想,主张“理不先于气”。这是因为气无其始,所以理亦无其始。他说:
原其所以能阖辟、能动静、能生克者而名之曰太极。气外无理,理者,气之宰也。所谓宰,非自外来而宰之,指其气之用事,能不失所以然之正者而谓之宰。理不先于气,气无始,理固无始。若曰理先于气,则是气有始也。老氏曰:“虚能生气”,是则气有始有限也。①
徐敬德在理气问题上的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此段引文中。现将要点归纳如下:一是理不先于气;二是气外无理,二者具有共存性;三是气无始而理固无始,二者具有共时性。徐敬德还以老氏主张为例批判道:若说理先于气等于承认气是有始有限的,则与老氏“虚能生气”论一般无二。这表明在理气先后的问题上,花潭坚持的是二者共存共时性。
徐敬德气论思想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理”的概念及其特性。在上段引文中,花潭将“太极(理)”定义为“原其所以能阖辟、能动静、能生克者”,即事物产生运动变化的原因。此“所以”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宰”,即“气外无理,理者,气之宰也”。问题是此“气之宰”可否理解为一般朱子学意义上的理对气的主宰作用?如果将此理解为主宰性,那么花潭哲学便可说是理气二元结构的理论体系。对“宰”的概念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可以发现,文中“气之宰”指的是事物运动变化时的条理或是规律。徐敬德之理是“指其气之用事,能不失所以然之正者”,亦即事物的内在法则。可见,在花潭哲学中“理”不具有主宰义。
作为气本论者,徐敬德将天地万物的变化归结为“机自尔”,意思是说事物的阖辟动静皆由内因决定而外力无与焉。他进一步解释道:“阴阳一用,动静一机,此所以流行循环不能自己也。”②“一阴一阳者,太一也。二故化,一故妙,非化之外,别有所谓妙者。二气之所以能生生化化而不已者,即太极之妙,若外化而语妙,非知易者也。”③此即徐敬德的“二化一妙”说。在他的哲学中,“妙”为事物运动的根本属性,而“化”则为运动变化之内因——“妙化”就是对立统一。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事物正是由内因之推动而生生化化、迁变不已。徐敬德的这一思想极具理论卓见,在韩国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尽管徐敬德气论很有创意,但是同时代的性理学家并未对其学说给予肯定,反而多有微词。李滉尝言:“因思花潭公所见于气数一边路熟。其为说未免认理为气,亦或有指气为理者。故今诸子亦或狃于其说,必欲以气为亘古今常存不灭之物,不知不觉之顷,已陷于释氏之见,诸公固为非矣。”①李滉认为徐敬德论气虽精到无余,却因主气太过于理未深透彻,颇有认理为气之病。而李珥亦批评道:“花潭则聪明过人,而厚重不足。其读书穷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聪明过人,故见之不难,厚重不足,故得少为足。其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了然目见,非他人读书依样之比,故便为至乐。以为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气局一节,继善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理无变而气有变,元气生生不息,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在。而花潭则以为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此花潭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②李珥虽也指责其说有认气为理之病,但仍肯定与退溪相比“花潭多自得之味”③。他还认可徐敬德对“理气不相离之妙处”已“了然目见”。
其实,李珥对徐敬德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花潭哲学之难解就在于其对“理气之源”等紧要处的细心体贴。徐氏以为:“理之一其虚,气之一其粗,合之则妙乎妙。”④他还说过:“气之湛一清虚者,既无其始,又无其终,此理气所以极妙底。学者苟能做工到此地头,始得觑破千圣不尽传之微旨矣。”⑤可见,他自己也认为此等处为理解其学说的关键。不过,徐敬德所谓理气不相离之妙实基于气一元论,而非构筑在理气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花潭学说对李珥主气论影响较大,但李珥还是直言“宁为退溪之依样,不必效花潭之自得也”⑥。李珥甚至预言:“恐珥读书愈久,而愈与公(指花潭——引者注)见背驰也。”⑦
简言之,李滉与李珥对徐敬德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气本论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后人对其学术性格的判定。由此亦可见,气学派与理学派学者无论在学术立场还是理论旨趣上皆相距甚远。
作为韩国气学派的理论先驱,徐敬德的学问和品格皆为后世学人所敬重,被尊为“近代儒林之表”①。李滉对其理论贡献称许道:“然吾东方,前此未有论著至此者,发明理气,始有此人耳。”②李珥也对其学问赞曰:“虽然偏全闲,花潭是自得之见也。”③
1772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花潭集》二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八《别类存目》五之中)。徐敬德是著作被收录《四库全书》的唯一的韩国哲学家,可谓千载一人而已。这也说明其哲学在韩国乃至东亚哲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徐敬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原理气》、《理气说》、《太虚说》、《鬼神死生论》以及《复其见天地之心说》等,现均被收录于《花潭集》(4卷)中。
第四节 李彦迪的理本论
——以“无极太极”之辨为中心
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学术论辩有“无极太极”之辨、“四端七情理气”之辨、“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人物性同异(湖洛论争)”之辨以及“心说”论争等。其中,“无极太极”之辨是对性理学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其余皆为对性理学心、性、情等核心概念的深度辨析。这些论辩的依次展开不仅促进了韩国性理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韩国儒学独特理论风格的形成。从韩国儒学各个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争辩中,我们可以发现韩国性理学家们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本节要考察的是韩国儒学史上首次出现的学术论争——“无极太极”之辨。
一、论辩的发端
李彦迪(1491—1553年),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谥号文元,庆州府人。李氏出生于庆州良佐村,10岁丧父,12岁时短暂受学于其舅父愚斋孙仲暾(1463—1529年),而愚斋曾为佔毕斋金宗直门人。我们只知道李彦迪的思想与愚斋之弟亦为其舅父的忘斋孙叔暾①有所不同。李氏学无师承②,于中宗九年(1514年)登第,始入仕途,历任吏曹判书、刑曹判书、左赞成等官职。作为朝鲜朝前期士林学者的“五贤”③之一,他既是朝鲜朝主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先驱,又是朝鲜朝性理学鼎盛期的揭幕人。李彦迪一生从宦多年,旋进旋退,颇不平顺。在他8岁时发生“戊午士祸”,14岁时发生“甲子士祸”,29岁和55岁时又发生“己卯士祸”、“乙巳士祸”。韩国历史上的“四大士祸”皆曾亲历。但是,李彦迪始终将“养真”与“经世”④作为其平生之志,为后学树立了一个有担当、有追求的儒者形象。他23岁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生志业在穷经,不是区区为利名。
明善诚身希孔孟,治心存道慕朱程。
达而济世凭忠义,穷且还山养性灵。
岂料屈蟠多不快,夜深推枕倚前楹。⑤
此诗写于中宗九年,正是其中生员试之年。从“明善诚身”、“治心存道”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其强烈的希慕圣贤之情。诗中所抒发的正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的儒家理想情怀和入世精神。可见,李彦迪在步入仕途之初便立下修齐治平的人生志向。
他的学问和思想对韩国性理学的影响,从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滉之评价可以概见。李滉尝言:
谨受而伏读之,反复参究,质之以古圣贤之言,于是始知先生(指晦斋——引者注)之于道学,其求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正也。而凡先生之出处大节,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先生在谪所,作《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又修《中庸九经衍义》,《衍义》未及成书,而用力尤深。此三书者,可以见先生之学。而其精诣之见,独得之妙,最在于与曹忘机汉辅《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也。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呜呼,我东国古被仁贤之化,而其学无传焉。丽氏之末以及本朝,非无豪杰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归之者。然考之当时,则率未尽明诚之实,称之后世,则又罔有渊源之征,使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②
此段文字引自李滉为李彦迪所撰写的“行状”,文中他对李氏的生平和学问做了简明扼要之概括,称道其有精诣之见和独得之妙。文中李滉虽然举了《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成稿《中庸九经衍义》等李氏代表作,但是他认为李氏学问之理论精髓在于与曹忘机堂(名汉辅,庆州人)的《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中。其实,李滉提到的《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稿《中庸九经衍义》都是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所作。他在江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六年,最终在此地辞世,享年63岁。而与忘机堂的无极太极论辩书则作于李氏二十七八岁时,可见其思想成熟之早。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著作所表达的观点是早年与忘机堂曹汉辅论辩时确立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节也将以李彦迪与曹汉辅的《论无极太极书》为中心,来探讨其理本论哲学思想的特点。
这场论辩发生在1517年(中宗十二年)至1518年。最初是忘斋孙叔暾与忘机堂曹汉辅①之间通过书信对“无极太极”问题展开相互问难。李彦迪读到这些书信后,便撰写《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以下简称《说后》)一文对之加以评述。曹汉辅旋即对李彦迪的《说后》提出了异议。于是,李氏和曹汉辅之间开始有书信往来,现存《晦斋集》中有李彦迪答忘机堂书信四封。但曹汉辅致李彦迪的书信皆已失传,只能通过现存的李彦迪答曹汉辅书信一窥其思想梗概。
这里我们首先对《说后》的主要内容做些简要分析,以便对李彦迪、孙叔暾和曹汉辅的观点有个总体的了解。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说后》的内容按文意分为若干个段落,抄录如下:
第一段落:“谨按:忘斋无极太极辨,其说盖出于陆象山,而昔子朱子辨之详矣。愚不敢容赘。若忘机堂之答书,则犹本于濂溪之旨,而其论甚高,其见又甚远矣。其语《中庸》之理,亦颇深奥开广。得其领要,可谓甚似而几矣。然其间不能无过于高远而有悖于吾儒之说者。愚请言之:夫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柢也。是乃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来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哉!此理虽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实体之所以寓,则又至近而至实。若欲讲明此理而徒骛于窅冥虚远之地,不复求之至近至实之处,则未有不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矣。”②
本段引文的观点可视为李氏在“无极太极”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文中李彦迪首先对忘斋和忘机堂观点的理论来源作了说明,指出忘斋的主张出自陆子学说,而忘机堂的观点则本于濂溪之旨。他进而声言,陆子的无极太极之说因朱子已详辩无须赘言,而妄机堂的学说则因过于高远而似有背于吾儒之旨处。由此可见,宋代朱陆之辨是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之辨的理论先河。李彦迪在本段还阐述了自己对无极太极问题的基本理解,主张并非太极之上复有无极,此至高至妙之理只能在至近而至实处求之,不然就会有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的危险。由此可见,他对道体之根源、行为之应然等问题越有借由自己的理解。不过,从李氏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来看,其见似与朱子并无二致。此其所以李滉评论其学说时直言“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
第二段落:“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也则是矣。其曰岂有论有论无、分内分外,滞于名数之末则过矣。其曰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则是矣。其曰大本达道浑然为一则何处更论无极太极,有中无中之有间则过矣。此极之理虽曰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发差者。是岂漫无名数之可言乎?而其体之具于吾心者则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然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容不辨者。安有得其浑然则更无伦序之可论,而必至于灭无之地而后为此道之极致哉。今徒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极言之,而不知夫粲然者之未始相离也。是以其说喜合恶离、去实入虚,卒为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而后已。岂非穷高极远而无所止者欤?”①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援引朱子之说对忘机堂的不当言论进行了逐一反驳,指出其“太极即无极”、“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等见解可以成立,但不分有无、分内分外以及有中无中而论无极太极却明显不妥。李氏以为太极之理虽然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无有毫发之差。①而且,其“体”之具于吾心者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同。故不能只重其浑然而轻其伦序,“喜合恶离,去实入虚”。
第三段落:“先儒言周子吃紧为人特著道体之极致,而其所说用工夫处只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尝使人日用之间必求见此无极之真而固守之也。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若论工夫则只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今忘机之说则都遗却此等工夫,遽欲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万物朝宗于我而运用无滞,是乃欲登天而不虑其无阶,欲涉海而不量其无桥。其卒坠于虚远之域而无所得也必矣。大抵忘机堂平生学术之误病于空虚,而其病根之所在则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以灭字说太虚体,是断非吾儒之说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谓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谓于穆不已者存焉。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著灭字于寂字之下。试以心言之:喜怒哀乐未发、浑然在中者,此心本然之体而谓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则喜怒哀乐发皆中节,而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谓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灭则是枯木死灰而已,其得不至于灭天性乎?然忘机于本来寂灭之下便没灭字不说,而却云虚而灵、寂而妙。灵妙之体充满太虚、处处呈露,则可见忘机亦言其实理而说此灭字不去。故如是岂非有所穷而遁者乎?”②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直言不讳批评忘机堂,以为其平生之误在于“空虚”二字,而其病根则在“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他在指出错误根源的同时,还断言以“灭”字说太虚体“断非吾儒之说”。“寂灭”是佛教用语,《涅槃经》上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一句。而“诸行无常”则又是佛教三法印之一,因此《涅槃经》上的这一句又可视为佛家基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众所周知,大乘佛教不承认现实世界的实在性。以“四大”为假合,以寂灭为圆觉,遂将人伦道德视如赘疣。而儒家所说的“寂”则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寂”,与佛家之寂灭有着本质的区别。
李彦迪还批评忘机堂曹汉辅不仅在太极之上复设无极,而且漠视形而下之人伦日用之修养工夫。如果只关注形而上之“灵妙之体”,就无从体认至近至实处的太极之理。他认为上天无声无臭可谓“寂”,然至寂之中又有“于穆不已”,其化育流行遂生鸢飞鱼跃之景象,所以在“太极”之上绝不可添加一“灭”字。
“自汉以来圣道塞而邪说行,其祸至于划人伦、灭天理而至今未已者,无非此一灭字为之害也。而忘机堂一生学术言语及以上议论之误,皆自此灭字中来。愚也不得不辨。若其超然高会一理浑然之体而的无疑,则实非今世俗儒高释所可几及。亦可谓智而过者矣。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矣。而不幸世无孔孟周程也,悲夫!”①
在本文结尾处,李氏总结异端之弊害全在一“灭”字,而忘机堂为学论议之误亦皆源自此一“灭”字。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撰文辨析。“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
由此而论,李氏批评忘机堂曹汉辅的用意在于揭露其异端思想,像文章中隐约出现的佛家倾向。《说后》一文写于中宗十二年(1517年)正月,即李彦迪27岁之时。曹汉辅何时作复则已无从查考。从年谱上的记载看,李彦迪答忘机堂曹汉辅的第一封书信是在中宗十三年(戊寅年即1518年)写的。他时年28岁。
二、论辩的主要内容及理论特点
前已言及,“无极太极论辩”起因于李彦迪所撰的《说后》。该文写于中宗十二年,翌年曹汉辅对此提出异议。于是,便有了“答忘机堂”的四封书信。
在论辩的过程中,晦斋李彦迪和忘机堂曹汉辅围绕“无极”、“太极”概念以及儒家修养论等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发生于朝鲜朝初期的此一论辩中,李彦迪从朱子学理本论的立场出发,批驳了具有佛道思想色彩的曹汉辅的主张。此论辩在学理上可理解为“无极太极”问题的性理学式解读和非性理学式解读的立场对立。
因为《说后》主要是李彦迪对孙叔暾和曹汉辅的“无极太极”说的评论文章,故只能了解到他的思想概貌。不过,在“答忘机堂”的四封书信中却可以发现李氏较为系统的性理学观点。而且,从《说后》和《答忘机堂书》中还可以看出,曹汉辅的观点的确受到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故李彦迪在《答忘机堂书》中,指责其所持的是佛家之寂灭论而非儒家之寂感论。李氏和曹汉辅之间的论辩作为性理学本体论问题之探讨在韩国儒学史上意义重大,说明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已具备相当的理论水平。下面将对四封书信之内容做逐一分析。
在《答忘机堂第一书·戊寅》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伏蒙示无极寂灭之旨、存养上达之要,开释指教不一而足。亦见尊伯不鄙迪而收之,欲教以进之也。感戴欣悚,若无所容措。”①可知,曹汉辅在读了李氏所写的《说后》之后,就“无极寂灭”和“存养上达”等本体论、修养论问题给李氏回信,这应该是曹汉辅在致李彦迪信中谈的主要问题。
于是,李彦迪在复信中首先解释自己为何撰写《说后》,然后针对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又陈述了己见。他说:
来教所云寂灭存养之论有似未合于道者。小子亦有管见须尽露于左右者,敢避其僭越之罪而无所辨明耶。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风雷之所以变,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周子所以谓之无极者,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非若老氏之出无入有、释氏之所谓空也。①
从整个论辩过程中李氏自谦的语气和态度来看,曹汉辅应较彼时才二十七八岁的李彦迪年长许多。所以李氏在信中陈述己见时显得比较谨慎。对于曹氏的寂灭存养之论,李彦迪十分谦虚地讲到“小子亦有管见须尽露于左右”,然后谈了自己对“太极”与“无极”概念的理解。他指出“太极”作为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是实然而不可易者,周子所以又称之为“无极”乃因其具“无方所、无形状”之特性。究其实与佛道两家所言“空”、“无”等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接着他借“理”、“气”之概念阐发了己见,并对曹氏的本体论进行了批评:
今如来教所云,无则不无而灵源独立,有则不有而还归澌尽。是专以气化而语此理之有无,岂云知道哉?所谓灵源者气也,非可以语理也。至无之中至有存焉,故曰“无极而太极”。有理而后有气,故曰“太极生两仪”。然则理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而言。何必见灵源之独立然后始可以言此理之不无乎?鸢飞鱼跃昭著上下,亘古亘今充塞宇宙。无一毫之空阙,无一息之间断。岂可但见万化之澌尽而遂指此极之体为寂灭乎?②
从内容中可以推知,曹汉辅将“灵源”视为宇宙本体。而李彦迪则认为所谓“灵源”者其实是气,不能将形而下之“气”视为宇宙的终极本体。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其实是“至无之中至有存焉”之义。此处的“而”应指“所当然之中”的“所以然之理”——太极即是“理”。①李氏进而提出自己的理气观——“有理而后有气”,“理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理与气的关系问题是朱子学的基本问题,李氏对此所持的正是传统朱子学以理为本的理气二元论立场。
他还指出曹氏所云寂感、寂灭之分似同而实异的,先儒对此已有至论,后学者不可以此为浮议而独以异端之说为是:
盖太极之体虽极微妙,而其用之广亦无不在。然其寓于人而行于日用者,则又至近而至实。是以君子之体是道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有以全其本然之天而绝其外诱之私。不使须臾之顷、毫忽之微,有所间断而离去。其行之于身也,则必造端乎夫妇以至于和兄弟顺父母,而有以尽己之性。及其尽性之至也,则又有以尽人物之性。而其功化之妙极于参天地赞化育,而人极于是乎立矣。此君子之道所以至近而不远,至实而非虚,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此非愚生之言,实千古圣贤所相传授而极言至论者也。②
文中李彦迪借圣贤之言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表明己见合乎儒家正统。太极与理气的问题属于天道,李氏遂借探讨寂灭的问题将话题转入人道。他认为道不远人,若离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于空虚。李彦迪引用《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之句来说明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安得不先于下学之实务而驰神空荡之地?可以为上达乎?天理不离于人事。人事之尽而足目俱到以臻于贯通之极,则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浑全。酬酢万变、左右逢源,无非为我之实用矣。”③李氏依据朱子“统体一太极”的思想为依据,提出天理不离于人事,以此批判曹氏的“存养上达”修养方法的根本错误。李彦迪说: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又曰:“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讵不信欤?且如存养之云,只是敬以直内,存之于未发之前以全其本然之天而已。苦曰游心于无极之真。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使人不为近思之学而驰心空妙。其害可胜言哉?又况虚灵本是吾心之体也。无极之真,本是虚灵之中所具之物也。但加存之之功而不以人欲之私蔽之,以致其广大高明之体可也。张南轩曰:“太极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惟当本于敬以涵养之。”正谓此也。今曰“游心于无极”,曰“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似以无极太极为心外之物而别以心游之于其间,然后得以为之主也。此等议论似甚未安。①
李彦迪在文中先讲明虚灵、无极之真以及吾心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儒家修身的正确方法。由此可见二人为学工夫之差异。李彦迪强调洒扫应对当中的“下学而上达”,而曹氏则主张带有“顿悟”性质的“存养而上达”。后者的主张当然会受到正统儒者的批评。在结尾处李彦迪写道:
来教又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亦见尊伯立言之勇而自信之笃也。然前圣后圣其揆一也。今以已往圣贤之书考之,存养上达之论无所不备。其曰“存心养性”,其曰“戒慎恐惧”,其曰“主静曰主敬”者,无非存养之意。而曷尝闻有如是之说乎?吕氏虚心求中之说,朱子非之。况以游心无极为教乎?孔子生知之圣也,亦曰“我下学而上达”,又曰“吾尝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况下于孔子者乎?故程子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欲人收已放之心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以此观之,其言之可易与不可易直验于已往之圣人而可见矣。何必有待于后来复起之圣人乎?天下之祸,莫大于甚似而难辨。惟其甚似,故能惑人;惟其难辨,故弥乱真。伏详赐书,无非杂儒释以为一。至有何必分辨之说,此小子所甚惧而不敢不争者也。伏见尊伯年高德邵,其于道体之妙亦可谓有所见矣。但以滞于寂灭之说,于其本源之地已有所差。而至于存养上达之论,则又与圣门之教大异。学者于是非之原毫厘有差,则害流于生民,祸及于后世。况其所差不止于毫厘乎?伏惟尊伯勿以愚言为鄙,更加着眼平心玩理。黜去寂灭游心之见,粹然以往圣之轨范自律。吾道幸甚!善在刍荛,圣人择之。况听者非圣人,言者非刍荛。而遽指言者为狂见而不察乎?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古之君子改过不吝,故年弥高而德弥进也。小子所望于尊伯者止此。①
从曹汉辅“游心于无极之真”以及“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等见解中确实可以感受到其思想明显混杂于佛理。所以李彦迪在此信的末尾处称忘机堂“无非杂儒释以为一”,与圣门之教的理论旨趣相去甚远。尽管二人年龄相差较大,李彦迪仍以昂扬的卫道精神据理力争。
接到曹汉辅的回信后,李彦迪在《答忘机堂第二书》中写道:“伏睹来教于无极上去‘游心’二字,于其体至寂下去一‘灭’字。是不以愚言为鄙,有所许采。幸甚幸甚!”②这表明忘机堂接受李氏在第一封信中的批评,已去掉无极之上的“游心”二字和其体至寂下的一“灭”字。但是,彦迪仍然觉得曹汉辅尽管在字句上对之前的表述做了些调整,却并未尽弃其思想中的佛、道立场。于是,他继续提出委婉的批评:
书中所论一本之理及中庸之旨,亦颇明白少疵、妙得领要。圣人之道,固如斯而已,更无高远难穷之事。迪敢不承教。③
文中提到的“一本之理”和“中庸之旨”分别指的是第一封信中所讨论的无极太极、寂灭等本体论的问题和有关存养上达的工夫论问题。可见,在内容上此信殆可视为第一封信之继续。李彦迪提到:
至如寂灭之说,生于前书粗辨矣。未蒙察允,今又举虚灵无极之真,乃曰“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是未免于借儒言而文异端之说。小子之惑滋甚。先儒(指朱子——引者注)于此四字盖尝析之曰:“此之虚,虚而有;彼之虚,虚而无;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灭。”然则彼此之虚寂同,而其归绝异,固不容不辨。而至于无极之云,只是形容此理之妙无影响声臭云耳,非如彼之所谓无也。故朱子曰:“老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讵不信欤?①李彦迪认为曹氏的“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实际上是借吾儒之言文饰异端之说。他举朱子之言阐明儒家的虚寂观念与异端之虚寂说犹如南北水火之相反,在理论归趣上决然不同。彼此之虚寂名同而实异。
李彦迪进而指出:
来教又曰:“主敬存心而上达天理。”此语固善,然于上达天理上却欠“下学人事”四字,与圣门之教有异。天理不离于人事。下学人事,自然上达天理。若不存下学工夫,直欲上达,则是释氏觉之之说。乌可讳哉?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则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便是上达境界。从事于斯,积久贯通,可以达乎浑然之极矣。而至于穷神知化之妙,亦不过即是而驯致耳。②
李彦迪在为学次第上重视“下学人事”,体现心性工夫之切近日用人伦的一面。他引孔子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之语以证明己之看法。最后李彦迪写道:
夫穷理,非徒知之为贵。知此理又须体之于身而践其实,乃可以进德。若徒知而不能然,则乌贵其穷理?而其所知者终亦不得而有之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然则非知之难,行之难。此君子所以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必顾行、行必顾言,不敢容易大言者也。不知尊伯亦有如是体察之功乎?亦有如是践履之实乎?大抵道理,天下之公共。不可以私智臆见论之。要须平心徐玩,务求实是可也。③
依李彦迪之见,所谓“穷理”指的是由亲身体验知晓此理,必以进德为期才是理学家所谓德性之知。他委婉指出若无“体察之功”、“践履之实”,则所见往往流为异端。作为晚辈祈盼曹氏痛去寂灭之见,又能主敬存心以达于天理。诚如此,“则尊伯之于斯道,可谓醇乎醇矣。”①前已论及曹李二人年龄差距较大。但是从信的内容来看,曹汉辅并未轻视一位新锐学者对己见之质疑。于是,有了他们之间的第三封书信。
在《答忘机堂第三书》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伏睹来喻所陈,虽云不滞寂灭之说有年,而寂灭之习似依旧未除。是以其论说浮于道理幽妙之致,而未及反躬体道之要。不免为旷荡空虚之归,而非切近的当之训。此小子所以未敢承命者也。”②于是李氏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体道经验和感悟。
从此信的内容可以推知,曹汉辅复信中的主张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大本”与“达道”,即“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的存养之道问题。彦迪在信中提到:
迪闻子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古今论道体,至此而无余蕴矣。愚请因此而伸之。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散诸三极之间。凡天地之内,无适而非此道之流行,无物而非此道之所体……当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此心之真寂然不动。是则所谓无极之妙也,而天下之大本在于是也。固当常加存养之功以立大本,而为酬酢万变之主。而后可以发无不中而得时措之宜。然于此心之始动几微之际,天理人欲战于毫忽之间,而谬为千里之远。可不于是而益加敬慎乎?是故君子既常戒惧于不睹不闻之地,以存其本然之,而不使须臾之离有以全其无时不然之体……自其一心一身以至万事万物,处之无不当,而行之每不违焉。则达道之行于是乎广矣,而下学之功尽善全美矣。二者相须,体道工夫莫有切于此者。固不可阙其一矣。
来教有曰:“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则固存养之谓矣,而于静时工夫则有矣。若夫顿除下学之务,略无体验省察之为,则于动时工夫盖未之及焉。是以其于求道之功疏荡不实,而未免流为异端空虚之说。
伏睹日用酬酢之际,不能无人欲之累。而或失于喜怒之际,未能全其大虚灵之本体者有矣。岂非虽粗有敬以直内工夫,而无此义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体道不能精密而或至于此乎。昔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子继之曰:“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然则圣门工夫虽曰主于静以立其本,亦必于其动处深加省察。盖不如是则无以克己复礼,而保固其中心之所存矣。故曰“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未有不制其外而能安其中者也。愚前所云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顾行行顾言者,此之谓也。安有遗其心官、随声逐色,失其本源之弊哉?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盖地位已到圣人,则此等工夫皆为筌蹄矣。若未到从容中道之地而都遗却择善省察工夫,但执虚灵之识。①
李彦迪在信中对儒家的“大本”与“达道”作了简单明了的论述,这表明他对之已有了深切之体悟。李彦迪在工夫论问题上的立场是,“常加存养之功以立大本,而为酬酢万变之主”。他主张“存养”不能像曹汉辅那样只强调“敬以直内”,而忽视“义以方外”。在李彦迪看来,不假修为即可克己复礼、酬酢万变如同不出门而欲适千里,不举足而欲登泰山,结果肯定是“必不能矣”。
二是曹汉辅认为为破世人执幻为真,故言“寂灭”。对此有悖儒家宗旨的“异端”之见,李彦迪批评道:
来教又曰:“为破世人执幻形为坚实,故曰寂灭。”此语又甚害理。盖人之有此形体,莫非天之所赋而至理寓焉。是以圣门之教,每于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尽夫天之所以赋我之则,而保守其虚灵明德之本体。岂流于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岂可以此为幻妄?必使人断除外相,独守虚灵之体,而乃可以为道乎?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此寂灭之教所以陷于空虚诞谩之境,而无所逃其违天灭理之罪者。①众所周知佛教主张“四大皆空”,其耽空沦寂之弊对儒家之教危害甚深。李彦迪依性理学“道器不离”、“体用一源”之旨对之予以批驳。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肯定了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这一点在讨论“下学上达”时讲得更透彻。
三是在“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上,曹汉辅认为“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对此李彦迪不以为然。他说:
今曰“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愚请以孔子申之。自生民以来,生知之圣未有盛于孔子者,亦未尝不事于下学……然则孔子不得为豪杰之士,而其所为亦不足法欤?若曰孔子之言所以勉学者也,于其己则不必,然则愚请以孔子所亲为者白之。孔子问礼于老聃,问官于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是非下学之事乎?问官之时,实昭公十七年而孔子年二十七矣。入太庙则孔子始仕时也。古人三十而后仕,则是时孔子年亦不下三十。其非童蒙明矣。夫以生知之圣,年又非童蒙,而犹不能无下学之事。况不及孔子?而遽尔顿除下学不用力,而可以上达天理乎?是分明释氏顿悟之教,乌可尚哉?孟子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若使尊伯于此异说之诞终身迷没,不知其非则已矣。今曰不滞者有年,则是已觉其非而欲改之也。退之云“说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请自今痛去寂灭之见,反于吾道之正。②
曹汉辅与李彦迪二人在为学之方上的分歧与宋代朱陆之间“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颇有相似之处。陆氏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将朱子的“博学于文”视为“支离事业”。朱子则批评象山为学浮躁,只好发高论而不“道中庸”,造说遂与佛老相似。③在为学之方上李彦迪以圣贤为例批驳了曹氏的观点,强调不论童蒙初学还是豪杰之士皆不能无下学之事。
《答忘机堂第四书》是两人之间最后一次通信,在复信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今承赐教,辞旨谆谆,反复不置,且去‘寂灭’二字而存‘下学人事’之功。迪之蒙许深矣,受赐至矣,更复何言!”①从中可推知,经过几次书信往来曹汉辅对李彦迪的批评有所接受,对自己的立场也做了调整。而且李彦迪也认可曹汉辅态度之转变。他在信中指出:“然而窃详辱教之旨,虽若尽去异说之谬、入于圣门之学,然其辞意之间未免有些病。而至于物我无间之论,则依旧坠于虚空之教。小子惑焉。”②但在李彦迪看来,忘机堂仍未彻底摒弃其原有思想。第四封信的讨论焦点是有关“主敬存心”的工夫论问题。李彦迪写道:
圣门之教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齐其外以养其内。内则无贰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俨然肃然,深省密察,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动直、中一外融,则可以驯致乎不勉不思从容中道之极矣。两件工夫不可偏废明矣。安有姑舍其体而先学其用之云哉?③
李彦迪将理学工夫论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简言之,即践行居敬穷理。这是基于伊洛渊源的正统解释。李彦迪在信中十分强调“敬”之工夫,这一思想对后来李滉的主敬工夫论颇有影响。李彦迪援引程伊川从《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中提炼出来的道德戒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本体工夫固不可不先,而省察工夫又尤为体道之切要”。他认为颜子亦循此四箴之路径优入圣域,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李彦迪主张为人要谨守“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由此他对曹氏在第三封复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一一做了答复。
一是“主敬存心”的问题。李彦迪以“衣”、“网”为例答复说:“伏睹来教有曰‘主敬存心’,则于直内工夫有矣,而未见义以方外省察工夫。岂非但得衣之领而断其百裔,但得网之纲而绝其万目者哉?人之形体固当先有骨髓,而后肌肤赖以充肥。然若但得骨髓,一切削去皮肤,则安得为人之体?而其骨髓亦必至于枯槁而无所用矣。况既去皮肤而于骨髓亦未深得者哉?愚前所谓常加存养以立大本,为酬酢万变之主者,固尊伯主敬存心、先立其体之说。初非毁而弃之。未蒙照察,遽加罪责,不胜战汗。”①前已言及李氏并不反对“主敬存心”,只是向忘机堂强调了修养工夫不能缺失“义以方外”。在他看来,两段工夫同等重要,必须同时并举。
二是“先立其体和下学人事”的问题。李彦迪对此回复道:“来教又曰:‘先立其体,然后下学人事。’此语亦似未当。下学人事时,固当常常主敬存心。安有断除人事,独守其心?必立其体。然后始可事于下学乎。所谓体既立则运用万变,纯乎一理之正而纵横自得者。固无背于圣经贤传之旨。然其所谓纯乎一理、纵横自得者,乃圣人从容中道之极致。体既立后,有多少工夫?恐未易遽至于此。伏惟更加精察。”②此问题还是前一问题的延伸。李彦迪在存养省察的问题上立场鲜明,就是坚持下学与上达同时并进。
三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问题。李彦迪谈了自己的理解,指出:“且如万物生于一理。仁者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然其一体之中,亲疏远近是非好恶之分自不可乱。故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语》又曰:‘惟仁人为能好人,能恶人。’以此言之,仁者虽一体万物,而其是非好恶之公亦行乎其中而不能无也。舜大圣人也,固非有间而滞于所执者。然而取诸人为善,舍己从人则舜亦不能无取舍之别矣。安有心无间则茫然与物为一?更无彼此取舍好恶是非之可言,然后为一视之仁哉。”③追求“天人合一”是儒家修己的最高理想。但李彦迪强调的是“一体之中,亲疏远近是非好恶之分自不可乱”。他认为儒者同时还要具备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从而做到择善而从。
在信的最后李彦迪语词恳切,寄望曹汉辅平心察理,勿以其有是非取舍为罪。此后曹氏再未复信,而两人的论辩也就此而告终。从现存四封书信的内容来看,李氏最终也没能说服忘机堂尽弃其原有立场。读此书信可以感受到一位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士大夫①的卫道意识。两人温文尔雅之论辩既流露了少壮学者李彦迪的锐气和担当,又展现了学界名宿曹汉辅的平和与谦逊。
三、论辩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无极太极”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围绕与朱子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发生的首次论辩。此次论辩不论对李彦迪太极说的形成还是朱子学在韩国的发展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论辩的过程中,李彦迪基于朱熹之理气二元论对具有佛道思想倾向的曹汉辅“无极太极”说进行了批驳。与此同时,他还以性理学为正统捎带批判佛道两家的理论。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论辩不仅令性理学之本体论得以确立,而且使儒佛与儒道之义理分际得以明晰。尽管此后还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四七理气”之辨、“人心道心”之辨和“人物性同异”之辨等等,但是此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视。
“四七理气”之辨则与“人心道心”之辨密切相关。后者也是朱子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韩国儒学史上令“四七理气”之辨得以进一步深化。本书将在论述四端七情论辩时设专节详述“人心道心”之辨。
与前一节介绍的徐敬德相比较,李彦迪虽亦重视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思想之旨趣却与徐氏大相径庭。徐敬德基于气本论之立场,主张“太虚即气”;而李彦迪则依据理本论之立场,将“太极”视为天理。“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①李彦迪从主理论出发,阐述了其“太极说”。他认为这种“理”是“无形无质”之存有,“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但理先气后,“有理而后有气”。②李彦迪进一步指出:“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有日月之形则有所以为日月之理,有山川之形则有所以为山川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③他以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天地万物之理(太极),而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后依然作为事物之所以然与大千世界密切结合。李彦迪又说:“天下之理体用相须、动静交养,岂可专于内而不于外体察哉?”④由此可见李彦迪哲学思想的主理论特色。
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著有《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中庸九经衍义》——后者虽未完稿,但是较为详细地反映了他的道德经世观。《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则是申述朱子之学的著作。在《大学章句补遗》一书中李氏曾言及朱子所作《格物补传》之不当处。例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原文“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下朱熹写道:“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接着又写道:“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⑤于是依程子之意作了格致章的补传。对此李氏指出:“朱子得其结语一句,知其为释格物致知之义,而未得其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所以发明始学穷理之要,亦甚明备。然愚尝读至于此,每叹本文之未得见。近岁闻中朝有大儒得其阙文于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见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见。取经文中二节,以为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复参玩,辞足义明,无欠于经文而有补于传义,又与上下文义脉络贯通。虽晦庵复起,亦或有取于斯矣。”①可见,他对朱子之《格物补传》有失当处极为自信。李彦迪以为《大学章句补遗》开头经文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②二节原为格致章的原文,如今被错误纳入经文之中。为此他主张应将此两节,重新归入格致章之原文之中。而“此谓知之至也”一句是结上文两节之意的。《大学章句补遗》写于1549年,李氏时年59岁,早已是成名的儒学大家。此文对研究李彦迪理学思想大有助益。相较于朱子,李氏更强调格物致知之“止于至善”。依李彦迪之见,致知宜有缓急先后,由近及于远,由人伦及于庶物,必有以见其至善之所在而知所止,然后其所知所得皆切于身心。
从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程朱之学,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蕴育,至李彦迪才有较具体系的性理学说。李氏的理气论和无极太极论在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他的思想在韩国儒学本土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李彦迪的性理学说成为日后李滉和李珥等人集朝鲜朝朱子学之大成的理论基础。李氏第一次将有关心性修养和经世致用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整理,为韩国儒学界确立了理本论哲学体系,而与曹汉辅之论辩集中反映了他的心性论思想。正是李彦迪将修身之存养工夫引向了心性论的进路。
李彦迪理本论思想对李滉的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滉十分推崇李彦迪,不仅称赞他的“立言垂后”之功,还曾为其作行状极言学力之深湛。李滉评论道:“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③还说:“近代晦斋之学甚正,观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义正,浑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④他认为李彦迪的学问“所得之深殆近世为最也”①。李珥尽管对李彦迪在“乙巳士祸”中的作为颇有微词,但对其学问还是相当首肯,尝言:“李彦迪博学能文,事亲至孝,好玩性理之书,手不释卷。持身庄重,口无择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学者亦以道学推之。”②
光海君二年(1610年),李彦迪还与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混作为“士林五贤”配享文庙。他的哲学著作有《求仁录》、《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中庸九经衍义》、《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答忘机堂书》以及《奉先杂仪》等。
概而言之,发生于16世纪初期的这场论辩反映了朝鲜朝初期的韩国儒者对理学本体论的不同理解。尽管这一论辩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力不及16世纪发生的“四端七情”之辨和“人心道心”之辨,但在理学本土化的初期即由深度的哲学思考树立了正统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后来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两位老少学者间展开的“无极太极”之辨在成就韩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的同时,还正式拉开了16世纪韩国儒学一系列精彩的学术论辩的序幕。
第五节 曹植的性理学
曹植(1501—1572年),字楗仲,号南冥,谥号文贞。他出生于庆尚道三嘉,5岁时移居汉阳。作为朝鲜朝著名的性理学家,曹南冥崇尚洙泗学的实践躬行精神,主张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因与李退溪同年,又并峙岭之左右,故合称岭南学派之双璧。庆尚右道的儒者大都从曹南冥之说,庆尚左道的儒者则多从李滉之说。后人称退溪学派为江左学派,南冥学派为江右学派。河谦镇(字叔亨,号晦峰、畏斋,1870—1946年)在《东儒学案》之《德山学案》写道:“退溪居岭左之陶山……南冥居岭右之德山……蔚然为百世道学之宗师。二先生以天品:则退溪浑厚天成,南冥高明刚大。以出处:则退溪早通仕籍,位至贰相;南冥隐居尚志,屡征不起。以学问:则退溪精研力索天人性命之理,无有余蕴;南冥反躬实践,敬义夹持之功,自有成法。”①本节将简要介绍一下岭南学派另一大儒曹南冥的思想。
与李退溪不同,曹南冥一生未仕,始终以教授为业。其为学极重“敬义”,尝曰:“吾家有此两个字,如天之有日月,洞万古而不易。圣贤千言万语,要其归,都不出二字外也。学必以自得为贵曰,徒靠册字上讲明义理,而无实得者,终不见受用,得之于心,口若难言,学者不以能言为贵。”②李甦平教授在其著作《韩国儒学史》中认为,虽然曹植与李滉都对朝鲜朝儒学作出了贡献,但贡献点却不尽相同。李退溪主要是在性理学方面深化、发展了朱子学说,从而奠定了他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显赫地位。而曹南冥则强调原典儒学的“敬义”和实践精神,遂自成一家之学而与退溪并峙。曹植为学以“敬义”标宗,其学一言蔽之就是“敬义”学。“敬义”在南冥学的体系中既是体(他以敬义为“心体”)也是用(他同样以敬义为工夫)。“敬义”由是贯穿三才、融通天人,达于真善美的统一。这是曹植“敬义”思想的基本要点。③
曹植以为“程朱以后不必著书”,只需反躬体验、持敬实行即可。他对现实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曾师事于曹南冥和李退溪的寒冈郑逑(字道可、可父,号寒冈、桧渊野人,1543—1620年)说过:“先生之于道义,亦可谓辛苦而后得之者矣。先生平生,未尝一念不在于世道。至于苍生愁苦之状,军国颠危之势,未尝不嘘唏掩抑。至或私自经画处置于胸中,而以为必先提掇于纪纲本源之地,则初非不屑夫天下之事者,怀德遯世,高洁自守,终世婆娑于穷山空谷之中。”④其主要学术著作有《南冥集》、《学记类编》等。其中《学记类编》分为上、下二卷。上卷又分“论道之统体”和“为学之要”两部分,并绘有二十二个图式加以阐释。下卷则列出儒者为学践行之法门,有“致知”、“存养”、“力行”、“克己”、“出处”、“治道”、“治法”、“临政处事”、“辟异端”等条目并附录两个图式。此二十四图便是与李退溪《圣学十图》齐名的南冥的《学记图》。
《学记图》最能体现曹植的学术思想。用图说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不仅是曹植的特点,也是朝鲜朝儒家学者的共同特色。韩国的图说可以追溯到朝鲜初期权阳村的《入学图说》。后来还相继出现过郑秋恋和李退溪合作的《天命图说》、李退溪的《圣学十图》、李栗谷的《心性情图》和《人心道心图说》等。以“图”示“说”,以“说”释“图”,二者之结合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曹植二十四图亦是如此。
关于《学记图》,有学者认为其中十幅最为重要,即“三才一太极图”、“太极图与通书表里图”、“天人一理图”(“天道图”和“天命图”)、“心统性情图”、“忠恕图”(“忠恕—贯图”)、“敬诚图”(“敬”图和“诚”图)、“审几图”(“几图”)、“为学次序图”(“小学”、“大学”图)、“博约图”和“易书学庸语孟一道图”。之所以推重此十图,乃因其表达了曹植的本体论思想。其实若从曹植的思想主旨来看,二十四图中最重要的十图应是“敬图”,“小学、大学图”,“诚图”,“人心、道心图”,“博约图”,“知言、养气图”,“易书学庸语孟一道图”,“心为严师图”,“几图”和“神明舍图”。因为曹植论学的最大特点就在“敬义”和“力行”。①不过,有人指出这十图中“忠恕图”(“忠恕—贯图”)、“博约图”并非曹植的“自图”。②尽管如此,二十四图仍被普遍视为“南冥学”的精髓,由此可理解和把握其为学之特色。
曹植虽与李滉同为岭南儒林之师表,但是李滉对其学术常表不满,曾评论说:“南冥虽以理学自负,然直是奇士,其议论识见每以新奇为高务,为惊世之论,是岂真知道理者哉。”③对于两人为学风格及思想特点,朝鲜朝后期的实学大家星湖李瀷(字子新,号星湖,1681—1763年)从其实学之视角指出:“檀君之世,鸿蒙未判,历千有余年,至箕子东封,天荒始破,不及于汉水以南。历九百余年至三韩,地纪尽辟为三国之幅员,历千有余年,圣朝建极,人文始阐。中世以后,退溪生于小白之下,南冥生于头流之东。皆岭南之地,上道尚‘仁’,下道主‘义’,儒化气节如海阔山高,于是乎文明之极矣。余生两贤之后,犹是文未坠地自此,以后如下滩之船其势难住,不知更有几重激湍坎窞在也。后来者,必将企余而起羡。”①的确如此,李滉崇“仁”,以高迈之学行潜心著书,弘阐天道性理;而曹植慕“义”,以刚毅之气节反躬践履,化导社会人心。
继踵乏人是南冥学派终为退溪学派所取代的重要原因。对此泽堂李植(字汝固,号泽堂、泽癯居士,1584—1647年)评论道:
岭南则退溪、南冥门脉颇异。退溪门下,西厓、鹤峰、柏潭最有名。而仕宦出入,不复讲学。吴德溪健,学行最高,游于两先生门,早卒无传。赵月川闲退老寿,而士心不附,亦无弟子。曹植高弟,寒冈、东冈为最,而声价皆不及郑仁弘。两冈兼宗退溪,故稍贰于仁弘。仁弘之恶,不待其诛戮而日彰,其门徒皆陷于梼杌,由是岭之下道,亦无学者,唯寒冈为完人。旅轩为高弟,旅轩殁,而亦无徒弟传述者,岭南之学亦止于是。湖南则上道,有李一斋;下道,有奇高峰。高峰早世,不及讲学。一斋弟子虽众,惟金公千镒,以节义著,学则无传焉。郑汝立出于其后,与李泼、郑介清,相应和雄豪一道,为无赖渊薮。及其叛乱,混被诛戮,湖俗浮薄,本不喜儒学,及汝立败,而人以为嚆矢,湖南学者,从此尽矣。②
文中泽堂对李滉、南冥学派的传承脉络作了概要式的说明,有助于我们了解岭南学派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流变状况。兼宗李滉和曹植的郑逑在其《寒冈年谱》(卷一,庚辰38岁)中,也有对于二人为学之异颇有议论。依郑逑之见,李滉德器浑厚,践履笃实,工夫纯熟,阶级分明,学者易于寻入;而曹植则器局峻整,才气豪迈,超然自得,特立独行,学者难以为受。
对于曹植之贡献,郑仁弘(字德远,号来庵,1535—1623年)推崇备至。他在《南冥先生集序》中写道:“惟我先生,早志腾扬,喜读左柳,有躏一世轶千古之气,旋自大悟,一弃旧学,回车易辙,特立独行,凭河不足以为勇,摧山不足喻其力,一向藏修,箴铭〓佩,揭扁堂室,雷龙有舍,鸡伏有堂。其精舍曰山天,壁栖敬义字,亹亹观省,所识者,前言也,往行也。所急者,向里也,践履也。日复一日,终始无间,其涵养之力,造诣之功,盖有不可量者。而当士林斩伐之余,士习偷靡,醉梦成风,人视道学,不啻如大市中平天冠。而先生奋起不顾,竖立万仞,使士风既偷而稍新,道学既蚀而复明。扶颓拯溺之功,在我东国,宜亦未有也。”①经历“己卯士祸”洗礼后整个士林士气低落,此时正是曹植接续“己卯士祸”之前的士林学风加以传扬,开启了为学必以自得为贵、反躬实践为特色的实践儒学传统。
要之,岭南学派的关注点是重振颓坏之社会纲纪,以确立伦理纲常,从而实现儒家所向往的王道社会。因而在性理学上自然倾向主理论,这就是理先气后论、理优位论以及理主气辅论皆出自岭南学脉之缘由。
第一节 金时习的太极论
金时习(1435—1493年)是朝鲜朝性理学家、文学家,在“生六臣”①中最为著名。他字悦卿,号梅月堂、东峰,生于江陵。金氏自幼聪慧,5岁便能读书缀文,13岁师事经学大家金泮、尹祥习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21岁皈依佛门出家,后还俗娶妻。其妻死后,复又还山,于成宗二十四年卒于鸿山无量寺。
一、太极说
太极说是金时习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太极”乃朱子学的核心概念,直接关系到对朱子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朱子曾说过:“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①太极只是理,未有天地,先有此理——“理”的在先并非时空意义上的先后,而是逻辑意义上的在先。
在韩国哲学史上,金时习是最早对“太极”问题进行论述的学者。他在《太极说》中写道:
太极者,无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谓之太极,别有极则非极也。极者,至极之要,理之至极,而不可加也。太者,包容之义,道之至大,而不可侔也。②
金氏以为并非“太极”之外另有“无极”。“太极”即是“理之至极”,乃事物存在的根据和最高原理。他进一步解释道:“阴阳外别有太极,则不能阴阳;太极里别有阴阳,则不可曰太极。阴而阳,阳而阴,动而静,静而动,其理之无极者,太极也。其气则动静辟阖而阴阳,其性则元亨而利贞也,其情则阴惨而阳舒也,其用则天地以之圆方。元气以之发育,万物以之遂性。其性之正者,太极之为阴阳也。”③可见,梅月堂将“太极”视为主宰“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之“理”。他在著作中对“理之主宰性”详细加以说明:
天地之间,生生不穷者道也,聚散往来者,理之气也。有聚故有散之名,有来故有往之名,有生故有死之名。名者,气之实事也。气之聚者,生而为人。人者,理之具而著者也。故有心焉。④
若夫寒暑往来,日月代明,昼夜之道,则此理之自然,气之所以为气,而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①
金时习将气之聚散、往来,即“生生不穷者道”视为理之主宰性所致。可见,他以“太极”为主宰气之运动的“所以然”之理。也有些学者主张,梅月堂是“唯气论者”或“气一元论者”。②有时他的言论确有类似倾向,比如说过“天地之间,惟一气橐籥耳”③等。
然此等言论是基于金时习“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④的思想。换言之,是基于金时习以气之聚散、往来来说明万物之生成的思想。这是仅将“理”视为气之运动法则的结果。不过,金时习同时也肯定理对气之主宰性,而且还强调理、气之区别。他曾讲过:“才有理,便有气。”⑤故其所言“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应理解为对“理气不离”的强调。梅月堂的理气二元论思想意在阐明理气之“造化”及其“相即不离”。
同时他还将“理”表述为“公共之理”。“天之生民,各与以性。性即理也,不谓之理,而谓之性者,理是泛言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在我之理,未尝不善。如父子有亲之理,以至朋友有信之理,便是人之性。如牛耕马驰,鸡司晨,犬护主,草木昆虫,各有形质,好恶不同,便是物之理,然而其源则一也。故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⑥此“公共之理”即为“理一”,所以万物皆与我为一体;同时“理”又是“分殊之理”,故天之生民必以性理,草木昆虫亦各有其物理。可见,金时习对“理”的认识大体接续朱子学说而来。
此外,梅月堂将人的“性理”阐发为“实理”。众所周知,“性即理”是程朱理学的基本命题,但是在具体的解释上每位理学家的视角各有不同。对于性理,梅月堂是这样认识的:
性与理,都无两般。先儒云,性即理也。天所命,人所受,而实理之具于吾心者也,盖初非有物。但是仁义礼智之在我,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尧舜,涂人,初无少异。惟气质有清浊粹驳之不齐,不能皆全,故汨于人欲而失之,谓之众人。无私欲之蔽而能尽其性,谓之圣人,其实未尝有殊也。子思之言天命,孟子之言性善者是也。彼告子之言生,荀子之言恶,杨子之言混,韩子之论三,释氏之作用,皆以气而遗其理也。①
道德与性理异乎?曰,无以异也。夫道者,性理之极处,初非有他歧可说。②
将“性理”理解为“实理”,即“天所命,人所受,而实理之具于吾心者”,此为朝鲜朝后期实学派的实心实理说的肇端。梅月堂之说既有助于防范性理的抽象化和空洞化,又有益于增强性理学家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在他看来,循此仁之性(实理)则可以自父子之亲以达至仁民爱物。
二、道佛观
梅月堂对佛、道也多持批判的态度。他曾以孟子“存心养性”之思想为依据批驳佛教“观心见性”说。“如浮屠氏观心则不可,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岂可以吾心观吾心。若云可观,心应有二。”③在此,他还阐述了自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理解,曰:“或问先圣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岂非二乎。曰,所谓人心者,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道心,源于性命之正,天理之公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遂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人欲卒无以胜夫天理之公矣。岂有但观而已乎。”④“道心为主,人心听命”,这是朱子人道说的主要观点。但是,将“人心”简单理解为“人欲之私”却有待斟酌。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韩国性理学尚处于理论建构阶段,仍需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金时习对道家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彼老氏者,体道而非率性之道。论德而非明命之德,则如之何其泽于世,垂于后也。”①老氏之学虽然也可称为已悟“道”本,但是其“道”并不是儒家所言“率性之道”,而其“德”亦非儒家所谓“明命之德”。因此,老氏之说就难以“泽于世,垂于后”。
在论述儒道两家之异时,梅月堂还提出“志为帅之气”的思想。他曾说过:“在圣人之道则不然。论养气,不论服气,盖在心为志,志发为气。志,气之帅也。”②这与郑道传、权近等人主张的“志帅气卒”的思想一脉相承。
由上所述,金时习是对儒释道的义理都有较深切体会的朝鲜朝初期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因而后人对其思想的学派属性也多有争论。退溪李滉即称其为“一种异人”。他评论道:“[篈]世人以金梅月之披缁,为不足观。在篈之意,以为梅月遯世一节,固未合于中庸之道。然而身中清,废中权,如此看则何如。[滉]梅月别是一种异人,近于索隐行怪之徒。而所值之世适然,遂成其高节耳。观其与柳襄阳(柳襄阳:本名,柳子汉,因曾任襄阳府使,故被称为“柳襄阳”——引者注)书,金鳌新话之类,恐不可太以高见远识许之也。”③而栗谷李珥则称梅月堂为“横谈竖论,多不失儒家宗旨。至如禅道二家,亦见大意”④。朝鲜朝中期著名性理学家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尤斋,谥号文正,1607—1689年)则在《梅月堂画像跋》中对其评论道:“其髭须虽在,而冠服则正缁流所著也。余尝按栗谷先生奉教所撰公传,公少为儒生,中为缁流,晚尝长发归正,临终时更为头陀像,盖三变其形矣,独乃留此缁像而自赞焉者,岂亦有意存乎其间耶。盖公出家放迹,实欲藏晦其身。然百世之下,见其气象精神于片幅之上者,犹知其为梅月公矣。”①但是,通过其性理说的分析可以看出,李珥在《金时习传》中“心儒迹佛”的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李珥写道:“自以声名早盛,而一朝逃世,心儒迹佛。取怪于时,乃故作狂易之态,以掩其实。士子有欲受学者,则逆击以木石,或弯弓将射,以试其诚。”②
概而言之,梅月堂的性理学思想肯定理对气的主宰性,但同时也强调二者之分别,所谓“才有理,便有气”。所以对其“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的思想应理解为对理气不离的重视。金时习的理气二元论思想强调理气之“造化”及其“相即不离”。梅月堂之学虽然在体系化方面有所不足,对朱子学的理解程度亦有欠缺,但是基本上还是笃守了朱子学的基本立场。金时习思想与李彦迪(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1491—1553年)对太极主理性的论述有所不同,却从“理气一体”、“理气造化”的角度解释“太极之理”的主宰性,由此开启了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无极太极论辩之先河。同时在他的学说中,还可以看到赵光祖道学思想的萌芽以及退溪李滉、栗谷李珥等人的性理学的端绪。
梅月堂金时习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说》、《生死说》、《神鬼说》、《易说》等,现均收录在《梅月堂集》(24卷)中。
第二节 赵光祖的道学论
朝鲜建国初期朝政由“事功派”(郑道传、权近等人)主导,他们以性理学(朱子学)为建国理念,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王朝建立后的短暂的繁荣期。但是随着李氏王朝的建立,退隐山林、远离政治争斗的“义理派”士人却并未完全退出社会政治的舞台。从世宗朝开始,他们逐渐重返朝政,对勋旧势力的腐败弊政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这一派继承圃隐郑梦周义理思想之衣钵,大体包括吉再、金叔滋、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人。与之同气相求的还有反对世祖篡位的“生六臣”、“死六臣”等节义派,他们都是继承圃隐郑梦周学脉的士林派学者。
中宗、明宗朝年间频发的“士祸”①,使大多数儒者逐渐远离现实政治,转而沉潜于对儒学义理问题之探究。于是,韩国士大夫们形成一股研究性理学义理的风潮。同时,这一时期性理学的“道学化”也得到加速发展。其实,15世纪中叶之前性理学的“道学化”现象已开始出现,掀起“道学化”思潮的正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林派学者。他们在至治主义思想的旗帜下试图彻底实现“大义(春秋大义)”,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道学思想正是支撑这些“士林派学者良心”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②本节将论述作为士林派学者翘楚的赵光祖的道学思想。
一、至治主义
赵光祖(1482—1519年),字孝直,号静庵,谥号文正,是朝鲜朝前期著名性理学家。他是士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金宏弼的高足。作为汉阳人,光祖出生于官僚两班世家。中宗五年(1510年)参加“春中进士会试”,中生员,入太学。中宗十年(1515年)又应谒圣别试以乙科状元及第,之后历任典籍监察、副提学、元子辅养官、大司宪等官职,从而确立了其朝鲜朝前期士林领袖之地位。后因遭勋旧势力的诬陷,在“己卯士祸”①中被中宗赐死。
赵光祖以“崇道学、正人心、法圣贤、兴至治”②为目标,热衷于“国是”之确立。他主张革弊扶新的社会改革,积极倡导至治主义,聚集了一批年轻士大夫反对勋旧派的专横。赵氏以为士大夫为学第一要务便是为生民而行道。他曾说过:“士生于世,业为学问者,冀得展其怀抱,有补于生民耳。孟子以亚圣,历聘齐、梁,岂有他意乎。但欲行其道而已。后世士子之事,自私而已。臣等面对六七度,徒以口舌,欲感君上,此特末耳。但君为君道,臣为臣道,则朝廷清而治道成矣。”③依其之见,君主若能“以道惟一”则德无不明,“治惟纯”则国无不理。但是,君主若不能“以道惟一”则德灭而国亡。他说:
伏以道惟一,而德无不明;治惟纯,而国无不理。不一乎道,不纯乎治,则二而暗,杂而乱。一纯二杂,罔不原乎是心,故正厥原,通微溥显,克一其居,而政化惟纯,德着而国昌。迷厥原,炽柱沈阘,二三其守,而政化乃杂,德灭而国亡。④
可见,“以道惟一”的“弘道”思想是赵氏道学的核心理念。他主张为了“弘道”,志士仁人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实现社会正义。那么其心目中的“道”又是何物呢?“夫道也者,本乎天,而依之于人,行之于事为之间,以为治国之方也。”①又曰:“夫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夫子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万物之多,莫不从此道而遂,天地之心,阴阳之感,亦莫不由此心而和。阴阳和,万物遂而后,无一物不成就于其间,而井井焉有别。”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③是孔子的主张,其要义是说人应有弘道的主观能动性。④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而仁又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所以说以人之理合于人之身才是道。赵光祖说:
天与人本乎一,而天未尝无其理于人。君与民本乎一,而君未尝无其道于民。故古之圣人以天地之大,兆民之众为一己,而观其理而处其道。观之以理,故负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处之以道,故凝精粗之体,领彝伦之节。是以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无所得逃于吾之心。而天下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万化之所以立,治道之所以成也。虽然道非心,无所依而立,心非诚,亦无所赖而行,为人主者,苟以观天理而处其道,由其诚而行其事,于为国乎何难。恭惟主上殿下,以干健坤顺之德,孜孜不息,出治之心既诚,为治之道已立。犹虑夫纪纲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其于尊礼先圣之余,进策臣等于泮宫,先之以先圣之事,遂及欲复隆古之治。⑤
对“天人一体”之道心的重视是赵光祖道学思想的根本精神。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是欲在李朝实现唐虞三代之治。因此,赵光祖要求学者为学当以圣贤自期,人主为政当以实现三代之治为期:“学者以圣贤为期,未必即至圣贤之域,人主以唐虞三代为期,未必即致唐虞三代之治。然立志如此,而用功于格致诚正,则渐至于圣贤之域,尧舜之治矣。若徒骛高远,而不下实功,则日趋浮虚之地而已……人君亦必以最贤者为师,次者为友,尊礼之,可也。”①在他看来,孔子之道只是与心相通之天理。学者只要“敬守此心”,对越上帝,就可以不背夫子之道。所谓“敬守此心”便是以诚心守道。
于是,赵光祖将心的“诚未诚”,视为天人离合、社会治乱之根据。他说:
然而所谓心、所谓道者,未尝不一于其间。而千万人事之虽殊,而其道心之所以为一者,天本一理而已。故以共天下之道,导与我为一之人,以共天下之心,感与我为一之心。感之而化其心,则天下之心化于吾心之正,莫敢不一于正。导之而导于吾道,则天下之人,善于吾道之大,莫敢不归于善。顾吾之道与心,诚未诚如何,而治乱分矣。②
他的至治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要求道德主体的自我省察和积极践履。而人主是否诚心守道最为关键。“所以治国者,道而已。所谓道者,率性之谓也。盖性无不有,故道无不在。大而礼乐刑政,小而制度文为,不假人力之为,而莫不各有当然之理,是乃古今帝王所共由为治;而充塞天地,贯彻古今,而实未尝外乎吾心之内;循之则国治,失之则国乱,不可须臾之可离也。是以使其此道之体,了然于心目之间,不敢有须臾之不明也。”③赵氏是朝鲜朝道学精神的确立者④。在他看来,治国即循道,若治国者离经叛道则国必乱。这就要求人君正心诚意、持敬慎独,先养己德,而后推之于行事。又说:
古云:至诚感神。又曰:不诚无物。君之遇臣,臣之事君,皆以诚实,则治化可期其成也。我国地方褊小,人君发一言,则八道之人,一朝皆得闻知。惟当于大臣则敬之,于群臣则体之,百工则来之,庶民则子之。患吾之所以遇臣爱民者有未诚耳,不患其难化也。后世治道渐下,不能复古者,盖以后世之君,无有真如古昔帝王故也。今之言者曰,欲复古之治道,徒为变乱旧章而已。此由知识庸下,直以所见为言也。近来士气稍稍振起,民之趋向,亦渐好矣。惟愿自上日加慎独诚实工夫,终始不渝,则治化可臻矣。若使世道,日渐污下,终不可变,则人道终归于禽兽矣。三代之治,今可复致者,虽不可易言,岂全无致之之道乎。自上先养己德,推之行事,则人皆诚服,不期化而自化矣。若吾德不修,而修饰于事为之间,则亦何益乎。须敦厚其德,使万化自明德中流出,则下民自然观瞻欣感,有不能已者矣。又非但拱手以守其德而已,必以礼乐刑政,提撕警觉,布置施设,如有可为之事,当振奋而力行也。①
赵光祖以为人主苟能遵道循理、以诚行事,则士气可振,治化可期,于为国亦无难事。作为当朝士林领袖,他将中宗朝(1506—1544年)视为实现理想政治的难得时机。在任副提学时,他曾向中宗进言道:“人主学问,非止澄明一心而已,当见诸施为之际。今者,圣学已至高明。若失此机,后不可图。”②赵光祖认为世宗朝(1419—1450年)是李氏王朝建立之后最为理想的时期,但“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使成宗朝(1470—1494年)刚刚培育起来的士气扫地以尽。他欲趁中宗即位之机重振士气,为朝鲜“立万世不拔之基”。赵氏言曰:“我国世宗朝,礼乐文物,制度施为,髣髴乎周时。而至于废朝初年,成宗梓宫,在殡未久,而宫中所为,已可寒心,惟其一身,不能善饬,故士大夫皆失恒心,终至迷乱而莫救。赖祖宗德泽深厚,浃于民心,故圣上即位之后,人心庶几向善,而然其旧染污俗,难可猝新也。当此机会,不正士习,不厚民生,不立万世不拔之基,则圣子神孙,将何所取法乎。自古欲治而不能善治者,必有小人喜为谗间生事故也。臣谓圣学,日进于高明,而又推诚以待大臣,则大臣不敢以杂语。陈于上前,而必尽心于国事矣。国事不出于大臣,则上下违咈不顺,而无以致治矣。”①朝鲜从15世纪末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勋旧派和士林派两大政治势力。二者围绕着土地和政权展开激烈的争斗,给朝鲜社会造成重大损失。士林派基于维护中小地主之利益的立场出发,极力谴责勋旧大臣土地兼并,他们传播程朱之学,宣扬事君以忠的节义精神。勋旧派则视士林派为“野生贵族”,每每伺机对其进行报复打压。从世祖(1455—1468年)时起,至16世纪60年代,大小“士祸”接连不断,其间多有流血事件。均以士林派的被害而告终,史称“士祸”。在“甲子士祸”中,赵光祖的恩师寒暄堂金宏弼(1454—1504年)亦遭到迫害。1545年(乙巳年)士林派又受尹元衡一派的打击,这就是“乙巳士祸”。1565年尹元衡一派被驱逐,士林派随之重回政治舞台,势力开始空前膨胀。中央政权遂为清一色的士林派所掌控。
二、性理说
15世纪的韩国因经历丽朝两朝更替和社会动荡,士林的士气有所受挫。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逐渐稳定,以冶隐吉再学统所代表的“义理”精神开始风靡半岛,继承其学统的士大夫试图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此一动向反映在15世纪末叶出现的“小学修身派”身上。此派以金宗直、金宏弼、金安国(号慕斋,1478—1543年)为代表,欲由高扬冶隐吉再以培育士林的“义理”精神。至16世纪初已成功在经延讲授“小学”。这表明他们的关注点已从个人修身之范围扩大至社会政治领域,在此过程中“心”的意义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以赵光祖为代表的至治主义则更是从“心”上寻找修身之依据。
赵光祖生活于朝鲜朝“士祸”期,所以强调为学应兼顾“学问”与“治道”,二者不可偏废。“虽曰存心于学问治道,而一有所嗜好,则所向不能专一矣。大抵心无二用,向善则背恶矣,夫文与书,可谓一事,而习文者,不暇于习书,理固然也,若意诚心正之功,到十分尽处,则可保无虞矣,不然则嗜好之害,不可不虑也。”②由此可见,他的道学思想所追求的是道德与政治、致知与践行的高度协调与统一,而重点则在于“实功”。
赵光祖的性理学说具有贵理贱气之“主理”论倾向。“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而“仁”则为理在人性上的显现。他曾说过:“理不为气所动……因论理气之分曰:理为主而气为理之所使,则可矣。”①又说:“春者,天之元也。四时自春而始,四端自仁而发。无春序不成,无仁不遂。”②光祖将“仁”比之于“春”,以为四季的流行自“春”而始,而人伦亦以“仁”为始端,这样便赋予“仁”以流行发育的功能,从而与天道合一。“虽天人之似殊兮,理在仁而靡爽,然则春于天,仁之于人,同一春也。”③他构筑了一个天人相贯、天人同理的“理一元”论性理哲学体系。在人性论上,主张人性是天理的体现,“性”与“理”同而不悖。静庵以为:“性无不善而气禀不齐,人之气不善,气之使然也。”④他又说过:“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义礼智之德。天理岂有恶哉,但为气禀所拘,故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厉猛,义之差也;谄谀过恭,礼之差也;奸谲诡诈,智之差也。理惟微而气易乘,故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⑤赵光祖对“心”非常重视,以为“心是活物,若有感而动”⑥,他的性理学说特别强调对“心”施以检束的修养工夫的必要性。“整齐严肃,则自然主一无适,而应物精当,言动中礼矣。常人之不能若此者,不能齐肃故也,此是圣学之始终,而形容之极难,必于心地惺惺,无昏杂懈弛之时,可见矣。故先儒以主一无适为言,夫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者,乃不昏惰之工夫也。”⑦他在继承朱子学的“诚”、“敬”工夫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持敬”、“去欲”修养方法。尽管士林学派学者很少论及认识论问题,赵光祖还是在强调“学以致用”的同时言及这些问题。他说:“大抵耳、目、鼻、声、色、臭味之欲,无非以气而出也。”①
作为道学政治的积极倡导者,静庵认为实践圣贤之学以复尧舜之治的关键就在于人主的正心诚意,所谓“道非心无所依而立,心非诚亦无所赖而行”。一生以行道为己任的赵光祖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阐发了“保民”、“泽民”等王道政治思想,还在执政期间提出诸多改革世弊的合理性方案。
简言之,赵光祖道学精神之主旨是由仁政实现儒家至治主义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严辨王霸义利,反对霸权政治,试图以存天理遏人欲来重塑社会纲常,从而构建一个充满正义的李朝社会。这正是儒家王道政治之理想。
静庵在其《戒心箴序》中写道:
人之于天地,禀刚柔以形,受健顺以性,气则四时,而心乃四德也,故气之大浩然无所不包,心之灵妙然无所不通。况人君一心,体天之大,天地之气,万物之理,皆包在吾心运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顺吾度,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谓灵妙者沈焉,梏于情私,不能流通。天理晦冥,气亦否屯,彝伦〓,而万物不遂。况人君声色臭味之诱,日凑于前,而势之高亢,又易骄欤。②
从以上引文可以一窥其诚实的人格和笃实的为学。这里需注意的是他对理气心性问题的阐释。静庵认为气之大浩然无所不包,心之灵妙然无所不通,天地之气、万物之理皆包在吾心运用之中。将理气摄于“心”来讨论不仅是静庵道学思想的特色,而且还是韩国重视人间性理之学术传统的发端。正是赵光祖理气论研究的路向转换成为日后李滉、李珥等人“四七理气”之辨的嚆矢。可见,肇始于圃隐郑梦周的义理派学术,传至静庵赵光祖已达新的理论高度。
后世学者对赵光祖多有称道,宋时烈即将其拟于宋代濂溪。时烈尝言:“余以为先生之生于我东者,实如濂溪之于宋朝也。岂必授受次第如贯珠,然后乃为道学之传哉。”①同为士林派学者的白仁杰(字士伟,号休菴,1497—1579年)则称美他说:“其丕阐绝学之功,优于郑梦周、金宏弼远矣。”②奇大升也赞道:“以东方学问相传之次而言之,则以梦周为东方理学之祖……金宗直学于叔滋,金宏弼学于宗直,而赵光祖学于宏弼,继其渊源之正,得其明诚之实,蔚然尤盛矣。”③号称朝鲜朝朱子学双璧之一的李滉同样对他推崇备至:“盖我东国先正之于道学,虽有不待文王而兴者,然其归终在于节义章句文词之间,求其专事为己,真实践履为学者惟寒暄为然。先生(指赵光祖——引者注)乃能当乱世冒险难而师事之,虽其当日讲论授受之旨,有不可得而闻者,观先生后来向道之诚,志业之卓如彼,其发端寔在于此矣。”④由此可见,至赵光祖朝鲜朝道学的义理思想已初具规模。
不过,最为推崇静庵赵光祖的还是李珥。李珥对静庵在李朝儒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作用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问:我朝学问,亦始于何代?曰:自前朝末始矣。权近入学图似龃龉,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视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至退陶先生,儒者模样已成矣。”⑤可见,尽管李珥承认朝鲜朝的理学传统由郑梦周始发其端,但是认为圃隐只是安社稷之臣,且其学又“规矩不精”,尚难称为儒者。只有赵光祖才是朝鲜朝性理学传统的真正始祖。李珥说过:“我国理学无传,前朝郑梦周始发其端,而规矩不精,我朝金宏弼接其绪,而犹未大著,及光祖倡道,学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学者,光祖之力也。”⑥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初,学者大多专注于功名和词章训诂,并未对道学的义理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直至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士林派学者出现后,道学研究才被引向义理探究之路。尤其是赵光祖以一己之力将道学研究推向了经世济国之实践性理学的轨道。①他的至治主义思想,后为李珥等人继承和发扬,不仅影响了朝鲜朝后期性理学的发展,而且还在韩国思想史上掀起了绵延几百年的实学思潮之狂飙。赵光祖的主要著作有《静庵集》(5卷)。
第三节 徐敬德的气本论
朝鲜朝开国百余年之后,朱子学发展终于迎来了鼎盛时期。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接连涌现出多位颇有理论建树的硕学鸿儒,如徐敬德、李彦迪、曹植(字楗仲,号南冥,1501—1572年)、李滉、奇大升、李珥、成浑等人。这一性理学家群体在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以及近世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节拟对徐敬德的哲学思想作些简要的论述。
一、太虚说
徐敬德(1489—1546年),字可久,号花潭、复斋,谥号文康。徐氏既是朝鲜朝前期代表性的性理学家之一,又是气本论哲学的理论先驱,世称“花潭先生”。他是开城府人,平生为学最得《大学》“格物致知”之旨。据《年谱》记载,徐氏18岁时当读《大学》至致知在格物一节,便慨然叹道:“为学而不先格物,读书安用?”②徐敬德志行甚高,不喜举业,曾卜筑精舍于开城五冠山下的花潭边,潜心道义,专以穷格为事,以此终其一生。他曾在一首《述怀》诗中吟道:
读书当日志经纶,晚岁还甘颜氏贫。
富贵有争难下手,林泉无禁可安身。
采山钓水堪充腹,咏月吟风足畅神。
学到不疑知快活,免教虚作百年人。①
隐居松都(开城)的花潭潜心治学,安贫乐道,其不拘形迹、狂放自适的形象由诗作跃然纸上。这首诗可视为其守道笃学之生平的真实写照。
徐敬德虽然其为学不尊朱子而多从邵雍和张载之说②,但是其所建构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在韩国儒学史上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李珥曾评论说:“敬德则深思远旨,多有自得之妙,非文字言语之学也。”③
关于“虚空与气”,张载论述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也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之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④他以为,气之本体乃无形的太虚,正是气的聚散形成万物与太虚。太虚、气和万物可谓同一实体的不同存在状态,这是张载气本论思想的立论基础。横渠的气一元学说不仅将中国古代哲学的气论思维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还促进了东亚儒家文化圈气论思想的深入发展。
作为韩国气学派的理论先驱,徐敬德确如李珥所言极重精思自得,其学说亦确有“自得之妙”。他不仅主张世界由“气”构成,而且还提出了独特的先后天理论。
首先,徐敬德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以为一切皆为“气之聚散而已”。他曾说过:“吾亦曰:‘死生人鬼,只是气之聚散而已’。”⑤还说过:“一气之分,为阴阳。阳极其鼓而为天,阴极其聚而为地,阳鼓之极,结其精者为日,阴聚之极,结其精者为月,余精之散为星辰,其在地为水火焉。”①在花潭看来,天地万物归根结底皆是先天之太虚。正是气的鼓、聚、凝、散之运动产生了千变万化的物质现象。因此,气的运动才是这包罗万象的世界的普遍本质,所以他以气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
其次,徐敬德将“气”之性质规定为“湛然虚静”,所谓“其湛然虚静,气之原也”②。他进而指出:“有聚散而无有无,气之本体然矣。气之湛一清虚者,弥漫无外之虚。聚之大者为天地,聚之小者为万物。聚散之势,有微著久速耳。大小之聚散于太虚,以大小有殊。虽一草一木之微者,其气终亦不散。况人之精神知觉,聚之大且久者哉!形魄见其有散,似归于尽没于无。”③依徐氏之见,气之本体“有聚散而无有无”。由此可知,其所言“湛一清虚”之气乃超时空之永恒存有物。他以气本论思想为基础对气之聚散运动给出自己的解释:即气之“聚”生成大千世界,“散”则还原为气;易言之,具体的事物只是“浮现一气中”而已。所以气虽看不见、摸不着,却作为实实在在的存有充塞着整个宇宙。徐敬德以为气“弥漫无外之远,逼塞充实,无有空阙、无一毫可容间也。然挹之则虚,执之则无,然而却实,不得谓之无也”④。
再次,在“太虚”与“气”的关系上,徐敬德相信因“虚静即气之体”,故太虚既无终始亦无穷尽。他说:“无外曰太虚,无始者曰气,虚即气也。虚本无穷,气亦无穷。气之源,其初一也。既曰气一,便涵二;太虚为一,其中涵二。既二也,斯不能无阖辟、无动静、无生克也。”⑤文中从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上对“太虚”与“气”作出了解释:太虚为“无外”,气为“无始”,二者皆无穷。花潭还指出二者初皆为“一”,但以其中涵“二”遂有事物的运动变化。“太虚,虚而不虚,虚则气。虚无穷无外,气亦无穷无外。既曰虚,安得谓之气?曰虚静,即气之体;聚散,其用也。知虚之不为虚,则不得谓之无。老氏曰:‘有生于无’,不知虚即气也。又曰:‘虚能生气。’非也。若曰:‘虚生气’,则方其末生,是无有气而虚为死也。既无有气,又何自而生?无始也,无生也。既无始,何所终?既无生,何所灭?老氏言虚无,佛氏言寂灭,是不识理气之源,又乌得知道。”①这里徐敬德对“太虚”和“气”的内涵、功用皆作了说明:太虚虚而不虚,虚即为“气”;“气”有体用,以虚静为体,而以聚散为用。引文中他在阐述其“太虚”说的同时,还指出了其与佛、老之寂灭虚无的本质区别。“有生于无”出自《老子》第四十章②,“虚能生气”亦与道家“有生于无”不无关系。对此,张横渠批判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③从徐敬德“虚静即气之体”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儒家气论与佛、老之学的本质区别。
二、先天说
徐敬德在论述“太虚”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先天说”:“太虚湛然无形,号之曰先天,其大无外,其先无始,其来不可究,其湛然虚静,气之原也。”④这就是其独特的“先天说”。从引文中可以概见,所谓“太虚”有三层含义:一太虚为世界的本原;二太虚(气)既无形迹亦无终始;三太虚即气。由此,徐敬德在韩国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气不灭”论。“虽一片香烛之气,见其有散于目前,其余气终亦不散,乌得谓之尽于无耶。”⑤举此实例的目的在于说明,气的存在形态虽从有变无也无损其根本属性,此为其“气不灭”论的基本主张。
接着,徐敬德进一步阐发气之“后天说”:
倏尔跃,忽尔辟,孰使之乎?自能尔也,亦自不得不尔,是谓理之时也。《易》所谓“感而遂通”,《庸》所谓“道自道”,周所谓“太极动而生阳”者也。不能无动静,无阖辟,其何故哉?机自尔也。既曰一气,一自含二;既曰太一,一便涵二。一不得不生二,二自能生克。生则克,克则生。气之自微以至鼓荡,其生克使之也。一生二。二者何谓也?阴阳也,动静也,亦曰坎离也。一者何谓也?阴阳之始,坎离之体,湛然为一者也。一气之分,为阴阳。阳极其鼓而为天,阴极其聚而为地。阳鼓之极,结其精者为日;阴聚之极,结其精者为月。余精之散为星辰,其在地为水火焉。是谓之后天,乃用事者也。①
徐敬德以先天、后天来说明本体界和现象界:气未用事时湛然虚静之状态谓之“先天”;气用事后变现之现象谓之“后天”。在太虚与气之聚散等问题的论述中,明显可见张载思想对他的影响。敬德门人朴淳(字和叔,号思庵,1523—1589年)就曾说过花潭所见得颇受张子《太和》等篇的影响。②同时,朴淳也充分肯定了徐敬德对张载气论的发展,指出:“张子所论‘清虚一大’,此穷源反本,前圣所未发也。花潭又推张子之未尽言者,极言竭论,可谓极高明也。”③朴淳虽为敬德的弟子,但与成浑、李珥等皆交好,故而学风较为开放。他讲“花潭又推张子之未尽言者,极言竭论”,可说是公允之言。
三、“二化一妙”论
如何解答“气”与“理”的关系,这是气论中十分重要的课题。为此,徐敬德特撰《理气说》一文,阐明其对理气问题的看法。在理学的首要问题理气先后上,徐氏基于“气为本”的思想,主张“理不先于气”。这是因为气无其始,所以理亦无其始。他说:
原其所以能阖辟、能动静、能生克者而名之曰太极。气外无理,理者,气之宰也。所谓宰,非自外来而宰之,指其气之用事,能不失所以然之正者而谓之宰。理不先于气,气无始,理固无始。若曰理先于气,则是气有始也。老氏曰:“虚能生气”,是则气有始有限也。①
徐敬德在理气问题上的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此段引文中。现将要点归纳如下:一是理不先于气;二是气外无理,二者具有共存性;三是气无始而理固无始,二者具有共时性。徐敬德还以老氏主张为例批判道:若说理先于气等于承认气是有始有限的,则与老氏“虚能生气”论一般无二。这表明在理气先后的问题上,花潭坚持的是二者共存共时性。
徐敬德气论思想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理”的概念及其特性。在上段引文中,花潭将“太极(理)”定义为“原其所以能阖辟、能动静、能生克者”,即事物产生运动变化的原因。此“所以”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宰”,即“气外无理,理者,气之宰也”。问题是此“气之宰”可否理解为一般朱子学意义上的理对气的主宰作用?如果将此理解为主宰性,那么花潭哲学便可说是理气二元结构的理论体系。对“宰”的概念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可以发现,文中“气之宰”指的是事物运动变化时的条理或是规律。徐敬德之理是“指其气之用事,能不失所以然之正者”,亦即事物的内在法则。可见,在花潭哲学中“理”不具有主宰义。
作为气本论者,徐敬德将天地万物的变化归结为“机自尔”,意思是说事物的阖辟动静皆由内因决定而外力无与焉。他进一步解释道:“阴阳一用,动静一机,此所以流行循环不能自己也。”②“一阴一阳者,太一也。二故化,一故妙,非化之外,别有所谓妙者。二气之所以能生生化化而不已者,即太极之妙,若外化而语妙,非知易者也。”③此即徐敬德的“二化一妙”说。在他的哲学中,“妙”为事物运动的根本属性,而“化”则为运动变化之内因——“妙化”就是对立统一。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事物正是由内因之推动而生生化化、迁变不已。徐敬德的这一思想极具理论卓见,在韩国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尽管徐敬德气论很有创意,但是同时代的性理学家并未对其学说给予肯定,反而多有微词。李滉尝言:“因思花潭公所见于气数一边路熟。其为说未免认理为气,亦或有指气为理者。故今诸子亦或狃于其说,必欲以气为亘古今常存不灭之物,不知不觉之顷,已陷于释氏之见,诸公固为非矣。”①李滉认为徐敬德论气虽精到无余,却因主气太过于理未深透彻,颇有认理为气之病。而李珥亦批评道:“花潭则聪明过人,而厚重不足。其读书穷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聪明过人,故见之不难,厚重不足,故得少为足。其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了然目见,非他人读书依样之比,故便为至乐。以为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气局一节,继善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理无变而气有变,元气生生不息,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在。而花潭则以为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此花潭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②李珥虽也指责其说有认气为理之病,但仍肯定与退溪相比“花潭多自得之味”③。他还认可徐敬德对“理气不相离之妙处”已“了然目见”。
其实,李珥对徐敬德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花潭哲学之难解就在于其对“理气之源”等紧要处的细心体贴。徐氏以为:“理之一其虚,气之一其粗,合之则妙乎妙。”④他还说过:“气之湛一清虚者,既无其始,又无其终,此理气所以极妙底。学者苟能做工到此地头,始得觑破千圣不尽传之微旨矣。”⑤可见,他自己也认为此等处为理解其学说的关键。不过,徐敬德所谓理气不相离之妙实基于气一元论,而非构筑在理气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花潭学说对李珥主气论影响较大,但李珥还是直言“宁为退溪之依样,不必效花潭之自得也”⑥。李珥甚至预言:“恐珥读书愈久,而愈与公(指花潭——引者注)见背驰也。”⑦
简言之,李滉与李珥对徐敬德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气本论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后人对其学术性格的判定。由此亦可见,气学派与理学派学者无论在学术立场还是理论旨趣上皆相距甚远。
作为韩国气学派的理论先驱,徐敬德的学问和品格皆为后世学人所敬重,被尊为“近代儒林之表”①。李滉对其理论贡献称许道:“然吾东方,前此未有论著至此者,发明理气,始有此人耳。”②李珥也对其学问赞曰:“虽然偏全闲,花潭是自得之见也。”③
1772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花潭集》二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八《别类存目》五之中)。徐敬德是著作被收录《四库全书》的唯一的韩国哲学家,可谓千载一人而已。这也说明其哲学在韩国乃至东亚哲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徐敬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原理气》、《理气说》、《太虚说》、《鬼神死生论》以及《复其见天地之心说》等,现均被收录于《花潭集》(4卷)中。
第四节 李彦迪的理本论
——以“无极太极”之辨为中心
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学术论辩有“无极太极”之辨、“四端七情理气”之辨、“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人物性同异(湖洛论争)”之辨以及“心说”论争等。其中,“无极太极”之辨是对性理学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其余皆为对性理学心、性、情等核心概念的深度辨析。这些论辩的依次展开不仅促进了韩国性理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韩国儒学独特理论风格的形成。从韩国儒学各个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争辩中,我们可以发现韩国性理学家们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本节要考察的是韩国儒学史上首次出现的学术论争——“无极太极”之辨。
一、论辩的发端
李彦迪(1491—1553年),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谥号文元,庆州府人。李氏出生于庆州良佐村,10岁丧父,12岁时短暂受学于其舅父愚斋孙仲暾(1463—1529年),而愚斋曾为佔毕斋金宗直门人。我们只知道李彦迪的思想与愚斋之弟亦为其舅父的忘斋孙叔暾①有所不同。李氏学无师承②,于中宗九年(1514年)登第,始入仕途,历任吏曹判书、刑曹判书、左赞成等官职。作为朝鲜朝前期士林学者的“五贤”③之一,他既是朝鲜朝主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先驱,又是朝鲜朝性理学鼎盛期的揭幕人。李彦迪一生从宦多年,旋进旋退,颇不平顺。在他8岁时发生“戊午士祸”,14岁时发生“甲子士祸”,29岁和55岁时又发生“己卯士祸”、“乙巳士祸”。韩国历史上的“四大士祸”皆曾亲历。但是,李彦迪始终将“养真”与“经世”④作为其平生之志,为后学树立了一个有担当、有追求的儒者形象。他23岁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生志业在穷经,不是区区为利名。
明善诚身希孔孟,治心存道慕朱程。
达而济世凭忠义,穷且还山养性灵。
岂料屈蟠多不快,夜深推枕倚前楹。⑤
此诗写于中宗九年,正是其中生员试之年。从“明善诚身”、“治心存道”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其强烈的希慕圣贤之情。诗中所抒发的正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的儒家理想情怀和入世精神。可见,李彦迪在步入仕途之初便立下修齐治平的人生志向。
他的学问和思想对韩国性理学的影响,从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滉之评价可以概见。李滉尝言:
谨受而伏读之,反复参究,质之以古圣贤之言,于是始知先生(指晦斋——引者注)之于道学,其求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正也。而凡先生之出处大节,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先生在谪所,作《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又修《中庸九经衍义》,《衍义》未及成书,而用力尤深。此三书者,可以见先生之学。而其精诣之见,独得之妙,最在于与曹忘机汉辅《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也。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呜呼,我东国古被仁贤之化,而其学无传焉。丽氏之末以及本朝,非无豪杰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归之者。然考之当时,则率未尽明诚之实,称之后世,则又罔有渊源之征,使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②
此段文字引自李滉为李彦迪所撰写的“行状”,文中他对李氏的生平和学问做了简明扼要之概括,称道其有精诣之见和独得之妙。文中李滉虽然举了《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成稿《中庸九经衍义》等李氏代表作,但是他认为李氏学问之理论精髓在于与曹忘机堂(名汉辅,庆州人)的《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中。其实,李滉提到的《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稿《中庸九经衍义》都是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所作。他在江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六年,最终在此地辞世,享年63岁。而与忘机堂的无极太极论辩书则作于李氏二十七八岁时,可见其思想成熟之早。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著作所表达的观点是早年与忘机堂曹汉辅论辩时确立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节也将以李彦迪与曹汉辅的《论无极太极书》为中心,来探讨其理本论哲学思想的特点。
这场论辩发生在1517年(中宗十二年)至1518年。最初是忘斋孙叔暾与忘机堂曹汉辅①之间通过书信对“无极太极”问题展开相互问难。李彦迪读到这些书信后,便撰写《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以下简称《说后》)一文对之加以评述。曹汉辅旋即对李彦迪的《说后》提出了异议。于是,李氏和曹汉辅之间开始有书信往来,现存《晦斋集》中有李彦迪答忘机堂书信四封。但曹汉辅致李彦迪的书信皆已失传,只能通过现存的李彦迪答曹汉辅书信一窥其思想梗概。
这里我们首先对《说后》的主要内容做些简要分析,以便对李彦迪、孙叔暾和曹汉辅的观点有个总体的了解。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说后》的内容按文意分为若干个段落,抄录如下:
第一段落:“谨按:忘斋无极太极辨,其说盖出于陆象山,而昔子朱子辨之详矣。愚不敢容赘。若忘机堂之答书,则犹本于濂溪之旨,而其论甚高,其见又甚远矣。其语《中庸》之理,亦颇深奥开广。得其领要,可谓甚似而几矣。然其间不能无过于高远而有悖于吾儒之说者。愚请言之:夫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柢也。是乃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来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哉!此理虽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实体之所以寓,则又至近而至实。若欲讲明此理而徒骛于窅冥虚远之地,不复求之至近至实之处,则未有不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矣。”②
本段引文的观点可视为李氏在“无极太极”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文中李彦迪首先对忘斋和忘机堂观点的理论来源作了说明,指出忘斋的主张出自陆子学说,而忘机堂的观点则本于濂溪之旨。他进而声言,陆子的无极太极之说因朱子已详辩无须赘言,而妄机堂的学说则因过于高远而似有背于吾儒之旨处。由此可见,宋代朱陆之辨是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之辨的理论先河。李彦迪在本段还阐述了自己对无极太极问题的基本理解,主张并非太极之上复有无极,此至高至妙之理只能在至近而至实处求之,不然就会有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的危险。由此可见,他对道体之根源、行为之应然等问题越有借由自己的理解。不过,从李氏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来看,其见似与朱子并无二致。此其所以李滉评论其学说时直言“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
第二段落:“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也则是矣。其曰岂有论有论无、分内分外,滞于名数之末则过矣。其曰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则是矣。其曰大本达道浑然为一则何处更论无极太极,有中无中之有间则过矣。此极之理虽曰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发差者。是岂漫无名数之可言乎?而其体之具于吾心者则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然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容不辨者。安有得其浑然则更无伦序之可论,而必至于灭无之地而后为此道之极致哉。今徒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极言之,而不知夫粲然者之未始相离也。是以其说喜合恶离、去实入虚,卒为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而后已。岂非穷高极远而无所止者欤?”①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援引朱子之说对忘机堂的不当言论进行了逐一反驳,指出其“太极即无极”、“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等见解可以成立,但不分有无、分内分外以及有中无中而论无极太极却明显不妥。李氏以为太极之理虽然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无有毫发之差。①而且,其“体”之具于吾心者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同。故不能只重其浑然而轻其伦序,“喜合恶离,去实入虚”。
第三段落:“先儒言周子吃紧为人特著道体之极致,而其所说用工夫处只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尝使人日用之间必求见此无极之真而固守之也。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若论工夫则只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今忘机之说则都遗却此等工夫,遽欲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万物朝宗于我而运用无滞,是乃欲登天而不虑其无阶,欲涉海而不量其无桥。其卒坠于虚远之域而无所得也必矣。大抵忘机堂平生学术之误病于空虚,而其病根之所在则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以灭字说太虚体,是断非吾儒之说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谓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谓于穆不已者存焉。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著灭字于寂字之下。试以心言之:喜怒哀乐未发、浑然在中者,此心本然之体而谓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则喜怒哀乐发皆中节,而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谓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灭则是枯木死灰而已,其得不至于灭天性乎?然忘机于本来寂灭之下便没灭字不说,而却云虚而灵、寂而妙。灵妙之体充满太虚、处处呈露,则可见忘机亦言其实理而说此灭字不去。故如是岂非有所穷而遁者乎?”②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直言不讳批评忘机堂,以为其平生之误在于“空虚”二字,而其病根则在“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他在指出错误根源的同时,还断言以“灭”字说太虚体“断非吾儒之说”。“寂灭”是佛教用语,《涅槃经》上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一句。而“诸行无常”则又是佛教三法印之一,因此《涅槃经》上的这一句又可视为佛家基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众所周知,大乘佛教不承认现实世界的实在性。以“四大”为假合,以寂灭为圆觉,遂将人伦道德视如赘疣。而儒家所说的“寂”则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寂”,与佛家之寂灭有着本质的区别。
李彦迪还批评忘机堂曹汉辅不仅在太极之上复设无极,而且漠视形而下之人伦日用之修养工夫。如果只关注形而上之“灵妙之体”,就无从体认至近至实处的太极之理。他认为上天无声无臭可谓“寂”,然至寂之中又有“于穆不已”,其化育流行遂生鸢飞鱼跃之景象,所以在“太极”之上绝不可添加一“灭”字。
“自汉以来圣道塞而邪说行,其祸至于划人伦、灭天理而至今未已者,无非此一灭字为之害也。而忘机堂一生学术言语及以上议论之误,皆自此灭字中来。愚也不得不辨。若其超然高会一理浑然之体而的无疑,则实非今世俗儒高释所可几及。亦可谓智而过者矣。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矣。而不幸世无孔孟周程也,悲夫!”①
在本文结尾处,李氏总结异端之弊害全在一“灭”字,而忘机堂为学论议之误亦皆源自此一“灭”字。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撰文辨析。“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
由此而论,李氏批评忘机堂曹汉辅的用意在于揭露其异端思想,像文章中隐约出现的佛家倾向。《说后》一文写于中宗十二年(1517年)正月,即李彦迪27岁之时。曹汉辅何时作复则已无从查考。从年谱上的记载看,李彦迪答忘机堂曹汉辅的第一封书信是在中宗十三年(戊寅年即1518年)写的。他时年28岁。
二、论辩的主要内容及理论特点
前已言及,“无极太极论辩”起因于李彦迪所撰的《说后》。该文写于中宗十二年,翌年曹汉辅对此提出异议。于是,便有了“答忘机堂”的四封书信。
在论辩的过程中,晦斋李彦迪和忘机堂曹汉辅围绕“无极”、“太极”概念以及儒家修养论等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发生于朝鲜朝初期的此一论辩中,李彦迪从朱子学理本论的立场出发,批驳了具有佛道思想色彩的曹汉辅的主张。此论辩在学理上可理解为“无极太极”问题的性理学式解读和非性理学式解读的立场对立。
因为《说后》主要是李彦迪对孙叔暾和曹汉辅的“无极太极”说的评论文章,故只能了解到他的思想概貌。不过,在“答忘机堂”的四封书信中却可以发现李氏较为系统的性理学观点。而且,从《说后》和《答忘机堂书》中还可以看出,曹汉辅的观点的确受到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故李彦迪在《答忘机堂书》中,指责其所持的是佛家之寂灭论而非儒家之寂感论。李氏和曹汉辅之间的论辩作为性理学本体论问题之探讨在韩国儒学史上意义重大,说明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已具备相当的理论水平。下面将对四封书信之内容做逐一分析。
在《答忘机堂第一书·戊寅》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伏蒙示无极寂灭之旨、存养上达之要,开释指教不一而足。亦见尊伯不鄙迪而收之,欲教以进之也。感戴欣悚,若无所容措。”①可知,曹汉辅在读了李氏所写的《说后》之后,就“无极寂灭”和“存养上达”等本体论、修养论问题给李氏回信,这应该是曹汉辅在致李彦迪信中谈的主要问题。
于是,李彦迪在复信中首先解释自己为何撰写《说后》,然后针对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又陈述了己见。他说:
来教所云寂灭存养之论有似未合于道者。小子亦有管见须尽露于左右者,敢避其僭越之罪而无所辨明耶。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风雷之所以变,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周子所以谓之无极者,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非若老氏之出无入有、释氏之所谓空也。①
从整个论辩过程中李氏自谦的语气和态度来看,曹汉辅应较彼时才二十七八岁的李彦迪年长许多。所以李氏在信中陈述己见时显得比较谨慎。对于曹氏的寂灭存养之论,李彦迪十分谦虚地讲到“小子亦有管见须尽露于左右”,然后谈了自己对“太极”与“无极”概念的理解。他指出“太极”作为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是实然而不可易者,周子所以又称之为“无极”乃因其具“无方所、无形状”之特性。究其实与佛道两家所言“空”、“无”等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接着他借“理”、“气”之概念阐发了己见,并对曹氏的本体论进行了批评:
今如来教所云,无则不无而灵源独立,有则不有而还归澌尽。是专以气化而语此理之有无,岂云知道哉?所谓灵源者气也,非可以语理也。至无之中至有存焉,故曰“无极而太极”。有理而后有气,故曰“太极生两仪”。然则理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而言。何必见灵源之独立然后始可以言此理之不无乎?鸢飞鱼跃昭著上下,亘古亘今充塞宇宙。无一毫之空阙,无一息之间断。岂可但见万化之澌尽而遂指此极之体为寂灭乎?②
从内容中可以推知,曹汉辅将“灵源”视为宇宙本体。而李彦迪则认为所谓“灵源”者其实是气,不能将形而下之“气”视为宇宙的终极本体。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其实是“至无之中至有存焉”之义。此处的“而”应指“所当然之中”的“所以然之理”——太极即是“理”。①李氏进而提出自己的理气观——“有理而后有气”,“理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理与气的关系问题是朱子学的基本问题,李氏对此所持的正是传统朱子学以理为本的理气二元论立场。
他还指出曹氏所云寂感、寂灭之分似同而实异的,先儒对此已有至论,后学者不可以此为浮议而独以异端之说为是:
盖太极之体虽极微妙,而其用之广亦无不在。然其寓于人而行于日用者,则又至近而至实。是以君子之体是道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有以全其本然之天而绝其外诱之私。不使须臾之顷、毫忽之微,有所间断而离去。其行之于身也,则必造端乎夫妇以至于和兄弟顺父母,而有以尽己之性。及其尽性之至也,则又有以尽人物之性。而其功化之妙极于参天地赞化育,而人极于是乎立矣。此君子之道所以至近而不远,至实而非虚,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此非愚生之言,实千古圣贤所相传授而极言至论者也。②
文中李彦迪借圣贤之言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表明己见合乎儒家正统。太极与理气的问题属于天道,李氏遂借探讨寂灭的问题将话题转入人道。他认为道不远人,若离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于空虚。李彦迪引用《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之句来说明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安得不先于下学之实务而驰神空荡之地?可以为上达乎?天理不离于人事。人事之尽而足目俱到以臻于贯通之极,则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浑全。酬酢万变、左右逢源,无非为我之实用矣。”③李氏依据朱子“统体一太极”的思想为依据,提出天理不离于人事,以此批判曹氏的“存养上达”修养方法的根本错误。李彦迪说: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又曰:“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讵不信欤?且如存养之云,只是敬以直内,存之于未发之前以全其本然之天而已。苦曰游心于无极之真。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使人不为近思之学而驰心空妙。其害可胜言哉?又况虚灵本是吾心之体也。无极之真,本是虚灵之中所具之物也。但加存之之功而不以人欲之私蔽之,以致其广大高明之体可也。张南轩曰:“太极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惟当本于敬以涵养之。”正谓此也。今曰“游心于无极”,曰“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似以无极太极为心外之物而别以心游之于其间,然后得以为之主也。此等议论似甚未安。①
李彦迪在文中先讲明虚灵、无极之真以及吾心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儒家修身的正确方法。由此可见二人为学工夫之差异。李彦迪强调洒扫应对当中的“下学而上达”,而曹氏则主张带有“顿悟”性质的“存养而上达”。后者的主张当然会受到正统儒者的批评。在结尾处李彦迪写道:
来教又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亦见尊伯立言之勇而自信之笃也。然前圣后圣其揆一也。今以已往圣贤之书考之,存养上达之论无所不备。其曰“存心养性”,其曰“戒慎恐惧”,其曰“主静曰主敬”者,无非存养之意。而曷尝闻有如是之说乎?吕氏虚心求中之说,朱子非之。况以游心无极为教乎?孔子生知之圣也,亦曰“我下学而上达”,又曰“吾尝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况下于孔子者乎?故程子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欲人收已放之心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以此观之,其言之可易与不可易直验于已往之圣人而可见矣。何必有待于后来复起之圣人乎?天下之祸,莫大于甚似而难辨。惟其甚似,故能惑人;惟其难辨,故弥乱真。伏详赐书,无非杂儒释以为一。至有何必分辨之说,此小子所甚惧而不敢不争者也。伏见尊伯年高德邵,其于道体之妙亦可谓有所见矣。但以滞于寂灭之说,于其本源之地已有所差。而至于存养上达之论,则又与圣门之教大异。学者于是非之原毫厘有差,则害流于生民,祸及于后世。况其所差不止于毫厘乎?伏惟尊伯勿以愚言为鄙,更加着眼平心玩理。黜去寂灭游心之见,粹然以往圣之轨范自律。吾道幸甚!善在刍荛,圣人择之。况听者非圣人,言者非刍荛。而遽指言者为狂见而不察乎?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古之君子改过不吝,故年弥高而德弥进也。小子所望于尊伯者止此。①
从曹汉辅“游心于无极之真”以及“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等见解中确实可以感受到其思想明显混杂于佛理。所以李彦迪在此信的末尾处称忘机堂“无非杂儒释以为一”,与圣门之教的理论旨趣相去甚远。尽管二人年龄相差较大,李彦迪仍以昂扬的卫道精神据理力争。
接到曹汉辅的回信后,李彦迪在《答忘机堂第二书》中写道:“伏睹来教于无极上去‘游心’二字,于其体至寂下去一‘灭’字。是不以愚言为鄙,有所许采。幸甚幸甚!”②这表明忘机堂接受李氏在第一封信中的批评,已去掉无极之上的“游心”二字和其体至寂下的一“灭”字。但是,彦迪仍然觉得曹汉辅尽管在字句上对之前的表述做了些调整,却并未尽弃其思想中的佛、道立场。于是,他继续提出委婉的批评:
书中所论一本之理及中庸之旨,亦颇明白少疵、妙得领要。圣人之道,固如斯而已,更无高远难穷之事。迪敢不承教。③
文中提到的“一本之理”和“中庸之旨”分别指的是第一封信中所讨论的无极太极、寂灭等本体论的问题和有关存养上达的工夫论问题。可见,在内容上此信殆可视为第一封信之继续。李彦迪提到:
至如寂灭之说,生于前书粗辨矣。未蒙察允,今又举虚灵无极之真,乃曰“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是未免于借儒言而文异端之说。小子之惑滋甚。先儒(指朱子——引者注)于此四字盖尝析之曰:“此之虚,虚而有;彼之虚,虚而无;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灭。”然则彼此之虚寂同,而其归绝异,固不容不辨。而至于无极之云,只是形容此理之妙无影响声臭云耳,非如彼之所谓无也。故朱子曰:“老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讵不信欤?①李彦迪认为曹氏的“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实际上是借吾儒之言文饰异端之说。他举朱子之言阐明儒家的虚寂观念与异端之虚寂说犹如南北水火之相反,在理论归趣上决然不同。彼此之虚寂名同而实异。
李彦迪进而指出:
来教又曰:“主敬存心而上达天理。”此语固善,然于上达天理上却欠“下学人事”四字,与圣门之教有异。天理不离于人事。下学人事,自然上达天理。若不存下学工夫,直欲上达,则是释氏觉之之说。乌可讳哉?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则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便是上达境界。从事于斯,积久贯通,可以达乎浑然之极矣。而至于穷神知化之妙,亦不过即是而驯致耳。②
李彦迪在为学次第上重视“下学人事”,体现心性工夫之切近日用人伦的一面。他引孔子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之语以证明己之看法。最后李彦迪写道:
夫穷理,非徒知之为贵。知此理又须体之于身而践其实,乃可以进德。若徒知而不能然,则乌贵其穷理?而其所知者终亦不得而有之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然则非知之难,行之难。此君子所以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必顾行、行必顾言,不敢容易大言者也。不知尊伯亦有如是体察之功乎?亦有如是践履之实乎?大抵道理,天下之公共。不可以私智臆见论之。要须平心徐玩,务求实是可也。③
依李彦迪之见,所谓“穷理”指的是由亲身体验知晓此理,必以进德为期才是理学家所谓德性之知。他委婉指出若无“体察之功”、“践履之实”,则所见往往流为异端。作为晚辈祈盼曹氏痛去寂灭之见,又能主敬存心以达于天理。诚如此,“则尊伯之于斯道,可谓醇乎醇矣。”①前已论及曹李二人年龄差距较大。但是从信的内容来看,曹汉辅并未轻视一位新锐学者对己见之质疑。于是,有了他们之间的第三封书信。
在《答忘机堂第三书》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伏睹来喻所陈,虽云不滞寂灭之说有年,而寂灭之习似依旧未除。是以其论说浮于道理幽妙之致,而未及反躬体道之要。不免为旷荡空虚之归,而非切近的当之训。此小子所以未敢承命者也。”②于是李氏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体道经验和感悟。
从此信的内容可以推知,曹汉辅复信中的主张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大本”与“达道”,即“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的存养之道问题。彦迪在信中提到:
迪闻子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古今论道体,至此而无余蕴矣。愚请因此而伸之。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散诸三极之间。凡天地之内,无适而非此道之流行,无物而非此道之所体……当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此心之真寂然不动。是则所谓无极之妙也,而天下之大本在于是也。固当常加存养之功以立大本,而为酬酢万变之主。而后可以发无不中而得时措之宜。然于此心之始动几微之际,天理人欲战于毫忽之间,而谬为千里之远。可不于是而益加敬慎乎?是故君子既常戒惧于不睹不闻之地,以存其本然之,而不使须臾之离有以全其无时不然之体……自其一心一身以至万事万物,处之无不当,而行之每不违焉。则达道之行于是乎广矣,而下学之功尽善全美矣。二者相须,体道工夫莫有切于此者。固不可阙其一矣。
来教有曰:“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则固存养之谓矣,而于静时工夫则有矣。若夫顿除下学之务,略无体验省察之为,则于动时工夫盖未之及焉。是以其于求道之功疏荡不实,而未免流为异端空虚之说。
伏睹日用酬酢之际,不能无人欲之累。而或失于喜怒之际,未能全其大虚灵之本体者有矣。岂非虽粗有敬以直内工夫,而无此义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体道不能精密而或至于此乎。昔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子继之曰:“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然则圣门工夫虽曰主于静以立其本,亦必于其动处深加省察。盖不如是则无以克己复礼,而保固其中心之所存矣。故曰“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未有不制其外而能安其中者也。愚前所云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顾行行顾言者,此之谓也。安有遗其心官、随声逐色,失其本源之弊哉?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盖地位已到圣人,则此等工夫皆为筌蹄矣。若未到从容中道之地而都遗却择善省察工夫,但执虚灵之识。①
李彦迪在信中对儒家的“大本”与“达道”作了简单明了的论述,这表明他对之已有了深切之体悟。李彦迪在工夫论问题上的立场是,“常加存养之功以立大本,而为酬酢万变之主”。他主张“存养”不能像曹汉辅那样只强调“敬以直内”,而忽视“义以方外”。在李彦迪看来,不假修为即可克己复礼、酬酢万变如同不出门而欲适千里,不举足而欲登泰山,结果肯定是“必不能矣”。
二是曹汉辅认为为破世人执幻为真,故言“寂灭”。对此有悖儒家宗旨的“异端”之见,李彦迪批评道:
来教又曰:“为破世人执幻形为坚实,故曰寂灭。”此语又甚害理。盖人之有此形体,莫非天之所赋而至理寓焉。是以圣门之教,每于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尽夫天之所以赋我之则,而保守其虚灵明德之本体。岂流于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岂可以此为幻妄?必使人断除外相,独守虚灵之体,而乃可以为道乎?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此寂灭之教所以陷于空虚诞谩之境,而无所逃其违天灭理之罪者。①众所周知佛教主张“四大皆空”,其耽空沦寂之弊对儒家之教危害甚深。李彦迪依性理学“道器不离”、“体用一源”之旨对之予以批驳。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肯定了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这一点在讨论“下学上达”时讲得更透彻。
三是在“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上,曹汉辅认为“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对此李彦迪不以为然。他说:
今曰“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愚请以孔子申之。自生民以来,生知之圣未有盛于孔子者,亦未尝不事于下学……然则孔子不得为豪杰之士,而其所为亦不足法欤?若曰孔子之言所以勉学者也,于其己则不必,然则愚请以孔子所亲为者白之。孔子问礼于老聃,问官于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是非下学之事乎?问官之时,实昭公十七年而孔子年二十七矣。入太庙则孔子始仕时也。古人三十而后仕,则是时孔子年亦不下三十。其非童蒙明矣。夫以生知之圣,年又非童蒙,而犹不能无下学之事。况不及孔子?而遽尔顿除下学不用力,而可以上达天理乎?是分明释氏顿悟之教,乌可尚哉?孟子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若使尊伯于此异说之诞终身迷没,不知其非则已矣。今曰不滞者有年,则是已觉其非而欲改之也。退之云“说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请自今痛去寂灭之见,反于吾道之正。②
曹汉辅与李彦迪二人在为学之方上的分歧与宋代朱陆之间“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颇有相似之处。陆氏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将朱子的“博学于文”视为“支离事业”。朱子则批评象山为学浮躁,只好发高论而不“道中庸”,造说遂与佛老相似。③在为学之方上李彦迪以圣贤为例批驳了曹氏的观点,强调不论童蒙初学还是豪杰之士皆不能无下学之事。
《答忘机堂第四书》是两人之间最后一次通信,在复信的开头李彦迪写道:“今承赐教,辞旨谆谆,反复不置,且去‘寂灭’二字而存‘下学人事’之功。迪之蒙许深矣,受赐至矣,更复何言!”①从中可推知,经过几次书信往来曹汉辅对李彦迪的批评有所接受,对自己的立场也做了调整。而且李彦迪也认可曹汉辅态度之转变。他在信中指出:“然而窃详辱教之旨,虽若尽去异说之谬、入于圣门之学,然其辞意之间未免有些病。而至于物我无间之论,则依旧坠于虚空之教。小子惑焉。”②但在李彦迪看来,忘机堂仍未彻底摒弃其原有思想。第四封信的讨论焦点是有关“主敬存心”的工夫论问题。李彦迪写道:
圣门之教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齐其外以养其内。内则无贰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俨然肃然,深省密察,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动直、中一外融,则可以驯致乎不勉不思从容中道之极矣。两件工夫不可偏废明矣。安有姑舍其体而先学其用之云哉?③
李彦迪将理学工夫论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简言之,即践行居敬穷理。这是基于伊洛渊源的正统解释。李彦迪在信中十分强调“敬”之工夫,这一思想对后来李滉的主敬工夫论颇有影响。李彦迪援引程伊川从《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中提炼出来的道德戒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本体工夫固不可不先,而省察工夫又尤为体道之切要”。他认为颜子亦循此四箴之路径优入圣域,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李彦迪主张为人要谨守“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由此他对曹氏在第三封复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一一做了答复。
一是“主敬存心”的问题。李彦迪以“衣”、“网”为例答复说:“伏睹来教有曰‘主敬存心’,则于直内工夫有矣,而未见义以方外省察工夫。岂非但得衣之领而断其百裔,但得网之纲而绝其万目者哉?人之形体固当先有骨髓,而后肌肤赖以充肥。然若但得骨髓,一切削去皮肤,则安得为人之体?而其骨髓亦必至于枯槁而无所用矣。况既去皮肤而于骨髓亦未深得者哉?愚前所谓常加存养以立大本,为酬酢万变之主者,固尊伯主敬存心、先立其体之说。初非毁而弃之。未蒙照察,遽加罪责,不胜战汗。”①前已言及李氏并不反对“主敬存心”,只是向忘机堂强调了修养工夫不能缺失“义以方外”。在他看来,两段工夫同等重要,必须同时并举。
二是“先立其体和下学人事”的问题。李彦迪对此回复道:“来教又曰:‘先立其体,然后下学人事。’此语亦似未当。下学人事时,固当常常主敬存心。安有断除人事,独守其心?必立其体。然后始可事于下学乎。所谓体既立则运用万变,纯乎一理之正而纵横自得者。固无背于圣经贤传之旨。然其所谓纯乎一理、纵横自得者,乃圣人从容中道之极致。体既立后,有多少工夫?恐未易遽至于此。伏惟更加精察。”②此问题还是前一问题的延伸。李彦迪在存养省察的问题上立场鲜明,就是坚持下学与上达同时并进。
三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问题。李彦迪谈了自己的理解,指出:“且如万物生于一理。仁者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然其一体之中,亲疏远近是非好恶之分自不可乱。故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语》又曰:‘惟仁人为能好人,能恶人。’以此言之,仁者虽一体万物,而其是非好恶之公亦行乎其中而不能无也。舜大圣人也,固非有间而滞于所执者。然而取诸人为善,舍己从人则舜亦不能无取舍之别矣。安有心无间则茫然与物为一?更无彼此取舍好恶是非之可言,然后为一视之仁哉。”③追求“天人合一”是儒家修己的最高理想。但李彦迪强调的是“一体之中,亲疏远近是非好恶之分自不可乱”。他认为儒者同时还要具备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从而做到择善而从。
在信的最后李彦迪语词恳切,寄望曹汉辅平心察理,勿以其有是非取舍为罪。此后曹氏再未复信,而两人的论辩也就此而告终。从现存四封书信的内容来看,李氏最终也没能说服忘机堂尽弃其原有立场。读此书信可以感受到一位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士大夫①的卫道意识。两人温文尔雅之论辩既流露了少壮学者李彦迪的锐气和担当,又展现了学界名宿曹汉辅的平和与谦逊。
三、论辩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无极太极”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围绕与朱子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发生的首次论辩。此次论辩不论对李彦迪太极说的形成还是朱子学在韩国的发展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论辩的过程中,李彦迪基于朱熹之理气二元论对具有佛道思想倾向的曹汉辅“无极太极”说进行了批驳。与此同时,他还以性理学为正统捎带批判佛道两家的理论。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论辩不仅令性理学之本体论得以确立,而且使儒佛与儒道之义理分际得以明晰。尽管此后还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四七理气”之辨、“人心道心”之辨和“人物性同异”之辨等等,但是此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视。
“四七理气”之辨则与“人心道心”之辨密切相关。后者也是朱子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韩国儒学史上令“四七理气”之辨得以进一步深化。本书将在论述四端七情论辩时设专节详述“人心道心”之辨。
与前一节介绍的徐敬德相比较,李彦迪虽亦重视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思想之旨趣却与徐氏大相径庭。徐敬德基于气本论之立场,主张“太虚即气”;而李彦迪则依据理本论之立场,将“太极”视为天理。“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①李彦迪从主理论出发,阐述了其“太极说”。他认为这种“理”是“无形无质”之存有,“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但理先气后,“有理而后有气”。②李彦迪进一步指出:“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有日月之形则有所以为日月之理,有山川之形则有所以为山川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③他以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天地万物之理(太极),而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后依然作为事物之所以然与大千世界密切结合。李彦迪又说:“天下之理体用相须、动静交养,岂可专于内而不于外体察哉?”④由此可见李彦迪哲学思想的主理论特色。
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著有《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中庸九经衍义》——后者虽未完稿,但是较为详细地反映了他的道德经世观。《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则是申述朱子之学的著作。在《大学章句补遗》一书中李氏曾言及朱子所作《格物补传》之不当处。例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原文“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下朱熹写道:“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接着又写道:“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⑤于是依程子之意作了格致章的补传。对此李氏指出:“朱子得其结语一句,知其为释格物致知之义,而未得其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所以发明始学穷理之要,亦甚明备。然愚尝读至于此,每叹本文之未得见。近岁闻中朝有大儒得其阙文于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见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见。取经文中二节,以为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复参玩,辞足义明,无欠于经文而有补于传义,又与上下文义脉络贯通。虽晦庵复起,亦或有取于斯矣。”①可见,他对朱子之《格物补传》有失当处极为自信。李彦迪以为《大学章句补遗》开头经文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②二节原为格致章的原文,如今被错误纳入经文之中。为此他主张应将此两节,重新归入格致章之原文之中。而“此谓知之至也”一句是结上文两节之意的。《大学章句补遗》写于1549年,李氏时年59岁,早已是成名的儒学大家。此文对研究李彦迪理学思想大有助益。相较于朱子,李氏更强调格物致知之“止于至善”。依李彦迪之见,致知宜有缓急先后,由近及于远,由人伦及于庶物,必有以见其至善之所在而知所止,然后其所知所得皆切于身心。
从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程朱之学,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蕴育,至李彦迪才有较具体系的性理学说。李氏的理气论和无极太极论在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他的思想在韩国儒学本土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李彦迪的性理学说成为日后李滉和李珥等人集朝鲜朝朱子学之大成的理论基础。李氏第一次将有关心性修养和经世致用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整理,为韩国儒学界确立了理本论哲学体系,而与曹汉辅之论辩集中反映了他的心性论思想。正是李彦迪将修身之存养工夫引向了心性论的进路。
李彦迪理本论思想对李滉的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滉十分推崇李彦迪,不仅称赞他的“立言垂后”之功,还曾为其作行状极言学力之深湛。李滉评论道:“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③还说:“近代晦斋之学甚正,观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义正,浑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④他认为李彦迪的学问“所得之深殆近世为最也”①。李珥尽管对李彦迪在“乙巳士祸”中的作为颇有微词,但对其学问还是相当首肯,尝言:“李彦迪博学能文,事亲至孝,好玩性理之书,手不释卷。持身庄重,口无择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学者亦以道学推之。”②
光海君二年(1610年),李彦迪还与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混作为“士林五贤”配享文庙。他的哲学著作有《求仁录》、《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中庸九经衍义》、《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答忘机堂书》以及《奉先杂仪》等。
概而言之,发生于16世纪初期的这场论辩反映了朝鲜朝初期的韩国儒者对理学本体论的不同理解。尽管这一论辩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力不及16世纪发生的“四端七情”之辨和“人心道心”之辨,但在理学本土化的初期即由深度的哲学思考树立了正统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后来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两位老少学者间展开的“无极太极”之辨在成就韩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的同时,还正式拉开了16世纪韩国儒学一系列精彩的学术论辩的序幕。
第五节 曹植的性理学
曹植(1501—1572年),字楗仲,号南冥,谥号文贞。他出生于庆尚道三嘉,5岁时移居汉阳。作为朝鲜朝著名的性理学家,曹南冥崇尚洙泗学的实践躬行精神,主张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因与李退溪同年,又并峙岭之左右,故合称岭南学派之双璧。庆尚右道的儒者大都从曹南冥之说,庆尚左道的儒者则多从李滉之说。后人称退溪学派为江左学派,南冥学派为江右学派。河谦镇(字叔亨,号晦峰、畏斋,1870—1946年)在《东儒学案》之《德山学案》写道:“退溪居岭左之陶山……南冥居岭右之德山……蔚然为百世道学之宗师。二先生以天品:则退溪浑厚天成,南冥高明刚大。以出处:则退溪早通仕籍,位至贰相;南冥隐居尚志,屡征不起。以学问:则退溪精研力索天人性命之理,无有余蕴;南冥反躬实践,敬义夹持之功,自有成法。”①本节将简要介绍一下岭南学派另一大儒曹南冥的思想。
与李退溪不同,曹南冥一生未仕,始终以教授为业。其为学极重“敬义”,尝曰:“吾家有此两个字,如天之有日月,洞万古而不易。圣贤千言万语,要其归,都不出二字外也。学必以自得为贵曰,徒靠册字上讲明义理,而无实得者,终不见受用,得之于心,口若难言,学者不以能言为贵。”②李甦平教授在其著作《韩国儒学史》中认为,虽然曹植与李滉都对朝鲜朝儒学作出了贡献,但贡献点却不尽相同。李退溪主要是在性理学方面深化、发展了朱子学说,从而奠定了他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显赫地位。而曹南冥则强调原典儒学的“敬义”和实践精神,遂自成一家之学而与退溪并峙。曹植为学以“敬义”标宗,其学一言蔽之就是“敬义”学。“敬义”在南冥学的体系中既是体(他以敬义为“心体”)也是用(他同样以敬义为工夫)。“敬义”由是贯穿三才、融通天人,达于真善美的统一。这是曹植“敬义”思想的基本要点。③
曹植以为“程朱以后不必著书”,只需反躬体验、持敬实行即可。他对现实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曾师事于曹南冥和李退溪的寒冈郑逑(字道可、可父,号寒冈、桧渊野人,1543—1620年)说过:“先生之于道义,亦可谓辛苦而后得之者矣。先生平生,未尝一念不在于世道。至于苍生愁苦之状,军国颠危之势,未尝不嘘唏掩抑。至或私自经画处置于胸中,而以为必先提掇于纪纲本源之地,则初非不屑夫天下之事者,怀德遯世,高洁自守,终世婆娑于穷山空谷之中。”④其主要学术著作有《南冥集》、《学记类编》等。其中《学记类编》分为上、下二卷。上卷又分“论道之统体”和“为学之要”两部分,并绘有二十二个图式加以阐释。下卷则列出儒者为学践行之法门,有“致知”、“存养”、“力行”、“克己”、“出处”、“治道”、“治法”、“临政处事”、“辟异端”等条目并附录两个图式。此二十四图便是与李退溪《圣学十图》齐名的南冥的《学记图》。
《学记图》最能体现曹植的学术思想。用图说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不仅是曹植的特点,也是朝鲜朝儒家学者的共同特色。韩国的图说可以追溯到朝鲜初期权阳村的《入学图说》。后来还相继出现过郑秋恋和李退溪合作的《天命图说》、李退溪的《圣学十图》、李栗谷的《心性情图》和《人心道心图说》等。以“图”示“说”,以“说”释“图”,二者之结合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曹植二十四图亦是如此。
关于《学记图》,有学者认为其中十幅最为重要,即“三才一太极图”、“太极图与通书表里图”、“天人一理图”(“天道图”和“天命图”)、“心统性情图”、“忠恕图”(“忠恕—贯图”)、“敬诚图”(“敬”图和“诚”图)、“审几图”(“几图”)、“为学次序图”(“小学”、“大学”图)、“博约图”和“易书学庸语孟一道图”。之所以推重此十图,乃因其表达了曹植的本体论思想。其实若从曹植的思想主旨来看,二十四图中最重要的十图应是“敬图”,“小学、大学图”,“诚图”,“人心、道心图”,“博约图”,“知言、养气图”,“易书学庸语孟一道图”,“心为严师图”,“几图”和“神明舍图”。因为曹植论学的最大特点就在“敬义”和“力行”。①不过,有人指出这十图中“忠恕图”(“忠恕—贯图”)、“博约图”并非曹植的“自图”。②尽管如此,二十四图仍被普遍视为“南冥学”的精髓,由此可理解和把握其为学之特色。
曹植虽与李滉同为岭南儒林之师表,但是李滉对其学术常表不满,曾评论说:“南冥虽以理学自负,然直是奇士,其议论识见每以新奇为高务,为惊世之论,是岂真知道理者哉。”③对于两人为学风格及思想特点,朝鲜朝后期的实学大家星湖李瀷(字子新,号星湖,1681—1763年)从其实学之视角指出:“檀君之世,鸿蒙未判,历千有余年,至箕子东封,天荒始破,不及于汉水以南。历九百余年至三韩,地纪尽辟为三国之幅员,历千有余年,圣朝建极,人文始阐。中世以后,退溪生于小白之下,南冥生于头流之东。皆岭南之地,上道尚‘仁’,下道主‘义’,儒化气节如海阔山高,于是乎文明之极矣。余生两贤之后,犹是文未坠地自此,以后如下滩之船其势难住,不知更有几重激湍坎窞在也。后来者,必将企余而起羡。”①的确如此,李滉崇“仁”,以高迈之学行潜心著书,弘阐天道性理;而曹植慕“义”,以刚毅之气节反躬践履,化导社会人心。
继踵乏人是南冥学派终为退溪学派所取代的重要原因。对此泽堂李植(字汝固,号泽堂、泽癯居士,1584—1647年)评论道:
岭南则退溪、南冥门脉颇异。退溪门下,西厓、鹤峰、柏潭最有名。而仕宦出入,不复讲学。吴德溪健,学行最高,游于两先生门,早卒无传。赵月川闲退老寿,而士心不附,亦无弟子。曹植高弟,寒冈、东冈为最,而声价皆不及郑仁弘。两冈兼宗退溪,故稍贰于仁弘。仁弘之恶,不待其诛戮而日彰,其门徒皆陷于梼杌,由是岭之下道,亦无学者,唯寒冈为完人。旅轩为高弟,旅轩殁,而亦无徒弟传述者,岭南之学亦止于是。湖南则上道,有李一斋;下道,有奇高峰。高峰早世,不及讲学。一斋弟子虽众,惟金公千镒,以节义著,学则无传焉。郑汝立出于其后,与李泼、郑介清,相应和雄豪一道,为无赖渊薮。及其叛乱,混被诛戮,湖俗浮薄,本不喜儒学,及汝立败,而人以为嚆矢,湖南学者,从此尽矣。②
文中泽堂对李滉、南冥学派的传承脉络作了概要式的说明,有助于我们了解岭南学派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流变状况。兼宗李滉和曹植的郑逑在其《寒冈年谱》(卷一,庚辰38岁)中,也有对于二人为学之异颇有议论。依郑逑之见,李滉德器浑厚,践履笃实,工夫纯熟,阶级分明,学者易于寻入;而曹植则器局峻整,才气豪迈,超然自得,特立独行,学者难以为受。
对于曹植之贡献,郑仁弘(字德远,号来庵,1535—1623年)推崇备至。他在《南冥先生集序》中写道:“惟我先生,早志腾扬,喜读左柳,有躏一世轶千古之气,旋自大悟,一弃旧学,回车易辙,特立独行,凭河不足以为勇,摧山不足喻其力,一向藏修,箴铭〓佩,揭扁堂室,雷龙有舍,鸡伏有堂。其精舍曰山天,壁栖敬义字,亹亹观省,所识者,前言也,往行也。所急者,向里也,践履也。日复一日,终始无间,其涵养之力,造诣之功,盖有不可量者。而当士林斩伐之余,士习偷靡,醉梦成风,人视道学,不啻如大市中平天冠。而先生奋起不顾,竖立万仞,使士风既偷而稍新,道学既蚀而复明。扶颓拯溺之功,在我东国,宜亦未有也。”①经历“己卯士祸”洗礼后整个士林士气低落,此时正是曹植接续“己卯士祸”之前的士林学风加以传扬,开启了为学必以自得为贵、反躬实践为特色的实践儒学传统。
要之,岭南学派的关注点是重振颓坏之社会纲纪,以确立伦理纲常,从而实现儒家所向往的王道社会。因而在性理学上自然倾向主理论,这就是理先气后论、理优位论以及理主气辅论皆出自岭南学脉之缘由。
附注
①“生六臣”是指愤慨于世祖的篡位及灭伦行为而守节去官的六人,即金时习、南孝温、元昊、李孟专、赵旅、成聃寿。“生六臣”以不事二君之志,主张要誓死效忠端宗。还有“死六臣”是指图谋使端宗复位而被发觉处刑之六人,即成三问、朴彭年、河纬地、李垲、俞应孚、柳诚源。以此生、死六臣为首的在野士林与“勋旧派”人士彼此对立。从成宗以后,在野士林中开始有人进出中央官职,这些人对“勋旧”势力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形成两派人士的反目。(参见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版,第108页;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5、145页)
①金时习:《神鬼说》,《梅月堂集》卷20,《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83页。
②参见刘明钟:《韩国思想史》,大邱:以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247页。
③金时习:《神鬼说》,《梅月堂集》卷20,《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83页。
④金时习:《太极说》,《梅月堂集》卷20,《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84页。
⑤金时习:《服气》,《杂著》,《梅月堂集》卷17,《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51页。
⑥金时习:《杂说》,《梅月堂集》卷23,《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417页。
①金时习:《性理》,《杂著》,《梅月堂集》卷17,《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48页。
②金时习:《性理》,《杂著》,《梅月堂集》卷17,《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47页。
③金时习:《杂说》,《梅月堂集》卷23,《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417页。
④金时习:《杂说》,《梅月堂集》卷23,《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417页。
①金时习:《性理》,《杂著》,《梅月堂集》卷17,《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47页。
②金时习:《服气》,《杂著》,《梅月堂集》卷17,《韩国文集丛刊》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51页。
③李滉:《答许美叔》,《退溪全书》(二)卷33,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189页。
④李珥:《金时习传》,《栗谷全书》(一)卷14《杂著》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92页。
①宋时烈:《梅月堂画像跋》,《跋》,《宋子大全》卷147,《韩国文集丛刊》11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61页。
②李珥:《金时习传》,《栗谷全书》(一)卷14《杂著》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92—293页。
①“士祸者,谓士林之受难事变也。自燕山(第十代)朝至明宗(第十三代)朝,士祸屡起。即燕山时,有戊午、甲子二大士祸。中宗(第十一代)时,有己卯士祸。明宗时,有乙巳、丁未士祸。许多士林,酷被斩伐之祸,这间可以谓之士祸期。”(参见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版,第116页)
②这里有必要对韩国儒学的“道学”称谓作一简要介绍。对于“性理学”与“道学”的称谓,尹丝淳教授以为,从根本上来讲,即广义上而言“性理学”与“道学”是同义语。但是,从狭义上而言,二者又有区别:“性理学”多带有探究天理、人性、义理等问题的理论意涵的主知主义色彩;“道学”则更多具有力行其原理的实践主义特点。易言之,“性理学”致力于对客观知识的探究,“道学”则追求实践真知和义理精神。相较而言,“道学”比“性理学”具有更为彻底的“修己”和“安人”一面。故“道学”是借义理、大义(春秋大义)的实现来继承和发展原始儒学道统的“性理学的实践儒学”。(参见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中卷),首尔:东明社1989年版,第144—152页)林月惠教授则指出:朝鲜儒者所谓“道学”内容,实包括朱子所诠释与发展的北宋诸子思想,以及朱子本人思想,其主轴是“程、朱学”。犹有进者,在朝鲜儒者看来,“道学”的内容精髓即是“程、朱学”,有时“道学”与“程、朱学”并称。朝鲜儒者虽然沿用宋代“道学”一词而与汉、唐儒学作区别,但从学派的择取来看,实际指涉“程、朱学”。又指出:性理学的学问性格是穷究天人之际,是深度的哲学思考与哲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作为“为己之学”的性理学也是实践哲学,必有完整的工夫论作为其哲学思考的起点与保证。因此,举凡涉及宇宙根源探问的理气问题,或是反躬自省而究其本源的心性问题,都是性理学关心的焦点。故在朝鲜儒者的思维里,“道学”、“程、朱学”、“性理学”虽有名言之不同,但实际上都是环绕朱子思想而展开的儒学思想。(参见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4—6页)上引二位学者对“道学”的论述,对我们理解韩儒所指称的“道学”概念颇有助益。概而言之,“性理学”与“道学”都主张“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强调“知行并进”的重要性,但是“道学”更为重视基于彻底的涵养省察——“修己”基础上的“安人”,即至治主义王道理想政治。故可将“律身行道”的践履精神,“经世致用”的辅国安民精神视为“道学”思想的根本特色,这一点在赵光祖、李珥等人身上反映得较突出。李珥曾曰:“夫道学者,格致以明乎善,诚正以修其身,蕴诸躬则为天德,施之政则为王道。”又曰:“夫所谓真儒者,进则行道于一时,使斯民有熙皡之乐;退则垂教于万世,使学者得大寐之醒。进而无道可行,退而无教可垂,则虽谓之真儒,吾不信也。”(李珥:《东湖问答·已巳》,《栗谷全书》(一)卷15《杂著》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316、317页)由是而观,朝鲜朝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亦是韩国儒学道学传统内在逻辑的自然展开。
①成宗时,金宗直作弔义帝文,以楚怀王比端宗,西楚霸王比世祖,隐然有诽谤世祖,同情端宗之嫌;而金宗直之弟子,当时担任史官的金驲孙将此弔文编入成宗实录,而引起了所谓“史草问题”。借此“史草问题”的机会,“勋旧”势力借王权而欲除去士林人物,故引起“戊午士祸”(1498年)。以此为发端,接二连三的“甲子士祸”(1504年)、“己卯士祸”(1519年)、“乙巳士祸”(1545年),造成无数士林派的牺牲,如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或被处斩或被流放,这些人物成了“道学派”的主流,后来大部分配享于文庙。此四次士祸,史称“四大士祸”。(参见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5页)
②李珥:《经筵日记》,《栗谷全书》(二)卷2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08页。
③赵光祖:《因不从改正功臣事辞职启三》,《启辞》,《静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22页。
④赵光祖:《弘文馆请罢昭格署疏》,《疏》,《静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8页。
①赵光祖:《谒圣试策》,《对策》,《静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6—17页。
②赵光祖:《谒圣试策》,《对策》,《静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6页。
③《论语·卫灵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7页。
④参见《孟子·尽心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67页。
⑤赵光祖:《谒圣试策》,《对策》,《静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5页。
①赵光祖:《侍读官时启六》,《经筵陈启》,《静庵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29页。
②赵光祖:《谒圣试策》,《对策》,《静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5—16页。
③赵光祖:《谒圣试策》,《对策》,《静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8页。
④宋时烈写道:“盖我箕邦,自殷师以后,上下数千年间道学堙晦,间有郑圃隐、金寒暄诸贤前后倡明之。然其承伊洛之渊源,志唐虞之熙雍,卓然以明德新民,为此学之标准者,则肇自先生(指赵光祖——引者注),不可诬也。”(赵光祖:《绫州谪庐遗墟追慕碑记》,《记》,《静庵集》附录卷4,《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99—100页)
①赵光祖:《参赞官副提学时启一》,《经筵陈启》,《静庵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1—32页。
②赵光祖:《复拜副提学时启十》,《经筵陈启》,《静庵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9页。
①赵光祖:《参赞官副提学时启一》,《经筵陈启》,《静庵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2页。
②赵光祖:《复拜副提学时启十四》,《经筵陈启》,《静庵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9—40页。
①赵光祖:《筵中记事二》,《筵中记事》,《静庵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9页。
②赵光祖:《春赋》,《赋》,《静庵集》卷1,《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2页。
③赵光祖:《春赋》,《赋》,《静庵集》卷1,《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12页。
④赵光祖:《筵中记事一》,《筵中记事》,《静庵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6页。
⑤赵光祖:《复拜副提学时启十三》,《经筵陈启》,《静庵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9页。
⑥赵光祖:《筵中记事一》,《筵中记事》,《静庵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6页。
⑦赵光祖:《复拜副提学时启七》,《经筵陈启》,《静庵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8页。
①赵光祖:《筵中记事二》,《筵中记事》,《静庵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9页。
②赵光祖:《戒心箴序》,《箴》,《静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23页。
①赵光祖:《深谷书院讲堂记》,《记》,《静庵集》附录卷4,《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99页。
②赵光祖:《请从祀疏略》,《附录》,《静庵集》附录卷3,《韩国文集丛刊》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87页。
③奇大升:《论思录下》,《别集附录》卷2,《高峰集》第二辑,韩国东洋哲学会影印1997年版,第140页。
④李滉:《静庵赵先生行状》,《行状》,《退溪集》卷48,《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558—559页。
⑤李珥:《语录上》,《栗谷全书》(二)卷3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57页。
⑥李珥:《经筵日记》(一),《栗谷全书》(二)卷2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09页。
①吴锡源教授也指出,道学与一般以知识为主,单纯追求理论的学问不同,带有很强的实践性。认为,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并通过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以人为本决定了其人道精神,从终极上阐明人道与天理决定了其哲学精神(突出表现为性理学),修炼人格、实践正义决定了其义理精神。他从栗谷的相关论述中总结出,韩国的道学思想兼具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特点。故道学含有理学和义理学等意义,所以只有同时具备纯正本质、缜密理论以及切合实际的实践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学。(参见吴锡源:《韩国儒学的义理思想》,邢丽菊、赵甜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153页)书中作者,对宋代道学思想与韩国道学派、韩国的士人精神与出处义理等问题作了具体阐发,这些论述对理解韩国道学思想特点及韩国儒学的义理精神皆有较大帮助。
②徐敬德:《年谱》,《花潭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19页。
①徐敬德:《诗》,《花潭集》卷1,《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292页。
②李泽堂(1584—1647年)曰:“徐花潭奋起寒微,高节终始。理数之学,追踵康节。静庵以后,无出其右。”栗谷曰:“其论理多主横渠之说,微与程朱不同,而自得之乐,非人所可测也。”(徐敬德:《遗事》,《花潭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29、332页)
③李珥:《经筵日记》(二),《栗谷全书》(二)卷29,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60页。
④张载:《正蒙·太和篇第一》,《张载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7页。
⑤徐敬德:《鬼神死生论》,《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7页。
①徐敬德:《原理气》,《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5页。
②徐敬德:《原理气》,《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5页。
③徐敬德:《鬼神死生论》,《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7页。
④徐敬德:《原理气》,《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5页。
⑤徐敬德:《理气说》,《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6页。
①徐敬德:《太虚说》,《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6—307页。
②“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庄子·列子》,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1页)
③张载:《正蒙·太和篇第一》,《张载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页。
④徐敬德:《原理气》,《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5页。
⑤徐敬德:《鬼神死生论》,《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7页。
①徐敬德:《原理气》,《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5页。
②徐敬德:《花潭集》附录《遗事》中记载:“十四日,朴和叔来见,稳讨张子《太和》篇。花潭所见得,尽是自此做出来也。”(徐敬德:《遗事》,《花潭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29页)
③徐敬德:《遗事》,《花潭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29页。
①徐敬德:《理气说》,《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6页。
②徐敬德:《复其见天地之心说》,《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8页。
③徐敬德:《理气说》,《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6页。
①李滉:《答南时甫》,《退溪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64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4—215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5页。
④徐敬德:《原理气》,《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6页。
⑤徐敬德:《鬼神死生论》,《花潭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07页。
⑥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5页。
⑦李珥:《经筵日记》(二),《栗谷全书》(二)卷29,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60页。
①洪履祥(1549—1615年,字元礼,号慕堂)曰:“花潭徐敬德,守道笃学,为近代儒林之表。”(徐敬德:《遗事》,《花潭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32页)
②李滉:《论人物》,《言行录》卷5,《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32—233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5页。
①忘斋孙叔暾的具体情况,今已无从查考,据载为愚斋孙仲暾之弟。(参见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
②退溪曰:“若吾先生,无授受之处,而自奋于斯学,暗然日章而德符于行,炳然笔出而言垂于后者,求之东方,殆鲜有其伦矣。”(李滉:《行状·晦斋李先生行状》,《退溪先生文集》卷49,《退溪集》,《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568页)
③士林派的“五贤”是指晦斋李彦迪、寒暄堂金宏弼(1454—1504年)、一蠹郑汝昌(1450—1504年)、静庵赵光祖(1482—1519年)、退溪李滉。(参见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尹思淳:《晦斋的“仁”思想》,载《李晦斋的思想与其世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1页)
④“奉次惠韵”诗中写道:“自叹平生心事谬,养真经世两堪羞。”在诗的末尾处,晦斋又加自注曰:“平生有志两事,今俱未遂,岂非可羞耶。”(李彦迪:《奉次惠韵》,《晦斋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76页)
⑤李彦迪:《山堂病起》,《晦斋集》卷1,《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53页。
①《孟子·尽心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51页。
②李滉:《行状·晦斋李先生行状》,《退溪先生文集》卷49,《退溪集》,《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567—568页。
①忘斋孙叔暾和忘机堂曹汉辅均无文集传世,故二人生平事迹及具体学说,今已无从详考。据《成宗实录》记载,忘机堂曹汉辅,曾经是成均馆的儒生。因不满馆长的教导方法,煽动学生集体休学。后被受杖刑,肃夺科举应试资格。忘机堂比忘斋年长一些。“丁巳/司宪府启:‘成均馆首善之地,而师弟之间,有父子之恩,今生员任沚、崔希哲、金俊孙、曹汉辅、李兢,愤长官生员寄斋,一样行楚,极目扬说,悖慢无礼。而又唱为诡激之说,鼓动诸生,效衰世卷堂之事,空馆而去。轻蔑朝廷,大毁名教,罪犯深重。若不痛惩,顽悍之徒,长恶不悛,污染风化,非细故也。请上项崔京哲,决杖一百,任沚拒逆不着,加二等,杖六十徒一年,金俊孙、曹汉辅、李兢,各杖九十收赎,皆永永停举,以戒后来。’从之。”(国史编撰委员会编:《成宗四年癸巳七月》,《朝鲜王朝实录》9卷32,首尔:探求党1984年版,第43页)
②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89页。
①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89—390页。
①此处李彦迪所持的是朱子的立场,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曾曰:“夫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此圣贤之言,所以或离或合,或异或同,而乃所以为道体之全也。今徒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乐言之,而不知夫所谓粲然者之未始相离也。是以信同疑异,喜合恶离,其论每陷于一偏,卒为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而已。岂不误哉!”(参见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②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0页。
①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0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1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1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1页。
①参见苏勇点校:《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2页。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3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3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3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4页。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4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4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4页。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4—395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5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5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5—396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6—397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7页。
③参见彭永捷:《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7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7页。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8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8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8页。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8页。
①李彦迪25岁时任庆州的“州学教官”,27岁时经“副正学”而转任“正学”官职。[参见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中),首尔:东明社1989年版,第206页]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1页。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1页。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6—397页。
④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杂著》,《晦斋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398页。
⑤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7页。
①李彦迪:《大学章句补遗序》,《拾遗》,《晦斋集》卷11,《韩国文集丛刊》2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456页。
②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页。
③李滉:《行状·晦斋李先生行状》,《退溪先生文集》卷49,《退溪集》,《韩国文集丛刊》3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567页。
④李滉:《论人物》,《言行录》卷5,《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32页。
①李滉:《论人物》,《言行录》卷5,《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31页。
②李珥:《经筵日记》(一),《栗谷全书》(二)卷2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09页。
①河谦镇:《东儒学案》中篇第11,《德山学案》。(转引自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372页)
②曹植:《行状》,《南冥集》,《韩国文集丛刊》3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58页。
③参见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页。
④曹植:《祭文》(门人郑逑),《南冥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3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530—531页。
①参见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373页。
②参见刘学智:《南冥“圣学二十四图”辨证》,载《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③李滉:《论人物》,《言行录》卷5,《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33页。
①李瀷:《东方人文》,《天地门》,《星湖僿说》卷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76年版,第18页。
②李植:《杂著(示儿代笔)》,《泽堂先生别集》卷15,《泽堂集》,《韩国文集丛刊》88,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版,第523页。
①曹植:《南冥先生集序》,《南冥集》,《韩国文集丛刊》3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