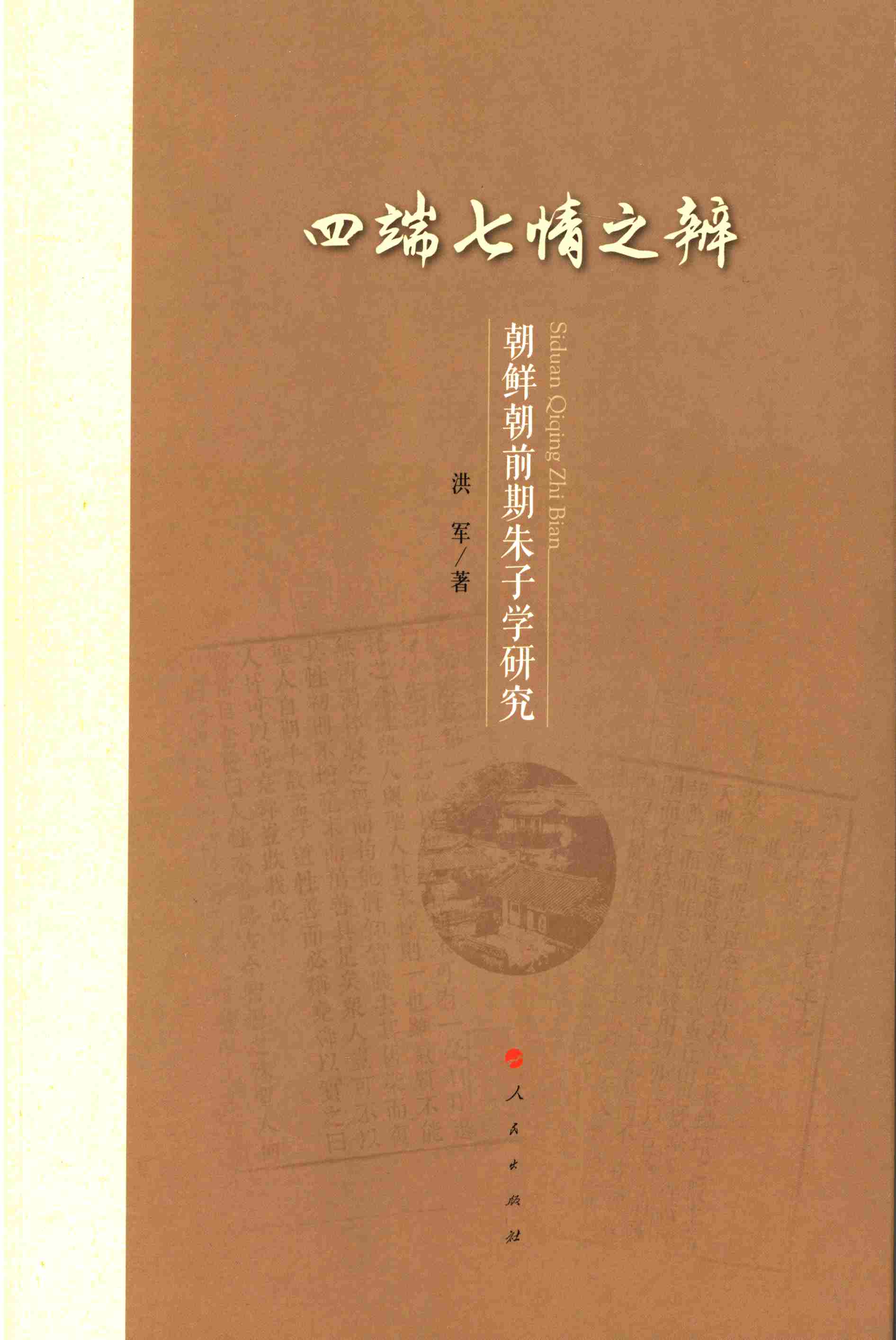内容
儒学思想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东周时代,其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他把“仁”作为儒学的核心理念,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后经由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历代儒学大师的补充与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主干。同时又传播至域外,如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为主的东南亚各国,在东方形成了以汉字及汉文典籍为媒介的儒家文化圈。尤其是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东亚,“独尊朱学(朱子学)”曾蔚为风尚,形成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东亚儒家文化圈”。
在东亚文化圈中受儒学思想影响最深、最广的国家无疑为韩国。对于韩国儒学,学界有过精辟论述。“何谓韩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一些对韩国历史和文化了解浮泛的人认为,韩国儒学就是中国儒学的移植和翻版。此言误矣!固然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学就是以孔子为首的儒者的学说及其思想的总汇。同时应该看到儒者的学说和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随着时势的需求而丰富。由此,儒学才能够像一棵长青之树,像一条湍流不息的长河,永葆青春,永不枯竭。”①诚如斯言,儒学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后便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历程,这种带着民族文化之烙印的儒学就不再是中国儒学的简单移植和翻版,而是具有独立性的“韩国儒学”抑或是“韩国儒教”。
韩国儒者以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精微的逻辑思辨,使儒学在传统的东亚思想世界里发生了重要变化,演变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韩国儒学”。朝鲜王朝(1392—1910年)开国后,朱子学迅速升格成国家意识形态之主流,遂为此后朝鲜朝五百年的官方哲学。
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今天,作为东亚儒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的韩国儒学也将会更加彰显其理论价值与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对高丽末期和朝鲜朝开国之际朱子学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朱子学传入之初的主要人物间的传承系谱的研究①,而对其义理流衍的理论特点关注不足。
本章拟由朱子学在丽末鲜初的传播发展之考察来论述早期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义理特点。
第一节 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
高丽朝后期从武臣执权时起,文教即进入衰落期,至13世纪末整个社会已呈斯文扫地之衰相。此时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新进士类”通过科举迅速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影响王朝政治的一股新兴势力。他们企图从元朝引进程朱理学(朱子学)以重拾社会秩序,进而挽救国家的命运。不过,朱子学的输入还与当时元朝社会思想之状况密切相关。元代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把朱子学定为官方哲学,还将与之对立的陆九渊心学列入另类,致使陆学只能流传于我国江南民间。因朱子学在元代思想界享有独尊地位,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高丽新进士类引进之首选。②这一特征在韩国思想界影响甚远。它一方面使朱子学成为此后朝鲜王朝五百年间的官方哲学,另一方面却影响和阻碍了陆王一系的心学思想在韩国的传播。
一、安珦
据史书记载,朱子学是高丽忠烈王时由安珦从元朝引入。③朱子学虽有“新儒学”、“宋学”、“程朱学”等不同称谓,但其内容则基本相同。①安珦(字士蕴,号晦轩,1243—1306年,朝鲜时代改称为安裕)为兴州(现今顺兴)人。作为高丽朝后期的儒学大家和教育家,被后世尊为韩国性理学的始祖。《高丽史节要》记载其为人庄重安详,在相府能谋善断,常育人才而以兴复斯文为己任。他是高丽忠烈王的宠臣,历任尚州判官、儒学提举、集贤殿大学士、佥议中赞等官职。1289年高丽朝设置儒学提举司,安珦被任命为首任“本国儒学提举”。是年他扈从忠烈王入元,在滞留元大都(燕京)期间始得《朱子全书》,知其为孔门之正脉。遂手录其书,并摹写孔子和朱熹画像而归。这其实为此后朱子学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归国后安珦讲究朱子之书,深致博约之功,努力传授朱子学。“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②他常以兴学育才为己任,“蓄儒琴一张,每遇士之可学者劝之”③。而且,安珦还曾随世子(忠宣王)来过元朝,再次目睹了文教在元朝社会的隆盛状况。
但是,彼时的高丽朝儒学与佛、老思想的盛况相比则呈现一派衰败之势。对此安珦曾作诗慨叹道:“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④这是安珦描绘当时的国子监文庙败落景象的一首诗。
为了重新振兴儒学和恢复荒废的儒学教育机构,他建议朝廷设置“赡学钱”。安珦以为“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⑤,兴学养贤的目的就在于传授孔孟之教,推行儒家的伦理道德。他还曾派博士金文鼎等入元,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等回国。他还荐举李㦃、李瑱等人为经史教授都监使,于是“禁内学馆内侍三都监五库愿学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诸生(指国学七斋与私学十二徒——引者注),横经受业者动以数以百计”⑥。安珦认为朱子发明圣人之道以攘斥禅佛之学,其功足以配仲尼。因此欲学仲尼之道,必须先学晦庵之学。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朱子学开始在高丽社会得到重视。安珦另一功绩是培养出了众多鸿儒硕学,著名者有禹倬、权溥、白颐正等人。其门生也为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珦卒后13年即忠肃王六年(1319年),朝廷为表彰其在兴学养贤方面的功绩,给予从祀文庙之殊荣。朝鲜朝时期则祭祀安珦于白云洞书院。在时任丰基郡守的李退溪的努力下,公元1550年被明宗赐名为“绍修书院”。“绍修书院”是朝鲜朝最早的赐额书院。
二、禹倬
高丽朝后期的名儒禹倬(字天章,又字卓甫,号白云,称为“易东先生”,1263—1342年)是安珦的大弟子,也是早期的朱子学主要传播者之一。禹倬为丹山(丹阳)人,他与白颐正、辛蒇、权溥并称为安珦门下的“四君子”。历任宁海司録、监察纠正等官职,曾官至成均(国学)祭酒。禹倬博通经史,对《易》学造诣尤深。其时,“《程传》(按:指程氏《易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①。可见,禹倬是以《易》学为中心接受程朱之学。禹倬对易学所进行的义理学式的分析,使过去具有神秘性、巫术性的占卜术,在理学的基础上变得更具有理性色彩。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程传》易学的先河,对丽末鲜初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的易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②可见,禹倬在韩国易学史上开启了以义理为中心的《易》学研究(义理易)之先河。
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退溪对禹倬德学十分敬仰,尊其为丽末鲜初的八大儒之一。③退溪不仅建议朝廷在安东创建“易东书院”,而且还对其易学研究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认为:“天相吾东,斯文有迪,我程《易传》,肇臻斯域。人罔窥测,视同发梗,不有先生,谁究谁省……孔演十翼,程氏攸宗,专用义理,发挥天衷。熟玩深味,靡不该通。知益以明,守益以正。以是教人,德业无竞。”①由此亦可推知,朝鲜朝以《易》为中心的程朱性理学传统始于禹倬。
三、权溥
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原名永,字齐万,号菊斋,1262—1346年)为安东人。忠烈王五年(1279年)他年仅18岁即已登第,历任佥议舍人、礼宾寺尹、词林院侍读学、佥议政丞等,封为永嘉府院君,谥文正。忠肃王元年(1314年)同闵漬一起编撰高丽朝太祖以来的实录,忠烈王二十八年(1302年)和忠宣王元年(1309年)分别作为圣节使和正朝使出使元朝。史称权溥“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读书,老不辍。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②。他翻刻朱子学著作,在普及程朱理学方面很有建树。据《栎翁稗说》记载:“我外舅政丞菊斋权公,得《四书集注》,镂板以广其传,学者又知有道学矣。”③而且,他还同其子权准褒集历代孝子64人并使婿李齐贤著赞,定名《孝行录》刊行于世。此外,权溥还注有《银台集》20卷,惜已失传。在他的努力下,忠惠王五年(1344年)高丽改订科举法,“六经义”和“四书疑”遂被定位“初场”之考试科目。④于是,《四书集注》便成为士人们应试所必备的教科书。
四、白颐正
白颐正(字若轩,号彝斋,1247—1323年)为蓝浦郡人,亦是高丽朝后期的名儒。高宗时登第入翰院累官至中书舍人⑤,历任佥议评理、商议会议都监事等,后被封为上党君。他也曾入元,且于元大都(燕京)生活了多年。忠烈王三十一年(1305年)白颐正作为忠宣王的侍臣入元,于忠肃王元年(1314年)归国①,归国时还带回《朱子家礼》等大量朱子学著作。在滞留燕京长达十年期间,白颐正不仅收集了大量程朱理学著作,而且对其学说亦进行了深入研究。《栎翁稗说》记载:“白彝斋颐正,从德陵留都下十年,多求程朱性理之书以归……学者又知有道学矣。”②《高丽史》亦称:“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道先师受孝珠(颐正)。”③与安珦相比,白颐正则在研究和进一步深化程朱理学方面贡献更大,而且,在高丽朱子学的传承方面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弟子朴忠佐(字子华,号耻菴,1287—1349年),官至判三司事,被封为咸阳府院君。其人喜读《周易》,终生致力易学(主要是研读“伊川易”)研究④;另一弟子李齐贤则培养出李穑等丽末鲜初的著名朱子学者。白颐正的遗稿有《燕居诗》、《詠唐尧》、《寒碧楼》、《与洪厓集句》等。
五、李齐贤
高丽末期政治家、史学家李齐贤(字仲恩,号益斋、栎翁,1287—1367年)为庆州人,亦是权溥之贤婿。在早期的朱子学传播者中,李齐贤是卓有建树的一代名儒。他亦有赴元留燕京生活之经历。李齐贤年15岁便登成均试状元榜,历任进贤馆提学、知密直司、政堂文学、判三司事、右政丞、门下侍中等职,被封为鸡林府院君,谥号文忠。1313年,忠宣王让位于太子忠肃王后便以大尉身份留居于元,在燕京构筑万卷堂与当时许多名儒交游。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他将李齐贤召至元大都(燕京)。其时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虞集等咸游王门,李齐贤与他们相从而学益进。门人李穑曾曰:“高丽益斋先生生是时。年未冠,文已有名当世,大为忠宣王器重,从居辇毂下。朝之大儒缙绅先生若牧庵姚公、阎公子静、赵公子昂、元公复初、张公养浩咸游王门,先生皆得与之交际,视易听新,摩厉变化,固已极其正大高明之学。而又奉使川蜀,从王吴会,往返万余里。山河之壮,风俗之异,古圣贤之遗迹,凡所为闳博绝特之观。既已包括而无余,则其疏荡奇气,殆不在子长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优游台阁,则功业成就,决不让向之数君子者。敛而东归,相五朝,四为冢宰,东民则幸矣。其如斯文何?虽然东人仰之如泰山,学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尔雅,皆先生化之也。”①姚燧是许衡(字仲平,号鲁斋,1209—1281年)的门人,元明善则是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1249—1333年)的弟子。时人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二人皆为元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与许衡不同,吴澄因与陆九渊同乡受陆学影响较大,可以说是兼讲朱陆的学者。由此可知,李齐贤应对其时的朱学和陆学都有所了解。
李齐贤在元朝滞留时间较长,其学问造诣亦曾让姚燧、元明善等元朝学者“称叹不置”②。李齐贤回国后,通过兴学养贤,积极推动朱子学的发展。而且,他还栽培李穀、李穑父子,成就了高丽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李齐贤视程朱理学为“实学”,所以在学风上非常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他主张“躬行心得”和“求新民之理”。李齐贤的思想中有较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每欲以经世之学来反对佛教、革新朝政。并且,他还向朝廷提出了诸多志向改革现实政治的建议——这与安垧、白颐正有较大区别。从李齐贤所提倡的“为学次序”③中又可以看出其对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学思想的重视。李齐贤的著作有《益斋乱稿》(10卷)、《栎翁稗说》(4卷)、《益斋长短句》等。
综上所述,作为儒学新形态的程朱理学(朱子学)主要是通过由出使元朝的使臣传入韩国。经过他们的积极倡导和推动,朱子学在高丽朝的知识界获得了初步的传播。④值得注意的是,从《高丽史》的记载来看,高丽朱子学的传承主要是由安珦及其弟子来完成。换言之,高丽的朱子学是由安珦开其端,并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加以传承并发扬之。因此,安珦在高丽乃至韩国儒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理应得到重视。但是,这一时期还处于韩国朱子学义理思想的萌发阶段,故在理论创获上成就有限。
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这一时期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朱子学义理在高丽社会得到初步普及的同时获得新进士林阶层的认同;二是为下一阶段韩国朱子学义理思想的勃发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
第二节 丽末鲜初的朱子学
至丽末鲜初即高丽、朝鲜两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思想界涌现出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吉再、朴础等著名朱子学者。刚刚传入半岛的朱子学顺应时代潮流,成为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并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一、李穑
高丽末期重臣、著名的朱子学家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是“丽末三隐”之一,历任典理正郎、内书舍人、政堂文学、判三司事等官职,谥文靖。作为李齐贤的门人和李穀的儿子,李穑可谓是继承了丽末朱子学正脉的一代儒学宗匠。他在韩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所谓“承上”、“继往”,是说他的儒学仍具有早期政治儒学的色彩;所谓“启下”、“开来”,是讲其学与高丽前期的政治儒学已有本质区别。李穑以朱子学为其政治儒学的核心内容。他说:“孔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出政治,正性情,以一风俗,以立万世大平之本。所谓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者,讵不信然。中灰于秦,仅出孔壁。诗书道缺,泯泯棼棼。至于唐韩愈氏,独知尊孔氏,文章遂变。然于《原道》一篇,足以见其得失矣。宋之世,宗韩氏学古文者,欧公数人而已。至于讲明邹鲁之学,黜二氏,诏万世,周程之功也。宋社既屋,其说北流。鲁斋许先生,用其学相世祖,中统至元之治,胥此焉出,呜呼盛哉。”②正如前文所述许衡是元朝正宗理学大儒,其学以朱子为宗,在北方影响甚大。李穑之父游学中国时与许鲁斋的门人颇有交往,受其父之影响的李穑既推崇韩欧之文章、周程之理学,又向往许氏以学辅治的为学径路。①“宋社既屋,其说北流”,表明李穑俨然将鲁斋视之为南宋灭亡后承传朱学之第一人。其时入元求学的高丽学者大都深受鲁斋之学的影响。由此论之,许衡不仅在朱学北传过程中功绩卓越,而且对丽末朱子学的发展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李穑在构建学理层面的儒学中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对丽末鲜初的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他的极具学术意义的理论主张,如“天则理”、“一而二,二而一”等,成为日后韩国性理学的基本理念。②他任成均馆大司成时不仅亲自讲授朱子学,还聘金九龙、郑梦周、李崇仁等为教官,培养了一大批儒生,为朱子学在高丽全境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丽史》上称,恭愍王十六年“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馆大司成,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士金九龙、郑梦周、朴尚忠、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日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坌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③。李穑将程朱理学视为儒学之正脉,强调学者应以“明明德”为首要之务。认为:“以吾儒言之,曰明命,以天言之;曰明德,以人言也。顾明命明明德,学者之事也。”④又说:“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非二物也。而天与人判而离也久矣,仲尼盖悲之,道统之传,不绝如线,幸而再传,有圣孙焉,著为一书,所以望后人者至矣。”⑤此处“明德”指的是“性”,即所谓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他看来,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由此李穑提出自己的“天人无间”思想:“虽道之在大虚,本无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气为然。是以大而为天地,明而为日月,散而为风雨霜露,峙而为山岳,流而为江河。秩然而为君臣父子之伦,粲然而为礼乐刑政之具,其于世道也,清明而为理,秽浊而为乱,皆气之所形也。天人无间,感应不惑。故彝伦叙而政教明,则日月顺轨,风雨以时。而景星、庆云、醴泉、朱草之瑞至焉。彝伦斁而政教废,则日月告凶,风雨为灾,而彗孛飞流、山崩水渴之变作焉。然则理乱之机,审之人事而可见,理乱之象,求之风月而足矣。”①他还以为今中原甫定,四方无虞,正是所谓“理世”。若能趁此机会修国之政刑,将会使百姓安康、物产丰盛。李穑进而又从“天人无间”论立场出发提出“天则理”思想:“天则理也,然后人始知人事之无非天矣。夫性也,在人物,指人物而名之曰人也物也,是跡也。求其所以然而辩之,则在人者性也,在物者亦性也。同一性也,则同一天也。”②他反对将天和人、命和性分而为二。
同时,李穑还基于性理学的道统观,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佛教的弊端提出了批评,指出:“佛氏入中国,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汉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为国,佛刹民居,参伍错综,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两宗为利之窟,川傍山曲无处非寺……佛大圣人也,好恶必与人同。安知已逝之灵,不耻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条禁,已为僧者,亦与度牒,而无度牒者,即充军伍。新创之寺,并令撤去,而不撤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尽髡缁。臣闻殿下奉事之诚,尤笃于列圣。其所以祈永国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窃惟佛者至圣至公,奉之极美不以为喜,待之甚薄不以为怒。况其经中分明有说‘布施功德,不及持经’,听政之余,惟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顿法,无所不可。但为上者,人所则效,虚费者,财所耗竭,防微杜渐,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臣愿于佛,亦宜如此。”③以上所引文字是恭愍王元年李穑所上《陈时务书》中的部分内容,《高丽史》和《东文选》皆有记载。他以为,制民产、兴王道就是要从辟异端开始,具体而言即为抑制佛教流弊的蔓延和佛教徒的发展。不过,需注意的是,李穑的斥佛论主张不是对佛教的教理本身进行批驳,像“佛大圣人也”、“佛者至圣至公”这样的言论还受到后世儒者的讥评。④但是,从上述李氏的抑佛言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丽末接受朱子学(新儒学)思想的新进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态度和此一时期思想界新的理论动向。
在政治上,李穑主张以“三纲五常”为立国之本,企图重建理想的儒家王道政治。在新旧王朝更替时他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革新派的田制改革。1392年革新派赵浚、郑道传等人与李成桂密切配合,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由此朱子学获得了官学的地位,进而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李穑的著作有《牧隐集》(55卷)。
二、郑梦周
“丽末三隐”之一的郑梦周(字达可,号圃隐,1337—1392年)亦是高丽末期的政治家、朱子学家、文学家,被李滉等人称为“东方理学之祖”①。恭愍朝登第,历任成均馆博士、政堂文学、右文馆大提学、侍中等官职,谥文忠。《高丽史》上称郑梦周“生而秀异”,并说:“以礼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指郑梦周——引者注),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脗合,诸儒尤加叹服。”②由此亦可知,郑氏的确天分甚高。早年曾从游于李穑门下,但是其为学并无一定师承③,多为自悟自得。权採还曾提到:“乌川圃隐郑文忠公生于高丽之季,天资粹美,学问精深。其为学也,以默识心融为要,以践履躬行为本。性理之学,倡道东方,一时名贤,咸推服焉。”④权氏对其为学特点的概括甚为精辟——朱子学的穷理与践履精神在郑梦周的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郑梦周一生好学不倦,不仅博览群书、精研义理,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广程朱之学。《高丽史》记载,他曾“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①。郑氏的心志和作为开了朝鲜儒教兴起之先河。
其时明朝已经开国。暗图废弃蒙元服饰的郑梦周敦请朝廷施行大明的衣冠文物。在丽末“亲元派”与“亲明派”的势力纷争中力主“绝元归明”之外交对策,终成作为《春秋》尊王攘夷观之变种的“尊华排胡论(华夷论)”的主要倡导者。
郑氏对朱子学有很深的体会,其理论造诣深得同时代学者的赞赏。李穑曾说:“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②以为他对朱子学的精深研究和哲学思考已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郑道传亦曾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至于《易》,知先天后天相为体用;于《书》,知精一执中为帝王传授心法;《诗》则本于民彝物则之训;《春秋》则辨其道谊功利之分。吾东方五百年,臻斯理者几何人哉。诸生各执其业,人人异说。随问讲析,分毫不差。”③可见,梦周不仅对“四书”之要有深切的体会,而且对“五经”之义亦有精湛的研究。
郑梦周以为“天人虽殊,其理则一”④,还说:“造化无偏气,圣人犹抑阴。一阳初动处,可以验吾心。”⑤他在坚持“天人一理”之立场的同时,主张理对气的优位性和主宰性,而对理的主宰性的重视恰恰是朱子学的核心要领。
在竭力倡导“濂洛之道”及朱子学的同时,他还对佛、老之说提出了质疑。“如天之圆,广大无边,如镜之照,了达微妙。此浮屠之所以喻道与心,而吾家亦许之以近理。然其圆也,可以应万事乎,其照也,可以穷精义乎。吾恨不得时遭乎灵山之会,诘一言于黄面老子。”①郑梦周从朱子学的立场出发指出佛、老理论的局限性。他还对儒佛的基本教理作了进一步的比较,认为:“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动静语默之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彼佛氏之教则不然,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是岂平常之道?”②郑氏主张儒者之道皆是日用平常之事,如饮食男女人所同,而此中便存有至理——所谓尧舜之道亦不外乎此。动静语默之间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但是佛氏之教则不然,虚伪乱常、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以观空寂灭为宗。③他将佛教指斥为以“观空寂灭为宗”的妖妄怪诞之教,并从教义、教理的层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同时,他还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以取代佛教仪式,行冠婚丧祭,并亲自为父母服丧了三年。郑氏是继李穑之后又一位提倡“崇儒抑佛”的朱子学者。与李穑等人不同,郑氏更多从人伦道德层面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驳,故其辟佛论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其对佛教教义和教理的精深了解。
郑梦周弟子众多,其门人大都成为引领朝鲜朝初期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学脉传承关系大致如下:④
仅从图1中看,在其门下涌现的勋旧派士人多于士林派学人。但是郑氏及其弟子吉再以自身的学行和践履诠释了性理学的理念和价值标准,由此确立了重价值判断过于事实判断的士林派的道统意识。所以韩国17世纪的儒学巨擘尤庵宋时烈(1607—1689年)曾对圃隐郑梦周称颂道:“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⑤
郑氏35岁和47岁时曾两度作为高丽使节入明,他也是在高丽朝廷内力倡亲明外交的代表人物。两朝更替之际,他对高丽王朝忠心耿耿,最终以身殉之,真正践行了孟子所谓“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的儒家教义。故后人赞曰:“公天分至高,豪迈绝伦。少有大志,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日诵《中庸》、《大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真积力久,独得濂洛不传之秘。故其措诸事业发于议论者,十不能二三,而光明正大,固已炳耀青史,真可谓命世之才矣。”①郑梦周的“忠臣不事二君”的至死不变之节义被李朝君臣高度推崇,这也是他被尊为“韩国义理学派之祖”②以及“东方理学之祖”的重要原因之一。郑梦周的著作有《圃隐集》(7卷)。
三、吉再
丽末鲜初期的著名朱子学者还有吉再(字再父,号冶隐,又号金鸟山人,谥号忠杰,1353—1419年),海平(善山)人。他曾受学于李穑、郑梦周、权近等人,与李穑、郑梦周同被尊为“丽末三隐”。作为朝鲜士林派学者的先驱,吉再为学极重真知与实得,主张学者应以忠孝礼义廉耻为先。《冶隐集》记载,吉再与弟子“讲论经书,必务合于程朱之旨,言必以忠孝为主”①。弃官退隐乡野则专心于读书涵养,还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大兴“私学”教育,开了朝鲜私学教育之风气。其学脉连绵不绝,如图1所示后学中涌现出金叔滋、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一大批活跃于朝鲜朝前期学界和政界的大儒。受其思想影响的岭南“士林派”后来逐渐成长为对抗腐败之“勋旧派”②的批判势力,且在成宗朝后成为主导中央朝政的重要力量。权近也对吉再称誉道:“呜呼!有高丽五百年培养教化,以励士风之效,萃先生之一身而收之。有朝鲜亿万年扶植纲常,以明臣节之本,自先生之一身而基之,其有功于名教甚大。”③吉再的义理思想和节义精神奠定了朝鲜朝初期儒学实践的发展方向,所以他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其实,郑梦周、吉再等人的义理精神与新罗花郎的为国尽忠之精神可谓一脉相承。④朝鲜朝前期义理派学者的理论探讨和教育实践活动,为韩国朱子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吉再的主要著作有:《冶隐集》、《冶隐续集》、《冶隐先生言行录拾遗》等。
高丽末至朝鲜朝开国前后是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初创期,因为正处于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此时在统治阶层内部和意识形态领域亲明与亲元、革新与守常、事大与自主之争异常激烈。朱子学作为新的理论学说传入韩国后,开始分化为强调人伦义理的保守势力和重视现实问题的革新势力。两派立场上的差异源自各自对性理学(朱子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理解。以郑梦周为首的“纲常论”者首重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强调忠孝节义,重视大义名分,因此这一派也被称为“节义论”者;以郑道传为首的“革新论”者则强调《周易》的变易思想,主张应根据时势之迁移主动求变,从而革新现实政治。①郑梦周、吉再、金叔滋、金宗直等属于“纲常论”者,他们基于春秋大义反对异姓革命,拒绝同革新势力妥协。于是新朝建立后他们或遭杀害,或被革职,余下的则大多归隐山林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以教化民众为务。结果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和政坛便被主张权变的郑道传、权近一系的革新势力(“事功派”,亦称“官学派”)所掌控。郑道传死后,权近继承其学风成为“事功派(官学派)”的领袖。此派学风特点是重视功利实用,必以经世为鹄的。此后,“事功派”又逐渐演变为“勋旧派”,成为“士林派”批判和拒斥的对象。
简言之,丽末鲜初期不仅是韩国高丽、朝鲜两个新旧王朝更替时期,而且还是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初创时期。此一时期的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可划分为两个阶段: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阶段和朝鲜朝开国前后义理的初步自觉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安珦、禹倬、白颐正、李齐贤等,而后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则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吉再等。朝鲜王朝开国后,朱子学迅速上升为社会主流思想,进而成为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
第三节 郑道传斥佛论与朱子学“官学”地位之确立
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②)生于庆尚道奉化,是丽末鲜初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诗人。他于1362年中进士第,先后在高丽朝任三司右使、右军都总制使等。1392年拥立李成桂(朝鲜太祖,1335—1408年)以创朝鲜王朝,成为李朝的开国功臣。作为性理学者郑氏向往儒家王道政治,提出以宰相制为主的朝政运作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措施,在新朝中央集权的两班官僚体制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后人誉为“朝鲜王朝的设计者”。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诸多领域,而哲学方面代表作有《佛氏杂辨》、《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等。此外,据传还有《学者指南图》。其中《佛氏杂辨》一书是朝鲜朝排佛崇儒国策的理论根据和基础。
郑道传是丽末重臣、著名朱子学者李穑的门人,同时还是权近的老师。在两朝交替之际,郑氏作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与李成桂相互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抑佛崇儒”的思想文化政策,并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学理上对佛教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驳。这是他的主要理论贡献。郑道传在斥佛过程中还吸收程朱的理学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性理学理论。本节仅对其性理学及斥佛论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一、郑道传的性理说
郑道传被称为“东方真儒”。正是通过他的积极阐发和努力,朱子学理气论、心性论的诸多观念和思想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朱子理学亦称为道学,其道器说与理气说密切相连,在新儒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多数性理学家皆将二说作为思想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借“道”、“器”、“理”、“气”一类的本体论概念探讨天地万物之源也就是世界之本源。
郑道传的道器说大体承袭了程朱的学说。“道则理也,形而上者也。器则物也,形而下者也。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即身心而有身心之道,近而即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远而即于天地万物,莫不各有其道焉。人在天地之间,不能一日离物而独立。是以,凡吾所以处事接物者,亦当各尽其道,而不可或有所差谬也。此吾儒之学所以自心而身而人而物,各尽其性而无不通也。盖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者也。”①以形上、形下区分道器的同时,他还强调了二者的不离不杂性,即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郑道传进而据此批评佛教,指出佛教昧于道器之辨而以道器为二物。“彼佛氏于道,虽无所得,以其用心积力之久,髣髴若有见处。然如管窥天,一向直上去,不能四通八达。其所见必陷于一偏见。其道不杂于器者,则以道与器歧而二之。乃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必欲摆脱群有,落于空寂见。其道不离于器者,则以器为道。乃曰善恶皆心,万法唯识,随顺一切,任用无为,猖狂放恣,无所不为。此程子所谓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者也。然其所谓道者,指心而言,乃反落于形而下者之器而不自如也。”①郑道传主张佛教“道与器歧而二之”的“道器”两极化的思想根于其“万法唯识”、“诸相非相”观念,结果导致“以器为道”,使“道”无别于形而下者之器。这表明郑氏不仅对程朱的道器说有准确的理解,而且对佛教理论要害处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在大作《天答》篇中,郑氏弟子权近对其“理”有进一步的解释。“天即理也,人动于气者也。理本无为而气用事,无为者静,故其道迟而常。用事者动,故其应速而变。灾祥之不正,皆气之使然也。是其气数之变,虽能胜其理之常者。然此特天之未定之时尔。气有消长,而理则不变,其久而天定,则理必得其常。而气亦随之以正,福善祸淫之理,岂或泯哉。”②以“道则理”和“天即理”来规定“理”,那么“道”和“天”就应理解为“太极”。“无极而太极”——理只是作为万物运动变化之所以然而存,所谓“凡所以为当然之则而不可易者是理也”。郑道传指出理具有无为、不变之特性,气则具有能用事、消长之特性。而且郑氏还把“理”理解为是纯粹而至善的形而上之存有亦即人之性。“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③在理气先后及理气关系问题上,他坚持了理在气先说以及理主宰气之说,所谓“于穆厥理,在天地先,气由我生,心亦禀焉”④。对此,权近则进一步解释道:“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四时于是而流行,万物于是而化生。人于其间,全得天地之理,亦全得天地之气,以贵于万物而与天地参焉。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又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①
在《佛氏杂辨》中,郑道传写道:“盖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毕竟先有太极,而天地万物之理,已浑然具于其中。故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如水之有源,万派流注,如木之有根,枝叶畅茂。此非人智力之所得而为也,亦非人智力之所得而遏也。然此固有难与初学言者,以其众人所易见者而言之。”②理先气后是关乎朱子哲学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理先气后,朱子的思想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年他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理在气先的思想是在离开南康之后经朱陈之辨和朱陆太极之辨才逐步形成的。理能生气说曾是其理先气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他的晚年定论则是逻辑在先——此说是在更高形态上返回本体论思想,可谓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并不是对立面的演进和交替,在本质上,是以不同形式确认理对于气的第一位性以及理的绝对性。③郑道传在朱子学这一基本问题上坚持“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的理先气后说。以道器规定理气,以强调二者不离不杂性,从而赋予理以“其尊无对”性——这样的理在气先的理解可以说是郑道传理气说的主要内容。上述思想我们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者的学说中亦可找到其端绪。
儒家以“内圣外王之道”为宗旨:内圣成己,外王成物。而内圣之学实质上也就是心性之学。作为研究人的本质以及自我价值应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内圣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宋儒融儒、道、佛三家心性理论为一体(以儒为主),建立了以自我超越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从而将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因此,理学亦称“道德性命”之学或“心性”之学,说明它是以心性为中心范畴的道德形而上学。
在郑道传的哲学著述中,对心性的论述所占比重较多,如《佛氏杂辨》19篇文章中“佛氏心性之辨”、“佛氏心迹之辨”、“儒佛同异之辨”、“辟异端之辨”以及《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等都集中涉及“心性”问题。其中,《心气理篇》的“心”是指佛教的“修心”,“气”是指道家的“养气”,“理”则指性理学的“性理”。即佛教因修心而视现实为虚妄,道家则为养生而否定思虑与分别。而以“理”为生成之理和当为之理的儒家性理学则可兼摄佛道的理论。①
郑道传的心性思想大体继承了朱子的心性情三分构架体系和“心统性情”论。权近在为三峰《心气理篇》中的《心难气》一文加注时说:“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漠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虽曰应万事,而是非错乱,岂足为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有其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郑道传认为“心”是理气之合,亦为一身神明之舍。此时的心中之理即为所禀之德,所谓“理者,心之所禀之德而气之所由生者也”③。他讲到的“德”乃仁义礼智之性,即天之所令而人之所得者。郑氏在《心问》篇中写道:“始者赋命之初,必与人以仁义礼智之性,是欲使人循是性而为善也。”④人心之理虽为上帝所命,但其义理之公因被物欲所胜,致使其善恶之报也有颠倒。若以义理养心则无物欲之蔽,由是全体虚明而大用不差。郑道传据此提出“志帅气卒”的思想:“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皆不坚守,弃臣从敌,以臣之微,孤立单薄。”⑤权近进一步解释曰:“志者,心之所之也。吾亦心之自称也。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注曰,志固心之所之,而气之将帅。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而为志之卒徒也。心为天君,以志统气而制物欲,犹人君之命将帅,以率徒众而御敌人也。故曰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然志苟不定,则物欲得以夺之,而理不能以胜私矣。故其志之为帅与其气之为徒卒者,皆不能坚守其正,反弃吾心而从物欲。故吾之此心,虽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单弱而薄劣也”①。“志”是心之所之,心是天君。以志统气而制物欲,犹人君之命将帅以率众御敌。故曰“志吾之帅,气吾徒卒”。“志”若不定则物欲得以夺之,而理不能以胜私。故其志之为帅与其气之为徒卒者,皆不能坚守其正,反弃吾心而从物欲。故吾之此心,虽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单弱而薄劣。以我一心之微,而当众欲之攻,虽甚微弱而薄劣。因此,郑道传写道:“诚敬为甲胄,义勇为矛戟,奉辞执言,且战且服,顺我者善,背我者恶,贤智者从,愚不肖逆,因败成功,几失后获。”②以为若能以诚敬为甲胄而自守,则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夺。义勇为矛戟而自卫,则所以裁制者严而欲不得侵犯。这便是“内外交相养之道”③。
因“志”为心之所之,故“志”不定则理不能胜私欲,或者说“志”不能统气而制物欲。若能以诚敬为甲胄而自守,则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夺;若能以义勇为矛戟而自卫,则所以裁制者严而欲不得侵犯天理,正所谓“方寸之间,私欲净尽,则吾心之理,即在天之理。在天之理,即吾心之理,脗合而无间者也。”④因此,学者“存心养气”应以“以义理为之主”。郑道传指出:“有心无我,利害之趋,有气无我,血肉之躯,蠢然以动,禽兽同归,其与异者,呜呼几希。”⑤对此权近则进一步解释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义理也。人而无义理则其所知觉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矣。其所运动者,亦蠢然徒生而已矣。虽曰为人,去禽兽何远哉。此儒者所以存心养气,必以义理为之主也。”⑥将是否存有“义理”视为人异于禽兽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
郑道传的心性论思想在其《佛氏心性之辨》一文中有较集中的论述。他写道:
心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气,虚灵不昧以主于一身者也。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盖心有知有为,性无知无为。故曰心能尽性,性不能知检其心,又曰心统情性,又曰心者神明之舍,性则其所具之理,观此心性之辨可知矣。彼佛氏以心为性,求其说而不得,乃曰:迷之则心,悟之则性。又曰:心性之异名,犹眼目之殊称至。楞严曰:圆妙明心,明妙圆性,以明与圆分而言之。普照曰:心外无佛,性外无法,又以佛与法分而言之,似略有所见矣。然皆得于想象髣髴之中而无豁然真实之见,其说多为游辞而无一定之论,其情可得矣。吾儒之说,曰尽心知性,此本心以穷理也。佛氏之说,曰观心见性,心即性也,是别以一心见此一心,心安有二乎哉?彼亦自知其说之穷,从而遁之曰:以心观心。如以口齿口,当以不观观之,此何等语欤?且吾儒曰:方寸之间,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其曰虚灵不昧者,心也;具众理者,性也;应万事者,情也。惟其此心具众理,故于事物之来应,之无不各得其当,所以处事物之当否而事物皆听命于我也。此吾儒之学内自身心,外而至于事物,自源徂流,一以通贯,如源头之水,流于万物,无非水也。如持有星之衡,称量天下之物。其物之轻重与权衡之铢两相称,此所谓元不曾间断者也。佛氏曰空寂灵知,随缘不变,无所谓理者具于其中,故于事物之来,滞者欲绝而去之,达者欲随而顺之,其绝而去之者,固己非矣,随而顺之者,亦非也。其言曰,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听其物之自为而已,无复制其是非而有以处之也。是其心如天上之月,其应也如千江之影,月真而影妄,其间未尝连续如持。无星之衡,称量天下之物,其轻重低昂惟物是顺。而我无以进退,称量之也。故曰: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学者所当明辨也。①
可见,郑道传是以程朱心性学说为基础展开了对佛教“性空”论的批评,并得出“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的结论。
二、郑道传的斥佛论
在韩国哲学史上,真正具系统性、理论性的斥佛论的出现始于郑道传、权近师徒。《佛氏杂辨》和《心气理篇》即为反映其斥佛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在同佛教的论战中,郑道传基于儒佛思想之异系统发挥性理学(朱子学)的观点并对佛教根本教义逐一进行了批驳。
《佛氏杂辨》就是一部从性理学的立场出发批驳佛家祈福之虚构性以及僧侣寺庙之弊害的著作。此外,其作还涉及佛教的理论弱点。此书写于1398年,主要围绕以下19个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以阐述其斥佛论主张。(1)佛氏轮回之辨;(2)佛氏因果之辨;(3)佛氏心性之辨;(4)佛氏作用是非之辨;(5)佛氏心迹之辨;(6)佛氏昧于道器之辨;(7)佛氏毁弃人伦之辨;(8)佛氏慈悲之辨;(9)佛氏真假之辨;(10)佛氏地狱之辨;(11)佛氏祸福之辨;(12)佛氏乞食之辨;(13)佛氏禅教之辨;(14)儒释同异之辨;(15)佛法入中国;(16)事佛得祸;(17)舍天道而谈佛果;(18)事佛甚谨年代尤促;(19)辟异端之辨。而且,在文中他还援引了许多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等人的有关抑佛扬儒的论述。
仅从《佛氏杂辨》题目来看,郑道传对佛教的批判是相当系统而全面的。在驳斥佛教“因果轮回”等基本教义的过程中,提出天地万物由“气”形成之气化论观点。《佛氏轮回之辨》中提到:
人物之生生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原夫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其己生者,生而过;未生者,来而续。其间不容一息之停也。佛之言曰: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于是,轮回之说兴焉。《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先儒解之曰: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于太虚之中,则知其死也,与气而俱散无复留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内。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天地阴阳之气交合复成人物。到得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复,是变了粗气为物,是合精与气而成物,精魄而气魂也。游魂为变,变则是魂魄相离,游散而变。变非变化之变,既是变则坚者、腐存者込无物也。天地间如烘炉,虽生物皆销铄己尽。安有已散者复合而已生者复来乎?今且验之,吾身一呼一吸之间,气一出焉,谓之一息。其呼而出者,非吸而入之也。然则人之气息亦生生不穷,而生者过,来者续之,理可见也。外而验之于物,凡草木自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一气通贯。当春夏时,其气滋至而华叶畅茂;至秋冬,其气收敛而华叶衰落;至明季春夏又复畅茂,非已落之叶返本归源而复生也。又井中之水,朝朝而汲之,喝饮食煮,煮而尽之;濯衣服者,日曝而干之,泯然无迹。而井中之泉,源源而出,无有穷尽,非已汲之水返其故处而复生也。且百谷之生也,春而种十石,秋而收百石,以至千万,其利倍蓰,是百谷亦生生也。今以佛氏轮回之说观之,凡有血气者自有定数,来来去去无复增损。然则天地之造物反不如农夫之生利也。且血气之属,不为人类,则为乌兽鱼龟昆虫。其数有定,此蕃则彼必耗矣,此耗则彼必蕃矣。不应一时俱蕃,一时俱耗矣。自今观之,当盛世人类蕃庶,乌兽鱼龟昆虫亦蕃庶;当衰世人物耗损,乌兽鱼龟昆虫亦耗损。是人与物皆为天地之气所生,故气盛则一时蕃庶,气衰则一时耗损,明矣。予愤佛氏轮回之说惑世尤甚。幽而质诸天地之化,明而验诸人物之生,得其说如此,与我同志者幸共鉴焉。
或问子引先儒之说,解《易》之游魂为变曰:魂与魄相离,魂气归于天,体魄降于地,是人死则魂魄各于天地,非佛氏所谓人死精神不灭者耶?曰:古者四时之火,皆取于木,是木中元有火,木热则生火。犹魄中元有魂,魄暖着为魂,故曰钻木出火。又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形魄也,神魂也。火缘木而存,犹魂魄合而生。火灭则烟气升而归于天,灰尽降而归于地。犹人死则魂气升于天,体魄降于地。火之烟气即人之魂气,火之灰尽即人之体魄。且火气灭矣,烟气灰尽不复合而为火。则人死之后,魂气体魄亦不复合而为物。其理岂不明甚也哉。①“轮回”乃梵文Samāra的意译,原意为“流转”。原是印度婆罗门教教义,后为佛家沿用发展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宣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果得不到“解脱”,则会永远在所谓“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或无阿修罗道而为“五道轮回”)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故称“六道轮回”。这种“轮回”说的核心是灵魂不灭,即人死后其精神不死。根据其人一生所做的“业”,灵魂还会在来生以至二生三生承受业报。①基于灵魂不灭论的“轮回”说是佛教世界观和信仰核心理论。
郑道传以朱子学“气化”论以及“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对之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②。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而“形质”与“神气”必然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人死了精神便无以存在,所谓“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同时,他还提出事物总是处于发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中的辩证思想。“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此“生生无穷”之运动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带有发展进步的质的变化。
郑道传以“气化”和“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说明了人与物类能够不断繁衍的原因,一方面有力地批驳了佛教“轮回”说的理论基础——精神不灭论,另一方面也使儒家关于“气”的理论得以挺立和张扬。③他还以此说为基础进一步批评了作为“轮回”之理论依据的“因果报应”说:“或曰吾子辨佛氏轮回之说至矣,子言人物皆得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今夫人则有智愚贤不肖、贫富贵贱寿夭之不同,物则有为人所畜役劳苦至死而不辞者,有未免纲罗钓戈之害、大小强弱之自相食者,天之生物,一赋一与何其偏而不均,如是耶?以此而言,释氏所谓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者,不其然乎。且生时所作善恶是之谓因,它日报应是之谓果。此其说不亦有所据欤?曰予于上论人物生生之理悉矣。知此则轮回之说自辨矣。轮回之说辨,则因果之说不辨而自明矣。”①可见,郑氏是把儒家“气”论思想作为其批评佛教的主要理论工具的。他以朱子学的“气禀”说批驳佛家因缘和合论和因果报应说:“夫所谓阴阳五行者,交运迭行、参差不齐,故其气也有通塞、偏正、清浊、厚薄、高下、长短之异焉。而人物之生,适当其时。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人与物之贵贱于此焉分。又在于人得其清者智且贤,得其浊者愚不肖,厚者富而薄者贫,高者贵而下者贱,长者寿而短者夭,此其大略也。虽物亦然。”②
朱熹认为当理化生形气之时,理气浑然相融,具体到形成人物的时候,理即具于形气之中形成人的气禀。人物的气禀不仅有偏与正的问题,还有清与浊的问题。③朱子说过:“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④郑道传援引朱学“气禀”说,进一步指出人与物之区别、人与人之差异皆由气禀的不同造成的,并非出于佛教所谓因果报应。他在《佛氏因果之辨》篇的文末写道:“圣人设教,使学者变化气质,至于圣贤治国者,转衰亡而进治安。此圣人所以回阴阳之气,以致参赞之功者。佛氏因果之说,岂能行于其间哉?”⑤可以看出,郑道传反对佛学主要是出于其“灭伦害国性”⑥。因此,他在《辟异端之辩》文中指出:“以予惛庸,不知力之不足,而以辟异端为己任者,非欲上继六圣一贤之心也。惧世之人惑于其说,而沦胥以陷,人之道至于灭矣。呜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必士师。邪说横流,坏人心术,人人得而辟之,不必圣贤。此予之所以望于诸公,而因以自勉焉者也。”⑦
朱熹反对佛学同样出于其对人伦道德的危害性,所谓“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①。不过,其对佛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禅宗。朱熹尝言:“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绝灭犹未至尽,佛则人伦坏;禅则又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故其为害最深。”②此外,他还认为佛教尤其是禅宗将“心”与“性”视为一物,沦空而耽寂。“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细见得真实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政使有存养之功,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亦不可谓之不能养,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③心性一旦沦空耽寂即如浮光掠影无以致存养之功。由此可见,朱子学与佛学在心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别。④
由上所述,郑道传欲构筑的“善恶因果报应”说既没有借助佛之法力,也没有借助天(上帝)之主宰,而是仰仗人的主观能动性亦即所谓“主体性”。他以为尽管人时有不善之行为,但因“理”的不变性和主宰性,只须力克私欲便可变化气质,从而将不善之行为变为善行。他强调人的“主体性”,要求人们依靠良善意志和自身努力来战胜“恶”。这说明无论行为之动机还是果报皆系于自身之作为。郑道传的理论虽无佛教因果报应说之效力,却洋溢着合理主义的精神。他确立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大有异于建立在补偿心理之基础上的佛家他律伦理。其说立足人的自律性、自觉性以否定仰赖他力之思想,在哲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⑤可见,郑氏不仅是与李成桂合作成就易姓革命并开创五百年朝鲜王朝的杰出政治家,而且还是开启朝鲜朝儒学独尊时代的深远影响的哲学家。
郑道传被誉为“东方真儒”,丽末鲜初排佛论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通过他对佛教教义的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性理学(朱子学)才确立了其在朝鲜朝的官方哲学的地位。而且,通过他的积极阐发,朱子学中理气论、心性论等领域的思想皆在此后朝鲜朝儒学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高丽史》有载:“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明孔孟程朱之道,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息邪学,明天理而正人心,吾东方真一人而已。”①
概言之,丽末鲜初朱子学被传入至最终确定为官方哲学,经历了以下三部曲:首先,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丽末新进士林的关注并被介绍到韩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运用于排斥佛教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派所利用,逐步确立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至此朱子学获得了朝鲜朝官学的独尊地位。另外,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至朝鲜朝初期韩国朱子学已呈现本土化倾向。像李穑的“天则理”思想、郑梦周的春秋大义和心性践履、吉再的节义精神以及基于性理学道器说的郑道传的斥佛论思想等,都为16世纪韩国性理学全盛时期的到来作了理论准备。
在东亚文化圈中受儒学思想影响最深、最广的国家无疑为韩国。对于韩国儒学,学界有过精辟论述。“何谓韩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一些对韩国历史和文化了解浮泛的人认为,韩国儒学就是中国儒学的移植和翻版。此言误矣!固然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学就是以孔子为首的儒者的学说及其思想的总汇。同时应该看到儒者的学说和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随着时势的需求而丰富。由此,儒学才能够像一棵长青之树,像一条湍流不息的长河,永葆青春,永不枯竭。”①诚如斯言,儒学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后便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历程,这种带着民族文化之烙印的儒学就不再是中国儒学的简单移植和翻版,而是具有独立性的“韩国儒学”抑或是“韩国儒教”。
韩国儒者以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精微的逻辑思辨,使儒学在传统的东亚思想世界里发生了重要变化,演变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韩国儒学”。朝鲜王朝(1392—1910年)开国后,朱子学迅速升格成国家意识形态之主流,遂为此后朝鲜朝五百年的官方哲学。
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今天,作为东亚儒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的韩国儒学也将会更加彰显其理论价值与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对高丽末期和朝鲜朝开国之际朱子学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朱子学传入之初的主要人物间的传承系谱的研究①,而对其义理流衍的理论特点关注不足。
本章拟由朱子学在丽末鲜初的传播发展之考察来论述早期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义理特点。
第一节 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
高丽朝后期从武臣执权时起,文教即进入衰落期,至13世纪末整个社会已呈斯文扫地之衰相。此时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新进士类”通过科举迅速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影响王朝政治的一股新兴势力。他们企图从元朝引进程朱理学(朱子学)以重拾社会秩序,进而挽救国家的命运。不过,朱子学的输入还与当时元朝社会思想之状况密切相关。元代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把朱子学定为官方哲学,还将与之对立的陆九渊心学列入另类,致使陆学只能流传于我国江南民间。因朱子学在元代思想界享有独尊地位,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高丽新进士类引进之首选。②这一特征在韩国思想界影响甚远。它一方面使朱子学成为此后朝鲜王朝五百年间的官方哲学,另一方面却影响和阻碍了陆王一系的心学思想在韩国的传播。
一、安珦
据史书记载,朱子学是高丽忠烈王时由安珦从元朝引入。③朱子学虽有“新儒学”、“宋学”、“程朱学”等不同称谓,但其内容则基本相同。①安珦(字士蕴,号晦轩,1243—1306年,朝鲜时代改称为安裕)为兴州(现今顺兴)人。作为高丽朝后期的儒学大家和教育家,被后世尊为韩国性理学的始祖。《高丽史节要》记载其为人庄重安详,在相府能谋善断,常育人才而以兴复斯文为己任。他是高丽忠烈王的宠臣,历任尚州判官、儒学提举、集贤殿大学士、佥议中赞等官职。1289年高丽朝设置儒学提举司,安珦被任命为首任“本国儒学提举”。是年他扈从忠烈王入元,在滞留元大都(燕京)期间始得《朱子全书》,知其为孔门之正脉。遂手录其书,并摹写孔子和朱熹画像而归。这其实为此后朱子学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归国后安珦讲究朱子之书,深致博约之功,努力传授朱子学。“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②他常以兴学育才为己任,“蓄儒琴一张,每遇士之可学者劝之”③。而且,安珦还曾随世子(忠宣王)来过元朝,再次目睹了文教在元朝社会的隆盛状况。
但是,彼时的高丽朝儒学与佛、老思想的盛况相比则呈现一派衰败之势。对此安珦曾作诗慨叹道:“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④这是安珦描绘当时的国子监文庙败落景象的一首诗。
为了重新振兴儒学和恢复荒废的儒学教育机构,他建议朝廷设置“赡学钱”。安珦以为“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⑤,兴学养贤的目的就在于传授孔孟之教,推行儒家的伦理道德。他还曾派博士金文鼎等入元,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等回国。他还荐举李㦃、李瑱等人为经史教授都监使,于是“禁内学馆内侍三都监五库愿学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诸生(指国学七斋与私学十二徒——引者注),横经受业者动以数以百计”⑥。安珦认为朱子发明圣人之道以攘斥禅佛之学,其功足以配仲尼。因此欲学仲尼之道,必须先学晦庵之学。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朱子学开始在高丽社会得到重视。安珦另一功绩是培养出了众多鸿儒硕学,著名者有禹倬、权溥、白颐正等人。其门生也为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珦卒后13年即忠肃王六年(1319年),朝廷为表彰其在兴学养贤方面的功绩,给予从祀文庙之殊荣。朝鲜朝时期则祭祀安珦于白云洞书院。在时任丰基郡守的李退溪的努力下,公元1550年被明宗赐名为“绍修书院”。“绍修书院”是朝鲜朝最早的赐额书院。
二、禹倬
高丽朝后期的名儒禹倬(字天章,又字卓甫,号白云,称为“易东先生”,1263—1342年)是安珦的大弟子,也是早期的朱子学主要传播者之一。禹倬为丹山(丹阳)人,他与白颐正、辛蒇、权溥并称为安珦门下的“四君子”。历任宁海司録、监察纠正等官职,曾官至成均(国学)祭酒。禹倬博通经史,对《易》学造诣尤深。其时,“《程传》(按:指程氏《易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①。可见,禹倬是以《易》学为中心接受程朱之学。禹倬对易学所进行的义理学式的分析,使过去具有神秘性、巫术性的占卜术,在理学的基础上变得更具有理性色彩。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程传》易学的先河,对丽末鲜初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的易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②可见,禹倬在韩国易学史上开启了以义理为中心的《易》学研究(义理易)之先河。
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退溪对禹倬德学十分敬仰,尊其为丽末鲜初的八大儒之一。③退溪不仅建议朝廷在安东创建“易东书院”,而且还对其易学研究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认为:“天相吾东,斯文有迪,我程《易传》,肇臻斯域。人罔窥测,视同发梗,不有先生,谁究谁省……孔演十翼,程氏攸宗,专用义理,发挥天衷。熟玩深味,靡不该通。知益以明,守益以正。以是教人,德业无竞。”①由此亦可推知,朝鲜朝以《易》为中心的程朱性理学传统始于禹倬。
三、权溥
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原名永,字齐万,号菊斋,1262—1346年)为安东人。忠烈王五年(1279年)他年仅18岁即已登第,历任佥议舍人、礼宾寺尹、词林院侍读学、佥议政丞等,封为永嘉府院君,谥文正。忠肃王元年(1314年)同闵漬一起编撰高丽朝太祖以来的实录,忠烈王二十八年(1302年)和忠宣王元年(1309年)分别作为圣节使和正朝使出使元朝。史称权溥“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读书,老不辍。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②。他翻刻朱子学著作,在普及程朱理学方面很有建树。据《栎翁稗说》记载:“我外舅政丞菊斋权公,得《四书集注》,镂板以广其传,学者又知有道学矣。”③而且,他还同其子权准褒集历代孝子64人并使婿李齐贤著赞,定名《孝行录》刊行于世。此外,权溥还注有《银台集》20卷,惜已失传。在他的努力下,忠惠王五年(1344年)高丽改订科举法,“六经义”和“四书疑”遂被定位“初场”之考试科目。④于是,《四书集注》便成为士人们应试所必备的教科书。
四、白颐正
白颐正(字若轩,号彝斋,1247—1323年)为蓝浦郡人,亦是高丽朝后期的名儒。高宗时登第入翰院累官至中书舍人⑤,历任佥议评理、商议会议都监事等,后被封为上党君。他也曾入元,且于元大都(燕京)生活了多年。忠烈王三十一年(1305年)白颐正作为忠宣王的侍臣入元,于忠肃王元年(1314年)归国①,归国时还带回《朱子家礼》等大量朱子学著作。在滞留燕京长达十年期间,白颐正不仅收集了大量程朱理学著作,而且对其学说亦进行了深入研究。《栎翁稗说》记载:“白彝斋颐正,从德陵留都下十年,多求程朱性理之书以归……学者又知有道学矣。”②《高丽史》亦称:“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道先师受孝珠(颐正)。”③与安珦相比,白颐正则在研究和进一步深化程朱理学方面贡献更大,而且,在高丽朱子学的传承方面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弟子朴忠佐(字子华,号耻菴,1287—1349年),官至判三司事,被封为咸阳府院君。其人喜读《周易》,终生致力易学(主要是研读“伊川易”)研究④;另一弟子李齐贤则培养出李穑等丽末鲜初的著名朱子学者。白颐正的遗稿有《燕居诗》、《詠唐尧》、《寒碧楼》、《与洪厓集句》等。
五、李齐贤
高丽末期政治家、史学家李齐贤(字仲恩,号益斋、栎翁,1287—1367年)为庆州人,亦是权溥之贤婿。在早期的朱子学传播者中,李齐贤是卓有建树的一代名儒。他亦有赴元留燕京生活之经历。李齐贤年15岁便登成均试状元榜,历任进贤馆提学、知密直司、政堂文学、判三司事、右政丞、门下侍中等职,被封为鸡林府院君,谥号文忠。1313年,忠宣王让位于太子忠肃王后便以大尉身份留居于元,在燕京构筑万卷堂与当时许多名儒交游。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他将李齐贤召至元大都(燕京)。其时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虞集等咸游王门,李齐贤与他们相从而学益进。门人李穑曾曰:“高丽益斋先生生是时。年未冠,文已有名当世,大为忠宣王器重,从居辇毂下。朝之大儒缙绅先生若牧庵姚公、阎公子静、赵公子昂、元公复初、张公养浩咸游王门,先生皆得与之交际,视易听新,摩厉变化,固已极其正大高明之学。而又奉使川蜀,从王吴会,往返万余里。山河之壮,风俗之异,古圣贤之遗迹,凡所为闳博绝特之观。既已包括而无余,则其疏荡奇气,殆不在子长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优游台阁,则功业成就,决不让向之数君子者。敛而东归,相五朝,四为冢宰,东民则幸矣。其如斯文何?虽然东人仰之如泰山,学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尔雅,皆先生化之也。”①姚燧是许衡(字仲平,号鲁斋,1209—1281年)的门人,元明善则是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1249—1333年)的弟子。时人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二人皆为元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与许衡不同,吴澄因与陆九渊同乡受陆学影响较大,可以说是兼讲朱陆的学者。由此可知,李齐贤应对其时的朱学和陆学都有所了解。
李齐贤在元朝滞留时间较长,其学问造诣亦曾让姚燧、元明善等元朝学者“称叹不置”②。李齐贤回国后,通过兴学养贤,积极推动朱子学的发展。而且,他还栽培李穀、李穑父子,成就了高丽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李齐贤视程朱理学为“实学”,所以在学风上非常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他主张“躬行心得”和“求新民之理”。李齐贤的思想中有较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每欲以经世之学来反对佛教、革新朝政。并且,他还向朝廷提出了诸多志向改革现实政治的建议——这与安垧、白颐正有较大区别。从李齐贤所提倡的“为学次序”③中又可以看出其对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学思想的重视。李齐贤的著作有《益斋乱稿》(10卷)、《栎翁稗说》(4卷)、《益斋长短句》等。
综上所述,作为儒学新形态的程朱理学(朱子学)主要是通过由出使元朝的使臣传入韩国。经过他们的积极倡导和推动,朱子学在高丽朝的知识界获得了初步的传播。④值得注意的是,从《高丽史》的记载来看,高丽朱子学的传承主要是由安珦及其弟子来完成。换言之,高丽的朱子学是由安珦开其端,并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加以传承并发扬之。因此,安珦在高丽乃至韩国儒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理应得到重视。但是,这一时期还处于韩国朱子学义理思想的萌发阶段,故在理论创获上成就有限。
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这一时期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朱子学义理在高丽社会得到初步普及的同时获得新进士林阶层的认同;二是为下一阶段韩国朱子学义理思想的勃发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
第二节 丽末鲜初的朱子学
至丽末鲜初即高丽、朝鲜两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思想界涌现出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吉再、朴础等著名朱子学者。刚刚传入半岛的朱子学顺应时代潮流,成为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并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一、李穑
高丽末期重臣、著名的朱子学家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是“丽末三隐”之一,历任典理正郎、内书舍人、政堂文学、判三司事等官职,谥文靖。作为李齐贤的门人和李穀的儿子,李穑可谓是继承了丽末朱子学正脉的一代儒学宗匠。他在韩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所谓“承上”、“继往”,是说他的儒学仍具有早期政治儒学的色彩;所谓“启下”、“开来”,是讲其学与高丽前期的政治儒学已有本质区别。李穑以朱子学为其政治儒学的核心内容。他说:“孔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出政治,正性情,以一风俗,以立万世大平之本。所谓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者,讵不信然。中灰于秦,仅出孔壁。诗书道缺,泯泯棼棼。至于唐韩愈氏,独知尊孔氏,文章遂变。然于《原道》一篇,足以见其得失矣。宋之世,宗韩氏学古文者,欧公数人而已。至于讲明邹鲁之学,黜二氏,诏万世,周程之功也。宋社既屋,其说北流。鲁斋许先生,用其学相世祖,中统至元之治,胥此焉出,呜呼盛哉。”②正如前文所述许衡是元朝正宗理学大儒,其学以朱子为宗,在北方影响甚大。李穑之父游学中国时与许鲁斋的门人颇有交往,受其父之影响的李穑既推崇韩欧之文章、周程之理学,又向往许氏以学辅治的为学径路。①“宋社既屋,其说北流”,表明李穑俨然将鲁斋视之为南宋灭亡后承传朱学之第一人。其时入元求学的高丽学者大都深受鲁斋之学的影响。由此论之,许衡不仅在朱学北传过程中功绩卓越,而且对丽末朱子学的发展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李穑在构建学理层面的儒学中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对丽末鲜初的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他的极具学术意义的理论主张,如“天则理”、“一而二,二而一”等,成为日后韩国性理学的基本理念。②他任成均馆大司成时不仅亲自讲授朱子学,还聘金九龙、郑梦周、李崇仁等为教官,培养了一大批儒生,为朱子学在高丽全境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丽史》上称,恭愍王十六年“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馆大司成,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士金九龙、郑梦周、朴尚忠、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日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坌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③。李穑将程朱理学视为儒学之正脉,强调学者应以“明明德”为首要之务。认为:“以吾儒言之,曰明命,以天言之;曰明德,以人言也。顾明命明明德,学者之事也。”④又说:“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非二物也。而天与人判而离也久矣,仲尼盖悲之,道统之传,不绝如线,幸而再传,有圣孙焉,著为一书,所以望后人者至矣。”⑤此处“明德”指的是“性”,即所谓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他看来,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由此李穑提出自己的“天人无间”思想:“虽道之在大虚,本无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气为然。是以大而为天地,明而为日月,散而为风雨霜露,峙而为山岳,流而为江河。秩然而为君臣父子之伦,粲然而为礼乐刑政之具,其于世道也,清明而为理,秽浊而为乱,皆气之所形也。天人无间,感应不惑。故彝伦叙而政教明,则日月顺轨,风雨以时。而景星、庆云、醴泉、朱草之瑞至焉。彝伦斁而政教废,则日月告凶,风雨为灾,而彗孛飞流、山崩水渴之变作焉。然则理乱之机,审之人事而可见,理乱之象,求之风月而足矣。”①他还以为今中原甫定,四方无虞,正是所谓“理世”。若能趁此机会修国之政刑,将会使百姓安康、物产丰盛。李穑进而又从“天人无间”论立场出发提出“天则理”思想:“天则理也,然后人始知人事之无非天矣。夫性也,在人物,指人物而名之曰人也物也,是跡也。求其所以然而辩之,则在人者性也,在物者亦性也。同一性也,则同一天也。”②他反对将天和人、命和性分而为二。
同时,李穑还基于性理学的道统观,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佛教的弊端提出了批评,指出:“佛氏入中国,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汉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为国,佛刹民居,参伍错综,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两宗为利之窟,川傍山曲无处非寺……佛大圣人也,好恶必与人同。安知已逝之灵,不耻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条禁,已为僧者,亦与度牒,而无度牒者,即充军伍。新创之寺,并令撤去,而不撤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尽髡缁。臣闻殿下奉事之诚,尤笃于列圣。其所以祈永国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窃惟佛者至圣至公,奉之极美不以为喜,待之甚薄不以为怒。况其经中分明有说‘布施功德,不及持经’,听政之余,惟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顿法,无所不可。但为上者,人所则效,虚费者,财所耗竭,防微杜渐,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臣愿于佛,亦宜如此。”③以上所引文字是恭愍王元年李穑所上《陈时务书》中的部分内容,《高丽史》和《东文选》皆有记载。他以为,制民产、兴王道就是要从辟异端开始,具体而言即为抑制佛教流弊的蔓延和佛教徒的发展。不过,需注意的是,李穑的斥佛论主张不是对佛教的教理本身进行批驳,像“佛大圣人也”、“佛者至圣至公”这样的言论还受到后世儒者的讥评。④但是,从上述李氏的抑佛言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丽末接受朱子学(新儒学)思想的新进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态度和此一时期思想界新的理论动向。
在政治上,李穑主张以“三纲五常”为立国之本,企图重建理想的儒家王道政治。在新旧王朝更替时他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革新派的田制改革。1392年革新派赵浚、郑道传等人与李成桂密切配合,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由此朱子学获得了官学的地位,进而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李穑的著作有《牧隐集》(55卷)。
二、郑梦周
“丽末三隐”之一的郑梦周(字达可,号圃隐,1337—1392年)亦是高丽末期的政治家、朱子学家、文学家,被李滉等人称为“东方理学之祖”①。恭愍朝登第,历任成均馆博士、政堂文学、右文馆大提学、侍中等官职,谥文忠。《高丽史》上称郑梦周“生而秀异”,并说:“以礼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指郑梦周——引者注),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脗合,诸儒尤加叹服。”②由此亦可知,郑氏的确天分甚高。早年曾从游于李穑门下,但是其为学并无一定师承③,多为自悟自得。权採还曾提到:“乌川圃隐郑文忠公生于高丽之季,天资粹美,学问精深。其为学也,以默识心融为要,以践履躬行为本。性理之学,倡道东方,一时名贤,咸推服焉。”④权氏对其为学特点的概括甚为精辟——朱子学的穷理与践履精神在郑梦周的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郑梦周一生好学不倦,不仅博览群书、精研义理,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广程朱之学。《高丽史》记载,他曾“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①。郑氏的心志和作为开了朝鲜儒教兴起之先河。
其时明朝已经开国。暗图废弃蒙元服饰的郑梦周敦请朝廷施行大明的衣冠文物。在丽末“亲元派”与“亲明派”的势力纷争中力主“绝元归明”之外交对策,终成作为《春秋》尊王攘夷观之变种的“尊华排胡论(华夷论)”的主要倡导者。
郑氏对朱子学有很深的体会,其理论造诣深得同时代学者的赞赏。李穑曾说:“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②以为他对朱子学的精深研究和哲学思考已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郑道传亦曾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至于《易》,知先天后天相为体用;于《书》,知精一执中为帝王传授心法;《诗》则本于民彝物则之训;《春秋》则辨其道谊功利之分。吾东方五百年,臻斯理者几何人哉。诸生各执其业,人人异说。随问讲析,分毫不差。”③可见,梦周不仅对“四书”之要有深切的体会,而且对“五经”之义亦有精湛的研究。
郑梦周以为“天人虽殊,其理则一”④,还说:“造化无偏气,圣人犹抑阴。一阳初动处,可以验吾心。”⑤他在坚持“天人一理”之立场的同时,主张理对气的优位性和主宰性,而对理的主宰性的重视恰恰是朱子学的核心要领。
在竭力倡导“濂洛之道”及朱子学的同时,他还对佛、老之说提出了质疑。“如天之圆,广大无边,如镜之照,了达微妙。此浮屠之所以喻道与心,而吾家亦许之以近理。然其圆也,可以应万事乎,其照也,可以穷精义乎。吾恨不得时遭乎灵山之会,诘一言于黄面老子。”①郑梦周从朱子学的立场出发指出佛、老理论的局限性。他还对儒佛的基本教理作了进一步的比较,认为:“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动静语默之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彼佛氏之教则不然,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是岂平常之道?”②郑氏主张儒者之道皆是日用平常之事,如饮食男女人所同,而此中便存有至理——所谓尧舜之道亦不外乎此。动静语默之间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但是佛氏之教则不然,虚伪乱常、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以观空寂灭为宗。③他将佛教指斥为以“观空寂灭为宗”的妖妄怪诞之教,并从教义、教理的层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同时,他还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以取代佛教仪式,行冠婚丧祭,并亲自为父母服丧了三年。郑氏是继李穑之后又一位提倡“崇儒抑佛”的朱子学者。与李穑等人不同,郑氏更多从人伦道德层面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驳,故其辟佛论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其对佛教教义和教理的精深了解。
郑梦周弟子众多,其门人大都成为引领朝鲜朝初期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学脉传承关系大致如下:④
仅从图1中看,在其门下涌现的勋旧派士人多于士林派学人。但是郑氏及其弟子吉再以自身的学行和践履诠释了性理学的理念和价值标准,由此确立了重价值判断过于事实判断的士林派的道统意识。所以韩国17世纪的儒学巨擘尤庵宋时烈(1607—1689年)曾对圃隐郑梦周称颂道:“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⑤
郑氏35岁和47岁时曾两度作为高丽使节入明,他也是在高丽朝廷内力倡亲明外交的代表人物。两朝更替之际,他对高丽王朝忠心耿耿,最终以身殉之,真正践行了孟子所谓“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的儒家教义。故后人赞曰:“公天分至高,豪迈绝伦。少有大志,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日诵《中庸》、《大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真积力久,独得濂洛不传之秘。故其措诸事业发于议论者,十不能二三,而光明正大,固已炳耀青史,真可谓命世之才矣。”①郑梦周的“忠臣不事二君”的至死不变之节义被李朝君臣高度推崇,这也是他被尊为“韩国义理学派之祖”②以及“东方理学之祖”的重要原因之一。郑梦周的著作有《圃隐集》(7卷)。
三、吉再
丽末鲜初期的著名朱子学者还有吉再(字再父,号冶隐,又号金鸟山人,谥号忠杰,1353—1419年),海平(善山)人。他曾受学于李穑、郑梦周、权近等人,与李穑、郑梦周同被尊为“丽末三隐”。作为朝鲜士林派学者的先驱,吉再为学极重真知与实得,主张学者应以忠孝礼义廉耻为先。《冶隐集》记载,吉再与弟子“讲论经书,必务合于程朱之旨,言必以忠孝为主”①。弃官退隐乡野则专心于读书涵养,还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大兴“私学”教育,开了朝鲜私学教育之风气。其学脉连绵不绝,如图1所示后学中涌现出金叔滋、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一大批活跃于朝鲜朝前期学界和政界的大儒。受其思想影响的岭南“士林派”后来逐渐成长为对抗腐败之“勋旧派”②的批判势力,且在成宗朝后成为主导中央朝政的重要力量。权近也对吉再称誉道:“呜呼!有高丽五百年培养教化,以励士风之效,萃先生之一身而收之。有朝鲜亿万年扶植纲常,以明臣节之本,自先生之一身而基之,其有功于名教甚大。”③吉再的义理思想和节义精神奠定了朝鲜朝初期儒学实践的发展方向,所以他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其实,郑梦周、吉再等人的义理精神与新罗花郎的为国尽忠之精神可谓一脉相承。④朝鲜朝前期义理派学者的理论探讨和教育实践活动,为韩国朱子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吉再的主要著作有:《冶隐集》、《冶隐续集》、《冶隐先生言行录拾遗》等。
高丽末至朝鲜朝开国前后是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初创期,因为正处于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此时在统治阶层内部和意识形态领域亲明与亲元、革新与守常、事大与自主之争异常激烈。朱子学作为新的理论学说传入韩国后,开始分化为强调人伦义理的保守势力和重视现实问题的革新势力。两派立场上的差异源自各自对性理学(朱子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理解。以郑梦周为首的“纲常论”者首重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强调忠孝节义,重视大义名分,因此这一派也被称为“节义论”者;以郑道传为首的“革新论”者则强调《周易》的变易思想,主张应根据时势之迁移主动求变,从而革新现实政治。①郑梦周、吉再、金叔滋、金宗直等属于“纲常论”者,他们基于春秋大义反对异姓革命,拒绝同革新势力妥协。于是新朝建立后他们或遭杀害,或被革职,余下的则大多归隐山林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以教化民众为务。结果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和政坛便被主张权变的郑道传、权近一系的革新势力(“事功派”,亦称“官学派”)所掌控。郑道传死后,权近继承其学风成为“事功派(官学派)”的领袖。此派学风特点是重视功利实用,必以经世为鹄的。此后,“事功派”又逐渐演变为“勋旧派”,成为“士林派”批判和拒斥的对象。
简言之,丽末鲜初期不仅是韩国高丽、朝鲜两个新旧王朝更替时期,而且还是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初创时期。此一时期的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可划分为两个阶段: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阶段和朝鲜朝开国前后义理的初步自觉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安珦、禹倬、白颐正、李齐贤等,而后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则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吉再等。朝鲜王朝开国后,朱子学迅速上升为社会主流思想,进而成为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
第三节 郑道传斥佛论与朱子学“官学”地位之确立
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②)生于庆尚道奉化,是丽末鲜初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诗人。他于1362年中进士第,先后在高丽朝任三司右使、右军都总制使等。1392年拥立李成桂(朝鲜太祖,1335—1408年)以创朝鲜王朝,成为李朝的开国功臣。作为性理学者郑氏向往儒家王道政治,提出以宰相制为主的朝政运作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措施,在新朝中央集权的两班官僚体制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后人誉为“朝鲜王朝的设计者”。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诸多领域,而哲学方面代表作有《佛氏杂辨》、《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等。此外,据传还有《学者指南图》。其中《佛氏杂辨》一书是朝鲜朝排佛崇儒国策的理论根据和基础。
郑道传是丽末重臣、著名朱子学者李穑的门人,同时还是权近的老师。在两朝交替之际,郑氏作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与李成桂相互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抑佛崇儒”的思想文化政策,并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学理上对佛教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驳。这是他的主要理论贡献。郑道传在斥佛过程中还吸收程朱的理学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性理学理论。本节仅对其性理学及斥佛论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一、郑道传的性理说
郑道传被称为“东方真儒”。正是通过他的积极阐发和努力,朱子学理气论、心性论的诸多观念和思想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朱子理学亦称为道学,其道器说与理气说密切相连,在新儒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多数性理学家皆将二说作为思想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借“道”、“器”、“理”、“气”一类的本体论概念探讨天地万物之源也就是世界之本源。
郑道传的道器说大体承袭了程朱的学说。“道则理也,形而上者也。器则物也,形而下者也。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即身心而有身心之道,近而即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远而即于天地万物,莫不各有其道焉。人在天地之间,不能一日离物而独立。是以,凡吾所以处事接物者,亦当各尽其道,而不可或有所差谬也。此吾儒之学所以自心而身而人而物,各尽其性而无不通也。盖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者也。”①以形上、形下区分道器的同时,他还强调了二者的不离不杂性,即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郑道传进而据此批评佛教,指出佛教昧于道器之辨而以道器为二物。“彼佛氏于道,虽无所得,以其用心积力之久,髣髴若有见处。然如管窥天,一向直上去,不能四通八达。其所见必陷于一偏见。其道不杂于器者,则以道与器歧而二之。乃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必欲摆脱群有,落于空寂见。其道不离于器者,则以器为道。乃曰善恶皆心,万法唯识,随顺一切,任用无为,猖狂放恣,无所不为。此程子所谓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者也。然其所谓道者,指心而言,乃反落于形而下者之器而不自如也。”①郑道传主张佛教“道与器歧而二之”的“道器”两极化的思想根于其“万法唯识”、“诸相非相”观念,结果导致“以器为道”,使“道”无别于形而下者之器。这表明郑氏不仅对程朱的道器说有准确的理解,而且对佛教理论要害处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在大作《天答》篇中,郑氏弟子权近对其“理”有进一步的解释。“天即理也,人动于气者也。理本无为而气用事,无为者静,故其道迟而常。用事者动,故其应速而变。灾祥之不正,皆气之使然也。是其气数之变,虽能胜其理之常者。然此特天之未定之时尔。气有消长,而理则不变,其久而天定,则理必得其常。而气亦随之以正,福善祸淫之理,岂或泯哉。”②以“道则理”和“天即理”来规定“理”,那么“道”和“天”就应理解为“太极”。“无极而太极”——理只是作为万物运动变化之所以然而存,所谓“凡所以为当然之则而不可易者是理也”。郑道传指出理具有无为、不变之特性,气则具有能用事、消长之特性。而且郑氏还把“理”理解为是纯粹而至善的形而上之存有亦即人之性。“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③在理气先后及理气关系问题上,他坚持了理在气先说以及理主宰气之说,所谓“于穆厥理,在天地先,气由我生,心亦禀焉”④。对此,权近则进一步解释道:“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四时于是而流行,万物于是而化生。人于其间,全得天地之理,亦全得天地之气,以贵于万物而与天地参焉。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又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①
在《佛氏杂辨》中,郑道传写道:“盖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毕竟先有太极,而天地万物之理,已浑然具于其中。故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如水之有源,万派流注,如木之有根,枝叶畅茂。此非人智力之所得而为也,亦非人智力之所得而遏也。然此固有难与初学言者,以其众人所易见者而言之。”②理先气后是关乎朱子哲学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理先气后,朱子的思想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年他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理在气先的思想是在离开南康之后经朱陈之辨和朱陆太极之辨才逐步形成的。理能生气说曾是其理先气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他的晚年定论则是逻辑在先——此说是在更高形态上返回本体论思想,可谓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并不是对立面的演进和交替,在本质上,是以不同形式确认理对于气的第一位性以及理的绝对性。③郑道传在朱子学这一基本问题上坚持“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的理先气后说。以道器规定理气,以强调二者不离不杂性,从而赋予理以“其尊无对”性——这样的理在气先的理解可以说是郑道传理气说的主要内容。上述思想我们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者的学说中亦可找到其端绪。
儒家以“内圣外王之道”为宗旨:内圣成己,外王成物。而内圣之学实质上也就是心性之学。作为研究人的本质以及自我价值应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内圣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宋儒融儒、道、佛三家心性理论为一体(以儒为主),建立了以自我超越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从而将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因此,理学亦称“道德性命”之学或“心性”之学,说明它是以心性为中心范畴的道德形而上学。
在郑道传的哲学著述中,对心性的论述所占比重较多,如《佛氏杂辨》19篇文章中“佛氏心性之辨”、“佛氏心迹之辨”、“儒佛同异之辨”、“辟异端之辨”以及《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等都集中涉及“心性”问题。其中,《心气理篇》的“心”是指佛教的“修心”,“气”是指道家的“养气”,“理”则指性理学的“性理”。即佛教因修心而视现实为虚妄,道家则为养生而否定思虑与分别。而以“理”为生成之理和当为之理的儒家性理学则可兼摄佛道的理论。①
郑道传的心性思想大体继承了朱子的心性情三分构架体系和“心统性情”论。权近在为三峰《心气理篇》中的《心难气》一文加注时说:“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漠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虽曰应万事,而是非错乱,岂足为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有其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郑道传认为“心”是理气之合,亦为一身神明之舍。此时的心中之理即为所禀之德,所谓“理者,心之所禀之德而气之所由生者也”③。他讲到的“德”乃仁义礼智之性,即天之所令而人之所得者。郑氏在《心问》篇中写道:“始者赋命之初,必与人以仁义礼智之性,是欲使人循是性而为善也。”④人心之理虽为上帝所命,但其义理之公因被物欲所胜,致使其善恶之报也有颠倒。若以义理养心则无物欲之蔽,由是全体虚明而大用不差。郑道传据此提出“志帅气卒”的思想:“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皆不坚守,弃臣从敌,以臣之微,孤立单薄。”⑤权近进一步解释曰:“志者,心之所之也。吾亦心之自称也。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注曰,志固心之所之,而气之将帅。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而为志之卒徒也。心为天君,以志统气而制物欲,犹人君之命将帅,以率徒众而御敌人也。故曰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然志苟不定,则物欲得以夺之,而理不能以胜私矣。故其志之为帅与其气之为徒卒者,皆不能坚守其正,反弃吾心而从物欲。故吾之此心,虽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单弱而薄劣也”①。“志”是心之所之,心是天君。以志统气而制物欲,犹人君之命将帅以率众御敌。故曰“志吾之帅,气吾徒卒”。“志”若不定则物欲得以夺之,而理不能以胜私。故其志之为帅与其气之为徒卒者,皆不能坚守其正,反弃吾心而从物欲。故吾之此心,虽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单弱而薄劣。以我一心之微,而当众欲之攻,虽甚微弱而薄劣。因此,郑道传写道:“诚敬为甲胄,义勇为矛戟,奉辞执言,且战且服,顺我者善,背我者恶,贤智者从,愚不肖逆,因败成功,几失后获。”②以为若能以诚敬为甲胄而自守,则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夺。义勇为矛戟而自卫,则所以裁制者严而欲不得侵犯。这便是“内外交相养之道”③。
因“志”为心之所之,故“志”不定则理不能胜私欲,或者说“志”不能统气而制物欲。若能以诚敬为甲胄而自守,则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夺;若能以义勇为矛戟而自卫,则所以裁制者严而欲不得侵犯天理,正所谓“方寸之间,私欲净尽,则吾心之理,即在天之理。在天之理,即吾心之理,脗合而无间者也。”④因此,学者“存心养气”应以“以义理为之主”。郑道传指出:“有心无我,利害之趋,有气无我,血肉之躯,蠢然以动,禽兽同归,其与异者,呜呼几希。”⑤对此权近则进一步解释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义理也。人而无义理则其所知觉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矣。其所运动者,亦蠢然徒生而已矣。虽曰为人,去禽兽何远哉。此儒者所以存心养气,必以义理为之主也。”⑥将是否存有“义理”视为人异于禽兽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
郑道传的心性论思想在其《佛氏心性之辨》一文中有较集中的论述。他写道:
心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气,虚灵不昧以主于一身者也。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盖心有知有为,性无知无为。故曰心能尽性,性不能知检其心,又曰心统情性,又曰心者神明之舍,性则其所具之理,观此心性之辨可知矣。彼佛氏以心为性,求其说而不得,乃曰:迷之则心,悟之则性。又曰:心性之异名,犹眼目之殊称至。楞严曰:圆妙明心,明妙圆性,以明与圆分而言之。普照曰:心外无佛,性外无法,又以佛与法分而言之,似略有所见矣。然皆得于想象髣髴之中而无豁然真实之见,其说多为游辞而无一定之论,其情可得矣。吾儒之说,曰尽心知性,此本心以穷理也。佛氏之说,曰观心见性,心即性也,是别以一心见此一心,心安有二乎哉?彼亦自知其说之穷,从而遁之曰:以心观心。如以口齿口,当以不观观之,此何等语欤?且吾儒曰:方寸之间,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其曰虚灵不昧者,心也;具众理者,性也;应万事者,情也。惟其此心具众理,故于事物之来应,之无不各得其当,所以处事物之当否而事物皆听命于我也。此吾儒之学内自身心,外而至于事物,自源徂流,一以通贯,如源头之水,流于万物,无非水也。如持有星之衡,称量天下之物。其物之轻重与权衡之铢两相称,此所谓元不曾间断者也。佛氏曰空寂灵知,随缘不变,无所谓理者具于其中,故于事物之来,滞者欲绝而去之,达者欲随而顺之,其绝而去之者,固己非矣,随而顺之者,亦非也。其言曰,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听其物之自为而已,无复制其是非而有以处之也。是其心如天上之月,其应也如千江之影,月真而影妄,其间未尝连续如持。无星之衡,称量天下之物,其轻重低昂惟物是顺。而我无以进退,称量之也。故曰: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学者所当明辨也。①
可见,郑道传是以程朱心性学说为基础展开了对佛教“性空”论的批评,并得出“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的结论。
二、郑道传的斥佛论
在韩国哲学史上,真正具系统性、理论性的斥佛论的出现始于郑道传、权近师徒。《佛氏杂辨》和《心气理篇》即为反映其斥佛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在同佛教的论战中,郑道传基于儒佛思想之异系统发挥性理学(朱子学)的观点并对佛教根本教义逐一进行了批驳。
《佛氏杂辨》就是一部从性理学的立场出发批驳佛家祈福之虚构性以及僧侣寺庙之弊害的著作。此外,其作还涉及佛教的理论弱点。此书写于1398年,主要围绕以下19个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以阐述其斥佛论主张。(1)佛氏轮回之辨;(2)佛氏因果之辨;(3)佛氏心性之辨;(4)佛氏作用是非之辨;(5)佛氏心迹之辨;(6)佛氏昧于道器之辨;(7)佛氏毁弃人伦之辨;(8)佛氏慈悲之辨;(9)佛氏真假之辨;(10)佛氏地狱之辨;(11)佛氏祸福之辨;(12)佛氏乞食之辨;(13)佛氏禅教之辨;(14)儒释同异之辨;(15)佛法入中国;(16)事佛得祸;(17)舍天道而谈佛果;(18)事佛甚谨年代尤促;(19)辟异端之辨。而且,在文中他还援引了许多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等人的有关抑佛扬儒的论述。
仅从《佛氏杂辨》题目来看,郑道传对佛教的批判是相当系统而全面的。在驳斥佛教“因果轮回”等基本教义的过程中,提出天地万物由“气”形成之气化论观点。《佛氏轮回之辨》中提到:
人物之生生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原夫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其己生者,生而过;未生者,来而续。其间不容一息之停也。佛之言曰: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于是,轮回之说兴焉。《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先儒解之曰: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于太虚之中,则知其死也,与气而俱散无复留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内。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天地阴阳之气交合复成人物。到得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复,是变了粗气为物,是合精与气而成物,精魄而气魂也。游魂为变,变则是魂魄相离,游散而变。变非变化之变,既是变则坚者、腐存者込无物也。天地间如烘炉,虽生物皆销铄己尽。安有已散者复合而已生者复来乎?今且验之,吾身一呼一吸之间,气一出焉,谓之一息。其呼而出者,非吸而入之也。然则人之气息亦生生不穷,而生者过,来者续之,理可见也。外而验之于物,凡草木自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一气通贯。当春夏时,其气滋至而华叶畅茂;至秋冬,其气收敛而华叶衰落;至明季春夏又复畅茂,非已落之叶返本归源而复生也。又井中之水,朝朝而汲之,喝饮食煮,煮而尽之;濯衣服者,日曝而干之,泯然无迹。而井中之泉,源源而出,无有穷尽,非已汲之水返其故处而复生也。且百谷之生也,春而种十石,秋而收百石,以至千万,其利倍蓰,是百谷亦生生也。今以佛氏轮回之说观之,凡有血气者自有定数,来来去去无复增损。然则天地之造物反不如农夫之生利也。且血气之属,不为人类,则为乌兽鱼龟昆虫。其数有定,此蕃则彼必耗矣,此耗则彼必蕃矣。不应一时俱蕃,一时俱耗矣。自今观之,当盛世人类蕃庶,乌兽鱼龟昆虫亦蕃庶;当衰世人物耗损,乌兽鱼龟昆虫亦耗损。是人与物皆为天地之气所生,故气盛则一时蕃庶,气衰则一时耗损,明矣。予愤佛氏轮回之说惑世尤甚。幽而质诸天地之化,明而验诸人物之生,得其说如此,与我同志者幸共鉴焉。
或问子引先儒之说,解《易》之游魂为变曰:魂与魄相离,魂气归于天,体魄降于地,是人死则魂魄各于天地,非佛氏所谓人死精神不灭者耶?曰:古者四时之火,皆取于木,是木中元有火,木热则生火。犹魄中元有魂,魄暖着为魂,故曰钻木出火。又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形魄也,神魂也。火缘木而存,犹魂魄合而生。火灭则烟气升而归于天,灰尽降而归于地。犹人死则魂气升于天,体魄降于地。火之烟气即人之魂气,火之灰尽即人之体魄。且火气灭矣,烟气灰尽不复合而为火。则人死之后,魂气体魄亦不复合而为物。其理岂不明甚也哉。①“轮回”乃梵文Samāra的意译,原意为“流转”。原是印度婆罗门教教义,后为佛家沿用发展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宣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果得不到“解脱”,则会永远在所谓“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或无阿修罗道而为“五道轮回”)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故称“六道轮回”。这种“轮回”说的核心是灵魂不灭,即人死后其精神不死。根据其人一生所做的“业”,灵魂还会在来生以至二生三生承受业报。①基于灵魂不灭论的“轮回”说是佛教世界观和信仰核心理论。
郑道传以朱子学“气化”论以及“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对之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②。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而“形质”与“神气”必然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人死了精神便无以存在,所谓“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同时,他还提出事物总是处于发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中的辩证思想。“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此“生生无穷”之运动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带有发展进步的质的变化。
郑道传以“气化”和“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说明了人与物类能够不断繁衍的原因,一方面有力地批驳了佛教“轮回”说的理论基础——精神不灭论,另一方面也使儒家关于“气”的理论得以挺立和张扬。③他还以此说为基础进一步批评了作为“轮回”之理论依据的“因果报应”说:“或曰吾子辨佛氏轮回之说至矣,子言人物皆得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今夫人则有智愚贤不肖、贫富贵贱寿夭之不同,物则有为人所畜役劳苦至死而不辞者,有未免纲罗钓戈之害、大小强弱之自相食者,天之生物,一赋一与何其偏而不均,如是耶?以此而言,释氏所谓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者,不其然乎。且生时所作善恶是之谓因,它日报应是之谓果。此其说不亦有所据欤?曰予于上论人物生生之理悉矣。知此则轮回之说自辨矣。轮回之说辨,则因果之说不辨而自明矣。”①可见,郑氏是把儒家“气”论思想作为其批评佛教的主要理论工具的。他以朱子学的“气禀”说批驳佛家因缘和合论和因果报应说:“夫所谓阴阳五行者,交运迭行、参差不齐,故其气也有通塞、偏正、清浊、厚薄、高下、长短之异焉。而人物之生,适当其时。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人与物之贵贱于此焉分。又在于人得其清者智且贤,得其浊者愚不肖,厚者富而薄者贫,高者贵而下者贱,长者寿而短者夭,此其大略也。虽物亦然。”②
朱熹认为当理化生形气之时,理气浑然相融,具体到形成人物的时候,理即具于形气之中形成人的气禀。人物的气禀不仅有偏与正的问题,还有清与浊的问题。③朱子说过:“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④郑道传援引朱学“气禀”说,进一步指出人与物之区别、人与人之差异皆由气禀的不同造成的,并非出于佛教所谓因果报应。他在《佛氏因果之辨》篇的文末写道:“圣人设教,使学者变化气质,至于圣贤治国者,转衰亡而进治安。此圣人所以回阴阳之气,以致参赞之功者。佛氏因果之说,岂能行于其间哉?”⑤可以看出,郑道传反对佛学主要是出于其“灭伦害国性”⑥。因此,他在《辟异端之辩》文中指出:“以予惛庸,不知力之不足,而以辟异端为己任者,非欲上继六圣一贤之心也。惧世之人惑于其说,而沦胥以陷,人之道至于灭矣。呜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必士师。邪说横流,坏人心术,人人得而辟之,不必圣贤。此予之所以望于诸公,而因以自勉焉者也。”⑦
朱熹反对佛学同样出于其对人伦道德的危害性,所谓“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①。不过,其对佛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禅宗。朱熹尝言:“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绝灭犹未至尽,佛则人伦坏;禅则又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故其为害最深。”②此外,他还认为佛教尤其是禅宗将“心”与“性”视为一物,沦空而耽寂。“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细见得真实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政使有存养之功,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亦不可谓之不能养,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③心性一旦沦空耽寂即如浮光掠影无以致存养之功。由此可见,朱子学与佛学在心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别。④
由上所述,郑道传欲构筑的“善恶因果报应”说既没有借助佛之法力,也没有借助天(上帝)之主宰,而是仰仗人的主观能动性亦即所谓“主体性”。他以为尽管人时有不善之行为,但因“理”的不变性和主宰性,只须力克私欲便可变化气质,从而将不善之行为变为善行。他强调人的“主体性”,要求人们依靠良善意志和自身努力来战胜“恶”。这说明无论行为之动机还是果报皆系于自身之作为。郑道传的理论虽无佛教因果报应说之效力,却洋溢着合理主义的精神。他确立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大有异于建立在补偿心理之基础上的佛家他律伦理。其说立足人的自律性、自觉性以否定仰赖他力之思想,在哲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⑤可见,郑氏不仅是与李成桂合作成就易姓革命并开创五百年朝鲜王朝的杰出政治家,而且还是开启朝鲜朝儒学独尊时代的深远影响的哲学家。
郑道传被誉为“东方真儒”,丽末鲜初排佛论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通过他对佛教教义的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性理学(朱子学)才确立了其在朝鲜朝的官方哲学的地位。而且,通过他的积极阐发,朱子学中理气论、心性论等领域的思想皆在此后朝鲜朝儒学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高丽史》有载:“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明孔孟程朱之道,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息邪学,明天理而正人心,吾东方真一人而已。”①
概言之,丽末鲜初朱子学被传入至最终确定为官方哲学,经历了以下三部曲:首先,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丽末新进士林的关注并被介绍到韩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运用于排斥佛教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派所利用,逐步确立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至此朱子学获得了朝鲜朝官学的独尊地位。另外,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至朝鲜朝初期韩国朱子学已呈现本土化倾向。像李穑的“天则理”思想、郑梦周的春秋大义和心性践履、吉再的节义精神以及基于性理学道器说的郑道传的斥佛论思想等,都为16世纪韩国性理学全盛时期的到来作了理论准备。
附注
①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①学界对韩国早期的朱子学传承系谱的主要研究著作有:崔英成:《韩国儒学通史》(上),首尔:simsan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622页;琴章泰:《朝鲜前期的儒学思想》,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1997年版,第3—258页;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214页等。
②参见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7页。
③金忠烈先生认为,朱子学传入韩国时间为忠烈王十六年(1290年)。(参见金忠烈:《高丽儒学史》,首尔:艺文书院1998年版,第354—355页)
①参见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9页。
②郑麟趾等:《安珦》,《列传》卷18,《高丽史》卷10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③郑麟趾等:《安珦》,《列传》卷18,《高丽史》卷10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④《题学宫》,《遗集》,《晦轩实纪》卷1,韩国全南大学校出版部1984年版,第204页。
⑤郑麟趾等:《安珦》,《列传》卷18,《高丽史》卷10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⑥郑麟趾等:《安珦》,《列传》卷18,《高丽史》卷10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①郑麟趾等:《禹倬》,《列传》卷22,《高丽史》卷109,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页。
②参见郭信焕:《周易浅见录和阳村权近的易学》,《精神文化研究》1984年夏季刊,1996年,第84页;转引自吴锡源:《韩国儒学的义理思想》,邢丽菊、赵甜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③参见李滉:《回示诏使书》,《退溪先生文集续集》卷8,《退溪全书》(三),第138页;《论人物》,《退溪先生言行录》卷5,《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31页。
①李滉:《易东书院成祭禹祭酒文》,《退溪全书》(二)卷4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1页。
②郑麟趾等:《权㫜》,《列传》卷20,《高丽史》卷107,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382页。
③《栎翁稗说》,《前集》二,《丽季明贤集》,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95年版,第356页。
④参见《忠惠王五年甲申8月条》,《高丽史节要》卷25,首尔:新书院2004年版,第88页。
⑤参见郑麟趾等:《白文节》,《列传》卷19,《高丽史》卷106,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9页。
①参见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②《栎翁稗说》,《前集》二,《丽季明贤集》,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95年版,第356页。
③郑麟趾等:《白文节》,《列传》卷19,《高丽史》卷106,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④参见郑麟趾等:《朴忠佐》,《列传》卷22,《高丽史》卷109,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
①李穑:《益斋先生乱稿序》,《文稿》卷7,《牧隐稿》,《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52页。
②郑麟趾等:《李齐贤》,《列传》卷23,《高丽史》卷110,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③郑麟趾等:《李齐贤》,《列传》卷23,《高丽史》卷110,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
④参见洪军:《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16页。
①参见洪军:《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16页。
②李穑:《选粹集序》,《文稿》卷9,《牧隐稿》,《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72页。
①参见张学智:《心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73页。
②参见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5页。
③郑麟趾等:《李穑》,《列传》卷28,《高丽史》卷11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
④李穑:《杲菴记》,《文稿》卷6,《牧隐稿》,《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48页。
⑤李穑:《可明说》,《文稿》卷10,《牧隐稿》,《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80页。
①李穑:《西京风月楼记》,《文稿》卷1,《牧隐稿》,《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8页。
②李穑:《直说三篇》,《文稿》卷10,《牧隐稿》,《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77页。
③郑麟趾等:《李穑》,《列传》卷28,《高丽史》卷11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页。
④参见李丙焘:《韩国儒学史》,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版,第92页。
①李滉:《类编》,《退溪先生言行通录》卷5,《退溪全书》(四),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97页。
②郑麟趾等:《郑梦周》,《列传》卷30,《高丽史》卷117,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另外,咸傅霖撰写其《行状》中也有此记载,但是与《高丽史》上的内容文字上稍有出入。《圃隐集》中写道:“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而公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云峰胡氏四书通,与公所论,靡不脗合,诸儒尤加叹服。”(郑梦周:《圃隐先生集·行状》,《圃隐集》,《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622页)
③参见琴章泰:《朝鲜前期的儒学思想》,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1997年版,第44—45页;崔英成:《韩国儒学通史》(上),首尔:simsan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
④郑梦周:《圃隐先生诗卷序》,《圃隐集序》,《圃隐集》,《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561页。
①郑麟趾等:《郑梦周》,《列传》卷30,《高丽史》卷117,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②郑麟趾等:《郑梦周》,《列传》卷30,《高丽史》卷117,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
③郑道传:《圃隐奉使稿序》,《三峰集》(上)卷3,首尔: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41—242页。
④郑梦周:《祭金得培文》,《杂著》,《圃隐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599页。
⑤郑梦周:《冬至吟》,《诗》,《圃隐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595页。
①郑梦周:《圆照卷子》,《杂著》,《圃隐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599页。
②郑梦周:《圃隐先生本传》,《圃隐集》,《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627页;另见郑麟趾等:《郑梦周》,《列传》卷30,《高丽史》卷117,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446页。
③参见琴章泰:《朝鲜前期的儒学思想》,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1997年版,第49—50页。
④参见琴章泰:《朝鲜前期的儒学思想》,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1997年版,第45—46页。
⑤《圃隐先生集续录·筵臣奏辞》,《圃隐先生文集》,首尔:回想社1985年版,第327页。
①郑梦周:《圃隐先生集·行状》,《圃隐集》,《韩国文集丛刊》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第636页。
②柳承国:《韩国儒学史》,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08年版,第179页。
①《冶隐先生言行录拾遗卷上·行状》,《国译冶隐先生文集》,首尔:光明印刷社1965年版,第36页。
②勋旧派人物不以圃隐系列的义理思想为根本,而是有视于当时政治的状况与社会变动,对因之而起的所有社会弊端欲以新的创意和力量加以改革的势力。在韩国儒学史上比起郑道传一派,郑梦周一系则更能继承传统学脉的渊源,此点可见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3页。
⑤参见尹丝淳:《三峰郑道传斥佛论的哲学涵义》,洪军译,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423—424页。
①郑麟趾等:《金子粹》,《列传》卷33,《高丽史》卷120,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