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
| 内容出处: | 《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953 |
| 颗粒名称: | 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6 |
| 页码: | 194-209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书院是朱熹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版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本文以类书《事林广记》的先贤图,与朱熹《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加以考量。此书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熹道统论做了旷日持久跨越三朝的宣传,为此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晚宋到元初,相关的历史文献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
| 关键词: | 朱熹 道统论 书院祭祀 |
内容
一、朱熹道统论与书院祭祀
道统,即传道之统。朱熹的道统论,即朱熹上承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并加以综合创新的一种新儒学“传道正统”的理念。
孟轲在《孟子·尽心下》中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孔子的传承系统,并以此传承为己任。唐代韩愈则在《原道》一文中重申了孟子之旨,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从而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韩愈的这个理论,开南宋朱熹道统学说之先河,史称“道统论”。“道”,是从儒学的核心思想——伦理纲常而言;“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故又称“道统心传说”。朱熹在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的《中庸章句序》中,首次使用了“道统”一词。他说: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即儒家道统学说的十六字心传,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据传,这十六个字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时,将“允执厥中”四字传授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又在此四字之前加上十二个字,这代代相传的十六个字至此定形。后来禹又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又下传给颜子、曾子、子思,子思传给孟子。据说,这个传承过程是一个“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过程,与后来佛教禅宗的“以心传心”、“自悟自解”的法统相似,故被后儒称为“十六字心传”,被视为是传统儒学,乃至中华文化传统中著名的传心要诀。
宋代理学家朱熹把这十六字作为解读《中庸》一书的钥匙。他认为子思之所以撰《中庸》,是因为子思担心这种传承时间“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②通过朱熹的章句,《中庸》这一儒家经典就成了阐释“十六字心传”的重要典籍。在十六字心传的代代传承中,很自然地又和儒学的传道之统联系在一起。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①
按朱熹的解释,舜后补益的“三言”,是为了阐明“尧之一言”的,故此十六字的关键,仍在后四字上。“允”,朱熹解释为“信也,是真个执得”。②“厥”,在此为虚词,故关键为“执中”。朱熹引程颐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故执中,就是行“天下之正道”;“允执厥中”,就是坚定不移地行“天下之正道”。为何要行正道?原因就在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何谓“人心”?“人心”何以“惟危”?朱熹认为,人心出之于“形气之私”。“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③
何谓道心?“道心”何以“惟微”?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④他说:“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⑤
正因为人心危殆不安,正因为道心精微难辨,故“惟精惟一”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实现“允执厥中”的前提。故朱熹说:“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所谓“精”,就是“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就是精微地辨析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区别而不混杂;所谓“一”,就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即坚守本心之正而抵御外界物欲的诱惑和困扰。
大体来说,道心与人心,在朱子理学中是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道心出于天理,得性命之正,为圣人所具有,是至善之心,为天命之性;人心大体可视为人欲,出于形气之私,为气质之性。故言“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①从道德修养来说,就是“必使道心常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只有这样,“则危者安,微者著”。危者才能转危为安,精微的儒学道义才能得以彰显。
“道”,指的就是他的理学核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封建伦理纲常。他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②“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陈荣捷先生说:“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③也就是说,“道统”的提出,与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无关。其要点在于“哲学性”,即对“道”的内涵的阐述,思想的继承方面是否有“授受”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对道统的谱系人物进行选择。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出的道统自尧、舜、禹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后孟子“没(殁)而遂失其传”,一直到二程兄弟出,才“续夫千载不传之绪”,道统得以重续,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承孟子,下延至二程兄弟的承传谱系。
在此必须指出,朱熹的道统论的提出,是与他在各地的书院讲学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时,曾有过在此书院祭祀孔圣,而以颜子、子思、曾子、孟子配祀的想法,后因故而未果。他后来回忆说:“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尝欲于云谷左立先圣四贤配,右立二程诸先生,后不曾及。”①此后不久,淳熙六年(1179年)他在任南康知军时,在江州立濂溪祠于军学,主祀周敦颐,而以二程配祀。此为全国祭祀学派先贤的创举。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又将此做法引入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这年十二月,竹林精舍经扩建后,改名为沧洲精舍。借此良机,朱熹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他采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具体操作祭祀仪式的《沧洲精舍释菜仪》,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此为全国书院祭祀孔圣,而以四位门人配祀的创举。而真正由皇家封赠配祀,曾子和子思均是在宋理宗咸淳三年(1267年),②晚于朱熹考亭崇祀70多年。
除祭祀孔圣和四配之外,朱熹认为,周、张、二程等继承了孟子的道统,因此在书院中祭祀这些先贤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惟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③
此文与《中庸章句序》中提出的道统谱系的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在孔圣之前,增加了一个“羲轩”;二是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并强调“周程授受”的关系;三是把“学虽殊辙”的邵雍、张载和司马光,也纳入其道统谱系之中。陈荣捷先生在阐释前两个不同时,认为朱熹的“道统之哲学性,不止基于《书》之十六字诀,而亦基于《易》之太极”。“朱子因须厘清理与气之关系,不得不采用太极阴阳之说。又因二程不言太极,不能不取周子之《太极图》而表彰之。”①由此可知,前设“羲轩”,实为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张目,强调的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伏羲《易》之间的内在联系。此亦即朱熹所说“不繇师传,默契道体”中的“默契”。在此,陈荣捷先生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朱熹的道统论的建构,是与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何俊先生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之学入手的“途径不外有三:一是反身而诚,取内倾的路子;二是于日用中求,取外向的路子;三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求”。②这第三条途径,正是朱熹为何会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等史学著作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何在沧洲精舍祭祀先贤的名单中,会出现以史学见长的司马光之名的原因。
大体而言,《中庸章句序》里的道统谱系,乃是朱熹为阐述《中庸》何为而作时顺带提出,并非专门叙述,故其中沿袭前人的成分居多,而《沧洲精舍告先圣文》里的道统谱系则充分展示了朱熹综合创新的新儒学道统观念。从淳熙十六年(1189年)序《中庸章句》到绍熙五年(1194年)撰《沧洲精舍告先圣文》,虽然不过是短短的五年时间,而朱熹的道统学说至此实际上已经走向全面成熟。
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朱熹道统论的创立,以及他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努力将此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使他的这个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其逝世以后,逐渐为当权者所认可,从思想界走向政界。这其中,他的学生黄榦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他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①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等的道统论,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他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又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②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居敬以主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③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二、朱熹道统论与建本类书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朱熹的道统论是和他在各地书院讲学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书院讲学是其传播道统论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在此之所以用“之一”,是因为朱熹道统论和他的理学思想还有一重要的传播媒介,这便是宋元时期建阳的雕版印刷业。对此,笔者曾有《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建阳刻书及其对武夷文化的传播》①等文,在此不作详述,而仅择其一端,即宋元时期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来加以考量。
何谓类书?类书是辑录史籍中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等,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便查询和检索的工具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由于类书荟群书之萃,既博且精,又通俗易懂,使读者翻阅起来有事半功倍之效,因此,闽北许多学者也动手编纂,且多在建阳刻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朱熹门人祝穆编纂的《事文类聚》、建安谢维新编纂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以及建阳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等。
《事林广记》,全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四十二卷。宋崇安人陈元靓编。陈元靓,号广寒仙裔,著有《博闻录》、《岁时广记》及此书。其行实,据建阳刘纯作《岁时广记引》,称“鳌峰之麓,梅溪之湾,有隐君子广寒之孙。涕唾功名,金玉篇籍,采九流之芳润,撷百氏之英华。……穷力积稔,萃成一书,目曰《岁时广记》”。②可见是一位隐居山林的饱学之士。在刘纯《岁时广记引》之后,又有理学家朱熹之孙朱鉴所作序,而刘纯则是朱熹学生刘爚之孙。由此可知,陈元靓与建阳当地的理学人物有密切的关系。
他所编《事林广记》约成书于宋理宗端平间,是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民间日用类书,开后来建阳书坊刻印日用类书之先河。《事林广记》的宋刻本今已不存,现存的最早刻本是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椿庄书院之名,在闽北的有关地方志书中不见记载,可能只是一个名为书院实为书堂的刻书作坊。1963年中华书局曾据此元刻本影印出版。书中续集卷四《文艺类·琴》中有“夫子杏坛之图”(图17-1),表现的是孔子率门弟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情景。卷五《先贤类》有周敦颐、二程(图17-2)、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图17-3)等人的全身像。除此之外,书中还以示意图的方式列出了周、程和延平四贤,以及朱门中44位主要弟子的传承关系,基本上体现出了朱熹考亭学派的主要阵容(图17-4)。
将书中的《先贤图》和示意图所列人物和朱熹的道统论相对照,可以看出,该书的编者受到朱熹很深的影响,而且是主要是受到了朱熹《沧洲精舍告先圣文》的影响。因为在朱熹此文中,提出了“恭惟道统,远自羲轩。……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节邵先生、横渠张先生、温国司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从祀”①的观点。而《先贤图》所列七位先贤,除朱熹外,正是周、二程、张载、邵雍和司马光,即图17-2:周敦颐、二程图像所谓“北宋六子”。
在此,还必须特别指出,学界有一种从海外流传进来的观点,认为在朱熹以前,北宋道学谱系承认的先驱者有司马光,而自朱熹之后,才出现“北宋五子”,即周、张、二程和邵雍,而将司马光排除在外。其根据是,在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一书中只有五子,而无司马光的言行事迹。这个说法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于,既然朱熹在成书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的《伊洛渊源录》中只承认五子,为何会在二十多年之后的绍熙五年(1194年),在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举行,有全体及门弟子参加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中,提出了“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这一观点呢?
除《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之外,朱熹还为“六子”各书写了一篇像赞,总名为《六先生像赞》。其中写司马光《涑水先生像赞》云:“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带,张拱徐趋。遗象凛然,可肃薄夫。”①他对司马光的评价有“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傥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之道义风节乎?”②而据朱门高弟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③一文的观点,乃“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黄榦所提出的朱熹直继二程的观点,没有被《事林广记》编者所接受,其原因,与朱熹讲学的地点就在考亭书院,而书院的所在地,就在建本的故乡——建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黄榦的讲学地点,则主要在福州等地,他在建阳的影响,尤其是对建阳刻书业的影响,则远不如朱熹。
此外,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下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有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其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同时,又下诏朱熹与周、张、二程从祀孔庙。这既是对宋代“五大道统圣人”地位的确立,同时也是官方对朱熹道统论的认同和肯定。宋建本《事林广记》之成书,正此时也。然而,奇怪的是,编者没有采用官方的五大道统圣人之说,而是仍然沿用朱熹的考亭沧洲精舍之说,由此可见,编者受朱熹影响之深。
据朱门弟子叶贺孙所记载的朱熹在考亭沧洲精舍祭祀先圣先贤的全过程,由于条件所限,书院“堂狭地润”,②所祭先贤,孔圣之外,其余均以纸牌子代替而非塑像或图像,而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图》则有效地弥补了朱熹当年的一个缺憾,为朱熹的道统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个立体和直观的效应。
《事林广记》于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印行之后,广为传播。元明间在建阳书坊曾被多次翻刻,内容则经过后人的不断删改或增补。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此书开了元明间建阳书坊编撰、刻印民间日用类书的先河。
《事林广记》的建阳刻本还有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安郑氏积诚堂刻本、元建阳余氏西园精舍刻本、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刻本、明弘治九年(1496年)建阳詹氏进德精舍刻本等。这些刻本的卷数多经后人的增删或合并,多少不尽相同。有的刻本则增加了一部分元明间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此书东传日本后,曾被日本人多次翻刻,称为“和刻本”。其中首次翻刻此书的,是日本京都山冈市兵卫,时在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所据底本为元泰定二年(1325年)建阳书坊刻本。之所以要将《事林广记》的众多版本在此加以介绍,是为了说明:其一,在时间上,此书从宋代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这就为朱熹的道统观做了旷日持久的且跨越三个朝代的宣传。其二,由于版本众多,其读者和受众当然也就越多,也就为朱熹的道统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其三,作为民间日用之书,《事林广记》的读者主要是普通的老百姓,这就为朱熹的道统论从书院崇祀仅限于儒家学者的层面,转而向普通百姓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媒介,为书院崇祀向民间信仰转化提供了某种可能。
必须指出,朱熹与周、张、二程并列,取得五大道统传人的地位,而从祀学宫,是在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下诏,称颂朱熹使“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令从祀庙堂。其后,各地书院纷纷祭祀朱子。宋宝庆二年(1226年),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于考亭书院内辟文公祠以崇祀朱熹,以黄榦配祀,真德秀为记。淳祐六年(1246年),临漳郡守方来在龙江书院讲堂之东建朱子祠以祀朱熹,以门人陈淳、黄榦配祀。宋嘉熙二年(1238年),福建建宁知府王埜创立建安书院祠朱子,而以真德秀配享。自此,各地书院崇祀朱熹者甚多,难以胜计。毫无疑问,这是借助于朝廷官方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的,与此形成呼应之势的,是出自民间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竟是在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编印成书,在时间上竟然早于宋理宗所下的诏书若干年!
一部民间日用类书,在普及朱熹的道统论,从书院到书本,从书院崇祀到民间信仰的进程中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以闽北为例,在元明以后的各地地方志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诸如“延平四贤”、“建阳七贤”、“建阳蔡氏九儒”、“光泽乌洲李氏七贤”等一系列与朱子理学学派人物有关的记载。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这部建版的畅销书中的道统意识的宣传必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还必须指出,从晚宋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诏从祀孔庙,朱熹取得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①到元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②其间经历了约72年,在这一改朝换代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走向衰败的晚宋和步入强盛的蒙元居然对朱子学几乎采用了同样的措施。然而,当我们刻意去追寻在这一时期有关朱子学的相关历史文献时,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相关历史文献可谓少之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的“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则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由于朱熹长期生活在闽北建阳、武夷山一带,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晚年定居建阳考亭,因此,以其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对南宋建阳的刻书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建阳刻书业的繁荣为闽学的兴起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③这是我在十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当我们认真分析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图》和朱熹的道统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这一观点,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又再一次得到印证。
在此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此建本类书《先贤图》中的朱熹像,其底本,即来自朱熹在建阳考亭的自画像,说明此书所画之先贤像均有所本,而非凭空想象。通常认为,朱熹自画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原立于考亭书院集成殿内的朱熹自画像明代石碑(此石刻现存建阳市博物馆),但与此元代建本版画相比,时间上又晚了数百年。此建本类书虽非专门的圣贤画传,且《先贤图》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但对开启后来出现的诸如明佚名氏《孔门儒教列传》、明吕维祺《圣贤像赞》,以及清代著名画家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中的圣贤图像,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统,即传道之统。朱熹的道统论,即朱熹上承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并加以综合创新的一种新儒学“传道正统”的理念。
孟轲在《孟子·尽心下》中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孔子的传承系统,并以此传承为己任。唐代韩愈则在《原道》一文中重申了孟子之旨,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从而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韩愈的这个理论,开南宋朱熹道统学说之先河,史称“道统论”。“道”,是从儒学的核心思想——伦理纲常而言;“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故又称“道统心传说”。朱熹在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的《中庸章句序》中,首次使用了“道统”一词。他说: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即儒家道统学说的十六字心传,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据传,这十六个字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时,将“允执厥中”四字传授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又在此四字之前加上十二个字,这代代相传的十六个字至此定形。后来禹又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又下传给颜子、曾子、子思,子思传给孟子。据说,这个传承过程是一个“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过程,与后来佛教禅宗的“以心传心”、“自悟自解”的法统相似,故被后儒称为“十六字心传”,被视为是传统儒学,乃至中华文化传统中著名的传心要诀。
宋代理学家朱熹把这十六字作为解读《中庸》一书的钥匙。他认为子思之所以撰《中庸》,是因为子思担心这种传承时间“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②通过朱熹的章句,《中庸》这一儒家经典就成了阐释“十六字心传”的重要典籍。在十六字心传的代代传承中,很自然地又和儒学的传道之统联系在一起。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①
按朱熹的解释,舜后补益的“三言”,是为了阐明“尧之一言”的,故此十六字的关键,仍在后四字上。“允”,朱熹解释为“信也,是真个执得”。②“厥”,在此为虚词,故关键为“执中”。朱熹引程颐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故执中,就是行“天下之正道”;“允执厥中”,就是坚定不移地行“天下之正道”。为何要行正道?原因就在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何谓“人心”?“人心”何以“惟危”?朱熹认为,人心出之于“形气之私”。“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③
何谓道心?“道心”何以“惟微”?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④他说:“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⑤
正因为人心危殆不安,正因为道心精微难辨,故“惟精惟一”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实现“允执厥中”的前提。故朱熹说:“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所谓“精”,就是“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就是精微地辨析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区别而不混杂;所谓“一”,就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即坚守本心之正而抵御外界物欲的诱惑和困扰。
大体来说,道心与人心,在朱子理学中是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道心出于天理,得性命之正,为圣人所具有,是至善之心,为天命之性;人心大体可视为人欲,出于形气之私,为气质之性。故言“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①从道德修养来说,就是“必使道心常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只有这样,“则危者安,微者著”。危者才能转危为安,精微的儒学道义才能得以彰显。
“道”,指的就是他的理学核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封建伦理纲常。他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②“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陈荣捷先生说:“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③也就是说,“道统”的提出,与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无关。其要点在于“哲学性”,即对“道”的内涵的阐述,思想的继承方面是否有“授受”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对道统的谱系人物进行选择。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出的道统自尧、舜、禹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后孟子“没(殁)而遂失其传”,一直到二程兄弟出,才“续夫千载不传之绪”,道统得以重续,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承孟子,下延至二程兄弟的承传谱系。
在此必须指出,朱熹的道统论的提出,是与他在各地的书院讲学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时,曾有过在此书院祭祀孔圣,而以颜子、子思、曾子、孟子配祀的想法,后因故而未果。他后来回忆说:“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尝欲于云谷左立先圣四贤配,右立二程诸先生,后不曾及。”①此后不久,淳熙六年(1179年)他在任南康知军时,在江州立濂溪祠于军学,主祀周敦颐,而以二程配祀。此为全国祭祀学派先贤的创举。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又将此做法引入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这年十二月,竹林精舍经扩建后,改名为沧洲精舍。借此良机,朱熹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他采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具体操作祭祀仪式的《沧洲精舍释菜仪》,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此为全国书院祭祀孔圣,而以四位门人配祀的创举。而真正由皇家封赠配祀,曾子和子思均是在宋理宗咸淳三年(1267年),②晚于朱熹考亭崇祀70多年。
除祭祀孔圣和四配之外,朱熹认为,周、张、二程等继承了孟子的道统,因此在书院中祭祀这些先贤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惟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③
此文与《中庸章句序》中提出的道统谱系的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在孔圣之前,增加了一个“羲轩”;二是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并强调“周程授受”的关系;三是把“学虽殊辙”的邵雍、张载和司马光,也纳入其道统谱系之中。陈荣捷先生在阐释前两个不同时,认为朱熹的“道统之哲学性,不止基于《书》之十六字诀,而亦基于《易》之太极”。“朱子因须厘清理与气之关系,不得不采用太极阴阳之说。又因二程不言太极,不能不取周子之《太极图》而表彰之。”①由此可知,前设“羲轩”,实为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张目,强调的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伏羲《易》之间的内在联系。此亦即朱熹所说“不繇师传,默契道体”中的“默契”。在此,陈荣捷先生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朱熹的道统论的建构,是与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何俊先生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之学入手的“途径不外有三:一是反身而诚,取内倾的路子;二是于日用中求,取外向的路子;三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求”。②这第三条途径,正是朱熹为何会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等史学著作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何在沧洲精舍祭祀先贤的名单中,会出现以史学见长的司马光之名的原因。
大体而言,《中庸章句序》里的道统谱系,乃是朱熹为阐述《中庸》何为而作时顺带提出,并非专门叙述,故其中沿袭前人的成分居多,而《沧洲精舍告先圣文》里的道统谱系则充分展示了朱熹综合创新的新儒学道统观念。从淳熙十六年(1189年)序《中庸章句》到绍熙五年(1194年)撰《沧洲精舍告先圣文》,虽然不过是短短的五年时间,而朱熹的道统学说至此实际上已经走向全面成熟。
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朱熹道统论的创立,以及他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努力将此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使他的这个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其逝世以后,逐渐为当权者所认可,从思想界走向政界。这其中,他的学生黄榦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他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①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等的道统论,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他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又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②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居敬以主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③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二、朱熹道统论与建本类书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朱熹的道统论是和他在各地书院讲学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书院讲学是其传播道统论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在此之所以用“之一”,是因为朱熹道统论和他的理学思想还有一重要的传播媒介,这便是宋元时期建阳的雕版印刷业。对此,笔者曾有《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建阳刻书及其对武夷文化的传播》①等文,在此不作详述,而仅择其一端,即宋元时期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来加以考量。
何谓类书?类书是辑录史籍中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等,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便查询和检索的工具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由于类书荟群书之萃,既博且精,又通俗易懂,使读者翻阅起来有事半功倍之效,因此,闽北许多学者也动手编纂,且多在建阳刻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朱熹门人祝穆编纂的《事文类聚》、建安谢维新编纂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以及建阳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等。
《事林广记》,全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四十二卷。宋崇安人陈元靓编。陈元靓,号广寒仙裔,著有《博闻录》、《岁时广记》及此书。其行实,据建阳刘纯作《岁时广记引》,称“鳌峰之麓,梅溪之湾,有隐君子广寒之孙。涕唾功名,金玉篇籍,采九流之芳润,撷百氏之英华。……穷力积稔,萃成一书,目曰《岁时广记》”。②可见是一位隐居山林的饱学之士。在刘纯《岁时广记引》之后,又有理学家朱熹之孙朱鉴所作序,而刘纯则是朱熹学生刘爚之孙。由此可知,陈元靓与建阳当地的理学人物有密切的关系。
他所编《事林广记》约成书于宋理宗端平间,是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民间日用类书,开后来建阳书坊刻印日用类书之先河。《事林广记》的宋刻本今已不存,现存的最早刻本是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椿庄书院之名,在闽北的有关地方志书中不见记载,可能只是一个名为书院实为书堂的刻书作坊。1963年中华书局曾据此元刻本影印出版。书中续集卷四《文艺类·琴》中有“夫子杏坛之图”(图17-1),表现的是孔子率门弟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情景。卷五《先贤类》有周敦颐、二程(图17-2)、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图17-3)等人的全身像。除此之外,书中还以示意图的方式列出了周、程和延平四贤,以及朱门中44位主要弟子的传承关系,基本上体现出了朱熹考亭学派的主要阵容(图17-4)。
将书中的《先贤图》和示意图所列人物和朱熹的道统论相对照,可以看出,该书的编者受到朱熹很深的影响,而且是主要是受到了朱熹《沧洲精舍告先圣文》的影响。因为在朱熹此文中,提出了“恭惟道统,远自羲轩。……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节邵先生、横渠张先生、温国司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从祀”①的观点。而《先贤图》所列七位先贤,除朱熹外,正是周、二程、张载、邵雍和司马光,即图17-2:周敦颐、二程图像所谓“北宋六子”。
在此,还必须特别指出,学界有一种从海外流传进来的观点,认为在朱熹以前,北宋道学谱系承认的先驱者有司马光,而自朱熹之后,才出现“北宋五子”,即周、张、二程和邵雍,而将司马光排除在外。其根据是,在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一书中只有五子,而无司马光的言行事迹。这个说法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于,既然朱熹在成书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的《伊洛渊源录》中只承认五子,为何会在二十多年之后的绍熙五年(1194年),在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举行,有全体及门弟子参加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中,提出了“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这一观点呢?
除《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之外,朱熹还为“六子”各书写了一篇像赞,总名为《六先生像赞》。其中写司马光《涑水先生像赞》云:“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带,张拱徐趋。遗象凛然,可肃薄夫。”①他对司马光的评价有“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傥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之道义风节乎?”②而据朱门高弟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③一文的观点,乃“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黄榦所提出的朱熹直继二程的观点,没有被《事林广记》编者所接受,其原因,与朱熹讲学的地点就在考亭书院,而书院的所在地,就在建本的故乡——建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黄榦的讲学地点,则主要在福州等地,他在建阳的影响,尤其是对建阳刻书业的影响,则远不如朱熹。
此外,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下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有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其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同时,又下诏朱熹与周、张、二程从祀孔庙。这既是对宋代“五大道统圣人”地位的确立,同时也是官方对朱熹道统论的认同和肯定。宋建本《事林广记》之成书,正此时也。然而,奇怪的是,编者没有采用官方的五大道统圣人之说,而是仍然沿用朱熹的考亭沧洲精舍之说,由此可见,编者受朱熹影响之深。
据朱门弟子叶贺孙所记载的朱熹在考亭沧洲精舍祭祀先圣先贤的全过程,由于条件所限,书院“堂狭地润”,②所祭先贤,孔圣之外,其余均以纸牌子代替而非塑像或图像,而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图》则有效地弥补了朱熹当年的一个缺憾,为朱熹的道统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个立体和直观的效应。
《事林广记》于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印行之后,广为传播。元明间在建阳书坊曾被多次翻刻,内容则经过后人的不断删改或增补。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此书开了元明间建阳书坊编撰、刻印民间日用类书的先河。
《事林广记》的建阳刻本还有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安郑氏积诚堂刻本、元建阳余氏西园精舍刻本、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刻本、明弘治九年(1496年)建阳詹氏进德精舍刻本等。这些刻本的卷数多经后人的增删或合并,多少不尽相同。有的刻本则增加了一部分元明间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此书东传日本后,曾被日本人多次翻刻,称为“和刻本”。其中首次翻刻此书的,是日本京都山冈市兵卫,时在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所据底本为元泰定二年(1325年)建阳书坊刻本。之所以要将《事林广记》的众多版本在此加以介绍,是为了说明:其一,在时间上,此书从宋代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这就为朱熹的道统观做了旷日持久的且跨越三个朝代的宣传。其二,由于版本众多,其读者和受众当然也就越多,也就为朱熹的道统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其三,作为民间日用之书,《事林广记》的读者主要是普通的老百姓,这就为朱熹的道统论从书院崇祀仅限于儒家学者的层面,转而向普通百姓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媒介,为书院崇祀向民间信仰转化提供了某种可能。
必须指出,朱熹与周、张、二程并列,取得五大道统传人的地位,而从祀学宫,是在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下诏,称颂朱熹使“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令从祀庙堂。其后,各地书院纷纷祭祀朱子。宋宝庆二年(1226年),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于考亭书院内辟文公祠以崇祀朱熹,以黄榦配祀,真德秀为记。淳祐六年(1246年),临漳郡守方来在龙江书院讲堂之东建朱子祠以祀朱熹,以门人陈淳、黄榦配祀。宋嘉熙二年(1238年),福建建宁知府王埜创立建安书院祠朱子,而以真德秀配享。自此,各地书院崇祀朱熹者甚多,难以胜计。毫无疑问,这是借助于朝廷官方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的,与此形成呼应之势的,是出自民间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竟是在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编印成书,在时间上竟然早于宋理宗所下的诏书若干年!
一部民间日用类书,在普及朱熹的道统论,从书院到书本,从书院崇祀到民间信仰的进程中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以闽北为例,在元明以后的各地地方志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诸如“延平四贤”、“建阳七贤”、“建阳蔡氏九儒”、“光泽乌洲李氏七贤”等一系列与朱子理学学派人物有关的记载。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这部建版的畅销书中的道统意识的宣传必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还必须指出,从晚宋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诏从祀孔庙,朱熹取得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①到元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②其间经历了约72年,在这一改朝换代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走向衰败的晚宋和步入强盛的蒙元居然对朱子学几乎采用了同样的措施。然而,当我们刻意去追寻在这一时期有关朱子学的相关历史文献时,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相关历史文献可谓少之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的“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则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由于朱熹长期生活在闽北建阳、武夷山一带,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晚年定居建阳考亭,因此,以其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对南宋建阳的刻书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建阳刻书业的繁荣为闽学的兴起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③这是我在十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当我们认真分析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图》和朱熹的道统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这一观点,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又再一次得到印证。
在此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此建本类书《先贤图》中的朱熹像,其底本,即来自朱熹在建阳考亭的自画像,说明此书所画之先贤像均有所本,而非凭空想象。通常认为,朱熹自画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原立于考亭书院集成殿内的朱熹自画像明代石碑(此石刻现存建阳市博物馆),但与此元代建本版画相比,时间上又晚了数百年。此建本类书虽非专门的圣贤画传,且《先贤图》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但对开启后来出现的诸如明佚名氏《孔门儒教列传》、明吕维祺《圣贤像赞》,以及清代著名画家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中的圣贤图像,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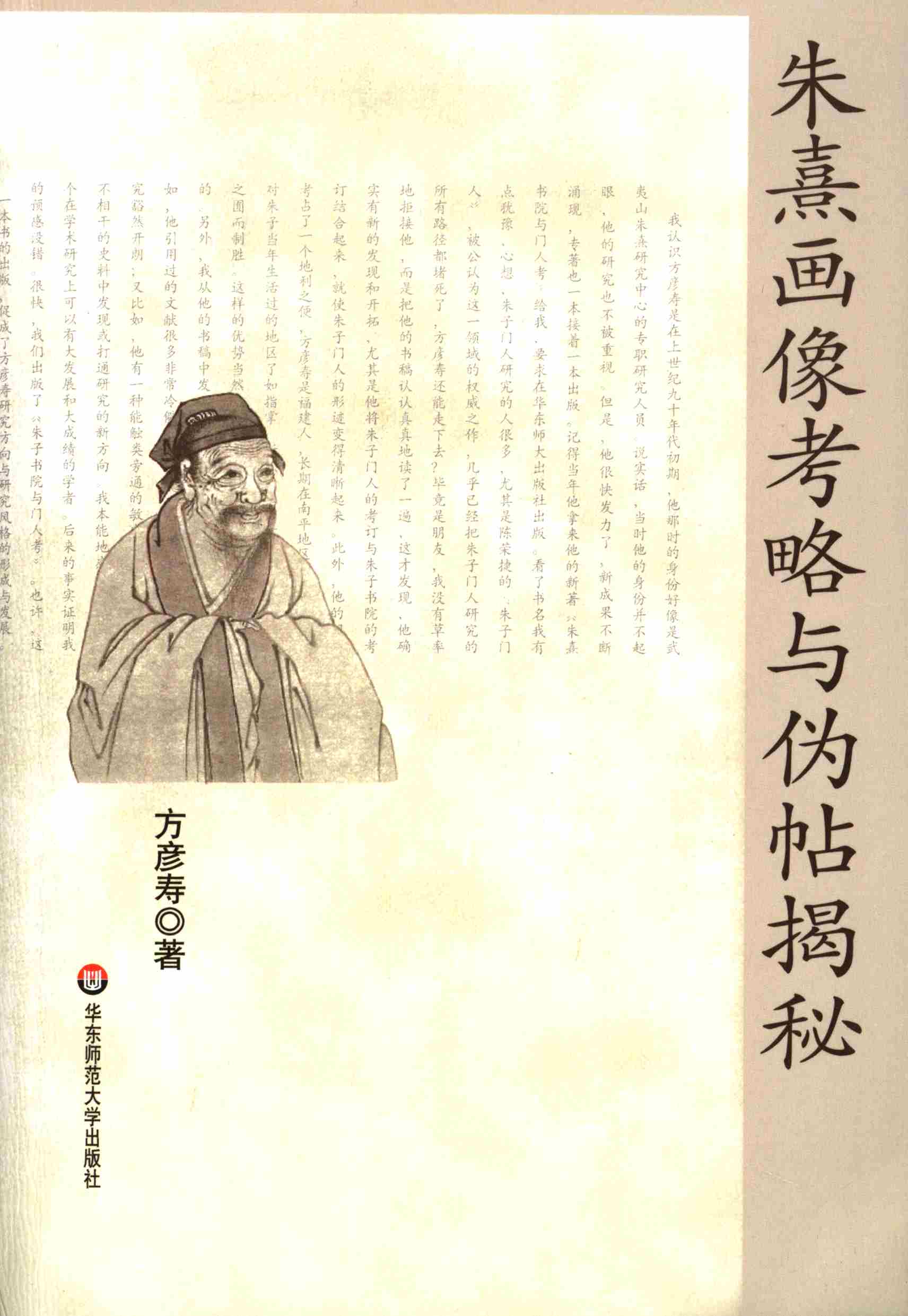
《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分上下两卷。卷上为朱熹画像考略,分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朱熹画像的产生与流传进行了考证和介绍。卷下为朱熹伪帖揭秘,主要内容为对近年出现在国内拍卖市场的号称“朱熹手迹”甚至被吹嘘为“国宝”,经过古今所谓名家鉴定的几幅伪帖。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