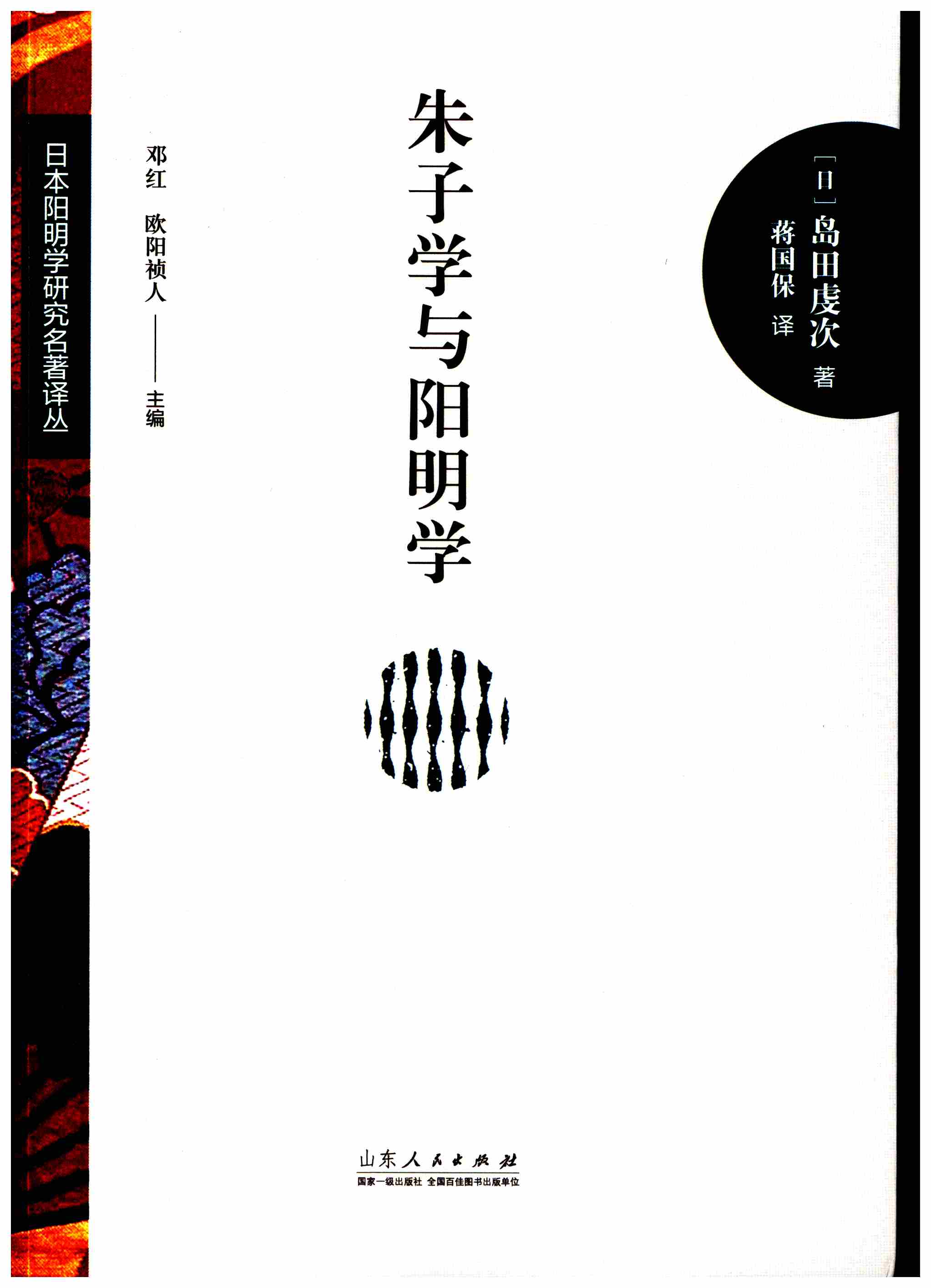第四章 懦教的叛逆者——贽(李卓吾)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阳明学》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908 |
| 颗粒名称: | 第四章 懦教的叛逆者——贽(李卓吾)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3 |
| 页码: | 121-143 |
| 摘要: | 本文讨论了宋以后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局面,即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纠葛,以及朱子学的“性即理”和陆王学的“心即理”的对立和抗争。文章指出,两者的目标相同,但对于实现目标的原理和方法却存在分歧。其中,“心即理”说由于将没区别性、情的原封不动的“心”设为理,导致了一系列与朱子学不同的倾向,如对情的肯定、对权威的轻视、对异端的包容等。而朱子学派则不断警告这些倾向的危险性。文章还提到了阳明学的“良知”说,并指出主观唯心论在阳明那里达到了顶峰,但其后不得不立于诡辩的境地。 |
| 关键词: | 朱子 研究 哲学 |
内容
—贽(李卓吾)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人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蒙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李贽《续焚书》卷四《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思想史的背景
宋(公元960年建国)以后的中国是士大夫的中国,士大夫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是广义的宋学[13]13。宋学,根据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家的分类,包括三个流派。第一是张载(张橫渠)所创立的唯物论,即“气”的哲学。第二是开始于程颐(程伊川)而由朱熹完成的客观唯心论,即“性即理”的哲学。这个所谓的朱子学,不久,永久地占据国教的地位,因为其过分的整齐性、完结性,终于没能期待值得一提的独创的后学[14]14。第三是陆九渊(陆象山)主张的主观唯心论,即“心即理”的哲学。作为其先驱,举程颢(伊川之兄程明道),最适当;作为其后劲,举明代的王守仁(王阳明),是定说。
这三派之中,唯物论的系统在现今的中国最被强调,从这个新的着眼做的思想史的发掘、改写,接连不断地取得成果[15]15。即便没等新中国成立,继承张横渠的大哲学家·清初的王夫之(王船山)的存在,也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切合思想史的纠葛而平心地思索时,这样的看法——这个
系统并没有起到另外二系统[那样]程度的作用,被认为毕竟还是妥当的。张横渠的“气”的哲学,事实上被完全吸收于朱子的“理气”说之中。即便王船山,生前不必说,直到死后一百五十年、清朝的末期再发现,其著述和思想也完全沉睡在湖南省的偏僻的乡村里,这说得不夸张。尽管不用说思想的确在那里存在着,应该珍视;而且,正因为那个缘故,死后一百五十至二百年之后,在[民国]民族主义风潮中,它起到了伟大的作用,这是不可怀疑的事实。
宋以后的思想史之最重要的局面,仍然在于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纠葛;朱子学的“性即理”和陆王学的“心即理”的对立、抗争。不用说,这并不是说一方是体制方面的思想,另一方是反体制方面的思想。体制的维持、名教的拥护,这是两者一致高唱的大理想。两者都是一样把“理”的存在作为前提、把“理”的死守作为使命的理想主义。要说那个抗争,简言之,不过是站在同一立场的霸权的争夺战。这样的说法,充分有道理。否,岂止那样,连立这样的说法(非官学的陆王学的方面,是更彻底的体制拥护性的,是对体制更彻底的奴隶性的)也是可能的。若借用张横渠—朱子的定义,不外乎“心是性与情的统一体”,但“性即理”仅是这个“心=性+情”的一部分,即相对于只不过把性作为理,“心即理”说是举心全体(其具体的内容就是五伦五常)作为理,能看作“为封建伦理提供一个更直接的根据的东西”。朱子的格物说,这样解释:事事物物里有“理”,通过穷之格之,可以检证、把握自己内在的“理”。对此,阳明抨击说:总而言之,这无非“求理于外”的观点,假如以为孝之理在为“外”的双亲,双亲如果死了,那么孝之理就消失了吗?自古以来,作为孝之最大的节目的丧、祭就是无意义的事吗?理完全在“内”,完全在“我心”,以此一事就可知(《传习录》,岩波文库本一二七页)。
诚然,目标也许相同,但对于那个相同的目标,所谓“性即理”“心即理”,其各自的原理,或者方法,都是整合性的吗?
我认为,“性即理”方面是整合性的,但“心即理”方面不是那样。其详细[内容]不具有解释的余裕,现在想暂时指出以下诸点,即“心即理”说由于把没区别性、情(情具有一直流到本性上的“欲”的倾向)的原封不动的“心”设为理,所以导致出这些倾向:情—欲望(所谓人欲)的肯定;“人之自然”的主张;对朱子学那般重视的“敬”的轻视;对宛如“六经是我心之注脚”这样的权威的轻视;对异端的包容的态度等[16]1[16]。而朱子学派却不停地严厉警告这几点。
虽然从客观唯心论方面不断地攻击其原理、方法的危险性,但主观唯心论的流派,程明道到陆象山直到王阳明,不管怎样,可能没有很大的破绽。王阳明的“良知”说(所谓良知,是根据孟子的语言,把像心即理那样的心标准化者)可以说是其顶峰。而且,在阳明那里达到顶点的主观唯心论,不久,假如就其目标而言,可以说不能不立于诡辩的境地,达到不使我那原本包藏着的祸心被发现[的地步]吧(阳明学左派)。作为其契机的是,良知的人的平等性,由于阳明,被热情地主张(满街都是圣人);人由于只有把“内”“良知”作为问题,反倒开辟了对于“外”的知识、技能等的积极评价之道,开放了自由主义的风气[17]17,等等。与此一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主观唯心论的系列从最初就伏流的“万物一体之仁”“生生不能止”之说是同良知结合的。良知已经不是个人的平静的修养项目,而成为应该实现万物一体的觉醒运动、精神的救世运动。
孔子汲汲遑遑,宛如寻找丢失的自己儿子,而无暇于席之暖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疾痛迫切,虽欲已而不容已者。所以孔子说“我不与斯人之徒(成为这个人的人们)而谁与”“洁其身(隐遁)而乱大伦(社会的存在这样的人正当应有的状态),果
(敢)哉。(然而这样的事实际)不难矣”[18]18[18]。啊,非真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谁知夫子之心矣。(《传习录》,同上二一八页)良知是作为万物一体虽欲已而不能已者,生生不能止者。“与其为数顷无源的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的井水之生意无穷”(《传习录》,同上六七页)。——假如省于吾心而[以为]非,则虽孔子之言亦不以为是(《传习录》,同上二〇五页)这样的良知,是主张万物一体、民是胞,物是与。但是,为动辄企图超越被派定的界限、本分的“生生不容已”的流动主义所保证的时候,就“抛弃五伦中的四伦”,仅以“朋友”一伦为“生命”,产生“只诚心诚意达性真,在恶名里埋没一世亦不顾及”这样的“阳明学左派”的“狂”[19]。最后的结局,勃发了应该说是思想之暴动的思潮。其时期,与正当那时开始的社会暴动、所谓“民变”的时期,正好一致[20]201。
思想的暴徒,那就是李卓吾。
生涯
李贽,字或号是卓吾,通常以李卓吾被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的读书人家,因为晋江县[县衙]在泉州的城内,总之是泉州城的人,生卒年代是明嘉靖元年至万历十年(1527—1602),即生于明朝文化最成熟的时期。其生年在阳明逝世的前年,卒年在“中国的卢梭”黄宗羲出生的八年前、明朝灭亡的四十二年前。就日本说,川中岛交战、太合的朝鲜征伐是他生涯中发生的事情,德川家康被任为征夷大将军是在其逝世的翌年,就是说是包括靠战国的安土·桃山时代。就欧洲说,哥伦布死后二十年诞生、是与马丁·路德大略相重二十多年、与米开朗琪罗相重三十多年的后辈,与蒙田完全是相重的同代人。无论日本还是欧洲,都处在历史的大转折点。
卓吾在那里出生、到二十至三十岁间一直生活在泉州这个地方。这是个很特异的城镇,和广东一起,是唐以来中国最大的外国贸易港,否,在元朝的时期里,是“世界两个最大的贸易港之一”(马可·波罗)。而且,因为当时的贸易是所谓的南海贸易,渡来很多伊斯兰教徒,因而,是在中国的伊斯兰(回族)的大中心地。现在仍遗留着的泉州的伊斯兰寺院·清真寺,一〇〇九年或一〇一〇年着手奠基(改建于元代)。可是,一旦进入明代,作为国是的海禁政策的结果,外国贸易全部衰落,因而泉州的繁荣也似乎同以前的时代无法比拟,但泉州与其附近(厦门等)仍然作为秘密贸易的中心地而具有高度的活气。此地的缙绅,甚至时常显示出左右中央政局的势力。李卓吾家原来也是泉州的商人。其先祖之中,也有人于明朝初期跑到波斯湾,且长期逗留,在那里娶当地人为妻的;还有人由于官命而做翻译官的工作,“引导日本和琉球的入贡使上京”。这些事,由于几年前在当地发现《族谱》之后才成为被人所知的事实。《族谱》还载明李卓吾的家代代是回族,即伊斯兰教徒。妻子黄氏好像也同样是回族。若把[他家]当作严格的回族家庭,则是当然的事[21]21。
二十六岁,通过科举第一关的乡试,获得举人的资格。这件事本身,只意味着向作为士大夫的正式成员迈出了第一步,没有一点出奇的地方。他晚年回忆那时之事的文章,因为的确是卓吾谱系,故准备引用。
成长之后也是个呆子,即便读(为科举考试准备的《四书集注》等)传注之类也不能理解,不能领会朱子的深意。因此感到厌恶,打算抛弃而结束[读经]。那样的话,就很闲暇,无以消磨时间,乃叹曰:“总之,因为不过是儿戏,无论剽窃、无论如何,若乱七八糟地摆着,就很多。说是考试官,也不可能从一到十都通孔圣的奥义”因此,取八股文之尖新而值得玩诵者,每日背诵数篇,至考试那一天,大约五百篇运用自如,一旦被分给答案用纸,就一个劲地开始作缮写人,
于是以优秀的成绩及第。(《焚书》三《卓吾略论》)以后,抛弃作为科举之正式演出的进士考试,在河南、南京、北京辗转任最下级的官吏,[又任]南京刑部员外郎这样的闲职,好容易在五十一岁的时候出任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然五十四岁就已经辞退。这就是他官历的全部。说到知府,总算是个官,但若看被派遣到云南这样的边境,总而言之,作为官吏也不是太显著的经历。
随着辞职而寄身于湖北省黄安县(汉口的东北方向)的耿氏檐下,不久,因同后来的户部尚书(大藏大臣)耿定向在思想上对立,强硬地提出绝交信,迁移到麻城县龙湖的芝佛院(五十九岁)。在这麻城的十多年间,是他作为思想家、评论家活动的最高潮时期。像代表作《藏书》六十八卷、《焚书》六卷,都出版于这个时期。作为反面又危险的思想家,来自正人君子的[对他的]憎恶和迫害,变换手段,变换面孔,越来越激烈,不能停止。在芝佛院,他的日常生活,与其说只是寄食者,事实上,倒不如说几乎接近僧陀,终于在某一天,断然剃发。这样,由于既不像僧又不像儒的奇奇怪怪的打扮[22][22],故喧嚣的舆论更喧嚣。夏日,不能忍耐头痒完全剃掉头发这件事,好像是实情,然有时候又自说:
因为无见识辈把自己呼为异端,我才进步成为异端,使竖子成名。
(《续焚书》一,《与曾继泉》)宛如好事的这一挑战的、战斗的态度,绝不只是这一端,直至临终,都是卓吾的特征。又,接着准备在这里介绍《自赞》、即应该说是其自画像的他的文章:
其性偏狭,其色矜高(高傲),其语卑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
(轻率)。其交际少,然若见面则热情地亲近。与(赞成)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长处;恶人也,已与那人绝交又欲终身害那个人。志在暖衣饱食,而自以伯夷叔齐为任;本来等同于(破廉耻的那个《孟子》中的)齐人,而又自谓饱道饫德;一介也不与人的事明明白白,而借口伊尹的故事;(为了人)不拔一毛的(事等同于杨朱)明明白白,又(模仿孟子说法)称杨朱为贼仁者;动则逆物,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如何?”子曰:“未可也”。像居士,其可乎哉!(《焚书》三)
事实上他是狷介而难以接近的人物,又是极度爱干净的人。某个传记里说,[他]“性爱扫地,即便数人专管扫地,尚不足。擦拭脸和身,确有水淫之感。”
一六〇〇年,七十四岁,麻城的宪官和以宪官作后盾的士大夫,作为过去几次对他迫害的总检举,终于对他下达了驱逐令,打毁芝佛院及为埋骨准备的塔[也同时]执行。他被崇拜者伴随着逃难,远逃至北京附近的通州,后年一六〇二年闰二月,被逮捕,三月十六日在北京的狱中自杀,享年七十六岁。著书、雕版、草稿,全部被烧毁,即便进入接着的清朝,其著述也被列在禁书目录之中[23]23。
李卓吾曾直接师事王心斋之子王东涯,对王龙溪一生倾倒,至于对王阳明的崇拜,则不待言。亦有《阳明先生年谱》《阳明先生道学钞》等著述。因太破格的缘故,他没列入《明儒学案》,但他是阳明学派的人,尤其是阳明学左派的人,这没有异议。
童心之说
假如把李卓吾的根本思想用一言来说,毕竟还是“童心”吧。以下介
绍收进《焚书》卷三的文学论的《童心说》。
龙洞山农在《西厢记》的序文的末尾说:“识者勿责怪余之尚未脱离童心可也。”但是,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假如以童心为不可,这就是以真心为不可。
所谓“真”,是“假”的相反概念。所谓“假”,是“借”的意思,似而非、虚伪,总而言之,指不是真的,是假的。
童心者,是与假无缘而纯粹真的东西(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假如失掉童心,就是失掉真心。假如失掉真心,就是失掉作为真人。做人若无真,就应该说已经全然没有“初”者。童子是人之初,
童心是心之初。心之初者,究竟是失掉也可以的东西吗?这段,遵循宋学里议论纷纷的“复初”说而曰:
可是,童心什么原因突然地失掉呢(胡然而遽失)?大概,最初闻见从耳目而入,成为内之主,于是童心被丢失。长大,道理乘闻见而入,成为内之主,于是童心被丢失。一旦久之,道理和闻见,日日越发多,因而所知所觉,日日越发广,在此时,越发知应好美名,而意欲扬之,于是童心被丢失;知应以不美之名为丑,而意欲掩(隐瞒)之,于是童心被丢失。
“道理”这个语词,作为消极价值的语言被使用方面,应该注意。在别的文章里,名教这个语词,仁者这个语词,都有在消极价值上被使用的例子。“天下之人得其所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人失所而忧,而汲汲然贻(送)得所之域。因为这种原因,以德礼格其心,以刑政絷(束缚)其四体,于是人始失所”(《焚书》一,《答耿中
丞》)。接着准备引用该书简中的一节:“……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的言)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供)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满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那么,继续[谈]童心说:
道理、闻见最初全都是从多读书、识义理来。古之圣人何尝不读书?但是,即便不读书,童心本来自在;即便多读书,依然由此护童心,无外乎使勿丢失,与学问者由于多读书、识义理反倒障(妨碍)它不同。学问者,既然以多读书、识义理障那个童心,[那么]圣人仍旧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的必要[性],在哪里呢?
这里能看到的,和他在别处发的“应畏者书哉”的叹息,是相同的叹息。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这样的逻辑:对于确实打动自己的东西来说,没有理由惧怕读书。本来,极度强调“内”的阳明的良知说,把读书和教养作为“外”的东西,对它的确是很警惕的。——被卓吾憎恶到那般程度者,他们不只是道学先生,毋宁指广泛的读书、教养之人。但是,由于那样,无非是引起体无完肤地批判和攻击。
童心既然被障,一旦发而成为言语,那言语就不是发自衷心的东西;见(表现)而成为政事,政事就无根柢;著而成为文辞,文辞不能达;既不是由于有含内者而章美的东西,也不是充实而生光辉的东西。欲求一句有德之言,终于不能得。缘由如何?因为童心已经被障,以无非由外而入的闻见道理为心。
已经以闻见道理为心。那么,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不是出自童心之言;言虽巧,同[真的]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正好是假人说假话,则事是假事、文是假文吗?其人已经假,实行起来则无不假。
于是,若以假言语假人,则假人喜;若以假事道假人,则假人喜;若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因为无所不假,故无所不喜。满场假也,矮人辨何也?矮人云云,是用所谓矮人观场、矮人剧值得看的比喻,指附和雷同他人做出的评价。卓吾最憎恶的是假,尤其对“假道学”(不只是道学先生,广泛地包括立足儒教主义的一般官僚)的伪善和无能,确实竭尽痛骂嘲笑之能事。但我想指出一点,即这个“假”和“真”的尖锐且执拗的对置,立足其上的“真”的热情的主张,不仅可以说是开始于阳明左派而在卓吾达到顶点的一个“党派”意识,同时又和“生生不能止”一起,也是嘉靖万历广泛的精神史的一个基调。卓吾的书席卷读书界,是因为他最鲜明地表现了时代意识。——那么,接着进入狭义的文艺论。
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因假人被湮灭而不尽被后世知者,决不少吧!何谓也?作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自童心者。假如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任何的创制体格(体裁)的文章都无不文。诗何必古选(《文选》)。文何必先秦。降而成为六朝(骈文),变而成为近体(律诗、绝句等),又变而成为传奇(小说),变而成为院本(脚本)、成为杂剧(歌舞伎)、成为《西厢记》、成为《水浒传》,成为今日的八股文。都是古今的至文,不能以时世的先后论(古代的东西最好)。如此去看时,我渐渐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事已至此,[说]什么六经,[说]什么语孟(《论语》《孟子》)。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是意识到所谓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拟古主义而说的,这不怀疑。尽管那样,也应该注意,将“诲淫”的俗文学《西厢记》、“诲盗”的俗文学《水浒传》之类表彰为古今之至文,而且,为了表
彰它们,连悍然降低六经、语孟也不辞的那个精神态度之激昂。
那六经、语、孟,不是那个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就是那个臣子极度赞美之语,又不然,则迂阔之门徒、懵懂之弟子们,记忆师之说,有头无尾,得后遣前,随其所见,记下来成为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决定目之为经,谁知大半不是圣人之言。纵然出自圣人之口,总而言之,是有所为而发的东西,只不过是应病予药、随时处方,打算救治这样的懵懂弟子、迂阔门徒的东西。如果药只不过为了医“假”这样的病,处方不能固执,怎么能率然视为万世之至论呢?然则,六经、语、孟,是道学先生的口实,假人的渊薮,断断乎不可能在童心之言前拿出来,是明白的。呜呼![吾]安得真正的大圣人之童心还未曾失者,一同语一次文哉!
以上是《童心说》的全文。而关于卓吾作为批评家、评论家的多方面的活动,现在不涉及。在当今的中国,认为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但阳明左派(泰州学派)—李卓吾是唯物论,想竭力将两者拉开的试图是显著的。这样的试图,在今日的中国,具有某种现实的意义的事,尽管能了解[24],但说它在学问上几乎不具有什么说服力,则非言过其实。假如排除凡是进步的、反抗的思想全都应该是唯物论这样的教条来思索的话,则宛如我曾经的论证,卓吾依然是主观唯心论者王阳明的“嫡派儿孙”,其“童心”可以说是“良知”的成年。
历史批判
作为《焚书》的代表性的一篇,我在上面解说了《童心说》。下面,想介绍《藏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里所说的“古今未曾有的过激思想
之史论”)中的总论性的两篇。不同于《焚书》是收集书简、杂多的随笔、诗等所谓的文集,《藏书》方面,由始至终的著述,都是世纪和列传,即被用纪传体写的中国史(从战国到元代)。在人物的分类方法上,又,在到处添加的评论上,“绝《纲目》(朱子的《通鉴纲目》)谱系的道学头巾习气,快捷轻俊,充满谋反气”[25]5。姑且不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说:“李贽之书,皆狂悖乖谬,以圣为非无法,尤其此书攻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莫不颠倒而易位,其罪不容诛”,在中国的史部之书中,它一定是最独特的一部书。
首先介绍第一篇《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简言之,是《藏书》全书的序文。
李氏曰,人之是非,原无定质,人之对于人的是非,亦无定论。因为无定质,故此是与彼非,并育不相害;因为无定论,故以此为是与以彼为非,并行而不相悖。这样看来,今日之是非,谓余李卓吾一人的(私的)是非可也,谓千万世之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再非是余所以为的非是,亦可也。余之是非,唯有任其可矣。这的确是典型的分类排列(raisonnement)的立场(黑格尔)。
前三代(夏、殷、周),现在不论。所谓后三代,是汉、唐、宋,其间千百余年,而全然无是非。是其人的确无是非吗?因为皆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以只不过是一点儿是非也没有。假如像这样去看,我是非人者,此又有不能已(止)者。这是非之争,如同四季[循环]似的、昼夜更迭,而无一致。昨日为是,今日为非;今日为非,而后日又是,即便使孔子复生于今日,不知究竟作如何的是非也。而能率
然以定本(一定不变的基准)行赏罚(批判、毁誉褒贬)吗?
……此书,只能自怡,但不能示人,故名之曰《藏书》[26],无奈一二好事朋友非要阅读,我即便断绝关系也不停止。只有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观,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则善矣”。诚然,卓吾的立场,也许是既可那么说也可这么说的立场。但是,同样不应该忽视附加这样一条:唯有不干以孔子的准则为准则、并且[照着]做的事。他的立场始终是战斗的,否,挑战的。——名教者流派迫害他,把他下狱,逼到死的地步,但假如接受其挑战而奋起相互光明磊落的论战,则儒教思想、中国思想,也许可能开创意想不到的生面!利玛窦已经来中国活动,卓吾同他也几次会见,对其人不惜赞辞(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的刊行,是在卓吾死于狱中的翌年);另一方面,佛教界,此时[出现]以卓吾的知己——紫柏真可为首而龙象辈出之生气勃勃的结尾——这进入清朝就极度地沉滞。对中国思想史来说,这确实不是千载难逢吗?我想在这里再次引用旧稿(参照注十三)中的话语:《易》有云:“物穷则变,变则通”,虽穷大概欲变,但终于不能变,这不是从思想史上看的明代的情况吗?被冠于本章开头的卓吾一文,的确应该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感慨来读。
那么,接着[介绍]《世纪总论》,也就是各论的总序。
李生曰,“一治一乱”(孟子语,有历史价值的意思)如同循环的环。战国以来,大概不知几治几乱也。正当其乱,仅保住首领(脑袋),已是幸福。一旦有幸逢“治”,若能饱食则足,不介意是否粗粝;能睡眠则满足,不介意是否大厦。这是极“质”极“野”而无文之时。不是喜好“野”,是势不得不“野”。虽然达到了质、野之极,然而是不自觉的。
一旦成为子孙一代,则不同,耳不闻金鼓之声、足不履行阵之险,只知安眠饱食之快。于是其势若不极“文”则不能止,所谓其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即便怎样的神圣(的天子)在上,也不能将它返回到质和野。但是,如果“文”极的话,天下之“乱”复起,英雄并生,逐鹿不止,虽圣人也只能顺(其时势)。儒者并提忠、质、文,究竟是怎样的意思呢,不了解。又,讲解以“忠”易“质”啦、以“质”救“文”啦,荒唐也太甚。这人世间,只是质与文两者。两者之生,来源于治、乱。所谓质,乱之终,治之始。就是说,中心(内心)希望不能不为质,非矫(作为)。如果积渐而至于文,则治之极、乱之兆也。这也因为中心希望不能不为文,所以都是忠(真心)。
秦的时期,文极也,于是天下大乱而汉兴。汉之初,天子不能备齐钧驷(卤簿用的马),虽欲不质,不可能也。(太仓的米)陈陈相因,以至于贯朽粟腐(这是说财政充实),自然导致武帝的大有为之业。所以,汉高祖的神圣,是尧以后的第一人,文帝的柔和,是被囚于羑里的(周的)文王以后的第一人,西楚霸王项羽是继承蚩尤而再兴霸业者,武帝是继承黄帝而扩大[疆域]规模者,全部是千古大圣人,不应该轻率地批判。群雄尚未死,则祸乱不止;离乱尚未甚,则神圣不生。一文一质、一治一乱,(其原理),于是(据本书)应该知矣。世纪·列传里的一个个人物论、时代批评,现在不提示。把项羽和武帝的功业叫作“千古大圣”(他还把秦之秦始皇称赞为“千古一帝”),这是他之崇拜不已的王阳明没有想到的事吧!即便在这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样的宋学的反功利主义,也完全[造成了]正相反的结果。
佛教及其他
关于卓吾,要想了解他,应该论述的问题,[诸如]不可思议地未能发现“万物一体说”,或者著名的男女平等说等,还很多,但现在想全部省略不论。最后想提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对于他的佛教的作用问题。
他之出生的家庭是回族(伊斯兰),这已经叙述了。从他的这个出身来解释他后来对儒教之权威的果敢地挑战,的确是诱惑性的尝试,但迄今,似乎谁也不敢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自己在那些为数很多的著作中,没有留下予这一点以暗示的一言半句。自己是回族出身,不必说。那么,何时何故放弃回族[信仰]呢?或者对一般回族,他的见解如何?等等,全然没有言及,这确实只能说不可思议。
他的学问系统,最重要的,首先是阳明学,特别是阳明学左派,这有他自己再三所说的话为证,难以动摇,在研究者之间,亦没有异论。而且,儒、佛、道三者一致是他的主张,他受与其说道教倒不如说道家思想、老庄思想的影响的事,也不能否定(例如,一三。页里引用了的那样的话,也可能视为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的影响)。尤其是,他一边明确地遵从老子一边极力主张“以民为愚”的政治,[又]赞美武断的政治家、张居正、辩护商人(前期商人)、肯定侯外庐评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臭味的强者,富者等,[这两方面]关联⑵]起来看,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然而现在不论。总之,关于卓吾的老庄之影响的问题,产生出所谓若不遵从老庄(它不是往往容易被认为的“邪说”,也是在私的领域里耽溺于那件事的自由)就不能出现那样的成果,是不可能那样想的。问题毋宁在这方面:理论上公开接受异端[28],企图统一的把握异端和圣人之学的主动态度,是在阳明心学之内屈身生长下去的。这个三教合一的问题,或者作为思想的节操的问题,或者仅仅作为宽容的问题,也许能理解,然而大概不恰当。他们企图确认:由于将“学”的原理向内的“良知”这一点集中,又由于从“良知”这样的穷极境回顾整个中国史,所以一切的学说,各自都是真学的契机①。打算超越区区“儒学”而积极地确立“学”那个东西、即“中国之学”的立场,至少是开辟了那个机运的端绪。不用说,其原理是宋学的形而上学的原理,而且,就像明代的各种各样的新机运全都是那般一样,在结局、结果上,没有达到什么结晶就彻底结束。异端和儒学的统一,虽然仍必须期待清末的“诸子学”复兴、“国学”的创立,但是,每当我打开明之遗民方以智的《东西均》(一六五二年之际)(这个如同难解之象征似的哲学随感集)之类[著作],不幸的是未发现仿佛能够确认的“新机运的端绪”。在《东西均》里,哪儿没有像三浦梅园《玄语》那样的感想呢?
但是,我最难理解的是关于卓吾的佛教的作用。卓吾笃信佛教,他自己也明说;即便根据其著述,也是清楚的。其佛教,仿效当时的风气,即禅净一致的风气。他特别喜好弄禅机的事为很多人所传,而像附录于《续焚书》的《永庆答问》那样的[言谈],对我们门外汉来说,是稍微滑稽生疏的机锋纵横的禅师式的记录。“我的肉体,外面的山河,扩展的土地,所见之虚空,都只不过是我的妙明真心之中的一点物相”。(《焚书》四,《解经文》)——这件事,同像以往叙述那样的他的过激的评论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我想谨仰识者的指教。在现在的中国,这些全都当作主观唯心论、神秘主义、时代之悲剧的矛盾的表现。总而言之,作为他的消极方面,且只作为那样的东西被评价,但果真可以那样评价吗?现今,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史习惯将清朝的龚自珍置于开卷第一,而这个龚氏另一面还是热心的佛教信徒。戊戌政变的思想指导者,否,在清末的改革、革命运动中直接起到点火作用的康有为;与其说是改革派莫如说是革命思想家,主
①译者注:“契机”的原文亦有“要素”意。动就义于刑场的谭嗣同;辛亥革命的“三尊”之一、彻底的民族革命主义者章炳麟,这些人,以天台、华严、唯识等为宗,尽管各不一样,但简言之都佛学深厚。佛教和激进的思想之关系,没有必要不仅从其消极的方面,而进一步作为积极的方面来把握吗?佛教另一面使这些人汪洋放恣直到难以收拾诸氏之思想地步,[但他们]究竟打算说什么呢?是肯定呢,还是否定?[其]道理一点也不明白。直到这样的地步,每每使做着却是事实。但是,例如像谭嗣同的《仁学》,没有佛教,果真能写成吗?又,卓吾的场合,无论是好还是坏,像佛教(禅)之持有的现实主义(它与思辨之极度的浪漫性,的确相表里)、舍身这样意图的实存主义的“心力”那样的思想,与[其]性格和阳明学一同作为积极要素起着作用,这不是必须承认的吗?假如果真那样,则那个作用之详细的道理,在理论上应该如何被理解呢?注释
[1] 这个定义根据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变化》(《哲学研究》,一九五七年二月)。又,参照岛田《关于体用的历史》(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论集,昭和三十六年〔1961〕)。
[2] 楠本正继《全体大用之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四号,昭和二十七年〔1952〕)。又,该氏《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昭和三十七年〔1962〕)。
[3] 这一点,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九三。年)第二篇《经学时代》第1。章《道学的初兴和道学的“二氏”之成分》的启示。
[4] 阖是封闭,辟是打开,宇宙的造化作用,是永远的“闭、开”这样的观点(《易经》),与《老子》的天地是风箱这样的说法,是相同的考虑吧。开是阳,闭是阴。
[5] 小岛祐马《中国学问的固定性和汉代以后的社会》(昭和七年〔1932〕)、尚收于该氏《古代中国研究》(昭和十八年〔1943〕)。
[6] 吉川幸次郎《近世中国的伦理思想》(岩波讲座伦理学,第一二册,昭和十六年〔1941〕)。
[7] 朱子的“气”的理论,历来很被忽视,现在幸亏有安田二郎《关于朱子的气》(收于《中国近代思想研究》)、山田庆儿《朱子的宇宙论》(东方学报、京都三七、昭和四十一年〔1966〕)。
[8] 安田二郎译《孟子字义疏证》(昭和二十三年〔1948〕、十九页)。
[9] 照想起来的列举,诸如个性主义、对异端的容忍态度、对文学•史学的肯定态度,等等。[10] 今中宽司《徂彼学之基础的研究》(昭和四十一年〔1966〕)持此说。但是,它可以说完全缺乏文献性的实证,而且推论的方法,奇妙地固定于大江文城氏及其他近来之学者关于叶适的论断。从那一点反复演绎下去的方法,怎么也不能领会。
[11] 山井涌《明清时代之“气”的哲学》(哲学杂志、七一一号,昭和二十六年〔1951〕)、山下龙二《罗钦顺与气的哲学》(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二七、昭和三十六年〔1962〕)等,是我国代表性的研究。
[12] 王龙溪,名畿,浙江绍兴人,一四九八--五八三年。是进
士,但官完全没有荣升。
[13] 以下此项,希望参照拙稿《中国近世的主观唯心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东方学报》京都,第二十八册,一九五八年)及本书的第一、二、三章。
[14]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二十页,是就德川时期的朱子学者所说。这就中国言,也适用。
[15] 侯外庐主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全六册,另外,张岱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侯外庐还有《中国哲学史略》(全一百一十页),此著有英译: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1959,Pekingo此外,为侯氏所编辑的“中国唯物主义哲学选集”,有五、六册。
[16] 详细论述参照拙著《中国近世思维之挫折》(一九四九年)及上列的拙稿。
[17] 就是说,从与荻生徂彳来把道作为对于我们是“外”的特定的圣人之作为恰好正相反的立场,却导致出相同的结果。
[18] 像这样的“隐遁”之排斥,王艮(王心斋)、王畿(王龙溪)以下,在阳明学左派那里,最显著,有时甚至大体上能认为具有出风头主义的特征。“吾人置身天地间,本不容退托”(龙溪),所谓退托,是说捏造借口而逃避(《东方学报》,前记拙稿四十四页以下)。这“不避嫌疑,不避诽谤”的态度,是通往所谓“狂”的态度。至于主动批判谈论“天命”者的心斋,又说“大人造命”;引用唐代的李泌之话语,李卓吾说:“君主与大臣造命。君主和大臣谈论天命,则礼乐刑政皆成为无用的东西”(《墨子批选》非命之条),都归属那个延伸上。
[19]孔子及孟子,把人的类型分为“中行”“狂”“狷”三类(或者加上“乡愿”,分为四类)。中行是中庸之人,最上,但很难得。狂是“进取”者,勇往迈进的理想主义,但往往不免言行不一致,这是其次。狷是“有不为”,照孟子的话,是“不屑不洁”者。最下等是“乡愿”,“阉然媚世”者,八面玲珑,“德之贼”(《论语·子路》《孟子·尽心下》)。阳明已经自以狂为任,到了阳明学左派,则强调“狂才是入圣学的真路”。“与其成为阔略无掩(缺点全部暴露)的狂士,不如成为完全无毁(完美无毁谤)的好人”。(王龙溪墓志铭里评价王龙溪的话)又,本文中,五伦云云,是李卓吾引用世之学者评价左派的何心隐的话(《焚书》三)。“以友为命”的热情的同志意识,是左派的特征。性真云云,是左派的王龙溪语。在《挫折》二八七页、中央公论社《世界的历史》第九卷一六四页,言及别的形式的、然而恐怕是同一来源的“狂”。总而言之,可以认为,“狂”与欧文·巴比特所说的“浪漫主义的人”,亲近点大概多。
[20]参照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筑摩书房《世界的历史》第十一卷)。“民变”(市民的蜂起)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争论的关联,战后特别受到注意。
[21]叶国庆《李贽先世考》(《历史研究》一九五八年二期)。若顺便
说,回族以回族身份接受科举(其原则不用说是儒教)而成为官吏的例子未必稀奇,但他的场合,被理解为放弃回教而改宗儒教的史料亦存在。
[22]受戒得不到政府的许可,而蓄髯比什么都更便于继续进行反社会的积极的评论家、著述家的活动……
[23]其后的事情,参照中央公论社《世界之历史》第九卷一五四页。又,应该一读広濑丰《吉田松阴之研究》(昭和十七年[1942])下卷二篇第二、三章。又,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九五七年五月《藏书》上下两册,十月《续藏书》(使用明代的稿本,死后出)全一册,十二月《焚书》全一册(死后出,只是省略了附录的《李温陵外纪》太可惜),六一年三月《焚书》全一册,经过周密地校订而出版,一般的人容易弄到。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事。
[24]中央公论社(《世界之历史》第九卷,一五二页)。
[25]内藤湖南《目睹书谭》二二页(一九O一年八月《日本人》)。
[26]顺便说,所谓《焚书》,是“因览者生怪憾,当焚弃”的意思。
[27]《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李贽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
一〇七五页。
[28]所谓异端,例如,被考虑为净土真宗的异安心那样的意思,这在现今很普通,然而在中国毋宁是异教之事,以儒教来说,叫作“外道”。而且,关于李卓吾之异端的最特异之处,毋宁是表彰墨子吧。除著有《墨子批选》之外,在《明灯道古录》的末尾处,也极口称赞墨子,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成为黄宗羲的科举之科目里增加诸子(《明夷待访录》)这样的议论的先驱。
思想史的背景
宋(公元960年建国)以后的中国是士大夫的中国,士大夫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是广义的宋学[13]13。宋学,根据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家的分类,包括三个流派。第一是张载(张橫渠)所创立的唯物论,即“气”的哲学。第二是开始于程颐(程伊川)而由朱熹完成的客观唯心论,即“性即理”的哲学。这个所谓的朱子学,不久,永久地占据国教的地位,因为其过分的整齐性、完结性,终于没能期待值得一提的独创的后学[14]14。第三是陆九渊(陆象山)主张的主观唯心论,即“心即理”的哲学。作为其先驱,举程颢(伊川之兄程明道),最适当;作为其后劲,举明代的王守仁(王阳明),是定说。
这三派之中,唯物论的系统在现今的中国最被强调,从这个新的着眼做的思想史的发掘、改写,接连不断地取得成果[15]15。即便没等新中国成立,继承张横渠的大哲学家·清初的王夫之(王船山)的存在,也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切合思想史的纠葛而平心地思索时,这样的看法——这个
系统并没有起到另外二系统[那样]程度的作用,被认为毕竟还是妥当的。张横渠的“气”的哲学,事实上被完全吸收于朱子的“理气”说之中。即便王船山,生前不必说,直到死后一百五十年、清朝的末期再发现,其著述和思想也完全沉睡在湖南省的偏僻的乡村里,这说得不夸张。尽管不用说思想的确在那里存在着,应该珍视;而且,正因为那个缘故,死后一百五十至二百年之后,在[民国]民族主义风潮中,它起到了伟大的作用,这是不可怀疑的事实。
宋以后的思想史之最重要的局面,仍然在于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纠葛;朱子学的“性即理”和陆王学的“心即理”的对立、抗争。不用说,这并不是说一方是体制方面的思想,另一方是反体制方面的思想。体制的维持、名教的拥护,这是两者一致高唱的大理想。两者都是一样把“理”的存在作为前提、把“理”的死守作为使命的理想主义。要说那个抗争,简言之,不过是站在同一立场的霸权的争夺战。这样的说法,充分有道理。否,岂止那样,连立这样的说法(非官学的陆王学的方面,是更彻底的体制拥护性的,是对体制更彻底的奴隶性的)也是可能的。若借用张横渠—朱子的定义,不外乎“心是性与情的统一体”,但“性即理”仅是这个“心=性+情”的一部分,即相对于只不过把性作为理,“心即理”说是举心全体(其具体的内容就是五伦五常)作为理,能看作“为封建伦理提供一个更直接的根据的东西”。朱子的格物说,这样解释:事事物物里有“理”,通过穷之格之,可以检证、把握自己内在的“理”。对此,阳明抨击说:总而言之,这无非“求理于外”的观点,假如以为孝之理在为“外”的双亲,双亲如果死了,那么孝之理就消失了吗?自古以来,作为孝之最大的节目的丧、祭就是无意义的事吗?理完全在“内”,完全在“我心”,以此一事就可知(《传习录》,岩波文库本一二七页)。
诚然,目标也许相同,但对于那个相同的目标,所谓“性即理”“心即理”,其各自的原理,或者方法,都是整合性的吗?
我认为,“性即理”方面是整合性的,但“心即理”方面不是那样。其详细[内容]不具有解释的余裕,现在想暂时指出以下诸点,即“心即理”说由于把没区别性、情(情具有一直流到本性上的“欲”的倾向)的原封不动的“心”设为理,所以导致出这些倾向:情—欲望(所谓人欲)的肯定;“人之自然”的主张;对朱子学那般重视的“敬”的轻视;对宛如“六经是我心之注脚”这样的权威的轻视;对异端的包容的态度等[16]1[16]。而朱子学派却不停地严厉警告这几点。
虽然从客观唯心论方面不断地攻击其原理、方法的危险性,但主观唯心论的流派,程明道到陆象山直到王阳明,不管怎样,可能没有很大的破绽。王阳明的“良知”说(所谓良知,是根据孟子的语言,把像心即理那样的心标准化者)可以说是其顶峰。而且,在阳明那里达到顶点的主观唯心论,不久,假如就其目标而言,可以说不能不立于诡辩的境地,达到不使我那原本包藏着的祸心被发现[的地步]吧(阳明学左派)。作为其契机的是,良知的人的平等性,由于阳明,被热情地主张(满街都是圣人);人由于只有把“内”“良知”作为问题,反倒开辟了对于“外”的知识、技能等的积极评价之道,开放了自由主义的风气[17]17,等等。与此一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主观唯心论的系列从最初就伏流的“万物一体之仁”“生生不能止”之说是同良知结合的。良知已经不是个人的平静的修养项目,而成为应该实现万物一体的觉醒运动、精神的救世运动。
孔子汲汲遑遑,宛如寻找丢失的自己儿子,而无暇于席之暖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疾痛迫切,虽欲已而不容已者。所以孔子说“我不与斯人之徒(成为这个人的人们)而谁与”“洁其身(隐遁)而乱大伦(社会的存在这样的人正当应有的状态),果
(敢)哉。(然而这样的事实际)不难矣”[18]18[18]。啊,非真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谁知夫子之心矣。(《传习录》,同上二一八页)良知是作为万物一体虽欲已而不能已者,生生不能止者。“与其为数顷无源的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的井水之生意无穷”(《传习录》,同上六七页)。——假如省于吾心而[以为]非,则虽孔子之言亦不以为是(《传习录》,同上二〇五页)这样的良知,是主张万物一体、民是胞,物是与。但是,为动辄企图超越被派定的界限、本分的“生生不容已”的流动主义所保证的时候,就“抛弃五伦中的四伦”,仅以“朋友”一伦为“生命”,产生“只诚心诚意达性真,在恶名里埋没一世亦不顾及”这样的“阳明学左派”的“狂”[19]。最后的结局,勃发了应该说是思想之暴动的思潮。其时期,与正当那时开始的社会暴动、所谓“民变”的时期,正好一致[20]201。
思想的暴徒,那就是李卓吾。
生涯
李贽,字或号是卓吾,通常以李卓吾被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的读书人家,因为晋江县[县衙]在泉州的城内,总之是泉州城的人,生卒年代是明嘉靖元年至万历十年(1527—1602),即生于明朝文化最成熟的时期。其生年在阳明逝世的前年,卒年在“中国的卢梭”黄宗羲出生的八年前、明朝灭亡的四十二年前。就日本说,川中岛交战、太合的朝鲜征伐是他生涯中发生的事情,德川家康被任为征夷大将军是在其逝世的翌年,就是说是包括靠战国的安土·桃山时代。就欧洲说,哥伦布死后二十年诞生、是与马丁·路德大略相重二十多年、与米开朗琪罗相重三十多年的后辈,与蒙田完全是相重的同代人。无论日本还是欧洲,都处在历史的大转折点。
卓吾在那里出生、到二十至三十岁间一直生活在泉州这个地方。这是个很特异的城镇,和广东一起,是唐以来中国最大的外国贸易港,否,在元朝的时期里,是“世界两个最大的贸易港之一”(马可·波罗)。而且,因为当时的贸易是所谓的南海贸易,渡来很多伊斯兰教徒,因而,是在中国的伊斯兰(回族)的大中心地。现在仍遗留着的泉州的伊斯兰寺院·清真寺,一〇〇九年或一〇一〇年着手奠基(改建于元代)。可是,一旦进入明代,作为国是的海禁政策的结果,外国贸易全部衰落,因而泉州的繁荣也似乎同以前的时代无法比拟,但泉州与其附近(厦门等)仍然作为秘密贸易的中心地而具有高度的活气。此地的缙绅,甚至时常显示出左右中央政局的势力。李卓吾家原来也是泉州的商人。其先祖之中,也有人于明朝初期跑到波斯湾,且长期逗留,在那里娶当地人为妻的;还有人由于官命而做翻译官的工作,“引导日本和琉球的入贡使上京”。这些事,由于几年前在当地发现《族谱》之后才成为被人所知的事实。《族谱》还载明李卓吾的家代代是回族,即伊斯兰教徒。妻子黄氏好像也同样是回族。若把[他家]当作严格的回族家庭,则是当然的事[21]21。
二十六岁,通过科举第一关的乡试,获得举人的资格。这件事本身,只意味着向作为士大夫的正式成员迈出了第一步,没有一点出奇的地方。他晚年回忆那时之事的文章,因为的确是卓吾谱系,故准备引用。
成长之后也是个呆子,即便读(为科举考试准备的《四书集注》等)传注之类也不能理解,不能领会朱子的深意。因此感到厌恶,打算抛弃而结束[读经]。那样的话,就很闲暇,无以消磨时间,乃叹曰:“总之,因为不过是儿戏,无论剽窃、无论如何,若乱七八糟地摆着,就很多。说是考试官,也不可能从一到十都通孔圣的奥义”因此,取八股文之尖新而值得玩诵者,每日背诵数篇,至考试那一天,大约五百篇运用自如,一旦被分给答案用纸,就一个劲地开始作缮写人,
于是以优秀的成绩及第。(《焚书》三《卓吾略论》)以后,抛弃作为科举之正式演出的进士考试,在河南、南京、北京辗转任最下级的官吏,[又任]南京刑部员外郎这样的闲职,好容易在五十一岁的时候出任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然五十四岁就已经辞退。这就是他官历的全部。说到知府,总算是个官,但若看被派遣到云南这样的边境,总而言之,作为官吏也不是太显著的经历。
随着辞职而寄身于湖北省黄安县(汉口的东北方向)的耿氏檐下,不久,因同后来的户部尚书(大藏大臣)耿定向在思想上对立,强硬地提出绝交信,迁移到麻城县龙湖的芝佛院(五十九岁)。在这麻城的十多年间,是他作为思想家、评论家活动的最高潮时期。像代表作《藏书》六十八卷、《焚书》六卷,都出版于这个时期。作为反面又危险的思想家,来自正人君子的[对他的]憎恶和迫害,变换手段,变换面孔,越来越激烈,不能停止。在芝佛院,他的日常生活,与其说只是寄食者,事实上,倒不如说几乎接近僧陀,终于在某一天,断然剃发。这样,由于既不像僧又不像儒的奇奇怪怪的打扮[22][22],故喧嚣的舆论更喧嚣。夏日,不能忍耐头痒完全剃掉头发这件事,好像是实情,然有时候又自说:
因为无见识辈把自己呼为异端,我才进步成为异端,使竖子成名。
(《续焚书》一,《与曾继泉》)宛如好事的这一挑战的、战斗的态度,绝不只是这一端,直至临终,都是卓吾的特征。又,接着准备在这里介绍《自赞》、即应该说是其自画像的他的文章:
其性偏狭,其色矜高(高傲),其语卑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
(轻率)。其交际少,然若见面则热情地亲近。与(赞成)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长处;恶人也,已与那人绝交又欲终身害那个人。志在暖衣饱食,而自以伯夷叔齐为任;本来等同于(破廉耻的那个《孟子》中的)齐人,而又自谓饱道饫德;一介也不与人的事明明白白,而借口伊尹的故事;(为了人)不拔一毛的(事等同于杨朱)明明白白,又(模仿孟子说法)称杨朱为贼仁者;动则逆物,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如何?”子曰:“未可也”。像居士,其可乎哉!(《焚书》三)
事实上他是狷介而难以接近的人物,又是极度爱干净的人。某个传记里说,[他]“性爱扫地,即便数人专管扫地,尚不足。擦拭脸和身,确有水淫之感。”
一六〇〇年,七十四岁,麻城的宪官和以宪官作后盾的士大夫,作为过去几次对他迫害的总检举,终于对他下达了驱逐令,打毁芝佛院及为埋骨准备的塔[也同时]执行。他被崇拜者伴随着逃难,远逃至北京附近的通州,后年一六〇二年闰二月,被逮捕,三月十六日在北京的狱中自杀,享年七十六岁。著书、雕版、草稿,全部被烧毁,即便进入接着的清朝,其著述也被列在禁书目录之中[23]23。
李卓吾曾直接师事王心斋之子王东涯,对王龙溪一生倾倒,至于对王阳明的崇拜,则不待言。亦有《阳明先生年谱》《阳明先生道学钞》等著述。因太破格的缘故,他没列入《明儒学案》,但他是阳明学派的人,尤其是阳明学左派的人,这没有异议。
童心之说
假如把李卓吾的根本思想用一言来说,毕竟还是“童心”吧。以下介
绍收进《焚书》卷三的文学论的《童心说》。
龙洞山农在《西厢记》的序文的末尾说:“识者勿责怪余之尚未脱离童心可也。”但是,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假如以童心为不可,这就是以真心为不可。
所谓“真”,是“假”的相反概念。所谓“假”,是“借”的意思,似而非、虚伪,总而言之,指不是真的,是假的。
童心者,是与假无缘而纯粹真的东西(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假如失掉童心,就是失掉真心。假如失掉真心,就是失掉作为真人。做人若无真,就应该说已经全然没有“初”者。童子是人之初,
童心是心之初。心之初者,究竟是失掉也可以的东西吗?这段,遵循宋学里议论纷纷的“复初”说而曰:
可是,童心什么原因突然地失掉呢(胡然而遽失)?大概,最初闻见从耳目而入,成为内之主,于是童心被丢失。长大,道理乘闻见而入,成为内之主,于是童心被丢失。一旦久之,道理和闻见,日日越发多,因而所知所觉,日日越发广,在此时,越发知应好美名,而意欲扬之,于是童心被丢失;知应以不美之名为丑,而意欲掩(隐瞒)之,于是童心被丢失。
“道理”这个语词,作为消极价值的语言被使用方面,应该注意。在别的文章里,名教这个语词,仁者这个语词,都有在消极价值上被使用的例子。“天下之人得其所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人失所而忧,而汲汲然贻(送)得所之域。因为这种原因,以德礼格其心,以刑政絷(束缚)其四体,于是人始失所”(《焚书》一,《答耿中
丞》)。接着准备引用该书简中的一节:“……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的言)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供)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满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那么,继续[谈]童心说:
道理、闻见最初全都是从多读书、识义理来。古之圣人何尝不读书?但是,即便不读书,童心本来自在;即便多读书,依然由此护童心,无外乎使勿丢失,与学问者由于多读书、识义理反倒障(妨碍)它不同。学问者,既然以多读书、识义理障那个童心,[那么]圣人仍旧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的必要[性],在哪里呢?
这里能看到的,和他在别处发的“应畏者书哉”的叹息,是相同的叹息。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这样的逻辑:对于确实打动自己的东西来说,没有理由惧怕读书。本来,极度强调“内”的阳明的良知说,把读书和教养作为“外”的东西,对它的确是很警惕的。——被卓吾憎恶到那般程度者,他们不只是道学先生,毋宁指广泛的读书、教养之人。但是,由于那样,无非是引起体无完肤地批判和攻击。
童心既然被障,一旦发而成为言语,那言语就不是发自衷心的东西;见(表现)而成为政事,政事就无根柢;著而成为文辞,文辞不能达;既不是由于有含内者而章美的东西,也不是充实而生光辉的东西。欲求一句有德之言,终于不能得。缘由如何?因为童心已经被障,以无非由外而入的闻见道理为心。
已经以闻见道理为心。那么,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不是出自童心之言;言虽巧,同[真的]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正好是假人说假话,则事是假事、文是假文吗?其人已经假,实行起来则无不假。
于是,若以假言语假人,则假人喜;若以假事道假人,则假人喜;若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因为无所不假,故无所不喜。满场假也,矮人辨何也?矮人云云,是用所谓矮人观场、矮人剧值得看的比喻,指附和雷同他人做出的评价。卓吾最憎恶的是假,尤其对“假道学”(不只是道学先生,广泛地包括立足儒教主义的一般官僚)的伪善和无能,确实竭尽痛骂嘲笑之能事。但我想指出一点,即这个“假”和“真”的尖锐且执拗的对置,立足其上的“真”的热情的主张,不仅可以说是开始于阳明左派而在卓吾达到顶点的一个“党派”意识,同时又和“生生不能止”一起,也是嘉靖万历广泛的精神史的一个基调。卓吾的书席卷读书界,是因为他最鲜明地表现了时代意识。——那么,接着进入狭义的文艺论。
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因假人被湮灭而不尽被后世知者,决不少吧!何谓也?作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自童心者。假如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任何的创制体格(体裁)的文章都无不文。诗何必古选(《文选》)。文何必先秦。降而成为六朝(骈文),变而成为近体(律诗、绝句等),又变而成为传奇(小说),变而成为院本(脚本)、成为杂剧(歌舞伎)、成为《西厢记》、成为《水浒传》,成为今日的八股文。都是古今的至文,不能以时世的先后论(古代的东西最好)。如此去看时,我渐渐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事已至此,[说]什么六经,[说]什么语孟(《论语》《孟子》)。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是意识到所谓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拟古主义而说的,这不怀疑。尽管那样,也应该注意,将“诲淫”的俗文学《西厢记》、“诲盗”的俗文学《水浒传》之类表彰为古今之至文,而且,为了表
彰它们,连悍然降低六经、语孟也不辞的那个精神态度之激昂。
那六经、语、孟,不是那个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就是那个臣子极度赞美之语,又不然,则迂阔之门徒、懵懂之弟子们,记忆师之说,有头无尾,得后遣前,随其所见,记下来成为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决定目之为经,谁知大半不是圣人之言。纵然出自圣人之口,总而言之,是有所为而发的东西,只不过是应病予药、随时处方,打算救治这样的懵懂弟子、迂阔门徒的东西。如果药只不过为了医“假”这样的病,处方不能固执,怎么能率然视为万世之至论呢?然则,六经、语、孟,是道学先生的口实,假人的渊薮,断断乎不可能在童心之言前拿出来,是明白的。呜呼![吾]安得真正的大圣人之童心还未曾失者,一同语一次文哉!
以上是《童心说》的全文。而关于卓吾作为批评家、评论家的多方面的活动,现在不涉及。在当今的中国,认为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但阳明左派(泰州学派)—李卓吾是唯物论,想竭力将两者拉开的试图是显著的。这样的试图,在今日的中国,具有某种现实的意义的事,尽管能了解[24],但说它在学问上几乎不具有什么说服力,则非言过其实。假如排除凡是进步的、反抗的思想全都应该是唯物论这样的教条来思索的话,则宛如我曾经的论证,卓吾依然是主观唯心论者王阳明的“嫡派儿孙”,其“童心”可以说是“良知”的成年。
历史批判
作为《焚书》的代表性的一篇,我在上面解说了《童心说》。下面,想介绍《藏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里所说的“古今未曾有的过激思想
之史论”)中的总论性的两篇。不同于《焚书》是收集书简、杂多的随笔、诗等所谓的文集,《藏书》方面,由始至终的著述,都是世纪和列传,即被用纪传体写的中国史(从战国到元代)。在人物的分类方法上,又,在到处添加的评论上,“绝《纲目》(朱子的《通鉴纲目》)谱系的道学头巾习气,快捷轻俊,充满谋反气”[25]5。姑且不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说:“李贽之书,皆狂悖乖谬,以圣为非无法,尤其此书攻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莫不颠倒而易位,其罪不容诛”,在中国的史部之书中,它一定是最独特的一部书。
首先介绍第一篇《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简言之,是《藏书》全书的序文。
李氏曰,人之是非,原无定质,人之对于人的是非,亦无定论。因为无定质,故此是与彼非,并育不相害;因为无定论,故以此为是与以彼为非,并行而不相悖。这样看来,今日之是非,谓余李卓吾一人的(私的)是非可也,谓千万世之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再非是余所以为的非是,亦可也。余之是非,唯有任其可矣。这的确是典型的分类排列(raisonnement)的立场(黑格尔)。
前三代(夏、殷、周),现在不论。所谓后三代,是汉、唐、宋,其间千百余年,而全然无是非。是其人的确无是非吗?因为皆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以只不过是一点儿是非也没有。假如像这样去看,我是非人者,此又有不能已(止)者。这是非之争,如同四季[循环]似的、昼夜更迭,而无一致。昨日为是,今日为非;今日为非,而后日又是,即便使孔子复生于今日,不知究竟作如何的是非也。而能率
然以定本(一定不变的基准)行赏罚(批判、毁誉褒贬)吗?
……此书,只能自怡,但不能示人,故名之曰《藏书》[26],无奈一二好事朋友非要阅读,我即便断绝关系也不停止。只有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观,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则善矣”。诚然,卓吾的立场,也许是既可那么说也可这么说的立场。但是,同样不应该忽视附加这样一条:唯有不干以孔子的准则为准则、并且[照着]做的事。他的立场始终是战斗的,否,挑战的。——名教者流派迫害他,把他下狱,逼到死的地步,但假如接受其挑战而奋起相互光明磊落的论战,则儒教思想、中国思想,也许可能开创意想不到的生面!利玛窦已经来中国活动,卓吾同他也几次会见,对其人不惜赞辞(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的刊行,是在卓吾死于狱中的翌年);另一方面,佛教界,此时[出现]以卓吾的知己——紫柏真可为首而龙象辈出之生气勃勃的结尾——这进入清朝就极度地沉滞。对中国思想史来说,这确实不是千载难逢吗?我想在这里再次引用旧稿(参照注十三)中的话语:《易》有云:“物穷则变,变则通”,虽穷大概欲变,但终于不能变,这不是从思想史上看的明代的情况吗?被冠于本章开头的卓吾一文,的确应该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感慨来读。
那么,接着[介绍]《世纪总论》,也就是各论的总序。
李生曰,“一治一乱”(孟子语,有历史价值的意思)如同循环的环。战国以来,大概不知几治几乱也。正当其乱,仅保住首领(脑袋),已是幸福。一旦有幸逢“治”,若能饱食则足,不介意是否粗粝;能睡眠则满足,不介意是否大厦。这是极“质”极“野”而无文之时。不是喜好“野”,是势不得不“野”。虽然达到了质、野之极,然而是不自觉的。
一旦成为子孙一代,则不同,耳不闻金鼓之声、足不履行阵之险,只知安眠饱食之快。于是其势若不极“文”则不能止,所谓其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即便怎样的神圣(的天子)在上,也不能将它返回到质和野。但是,如果“文”极的话,天下之“乱”复起,英雄并生,逐鹿不止,虽圣人也只能顺(其时势)。儒者并提忠、质、文,究竟是怎样的意思呢,不了解。又,讲解以“忠”易“质”啦、以“质”救“文”啦,荒唐也太甚。这人世间,只是质与文两者。两者之生,来源于治、乱。所谓质,乱之终,治之始。就是说,中心(内心)希望不能不为质,非矫(作为)。如果积渐而至于文,则治之极、乱之兆也。这也因为中心希望不能不为文,所以都是忠(真心)。
秦的时期,文极也,于是天下大乱而汉兴。汉之初,天子不能备齐钧驷(卤簿用的马),虽欲不质,不可能也。(太仓的米)陈陈相因,以至于贯朽粟腐(这是说财政充实),自然导致武帝的大有为之业。所以,汉高祖的神圣,是尧以后的第一人,文帝的柔和,是被囚于羑里的(周的)文王以后的第一人,西楚霸王项羽是继承蚩尤而再兴霸业者,武帝是继承黄帝而扩大[疆域]规模者,全部是千古大圣人,不应该轻率地批判。群雄尚未死,则祸乱不止;离乱尚未甚,则神圣不生。一文一质、一治一乱,(其原理),于是(据本书)应该知矣。世纪·列传里的一个个人物论、时代批评,现在不提示。把项羽和武帝的功业叫作“千古大圣”(他还把秦之秦始皇称赞为“千古一帝”),这是他之崇拜不已的王阳明没有想到的事吧!即便在这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样的宋学的反功利主义,也完全[造成了]正相反的结果。
佛教及其他
关于卓吾,要想了解他,应该论述的问题,[诸如]不可思议地未能发现“万物一体说”,或者著名的男女平等说等,还很多,但现在想全部省略不论。最后想提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对于他的佛教的作用问题。
他之出生的家庭是回族(伊斯兰),这已经叙述了。从他的这个出身来解释他后来对儒教之权威的果敢地挑战,的确是诱惑性的尝试,但迄今,似乎谁也不敢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自己在那些为数很多的著作中,没有留下予这一点以暗示的一言半句。自己是回族出身,不必说。那么,何时何故放弃回族[信仰]呢?或者对一般回族,他的见解如何?等等,全然没有言及,这确实只能说不可思议。
他的学问系统,最重要的,首先是阳明学,特别是阳明学左派,这有他自己再三所说的话为证,难以动摇,在研究者之间,亦没有异论。而且,儒、佛、道三者一致是他的主张,他受与其说道教倒不如说道家思想、老庄思想的影响的事,也不能否定(例如,一三。页里引用了的那样的话,也可能视为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的影响)。尤其是,他一边明确地遵从老子一边极力主张“以民为愚”的政治,[又]赞美武断的政治家、张居正、辩护商人(前期商人)、肯定侯外庐评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臭味的强者,富者等,[这两方面]关联⑵]起来看,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然而现在不论。总之,关于卓吾的老庄之影响的问题,产生出所谓若不遵从老庄(它不是往往容易被认为的“邪说”,也是在私的领域里耽溺于那件事的自由)就不能出现那样的成果,是不可能那样想的。问题毋宁在这方面:理论上公开接受异端[28],企图统一的把握异端和圣人之学的主动态度,是在阳明心学之内屈身生长下去的。这个三教合一的问题,或者作为思想的节操的问题,或者仅仅作为宽容的问题,也许能理解,然而大概不恰当。他们企图确认:由于将“学”的原理向内的“良知”这一点集中,又由于从“良知”这样的穷极境回顾整个中国史,所以一切的学说,各自都是真学的契机①。打算超越区区“儒学”而积极地确立“学”那个东西、即“中国之学”的立场,至少是开辟了那个机运的端绪。不用说,其原理是宋学的形而上学的原理,而且,就像明代的各种各样的新机运全都是那般一样,在结局、结果上,没有达到什么结晶就彻底结束。异端和儒学的统一,虽然仍必须期待清末的“诸子学”复兴、“国学”的创立,但是,每当我打开明之遗民方以智的《东西均》(一六五二年之际)(这个如同难解之象征似的哲学随感集)之类[著作],不幸的是未发现仿佛能够确认的“新机运的端绪”。在《东西均》里,哪儿没有像三浦梅园《玄语》那样的感想呢?
但是,我最难理解的是关于卓吾的佛教的作用。卓吾笃信佛教,他自己也明说;即便根据其著述,也是清楚的。其佛教,仿效当时的风气,即禅净一致的风气。他特别喜好弄禅机的事为很多人所传,而像附录于《续焚书》的《永庆答问》那样的[言谈],对我们门外汉来说,是稍微滑稽生疏的机锋纵横的禅师式的记录。“我的肉体,外面的山河,扩展的土地,所见之虚空,都只不过是我的妙明真心之中的一点物相”。(《焚书》四,《解经文》)——这件事,同像以往叙述那样的他的过激的评论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我想谨仰识者的指教。在现在的中国,这些全都当作主观唯心论、神秘主义、时代之悲剧的矛盾的表现。总而言之,作为他的消极方面,且只作为那样的东西被评价,但果真可以那样评价吗?现今,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史习惯将清朝的龚自珍置于开卷第一,而这个龚氏另一面还是热心的佛教信徒。戊戌政变的思想指导者,否,在清末的改革、革命运动中直接起到点火作用的康有为;与其说是改革派莫如说是革命思想家,主
①译者注:“契机”的原文亦有“要素”意。动就义于刑场的谭嗣同;辛亥革命的“三尊”之一、彻底的民族革命主义者章炳麟,这些人,以天台、华严、唯识等为宗,尽管各不一样,但简言之都佛学深厚。佛教和激进的思想之关系,没有必要不仅从其消极的方面,而进一步作为积极的方面来把握吗?佛教另一面使这些人汪洋放恣直到难以收拾诸氏之思想地步,[但他们]究竟打算说什么呢?是肯定呢,还是否定?[其]道理一点也不明白。直到这样的地步,每每使做着却是事实。但是,例如像谭嗣同的《仁学》,没有佛教,果真能写成吗?又,卓吾的场合,无论是好还是坏,像佛教(禅)之持有的现实主义(它与思辨之极度的浪漫性,的确相表里)、舍身这样意图的实存主义的“心力”那样的思想,与[其]性格和阳明学一同作为积极要素起着作用,这不是必须承认的吗?假如果真那样,则那个作用之详细的道理,在理论上应该如何被理解呢?注释
[1] 这个定义根据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变化》(《哲学研究》,一九五七年二月)。又,参照岛田《关于体用的历史》(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论集,昭和三十六年〔1961〕)。
[2] 楠本正继《全体大用之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四号,昭和二十七年〔1952〕)。又,该氏《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昭和三十七年〔1962〕)。
[3] 这一点,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九三。年)第二篇《经学时代》第1。章《道学的初兴和道学的“二氏”之成分》的启示。
[4] 阖是封闭,辟是打开,宇宙的造化作用,是永远的“闭、开”这样的观点(《易经》),与《老子》的天地是风箱这样的说法,是相同的考虑吧。开是阳,闭是阴。
[5] 小岛祐马《中国学问的固定性和汉代以后的社会》(昭和七年〔1932〕)、尚收于该氏《古代中国研究》(昭和十八年〔1943〕)。
[6] 吉川幸次郎《近世中国的伦理思想》(岩波讲座伦理学,第一二册,昭和十六年〔1941〕)。
[7] 朱子的“气”的理论,历来很被忽视,现在幸亏有安田二郎《关于朱子的气》(收于《中国近代思想研究》)、山田庆儿《朱子的宇宙论》(东方学报、京都三七、昭和四十一年〔1966〕)。
[8] 安田二郎译《孟子字义疏证》(昭和二十三年〔1948〕、十九页)。
[9] 照想起来的列举,诸如个性主义、对异端的容忍态度、对文学•史学的肯定态度,等等。[10] 今中宽司《徂彼学之基础的研究》(昭和四十一年〔1966〕)持此说。但是,它可以说完全缺乏文献性的实证,而且推论的方法,奇妙地固定于大江文城氏及其他近来之学者关于叶适的论断。从那一点反复演绎下去的方法,怎么也不能领会。
[11] 山井涌《明清时代之“气”的哲学》(哲学杂志、七一一号,昭和二十六年〔1951〕)、山下龙二《罗钦顺与气的哲学》(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二七、昭和三十六年〔1962〕)等,是我国代表性的研究。
[12] 王龙溪,名畿,浙江绍兴人,一四九八--五八三年。是进
士,但官完全没有荣升。
[13] 以下此项,希望参照拙稿《中国近世的主观唯心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东方学报》京都,第二十八册,一九五八年)及本书的第一、二、三章。
[14]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二十页,是就德川时期的朱子学者所说。这就中国言,也适用。
[15] 侯外庐主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全六册,另外,张岱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侯外庐还有《中国哲学史略》(全一百一十页),此著有英译: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1959,Pekingo此外,为侯氏所编辑的“中国唯物主义哲学选集”,有五、六册。
[16] 详细论述参照拙著《中国近世思维之挫折》(一九四九年)及上列的拙稿。
[17] 就是说,从与荻生徂彳来把道作为对于我们是“外”的特定的圣人之作为恰好正相反的立场,却导致出相同的结果。
[18] 像这样的“隐遁”之排斥,王艮(王心斋)、王畿(王龙溪)以下,在阳明学左派那里,最显著,有时甚至大体上能认为具有出风头主义的特征。“吾人置身天地间,本不容退托”(龙溪),所谓退托,是说捏造借口而逃避(《东方学报》,前记拙稿四十四页以下)。这“不避嫌疑,不避诽谤”的态度,是通往所谓“狂”的态度。至于主动批判谈论“天命”者的心斋,又说“大人造命”;引用唐代的李泌之话语,李卓吾说:“君主与大臣造命。君主和大臣谈论天命,则礼乐刑政皆成为无用的东西”(《墨子批选》非命之条),都归属那个延伸上。
[19]孔子及孟子,把人的类型分为“中行”“狂”“狷”三类(或者加上“乡愿”,分为四类)。中行是中庸之人,最上,但很难得。狂是“进取”者,勇往迈进的理想主义,但往往不免言行不一致,这是其次。狷是“有不为”,照孟子的话,是“不屑不洁”者。最下等是“乡愿”,“阉然媚世”者,八面玲珑,“德之贼”(《论语·子路》《孟子·尽心下》)。阳明已经自以狂为任,到了阳明学左派,则强调“狂才是入圣学的真路”。“与其成为阔略无掩(缺点全部暴露)的狂士,不如成为完全无毁(完美无毁谤)的好人”。(王龙溪墓志铭里评价王龙溪的话)又,本文中,五伦云云,是李卓吾引用世之学者评价左派的何心隐的话(《焚书》三)。“以友为命”的热情的同志意识,是左派的特征。性真云云,是左派的王龙溪语。在《挫折》二八七页、中央公论社《世界的历史》第九卷一六四页,言及别的形式的、然而恐怕是同一来源的“狂”。总而言之,可以认为,“狂”与欧文·巴比特所说的“浪漫主义的人”,亲近点大概多。
[20]参照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筑摩书房《世界的历史》第十一卷)。“民变”(市民的蜂起)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争论的关联,战后特别受到注意。
[21]叶国庆《李贽先世考》(《历史研究》一九五八年二期)。若顺便
说,回族以回族身份接受科举(其原则不用说是儒教)而成为官吏的例子未必稀奇,但他的场合,被理解为放弃回教而改宗儒教的史料亦存在。
[22]受戒得不到政府的许可,而蓄髯比什么都更便于继续进行反社会的积极的评论家、著述家的活动……
[23]其后的事情,参照中央公论社《世界之历史》第九卷一五四页。又,应该一读広濑丰《吉田松阴之研究》(昭和十七年[1942])下卷二篇第二、三章。又,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九五七年五月《藏书》上下两册,十月《续藏书》(使用明代的稿本,死后出)全一册,十二月《焚书》全一册(死后出,只是省略了附录的《李温陵外纪》太可惜),六一年三月《焚书》全一册,经过周密地校订而出版,一般的人容易弄到。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事。
[24]中央公论社(《世界之历史》第九卷,一五二页)。
[25]内藤湖南《目睹书谭》二二页(一九O一年八月《日本人》)。
[26]顺便说,所谓《焚书》,是“因览者生怪憾,当焚弃”的意思。
[27]《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李贽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
一〇七五页。
[28]所谓异端,例如,被考虑为净土真宗的异安心那样的意思,这在现今很普通,然而在中国毋宁是异教之事,以儒教来说,叫作“外道”。而且,关于李卓吾之异端的最特异之处,毋宁是表彰墨子吧。除著有《墨子批选》之外,在《明灯道古录》的末尾处,也极口称赞墨子,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成为黄宗羲的科举之科目里增加诸子(《明夷待访录》)这样的议论的先驱。
相关人物
朱子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