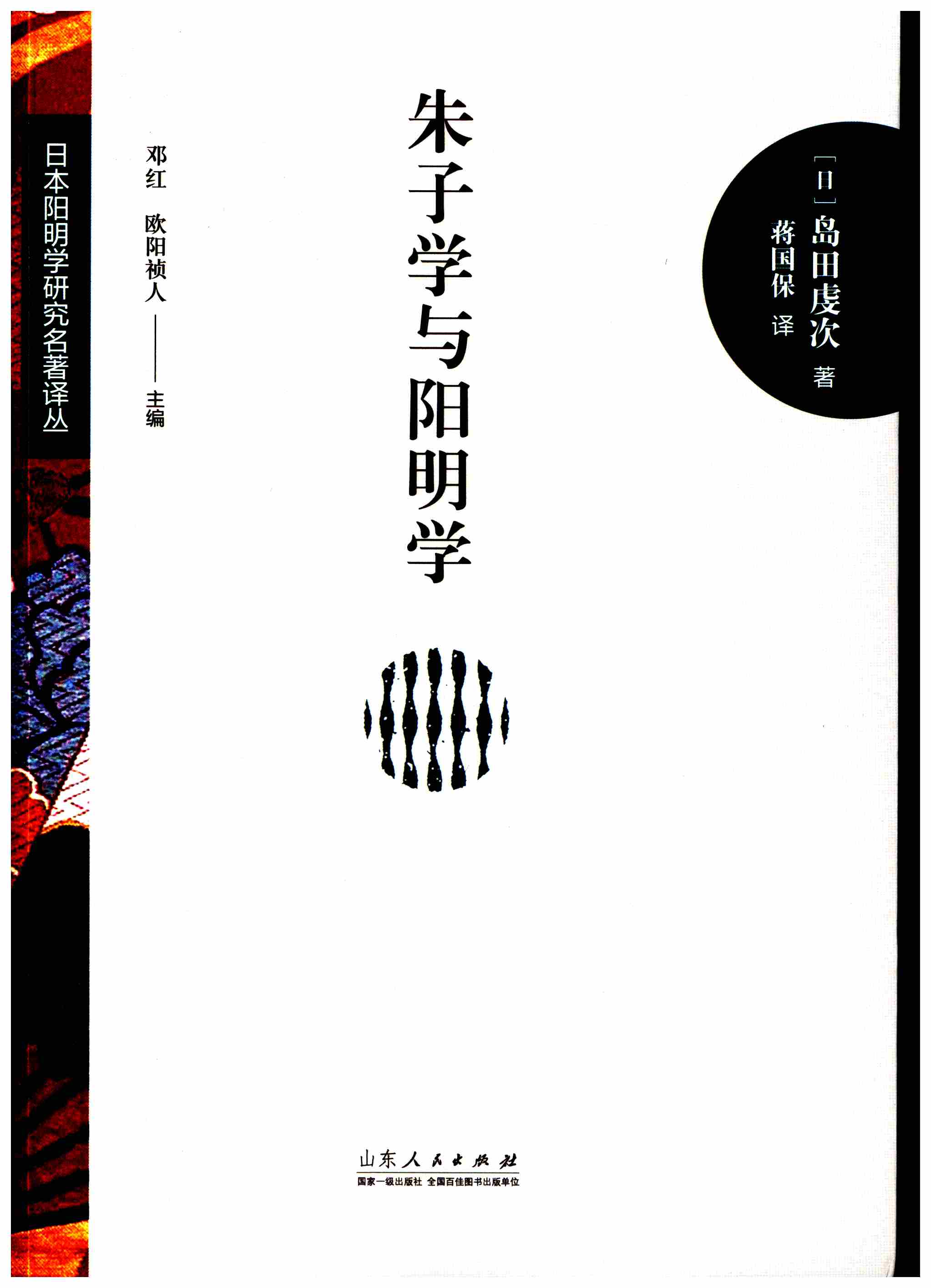内容
伊川和明道
程伊川(1033—1107),名颐。明道之弟,比明道小一岁。少年时期,兄弟俩就学于周濂溪的事,如同已述。随后上都城(开封)的太学,接受胡瑷的教育。胡瑷与其说是思想家,倒不如应该说是大教育家,是首先提出“明体达用”这一士大夫教育之大目标的人,这已经一言带过。不久,伊川在宫中被任为讲读官。他获得真诚的侍讲这一崇高的名声,很多的士大夫成为他的弟子,但在另一方面,因为以天下为已任,于议论和批判的场合,直言无忌,似乎又树立了相当多的敌对。著名的苏轼(苏东坡)恰好同时在翰林院,他名声很高,是文学者的领袖。文学家讨厌规规矩矩的道学先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同样的。此种场合,程氏的一派同苏氏(出身于蜀即四川省)的一派彼此不和,被称为洛党、蜀党。不久,受所谓的新法党、旧法党之争牵连,终于被打成流放者。后来,虽能恢复原官,但这回又因为建立以邪说惑人的党派这样的理由,受到了被河南府检察、其门下所有的学生放逐、身为领袖的伊川登记于党人目录这样的处分,但据说从四方投奔来的门生依然不离去。患病垂危时,弟子向前靠近说,先生平生的学问现在即将有用。听到这样说,伊川略微睁开眼,责备道,对道的学问来说,有用这样的说法不正确。“其人尚未出寝门而先生殁”。道学的根本理念是讲不为了什么,只是为了道本身而学习道、实践道(“无所为而为”,张拭之语)。伊川的临终一语,可以说使道学先生的面目栩栩如生。
据说明道春风和气,伊川秋霜烈日,明道和伊川,在性格方面非常的不同。[伊川]曾瞑目静坐,二个弟子侍立。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日暮,伊川告之曰:归休吧。二个弟子退而一看,外面的雪积有一尺多厚。
仁和爱的关系
儒教的中心教义是仁,其最普通的意思是“爱人”。但是,如果像唐以前那样,把儒教以周公为中心来考虑的话,则中心教义未必是仁,也许可以说“礼”就是其中心教义。但是,如同已经叙述的那样,所谓儒教,唐以后改变了面目,开始强烈地意识孔子之教这样的意思。于是像韩愈的《原道》的场合那样,其开头就有“博爱之谓仁”,仁就是爱。
与此相反,一进入宋代,各种各样的仁说就兴盛起来。其第一位的仁说,就是已经举出的程明道的仁说。对于这个仁说,朱子是非常警惕的,这已一言带过。总的说来,朱子对程氏兄弟表示非常的敬意,当作自己的先驱者。但在实际的思想内容的继承这方面,可以说差不多完全继承了伊川。关于仁的思索也是其一例。伊川首先如下那样的主张:因《孟子》里有“恻隐之心,仁也”(《告子上》)这样的话,故后世终于以爱为仁。恻隐、怜悯,即便的确当作爱,但因为爱是情,仁是性,所以不能直接地把爱视为仁。孟子确实把恻隐作为仁,但必须注意在它前面已经说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只限于有“仁之端”,当然不能直接等同“仁”本身。仁者不用说是广泛地爱吧。但是,像韩愈那样,直接把博爱当作仁是错误的。云云。
那么,伊川关于仁提供了怎样的定义呢?他之仁的定义是“公而以人体之”,(《近思录》二)其意思,如朱子的解释那样,就是这样的意思(公而无私就是仁)吧。但是,伊川的这个仁的定义,就其自身而论,其实不是有思想史性质之重大意义的定义。[说它有]像明道的“万物一体之仁”
对那以后的思想史所具有的那样重大的意义,是不能承认的。
体和用的严格区别
但是,可以说伊川的仁说的前半,即对仁〓爱的批判方面,后来作为所谓朱子学的集大成的独特思想的一个要素来考虑时,则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断然地分开爱与仁,以为相对于前者是已发之“情”,后者则是未发之“性”。仅仅这一点,也许不能具有充分的意义。但是,若参照后来在朱子那里最终被整理为下列的范畴系列来考虑的话,就能够认识:应该说朱子学之可谓核心的逻辑,此时已经大致明确地形成了。
假如以常见的例子说,[不妨看]《论语·学而篇》第二条: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此条最后一句,在朱子学,读为“行仁之本”,决不读为“是仁之本”。像该条的朱子注所明说的那样,这是根据伊川的逻辑。像仁是体,爱是用那样,这个场合,仁是体,孝悌是用。孝悌作为对双亲的爱,是最大的爱,因此可以说孝悌是实践仁的开端,是实行仁之本。但是,把不过是情、不过是用的孝悌,说成是性、是体的仁,是那个仁之本,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相比哥哥明道之学问的、思想的态度是浑一的、直觉的,弟弟伊川是分析的、思辨的、逻辑的,这是公认的。伊川强调“思(致知)”这样的事情。例如,即便作为为了克服人欲的方法,也强调“思”这件事,说“学莫贵于思,唯思能窒欲”(《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天下物皆可以理照”(《二程遗书》卷十八),这是他的信念。从这里产生了后来的朱子把其作为先驱的他的格物说。关于这一点,打算在后面朱子那一章里涉及,而像这样的伊川的分析的态度,在仁说里,仁和爱也被区别。
阴阳和道
应该与此并行地被考虑的再一个学说,是对于《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的他的解释。他说: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
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一五)在这里我们接触到极应注意的新的见解。历来把“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易经》的话,解为阴和阳二气之缊,而把阴阳二气的缊直接考虑为道。与此相反,伊川指出,道即便不是离阴阳者,但阴阳那个东西和道明显的立场不同。这说的是,《易》里另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明白的定义,以伊川的考虑,根据这个定义的场合,道和阴阳明显的立场不同。
为什么?因为阴阳是气,气即物质,总之是作为形而下(其意思是能取得形状)的器。不会是阴阳即道[之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意思一定有别的什么[解释]。不是说“阴阳”而是说“一阴一阳”具有什么意思。这不是指阴阳本身,一定是指“所以阴阳”者,即在阴阳这一现象的背后作为阴
阳之根据的东西,这就是道。这样的想法,明显与前面就仁区别仁与爱的想法相似。明道说过“器即道,道即器”,但伊川对其制定了层次性的区别。不是“阴阳”而是“所以阴阳”是道这样的观点,后来为朱子所继承,成为构成贯通朱子学的基本逻辑。道(也可称之为“理”)这样的语词,含有“当然”与“所以然”这样双重含义。“当然”即确应如此,就是作为规范的意思;而“所以然”即所以如此,换言之,就是作为根据的意思。若遵从朱子,那个道是根据这样的意思,现在被赋予理论化的端绪。
性即理的端绪
继承程伊川之思想的朱子,经常赞不绝口的伊川的话是“性即理”。伊川的“性即理”和张横渠的“心统性情”这样两句话,对朱子来说,是所谓“颠扑不破的大真理”。假如以一句话称谓朱子的伦理说,则不外乎“性即理”这三个字,这是数百年来的定论。此说与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斗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壮观的事情,而其端绪确实由伊川开启。
本来,在中国,关于这个“性”的议论,自古持续地被讨论的问题不多。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以后,历经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告子的“性无善恶”“性为生”(《孟子·告子上》)等众所周知的性说,直至唐代韩愈的“性有上、中、下三品”说,性是中国的思想家最爱的论题。其中,“性恶”或者“性无善恶”说,与其说在宋代,倒不如说只要是儒家,通观历代,几乎无信奉者。宋学的根本前提,断然是性善说。其场合,留下二个立场。一是明道所陈述的“生之谓性”——就是说这虽是告子的说法,但因为已被孟子所否定,故不便公开说那是告子的主张;再一个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的性。伊川解释这二者,认为“生之谓性”的性是孔子的“性相近”的性,就是说禀受(出生带的)这样的意思;与此相对,所谓天命之性,因为称谓“性之理”,所以应该说是先天
的道德性。总之,“生之谓性”的性,是说或多或少为气所覆盖、所歪曲的性。他把那个天命之性称为“极本究源之性”,而把生—性这一方面称为“气质之性”,并根据孟子的所谓“养气”法排除对后者的气的障碍,这样来实现一如本来、就是说一如理的性,来放置修养的原理。张横渠也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变化气质”这样的思想,不久为朱子所继承。
饿死和节义
虽然无充分引用之余地,但[表明]伊川的哲学已经是十二分的“理”的哲学。伊川的场合,“理”之强调,达到了极特征性的人生观,即“非天理则人欲”这样的人生观。作为宋学之核心的“天理·人欲”概念,现在伊川那里头一次出现。伊川说:
本来,人既然有身,便有自私,难以与道合一,应该说是当然的。
(《近思录》五)“不为天理即私欲……不为人欲皆天理”,像这样天理人欲之间的紧张,造成严厉的“名教”主义结果,是容易想象的。著名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第二十二卷)这样的严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避免的事。问可否与寡妇结婚,伊川回答说:
“不应该结婚,若与失节者结婚,这就成为自己也失节。”接着,对“贫而无亲属的寡妇场合,能允许再婚吗?”这一提问,回答说:“在后世,说那样的事情,是因唯恐饿死、冻死。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敬
伊川注重分析的、理论的研究(穷理)的事,已经论述了。与这样的知性的态度匹敌,他强调的是“敬”。其思想的源流,大概源于濂溪的“静”。这也同“性即理”之说与“所以阴阳之道”这一观点等一起,予朱子以重大的影响。作为学问之重要方法(与理的知性的追求的穷理(格物致知)匹敌的另一个方法)的“居敬”,同样在伊川那里被讲解。所谓“敬”是什么呢?伊川定义为“主一”即“以一为主”。那么,一是什么呢?这是说“无适”,即“莫行”。总而言之,所谓“敬”,就是心哪儿都不去使,维持专一集中的状态。这即便在普通一般的场合似乎也说的,但其中心的局面恐怕就是不断地维持对于道德性的东西、道德法则的精神集中、敬畏之念。程氏之门人谢上蔡说所谓敬是“常惺惺之法”,就是说经常觉悟之法,同样是这个意思吧。这样,“敬”纯粹是内面性的原理,但它绝不是与外在的物没有关系。“有盘坐而心不慢者吗”。外表上保持脸部紧张的严肃态度,这虽然绝不是直接维持敬的方法,但“敬”应该从这儿开始。“如果据敬涵养心,天理自然明显起来”。不管怎样,与知性的所谓“穷理”匹敌,“敬”被提倡。“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近思录》二),这一车之双轮性的口号被提出,又是具有作为朱子的先驱的重大意义。
张横渠
张横渠(1020—1077),名载,今陕西省西安之西的郿县之横渠镇人。小时候双亲见背,然具有非凡的气质,尤其喜好议论军事。十八岁,时恰当西夏的李元昊不断入侵宋朝之际,希望建树伟大的功勋,而会见范仲淹
叙说其抱负。了解他之气量的范仲淹晓喻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岂以兵为事”,而且赠予《中庸》一册。在此时,他幡然立志于道。但是,最初的时期,热衷于佛教和道教思想的研究,但不久去都城见程氏兄弟(同张载是亲戚),于此时开始完全抛弃异学。这一时代,由于异民族的屡屡入侵,绝不是平稳无事。又,提起范仲淹,则是缔造北宋之可谓极盛期的名臣中的名臣。这个范仲淹指导横渠的话,的确应该说是特征性的。从原始儒教以来,儒教虽然各式各样地改变面貌,但贯穿儒教历史而不变的东西之一,就是力之否定、军事之蔑视。
不久,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当上了地方官,又被任命为宫中的编撰官。后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辞官归乡,每日静坐于一室,“伏而读,仰而思,若有所得,即便在夜中,也要秉烛而书之”,写出了代表作《正蒙》。据说他是个刚毅之人,努力复兴古礼,因此关中的风俗为之一变。又认为假如要实现三代(夏殷周,中国的黄金时代)之治,无论如何也必须从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始,于是与同志们一起买进土地,把它区分为井田,尝试先王遗法的井田法的实施。为了实施井田制的研究好像非常精练,但没有实现其志而含冤死去。
气的哲学
张横渠的思想是“气”的哲学。现代中国的哲学界,认为在中国的哲学之历史里有三个流派:普通是把伊川,朱子的“性即理”的哲学视为客观唯心论(客观的观念论);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哲学视为主观唯心论(主观的观念论);把张横渠以及远承张横渠之思想的明末清初的王船山的“气”之哲学视为唯物论,并将其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最高的哲学,而予张横渠的哲学以高度的评价。他的哲学是气的哲学,这是明白的。但所谓“气”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样的观点(与其说
气不是单纯的物质,倒不如说它应该是生命的原理、生命原体)恐怕是可以存立的,但目前在包括像这样的生机论的东西的意思上,[将气]当作物质原理。[那么]所谓气之哲学是唯物论,绝不是不合道理的断定。
他把宇宙考虑为“虚”。“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就是说天地的根本性质在于虚这方面。虚的极致,便为“太虚”,它是天地宇宙的别名。所谓“太虚”,简言之不外乎气之充满。太虚之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归太虚”(《正蒙·太和篇》),即万物是由气之凝聚而构成的东西,那个气乃是构成宇宙那个东西所依靠的东西。人和万物也浮在“气之海”。在宇宙内,气是难以想象的存在。
气块然为太虚,或升或降,或动或静,或屈或伸,飞扬而一瞬也
不停,这就是《易》所说的“缊”。《正蒙·太和篇》
虽然到哪儿都相同一个气,但同时常常必定是阴阳二气。二而一,一而二,在本质上是矛盾着的存在。一切的存在不外乎从像这样的气(阴阳)之自己运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这宛如水同冰的关系。所有的存在在变化途中,只是暂时的形态,就如同水的一部分变成冰浮着那样的东西(太和篇)。即便在我们的肉眼不能认识的任何存在场合,宇宙里也“无无”(太和篇),虚无的空间这样的东西哪儿也不存在。不是说有了虚无的空间后,气才充满于其中,气有其自体,就是空间。把“无”作为其哲学之原理的佛教之误,从这一点上亦可了解。
由像这样的气的自己运动产生出万物,换言之,万物“由气而化”才有“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所谓“道”,就是宛如野马,即春天的原野里到处洋溢的蜉蝣似的缊气的自己运动过程那个东西。虽然把旺盛的活动状态包含于内,但保持无比的调和即“太和”,这
之中就有“道”。所以,风雨、霜雪、万物、山川,作为一而“无非教也”。像这样的气的作用,是超越普通人的常识的灵妙的东西,其取名为“鬼神”。所谓“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假如视所谓“生”为气之集结,所谓“死”则为气之解散,则死与生之间,应该说不存在任何不可理解的深渊。
天地 吾 同胞
作为横渠的著述,最著名的是陈述其唯物论哲学的《正蒙》和仅二百五十三字的《西铭》(《近思录》二)。《西铭》是悬挂于他之书斋的西窗的规诫文字(铭),与挂在东窗的《东铭》成双的文章。但《东铭》的事几乎不被说起,净成为问题的是《西铭》。《西铭》首先如下似的开始: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人是微弱的存在,但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在其中间作为三者混然、即《中庸》所谓“与天地参”而活着者。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塞于天地之间的东西,不用说是气。禀受那天之阳气、地之阴气而存在我这样肉体的存在。假如注意那天地之气与聚而形成吾肉体之气的同一性,则可以说“聚亦吾体,散亦吾体”(《正蒙·太和篇》)。大凡充满于天地间的东西都可以说是气——吾。但人不仅仅是气,由于人最高度地藏有天命之“性”(道德性),故成为万物之灵长,可以说是宇宙间的气之“帅”(“志,气之帅也”。孟子语)。他首先这样指出在宇宙里人的地位,接着说
万民皆兄弟、万物皆朋友。朱子就此处注曰:因为是同胞,故“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而且,因为是吾友,故大凡存在于天地间的东西,动物,植物,具有感觉作用的东西和不具有感觉作用的东西,全部使其全生——性。这就是儒者之道,它参天地、赞助天地之化育以后才可以说完全地完成了其使命……
宇宙的家族主义
《西铭》进而继续说: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
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与天地)合德,贤其秀也,凡天
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以下,接连书写为子者的心得,但人们在这里也许不能读懂典型的家父长主义、充其量是家父长的恩情主义以外的意思。这确实是理所当然。假如从“万物一体之仁”说过度地引申出平等主义,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这未必把握了真相。孟子的话语里有“亲亲、仁民、爱物”,但儒教的爱的学说,主张对于像这样的骨肉之亲、一般人民、进而那以外的场合,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爱都必须有差等。“万物一体之仁”也绝不是指向打破这一前提的学说。这或者是宇宙性的家父长主义,《西铭》也许可以说正指示了那件事。像这样的看法也不是没有理由,但我想怀疑:所谓视天地为“我与众所共有的一大父母”(关于《西铭》的朱子之语)这样的宇宙性的家族主义,与强烈的理想主义相结合时,不用说没有起到平均主义的乌托邦主义(同胞主义)的作用吧。
果然,《西铭》著作的当时,其同时代就有人怀疑这个《西铭》,说不
就是墨子的“兼爱”吗?(《朱子语类》九八)据说又有人把这个《西铭》比作异端邪说的杨、墨,骂为“名教之大贼”(《朱子文集》七一《记林黄中辨易西铭》)。我仍然想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样的口号作为指向平等的思想来评价。事实上,后世引用《西铭》,大部分是把这一“民胞物与”作为平等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抗议的口号来引用。朱子任知事的时候,据说遇到过士大夫的子弟乘马将普通人家的孩子撞成濒死之重伤的事件,官僚都为士大夫的子弟辩护,但朱子诵读《西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一段,终于没有听从(《朱子语类》卷一〇六)。程明道称赞这个《西铭》为《孟子》以后最伟大的文献,评价:《孟子》以后只有韩愈的《原道》可以说,但不用说《西铭》应该是《原道》的宗祖。明道以前也指出,它值得[进]明道的“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谱系。在程氏的学派里,《西铭》是被作为一种教科书使用。
邵康节和图书象数之学
作为波及宋学的道家——道教性的思想之影响,已提过那样的一种宇宙的感情、夺取宇宙造化之机这样的志向。但作为那样道家系统的思想家之最著名者,可以举邵雍,即邵康节(1011—1077年、洛阳人)。他是继承宋初著名道士陈抟(陈希夷)的系统的学者,学过在道家内部所传的图书先天象数之学。所谓图书,是指河图洛书,就是说远古时从黄河与洛水中出现的形而上学的图表;所谓先天,在易之哲理的解释里有所谓的先天说、后天说,其先天象数,所说的就是易之解释学之中根据图像方法的象学和根据一种数理哲学的数学,简言之,就是易之宇宙理论或者宇宙时间理论的极其密教性质的东西,是在道家道士之间绵绵流传下来的东西。
他步入而立之年,时当著名的庆历时代,是由于范仲淹、文彦博、欧
阳修等这样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北宋迎来了最初的高潮时代。而且,他的晚年,是著名的王安石时代,这时还有司马光、苏轼等,与王安石对立,活跃在政界;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等大思想家也全都是与其同时代的人。当时,富弼和司马光等要人,退出官界而居于洛阳。程明道、程伊川等也在此地鼓吹新的理想主义哲学,同时张横渠也曾一度在这里讲课。当时的洛阳,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壮观。富弼、司马光辈为邵康节提供买于洛阳的住宅。他乘着被一个随从拉的小车,兴高如愿地外出。士大夫一旦听到熟悉的他的车声,即争着出迎,以至于孩子和男仆,都只说“吾家先生至也”,不称呼其姓名和字。据说身份高贵之人、卑贱之人,贤明之人、愚蠢之人,全都以诚接待,大家一起举杯,笑语喧嚷地度日。屡次被政府授官,但都没有就任。在洛阳的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声而面带愁容,说二年以内要出现南人宰相,而且以后天下开始多事起来。这是预言王安石的出现,它是著名的传说。
宇宙时间的周期
他的学问,如上面所说是图书象数之学,但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那个“数学”。二程将其数学评为“空中楼阁”,好像不怎么认真理睬。但是,它给予朱子相当影响。他的数学之中最通俗的部分,就是那个《皇极经世书》内能看到的“元、会、运、世”之说。这应该说从时间方面观察的宇宙哲学,或者宇宙时间的周期。所谓的元、会、运、世,即一世是三十年,十二世是一运(三百六十年),三十运一会(一万八百年),十二会一元,就是说它的计算是30×12×30×12。总而言之,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旦来到一元,天地就更新。《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一元之数,不过是最初的循环单位,宇宙时间进而元之世(129600年×30)、元之运(129600年×30×
12)、元之会(129600年×30×12×30),元之元(1296002年),无论怎样也前进,最后计算至“元之元之元之元·二万八千二百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年”。邵康节的“元会运世”之说
这个一元,现在如果稍加说明,则如上图所示,被比作一昼夜,前半相当于阳,后半相当于阴。认为最初的一万八百年(第一会)天开,接着的一万八百年(第二会)期间地辟,第三个一万八百年(第三会)的期间内产生人、产生万物。而且,第六个一万八百年这一期间,若用《易》来说,则是相当于乾卦的天地全盛时期,据说尧是此会的第三十运的第九世,即如果从元之开始说,则自六万四千七百十年至六万四千八百年之间,为尧的治世。又,康节生活的时代,譬如宋之熙宁元年(1068),是这一会(第六会)的第十运,若从元之开始通算的话,则是第百九十运的第二世的第十五年,即从开始数为六万八千八十五年。经过天地全盛的时期,宇宙时间开始渐渐地趋向下坡。
像这样的元会运世之说,另外的各种各样的康节之说,果真指什么呢?“总而言之,若不把先生从地下叫起来请教,则无论如何也不能通其旨”(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关于这一循环的进行,也有如下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以为从第一世开始一直向上至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在这个极处,再
一变回归原始,第二元开始。另一种解释以为一元即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内,前半向上,后半下降,其下降之极,便是第二元的开始,再转变向上。现在姑且根据后说。哪一说正确呢?我亦不能决定。
以物观物
上面叙述的是他的所谓“数学”,他还提倡“观物”,那是说“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观物内篇》)。例如,像古今之区别一样,固然以我而观便产生了昔与今的区别,但若把观的我完全取消而观的话,这样的区别就全消失。
以物观物是“性”,以我观物是“情”,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观
物外篇》)。他的思想,虽然由道家的“数学”出发而含有[道家思想内容],但儒教的色彩也非常浓,所谓宋学性的说教也绝不少。朱子对邵康节也大表敬意。所以就有[这样]的事——也把他列在朱子学的先驱之内,与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这四人合并,称为“北宋的五子”。前面把宋学的思想特征规定为泛神论的世界观,而最出色地表现了这个特征者恐怕就是这个邵康节。他有《击壤集》这样的诗集,它在中国的诗集中是很古怪的,通篇应该说是所谓的思想诗。例如《观易吟》这样的诗: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之备我,肯把三才(天地人)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像这样的诗,恐怕可以说以最不压抑的形式表现了作为宋学之基础的泛神论。朱子评价其学问,以为它“包括宇宙,终始古今”,但我想无论如何也应该知道在宋初出现了像“元会运世”学说那样雄大的思想。它与司马光编篡的名著《资治通鉴》、欧阳修编篡《新唐书》和《五代书》,都是同时代的;与产生出欧阳修的批判性的经学与春秋学,也是同时代。但是,遗憾的是,其雄大也不免[让人]有只是由相同程序之平面性的重复而完成之感。
程伊川(1033—1107),名颐。明道之弟,比明道小一岁。少年时期,兄弟俩就学于周濂溪的事,如同已述。随后上都城(开封)的太学,接受胡瑷的教育。胡瑷与其说是思想家,倒不如应该说是大教育家,是首先提出“明体达用”这一士大夫教育之大目标的人,这已经一言带过。不久,伊川在宫中被任为讲读官。他获得真诚的侍讲这一崇高的名声,很多的士大夫成为他的弟子,但在另一方面,因为以天下为已任,于议论和批判的场合,直言无忌,似乎又树立了相当多的敌对。著名的苏轼(苏东坡)恰好同时在翰林院,他名声很高,是文学者的领袖。文学家讨厌规规矩矩的道学先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同样的。此种场合,程氏的一派同苏氏(出身于蜀即四川省)的一派彼此不和,被称为洛党、蜀党。不久,受所谓的新法党、旧法党之争牵连,终于被打成流放者。后来,虽能恢复原官,但这回又因为建立以邪说惑人的党派这样的理由,受到了被河南府检察、其门下所有的学生放逐、身为领袖的伊川登记于党人目录这样的处分,但据说从四方投奔来的门生依然不离去。患病垂危时,弟子向前靠近说,先生平生的学问现在即将有用。听到这样说,伊川略微睁开眼,责备道,对道的学问来说,有用这样的说法不正确。“其人尚未出寝门而先生殁”。道学的根本理念是讲不为了什么,只是为了道本身而学习道、实践道(“无所为而为”,张拭之语)。伊川的临终一语,可以说使道学先生的面目栩栩如生。
据说明道春风和气,伊川秋霜烈日,明道和伊川,在性格方面非常的不同。[伊川]曾瞑目静坐,二个弟子侍立。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日暮,伊川告之曰:归休吧。二个弟子退而一看,外面的雪积有一尺多厚。
仁和爱的关系
儒教的中心教义是仁,其最普通的意思是“爱人”。但是,如果像唐以前那样,把儒教以周公为中心来考虑的话,则中心教义未必是仁,也许可以说“礼”就是其中心教义。但是,如同已经叙述的那样,所谓儒教,唐以后改变了面目,开始强烈地意识孔子之教这样的意思。于是像韩愈的《原道》的场合那样,其开头就有“博爱之谓仁”,仁就是爱。
与此相反,一进入宋代,各种各样的仁说就兴盛起来。其第一位的仁说,就是已经举出的程明道的仁说。对于这个仁说,朱子是非常警惕的,这已一言带过。总的说来,朱子对程氏兄弟表示非常的敬意,当作自己的先驱者。但在实际的思想内容的继承这方面,可以说差不多完全继承了伊川。关于仁的思索也是其一例。伊川首先如下那样的主张:因《孟子》里有“恻隐之心,仁也”(《告子上》)这样的话,故后世终于以爱为仁。恻隐、怜悯,即便的确当作爱,但因为爱是情,仁是性,所以不能直接地把爱视为仁。孟子确实把恻隐作为仁,但必须注意在它前面已经说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只限于有“仁之端”,当然不能直接等同“仁”本身。仁者不用说是广泛地爱吧。但是,像韩愈那样,直接把博爱当作仁是错误的。云云。
那么,伊川关于仁提供了怎样的定义呢?他之仁的定义是“公而以人体之”,(《近思录》二)其意思,如朱子的解释那样,就是这样的意思(公而无私就是仁)吧。但是,伊川的这个仁的定义,就其自身而论,其实不是有思想史性质之重大意义的定义。[说它有]像明道的“万物一体之仁”
对那以后的思想史所具有的那样重大的意义,是不能承认的。
体和用的严格区别
但是,可以说伊川的仁说的前半,即对仁〓爱的批判方面,后来作为所谓朱子学的集大成的独特思想的一个要素来考虑时,则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断然地分开爱与仁,以为相对于前者是已发之“情”,后者则是未发之“性”。仅仅这一点,也许不能具有充分的意义。但是,若参照后来在朱子那里最终被整理为下列的范畴系列来考虑的话,就能够认识:应该说朱子学之可谓核心的逻辑,此时已经大致明确地形成了。
假如以常见的例子说,[不妨看]《论语·学而篇》第二条: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此条最后一句,在朱子学,读为“行仁之本”,决不读为“是仁之本”。像该条的朱子注所明说的那样,这是根据伊川的逻辑。像仁是体,爱是用那样,这个场合,仁是体,孝悌是用。孝悌作为对双亲的爱,是最大的爱,因此可以说孝悌是实践仁的开端,是实行仁之本。但是,把不过是情、不过是用的孝悌,说成是性、是体的仁,是那个仁之本,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相比哥哥明道之学问的、思想的态度是浑一的、直觉的,弟弟伊川是分析的、思辨的、逻辑的,这是公认的。伊川强调“思(致知)”这样的事情。例如,即便作为为了克服人欲的方法,也强调“思”这件事,说“学莫贵于思,唯思能窒欲”(《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天下物皆可以理照”(《二程遗书》卷十八),这是他的信念。从这里产生了后来的朱子把其作为先驱的他的格物说。关于这一点,打算在后面朱子那一章里涉及,而像这样的伊川的分析的态度,在仁说里,仁和爱也被区别。
阴阳和道
应该与此并行地被考虑的再一个学说,是对于《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的他的解释。他说: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
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一五)在这里我们接触到极应注意的新的见解。历来把“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易经》的话,解为阴和阳二气之缊,而把阴阳二气的缊直接考虑为道。与此相反,伊川指出,道即便不是离阴阳者,但阴阳那个东西和道明显的立场不同。这说的是,《易》里另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明白的定义,以伊川的考虑,根据这个定义的场合,道和阴阳明显的立场不同。
为什么?因为阴阳是气,气即物质,总之是作为形而下(其意思是能取得形状)的器。不会是阴阳即道[之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意思一定有别的什么[解释]。不是说“阴阳”而是说“一阴一阳”具有什么意思。这不是指阴阳本身,一定是指“所以阴阳”者,即在阴阳这一现象的背后作为阴
阳之根据的东西,这就是道。这样的想法,明显与前面就仁区别仁与爱的想法相似。明道说过“器即道,道即器”,但伊川对其制定了层次性的区别。不是“阴阳”而是“所以阴阳”是道这样的观点,后来为朱子所继承,成为构成贯通朱子学的基本逻辑。道(也可称之为“理”)这样的语词,含有“当然”与“所以然”这样双重含义。“当然”即确应如此,就是作为规范的意思;而“所以然”即所以如此,换言之,就是作为根据的意思。若遵从朱子,那个道是根据这样的意思,现在被赋予理论化的端绪。
性即理的端绪
继承程伊川之思想的朱子,经常赞不绝口的伊川的话是“性即理”。伊川的“性即理”和张横渠的“心统性情”这样两句话,对朱子来说,是所谓“颠扑不破的大真理”。假如以一句话称谓朱子的伦理说,则不外乎“性即理”这三个字,这是数百年来的定论。此说与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斗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壮观的事情,而其端绪确实由伊川开启。
本来,在中国,关于这个“性”的议论,自古持续地被讨论的问题不多。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以后,历经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告子的“性无善恶”“性为生”(《孟子·告子上》)等众所周知的性说,直至唐代韩愈的“性有上、中、下三品”说,性是中国的思想家最爱的论题。其中,“性恶”或者“性无善恶”说,与其说在宋代,倒不如说只要是儒家,通观历代,几乎无信奉者。宋学的根本前提,断然是性善说。其场合,留下二个立场。一是明道所陈述的“生之谓性”——就是说这虽是告子的说法,但因为已被孟子所否定,故不便公开说那是告子的主张;再一个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的性。伊川解释这二者,认为“生之谓性”的性是孔子的“性相近”的性,就是说禀受(出生带的)这样的意思;与此相对,所谓天命之性,因为称谓“性之理”,所以应该说是先天
的道德性。总之,“生之谓性”的性,是说或多或少为气所覆盖、所歪曲的性。他把那个天命之性称为“极本究源之性”,而把生—性这一方面称为“气质之性”,并根据孟子的所谓“养气”法排除对后者的气的障碍,这样来实现一如本来、就是说一如理的性,来放置修养的原理。张横渠也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变化气质”这样的思想,不久为朱子所继承。
饿死和节义
虽然无充分引用之余地,但[表明]伊川的哲学已经是十二分的“理”的哲学。伊川的场合,“理”之强调,达到了极特征性的人生观,即“非天理则人欲”这样的人生观。作为宋学之核心的“天理·人欲”概念,现在伊川那里头一次出现。伊川说:
本来,人既然有身,便有自私,难以与道合一,应该说是当然的。
(《近思录》五)“不为天理即私欲……不为人欲皆天理”,像这样天理人欲之间的紧张,造成严厉的“名教”主义结果,是容易想象的。著名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第二十二卷)这样的严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避免的事。问可否与寡妇结婚,伊川回答说:
“不应该结婚,若与失节者结婚,这就成为自己也失节。”接着,对“贫而无亲属的寡妇场合,能允许再婚吗?”这一提问,回答说:“在后世,说那样的事情,是因唯恐饿死、冻死。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敬
伊川注重分析的、理论的研究(穷理)的事,已经论述了。与这样的知性的态度匹敌,他强调的是“敬”。其思想的源流,大概源于濂溪的“静”。这也同“性即理”之说与“所以阴阳之道”这一观点等一起,予朱子以重大的影响。作为学问之重要方法(与理的知性的追求的穷理(格物致知)匹敌的另一个方法)的“居敬”,同样在伊川那里被讲解。所谓“敬”是什么呢?伊川定义为“主一”即“以一为主”。那么,一是什么呢?这是说“无适”,即“莫行”。总而言之,所谓“敬”,就是心哪儿都不去使,维持专一集中的状态。这即便在普通一般的场合似乎也说的,但其中心的局面恐怕就是不断地维持对于道德性的东西、道德法则的精神集中、敬畏之念。程氏之门人谢上蔡说所谓敬是“常惺惺之法”,就是说经常觉悟之法,同样是这个意思吧。这样,“敬”纯粹是内面性的原理,但它绝不是与外在的物没有关系。“有盘坐而心不慢者吗”。外表上保持脸部紧张的严肃态度,这虽然绝不是直接维持敬的方法,但“敬”应该从这儿开始。“如果据敬涵养心,天理自然明显起来”。不管怎样,与知性的所谓“穷理”匹敌,“敬”被提倡。“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近思录》二),这一车之双轮性的口号被提出,又是具有作为朱子的先驱的重大意义。
张横渠
张横渠(1020—1077),名载,今陕西省西安之西的郿县之横渠镇人。小时候双亲见背,然具有非凡的气质,尤其喜好议论军事。十八岁,时恰当西夏的李元昊不断入侵宋朝之际,希望建树伟大的功勋,而会见范仲淹
叙说其抱负。了解他之气量的范仲淹晓喻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岂以兵为事”,而且赠予《中庸》一册。在此时,他幡然立志于道。但是,最初的时期,热衷于佛教和道教思想的研究,但不久去都城见程氏兄弟(同张载是亲戚),于此时开始完全抛弃异学。这一时代,由于异民族的屡屡入侵,绝不是平稳无事。又,提起范仲淹,则是缔造北宋之可谓极盛期的名臣中的名臣。这个范仲淹指导横渠的话,的确应该说是特征性的。从原始儒教以来,儒教虽然各式各样地改变面貌,但贯穿儒教历史而不变的东西之一,就是力之否定、军事之蔑视。
不久,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当上了地方官,又被任命为宫中的编撰官。后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辞官归乡,每日静坐于一室,“伏而读,仰而思,若有所得,即便在夜中,也要秉烛而书之”,写出了代表作《正蒙》。据说他是个刚毅之人,努力复兴古礼,因此关中的风俗为之一变。又认为假如要实现三代(夏殷周,中国的黄金时代)之治,无论如何也必须从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始,于是与同志们一起买进土地,把它区分为井田,尝试先王遗法的井田法的实施。为了实施井田制的研究好像非常精练,但没有实现其志而含冤死去。
气的哲学
张横渠的思想是“气”的哲学。现代中国的哲学界,认为在中国的哲学之历史里有三个流派:普通是把伊川,朱子的“性即理”的哲学视为客观唯心论(客观的观念论);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哲学视为主观唯心论(主观的观念论);把张横渠以及远承张横渠之思想的明末清初的王船山的“气”之哲学视为唯物论,并将其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最高的哲学,而予张横渠的哲学以高度的评价。他的哲学是气的哲学,这是明白的。但所谓“气”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样的观点(与其说
气不是单纯的物质,倒不如说它应该是生命的原理、生命原体)恐怕是可以存立的,但目前在包括像这样的生机论的东西的意思上,[将气]当作物质原理。[那么]所谓气之哲学是唯物论,绝不是不合道理的断定。
他把宇宙考虑为“虚”。“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就是说天地的根本性质在于虚这方面。虚的极致,便为“太虚”,它是天地宇宙的别名。所谓“太虚”,简言之不外乎气之充满。太虚之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归太虚”(《正蒙·太和篇》),即万物是由气之凝聚而构成的东西,那个气乃是构成宇宙那个东西所依靠的东西。人和万物也浮在“气之海”。在宇宙内,气是难以想象的存在。
气块然为太虚,或升或降,或动或静,或屈或伸,飞扬而一瞬也
不停,这就是《易》所说的“缊”。《正蒙·太和篇》
虽然到哪儿都相同一个气,但同时常常必定是阴阳二气。二而一,一而二,在本质上是矛盾着的存在。一切的存在不外乎从像这样的气(阴阳)之自己运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这宛如水同冰的关系。所有的存在在变化途中,只是暂时的形态,就如同水的一部分变成冰浮着那样的东西(太和篇)。即便在我们的肉眼不能认识的任何存在场合,宇宙里也“无无”(太和篇),虚无的空间这样的东西哪儿也不存在。不是说有了虚无的空间后,气才充满于其中,气有其自体,就是空间。把“无”作为其哲学之原理的佛教之误,从这一点上亦可了解。
由像这样的气的自己运动产生出万物,换言之,万物“由气而化”才有“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所谓“道”,就是宛如野马,即春天的原野里到处洋溢的蜉蝣似的缊气的自己运动过程那个东西。虽然把旺盛的活动状态包含于内,但保持无比的调和即“太和”,这
之中就有“道”。所以,风雨、霜雪、万物、山川,作为一而“无非教也”。像这样的气的作用,是超越普通人的常识的灵妙的东西,其取名为“鬼神”。所谓“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假如视所谓“生”为气之集结,所谓“死”则为气之解散,则死与生之间,应该说不存在任何不可理解的深渊。
天地 吾 同胞
作为横渠的著述,最著名的是陈述其唯物论哲学的《正蒙》和仅二百五十三字的《西铭》(《近思录》二)。《西铭》是悬挂于他之书斋的西窗的规诫文字(铭),与挂在东窗的《东铭》成双的文章。但《东铭》的事几乎不被说起,净成为问题的是《西铭》。《西铭》首先如下似的开始: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人是微弱的存在,但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在其中间作为三者混然、即《中庸》所谓“与天地参”而活着者。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塞于天地之间的东西,不用说是气。禀受那天之阳气、地之阴气而存在我这样肉体的存在。假如注意那天地之气与聚而形成吾肉体之气的同一性,则可以说“聚亦吾体,散亦吾体”(《正蒙·太和篇》)。大凡充满于天地间的东西都可以说是气——吾。但人不仅仅是气,由于人最高度地藏有天命之“性”(道德性),故成为万物之灵长,可以说是宇宙间的气之“帅”(“志,气之帅也”。孟子语)。他首先这样指出在宇宙里人的地位,接着说
万民皆兄弟、万物皆朋友。朱子就此处注曰:因为是同胞,故“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而且,因为是吾友,故大凡存在于天地间的东西,动物,植物,具有感觉作用的东西和不具有感觉作用的东西,全部使其全生——性。这就是儒者之道,它参天地、赞助天地之化育以后才可以说完全地完成了其使命……
宇宙的家族主义
《西铭》进而继续说: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
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与天地)合德,贤其秀也,凡天
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以下,接连书写为子者的心得,但人们在这里也许不能读懂典型的家父长主义、充其量是家父长的恩情主义以外的意思。这确实是理所当然。假如从“万物一体之仁”说过度地引申出平等主义,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这未必把握了真相。孟子的话语里有“亲亲、仁民、爱物”,但儒教的爱的学说,主张对于像这样的骨肉之亲、一般人民、进而那以外的场合,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爱都必须有差等。“万物一体之仁”也绝不是指向打破这一前提的学说。这或者是宇宙性的家父长主义,《西铭》也许可以说正指示了那件事。像这样的看法也不是没有理由,但我想怀疑:所谓视天地为“我与众所共有的一大父母”(关于《西铭》的朱子之语)这样的宇宙性的家族主义,与强烈的理想主义相结合时,不用说没有起到平均主义的乌托邦主义(同胞主义)的作用吧。
果然,《西铭》著作的当时,其同时代就有人怀疑这个《西铭》,说不
就是墨子的“兼爱”吗?(《朱子语类》九八)据说又有人把这个《西铭》比作异端邪说的杨、墨,骂为“名教之大贼”(《朱子文集》七一《记林黄中辨易西铭》)。我仍然想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样的口号作为指向平等的思想来评价。事实上,后世引用《西铭》,大部分是把这一“民胞物与”作为平等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抗议的口号来引用。朱子任知事的时候,据说遇到过士大夫的子弟乘马将普通人家的孩子撞成濒死之重伤的事件,官僚都为士大夫的子弟辩护,但朱子诵读《西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一段,终于没有听从(《朱子语类》卷一〇六)。程明道称赞这个《西铭》为《孟子》以后最伟大的文献,评价:《孟子》以后只有韩愈的《原道》可以说,但不用说《西铭》应该是《原道》的宗祖。明道以前也指出,它值得[进]明道的“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谱系。在程氏的学派里,《西铭》是被作为一种教科书使用。
邵康节和图书象数之学
作为波及宋学的道家——道教性的思想之影响,已提过那样的一种宇宙的感情、夺取宇宙造化之机这样的志向。但作为那样道家系统的思想家之最著名者,可以举邵雍,即邵康节(1011—1077年、洛阳人)。他是继承宋初著名道士陈抟(陈希夷)的系统的学者,学过在道家内部所传的图书先天象数之学。所谓图书,是指河图洛书,就是说远古时从黄河与洛水中出现的形而上学的图表;所谓先天,在易之哲理的解释里有所谓的先天说、后天说,其先天象数,所说的就是易之解释学之中根据图像方法的象学和根据一种数理哲学的数学,简言之,就是易之宇宙理论或者宇宙时间理论的极其密教性质的东西,是在道家道士之间绵绵流传下来的东西。
他步入而立之年,时当著名的庆历时代,是由于范仲淹、文彦博、欧
阳修等这样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北宋迎来了最初的高潮时代。而且,他的晚年,是著名的王安石时代,这时还有司马光、苏轼等,与王安石对立,活跃在政界;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等大思想家也全都是与其同时代的人。当时,富弼和司马光等要人,退出官界而居于洛阳。程明道、程伊川等也在此地鼓吹新的理想主义哲学,同时张横渠也曾一度在这里讲课。当时的洛阳,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壮观。富弼、司马光辈为邵康节提供买于洛阳的住宅。他乘着被一个随从拉的小车,兴高如愿地外出。士大夫一旦听到熟悉的他的车声,即争着出迎,以至于孩子和男仆,都只说“吾家先生至也”,不称呼其姓名和字。据说身份高贵之人、卑贱之人,贤明之人、愚蠢之人,全都以诚接待,大家一起举杯,笑语喧嚷地度日。屡次被政府授官,但都没有就任。在洛阳的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声而面带愁容,说二年以内要出现南人宰相,而且以后天下开始多事起来。这是预言王安石的出现,它是著名的传说。
宇宙时间的周期
他的学问,如上面所说是图书象数之学,但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那个“数学”。二程将其数学评为“空中楼阁”,好像不怎么认真理睬。但是,它给予朱子相当影响。他的数学之中最通俗的部分,就是那个《皇极经世书》内能看到的“元、会、运、世”之说。这应该说从时间方面观察的宇宙哲学,或者宇宙时间的周期。所谓的元、会、运、世,即一世是三十年,十二世是一运(三百六十年),三十运一会(一万八百年),十二会一元,就是说它的计算是30×12×30×12。总而言之,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旦来到一元,天地就更新。《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一元之数,不过是最初的循环单位,宇宙时间进而元之世(129600年×30)、元之运(129600年×30×
12)、元之会(129600年×30×12×30),元之元(1296002年),无论怎样也前进,最后计算至“元之元之元之元·二万八千二百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年”。邵康节的“元会运世”之说
这个一元,现在如果稍加说明,则如上图所示,被比作一昼夜,前半相当于阳,后半相当于阴。认为最初的一万八百年(第一会)天开,接着的一万八百年(第二会)期间地辟,第三个一万八百年(第三会)的期间内产生人、产生万物。而且,第六个一万八百年这一期间,若用《易》来说,则是相当于乾卦的天地全盛时期,据说尧是此会的第三十运的第九世,即如果从元之开始说,则自六万四千七百十年至六万四千八百年之间,为尧的治世。又,康节生活的时代,譬如宋之熙宁元年(1068),是这一会(第六会)的第十运,若从元之开始通算的话,则是第百九十运的第二世的第十五年,即从开始数为六万八千八十五年。经过天地全盛的时期,宇宙时间开始渐渐地趋向下坡。
像这样的元会运世之说,另外的各种各样的康节之说,果真指什么呢?“总而言之,若不把先生从地下叫起来请教,则无论如何也不能通其旨”(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关于这一循环的进行,也有如下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以为从第一世开始一直向上至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在这个极处,再
一变回归原始,第二元开始。另一种解释以为一元即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内,前半向上,后半下降,其下降之极,便是第二元的开始,再转变向上。现在姑且根据后说。哪一说正确呢?我亦不能决定。
以物观物
上面叙述的是他的所谓“数学”,他还提倡“观物”,那是说“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观物内篇》)。例如,像古今之区别一样,固然以我而观便产生了昔与今的区别,但若把观的我完全取消而观的话,这样的区别就全消失。
以物观物是“性”,以我观物是“情”,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观
物外篇》)。他的思想,虽然由道家的“数学”出发而含有[道家思想内容],但儒教的色彩也非常浓,所谓宋学性的说教也绝不少。朱子对邵康节也大表敬意。所以就有[这样]的事——也把他列在朱子学的先驱之内,与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这四人合并,称为“北宋的五子”。前面把宋学的思想特征规定为泛神论的世界观,而最出色地表现了这个特征者恐怕就是这个邵康节。他有《击壤集》这样的诗集,它在中国的诗集中是很古怪的,通篇应该说是所谓的思想诗。例如《观易吟》这样的诗: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之备我,肯把三才(天地人)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像这样的诗,恐怕可以说以最不压抑的形式表现了作为宋学之基础的泛神论。朱子评价其学问,以为它“包括宇宙,终始古今”,但我想无论如何也应该知道在宋初出现了像“元会运世”学说那样雄大的思想。它与司马光编篡的名著《资治通鉴》、欧阳修编篡《新唐书》和《五代书》,都是同时代的;与产生出欧阳修的批判性的经学与春秋学,也是同时代。但是,遗憾的是,其雄大也不免[让人]有只是由相同程序之平面性的重复而完成之感。
相关人物
朱子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