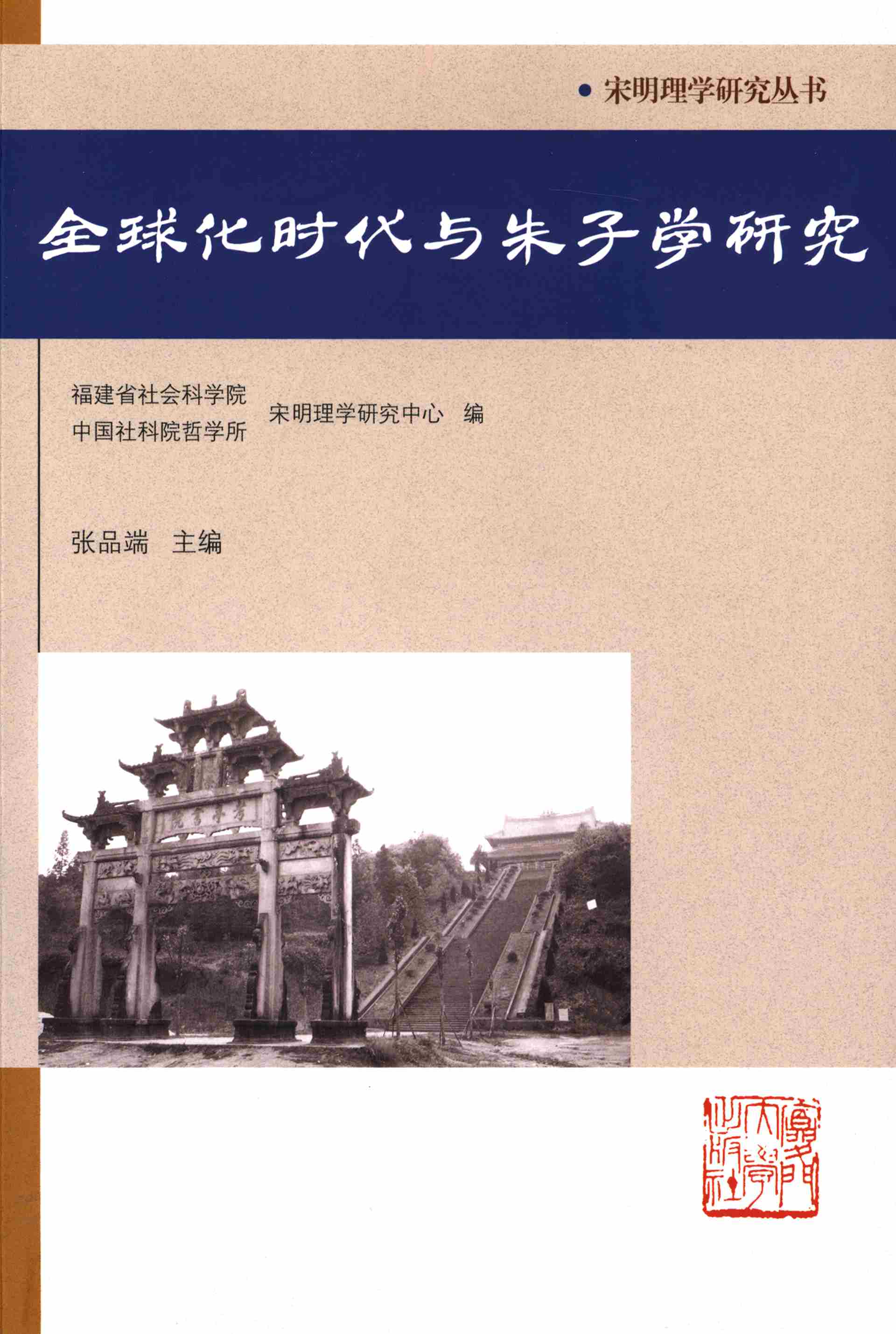17世纪朝鲜朱子学的转变
| 内容出处: | 《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335 |
| 颗粒名称: | 17世纪朝鲜朱子学的转变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1 |
| 页码: | 346-366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17世纪韩国儒学史中新经书解释的出现及其意义,重新思考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
| 关键词: | 韩国儒学 新经书解释 17世纪 |
内容
17世纪被认为是韩国儒学史发生思想转换的年代。朝鲜半岛在1592—1636年这四十余年间,接连遭到日本丰臣秀吉和北方后金政权的4次入侵。在此苦难的时代,经书解释开始出现不同于朱子学解释的异说。学界对于这些新的解释赋予如下述意义:这是一部分的儒者为了度过时代难关,尝试摸索新思想以取代旧有朱子学的一环。
本文认为这种意义赋予20世纪前后的知识人直面国家、民族的危机时,想要从儒学史中找出“近代”思想之萌芽的情况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过程里,他们从17世纪儒者的著作中,导出时人认为有思想——即朱子学——没办法克服现今危险这样的见解。然而尽管20世纪的知识人确实怀抱这样的问题意识,17世纪的儒者是否真的也与他们相同呢?本文对此想要重新确认。
为了确认这件事,有必要考虑17世纪的社会环境让儒者究竟是对朱子学开始抱持怀疑,还是怀抱着更强的使命感去面对朱子学研究?首先有别于朱熹之经书解释的新解释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还有给予注释的作者提出新学说的整个过程究竟是什么样貌?而当时的社会又是如何理解这样的事呢?本文将分析其周遭同辈及政敌的反应,可以得到他们如何认知这件事的某些提示。他们是所谓那些朝着具有权威的思想体系发起挑战的人吗?而这些新学说的提出者,自己是否又以朱子学的批判者自居呢?
儒者生存的年代与20世纪前后的知识人所直面的东亚情势相差甚远,职是之故,从西洋式殖民模式里探求救国方法的近代知识人,与怀抱着以中国为中心之天下意识的朝鲜时代儒者,或以“国”,或以“天下”所确立之志向,自然不会得出同样的东西。然而殖民地时代的韩国知识人在赋予儒者之事业以意义时,或许却忘了朝鲜时代儒者生存的现实环境,以及他们的生存之道。
殖民时代的韩国知识人,以取回作为近代国民国家的韩国之主权为其第一要务。有着这样现实需求的他们,没有足够从容去踏实地思考、去站在过往朝鲜时代儒者的视角省视其穷尽一生所追求为何物?而韩国儒学史整体又有何内涵,在20世纪后半出生的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当时的知识人所背负的使命感之重量。尽管本文是探讨韩国儒学史并试图修正其在后来定位的,但也希望学习当时知识人的志向,于21世纪的学术界中被赋予部分使命。
一、新的经书解释之出现
虽然朝鲜时代以朱子学为国是,以朱子学的经书解释为科举考试基准,但也存在提出与朱熹注释相异见解的人,他们有不少人因为招来物议,最终被处罚。这些著作异于朱熹注释者的登场及对于他们的牵制或批判的记录,从来都被理解成持有朱子学批判意识的一侧,被朱子学侧弹压的状况。“朱子学侧与反朱子学侧的对立图式”如此被确立。在那样的图式中,17世纪的儒学史从两个对立的轴被说明——朱子学的深化研究和教条化,对立对朱子学的怀疑和批判。但是本文指出,17世纪的儒学史应该是在超越这两个对立轴的地平面上所展开的。
一般而言,对于某个对象的研究若到了极为细密的阶段,会产生视野的窄化,或是动则被固定观念所局限,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在研究之际注意到该思想体系的缺点,将此研究对象客观化,开始能够批判性地认识它,这样的可能性也变得越高。就算是看起来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如果彻底去追究,它也很有可能从自身浮现破绽。如同后述,17世纪韩国的朱子学者一边比对朱熹的各种著述,一边研究朱子学,认识到朱熹的学说经历数度变化,更进一步确认在朱熹的复数言说之间,存在不少矛盾。
承上所述,朝鲜时代儒者的研究可能无法断定,绝不可能成为原动力,产生异于朱熹注释的创见,也无法单单认为这些研究只有迈向朱子学教条化一途。无批判地信奉,是因对作为对象的知识还未彻底研究的状况下才容易产生。接着,拥有数百年经书学习历史的朝鲜时代士大夫,只是不断重复朱熹的解释就能获得满足,其中只有尹鑴(1617—1680)、朴世堂(1629—1703)等数人对朱熹注释提倡异见,这是有说服力的解读吗?
朱子学研究的深化和异于朱熹注释的经书解释,两者皆由儒者们的信念所生。如果过去的儒学史研究所描绘的图式脱离了这种信念,就意味着它还有修正的余地。接着,若详细分析朱子学研究的过程及异于朱注之注释诞生过程,应当可以确认前述韩国儒学史对立图式的两个轴之间如何有所关联。
提出异于朱熹注释的见解而招来物议,最后被处罚,尹鑴和朴世堂常被举为代表例。一直以来,从尹鑴和朴世堂的著作及当时对于这两者的反应思想,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
第一,因为他们对朱子学提出异见,所以被攻击是“斯文乱贼”,然后被处罚。
第二,他们出于批判朱子学的意图,促成新的经书解释。
第三,他们的解释和大多数朱子学者的解释,相比之下是着眼点极为不同的东西。
从这些要素出发,“抱持对朱子学的批判意识,执笔新的经书解释,在严格的思想统治的栅栏中,对朱子学掀起反旗。从这件事开始,可以看出近代性意识的萌芽”这样的思想转换。
但是上述三个要素不一定与史实一致。首先,对于第一个要素,如前面所述,1960年代李丙焘的“呼唤学问的自由,希望脱离旧壳,他们进步且启蒙的态度和思想非常重要且优秀。……在极为严苛的党论中,提倡反对朱子学的异说,实为大胆,或者不能不称许他们这是出于学问良心的一种义愤”①,是代表性见解。但是如同后来研究所论证,对两人的处罚至少都由复数原因导致,他们争议性的著作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此论证已逐渐成为现在学界的通说。
1644年,尹鑴完成《中庸说》时28岁。而完成《大学古本别录》是1671年,他55岁的时候。这段时间当然不用说,如果这段时间之后,他所属的“南人”党派也执掌政权的话,他大概会继续保持在政界的地位并活跃着,也会出席宫中的经筵(文官对国王讲解经书的读书会)。1680年,他迈入64岁,不久后被贬,接着不久就被赐死。但是尹鑴被赐死后9年的1689年,“南人”又重掌政权,追封他为领议政。但是以朱子学为国是的朝鲜朝,为什么会追赠“斯文乱贼”尹鑴为领议政呢?导致被赐死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他是“斯文乱贼”,而是因为他在围绕国丧之礼的议论中和宋时烈(1607—1689)加深了对立。追封之事可以作为当时人也如此想的证据。
朴世堂的状况则是《四书思辨录》,主要在1680年代依序写成,其中特别造成物议的《大学思辨录》在1680年52岁时完成。①只是这本著作产生问题的时间是1702年(朴世堂74岁)。②他在这一年写了李景奭(1595—1671)的神道碑铭。李景奭是17世纪初期、中期,仁祖、孝宗、显宗三代,50年间活跃的名相。他在丙子胡乱(丙子战争)后,负责撰写清朝要求建立的三田渡碑的碑文。但由于碑文内容十分屈辱,受到宋时烈等人的谴责。李景奭死后,朴世堂在他的神道碑铭中,写了许多对宋时烈的批判,刺激了宋时烈门下众人。1703年,信奉宋时烈的儒生上疏批评神道铭碑和《思辨录》。攻击朴世堂侮辱朱熹,并藉此批判宋时烈。朴世堂的《年谱》记载,这些儒生认为只提神道铭碑恐怕很难使他被处罚,所以将《思辨录》一起取来攻击。因为这件事,朴世堂被剥夺官职,作为罪人,被放逐出城门外。那之后,流放的命令由于门人的辩护上疏而撤回,但是朴世堂在3个月后就去世了。
朴世堂去世后的1704年和1710年,他又再度遭受继承宋时烈的老论派的谴责。当时士大夫家以三年上食为礼俗。三年上食指的是临父母之丧,卒哭(指丧礼中没有定时的哭结束,此后只在朝夕的定时哭丧)之后的3年间,朝夕为亡者奉上“餐食”的礼仪。宋时烈留下的《戒子孙文》说,三年上食并非古礼,命子孙不要遵行。这件事情被视为问题。③又在建立十代祖尚衷碑石的肃宗八年(1682年),宋时烈想要使用清朝的年号康熙之事,也在他死后成为再次被攻击的标靶。因为此见解与宋时烈等人相反,后者在明朝灭亡后仍主张继续使用明朝年号崇祯。老论派位居权力中心时,和宋时烈对立的朴世堂所有发言,被不断重复视为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是“斯文乱贼”的印象逐渐被固定。①
接着分析第二个要素。尹鑴和朴世堂出于批判朱子学的意图而完成新的经书解释,如果把他们的著作和构成朱子学核心的理论或方法论拿来对照,分析比较后便能确认。例如他们是否反对朱子学的理气论,他们是否批判“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等方法。第三个要素,他们的解释和大多数朱子学者的解释,相比之下是否着眼点极为不同?
二、问题焦点
尹鑴和朴世堂完成新的注释后,都让师友看过。从后者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儒者如何看待与朱熹注释见解相异的著述。
尹鑴完成作为新批注的《读书记》后,曾拿给相同政治党派的前辈许穆(1595—1682)看。许穆读后,如下回复尹鑴:
蒙示读书记数篇,多发越动人。非吾希仲,安得有此说话。爱诵三复,胸次爽然。恨所欠者,其见太高,其言太易。高爽有余,而谦约不足;刚勇有余,而谨厚不足。②
许穆称赞尹鑴注释有感人的优秀内容,但是说的方式太轻率,谦虚严谨的态度不足是缺点。《读书记》在今日被视为反朱子学,其中含有异于朱熹注释之说。许穆既然反复读过《读书记》3次,应该知道其中异于朱子学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提到“不该改动朱熹注释”之类的话。他并未对研究经书得出新见解这件事有违和感。这么说来,如果尹鑴使用更加谨慎的态度下笔,或许就只会被许穆称赞,而不被指摘了。
朴世堂也将记载了异于朱熹见解的著作,拿给同属于西人党派的好友尹拯(1629—1714)看。尹拯给予他以下的忠告:
近观浦翁(赵翼)文字,其用功之笃,可谓至矣。而至于不免异同之处,辄曰不敢自是己见,唯以备一说云云。其致谨又如是。……诚见老兄用力之勤,而其枉费工夫处为可惜。且过于主张,而谓古人为错会者,无论言之得失,气象已不好,尤为可惜。①
对于强力推出自说并说先人见解有误的朴世堂的态度,尹拯感到违和,朴世堂的说法本身正确与否反倒未讨论。尹拯认为与先人见解相异时,应该要以赵翼的态度为模范。在经书钻研的过程中,的确会有不同的权威,提出自家说法的状况,此事本是不得已。但在那样的状况下,赵翼会保持谦逊的姿态,不说自己的看法正确,只说作为一种说法提出。也就是说,赵翼尽管得到应该获得好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会采取以自说为是、先人业绩为非的态度。
但是被称赞是对的态度的赵翼,尽管《朝鲜王朝实录(孝宗实录)》认可他“潜心性理之学”,却同时记载“其所著《书经浅说》《庸学困得》等书中,颇改朱子《章句》,人以此疵之”②。也就是说,赵翼也因为写了不同于朱熹见解的注释书,而被某些人非难。与此相对,拥护赵翼者是宋时烈。
对于批判赵翼的声音,宋时烈及其同宗兼政治同志的宋浚吉(1606—1672)说:“尹鑴凌侮朱子而自是己说,某爷有疑于心而求质于知者,迥然白黑之不同。”③他们藉比较尹鑴和赵翼的态度、意图,以拥护赵翼。如果《孝宗实录》所说属实,赵翼就是一边致力朱子学研究,一边撰写和朱熹不同的经书解释。宋时烈、宋浚吉拥护同一党派的学问前辈赵翼,他们不是用“赵翼未持有违背朱子的见解”的说法辩驳,反而承认他“持有怀疑”这件事,即赵翼提出和朱熹不同见解的这一点,未被视为问题。而且如同前面引用的尹拯书信,赵翼新注释的谦逊写法获得称赞。
因此,从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比起是否提出和朱子不同的见解,提出自说的意图和态度更重要”的想法。朝鲜时代的士大夫不问尹鑴、朴世堂主张之得失,仅以其心可议为理由批判他们。讽刺的是,进入21世纪后,同样也不问注释内容实际如何,尹鑴、朴世堂的注释因为勇敢地主张朱熹之说有误,反而被赞扬是带有近代性的知识分子。
之后,宋时烈被批评他不公平地拥护赵翼。听到批判自己的消息后,宋时烈写给赵翼之孙赵持恒以下的信曰:
比因人闻一种论议,则以为尤丈(宋时烈)于镌以改注《中庸》等事,斥绝之既严,至其党与,亦甚痛斥。以是辗转,致有今日之事。浦渚赵相(赵翼),亦于《大学》改注,至曰沉潜三十年,不知朱说之是,愚说之非也。其为说若是,则难免非责,而拒辟之事终不加焉。今于墓道文字,赞扬无余,则鑴之党与见斥者,其可服罪乎。或已撰出,则还推灭去,似无彼此取笑之资云云。……此文若出,必有一场纷纭,以增斯文之厄,不是小事也。再昨招宋炳夏商量,①又更审其祖考(宋浚吉)所撰行状。则记先老爷(赵翼)雅言,以为孔子之后集群儒而大成者朱子也,其功多于孟子云云。若于《大学》,果有如言者之说,则其雅言岂有如此之理耶?以故使炳夏搜送刊行文集,则归报以不得,极可叹也。②
从上面的文章可以看出关于赵翼的传闻,一个是说他写了和朱熹不同的注释,另一个是他曾说过“不知朱说之是,愚说之非也”。然而宋时烈最在意的,不是赵翼的注释是否与朱熹之说相背,而是他是否说过轻视朱熹的言论。
从以上的例子来看,赵翼、尹鑴、朴世堂的注释,皆被同党派的同伴认为有学术价值。但是根据是否无视朱子学说的权威,态度上是否以自说为是,从同伴获得的评价有所差异。也就是说,欲破坏朱子学权威的不逊态度会被责备,但是提出与朱熹不同解释这件事本身,未被直接排斥。
这种想法并未随着时间变化。朝鲜时代后期的文臣徐滢修③(1749—1824)也说,能够认可对朱熹之说提出异见,但是直接指责朱熹有错的方法必须批判:
虽以朱子之步步趋趋于程子,如《易》《诗》《语》《孟》,未尝尽遵程说。《大学》《中庸》,宗程尤笃,而订正尤多。……朱子诚不能无误矣。……昔陈大章④熟《通鉴》,检得疏谬处,做一辨驳文字,以示其友。其友曰:不消如此,只注其下,云应作如何足矣。宇宙间几部大书,譬如父祖遗训,万一偶误,只好说我当日记得如此。若侃侃辨证,便非立言之体。《通鉴》尚然,况经传笺注乎。⑤
徐滢修以朱熹对程子态度作为自己议论的依据,他区分以程子学说为优先,和全盘接受程子学说两件事之别。朱熹比什么都尊重程子之说,但是解释经书时并不只限于跟随程说。例如对朱熹思想体系来说,最重要的《大学》《中庸》解释,一边宗于程子之说,一边在许多地方有所修正。徐滢修基于朱熹的做法,认为既然朱熹之说也有需要订正的地方,那么它的订正工作便是正当的。但是强调朱熹的错误,以强行主张自说是不行的。换言之,不是“不能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而是“不能抱持强调朱子之误以提出自说的意图和态度”。
三、“改朱子之注”
对于一本新的著作,作者的师友所关心的,不是其观点是否与朱子相同,而是写作态度。但是就像赵翼被非难大改《章句》一样,以改朱子之注的名目遭受政治攻击的事情时常发生。那么,对于这种攻击的反驳内容为何?还有这些作者真的改了朱熹的注吗?
赵翼写了《大学》注释的《大学困得》,其“诚意章”认为朱熹的注释并未正确解释经文,提出了新的解释。在朱子学中,当把《大学》的内容以知与行归纳的时候,“诚意”作为进入行的第一步,是被重视的条目。因为“欲为这事,是意”①,如果在意识萌芽的时候为善去恶,实践也如意识一般能够达成。对于《大学》的“诚意”,朱熹的想法大致从两处注释可以看出。首先是朱熹《大学章句》的经一章的注释②,写道:“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③接着,对于《大学》诚意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传六章做以下解说:
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①
朱熹将“诚意”解释为自我修养的第一阶段。对于《大学》中用来说明“诚意”的“毋自欺”等句,朱熹的理解是,如厌恶恶臭、爱好美色一样,致力为善去恶。而“自谦”的解释则是,应该为了使自己快足而努力,不要以外部标准为标准,为了做给别人看而努力。
对于朱熹的注释,赵翼的问题意识是,在“诚意”这样的自我修养中,“毋自欺”和“自谦”具体而言是何种行为?如同前述,朱熹将“毋自欺”和“自谦”都解释成诚意的修养方法。要言之,努力不要对自己的念头有所欺瞒是“毋自欺”,为了使自己能感到满意而努力是“自谦”。最后作结于努力勿为他人评价而非自我意识为标准的“为人之学”。
对此,赵翼认为《大学》所言诚意的修养方法只有“毋自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即“自谦”)指的是由修养所得到的效果。②从赵翼的想法来看,此章应该这样解释:如果善加修养诚意,便能达到自足的状态。“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非如朱熹所说是修养的方法,“毋自欺”也不是朱熹解释的“不要为了让别人看而做”。所以《大学》传文的内容是按照“毋自欺(努力)”到“自谦(效果)”的顺序排列。朱熹因为先解释自谦,所以依此读出勿自欺的意义。但若如此解释,便和传文的顺序对不上,赵翼的说明如下:
(朱子)章句谓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以如好如恶为实用其力之事,以徇外为人为自欺之事。使以如恶如好为在先事,以毋自欺为在后事,以传文先后易置之。此窃恐其未必合于传文本旨也。③
之后,赵翼又作了两篇文章:《后说中》(1638年7月)、《后说下》(1653年2月),将自己无法免于提出异于朱熹见解的经过做详细说明。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从朱熹书信中找出可以为己说做旁证的文句,认为《章句》的注只是朱熹的一时见解,定论应该如这些信件所言。他主张自己的见解虽然和《章句》多少有所不同,但是并未改变朱熹的定论。赵翼罗列以朱熹《答张敬夫书》为首的十五通书信,加上《心经附注》和《书杨龟山话后》共17篇文章中关于“自欺”的文句,就何者为朱熹的定论,论述如下:
由是观之,则朱子平生所说自欺之语,皆是谓欺其心也,未见其以为人为自欺也。唯独于《大学章句》,以徇外为人释之,及小注一两条谓为为人耳,其言不同如此。且谓为欺心,其平生所说皆然,谓为为人独见,此三两处耳。然则窃恐此所释,乃朱子偶然一时所见,非其平生定论也。后之读者,徒见《章句》所释如此,而不考朱子他时所言,便谓朱子之旨只如此,《大学》本旨只如此。则窃恐其不得为深究朱子之旨者也。区区妄说,虽于《章句》之言有不同,其于朱子平生所言之意,则实吻合。然则谓其异于《章句》则可,谓其异于朱子之旨,则实不然也。①
赵翼主张自己的见解尽管可以说异于《章句》,但实际上并未背离朱熹本旨。即他不否认改了朱熹的注这一点,但是强调自己正因为尊重朱子学所以改了注,采取“透过改注使朱子学本来的想法更加明确”的姿态。他将自己的新解释合并在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中,在相信能使该体系更加完备的状况下,提出上述说明。从赵翼的文集可以知道,上述主张不是他在腹中批判朱子学之非,却因为害怕他人目光所以做出的辩解。
虽然如此,因为改朱熹之注的理由,著作被焚书处分的情况不是没有。那么,受到焚书等严厉处分的作者,是如何证明自身著作之清白的呢?让我们以崔锡鼎(1646—1715)的《礼记类编》(以下称为《类编》)为例。
《类编》完成于1693年,在1700年和1707年刊行。刊行后,皇帝广赐诸臣,因此读过的人非常多。此书如书名所示,将《礼记》经文从原本的顺序,重新分类进行编辑,各项类别按照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建立。例如设“家礼”的篇目,其中收纳《曲礼》《少仪》《内则》篇;在“邦国礼”的篇目下,收纳《王制》《月令》《玉藻》篇。将《大学》《中庸》放回《礼记》,以“学礼”的篇目收纳,并视《孝经》为原本属于《礼记》的一部分,将其编入《类编》中。1700年11月的初刊本形式是,先在各卷开头记上简略说明,收录分类编辑的经文,然后在各卷末尾加上附注。②1707年再刊时,将《礼记》经文如同《四书大全》般,按照段落分记,在各段落下方附上南宋陈澔(1260—1341)的《礼记集说》的解说,其下又加上崔锡鼎自己的“附注”。《礼记集说》在《大学》《中庸》的部分未附注释,只记上“朱子章句”四字而已。而崔锡鼎则在《大学》《中庸》部分载录朱熹《章句》的注释,并和其他章一样,加上自己的“附注”①。
崔锡鼎在序文中提及《类编》的编纂理由及主要方针,要约如下:自秦焚书以来,六经失散,礼乐相关的书物损失尤重。朱熹就《易经》撰写《周易本义》,《诗经》撰写《诗集传》。至于《书经》,则使弟子蔡沈执笔《书集传》;于礼则以《仪礼》为中心,加上其他经书、史书、诸子百家之文,著成《仪礼经传通解》以传世。《仪礼经传通解》从诸多书物,大量引用各式各样的文章,重复处不少,且不属于特定的经。在这样的状况下,内容之庞大,使学习者难得要领。《礼记》虽本是汉儒收集关于礼乐的片段记载并编成的书,但是因为它包含古代圣人言礼之文,从永乐年间(1403—1424)以来就位列五经,不容忽视。只是以朱熹为首的先儒认为《礼记》由汉儒搜集编辑而成,对其文献内容多有怀疑。尽管朱熹有所怀疑,却未曾进行《礼记》的校勘。因此,关于文本的问题很多,笺注者尽管时被怀疑,至今却没有人辟清这些问题,长久以来,学习者皆为此苦恼。崔锡鼎深刻认识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性,于是立志删定,多次来回修改,终于完成此书。②
至于编辑方针,崔锡鼎根据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建立数个项目,将《礼记》篇章分类,放在每个项目底下。此书取名为《类编》的理由则是,朱熹曾惋惜唐代魏征所作《类礼》未能传世,因此崔锡鼎同样怀着希望《类礼》能有所流传的心情,将本书命名为《类编》。③
从上述序文可知,崔锡鼎编纂《类编》的目的如下:
第一,重整散乱的经书。
第二,继承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意志。
崔锡鼎充分理解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旨趣,并担负起这项尽管必须进行却未被进行的工作。即对他而言,《礼记类编》的编纂是自认为继承朱熹之道的表现。
崔锡鼎于1700年(肃宗二十六年,55岁)向肃宗建议进讲《春秋》和《礼记》,且《礼记》讲学使用自撰《礼记类编》,获得许可。①该年11月,王命校书馆刊行《礼记类编》。②然而此书刊行数年后,被视为“求异乎朱子”的著作,开始受到攻击。
宋时烈门人郑澔(1648—1736)写信给同门的权尚夏(1641—1721),劝他批判崔锡鼎的《礼记类编》以正世道。③权尚夏没有响应此事,但是之后,权尚夏的弟子尹凤九以尹瀗等年轻读书人提出公论的形式,写了代理上疏文。④尹瀗等人上疏的内幕,其实由宋时烈门下的运作所导致。上疏中他们要求毁去《礼记类编》的版刻,并撤回朝廷进讲之命。⑤
崔锡鼎次次上书,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举出先儒李彦迪(1491—1553)和赵翼等人的著作,说他们也曾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⑥他指出李彦迪及宋时烈等人拥护的赵翼都没有完全根据朱熹解释,控诉说自己的著作和两人一样,非“求异乎朱子”。
真正切断攻防保险丝的是,1709年1月同副承旨李观命(1661—1733)的上疏,内容如下:
今伏闻有以《礼记类编》,刊进于中宸,将欲参讲于法筵。臣取考其说,则求异乎朱子者,固不可毛举。而至若《庸》《学》,朱子自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微辞奥旨,阐明无憾,则此岂后人所可容议者。而《大学》第四章,揽而合之于第三章,而统之曰,右释止于至善,而去其释本末一章。《中庸》第二十八九章之正文,割截句语,釽裂数行,移东而入西,缴下而就上。至于“费隐”一章,义理最深,章句所解,至矣尽矣。而今其附注二条,显有所信本旨底意。且程子之表出《庸》《学》,意非偶然。而今此《类编》为名,不过分类便览之书。则其为体段,亦非经书之比,乃复还编《庸》《学》于其中,使先贤表章之本意,暗昧而不明。……既命刊行,又将参讲,则四方闻之,必以轻信异言,妄疑于殿下,诚非细故也。古人有言:“经文一字之误,流血千里。”①
李观命说崔锡鼎“求异乎朱子者,固不可毛举”,客观来看真的能说服人吗?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他主张的第一个问题——合并《大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为一章。崔锡鼎按照朱熹《大学章句》顺序记录经文,同时也记上朱熹的注。也就是他并未将朱熹分成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两章合并,也未主张以上是第三章。所以“将《大学》第四章并入第三章”的李观命指控并不成立。
那么为何李观命有此批判?那是因为朱熹在第三章末写有“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在第四章末写有“右传之四章,释本末”。崔锡鼎则将朱熹的“释止于至善”一句移到第四章末。由于这个部分没有其他说明,只是抄录朱熹原文而已。崔锡鼎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清楚,但是可以推测,崔锡鼎可能认为第三章的说明是一直延续到第四章的。如果是这样,便能解释为什么朱熹标记第三章关于“止于至善”,第四章关于“本末”,但是崔锡鼎却把第三、四章共同当作关于“止于至善”的文句解释。也因为如此,李观命批判他将第四章并入第三章。
然而,若看后面的第五章,崔锡鼎虽然把朱熹的格物补传(第五章)用比《大学》本文低一格的形式抄录,仍一句一句附上附注,也就是结构上将其视为经文对待,且附上“以上朱子补亡,所谓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者也”的附注,将朱熹所作的补亡文章明确地升格成第五章的格物传。崔锡鼎同意“《大学》是体现学习者修学顺序之书”的朱熹想法①,基于此,他以充实八条目的形式增添解释。又他移动了《礼记》诸篇的经文以进行编辑,但是对于《大学》《中庸》两章,却都是直接抄录章句内容,没有变动。
再让我们看李观命主张的第二个问题,即崔锡鼎割裂、移动《中庸》第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的内容。据《中庸章句》,第二十八章为“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一见可知,此章中“子曰”有两处。然后第二十九章没有“子曰”,直接从“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开始。一般而言,“子曰”放在章首较为自然。因此,一章内有两个“子曰”的第二十八章及没有“子曰”的第二十九章,无疑需要注释者的说明。
对此,朱熹《中庸章句》认为第二十八章的结构,第一个“子曰”孔子之言的引用,接着是子思的评论,而第二个的“子曰”是再次引用孔子之言。崔锡鼎则视第二个“子曰”为次章(第二十九章)的开始,又说原本二十九章开头的“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一句,“王天下有三重焉”应该要移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之前,而“其寡过矣乎”则留在原处,接续“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的句子。他引用《章句》收录的吕大临注“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表示移动上述七字的想法不是自己恣意妄为。也就是崔锡鼎的行为,不是“因为朱子之注有误,所以改动它”,而是从《章句》的注获得根据,使其更加精细的结果。
从吕氏注释如何得出与朱熹《章句》不同的结果?以下试着类推:《中庸》第二十八章的正文有两个“子曰”,同时,接续的第二十九章开头没有“子曰”。承此,当然需要说明。朱熹《章句》并未变更章的分隔,但是在第二十九章的注释却用了吕氏之注,吕注表示第二十九章的“三重”指的是第二十八章的“议礼、制度、考文”。崔锡鼎以此为根据,与吕氏注之趣旨呼应,将二十九章的“三重”部分,移到第二十八章的“议礼、制度、考文”之前。尽管这与朱熹的分章相异,却不一定背离朱熹的意思。因为朱熹自己虽然赞同吕氏注,却没有移动正文。因此可以解释为,崔锡鼎读取此意后,将其实行。这是朱熹如果还在世或许也会进行的工作。
李观命主张的第三个问题又是如何?附在《中庸》“费隐”章的两条崔锡鼎“附注”,明显意图主张自己认为的“费隐”章宗旨,并非朱熹宗旨吗?“费隐”章从“君子之道费而隐”开始,即“君子之道谁都知道、谁都可以做,同时却有圣人也做不到的地方”这样的内容。此章的崔锡鼎“附注”被批判的句子是“见《经说》①及《辑略》②,似与《章句》所解有异”③。还有一个是对《章句》引用的侯诗圣(河东侯氏,程颐弟子)注的批判。前者指的是在《河南程氏经说》和《中庸辑略》中,程氏从“常道”(《河南程氏经说》)和“日用”(《中庸辑略》)的角度解释“费”字,但是《中庸章句》以“范围之广”解释,所以程子和朱子的解释并不一致。此外,崔锡鼎“附注”被批判的第二处,指称朱熹《中庸章句》引用的河东侯氏的说法不当。崔锡鼎在此使用的方法是从《朱子语类》直接引用与侯说相反的内容,最后再加上“此一条见朱子语类”一句结尾。也就是他不是以自说对朱熹《章句》提倡异见,而是使用朱熹的话语(即《朱子语类》),对朱熹的解释提出异议。因此,崔锡鼎的注释虽然改了朱熹之注,但因为提出朱熹的文句作为根据,无法确定他是否“求异乎朱子”。
李观命主张的第四个问题是将《大学》《中庸》放回《礼记》的做法,违反了先贤将此两篇提出作为独立书籍的本意。的确,《礼记类编》将朱子学中俨然成为四书之两轴的《大学》、《中庸》放回《礼记》,并以“学礼”的篇目收纳,又说《孝经》实际上是戴记的一篇而将其编入《礼记类编》。但是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也在“学礼”的项目收入《大学》《中庸》,《礼记类编》只是根据它的编排。崔锡鼎后来的上疏文实际上也如此反驳。再者,关于编入《孝经》之事。考虑到朱熹屡说“《孝经》是后人缀缉”“据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④等言,我们也无法确定崔锡鼎是否就因此“求异乎朱子”。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虽然崔锡鼎的“附注”与《章句》的朱熹注有时见解不同,但是无法说是“求异乎朱子”,即从客观立场来看,实在很难同意李观命的批判。实际上,对于李观命的上疏,肃宗直接批示:“至于新刊《礼记类编》,予已翻阅矣。此岂可与《思辨录》,比而论之乎?其所为言,用意至深。噫!《类编》序文中有曰,其规模义例,悉仿朱子《通解》,而一言一句,不敢妄有所删削。”①将上疏驳回。肃宗应是在全部确认过李观命主张的基础上,将批判之声驳回。只是肃宗重视的是“仿效朱子”的作者意思,各个注释实际上是否异于朱熹,这件事本身并未被当成问题。
崔锡鼎呈上疏文,逐一反驳李观命的批评。他举例反驳,先儒李彦迪也曾著书改订朱熹《大学章句》,李珥(1536—1584)却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因为两人都笃信朱子。接着又仔细说明,《礼记类编》的样式是根据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而来,其他的编辑方针也全依据朱熹说过的话。②但是环绕着《礼记类编》的议论仍日益扩大,不仅官僚争相上疏,③连成均馆和四学④的儒生都集体上疏,骚动无法平息。⑤结果,最后如同李观命上疏文的要求,已经发出的《礼记类编》被回收焚烧,毁去此书之版本的要求也被许可,执行的命令下达后才终于完结此事。⑥
《礼记类编》被焚烧处分的真正理由,先行研究已经论证。这是老论派出于政治目的,要攻击被肃宗所信任的崔锡鼎,所以才利用《礼记类编》⑦。那么《礼记类编》是否真的改了朱子的注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改了”。但是作者崔锡鼎并不认为“改了”这件事本身是问题,因为他确信自己的学问皆以朱熹的文句为基础。他的周遭也有抱持同样认识的人,就见解异于朱熹这一点批判他的人,只有出于政治目的批判他的一派而已。
四、异见提出者的自我认同
那么改朱熹之注者或未持政治目的的儒者的问题关心,其中是否有包含对朱子学的问题意识?如果他们对朱子学持有批判意识,并基于此想改动朱熹的经书解释,他们的自我认同便可以说是“朱子学批判者”。他们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时,自我认识为何?
赵翼被非难“大改朱子《章句》”,因为有宋时烈的庇护,尽管受到对立党派批判也得免于祸,但是赵翼果真可以说是以超越朱子学的新思想为目标吗?而且提出异于朱熹的注释是此目标的一环?
赵翼任职直提学的1624年(仁祖二年),向仁祖献上《大学困得》《论语浅说》。①1646年(仁祖二十四年)献上改订版的《大学困得》,以备为世子(后之孝宗)讲学,同时他也建议仁祖一读。②孝宗即位之年,再度奉上《大学困得》《论语浅说》之际,举出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异于朱熹解释的《大学》诚意章的注,说明自己对这一章的解说,是藉由平生思索所得到的结果。③在朱子学作为官学的背景下,如果《大学困得》以批判朱子为目的执笔,那么赵翼可以像这样,自负于书中改动朱熹注释的诚意章,认为是自己平生思索的结果吗?况且还可以这么积极地劝国王一读吗?这么说,赵翼本人应该只视这部“大改朱子《章句》”的著作为经书研究的成果,不带有朱子学批判的问题关心。
被说是改了朱熹的注,著作被烧毁的崔锡鼎又是如何?他曾对朱子学持有怀疑吗?崔锡鼎曾经写信给因为信奉阳明学而被批判的好友郑齐斗(1649—1736),书信内容如下:
士仰(郑齐斗的字)足下,顷年因士友闲,得闻足下主阳明之学,于心窃惑焉。昨岁拜玄石丈(朴世采)坡山,玄丈忧足下之迷溺于异学而不知返。……夫天下之理一也,苟理之所在,则固未可以人而轻重。然古人论学之旨,莫要于《大学》,而朱子训义,至明且备。阳明子乃斥以支离决裂,出新义于程朱之表,而其言语文字,具载遗集及《传习录》中。其论说之偏正,学术之醇疵,诚有可得而言者。则足下之信而好之如此者,无乃信其不当信而好其不当好也耶。仆年十三,读《大学》及《或问》,厥后盖尝屡读而精研矣。中闲见张溪谷(张维,1587—1638)文字,赞叹阳明之学,不一而足。于是遂求阳明文集、语录而读之。乍看诚有起诣新奇可以惊人处,既而反复而读之,博极而求之,则徒见其辞语妙畅,文章辨博,而学问蹊径,率皆颠倒眩乱。非但背驰于朱子,将与孔曾相传之旨,一南一北。有不容于无辨者,遂妄者辨学一说,思欲与同志者讲确而未能也。①
这封信写于1692年,也是可以窥探崔锡鼎快完成《礼记类编》时想法的材料。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改动朱熹的注,撰写《礼记类编》时,是一位坚定相信朱子学道理的朱子学者。换言之,崔锡鼎正因为是位比什么都尊重朱熹经书解释本意的朱子学者,所以才改动朱熹的注。
这位经书解释与朱熹相异,被批评改朱注者,不仅未持有反朱子学的意图,甚至还表现出对朱子学道理的确信。承此,实在很难同意“他期望克服朱子学,所以改朱熹之注”的说法。
连带来看,当崔锡鼎《礼记类编》因为改朱注而引起全国性的议论时,不属于出于政治目的攻击他的群体的人,对于《礼记类编》是否背离朱子学这个问题抱有兴趣吗?
这个“事件”发生之际,和崔锡鼎同属少论的尹拯这么说道:“崔相(崔锡鼎)虽以晦(李彦迪)、栗(李珥)两先生自解,而既不免异于朱子。则砭者之锋,安能免也。只当安受而已,不必较也。”②
如同前述,崔锡鼎举李彦迪改朱熹《大学章句》却受到李珥高度评价为例,诉说自己著作的正当性。但是尹拯认为崔锡鼎没有必要那样反驳,就此承认攻击者的言论就好。因为崔锡鼎著作包含异于朱熹的见解是事实,对方以事实为理由攻击,回避不了。从尹拯的话,看不出持有异于朱熹的见解或表现该种见解本身很严重的想法。
此外,不是所有宋时烈门下的人都参加了追讨崔锡鼎的活动。权尚夏从同门的郑澔处收到两封劝他攻击崔锡鼎《礼记类编》的书信,仍没有动作,就算被宋时烈门下的人大加责备,直到最后也未曾涉足。①
《礼记类编》尽管受焚毁的处分,但刊行本早已分送到南边的全罗道、庆尚道等地域,在儒者社会中流传,被广泛地阅读。②其中有一部分被藏在家里,免于焚毁,之后为《礼记》研究者屡屡引用。焚书数十年后,成海应(1760—1839)以“崔氏锡鼎《礼记类编·深衣篇》附注曰”的形式引用了崔锡鼎的“附注”。③成海应研究《礼记》深衣篇之际,从汉代郑玄注、唐代孔颖达疏到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引用说法,不但网罗中国之说,同时还加上崔锡鼎的“附注”,作为《礼记》的先行研究参考。
另外,政治党派从属少论的崔锡鼎所著《礼记类编》受到严重处分,对此,从属南人的李万敷(1664—1732)如下说道:
其书苟有不是处,则为崔相之友者论辩之可也,本不关朝廷之是非。老论以此为击去崔相把柄,岂非党论所使乎?④
乍看之下,李万敷似乎是从南人的政治立场,批判老论的朱子学原理主义。李万敷15岁的时候,因为父亲李沃(1641—1698)被处以流放之刑,他很早就不得不放弃官场之路。导致流放的直接原因没有其他,就是因为李沃曾主张对老论领袖宋时烈处以极刑。⑤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父亲,李万敷才特别嫌恶老论及其朱子学原理主义。但是只从这一点说明上面引文并不充分。
李万敷和曹夏畴、李淑、李潜等好友时常进行学术讨论。让我们看一下记录其讨论的“中原讲义”。①曹夏畴批评朱熹的《大学》注释“杂乱烦琐”,主张“宋季学者,趋末无实,岂非朱子启之乎”。李万敷回道:“此乃后人自流之弊,岂朱子所启也?”并且他在结尾处断言道:“澄叔(李淑的字)尝言,曹兄有思而不学之病。以此数说观之,其病不但止于不学而已也。”又李万敷在其他文章提到曹夏畴时,说:“君叙公以弟为中毒于程朱,程朱之道,大中至正,本无毒可中人。然如果为所中,岂不幸甚。”②
从两人的讨论中至少能看出,他们一人严厉批判朱熹经学解释带来的弊害,另一人坚定地相信朱子学的正确。如果以过去韩国儒学史上的对立图式来区分,上记曹夏畴是嫌恶与老论派绑在一起的朱子学派,所以进行朱子学批判的一边,而李万敷则会是朱子学派那一边。但是如此一来,批判围剿崔锡鼎的老论派李万敷,和积极维护朱子学、被视为程朱学中毒的李万敷,很难说是同一个人。
五、结语
以上讨论显示,17世纪被说改了朱子之注的经书解释,至少在著述之际,看不出这些作者持有对朱子学的怀疑与批判意识。又对于持有和朱子学不同学说者未严格看待的人,却对不认同朱子学贡献的好友发言做严厉的批判。这么看来,分为拥护朱子学侧和批判朱子学侧,如此说明韩国儒学史有其困难。
那么冒着得到改朱注之“罪”的风险,撰写异于朱熹见解的经书注释的人,实际上是抱持什么想法呢?接着,他们不仅把著作给亲友过目,甚至献给国王,是为了什么?
这恐怕出自于“作为道统继承者必须完成此任务”的认识。当时在东亚普遍的想法是自称中华的根据来自圣人的存在,继承作为圣人文言的经书,正是中华道统后继者的责任。如果是道统的后继者,不会任经书处于散乱不明的状态。对于继承朱子学式道统的朝鲜时代的儒者,中华继承的实质就是担负起朱熹在未完状态遗留下来的责任,确定经书意涵和整理经书。但不是谁都可以继承朱熹、肩负这样的任务。如果做得不好,会被人说是“侮辱朱子”“改朱子之注”,甚至是“斯文乱贼”等,提供攻击材料给政治对手。只要是士大夫社会的成员不认可“你是朱子的后继者,拥有进行朱子学后续工作的资格”,或是自己无法强力主张“我是朱子的后继者,拥有进行朱子学后续工作的资格”,自任承继朱熹之迹者,就有可能如上述般被问罪。接着,他们还不能不证明自己的创见能够使朱子学体系更加完备。朝鲜时代的儒者正因为怀抱着这样的抱负,才冒着政治上的危险也要完成朱熹未完的工作,同时也为了确认自己是道统的嫡流,努力想完成该责任。
本文认为这种意义赋予20世纪前后的知识人直面国家、民族的危机时,想要从儒学史中找出“近代”思想之萌芽的情况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过程里,他们从17世纪儒者的著作中,导出时人认为有思想——即朱子学——没办法克服现今危险这样的见解。然而尽管20世纪的知识人确实怀抱这样的问题意识,17世纪的儒者是否真的也与他们相同呢?本文对此想要重新确认。
为了确认这件事,有必要考虑17世纪的社会环境让儒者究竟是对朱子学开始抱持怀疑,还是怀抱着更强的使命感去面对朱子学研究?首先有别于朱熹之经书解释的新解释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还有给予注释的作者提出新学说的整个过程究竟是什么样貌?而当时的社会又是如何理解这样的事呢?本文将分析其周遭同辈及政敌的反应,可以得到他们如何认知这件事的某些提示。他们是所谓那些朝着具有权威的思想体系发起挑战的人吗?而这些新学说的提出者,自己是否又以朱子学的批判者自居呢?
儒者生存的年代与20世纪前后的知识人所直面的东亚情势相差甚远,职是之故,从西洋式殖民模式里探求救国方法的近代知识人,与怀抱着以中国为中心之天下意识的朝鲜时代儒者,或以“国”,或以“天下”所确立之志向,自然不会得出同样的东西。然而殖民地时代的韩国知识人在赋予儒者之事业以意义时,或许却忘了朝鲜时代儒者生存的现实环境,以及他们的生存之道。
殖民时代的韩国知识人,以取回作为近代国民国家的韩国之主权为其第一要务。有着这样现实需求的他们,没有足够从容去踏实地思考、去站在过往朝鲜时代儒者的视角省视其穷尽一生所追求为何物?而韩国儒学史整体又有何内涵,在20世纪后半出生的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当时的知识人所背负的使命感之重量。尽管本文是探讨韩国儒学史并试图修正其在后来定位的,但也希望学习当时知识人的志向,于21世纪的学术界中被赋予部分使命。
一、新的经书解释之出现
虽然朝鲜时代以朱子学为国是,以朱子学的经书解释为科举考试基准,但也存在提出与朱熹注释相异见解的人,他们有不少人因为招来物议,最终被处罚。这些著作异于朱熹注释者的登场及对于他们的牵制或批判的记录,从来都被理解成持有朱子学批判意识的一侧,被朱子学侧弹压的状况。“朱子学侧与反朱子学侧的对立图式”如此被确立。在那样的图式中,17世纪的儒学史从两个对立的轴被说明——朱子学的深化研究和教条化,对立对朱子学的怀疑和批判。但是本文指出,17世纪的儒学史应该是在超越这两个对立轴的地平面上所展开的。
一般而言,对于某个对象的研究若到了极为细密的阶段,会产生视野的窄化,或是动则被固定观念所局限,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在研究之际注意到该思想体系的缺点,将此研究对象客观化,开始能够批判性地认识它,这样的可能性也变得越高。就算是看起来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如果彻底去追究,它也很有可能从自身浮现破绽。如同后述,17世纪韩国的朱子学者一边比对朱熹的各种著述,一边研究朱子学,认识到朱熹的学说经历数度变化,更进一步确认在朱熹的复数言说之间,存在不少矛盾。
承上所述,朝鲜时代儒者的研究可能无法断定,绝不可能成为原动力,产生异于朱熹注释的创见,也无法单单认为这些研究只有迈向朱子学教条化一途。无批判地信奉,是因对作为对象的知识还未彻底研究的状况下才容易产生。接着,拥有数百年经书学习历史的朝鲜时代士大夫,只是不断重复朱熹的解释就能获得满足,其中只有尹鑴(1617—1680)、朴世堂(1629—1703)等数人对朱熹注释提倡异见,这是有说服力的解读吗?
朱子学研究的深化和异于朱熹注释的经书解释,两者皆由儒者们的信念所生。如果过去的儒学史研究所描绘的图式脱离了这种信念,就意味着它还有修正的余地。接着,若详细分析朱子学研究的过程及异于朱注之注释诞生过程,应当可以确认前述韩国儒学史对立图式的两个轴之间如何有所关联。
提出异于朱熹注释的见解而招来物议,最后被处罚,尹鑴和朴世堂常被举为代表例。一直以来,从尹鑴和朴世堂的著作及当时对于这两者的反应思想,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
第一,因为他们对朱子学提出异见,所以被攻击是“斯文乱贼”,然后被处罚。
第二,他们出于批判朱子学的意图,促成新的经书解释。
第三,他们的解释和大多数朱子学者的解释,相比之下是着眼点极为不同的东西。
从这些要素出发,“抱持对朱子学的批判意识,执笔新的经书解释,在严格的思想统治的栅栏中,对朱子学掀起反旗。从这件事开始,可以看出近代性意识的萌芽”这样的思想转换。
但是上述三个要素不一定与史实一致。首先,对于第一个要素,如前面所述,1960年代李丙焘的“呼唤学问的自由,希望脱离旧壳,他们进步且启蒙的态度和思想非常重要且优秀。……在极为严苛的党论中,提倡反对朱子学的异说,实为大胆,或者不能不称许他们这是出于学问良心的一种义愤”①,是代表性见解。但是如同后来研究所论证,对两人的处罚至少都由复数原因导致,他们争议性的著作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此论证已逐渐成为现在学界的通说。
1644年,尹鑴完成《中庸说》时28岁。而完成《大学古本别录》是1671年,他55岁的时候。这段时间当然不用说,如果这段时间之后,他所属的“南人”党派也执掌政权的话,他大概会继续保持在政界的地位并活跃着,也会出席宫中的经筵(文官对国王讲解经书的读书会)。1680年,他迈入64岁,不久后被贬,接着不久就被赐死。但是尹鑴被赐死后9年的1689年,“南人”又重掌政权,追封他为领议政。但是以朱子学为国是的朝鲜朝,为什么会追赠“斯文乱贼”尹鑴为领议政呢?导致被赐死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他是“斯文乱贼”,而是因为他在围绕国丧之礼的议论中和宋时烈(1607—1689)加深了对立。追封之事可以作为当时人也如此想的证据。
朴世堂的状况则是《四书思辨录》,主要在1680年代依序写成,其中特别造成物议的《大学思辨录》在1680年52岁时完成。①只是这本著作产生问题的时间是1702年(朴世堂74岁)。②他在这一年写了李景奭(1595—1671)的神道碑铭。李景奭是17世纪初期、中期,仁祖、孝宗、显宗三代,50年间活跃的名相。他在丙子胡乱(丙子战争)后,负责撰写清朝要求建立的三田渡碑的碑文。但由于碑文内容十分屈辱,受到宋时烈等人的谴责。李景奭死后,朴世堂在他的神道碑铭中,写了许多对宋时烈的批判,刺激了宋时烈门下众人。1703年,信奉宋时烈的儒生上疏批评神道铭碑和《思辨录》。攻击朴世堂侮辱朱熹,并藉此批判宋时烈。朴世堂的《年谱》记载,这些儒生认为只提神道铭碑恐怕很难使他被处罚,所以将《思辨录》一起取来攻击。因为这件事,朴世堂被剥夺官职,作为罪人,被放逐出城门外。那之后,流放的命令由于门人的辩护上疏而撤回,但是朴世堂在3个月后就去世了。
朴世堂去世后的1704年和1710年,他又再度遭受继承宋时烈的老论派的谴责。当时士大夫家以三年上食为礼俗。三年上食指的是临父母之丧,卒哭(指丧礼中没有定时的哭结束,此后只在朝夕的定时哭丧)之后的3年间,朝夕为亡者奉上“餐食”的礼仪。宋时烈留下的《戒子孙文》说,三年上食并非古礼,命子孙不要遵行。这件事情被视为问题。③又在建立十代祖尚衷碑石的肃宗八年(1682年),宋时烈想要使用清朝的年号康熙之事,也在他死后成为再次被攻击的标靶。因为此见解与宋时烈等人相反,后者在明朝灭亡后仍主张继续使用明朝年号崇祯。老论派位居权力中心时,和宋时烈对立的朴世堂所有发言,被不断重复视为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是“斯文乱贼”的印象逐渐被固定。①
接着分析第二个要素。尹鑴和朴世堂出于批判朱子学的意图而完成新的经书解释,如果把他们的著作和构成朱子学核心的理论或方法论拿来对照,分析比较后便能确认。例如他们是否反对朱子学的理气论,他们是否批判“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等方法。第三个要素,他们的解释和大多数朱子学者的解释,相比之下是否着眼点极为不同?
二、问题焦点
尹鑴和朴世堂完成新的注释后,都让师友看过。从后者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儒者如何看待与朱熹注释见解相异的著述。
尹鑴完成作为新批注的《读书记》后,曾拿给相同政治党派的前辈许穆(1595—1682)看。许穆读后,如下回复尹鑴:
蒙示读书记数篇,多发越动人。非吾希仲,安得有此说话。爱诵三复,胸次爽然。恨所欠者,其见太高,其言太易。高爽有余,而谦约不足;刚勇有余,而谨厚不足。②
许穆称赞尹鑴注释有感人的优秀内容,但是说的方式太轻率,谦虚严谨的态度不足是缺点。《读书记》在今日被视为反朱子学,其中含有异于朱熹注释之说。许穆既然反复读过《读书记》3次,应该知道其中异于朱子学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提到“不该改动朱熹注释”之类的话。他并未对研究经书得出新见解这件事有违和感。这么说来,如果尹鑴使用更加谨慎的态度下笔,或许就只会被许穆称赞,而不被指摘了。
朴世堂也将记载了异于朱熹见解的著作,拿给同属于西人党派的好友尹拯(1629—1714)看。尹拯给予他以下的忠告:
近观浦翁(赵翼)文字,其用功之笃,可谓至矣。而至于不免异同之处,辄曰不敢自是己见,唯以备一说云云。其致谨又如是。……诚见老兄用力之勤,而其枉费工夫处为可惜。且过于主张,而谓古人为错会者,无论言之得失,气象已不好,尤为可惜。①
对于强力推出自说并说先人见解有误的朴世堂的态度,尹拯感到违和,朴世堂的说法本身正确与否反倒未讨论。尹拯认为与先人见解相异时,应该要以赵翼的态度为模范。在经书钻研的过程中,的确会有不同的权威,提出自家说法的状况,此事本是不得已。但在那样的状况下,赵翼会保持谦逊的姿态,不说自己的看法正确,只说作为一种说法提出。也就是说,赵翼尽管得到应该获得好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会采取以自说为是、先人业绩为非的态度。
但是被称赞是对的态度的赵翼,尽管《朝鲜王朝实录(孝宗实录)》认可他“潜心性理之学”,却同时记载“其所著《书经浅说》《庸学困得》等书中,颇改朱子《章句》,人以此疵之”②。也就是说,赵翼也因为写了不同于朱熹见解的注释书,而被某些人非难。与此相对,拥护赵翼者是宋时烈。
对于批判赵翼的声音,宋时烈及其同宗兼政治同志的宋浚吉(1606—1672)说:“尹鑴凌侮朱子而自是己说,某爷有疑于心而求质于知者,迥然白黑之不同。”③他们藉比较尹鑴和赵翼的态度、意图,以拥护赵翼。如果《孝宗实录》所说属实,赵翼就是一边致力朱子学研究,一边撰写和朱熹不同的经书解释。宋时烈、宋浚吉拥护同一党派的学问前辈赵翼,他们不是用“赵翼未持有违背朱子的见解”的说法辩驳,反而承认他“持有怀疑”这件事,即赵翼提出和朱熹不同见解的这一点,未被视为问题。而且如同前面引用的尹拯书信,赵翼新注释的谦逊写法获得称赞。
因此,从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比起是否提出和朱子不同的见解,提出自说的意图和态度更重要”的想法。朝鲜时代的士大夫不问尹鑴、朴世堂主张之得失,仅以其心可议为理由批判他们。讽刺的是,进入21世纪后,同样也不问注释内容实际如何,尹鑴、朴世堂的注释因为勇敢地主张朱熹之说有误,反而被赞扬是带有近代性的知识分子。
之后,宋时烈被批评他不公平地拥护赵翼。听到批判自己的消息后,宋时烈写给赵翼之孙赵持恒以下的信曰:
比因人闻一种论议,则以为尤丈(宋时烈)于镌以改注《中庸》等事,斥绝之既严,至其党与,亦甚痛斥。以是辗转,致有今日之事。浦渚赵相(赵翼),亦于《大学》改注,至曰沉潜三十年,不知朱说之是,愚说之非也。其为说若是,则难免非责,而拒辟之事终不加焉。今于墓道文字,赞扬无余,则鑴之党与见斥者,其可服罪乎。或已撰出,则还推灭去,似无彼此取笑之资云云。……此文若出,必有一场纷纭,以增斯文之厄,不是小事也。再昨招宋炳夏商量,①又更审其祖考(宋浚吉)所撰行状。则记先老爷(赵翼)雅言,以为孔子之后集群儒而大成者朱子也,其功多于孟子云云。若于《大学》,果有如言者之说,则其雅言岂有如此之理耶?以故使炳夏搜送刊行文集,则归报以不得,极可叹也。②
从上面的文章可以看出关于赵翼的传闻,一个是说他写了和朱熹不同的注释,另一个是他曾说过“不知朱说之是,愚说之非也”。然而宋时烈最在意的,不是赵翼的注释是否与朱熹之说相背,而是他是否说过轻视朱熹的言论。
从以上的例子来看,赵翼、尹鑴、朴世堂的注释,皆被同党派的同伴认为有学术价值。但是根据是否无视朱子学说的权威,态度上是否以自说为是,从同伴获得的评价有所差异。也就是说,欲破坏朱子学权威的不逊态度会被责备,但是提出与朱熹不同解释这件事本身,未被直接排斥。
这种想法并未随着时间变化。朝鲜时代后期的文臣徐滢修③(1749—1824)也说,能够认可对朱熹之说提出异见,但是直接指责朱熹有错的方法必须批判:
虽以朱子之步步趋趋于程子,如《易》《诗》《语》《孟》,未尝尽遵程说。《大学》《中庸》,宗程尤笃,而订正尤多。……朱子诚不能无误矣。……昔陈大章④熟《通鉴》,检得疏谬处,做一辨驳文字,以示其友。其友曰:不消如此,只注其下,云应作如何足矣。宇宙间几部大书,譬如父祖遗训,万一偶误,只好说我当日记得如此。若侃侃辨证,便非立言之体。《通鉴》尚然,况经传笺注乎。⑤
徐滢修以朱熹对程子态度作为自己议论的依据,他区分以程子学说为优先,和全盘接受程子学说两件事之别。朱熹比什么都尊重程子之说,但是解释经书时并不只限于跟随程说。例如对朱熹思想体系来说,最重要的《大学》《中庸》解释,一边宗于程子之说,一边在许多地方有所修正。徐滢修基于朱熹的做法,认为既然朱熹之说也有需要订正的地方,那么它的订正工作便是正当的。但是强调朱熹的错误,以强行主张自说是不行的。换言之,不是“不能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而是“不能抱持强调朱子之误以提出自说的意图和态度”。
三、“改朱子之注”
对于一本新的著作,作者的师友所关心的,不是其观点是否与朱子相同,而是写作态度。但是就像赵翼被非难大改《章句》一样,以改朱子之注的名目遭受政治攻击的事情时常发生。那么,对于这种攻击的反驳内容为何?还有这些作者真的改了朱熹的注吗?
赵翼写了《大学》注释的《大学困得》,其“诚意章”认为朱熹的注释并未正确解释经文,提出了新的解释。在朱子学中,当把《大学》的内容以知与行归纳的时候,“诚意”作为进入行的第一步,是被重视的条目。因为“欲为这事,是意”①,如果在意识萌芽的时候为善去恶,实践也如意识一般能够达成。对于《大学》的“诚意”,朱熹的想法大致从两处注释可以看出。首先是朱熹《大学章句》的经一章的注释②,写道:“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③接着,对于《大学》诚意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传六章做以下解说:
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①
朱熹将“诚意”解释为自我修养的第一阶段。对于《大学》中用来说明“诚意”的“毋自欺”等句,朱熹的理解是,如厌恶恶臭、爱好美色一样,致力为善去恶。而“自谦”的解释则是,应该为了使自己快足而努力,不要以外部标准为标准,为了做给别人看而努力。
对于朱熹的注释,赵翼的问题意识是,在“诚意”这样的自我修养中,“毋自欺”和“自谦”具体而言是何种行为?如同前述,朱熹将“毋自欺”和“自谦”都解释成诚意的修养方法。要言之,努力不要对自己的念头有所欺瞒是“毋自欺”,为了使自己能感到满意而努力是“自谦”。最后作结于努力勿为他人评价而非自我意识为标准的“为人之学”。
对此,赵翼认为《大学》所言诚意的修养方法只有“毋自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即“自谦”)指的是由修养所得到的效果。②从赵翼的想法来看,此章应该这样解释:如果善加修养诚意,便能达到自足的状态。“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非如朱熹所说是修养的方法,“毋自欺”也不是朱熹解释的“不要为了让别人看而做”。所以《大学》传文的内容是按照“毋自欺(努力)”到“自谦(效果)”的顺序排列。朱熹因为先解释自谦,所以依此读出勿自欺的意义。但若如此解释,便和传文的顺序对不上,赵翼的说明如下:
(朱子)章句谓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以如好如恶为实用其力之事,以徇外为人为自欺之事。使以如恶如好为在先事,以毋自欺为在后事,以传文先后易置之。此窃恐其未必合于传文本旨也。③
之后,赵翼又作了两篇文章:《后说中》(1638年7月)、《后说下》(1653年2月),将自己无法免于提出异于朱熹见解的经过做详细说明。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从朱熹书信中找出可以为己说做旁证的文句,认为《章句》的注只是朱熹的一时见解,定论应该如这些信件所言。他主张自己的见解虽然和《章句》多少有所不同,但是并未改变朱熹的定论。赵翼罗列以朱熹《答张敬夫书》为首的十五通书信,加上《心经附注》和《书杨龟山话后》共17篇文章中关于“自欺”的文句,就何者为朱熹的定论,论述如下:
由是观之,则朱子平生所说自欺之语,皆是谓欺其心也,未见其以为人为自欺也。唯独于《大学章句》,以徇外为人释之,及小注一两条谓为为人耳,其言不同如此。且谓为欺心,其平生所说皆然,谓为为人独见,此三两处耳。然则窃恐此所释,乃朱子偶然一时所见,非其平生定论也。后之读者,徒见《章句》所释如此,而不考朱子他时所言,便谓朱子之旨只如此,《大学》本旨只如此。则窃恐其不得为深究朱子之旨者也。区区妄说,虽于《章句》之言有不同,其于朱子平生所言之意,则实吻合。然则谓其异于《章句》则可,谓其异于朱子之旨,则实不然也。①
赵翼主张自己的见解尽管可以说异于《章句》,但实际上并未背离朱熹本旨。即他不否认改了朱熹的注这一点,但是强调自己正因为尊重朱子学所以改了注,采取“透过改注使朱子学本来的想法更加明确”的姿态。他将自己的新解释合并在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中,在相信能使该体系更加完备的状况下,提出上述说明。从赵翼的文集可以知道,上述主张不是他在腹中批判朱子学之非,却因为害怕他人目光所以做出的辩解。
虽然如此,因为改朱熹之注的理由,著作被焚书处分的情况不是没有。那么,受到焚书等严厉处分的作者,是如何证明自身著作之清白的呢?让我们以崔锡鼎(1646—1715)的《礼记类编》(以下称为《类编》)为例。
《类编》完成于1693年,在1700年和1707年刊行。刊行后,皇帝广赐诸臣,因此读过的人非常多。此书如书名所示,将《礼记》经文从原本的顺序,重新分类进行编辑,各项类别按照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建立。例如设“家礼”的篇目,其中收纳《曲礼》《少仪》《内则》篇;在“邦国礼”的篇目下,收纳《王制》《月令》《玉藻》篇。将《大学》《中庸》放回《礼记》,以“学礼”的篇目收纳,并视《孝经》为原本属于《礼记》的一部分,将其编入《类编》中。1700年11月的初刊本形式是,先在各卷开头记上简略说明,收录分类编辑的经文,然后在各卷末尾加上附注。②1707年再刊时,将《礼记》经文如同《四书大全》般,按照段落分记,在各段落下方附上南宋陈澔(1260—1341)的《礼记集说》的解说,其下又加上崔锡鼎自己的“附注”。《礼记集说》在《大学》《中庸》的部分未附注释,只记上“朱子章句”四字而已。而崔锡鼎则在《大学》《中庸》部分载录朱熹《章句》的注释,并和其他章一样,加上自己的“附注”①。
崔锡鼎在序文中提及《类编》的编纂理由及主要方针,要约如下:自秦焚书以来,六经失散,礼乐相关的书物损失尤重。朱熹就《易经》撰写《周易本义》,《诗经》撰写《诗集传》。至于《书经》,则使弟子蔡沈执笔《书集传》;于礼则以《仪礼》为中心,加上其他经书、史书、诸子百家之文,著成《仪礼经传通解》以传世。《仪礼经传通解》从诸多书物,大量引用各式各样的文章,重复处不少,且不属于特定的经。在这样的状况下,内容之庞大,使学习者难得要领。《礼记》虽本是汉儒收集关于礼乐的片段记载并编成的书,但是因为它包含古代圣人言礼之文,从永乐年间(1403—1424)以来就位列五经,不容忽视。只是以朱熹为首的先儒认为《礼记》由汉儒搜集编辑而成,对其文献内容多有怀疑。尽管朱熹有所怀疑,却未曾进行《礼记》的校勘。因此,关于文本的问题很多,笺注者尽管时被怀疑,至今却没有人辟清这些问题,长久以来,学习者皆为此苦恼。崔锡鼎深刻认识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性,于是立志删定,多次来回修改,终于完成此书。②
至于编辑方针,崔锡鼎根据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建立数个项目,将《礼记》篇章分类,放在每个项目底下。此书取名为《类编》的理由则是,朱熹曾惋惜唐代魏征所作《类礼》未能传世,因此崔锡鼎同样怀着希望《类礼》能有所流传的心情,将本书命名为《类编》。③
从上述序文可知,崔锡鼎编纂《类编》的目的如下:
第一,重整散乱的经书。
第二,继承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意志。
崔锡鼎充分理解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旨趣,并担负起这项尽管必须进行却未被进行的工作。即对他而言,《礼记类编》的编纂是自认为继承朱熹之道的表现。
崔锡鼎于1700年(肃宗二十六年,55岁)向肃宗建议进讲《春秋》和《礼记》,且《礼记》讲学使用自撰《礼记类编》,获得许可。①该年11月,王命校书馆刊行《礼记类编》。②然而此书刊行数年后,被视为“求异乎朱子”的著作,开始受到攻击。
宋时烈门人郑澔(1648—1736)写信给同门的权尚夏(1641—1721),劝他批判崔锡鼎的《礼记类编》以正世道。③权尚夏没有响应此事,但是之后,权尚夏的弟子尹凤九以尹瀗等年轻读书人提出公论的形式,写了代理上疏文。④尹瀗等人上疏的内幕,其实由宋时烈门下的运作所导致。上疏中他们要求毁去《礼记类编》的版刻,并撤回朝廷进讲之命。⑤
崔锡鼎次次上书,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举出先儒李彦迪(1491—1553)和赵翼等人的著作,说他们也曾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⑥他指出李彦迪及宋时烈等人拥护的赵翼都没有完全根据朱熹解释,控诉说自己的著作和两人一样,非“求异乎朱子”。
真正切断攻防保险丝的是,1709年1月同副承旨李观命(1661—1733)的上疏,内容如下:
今伏闻有以《礼记类编》,刊进于中宸,将欲参讲于法筵。臣取考其说,则求异乎朱子者,固不可毛举。而至若《庸》《学》,朱子自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微辞奥旨,阐明无憾,则此岂后人所可容议者。而《大学》第四章,揽而合之于第三章,而统之曰,右释止于至善,而去其释本末一章。《中庸》第二十八九章之正文,割截句语,釽裂数行,移东而入西,缴下而就上。至于“费隐”一章,义理最深,章句所解,至矣尽矣。而今其附注二条,显有所信本旨底意。且程子之表出《庸》《学》,意非偶然。而今此《类编》为名,不过分类便览之书。则其为体段,亦非经书之比,乃复还编《庸》《学》于其中,使先贤表章之本意,暗昧而不明。……既命刊行,又将参讲,则四方闻之,必以轻信异言,妄疑于殿下,诚非细故也。古人有言:“经文一字之误,流血千里。”①
李观命说崔锡鼎“求异乎朱子者,固不可毛举”,客观来看真的能说服人吗?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他主张的第一个问题——合并《大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为一章。崔锡鼎按照朱熹《大学章句》顺序记录经文,同时也记上朱熹的注。也就是他并未将朱熹分成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两章合并,也未主张以上是第三章。所以“将《大学》第四章并入第三章”的李观命指控并不成立。
那么为何李观命有此批判?那是因为朱熹在第三章末写有“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在第四章末写有“右传之四章,释本末”。崔锡鼎则将朱熹的“释止于至善”一句移到第四章末。由于这个部分没有其他说明,只是抄录朱熹原文而已。崔锡鼎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清楚,但是可以推测,崔锡鼎可能认为第三章的说明是一直延续到第四章的。如果是这样,便能解释为什么朱熹标记第三章关于“止于至善”,第四章关于“本末”,但是崔锡鼎却把第三、四章共同当作关于“止于至善”的文句解释。也因为如此,李观命批判他将第四章并入第三章。
然而,若看后面的第五章,崔锡鼎虽然把朱熹的格物补传(第五章)用比《大学》本文低一格的形式抄录,仍一句一句附上附注,也就是结构上将其视为经文对待,且附上“以上朱子补亡,所谓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者也”的附注,将朱熹所作的补亡文章明确地升格成第五章的格物传。崔锡鼎同意“《大学》是体现学习者修学顺序之书”的朱熹想法①,基于此,他以充实八条目的形式增添解释。又他移动了《礼记》诸篇的经文以进行编辑,但是对于《大学》《中庸》两章,却都是直接抄录章句内容,没有变动。
再让我们看李观命主张的第二个问题,即崔锡鼎割裂、移动《中庸》第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的内容。据《中庸章句》,第二十八章为“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一见可知,此章中“子曰”有两处。然后第二十九章没有“子曰”,直接从“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开始。一般而言,“子曰”放在章首较为自然。因此,一章内有两个“子曰”的第二十八章及没有“子曰”的第二十九章,无疑需要注释者的说明。
对此,朱熹《中庸章句》认为第二十八章的结构,第一个“子曰”孔子之言的引用,接着是子思的评论,而第二个的“子曰”是再次引用孔子之言。崔锡鼎则视第二个“子曰”为次章(第二十九章)的开始,又说原本二十九章开头的“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一句,“王天下有三重焉”应该要移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之前,而“其寡过矣乎”则留在原处,接续“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的句子。他引用《章句》收录的吕大临注“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表示移动上述七字的想法不是自己恣意妄为。也就是崔锡鼎的行为,不是“因为朱子之注有误,所以改动它”,而是从《章句》的注获得根据,使其更加精细的结果。
从吕氏注释如何得出与朱熹《章句》不同的结果?以下试着类推:《中庸》第二十八章的正文有两个“子曰”,同时,接续的第二十九章开头没有“子曰”。承此,当然需要说明。朱熹《章句》并未变更章的分隔,但是在第二十九章的注释却用了吕氏之注,吕注表示第二十九章的“三重”指的是第二十八章的“议礼、制度、考文”。崔锡鼎以此为根据,与吕氏注之趣旨呼应,将二十九章的“三重”部分,移到第二十八章的“议礼、制度、考文”之前。尽管这与朱熹的分章相异,却不一定背离朱熹的意思。因为朱熹自己虽然赞同吕氏注,却没有移动正文。因此可以解释为,崔锡鼎读取此意后,将其实行。这是朱熹如果还在世或许也会进行的工作。
李观命主张的第三个问题又是如何?附在《中庸》“费隐”章的两条崔锡鼎“附注”,明显意图主张自己认为的“费隐”章宗旨,并非朱熹宗旨吗?“费隐”章从“君子之道费而隐”开始,即“君子之道谁都知道、谁都可以做,同时却有圣人也做不到的地方”这样的内容。此章的崔锡鼎“附注”被批判的句子是“见《经说》①及《辑略》②,似与《章句》所解有异”③。还有一个是对《章句》引用的侯诗圣(河东侯氏,程颐弟子)注的批判。前者指的是在《河南程氏经说》和《中庸辑略》中,程氏从“常道”(《河南程氏经说》)和“日用”(《中庸辑略》)的角度解释“费”字,但是《中庸章句》以“范围之广”解释,所以程子和朱子的解释并不一致。此外,崔锡鼎“附注”被批判的第二处,指称朱熹《中庸章句》引用的河东侯氏的说法不当。崔锡鼎在此使用的方法是从《朱子语类》直接引用与侯说相反的内容,最后再加上“此一条见朱子语类”一句结尾。也就是他不是以自说对朱熹《章句》提倡异见,而是使用朱熹的话语(即《朱子语类》),对朱熹的解释提出异议。因此,崔锡鼎的注释虽然改了朱熹之注,但因为提出朱熹的文句作为根据,无法确定他是否“求异乎朱子”。
李观命主张的第四个问题是将《大学》《中庸》放回《礼记》的做法,违反了先贤将此两篇提出作为独立书籍的本意。的确,《礼记类编》将朱子学中俨然成为四书之两轴的《大学》、《中庸》放回《礼记》,并以“学礼”的篇目收纳,又说《孝经》实际上是戴记的一篇而将其编入《礼记类编》。但是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也在“学礼”的项目收入《大学》《中庸》,《礼记类编》只是根据它的编排。崔锡鼎后来的上疏文实际上也如此反驳。再者,关于编入《孝经》之事。考虑到朱熹屡说“《孝经》是后人缀缉”“据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④等言,我们也无法确定崔锡鼎是否就因此“求异乎朱子”。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虽然崔锡鼎的“附注”与《章句》的朱熹注有时见解不同,但是无法说是“求异乎朱子”,即从客观立场来看,实在很难同意李观命的批判。实际上,对于李观命的上疏,肃宗直接批示:“至于新刊《礼记类编》,予已翻阅矣。此岂可与《思辨录》,比而论之乎?其所为言,用意至深。噫!《类编》序文中有曰,其规模义例,悉仿朱子《通解》,而一言一句,不敢妄有所删削。”①将上疏驳回。肃宗应是在全部确认过李观命主张的基础上,将批判之声驳回。只是肃宗重视的是“仿效朱子”的作者意思,各个注释实际上是否异于朱熹,这件事本身并未被当成问题。
崔锡鼎呈上疏文,逐一反驳李观命的批评。他举例反驳,先儒李彦迪也曾著书改订朱熹《大学章句》,李珥(1536—1584)却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因为两人都笃信朱子。接着又仔细说明,《礼记类编》的样式是根据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而来,其他的编辑方针也全依据朱熹说过的话。②但是环绕着《礼记类编》的议论仍日益扩大,不仅官僚争相上疏,③连成均馆和四学④的儒生都集体上疏,骚动无法平息。⑤结果,最后如同李观命上疏文的要求,已经发出的《礼记类编》被回收焚烧,毁去此书之版本的要求也被许可,执行的命令下达后才终于完结此事。⑥
《礼记类编》被焚烧处分的真正理由,先行研究已经论证。这是老论派出于政治目的,要攻击被肃宗所信任的崔锡鼎,所以才利用《礼记类编》⑦。那么《礼记类编》是否真的改了朱子的注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改了”。但是作者崔锡鼎并不认为“改了”这件事本身是问题,因为他确信自己的学问皆以朱熹的文句为基础。他的周遭也有抱持同样认识的人,就见解异于朱熹这一点批判他的人,只有出于政治目的批判他的一派而已。
四、异见提出者的自我认同
那么改朱熹之注者或未持政治目的的儒者的问题关心,其中是否有包含对朱子学的问题意识?如果他们对朱子学持有批判意识,并基于此想改动朱熹的经书解释,他们的自我认同便可以说是“朱子学批判者”。他们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时,自我认识为何?
赵翼被非难“大改朱子《章句》”,因为有宋时烈的庇护,尽管受到对立党派批判也得免于祸,但是赵翼果真可以说是以超越朱子学的新思想为目标吗?而且提出异于朱熹的注释是此目标的一环?
赵翼任职直提学的1624年(仁祖二年),向仁祖献上《大学困得》《论语浅说》。①1646年(仁祖二十四年)献上改订版的《大学困得》,以备为世子(后之孝宗)讲学,同时他也建议仁祖一读。②孝宗即位之年,再度奉上《大学困得》《论语浅说》之际,举出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异于朱熹解释的《大学》诚意章的注,说明自己对这一章的解说,是藉由平生思索所得到的结果。③在朱子学作为官学的背景下,如果《大学困得》以批判朱子为目的执笔,那么赵翼可以像这样,自负于书中改动朱熹注释的诚意章,认为是自己平生思索的结果吗?况且还可以这么积极地劝国王一读吗?这么说,赵翼本人应该只视这部“大改朱子《章句》”的著作为经书研究的成果,不带有朱子学批判的问题关心。
被说是改了朱熹的注,著作被烧毁的崔锡鼎又是如何?他曾对朱子学持有怀疑吗?崔锡鼎曾经写信给因为信奉阳明学而被批判的好友郑齐斗(1649—1736),书信内容如下:
士仰(郑齐斗的字)足下,顷年因士友闲,得闻足下主阳明之学,于心窃惑焉。昨岁拜玄石丈(朴世采)坡山,玄丈忧足下之迷溺于异学而不知返。……夫天下之理一也,苟理之所在,则固未可以人而轻重。然古人论学之旨,莫要于《大学》,而朱子训义,至明且备。阳明子乃斥以支离决裂,出新义于程朱之表,而其言语文字,具载遗集及《传习录》中。其论说之偏正,学术之醇疵,诚有可得而言者。则足下之信而好之如此者,无乃信其不当信而好其不当好也耶。仆年十三,读《大学》及《或问》,厥后盖尝屡读而精研矣。中闲见张溪谷(张维,1587—1638)文字,赞叹阳明之学,不一而足。于是遂求阳明文集、语录而读之。乍看诚有起诣新奇可以惊人处,既而反复而读之,博极而求之,则徒见其辞语妙畅,文章辨博,而学问蹊径,率皆颠倒眩乱。非但背驰于朱子,将与孔曾相传之旨,一南一北。有不容于无辨者,遂妄者辨学一说,思欲与同志者讲确而未能也。①
这封信写于1692年,也是可以窥探崔锡鼎快完成《礼记类编》时想法的材料。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改动朱熹的注,撰写《礼记类编》时,是一位坚定相信朱子学道理的朱子学者。换言之,崔锡鼎正因为是位比什么都尊重朱熹经书解释本意的朱子学者,所以才改动朱熹的注。
这位经书解释与朱熹相异,被批评改朱注者,不仅未持有反朱子学的意图,甚至还表现出对朱子学道理的确信。承此,实在很难同意“他期望克服朱子学,所以改朱熹之注”的说法。
连带来看,当崔锡鼎《礼记类编》因为改朱注而引起全国性的议论时,不属于出于政治目的攻击他的群体的人,对于《礼记类编》是否背离朱子学这个问题抱有兴趣吗?
这个“事件”发生之际,和崔锡鼎同属少论的尹拯这么说道:“崔相(崔锡鼎)虽以晦(李彦迪)、栗(李珥)两先生自解,而既不免异于朱子。则砭者之锋,安能免也。只当安受而已,不必较也。”②
如同前述,崔锡鼎举李彦迪改朱熹《大学章句》却受到李珥高度评价为例,诉说自己著作的正当性。但是尹拯认为崔锡鼎没有必要那样反驳,就此承认攻击者的言论就好。因为崔锡鼎著作包含异于朱熹的见解是事实,对方以事实为理由攻击,回避不了。从尹拯的话,看不出持有异于朱熹的见解或表现该种见解本身很严重的想法。
此外,不是所有宋时烈门下的人都参加了追讨崔锡鼎的活动。权尚夏从同门的郑澔处收到两封劝他攻击崔锡鼎《礼记类编》的书信,仍没有动作,就算被宋时烈门下的人大加责备,直到最后也未曾涉足。①
《礼记类编》尽管受焚毁的处分,但刊行本早已分送到南边的全罗道、庆尚道等地域,在儒者社会中流传,被广泛地阅读。②其中有一部分被藏在家里,免于焚毁,之后为《礼记》研究者屡屡引用。焚书数十年后,成海应(1760—1839)以“崔氏锡鼎《礼记类编·深衣篇》附注曰”的形式引用了崔锡鼎的“附注”。③成海应研究《礼记》深衣篇之际,从汉代郑玄注、唐代孔颖达疏到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引用说法,不但网罗中国之说,同时还加上崔锡鼎的“附注”,作为《礼记》的先行研究参考。
另外,政治党派从属少论的崔锡鼎所著《礼记类编》受到严重处分,对此,从属南人的李万敷(1664—1732)如下说道:
其书苟有不是处,则为崔相之友者论辩之可也,本不关朝廷之是非。老论以此为击去崔相把柄,岂非党论所使乎?④
乍看之下,李万敷似乎是从南人的政治立场,批判老论的朱子学原理主义。李万敷15岁的时候,因为父亲李沃(1641—1698)被处以流放之刑,他很早就不得不放弃官场之路。导致流放的直接原因没有其他,就是因为李沃曾主张对老论领袖宋时烈处以极刑。⑤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父亲,李万敷才特别嫌恶老论及其朱子学原理主义。但是只从这一点说明上面引文并不充分。
李万敷和曹夏畴、李淑、李潜等好友时常进行学术讨论。让我们看一下记录其讨论的“中原讲义”。①曹夏畴批评朱熹的《大学》注释“杂乱烦琐”,主张“宋季学者,趋末无实,岂非朱子启之乎”。李万敷回道:“此乃后人自流之弊,岂朱子所启也?”并且他在结尾处断言道:“澄叔(李淑的字)尝言,曹兄有思而不学之病。以此数说观之,其病不但止于不学而已也。”又李万敷在其他文章提到曹夏畴时,说:“君叙公以弟为中毒于程朱,程朱之道,大中至正,本无毒可中人。然如果为所中,岂不幸甚。”②
从两人的讨论中至少能看出,他们一人严厉批判朱熹经学解释带来的弊害,另一人坚定地相信朱子学的正确。如果以过去韩国儒学史上的对立图式来区分,上记曹夏畴是嫌恶与老论派绑在一起的朱子学派,所以进行朱子学批判的一边,而李万敷则会是朱子学派那一边。但是如此一来,批判围剿崔锡鼎的老论派李万敷,和积极维护朱子学、被视为程朱学中毒的李万敷,很难说是同一个人。
五、结语
以上讨论显示,17世纪被说改了朱子之注的经书解释,至少在著述之际,看不出这些作者持有对朱子学的怀疑与批判意识。又对于持有和朱子学不同学说者未严格看待的人,却对不认同朱子学贡献的好友发言做严厉的批判。这么看来,分为拥护朱子学侧和批判朱子学侧,如此说明韩国儒学史有其困难。
那么冒着得到改朱注之“罪”的风险,撰写异于朱熹见解的经书注释的人,实际上是抱持什么想法呢?接着,他们不仅把著作给亲友过目,甚至献给国王,是为了什么?
这恐怕出自于“作为道统继承者必须完成此任务”的认识。当时在东亚普遍的想法是自称中华的根据来自圣人的存在,继承作为圣人文言的经书,正是中华道统后继者的责任。如果是道统的后继者,不会任经书处于散乱不明的状态。对于继承朱子学式道统的朝鲜时代的儒者,中华继承的实质就是担负起朱熹在未完状态遗留下来的责任,确定经书意涵和整理经书。但不是谁都可以继承朱熹、肩负这样的任务。如果做得不好,会被人说是“侮辱朱子”“改朱子之注”,甚至是“斯文乱贼”等,提供攻击材料给政治对手。只要是士大夫社会的成员不认可“你是朱子的后继者,拥有进行朱子学后续工作的资格”,或是自己无法强力主张“我是朱子的后继者,拥有进行朱子学后续工作的资格”,自任承继朱熹之迹者,就有可能如上述般被问罪。接着,他们还不能不证明自己的创见能够使朱子学体系更加完备。朝鲜时代的儒者正因为怀抱着这样的抱负,才冒着政治上的危险也要完成朱熹未完的工作,同时也为了确认自己是道统的嫡流,努力想完成该责任。
附注
①[韩]李丙焘:《朴西溪和反朱子学的思想》,《大东文化研究》第3期,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66年,第1页。
①《思辨录》的著作年代:《大学》(1680年,52岁)、《中庸》(1678年,59岁)、《论语》(1688年,60岁)、《孟子》(1689年,61岁)。之后,又加上《尚书》(1691年,63岁)、《毛诗》(1693年,65岁开始执笔,未完成)。
②《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肃宗二十九年(1703年)四月二十三日:“世堂之有此书,几三十年,搢绅之间,多有闻而之者。而初未闻历诋之言,亦未有请讨之举。今因相臣碑文,遽生恨怒,喧喧鼓扇。”
③围绕三年上食的论点,参见李曦载:《朴世堂的儒教仪礼观——以三年上食论争为中心》,《宗教研究》第46号,首尔:韩国宗教学会,2007年。
①金世奉:《西溪朴世堂的〈大学〉认识和社会回响》(《东洋古典研究》第34辑,首尔:东洋古典学会,2009年)指出,《思辨录》成为问题的根本理由,是因为朴世堂批判宋时烈,使其门人有所动作。
②[韩]许穆:《记言》卷三,《答希仲》,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9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3页。
①[韩]尹拯:《与朴季肯》(辛未四月六日)之附录《论大学格致·孟子井有人章》,《明斋遗稿》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238页。
②《朝鲜王朝实录(孝宗实录)》孝宗六年三月十日。
③[韩]宋时烈:《答赵光甫》(癸亥)附录,《宋子大全》卷七七,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528页。
①宋炳夏(1646—1697)是宋浚吉之孙,宋时烈门人。
②[韩]宋时烈:《答赵汝常》附录,《宋子大全》卷一一六,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148页。
③从属西人分出来的少论派。
④清朝的陈大章(1659—1727)。
⑤[韩]徐滢修:《题毛西河集卷》,《明皋全集》卷十,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6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196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2页。
②《大学》原本是五经之一的《礼记》中的一篇,但是朱熹将《大学》分成经一章和传十章,认为“经”是曾子记录孔子思想的内容,“传”是由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想法。
③朱熹:《大学章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据说朱熹于过世前三日将“一于善”三字改成“无自慊”,唯本文依照通行诸本记为“一于善”。
①朱熹:《大学章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②“此章言诚意工夫,只此数句尽矣。而其用功之实,只是毋自欺三字而已,自慊其效验也。”载赵翼:《大学困得》,《浦渚先生遗书》卷一。
③[韩]赵翼:《大学困得》,《浦渚先生遗书》卷一,第15页。
①[韩]赵翼:《大学困得》,《浦渚先生遗书》卷一,第37页。
②参照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礼记类编》(记号:〓〓古1234—24)。
①参照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礼记类编大全》(记号:〓古朝6—11)。
②[韩]崔锡鼎:《礼记类编序》,《明谷集》卷七,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563页。“易书诗春秋礼乐,谓之六经,皆道之所寓也。自秦焚书,经籍亡佚,而礼乐尤残缺。汉魏以来,专门训诂,率多迂谬,后学无以识圣人之意。朱夫子身任斯道,羽翼圣言,易有本义,诗书有传,礼有经传通解。于是古经之旨,焕然复明。然《通解》一书,规模甚大,杂取诸经子史而成书。今若取以列于经书,则体既不伦,文多重出,且其卷帙繁委,初学未易领要。《戴记》四十九篇,出于汉儒之搜辑,虽未若四经之纯粹,要之,古圣人言礼之书,独此在耳。又自中朝永乐以来,立之学官,以列于五经,顾恶得以出于汉儒而或轻之哉。特其未经后贤之勘正,编简多错而大义因之不章,笺注多疑而微词以之未阐,学者病之久矣。锡鼎弗揆僭妄,有志删定,累易稿而始就”。又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记号:〓古朝6—11)中,序文的著成年月是癸酉(1693年)夏四月。
③[韩]崔锡鼎:《礼记类编序》,《明谷集》卷七,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563页。“凡五十篇,名之曰《礼记类编》。昔唐魏征撰《类礼》二十卷,朱子有所称述,而惜其不传。名以类编,亦此意也。”
①参照《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肃宗二十六年(1700年)十月四日。
②[韩]崔锡鼎:《新印礼记类编序》,《明谷集》卷八,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569页。从本序可知,此书经由肃宗之命,由校书馆铸字刊行。当时崔锡鼎的官位是判敦宁府事(职司王族亲族事务的敦宁府,正一品官)。
③[韩]郑澔:《与遂庵书》,《丈岩集》卷十,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7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226页。及同书《答遂庵书》,第227页。
④[韩]尹凤九:《代四学儒生尹瀗等办崔锡鼎礼记类编疏(己丑)》,《屏溪集》卷六,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04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第128页。
⑤《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三月十二日:“四学儒生尹漶等四十余人,上疏请亟将新刊类编,毁去其板子,仍收法筵参讲之命。”
⑥[韩]崔锡鼎:《屏溪集》卷二十,《因学儒尹瀗疏陈情辞职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04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第262页。
①《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一月十八日。当时,李观命的官位是同副承旨(职司出纳王命的行政机关承政院,正三品官)。
①崔锡鼎引用《大学》编目开头的朱熹《大学章句序》:“《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和《章句》:“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
①《河南程氏经说·中庸解》,《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②《中庸辑略》是南宋石〓(1128—1182)编集,朱熹删订的书。从程子开始,收集诸家关于《中庸》的说法。最初的书名是《中庸集解》,删订后改名《中庸辑略》。参照石〓编,朱熹删订,罗佐之校点:《中庸辑略》,《儒藏精华编》第10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该当处之程子之注,见第30页。
③《礼记类编》卷十一,癸酉(1693年)夏四月刊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第55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27页。
①《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一月十八日。
②《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一月二十一日。
③《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二月一日。
④四学,即设立于首尔之中央、东、南、西、北的四所官学。朝鲜王朝第三代国王的太宗十一年(1411年)设立,持续至第二十六代的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鲜朝初期原本也设有北学,但后来关闭。此外官学还有首尔的成均馆,地方乡校等。
⑤《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二月十四日。
⑥《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六年(1710年)三月十三日。
⑦参照梁基正:《礼记类编的编刊、毁版及火书研究》,首尔:成均馆大学修士论文,2011年,第82~84页。
①[韩]赵翼:《进大学困得论语浅说疏》,《浦渚集》卷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45页。此上疏文于甲子年(1624年)进呈。
②[韩]赵翼:《进大学困得疏》,《浦渚集》卷五,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92页。丙戌年(1646年,仁祖二十四年)作。
③[韩]赵翼:《进庸学困得疏》,《浦渚集》卷六,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107页。“为善之功,必以诚实为要。此诚意工夫是也。臣之说此章,尤是平生极意思索而得之者也”。此疏未记录年月,但从内容可以推测是孝宗即位年的秋或冬天。孝宗于1649年5月即位,但记有“春奉《论》《孟》于世子。世子即位,欲奉《庸》《学》,唯手边无草本,持故乡之写本再写以进上,足费时”。
①[韩]崔锡鼎:《与郑士仰书(壬申)》,《明谷集》卷一三,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120页。壬申年为1692年。
②[韩]崔锡鼎:《答罗显道(九月十二日)》,《明谷集》卷一五,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358页。
①权尚夏门人成晚征(1659—1711)之《秋潭先生文集》卷五,《答韩仁夫(己丑)》,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续第52册,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8年,第533页。“《礼记类编》出后,师门独无明斥之举,不但众人疑之,相知如攀桂,亦以书责之”。
②[韩]崔昌大:《先考议政府领议政府君行状》,《昆仑集》卷一九,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8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第358页。“庚辰,具疏投进。上命校书馆印布正文,其后玉堂权尚游、尹趾仁请下两南,并注疏印进,学士大夫皆印藏而赏”。
③[韩]成海应:《深衣考》,《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一五,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76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37页。
④[韩]李万敷:《露阴山房续录》,《息山集》卷一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7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第283页。
⑤参照《肃宗实录》肃宗四年四月、五年三月记事。
①《中原讲义》卷一二,第270页。
②《中原讲义》卷五,《与李仲渊》,第134页。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