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儒学观点看朝鲜朝主理主气两派的义理形态
| 内容出处: | 《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307 |
| 颗粒名称: | 从当代儒学观点看朝鲜朝主理主气两派的义理形态 |
| 其他题名: | 兼论朱子为主理的形态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5 |
| 页码: | 274-28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学认为人心对道德之理有先验知识,通过格物致知进一步了解此理。朱子的成德理论以“主理”为核心,强调道德行为由道德法则直接决定意志。即使气质昏昧之人也有本具之明德,可在日用中体现。 |
| 关键词: | 朱子学 道德法则 儒学 |
内容
一、引言
从1990年起,我因为应韩国友人的邀约,参加有关韩国朝鲜朝儒学的会议,开始阅读有关的文献,理解到朝鲜朝儒学虽然以朱子的性理学为主,但内容十分丰富,对朱子一系的义理问题有细密的讨论,并有新的发展。这一部分的文献,应该是研究宋明理学者不能不注意的。对于朝鲜朝的儒学发展,我的研究虽然不够详细,但对其中的重要论争,如无极太极之辩、四七之辩、人心道心之辩、湖洛论争等,都做了探讨。对于朝鲜朝后期的儒学不同学派的争论,也以田艮斋为核心,做了一些研究,出版了两本专著。①除了对朝鲜朝儒学的重要人物的主张有所讨论外,又有一种特别的收获,从韩儒对朱子的诠释,让我对朱子学的义理形态的理解产生了变化。我本来遵从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的衡定,即朱子是心性情三分、理气二分,心通过格物穷理,而于对象处寻找对性理意义的理解。故是意志的他律,用格物穷理所得的超越所以然来规定道德的当然之理,使道德意义有所减杀。故朱子是泛认知主义的他律伦理学,而且在朱子的成德之教中,道德实践的动力是不足的。牟先生根据以上的论述,于是判定朱子为儒学的别子(程伊川是“别子为祖”,朱子是“继别为宗”),并非孔孟易庸,及周张大程等儒学义理的正宗形态。我近年从对朝鲜儒学的研究,又加上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进一步探索,似乎可以为朱子学给出不同于牟先生的衡定。我认为可以以“主理”来说明朱子的成德理论,即朱子根据人对性理本有所知,而将此性理抽出进一步了解,这就是致知格物。而这对理的了解,就是对道德法则做了解,即要明白人的真正道德行为,是由道德法则直接决定意志而产生的①。而此所谓法则对意志的直接决定,即表示人之从事道德或义务性的行为,是因为此行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只能是因为理所当然而行,才是道德的行为。如果为了别的目的而表现善的行为,此行为只有表现上的善,而没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这是孟子以来儒者以义利之辨来说明道德的共识。朱子对于道德之理意义的理解是清楚的,我们可以用“要充分明白此理,才可以给出恰当的,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的行为”来理解朱子的义理形态。而此一形态因为是根据本知的何谓道德或义务(道德之理)而做的进一步了解,故并非是从意志所对的对象来寻找道德之理。朱子的格物致知论似乎是以心知来理解性理,而显心、理为二之相。于是就会被认为是依心外之理的规定而行,此便是他律的形态。但据朱子的《大学章句》,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此明德应以心为主来理解,心具众理之具也应是本具。②据朱子《大学章句》此处的注解,明德虽然“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此表示了明德是虽然昏昧之极的人也可以有之,而且在日用中会随时表露出来,于是人就可以根据此表现在日用中的明德来做进一步的讲明。据此可以肯定朱子是认为人对于道德之理是本来就有所知的,即使没有通过格物致知,此对道德法则的了解,气质昏昧之人也可以在日用生活中了解。朱子的《大学或问》对此义有进一步的发明:“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能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此段明白表示了明德须以心为主来规定,虽然是至愚之人,此本有之明德也会有明朗的体现。据此可知朱子确主张人对于道德之理是本知的,虽然明德是具理之心,而非心即理之心,但此明德之心本具理。此本具的意思,也可以从虽昏昧之极的人,在介然之顷也可以有所觉,而本体已洞然之说来证实。即依朱子,人对于性理之知是人人本有,虽下愚者也有的。如果依此理解,则人是对道德有先验的理性知识者,此可以肯定。由以上的讨论,可知朱子确认为明德常发见于日用,是人人可知的,是以每个人都不能够自昧。所谓自昧,即以为自己不明白何谓道德之理。故朱子注语中所说的“虚灵不昧”,虚灵是指心的作用,而不昧是就理来说的。理随时都会显于心,人不能假装不知道。
由于朱子认为人心对于理有本知,故朱子的“格物补传”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是就本有的对于理之知做进一步的了解,或可说是将本知之理抽出来做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是对于本具或本知之理抽出来做进一步了解,故不能够根据心理为二,就说心要进一步求知的理,是从心所对的对象处得来。由于要进一步知之,故把心中所具之理或本具之理抽出来而成为对象。以求穷尽的了解之,固然此一形态并非心即理之意,但也不能因为心与理为二就说此理与心本来是平行为二,必须通过后天的认知才可以理解。如果是从本知之理而求进一步了解,则可以是根据随时可以显现在伦常日用中的人对于当然之理的了解为线索,并不是对性理或道德之理全无所知,而要通过格物穷理才可以知道何谓道德之理或性理。
依上说,则朱子的格物致知论或理气论,理一分殊等说,是从在人伦关系中,随时可见的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当然而不容已”之理,来推证所以然而不可易的天理①。由于这是从所当然出发,而追问其故(在明白到当然之理时,内心会有不容人不去实践的自我要求,所谓不容已)。即追问何以对当然之道德之理人会有不能不依循之来实践,何以会对此理有不容质疑的感受。能就当然处做这种追问,很自然就会认为一定有一所以然之理。而此所以然之理是存在之理,是存在之理是决定事事物物的存在者。既然是存在之理,便是最后的,确定而不可移动的。朱子此一思路,既然是从人伦活动中的当然而不容已处,推证所以然而不可易,则应该还是道德的形上学,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道德学(或伦理学)。当然,如果把朱子的理气论,及要从当然之不容已进至所以然而不可易,这种形上学的理论,理解为是为了说明当然之理是人必然要遵守的而建构,则好像是以形上学的理论来说明道德价值,于是有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嫌。如果是这样,则朱子难免于为“他律的伦理学”。但我们也可以将朱子从当然而不容已,必须进到所以然而不可易,才能稳定住人道德实践的信心,来理解这一形上学的建构。即这是为了实践上的需要,于是要把当然之理理解为所以然之理。而之所以要进这一步,除了是要以道德之理担负说明存在的责任外(此即道德的形上学),也是为了满足道德实践的要求者。即如果道德的实践只是人伦生活之理,而不是在天地间本有的、绝对普遍之理,则对于从事道德实践而体认到的此理之普遍性、无限性,是不能有充分说明的。而且如果不能进至这一步,即如果道德之理不就是普遍的,使一切存在能存在的根据,则人对于从事道德实践并不容易有不可摇动的信心。譬如在人努力实践后,遭遇到不合理的现实情况,甚至终身行道后,道仍然不能实现,此时人会有天道何在的怀疑。如果不克服此一怀疑,是否能继续努力实践,是有问题的。故必须从当然之理进至形上学理论,如孔子从四十而不惑,进至五十而知天命,才能解决此一实践上产生的怀疑。这好比康德在说明德福一致(圆善)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实现对象时,必须肯定上帝的存在。这是有实践的要求而肯定上帝,而为道德的神学。如果不做这一步的肯定,康德也认为会使人对道德实践不能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故朱子的格物致知论,要从当然而不容已之理,进至所以然而不可易,也是由实践上的要求,而以形上学的理论给出的理之必然来稳定住人实践道德的信念。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思辨的形上学来做道德实践理论的根据。
如上说不误,即所当然的实践上的肯定,是所以当然的依据。于是实践的要求,是先于形上学的理论者,则朱子的形态,如同康德所说的,是从道德法则或以道德法则为先来理解何谓无条件的实践。即从人对道德法则本有所知或本明处来理解何谓道德实践。对于此法则愈了解,当然便愈会要求自己从事无条件的道德实践。对于道德法则本身所含的意义,如果能够做充分的了解,当然会引发人的道德意识,而逐渐排除感性欲望的影响,要求自己纯然的按理而行。此一明理的过程也应该就是纯净化自己的生命的过程。除了这种形态之外,依康德,也可以从自由意志或以自由意志为先来理解何谓无条件的实践①。而此后一形态,应该就是孟子、陆王的说法,如阳明说“致知存乎心悟”,或王龙溪所说的“从心悟入”②,就是以自由意志为先,来明白何谓无条件的实践。如果程朱陆王的不同,只是从理(法则)或从本心、良知(自由意志)来体会何谓道德行动的不同,则程朱陆王的不同,并非对于何谓道德有不同的理解,只是就成德之教的入路不同。二系可以同为有效的成德之教的理论形态。二系的工夫论对于人的成德,都是有效的。③当然在此处也需要思考朱子的成德理论是否属于他律的形态,如果属于他律的道德学,则依康德的说法,他律是假的道德之源。如果朱子是他律的形态,则不可能有真正成德的效果。而依上文所说,格物穷理所显示的心理为二之相,是在将本知之理抽出来做进一步了解而产生的,而不是心对于理毫无所知,要在事事物物中寻找何谓道德之理。如果是后者的情况,当然是会以空泛的所以然之理来规定道德之理,如此对道德之理的理解应该是不切的,但假如是从本知之理而做进一步的了解。而此本知之理是从当然而不容已处来体证的,所以要格物穷理是要对此理做更进一步的了解,从实践的不容已的要求而进至对此理何以是必然而且是真实的做一论证。故是道德的形上学,则不能因为心理为二就说其为他律的伦理学,此依本知之理或进一步穷理而真知之理来实践。由于是依道德之理(即为义务而义务之理)或让当然之理直接决定人的意志,要人只因为理的缘故而从事实践,则此实践行动当然是道德实践,因为是按照无条件律令的道德之理而实践之故。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仍然是他律性的行动呢?这必须深思,固然此时是心按照道德法则而行,心与理仍然是二。因为此心并不是道德之理的纯然流露,也可以说是心接受理的要求或责成,而要努力勉强的按理而行。但这种情况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道德实践的感受,而当在本心出现时,通过逆觉体证,让本心充分体现,如如之心就是如如之性或理,心与理完全是一,心之活动就是理的体现而不是心按照理的规定而行的情况。这当然也是最真实的道德活动的体现,而且是其中所表现的道德行动是自然而然,毫无勉强的。但如果以这种自然而然的表现道德行为的境界才是自律的道德,而勉强依理而要求自己努力实践,则是他律的,不算是道德行为。则恐怕此自律的规定太严格,境界也太高。①康德虽然肯定意志的自我立法才是自律,但人在从事道德实践时,也只能勉强的责成自己去服从义务,在神圣意志处,则是不用责成的。人并非神圣意志者,而且自由意志只是设准而不是具体的,故依康德,人在从事道德实践时,道德法则与实践的主体并不能是一。如此一来,康德所主张的真正道德实践,难道是人从来都不能产生过吗?人自以为从事道德实践,虽然其所依据的道德法则是自己给出来的,但法则与实践的主体并不是一,是以会有责成、勉强的情况,难道这仍然是他律的形态吗?如果是他律就是假的道德行动了,这一判断应该不对,或者过严了。②此依自己给出的道德法则努力实践,不断要求自己的发心动念要符合道德法则,这应该就是道德实践了。依此而行,人就可以成德。如果此说可通,则朱子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工夫论应该是儒家成德之教一可行的理论形态。
这是我近年由于研究韩国儒学,而对当代儒学、康德哲学融会而产生的一点收获。顺着这一线索,以下希望能概括叙述一下我对朝鲜朝儒学发展的一些理解,特重其中一些论辩所显出的哲学含义。
二、朝鲜朝儒学主理主气两系的区分
日人高桥亨对朝鲜朝儒学区分为主理与主气两派,用此来说明李退溪与李栗谷二人的不同形态,及依循此两义理形态而发展的两系。这一区分可能过简,在义理形态的区分或内容的说明上或有不恰当处,如栗谷虽然主张气发理乘一途之论,但并非主张唯气论或以气为本体(徐敬德花潭才是以气为本体,栗谷对于花潭虽有欣赏,言其有自得之味,但并不赞成其气论)。依栗谷,理仍然是天下之大本,为气化之根柢。而退溪虽主张四端是理发,但也不得不承认理发而气随之,即四端有气的活动在。而七情虽然是气发,但也不能没有理,故曰气发理乘。即退溪对于有理即有气,有气即有理,理气二分而不离之义,也必须承认。高桥氏此说近年很受韩国学界及台湾研究韩国儒学的专家(如林月惠、李明辉等)的批评,认为此一区分并不合理。但我认为此一区分仍有其方便处,只要明白主理主气区分是相对比较而言,并非一以理为本体,一以气为本体。而且主理主气这一区分本来也是朝鲜儒者所使用过的概念,并非高桥氏的发明。如郭钟锡(号俛宇)就称其老师李寒洲及自己的主张为“主理”,而批评“主气”之论。①又朝鲜朝的儒学派别及论争很多,用主理与主气来概括,当然是犯了太简约的毛病(如郑霞谷的阳明学也持论深入,不能归在主理主气两系),但虽如此,这两系也的确是朝鲜儒学史上最显著的两派,用来概括程朱理学在韩国的发展,应该也能明白表意。
退、栗二系虽然都遵从朱子的理气论,但退溪强调了在道德情感的活动中理的作用,而栗谷则认为善情之生发,是由于清气。在此关键的问题上主张之不同,以主理与主气来区别,确能表意。此关键问题是对道德实践何以可能说明问题,依退溪或主理一系,实践之可能根据在于理在心有直接的作用,而栗谷或主气一系实践的根据在于人具有本然之气,只要通过养气就可以使气恢复为本然,而本然之气是所谓清气,善是清气之发。
三、李退溪四端为理发之说的哲学含义
退溪主张孟子所说的四端,一定是理发,而且主张四端是从中而发。此说表面引用朱子的说法为据,但他主要的论据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提出的,其论证很有哲学性,能够表达出有他对道德或性理的理解。他认为四端据孟子,是纯善的。而如果四端为纯善,则四端一定是纯理而发,不能夹杂有任何气的成分,这是从四端的纯善而推论出使四端生发的根源只能是理。此一想法如果用康德所说的道德行为是由道德法则直接决定意志而产生,就很明白。道德行为不能是为了其他缘故而行的行为,只能是因为此行为该行而行,这就表示产生此行为的意志只因为该行为是该行而行。而此该行而行的想法就是只因为理所当然之故,故可以说此时的意志是为道德法则所直接决定。而所谓道德法则须从孟子所谓的义利之辨来了解,即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只因为理所当然而行,不能为了其他的缘故或条件,此如康德所说道德法则是无条件的,为定然的律令。李退溪所说的理发如果从法则直接决定意志来了解,就可以说得清楚,而且不必进一步说退溪肯定心即理。法则直接决定意志可以只从人去给出行动的时候,只因为理所当然而行。这虽表现了理的直接决定性,但并不必含理本身是活动的,即只需说心因为而且是只因为理的缘故而行,就是理发了。在恻隐之心,或情上见出这是只因理而发,而不是理本身有发用。①因为此时心或主体除了为了理之外,没有因为其他而给出行动,于是法则或理是心给出行动的动力,虽然此动力不一定就是心本身提供的,理在心之外,心的虚灵明觉不即是理。但只要心只因为理而行,则理对于心也可以说是给出了动力,可能如此解既表示了理发说所含的法则是意志的直接决定之义外,又不必将退溪学理解为往心学靠近。对于心与理的不同,退溪并非不清楚,他虽然认为心是理气合(此是陈淳的说法),但这是表示理在心中为心所本知,而且心的做意或决定行动可以纯因理而发。故理发在退溪应是理在心中有其发用之意,而所谓理在心中有其发用是心纯依理而发。
另外,退溪所说四端从中而出,七情从外而发,此一区分也有其道理,他这样区分就表示了四端等的行动是由自己决定而给出来的。固然恻隐之发必须要因应对象而后有,但并非所看到的对象决定了人给出恻隐之心或恻隐之情。此恻隐是自发自觉,即自己决定而给出来,才产生的,并非由外在的对象决定。故孟子分析恻隐之心时表示了此心并非因其他的目的、条件而发,只是内心感觉到非要如此不可而发,孟子此一分析也等于是康德所说真正的道德行为必须从自由意志发出来之意。由于道德行为是法则直接决定意志而给出来的,故此给出道德行为的意志只能是因为理所当然而行。此时的意志并不能受任何其他的因素影响,故虽然恻隐是见孺子入井而发,但所以要给出这恻隐与其后的往救孺子的行动,也是意志自己决定的,并不是受其他原因影响而产生的他律性的,或因着刺激而一定有反应的行为。明白此真正道德行为是出于自由意志之义,就可知退溪所说“四端从中而发”是一定要有的讲法。
四、栗谷的反对理发说与其从理气不离而阐发的特殊见解
由上述可知,退溪的四端理发说很能表达出道德行为的特性。由于是如此,故可说退溪之说有其不易摇动的立论基础。当然栗谷对退溪主张的反对也有其论据,也相当能够服人。栗谷认为如果四端是理发而气随,七情是气发而理乘,则理气就有时间上的先后或离合可讲。如果理气有离合有先后,就不能够说明天地生化,因为假如四端是理先发,则理发时便无气,而七情是气先发,则此时便无理。故此说表示了理气有先后,而且这样一来也会有理气可以分开,然后再合起来之义,这是所谓理气有离合。如果理气有先后离合,则气化的活动可以不以理做根据,而理可以超然独立,不需要气来表现其意义或作用,这是不通的。栗谷此说哲学性很强,当然此所谓哲学性是就宇宙论、形上学的意义来说。可以说栗谷在客观面形上学或存有论的理论上特别有明白的分析,从宇宙论上看,当然是理气不能离的,如果理气不离,则四端七情的生发,就不能有此先发彼跟随的区别,只能说有理就有气,有气就有理。而如果从此一宇宙论或理气论的观点来做标准,四端七情都只能是气发而理乘,即发是气发,气之发处都有理为根据,理无所不在,一切气化流行都有理作为根柢,不能有气自发而没有理的可能,也不能有理独行而不借着气的情况。但这样一来,四端七情就不能有意义上的或层次上的区分,故奇高峰及李栗谷都认为七情是总说全部的情,四端是七情中的善情,故说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这在宇宙论上说是很合理的,但不能表达意志为法则所直接决定而有自由自决之义。这可以看出宇宙论的理论对于道德行动的说明是有问题的,此所以康德认为在道德行动上所必须肯定的自由,与从自然因果上必须肯定的因果必然性是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因果的必然性对于经验事实的说明为必须,就否定了道德实践所要肯定的意志自由。这两者都要成立,而且在二者相冲突时,理性的实践应用应该是可以优先的,即不能因为理性的理论应用不能肯定自由(由于事出必有因,在因果的必然关联下,不能有自由),就认为道德实践上所必须有的自由不能成立。依此意,吾人可说,虽然在宇宙论理气论的理论上对于存在界的说明不能够主张理先发或理独自发用,但从人的道德实践必须按理而发排拒其他影响,此意上说需肯定理独自的作用。这也可以用实践理性的优先性来解决栗谷的质疑,如果认为不必因为栗谷的质疑就否定了四端由纯理而发,则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虽然可以说明宇宙气化活动的情况,但并不能用来说明道德实践的活动,从能否说明道德实践活动的真义,就可以看出退溪主理、栗谷主气这一区分的意义。主气之说就是由于主张有气即便有理,而否认了理的独立作用,而主理就是从道德实践的体会处肯定理非直接决定意志不可,虽然主气论不否认理作为存在的根据,但在道德实践上对于道德上的善产生只能从因为气清所以理得以实现来解释。道德的善如果由于气清才可能,不是由气决定吗?故说栗谷一系为“主气”,其实未尝不可,而且如此说就可以看出栗谷一系对于道德实践的意义及其真实的可能说明不够,甚至很不成功。即如果“善者清气之发”①,如果为善是靠清气才可能,则性理的作用或动力就不能说了。当然栗谷对退溪理发说的批评如前文所说,在宇宙论的理论上是非常合理的,于朱子的理气论也有根据,因为理是不活动的,活动者是气,则理气的关系应如栗谷所说。故退溪与栗谷此一不同的主张,在朝鲜朝儒学中栗谷是占上风的。
栗谷对于理气不离很有体会,由此而有一些特别的见解阐发出来,既然善是清气之发,则成德的要点在于养气,即恢复气之本然。他认为气有湛一清虚的本体,如果维持或恢复此气之本然,性理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表现出来。如果气质有清浊厚薄的不齐,则理虽然清通,也只能表现有善恶参差的情况。这是栗谷的工夫论要点。由于理气不离,而且理通气局,故栗谷认为不合理处也应当有理,这是他对于程子所说的理有善恶的说明。另外由于理气之不离而气是有聚散变化的,故栗谷认为现在所见的天地(也可以说是世界或宇宙)已经生灭了许多次。此即其天地有无限生灭说,因为理是不能没有的恒常存在,而有理即有气,故气也是常存的。既然气是常存,但有聚散变化,而天地是气化所组成的,则天地一定经历过许多次的聚散变化,故吾人所处的天地一定已经生灭过多次。此一见解非常有哲学的深度,可以为有聚散变化的天地何以要存在,及对人类文明的存在既然是不能常存的,则其存在有何意义的问题给出一个说明。即人类文明虽然可以毁灭,但既然有理便必有气,天地可以有无穷生灭,人类的文明也可以有无限次的存在。这是生灭与不生灭综合起来的宇宙观。生灭可以容易推出其存在是可有可无的,即其存在并非必然的存在,但假如有生有灭是由恒常存在之气所构成,而且又由恒常之理作为生灭的根据,则此生而又灭的存在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故可说既生灭又是不生灭。于是人生的存在固然是有生有灭的暂时存在,但又可以体现出永恒的理的意义。于是人世间之存在为不能没有的,即其存在是有理上的必然性,这也是可以说的。这也可以用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即有限而无限”之意来说明。
五、奇芦沙主理论证中的道德含义
奇正镇(号芦沙,1798—1879)对于栗谷的说法,甚不以为然,晚年正式提出反对的见解。芦沙论证理为气之主宰,故理是有尊位的,而认为栗谷的理气论使理好像成为附骥尾的存在,可有可无。他认为圣贤典籍历来都主张理是气的主宰,则理一定有他的主宰性,无论气的作用如何强大,但都必须接受理的主宰。如果可以如此说,则理的主宰性如何表现呢?芦沙于此就给出了理完全不借着气,但有其主宰性的力量之说。他论证理为气之主宰,气不能决定理,如云理之乘气是原来所乘,并非气来而后理乘之。又说天地间虽看起来都是气在作用、活动,但气之所以能如此,是有看不见的理给出决定。故看到气的活动,就如同看到理的主宰性或决定性。如同贵人乘坐马车出游,我们看到马车在走动时,虽然看不到贵人的活动,但由于有贵人的决定,才会有马车及马车上马夫的种种活动。此譬喻是说,理的决定性虽然没有在气的活动中被看到,但其实是理主宰着气。没有贵人的发号施令,可见的马车活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此如同没有理的给出主宰,气化的活动是不可能的。于是不能因为只看到形而下的气在活动,于是认为无形的理只能靠气才能表现其作用,或认为理的作用受到气的限制。此明白地反对栗谷的“理通气局”说。芦沙又认为理的做主之作用,完全不藉赖气的能力,单靠理本身的力量,就可以给出主宰性的、根本的作用。他举例说,西汉末的更始帝,才智平庸,只因为他姓刘,就被拥立,称帝了一段时间。这就譬喻单只是理而没有气的作用,就可以给出主宰的力量。对于理一分殊的意义,芦沙也做了特别的诠释。他认为理本身就含着分殊,并不是理之一因为气的作用,而成为分殊之理,各存在物都是由理作为根据。故处处都表现了理的意义,这是理的分殊。而分殊之理其实都是理,其为理,一也。故分殊之理就是理之一,而不是先有理一,因为气的局限,而成为分殊之理。芦沙这些证明理为气之主宰,理一定有其作用,虽然其作用于气的活动变化中看不出来,这些论辩都很有精思。
而理的主宰既然完全不借着气,则如何去理解这种主宰性呢?我认为必须通过道德实践的无条件性来理解理的作用,如上文所说,道德法则对于意志有直接的决定性,即我们只能纯粹为了理所当然之故而行,完全不为其他,才可以给出真正的道德行动。这是我们稍微反省何谓道德义务就一定明白的道理。既然是如此,则道德的行为动机假如掺杂了一点感性的欲望、气性的要求,那就不能是道德的行动了。这就可以说明愈没有气的作用愈会有道德的理的意义,能够给出真正的道德行为完全或只能是因为理的缘故,这样不是就可以说明理的力量或作用了吗?理的作用是单靠他自己就可以成为道德行动的动机或存心,而只能够是以纯理(或纯粹理性)作为行动的动机或原则,才可以给出具有真正道德价值的行为。掺杂了一点感性的欲求的话,那么无条件的道德行为就成了有条件的、有所为而为,于是该行动的道德价值就会全部消失无踪了。从这一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芦沙对于理必有作用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他的论证是很有效力的,在人愈能拒绝感性的作用干扰时,愈可以显出理的主宰性。而如果理能显出这种纯粹的、不依于气的主宰性,就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行为,这一论证除了说明道德之理是无条件的法则,单靠其自己就可以决定意志而成就道德行为之外,也可以说明理不需要像气一般的活动,而可以使表面有最大力量的气也需要服从的缘故。
人如果通过内省,而发现自己的行动是于理不合时,则不管他地位多高、有多大的势力,也不免惭愧内疚。于是理的作用在人知理的时候,就会给出来。如果是这样,则理是否有活动性,便不是能否产生真正道德行为的关键。道德之理只靠他自己,就可以产生动力,不必有实际的活动性,才可以产生使人依循之而产生的力量。依此意,则理即使为存有而不活动,照样可以提供实践的动力。当然,此动力的产生,如同康德所说,是法则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影响力,此时行动的主体必会产生对于道德法则的尊敬。由尊敬而接近法则,而给出实践的行动。
六、寒洲学派与华西学派对主理说的发展
李震相(号寒洲,1818—1885)有“心即理”说,他认为心的本体是理,而其外表的作用是气。如同和氏璧的情况,即外表是石,里头是玉。他如此规定心,就表示心不能只从气来理解,理是作为心的本质,于是也有它的作用表现。如心统性情之“统”,就是理的作用。他又用“理一”与“分殊”的不同,来区别“心之统”所表现的“理”与他所统的“性”,也有其精思。李华西则认为心可以以理言与以气言,又认为明德是理,都表示了理有其作用。寒洲与华西两派对理的理解,都强调了理本身就有其作用,其作用可以从心的活动中直接体会到。他们虽然不能如陆王直接以心为理,但也可以说是往心即理趋近。田愚(号艮斋,1841—1922)对于这两派的主张都加以反对,认为如此说心,使心与理的界限不清,不能够让理维持作为实践的标准之义,也会引发心的僭越、自主。艮斋认为这是违反传统儒学大义的,他认为儒学的第一义是肯定心性为二、“性师心弟”才是儒学的合理主张。本来按照儒学成德之教的要求,能够给出一个人人都能自发的为善根据,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所以然之理,如果只是静态的,则是否能够给出实践的真实动力呢?由于这一思考或要求,退溪主张理发,而寒洲、华西主张理有它实在的作用,也是合理的。当然,如果透过奇芦沙的论证,说明理的作用或力量由于是单靠理而给出的,不依于任何有形可见的气化作用,顺着此一论证,则理应该可以不用活动,就能给出其对气的主宰性。而如果通过道德法则的含义来理解,如上文所说,道德法则是对意志给出直接的、无条件的决定者。既然是无条件的决定,则任何现实可见的作用,或功效、利益,都不必加进来,作为理的力量构成要素。相反,越理解道德之理的无条件性,就越可以排除一切有形的或对人的感性有吸引力的种种现实作用,来直接肯定理本身的力量。越能拨开现实有用的想法,越能理解道德法则的力量。我们的存心越能纯粹,就越会遵守此一以无条件的律令颁布的道德法则。如此理的主宰性力量,就不必借着活动才能起用。这应该就是朱子所谓“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①之意。理的这一种不藉任何其他功能就可以独立起用的意思,越了解之,越会让人肃然起敬。故理所当然之理,当然有他的力量。
七、主气派所提出的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结穴于田艮斋气体本清说
朝鲜儒学主气派的李栗谷一系,固然不能给出上文所说的理作为实践动力的说明,但也有其他的贡献,对于理解朱子学的义理形态也有帮助。栗谷系的学者大都认为心虽然是气,但心之为气,是气之精者。栗谷肯定有气之本然,或本然之气,即肯定了人生命中有本来清明的气之本体。如果人能检束其气(心气),就可以恢复气之本然,即恢复清明的气之本体。而善是从清气发生出来的,故如果人有本然的清气本体,则只要通过养气,就可以恢复清气而为善。此一对人本有清气之本体的肯定,也可以作为人人可以为善的超越根据。栗谷此说为后来的李柬(巍岩)所强调,吴熙常(老洲)认为心气是清明而与理无间的,也应是承此义而发展。到朝鲜朝最后期的田艮斋,则正式提出“气质体清”之说,认为人在其生命开始时所禀受到的气,是有清明的气之本体在其中的,此气之体并不会因着后天的活动变化而失去。此一肯定可能也可以说明朱子学所以重视涵养之故,即人如果能有涵养的功力,本有的清明气之体就可以出现。此所谓“才歇即清”,而人就可以为善。当然对于此气之本体的肯定与证成恐怕有困难,而且善的行为如果是由清气而有,如栗谷所说的,“善者,清气之发”,则性理的作用恐怕太弱化,也不能说明何以在见孺子入井的情形下,人人都会有要求自己无条件地往救孺子之想法。这是无分于气性清浊之人都会有自我要求,此一问题在艮斋的弟子继续有所讨论。
田艮斋的思想以“性师心弟”为主旨,他认为性理是标准。标准是不能变化的,故性理不会活动。艮斋此说给出了性理是不活动的理由。心是活动,故心是气。但心之为气是虚灵的,故“心可以学性”。从心之虚灵与心可以明理,也可以说心是善的,但心虽然善,会流于恶,因为心是会变化的。这是艮斋承继吴老洲所说的“心本善而不可恃”之义。既然心之虚灵可以学性而为善,但不可恃,则心对性的态度应该是如同学生以恭敬的态度来从师问学一样。心自居为弟子,事事以性理为遵从的标准,不敢自以为是,即弟子永远以老师为学习对象。艮斋认为心这种对性理的态度是最恰当合理的,如果心以为自己就是理,那就是僭越。他认为人间的种种毛病都是由于心的妄自尊大,僭越了性理的位置而产生。艮斋此说大略同于上文所说康德论尊敬的意思,也表达了心性为二的必要,即如果太强调心性是一,会引发人的骄傲自大。另外,从“心学性”之义,也给出了朱子一系学者所以强调读书明理的说明。即由于心虽然可以通彻于理,但心之虚灵并不等于是理。心会活动变化,故对于本来知道的道德之理不一定能持守,在这种情形下,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必要的。朱子强调读书以明理,虽然也涉及一草一木之理,但还是以求知道德之理为主的。而对于道德之理的了解,从“心学性”之言,也可以说明读书的必要。即心若以性为学习对象的话,则读书就可以作为明理学习的好方法。故艮斋的说法既说明了心性为二的必要,也说明了读书在心性为二的系统下是必要的。
通过上述对朝鲜儒学两系义理的分析,可知朝鲜的性理学虽然以朱子思想为主,但并非只重复朱子本有的义理内容,而是有进一步发展的。而通过他们的有关论辩,可以看出其中有许多很有哲学意义的理论发明。而最重要的是可以给出对朱子思想的不同的诠释,如栗谷一系对朱子学的理解,很接近当代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的诠释,但虽相近,也有不同。如上文所说,从李栗谷到田艮斋,都肯定心虽然是气,但作为气之灵的心并非一般的形气,而是可以通彻于理的,只要维持本性是清虚的气之本然,或本清的气体,就可以表现善的行为。这是主气一系对于成德如何可能,给出一个说明,即肯定了人人都有成德的超越根据。只是从气体本清来保证成德人人可能,论证不够坚强,而且如果道德的善行由于清气而有,则道德实践所必须的意志的自我立法、自觉、自由等义,就比较不好说了。而主理的退溪、芦沙、寒洲、华西一系,则突显了理必须有其作用,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之义。此系的理论对于说明朱子学,我认为特别有贡献,可以参考他们的理解,重新诠释朱子学。或许可以用主理的观点来理解朱子学的形态,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如果这一诠释可通,则朱子系(包括程伊川及朱子的重要弟子)的义理,应可与陆王系并列,而为儒家成德之教的两个可行的理论形态。
从1990年起,我因为应韩国友人的邀约,参加有关韩国朝鲜朝儒学的会议,开始阅读有关的文献,理解到朝鲜朝儒学虽然以朱子的性理学为主,但内容十分丰富,对朱子一系的义理问题有细密的讨论,并有新的发展。这一部分的文献,应该是研究宋明理学者不能不注意的。对于朝鲜朝的儒学发展,我的研究虽然不够详细,但对其中的重要论争,如无极太极之辩、四七之辩、人心道心之辩、湖洛论争等,都做了探讨。对于朝鲜朝后期的儒学不同学派的争论,也以田艮斋为核心,做了一些研究,出版了两本专著。①除了对朝鲜朝儒学的重要人物的主张有所讨论外,又有一种特别的收获,从韩儒对朱子的诠释,让我对朱子学的义理形态的理解产生了变化。我本来遵从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的衡定,即朱子是心性情三分、理气二分,心通过格物穷理,而于对象处寻找对性理意义的理解。故是意志的他律,用格物穷理所得的超越所以然来规定道德的当然之理,使道德意义有所减杀。故朱子是泛认知主义的他律伦理学,而且在朱子的成德之教中,道德实践的动力是不足的。牟先生根据以上的论述,于是判定朱子为儒学的别子(程伊川是“别子为祖”,朱子是“继别为宗”),并非孔孟易庸,及周张大程等儒学义理的正宗形态。我近年从对朝鲜儒学的研究,又加上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进一步探索,似乎可以为朱子学给出不同于牟先生的衡定。我认为可以以“主理”来说明朱子的成德理论,即朱子根据人对性理本有所知,而将此性理抽出进一步了解,这就是致知格物。而这对理的了解,就是对道德法则做了解,即要明白人的真正道德行为,是由道德法则直接决定意志而产生的①。而此所谓法则对意志的直接决定,即表示人之从事道德或义务性的行为,是因为此行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只能是因为理所当然而行,才是道德的行为。如果为了别的目的而表现善的行为,此行为只有表现上的善,而没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这是孟子以来儒者以义利之辨来说明道德的共识。朱子对于道德之理意义的理解是清楚的,我们可以用“要充分明白此理,才可以给出恰当的,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的行为”来理解朱子的义理形态。而此一形态因为是根据本知的何谓道德或义务(道德之理)而做的进一步了解,故并非是从意志所对的对象来寻找道德之理。朱子的格物致知论似乎是以心知来理解性理,而显心、理为二之相。于是就会被认为是依心外之理的规定而行,此便是他律的形态。但据朱子的《大学章句》,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此明德应以心为主来理解,心具众理之具也应是本具。②据朱子《大学章句》此处的注解,明德虽然“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此表示了明德是虽然昏昧之极的人也可以有之,而且在日用中会随时表露出来,于是人就可以根据此表现在日用中的明德来做进一步的讲明。据此可以肯定朱子是认为人对于道德之理是本来就有所知的,即使没有通过格物致知,此对道德法则的了解,气质昏昧之人也可以在日用生活中了解。朱子的《大学或问》对此义有进一步的发明:“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能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此段明白表示了明德须以心为主来规定,虽然是至愚之人,此本有之明德也会有明朗的体现。据此可知朱子确主张人对于道德之理是本知的,虽然明德是具理之心,而非心即理之心,但此明德之心本具理。此本具的意思,也可以从虽昏昧之极的人,在介然之顷也可以有所觉,而本体已洞然之说来证实。即依朱子,人对于性理之知是人人本有,虽下愚者也有的。如果依此理解,则人是对道德有先验的理性知识者,此可以肯定。由以上的讨论,可知朱子确认为明德常发见于日用,是人人可知的,是以每个人都不能够自昧。所谓自昧,即以为自己不明白何谓道德之理。故朱子注语中所说的“虚灵不昧”,虚灵是指心的作用,而不昧是就理来说的。理随时都会显于心,人不能假装不知道。
由于朱子认为人心对于理有本知,故朱子的“格物补传”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是就本有的对于理之知做进一步的了解,或可说是将本知之理抽出来做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是对于本具或本知之理抽出来做进一步了解,故不能够根据心理为二,就说心要进一步求知的理,是从心所对的对象处得来。由于要进一步知之,故把心中所具之理或本具之理抽出来而成为对象。以求穷尽的了解之,固然此一形态并非心即理之意,但也不能因为心与理为二就说此理与心本来是平行为二,必须通过后天的认知才可以理解。如果是从本知之理而求进一步了解,则可以是根据随时可以显现在伦常日用中的人对于当然之理的了解为线索,并不是对性理或道德之理全无所知,而要通过格物穷理才可以知道何谓道德之理或性理。
依上说,则朱子的格物致知论或理气论,理一分殊等说,是从在人伦关系中,随时可见的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当然而不容已”之理,来推证所以然而不可易的天理①。由于这是从所当然出发,而追问其故(在明白到当然之理时,内心会有不容人不去实践的自我要求,所谓不容已)。即追问何以对当然之道德之理人会有不能不依循之来实践,何以会对此理有不容质疑的感受。能就当然处做这种追问,很自然就会认为一定有一所以然之理。而此所以然之理是存在之理,是存在之理是决定事事物物的存在者。既然是存在之理,便是最后的,确定而不可移动的。朱子此一思路,既然是从人伦活动中的当然而不容已处,推证所以然而不可易,则应该还是道德的形上学,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道德学(或伦理学)。当然,如果把朱子的理气论,及要从当然之不容已进至所以然而不可易,这种形上学的理论,理解为是为了说明当然之理是人必然要遵守的而建构,则好像是以形上学的理论来说明道德价值,于是有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嫌。如果是这样,则朱子难免于为“他律的伦理学”。但我们也可以将朱子从当然而不容已,必须进到所以然而不可易,才能稳定住人道德实践的信心,来理解这一形上学的建构。即这是为了实践上的需要,于是要把当然之理理解为所以然之理。而之所以要进这一步,除了是要以道德之理担负说明存在的责任外(此即道德的形上学),也是为了满足道德实践的要求者。即如果道德的实践只是人伦生活之理,而不是在天地间本有的、绝对普遍之理,则对于从事道德实践而体认到的此理之普遍性、无限性,是不能有充分说明的。而且如果不能进至这一步,即如果道德之理不就是普遍的,使一切存在能存在的根据,则人对于从事道德实践并不容易有不可摇动的信心。譬如在人努力实践后,遭遇到不合理的现实情况,甚至终身行道后,道仍然不能实现,此时人会有天道何在的怀疑。如果不克服此一怀疑,是否能继续努力实践,是有问题的。故必须从当然之理进至形上学理论,如孔子从四十而不惑,进至五十而知天命,才能解决此一实践上产生的怀疑。这好比康德在说明德福一致(圆善)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实现对象时,必须肯定上帝的存在。这是有实践的要求而肯定上帝,而为道德的神学。如果不做这一步的肯定,康德也认为会使人对道德实践不能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故朱子的格物致知论,要从当然而不容已之理,进至所以然而不可易,也是由实践上的要求,而以形上学的理论给出的理之必然来稳定住人实践道德的信念。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思辨的形上学来做道德实践理论的根据。
如上说不误,即所当然的实践上的肯定,是所以当然的依据。于是实践的要求,是先于形上学的理论者,则朱子的形态,如同康德所说的,是从道德法则或以道德法则为先来理解何谓无条件的实践。即从人对道德法则本有所知或本明处来理解何谓道德实践。对于此法则愈了解,当然便愈会要求自己从事无条件的道德实践。对于道德法则本身所含的意义,如果能够做充分的了解,当然会引发人的道德意识,而逐渐排除感性欲望的影响,要求自己纯然的按理而行。此一明理的过程也应该就是纯净化自己的生命的过程。除了这种形态之外,依康德,也可以从自由意志或以自由意志为先来理解何谓无条件的实践①。而此后一形态,应该就是孟子、陆王的说法,如阳明说“致知存乎心悟”,或王龙溪所说的“从心悟入”②,就是以自由意志为先,来明白何谓无条件的实践。如果程朱陆王的不同,只是从理(法则)或从本心、良知(自由意志)来体会何谓道德行动的不同,则程朱陆王的不同,并非对于何谓道德有不同的理解,只是就成德之教的入路不同。二系可以同为有效的成德之教的理论形态。二系的工夫论对于人的成德,都是有效的。③当然在此处也需要思考朱子的成德理论是否属于他律的形态,如果属于他律的道德学,则依康德的说法,他律是假的道德之源。如果朱子是他律的形态,则不可能有真正成德的效果。而依上文所说,格物穷理所显示的心理为二之相,是在将本知之理抽出来做进一步了解而产生的,而不是心对于理毫无所知,要在事事物物中寻找何谓道德之理。如果是后者的情况,当然是会以空泛的所以然之理来规定道德之理,如此对道德之理的理解应该是不切的,但假如是从本知之理而做进一步的了解。而此本知之理是从当然而不容已处来体证的,所以要格物穷理是要对此理做更进一步的了解,从实践的不容已的要求而进至对此理何以是必然而且是真实的做一论证。故是道德的形上学,则不能因为心理为二就说其为他律的伦理学,此依本知之理或进一步穷理而真知之理来实践。由于是依道德之理(即为义务而义务之理)或让当然之理直接决定人的意志,要人只因为理的缘故而从事实践,则此实践行动当然是道德实践,因为是按照无条件律令的道德之理而实践之故。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仍然是他律性的行动呢?这必须深思,固然此时是心按照道德法则而行,心与理仍然是二。因为此心并不是道德之理的纯然流露,也可以说是心接受理的要求或责成,而要努力勉强的按理而行。但这种情况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道德实践的感受,而当在本心出现时,通过逆觉体证,让本心充分体现,如如之心就是如如之性或理,心与理完全是一,心之活动就是理的体现而不是心按照理的规定而行的情况。这当然也是最真实的道德活动的体现,而且是其中所表现的道德行动是自然而然,毫无勉强的。但如果以这种自然而然的表现道德行为的境界才是自律的道德,而勉强依理而要求自己努力实践,则是他律的,不算是道德行为。则恐怕此自律的规定太严格,境界也太高。①康德虽然肯定意志的自我立法才是自律,但人在从事道德实践时,也只能勉强的责成自己去服从义务,在神圣意志处,则是不用责成的。人并非神圣意志者,而且自由意志只是设准而不是具体的,故依康德,人在从事道德实践时,道德法则与实践的主体并不能是一。如此一来,康德所主张的真正道德实践,难道是人从来都不能产生过吗?人自以为从事道德实践,虽然其所依据的道德法则是自己给出来的,但法则与实践的主体并不是一,是以会有责成、勉强的情况,难道这仍然是他律的形态吗?如果是他律就是假的道德行动了,这一判断应该不对,或者过严了。②此依自己给出的道德法则努力实践,不断要求自己的发心动念要符合道德法则,这应该就是道德实践了。依此而行,人就可以成德。如果此说可通,则朱子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工夫论应该是儒家成德之教一可行的理论形态。
这是我近年由于研究韩国儒学,而对当代儒学、康德哲学融会而产生的一点收获。顺着这一线索,以下希望能概括叙述一下我对朝鲜朝儒学发展的一些理解,特重其中一些论辩所显出的哲学含义。
二、朝鲜朝儒学主理主气两系的区分
日人高桥亨对朝鲜朝儒学区分为主理与主气两派,用此来说明李退溪与李栗谷二人的不同形态,及依循此两义理形态而发展的两系。这一区分可能过简,在义理形态的区分或内容的说明上或有不恰当处,如栗谷虽然主张气发理乘一途之论,但并非主张唯气论或以气为本体(徐敬德花潭才是以气为本体,栗谷对于花潭虽有欣赏,言其有自得之味,但并不赞成其气论)。依栗谷,理仍然是天下之大本,为气化之根柢。而退溪虽主张四端是理发,但也不得不承认理发而气随之,即四端有气的活动在。而七情虽然是气发,但也不能没有理,故曰气发理乘。即退溪对于有理即有气,有气即有理,理气二分而不离之义,也必须承认。高桥氏此说近年很受韩国学界及台湾研究韩国儒学的专家(如林月惠、李明辉等)的批评,认为此一区分并不合理。但我认为此一区分仍有其方便处,只要明白主理主气区分是相对比较而言,并非一以理为本体,一以气为本体。而且主理主气这一区分本来也是朝鲜儒者所使用过的概念,并非高桥氏的发明。如郭钟锡(号俛宇)就称其老师李寒洲及自己的主张为“主理”,而批评“主气”之论。①又朝鲜朝的儒学派别及论争很多,用主理与主气来概括,当然是犯了太简约的毛病(如郑霞谷的阳明学也持论深入,不能归在主理主气两系),但虽如此,这两系也的确是朝鲜儒学史上最显著的两派,用来概括程朱理学在韩国的发展,应该也能明白表意。
退、栗二系虽然都遵从朱子的理气论,但退溪强调了在道德情感的活动中理的作用,而栗谷则认为善情之生发,是由于清气。在此关键的问题上主张之不同,以主理与主气来区别,确能表意。此关键问题是对道德实践何以可能说明问题,依退溪或主理一系,实践之可能根据在于理在心有直接的作用,而栗谷或主气一系实践的根据在于人具有本然之气,只要通过养气就可以使气恢复为本然,而本然之气是所谓清气,善是清气之发。
三、李退溪四端为理发之说的哲学含义
退溪主张孟子所说的四端,一定是理发,而且主张四端是从中而发。此说表面引用朱子的说法为据,但他主要的论据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提出的,其论证很有哲学性,能够表达出有他对道德或性理的理解。他认为四端据孟子,是纯善的。而如果四端为纯善,则四端一定是纯理而发,不能夹杂有任何气的成分,这是从四端的纯善而推论出使四端生发的根源只能是理。此一想法如果用康德所说的道德行为是由道德法则直接决定意志而产生,就很明白。道德行为不能是为了其他缘故而行的行为,只能是因为此行为该行而行,这就表示产生此行为的意志只因为该行为是该行而行。而此该行而行的想法就是只因为理所当然之故,故可以说此时的意志是为道德法则所直接决定。而所谓道德法则须从孟子所谓的义利之辨来了解,即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只因为理所当然而行,不能为了其他的缘故或条件,此如康德所说道德法则是无条件的,为定然的律令。李退溪所说的理发如果从法则直接决定意志来了解,就可以说得清楚,而且不必进一步说退溪肯定心即理。法则直接决定意志可以只从人去给出行动的时候,只因为理所当然而行。这虽表现了理的直接决定性,但并不必含理本身是活动的,即只需说心因为而且是只因为理的缘故而行,就是理发了。在恻隐之心,或情上见出这是只因理而发,而不是理本身有发用。①因为此时心或主体除了为了理之外,没有因为其他而给出行动,于是法则或理是心给出行动的动力,虽然此动力不一定就是心本身提供的,理在心之外,心的虚灵明觉不即是理。但只要心只因为理而行,则理对于心也可以说是给出了动力,可能如此解既表示了理发说所含的法则是意志的直接决定之义外,又不必将退溪学理解为往心学靠近。对于心与理的不同,退溪并非不清楚,他虽然认为心是理气合(此是陈淳的说法),但这是表示理在心中为心所本知,而且心的做意或决定行动可以纯因理而发。故理发在退溪应是理在心中有其发用之意,而所谓理在心中有其发用是心纯依理而发。
另外,退溪所说四端从中而出,七情从外而发,此一区分也有其道理,他这样区分就表示了四端等的行动是由自己决定而给出来的。固然恻隐之发必须要因应对象而后有,但并非所看到的对象决定了人给出恻隐之心或恻隐之情。此恻隐是自发自觉,即自己决定而给出来,才产生的,并非由外在的对象决定。故孟子分析恻隐之心时表示了此心并非因其他的目的、条件而发,只是内心感觉到非要如此不可而发,孟子此一分析也等于是康德所说真正的道德行为必须从自由意志发出来之意。由于道德行为是法则直接决定意志而给出来的,故此给出道德行为的意志只能是因为理所当然而行。此时的意志并不能受任何其他的因素影响,故虽然恻隐是见孺子入井而发,但所以要给出这恻隐与其后的往救孺子的行动,也是意志自己决定的,并不是受其他原因影响而产生的他律性的,或因着刺激而一定有反应的行为。明白此真正道德行为是出于自由意志之义,就可知退溪所说“四端从中而发”是一定要有的讲法。
四、栗谷的反对理发说与其从理气不离而阐发的特殊见解
由上述可知,退溪的四端理发说很能表达出道德行为的特性。由于是如此,故可说退溪之说有其不易摇动的立论基础。当然栗谷对退溪主张的反对也有其论据,也相当能够服人。栗谷认为如果四端是理发而气随,七情是气发而理乘,则理气就有时间上的先后或离合可讲。如果理气有离合有先后,就不能够说明天地生化,因为假如四端是理先发,则理发时便无气,而七情是气先发,则此时便无理。故此说表示了理气有先后,而且这样一来也会有理气可以分开,然后再合起来之义,这是所谓理气有离合。如果理气有先后离合,则气化的活动可以不以理做根据,而理可以超然独立,不需要气来表现其意义或作用,这是不通的。栗谷此说哲学性很强,当然此所谓哲学性是就宇宙论、形上学的意义来说。可以说栗谷在客观面形上学或存有论的理论上特别有明白的分析,从宇宙论上看,当然是理气不能离的,如果理气不离,则四端七情的生发,就不能有此先发彼跟随的区别,只能说有理就有气,有气就有理。而如果从此一宇宙论或理气论的观点来做标准,四端七情都只能是气发而理乘,即发是气发,气之发处都有理为根据,理无所不在,一切气化流行都有理作为根柢,不能有气自发而没有理的可能,也不能有理独行而不借着气的情况。但这样一来,四端七情就不能有意义上的或层次上的区分,故奇高峰及李栗谷都认为七情是总说全部的情,四端是七情中的善情,故说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这在宇宙论上说是很合理的,但不能表达意志为法则所直接决定而有自由自决之义。这可以看出宇宙论的理论对于道德行动的说明是有问题的,此所以康德认为在道德行动上所必须肯定的自由,与从自然因果上必须肯定的因果必然性是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因果的必然性对于经验事实的说明为必须,就否定了道德实践所要肯定的意志自由。这两者都要成立,而且在二者相冲突时,理性的实践应用应该是可以优先的,即不能因为理性的理论应用不能肯定自由(由于事出必有因,在因果的必然关联下,不能有自由),就认为道德实践上所必须有的自由不能成立。依此意,吾人可说,虽然在宇宙论理气论的理论上对于存在界的说明不能够主张理先发或理独自发用,但从人的道德实践必须按理而发排拒其他影响,此意上说需肯定理独自的作用。这也可以用实践理性的优先性来解决栗谷的质疑,如果认为不必因为栗谷的质疑就否定了四端由纯理而发,则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虽然可以说明宇宙气化活动的情况,但并不能用来说明道德实践的活动,从能否说明道德实践活动的真义,就可以看出退溪主理、栗谷主气这一区分的意义。主气之说就是由于主张有气即便有理,而否认了理的独立作用,而主理就是从道德实践的体会处肯定理非直接决定意志不可,虽然主气论不否认理作为存在的根据,但在道德实践上对于道德上的善产生只能从因为气清所以理得以实现来解释。道德的善如果由于气清才可能,不是由气决定吗?故说栗谷一系为“主气”,其实未尝不可,而且如此说就可以看出栗谷一系对于道德实践的意义及其真实的可能说明不够,甚至很不成功。即如果“善者清气之发”①,如果为善是靠清气才可能,则性理的作用或动力就不能说了。当然栗谷对退溪理发说的批评如前文所说,在宇宙论的理论上是非常合理的,于朱子的理气论也有根据,因为理是不活动的,活动者是气,则理气的关系应如栗谷所说。故退溪与栗谷此一不同的主张,在朝鲜朝儒学中栗谷是占上风的。
栗谷对于理气不离很有体会,由此而有一些特别的见解阐发出来,既然善是清气之发,则成德的要点在于养气,即恢复气之本然。他认为气有湛一清虚的本体,如果维持或恢复此气之本然,性理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表现出来。如果气质有清浊厚薄的不齐,则理虽然清通,也只能表现有善恶参差的情况。这是栗谷的工夫论要点。由于理气不离,而且理通气局,故栗谷认为不合理处也应当有理,这是他对于程子所说的理有善恶的说明。另外由于理气之不离而气是有聚散变化的,故栗谷认为现在所见的天地(也可以说是世界或宇宙)已经生灭了许多次。此即其天地有无限生灭说,因为理是不能没有的恒常存在,而有理即有气,故气也是常存的。既然气是常存,但有聚散变化,而天地是气化所组成的,则天地一定经历过许多次的聚散变化,故吾人所处的天地一定已经生灭过多次。此一见解非常有哲学的深度,可以为有聚散变化的天地何以要存在,及对人类文明的存在既然是不能常存的,则其存在有何意义的问题给出一个说明。即人类文明虽然可以毁灭,但既然有理便必有气,天地可以有无穷生灭,人类的文明也可以有无限次的存在。这是生灭与不生灭综合起来的宇宙观。生灭可以容易推出其存在是可有可无的,即其存在并非必然的存在,但假如有生有灭是由恒常存在之气所构成,而且又由恒常之理作为生灭的根据,则此生而又灭的存在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故可说既生灭又是不生灭。于是人生的存在固然是有生有灭的暂时存在,但又可以体现出永恒的理的意义。于是人世间之存在为不能没有的,即其存在是有理上的必然性,这也是可以说的。这也可以用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即有限而无限”之意来说明。
五、奇芦沙主理论证中的道德含义
奇正镇(号芦沙,1798—1879)对于栗谷的说法,甚不以为然,晚年正式提出反对的见解。芦沙论证理为气之主宰,故理是有尊位的,而认为栗谷的理气论使理好像成为附骥尾的存在,可有可无。他认为圣贤典籍历来都主张理是气的主宰,则理一定有他的主宰性,无论气的作用如何强大,但都必须接受理的主宰。如果可以如此说,则理的主宰性如何表现呢?芦沙于此就给出了理完全不借着气,但有其主宰性的力量之说。他论证理为气之主宰,气不能决定理,如云理之乘气是原来所乘,并非气来而后理乘之。又说天地间虽看起来都是气在作用、活动,但气之所以能如此,是有看不见的理给出决定。故看到气的活动,就如同看到理的主宰性或决定性。如同贵人乘坐马车出游,我们看到马车在走动时,虽然看不到贵人的活动,但由于有贵人的决定,才会有马车及马车上马夫的种种活动。此譬喻是说,理的决定性虽然没有在气的活动中被看到,但其实是理主宰着气。没有贵人的发号施令,可见的马车活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此如同没有理的给出主宰,气化的活动是不可能的。于是不能因为只看到形而下的气在活动,于是认为无形的理只能靠气才能表现其作用,或认为理的作用受到气的限制。此明白地反对栗谷的“理通气局”说。芦沙又认为理的做主之作用,完全不藉赖气的能力,单靠理本身的力量,就可以给出主宰性的、根本的作用。他举例说,西汉末的更始帝,才智平庸,只因为他姓刘,就被拥立,称帝了一段时间。这就譬喻单只是理而没有气的作用,就可以给出主宰的力量。对于理一分殊的意义,芦沙也做了特别的诠释。他认为理本身就含着分殊,并不是理之一因为气的作用,而成为分殊之理,各存在物都是由理作为根据。故处处都表现了理的意义,这是理的分殊。而分殊之理其实都是理,其为理,一也。故分殊之理就是理之一,而不是先有理一,因为气的局限,而成为分殊之理。芦沙这些证明理为气之主宰,理一定有其作用,虽然其作用于气的活动变化中看不出来,这些论辩都很有精思。
而理的主宰既然完全不借着气,则如何去理解这种主宰性呢?我认为必须通过道德实践的无条件性来理解理的作用,如上文所说,道德法则对于意志有直接的决定性,即我们只能纯粹为了理所当然之故而行,完全不为其他,才可以给出真正的道德行动。这是我们稍微反省何谓道德义务就一定明白的道理。既然是如此,则道德的行为动机假如掺杂了一点感性的欲望、气性的要求,那就不能是道德的行动了。这就可以说明愈没有气的作用愈会有道德的理的意义,能够给出真正的道德行为完全或只能是因为理的缘故,这样不是就可以说明理的力量或作用了吗?理的作用是单靠他自己就可以成为道德行动的动机或存心,而只能够是以纯理(或纯粹理性)作为行动的动机或原则,才可以给出具有真正道德价值的行为。掺杂了一点感性的欲求的话,那么无条件的道德行为就成了有条件的、有所为而为,于是该行动的道德价值就会全部消失无踪了。从这一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芦沙对于理必有作用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他的论证是很有效力的,在人愈能拒绝感性的作用干扰时,愈可以显出理的主宰性。而如果理能显出这种纯粹的、不依于气的主宰性,就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行为,这一论证除了说明道德之理是无条件的法则,单靠其自己就可以决定意志而成就道德行为之外,也可以说明理不需要像气一般的活动,而可以使表面有最大力量的气也需要服从的缘故。
人如果通过内省,而发现自己的行动是于理不合时,则不管他地位多高、有多大的势力,也不免惭愧内疚。于是理的作用在人知理的时候,就会给出来。如果是这样,则理是否有活动性,便不是能否产生真正道德行为的关键。道德之理只靠他自己,就可以产生动力,不必有实际的活动性,才可以产生使人依循之而产生的力量。依此意,则理即使为存有而不活动,照样可以提供实践的动力。当然,此动力的产生,如同康德所说,是法则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影响力,此时行动的主体必会产生对于道德法则的尊敬。由尊敬而接近法则,而给出实践的行动。
六、寒洲学派与华西学派对主理说的发展
李震相(号寒洲,1818—1885)有“心即理”说,他认为心的本体是理,而其外表的作用是气。如同和氏璧的情况,即外表是石,里头是玉。他如此规定心,就表示心不能只从气来理解,理是作为心的本质,于是也有它的作用表现。如心统性情之“统”,就是理的作用。他又用“理一”与“分殊”的不同,来区别“心之统”所表现的“理”与他所统的“性”,也有其精思。李华西则认为心可以以理言与以气言,又认为明德是理,都表示了理有其作用。寒洲与华西两派对理的理解,都强调了理本身就有其作用,其作用可以从心的活动中直接体会到。他们虽然不能如陆王直接以心为理,但也可以说是往心即理趋近。田愚(号艮斋,1841—1922)对于这两派的主张都加以反对,认为如此说心,使心与理的界限不清,不能够让理维持作为实践的标准之义,也会引发心的僭越、自主。艮斋认为这是违反传统儒学大义的,他认为儒学的第一义是肯定心性为二、“性师心弟”才是儒学的合理主张。本来按照儒学成德之教的要求,能够给出一个人人都能自发的为善根据,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所以然之理,如果只是静态的,则是否能够给出实践的真实动力呢?由于这一思考或要求,退溪主张理发,而寒洲、华西主张理有它实在的作用,也是合理的。当然,如果透过奇芦沙的论证,说明理的作用或力量由于是单靠理而给出的,不依于任何有形可见的气化作用,顺着此一论证,则理应该可以不用活动,就能给出其对气的主宰性。而如果通过道德法则的含义来理解,如上文所说,道德法则是对意志给出直接的、无条件的决定者。既然是无条件的决定,则任何现实可见的作用,或功效、利益,都不必加进来,作为理的力量构成要素。相反,越理解道德之理的无条件性,就越可以排除一切有形的或对人的感性有吸引力的种种现实作用,来直接肯定理本身的力量。越能拨开现实有用的想法,越能理解道德法则的力量。我们的存心越能纯粹,就越会遵守此一以无条件的律令颁布的道德法则。如此理的主宰性力量,就不必借着活动才能起用。这应该就是朱子所谓“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①之意。理的这一种不藉任何其他功能就可以独立起用的意思,越了解之,越会让人肃然起敬。故理所当然之理,当然有他的力量。
七、主气派所提出的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结穴于田艮斋气体本清说
朝鲜儒学主气派的李栗谷一系,固然不能给出上文所说的理作为实践动力的说明,但也有其他的贡献,对于理解朱子学的义理形态也有帮助。栗谷系的学者大都认为心虽然是气,但心之为气,是气之精者。栗谷肯定有气之本然,或本然之气,即肯定了人生命中有本来清明的气之本体。如果人能检束其气(心气),就可以恢复气之本然,即恢复清明的气之本体。而善是从清气发生出来的,故如果人有本然的清气本体,则只要通过养气,就可以恢复清气而为善。此一对人本有清气之本体的肯定,也可以作为人人可以为善的超越根据。栗谷此说为后来的李柬(巍岩)所强调,吴熙常(老洲)认为心气是清明而与理无间的,也应是承此义而发展。到朝鲜朝最后期的田艮斋,则正式提出“气质体清”之说,认为人在其生命开始时所禀受到的气,是有清明的气之本体在其中的,此气之体并不会因着后天的活动变化而失去。此一肯定可能也可以说明朱子学所以重视涵养之故,即人如果能有涵养的功力,本有的清明气之体就可以出现。此所谓“才歇即清”,而人就可以为善。当然对于此气之本体的肯定与证成恐怕有困难,而且善的行为如果是由清气而有,如栗谷所说的,“善者,清气之发”,则性理的作用恐怕太弱化,也不能说明何以在见孺子入井的情形下,人人都会有要求自己无条件地往救孺子之想法。这是无分于气性清浊之人都会有自我要求,此一问题在艮斋的弟子继续有所讨论。
田艮斋的思想以“性师心弟”为主旨,他认为性理是标准。标准是不能变化的,故性理不会活动。艮斋此说给出了性理是不活动的理由。心是活动,故心是气。但心之为气是虚灵的,故“心可以学性”。从心之虚灵与心可以明理,也可以说心是善的,但心虽然善,会流于恶,因为心是会变化的。这是艮斋承继吴老洲所说的“心本善而不可恃”之义。既然心之虚灵可以学性而为善,但不可恃,则心对性的态度应该是如同学生以恭敬的态度来从师问学一样。心自居为弟子,事事以性理为遵从的标准,不敢自以为是,即弟子永远以老师为学习对象。艮斋认为心这种对性理的态度是最恰当合理的,如果心以为自己就是理,那就是僭越。他认为人间的种种毛病都是由于心的妄自尊大,僭越了性理的位置而产生。艮斋此说大略同于上文所说康德论尊敬的意思,也表达了心性为二的必要,即如果太强调心性是一,会引发人的骄傲自大。另外,从“心学性”之义,也给出了朱子一系学者所以强调读书明理的说明。即由于心虽然可以通彻于理,但心之虚灵并不等于是理。心会活动变化,故对于本来知道的道德之理不一定能持守,在这种情形下,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必要的。朱子强调读书以明理,虽然也涉及一草一木之理,但还是以求知道德之理为主的。而对于道德之理的了解,从“心学性”之言,也可以说明读书的必要。即心若以性为学习对象的话,则读书就可以作为明理学习的好方法。故艮斋的说法既说明了心性为二的必要,也说明了读书在心性为二的系统下是必要的。
通过上述对朝鲜儒学两系义理的分析,可知朝鲜的性理学虽然以朱子思想为主,但并非只重复朱子本有的义理内容,而是有进一步发展的。而通过他们的有关论辩,可以看出其中有许多很有哲学意义的理论发明。而最重要的是可以给出对朱子思想的不同的诠释,如栗谷一系对朱子学的理解,很接近当代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的诠释,但虽相近,也有不同。如上文所说,从李栗谷到田艮斋,都肯定心虽然是气,但作为气之灵的心并非一般的形气,而是可以通彻于理的,只要维持本性是清虚的气之本然,或本清的气体,就可以表现善的行为。这是主气一系对于成德如何可能,给出一个说明,即肯定了人人都有成德的超越根据。只是从气体本清来保证成德人人可能,论证不够坚强,而且如果道德的善行由于清气而有,则道德实践所必须的意志的自我立法、自觉、自由等义,就比较不好说了。而主理的退溪、芦沙、寒洲、华西一系,则突显了理必须有其作用,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之义。此系的理论对于说明朱子学,我认为特别有贡献,可以参考他们的理解,重新诠释朱子学。或许可以用主理的观点来理解朱子学的形态,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如果这一诠释可通,则朱子系(包括程伊川及朱子的重要弟子)的义理,应可与陆王系并列,而为儒家成德之教的两个可行的理论形态。
附注
①见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简体版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及《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续编》,台北:台湾大学人社高研院东亚儒学研究中心,2017年。
①康德说:“行动之道德价值中那本质的东西便是:道德法则定须直接地决定意志。如果意志底决定实依照道德法则而发生,但只因着一种情感,不管是那一种,始能如此……则这行动将只有合法性,但无道德性。”见康德著,牟宗三译注:《实践理性底批判》卷一,《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265页。
②牟宗三先生认为明德应是性理,而具众理是虚灵不昧的心知之明,以认知地管摄之而具。故依牟先生的理解,此心之具众理是后天的具,也可以说是当具而非本具。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三),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第374页。
①朱熹《大学或问》卷二:“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①康德说:“这样,‘自由’与‘一无条件的实践法则’是互相涵蕴的。现在,在这里,我不问是否它们两者事实上是不同的,抑或是否一个无条件的法则不宁只是一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而此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又是与积极的自由之概念为同一的。我只问我们的关于‘无条件地实践的东西’之知识从何处开始,是否它是从自由开始,抑或是从实践的法则开始?”见康德:《实践理性底批判》卷一,第165页。此段当然先说明道德法则与自由相含之意,也表示了从道德法则可以认知自由,而自由是道德的存在根据。但此段文不只表示上述之意,从以法则或自由为先来了解何谓无条件地实践,可知对于无条件的实践(即道德实践)可以通过以法则为先来了解或以自由为先来了解。这等于说对于道德之意义可以从理来契入,也可以从本心(即自由意志)来契入。
②阳明之语见《大学古本序》;龙溪之语见《闻讲书院会语》,《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③此意详见杨祖汉:《程朱、陆王二系的会通》,《当代儒学研究》第24期,“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2018年6月,第47~68页。
①刘述先教授对于牟先生所规定的自律之意有以下的批评:牟先生又限定只有如明道那样直接由本体论的方式去体证他所谓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才是“自律道德”。这也不符合西方哲学一般对于此词之理解。在西方哲学传统,由苏格拉底以来,倡导“唯智主义的伦理学”(intellectualistic ethics),人依照真理(truth)行所当为(virtue for virtue's sake),就是自律道德。行德是为了德性以外的快乐、功利,才是“他律道德”。见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刘先生此说可供参考。
②牟先生在他译著的《实践理性底批判》中认为康德这一形态“似乎亦可以说是另一种他律道德”,这一衡定可能太严格了。牟先生之说,见牟宗三:《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316页。
①[韩]郭钟锡:《俛宇集》卷七六,《答李子明·别纸》,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340集,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4年,第119页。
①退溪明白说到,所谓理发是理在心中发用之意(文献待查)。在《圣学十图》讨论四端理发气随等,是在“心统性情图”中,可见所谓理发是理在心中给出作用。而如果心理解道德行动是纯依理而发的,即是由法则直接决定意志而产生的,则也可以说理在心中给出直接的影响或作用。
①见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卷十四。关于此说的讨论,杨祖汉:《吴石农、权阳斋对田艮斋“气质体清”说的继承》(艮斋学国际学术会议,全北大学,2016年10月)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6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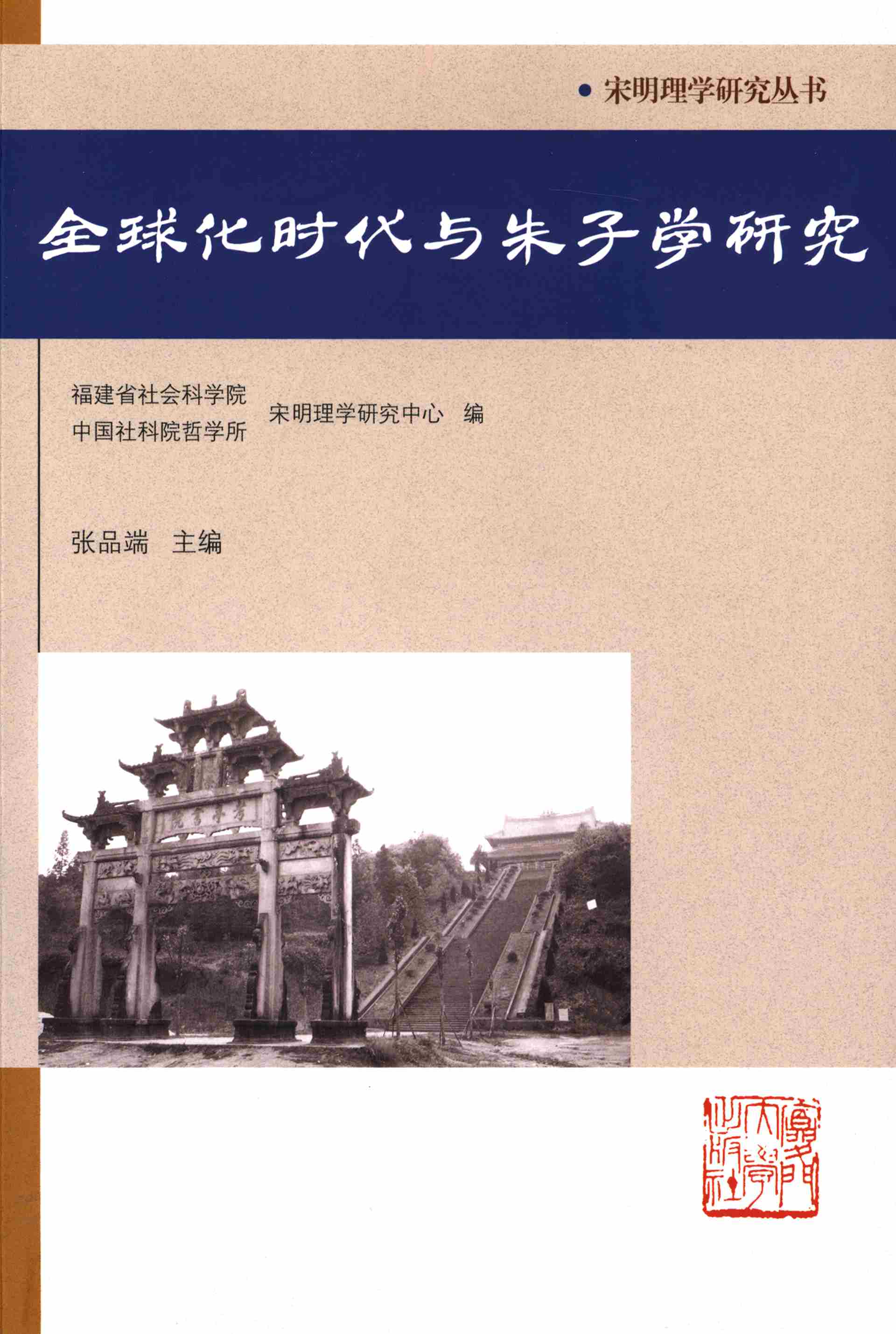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杨祖汉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