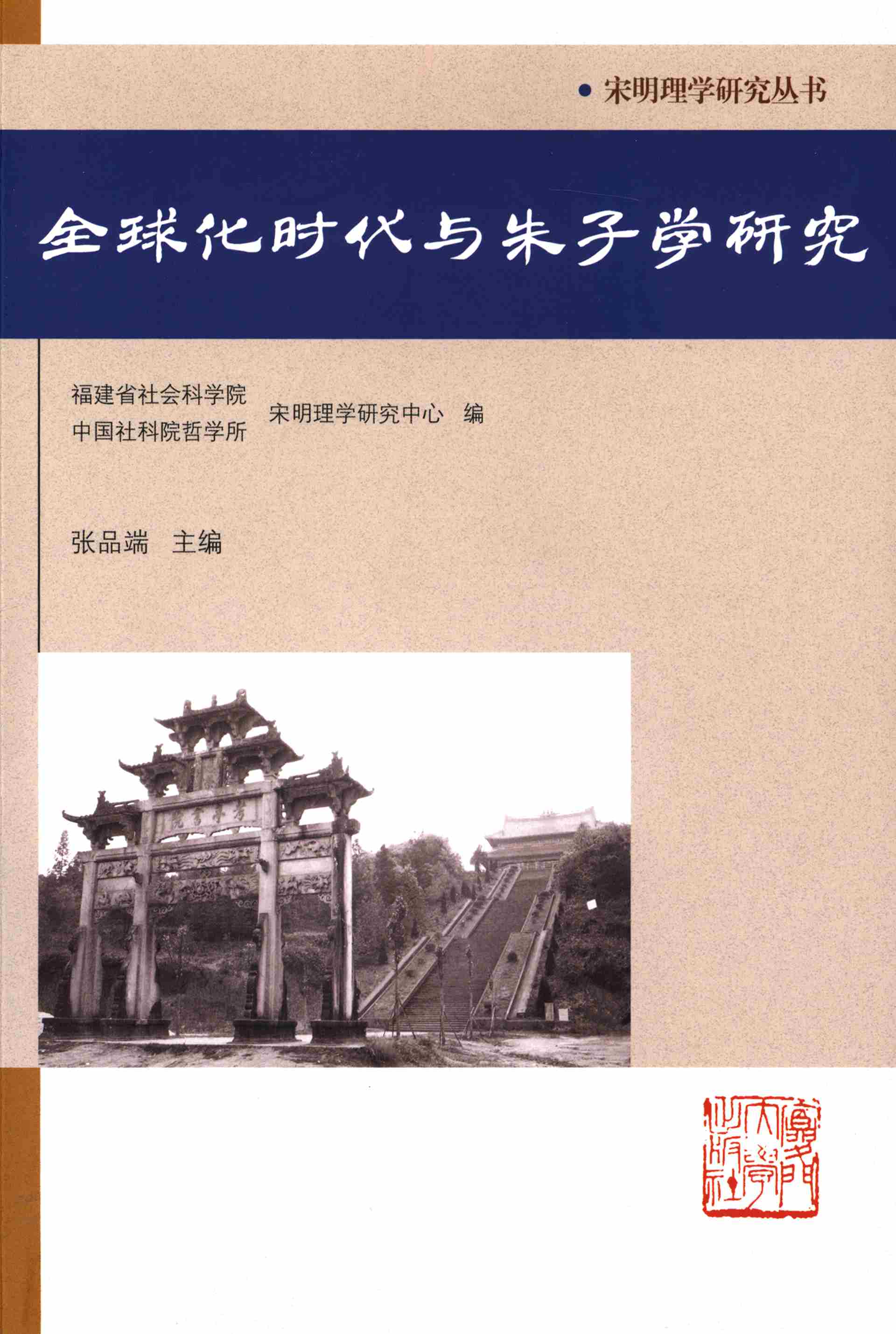三、智藏说如何可能:智藏之于心性论的衡定
| 内容出处: | 《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231 |
| 颗粒名称: | 三、智藏说如何可能:智藏之于心性论的衡定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9 |
| 页码: | 147-15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本文主要讨论了朱子对于“性”的理解问题,以及五常与两种四德德性范畴之间的转置互通。通过解析《太极图说》等文献,文章指出理和气的关系是不离不杂的,性只是理,且性是纯善的。同时,文章也探讨了五常之信与仁义礼智四德之间的关系,以及智之为德的重要性。 |
| 关键词: | 朱子 智藏说 玉山讲义 |
内容
关于智为何能藏,而如何可藏的讨论,根据笔者的理解,其实应分以下数点予以讨论:
(一)理解性善之进路:《太极图说》
首先是朱子对于“性”的理解问题。朱子对于“性”生成本有的接受,是从濂溪处进行消化的,濂溪《太极图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①
在朱子的理解,理和气的关系是不离不杂的。理与气当然是不同的(不杂),但却需要有气才能得以彰显实现(不离)。故朱子除了认定“性只是此理”①外,由于“性则纯是善底”②,且“性是天生成许多道理”③、“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④,及人之所以生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⑤,这是朱子承袭《中庸》、《易传》和濂溪发展出的理解。是以《玉山讲义》第二段文字曰“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按韩愈所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一句,乃出自其《原性》。该句本作“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⑥,就是以仁、礼、信、义、智等为性之内容。故可知人之五常之“性”,亦即本有而立。
(二)“五常”与两种“四德”德性范畴间的转置互通
不过这里随之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仁义礼智、仁义中正两种“四德”之间的相配问题。我们先以仁义礼智为主来看这种问题。本来孟子原先就只以仁义礼智说心性之善,且若以五常言性,“信”德显然就无法统合。这点《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中也有提及。其曰:
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⑦
原来理(性作为朱子思想体系中终极的存有,无论由何种角度(由事随感而发显)切入,此中之理皆同体于一。且五常间也无所谓特定的分别次序可言,是“浑然不可分”的。朱子甚至说:
理,只是一个理。理举着,全无欠阙。且如言着仁,则都在仁上;言着诚,则都在诚上;言着忠恕,则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则都在忠信上。只为只是这个道理,自然血脉贯通。⑧
如此则只要将最终价值及归趋指向理/性,其实无论以何种道德范畴为出发点,皆无害于进德工夫。不过,“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①“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②“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③,且“性是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④,性/理中之万理,终究可归摄入仁、义、礼、智四大范畴之内,进而回归于以仁包四德(以专言言仁),如是则性之为体则显然可知。是以“信”之理便由肯定其为实有加以融摄:
或问:“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⑤
亦如上一节朱子所答第三段文字所说的:“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
如此便能顺利将五常之“信”收摄至四德上,甚至是全然肯定性理之真实无妄上。且最终之理乃通同为一,亦不须在德性分类间多绕工夫。
然而我们所需注意的乃是智之为德的关系。承《太极图说》所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本来理本是一,在“理”的层次上强分彼此是无意义的,但在“事”的层次上,总是有所差别。盖“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⑥,所以关于仁义中正与仁义礼智的辨析,还是有其必要性,《语类》中于此有言: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何不曰仁义中正?”曰:“此亦是且恁地说,当初某看时,也疑此。只要去强说,又说不得。后来子细看,乃知中正即是礼智,无可疑者。”⑦
又曰:
“中正仁义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义中正而已矣’,以圣人之心言之,犹孟子言‘仁义礼智’也。”①
原来“中正”就是“礼智”,那为什么要以“中正”代替“礼智”呢?朱子认为“中正”二字不仅“较有力”②,且能更为贴近说明并确实描述该德性:
问:“周子不言‘礼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礼智说得犹宽,中正则切而实矣。且谓之礼,尚或有不中节处。若谓之中,则无过不及,无非礼之礼,乃节文恰好处也。谓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谓之正,则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实也。”③
依照《玉山讲义》的理解,上文第三段文字曰:“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第四段文字则曰:“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且专以智本身来说,智本身所代表的是先天赋予人所本有,保证人能知觉且分别是非的道理。暂且先就能分别是非的标准来说,当然是要能知亲爱、别善恶,也就是能知其“正”,以做出最符合当下情况应有的判断。而此标准不是靠什么外在的环境或条件去影响,“正”当然也是同出于智的,故“知是非之正为智,故《通书》以正为智”④。《语类》亦有问答记曰:
问:“智与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见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唤做智了。”问:“只是真见得是,真见得非。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⑤
就如同“中”之于“礼”一样,“正”在此其实指的不过是智德本有且应有的标准罢了。因此“中正”终究不能将“礼智”的地位替换过来。不过朱子认为“正”之所以成为智之标准,还有其他的原因:
问:“‘中即礼,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于四德属贞,智要正。”⑥
问:“中正即礼智,何以不直言‘礼智’,而曰‘中正’?”曰:“‘礼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实。且中者,礼之极;正者,智之体。正是智亲切处。伊川解‘贞’字,谓‘正而固’也。一‘正’字未尽,必兼‘固’字。所谓‘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智是端的真知,恁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
所以‘正’字较亲切。”①
如同第一小节所言,朱子对性善的理解乃直承濂溪《太极图说》而来。因此,天命直接下贯善性于四时万物,天之四德“元亨利贞”与四时“春夏秋冬”及人之四德“仁义礼智”间便有一秩序性的比配关系,因而成为《仁说》以来至《玉山讲义》一贯的观点,也是智之所以能藏,即智藏说之得以成立的直接理据所在。
(三)天人四时四德的相合与智藏说的成立
依《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且阴阳互为其根,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最后生成人类、四时及万物,这点上文已经反复述及。朱子甚至说:“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②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这种理解的进路对朱子之于四端的看法有着什么影响。
在朱子,“生之理谓性”③,朱子定稿于四十四岁(乾道九年,1173年)④的《仁说》之首二段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仁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⑤
故可知朱子取元亨利贞比配春夏秋冬,并以此说解仁义礼智之思路于其中年时即已成形,可说是其一贯的理解。此段文字依李明辉先生的分判,朱子于此列举了四组不同的秩序,分别是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存有—伦理学的(onto-ethical)秩序(仁义礼智)及伦理—心理学的(ethico-psychological)秩序(爱恭宜别)。其中爱恭宜别是恻隐、辞让、羞恶、是非等四端的另一种说法。此外,复将第一组秩序(元亨利贞)与第二组秩序(春夏秋冬)视为理气关系,而第三组秩序(仁义礼智)与第四组秩序的关系则是性与情的已发未发关系,且性情关系是理气关系的特殊化①。朱子之《元亨利贞说》则更能简洁地把这个部分说清楚: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②
此中朱子以元亨利贞属性,生长收藏属情。而根据《仁说》所言,万物之所以生长收藏,是因为仁之生气贯穿于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现象所致,如此则元亨利贞自与春夏秋冬在“生”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程序。是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③且朱子又言:“‘元亨利贞’,其发见有次序。仁义礼智,在里面自有次序,到发见时随感而动,却无次序。”④
而仁义礼智则是“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⑤,是可知两者的关系是建立在由元亨利贞与仁义理智“里面”“生时”的内在秩序上。且智于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比配下,乃是保证理中之所以能知觉善恶,并因此做出正确判断,且能长留于心(即“贞而固”)之理。故前引《玉山讲义》第四段文字曰:
“‘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故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如此,“智则仁之分别”就是“冬则生之藏”,“智”与“藏”的关系便因此而建立。是则智之所以能藏,盖因其配同于四时之“冬”。也就是说,因为冬者有敛藏的意思,为使春日再行发散生物,生意到此依理自然翕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冬之所以敛藏,并不是在气上说,而是在理上见其事:
问:“‘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元亨是春夏,利贞是秋冬。秋冬生气既散,何以谓之收敛?”曰:“其气已散,收敛者乃其理耳。”曰:“冬间地下气暖,便也是气收敛在内。”曰:“上面气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来,却不是已散之气复为生气也。”①
故可知智所表现者,由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来看,乃理中能敛藏之理。是以《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的末段,也就是上引文中的第六段文字即扩充此意曰:“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
智由宇宙论所理解的敛藏之理,本由四时化生循环可见,故言“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然而于此“藏”尚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无迹”,即“藏迹”之意。为什么智相较于仁、义、礼等三德,“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呢?原来:
“仁礼属阳,属健;义知属阴,属顺”。问:“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②
关于阴阳健顺的分际,第三节所引、智藏说文献基础之第五段文字,即《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曰:“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自四而两,自两而一,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此是发挥《玉山讲义》中“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句而来。
为何仁义礼智又可归摄至仁义二德下呢?首先关于仁与礼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曰: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①
原来仁礼同是“敷施出来底”,在总体发生及形之于外的意义上就是作用处,代表阳德、属刚。然而为何不是仁属柔、义属刚呢?袁机仲便曾以此请问于朱子,朱子答曰:“殊不知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②故不仅在发用和敛藏关系上可见阴阳刚柔,四时替换亦可见阴阳刚柔。这便是体现《易传》天、地、人三才同一的意义。且这里所谓仁、义、礼的作用,便是四时春、夏、秋中之生、长、收,也是人之四德仁、义、礼中“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更是四端中之恻隐、辞让、羞恶。因为朱子于此将智之彰显发用定义得相当明白,“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当然,这里的“更无作用”乃是相较于内外发用而言,并不是全然的身外长物。
此外,“伊川常说:‘如今人说,力行是浅近事,惟知为上,知最为要紧。’《中庸》说‘知仁勇’,把知做擗初头说,可见知是要紧”。贺孙问:“孟子四端,何为以知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见,到一阳初动,这生意方从中出,也未发露,十二月也未尽发露。只管养在这里,到春方发生,到夏一齐都长,秋渐成,渐藏,冬依旧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终始’亦见得,无终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生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①
关于朱子于此理解孟子因循环而列智于四德之末,以及智藏有仁、义、礼另三德的看法,未必符合孟子原意,此待下文论及。但我们注意到,当智之理藏迹在知觉判断后,随即交由仁、义、礼等三德发用,如“问:‘有节文便是礼,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②。故曰: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为宾主,然仁智其总统也。‘恭而无礼则劳’,是以礼为主也;‘君子义以为质’,是以义为主也。盖四德未尝相离,遇事则迭见层出,要在人默而识之。”曰:“说得是。”③
“四德未尝相离”,即是上文朱子所谓“发时无次第”。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时机点,四德各有以之为主的发用处,此就是“性之四端,迭为宾主”。但回过头来,若无仁之生意贯穿四德,非“一阳初动”,四德便无以为用,是以最终仍是归摄而言“仁智其总统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宇宙论的比配上,智藏的重要是在于循环意义及终始意义上。不仅仁义礼智本身以仁为总摄而循环,智本身同时也是“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更是天地化生中“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的固然之理。且使人默而识之,又可以说是智之理应有的工夫论展现。故朱子赞以“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可说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一)理解性善之进路:《太极图说》
首先是朱子对于“性”的理解问题。朱子对于“性”生成本有的接受,是从濂溪处进行消化的,濂溪《太极图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①
在朱子的理解,理和气的关系是不离不杂的。理与气当然是不同的(不杂),但却需要有气才能得以彰显实现(不离)。故朱子除了认定“性只是此理”①外,由于“性则纯是善底”②,且“性是天生成许多道理”③、“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④,及人之所以生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⑤,这是朱子承袭《中庸》、《易传》和濂溪发展出的理解。是以《玉山讲义》第二段文字曰“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按韩愈所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一句,乃出自其《原性》。该句本作“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⑥,就是以仁、礼、信、义、智等为性之内容。故可知人之五常之“性”,亦即本有而立。
(二)“五常”与两种“四德”德性范畴间的转置互通
不过这里随之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仁义礼智、仁义中正两种“四德”之间的相配问题。我们先以仁义礼智为主来看这种问题。本来孟子原先就只以仁义礼智说心性之善,且若以五常言性,“信”德显然就无法统合。这点《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中也有提及。其曰:
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⑦
原来理(性作为朱子思想体系中终极的存有,无论由何种角度(由事随感而发显)切入,此中之理皆同体于一。且五常间也无所谓特定的分别次序可言,是“浑然不可分”的。朱子甚至说:
理,只是一个理。理举着,全无欠阙。且如言着仁,则都在仁上;言着诚,则都在诚上;言着忠恕,则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则都在忠信上。只为只是这个道理,自然血脉贯通。⑧
如此则只要将最终价值及归趋指向理/性,其实无论以何种道德范畴为出发点,皆无害于进德工夫。不过,“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①“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②“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③,且“性是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④,性/理中之万理,终究可归摄入仁、义、礼、智四大范畴之内,进而回归于以仁包四德(以专言言仁),如是则性之为体则显然可知。是以“信”之理便由肯定其为实有加以融摄:
或问:“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⑤
亦如上一节朱子所答第三段文字所说的:“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
如此便能顺利将五常之“信”收摄至四德上,甚至是全然肯定性理之真实无妄上。且最终之理乃通同为一,亦不须在德性分类间多绕工夫。
然而我们所需注意的乃是智之为德的关系。承《太极图说》所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本来理本是一,在“理”的层次上强分彼此是无意义的,但在“事”的层次上,总是有所差别。盖“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⑥,所以关于仁义中正与仁义礼智的辨析,还是有其必要性,《语类》中于此有言: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何不曰仁义中正?”曰:“此亦是且恁地说,当初某看时,也疑此。只要去强说,又说不得。后来子细看,乃知中正即是礼智,无可疑者。”⑦
又曰:
“中正仁义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义中正而已矣’,以圣人之心言之,犹孟子言‘仁义礼智’也。”①
原来“中正”就是“礼智”,那为什么要以“中正”代替“礼智”呢?朱子认为“中正”二字不仅“较有力”②,且能更为贴近说明并确实描述该德性:
问:“周子不言‘礼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礼智说得犹宽,中正则切而实矣。且谓之礼,尚或有不中节处。若谓之中,则无过不及,无非礼之礼,乃节文恰好处也。谓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谓之正,则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实也。”③
依照《玉山讲义》的理解,上文第三段文字曰:“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第四段文字则曰:“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且专以智本身来说,智本身所代表的是先天赋予人所本有,保证人能知觉且分别是非的道理。暂且先就能分别是非的标准来说,当然是要能知亲爱、别善恶,也就是能知其“正”,以做出最符合当下情况应有的判断。而此标准不是靠什么外在的环境或条件去影响,“正”当然也是同出于智的,故“知是非之正为智,故《通书》以正为智”④。《语类》亦有问答记曰:
问:“智与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见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唤做智了。”问:“只是真见得是,真见得非。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⑤
就如同“中”之于“礼”一样,“正”在此其实指的不过是智德本有且应有的标准罢了。因此“中正”终究不能将“礼智”的地位替换过来。不过朱子认为“正”之所以成为智之标准,还有其他的原因:
问:“‘中即礼,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于四德属贞,智要正。”⑥
问:“中正即礼智,何以不直言‘礼智’,而曰‘中正’?”曰:“‘礼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实。且中者,礼之极;正者,智之体。正是智亲切处。伊川解‘贞’字,谓‘正而固’也。一‘正’字未尽,必兼‘固’字。所谓‘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智是端的真知,恁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
所以‘正’字较亲切。”①
如同第一小节所言,朱子对性善的理解乃直承濂溪《太极图说》而来。因此,天命直接下贯善性于四时万物,天之四德“元亨利贞”与四时“春夏秋冬”及人之四德“仁义礼智”间便有一秩序性的比配关系,因而成为《仁说》以来至《玉山讲义》一贯的观点,也是智之所以能藏,即智藏说之得以成立的直接理据所在。
(三)天人四时四德的相合与智藏说的成立
依《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且阴阳互为其根,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最后生成人类、四时及万物,这点上文已经反复述及。朱子甚至说:“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②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这种理解的进路对朱子之于四端的看法有着什么影响。
在朱子,“生之理谓性”③,朱子定稿于四十四岁(乾道九年,1173年)④的《仁说》之首二段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仁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⑤
故可知朱子取元亨利贞比配春夏秋冬,并以此说解仁义礼智之思路于其中年时即已成形,可说是其一贯的理解。此段文字依李明辉先生的分判,朱子于此列举了四组不同的秩序,分别是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存有—伦理学的(onto-ethical)秩序(仁义礼智)及伦理—心理学的(ethico-psychological)秩序(爱恭宜别)。其中爱恭宜别是恻隐、辞让、羞恶、是非等四端的另一种说法。此外,复将第一组秩序(元亨利贞)与第二组秩序(春夏秋冬)视为理气关系,而第三组秩序(仁义礼智)与第四组秩序的关系则是性与情的已发未发关系,且性情关系是理气关系的特殊化①。朱子之《元亨利贞说》则更能简洁地把这个部分说清楚: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②
此中朱子以元亨利贞属性,生长收藏属情。而根据《仁说》所言,万物之所以生长收藏,是因为仁之生气贯穿于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现象所致,如此则元亨利贞自与春夏秋冬在“生”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程序。是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③且朱子又言:“‘元亨利贞’,其发见有次序。仁义礼智,在里面自有次序,到发见时随感而动,却无次序。”④
而仁义礼智则是“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⑤,是可知两者的关系是建立在由元亨利贞与仁义理智“里面”“生时”的内在秩序上。且智于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比配下,乃是保证理中之所以能知觉善恶,并因此做出正确判断,且能长留于心(即“贞而固”)之理。故前引《玉山讲义》第四段文字曰:
“‘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故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如此,“智则仁之分别”就是“冬则生之藏”,“智”与“藏”的关系便因此而建立。是则智之所以能藏,盖因其配同于四时之“冬”。也就是说,因为冬者有敛藏的意思,为使春日再行发散生物,生意到此依理自然翕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冬之所以敛藏,并不是在气上说,而是在理上见其事:
问:“‘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元亨是春夏,利贞是秋冬。秋冬生气既散,何以谓之收敛?”曰:“其气已散,收敛者乃其理耳。”曰:“冬间地下气暖,便也是气收敛在内。”曰:“上面气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来,却不是已散之气复为生气也。”①
故可知智所表现者,由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来看,乃理中能敛藏之理。是以《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的末段,也就是上引文中的第六段文字即扩充此意曰:“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
智由宇宙论所理解的敛藏之理,本由四时化生循环可见,故言“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然而于此“藏”尚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无迹”,即“藏迹”之意。为什么智相较于仁、义、礼等三德,“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呢?原来:
“仁礼属阳,属健;义知属阴,属顺”。问:“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②
关于阴阳健顺的分际,第三节所引、智藏说文献基础之第五段文字,即《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曰:“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自四而两,自两而一,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此是发挥《玉山讲义》中“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句而来。
为何仁义礼智又可归摄至仁义二德下呢?首先关于仁与礼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曰: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①
原来仁礼同是“敷施出来底”,在总体发生及形之于外的意义上就是作用处,代表阳德、属刚。然而为何不是仁属柔、义属刚呢?袁机仲便曾以此请问于朱子,朱子答曰:“殊不知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②故不仅在发用和敛藏关系上可见阴阳刚柔,四时替换亦可见阴阳刚柔。这便是体现《易传》天、地、人三才同一的意义。且这里所谓仁、义、礼的作用,便是四时春、夏、秋中之生、长、收,也是人之四德仁、义、礼中“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更是四端中之恻隐、辞让、羞恶。因为朱子于此将智之彰显发用定义得相当明白,“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当然,这里的“更无作用”乃是相较于内外发用而言,并不是全然的身外长物。
此外,“伊川常说:‘如今人说,力行是浅近事,惟知为上,知最为要紧。’《中庸》说‘知仁勇’,把知做擗初头说,可见知是要紧”。贺孙问:“孟子四端,何为以知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见,到一阳初动,这生意方从中出,也未发露,十二月也未尽发露。只管养在这里,到春方发生,到夏一齐都长,秋渐成,渐藏,冬依旧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终始’亦见得,无终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生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①
关于朱子于此理解孟子因循环而列智于四德之末,以及智藏有仁、义、礼另三德的看法,未必符合孟子原意,此待下文论及。但我们注意到,当智之理藏迹在知觉判断后,随即交由仁、义、礼等三德发用,如“问:‘有节文便是礼,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②。故曰: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为宾主,然仁智其总统也。‘恭而无礼则劳’,是以礼为主也;‘君子义以为质’,是以义为主也。盖四德未尝相离,遇事则迭见层出,要在人默而识之。”曰:“说得是。”③
“四德未尝相离”,即是上文朱子所谓“发时无次第”。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时机点,四德各有以之为主的发用处,此就是“性之四端,迭为宾主”。但回过头来,若无仁之生意贯穿四德,非“一阳初动”,四德便无以为用,是以最终仍是归摄而言“仁智其总统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宇宙论的比配上,智藏的重要是在于循环意义及终始意义上。不仅仁义礼智本身以仁为总摄而循环,智本身同时也是“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更是天地化生中“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的固然之理。且使人默而识之,又可以说是智之理应有的工夫论展现。故朱子赞以“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可说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