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智藏说的理论建构及其意义——以《玉山讲义》为中心
| 内容出处: | 《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228 |
| 颗粒名称: | 朱子智藏说的理论建构及其意义——以《玉山讲义》为中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3 |
| 页码: | 142-164 |
| 摘要: | 本文以《玉山讲义》为中心,讨论了朱子的智藏说及其与其他重要学说观念的内在关系,介绍了《玉山讲义》的背景与评价,分析了朱子提出智藏说的文献基础。 |
| 关键词: | 朱子 智藏说 玉山讲义 |
内容
孟子以四端即心言性,遂成仁教规模。然自两汉以下,历代尚乏解人,直至韩愈提揭道统,乃渐为学者所重。朱子自参究中和问题以来,至新说成后,其义理形态即已然成形。而由其中年体会之《仁说》为发端,至晚年所讲《玉山讲义》中所显之智藏说,在日本经山崎闇斋大力提揭后,遂成为闇斋以下之崎门学派学者一个重要的思想论题及学脉根源。冈田武彦先生的《朱子与智藏》①和《朱子的智藏说及其由来与继承》②二文,可说是近代首先以学术论文形式讨论智藏说的先导作,而难波征男先生的《日本朱子学与将来世代——智藏论》③则是偏重从继承的角度对智藏说进行再评价。故本文将以《玉山讲义》为中心,旁及朱子其他文献资料,回头将智藏思想置于朱子思想中进行考察,以尝试推导出智藏说是如何自朱子的学思系统中产生的,并讨论智为何能藏,且如何可藏等种种界说,及其与朱子其他重要学说观念的内在关系。
一、《玉山讲义》的背景与评价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南宋光宗绍熙五年甲寅(1195),朱子六十五岁下言:“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讲学于县庠。”“邑宰司马迈请为诸生讲说,先生辞,不获,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迈刻讲义一篇以传于世,此乃先生晚年亲切之训,读者其深味之。”①其中“玉山”,即今之江西省玉山县。按绍熙五年七月,光宗赵惇内禅,宁宗赵扩即位。八月,朱子入朝任侍讲,至十月十四日始讲。后由于进言得罪权臣韩侂胄,宁宗亦不喜朱子,便借故结束了朱子侍讲之职,前后仅四十六日②。故十一月十一日,朱子返闽途经江西省玉山县时,邑宰司马迈便趁此机会请其为诸生演讲。此整理后的讲答内容,由司马迈刻行传世。而此《讲义》,即今收于《朱子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七十四的《玉山讲义》③。
在《玉山讲义》中,有程拱④起问二事,朱子亦分别答之。其首问为孔孟“专言仁”与“兼言仁义”的意义与差别何在?与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有程珙起而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⑤另一问则是相较三代以前的圣贤以“中”“极”为本,孔子为何直接揭示“仁”以教人的问题:珙又请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着便是‘仁’,何也?”⑥
关于这个问题,朱子认为这是“列圣相传到此,方渐次说亲切处尔。夫子所以贤于尧、舜,于此亦可见其一端也。”⑦并举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⑧为例,以善性和气禀皆吾人天生而必有,故“古今圣愚,同此一性,则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笃信力行,则天下之理虽有至难,犹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为之不难乎?然或气禀昏愚而物欲深固,则其势虽顺且易,亦须勇猛着力,痛切加功,然后可以复于其初”①。此外,“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②,是以“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③,希望当时在玉山县庠听讲的诸生在“虚心涵泳、博考征验、不急于功利”的心态下戮力进德修业,“毋使今日之讲徒为空言,则区区之望也”④。而该次讲演也到此结束了⑤。
关于此讲义之价值及意义,不只《年谱》给予正面评价,近儒陈荣捷(1901—1994)先生认为“诸《年谱》谓此是朱子晚年亲切之词,读者其深味之。此言诚是。……讲时随口答问。归后偶与一朋友,因其未喻,录以报之。惟其出于胸中,可谓之晚年定论。日本盛行,非无故也”⑥。复以之为朱子论修养的基本文献,并评曰:“《玉山讲义》虽短,而于性善、四端、气禀,天理人欲,尊德性道问学,无不包括。直可以谓之朱子伦理学之轮廓。”⑦而束景南先生更将《玉山讲义》理解为记录了朱子归闽途中“一路反思所达到的最新认识,标志着他从被驱逐出朝的消沉中重新自强振厉起来的精神转折,甚至可以说,他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做的一次最精约明晰的理论概括”⑧。故可知此讲义于吾人了解朱子晚年思想实有其重要的文献意义。
二、朱子提出智藏说的文献基础
为方便通盘理解及下文讨论引用,现将朱子针对程珙第一问所答内容分为四段,并全录于下:
(一)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
(二)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
(三)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各自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
(四)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故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着习察,无不是着工夫处矣。①
以上便是朱子所答之全文引录。此下的讨论若有需要这四小段文字时,则直接引用,不另出注。此外,与智藏说直接相关的文献还有《文集》卷58中《答陈器之》第二书的最后两段文字:
(五)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收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
(六)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②
该书篇名下注曰“问《玉山讲义》”,这里笔者之所以引述后半部分文字,乃是因为前半部分文字与朱子所答大半重复,故不予多录。以上这一大段论述,第一段文字是朱子智藏说,乃至其学思体系之所以成立的重要基本态度,我们暂时将它留在最后才谈。至于第二至第五段文字的义理脉络,我们可以很快地联想到,智藏说的提立与朱子对性善及四端的理解应有密切的关系。而第六段,也就是最后一段的文字则申论智藏的价值及意义,故以下先针对第二至第五段文字的义理进行解读。
三、智藏说如何可能:智藏之于心性论的衡定
关于智为何能藏,而如何可藏的讨论,根据笔者的理解,其实应分以下数点予以讨论:
(一)理解性善之进路:《太极图说》
首先是朱子对于“性”的理解问题。朱子对于“性”生成本有的接受,是从濂溪处进行消化的,濂溪《太极图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①
在朱子的理解,理和气的关系是不离不杂的。理与气当然是不同的(不杂),但却需要有气才能得以彰显实现(不离)。故朱子除了认定“性只是此理”①外,由于“性则纯是善底”②,且“性是天生成许多道理”③、“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④,及人之所以生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⑤,这是朱子承袭《中庸》、《易传》和濂溪发展出的理解。是以《玉山讲义》第二段文字曰“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按韩愈所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一句,乃出自其《原性》。该句本作“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⑥,就是以仁、礼、信、义、智等为性之内容。故可知人之五常之“性”,亦即本有而立。
(二)“五常”与两种“四德”德性范畴间的转置互通
不过这里随之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仁义礼智、仁义中正两种“四德”之间的相配问题。我们先以仁义礼智为主来看这种问题。本来孟子原先就只以仁义礼智说心性之善,且若以五常言性,“信”德显然就无法统合。这点《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中也有提及。其曰:
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⑦
原来理(性作为朱子思想体系中终极的存有,无论由何种角度(由事随感而发显)切入,此中之理皆同体于一。且五常间也无所谓特定的分别次序可言,是“浑然不可分”的。朱子甚至说:
理,只是一个理。理举着,全无欠阙。且如言着仁,则都在仁上;言着诚,则都在诚上;言着忠恕,则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则都在忠信上。只为只是这个道理,自然血脉贯通。⑧
如此则只要将最终价值及归趋指向理/性,其实无论以何种道德范畴为出发点,皆无害于进德工夫。不过,“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①“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②“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③,且“性是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④,性/理中之万理,终究可归摄入仁、义、礼、智四大范畴之内,进而回归于以仁包四德(以专言言仁),如是则性之为体则显然可知。是以“信”之理便由肯定其为实有加以融摄:
或问:“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⑤
亦如上一节朱子所答第三段文字所说的:“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
如此便能顺利将五常之“信”收摄至四德上,甚至是全然肯定性理之真实无妄上。且最终之理乃通同为一,亦不须在德性分类间多绕工夫。
然而我们所需注意的乃是智之为德的关系。承《太极图说》所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本来理本是一,在“理”的层次上强分彼此是无意义的,但在“事”的层次上,总是有所差别。盖“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⑥,所以关于仁义中正与仁义礼智的辨析,还是有其必要性,《语类》中于此有言: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何不曰仁义中正?”曰:“此亦是且恁地说,当初某看时,也疑此。只要去强说,又说不得。后来子细看,乃知中正即是礼智,无可疑者。”⑦
又曰:
“中正仁义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义中正而已矣’,以圣人之心言之,犹孟子言‘仁义礼智’也。”①
原来“中正”就是“礼智”,那为什么要以“中正”代替“礼智”呢?朱子认为“中正”二字不仅“较有力”②,且能更为贴近说明并确实描述该德性:
问:“周子不言‘礼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礼智说得犹宽,中正则切而实矣。且谓之礼,尚或有不中节处。若谓之中,则无过不及,无非礼之礼,乃节文恰好处也。谓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谓之正,则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实也。”③
依照《玉山讲义》的理解,上文第三段文字曰:“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第四段文字则曰:“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且专以智本身来说,智本身所代表的是先天赋予人所本有,保证人能知觉且分别是非的道理。暂且先就能分别是非的标准来说,当然是要能知亲爱、别善恶,也就是能知其“正”,以做出最符合当下情况应有的判断。而此标准不是靠什么外在的环境或条件去影响,“正”当然也是同出于智的,故“知是非之正为智,故《通书》以正为智”④。《语类》亦有问答记曰:
问:“智与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见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唤做智了。”问:“只是真见得是,真见得非。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⑤
就如同“中”之于“礼”一样,“正”在此其实指的不过是智德本有且应有的标准罢了。因此“中正”终究不能将“礼智”的地位替换过来。不过朱子认为“正”之所以成为智之标准,还有其他的原因:
问:“‘中即礼,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于四德属贞,智要正。”⑥
问:“中正即礼智,何以不直言‘礼智’,而曰‘中正’?”曰:“‘礼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实。且中者,礼之极;正者,智之体。正是智亲切处。伊川解‘贞’字,谓‘正而固’也。一‘正’字未尽,必兼‘固’字。所谓‘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智是端的真知,恁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
所以‘正’字较亲切。”①
如同第一小节所言,朱子对性善的理解乃直承濂溪《太极图说》而来。因此,天命直接下贯善性于四时万物,天之四德“元亨利贞”与四时“春夏秋冬”及人之四德“仁义礼智”间便有一秩序性的比配关系,因而成为《仁说》以来至《玉山讲义》一贯的观点,也是智之所以能藏,即智藏说之得以成立的直接理据所在。
(三)天人四时四德的相合与智藏说的成立
依《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且阴阳互为其根,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最后生成人类、四时及万物,这点上文已经反复述及。朱子甚至说:“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②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这种理解的进路对朱子之于四端的看法有着什么影响。
在朱子,“生之理谓性”③,朱子定稿于四十四岁(乾道九年,1173年)④的《仁说》之首二段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仁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⑤
故可知朱子取元亨利贞比配春夏秋冬,并以此说解仁义礼智之思路于其中年时即已成形,可说是其一贯的理解。此段文字依李明辉先生的分判,朱子于此列举了四组不同的秩序,分别是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存有—伦理学的(onto-ethical)秩序(仁义礼智)及伦理—心理学的(ethico-psychological)秩序(爱恭宜别)。其中爱恭宜别是恻隐、辞让、羞恶、是非等四端的另一种说法。此外,复将第一组秩序(元亨利贞)与第二组秩序(春夏秋冬)视为理气关系,而第三组秩序(仁义礼智)与第四组秩序的关系则是性与情的已发未发关系,且性情关系是理气关系的特殊化①。朱子之《元亨利贞说》则更能简洁地把这个部分说清楚: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②
此中朱子以元亨利贞属性,生长收藏属情。而根据《仁说》所言,万物之所以生长收藏,是因为仁之生气贯穿于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现象所致,如此则元亨利贞自与春夏秋冬在“生”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程序。是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③且朱子又言:“‘元亨利贞’,其发见有次序。仁义礼智,在里面自有次序,到发见时随感而动,却无次序。”④
而仁义礼智则是“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⑤,是可知两者的关系是建立在由元亨利贞与仁义理智“里面”“生时”的内在秩序上。且智于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比配下,乃是保证理中之所以能知觉善恶,并因此做出正确判断,且能长留于心(即“贞而固”)之理。故前引《玉山讲义》第四段文字曰:
“‘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故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如此,“智则仁之分别”就是“冬则生之藏”,“智”与“藏”的关系便因此而建立。是则智之所以能藏,盖因其配同于四时之“冬”。也就是说,因为冬者有敛藏的意思,为使春日再行发散生物,生意到此依理自然翕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冬之所以敛藏,并不是在气上说,而是在理上见其事:
问:“‘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元亨是春夏,利贞是秋冬。秋冬生气既散,何以谓之收敛?”曰:“其气已散,收敛者乃其理耳。”曰:“冬间地下气暖,便也是气收敛在内。”曰:“上面气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来,却不是已散之气复为生气也。”①
故可知智所表现者,由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来看,乃理中能敛藏之理。是以《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的末段,也就是上引文中的第六段文字即扩充此意曰:“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
智由宇宙论所理解的敛藏之理,本由四时化生循环可见,故言“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然而于此“藏”尚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无迹”,即“藏迹”之意。为什么智相较于仁、义、礼等三德,“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呢?原来:
“仁礼属阳,属健;义知属阴,属顺”。问:“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②
关于阴阳健顺的分际,第三节所引、智藏说文献基础之第五段文字,即《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曰:“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自四而两,自两而一,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此是发挥《玉山讲义》中“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句而来。
为何仁义礼智又可归摄至仁义二德下呢?首先关于仁与礼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曰: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①
原来仁礼同是“敷施出来底”,在总体发生及形之于外的意义上就是作用处,代表阳德、属刚。然而为何不是仁属柔、义属刚呢?袁机仲便曾以此请问于朱子,朱子答曰:“殊不知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②故不仅在发用和敛藏关系上可见阴阳刚柔,四时替换亦可见阴阳刚柔。这便是体现《易传》天、地、人三才同一的意义。且这里所谓仁、义、礼的作用,便是四时春、夏、秋中之生、长、收,也是人之四德仁、义、礼中“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更是四端中之恻隐、辞让、羞恶。因为朱子于此将智之彰显发用定义得相当明白,“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当然,这里的“更无作用”乃是相较于内外发用而言,并不是全然的身外长物。
此外,“伊川常说:‘如今人说,力行是浅近事,惟知为上,知最为要紧。’《中庸》说‘知仁勇’,把知做擗初头说,可见知是要紧”。贺孙问:“孟子四端,何为以知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见,到一阳初动,这生意方从中出,也未发露,十二月也未尽发露。只管养在这里,到春方发生,到夏一齐都长,秋渐成,渐藏,冬依旧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终始’亦见得,无终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生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①
关于朱子于此理解孟子因循环而列智于四德之末,以及智藏有仁、义、礼另三德的看法,未必符合孟子原意,此待下文论及。但我们注意到,当智之理藏迹在知觉判断后,随即交由仁、义、礼等三德发用,如“问:‘有节文便是礼,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②。故曰: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为宾主,然仁智其总统也。‘恭而无礼则劳’,是以礼为主也;‘君子义以为质’,是以义为主也。盖四德未尝相离,遇事则迭见层出,要在人默而识之。”曰:“说得是。”③
“四德未尝相离”,即是上文朱子所谓“发时无次第”。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时机点,四德各有以之为主的发用处,此就是“性之四端,迭为宾主”。但回过头来,若无仁之生意贯穿四德,非“一阳初动”,四德便无以为用,是以最终仍是归摄而言“仁智其总统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宇宙论的比配上,智藏的重要是在于循环意义及终始意义上。不仅仁义礼智本身以仁为总摄而循环,智本身同时也是“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更是天地化生中“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的固然之理。且使人默而识之,又可以说是智之理应有的工夫论展现。故朱子赞以“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可说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四、智藏之发挥及其于朱子义理系统中的作用
在讨论完智藏说之如何提立及其在朱子理气心性论中之位置与意义后,接下来当由智藏说为一着眼点,探讨智藏动静关系的展开及其体用异解。
(一)成德意义下的动静关系:从主静、主敬到格物致知
依照上节最后所言,四端可归摄于仁义,且又因仁义所本之阴阳而有刚柔健顺等诸属性,当然本节的重点“动静”也因此而生。在此且让我们再回到朱子对濂溪“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的讨论: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此四物常在这里流转,然常靠着个静做主。若无夜,则做得昼不分晓;若无冬,则做得春夏不长茂。如人终日应接,却归来这里空处少歇,便精神较健。如生物而无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气也会竭了。中仁是动,正义是静。《通书》都是恁地说,如云“礼先而乐后”。①
根据我们上文所言天人四时四德的相配关系,主静的意思不仅可由四时得见,元亨利贞上也同样可见此意: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何也?”曰:“中正仁义分属动静,而圣人则主于静。盖正所以能中,义所以能仁。‘克己复礼’,义也,义故能仁。易言‘利贞者,性情也’。元亨是发用处,必至于利贞,乃见干之实体。万物到秋冬收敛成实,方见得他本质,故曰‘性情’。此亦主静之说也。”②
我们已可理解,朱子认为仁主生属刚,义主属柔,故仁礼即是动,而义智即是静,在化生循环中,相互为用。但为何四德之流转,又“常靠着个静做主”呢?原来“至于主静,是以正与义为体,中与仁为用。圣人只是主静,自有动底道理。譬如人说话,也须是先沉默,然后可以说话。盖沉默中便有个言语底意思”③。《太极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故化生之始,乃在于“动”,也就是“干之实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便是静后见得动恁地好”①。是以所谓“主静”,并不是单纯地以“静”为归宗,而是要在“静”中观其“动”意。故曰:
问:“太极‘主静’之说,是先静后动否?”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虽是合下静,静而后动,若细推时,未静时须先动来,所谓‘如环无端,互为其根’。谓如在人,人之动作及其成就,却只在静。便如浑沦未判之前,亦须曾明盛一番来。只是这道理层层流转,不可穷诘,太极图中尽之。动极生静,亦非是又别有一个静来继此动。但动极则自然静,静极则自然动。推而上之,没理会处。”②
而此“静”该当作何解?朱子续曰:
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③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云“敬则自虚静”。须是如此做工夫。④
故“静”当以“无欲”为要,乃是工夫意义上之“静”,并非佛老本体意义上的“虚静”。故随顺以上对“静”字的理解,由“静”推扩至“敬”的工夫论处便可见了。所以《答张钦夫》曰:
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则无以着此心之妙。人虽欲仁,而或不敬,则无以致求仁之功。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立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以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尝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通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然则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者,在此而已。盖主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则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①
“敬”贯穿动静语默,静中有工夫(庄敬以涵养,即伊川“涵养须用敬”之意),动中亦有工夫(敬以致察,即伊川“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意)②。而所谓“敬则心之贞”,贞就是收敛凝成之意。由上节可知,智所表现者,以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来看,乃理中能敛藏之理。然而“敬”与“智藏”的关系并不只于敛藏之理上,这里笔者引孟子言曰: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③
又“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④,是可推出智之实,乃在知仁义而弗去。然而此处“知”的意思和“智”德之理很明显是有差距的。要讨论这个问题前,首先须注意,朱子一向反对直接以觉训仁。此中义理脉络,许多前辈学者早已深入讨论,故于此即不述及,笔者只想因智藏说补充朱子反对以觉训仁的理由,甚至是如《玉山讲义》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的思想关系。总归一句,这都是因为朱子将所谓的“知觉”归于智之理,而仁只是“心之德,爱之理”所致。其辨曰:
问:“以爱名仁,是仁之迹;以觉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为仁。’毕竟仁之全体如何识认?‘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是仁之体否?”先生曰:“觉,决不可以言仁,虽足以知仁,自属智了。爱分明是仁之迹。”⑤
由此可知,“仁固有知觉;唤知觉做仁,却不得”⑥,且“所知觉者是理,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⑦,知觉与仁的关系,不过是仁中所包含的智理发用而生,并不是仁本身就是知觉。而此智理所发用于心者,便是知觉。所以这个知觉的意义:
问:横渠谓:“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如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先生谓:尽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尽心是知至之事。如何?”曰:“心与性只一般,知与尽不同。所谓知,便是心了。”问:“知是心之神明,似与四端所谓智不同?”曰:“此‘知’字义又大。然孔子多说仁、智,如‘元亨利贞’,元便是仁,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无贞,则元无起处;无智,则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终始。’有终便有始。智之所以为大者,以其有知也。”①
在心统性情的意义上,此“知”所涵盖的层面当然比智德之“智”来得广泛。且在朱子,其“知”有二:“直卿曰:‘五常中说知有两般:就知识处看,用着知识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为是为非者,亦知也。一属理,一属情。’曰:‘固是,道德皆有体有用。’”②
我们可以说,在情上发用、以知识积累应事者,可同于张载所提揭的“见闻之知”;而就理上所看,能知善恶是非的,乃同于“德性之知”。我们知道,“德性之知”本不是经由经验知识而能得;可是前文引文中有“其智愈大,其藏愈深”一句,这很明显是在善性的存养扩充上立论。不过落实到工夫实践上来说,就如同“敬则心之贞”一样,终究要回到“心”的角度来讨论。
朱子所谓心与知觉的关系,虽然心是“气之精爽”③,且“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④,然而就整体发用处来说,总体亦称为“知觉”。故言曰: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邪?”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问:“心之发处是气否?”曰:“也只是知觉。”⑤
若再与上文合观,则笔者认为朱子所谓大于智德的“知”,或是能越藏越大的“智”,都是落于情上的“知觉”来说的。其证据是朱子论知行关系时言:
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①
林子渊问知止至能得,曰:“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失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②
儒家本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要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才能更见其真谛。孟子曾评曰: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③
而朱子《集注》解曰: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尽。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④
朱子认为伯夷、伊尹及柳下惠之所以未能尽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开始就未能正确地通体认知大道;又《语类》曰:
又问:“‘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工夫紧要处,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极于一偏,缘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终之成也亦各至于一偏之极。孔子合下尽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无所不尽。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该毕备,而无一德一行之或阙。”⑤
问“圣智”,曰:“智是知得到,圣是行得到。”⑥
所以不仅智为吾人作工夫之首要处,且智德之充养,乃在于事上发用的时时涵养察识,及格物致知:
问:“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极尽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学者必须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则无不明矣。‘致’字,如推开去。譬如暗室中见些子明处,便寻从此明处去。忽然出到外面,见得大小大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事事物物,各有个至极之处。所谓‘止’者,即至极之处也。然须是极尽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八分,犹有二分未尽,也不是。须是极尽,方得。”又
曰:“知在我,理在物。”①
而总归于自身时(其实道德实践从未离于自身),“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②,内外一体。所谓“‘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载、圣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见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来之事,便是‘知来’”③。
德性之知之所以不萌于见闻,就是此中众理,早为吾人本身所固有。不过这样的界定,却无害于不断地在经验中确认自家德性的正向循环认知(故朱子主张先涵养后察识),回过头来审视前文,如此才是“心官至灵,藏往知来”④的理境。
(二)终始意义下的体用理境:仁智双彰之谓圣
《论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⑤这本来是随顺着个人修养气质禀性所好所向的气象描述语,而朱子引申解曰:
问:“‘知者动,仁者静’,动是运动周流,静是安静不迁,此以成德之体而言也。若论仁知之本体,知则渊深不测,众理于是而敛藏,所谓‘诚之复’,则未尝不静;仁者包藏发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谓‘诚之通’,则未尝不动。”曰:“知者动意思常多,故以动为主;仁者静意思常多,故以静为主。今夫水渊深不测,是静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于动。山包藏发育之意,是动也,而安重不迁,故主于静。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静也,毕竟他是动物。故知动仁静,是体段模样意思如此也,常以心体之便见。”①
仁德与智德动静相生,互为其根,这点我们在上一小节已经予以说明。然而当我们回到终始意义上加以进一步的探讨,仁智交接之际不仅可见“万化之机轴”,仁智的相互彰显更是吾人迈向成德修业的必然之路。孟子有言: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②
而《朱子语类》曰:
“成己,仁也”,是体;“成物,知也”,是用。“学不厌,知也”,是体;“教不倦,仁也”,是用。③
此乃合《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④一同作解。故引申言曰:
“克己复礼为仁”,岂不是成己?“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岂不是成物?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⑤
《论语》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⑥此是道德心之不容已,而由其发用处,可见智实成乎万物。不过前文已述及,智乃是敛藏之理,故尽管智是成物,一旦发用便即伏藏,犹未可见其显。所以:
“显诸仁,藏诸用”,二句只是一事。“显诸仁”是可见底,便是“继之者善也”;“藏诸用”是不可见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诸用”是“显诸仁”底骨子,正如说“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张文定公说“事未判属阳,已判属阴”,亦是此意。“显诸仁,藏诸用”,亦如“元亨利贞”,元亨是发用流行处,利贞便是流行底骨子。又曰:“显诸仁”,德之所以盛;“藏诸用”,业之所以成。譬如一树,一根生许多枝叶花实,此是“显诸仁”处。及至结实,一核成一个种子,此是“藏诸用”处。生生不已,所谓“日新”也;万物无不具此理,所谓“富有”也。⑦
即体而用,而后又藏其用。是以智藏乃是“退藏于密”:
“退藏于密”,密是主静处。“万化出焉”者,动中之静固是静。又有大静,万化森然者。①
“退藏于密”时,固是不用这物事。“吉凶与民同患”,也不用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于密”,是不用事时。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时,先安排在这里了;事到时,恁地来,恁地应。②
由此可见天地生生大化之德与圣人参赞化育之妙。
五、结语
关于智藏的成立及发挥,已备言于前,此不再赘述。笔者只是想在结语处对朱子确认性善的整体理解进路做一些反省式的响应:
本来依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性善的内容固然可以是仁义理智,但其彰显乃是由仁义内在的本心所自然生发而见。故德性的动源,实是道德本心上事而已。但是在朱子的人性论理解里,一切“生”之所以为生的根源只能是太极的“动”之理。此外,朱子以“性即理”作为一切德性原则的总归,故认为“知性”反而应先于“尽心”③。所以朱子念兹在兹的“生意”、“生生之理”,其实也多止于“化生”,而未能说是“创生”。
过去以天地化生来比附人事者,首推董仲舒。葛荣晋先生认为,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从外部之阴阳学说为“仁”寻找其宇宙论根据④。牟宗三先生对于汉儒天人感应观的解释,曾有着如下的看法:(1)汉人的思想一切都系统化、具体化、切实化,他们没有神秘,一切都予以解析,汉时的天人感应观就由这种根本特性而产生出。(2)有了此根本特性,还不足以言感应,必须有以下三个根本原则,感应说始能建设起来。此三原则是:(1)宇宙条理;(2)天人同情;(3)天人合一。这三个原则实在说来是分不开的,举一可以赅三。①的确,董仲舒藉由着阴阳五行建立了一套绵密的气化宇宙观,但我们都知道,董仲舒这套理路无论是在“天”或是在“人”,毕竟流于机械性,也同归于“化生”。如从通篇文章来看,朱子沿用了这种诠释传统来证成儒家的形上哲学,其偏于气化上的理解意味就浓重了许多。无怪乎方东美先生做出了朱子为董仲舒所惑,是以不能直接传承真正孔子精神的酷评②。
然而在吾人研读朱子哲学时,必须时时回头审视其理气不离不杂在化生成物上的意义,就如同《玉山讲义》第一段文字中所表述朱子的基本态度一样,朱子之所以对仁义礼智等四端的理解进行如此高度且细密的分判,除了本身强烈的理论兴趣外,更是为了在实践上确立道德与吾人自身内在而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就是因为朱子事事物物都要求个根柢,“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如此才能“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庶几免于“支离”。所以尽管朱子形上学气化意味甚重,但他不是单纯地将天人关系牵拉比附。当然,他也未曾离理言气,这是因为无论天地大化或是人物诸德,全都贯有一最终指导归趋的理的关系。这一基本立场在吾人理解朱子学说体系是极为重要的。是以当我们以这种观点来看待所谓的智藏说时,虽然因其动静体用而在各种不同的经典与境下有其别出的用意,但“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着习察,无不是着工夫处矣”。
一、《玉山讲义》的背景与评价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南宋光宗绍熙五年甲寅(1195),朱子六十五岁下言:“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讲学于县庠。”“邑宰司马迈请为诸生讲说,先生辞,不获,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迈刻讲义一篇以传于世,此乃先生晚年亲切之训,读者其深味之。”①其中“玉山”,即今之江西省玉山县。按绍熙五年七月,光宗赵惇内禅,宁宗赵扩即位。八月,朱子入朝任侍讲,至十月十四日始讲。后由于进言得罪权臣韩侂胄,宁宗亦不喜朱子,便借故结束了朱子侍讲之职,前后仅四十六日②。故十一月十一日,朱子返闽途经江西省玉山县时,邑宰司马迈便趁此机会请其为诸生演讲。此整理后的讲答内容,由司马迈刻行传世。而此《讲义》,即今收于《朱子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七十四的《玉山讲义》③。
在《玉山讲义》中,有程拱④起问二事,朱子亦分别答之。其首问为孔孟“专言仁”与“兼言仁义”的意义与差别何在?与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有程珙起而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⑤另一问则是相较三代以前的圣贤以“中”“极”为本,孔子为何直接揭示“仁”以教人的问题:珙又请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着便是‘仁’,何也?”⑥
关于这个问题,朱子认为这是“列圣相传到此,方渐次说亲切处尔。夫子所以贤于尧、舜,于此亦可见其一端也。”⑦并举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⑧为例,以善性和气禀皆吾人天生而必有,故“古今圣愚,同此一性,则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笃信力行,则天下之理虽有至难,犹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为之不难乎?然或气禀昏愚而物欲深固,则其势虽顺且易,亦须勇猛着力,痛切加功,然后可以复于其初”①。此外,“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②,是以“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③,希望当时在玉山县庠听讲的诸生在“虚心涵泳、博考征验、不急于功利”的心态下戮力进德修业,“毋使今日之讲徒为空言,则区区之望也”④。而该次讲演也到此结束了⑤。
关于此讲义之价值及意义,不只《年谱》给予正面评价,近儒陈荣捷(1901—1994)先生认为“诸《年谱》谓此是朱子晚年亲切之词,读者其深味之。此言诚是。……讲时随口答问。归后偶与一朋友,因其未喻,录以报之。惟其出于胸中,可谓之晚年定论。日本盛行,非无故也”⑥。复以之为朱子论修养的基本文献,并评曰:“《玉山讲义》虽短,而于性善、四端、气禀,天理人欲,尊德性道问学,无不包括。直可以谓之朱子伦理学之轮廓。”⑦而束景南先生更将《玉山讲义》理解为记录了朱子归闽途中“一路反思所达到的最新认识,标志着他从被驱逐出朝的消沉中重新自强振厉起来的精神转折,甚至可以说,他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做的一次最精约明晰的理论概括”⑧。故可知此讲义于吾人了解朱子晚年思想实有其重要的文献意义。
二、朱子提出智藏说的文献基础
为方便通盘理解及下文讨论引用,现将朱子针对程珙第一问所答内容分为四段,并全录于下:
(一)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
(二)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
(三)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各自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
(四)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故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着习察,无不是着工夫处矣。①
以上便是朱子所答之全文引录。此下的讨论若有需要这四小段文字时,则直接引用,不另出注。此外,与智藏说直接相关的文献还有《文集》卷58中《答陈器之》第二书的最后两段文字:
(五)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收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
(六)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②
该书篇名下注曰“问《玉山讲义》”,这里笔者之所以引述后半部分文字,乃是因为前半部分文字与朱子所答大半重复,故不予多录。以上这一大段论述,第一段文字是朱子智藏说,乃至其学思体系之所以成立的重要基本态度,我们暂时将它留在最后才谈。至于第二至第五段文字的义理脉络,我们可以很快地联想到,智藏说的提立与朱子对性善及四端的理解应有密切的关系。而第六段,也就是最后一段的文字则申论智藏的价值及意义,故以下先针对第二至第五段文字的义理进行解读。
三、智藏说如何可能:智藏之于心性论的衡定
关于智为何能藏,而如何可藏的讨论,根据笔者的理解,其实应分以下数点予以讨论:
(一)理解性善之进路:《太极图说》
首先是朱子对于“性”的理解问题。朱子对于“性”生成本有的接受,是从濂溪处进行消化的,濂溪《太极图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①
在朱子的理解,理和气的关系是不离不杂的。理与气当然是不同的(不杂),但却需要有气才能得以彰显实现(不离)。故朱子除了认定“性只是此理”①外,由于“性则纯是善底”②,且“性是天生成许多道理”③、“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④,及人之所以生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⑤,这是朱子承袭《中庸》、《易传》和濂溪发展出的理解。是以《玉山讲义》第二段文字曰“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按韩愈所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一句,乃出自其《原性》。该句本作“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⑥,就是以仁、礼、信、义、智等为性之内容。故可知人之五常之“性”,亦即本有而立。
(二)“五常”与两种“四德”德性范畴间的转置互通
不过这里随之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仁义礼智、仁义中正两种“四德”之间的相配问题。我们先以仁义礼智为主来看这种问题。本来孟子原先就只以仁义礼智说心性之善,且若以五常言性,“信”德显然就无法统合。这点《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中也有提及。其曰:
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⑦
原来理(性作为朱子思想体系中终极的存有,无论由何种角度(由事随感而发显)切入,此中之理皆同体于一。且五常间也无所谓特定的分别次序可言,是“浑然不可分”的。朱子甚至说:
理,只是一个理。理举着,全无欠阙。且如言着仁,则都在仁上;言着诚,则都在诚上;言着忠恕,则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则都在忠信上。只为只是这个道理,自然血脉贯通。⑧
如此则只要将最终价值及归趋指向理/性,其实无论以何种道德范畴为出发点,皆无害于进德工夫。不过,“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①“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②“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③,且“性是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④,性/理中之万理,终究可归摄入仁、义、礼、智四大范畴之内,进而回归于以仁包四德(以专言言仁),如是则性之为体则显然可知。是以“信”之理便由肯定其为实有加以融摄:
或问:“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⑤
亦如上一节朱子所答第三段文字所说的:“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
如此便能顺利将五常之“信”收摄至四德上,甚至是全然肯定性理之真实无妄上。且最终之理乃通同为一,亦不须在德性分类间多绕工夫。
然而我们所需注意的乃是智之为德的关系。承《太极图说》所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本来理本是一,在“理”的层次上强分彼此是无意义的,但在“事”的层次上,总是有所差别。盖“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⑥,所以关于仁义中正与仁义礼智的辨析,还是有其必要性,《语类》中于此有言: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何不曰仁义中正?”曰:“此亦是且恁地说,当初某看时,也疑此。只要去强说,又说不得。后来子细看,乃知中正即是礼智,无可疑者。”⑦
又曰:
“中正仁义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义中正而已矣’,以圣人之心言之,犹孟子言‘仁义礼智’也。”①
原来“中正”就是“礼智”,那为什么要以“中正”代替“礼智”呢?朱子认为“中正”二字不仅“较有力”②,且能更为贴近说明并确实描述该德性:
问:“周子不言‘礼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礼智说得犹宽,中正则切而实矣。且谓之礼,尚或有不中节处。若谓之中,则无过不及,无非礼之礼,乃节文恰好处也。谓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谓之正,则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实也。”③
依照《玉山讲义》的理解,上文第三段文字曰:“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第四段文字则曰:“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且专以智本身来说,智本身所代表的是先天赋予人所本有,保证人能知觉且分别是非的道理。暂且先就能分别是非的标准来说,当然是要能知亲爱、别善恶,也就是能知其“正”,以做出最符合当下情况应有的判断。而此标准不是靠什么外在的环境或条件去影响,“正”当然也是同出于智的,故“知是非之正为智,故《通书》以正为智”④。《语类》亦有问答记曰:
问:“智与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见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唤做智了。”问:“只是真见得是,真见得非。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⑤
就如同“中”之于“礼”一样,“正”在此其实指的不过是智德本有且应有的标准罢了。因此“中正”终究不能将“礼智”的地位替换过来。不过朱子认为“正”之所以成为智之标准,还有其他的原因:
问:“‘中即礼,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于四德属贞,智要正。”⑥
问:“中正即礼智,何以不直言‘礼智’,而曰‘中正’?”曰:“‘礼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实。且中者,礼之极;正者,智之体。正是智亲切处。伊川解‘贞’字,谓‘正而固’也。一‘正’字未尽,必兼‘固’字。所谓‘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智是端的真知,恁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
所以‘正’字较亲切。”①
如同第一小节所言,朱子对性善的理解乃直承濂溪《太极图说》而来。因此,天命直接下贯善性于四时万物,天之四德“元亨利贞”与四时“春夏秋冬”及人之四德“仁义礼智”间便有一秩序性的比配关系,因而成为《仁说》以来至《玉山讲义》一贯的观点,也是智之所以能藏,即智藏说之得以成立的直接理据所在。
(三)天人四时四德的相合与智藏说的成立
依《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且阴阳互为其根,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最后生成人类、四时及万物,这点上文已经反复述及。朱子甚至说:“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②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这种理解的进路对朱子之于四端的看法有着什么影响。
在朱子,“生之理谓性”③,朱子定稿于四十四岁(乾道九年,1173年)④的《仁说》之首二段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仁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⑤
故可知朱子取元亨利贞比配春夏秋冬,并以此说解仁义礼智之思路于其中年时即已成形,可说是其一贯的理解。此段文字依李明辉先生的分判,朱子于此列举了四组不同的秩序,分别是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存有—伦理学的(onto-ethical)秩序(仁义礼智)及伦理—心理学的(ethico-psychological)秩序(爱恭宜别)。其中爱恭宜别是恻隐、辞让、羞恶、是非等四端的另一种说法。此外,复将第一组秩序(元亨利贞)与第二组秩序(春夏秋冬)视为理气关系,而第三组秩序(仁义礼智)与第四组秩序的关系则是性与情的已发未发关系,且性情关系是理气关系的特殊化①。朱子之《元亨利贞说》则更能简洁地把这个部分说清楚: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②
此中朱子以元亨利贞属性,生长收藏属情。而根据《仁说》所言,万物之所以生长收藏,是因为仁之生气贯穿于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现象所致,如此则元亨利贞自与春夏秋冬在“生”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程序。是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③且朱子又言:“‘元亨利贞’,其发见有次序。仁义礼智,在里面自有次序,到发见时随感而动,却无次序。”④
而仁义礼智则是“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⑤,是可知两者的关系是建立在由元亨利贞与仁义理智“里面”“生时”的内在秩序上。且智于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比配下,乃是保证理中之所以能知觉善恶,并因此做出正确判断,且能长留于心(即“贞而固”)之理。故前引《玉山讲义》第四段文字曰:
“‘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故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如此,“智则仁之分别”就是“冬则生之藏”,“智”与“藏”的关系便因此而建立。是则智之所以能藏,盖因其配同于四时之“冬”。也就是说,因为冬者有敛藏的意思,为使春日再行发散生物,生意到此依理自然翕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冬之所以敛藏,并不是在气上说,而是在理上见其事:
问:“‘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元亨是春夏,利贞是秋冬。秋冬生气既散,何以谓之收敛?”曰:“其气已散,收敛者乃其理耳。”曰:“冬间地下气暖,便也是气收敛在内。”曰:“上面气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来,却不是已散之气复为生气也。”①
故可知智所表现者,由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来看,乃理中能敛藏之理。是以《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的末段,也就是上引文中的第六段文字即扩充此意曰:“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
智由宇宙论所理解的敛藏之理,本由四时化生循环可见,故言“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然而于此“藏”尚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无迹”,即“藏迹”之意。为什么智相较于仁、义、礼等三德,“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呢?原来:
“仁礼属阳,属健;义知属阴,属顺”。问:“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②
关于阴阳健顺的分际,第三节所引、智藏说文献基础之第五段文字,即《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曰:“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自四而两,自两而一,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此是发挥《玉山讲义》中“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句而来。
为何仁义礼智又可归摄至仁义二德下呢?首先关于仁与礼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曰: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①
原来仁礼同是“敷施出来底”,在总体发生及形之于外的意义上就是作用处,代表阳德、属刚。然而为何不是仁属柔、义属刚呢?袁机仲便曾以此请问于朱子,朱子答曰:“殊不知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②故不仅在发用和敛藏关系上可见阴阳刚柔,四时替换亦可见阴阳刚柔。这便是体现《易传》天、地、人三才同一的意义。且这里所谓仁、义、礼的作用,便是四时春、夏、秋中之生、长、收,也是人之四德仁、义、礼中“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更是四端中之恻隐、辞让、羞恶。因为朱子于此将智之彰显发用定义得相当明白,“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当然,这里的“更无作用”乃是相较于内外发用而言,并不是全然的身外长物。
此外,“伊川常说:‘如今人说,力行是浅近事,惟知为上,知最为要紧。’《中庸》说‘知仁勇’,把知做擗初头说,可见知是要紧”。贺孙问:“孟子四端,何为以知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见,到一阳初动,这生意方从中出,也未发露,十二月也未尽发露。只管养在这里,到春方发生,到夏一齐都长,秋渐成,渐藏,冬依旧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终始’亦见得,无终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生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①
关于朱子于此理解孟子因循环而列智于四德之末,以及智藏有仁、义、礼另三德的看法,未必符合孟子原意,此待下文论及。但我们注意到,当智之理藏迹在知觉判断后,随即交由仁、义、礼等三德发用,如“问:‘有节文便是礼,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②。故曰: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为宾主,然仁智其总统也。‘恭而无礼则劳’,是以礼为主也;‘君子义以为质’,是以义为主也。盖四德未尝相离,遇事则迭见层出,要在人默而识之。”曰:“说得是。”③
“四德未尝相离”,即是上文朱子所谓“发时无次第”。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时机点,四德各有以之为主的发用处,此就是“性之四端,迭为宾主”。但回过头来,若无仁之生意贯穿四德,非“一阳初动”,四德便无以为用,是以最终仍是归摄而言“仁智其总统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宇宙论的比配上,智藏的重要是在于循环意义及终始意义上。不仅仁义礼智本身以仁为总摄而循环,智本身同时也是“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更是天地化生中“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的固然之理。且使人默而识之,又可以说是智之理应有的工夫论展现。故朱子赞以“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可说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四、智藏之发挥及其于朱子义理系统中的作用
在讨论完智藏说之如何提立及其在朱子理气心性论中之位置与意义后,接下来当由智藏说为一着眼点,探讨智藏动静关系的展开及其体用异解。
(一)成德意义下的动静关系:从主静、主敬到格物致知
依照上节最后所言,四端可归摄于仁义,且又因仁义所本之阴阳而有刚柔健顺等诸属性,当然本节的重点“动静”也因此而生。在此且让我们再回到朱子对濂溪“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的讨论: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此四物常在这里流转,然常靠着个静做主。若无夜,则做得昼不分晓;若无冬,则做得春夏不长茂。如人终日应接,却归来这里空处少歇,便精神较健。如生物而无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气也会竭了。中仁是动,正义是静。《通书》都是恁地说,如云“礼先而乐后”。①
根据我们上文所言天人四时四德的相配关系,主静的意思不仅可由四时得见,元亨利贞上也同样可见此意: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何也?”曰:“中正仁义分属动静,而圣人则主于静。盖正所以能中,义所以能仁。‘克己复礼’,义也,义故能仁。易言‘利贞者,性情也’。元亨是发用处,必至于利贞,乃见干之实体。万物到秋冬收敛成实,方见得他本质,故曰‘性情’。此亦主静之说也。”②
我们已可理解,朱子认为仁主生属刚,义主属柔,故仁礼即是动,而义智即是静,在化生循环中,相互为用。但为何四德之流转,又“常靠着个静做主”呢?原来“至于主静,是以正与义为体,中与仁为用。圣人只是主静,自有动底道理。譬如人说话,也须是先沉默,然后可以说话。盖沉默中便有个言语底意思”③。《太极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故化生之始,乃在于“动”,也就是“干之实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便是静后见得动恁地好”①。是以所谓“主静”,并不是单纯地以“静”为归宗,而是要在“静”中观其“动”意。故曰:
问:“太极‘主静’之说,是先静后动否?”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虽是合下静,静而后动,若细推时,未静时须先动来,所谓‘如环无端,互为其根’。谓如在人,人之动作及其成就,却只在静。便如浑沦未判之前,亦须曾明盛一番来。只是这道理层层流转,不可穷诘,太极图中尽之。动极生静,亦非是又别有一个静来继此动。但动极则自然静,静极则自然动。推而上之,没理会处。”②
而此“静”该当作何解?朱子续曰:
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③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云“敬则自虚静”。须是如此做工夫。④
故“静”当以“无欲”为要,乃是工夫意义上之“静”,并非佛老本体意义上的“虚静”。故随顺以上对“静”字的理解,由“静”推扩至“敬”的工夫论处便可见了。所以《答张钦夫》曰:
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则无以着此心之妙。人虽欲仁,而或不敬,则无以致求仁之功。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立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以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尝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通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然则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者,在此而已。盖主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则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①
“敬”贯穿动静语默,静中有工夫(庄敬以涵养,即伊川“涵养须用敬”之意),动中亦有工夫(敬以致察,即伊川“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意)②。而所谓“敬则心之贞”,贞就是收敛凝成之意。由上节可知,智所表现者,以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来看,乃理中能敛藏之理。然而“敬”与“智藏”的关系并不只于敛藏之理上,这里笔者引孟子言曰: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③
又“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④,是可推出智之实,乃在知仁义而弗去。然而此处“知”的意思和“智”德之理很明显是有差距的。要讨论这个问题前,首先须注意,朱子一向反对直接以觉训仁。此中义理脉络,许多前辈学者早已深入讨论,故于此即不述及,笔者只想因智藏说补充朱子反对以觉训仁的理由,甚至是如《玉山讲义》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的思想关系。总归一句,这都是因为朱子将所谓的“知觉”归于智之理,而仁只是“心之德,爱之理”所致。其辨曰:
问:“以爱名仁,是仁之迹;以觉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为仁。’毕竟仁之全体如何识认?‘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是仁之体否?”先生曰:“觉,决不可以言仁,虽足以知仁,自属智了。爱分明是仁之迹。”⑤
由此可知,“仁固有知觉;唤知觉做仁,却不得”⑥,且“所知觉者是理,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⑦,知觉与仁的关系,不过是仁中所包含的智理发用而生,并不是仁本身就是知觉。而此智理所发用于心者,便是知觉。所以这个知觉的意义:
问:横渠谓:“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如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先生谓:尽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尽心是知至之事。如何?”曰:“心与性只一般,知与尽不同。所谓知,便是心了。”问:“知是心之神明,似与四端所谓智不同?”曰:“此‘知’字义又大。然孔子多说仁、智,如‘元亨利贞’,元便是仁,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无贞,则元无起处;无智,则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终始。’有终便有始。智之所以为大者,以其有知也。”①
在心统性情的意义上,此“知”所涵盖的层面当然比智德之“智”来得广泛。且在朱子,其“知”有二:“直卿曰:‘五常中说知有两般:就知识处看,用着知识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为是为非者,亦知也。一属理,一属情。’曰:‘固是,道德皆有体有用。’”②
我们可以说,在情上发用、以知识积累应事者,可同于张载所提揭的“见闻之知”;而就理上所看,能知善恶是非的,乃同于“德性之知”。我们知道,“德性之知”本不是经由经验知识而能得;可是前文引文中有“其智愈大,其藏愈深”一句,这很明显是在善性的存养扩充上立论。不过落实到工夫实践上来说,就如同“敬则心之贞”一样,终究要回到“心”的角度来讨论。
朱子所谓心与知觉的关系,虽然心是“气之精爽”③,且“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④,然而就整体发用处来说,总体亦称为“知觉”。故言曰: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邪?”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问:“心之发处是气否?”曰:“也只是知觉。”⑤
若再与上文合观,则笔者认为朱子所谓大于智德的“知”,或是能越藏越大的“智”,都是落于情上的“知觉”来说的。其证据是朱子论知行关系时言:
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①
林子渊问知止至能得,曰:“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失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②
儒家本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要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才能更见其真谛。孟子曾评曰: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③
而朱子《集注》解曰: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尽。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④
朱子认为伯夷、伊尹及柳下惠之所以未能尽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开始就未能正确地通体认知大道;又《语类》曰:
又问:“‘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工夫紧要处,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极于一偏,缘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终之成也亦各至于一偏之极。孔子合下尽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无所不尽。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该毕备,而无一德一行之或阙。”⑤
问“圣智”,曰:“智是知得到,圣是行得到。”⑥
所以不仅智为吾人作工夫之首要处,且智德之充养,乃在于事上发用的时时涵养察识,及格物致知:
问:“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极尽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学者必须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则无不明矣。‘致’字,如推开去。譬如暗室中见些子明处,便寻从此明处去。忽然出到外面,见得大小大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事事物物,各有个至极之处。所谓‘止’者,即至极之处也。然须是极尽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八分,犹有二分未尽,也不是。须是极尽,方得。”又
曰:“知在我,理在物。”①
而总归于自身时(其实道德实践从未离于自身),“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②,内外一体。所谓“‘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载、圣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见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来之事,便是‘知来’”③。
德性之知之所以不萌于见闻,就是此中众理,早为吾人本身所固有。不过这样的界定,却无害于不断地在经验中确认自家德性的正向循环认知(故朱子主张先涵养后察识),回过头来审视前文,如此才是“心官至灵,藏往知来”④的理境。
(二)终始意义下的体用理境:仁智双彰之谓圣
《论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⑤这本来是随顺着个人修养气质禀性所好所向的气象描述语,而朱子引申解曰:
问:“‘知者动,仁者静’,动是运动周流,静是安静不迁,此以成德之体而言也。若论仁知之本体,知则渊深不测,众理于是而敛藏,所谓‘诚之复’,则未尝不静;仁者包藏发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谓‘诚之通’,则未尝不动。”曰:“知者动意思常多,故以动为主;仁者静意思常多,故以静为主。今夫水渊深不测,是静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于动。山包藏发育之意,是动也,而安重不迁,故主于静。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静也,毕竟他是动物。故知动仁静,是体段模样意思如此也,常以心体之便见。”①
仁德与智德动静相生,互为其根,这点我们在上一小节已经予以说明。然而当我们回到终始意义上加以进一步的探讨,仁智交接之际不仅可见“万化之机轴”,仁智的相互彰显更是吾人迈向成德修业的必然之路。孟子有言: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②
而《朱子语类》曰:
“成己,仁也”,是体;“成物,知也”,是用。“学不厌,知也”,是体;“教不倦,仁也”,是用。③
此乃合《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④一同作解。故引申言曰:
“克己复礼为仁”,岂不是成己?“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岂不是成物?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⑤
《论语》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⑥此是道德心之不容已,而由其发用处,可见智实成乎万物。不过前文已述及,智乃是敛藏之理,故尽管智是成物,一旦发用便即伏藏,犹未可见其显。所以:
“显诸仁,藏诸用”,二句只是一事。“显诸仁”是可见底,便是“继之者善也”;“藏诸用”是不可见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诸用”是“显诸仁”底骨子,正如说“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张文定公说“事未判属阳,已判属阴”,亦是此意。“显诸仁,藏诸用”,亦如“元亨利贞”,元亨是发用流行处,利贞便是流行底骨子。又曰:“显诸仁”,德之所以盛;“藏诸用”,业之所以成。譬如一树,一根生许多枝叶花实,此是“显诸仁”处。及至结实,一核成一个种子,此是“藏诸用”处。生生不已,所谓“日新”也;万物无不具此理,所谓“富有”也。⑦
即体而用,而后又藏其用。是以智藏乃是“退藏于密”:
“退藏于密”,密是主静处。“万化出焉”者,动中之静固是静。又有大静,万化森然者。①
“退藏于密”时,固是不用这物事。“吉凶与民同患”,也不用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于密”,是不用事时。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时,先安排在这里了;事到时,恁地来,恁地应。②
由此可见天地生生大化之德与圣人参赞化育之妙。
五、结语
关于智藏的成立及发挥,已备言于前,此不再赘述。笔者只是想在结语处对朱子确认性善的整体理解进路做一些反省式的响应:
本来依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性善的内容固然可以是仁义理智,但其彰显乃是由仁义内在的本心所自然生发而见。故德性的动源,实是道德本心上事而已。但是在朱子的人性论理解里,一切“生”之所以为生的根源只能是太极的“动”之理。此外,朱子以“性即理”作为一切德性原则的总归,故认为“知性”反而应先于“尽心”③。所以朱子念兹在兹的“生意”、“生生之理”,其实也多止于“化生”,而未能说是“创生”。
过去以天地化生来比附人事者,首推董仲舒。葛荣晋先生认为,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从外部之阴阳学说为“仁”寻找其宇宙论根据④。牟宗三先生对于汉儒天人感应观的解释,曾有着如下的看法:(1)汉人的思想一切都系统化、具体化、切实化,他们没有神秘,一切都予以解析,汉时的天人感应观就由这种根本特性而产生出。(2)有了此根本特性,还不足以言感应,必须有以下三个根本原则,感应说始能建设起来。此三原则是:(1)宇宙条理;(2)天人同情;(3)天人合一。这三个原则实在说来是分不开的,举一可以赅三。①的确,董仲舒藉由着阴阳五行建立了一套绵密的气化宇宙观,但我们都知道,董仲舒这套理路无论是在“天”或是在“人”,毕竟流于机械性,也同归于“化生”。如从通篇文章来看,朱子沿用了这种诠释传统来证成儒家的形上哲学,其偏于气化上的理解意味就浓重了许多。无怪乎方东美先生做出了朱子为董仲舒所惑,是以不能直接传承真正孔子精神的酷评②。
然而在吾人研读朱子哲学时,必须时时回头审视其理气不离不杂在化生成物上的意义,就如同《玉山讲义》第一段文字中所表述朱子的基本态度一样,朱子之所以对仁义礼智等四端的理解进行如此高度且细密的分判,除了本身强烈的理论兴趣外,更是为了在实践上确立道德与吾人自身内在而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就是因为朱子事事物物都要求个根柢,“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如此才能“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庶几免于“支离”。所以尽管朱子形上学气化意味甚重,但他不是单纯地将天人关系牵拉比附。当然,他也未曾离理言气,这是因为无论天地大化或是人物诸德,全都贯有一最终指导归趋的理的关系。这一基本立场在吾人理解朱子学说体系是极为重要的。是以当我们以这种观点来看待所谓的智藏说时,虽然因其动静体用而在各种不同的经典与境下有其别出的用意,但“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着习察,无不是着工夫处矣”。
附注
①[日]冈田武彦:《朱子と智藏》,《中国思想における理想と现实》,东京都:木耳社,1983年,第267~279页。
②[日]冈田武彦:《朱子の智藏说とその由来およひ继承》,《中国思想における理想と现实》,东京都:木耳社,1983年,第281~304页。
③朱杰人主编:《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3~411页。
①王懋竑编、何忠礼点校:《朱子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1页。
②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89~937页。
③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2~3737页。本文引用《朱子文集》皆以此版本为主,篇名、分段及标点则由笔者稍作改定。
④程珙,字仲璧,号柳湖,江西鄱阳人。陈荣捷辨其不应列朱子门人,见陈荣捷著:《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⑤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2页。
⑥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4页。
⑦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5页。
⑧该章出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可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351~352页。以下凡引《四书章句集注》,皆以此本为主。
①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6页。
②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6页。
③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6~3737页。
④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7页。
⑤朱子对程珙第二问所答内容虽然重要,却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笔者于此先将该答语进行摘要式的叙述,至于第一问之回答,将于下节全文引录。
⑥陈荣捷:《朱熹》,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10页。
⑦陈先生于《朱熹》之第八章“朱子论修养”中,全以《玉山讲义》中之相关论述为主加以疏解发挥。该章见陈荣捷:《朱熹》,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93~104页;所引评句则见第95页。
⑧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3页。
①朱熹:《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七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733~3734页。
②朱熹:《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五八,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2825页。
①陈荣捷编著,杨儒宾等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99~400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页。
⑤此为朱子释《中庸》“天命之谓性”之语。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⑥陈荣捷编著,杨儒宾等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⑦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0页。
⑧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0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1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7页。
④朱熹:《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五八,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2825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4~105页。
⑥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2页。
⑦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1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1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1~2382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1~2382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2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2页。
⑥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2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2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1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页。
④此系年笔者以刘述先所考论为基准。见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第139~146页。
⑤朱熹:《仁说》,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六七,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390~3391页。
①相关讨论请参见李明辉:《朱子的“仁说”及其与湖乡学派的辩论》,《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88~90页。
②朱熹:《元亨利贞说》,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六七,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361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91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91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2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1~2392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7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6~107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6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90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89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8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1~2392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4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4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3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5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5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5页。
①朱熹:《答张钦夫》书十八,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三二,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1273~1274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台北:正中书局,2005年,第189~190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495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402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8页。
⑥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8页。
⑦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5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23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2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5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5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8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8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1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440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1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67页。
⑥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69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1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0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26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5页。
⑤黎靖德:《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22~823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44~45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81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81页。
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⑦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98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26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26页。
③如《朱子语类》言:“人往往说先尽其心而后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况其语脉是‘尽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着这道理,尽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尽其心。若只要理会尽心,不知如何地尽。”又:“‘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能尽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则知天矣。知性知天,则能尽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尽其心。‘物格而后知至’”等。见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22页。
④葛荣晋:《“仁”范畴的历史演变》,张岱年等著,苑淑娅编:《中国观念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①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②方东美著,孙智燊译:《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93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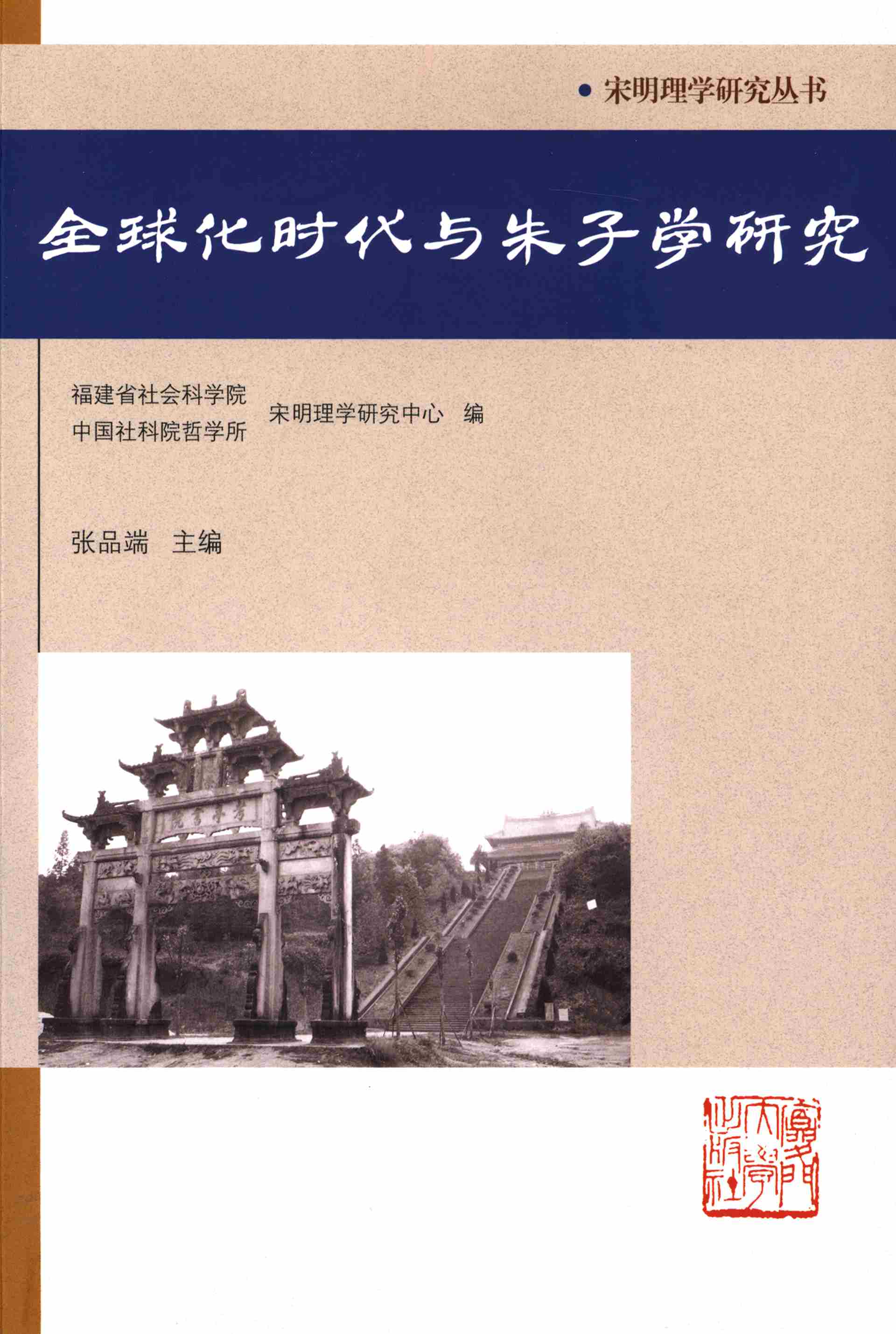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江俊亿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