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法因天理论
| 内容出处: | 《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201 |
| 颗粒名称: | 宋明理学法因天理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107-118 |
| 摘要: | 本文阐述了宋明理学义理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即“法者,因天理”,其中“国法”源于“天理”,具有法律渊源的重要意义。宋明理学通过天理、理性、理气论的构建,说明了性的来源与差异性,以及圣人对亿兆之君师的任命与教化,以实现人性的复归。 |
| 关键词: | 宋明理学 国法 法律思想 |
内容
在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属性问题上,学者议论纷纷。梁启超先生1904年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提出儒家法即为自然法,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最早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这个命题①。瞿同祖肯定了中国法律之儒家化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是“身份法律”②,而梁漱溟则首议传统法律为伦理文化属性③。梁治平先生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里,曾对中国社会“礼法文化”这一概念做了详细阐发④;徐忠明进一步发挥,提出传统法律文化根本精神是“宗法伦理”⑤。俞荣根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法律思想是以礼法文化为基本特征“伦理法”,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实系“把宗法家族伦理作为大经大法的法文化体系”。⑥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传统法律思想属性定为公法文化属性、义务本位主义,或“家庭主义”,或“皇权主义”等。诸如此类,对传统法律文化属性做了整体性概括。也有学者对传统法律属性从阶段性发展做出划分。一般而言,大都是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进程划分为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两个过程。也有多阶段划分,如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分为“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与“欧、美法侵入时代”四时代①。胡旭晟则划分为“混沌法”“道德法”“独立法”三个阶段,认“道德法”阶段为主流②。就此而言,纵观中国传统法律发展轨迹,笔者认为在阶段性上出现两个阶段,一是从先秦到汉唐的伦理法阶段,二是从宋到清的义理法阶段。笔者曾在2004年提出“朱熹义理法律属性”的观点,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伦理法与以朱熹为代表的义理法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伦理法律思想与义理法律思想的根本立法司法原则的差异性③,引起了学术界一定的反响。但从一些学者引用与论述中,对于以朱子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义理法律思想的属性还缺乏相应的认识,有必要对此进一步加以论述。
明理学家薛瑄曾将传统法律精辟概括为“法者,因天理,顺人情”④,说明了传统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基本联系。而这也是宋明理学法统核心内容。笔者曾专文阐述了宋明理学“法顺人情”的法律思想。为此,本文以“法者,因天理”为中心,阐述宋明理学义理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因”的基本字义具有“原故、原由,依靠、凭借,顺应,连接,因袭、承袭”,宋明理学以一“因”字高度概括了法与理之间的关系。“法者,天下之理”⑤,具有“国法”依靠、源于、顺应、亲近维护以及因袭“天理”等含义,揭示了宋明理学法的渊源、法的目标、法的含义与作用,法的正当性问题。这明确了宋明理学“以理统法”意义。
一、“国法”源于“天理”
“天理”在宋明理学思想体系中既包含道理、规律,也具有秩序、准则、规定性的意义。“国法”源于“天理”,即天理是国法的原体,主要涉及于“法律渊源”问题。两宋之前伦理法时期的法律起源论,主要形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命说、以孟子为核心的心性情义说及以荀子为代表的物欲明分说等观念。而宋明理学则构建了由“天—理—性—气—人物”的天理、理性、理气论。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性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以为法天下。则谓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①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有聪明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②
在此,理学家首先说明了“性即理”,“性”是“天”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之“理”。“性”“理”“天理”和“天道”都是词异义同,“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③。接着论证了“天”生万物,性来源于天,此性可以区分为人性与物性,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使人赋予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存在现实意义。又以“性虽同,而气禀或异”不能齐,“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以仁义礼智之性矣”,形成人物差异性,故而又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学而知之的大贤”“困而学之的众人”与“困而不学的下民”。“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溺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也”④。为实现“以复其性”,天必命“生而知之的圣人”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诸如尧舜等圣人,继天立极,设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治而教,针对其他气禀厚薄之别者,或“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⑤。施以德礼政刑四个不同层次的方略,“人之气质有浅深厚薄之不同,故惑者不能齐之,必以礼齐之。齐之不从,则刑不可废”①。故而圣人、亿兆之师是“天命之”“继天立极”的结果,代天理物:“圣人纯于义理而无人欲之私,则其所以代天而理物。”②宋明理学正是从“天—理—性—气—人物”体系出发,强调“天”即“理”,“性”“法”来源于天。而此“天理”之天,而非纯自然之天。宋明理学是将天理作为天之本源的宇宙本体论角度来说明,万物聚和,而且将之前的天道说、人性论集合一体,通过性、气等沟通天与人(物)之间的联系,解释人之性、道德性命都在于天。天理无疑也是包括人的万物准则,因而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源流,而且还具有人的意识属性、社会普遍性意义,以解释了万物本源。这不同于董仲舒那种有人格、有意志、至高无上的宗教神的天。宋明理学的“法得之于天”与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法渊源有相当的差异性,克服汉儒所谓“人附于天”的模式,从本原上论证天理与人法的一体。而沿袭“天”之名,赋予新义,借以天的概念广泛流传,造就天理的法律起源论,而更具有理论严肃性与社会普遍性的统一。
以“天理”是万物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为一理,推演出法源于天理,其创制也就是圣人继天立极的结果。国法也是天理的产物,“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是天理自然当如此”③。明朝丘浚就直接认为君贤圣人立法设刑是“承天意”,继天理的,“号令之颁,政事之施,教条之节,礼乐之度之具,刑赏征讨之举”,皆“非君之自为之也,承天意也”④。指出刑狱之制如同礼乐之制“作于圣人,非圣人所自为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气而为之耳”⑤,目的是“去天下之梗”。而要实现“去天下之梗”,就“必用刑狱断制之”⑥。他所说的“天意”,也就是朱熹的“天理”。严复《法意》按语提出:“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认为传统中国就是“理为法之原”,“国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理”。①“理”是天之理,是国法根源,宋明理学通过将情与理结合,使之获得合理性。
二、“国法”维护“天理”
“法者,因天理”的第二层意义是因具有“亲近”之意,引申为国法,作为天理的支撑而必须维护天理。自宋以来,通常“天理、国法、人情”连用。《名公书判清明集》书判中大量出现“实情、事理、国法”,黄宗智认为“不管儒家的理想制度如何,在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是道理、实情、律例三者”②。宋明理学将天理作为最高范畴,是国法与人情依据,故而“天理与国法、人情”处于不同层次上,天理处于高一层次,人情与国法并列同属于天里的从属层次。由此,经常以“准情用法”“情法两尽”,或“情法两平”并列说明司法运用,国法与人情共同成为天理的支撑。
宋明理学以“国法”作为天理的支撑,维护着“天理”。可以通过对于法的定义、作用以及法律目标的考察作为反映。
首先,从义理之法定义看,宋明理学对传统法律的定义有自己新的高度概括与更多阐发。
法为理。“法字、礼字,实理字”“法者,天下之理”③,这是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独创性的一面。虽然早在《礼记·乐记》就有“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礼不动”的说法,但《乐记》之“理”仅仅只有“道理”之意义。孔颖达疏:“礼谓道理,言礼者,使万事合于道理也。”而宋明理学的理既是道理之理,也是治理、条理之理,更是天理之理。宋明理学也有“法者,道之用也”④。如此之提法,将法上升到“天理”之意义的高度。
以“法为理”为统领,宋明理学继承传统法律,将法视为“刑法”的理路,训“典刑”很明确:“法不用则为法,法用则为刑;民不犯则为法,民犯之则为刑。”①真德秀则认为“制定于平昔者谓之法,施用于临时者谓之罚。法者,罚之体;罚者,法之用。其实一而已矣”②。明确概说了“刑者,天讨有罪之具”③。
同时,宋明理学的法为礼。宋儒认为“礼者,圣人之法制也”④“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⑤。以“礼”入“法”,强调的是礼的规范性的一面,“盖礼与刑,二者出此则入彼。立典于此而示民,以礼节之所当然,而又象刑于彼而示民,以法禁之所必然。所当然者,祀典之常制。所必然者,有司之成法。降下其典于民,使其知必如此。则为合于礼,不如此则为犯于刑。启其善端,遏其邪念,折而转之,使不入于刑,而入于礼焉”⑥。而礼本身就是天理意义,“礼者,理也。理无物而不备,故礼亦无时而不足”⑦、“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礼”⑧。而且程朱理学将礼谓“天理之节文”、“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⑨,视为通识。礼是源于天理的高度创制,礼是内蕴天理的“制度”“节文”,具有天理之“用”属性。
从宋明理学对“法”含义的概说,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走过了一条从法为刑,到法为礼,直至法为理的发展轨迹。宋明理学释法为理,理以礼的规范实现法的内容和目的。
其次,宋明理学围绕天理,将法的作用归纳以下四方面:一是明理防范,这是法的预防作用。用刑以防奸,这是古今通义,“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①。这是对《大戴礼记》“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禁畏,这是法的警示作用。程颐指出“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以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留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②。三是明刑以弼五教,这是作为天理维护者法的教化作用。“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盖三纲五常,天理各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③。四是“以刑去刑”,辟以止辟。这是法的惩戒作用。朱熹指出“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严其中”④,仁爱之实是天理的要求。理学家认为以法用刑是符合“自然之理”,丘濬说:“是知圣人为治,不能以不用刑,此盖天地自然之理”⑤。对于天理伦理秩序的侵害,就应当予以处罚,惩罚犯罪当然也是符合天理的内在要求。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对法的作用有以概论:“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愤、释人之怨、遂人恶恶之情者也,所以叙彝伦、正名分、定民志、息祸乱,为万世法者也。”⑥国法因“天理”而产生,以“天理”为指导,维护传统社会纲常之“天理”便是国法之重任。
最后,国法的理想目标在于息讼。宋以前传统社会以伦理法为属性,“无讼”的理想法律目标,带有原始空想性特征成分,这一美好理想始终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宋明理学则是将“息讼”作为其理治社会的理想法律目标。“息讼”观的前提就是承认对法律诉讼现实存在,对于国法的合理性给予了认可。
二程认为“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国法之“讼”是符合天理中正性要求的,“讼者,求辩其曲直也。讼者,求辩其是非也。辩之当,乃中正也。故利见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①、“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②,直接承认了争讼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能够较为理性地“无讼”目标,更多的是接受了孟子“省刑罚”理念,反映了从先秦儒家“和为贵”到宋儒“理而后和”、“和而解”理论演化发展,由“无讼”的理想走向更具有务实性的“息讼”。“无讼”目标最主要是在于防讼,而息讼则要求止讼、限讼与利讼共存。就诉讼理念而言,司法不再将诉讼视为民间细故,甚至“为政者皆知以民事为急”。为达到维护天理,就必须采取适应社会生活的积极司法措施,日益细化诉讼规则,“情理兼顾”和“情法两尽”,顺应“天理、国法、人情”一体的现实追求。国法的内涵、作用以及理想目标必须符合天理的规定性,国法是维护天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三、“国法”顺应“天理”
“国法”顺应“天理”,就是说国法的创建、修改以及适用都必须符合“理”之“势”,要适应天理发展的趋向与需要。一方面只要是合理的就必然能够成势,“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而另一方面,顺势就必然能够达到合理,“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③,“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也”④,不可逆理而为:“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以成者势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⑤应当因势顺理,达到天下平的最高境界。而宋明理学的“势”是时势、形势、趋势,需要仔细研究、估计时势和审视权变,顺势而为。对于国法而言,宋明理学主张既要注重法律的规定性,又要视义理而为权的灵活性,坚持“法有定制”、依法审判、“随时制宜”的理性原则,这也是宋明理学义理化法律思想的又一表现。
一是法有定制:明儒丘浚主张“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不仅“能施行于一时”,且应“为法于百世”①。他主张立法应该保持“经常”:“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②丘浚论述:
人之有罪者,或犯于有司,则当随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罚焉;或轻或重,必当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则,非明矣。雷之威岁岁有常,虩虩之声震惊百里,如国家有律令之制,违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轻或重,皆定制,不可变渝也。否则,非敕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不常。则随其所犯而施之以责罚,必明必允,使吾所罚者,与其一定之法,无或出入,无相背戾,常整饬而严谨焉。用狱如此,无不利者矣。③
强调了重视“立法稳定”问题。对于朱熹,也认为不能轻易地改变原有立法,指出“圣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兼当时人习惯,亦不以为异也”④。旧法的确是不再适合时宜也应当是“小变其法”,旧法对于现实并“无大利害”就“不必议更张”,“兴其滞补其弊”。而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把握,于时并不有害的旧法则更是不能轻易地变法,而应当“谨守常法”。吕坤曾上疏曰:“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轻其重,太祖既定为律,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例不得为一定之法。”⑤这反映了宋明理学立法谨慎态度和保持立法的稳定性与一贯性。因此,在传统法律条款的制定实践中,宋元明清的基本法律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立法者尽可能将犯罪情节、刑罚上做出准确的描述与精确规定,以减少司法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
二是依法审判。宋明理学为追求息讼理想目标,实现更为广义的利益平衡,也必然要求做到“合理”“合情”与“合法”,由此才能够避免民众对司法行为正当性的质疑,服判息讼。宋明理学法律义理化要求在以“义理之所当否”为辨别是非的根本准则同时,也将追求法律事实的客观实在作为重要内容,更为重视“案件的事理情节”与依律例断案,使之成为司法的重要依据。由人伦理性向科学理性、知识理性并举转变。因此,在宋以后,司法技术层面的“案情、实情”,追求“法律情节”合理性是司法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求其理所安”“夺于公证”:“以众说互相法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别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证,而无以误。”①而依法审判已经成为常态,曲法被视为逆理。故而张晋藩先生说:“从现存的司法档案中可以看出,依律例断案是清代民事案件审理的最基本形式。”②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与律例相背,“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③。肯定了依法审判的意义。
同时,“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饬法明伦,而法有轻重”④,因而需要“酌之理,参之分”予以处置。这就必将涉及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具体运用。“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皆执一之论,未尽于义也。义既未安,则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为公器也。不得于义,则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则不得为义”。充分肯定了“法者天下之公器”,要求“惟善持法”,承认了法的公正性。在此,程颐又阐释法与义关系,提出义的实现前提在于法为公器,而且“法王于义,义当而谓之屈法,不知法者也”⑤。强调了法的公正性,保障了义理的实现,同时不能够因为强求于义理而“屈法、不知法”,亵渎法的公正性。为追求天理,实现司法的公正性,理学家也要求执法者不能受制于人情而违法。程颐指出:“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率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防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⑥这就是说,如果因为“害于近戚,防于贵家”就会牵于人情,势必导致“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丧失法公正性,也就无法保障司法正义。不一味随意顺从不当人情这一理念为宋之士大夫普遍所接受,朱熹也指出:“处乡曲,固要人情周尽,但要分别是非,不要一面随顺,失了自家。”⑦
真德秀反对“殉人情”,“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骨瓦)公法,以殉人情”①。显然,理学家主张在法律运用中要“准情酌理”,于法外推情察理”,而又不“与律例十分相背”。司法者据实情判决无疑能体现天理的正义性,而司法者审判过程中遵循“情理”以合理规避律例,同样也是谋求实现利益平衡。这种利益平衡衡量的标准就是“天理、人情”,所以国法没有成为天理、人情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国法是利益平衡的具体体现。
三是随时制宜。“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矣”②,宋明理学之法律强调因势顺理、顺事制法、随时制宜的原则。定罪量刑,应随时势的变化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更改,以求因事而立的,“上古世淳而人朴,顺事而为治耳。至尧始为治道,因事制法,著见功迹,而可为典常也。不惟随时,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③、“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焉,则何义之有”④?这里说明二程认为对待以往制定的法律,要根据义理与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不能守成不变,“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二程认为: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说,独答颜回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一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见,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⑤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二程虽然说过孔子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但即使是三王之法,也要“损益文质,随时之宜”,只有随时顺事所制定的法律才能够符合时代要求。朱熹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认为“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①。强调祖宗之法也是“随时”,“若经世一事,向使先生见用,其将如何?曰:亦是只是随时。”②先人立法之初本身就存在弊端,“虽是圣人法,岂有无弊者”、“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③。同时由于后人“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甚至认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④。故而对于不适时宜、有弊立法就必须“变而通之”,“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⑤、“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必裁酌从今之宜而为之也”,力求做到“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变”⑥。
王夫之从律法应因“势”顺“理”出发,提出“趋时更新”,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王夫之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⑦古代的制度法令只能适应于古代社会,而今天的治国方法也不一定能适应于后世。“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举凡一兴一废,一繁一简,因乎时而不可执也”⑧,王夫之认为律令的制定和变更必须因时因地而异。法律不因时而变,就会固守古制,墨守成法。
明理学家薛瑄曾将传统法律精辟概括为“法者,因天理,顺人情”④,说明了传统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基本联系。而这也是宋明理学法统核心内容。笔者曾专文阐述了宋明理学“法顺人情”的法律思想。为此,本文以“法者,因天理”为中心,阐述宋明理学义理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因”的基本字义具有“原故、原由,依靠、凭借,顺应,连接,因袭、承袭”,宋明理学以一“因”字高度概括了法与理之间的关系。“法者,天下之理”⑤,具有“国法”依靠、源于、顺应、亲近维护以及因袭“天理”等含义,揭示了宋明理学法的渊源、法的目标、法的含义与作用,法的正当性问题。这明确了宋明理学“以理统法”意义。
一、“国法”源于“天理”
“天理”在宋明理学思想体系中既包含道理、规律,也具有秩序、准则、规定性的意义。“国法”源于“天理”,即天理是国法的原体,主要涉及于“法律渊源”问题。两宋之前伦理法时期的法律起源论,主要形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命说、以孟子为核心的心性情义说及以荀子为代表的物欲明分说等观念。而宋明理学则构建了由“天—理—性—气—人物”的天理、理性、理气论。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性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以为法天下。则谓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①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有聪明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②
在此,理学家首先说明了“性即理”,“性”是“天”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之“理”。“性”“理”“天理”和“天道”都是词异义同,“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③。接着论证了“天”生万物,性来源于天,此性可以区分为人性与物性,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使人赋予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存在现实意义。又以“性虽同,而气禀或异”不能齐,“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以仁义礼智之性矣”,形成人物差异性,故而又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学而知之的大贤”“困而学之的众人”与“困而不学的下民”。“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溺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也”④。为实现“以复其性”,天必命“生而知之的圣人”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诸如尧舜等圣人,继天立极,设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治而教,针对其他气禀厚薄之别者,或“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⑤。施以德礼政刑四个不同层次的方略,“人之气质有浅深厚薄之不同,故惑者不能齐之,必以礼齐之。齐之不从,则刑不可废”①。故而圣人、亿兆之师是“天命之”“继天立极”的结果,代天理物:“圣人纯于义理而无人欲之私,则其所以代天而理物。”②宋明理学正是从“天—理—性—气—人物”体系出发,强调“天”即“理”,“性”“法”来源于天。而此“天理”之天,而非纯自然之天。宋明理学是将天理作为天之本源的宇宙本体论角度来说明,万物聚和,而且将之前的天道说、人性论集合一体,通过性、气等沟通天与人(物)之间的联系,解释人之性、道德性命都在于天。天理无疑也是包括人的万物准则,因而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源流,而且还具有人的意识属性、社会普遍性意义,以解释了万物本源。这不同于董仲舒那种有人格、有意志、至高无上的宗教神的天。宋明理学的“法得之于天”与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法渊源有相当的差异性,克服汉儒所谓“人附于天”的模式,从本原上论证天理与人法的一体。而沿袭“天”之名,赋予新义,借以天的概念广泛流传,造就天理的法律起源论,而更具有理论严肃性与社会普遍性的统一。
以“天理”是万物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为一理,推演出法源于天理,其创制也就是圣人继天立极的结果。国法也是天理的产物,“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是天理自然当如此”③。明朝丘浚就直接认为君贤圣人立法设刑是“承天意”,继天理的,“号令之颁,政事之施,教条之节,礼乐之度之具,刑赏征讨之举”,皆“非君之自为之也,承天意也”④。指出刑狱之制如同礼乐之制“作于圣人,非圣人所自为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气而为之耳”⑤,目的是“去天下之梗”。而要实现“去天下之梗”,就“必用刑狱断制之”⑥。他所说的“天意”,也就是朱熹的“天理”。严复《法意》按语提出:“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认为传统中国就是“理为法之原”,“国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理”。①“理”是天之理,是国法根源,宋明理学通过将情与理结合,使之获得合理性。
二、“国法”维护“天理”
“法者,因天理”的第二层意义是因具有“亲近”之意,引申为国法,作为天理的支撑而必须维护天理。自宋以来,通常“天理、国法、人情”连用。《名公书判清明集》书判中大量出现“实情、事理、国法”,黄宗智认为“不管儒家的理想制度如何,在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是道理、实情、律例三者”②。宋明理学将天理作为最高范畴,是国法与人情依据,故而“天理与国法、人情”处于不同层次上,天理处于高一层次,人情与国法并列同属于天里的从属层次。由此,经常以“准情用法”“情法两尽”,或“情法两平”并列说明司法运用,国法与人情共同成为天理的支撑。
宋明理学以“国法”作为天理的支撑,维护着“天理”。可以通过对于法的定义、作用以及法律目标的考察作为反映。
首先,从义理之法定义看,宋明理学对传统法律的定义有自己新的高度概括与更多阐发。
法为理。“法字、礼字,实理字”“法者,天下之理”③,这是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独创性的一面。虽然早在《礼记·乐记》就有“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礼不动”的说法,但《乐记》之“理”仅仅只有“道理”之意义。孔颖达疏:“礼谓道理,言礼者,使万事合于道理也。”而宋明理学的理既是道理之理,也是治理、条理之理,更是天理之理。宋明理学也有“法者,道之用也”④。如此之提法,将法上升到“天理”之意义的高度。
以“法为理”为统领,宋明理学继承传统法律,将法视为“刑法”的理路,训“典刑”很明确:“法不用则为法,法用则为刑;民不犯则为法,民犯之则为刑。”①真德秀则认为“制定于平昔者谓之法,施用于临时者谓之罚。法者,罚之体;罚者,法之用。其实一而已矣”②。明确概说了“刑者,天讨有罪之具”③。
同时,宋明理学的法为礼。宋儒认为“礼者,圣人之法制也”④“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⑤。以“礼”入“法”,强调的是礼的规范性的一面,“盖礼与刑,二者出此则入彼。立典于此而示民,以礼节之所当然,而又象刑于彼而示民,以法禁之所必然。所当然者,祀典之常制。所必然者,有司之成法。降下其典于民,使其知必如此。则为合于礼,不如此则为犯于刑。启其善端,遏其邪念,折而转之,使不入于刑,而入于礼焉”⑥。而礼本身就是天理意义,“礼者,理也。理无物而不备,故礼亦无时而不足”⑦、“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礼”⑧。而且程朱理学将礼谓“天理之节文”、“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⑨,视为通识。礼是源于天理的高度创制,礼是内蕴天理的“制度”“节文”,具有天理之“用”属性。
从宋明理学对“法”含义的概说,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走过了一条从法为刑,到法为礼,直至法为理的发展轨迹。宋明理学释法为理,理以礼的规范实现法的内容和目的。
其次,宋明理学围绕天理,将法的作用归纳以下四方面:一是明理防范,这是法的预防作用。用刑以防奸,这是古今通义,“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①。这是对《大戴礼记》“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禁畏,这是法的警示作用。程颐指出“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以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留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②。三是明刑以弼五教,这是作为天理维护者法的教化作用。“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盖三纲五常,天理各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③。四是“以刑去刑”,辟以止辟。这是法的惩戒作用。朱熹指出“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严其中”④,仁爱之实是天理的要求。理学家认为以法用刑是符合“自然之理”,丘濬说:“是知圣人为治,不能以不用刑,此盖天地自然之理”⑤。对于天理伦理秩序的侵害,就应当予以处罚,惩罚犯罪当然也是符合天理的内在要求。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对法的作用有以概论:“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愤、释人之怨、遂人恶恶之情者也,所以叙彝伦、正名分、定民志、息祸乱,为万世法者也。”⑥国法因“天理”而产生,以“天理”为指导,维护传统社会纲常之“天理”便是国法之重任。
最后,国法的理想目标在于息讼。宋以前传统社会以伦理法为属性,“无讼”的理想法律目标,带有原始空想性特征成分,这一美好理想始终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宋明理学则是将“息讼”作为其理治社会的理想法律目标。“息讼”观的前提就是承认对法律诉讼现实存在,对于国法的合理性给予了认可。
二程认为“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国法之“讼”是符合天理中正性要求的,“讼者,求辩其曲直也。讼者,求辩其是非也。辩之当,乃中正也。故利见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①、“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②,直接承认了争讼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能够较为理性地“无讼”目标,更多的是接受了孟子“省刑罚”理念,反映了从先秦儒家“和为贵”到宋儒“理而后和”、“和而解”理论演化发展,由“无讼”的理想走向更具有务实性的“息讼”。“无讼”目标最主要是在于防讼,而息讼则要求止讼、限讼与利讼共存。就诉讼理念而言,司法不再将诉讼视为民间细故,甚至“为政者皆知以民事为急”。为达到维护天理,就必须采取适应社会生活的积极司法措施,日益细化诉讼规则,“情理兼顾”和“情法两尽”,顺应“天理、国法、人情”一体的现实追求。国法的内涵、作用以及理想目标必须符合天理的规定性,国法是维护天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三、“国法”顺应“天理”
“国法”顺应“天理”,就是说国法的创建、修改以及适用都必须符合“理”之“势”,要适应天理发展的趋向与需要。一方面只要是合理的就必然能够成势,“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而另一方面,顺势就必然能够达到合理,“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③,“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也”④,不可逆理而为:“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以成者势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⑤应当因势顺理,达到天下平的最高境界。而宋明理学的“势”是时势、形势、趋势,需要仔细研究、估计时势和审视权变,顺势而为。对于国法而言,宋明理学主张既要注重法律的规定性,又要视义理而为权的灵活性,坚持“法有定制”、依法审判、“随时制宜”的理性原则,这也是宋明理学义理化法律思想的又一表现。
一是法有定制:明儒丘浚主张“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不仅“能施行于一时”,且应“为法于百世”①。他主张立法应该保持“经常”:“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②丘浚论述:
人之有罪者,或犯于有司,则当随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罚焉;或轻或重,必当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则,非明矣。雷之威岁岁有常,虩虩之声震惊百里,如国家有律令之制,违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轻或重,皆定制,不可变渝也。否则,非敕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不常。则随其所犯而施之以责罚,必明必允,使吾所罚者,与其一定之法,无或出入,无相背戾,常整饬而严谨焉。用狱如此,无不利者矣。③
强调了重视“立法稳定”问题。对于朱熹,也认为不能轻易地改变原有立法,指出“圣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兼当时人习惯,亦不以为异也”④。旧法的确是不再适合时宜也应当是“小变其法”,旧法对于现实并“无大利害”就“不必议更张”,“兴其滞补其弊”。而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把握,于时并不有害的旧法则更是不能轻易地变法,而应当“谨守常法”。吕坤曾上疏曰:“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轻其重,太祖既定为律,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例不得为一定之法。”⑤这反映了宋明理学立法谨慎态度和保持立法的稳定性与一贯性。因此,在传统法律条款的制定实践中,宋元明清的基本法律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立法者尽可能将犯罪情节、刑罚上做出准确的描述与精确规定,以减少司法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
二是依法审判。宋明理学为追求息讼理想目标,实现更为广义的利益平衡,也必然要求做到“合理”“合情”与“合法”,由此才能够避免民众对司法行为正当性的质疑,服判息讼。宋明理学法律义理化要求在以“义理之所当否”为辨别是非的根本准则同时,也将追求法律事实的客观实在作为重要内容,更为重视“案件的事理情节”与依律例断案,使之成为司法的重要依据。由人伦理性向科学理性、知识理性并举转变。因此,在宋以后,司法技术层面的“案情、实情”,追求“法律情节”合理性是司法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求其理所安”“夺于公证”:“以众说互相法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别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证,而无以误。”①而依法审判已经成为常态,曲法被视为逆理。故而张晋藩先生说:“从现存的司法档案中可以看出,依律例断案是清代民事案件审理的最基本形式。”②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与律例相背,“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③。肯定了依法审判的意义。
同时,“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饬法明伦,而法有轻重”④,因而需要“酌之理,参之分”予以处置。这就必将涉及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具体运用。“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皆执一之论,未尽于义也。义既未安,则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为公器也。不得于义,则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则不得为义”。充分肯定了“法者天下之公器”,要求“惟善持法”,承认了法的公正性。在此,程颐又阐释法与义关系,提出义的实现前提在于法为公器,而且“法王于义,义当而谓之屈法,不知法者也”⑤。强调了法的公正性,保障了义理的实现,同时不能够因为强求于义理而“屈法、不知法”,亵渎法的公正性。为追求天理,实现司法的公正性,理学家也要求执法者不能受制于人情而违法。程颐指出:“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率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防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⑥这就是说,如果因为“害于近戚,防于贵家”就会牵于人情,势必导致“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丧失法公正性,也就无法保障司法正义。不一味随意顺从不当人情这一理念为宋之士大夫普遍所接受,朱熹也指出:“处乡曲,固要人情周尽,但要分别是非,不要一面随顺,失了自家。”⑦
真德秀反对“殉人情”,“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骨瓦)公法,以殉人情”①。显然,理学家主张在法律运用中要“准情酌理”,于法外推情察理”,而又不“与律例十分相背”。司法者据实情判决无疑能体现天理的正义性,而司法者审判过程中遵循“情理”以合理规避律例,同样也是谋求实现利益平衡。这种利益平衡衡量的标准就是“天理、人情”,所以国法没有成为天理、人情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国法是利益平衡的具体体现。
三是随时制宜。“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矣”②,宋明理学之法律强调因势顺理、顺事制法、随时制宜的原则。定罪量刑,应随时势的变化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更改,以求因事而立的,“上古世淳而人朴,顺事而为治耳。至尧始为治道,因事制法,著见功迹,而可为典常也。不惟随时,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③、“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焉,则何义之有”④?这里说明二程认为对待以往制定的法律,要根据义理与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不能守成不变,“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二程认为: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说,独答颜回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一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见,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⑤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二程虽然说过孔子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但即使是三王之法,也要“损益文质,随时之宜”,只有随时顺事所制定的法律才能够符合时代要求。朱熹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认为“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①。强调祖宗之法也是“随时”,“若经世一事,向使先生见用,其将如何?曰:亦是只是随时。”②先人立法之初本身就存在弊端,“虽是圣人法,岂有无弊者”、“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③。同时由于后人“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甚至认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④。故而对于不适时宜、有弊立法就必须“变而通之”,“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⑤、“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必裁酌从今之宜而为之也”,力求做到“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变”⑥。
王夫之从律法应因“势”顺“理”出发,提出“趋时更新”,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王夫之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⑦古代的制度法令只能适应于古代社会,而今天的治国方法也不一定能适应于后世。“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举凡一兴一废,一繁一简,因乎时而不可执也”⑧,王夫之认为律令的制定和变更必须因时因地而异。法律不因时而变,就会固守古制,墨守成法。
附注
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11页。
②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1~391页。
③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卷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0页。
④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2~231页。
⑤徐忠明、任强:《中国法律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64页。
⑥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1~134页。
①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②胡旭晟:《法的道德历程——法律史的伦理解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③徐公喜:《朱熹义理法律思想论》,《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
④《薛文清公要语》,陈弘谋辑:《从政遗规》,北京:国民出版社,1940年,第23页。
⑤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60页。
①朱熹:《中庸章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②朱熹:《大学章句序》,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③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公冶长第五》,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④朱熹:《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⑤朱熹:《戊申延和奏札一》,《朱文公文集》卷一四,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6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二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05页。
②朱熹:《中庸或问下》,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96页。
③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页。
④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原序》,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⑤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三六,《总论礼乐之道》,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
⑥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十,《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上》,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52~853页。
①严复:《严复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35页。
②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③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60页。
④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9页。
①黄淮、杨士奇编,吴相湘校点:《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28218页。
②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十,《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上》,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53页。
③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原序》,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④李觏:《李觏集》卷二,《礼论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23页。
⑤李觏:《直觏李先生文集》卷二,《礼论后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2~23页。
⑥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一〇一,《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下》,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62页。
⑦吕祖谦撰,胡宗楙校点:《东莱外集》卷一,《续金华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
⑧张栻撰,王蓉贵、杨世文校点:《答吕季克》,《南轩集》卷二六,《张栻全集》,吉林: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916页。
⑨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第一》,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①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二,《噬嗑》,《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04页。
②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蒙》,《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20页。
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四,《戊申延和奏札一》,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6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七八,《大禹谟》,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62~2663页。
⑤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一〇四,《慎刑宪·制刑狱之具》,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88页。
⑥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一,《中宗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92页。
①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一〇六,《慎刑宪·详听断之法》,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902页。
②崔述撰,顾颉刚校点:《讼论》,《崔东壁遗书》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01页。
③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9、601页。
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0页。
⑤王夫之:《诗广传》卷三,《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421页。
①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一〇一,《总论刑制之义》,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933页。
②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二四,《制国用·经制之义下》,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③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一〇,《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上》,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53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七,《曲礼》,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45页。
⑤张廷玉撰:《明史》卷二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40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0~321页。
②张晋藩:《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207页。
③方大湜:《平平言》卷二,鄂省藩署,1890年,第62页。
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德宗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4页。
⑤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八,《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5页。
⑥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56页。
⑦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一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77页。
①张四维:《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官吏门·谕州县官僚》,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页。
②王夫之:《宋论》卷一五,《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335页。
③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8页。
④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
⑤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七,《伊川先生语三》,《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页。
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〇,《读两陈谏议遗墨》卷十四,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81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八,《朱子五·论治道》,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25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八,《朱子五·论治道》,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13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八,《朱子五·论治道》,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17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六,《礼三·总论》,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14页。
⑥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九,《礼六·丧二》,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14页。
⑦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8~2549页。
⑧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8~369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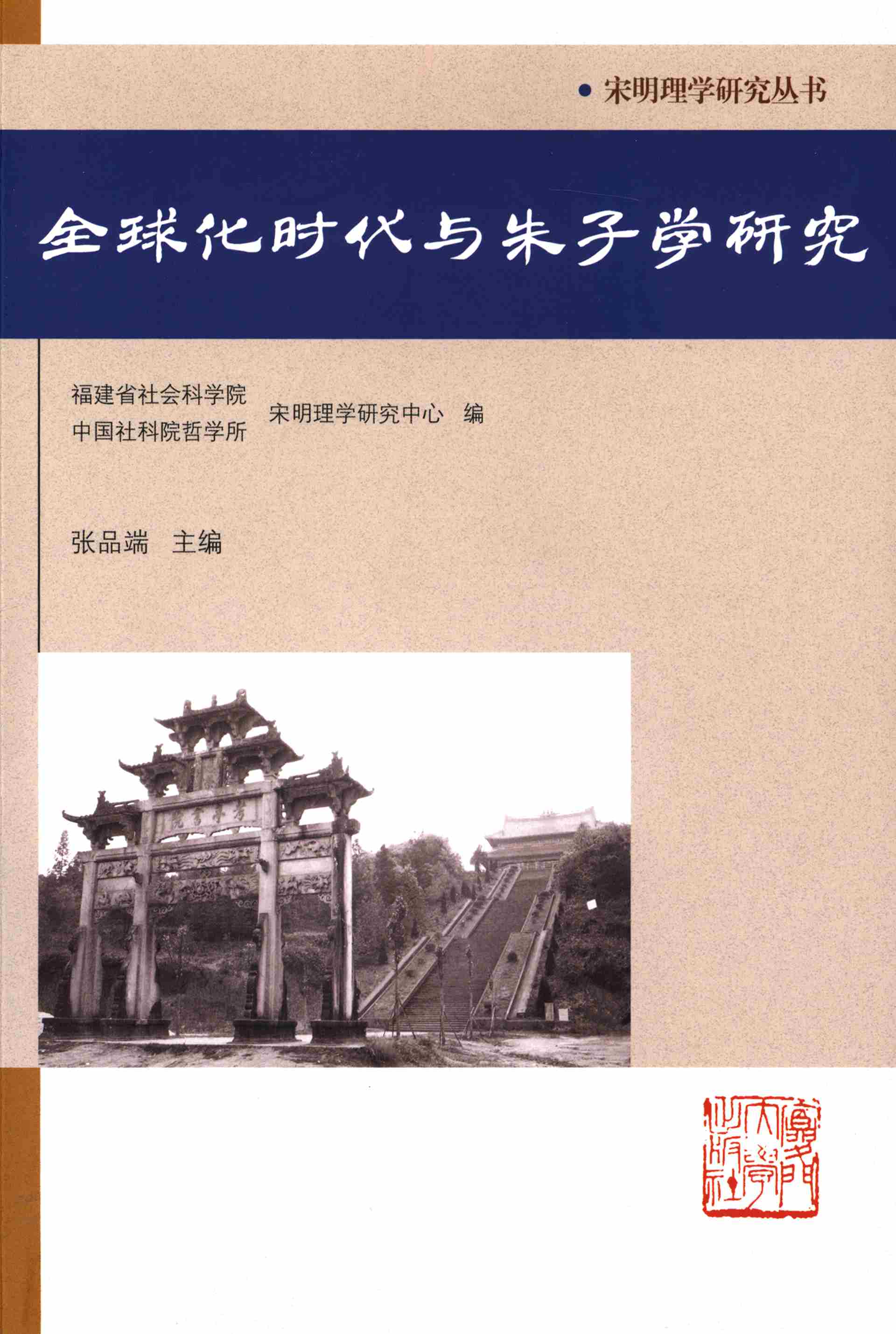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徐公喜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