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
| 内容出处: | 《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185 |
| 颗粒名称: | 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42-5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在宋代新儒学中的地位重要,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发端。朱熹等理学家对范仲淹等先驱的追溯备受重视。范仲淹门下多贤士,与“宋初三先生”关系密切。 |
| 关键词: | 范仲淹 新儒学 理学 |
内容
宋代的理学又称“道学”,这是比较确定的。而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本是对“理学”或“道学”的英译①,但是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美国汉学界也有对“新儒学”之称谓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新儒学所指相当含糊不清,主张将其搁置起来,而只以“道学”指称程朱学派;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儒学专指“理学”和“心学”,抑或理学属于“正统的新儒学”,而其他宋代以来的儒学则属于一般(广义)的新儒学②。
我近年来比较赞成钱穆先生的一个说法,即他在《朱子学提纲》中所说:“理学兴起以前,已先有一大批宋儒。此一大批宋儒,早可称为是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③依此说,“新儒家”之称可有广狭之别,广义的“新儒家”包括范仲淹、欧阳修和“宋初三先生”等,狭义的“新儒家”则专指宋明理学家(包括理学和心学)。
钱穆先生还曾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④这里说的“宋学”应即指广义的宋代新儒学,“两端”之一的“革新政令”是以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为代表。而之二的“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则尤指自周敦颐始的“伊洛渊源”或“濂洛关闽”之学。
自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以来,学界一般都把理学的先驱追溯到唐代的韩愈和李翱。从古文运动、排斥佛老、道统论和心性论来说,的确可以这样联系,但这毕竟只是后人或今人的一种思想史叙述,而不是理学家自己的说法。我认为追溯理学的先驱,还应该重视朱熹的以下说法:
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①
这里的“亦有其渐”,就是指道学或理学的先驱。我认为追溯理学的先驱,还是应重视朱熹所说过的,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讲起,他们就是广义的宋代新儒学的发端。
一、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
“宋初三先生”在宋代新儒学中的地位早已得到承认,如全祖望所作《宋元学案·序录》云:
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学案》。
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石介),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学案》。
考《宋元学案》的这两段“序录”,其实是本于黄百家所引黄震所说: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②
这条引文是出自《黄氏日抄》卷四十五。而黄震之说实又是本于上述朱熹所论的“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差别只是缺少了“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黄震对范仲淹并不是不了解,如他也曾说:“本朝人物,范文正公本朝第一等人。”①但他可能不太熟悉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故他在讲“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时没有把范仲淹放在前面。这一忽略致使宋初的一段学术史不明,乃至《宋元学案》在《安定学案》《泰山学案》之后才是《高平学案》和《庐陵学案》。全祖望《序录》说:
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述《高平学案》。
这一顺序的颠倒,以及把范仲淹作为“安定、泰山而外”的一支,其误在王梓材的“案语”中已经点明了:“高平行辈不后于安定、泰山,而庐陵亦当时斯道之疏附也。谢山以梨洲编次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故以高平、庐陵次之。”(《序录》案语)梓材又云:“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高平学案》案语)、“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四先生皆在文正门下”(《泰山学案》案语)。王氏所说《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当即指胡瑗曾为程颐所尊敬的老师。他所说“宋初三先生”及李觏“皆在文正门下”,是本于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所云:“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②这才是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真实关系,即“宋初三先生”及李觏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
《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
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这段引文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所引《杨公笔录》(宋杨延龄撰),全祖望谨按:“此段稍可疑,宜再考。(泰山)先生婿于李文定公时,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长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对于全祖望所疑,王梓材已加辨正:“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以端拱三年己丑生,实长于泰山三岁。”按“端拱三年”为“端拱二年”之误,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孙复生于992年,范比孙确实年长三岁。全祖望疑孙复“稍长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此亦全氏之疏误,意在否认孙复之学本于范仲淹。而上述史料不仅见于宋代的《东轩笔录》和《杨公笔录》,而且亦被朱熹编入《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三,故其当确信无疑。
《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当即孙复四举进士不第之时。他在“退居泰山”之前,约有一年的时间从学于范仲淹,他的“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授以《春秋》”。在孙复苦学于泰山期间,石介“躬执弟子礼,师事之”①。其间,范仲淹与孙复有书信往还,《范文正公集·尺牍》中有给孙复的信,《孙明复小集》中亦有《寄范天章书》等等。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胡瑗生于公元993年(比孙复小一岁),13岁时是1006年,而孙复离开睢阳时是1028年。也就是说,在胡瑗13岁“通五经”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贫困坎坷,然后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安定学案》载其在泰山苦学的情况:“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在此期间,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砺,而范仲淹的“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当已通过孙复而传达给了胡瑗、石介②。
二、范仲淹与“明体达用之学”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1043—1044),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这一改革的思想在范仲淹的心中沉潜了近二十年,比较典型的表述是他在《上执政书》中所说:“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①。所谓“举县令,择郡守”就是要整饬吏治,所谓“慎选举,敦教育”就是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这两条的关系,前条是要罢免一批不合格的官员,后条是要培养并选拔一批“明体达用”的新儒,以取代那些不合格的官员。
范仲淹的教育实践,始于他在天圣五年(1027年)丁母忧期间应晏殊之邀,执掌应天(睢阳)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②《宋史·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所谓“自殊始”,实即自范仲淹始。
范仲淹在天圣八年(1030年)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如能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十数年间,异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③
他所说的“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已经包含后来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之意。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知苏州,奏请立郡学。当时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④。胡瑗在苏州“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⑤,可见当时苏学之盛。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在陕甘抗击西夏,其“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是在此年。而胡瑗被“辟丹州推官”⑥,遂成为“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⑦。不久,胡瑗丁父忧。服除后,应范仲淹好友滕宗谅之邀,往湖州任教授。《安定学案》载:
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胡瑗之“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又称“苏、湖教法”,实际上是贯彻实践了范仲淹的教育思想,而且是范仲淹提供了这种教育实践的机会。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始行庆历新政。在此期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著为令”①。正是因为庆历新政,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才以朝廷政令的形式在全国得到推广。
钱穆先生曾论“明体达用之学”的意义:“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②这里说的“宋儒所以自立其学”,当就是宋代的“新儒学”,尔后宋代的“理学”或“道学”也包括在内。
三、“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宋元学案·序录》云:“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高平学案》把韩琦、欧阳修列为“高平同调”,把富弼、张方平、李觏等列为“高平门人”,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刘牧的易学、刘敞的经学、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等,都与范仲淹以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蜀学为例,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说: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①
观此可知,庆历新政对当时的士人发生了广泛重要的影响,乃至偏处四川眉山乡校尚为七八岁童子的苏轼,亦受其感召。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所颂者十一人,而“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并为人杰,是当时士人所争以为师者。三苏的蜀学初被张方平所赏识,继而得到欧阳修的推荐,故《宋元学案》将苏洵列为“庐陵学侣”,而苏轼、苏辙则在“庐陵门人”。当苏轼、苏辙在嘉祐二年(1057年)举进士时,范仲淹已于皇祐四年(1052年)病逝,苏轼以不识范仲淹为“平生之恨(憾)”。而在范仲淹死37年之后,仍愿“自托于门下士之末”。
再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例。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后经友人曾巩的引荐,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推举,故而《宋元学案》将曾巩和王安石都列为“庐陵门人”。当范仲淹于皇祐四年(1052年)病逝时,王安石作《祭范颍州文》,首言“呜呼我公,一世之师”,这与欧阳修在《祭资政范公文》中说“举世之善,谁非公徒”是一致的。王安石又评价范仲淹“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王安石对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也给予高度评价:“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②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关于此书与庆历新政的联系,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所附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云:
荆公之学,原本经术,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然其后卒以新法误天下,而为当时所排击。后世所口实,则非公所学之谬,谋国之过也。……公有志于任天下之重,在于变更法度,慎选人才。先是范文正公应诏条陈十事,所援《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甚切。……又论明黜陟,必三载考绩;精贡举,必先策论而后诗赋。此皆为公书中所必欲行者,而范公已先言之。①
此处说王安石的《言事书》“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未免夸大其词。但说《言事书》主张“变更法度,慎选人才”,这在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已先言之”,却是符合实际的。嘉祐初年,胡瑗管勾太学,声望甚高,王安石作有《寄赠胡先生》云:“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吾愿圣帝营太平,补葺廊庙枝倾颓。……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构架桷与榱。”②从此诗可看出,王安石当时亦极力推崇胡瑗。但是在宋神宗即位的熙宁元年(1068年)以后,王安石逐渐附从神宗的意旨,将改革的方向转变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③,因而有熙宁变法,乃至引起新旧党争。
当然,更重要的应讲明范仲淹、胡瑗等与理学家的关系。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之开山,在《宋元学案》中被列为“高平讲友”,但未说何据。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比范仲淹小28岁,将其列为“高平讲友”实在有些勉强。然而周敦颐与范仲淹确实有着思想上的联系,且其早年当亦受到范仲淹的影响。据茅星来《近思录集注·附说》,景祐四年(1037年)周敦颐21岁,“母郑氏卒,葬于润州丹徒县龙图公(郑向)之墓侧。康定元年庚辰(1040年)服除,授洪州分宁县主簿”。也就是说,1037—1040年周敦颐在润州(今镇江)丹徒县为其母守墓三年。而范仲淹在景祐四年(1037年)徙知润州,宝元元年(1038年)冬十一月徙知越州(今绍兴)。周敦颐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与范仲淹同在润州,就范仲淹在当时的地位、声望及其在润州建郡学而言,周敦颐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的④。庆历四年(1044年),周敦颐改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两年后,二程受学于周敦颐。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⑤这一“孔颜乐处”的话题在宋明理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发其端者实为范仲淹。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即范仲淹中进士的前一年,他就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①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亦教导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②。当范仲淹晚年徙知杭州时,“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③嘉祐二年(1057年),胡瑗在太学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胡瑗、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重视当都源自范仲淹,而“孔颜乐处”正是宋代新儒学为士人提供的一个有别于佛、道二教的儒者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地④。
《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庆历二年(1042年),张载作《庆州大顺城记》,记述范仲淹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率军筑大顺城,击败西夏军。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张载约有三年的时间与范仲淹同在西北前线。⑤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是正确的。
从宋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宋学的主流毕竟是以二程之洛学为主的“伊洛渊源”(此“伊洛渊源”至朱熹而集大成,从而有“濓洛关闽”的理学谱系)。但如黄震所说:“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亦如黄百家所说:“(安定)先生之学,实与孙明复开伊洛之先。”⑥将“伊洛渊源”上溯至“宋初三先生”,进而明确此三先生乃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这符合宋学发展的实际。朱熹作《伊川先生年谱》云:
(程颐)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业于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⑦
按,“皇祐二年”时,胡瑗尚未居太学,此应为“嘉祐二年”之误①。当时程颐25岁,“上书阙下”,即写了《上仁宗皇帝书》,这比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早一年。由此两书可见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改革思想的延续。程颐上书“不报”,于是“闲游太学”。当时胡瑗“主教导”,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②。《宋元学案》将程颐列为“安定门人”,又将二程列为“濓溪门人”,这也应是正确的。
周、张、二程虽然与范仲淹、胡瑗等有着学术源流和思想上的联系,但他们毕竟是“新儒中之新儒”。他们比范仲淹、胡瑗等所更“新”者,是建立了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开山就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义”,以及对二程“性即理也”和张载“心统性情”等的阐发,遂有了“濂洛关闽”的理学谱系,又有了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的新经学体系。这就是“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也就是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
明确了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的关系,我想对“理学”的理解也有以下几点意义:
(一)宋代“新儒学”之初起,是要“改革政令”,也就是要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这仍延续了先秦儒学的“内圣外王”之旨。虽然“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但是理学家仍不失“内圣外王”的抱负。他们后来的“内向化”,形成“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局面,实是因为在熙宁变法之后受到了种种政治形势和政治制度的限制和束缚,如他们提出了以“格君心之非”为治世的“大根本”,但实际上“君心”并不是他们所能“格”的③。
(二)宋代“新儒学”先有了“孔颜乐处”的价值取向,有了儒家所区别于佛、道二教的安身立命之地,然后才有了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价值优先仍然是理学思想体系的重点或宗旨。如作为理学之开山的《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讲起,推衍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而其归结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所谓“立人极”,就是要确立最高的价值标准。
(三)宋代“新儒学”虽然是以“理学”为思想理论的主流,但是庆历之际也有多种“学统”兴起,在“理学”内部也并非只有“濂洛关闽”一条线索。因此,对宋代新儒学的学派多样性和思想内容丰富性也应有新的理解。
(四)“明体达用之学”乃是“宋儒所以自立其学”者,宋代的理学家虽然较专注于“内圣”,但是对“明体达用之学”也是给予肯定的。特别是朱熹晚年的《学校贡举私议》,其旨义更符合“明体达用之学”。反思元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只设“德行明经”一科,后又以八股文取士,这应是元代以后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曾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作为改革的依据,这也不是偶然的①。
我近年来比较赞成钱穆先生的一个说法,即他在《朱子学提纲》中所说:“理学兴起以前,已先有一大批宋儒。此一大批宋儒,早可称为是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③依此说,“新儒家”之称可有广狭之别,广义的“新儒家”包括范仲淹、欧阳修和“宋初三先生”等,狭义的“新儒家”则专指宋明理学家(包括理学和心学)。
钱穆先生还曾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④这里说的“宋学”应即指广义的宋代新儒学,“两端”之一的“革新政令”是以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为代表。而之二的“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则尤指自周敦颐始的“伊洛渊源”或“濂洛关闽”之学。
自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以来,学界一般都把理学的先驱追溯到唐代的韩愈和李翱。从古文运动、排斥佛老、道统论和心性论来说,的确可以这样联系,但这毕竟只是后人或今人的一种思想史叙述,而不是理学家自己的说法。我认为追溯理学的先驱,还应该重视朱熹的以下说法:
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①
这里的“亦有其渐”,就是指道学或理学的先驱。我认为追溯理学的先驱,还是应重视朱熹所说过的,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讲起,他们就是广义的宋代新儒学的发端。
一、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
“宋初三先生”在宋代新儒学中的地位早已得到承认,如全祖望所作《宋元学案·序录》云:
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学案》。
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石介),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学案》。
考《宋元学案》的这两段“序录”,其实是本于黄百家所引黄震所说: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②
这条引文是出自《黄氏日抄》卷四十五。而黄震之说实又是本于上述朱熹所论的“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差别只是缺少了“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黄震对范仲淹并不是不了解,如他也曾说:“本朝人物,范文正公本朝第一等人。”①但他可能不太熟悉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故他在讲“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时没有把范仲淹放在前面。这一忽略致使宋初的一段学术史不明,乃至《宋元学案》在《安定学案》《泰山学案》之后才是《高平学案》和《庐陵学案》。全祖望《序录》说:
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述《高平学案》。
这一顺序的颠倒,以及把范仲淹作为“安定、泰山而外”的一支,其误在王梓材的“案语”中已经点明了:“高平行辈不后于安定、泰山,而庐陵亦当时斯道之疏附也。谢山以梨洲编次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故以高平、庐陵次之。”(《序录》案语)梓材又云:“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高平学案》案语)、“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四先生皆在文正门下”(《泰山学案》案语)。王氏所说《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当即指胡瑗曾为程颐所尊敬的老师。他所说“宋初三先生”及李觏“皆在文正门下”,是本于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所云:“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②这才是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真实关系,即“宋初三先生”及李觏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
《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
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这段引文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所引《杨公笔录》(宋杨延龄撰),全祖望谨按:“此段稍可疑,宜再考。(泰山)先生婿于李文定公时,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长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对于全祖望所疑,王梓材已加辨正:“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以端拱三年己丑生,实长于泰山三岁。”按“端拱三年”为“端拱二年”之误,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孙复生于992年,范比孙确实年长三岁。全祖望疑孙复“稍长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此亦全氏之疏误,意在否认孙复之学本于范仲淹。而上述史料不仅见于宋代的《东轩笔录》和《杨公笔录》,而且亦被朱熹编入《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三,故其当确信无疑。
《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当即孙复四举进士不第之时。他在“退居泰山”之前,约有一年的时间从学于范仲淹,他的“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授以《春秋》”。在孙复苦学于泰山期间,石介“躬执弟子礼,师事之”①。其间,范仲淹与孙复有书信往还,《范文正公集·尺牍》中有给孙复的信,《孙明复小集》中亦有《寄范天章书》等等。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胡瑗生于公元993年(比孙复小一岁),13岁时是1006年,而孙复离开睢阳时是1028年。也就是说,在胡瑗13岁“通五经”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贫困坎坷,然后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安定学案》载其在泰山苦学的情况:“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在此期间,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砺,而范仲淹的“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当已通过孙复而传达给了胡瑗、石介②。
二、范仲淹与“明体达用之学”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1043—1044),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这一改革的思想在范仲淹的心中沉潜了近二十年,比较典型的表述是他在《上执政书》中所说:“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①。所谓“举县令,择郡守”就是要整饬吏治,所谓“慎选举,敦教育”就是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这两条的关系,前条是要罢免一批不合格的官员,后条是要培养并选拔一批“明体达用”的新儒,以取代那些不合格的官员。
范仲淹的教育实践,始于他在天圣五年(1027年)丁母忧期间应晏殊之邀,执掌应天(睢阳)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②《宋史·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所谓“自殊始”,实即自范仲淹始。
范仲淹在天圣八年(1030年)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如能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十数年间,异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③
他所说的“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已经包含后来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之意。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知苏州,奏请立郡学。当时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④。胡瑗在苏州“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⑤,可见当时苏学之盛。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在陕甘抗击西夏,其“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是在此年。而胡瑗被“辟丹州推官”⑥,遂成为“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⑦。不久,胡瑗丁父忧。服除后,应范仲淹好友滕宗谅之邀,往湖州任教授。《安定学案》载:
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胡瑗之“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又称“苏、湖教法”,实际上是贯彻实践了范仲淹的教育思想,而且是范仲淹提供了这种教育实践的机会。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始行庆历新政。在此期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著为令”①。正是因为庆历新政,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才以朝廷政令的形式在全国得到推广。
钱穆先生曾论“明体达用之学”的意义:“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②这里说的“宋儒所以自立其学”,当就是宋代的“新儒学”,尔后宋代的“理学”或“道学”也包括在内。
三、“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宋元学案·序录》云:“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高平学案》把韩琦、欧阳修列为“高平同调”,把富弼、张方平、李觏等列为“高平门人”,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刘牧的易学、刘敞的经学、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等,都与范仲淹以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蜀学为例,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说: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①
观此可知,庆历新政对当时的士人发生了广泛重要的影响,乃至偏处四川眉山乡校尚为七八岁童子的苏轼,亦受其感召。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所颂者十一人,而“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并为人杰,是当时士人所争以为师者。三苏的蜀学初被张方平所赏识,继而得到欧阳修的推荐,故《宋元学案》将苏洵列为“庐陵学侣”,而苏轼、苏辙则在“庐陵门人”。当苏轼、苏辙在嘉祐二年(1057年)举进士时,范仲淹已于皇祐四年(1052年)病逝,苏轼以不识范仲淹为“平生之恨(憾)”。而在范仲淹死37年之后,仍愿“自托于门下士之末”。
再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例。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后经友人曾巩的引荐,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推举,故而《宋元学案》将曾巩和王安石都列为“庐陵门人”。当范仲淹于皇祐四年(1052年)病逝时,王安石作《祭范颍州文》,首言“呜呼我公,一世之师”,这与欧阳修在《祭资政范公文》中说“举世之善,谁非公徒”是一致的。王安石又评价范仲淹“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王安石对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也给予高度评价:“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②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关于此书与庆历新政的联系,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所附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云:
荆公之学,原本经术,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然其后卒以新法误天下,而为当时所排击。后世所口实,则非公所学之谬,谋国之过也。……公有志于任天下之重,在于变更法度,慎选人才。先是范文正公应诏条陈十事,所援《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甚切。……又论明黜陟,必三载考绩;精贡举,必先策论而后诗赋。此皆为公书中所必欲行者,而范公已先言之。①
此处说王安石的《言事书》“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未免夸大其词。但说《言事书》主张“变更法度,慎选人才”,这在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已先言之”,却是符合实际的。嘉祐初年,胡瑗管勾太学,声望甚高,王安石作有《寄赠胡先生》云:“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吾愿圣帝营太平,补葺廊庙枝倾颓。……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构架桷与榱。”②从此诗可看出,王安石当时亦极力推崇胡瑗。但是在宋神宗即位的熙宁元年(1068年)以后,王安石逐渐附从神宗的意旨,将改革的方向转变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③,因而有熙宁变法,乃至引起新旧党争。
当然,更重要的应讲明范仲淹、胡瑗等与理学家的关系。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之开山,在《宋元学案》中被列为“高平讲友”,但未说何据。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比范仲淹小28岁,将其列为“高平讲友”实在有些勉强。然而周敦颐与范仲淹确实有着思想上的联系,且其早年当亦受到范仲淹的影响。据茅星来《近思录集注·附说》,景祐四年(1037年)周敦颐21岁,“母郑氏卒,葬于润州丹徒县龙图公(郑向)之墓侧。康定元年庚辰(1040年)服除,授洪州分宁县主簿”。也就是说,1037—1040年周敦颐在润州(今镇江)丹徒县为其母守墓三年。而范仲淹在景祐四年(1037年)徙知润州,宝元元年(1038年)冬十一月徙知越州(今绍兴)。周敦颐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与范仲淹同在润州,就范仲淹在当时的地位、声望及其在润州建郡学而言,周敦颐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的④。庆历四年(1044年),周敦颐改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两年后,二程受学于周敦颐。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⑤这一“孔颜乐处”的话题在宋明理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发其端者实为范仲淹。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即范仲淹中进士的前一年,他就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①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亦教导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②。当范仲淹晚年徙知杭州时,“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③嘉祐二年(1057年),胡瑗在太学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胡瑗、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重视当都源自范仲淹,而“孔颜乐处”正是宋代新儒学为士人提供的一个有别于佛、道二教的儒者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地④。
《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庆历二年(1042年),张载作《庆州大顺城记》,记述范仲淹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率军筑大顺城,击败西夏军。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张载约有三年的时间与范仲淹同在西北前线。⑤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是正确的。
从宋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宋学的主流毕竟是以二程之洛学为主的“伊洛渊源”(此“伊洛渊源”至朱熹而集大成,从而有“濓洛关闽”的理学谱系)。但如黄震所说:“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亦如黄百家所说:“(安定)先生之学,实与孙明复开伊洛之先。”⑥将“伊洛渊源”上溯至“宋初三先生”,进而明确此三先生乃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这符合宋学发展的实际。朱熹作《伊川先生年谱》云:
(程颐)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业于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⑦
按,“皇祐二年”时,胡瑗尚未居太学,此应为“嘉祐二年”之误①。当时程颐25岁,“上书阙下”,即写了《上仁宗皇帝书》,这比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早一年。由此两书可见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改革思想的延续。程颐上书“不报”,于是“闲游太学”。当时胡瑗“主教导”,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②。《宋元学案》将程颐列为“安定门人”,又将二程列为“濓溪门人”,这也应是正确的。
周、张、二程虽然与范仲淹、胡瑗等有着学术源流和思想上的联系,但他们毕竟是“新儒中之新儒”。他们比范仲淹、胡瑗等所更“新”者,是建立了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开山就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义”,以及对二程“性即理也”和张载“心统性情”等的阐发,遂有了“濂洛关闽”的理学谱系,又有了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的新经学体系。这就是“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也就是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
明确了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的关系,我想对“理学”的理解也有以下几点意义:
(一)宋代“新儒学”之初起,是要“改革政令”,也就是要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这仍延续了先秦儒学的“内圣外王”之旨。虽然“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但是理学家仍不失“内圣外王”的抱负。他们后来的“内向化”,形成“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局面,实是因为在熙宁变法之后受到了种种政治形势和政治制度的限制和束缚,如他们提出了以“格君心之非”为治世的“大根本”,但实际上“君心”并不是他们所能“格”的③。
(二)宋代“新儒学”先有了“孔颜乐处”的价值取向,有了儒家所区别于佛、道二教的安身立命之地,然后才有了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价值优先仍然是理学思想体系的重点或宗旨。如作为理学之开山的《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讲起,推衍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而其归结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所谓“立人极”,就是要确立最高的价值标准。
(三)宋代“新儒学”虽然是以“理学”为思想理论的主流,但是庆历之际也有多种“学统”兴起,在“理学”内部也并非只有“濂洛关闽”一条线索。因此,对宋代新儒学的学派多样性和思想内容丰富性也应有新的理解。
(四)“明体达用之学”乃是“宋儒所以自立其学”者,宋代的理学家虽然较专注于“内圣”,但是对“明体达用之学”也是给予肯定的。特别是朱熹晚年的《学校贡举私议》,其旨义更符合“明体达用之学”。反思元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只设“德行明经”一科,后又以八股文取士,这应是元代以后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曾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作为改革的依据,这也不是偶然的①。
附注
①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新儒家’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与‘道学’完全相等。”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8页。
②参见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14、80页。
③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8、16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①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十九。类此,南宋时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亦有云:“先儒论本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②此又见《宋史·范仲淹传》所附范纯仁传,又被《泰山学案》王梓材按语所引。
①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说:“范仲淹应试时胡瑗只有二十五岁,大概还在泰山十年苦学的期间,自然绝无可能有任何影响。”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94页。此失误即因不明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所致。
①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③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④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宋史·范仲淹传》。
⑥《宋史·胡瑗传》。
⑦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
①欧阳修:《胡先生墓表》,《欧阳文忠全集》卷二十五,四部备要本。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
①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四,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②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①詹大和等撰:《王安石年谱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15~316页。
②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③《宋史全文》卷十一,内府藏本。
④度正《周敦颐年谱》有云:“先生遂扶柩厝于龙图公墓侧。是岁居润,读书鹤林寺。时范文正公(仲淹)、胡文恭(宿)诸名士与之游。”参见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⑤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①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宋史·张载传》。
③詹大和等撰:《王安石年谱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④参见李存山:《儒家的“乐”与“忧”》,《中国儒学》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⑤《邵氏闻见录》卷十五云:“子厚少豪其才,欲结客,取熙河隍鄯之地。范文正公帅延安,闻之,馆于府第。”
⑥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⑦程颢、程颐:《二程遗书》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①参见李存山:《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杭州研究》2010年第2期。
②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参见李存山:《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①参见李存山:《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2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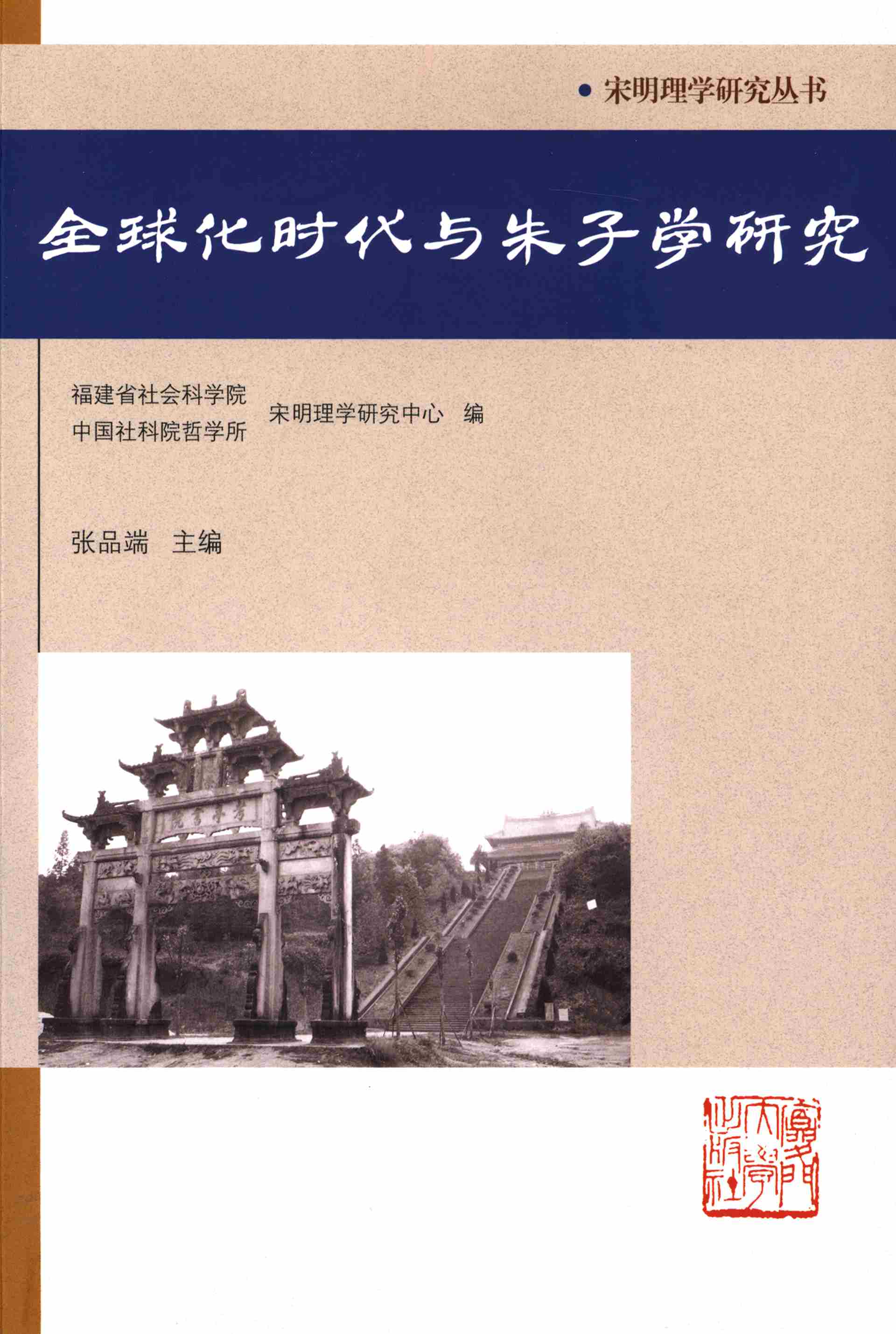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李存山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