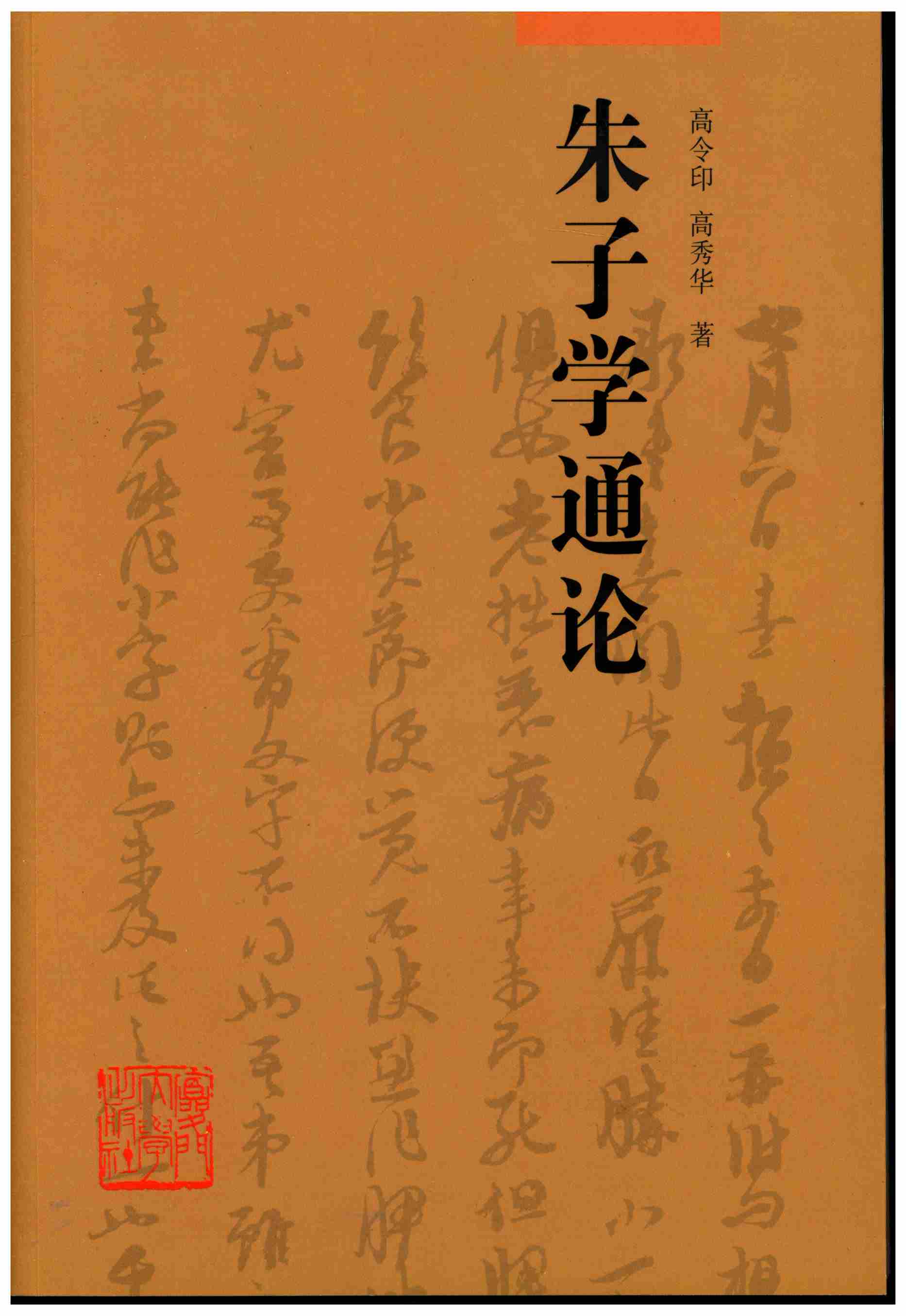内容
一 衍变的内在倾向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差不多又经过了三四十年,至元仁宗时(1312—1320年)就遍及全国。朱子学在福建的传衍和分化是个雏型,全国朱子学的派别和衍变是其在福建传衍和分化的扩大和发展。
由于朱熹综罗百代、集诸儒学之大成,非某个后继者所能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集大成,体系庞大,因而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对全国朱子学衍变的内在倾向,今人蒙培元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说:
简单地说,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矛盾。一个是理本体论同气化学说的矛盾,即唯心主义体系同唯物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一是理本体论同心本体论的矛盾,即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矛盾。此外,方法论和体系之间也有矛盾,最明显的是他的“格物穷理”说同“明明德”的根本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说,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同时又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这些矛盾是朱熹本人无法解决的。这就决定了朱熹哲学必然要分化。①
蒙培元对南宋末、元、明时代哪个朱子学家属于哪一哲学倾向,以及按唯物论和唯心论来划分中国古代哲学,还可以深入讨论,但是其这里的概括说明是很确切的,为研究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提供了指导性线索。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成为整个国家的正宗思想后,它根据理论自身的规律和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进行衍化。基于上述黄榦是朱子学由闽至全国的桥梁,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是在黄榦思想中开其端的。黄榦固守师说,只是在体之用上有所阐发。南宋末黄震曰:
晦庵论近思先太极说;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后能不愠,非不愠然后为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余;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易肆,故当谨耳。②
这里黄震叙述了黄榦思想与朱熹思想之不同,在黄榦思想中就埋下朱子学日后分化的根苗。体用关系体现为理一分殊,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的先验原则与现实人的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他引用孟子的四端说来说明道德的体用关系。黄榦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③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道德之体,有此体必然表现为与此体相联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道德之实践(用);抽象的天理世俗化,为人人得以遵循的道德准则,通过格物明理实现人内心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善;实际上,格物明理和明内心的道德之善是对立的。这是黄榦哲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
朱子学于元初盛行于全国之后,其衍化大致有三派:一是以赵复、许衡为代表的北方一派,一是以何基、许谦为代表的浙江金华北山学派,一是以饶鲁、吴澄为代表的江西广汉双峰学派。这三派大致按上述黄榦思想中的三种倾向进行衍变和分化,走向不同的学术道路,因而使朱子学原来理论上的裂痕走向解体的道路。
朱熹思想的解体和分化促使朱子学的演进,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本身的发展必然会解体和分化,同时其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其后一二个后继者所能继承和发展的。南宋至明朝末年,朱熹思想向两个方向分化和发展: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黄震、文天祥,元、明朝的刘因、薛瑄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罗钦顺、王廷相等为代表的气学。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论争,就是这两种方向发展的结果。最后出现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陈献章、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和以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学,都是从朱熹思想体系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发展过程,由内圣成德而外王事功,中国社会由古代孕育着近代。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孔子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朱熹,其内圣成德达到了成熟和综合点,其后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即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的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时期,西方社会也正开始近代化,出现“文艺复兴”。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是与西方同步的,或者说早于西方。牟宗三在讲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时,深刻指出:
三大儒的意识是顺着宋明数百年内圣学之成熟而要求开外王事功的意识。这一意识正合乎西方17、18、19世纪300年开近代文明的方向。时间即相合,方向也相同。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其中的历史运会当该切实正视。须知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民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所以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王船山有《黄书》之作。满清200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向僵滞,整个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两三百年之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
一下,相去遂不可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①
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就是他顺应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理想往前发展,推翻清王朝,开出一个外王事功的大时代,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
二 黄震 金华四先生
南宋末年浙江朱子学有辅广系黄震、黄榦系金华四先生等。对此,《宋元学案》有所综合评述。其曰:
四明之传,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平生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即江西)诸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子(金华四先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黄震)折衷诸儒,即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②
浙江的朱子学,对朱熹的思想,黄震有较大的修正,金华四先生则是墨守朱熹家法,因此分开论述。
黄震(约1213—1280年),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文洁先生,浙江慈溪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历官吴县、华亭县、长洲县尉,史馆校阅,广协、绍兴通判,抚州知府,江西、浙东提举常平等。宋亡后,“日惟一食,仰天长恨,祈速死”,最终“饿于宝幢而卒”③。其著作有《黄氏日抄》(即《慈湖黄氏日钞分类》)、《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戊辰修史传》、《仰天遗草》等。
黄震对天理的论述,基本上与朱熹同。而在讲到理与道的关系时却对朱熹有所修正。如黄震说: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④
黄震强调,道不在天地人事之外。这跟朱熹的讲法是有所不同的。朱熹认为,作为道德伦理准则的理,是人道;作为万物本原的理,是天道,而天之道则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外的。这就对朱熹之“理在事先”的观点有所修正。由此,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之“道不必贯而本一”的观点。他说:
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①
他认为,朱熹后学“舍孝弟忠信不讲而独讲一贯”②的倾向,是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论的断章取义,是道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观点。
黄震认为,朱熹等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是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不一致的。他说:
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虚空中别可言性,则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说也。③
他认为,“性相近”包括了气质和天地之性,而不是朱熹等所说的只是“气质之性”的观点。朱熹认为,“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哪里有三品来?”④在朱熹看来,韩愈的性三品是指气质之性,而天地之性没有三品的问题。对此,黄震说:
性有三品之说,正从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来,于理无毫发之背。至伊、洛添气质之说,又较精微。盖风气日开,议论日精,得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对说,而后孟子专指性善之说举以属之天地之性,其说方使无偏。此于孟子之说有功而于孔子之说无伤。实则孔子言性,包举大体;孟子之说,特指本源而言。性无出于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说本于上智、下愚之说,而后进喜闻伊、洛近日之说,或至攻诋昌黎耶?⑤
在黄震看来,韩愈之性三品说,同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二程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一致的,而朱熹却说性三品不包括天地之性,不是相矛盾吗?
在知行问题上,黄震强调躬行。他说:
自晦翁之学盛行,而义理之说大明。天下虽翕然而向方,流弊亦随之而渐生。盖论说之求多,恐躬行之或缺,苟曾用力于躬行,何暇往事乎口说?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见言晦翁之学者几人,往往不知其躬行。
……世所谓《中庸》、《大学》者,身未必行,惟见笔舍华靡。①
在这里,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笔舌华靡”的空谈义理、不知躬行的行为。
由上可见,黄震对朱熹并不盲目信从,而是有所立异的。因此,黄震在朱子学发展史上,不仅有继承,也是有所发展的,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的。
金华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9年,字子恭,学者称北山先生)及其弟子王柏(1192—1274年,字会之,号鲁斋)、柏弟子金履祥(1232—1303年,又名祥、开祥,字吉父,号次农,因家居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祥弟子许谦(1270—1337年,字益子,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生),是朱子学浙江金华之主要传人,被朝廷列为朱子学的正宗。《宋元学案》专立《北山四先生学案》,详述其朱子学思想。
北山学派的何基等人,严守朱子学门户,强调读书传览为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何基语录》说:
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②
他们抱住朱熹的《四书集注》寸步不离,确守师说。清初黄宗羲说: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③
北山学派由确守师说,只注重读书穷理,继承和发挥朱子学训释儒家经典的传统,虽然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但是由于走向章句训诂的道路,使朱子学变成烦琐哲学,没有开辟出新的境界。特别是其中的王柏,他的《诗疑》、《书疑》,原是对朱熹《诗集传》的继承,却走向极端,偏离了儒学正统,受到后世朱子学者的批评。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更觉朱子学正统派的空言无实。清代前期,虽有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及其他理学名臣大倡朱子学,使其一时兴盛;清末有朱次琦(1807—1881年,广东南海人)、杨昌济(1871—1920年,湖南长沙人)、辜鸿铭(1897—1928年,福建厦门人)等人提出重整朱子学,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和朱次琦同时的文廷式(光绪帝珍妃的老师)曾谓朱熹“训门人语多痛切,数十世后如见其人”。①朱次琦提出“朱子百世之师”,朱子“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之力也”。②
杨昌济曾先后留学日、英、德等国9年。他在五四运动前期的中西哲学论争中,采取调和折衷态度,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实际上他立足于程朱理学。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讲授伦理学。他说:
所谓不限于西洋之理论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③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学应为体(正宗),特别是朱熹的著作应尊为儒家思想的典范。他为讲授伦理学而编写的《论语类钞》共38条,其中有朱熹语录释《论语》者达22条,占三分之二。如第22条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首先就引用了朱熹一大段语录,即: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道,譬则天地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这就是说,太极(道之体、一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万殊各得其所”就是太极(道之体、一本)的体现或作用。这段是朱熹“理一分殊”的典型表述,杨昌济解释说:
宇宙为一全体(即一本、太极),宇宙间所有一切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同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④
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熹下列一段话,其曰:“吾子之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有见者也。”⑤杨昌济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来论证如何积累知识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此外,杨昌济还通过研究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吸取和发扬朱子学。
由上可见,直到清末和民初,朱子学正统派在一些学者中和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就全国来说,朱子学终未能真正恢复其元气,在理论上未有多大进展,而且趋于终结,这就是由自我窒息而后日趋沉寂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三 双峰学派 饶鲁 吴澄
《宋元学案》谓,黄榦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江右即江西,其代表者为双峰学派之饶鲁、吴澄等。“双峰(饶鲁)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吴澄)”,其学术活动时期为宋末元初。
饶鲁(生卒不详),字伯舆、仲元,号双峰,江西余干人。据载,“庚申(1206年),诏饶州布衣饶鲁,不事科举,一意经学,补迪功郎、饶州教授”①。其著作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学庸纂述》、《西铭录》、《近思录注》等。
对于饶鲁之朱子学,有谓不拘于章句,一如朱子之于二程,“共派而分流,异出而同归”②。可知饶鲁不是墨守朱熹门户的。饶鲁认为,理气不相离,气以理为主,理以气为辅,气为理之衬贴。他说:
“浩然之气”,全靠道义在这里面做骨子。无这道义,气便软弱。盖缘有是理而后有是气,理是气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气。以有太极在底面做主,所以它底凭地浩然。③
这里全是朱熹之理气关系的说法。他又说:
“发育万物”,以道之功用而言,万物发生长育于阴阳五行之气,道即阴阳五行之理。是气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峻极于天”,以道之体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无过于天者。天之所以为天,虽不过阴阳五行浑沦磅礴之气。而有是气,必具是理。是气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全体大用,极于至大而无外有如此者。④
此是说理气相即不二。这里还讲了道的体用关系,即其所谓“道之体段”、“道之功用”。道是弥沦天地的,是主宰天地之气的。
饶鲁继而认为人道的极则是天理。他从性为人所禀之天理出发,发挥了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观点。他在疏解张载的《西铭》时说:
《西铭》一书,规模宏大而条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尽。然其大旨,不过中分为两节。前一节明人为天地之子;后一节言人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何谓人为天地之子?盖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是性,犹子受父母之气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举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为大父母。故以人而观天地,常漠然与己如不相关。人与天地既漠然如不相关,则其所存所发宜乎?①
由此,他得出:“言天以至健而始万物,则父之道也;地以至顺而成万物,则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间,禀天地之气以为形,而怀天地之理以为性,岂非学之道乎?”他把天人地释为父子母,是有新意的。在他看来,人之所以生,是天地之气以为形,天地之理以为性,故天地与人,犹如父母之与子。因而天地与我一体,即他所说的“物吾党与”。
饶鲁进一步指出,人本身具有善端,人都有自新的欲望,即所谓民之心本自好善而恶恶,熟不欲自新?因为,仁即心,心之存即是识仁而成仁心。他说:
诚意、正心、修身不是三事。颜子问仁,夫子告以非礼勿视、听、言、动,紧要在四个“勿”字上。仁属心,视、听、言、动属身,“勿”与“不勿”属意。若能“勿”时,则身之视、听、言、动便合礼,而心之仁则存,以此见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在意之诚不诚。所以,《中庸》、《孟子》只说“诚身”便贯了。②
这里的说法与朱熹之心统性情说不同。在朱熹那里,人禀受天道为性,故性具天理;心不等于性,故心不等于天理。而饶鲁却认为,心即仁,故仁同于天理。这同陆九渊的“心即理”相似。在饶鲁看来,心之能存与否,全在身之视、听、言、动,而视、听、言、动又在于“意之诚不诚”,故“诚”就将诚意、正心、修身三事贯串起来。诚即无妄、不自欺意。
饶鲁提出以敬为诚的存养省察工夫。由此他喜欢静坐。他说:静坐时,须心主于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言于敬,亦静坐不得。心是个活的物,若无所用,则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圣人说“难矣哉”,意甚该涵。③
他认为,通过静坐,就能收敛“野马”之心,使本来的善性得以充分发挥。这与禅家的“修心”、“守心”相类似。
上面讲的居敬,只是饶鲁为学之一。他认为,为学四方,即立志、居敬、穷理、反省。①他的为学之方由“立志”始,然后居敬、穷理,而终止于反身。这是内外结合的方法,是符合理学家的“涵养须用敬,进德在致知”的原则的。
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历官元朝之国子司业、国史院编修、制诰、集贤殿直学士等。著有《五经纂言》、《皇极经世续书》、《道统图》等,清人辑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吴文正公外集》。
在元代,吴澄与许衡为名儒。许是北方人,于元初“粗迹”朱子学。吴是南方人,直承朱子学大家,是“正学真传”。因此,元代朱子学有“南吴北许”之称。
吴澄以朱熹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其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享,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②
这段话值得注意者,一是韩愈论道始于尧舜,而吴澄则据董仲舒意谓道始于天,此说出了宋明儒的本体论。二是其用《周易》之元、亨、利、贞把历史顺序规定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段,每一段又分元、亨、利、贞。三是他把朱熹说成是“利”,而不是终结“贞”,一方面他不把朱熹看成为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似乎把自己看成是“贞”的地位,以跻身宋儒诸子的继承者之列。所以,上引《元史》本传接着谓其“以斯文自任如此”。
吴澄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是对朱熹的经学有较大的补充和发挥。他的《五经纂言》,实际上完成了朱熹的未竟之业。朱熹曾与吕祖谦等商议编次“三礼”,而终老未及为。朱熹曾说:
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附于本经之下。③
但是,朱熹只留下草创本《仪礼经传通解》。后来,黄榦等也曾治礼,没有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吴澄从中年到晚年,几乎倾一生精力,完成《五经纂言》,实现了朱熹的未竟之业。他在《诸经序说》中说:
朱子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谓三礼体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书,于此至惓惓也。《(仪礼)经传通解》,乃其编类草稿,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无禄弗逮,遂为万世缺典,每伏读而为之惋惜。然三百三千,不存盖十之八九矣,朱子补其遗缺,则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而各疏其下。夫以《易》、《诗》、《书》、《春秋》之四经,既幸而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而乱,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经者哉?徒知尊信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亦岂朱子所望于后学者哉!呜呼!由朱子而来,至于今将百年,以予之不肖,犹幸得私淑其书,用其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经,重加伦纪。①
吴澄“辄因”朱熹筹画之意,以《仪礼》十七篇为经,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例,将《礼记》(大小戴记和郑注)分类编次,纂成《仪礼逸经》八篇。就是把《礼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礼记》中的《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此二篇并与《小戴礼记》相参校),又把郑玄《三礼注》中的《中霤》、《禘于太庙》、《五居明堂》,共成二卷八篇。另外,又将大、小戴记中的《冠仪》、《昏仪》等八篇,和《礼记》中的《乡射仪》、《大射仪》二篇,辑成《仪礼传》十篇。这样,吴澄把汉以来流传的《礼记》(大小戴记,以至郑玄《三礼注》等)肢解,核订异同,重新编纂,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这不仅完成了朱熹生前的夙愿,而且经过这样的整理,使流传千百年来“难读”的一部《仪礼》,得见崖略,诚是经学史上的一大贡献。②
吴澄治五经不守朱子学门户。如其《易纂言》,自称“用功至久,皆自得于心,有功于世为最大”③。在这部《易》学中,就有和会朱陆的地方。
在本体论上,吴澄认为太极即道。他说:
所谓极也,道也者,无形无象,无可执著。虽称曰极,而无所谓极也;虽无所谓极,而实为天地万物之极。④
“太极”所以能起主宰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含有动静之理,它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如人之乘马,人随马的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它“常常如此,始终一般,无增无减,无分无合”。所以太极尽管包含动静之理,而主宰世界的生成、变化,它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⑤
吴澄进一步把太极说成是理、天理,而把理、天理释为天地万物之所以然者。他说:
气之循序而运行者为四时,气之往来屈伸而生成万物者为鬼神,命各虽殊,其实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①
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②
太极与理的关系,就宇宙本原来说是太极,就宇宙化生二气五行以至万物的过程来说是理。这样,理就是万物所以形成的理,而太极就是理的全体。万物中具体的理与本原的太极是万理一原的关系。所以,整个世界由它的本原到化生万事万物的现象界,都是由于太极和理的一系列的作用。
吴澄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太极,是人道的极则,也就是天理。那么,人是如何去认识它呢?是从吾心去体认,还是从万物去参究呢?是立之于本心,还是格之于外物呢?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在朱、陆之后,吴澄则是“和会”两家之说,形成了他自己的认识方法。
在吴澄看来,湛然纯善的天地之性附于人的时候,随着各人气质的清浊不同,而有善恶之分,因而有了气质之性。但是,即使是那些因气浊而恶的人,其天地之性亦在“其中”,只是“拘碍沦染”于浊气而已。悬之于高远的天地之性,不仅予性善的人,而且也予性恶的人。这就给具有气质之性的那些恶与不善的人找到了通向天地之性的可能和信心。他说:
人之明德,即天所以与我之明命也,自天所赋于人而言而谓之命,自人所得于天而言则谓之德,其实则一而已。然常人为气禀物欲之所昏,而不察乎此,是以昏昧蔽塞不能自明,至于梏其性而忘之也。故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所以与我之明德而有察焉,则必然因其所发,而致其学问思辨推究之功,又能因其所明,而致其存养省察推行之实,则吾之明德,亦得以充其本体之全,以无气质物欲之累,而能明其大德与尧无异矣。③
在吴澄看来,“明其德”不是由身外格物以明理,而是求之于己,自明其心。故他自己概括其方法为“自新”。可见,他主张自省自思而达到自觉,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相违背的,而与心学派明心穷理却是接近的。
吴澄认为,自省自思而自觉即是诚与敬。他说:“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敬为之主。……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①他又说:
凡所应接,皆当主于一心,主于一,则此心有主,而闇室屋漏之处自无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积久,无一事而不主一,则应接之处,心专无二。能如此,则事物未接之时把捉得住心,能无适矣。②黄直卿(榦)谓敬字之义,近于畏者,最切于己。凡一念之发,一事之动,必思之曰:此天理抑与人欲也?苟人欲而非天理,则不敢为,惴惴儆慎,无或有慢忽之心,其为之敬也。③
吴澄所谓敬,就是在“一念之发,一事之动”时皆以天理来约束思维;凡一念一事,都要想一想这是天理还是人欲。他完全排除了外物之诱惑。先秦思孟学派提出“诚者天之道”,是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为人道的极则。人能“思诚”即可达于“天之道”的诚。④吴澄所谓“思诚”,就是思我心中固有的诚。他说:
人之初生,已知爱其亲,此实心自幼而有者,所谓诚也。爱亲,仁也。充之而为义、为礼、为智,皆诚也,而仁之实足以该之。然幼而有是实心,长而不能行,何也?夫诚也者,与生俱生,无时不然也,其弗能有者,弗思焉尔。五官之主曰思……所以复其真实固有之诚也。⑤
他把诚说成是与生俱来,自幼而有。诚的内容就是爱其亲,也就是仁,它充实显露之后就是义、礼、智。在吴澄看来,它是具体的,并非是悬之于心外的一种神秘境界。而要保持自幼而有的诚,就是思。所谓思,就是去其恶欲和复性的冥悟过程。这样,就是去掉“人欲”,以达到所谓真实“不妄”、“不自欺”。由此进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双峰学派是沿着黄榦的明内心的道德之善走过来的,反对单纯读书明理,强调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双峰语录》有说:
若但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言语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⑥
在饶鲁看来,道理须是涵养,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来?可见,双峰学派是沿着黄榦的明内心道德之善的思路上往前衍变的,其心学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吴澄的心学思想更加明显。韩国李朝李退溪在讲到吴澄时曰:
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公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①
吴澄对朱熹和陆九渊两家都很推崇,他在《与许左丞书》中认为,“朱、陆二氏之为教一也”②。全祖望谓吴澄“固朱学”、“兼主陆学”。③
到了明代,先有吴与弼(1391—1469年,号康斋,江西崇仁人)提出“敬义夹持,明诚两进”④,发明代心学之端;再经陈献章(1428—1500年,号白沙,广东新会白沙里人)而至王阳明,把朱子学衍变为心学。王阳明是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者,即心学从朱子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并与朱子学相对立。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阳明学是理学由烦琐变为简易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社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启蒙思想的出现而要求冲破朱子学一统天下的结果。阳明学差不多盛行了一百年,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明末清初,正统派朱子学抬头和王夫之等人战斗的气论实学的出现,王学即告终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 北方学派 许衡
元初朱子学传入北方后,很快就形成为以赵复、许衡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李退溪在讲到赵复时说:
姚公(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公(按指赵复)传其学。由是许公衡、郝公
经、刘公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公始。⑤当时属于北方朱子学派的还有窦默等人。全祖望谓“河北之学传至江汉(赵复)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⑥
这里主要论述许衡。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等。他为元朝统治者策划“立国规模”,即运用朱子学治国,其朱子学思想被称为道统正脉。他在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期间,向蒙古弟子传播朱子学,使当时学人皆诵习程朱之学,有“以夏变夷”之功。卒赐荣禄大夫,谥文正。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诏祀孔庙。
许衡的著作有《大学要略》、《大学直讲》、《稽古千文》等,后辑为《鲁斋遗书》。近年台湾中文出版社据日本宪文九年(1669年)刻本影印出版《鲁斋全书》。
许衡为学,一以朱熹之言为归。实际上,他主要发扬朱熹的心学思想,把朱子学变成以“尊德性”为主的践履之学。他认为,朱熹的著述太多,重点不突出。“许文正公表彰朱子之书,天下乐为简易之说者。”①他沿着“简易”的方向,在朱熹的心说上兜圈子,为后来的心学一派开辟出道路。
许衡认为,人皆“禀天命之性为明德之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与尧舜神明为一”,但是在践履上一般人与尧舜圣人就不同了。他说:
众人多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能长存:或发于一件善念,便有被气禀物欲之私昏蔽了,故临事时对人旋安排把捉;未临事之前,与无人独处,却便放肆为恶。②
此谓善念到临事时就可以检验出来了。他特别强调慎独,在“与无人独处”时亦不能放肆为恶,必须谨慎而不敢疏忽才行。所以,他十分强调《大学》所讲的慎独工夫。他说:
幽暗之中,细微之事,人以为可忽者,殊不知其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更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所以,君子之心既常戒惧,而于此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虽人所不知,而独知之地,尤必极其谨慎而不敢忽。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③
他强调,“独是自家心里独知处;好善恶恶,实与不实,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
心里独自知道这等去处。君子必要谨慎,以审其几微。”①
在许衡看来,意念未发时之戒慎恐惧,能存天理之本然,其工夫是存养;由存养至慎独,能谨慎己所独知,从而遏人欲于将萌以至方萌。其工夫是省察。他说:
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者,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是气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长。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执之不使变迁。如此,则应物无少差谬。此所谓致知也,省察之事也。②
如能时时内自省察,无有不善,就能无愧于心。慎独是省察的前提和基础。气禀物欲之拘蔽于人既不容忽,人的尽心工夫就会连续不断,性中本然之理(善)即能永存。
许衡进一步指出,持敬则能身心收敛,身心常存。他说:为学之初,先要持敬。敬则身心收敛,气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浊者不得长;美者愈美,而恶者不得行。静而敬,常念天地鬼神临之,不敢少忽;动而敬,自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日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礼记》一书近千万言,最后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从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恶,皆从不敬上生。……这一件先能着力,然后可以论学。③
他所讲的这些,就是朱熹所讲的收摄涵养此心,敬之以恒,敬之忽失,就是常惺惺法,提心吊胆,便心不失其正。
在许衡看来,慎独为省察,持敬为涵养。在省察与涵养间他又加了个格物致知,这是许衡心学之独到处。他明确提出,“知其性是格物”④。此性是心体之性。知此心体之性,非格物不可。他说: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此解说个“穷”字;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此说个“理”字。所以然者是本然也;所当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当然者是义也。每一事、每一物,须有所以然与所当然。⑤
理固然为心体所内具,通过格物穷旭,如能自显心体所本具之理,此理即人之性。由知物之所当然,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物之所以然是其所当然之理由,此理由人于当初所未知。通过格物而致知。
由上可知许衡之心学体系了。他的结论是心与理为一。据记载:
问: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如何?先生曰:便是一以贯之。再问:理出于天,天出于理?先生曰: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①
由此,他便得出人、物后之于理的结论。他说:
有是理而后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诚有是理,而后成木之一物。表里粗细无不到,如成果实相似,如水之流满出东西南北,皆可体力而用行。积实于中,发理于外,则于恻隐、于羞恶,内无不实,而外自无不应。凡物之生,心得此理而后有形,无理则无形。②
由上可见,许衡为学皆朱子之义理,其特点是强调践履工夫,使心性真正体现于天理之中,达到完善的人格境界。所以,把许衡之学视为求心之学。
五 由郝经到王夫之
上述由黄榦开其端的朱子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在元代北方朱子学学派中都可以找到代表人物。元明北方朱子学派没有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思想基础,但是,北方朱子学派呈现出了朱子学中气论实学的思想倾向。当时北方朱子学派中的郝经、刘因等代表了这种倾向。
郝经(1223—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著《续后汉书》、《陵川集》等。早年“搜览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③,学问极为渊博。元初,郝经受学姚枢。先是姚枢在燕京(北京)建太极书院,请朱子学家赵复讲学于其中,姚枢得赵复所传;后来姚枢隐居苏门,许衡、郝经、刘因得其书而承其学。但是,郝经与赵复、姚枢的思想有所不同。例如,郝经把太极(理)看作“浑沦”,即看作是物。他在《太极图说》中认为,无极而太极者,包本末,贯隐显,一体用,极始终。他说:
浑沦圆转,而无上下内外,开廓布置而皆上下内外,含弘天地人物,包括鬼神造化,混然一大活物,旁行而不流,无所不往而未尝去,居其所而变动无穷焉。圣人无以指名,故名之曰太极。④
郝经这种对太极(理)的界说,就中孕育着气论实学的因素。今人龚道运说:
郝经言道或太极之为生生之理,乃就阴阳之气之生生之所以然而言。此理贯而主乎此生生之气流行中而为其理者,故曰理入于气。抑此理之入乎气,亦可谓其承先之气,以其后之气,而行乎气之中。所谓理不离气,即自理不离其所承之气与所起之气,如位于己化已息之气与方生方起之气之间而言耳。①
郝经对理气关系的认识含有二元论的倾向。
刘因(1249—1293年),字梦吉,号静修,河北徐水(今保定)人。征诏为右赞善大夫,未几即辞归里,具有民族意识。有《静修集》行于世。
刘因在本体论上提出太虚元气说。他在《匏瓜亭》中说:
匏瓜陨自天,中涵太虚气。造物全其真,世人若其味。虽得尽天年,惜坐无用器。伊谁窍混沌,大朴分为二。②
显然,这是张载的太虚即气的思想。他认为,事物都是由太虚之气所产生,并提出天地万物产生之前气为混沌之状。他虽未肯定气是本原,但其气论实学思想倾向比上述郝经更为明显。
刘因等人朱子学气论实学思想的倾向,到了明代前期的薛瑄(1389—1464年,号敬轩,山西河津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从朱熹的笃行出发,强调气的重要性。薛瑄在论到朱熹的《四书集注》时说:
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之心殆无余蕴。学者当以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③薛瑄明确指出,他的代表作是按照张载的《正蒙》方式写的。他对朱熹的
理气论进行了改造,把气提到和理同样的地位,具有了初步的气论实学思想。但是,他们仍未超出朱熹的思想体系。薛瑄的思想对明代中期的罗钦顺、王廷相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通过对王学的批判和朱学的改造,继承张载的思想传统,把朱熹思想体系中的气学倾向发展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并从朱子学中分化出来。
罗钦顺(1465—1574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的气论实学思想,是明末清初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居衡山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①《朱学论丛》,台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②《静修集》卷六。③《四书录》卷二。
南衡阳人)对理学进行总评判的先声。王夫之是中国气论实学的集大成者。因为王夫之的思想作为朱熹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所讨论的基本范畴大致相同而内涵相反。王夫之的思想是朱熹思想体系漫长衍变和分化过程的最后结局。在王夫之之后,朱子学尽管仍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占重要地位,但是就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史来说,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气论实学思想已占有主导地位。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差不多又经过了三四十年,至元仁宗时(1312—1320年)就遍及全国。朱子学在福建的传衍和分化是个雏型,全国朱子学的派别和衍变是其在福建传衍和分化的扩大和发展。
由于朱熹综罗百代、集诸儒学之大成,非某个后继者所能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集大成,体系庞大,因而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对全国朱子学衍变的内在倾向,今人蒙培元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说:
简单地说,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矛盾。一个是理本体论同气化学说的矛盾,即唯心主义体系同唯物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一是理本体论同心本体论的矛盾,即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矛盾。此外,方法论和体系之间也有矛盾,最明显的是他的“格物穷理”说同“明明德”的根本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说,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同时又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这些矛盾是朱熹本人无法解决的。这就决定了朱熹哲学必然要分化。①
蒙培元对南宋末、元、明时代哪个朱子学家属于哪一哲学倾向,以及按唯物论和唯心论来划分中国古代哲学,还可以深入讨论,但是其这里的概括说明是很确切的,为研究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提供了指导性线索。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成为整个国家的正宗思想后,它根据理论自身的规律和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进行衍化。基于上述黄榦是朱子学由闽至全国的桥梁,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是在黄榦思想中开其端的。黄榦固守师说,只是在体之用上有所阐发。南宋末黄震曰:
晦庵论近思先太极说;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后能不愠,非不愠然后为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余;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易肆,故当谨耳。②
这里黄震叙述了黄榦思想与朱熹思想之不同,在黄榦思想中就埋下朱子学日后分化的根苗。体用关系体现为理一分殊,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的先验原则与现实人的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他引用孟子的四端说来说明道德的体用关系。黄榦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③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道德之体,有此体必然表现为与此体相联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道德之实践(用);抽象的天理世俗化,为人人得以遵循的道德准则,通过格物明理实现人内心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善;实际上,格物明理和明内心的道德之善是对立的。这是黄榦哲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
朱子学于元初盛行于全国之后,其衍化大致有三派:一是以赵复、许衡为代表的北方一派,一是以何基、许谦为代表的浙江金华北山学派,一是以饶鲁、吴澄为代表的江西广汉双峰学派。这三派大致按上述黄榦思想中的三种倾向进行衍变和分化,走向不同的学术道路,因而使朱子学原来理论上的裂痕走向解体的道路。
朱熹思想的解体和分化促使朱子学的演进,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本身的发展必然会解体和分化,同时其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其后一二个后继者所能继承和发展的。南宋至明朝末年,朱熹思想向两个方向分化和发展: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黄震、文天祥,元、明朝的刘因、薛瑄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罗钦顺、王廷相等为代表的气学。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论争,就是这两种方向发展的结果。最后出现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陈献章、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和以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学,都是从朱熹思想体系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发展过程,由内圣成德而外王事功,中国社会由古代孕育着近代。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孔子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朱熹,其内圣成德达到了成熟和综合点,其后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即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的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时期,西方社会也正开始近代化,出现“文艺复兴”。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是与西方同步的,或者说早于西方。牟宗三在讲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时,深刻指出:
三大儒的意识是顺着宋明数百年内圣学之成熟而要求开外王事功的意识。这一意识正合乎西方17、18、19世纪300年开近代文明的方向。时间即相合,方向也相同。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其中的历史运会当该切实正视。须知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民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所以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王船山有《黄书》之作。满清200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向僵滞,整个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两三百年之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
一下,相去遂不可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①
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就是他顺应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理想往前发展,推翻清王朝,开出一个外王事功的大时代,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
二 黄震 金华四先生
南宋末年浙江朱子学有辅广系黄震、黄榦系金华四先生等。对此,《宋元学案》有所综合评述。其曰:
四明之传,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平生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即江西)诸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子(金华四先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黄震)折衷诸儒,即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②
浙江的朱子学,对朱熹的思想,黄震有较大的修正,金华四先生则是墨守朱熹家法,因此分开论述。
黄震(约1213—1280年),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文洁先生,浙江慈溪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历官吴县、华亭县、长洲县尉,史馆校阅,广协、绍兴通判,抚州知府,江西、浙东提举常平等。宋亡后,“日惟一食,仰天长恨,祈速死”,最终“饿于宝幢而卒”③。其著作有《黄氏日抄》(即《慈湖黄氏日钞分类》)、《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戊辰修史传》、《仰天遗草》等。
黄震对天理的论述,基本上与朱熹同。而在讲到理与道的关系时却对朱熹有所修正。如黄震说: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④
黄震强调,道不在天地人事之外。这跟朱熹的讲法是有所不同的。朱熹认为,作为道德伦理准则的理,是人道;作为万物本原的理,是天道,而天之道则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外的。这就对朱熹之“理在事先”的观点有所修正。由此,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之“道不必贯而本一”的观点。他说:
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①
他认为,朱熹后学“舍孝弟忠信不讲而独讲一贯”②的倾向,是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论的断章取义,是道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观点。
黄震认为,朱熹等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是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不一致的。他说:
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虚空中别可言性,则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说也。③
他认为,“性相近”包括了气质和天地之性,而不是朱熹等所说的只是“气质之性”的观点。朱熹认为,“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哪里有三品来?”④在朱熹看来,韩愈的性三品是指气质之性,而天地之性没有三品的问题。对此,黄震说:
性有三品之说,正从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来,于理无毫发之背。至伊、洛添气质之说,又较精微。盖风气日开,议论日精,得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对说,而后孟子专指性善之说举以属之天地之性,其说方使无偏。此于孟子之说有功而于孔子之说无伤。实则孔子言性,包举大体;孟子之说,特指本源而言。性无出于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说本于上智、下愚之说,而后进喜闻伊、洛近日之说,或至攻诋昌黎耶?⑤
在黄震看来,韩愈之性三品说,同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二程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一致的,而朱熹却说性三品不包括天地之性,不是相矛盾吗?
在知行问题上,黄震强调躬行。他说:
自晦翁之学盛行,而义理之说大明。天下虽翕然而向方,流弊亦随之而渐生。盖论说之求多,恐躬行之或缺,苟曾用力于躬行,何暇往事乎口说?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见言晦翁之学者几人,往往不知其躬行。
……世所谓《中庸》、《大学》者,身未必行,惟见笔舍华靡。①
在这里,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笔舌华靡”的空谈义理、不知躬行的行为。
由上可见,黄震对朱熹并不盲目信从,而是有所立异的。因此,黄震在朱子学发展史上,不仅有继承,也是有所发展的,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的。
金华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9年,字子恭,学者称北山先生)及其弟子王柏(1192—1274年,字会之,号鲁斋)、柏弟子金履祥(1232—1303年,又名祥、开祥,字吉父,号次农,因家居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祥弟子许谦(1270—1337年,字益子,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生),是朱子学浙江金华之主要传人,被朝廷列为朱子学的正宗。《宋元学案》专立《北山四先生学案》,详述其朱子学思想。
北山学派的何基等人,严守朱子学门户,强调读书传览为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何基语录》说:
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②
他们抱住朱熹的《四书集注》寸步不离,确守师说。清初黄宗羲说: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③
北山学派由确守师说,只注重读书穷理,继承和发挥朱子学训释儒家经典的传统,虽然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但是由于走向章句训诂的道路,使朱子学变成烦琐哲学,没有开辟出新的境界。特别是其中的王柏,他的《诗疑》、《书疑》,原是对朱熹《诗集传》的继承,却走向极端,偏离了儒学正统,受到后世朱子学者的批评。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更觉朱子学正统派的空言无实。清代前期,虽有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及其他理学名臣大倡朱子学,使其一时兴盛;清末有朱次琦(1807—1881年,广东南海人)、杨昌济(1871—1920年,湖南长沙人)、辜鸿铭(1897—1928年,福建厦门人)等人提出重整朱子学,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和朱次琦同时的文廷式(光绪帝珍妃的老师)曾谓朱熹“训门人语多痛切,数十世后如见其人”。①朱次琦提出“朱子百世之师”,朱子“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之力也”。②
杨昌济曾先后留学日、英、德等国9年。他在五四运动前期的中西哲学论争中,采取调和折衷态度,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实际上他立足于程朱理学。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讲授伦理学。他说:
所谓不限于西洋之理论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③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学应为体(正宗),特别是朱熹的著作应尊为儒家思想的典范。他为讲授伦理学而编写的《论语类钞》共38条,其中有朱熹语录释《论语》者达22条,占三分之二。如第22条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首先就引用了朱熹一大段语录,即: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道,譬则天地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这就是说,太极(道之体、一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万殊各得其所”就是太极(道之体、一本)的体现或作用。这段是朱熹“理一分殊”的典型表述,杨昌济解释说:
宇宙为一全体(即一本、太极),宇宙间所有一切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同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④
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熹下列一段话,其曰:“吾子之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有见者也。”⑤杨昌济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来论证如何积累知识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此外,杨昌济还通过研究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吸取和发扬朱子学。
由上可见,直到清末和民初,朱子学正统派在一些学者中和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就全国来说,朱子学终未能真正恢复其元气,在理论上未有多大进展,而且趋于终结,这就是由自我窒息而后日趋沉寂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三 双峰学派 饶鲁 吴澄
《宋元学案》谓,黄榦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江右即江西,其代表者为双峰学派之饶鲁、吴澄等。“双峰(饶鲁)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吴澄)”,其学术活动时期为宋末元初。
饶鲁(生卒不详),字伯舆、仲元,号双峰,江西余干人。据载,“庚申(1206年),诏饶州布衣饶鲁,不事科举,一意经学,补迪功郎、饶州教授”①。其著作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学庸纂述》、《西铭录》、《近思录注》等。
对于饶鲁之朱子学,有谓不拘于章句,一如朱子之于二程,“共派而分流,异出而同归”②。可知饶鲁不是墨守朱熹门户的。饶鲁认为,理气不相离,气以理为主,理以气为辅,气为理之衬贴。他说:
“浩然之气”,全靠道义在这里面做骨子。无这道义,气便软弱。盖缘有是理而后有是气,理是气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气。以有太极在底面做主,所以它底凭地浩然。③
这里全是朱熹之理气关系的说法。他又说:
“发育万物”,以道之功用而言,万物发生长育于阴阳五行之气,道即阴阳五行之理。是气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峻极于天”,以道之体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无过于天者。天之所以为天,虽不过阴阳五行浑沦磅礴之气。而有是气,必具是理。是气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全体大用,极于至大而无外有如此者。④
此是说理气相即不二。这里还讲了道的体用关系,即其所谓“道之体段”、“道之功用”。道是弥沦天地的,是主宰天地之气的。
饶鲁继而认为人道的极则是天理。他从性为人所禀之天理出发,发挥了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观点。他在疏解张载的《西铭》时说:
《西铭》一书,规模宏大而条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尽。然其大旨,不过中分为两节。前一节明人为天地之子;后一节言人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何谓人为天地之子?盖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是性,犹子受父母之气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举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为大父母。故以人而观天地,常漠然与己如不相关。人与天地既漠然如不相关,则其所存所发宜乎?①
由此,他得出:“言天以至健而始万物,则父之道也;地以至顺而成万物,则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间,禀天地之气以为形,而怀天地之理以为性,岂非学之道乎?”他把天人地释为父子母,是有新意的。在他看来,人之所以生,是天地之气以为形,天地之理以为性,故天地与人,犹如父母之与子。因而天地与我一体,即他所说的“物吾党与”。
饶鲁进一步指出,人本身具有善端,人都有自新的欲望,即所谓民之心本自好善而恶恶,熟不欲自新?因为,仁即心,心之存即是识仁而成仁心。他说:
诚意、正心、修身不是三事。颜子问仁,夫子告以非礼勿视、听、言、动,紧要在四个“勿”字上。仁属心,视、听、言、动属身,“勿”与“不勿”属意。若能“勿”时,则身之视、听、言、动便合礼,而心之仁则存,以此见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在意之诚不诚。所以,《中庸》、《孟子》只说“诚身”便贯了。②
这里的说法与朱熹之心统性情说不同。在朱熹那里,人禀受天道为性,故性具天理;心不等于性,故心不等于天理。而饶鲁却认为,心即仁,故仁同于天理。这同陆九渊的“心即理”相似。在饶鲁看来,心之能存与否,全在身之视、听、言、动,而视、听、言、动又在于“意之诚不诚”,故“诚”就将诚意、正心、修身三事贯串起来。诚即无妄、不自欺意。
饶鲁提出以敬为诚的存养省察工夫。由此他喜欢静坐。他说:静坐时,须心主于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言于敬,亦静坐不得。心是个活的物,若无所用,则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圣人说“难矣哉”,意甚该涵。③
他认为,通过静坐,就能收敛“野马”之心,使本来的善性得以充分发挥。这与禅家的“修心”、“守心”相类似。
上面讲的居敬,只是饶鲁为学之一。他认为,为学四方,即立志、居敬、穷理、反省。①他的为学之方由“立志”始,然后居敬、穷理,而终止于反身。这是内外结合的方法,是符合理学家的“涵养须用敬,进德在致知”的原则的。
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历官元朝之国子司业、国史院编修、制诰、集贤殿直学士等。著有《五经纂言》、《皇极经世续书》、《道统图》等,清人辑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吴文正公外集》。
在元代,吴澄与许衡为名儒。许是北方人,于元初“粗迹”朱子学。吴是南方人,直承朱子学大家,是“正学真传”。因此,元代朱子学有“南吴北许”之称。
吴澄以朱熹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其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享,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②
这段话值得注意者,一是韩愈论道始于尧舜,而吴澄则据董仲舒意谓道始于天,此说出了宋明儒的本体论。二是其用《周易》之元、亨、利、贞把历史顺序规定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段,每一段又分元、亨、利、贞。三是他把朱熹说成是“利”,而不是终结“贞”,一方面他不把朱熹看成为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似乎把自己看成是“贞”的地位,以跻身宋儒诸子的继承者之列。所以,上引《元史》本传接着谓其“以斯文自任如此”。
吴澄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是对朱熹的经学有较大的补充和发挥。他的《五经纂言》,实际上完成了朱熹的未竟之业。朱熹曾与吕祖谦等商议编次“三礼”,而终老未及为。朱熹曾说:
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附于本经之下。③
但是,朱熹只留下草创本《仪礼经传通解》。后来,黄榦等也曾治礼,没有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吴澄从中年到晚年,几乎倾一生精力,完成《五经纂言》,实现了朱熹的未竟之业。他在《诸经序说》中说:
朱子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谓三礼体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书,于此至惓惓也。《(仪礼)经传通解》,乃其编类草稿,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无禄弗逮,遂为万世缺典,每伏读而为之惋惜。然三百三千,不存盖十之八九矣,朱子补其遗缺,则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而各疏其下。夫以《易》、《诗》、《书》、《春秋》之四经,既幸而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而乱,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经者哉?徒知尊信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亦岂朱子所望于后学者哉!呜呼!由朱子而来,至于今将百年,以予之不肖,犹幸得私淑其书,用其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经,重加伦纪。①
吴澄“辄因”朱熹筹画之意,以《仪礼》十七篇为经,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例,将《礼记》(大小戴记和郑注)分类编次,纂成《仪礼逸经》八篇。就是把《礼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礼记》中的《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此二篇并与《小戴礼记》相参校),又把郑玄《三礼注》中的《中霤》、《禘于太庙》、《五居明堂》,共成二卷八篇。另外,又将大、小戴记中的《冠仪》、《昏仪》等八篇,和《礼记》中的《乡射仪》、《大射仪》二篇,辑成《仪礼传》十篇。这样,吴澄把汉以来流传的《礼记》(大小戴记,以至郑玄《三礼注》等)肢解,核订异同,重新编纂,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这不仅完成了朱熹生前的夙愿,而且经过这样的整理,使流传千百年来“难读”的一部《仪礼》,得见崖略,诚是经学史上的一大贡献。②
吴澄治五经不守朱子学门户。如其《易纂言》,自称“用功至久,皆自得于心,有功于世为最大”③。在这部《易》学中,就有和会朱陆的地方。
在本体论上,吴澄认为太极即道。他说:
所谓极也,道也者,无形无象,无可执著。虽称曰极,而无所谓极也;虽无所谓极,而实为天地万物之极。④
“太极”所以能起主宰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含有动静之理,它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如人之乘马,人随马的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它“常常如此,始终一般,无增无减,无分无合”。所以太极尽管包含动静之理,而主宰世界的生成、变化,它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⑤
吴澄进一步把太极说成是理、天理,而把理、天理释为天地万物之所以然者。他说:
气之循序而运行者为四时,气之往来屈伸而生成万物者为鬼神,命各虽殊,其实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①
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②
太极与理的关系,就宇宙本原来说是太极,就宇宙化生二气五行以至万物的过程来说是理。这样,理就是万物所以形成的理,而太极就是理的全体。万物中具体的理与本原的太极是万理一原的关系。所以,整个世界由它的本原到化生万事万物的现象界,都是由于太极和理的一系列的作用。
吴澄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太极,是人道的极则,也就是天理。那么,人是如何去认识它呢?是从吾心去体认,还是从万物去参究呢?是立之于本心,还是格之于外物呢?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在朱、陆之后,吴澄则是“和会”两家之说,形成了他自己的认识方法。
在吴澄看来,湛然纯善的天地之性附于人的时候,随着各人气质的清浊不同,而有善恶之分,因而有了气质之性。但是,即使是那些因气浊而恶的人,其天地之性亦在“其中”,只是“拘碍沦染”于浊气而已。悬之于高远的天地之性,不仅予性善的人,而且也予性恶的人。这就给具有气质之性的那些恶与不善的人找到了通向天地之性的可能和信心。他说:
人之明德,即天所以与我之明命也,自天所赋于人而言而谓之命,自人所得于天而言则谓之德,其实则一而已。然常人为气禀物欲之所昏,而不察乎此,是以昏昧蔽塞不能自明,至于梏其性而忘之也。故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所以与我之明德而有察焉,则必然因其所发,而致其学问思辨推究之功,又能因其所明,而致其存养省察推行之实,则吾之明德,亦得以充其本体之全,以无气质物欲之累,而能明其大德与尧无异矣。③
在吴澄看来,“明其德”不是由身外格物以明理,而是求之于己,自明其心。故他自己概括其方法为“自新”。可见,他主张自省自思而达到自觉,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相违背的,而与心学派明心穷理却是接近的。
吴澄认为,自省自思而自觉即是诚与敬。他说:“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敬为之主。……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①他又说:
凡所应接,皆当主于一心,主于一,则此心有主,而闇室屋漏之处自无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积久,无一事而不主一,则应接之处,心专无二。能如此,则事物未接之时把捉得住心,能无适矣。②黄直卿(榦)谓敬字之义,近于畏者,最切于己。凡一念之发,一事之动,必思之曰:此天理抑与人欲也?苟人欲而非天理,则不敢为,惴惴儆慎,无或有慢忽之心,其为之敬也。③
吴澄所谓敬,就是在“一念之发,一事之动”时皆以天理来约束思维;凡一念一事,都要想一想这是天理还是人欲。他完全排除了外物之诱惑。先秦思孟学派提出“诚者天之道”,是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为人道的极则。人能“思诚”即可达于“天之道”的诚。④吴澄所谓“思诚”,就是思我心中固有的诚。他说:
人之初生,已知爱其亲,此实心自幼而有者,所谓诚也。爱亲,仁也。充之而为义、为礼、为智,皆诚也,而仁之实足以该之。然幼而有是实心,长而不能行,何也?夫诚也者,与生俱生,无时不然也,其弗能有者,弗思焉尔。五官之主曰思……所以复其真实固有之诚也。⑤
他把诚说成是与生俱来,自幼而有。诚的内容就是爱其亲,也就是仁,它充实显露之后就是义、礼、智。在吴澄看来,它是具体的,并非是悬之于心外的一种神秘境界。而要保持自幼而有的诚,就是思。所谓思,就是去其恶欲和复性的冥悟过程。这样,就是去掉“人欲”,以达到所谓真实“不妄”、“不自欺”。由此进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双峰学派是沿着黄榦的明内心的道德之善走过来的,反对单纯读书明理,强调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双峰语录》有说:
若但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言语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⑥
在饶鲁看来,道理须是涵养,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来?可见,双峰学派是沿着黄榦的明内心道德之善的思路上往前衍变的,其心学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吴澄的心学思想更加明显。韩国李朝李退溪在讲到吴澄时曰:
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公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①
吴澄对朱熹和陆九渊两家都很推崇,他在《与许左丞书》中认为,“朱、陆二氏之为教一也”②。全祖望谓吴澄“固朱学”、“兼主陆学”。③
到了明代,先有吴与弼(1391—1469年,号康斋,江西崇仁人)提出“敬义夹持,明诚两进”④,发明代心学之端;再经陈献章(1428—1500年,号白沙,广东新会白沙里人)而至王阳明,把朱子学衍变为心学。王阳明是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者,即心学从朱子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并与朱子学相对立。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阳明学是理学由烦琐变为简易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社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启蒙思想的出现而要求冲破朱子学一统天下的结果。阳明学差不多盛行了一百年,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明末清初,正统派朱子学抬头和王夫之等人战斗的气论实学的出现,王学即告终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 北方学派 许衡
元初朱子学传入北方后,很快就形成为以赵复、许衡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李退溪在讲到赵复时说:
姚公(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公(按指赵复)传其学。由是许公衡、郝公
经、刘公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公始。⑤当时属于北方朱子学派的还有窦默等人。全祖望谓“河北之学传至江汉(赵复)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⑥
这里主要论述许衡。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等。他为元朝统治者策划“立国规模”,即运用朱子学治国,其朱子学思想被称为道统正脉。他在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期间,向蒙古弟子传播朱子学,使当时学人皆诵习程朱之学,有“以夏变夷”之功。卒赐荣禄大夫,谥文正。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诏祀孔庙。
许衡的著作有《大学要略》、《大学直讲》、《稽古千文》等,后辑为《鲁斋遗书》。近年台湾中文出版社据日本宪文九年(1669年)刻本影印出版《鲁斋全书》。
许衡为学,一以朱熹之言为归。实际上,他主要发扬朱熹的心学思想,把朱子学变成以“尊德性”为主的践履之学。他认为,朱熹的著述太多,重点不突出。“许文正公表彰朱子之书,天下乐为简易之说者。”①他沿着“简易”的方向,在朱熹的心说上兜圈子,为后来的心学一派开辟出道路。
许衡认为,人皆“禀天命之性为明德之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与尧舜神明为一”,但是在践履上一般人与尧舜圣人就不同了。他说:
众人多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能长存:或发于一件善念,便有被气禀物欲之私昏蔽了,故临事时对人旋安排把捉;未临事之前,与无人独处,却便放肆为恶。②
此谓善念到临事时就可以检验出来了。他特别强调慎独,在“与无人独处”时亦不能放肆为恶,必须谨慎而不敢疏忽才行。所以,他十分强调《大学》所讲的慎独工夫。他说:
幽暗之中,细微之事,人以为可忽者,殊不知其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更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所以,君子之心既常戒惧,而于此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虽人所不知,而独知之地,尤必极其谨慎而不敢忽。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③
他强调,“独是自家心里独知处;好善恶恶,实与不实,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
心里独自知道这等去处。君子必要谨慎,以审其几微。”①
在许衡看来,意念未发时之戒慎恐惧,能存天理之本然,其工夫是存养;由存养至慎独,能谨慎己所独知,从而遏人欲于将萌以至方萌。其工夫是省察。他说:
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者,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是气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长。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执之不使变迁。如此,则应物无少差谬。此所谓致知也,省察之事也。②
如能时时内自省察,无有不善,就能无愧于心。慎独是省察的前提和基础。气禀物欲之拘蔽于人既不容忽,人的尽心工夫就会连续不断,性中本然之理(善)即能永存。
许衡进一步指出,持敬则能身心收敛,身心常存。他说:为学之初,先要持敬。敬则身心收敛,气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浊者不得长;美者愈美,而恶者不得行。静而敬,常念天地鬼神临之,不敢少忽;动而敬,自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日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礼记》一书近千万言,最后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从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恶,皆从不敬上生。……这一件先能着力,然后可以论学。③
他所讲的这些,就是朱熹所讲的收摄涵养此心,敬之以恒,敬之忽失,就是常惺惺法,提心吊胆,便心不失其正。
在许衡看来,慎独为省察,持敬为涵养。在省察与涵养间他又加了个格物致知,这是许衡心学之独到处。他明确提出,“知其性是格物”④。此性是心体之性。知此心体之性,非格物不可。他说: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此解说个“穷”字;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此说个“理”字。所以然者是本然也;所当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当然者是义也。每一事、每一物,须有所以然与所当然。⑤
理固然为心体所内具,通过格物穷旭,如能自显心体所本具之理,此理即人之性。由知物之所当然,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物之所以然是其所当然之理由,此理由人于当初所未知。通过格物而致知。
由上可知许衡之心学体系了。他的结论是心与理为一。据记载:
问: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如何?先生曰:便是一以贯之。再问:理出于天,天出于理?先生曰: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①
由此,他便得出人、物后之于理的结论。他说:
有是理而后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诚有是理,而后成木之一物。表里粗细无不到,如成果实相似,如水之流满出东西南北,皆可体力而用行。积实于中,发理于外,则于恻隐、于羞恶,内无不实,而外自无不应。凡物之生,心得此理而后有形,无理则无形。②
由上可见,许衡为学皆朱子之义理,其特点是强调践履工夫,使心性真正体现于天理之中,达到完善的人格境界。所以,把许衡之学视为求心之学。
五 由郝经到王夫之
上述由黄榦开其端的朱子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在元代北方朱子学学派中都可以找到代表人物。元明北方朱子学派没有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思想基础,但是,北方朱子学派呈现出了朱子学中气论实学的思想倾向。当时北方朱子学派中的郝经、刘因等代表了这种倾向。
郝经(1223—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著《续后汉书》、《陵川集》等。早年“搜览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③,学问极为渊博。元初,郝经受学姚枢。先是姚枢在燕京(北京)建太极书院,请朱子学家赵复讲学于其中,姚枢得赵复所传;后来姚枢隐居苏门,许衡、郝经、刘因得其书而承其学。但是,郝经与赵复、姚枢的思想有所不同。例如,郝经把太极(理)看作“浑沦”,即看作是物。他在《太极图说》中认为,无极而太极者,包本末,贯隐显,一体用,极始终。他说:
浑沦圆转,而无上下内外,开廓布置而皆上下内外,含弘天地人物,包括鬼神造化,混然一大活物,旁行而不流,无所不往而未尝去,居其所而变动无穷焉。圣人无以指名,故名之曰太极。④
郝经这种对太极(理)的界说,就中孕育着气论实学的因素。今人龚道运说:
郝经言道或太极之为生生之理,乃就阴阳之气之生生之所以然而言。此理贯而主乎此生生之气流行中而为其理者,故曰理入于气。抑此理之入乎气,亦可谓其承先之气,以其后之气,而行乎气之中。所谓理不离气,即自理不离其所承之气与所起之气,如位于己化已息之气与方生方起之气之间而言耳。①
郝经对理气关系的认识含有二元论的倾向。
刘因(1249—1293年),字梦吉,号静修,河北徐水(今保定)人。征诏为右赞善大夫,未几即辞归里,具有民族意识。有《静修集》行于世。
刘因在本体论上提出太虚元气说。他在《匏瓜亭》中说:
匏瓜陨自天,中涵太虚气。造物全其真,世人若其味。虽得尽天年,惜坐无用器。伊谁窍混沌,大朴分为二。②
显然,这是张载的太虚即气的思想。他认为,事物都是由太虚之气所产生,并提出天地万物产生之前气为混沌之状。他虽未肯定气是本原,但其气论实学思想倾向比上述郝经更为明显。
刘因等人朱子学气论实学思想的倾向,到了明代前期的薛瑄(1389—1464年,号敬轩,山西河津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从朱熹的笃行出发,强调气的重要性。薛瑄在论到朱熹的《四书集注》时说:
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之心殆无余蕴。学者当以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③薛瑄明确指出,他的代表作是按照张载的《正蒙》方式写的。他对朱熹的
理气论进行了改造,把气提到和理同样的地位,具有了初步的气论实学思想。但是,他们仍未超出朱熹的思想体系。薛瑄的思想对明代中期的罗钦顺、王廷相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通过对王学的批判和朱学的改造,继承张载的思想传统,把朱熹思想体系中的气学倾向发展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并从朱子学中分化出来。
罗钦顺(1465—1574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的气论实学思想,是明末清初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居衡山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①《朱学论丛》,台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②《静修集》卷六。③《四书录》卷二。
南衡阳人)对理学进行总评判的先声。王夫之是中国气论实学的集大成者。因为王夫之的思想作为朱熹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所讨论的基本范畴大致相同而内涵相反。王夫之的思想是朱熹思想体系漫长衍变和分化过程的最后结局。在王夫之之后,朱子学尽管仍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占重要地位,但是就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史来说,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气论实学思想已占有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