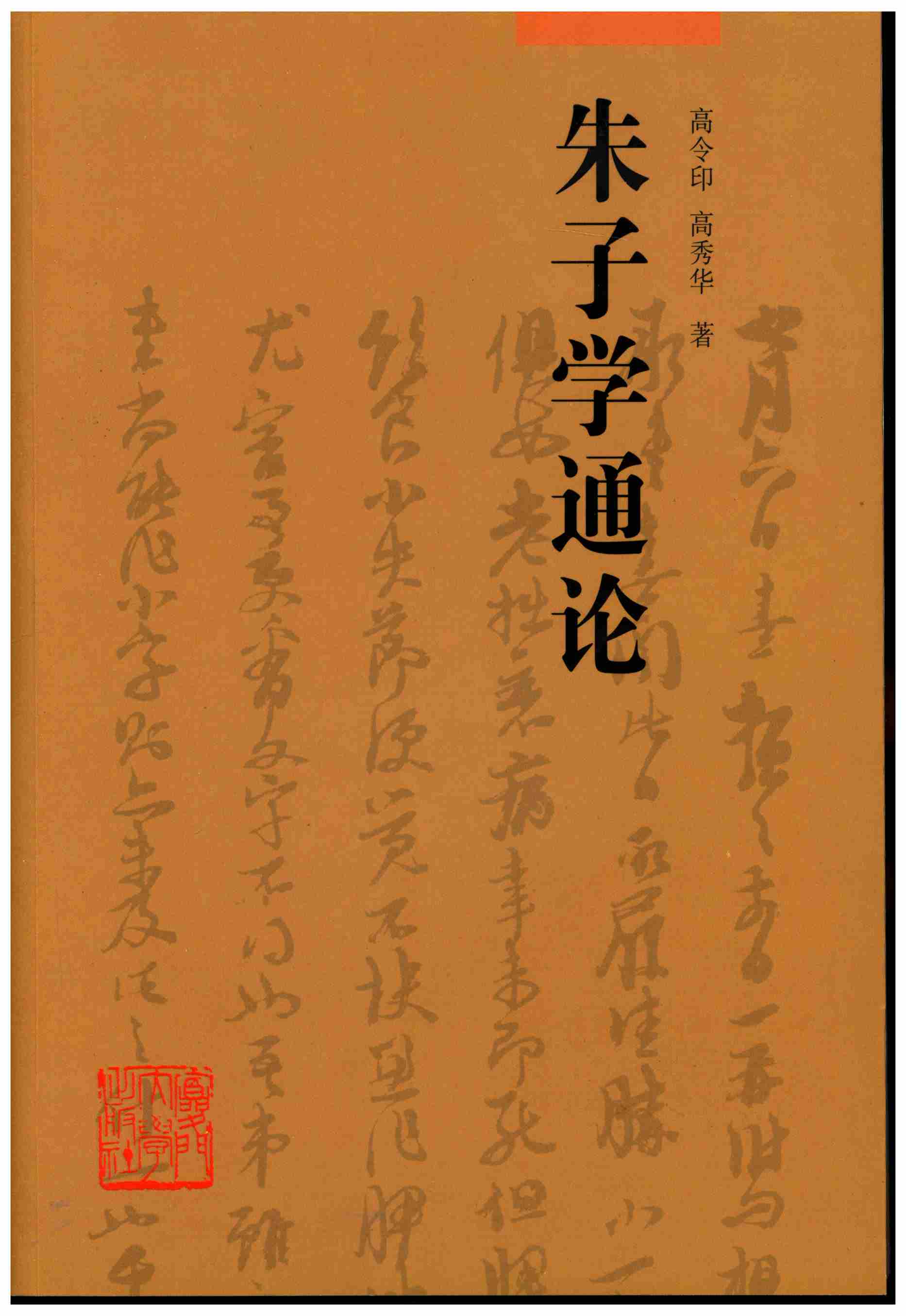内容
一 概述
清代自仁宗嘉庆(1796—1820年)以后,盛极而衰,进入后期。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约有一个半世纪。
清代中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活跃起来,但是仍然是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还是较为稳固的。到了道光年间,清王朝百孔千疮,国势江河日下。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支绌。官吏贪污成风,赋税日益加重,高利贷剥削极为猖狂。官僚、地主、豪富兼并土地更为严重,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农民反抗斗争更加频繁。整个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中国封建社会已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就在这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妄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宋元明以至清初历代王朝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到了清代中期,鉴于朝廷“文网”(文字狱)太密,一些学者不敢触及实际问题,导致所谓“乾嘉考据学”(汉学)盛行,压倒理学(宋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知古不知今的学风。这个学风得到朝廷的支持和提倡。清代中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是宋学和汉学占主导地位,是一片“万马齐喑”的沉寂气氛。鸦片战争后,严重的社会危机、民族灾难和人民群众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特别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西方自然科学和各种学说逐渐输入,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产生于西汉的今文经学,把《春秋公羊传》(今文经)的经义和当时的谶纬迷信相结合,牵强附会地任意解释经书的内容,为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当时的正统学派。今文经学又称为公羊学。清代今文经学派主要利用公羊学中的专制主义和改制思想,借题发挥,议论时政。康有为、梁启超等以今文经学为工具宣传变法维新主张。于是,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大兴。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学和旧学、西学和中学之争,实际上是今文经学和宋学(程朱理学)、汉学(古文经学)之争。当时属于程朱学派的方东树、唐鉴、倭仁、曾国藩、辜鸿铭等,都是旧学、中学中的主要人物。从整个清代后期的思想文化界来说,今文经学(公羊学)占据时代思潮的主流,程朱理学不振,但是由于出现倭仁、曾国藩等“理学名臣”,曾出现所谓“咸同(即咸丰同治年间)理学中兴”。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朱子学是为封建守旧派服务的。
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朱子学始终没有断绝。它顽强地存在着,并在社会上发挥重大作用。一般来说,在近代中国,辛亥革命前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仍然是朱子学;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民国,官方的统治思想在变化中,而程朱理学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朱子学仍然具有广泛的深刻的影响。
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的福建,朱子学内为新旧思想的论争亦十分激烈。一方面,以陈寿祺(闽侯人)、陈乔枞(闽侯人)、郭尚先(莆田人)、严复(闽侯人)、曾克耑(福州人)等为代表,治公羊学、西学,反对朱子学。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治西汉今文辑佚之学,以著名的福州鳌峰书院和浙江诂经精舍为据点,登台授徒,著书立说。他们著有《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定本》、《今文尚书遗说考》等,宣扬公羊学,有功于今文经学。郭尚先官至侍讲学士,治经世有为之学,学问渊博,其与林则徐为莫逆之交,议论时弊,要求改革国内政治,反对外国侵略;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哲学上反对天人感应论和鬼神说,提出物质决定意识。他著有《增默庵文集》8卷。严复是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学术和政治制度的学者,是西学、新学的主要人物。他宣扬达尔文“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观点,激发当时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并向清王朝提出变法维新的要求。他提出为学要有实和用,斥责朱子学、汉学为无实、无用之学,并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著有《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等。曾克耑接受严复的政治思想,反对程朱理学,著有《颂桔庐丛稿》、《曾氏家学》(是书于1961年在香港印行)等。
另一方面,以孟超然(闽侯人)、陈庚焕(长乐人)、刘存仁(闽县人)、林春溥(闽县人)、陈庆镛(晋江人)、郑星驷(福州人)、辜鸿铭(厦门同安人)等为代表,坚持程朱理学,反对西学、新学,成为守旧派、洋务派的理论代表。例如,郑星驷在学术上极力推崇孔孟程朱、著《崇孔辟邪录》,此外还治汉学,著《尚书一贯录》、《春秋传分图便览》等。其著作汇编为一百余万字的《郑星驷著述》(福建省图书馆有其手抄本)。林春溥授翰林院编修,后主讲于著名的福州鳌峰书院19年。林春溥著《春秋经传比事》、《四书拾遗》、《孔子世家补考》、《孔门师弟年表》、《孟子列纂补证》、《孟子后书补证》、《开辟传疑》、《古书拾遗》、《开卷偶得》等,汇辑为《竹柏山房丛书》。林春溥学术以宋学为主,兼治汉学,治经以性命义理和训诂考据并重,力图把宋学和汉学结合起来。他认为,朱熹学说虽集诸儒之大成,并未到顶点,后人又把朱熹学说发展了。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圣贤之言精微广大,无所不包,绎之有不尽之。”①因此,他认为朱子学必须创新才行。这是近代福建朱子学学者的一大特点。他提出“玄黄既判未有人而先有物”②的命题。林春溥又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人。人有血气性欲以相接则必争。故愚者常待命于智,而弱者常求庇于强,其智而强者因得结其辟而指挥之,如是者盖往往而聚,遂各据其方,各长其世,和相安,怒相并,大小分合又各就其胜己者而听命焉,时则有大国小国而莫统于一。③尽管林春溥这里讲的国家的形成、社会矛盾的产生是不科学的,但他认为社会国家的出现不是天意,也不是圣人之意,而是自然发展的过程,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是有合理因素的。
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福建朱子学主要以孟超然、陈庚焕、刘存仁、陈庆镛为代表,下面加以论述。
二 孟超然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孟超然(1730—1797年),字朝举,号瓶庵,福建闽县(今福州闽侯)人。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郎中、广西典试、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川督学等。
孟超然从政廉正,遇士有礼。《清史稿》孟超然本传谓他督学四川时,以蜀民父子兄弟异居者众,曾作《厚俗论》以箴其失。后来蜀民为之立“去思碑”。其他任职,亦政绩显著。①孟超然的主导思想比较守旧。例如,说王安石变法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并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把王安石视同蔡京、秦桧等。
孟超然于42岁时以亲老辞官归隐,杜门不出,潜心读书。后来主讲于福州鳌峰书院。孟超然在书院终日与门人谈经论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陈寿祺就是其门人。孟超然在《晚闻录序》等著述中,极力推崇朱熹思想,如谓“《朱子全集》其精深博大,不可不涉猎竟也”。孟超然面对当时汉学盛行,极力维护宋学的学术地位。他认为,宋学在某些支节上可能有所失,但是它是“王制”,是先王之道,是正统的孔孟之道,而汉学(“新学”)非王制。这是宋学和汉学根本区别之所在。其实汉学也是宣扬王制,他们注释的经书都是儒家经典;宋学和汉学的区别不在王制,而是在治学方法之不同。孟超然是从门户之见出发的。
孟超然的著述有《孟氏八录》(包括《丧礼略》、《诚是录》、《焚香录》、《求复录》、《晚闻录》、《广爱录》、《家诚录》、《瓜棚避暑录》)、《使粤日记》、《使蜀日记》、《屏庵居士诗文钞》等,结辑为《亦园亭全集》、《屏庵先生遗书》等。
(二)世界观
孟超然基于其“阴阳自然之理”、“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②的世界观,提出“人之贵贱寿夭系于天(按指自然之理),贤愚系于人(按指事在人为),固无关预于葬”③,不是天命决定的。孟超然认为星命堪舆之说的要害在于不相信人的作为,经不住实践检验,一经实践其原形即毕露。孟超然所撰述的《诚是录》、《丧礼略》等数篇,就是为破除星命堪舆家的风水迷信思想的,是孟超然思想中较为有价值的部分。
孟超然在《书熊公子星命册后》中对人的所谓命运进行了新的解释。他反对星命学家的宿命论,提出“不伐其天机”的“安命之说”,即认为顺其天理自然即是命。在孟超然看来,客观事物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如做生意者每日“赢缩大略可睹”。所谓“不伐其天机”,就是不要违反天时地利,遵循其发展规律。
孟超然认为,朱熹是反对风水迷信的。他说:
福建江西之明地理者以为朱子笃信堪舆。不知韦斋公之葬始或未善,则不得不迁(按指朱熹改葬父墓)。而孝宗山陵用台史言,则明置之迫狭之所、水石沙砾之中,为人臣子于此诚有所不安者,岂笃信葬师之谓乎(按指朱熹上疏极言不宜专用台史之说)?《尧山堂外纪》载:朱子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得人善地者,索笔题云: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①
对于朱熹两次迁韦斋墓、上书言孝宗山陵问题以及《尧山堂外纪》记载等是否因朱熹笃信堪舆,可以具体分析。但是,在朱熹思想中,相信堪舆星命还是比较严重的,如为其妻刘氏和自己选择墓地等。这里,孟超然是从门户之见出发的。
孟超然带头破除迷信,破除陋俗。他在《诚是录》中说:“我家葬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迄无他故。吾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于丧家尤甚。”②孟超然又说:
(其父死)去俗惑,初终不设乐师醮,不延僧道哭灵舆,饭舍时不易吉服,死之者不以僧道报亡,七七不作佛事,不祭冥王,朔奠不改晦日不设酒,三年内不赴酒食之会,不贺人喜庆事,凡此者皆反俗所为。③
孟超然以父丧破时俗,其目的是使人们“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④孟超然的这种做法和这种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孟超然指出,破除风水迷信是为了加强伦理道德修养。他说:
濂浦林氏三世五尚书……子孙数传俱谨守名节,不附权贵,簪缨累代。谁曰不宜?若使如严分宜(嵩)父子揽权纳贿,江西杨廖蔡师如林,能使之不倾覆乎?呜呼!观此亦可以悟矣。①
因此,孟超然提出只要一切举动“合乎理”就可以了。孟超然对“早晚于祖宗神明前再拜焚香”也做了说明,认为是“收摄心之法”,“心境一收摄,觉吾身无不当敬之事”。②
(三)内省体验的认识论
孟超然认为,众理先天地具于人的心中。“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之理,便无可贵。”心中所具之理,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本性。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是者为失其本心。庄周之非尧舜犹为寓言,嵇康之薄汤武亦有微指。其曰:“李贽之讥濂洛、毛奇龄之薄程朱,皆可谓之失其本心者也。”③因此,在孟超然看来,所谓认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存心。就是使心不要失散。孟超然说:“圣贤之学惟以存心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者澄然莹澈,广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视听言动一循乎理,好恶用舍各中乎节。”④又说:
暇时速须敛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义理。事物之来,随事省察,务令动静有节,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则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众理易明矣。此外别无着力处。⑤
这就是说,人之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道德本性,因有外界“物欲”所诱惑,有放逸、散失的可能,必须存心、守心。二是收放心。孟超然用《易经》复卦解释“收放心”,提出“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⑥等,以说明把失、放逸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心寻找回来。
对于如何达到存心和收放心的目的,孟超然提出主敬致知穷理。他认为,主敬致知穷理的过程就是存心和收放心的过程。孟超然说: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旧习之非,将日改月化于冥冥之中矣。(《晚闻录》)主敬致知,谨之于细微杂乱之域,而养之于虚间静说之中。⑦
孟超然认为,主敬为存心之要,致知为收放心(进学)之功,二者交发使用,则天理于心益固。在孟超然看来,这种主敬致知穷理的过程,是细微虚静,潜移默化的过程。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中反复说明,认识要接触实际。他提出“体贴人情即是体认天理”、“境遇中千头万绪皆是磨炼德性之资”。认识要学习和思考,主张“学须博乃可精”。孟超然曾提出为学四戒。其曰:“专守一家言者,隘也;泛涉而无归宿者,滥也;出言不知拣择者,秽也;务为夸大者,妄也。去此四病乃可以言诗言文。”①孟超然所概括的隘、滥、秽、妄四字学戒,确为至言,值得借鉴。孟超然提出静思的认识论。他说:
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②
认识要无偏见。他又说:“学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达,方于致知穷理有得力处。”③“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达”,就是思想上没有偏见,认识事物时没有成见,不带老框框。
(四)道德修养论
孟超然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是治心,治心之要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孟超然说:“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是为学之要。所以修身立命者全在此。近分为四门备载先儒之语,时时观览可以治心。”④“学治心之法,以惩忿窒欲为事,或冀持之,久久可以究养。”⑤“治心”、“究养”就是治本,“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以培壅本根,澄清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益光大而光明矣。”在孟超然看来,治本是对照圣贤教导,有过必改,就是变化气质。孟超然说:
吕成公(按指吕泾野)少卞急,一日诵《论语》,躬身厚而薄责于人。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朱子尝曰:学如伯恭(按指吕祖谦),方是能变化气质。⑥
孟超然这里所讲的转变卞急(躁急)性格,就是变化气质。人的本性(仁、义、礼、智)虽然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天理要和人的气质相结合,必须使气禀由浑浊变化的清明,愚不肖即为智贤。“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就是对己严,待人宽;自己严格履行伦理道德,以身作则,有利于影响别人。这即是道德修养的提高,气质的变化。
孟超然的这种通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是与其世界观和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孟超然以《周易》剥、复两卦和损益两卦所包含的“阴阳消长之机”加以论证。他认为,《易》言阴阳消长之机莫著于剥复(两卦)。《系辞》曰复以自知而不远之复,惟颜子能之;其次则困心衡为频复之厉最下迷复凶矣。他说:
吾不有自知者存耶?其往者或以为缘尘变灭然,吾不知之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象》曰山泽之象深下增高有损道焉,君子则以惩忿窒欲;风雷之象奋发疾速有益道焉,君子则以迁善改过矣。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其于复也或庶几乎!①
孟超然把这种“阴阳自然之理”用于道德修养上,就得出“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命题。“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反复下去,就可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进一步提出“纯乎天理”的道德境界。他又在《焚香录》中认为,这种境界是“仁体事而无不在,故道德统贯以仁”。就是说,“纯乎天理”的境界在道德行为上主要是表现为仁。在这里,孟超然还提出仁和孝的关系,认为仁中有孝,只是未发露出来。他说:
天下无性外之物,岂性外别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见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摄孝悌在其中,但未发出来,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与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无孝悌也,犹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济,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枣),非有彼而无此也。②
在这里,孟超然论证性与仁(包括孝悌)、义、礼、智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犹如气是从水、火、木、金、土和木是从梧、檟、樲、棘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一样。但是,孟超然所讲的仁、义、礼、智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无稽之谈。
孟超然极端鄙视那些言清行浊、言过其实的伪君子。例如,孟超然讲到湛甘泉时说:
湛甘泉讲学当时以为儒宗,又享眉寿。余最恨其晚年序《严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为天,文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矣。以八十岁老尚书献媚同年宰辅至于此极哉!近读嘉靖十一年冯子仁恩应诏上疏备指大臣邪正中云:礼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讲学素行未合人心,则知为侍郎日已不免人訾议矣。甘泉论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言,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③此亦可从反面看出孟超然之高尚。
三 陈庚焕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庚焕(1757—1820年),字道由,号惕园,福建长乐人,世居福州鳌峰坊。陈庚焕“幼年承家学,立志即希古贤儒,操行敦笃,充养和粹”。①所谓“幼年承家学”,主要是其母的教导。据记载:“母夙尝儆之曰:朱子之书不可不读,然汝终日把在手里何益?朱子一生作多少事,汝事至难断而诚不足动人,虽朱子之言背诵如流与汝何与?后贡士(按指陈庚焕)授徒尝述以勉后生。”陈庚焕早年主要是“读《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心有感奋,逐专务实践,不徒事文艺之学”②;后来,就学于福州鳌峰书院,专门研究张伯行所刊印的程朱理学著作。由于自清代乾嘉以后,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促使当时许多学者研究自然科学。陈庚焕写了《地球考》(上中下)、《南北极赤道考》、《云汉考》等五篇论文。这也说明他不是空谈心性的,也是关心世事的。
陈庚焕所著《性道图》、《果核喻性》、《五伦说》,显示出其朱子学思想的特点。他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以“行修”为线索,把朱子学的主要范畴贯串起来,形成了一种以“行修”为特点的理学范畴体系。陈庚焕说:
天人一理。天人一气。天,道所从出。命,天之所赋。性,心之所具。道,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理,在物为理。义,处事为义。德,行道有得于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有阴阳五行之理,乃有阴阳五行之气。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性即理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天,譬如朝廷。命.敕命。性,譬如敕内所载职掌。情,譬如官吏施行。道,譬如照敕施行各有法律。理,譬如事事皆有成例。义,譬如照律例断案。德,譬如老吏律例烂熟胸中,不用检案。③
由此可见,陈庚焕的思想体系为天命→性情→道理→义德。这就是说,天命具于人心为性,性之发为情,发而符合事物道理(中节),则表现为处事有义,对人有德。
陈庚焕明确指出,维护皇权就是维护天命,从而天下人才安居乐业,有好日子过。陈庚焕说:
天下的人多得很,人生一世事情也说不尽,只有五伦两个字可以包括。朝廷是个天,大家戴着天,才得好好的过日子。若不是靠着王法,那些横行霸道的人都要强抢强夺,不要说田房衣物等件保不住,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也不能相保了。所以君臣这一伦是第一件最要紧的,有了这一件才有那四件。普天下不论做官不做官,通是朝廷的臣子,大家都要依着朝廷的规矩法度,不要违条犯法,好好的做人,这才算顺了天。①
这段话反映了中国封建地主阶层守旧派对自己历史命运的恐惧心理。在陈庚焕时代,中国封建制度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中国即将进入近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陈庚焕还宣扬已被历代先进思想家批判得遍体鳞伤的天命论,说明中国封建地主阶层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到了穷途末路。
陈庚焕的著述有《童子摭谈》、《易堂德稳录》、《尊闻录》、《于麓塾谭》、《五经补义》、《二十二史图说》、《师门辧香录》、《约语追记》、《庄岳谈》、《谬言意言附识》、《北窗随笔》、《富德随笔》、《地球考》、《南北极赤道考》、《云汉考》、《性道图》、《气禀说》、《崇德同心录》等,结辑有《惕园丛书》、《惕园初稿》、《惕园全集》等。
(二)天道理气说
陈庚焕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天,认为“天,道之所由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譬如朝廷”。②陈庚焕说:
夫道散殊天地之间,万变而不可究诘,疑若至纷且赜不可以骤通矣。然其大原之于天。沿委溯源,由源达委,则不啻如川之流,脉络分明,分合千万里,而其始本无不通也。③
陈庚焕在《性道图》中认为,天是最原始的本原,天产生道,天通过“道散万殊天(按此处为自然之天,非本原之天)地之间”,“道,日用事物当行之理”,“道,譬如(官吏)照敕施行各有法律”;天与天地中万殊(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脉络、分合如川之流就是道,因而天与道的关系是源与委(端末)的关系。
陈庚焕讲到天和理的关系时,一方面,他把天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即理也。一气运行,以生物为心。天之主宰曰帝,即理气之主宰。另一方面,认为天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在物为理,一草一木具有至理,“理,譬如事事皆有成例”。④
陈庚焕在《性道图》中进一步指出,天之主宰即理气之主宰,就是“天有阴阳五行之理,乃有阴阳五行之气;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即天是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道理来化生天地万物的。对于阴阳五行化生天地万物的过程,陈庚焕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又说:
阴,气静为阴;阳,气动为阳。阴,顺;阳,健。静极复动,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阳,元(生物之始)、亨(生物之通);阴,利(生物之遂)、贞(生物之正而固)。木,其气发生不息。火,其气盛长分明。土,其气敦厚坚实,贯五行,分主四季。金,其气收敛斩截。水,其气流通澄定。①
尽管陈庚焕的这些说法是不科学的,但是他通过动和静、健和顺、元亨和利贞的对立统一关系把阴阳和五行联串起来,企图用气之发生(木)、成长(火)、收敛(金)、流通(水)和形成(土)来说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含有合理因素,具有某些辩证法成分。
陈庚焕认为,“天人一理,天人一气”。这就是说,自然界(天)和社会(人)都是天(本原之一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化生的。他说:
木,东方,春,仁(蔼然仁民爱物之心),恻隐。火,南方,夏,礼(秩然上下亲疏之序),恭敬辞让。土、中央,夏季,信(实仁实礼实义实智)。金,西方,秋,义(肃然收敛裁决之宜),羞恶。水,北方,冬,智(肃然辨别谋画之识),是非。②
如果说陈庚焕用阴阳五行之气来说明自然万物化生的过程还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和辩证法成分的话,那么他用阴阳五行之气附会五德则全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价值。
陈庚焕认为,天地万物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别性,其统一性在于它的理气性,其差别性在于它得理气之偏塞或正通。陈庚焕说:
天之生物一气而已,天之降命一理而已。气以成形,理以成性。性之理无形(按指为何物未定),即随形气而中寓。因此,一气之中得其偏且塞,而性亦因偏且塞者,则为物;得其正且通,而性亦得以正则通者,则为人。③
在这里,陈庚焕讲了千差万别的世界万物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理气,理气贯串于世界万物之中。
(三)以好善为中心的认识论
陈庚焕在《识警》中反复讲了认识论问题。他认为,就像“天之帝(理)主乎万物”一样,人之心(大脑)主乎人体,“少有痛痒,此心无不立觉也”;“一念之动,即上帝(理)临汝”。这就是说,主体有认识客体的能力,世界是可知的。陈庚焕说:
顿悟之见果不足恃也。夫人生动静皆在天地一气中,天之帝主乎万物,譬则人之心主乎百体也。人属于天,譬则百体之皮肉属于心。少有痛痒,此心无不立觉也。人之心与天之心本无一息不相通,则一念之动,即上帝临汝,固无待日月照临,始足有悚也。然众人之心鲜知天人之合一,至于对青天而不惧,则几于无忌惮矣,况与有闻于天人合一之理者乎!①
陈庚焕这里所谓“天人合一之理”,不是汉人董仲舒式的天人感应论,是指主观能认识客观,主观和客观是可以相一致的。不过,这里必须特别说明的是,陈庚焕所说的人心的认识对象天心(天命之理),主要的并不是天地万物,而是善与不善。在陈庚焕看来,所谓认识,就是认识道德的善与不善。陈庚焕认为,天下大矣,天下之事难知难行者众,而孟子以好善一言蔽之。人所以当大任成大功,未有不由此者。盖善量之无穷,而不可以一端竟。他说:
人无论智愚贤不肖,莫不各有所知,各有所能,即莫不各有所善。天下之善散在天下之人,以一人之耳目思求之,诚有所不足;合天下之耳目心思以共求之,曷尝不有余。②
尽管陈庚焕把认识的范围限制在认识善,但是陈庚焕提出求善必须“合天下之耳目心思以共求之”,就其抽象思维来说是合理的。
陈庚焕提出认识首先必须清虚其心。清其心,毋以欲汩之;虚其心,毋以己与之。陈庚焕清虚其心的思想,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要保持心的洁净。有洁净的心才会有正确的认识。所谓洁净的心,就是认识不要带着成见,不要先入为主。陈庚焕说:心者神明之舍。“明命之赫然,于是乎在上帝之临汝,于是乎式凭亦至严而不可亵矣。人于像设龛几之旁,未有敢加以污秽之物者,诚知其不可亵也。乃于神明所舍,顾使猥鄙之念憧憧往来,亵天之明,毋乃实甚。”③这就是说,认识不要带着成见,不要一味守旧,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认识。陈庚焕所说“神明之舍”不能有“猥鄙之念憧憧往来”,是比较深刻的。第二,主静、主敬要适当,不能偏着于静或著意矜持。陈庚焕说:
心本虚灵不可执滞。要常主静,若偏著静,则事物之条有不能顺应矣;要常主敬,若著意矜持,则跼蹐不宁而心反乱矣。①
这就是说,运用心,必须时时提掇光明,勿使滞,亦勿使放,不滞不放而至于不偏。在这里,陈庚焕对主静、主敬有新的见解。陈庚焕吸取道家的“虚”而剔弃其“无”,认为人心虚而实有,而不是虚而空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曾在其《太极图说》中提出,未有天地之前的“无极”是静的,因而人的天性是静的和无欲的。由此,理学家用主静来保持人的无欲天性。陈庚焕认为,人心有认识事物的能力,不能人为地控制人心对事物的认识(“心本虚灵不可执滞”);要常主静,但不能“偏著于静”,如果“偏著于静”就不能吸取新东西(“事物之条有不能顺应矣”);要常主敬,但不能“著意矜持”,即一味回避外物引诱,那就违反人的理性,使“心反乱矣”。因此,陈庚焕提出要达到“勿使滞,亦勿使放,不滞不放,则不偏”的主静、主敬境界。②陈庚焕又说:
人心方寸之中,空洞无物,而生意盎然中满。静则仁、义、礼、智、信五性悉涵此生意之中;动则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四端悉据此生意而发,推之亲亲、仁民、爱物,极之齐家、治国、平天下,厥施不穷,莫不本此虚中之一生意,则与是核之芽于虚,不正同欤!老子有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为形而下之器,言者信然矣。若夫形而上之道,则其无也,其虚也;其虚也,其实理之所由中涵也。然则仁之虚也,直不滞于有耳,而岂沦于无哉!③
陈庚焕这段话是对朱子学主静、主敬之说的绝好阐释,充实和发展了朱子学。
对知和行、学和用的关系,陈庚焕讲得更为深刻。第一,知和行、学和用相比,行、用更为重要。学必求有用,无用之学非学。陈庚焕说:
学也者将以修己教人、明道而经世也。理学之弊失之迂,心学之弊失之偏,文学之弊失之浮与杂。其究也,则皆失之伪,殊途同归均于无用,非徒无益而又害之。④
陈庚焕把理学、心学和文学分别概括为迂、偏、浮杂值得重视。他把不能修己教人、明道经世的无用之学看成是伪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第二,践履不完全仅是道德实践,还包含有事功实践之内容。要经世和修身并重。陈庚焕说:
学须见诸实事。若作官者必征诸实政。居高位而不能进贤、退不肖,为民兴利除弊,空谈学术性命,无益也;日用伦物之间事实行之,方是实学。①
所谓经世,盖只是求其有用也。书生虽未有经世事。然经世之本在身,源在心,其端在一家一乡。读书而以之诚自治其身心,抵之以料理一家一乡之事,各得其理,方为有用。②第三,强调行、用要贯彻认识过程的各个环节。陈庚焕说:
以实心读圣贤之书必返躬以体其实,以是心权天下之理必随时以处其中。言道言教必本人伦而不为高论,言敬言静必切日用而不为空谈,毋事门户必折衷于圣人,毋事安排必徐候其自得。如是以为学,则有体有用而无差,如是以为教,则易知易从而无弊。如是以为文,则明经之文足以适用。③
在陈庚焕看来,“孔门之论学,必归诸人伦之大,行必尽诚。”④“学贵能行。朱子一生作多少事?汝事至不能断,而诚不足以动人。虽朱之书日把在手里,何益?”⑤陈庚焕特别强调“行必诚”,体现在自己身上。方志有谓庚焕“学务实践,以程朱为宗,每日言动必簿记以时时省察”。⑥
(四)人性论和道德伦理思想
陈庚焕把心看作是“神明之舍,譬如官府衙门”;而“心之神明,譬如舍中之主人翁也”。⑦陈庚焕说:“是神明者,固天之所降,而人所以与天通,所谓人为天地之心者也。”⑧在陈庚焕看来,所谓“神明”,就是指人的聪明才智,人的认识和体验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有的;因为人有这种能力,所以在宇宙的三大组成部分天、地、人中,人为核心。
陈庚焕反复说明,人心中之“主人翁”具有聪明才智,其表现在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上,而五常之性是天命所授予的理,即天理。天理(五常)是“舍(心)中”之“主人翁”(神明)的“祖父”所给予的,是供其应万事之用的。他描述了天、理、心、神明、五常之间的关系。他说:
程子曰心者,神明之舍。然则心之神明,譬则舍中之主人翁也;性者心所具之理,譬者舍中之器物也;天者理之所从出,譬者舍中器物本祖父所留贻也。心之所具之理,譬则主人翁之收其百器万物也;其以众理应万事,譬则以百器百物供百事之用也。①
他还对“神明之舍”(心)中的“器物”五常(天理)作了详细的论述,发前人所未发。
陈庚焕指出,人心中所固有之天理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做人的规矩,一举一动都能遵循此规矩才是人,否则就不是人。天理五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是人的本质,是人与物的界限。大家心上本来都有这个道理,其实只在该不该上分别。“一举一动都有个规矩,依着规矩才像个人。”②要晓得这礼节规矩都是天地自然的道理,不是古来制礼的圣人强加给人的。
陈庚焕认为,人们的气质有昏明薄厚弱强之不同。他用糖和米屑合成糖粿作比喻。糖之性甜,似理之性善,糖胜米屑则味甜,犹理胜气则禀赋之质好。陈庚焕说:
盖糖,性也;米屑,气也。炊屑成粿,气以形成也。合糖于屑,气形成而理亦赋焉者也。既出于甑,则见米屑所成而不复见糖。气有质而理无形,道心之微也。糖之本甜犹性本善。既杂于屑,则不能自全。其天味之完否?一因乎屑,气质之性有所囿人心之危也。糖与屑相济则甜美,赋质之纯者也。屑胜糖则味减,赋质之偏者也。③人之生也,既同得此正且通之气矣,而其质之所禀,昏明厚薄强弱之不齐,其等级差次至不可以数计,则又何也?盖即同此正且通之气,而其发也始必厚而烽(自注:俗所谓气头),及其长也必薄而力减(自注:俗所谓气尾),其精而上浮者必清而明,其粗而下沉者必浊而昏(自注:俗所谓底面),固有不能齐者矣。又况所谓昏明厚薄强弱者,又复相盈相摩滚同混合于流行消息之中,其纷错杂糅又安可以究诘,惟圣人之生于纷错杂糅之中独值其精粹不错者而禀之,自圣人而下则皆随其所值之纷错杂糅而各禀以为质。则其昏明厚薄强弱之参错不齐又何足怪哉!④
这里陈庚焕讲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用理气来解释人的同一性和差别性。二是指出人有等级差别的原因:(一)其气之发生作用的时间先后不同,(二)其气之精粗不同,(三)其气之互相摩擦运动的结果或精粹或杂糅不同。在这里,陈庚焕用比喻的方式把人的气质说得很清楚。
陈庚焕提出必须先认识天理,然后以天理去剖析道心和人心,变化气质,使道心常存,人心听命,依理而行,便呈现出五常之德。陈庚焕说:
学者即此寓于气中之理,辨其孰为受命于天、不杂于气之道心(自注:仁义礼智信之本心是也),孰为性杂于气,写形俱生之人心(自注: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心是也)。辨之必审,是之谓惟精;养其理道之本心,使无少放逸而或动于血气。范其情欲之人心,使无少纵肆而害其本心。持之必坚,是之谓惟一。①
陈庚焕这里所谓“养其理道之本心”,就是使道心常存(即“无少放逸”);所谓“范其情欲之心”,就是使人心听命(即“无纵肆”);所谓“惟精”、“惟一”,就是要体会和懂得人心、道心这种精微的道理,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存道心去人心、存天理去人欲。
去人欲而存天理就是事天,遵循天理五常之德。陈庚焕提出畏天、循理、待人三个方面为事天之要。他说:“畏天:天生我为人,要我循道理;无理逆天心,哪得天心喜。”“循理:既做读书人,如何不循理。”“待人:待人当如何?近情与近理,要决只一言,将心比心耳。”②陈庚焕之所以把待人也作为事天之要,就是因为“人事尽,始可以言天”③,事人即为事天。
总之,陈庚焕尽心、知性、知天、事天的命题,发挥了人心中以仁为核心的五常之性,就认识了人的本性;认识了人的本性,也就认识了天理;保存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就是事天、畏天、循理、待人,是事天的最好形式。
另外,陈庚焕还把这种心、性、天三者结合为一体的思想概括为“道之体用”,即知和行的问题。上面提到的陈庚焕讲的惟精和惟一,就是知和行。陈庚焕说:
道之体用。穷理养心,使此理常明,此心常存,方寸之中纯是天理,都无人欲,活活泼泼、不偏不滞者,道之体也;及至举念、说话、做事都从此活活泼泼不偏不滞的心里发出来,便自然有个好的道理,再不至差了念头,说错做错,这便是道之用。④
在陈庚焕看来,“道之体用”就是道的本体和作用。尽心、知性、知天、言性、言理,使心中“纯是天理,都无人欲”,就是道之体;“举念、说话、做事”都遵循天理五常,就是道之用。在陈庚焕看来,分析道之体用极端重要,“体用二字剖析精明,故得其旨皆不蹈虚谈性命之讥,亦不流穿凿支离之弊”。①在体和用之中,陈庚焕把用看得更为重要。陈庚焕说:
程朱以后性理之书备矣,学者粗涉其书即可拾其唾余。言性言理都不难。剖析精微惟五伦二字,必要认得实理,切实行到恰好地步,善乎!汤文正公汤斌有言:开口说太极不准,切实行五伦不易。②
这是反对空谈性理,把抽象的性理拉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强调用五常之德的践履体现性理。
四 刘存仁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刘存仁(1774—1850年),字炯甫,又字念莪,晚号蘧园,福建闽县(今福州市闽侯县)人。宣宗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曾入林则徐幕府,为林所信任。历官甘肃渭源、永昌、平罗等县知县,甘肃泰州、直隶州知府。晚年被聘为福州道南书院院长。
刘存仁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陈寿祺的门人,一生笃信程朱之学,其在主持福州道南书院期间,朱子学思想臻至成熟。刘存仁认为,宋代学术最为昌明。他说:
宋世理学昌明,大儒辈出,《语录》、《性理》诸编,圣学之阶梯,大道之途径,躬行实践以求义理则甚精,以求经济则甚实,明体达用厥功懋矣。③
他认为,理学在宋代并不是空疏不实之学,而是“以求经济则甚实,明体达用厥功懋”。他提出“道(按即理学)外无儒,儒外无道”的观点,认为“通经学古”、治理学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儒学。刘存仁说:
元史臣之撰宋史,始以道学、儒学等分为二传。后之言程朱之学者空疏无据,不复以通经学古为务,于是谈复古者用是为诟病,以考订为是,以训诂为功,其甚者欲尽废程朱而宋汉,穿凿附会,琐细驳杂,而学愈晦,不知道外无儒,儒外无道。④在刘存仁看来,当时治汉学(考据学)的人是程朱理学末流,也是程朱之学者。他从经世致用观点出发,对古今学术提出一些较为客观的看法,具有折衷调和论的特点。他认为,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其实门户之见未融,逞私心而轨于公道者。汉承天学之后,递禀师承,其学者笃信师说,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其弊杂之以纤纬,乱之以怪僻。他说:
宋世名儒辈出,摆落杂芜,独标精蕴,于圣人之旨为近。要之,汉学自有根柢,不得以浅陋讥之;宋学俱有精微,不得以空疏目之。故吾谓今日学者贵通汉宋之邮而得其要领。依声附影、随俗转移,无当也。①
刘存仁这里所谓汉学,是指汉代的经学,不是指清代的汉学。刘存仁认为,清代的汉代经学“训诂相传莫敢相异”、“根柢”深;清代的汉学“猎词华以博取利名”,“以荣辱为欣戚”。刘存仁说:今世之学猎词华以博取科名,而于心身性命之理、人伦日用之常置而不讲。“名心一炽,弛函纷华。得志则利禄汩没,失意则英华销损。以外来之荣辱为欣戚,于德性毫无所补。”②刘存仁这里所谓“外来之荣辱”,是与心内“性命之理”相对讲的。刘存仁把科名、利禄、失意等称为“外来之荣辱”,把性命、道德之修养看成是内心反省功夫。
刘存仁对陆王学说不持门户之见,不因人废言。南宋时,在朱熹和陆九渊鹅湖之会上,朱曾指责陆为学“易简”,即不做格物读书穷理工夫而直接体验“心即理”。此后历代朱子学者大都坚持朱对陆的这种观点。刘存仁却肯定了“易简”功夫的合理性。刘存仁说:
天地之道,易简而已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③
刘存仁认为,天地的运动变化就是易简,通过易简方法“天下之理得矣”。刘存仁对王阳明的主静说亦作了肯定,认为是符合程子的动静之理的。刘存仁说:
始悟程子静亦定、动亦定之理。嗣读阳明先生答伦彦式书发挥透彻。其书云: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循理焉,虽酬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④
周敦颐认为,在未有天地之前的“无极”是静的,因而人的天性应该是“静”的和“无欲”的。王阳明认为,静不是不动,循理无欲即谓静。只要是循理,“酬酢万变”亦谓之静。在刘存仁看来,王阳明的这种观点是和周敦颐的“主静无欲”是一致的。
(二)哲学和政治思想
在刘存仁的世界观中,天、性、理三个范畴具有相同意义。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则性,性即理,因此天、性、理是一致的。性、理的大原是天,那么天是怎样的呢?刘存仁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以无心而成化也。”①刘存仁把天看成是客观事物变化的现象。“天以无心而成化”,就是天是自然而然的,它是没有意志的。天既如此,天理寓于事物之中,即为事物之性。刘存仁所谓天即理、理即性,就是天、性、理统一于事物之中。
对于道,刘存仁也是力图到事物中去寻找。他认为,道存在于人伦日用和诸文之中。他说:
道寄诸文。文者贯道之器,道与器二而一者也;制义代圣贤立言,必词依乎质,又当乎理充实完满而无一毫之亏。②
在这里,他把文章看成是载道(义、理)的器具(质)。他的文是指“代圣贤立言”和“世之知言者”,即正确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文章是载道(义、理)的器具(质),是道(义、理)得以表现出来所依赖的质(器具)。刘存仁的这种说法是有合理因素的,是与今天所讲的语言(包括文字)是思维外壳、是思维工具的观点相接近的。
对于世界万物是怎样从天、理、道这些本原中产生出来的,刘存仁提出“食色性也,阴阳理也。氤氲化醇,万物化生”的观点。他说:
二气流行,寒暑循环。一气贯注,天地得之以立心,人物得之以立命。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言而万理毕。③
天地间人情物理,纷纭蕃变,理一以贯之。刘存仁认为,阴阳“二气流行,寒暑循环”的过程,就是自然界(天地)和社会(人)产生的过程。刘存仁借用孔子《论语·尧曰》中所说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说明世界万物产生的情况。这就是说,阴阳二气流行、循环产生天地万物的道理是非常微妙的,这种精微和唯一的道理就是合乎中庸(不偏不倚)的要求,即“天地间万事万化无不本诸中和”。本来,“惟精惟一”是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①即人心物欲危险和道心伦常微妙;“允执厥中”是指应该体会这种微妙和唯一的道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中庸(不偏不倚)。②
对于人能否认识天地万物,刘存仁作了肯定的回答。刘存仁认为,主观和客观是会发生感应的,“夫感者物也,所以感之者,吾心之神也”;“心气和平,则事理亦通达矣”。“凡事有一定道理。所谓方也,必此心清明,于道理上见得圆满充实,无一毫之欠缺,而后折中至当。顺事恕放,故曰知者不惑”。他说:
人心惟思为最虚最灵,万籁俱寂,胚胎未形,腾九天而入九渊,神妙变化,不可方物,思路绝而风云通,思之思之,鬼神亦将来告知,而沉于人乎?《管子·内业篇》云: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报也。故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是以鼓之舞之以尽神。故曰神而明之者存乎人。又曰知几其神。当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夫感者物也,所以感之者,吾心之神也。神与神遇而情生焉,有不知其情生文、文生情也。③
在这里,刘存仁讲到人心惟思,它要依赖由胚胎发展而来的物质器官。讲到了人的思维要有物质基础。在这段中,刘存仁详细地讲了主观是能认识客观的。由于主观能认识客观,刘存仁提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天下事无不可为”。④
刘存仁还深刻地讲了知行的问题。他认为,行难,必须在“窒碍难行处见得道理圆满充实,方是理足”。“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何能事事称意,必于窒碍难行处见得道理圆满充实,方是理足”。应事接物到恰到好处最难。孔子之从心不踰矩,朱子不偏不倚之谓中,还要依理而行,“应事接物到恰好”。⑤
刘存仁承认古之圣贤是先知先觉的,有“扶世翼教”、“担荷宙宇之责”。刘存仁说:
上之圣经贤传,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有维持风教、担荷宇宙之责,不忍一夫之失所,大声疾呼,偕之中道,赞助元化,保合太和,用以扶世翼教,使之家喻户晓焉,所谓圣为天口也。①
在这里他把圣贤看成是“天口”,是依天命教化人的,因而圣贤对人们是“偕之中道,赞助元化,保合太和”的,即人们完全是圣贤培育起来的。在这里,刘存仁就把我们前面叙述的他的认识论的一点合理成分完全取消了。
在变化气质问题上,刘存仁特别强调存心养气。在刘存仁看来,存心为道心,道心发之气为道气,道气即为勇气。刘存仁认为,存诸心者为道心,则发诸气为道气。刘存仁认为,“人固当存其心,亦不可不致养其气。大将提百万之师,一鼓作气,置之死地而后生,试之危地而后存,气足以胜之也。”“道义而塞天地,其本归于不慊则馁。说理充实圆满,即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之意。”“千古之忠臣志士孝子悌孙义夫节妇皆一气所弥纶鼓荡,亘万世,横四海,以维持不坏。”在这里,刘存仁所谓的气虽似气节之气,但是他比之道义,是忠臣志士的勇气,“弥纶鼓荡,亘万世,横四海”,是无所畏惧的。
在近代,地处沿海的福建,深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更加激发起人民的爱国热忱。因此,这时的福建人特别强调要有勇气、志气。福建侯官人林则徐销毁英国鸦片烟的勇敢精神,就是其佼佼者。清代福建朱子学学者大都提倡志气、勇气,就是基于这种时代精神的。
刘存仁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人民,要兵民联成一气才有力量。他说:
兵与民联为一气,迨至兵与民合,而气愈旺守愈固,外匪闻风而胆落,此不战而击人之上策。②
刘存仁反对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太容忍的不抵抗主义。刘存仁以南宋对金的容忍为例来说明忍害之大,以激发广大人民和清政府中的爱国官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坚决抵抗,决不容忍。
同时,刘存仁还提出一些变法主张和加强边防的军事措施。当时社会需要变革,刘存仁虽属守旧派,也看出一些社会的重大问题。穷则变,变则通,边防的军事措施也要变革。他说:“龚海峰先生坚壁清野之义诚有可采。但南北异宜变通,利用古书犹古方对症下药,知加减变通者为良医。”③
五 陈庆镛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庆镛(1745—1858年),字乾翔,号颂南,学者称颂南先生,福州人。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给事中、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等。
陈庆镛极重视经世致用,他为政“留心经济,不汲汲为仕,凡军实之所储,度支之所出,边备之所防,河渠漕挽之所疏浚,输讲画条贯物得要略而后止”。①陈庆镛主张渡江重平夷之策,反对外国侵略者。他曾向朝廷提出御寇之策。他说:
盛京之奉天,直隶之天津,江苏之崇明,浙之定海,闽之厦门、福州,粤之虎门,山东之登州,备各战船十只或四十二只堵截要害,以俟其来者而应之,所向披靡。②
此外,陈庆镛还屡次上疏建议朝廷在台湾加强武备,防止和抵抗英国等帝国主义者侵略。他还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干涉中国内政,对卖国投降官吏深恶痛绝。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批评朝廷起用已治罪的皇亲卖国贼琦善、奕经、文蔚等人是刑赏失措,致使皇帝复革琦善等人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于是,陈庆镛“直声震海内”。③他以正直敢言的御史名世。
陈庆镛服膺宋儒,而又精研汉学,覃心考据于声韵文字之学。其治经务求是,以致用为目的。他曾自题“六经宗孔孟,百行学程朱”④的楹语。陈庆镛认为,汉学、宋学的共同点都是主张明经致用,都推崇圣贤。陈庆镛说:
汉人多讲阴阳,而宋人则专主理数。《易》旨无穷,当合汉宋而通之,无门户之见,乃可以言《易》辞,言六爻,发挥旁通。⑤
他认为,言象言数不如言理为密。应以理为主,象次之,数更次之。陈庆镛所谓“汉人多讲阴阳”,是指西汉董仲舒一派的“天人感应论”。天人感应论通过歪曲先秦阴阳五行学说,用阴阳五行把天与人沟通起来。陈庆镛认为,《周易》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宋儒专讲《周易》中的理是不全面的,应吸取汉儒关于《易》象、数的观点。陈庆镛这种反对门户之见的治学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
陈庆镛提出对各种学说都应该兼收并蓄。他说:
学为有用之文,则又本之《易》以导其源,本之《书》以充其识,本之《诗》以博其趣,本之《礼》以究其精微,本之《春秋》以考其得失,本之马、班、范、陈以助其波澜出入,本之管、韩、庄、列以极其苯䔿奥窔。①
陈庆镛认为,凡是有用之文都应该学习。他举出《易》、《诗》、《礼》、《春秋》以及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管子、韩非、庄子、列子等诸子之书,都要学习。
对于陈庆镛的人品性格、学问事功和启迪后学的情况,其门人龚显曾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述,其曰:
(吾师)诵谏草者,成舌挠不得下,海内名俊,想风望采,蹑履投刺,争以一瞻颜色者为幸,晷盖无虚。先生植品既高,文章学问,又足牢笼百氏,震动时贤。于是有阮文达公元孙,先生经世之师;何先生绍基、魏先生源、张先生穆、苗先生夔、赵先生振作、朱先生琦、梅先生曾亮诸君子为元友;何先生秋涛为之徒,相与挋刷精思,切劘道谊,学益懋,品益高,而名亦益显。然后知执一卷奏议以重先生者,其不足以概先生而儤先生也。②
何绍基、魏源、何秋涛等是近代著名的学者,皆为陈庆镛的友徒,由此可知陈庆镛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
陈庆镛的著述有《齐侯罍铭通释》、《籀经堂钟鼎文释题跋尾》、《说文释文校本古籀》、《三家诗考》等,结辑为《籀经堂类稿》。
(二)器识论
在陈庆镛的哲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器识论。陈庆镛所谓“识”有世界观之意,是为学为文的指导思想。陈庆镛说:
夫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无其识,其词不足以达识。苟足以达矣,而或谓过高之论,或限以一丘一壑拘于墟而不足以观河海之大也,局于量而不足以仰泰山之高也,又何以称于其后及久而不衰。③读叙谱状叔寿兄诸文,得其所以立爱之道焉;读赠言劝友慎交诸文,得其所以交游之道焉;读论经论史论子诸文,得其所以为学之道焉;读议兵、议律、议法、议钞弊、论海道诸文,得其所以行政之道焉。夫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非其学之大不能见乎道之源也,非其议之一高不能达乎政之本。有其学有其识,宜出而膺司牧之职慰苍生之望知。④陈庆镛在这里提出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命题是深刻的。学者首先要有一定的世界观,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达识”,即具有高的思想境界;“见乎道之大原”、“达乎政之本”、“称于其后及久而不衰”,才能不流于就事论事、经不起时代的考验。陈庆镛还特别强调,“有其学有其识,宜出而而膺司牧之职慰苍生之望”,就是见其文和其才知其所能而为众望所归。陈庆镛的这些议论表明他主张文艺要把思想摆在第一位,艺术摆在第二位。
陈庆镛以“器识”为中心,进一步提出明、论、辨以及精、广、妄、疏等为学诸范畴。他认为,识足以达时事之宜,明足以破千古之蔀,论足以剪繁芜之失,辨足以息群喙之鸣,然后驰骤纵横,必求于是而后止。故治经贵精力,治史贵广博,读未数行辄评隙,失之妄,读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断、失之疏。在为学中,陈庆镛认为,有“识”才能为当世服务,有“明”才能破千古之蔽(蔀),有“论”才能找出发展规律,有“辨”才能胜于别人,“识”、“明”、“论”、“辨”都具备了,就能“驰骤纵横”、应心得手。“治经贵精”,才能“失之妄”;“治史贵广”、“失之疏”。①陈庆镛这种对为学之德和为学之方的概括是深刻的。
陈庆镛还认为,学者如果没有“器识”,为学既“不能入”,尤“不能出”。“不能入”和“不能出”是学之大患。陈庆镛说:
凡学之患,患于不能入,尤患于不能出。丛籍鳞次,手翻翻不辍,一辍辍遗,即偶有一二得心,而于古人回穴奥窔终莫能晰,饾饤耳食,如是者不能入。又或紊昔贤往事,钩稽条画,谓某也醇、某也肆、某郅隆。②
在陈庆镛看来,所谓“不能入”就是“手翻翻不辍、一辍辍遗”,一点也学不到手;即使偶然有一点心得,也不能分析,而且一耳进一耳出,很快就会忘棹。所谓“不能出”,就是学了不能用,虽讲得头头是道,均与原意不合;特别是眼高手低,自己不会执笔为文。这种对为学之患的刻画真是绘声绘色。
陈庆镛特强调,为学处世都要务实,他名自己的书屋为“实事求是斋”。他提出要随实应化,不能虚浮,不可拘泥于前人古人之言。“圣人不凝于物而能与世推移”。③陈庆镛说:“参伍错综,惟变所适,不可以孔子之言泥周公之言,更不可以周公之言泥文王之言。”④又说:
列子谓燕人而长于楚者老而归于燕,过鲁之城社,或绐以为燕也,愀然变容;过冢墓以为先人之陇也,泣然流涕。及真见燕之城社庐墓悲心反减。今世之大家勋阀往往援疏旗之贵者显者联为谱系,傅会成书,相与叙及,辄曰我伯叔兄弟也,而于其真伯叔兄弟漠然概不相关,是何异燕人之见绐者据以为真而为有识者所窃笑哉。①
陈庆镛所举的《列子》等的例子,就是强调务实,反对浮夸虚言。尽管这些例子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但是它说明了认识论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陈庆镛把圣贤之道归结为仁、义、礼、智、信五伦,五伦具即为道心,并对五伦作了言简意赅的解释。陈庆镛对五伦和道心的解释有点独出心裁,值得注意。他说:
圣贤之道无他,付诸心之谓仁,施诸当之谓义,止诸节之谓礼,达诸事之谓知,践诸实之谓信,全而合之之谓道心。得乎道之谓德。圣人之所为,不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如是焉已。众人之所为,亦不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与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如是焉已。孟子曰:圣人,人伦之至也;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尧舜无难知难从之事,而人则不如尧、不如舜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于是卤莽灭裂之言盈天下,张道益炽而离道益歧。②
陈庆镛认为,圣人和众人之所为是一样的,皆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与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因此尧舜与人同耳。尽管这种“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古已有之,但是陈庆镛这里是为说明“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是有现实意义的。③
陈庆镛提出要从自己日常生活和周围具体事物做起,就能达到所要求的思想境界。陈庆镛曾谓:“儒者有闻过相规,见善相示,余常持此以论交。”④
清代自仁宗嘉庆(1796—1820年)以后,盛极而衰,进入后期。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约有一个半世纪。
清代中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活跃起来,但是仍然是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还是较为稳固的。到了道光年间,清王朝百孔千疮,国势江河日下。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支绌。官吏贪污成风,赋税日益加重,高利贷剥削极为猖狂。官僚、地主、豪富兼并土地更为严重,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农民反抗斗争更加频繁。整个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中国封建社会已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就在这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妄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宋元明以至清初历代王朝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到了清代中期,鉴于朝廷“文网”(文字狱)太密,一些学者不敢触及实际问题,导致所谓“乾嘉考据学”(汉学)盛行,压倒理学(宋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知古不知今的学风。这个学风得到朝廷的支持和提倡。清代中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是宋学和汉学占主导地位,是一片“万马齐喑”的沉寂气氛。鸦片战争后,严重的社会危机、民族灾难和人民群众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特别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西方自然科学和各种学说逐渐输入,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产生于西汉的今文经学,把《春秋公羊传》(今文经)的经义和当时的谶纬迷信相结合,牵强附会地任意解释经书的内容,为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当时的正统学派。今文经学又称为公羊学。清代今文经学派主要利用公羊学中的专制主义和改制思想,借题发挥,议论时政。康有为、梁启超等以今文经学为工具宣传变法维新主张。于是,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大兴。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学和旧学、西学和中学之争,实际上是今文经学和宋学(程朱理学)、汉学(古文经学)之争。当时属于程朱学派的方东树、唐鉴、倭仁、曾国藩、辜鸿铭等,都是旧学、中学中的主要人物。从整个清代后期的思想文化界来说,今文经学(公羊学)占据时代思潮的主流,程朱理学不振,但是由于出现倭仁、曾国藩等“理学名臣”,曾出现所谓“咸同(即咸丰同治年间)理学中兴”。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朱子学是为封建守旧派服务的。
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朱子学始终没有断绝。它顽强地存在着,并在社会上发挥重大作用。一般来说,在近代中国,辛亥革命前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仍然是朱子学;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民国,官方的统治思想在变化中,而程朱理学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朱子学仍然具有广泛的深刻的影响。
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的福建,朱子学内为新旧思想的论争亦十分激烈。一方面,以陈寿祺(闽侯人)、陈乔枞(闽侯人)、郭尚先(莆田人)、严复(闽侯人)、曾克耑(福州人)等为代表,治公羊学、西学,反对朱子学。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治西汉今文辑佚之学,以著名的福州鳌峰书院和浙江诂经精舍为据点,登台授徒,著书立说。他们著有《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定本》、《今文尚书遗说考》等,宣扬公羊学,有功于今文经学。郭尚先官至侍讲学士,治经世有为之学,学问渊博,其与林则徐为莫逆之交,议论时弊,要求改革国内政治,反对外国侵略;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哲学上反对天人感应论和鬼神说,提出物质决定意识。他著有《增默庵文集》8卷。严复是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学术和政治制度的学者,是西学、新学的主要人物。他宣扬达尔文“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观点,激发当时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并向清王朝提出变法维新的要求。他提出为学要有实和用,斥责朱子学、汉学为无实、无用之学,并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著有《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等。曾克耑接受严复的政治思想,反对程朱理学,著有《颂桔庐丛稿》、《曾氏家学》(是书于1961年在香港印行)等。
另一方面,以孟超然(闽侯人)、陈庚焕(长乐人)、刘存仁(闽县人)、林春溥(闽县人)、陈庆镛(晋江人)、郑星驷(福州人)、辜鸿铭(厦门同安人)等为代表,坚持程朱理学,反对西学、新学,成为守旧派、洋务派的理论代表。例如,郑星驷在学术上极力推崇孔孟程朱、著《崇孔辟邪录》,此外还治汉学,著《尚书一贯录》、《春秋传分图便览》等。其著作汇编为一百余万字的《郑星驷著述》(福建省图书馆有其手抄本)。林春溥授翰林院编修,后主讲于著名的福州鳌峰书院19年。林春溥著《春秋经传比事》、《四书拾遗》、《孔子世家补考》、《孔门师弟年表》、《孟子列纂补证》、《孟子后书补证》、《开辟传疑》、《古书拾遗》、《开卷偶得》等,汇辑为《竹柏山房丛书》。林春溥学术以宋学为主,兼治汉学,治经以性命义理和训诂考据并重,力图把宋学和汉学结合起来。他认为,朱熹学说虽集诸儒之大成,并未到顶点,后人又把朱熹学说发展了。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圣贤之言精微广大,无所不包,绎之有不尽之。”①因此,他认为朱子学必须创新才行。这是近代福建朱子学学者的一大特点。他提出“玄黄既判未有人而先有物”②的命题。林春溥又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人。人有血气性欲以相接则必争。故愚者常待命于智,而弱者常求庇于强,其智而强者因得结其辟而指挥之,如是者盖往往而聚,遂各据其方,各长其世,和相安,怒相并,大小分合又各就其胜己者而听命焉,时则有大国小国而莫统于一。③尽管林春溥这里讲的国家的形成、社会矛盾的产生是不科学的,但他认为社会国家的出现不是天意,也不是圣人之意,而是自然发展的过程,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是有合理因素的。
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福建朱子学主要以孟超然、陈庚焕、刘存仁、陈庆镛为代表,下面加以论述。
二 孟超然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孟超然(1730—1797年),字朝举,号瓶庵,福建闽县(今福州闽侯)人。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郎中、广西典试、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川督学等。
孟超然从政廉正,遇士有礼。《清史稿》孟超然本传谓他督学四川时,以蜀民父子兄弟异居者众,曾作《厚俗论》以箴其失。后来蜀民为之立“去思碑”。其他任职,亦政绩显著。①孟超然的主导思想比较守旧。例如,说王安石变法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并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把王安石视同蔡京、秦桧等。
孟超然于42岁时以亲老辞官归隐,杜门不出,潜心读书。后来主讲于福州鳌峰书院。孟超然在书院终日与门人谈经论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陈寿祺就是其门人。孟超然在《晚闻录序》等著述中,极力推崇朱熹思想,如谓“《朱子全集》其精深博大,不可不涉猎竟也”。孟超然面对当时汉学盛行,极力维护宋学的学术地位。他认为,宋学在某些支节上可能有所失,但是它是“王制”,是先王之道,是正统的孔孟之道,而汉学(“新学”)非王制。这是宋学和汉学根本区别之所在。其实汉学也是宣扬王制,他们注释的经书都是儒家经典;宋学和汉学的区别不在王制,而是在治学方法之不同。孟超然是从门户之见出发的。
孟超然的著述有《孟氏八录》(包括《丧礼略》、《诚是录》、《焚香录》、《求复录》、《晚闻录》、《广爱录》、《家诚录》、《瓜棚避暑录》)、《使粤日记》、《使蜀日记》、《屏庵居士诗文钞》等,结辑为《亦园亭全集》、《屏庵先生遗书》等。
(二)世界观
孟超然基于其“阴阳自然之理”、“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②的世界观,提出“人之贵贱寿夭系于天(按指自然之理),贤愚系于人(按指事在人为),固无关预于葬”③,不是天命决定的。孟超然认为星命堪舆之说的要害在于不相信人的作为,经不住实践检验,一经实践其原形即毕露。孟超然所撰述的《诚是录》、《丧礼略》等数篇,就是为破除星命堪舆家的风水迷信思想的,是孟超然思想中较为有价值的部分。
孟超然在《书熊公子星命册后》中对人的所谓命运进行了新的解释。他反对星命学家的宿命论,提出“不伐其天机”的“安命之说”,即认为顺其天理自然即是命。在孟超然看来,客观事物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如做生意者每日“赢缩大略可睹”。所谓“不伐其天机”,就是不要违反天时地利,遵循其发展规律。
孟超然认为,朱熹是反对风水迷信的。他说:
福建江西之明地理者以为朱子笃信堪舆。不知韦斋公之葬始或未善,则不得不迁(按指朱熹改葬父墓)。而孝宗山陵用台史言,则明置之迫狭之所、水石沙砾之中,为人臣子于此诚有所不安者,岂笃信葬师之谓乎(按指朱熹上疏极言不宜专用台史之说)?《尧山堂外纪》载:朱子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得人善地者,索笔题云: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①
对于朱熹两次迁韦斋墓、上书言孝宗山陵问题以及《尧山堂外纪》记载等是否因朱熹笃信堪舆,可以具体分析。但是,在朱熹思想中,相信堪舆星命还是比较严重的,如为其妻刘氏和自己选择墓地等。这里,孟超然是从门户之见出发的。
孟超然带头破除迷信,破除陋俗。他在《诚是录》中说:“我家葬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迄无他故。吾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于丧家尤甚。”②孟超然又说:
(其父死)去俗惑,初终不设乐师醮,不延僧道哭灵舆,饭舍时不易吉服,死之者不以僧道报亡,七七不作佛事,不祭冥王,朔奠不改晦日不设酒,三年内不赴酒食之会,不贺人喜庆事,凡此者皆反俗所为。③
孟超然以父丧破时俗,其目的是使人们“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④孟超然的这种做法和这种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孟超然指出,破除风水迷信是为了加强伦理道德修养。他说:
濂浦林氏三世五尚书……子孙数传俱谨守名节,不附权贵,簪缨累代。谁曰不宜?若使如严分宜(嵩)父子揽权纳贿,江西杨廖蔡师如林,能使之不倾覆乎?呜呼!观此亦可以悟矣。①
因此,孟超然提出只要一切举动“合乎理”就可以了。孟超然对“早晚于祖宗神明前再拜焚香”也做了说明,认为是“收摄心之法”,“心境一收摄,觉吾身无不当敬之事”。②
(三)内省体验的认识论
孟超然认为,众理先天地具于人的心中。“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之理,便无可贵。”心中所具之理,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本性。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是者为失其本心。庄周之非尧舜犹为寓言,嵇康之薄汤武亦有微指。其曰:“李贽之讥濂洛、毛奇龄之薄程朱,皆可谓之失其本心者也。”③因此,在孟超然看来,所谓认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存心。就是使心不要失散。孟超然说:“圣贤之学惟以存心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者澄然莹澈,广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视听言动一循乎理,好恶用舍各中乎节。”④又说:
暇时速须敛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义理。事物之来,随事省察,务令动静有节,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则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众理易明矣。此外别无着力处。⑤
这就是说,人之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道德本性,因有外界“物欲”所诱惑,有放逸、散失的可能,必须存心、守心。二是收放心。孟超然用《易经》复卦解释“收放心”,提出“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⑥等,以说明把失、放逸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心寻找回来。
对于如何达到存心和收放心的目的,孟超然提出主敬致知穷理。他认为,主敬致知穷理的过程就是存心和收放心的过程。孟超然说: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旧习之非,将日改月化于冥冥之中矣。(《晚闻录》)主敬致知,谨之于细微杂乱之域,而养之于虚间静说之中。⑦
孟超然认为,主敬为存心之要,致知为收放心(进学)之功,二者交发使用,则天理于心益固。在孟超然看来,这种主敬致知穷理的过程,是细微虚静,潜移默化的过程。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中反复说明,认识要接触实际。他提出“体贴人情即是体认天理”、“境遇中千头万绪皆是磨炼德性之资”。认识要学习和思考,主张“学须博乃可精”。孟超然曾提出为学四戒。其曰:“专守一家言者,隘也;泛涉而无归宿者,滥也;出言不知拣择者,秽也;务为夸大者,妄也。去此四病乃可以言诗言文。”①孟超然所概括的隘、滥、秽、妄四字学戒,确为至言,值得借鉴。孟超然提出静思的认识论。他说:
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②
认识要无偏见。他又说:“学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达,方于致知穷理有得力处。”③“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达”,就是思想上没有偏见,认识事物时没有成见,不带老框框。
(四)道德修养论
孟超然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是治心,治心之要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孟超然说:“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是为学之要。所以修身立命者全在此。近分为四门备载先儒之语,时时观览可以治心。”④“学治心之法,以惩忿窒欲为事,或冀持之,久久可以究养。”⑤“治心”、“究养”就是治本,“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以培壅本根,澄清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益光大而光明矣。”在孟超然看来,治本是对照圣贤教导,有过必改,就是变化气质。孟超然说:
吕成公(按指吕泾野)少卞急,一日诵《论语》,躬身厚而薄责于人。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朱子尝曰:学如伯恭(按指吕祖谦),方是能变化气质。⑥
孟超然这里所讲的转变卞急(躁急)性格,就是变化气质。人的本性(仁、义、礼、智)虽然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天理要和人的气质相结合,必须使气禀由浑浊变化的清明,愚不肖即为智贤。“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就是对己严,待人宽;自己严格履行伦理道德,以身作则,有利于影响别人。这即是道德修养的提高,气质的变化。
孟超然的这种通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是与其世界观和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孟超然以《周易》剥、复两卦和损益两卦所包含的“阴阳消长之机”加以论证。他认为,《易》言阴阳消长之机莫著于剥复(两卦)。《系辞》曰复以自知而不远之复,惟颜子能之;其次则困心衡为频复之厉最下迷复凶矣。他说:
吾不有自知者存耶?其往者或以为缘尘变灭然,吾不知之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象》曰山泽之象深下增高有损道焉,君子则以惩忿窒欲;风雷之象奋发疾速有益道焉,君子则以迁善改过矣。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其于复也或庶几乎!①
孟超然把这种“阴阳自然之理”用于道德修养上,就得出“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命题。“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反复下去,就可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进一步提出“纯乎天理”的道德境界。他又在《焚香录》中认为,这种境界是“仁体事而无不在,故道德统贯以仁”。就是说,“纯乎天理”的境界在道德行为上主要是表现为仁。在这里,孟超然还提出仁和孝的关系,认为仁中有孝,只是未发露出来。他说:
天下无性外之物,岂性外别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见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摄孝悌在其中,但未发出来,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与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无孝悌也,犹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济,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枣),非有彼而无此也。②
在这里,孟超然论证性与仁(包括孝悌)、义、礼、智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犹如气是从水、火、木、金、土和木是从梧、檟、樲、棘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一样。但是,孟超然所讲的仁、义、礼、智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无稽之谈。
孟超然极端鄙视那些言清行浊、言过其实的伪君子。例如,孟超然讲到湛甘泉时说:
湛甘泉讲学当时以为儒宗,又享眉寿。余最恨其晚年序《严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为天,文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矣。以八十岁老尚书献媚同年宰辅至于此极哉!近读嘉靖十一年冯子仁恩应诏上疏备指大臣邪正中云:礼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讲学素行未合人心,则知为侍郎日已不免人訾议矣。甘泉论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言,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③此亦可从反面看出孟超然之高尚。
三 陈庚焕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庚焕(1757—1820年),字道由,号惕园,福建长乐人,世居福州鳌峰坊。陈庚焕“幼年承家学,立志即希古贤儒,操行敦笃,充养和粹”。①所谓“幼年承家学”,主要是其母的教导。据记载:“母夙尝儆之曰:朱子之书不可不读,然汝终日把在手里何益?朱子一生作多少事,汝事至难断而诚不足动人,虽朱子之言背诵如流与汝何与?后贡士(按指陈庚焕)授徒尝述以勉后生。”陈庚焕早年主要是“读《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心有感奋,逐专务实践,不徒事文艺之学”②;后来,就学于福州鳌峰书院,专门研究张伯行所刊印的程朱理学著作。由于自清代乾嘉以后,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促使当时许多学者研究自然科学。陈庚焕写了《地球考》(上中下)、《南北极赤道考》、《云汉考》等五篇论文。这也说明他不是空谈心性的,也是关心世事的。
陈庚焕所著《性道图》、《果核喻性》、《五伦说》,显示出其朱子学思想的特点。他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以“行修”为线索,把朱子学的主要范畴贯串起来,形成了一种以“行修”为特点的理学范畴体系。陈庚焕说:
天人一理。天人一气。天,道所从出。命,天之所赋。性,心之所具。道,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理,在物为理。义,处事为义。德,行道有得于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有阴阳五行之理,乃有阴阳五行之气。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性即理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天,譬如朝廷。命.敕命。性,譬如敕内所载职掌。情,譬如官吏施行。道,譬如照敕施行各有法律。理,譬如事事皆有成例。义,譬如照律例断案。德,譬如老吏律例烂熟胸中,不用检案。③
由此可见,陈庚焕的思想体系为天命→性情→道理→义德。这就是说,天命具于人心为性,性之发为情,发而符合事物道理(中节),则表现为处事有义,对人有德。
陈庚焕明确指出,维护皇权就是维护天命,从而天下人才安居乐业,有好日子过。陈庚焕说:
天下的人多得很,人生一世事情也说不尽,只有五伦两个字可以包括。朝廷是个天,大家戴着天,才得好好的过日子。若不是靠着王法,那些横行霸道的人都要强抢强夺,不要说田房衣物等件保不住,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也不能相保了。所以君臣这一伦是第一件最要紧的,有了这一件才有那四件。普天下不论做官不做官,通是朝廷的臣子,大家都要依着朝廷的规矩法度,不要违条犯法,好好的做人,这才算顺了天。①
这段话反映了中国封建地主阶层守旧派对自己历史命运的恐惧心理。在陈庚焕时代,中国封建制度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中国即将进入近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陈庚焕还宣扬已被历代先进思想家批判得遍体鳞伤的天命论,说明中国封建地主阶层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到了穷途末路。
陈庚焕的著述有《童子摭谈》、《易堂德稳录》、《尊闻录》、《于麓塾谭》、《五经补义》、《二十二史图说》、《师门辧香录》、《约语追记》、《庄岳谈》、《谬言意言附识》、《北窗随笔》、《富德随笔》、《地球考》、《南北极赤道考》、《云汉考》、《性道图》、《气禀说》、《崇德同心录》等,结辑有《惕园丛书》、《惕园初稿》、《惕园全集》等。
(二)天道理气说
陈庚焕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天,认为“天,道之所由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譬如朝廷”。②陈庚焕说:
夫道散殊天地之间,万变而不可究诘,疑若至纷且赜不可以骤通矣。然其大原之于天。沿委溯源,由源达委,则不啻如川之流,脉络分明,分合千万里,而其始本无不通也。③
陈庚焕在《性道图》中认为,天是最原始的本原,天产生道,天通过“道散万殊天(按此处为自然之天,非本原之天)地之间”,“道,日用事物当行之理”,“道,譬如(官吏)照敕施行各有法律”;天与天地中万殊(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脉络、分合如川之流就是道,因而天与道的关系是源与委(端末)的关系。
陈庚焕讲到天和理的关系时,一方面,他把天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即理也。一气运行,以生物为心。天之主宰曰帝,即理气之主宰。另一方面,认为天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在物为理,一草一木具有至理,“理,譬如事事皆有成例”。④
陈庚焕在《性道图》中进一步指出,天之主宰即理气之主宰,就是“天有阴阳五行之理,乃有阴阳五行之气;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即天是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道理来化生天地万物的。对于阴阳五行化生天地万物的过程,陈庚焕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又说:
阴,气静为阴;阳,气动为阳。阴,顺;阳,健。静极复动,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阳,元(生物之始)、亨(生物之通);阴,利(生物之遂)、贞(生物之正而固)。木,其气发生不息。火,其气盛长分明。土,其气敦厚坚实,贯五行,分主四季。金,其气收敛斩截。水,其气流通澄定。①
尽管陈庚焕的这些说法是不科学的,但是他通过动和静、健和顺、元亨和利贞的对立统一关系把阴阳和五行联串起来,企图用气之发生(木)、成长(火)、收敛(金)、流通(水)和形成(土)来说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含有合理因素,具有某些辩证法成分。
陈庚焕认为,“天人一理,天人一气”。这就是说,自然界(天)和社会(人)都是天(本原之一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化生的。他说:
木,东方,春,仁(蔼然仁民爱物之心),恻隐。火,南方,夏,礼(秩然上下亲疏之序),恭敬辞让。土、中央,夏季,信(实仁实礼实义实智)。金,西方,秋,义(肃然收敛裁决之宜),羞恶。水,北方,冬,智(肃然辨别谋画之识),是非。②
如果说陈庚焕用阴阳五行之气来说明自然万物化生的过程还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和辩证法成分的话,那么他用阴阳五行之气附会五德则全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价值。
陈庚焕认为,天地万物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别性,其统一性在于它的理气性,其差别性在于它得理气之偏塞或正通。陈庚焕说:
天之生物一气而已,天之降命一理而已。气以成形,理以成性。性之理无形(按指为何物未定),即随形气而中寓。因此,一气之中得其偏且塞,而性亦因偏且塞者,则为物;得其正且通,而性亦得以正则通者,则为人。③
在这里,陈庚焕讲了千差万别的世界万物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理气,理气贯串于世界万物之中。
(三)以好善为中心的认识论
陈庚焕在《识警》中反复讲了认识论问题。他认为,就像“天之帝(理)主乎万物”一样,人之心(大脑)主乎人体,“少有痛痒,此心无不立觉也”;“一念之动,即上帝(理)临汝”。这就是说,主体有认识客体的能力,世界是可知的。陈庚焕说:
顿悟之见果不足恃也。夫人生动静皆在天地一气中,天之帝主乎万物,譬则人之心主乎百体也。人属于天,譬则百体之皮肉属于心。少有痛痒,此心无不立觉也。人之心与天之心本无一息不相通,则一念之动,即上帝临汝,固无待日月照临,始足有悚也。然众人之心鲜知天人之合一,至于对青天而不惧,则几于无忌惮矣,况与有闻于天人合一之理者乎!①
陈庚焕这里所谓“天人合一之理”,不是汉人董仲舒式的天人感应论,是指主观能认识客观,主观和客观是可以相一致的。不过,这里必须特别说明的是,陈庚焕所说的人心的认识对象天心(天命之理),主要的并不是天地万物,而是善与不善。在陈庚焕看来,所谓认识,就是认识道德的善与不善。陈庚焕认为,天下大矣,天下之事难知难行者众,而孟子以好善一言蔽之。人所以当大任成大功,未有不由此者。盖善量之无穷,而不可以一端竟。他说:
人无论智愚贤不肖,莫不各有所知,各有所能,即莫不各有所善。天下之善散在天下之人,以一人之耳目思求之,诚有所不足;合天下之耳目心思以共求之,曷尝不有余。②
尽管陈庚焕把认识的范围限制在认识善,但是陈庚焕提出求善必须“合天下之耳目心思以共求之”,就其抽象思维来说是合理的。
陈庚焕提出认识首先必须清虚其心。清其心,毋以欲汩之;虚其心,毋以己与之。陈庚焕清虚其心的思想,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要保持心的洁净。有洁净的心才会有正确的认识。所谓洁净的心,就是认识不要带着成见,不要先入为主。陈庚焕说:心者神明之舍。“明命之赫然,于是乎在上帝之临汝,于是乎式凭亦至严而不可亵矣。人于像设龛几之旁,未有敢加以污秽之物者,诚知其不可亵也。乃于神明所舍,顾使猥鄙之念憧憧往来,亵天之明,毋乃实甚。”③这就是说,认识不要带着成见,不要一味守旧,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认识。陈庚焕所说“神明之舍”不能有“猥鄙之念憧憧往来”,是比较深刻的。第二,主静、主敬要适当,不能偏着于静或著意矜持。陈庚焕说:
心本虚灵不可执滞。要常主静,若偏著静,则事物之条有不能顺应矣;要常主敬,若著意矜持,则跼蹐不宁而心反乱矣。①
这就是说,运用心,必须时时提掇光明,勿使滞,亦勿使放,不滞不放而至于不偏。在这里,陈庚焕对主静、主敬有新的见解。陈庚焕吸取道家的“虚”而剔弃其“无”,认为人心虚而实有,而不是虚而空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曾在其《太极图说》中提出,未有天地之前的“无极”是静的,因而人的天性是静的和无欲的。由此,理学家用主静来保持人的无欲天性。陈庚焕认为,人心有认识事物的能力,不能人为地控制人心对事物的认识(“心本虚灵不可执滞”);要常主静,但不能“偏著于静”,如果“偏著于静”就不能吸取新东西(“事物之条有不能顺应矣”);要常主敬,但不能“著意矜持”,即一味回避外物引诱,那就违反人的理性,使“心反乱矣”。因此,陈庚焕提出要达到“勿使滞,亦勿使放,不滞不放,则不偏”的主静、主敬境界。②陈庚焕又说:
人心方寸之中,空洞无物,而生意盎然中满。静则仁、义、礼、智、信五性悉涵此生意之中;动则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四端悉据此生意而发,推之亲亲、仁民、爱物,极之齐家、治国、平天下,厥施不穷,莫不本此虚中之一生意,则与是核之芽于虚,不正同欤!老子有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为形而下之器,言者信然矣。若夫形而上之道,则其无也,其虚也;其虚也,其实理之所由中涵也。然则仁之虚也,直不滞于有耳,而岂沦于无哉!③
陈庚焕这段话是对朱子学主静、主敬之说的绝好阐释,充实和发展了朱子学。
对知和行、学和用的关系,陈庚焕讲得更为深刻。第一,知和行、学和用相比,行、用更为重要。学必求有用,无用之学非学。陈庚焕说:
学也者将以修己教人、明道而经世也。理学之弊失之迂,心学之弊失之偏,文学之弊失之浮与杂。其究也,则皆失之伪,殊途同归均于无用,非徒无益而又害之。④
陈庚焕把理学、心学和文学分别概括为迂、偏、浮杂值得重视。他把不能修己教人、明道经世的无用之学看成是伪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第二,践履不完全仅是道德实践,还包含有事功实践之内容。要经世和修身并重。陈庚焕说:
学须见诸实事。若作官者必征诸实政。居高位而不能进贤、退不肖,为民兴利除弊,空谈学术性命,无益也;日用伦物之间事实行之,方是实学。①
所谓经世,盖只是求其有用也。书生虽未有经世事。然经世之本在身,源在心,其端在一家一乡。读书而以之诚自治其身心,抵之以料理一家一乡之事,各得其理,方为有用。②第三,强调行、用要贯彻认识过程的各个环节。陈庚焕说:
以实心读圣贤之书必返躬以体其实,以是心权天下之理必随时以处其中。言道言教必本人伦而不为高论,言敬言静必切日用而不为空谈,毋事门户必折衷于圣人,毋事安排必徐候其自得。如是以为学,则有体有用而无差,如是以为教,则易知易从而无弊。如是以为文,则明经之文足以适用。③
在陈庚焕看来,“孔门之论学,必归诸人伦之大,行必尽诚。”④“学贵能行。朱子一生作多少事?汝事至不能断,而诚不足以动人。虽朱之书日把在手里,何益?”⑤陈庚焕特别强调“行必诚”,体现在自己身上。方志有谓庚焕“学务实践,以程朱为宗,每日言动必簿记以时时省察”。⑥
(四)人性论和道德伦理思想
陈庚焕把心看作是“神明之舍,譬如官府衙门”;而“心之神明,譬如舍中之主人翁也”。⑦陈庚焕说:“是神明者,固天之所降,而人所以与天通,所谓人为天地之心者也。”⑧在陈庚焕看来,所谓“神明”,就是指人的聪明才智,人的认识和体验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有的;因为人有这种能力,所以在宇宙的三大组成部分天、地、人中,人为核心。
陈庚焕反复说明,人心中之“主人翁”具有聪明才智,其表现在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上,而五常之性是天命所授予的理,即天理。天理(五常)是“舍(心)中”之“主人翁”(神明)的“祖父”所给予的,是供其应万事之用的。他描述了天、理、心、神明、五常之间的关系。他说:
程子曰心者,神明之舍。然则心之神明,譬则舍中之主人翁也;性者心所具之理,譬者舍中之器物也;天者理之所从出,譬者舍中器物本祖父所留贻也。心之所具之理,譬则主人翁之收其百器万物也;其以众理应万事,譬则以百器百物供百事之用也。①
他还对“神明之舍”(心)中的“器物”五常(天理)作了详细的论述,发前人所未发。
陈庚焕指出,人心中所固有之天理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做人的规矩,一举一动都能遵循此规矩才是人,否则就不是人。天理五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是人的本质,是人与物的界限。大家心上本来都有这个道理,其实只在该不该上分别。“一举一动都有个规矩,依着规矩才像个人。”②要晓得这礼节规矩都是天地自然的道理,不是古来制礼的圣人强加给人的。
陈庚焕认为,人们的气质有昏明薄厚弱强之不同。他用糖和米屑合成糖粿作比喻。糖之性甜,似理之性善,糖胜米屑则味甜,犹理胜气则禀赋之质好。陈庚焕说:
盖糖,性也;米屑,气也。炊屑成粿,气以形成也。合糖于屑,气形成而理亦赋焉者也。既出于甑,则见米屑所成而不复见糖。气有质而理无形,道心之微也。糖之本甜犹性本善。既杂于屑,则不能自全。其天味之完否?一因乎屑,气质之性有所囿人心之危也。糖与屑相济则甜美,赋质之纯者也。屑胜糖则味减,赋质之偏者也。③人之生也,既同得此正且通之气矣,而其质之所禀,昏明厚薄强弱之不齐,其等级差次至不可以数计,则又何也?盖即同此正且通之气,而其发也始必厚而烽(自注:俗所谓气头),及其长也必薄而力减(自注:俗所谓气尾),其精而上浮者必清而明,其粗而下沉者必浊而昏(自注:俗所谓底面),固有不能齐者矣。又况所谓昏明厚薄强弱者,又复相盈相摩滚同混合于流行消息之中,其纷错杂糅又安可以究诘,惟圣人之生于纷错杂糅之中独值其精粹不错者而禀之,自圣人而下则皆随其所值之纷错杂糅而各禀以为质。则其昏明厚薄强弱之参错不齐又何足怪哉!④
这里陈庚焕讲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用理气来解释人的同一性和差别性。二是指出人有等级差别的原因:(一)其气之发生作用的时间先后不同,(二)其气之精粗不同,(三)其气之互相摩擦运动的结果或精粹或杂糅不同。在这里,陈庚焕用比喻的方式把人的气质说得很清楚。
陈庚焕提出必须先认识天理,然后以天理去剖析道心和人心,变化气质,使道心常存,人心听命,依理而行,便呈现出五常之德。陈庚焕说:
学者即此寓于气中之理,辨其孰为受命于天、不杂于气之道心(自注:仁义礼智信之本心是也),孰为性杂于气,写形俱生之人心(自注: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心是也)。辨之必审,是之谓惟精;养其理道之本心,使无少放逸而或动于血气。范其情欲之人心,使无少纵肆而害其本心。持之必坚,是之谓惟一。①
陈庚焕这里所谓“养其理道之本心”,就是使道心常存(即“无少放逸”);所谓“范其情欲之心”,就是使人心听命(即“无纵肆”);所谓“惟精”、“惟一”,就是要体会和懂得人心、道心这种精微的道理,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存道心去人心、存天理去人欲。
去人欲而存天理就是事天,遵循天理五常之德。陈庚焕提出畏天、循理、待人三个方面为事天之要。他说:“畏天:天生我为人,要我循道理;无理逆天心,哪得天心喜。”“循理:既做读书人,如何不循理。”“待人:待人当如何?近情与近理,要决只一言,将心比心耳。”②陈庚焕之所以把待人也作为事天之要,就是因为“人事尽,始可以言天”③,事人即为事天。
总之,陈庚焕尽心、知性、知天、事天的命题,发挥了人心中以仁为核心的五常之性,就认识了人的本性;认识了人的本性,也就认识了天理;保存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就是事天、畏天、循理、待人,是事天的最好形式。
另外,陈庚焕还把这种心、性、天三者结合为一体的思想概括为“道之体用”,即知和行的问题。上面提到的陈庚焕讲的惟精和惟一,就是知和行。陈庚焕说:
道之体用。穷理养心,使此理常明,此心常存,方寸之中纯是天理,都无人欲,活活泼泼、不偏不滞者,道之体也;及至举念、说话、做事都从此活活泼泼不偏不滞的心里发出来,便自然有个好的道理,再不至差了念头,说错做错,这便是道之用。④
在陈庚焕看来,“道之体用”就是道的本体和作用。尽心、知性、知天、言性、言理,使心中“纯是天理,都无人欲”,就是道之体;“举念、说话、做事”都遵循天理五常,就是道之用。在陈庚焕看来,分析道之体用极端重要,“体用二字剖析精明,故得其旨皆不蹈虚谈性命之讥,亦不流穿凿支离之弊”。①在体和用之中,陈庚焕把用看得更为重要。陈庚焕说:
程朱以后性理之书备矣,学者粗涉其书即可拾其唾余。言性言理都不难。剖析精微惟五伦二字,必要认得实理,切实行到恰好地步,善乎!汤文正公汤斌有言:开口说太极不准,切实行五伦不易。②
这是反对空谈性理,把抽象的性理拉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强调用五常之德的践履体现性理。
四 刘存仁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刘存仁(1774—1850年),字炯甫,又字念莪,晚号蘧园,福建闽县(今福州市闽侯县)人。宣宗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曾入林则徐幕府,为林所信任。历官甘肃渭源、永昌、平罗等县知县,甘肃泰州、直隶州知府。晚年被聘为福州道南书院院长。
刘存仁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陈寿祺的门人,一生笃信程朱之学,其在主持福州道南书院期间,朱子学思想臻至成熟。刘存仁认为,宋代学术最为昌明。他说:
宋世理学昌明,大儒辈出,《语录》、《性理》诸编,圣学之阶梯,大道之途径,躬行实践以求义理则甚精,以求经济则甚实,明体达用厥功懋矣。③
他认为,理学在宋代并不是空疏不实之学,而是“以求经济则甚实,明体达用厥功懋”。他提出“道(按即理学)外无儒,儒外无道”的观点,认为“通经学古”、治理学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儒学。刘存仁说:
元史臣之撰宋史,始以道学、儒学等分为二传。后之言程朱之学者空疏无据,不复以通经学古为务,于是谈复古者用是为诟病,以考订为是,以训诂为功,其甚者欲尽废程朱而宋汉,穿凿附会,琐细驳杂,而学愈晦,不知道外无儒,儒外无道。④在刘存仁看来,当时治汉学(考据学)的人是程朱理学末流,也是程朱之学者。他从经世致用观点出发,对古今学术提出一些较为客观的看法,具有折衷调和论的特点。他认为,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其实门户之见未融,逞私心而轨于公道者。汉承天学之后,递禀师承,其学者笃信师说,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其弊杂之以纤纬,乱之以怪僻。他说:
宋世名儒辈出,摆落杂芜,独标精蕴,于圣人之旨为近。要之,汉学自有根柢,不得以浅陋讥之;宋学俱有精微,不得以空疏目之。故吾谓今日学者贵通汉宋之邮而得其要领。依声附影、随俗转移,无当也。①
刘存仁这里所谓汉学,是指汉代的经学,不是指清代的汉学。刘存仁认为,清代的汉代经学“训诂相传莫敢相异”、“根柢”深;清代的汉学“猎词华以博取利名”,“以荣辱为欣戚”。刘存仁说:今世之学猎词华以博取科名,而于心身性命之理、人伦日用之常置而不讲。“名心一炽,弛函纷华。得志则利禄汩没,失意则英华销损。以外来之荣辱为欣戚,于德性毫无所补。”②刘存仁这里所谓“外来之荣辱”,是与心内“性命之理”相对讲的。刘存仁把科名、利禄、失意等称为“外来之荣辱”,把性命、道德之修养看成是内心反省功夫。
刘存仁对陆王学说不持门户之见,不因人废言。南宋时,在朱熹和陆九渊鹅湖之会上,朱曾指责陆为学“易简”,即不做格物读书穷理工夫而直接体验“心即理”。此后历代朱子学者大都坚持朱对陆的这种观点。刘存仁却肯定了“易简”功夫的合理性。刘存仁说:
天地之道,易简而已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③
刘存仁认为,天地的运动变化就是易简,通过易简方法“天下之理得矣”。刘存仁对王阳明的主静说亦作了肯定,认为是符合程子的动静之理的。刘存仁说:
始悟程子静亦定、动亦定之理。嗣读阳明先生答伦彦式书发挥透彻。其书云: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循理焉,虽酬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④
周敦颐认为,在未有天地之前的“无极”是静的,因而人的天性应该是“静”的和“无欲”的。王阳明认为,静不是不动,循理无欲即谓静。只要是循理,“酬酢万变”亦谓之静。在刘存仁看来,王阳明的这种观点是和周敦颐的“主静无欲”是一致的。
(二)哲学和政治思想
在刘存仁的世界观中,天、性、理三个范畴具有相同意义。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则性,性即理,因此天、性、理是一致的。性、理的大原是天,那么天是怎样的呢?刘存仁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以无心而成化也。”①刘存仁把天看成是客观事物变化的现象。“天以无心而成化”,就是天是自然而然的,它是没有意志的。天既如此,天理寓于事物之中,即为事物之性。刘存仁所谓天即理、理即性,就是天、性、理统一于事物之中。
对于道,刘存仁也是力图到事物中去寻找。他认为,道存在于人伦日用和诸文之中。他说:
道寄诸文。文者贯道之器,道与器二而一者也;制义代圣贤立言,必词依乎质,又当乎理充实完满而无一毫之亏。②
在这里,他把文章看成是载道(义、理)的器具(质)。他的文是指“代圣贤立言”和“世之知言者”,即正确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文章是载道(义、理)的器具(质),是道(义、理)得以表现出来所依赖的质(器具)。刘存仁的这种说法是有合理因素的,是与今天所讲的语言(包括文字)是思维外壳、是思维工具的观点相接近的。
对于世界万物是怎样从天、理、道这些本原中产生出来的,刘存仁提出“食色性也,阴阳理也。氤氲化醇,万物化生”的观点。他说:
二气流行,寒暑循环。一气贯注,天地得之以立心,人物得之以立命。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言而万理毕。③
天地间人情物理,纷纭蕃变,理一以贯之。刘存仁认为,阴阳“二气流行,寒暑循环”的过程,就是自然界(天地)和社会(人)产生的过程。刘存仁借用孔子《论语·尧曰》中所说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说明世界万物产生的情况。这就是说,阴阳二气流行、循环产生天地万物的道理是非常微妙的,这种精微和唯一的道理就是合乎中庸(不偏不倚)的要求,即“天地间万事万化无不本诸中和”。本来,“惟精惟一”是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①即人心物欲危险和道心伦常微妙;“允执厥中”是指应该体会这种微妙和唯一的道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中庸(不偏不倚)。②
对于人能否认识天地万物,刘存仁作了肯定的回答。刘存仁认为,主观和客观是会发生感应的,“夫感者物也,所以感之者,吾心之神也”;“心气和平,则事理亦通达矣”。“凡事有一定道理。所谓方也,必此心清明,于道理上见得圆满充实,无一毫之欠缺,而后折中至当。顺事恕放,故曰知者不惑”。他说:
人心惟思为最虚最灵,万籁俱寂,胚胎未形,腾九天而入九渊,神妙变化,不可方物,思路绝而风云通,思之思之,鬼神亦将来告知,而沉于人乎?《管子·内业篇》云: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报也。故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是以鼓之舞之以尽神。故曰神而明之者存乎人。又曰知几其神。当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夫感者物也,所以感之者,吾心之神也。神与神遇而情生焉,有不知其情生文、文生情也。③
在这里,刘存仁讲到人心惟思,它要依赖由胚胎发展而来的物质器官。讲到了人的思维要有物质基础。在这段中,刘存仁详细地讲了主观是能认识客观的。由于主观能认识客观,刘存仁提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天下事无不可为”。④
刘存仁还深刻地讲了知行的问题。他认为,行难,必须在“窒碍难行处见得道理圆满充实,方是理足”。“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何能事事称意,必于窒碍难行处见得道理圆满充实,方是理足”。应事接物到恰到好处最难。孔子之从心不踰矩,朱子不偏不倚之谓中,还要依理而行,“应事接物到恰好”。⑤
刘存仁承认古之圣贤是先知先觉的,有“扶世翼教”、“担荷宙宇之责”。刘存仁说:
上之圣经贤传,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有维持风教、担荷宇宙之责,不忍一夫之失所,大声疾呼,偕之中道,赞助元化,保合太和,用以扶世翼教,使之家喻户晓焉,所谓圣为天口也。①
在这里他把圣贤看成是“天口”,是依天命教化人的,因而圣贤对人们是“偕之中道,赞助元化,保合太和”的,即人们完全是圣贤培育起来的。在这里,刘存仁就把我们前面叙述的他的认识论的一点合理成分完全取消了。
在变化气质问题上,刘存仁特别强调存心养气。在刘存仁看来,存心为道心,道心发之气为道气,道气即为勇气。刘存仁认为,存诸心者为道心,则发诸气为道气。刘存仁认为,“人固当存其心,亦不可不致养其气。大将提百万之师,一鼓作气,置之死地而后生,试之危地而后存,气足以胜之也。”“道义而塞天地,其本归于不慊则馁。说理充实圆满,即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之意。”“千古之忠臣志士孝子悌孙义夫节妇皆一气所弥纶鼓荡,亘万世,横四海,以维持不坏。”在这里,刘存仁所谓的气虽似气节之气,但是他比之道义,是忠臣志士的勇气,“弥纶鼓荡,亘万世,横四海”,是无所畏惧的。
在近代,地处沿海的福建,深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更加激发起人民的爱国热忱。因此,这时的福建人特别强调要有勇气、志气。福建侯官人林则徐销毁英国鸦片烟的勇敢精神,就是其佼佼者。清代福建朱子学学者大都提倡志气、勇气,就是基于这种时代精神的。
刘存仁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人民,要兵民联成一气才有力量。他说:
兵与民联为一气,迨至兵与民合,而气愈旺守愈固,外匪闻风而胆落,此不战而击人之上策。②
刘存仁反对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太容忍的不抵抗主义。刘存仁以南宋对金的容忍为例来说明忍害之大,以激发广大人民和清政府中的爱国官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坚决抵抗,决不容忍。
同时,刘存仁还提出一些变法主张和加强边防的军事措施。当时社会需要变革,刘存仁虽属守旧派,也看出一些社会的重大问题。穷则变,变则通,边防的军事措施也要变革。他说:“龚海峰先生坚壁清野之义诚有可采。但南北异宜变通,利用古书犹古方对症下药,知加减变通者为良医。”③
五 陈庆镛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庆镛(1745—1858年),字乾翔,号颂南,学者称颂南先生,福州人。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给事中、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等。
陈庆镛极重视经世致用,他为政“留心经济,不汲汲为仕,凡军实之所储,度支之所出,边备之所防,河渠漕挽之所疏浚,输讲画条贯物得要略而后止”。①陈庆镛主张渡江重平夷之策,反对外国侵略者。他曾向朝廷提出御寇之策。他说:
盛京之奉天,直隶之天津,江苏之崇明,浙之定海,闽之厦门、福州,粤之虎门,山东之登州,备各战船十只或四十二只堵截要害,以俟其来者而应之,所向披靡。②
此外,陈庆镛还屡次上疏建议朝廷在台湾加强武备,防止和抵抗英国等帝国主义者侵略。他还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干涉中国内政,对卖国投降官吏深恶痛绝。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批评朝廷起用已治罪的皇亲卖国贼琦善、奕经、文蔚等人是刑赏失措,致使皇帝复革琦善等人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于是,陈庆镛“直声震海内”。③他以正直敢言的御史名世。
陈庆镛服膺宋儒,而又精研汉学,覃心考据于声韵文字之学。其治经务求是,以致用为目的。他曾自题“六经宗孔孟,百行学程朱”④的楹语。陈庆镛认为,汉学、宋学的共同点都是主张明经致用,都推崇圣贤。陈庆镛说:
汉人多讲阴阳,而宋人则专主理数。《易》旨无穷,当合汉宋而通之,无门户之见,乃可以言《易》辞,言六爻,发挥旁通。⑤
他认为,言象言数不如言理为密。应以理为主,象次之,数更次之。陈庆镛所谓“汉人多讲阴阳”,是指西汉董仲舒一派的“天人感应论”。天人感应论通过歪曲先秦阴阳五行学说,用阴阳五行把天与人沟通起来。陈庆镛认为,《周易》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宋儒专讲《周易》中的理是不全面的,应吸取汉儒关于《易》象、数的观点。陈庆镛这种反对门户之见的治学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
陈庆镛提出对各种学说都应该兼收并蓄。他说:
学为有用之文,则又本之《易》以导其源,本之《书》以充其识,本之《诗》以博其趣,本之《礼》以究其精微,本之《春秋》以考其得失,本之马、班、范、陈以助其波澜出入,本之管、韩、庄、列以极其苯䔿奥窔。①
陈庆镛认为,凡是有用之文都应该学习。他举出《易》、《诗》、《礼》、《春秋》以及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管子、韩非、庄子、列子等诸子之书,都要学习。
对于陈庆镛的人品性格、学问事功和启迪后学的情况,其门人龚显曾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述,其曰:
(吾师)诵谏草者,成舌挠不得下,海内名俊,想风望采,蹑履投刺,争以一瞻颜色者为幸,晷盖无虚。先生植品既高,文章学问,又足牢笼百氏,震动时贤。于是有阮文达公元孙,先生经世之师;何先生绍基、魏先生源、张先生穆、苗先生夔、赵先生振作、朱先生琦、梅先生曾亮诸君子为元友;何先生秋涛为之徒,相与挋刷精思,切劘道谊,学益懋,品益高,而名亦益显。然后知执一卷奏议以重先生者,其不足以概先生而儤先生也。②
何绍基、魏源、何秋涛等是近代著名的学者,皆为陈庆镛的友徒,由此可知陈庆镛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
陈庆镛的著述有《齐侯罍铭通释》、《籀经堂钟鼎文释题跋尾》、《说文释文校本古籀》、《三家诗考》等,结辑为《籀经堂类稿》。
(二)器识论
在陈庆镛的哲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器识论。陈庆镛所谓“识”有世界观之意,是为学为文的指导思想。陈庆镛说:
夫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无其识,其词不足以达识。苟足以达矣,而或谓过高之论,或限以一丘一壑拘于墟而不足以观河海之大也,局于量而不足以仰泰山之高也,又何以称于其后及久而不衰。③读叙谱状叔寿兄诸文,得其所以立爱之道焉;读赠言劝友慎交诸文,得其所以交游之道焉;读论经论史论子诸文,得其所以为学之道焉;读议兵、议律、议法、议钞弊、论海道诸文,得其所以行政之道焉。夫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非其学之大不能见乎道之源也,非其议之一高不能达乎政之本。有其学有其识,宜出而膺司牧之职慰苍生之望知。④陈庆镛在这里提出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命题是深刻的。学者首先要有一定的世界观,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达识”,即具有高的思想境界;“见乎道之大原”、“达乎政之本”、“称于其后及久而不衰”,才能不流于就事论事、经不起时代的考验。陈庆镛还特别强调,“有其学有其识,宜出而而膺司牧之职慰苍生之望”,就是见其文和其才知其所能而为众望所归。陈庆镛的这些议论表明他主张文艺要把思想摆在第一位,艺术摆在第二位。
陈庆镛以“器识”为中心,进一步提出明、论、辨以及精、广、妄、疏等为学诸范畴。他认为,识足以达时事之宜,明足以破千古之蔀,论足以剪繁芜之失,辨足以息群喙之鸣,然后驰骤纵横,必求于是而后止。故治经贵精力,治史贵广博,读未数行辄评隙,失之妄,读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断、失之疏。在为学中,陈庆镛认为,有“识”才能为当世服务,有“明”才能破千古之蔽(蔀),有“论”才能找出发展规律,有“辨”才能胜于别人,“识”、“明”、“论”、“辨”都具备了,就能“驰骤纵横”、应心得手。“治经贵精”,才能“失之妄”;“治史贵广”、“失之疏”。①陈庆镛这种对为学之德和为学之方的概括是深刻的。
陈庆镛还认为,学者如果没有“器识”,为学既“不能入”,尤“不能出”。“不能入”和“不能出”是学之大患。陈庆镛说:
凡学之患,患于不能入,尤患于不能出。丛籍鳞次,手翻翻不辍,一辍辍遗,即偶有一二得心,而于古人回穴奥窔终莫能晰,饾饤耳食,如是者不能入。又或紊昔贤往事,钩稽条画,谓某也醇、某也肆、某郅隆。②
在陈庆镛看来,所谓“不能入”就是“手翻翻不辍、一辍辍遗”,一点也学不到手;即使偶然有一点心得,也不能分析,而且一耳进一耳出,很快就会忘棹。所谓“不能出”,就是学了不能用,虽讲得头头是道,均与原意不合;特别是眼高手低,自己不会执笔为文。这种对为学之患的刻画真是绘声绘色。
陈庆镛特强调,为学处世都要务实,他名自己的书屋为“实事求是斋”。他提出要随实应化,不能虚浮,不可拘泥于前人古人之言。“圣人不凝于物而能与世推移”。③陈庆镛说:“参伍错综,惟变所适,不可以孔子之言泥周公之言,更不可以周公之言泥文王之言。”④又说:
列子谓燕人而长于楚者老而归于燕,过鲁之城社,或绐以为燕也,愀然变容;过冢墓以为先人之陇也,泣然流涕。及真见燕之城社庐墓悲心反减。今世之大家勋阀往往援疏旗之贵者显者联为谱系,傅会成书,相与叙及,辄曰我伯叔兄弟也,而于其真伯叔兄弟漠然概不相关,是何异燕人之见绐者据以为真而为有识者所窃笑哉。①
陈庆镛所举的《列子》等的例子,就是强调务实,反对浮夸虚言。尽管这些例子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但是它说明了认识论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陈庆镛把圣贤之道归结为仁、义、礼、智、信五伦,五伦具即为道心,并对五伦作了言简意赅的解释。陈庆镛对五伦和道心的解释有点独出心裁,值得注意。他说:
圣贤之道无他,付诸心之谓仁,施诸当之谓义,止诸节之谓礼,达诸事之谓知,践诸实之谓信,全而合之之谓道心。得乎道之谓德。圣人之所为,不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如是焉已。众人之所为,亦不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与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如是焉已。孟子曰:圣人,人伦之至也;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尧舜无难知难从之事,而人则不如尧、不如舜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于是卤莽灭裂之言盈天下,张道益炽而离道益歧。②
陈庆镛认为,圣人和众人之所为是一样的,皆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与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因此尧舜与人同耳。尽管这种“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古已有之,但是陈庆镛这里是为说明“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是有现实意义的。③
陈庆镛提出要从自己日常生活和周围具体事物做起,就能达到所要求的思想境界。陈庆镛曾谓:“儒者有闻过相规,见善相示,余常持此以论交。”④
附注
①《四书拾遗自序》。
②《开辟传疑》。
③《开辟传疑序考》。
①《清史稿》卷四七九《孟超然传》。
②《瓜棚避暑录》。
③《诚是录》。
①《诚是录》。
②《诚是录》。
③《丧礼辑录序》。
④《诚是录》。
①《诚是录》。
②《瓜棚避暑录》。
③《瓜棚避暑录》。
④《求复录》。
⑤《晚闻录》。
⑥《克省录序》。
⑦《求复录》。
①《瓜棚避暑录》。
②《诚是录》。
③《晚闻录》。
④《焚香录》。
⑤《答郑云门书》。
⑥《求复录》。
①《克省录序》。
②《瓜棚避暑录》。
③《瓜棚避暑录》。
①[清]余潜士:《惕园全集序》。
②以上见《畅园全集·乡贤事实》。
③《性道图》。
①《五伦说》。
②《性道图》。
③《无恩而无不通为圣人论》。
④《性道图》。
①《性道图》。
②《性道图》。
③《气禀说》。
①《识警》。
②《好善伏于天下论》。
③《故纸随笔》。
①《约语追记》。
②《约语补录》。
③《虚仁李说》。
④《问学赘说》。
①《约语追记》。
②《与余耕顿茂才潜士书》。
③《问学赘说》。
④《永福余而遂七十寿序》。
⑤《与余耕邨才潜士书》。
⑥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
⑦《尽心近譬》。
⑧《故纸随笔》。
①《尽心近譬》。
②《谈五常》。
③《糖粿喻气质之性》。
④《气禀说》。
①《气禀说》。
②《童子摭谈》。
③《与陈茂坚书》。
④《与余耕顿茂才潜士书》。
①转引自[清]陈宗英:《惕园先生行述》。
②《约语补录》。
③《劝学刍言》。
④《劝学刍言》。
①《劝学刍言》。
②《与姚懋勤书》。
③《劝学刍言》。
④《立志说》。
①《劝学刍言》。
②《刘石湖制义跋》。
③《劝学刍言》。
①《尚书·大禹谟》。
②《劝学刍言》。
③《劝学刍言》。
④《劝学刍言》。
⑤《送五弟晓农之福清序》。
①《送五弟晓农之福清序》。
②《屺云楼文钞·复倪粹卿书》。
③《屺云楼文钞·复倪粹卿书》。
①《李梅生小芋香馆诗钞序》。
②《苏鳌石亦佳室诗文钞序》。
③道光《福建通志》总卷三八·分卷五。
④道光《福建通志》总卷三八·分卷五。
⑤《蒋慕生“易”说引》。
①《彭仲山无近名斋文钞序》。
②《籀经堂类稿序》。
③《郑云麓先生文集序》。
④《彭仲山无近名斋文钞序》。
①《吕西邨类稿序》。
②《吕西邨类稿序》。
③《蒋恭生易说引》。
④《易经儿说序》。
①《福州郭氏族谱序》。
②《郭榴山易录序》。
③《郭榴山易录序》。
④《张石洲烟雨归耕图序》。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