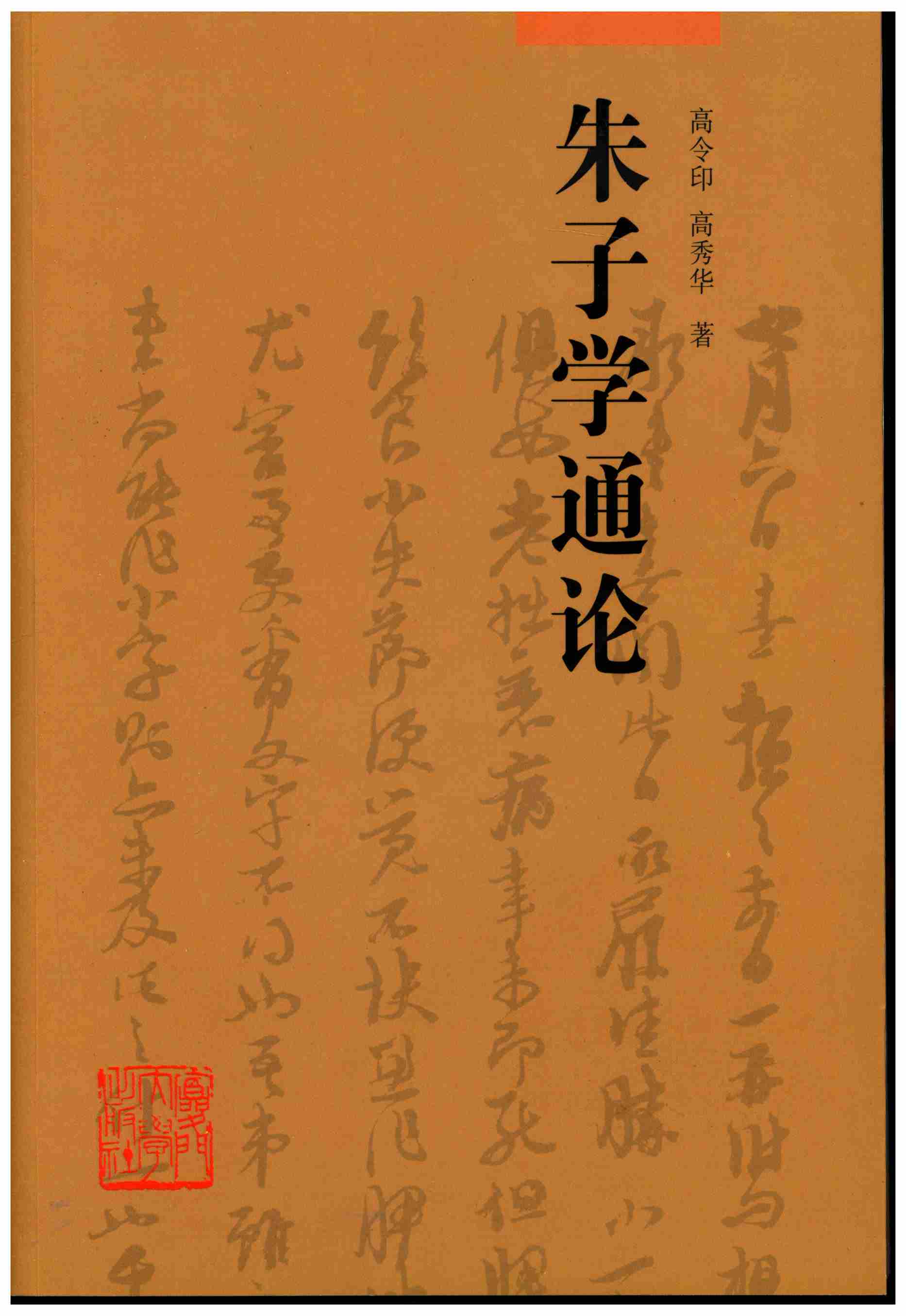内容
一 概述
朱熹之后的朱子学,基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朱子学的发源地福建(闽中)与全国的朱子学衍变和发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分开来论述。本章先论述闽中的朱子学(闽学)的传衍分化和派别,全国性的将在下面论述。
南宋王朝是与北方金朝的对峙而存在的。后来,蒙古族的元朝崛起于漠北,宋朝联蒙攻金,于1234年灭金;1270年蒙又灭宋。蒙灭宋后,其首领忽必烈任用汉化契丹人耶律楚材,并经宋降蒙的儒生窦默、姚枢、许衡、刘秉忠等人策划,取《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在元朝统一中国的90年(1280—1368年)中,利用儒家的政治制度来统治全国。由于蒙古族的经济、文化比宋、金落后,他们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尤其残酷,横征暴敛,赋役极重。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对汉人和南人仇视。福建是南人居住的主要地区之一,福建人受元朝的剥削压迫最为严重,反抗元朝统治也最为激烈。这种社会环境对福建朱子学具有深刻的影响。
蒙古贵族统治者在思想上利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宋朝遗留下来的一批儒学家,如窦默、许衡等都被请到朝廷,有的任国子监丞,专门传授儒学,他们被称为元代大儒。在儒学当中,蒙古族统治者又特别提倡程朱理学。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很快由福建地区发展到全国。清人皮锡瑞说:
朱学统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时,程学(按指二程洛学及其后继者朱子学)盛于南,苏学(按指宋时蜀学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姚枢、许衡、窦默、刘因辈翕然从之。①
朱子学原盛行于福建,在元初由闽而至江、浙、皖、赣、两湖、两广、冀、鲁、晋、豫、川、陕等。
至元仁宗时(1312—1320年),朱子学遍及全国。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义军推翻元朝,在南京称帝,国号为明。朱明王朝存在了270年之久,国势在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达到了顶点,到了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7年)由盛而衰,史家称为前期。从朱子学在明代的发展来看,与其相对立的王阳明学说兴起于嘉靖初年,此后朱子学在明代由独盛而稍衰,使明代朱子学形成为两个不同的时期。
元代全国朱子学盛行,相比之下似乎福建朱子学不如全国。当时闽籍朱子学的主要学者如熊禾、陈普、吴海等,没有居于全国地位。其实,从学术思想上看,当时福建的闽学并不落后于全国朱子学。一些主要的福建闽学学者之所以未居于全国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民族气节,不仅不肯仕宦于朝廷,有的还积极进行反抗,因而不仅得不到朝廷的褒扬,还受到诬蔑和打击。他们隐姓埋名,深居山林,从事于教育和学术活动,为士人所罕知。他们忠实于朱熹的思想,是真正的朱子学者。当时,福建闽学人才济济,除下面将要评述的熊禾、陈普、吴海等外,知名者还有丘葵(字吉甫,同安人)、韩信同(字伯循,宁德人)、欧阳光(字以大,长乐人)、张复(字伯阳,建瓯人)、黄镇成(字元定,邵武人)、刘有定(字能静,莆田人)、张复(字伯阳,建瓯人)、黄清老(字子肖,邵武人)、林广发(字明卿,龙溪人)、陈旅(字众仲,莆田人)、雷杭(字颜舟,建瓯人)、陈自新(字贡义,宁德人)、李应龙(字玉林,光泽人)、郭堂(字德基,长乐人)、郑仪孙(号翠屏,建瓯人)、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人)等。他们大都一生从事于朱子学,各自著作数种。
在明代前期,闽籍朱子学学者忠实地阐发朱熹学说。例如,林瀚(字亨大,闽县人),学术醇正,以朱子学为宗,在朝廷正直无私,不以皇帝和宰辅颜色行事,不计较利禄,为世所敬重;林玭(字廷珍,侯官人),以朱子《易》学倡教东南,学务穷理,笃于躬行;郑守道(字用行,侯官人),著《太极图说解》、《大学解》,旨精袐具,全是朱子学风格,有功于后学,等等。
宋元之际至明代中叶,福建朱子学与当时全国朱子学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或者叫做优点。
第一,这个时期福建的朱子学学者大多数坚持朱熹的民族气节论,不肯到朝廷做官为蒙古族统治者服务。熊禾、陈普在南宋末年曾任过地方官,入元后朝廷几次征召不出,甘受贫困,宁可饿死。郑仪孙在宋亡后隐居山林不仕。敖继公中进士后归里务农。邱葵力辞元官。吴海生活在元朝末年,也未曾出来仕元。
第二,福建朱子学学者务实学,强调“躬行”。他们认为,道并非超出于人事之外,道即在人事之中。他们讲学和著述的内容务实切近,反对好高骛远。他们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把“躬行”看成是精义理。他们激烈抨击当时一些空谈心性的理学学者,明确提出研究理学的目的是为了道德践履。他们把朱熹关于“知行相须互发”的观点发挥为要重视“躬行”的实学。
第三,这个时期福建朱子学学者大都潜心于“五经”、“四书”的注疏。他们视注疏“五经”为务本之学,多自幼即为之。由于他们不想仕元,不随流俗,因此他们所注疏的“五经”有自己的特点,以经注发挥朱子学思想,有功于后学。例如,熊禾是元朝的经学家,除《仪礼》外,他对《诗》、《书》、《易》、《春秋》、《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等皆有注疏。他采用集疏,以朱子之说为主,融合诸家之精华,阐发自己的朱子学观点。据不完全统计,元代福建朱子学学者有关经书的注疏达100多种。明代前期福建朱子学学者以精湛研究《易经》闻名全国。其著作有几百种,数量之多全国第一。仅晋江一地研究《易》著名者有数十家,著作达八九十种。明代全国研究《易》者首推晋江,而晋江以蔡(清)、陈(琛)、苏(浚)三家为最。蔡清著《易经蒙引》、陈琛著《易经通典》、苏浚著《易说》,皆为研究《易》学之杰作。蔡清之《易》精而密,陈琛之《易》高而朗,苏浚之《易》渊源蔡清,而其超广洞达,气象绝类陈琛。此三人之《易》学理论,相为表里。其共同的特点是羽翼和发挥朱子学。
第四,福建朱子学学者从不同方面阐发了朱子学。例如,陈普跟随朱熹推崇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通过讲解《太极图说》来说明自己的哲学观点,阐发了朱子学。熊禾在注疏儒家经典中,全面阐发了朱熹的思想。吴海对朱熹的“主敬”说有较深的研究,特别重视道德践履。明人朱衡说:
明以后诸儒,如元吴朝宗(按指吴海)……善守程朱门户,勿为异说所惑,是均有传道(按指朱子学)之功。①
吴海身体力行,凡朱熹之明体达用之学,修己治人之术,罔不一一体验于身心之间,而犹歉然不敢自持,乃颜其读书之室曰闻过斋。
第五,捍卫朱子学。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年),陈宪章、王阳明心学兴起,广泛传播。这时,福建朱子学者绝大部分不为异端所惑,挺身而出,奋起捍卫朱子学。例如,马森(字孔养,侯官人),提出理学必须以朱子学为宗,不可动摇,陆王心学非理学之正脉,不可接受;孔端仪(字子明,莆田人),著《考亭渊源录》,力排王学,言行举止一依朱熹;卢一诚(字诚之,福清人),坚持朱子立场,拒绝参加阳明学社;童世坚(字克刚,连城人),受业于王阳明,归而笃信朱子学,谓王学不若朱学有把握;杨道昭(号天游,建阳人),与王学学者王心斋、王龙溪等反复辩论,激烈抨击阳明学说,称颂朱子学;周瑛(字梁石,漳浦人),以朱熹居敬穷理之说批评王学先驱陈白沙心学;方良永(字寿卿,莆田人),谓言心学者不知其妄;等等。
下面我们选择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福建籍朱子学学者熊禾、陈普、吴海、陈真晟、周瑛、蔡清等加以评述,以窥一斑。
二 熊禾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熊禾(1247—1312年),字位辛,又字去非、退斋,号勿庵、勿轩,学者称勿轩先生,福建建阳人。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熊禾在宋官至汀州司户参军,多有政绩。入元后基于十分强烈的民族大义,誓不仕宦。他在元朝生活33年始终批元颂宋,特别是表彰宋儒,自称“宋之义士元之顽民”。熊禾隐居福建崇安武夷山,筑洪源书堂、武夷书堂,晚年主持建阳鳌峰书院,前后30多年,从事讲学、著述和刻书,研究传播朱子学和其他儒家典籍。
熊禾的著述有《易学图传》、《易经讲义》、《周易集疏》、《勿轩易学启蒙图传》、《春秋通义》、《春秋通解》、《三礼考略》、《四书标题》、《诗选正宗》、《勿轩诗集》、《小学句解》、《注解朱文公先生小学集注大成》、《文公要语》等,结辑有《勿轩集》等,《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正谊堂全书》、《元诗初选集》等有选录。
熊禾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即朱熹——辅广——刘敬堂——熊禾。熊禾在朱子学、经学和教育上卓有贡献,他不仅是元代著名的朱子学家,还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
熊禾竭力推崇朱熹,认为朱熹是孔子第二。他反复强调,“朱文公,百世之师,即今夫子。徽国公(即朱熹)千年之墓视昔孔林。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地。”①他说:
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朱子倡明斯道。……“四书”(按指朱熹《四书集注》)衍洙泗之传,《纲目》(按指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接《春秋》之笔。当今寰海数州之内,何人不读其书。①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人心无所为主。②
熊禾把朱熹章句集注“四书”和孔子整理“六经”并列,俨然视朱熹为孔子之后儒者第一人。熊禾这种评价,为尔后朱熹在儒家中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基础。历代至今公认为朱熹为孔子后儒学之第一人,应是熊禾首先倡导的。
熊禾认为,朱子学的中心思想是治国之大道。他说:
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仪礼、兵刑之具。……文公嘱之门人黄氏榦,且曰:“如用之,固当尽天地之变,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风气,损文就质以求其中可也。”③
他认为,朱子学足以为天地立心、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熊禾准确地认识到朱子学对社会国家的重大作用。不出熊禾所料,朱子学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
熊禾以继朱子学绝续为己任。他认为,“文公殁且百年,门人传习寖益失真,余以为文公之学不行,文公之道不传也。昔游浙中,尝因受业敬堂刘先生,得闻文公晚年所以与勉斋黄先生、潜室陈先生论学之要旨,然后乃知文公之学,其体全体,其用大用,与世之所言第以资诵说者固不同也。”④他又说:
考亭夫子集其大成,平生精力在《易》、《诗》、“四书”。《仪礼》未完书,开端而未竟,九峰蔡氏犹未大畅厥旨。“三礼”,虽有《通解》,而勉斋黄氏、信斋杨氏粗完《丧》、《祭》二书,其授受损益精意尚无能续。若《春秋》,则不过发其大义而已。余虽与君讲求十有七年,《易》、《诗》、《书》仅就绪,《春秋》更加重纂,则皇帝王霸之道亦或粗备。“三礼”乃文公与门人三世未竟之书,君当分任此责,以毕吾志。⑤
这是熊禾在其主持的螯峰书院内与其门人说的。熊禾还谓,这是朱熹“所俟于来学乎,当吾世不完,则亦愧负师训多矣!”①熊禾未食其言,他用二三十年的工夫,孜孜不倦致力于儒家经典。他为学以朱熹诸书是信是行。熊禾用朱子学阐释儒家经典,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
熊禾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是维护朱子学的。他“衍紫阳之正脉,作诗云:斯文一缕千钧日,我辈三经五典身。’其担当斯道为何如哉!”②熊禾不仅是在福建朱子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在全国朱子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二)人能胜天的世界观
熊禾吸取张载“太虚即气”的命题,认为天地间一气而已。他说:“生生而直遂者(按指充实的物)皆阳(气)也,而其虚处即阴(气)。”③在熊禾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太虚即气,因此天地间皆气。阳气生物,故曰实,而阴气为虚也。熊禾把这种虚直的世界观用于社会生活中。他认为,自己不仕元朝,甘于贫困,默默无闻的隐居山林,是虚;但自己著述讲学,有益于后世,却是实。
在熊禾看来,道或理不在事物之外,而在事物之中。因此,在熊禾哲学中,道或理似乎不具世界本原的含义。他认为,道或理是事物的自然规律,人能顺乎自然,其乐无穷。熊禾说:
宇宙间无一物非道,则亦无一处非可乐。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岂好游者,要其胸中自有乐地,故随其所寓,自然景与心会,趣与理融,无所不自适也。④
熊禾的道除了具有事物的自然规律的含义之外,还具有人生应行之路的含义。他把世界观和伦理道德观点结合起来,在《纪典议》中提出道具有立德、立功、立言的含义,认为此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学者言必根于理,文必称行。自然和社会都是有规律的,即皆有其自然之理,当行之路。圣贤是根据事物的规律立教养之法的,而未掺杂一毫私欲于其间。⑤
熊禾认为,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天道有往必复之几,地气无有不伸之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熊禾说:
“易”字从日从月。日中有一为奇,阳数也;月中有二为偶,阴数也。合日月为“易”。故观《图》(按指《河图》)、《书》(按指《洛书》)迭出,可见天地自然之“易”。“易”之作虽则乎《图》、《书》,而其为义,尤莫蓄于日月。盖易者阴阳之道,卦则阴阳之物,爻则阴阳之动也。然有交易、变易之义,在天则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所谓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是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所谓天地设位卑高以陈是也。在《易》书则一阴一阳各有定位,所谓刚柔立本、八卦相错是也。一刚一柔迭相推荡,所谓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是故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人事之吉凶悔吝,物类之得失忧虑。与夫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莫不于是乎尽矣。①
这里充分地表达出了熊禾的辩证法。
熊禾主张遵天命,尽人力。他认为,为君者有拨乱之志,为臣者有尽忠之节。人事既尽,能以天道为定命,故能臻兹大业。这是他强调人定胜天,命自我立。他说:
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孟子不谓命,又曰得之有命,然则将孰从?盖命有二,以性言则理一而已,以气言则分有万之不齐。智愚贤否一类也,富贵贫贱寿夭一类也。以理制数,以性御气,愚可明,柔可强,勤之可以不匮也,仁义之可以得天爵也,修养之可以延年也,为善之可以获福也,孰谓其不可变乎!是故君子但当言理,不当言数;但当论性,不当论命;当然在我,适于在天。敢问三代盛时,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阴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选,科目未兴,科甲之星夫何丽?②
熊禾是把天命看成理,不是人格神;理是事物之道理或规定性,只要人们按照事物之理或规定办事,如修养之可以延年,为善可以获福,愚可明,柔可强,勤之可以不匮。这就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的,自己的命运是自己掌握的。由此可见,熊禾先承认天命,其后又否认了天命。
(三)全体大用的认识修养论
熊禾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例如,天文历法不是天地产生前就有的,也不是天地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人们长期观察天地四时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黄帝颛顼虽云造历,盖未详也。至(尧)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时,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丽于天者,始则而象之岁分为四时,又分为十二月,又分为三百六十日,因其气盈朔虚又为置闰以应周天之度,于是天道可得成矣。这就是说,天文历法是人们根据日月星辰的变化而逐渐认识的,不是上天赐给或圣人头脑里空想出来的。这种讲法是符合科学思想的。熊禾由此推论出朱子学的体系是有体有用,而且体全用大。他说:
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载道之文也。言学而无见于道,则不足以为学;言道而无得乎道之全体,则亦不足以为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时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语之有关于世教亦可以为立言,而皆无见乎道体之全,则亦不足与乎道统之正矣。①
正是由于朱子学体全用大用,是致用之学,因此必须学用结合,即儒道与吏治为一,讲学与论政为一,德权与笃行为一。他反复强调,朱子学体全体、用大,为讲学论政之本。
熊禾基于其学以致用的思想,反对不关心社会国家的空谈,激烈抨击和蔑视不关心世事的儒生下士。熊禾遵循孔子、朱熹教导的“为己之学”,明确提出,研究理论的目的在有功于社会和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自己就是如此做的。熊禾说:
余弱冠读《大学》,玩索有得,始喟然叹曰:“学在是矣!”自此益穷研“四书”以及诸经,务为明体达用之学;每病今世之学者,议论徒多而践履益薄,词华虽工而事功益不竞。②
熊禾特别主张知行统一、实事求是。他说:
余壮而读书颇识《大学》知行之要,益求实事,不竞虚文。勉焉自力于躬行,切亦有志于世故。③他认为,若以敬为宅心之要,盖心存则众理具而万事之纲举,非心存之外别有所谓敬。圣贤之学不讲,人心失其主,理乖事谬,世道随之。“万事具万理,万理在万事,而其妙蓄于人心,一物不体则一理息,一理息则一事废。敬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也。”“心生生不穷者,道也;敬则生矣,生则恶可己也。怠焉则放,放则死矣。此千古圣贤传授心法之妙,学者深体而屡省之也。”④这就是说,只有敬才能生道,才能存道。因此,敬是学者特别要“深体而屡省之”的。
在践履道德伦理上,熊禾还宣扬无物欲而乐道的思想。他认为,“人生苟不以外物为累,则虽羹藜饭糗莫非珍馔,粗绘大布何异衮冕,而荜门圭窦又皆吞风吐月之大厦也。”①嵇山之隐,陋巷之居,虽以四海九州之富、钎朱怀金之贵,而不以易其所乐者哉!熊禾基于他的这种“不以外物为累”的思想,誓不仕元,甘受贫困,宁可饿死。因此,熊禾的无物欲而乐道的思想,并不完全都是禁欲主义的。
此外,熊禾还强调践履道德伦理要心悟躬践。他认为,凡病必有治,治必有要,不独医为然。人的思想病即道德上的欠缺也是可以医治的,而道德修养是有其要旨的。自治治人之道的宗旨在于,“药灵丸不大,棋妙子无多,心悟躬践”,即在于心中真正领悟和实行。②
三 陈普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普(1253—1325年),字尚德,所居有石堂山,自号石堂,学者称石堂先生,福建宁德人。他是朱熹四传弟子,即朱熹—辅广—刘敬堂—熊禾—陈普。陈普一生未做官,为阐发和传播朱子学而奋斗终身。他学问极为渊博,不仅精通朱子学,还对声律、天文、地理、算术等有很精湛的研究。
陈普的著述有《仪礼注释》、《孟子纂要》、《四书集解》、《石堂先生诗》、《朱子武夷棹歌注》等,结辑有《石堂先生遗集》等,《丛书集成初编》、《元诗选》等有选录。
陈普一生以讲学为务,反复强调朱子学的核心问题。陈普说:
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皆在“四书”、“六经”中,如斗极、列宿之在天,五岳、四渎之在地,舍此不求,更求何事?……普读书不多,于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里,姑据来示一二,则其于思孟程朱之大义已有胡越参辰(按指对立两端)之拟。……《诗》、《书》、《易》、《礼》、“四书”微周程朱,学者至于今犹夜行耳。……陆学多犯朱学明辨是非处。③
陈普认为,朱学和陆学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朱学正确而陆学错误,竭力伸朱排陆。在陈普看来,陆学违背儒家正统,是欺世盗名之学。
(二)哲学思想
陈普在论说世界本原的过程中,理学家们常用的无极、太极、道、则、性等都有提到。陈普认为,这些范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理的。
首先,陈普认为,理是事物道理之极至,故又叫做太极,而无极太极只是一个理。天下之物,其形体、性情、位分、度数,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当然。他说:
太极不过道理之总名尔。物有去来、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间,耿耿于人心目中。所以圣人提出,濂洛画出。其所提出画出,只是一个所以为物者而已。思之而见,察之而得。然则形迹声臭可以耳目闻者见,故谓之无极。无极太极只是一个,非有二也。①事物之理是不变的,应该如此,永远如此,是不能变易的,如对君永远要忠等。陈普强调,理之至极不可变易,就是为了说明三纲五常、人伦道德是永恒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其次,陈普认为,理是事物之则、之性。他指出,有物必有则,有形必有性。则,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极。物与形出于气,而则与性,即太极之各具于物者,与物未尝相离。物有去来生死,其则其性乃道理之本体无时而不在。故须别作一处,盖欲使之见其则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理是事物的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性)。理表现在物上则为性。事物之则之性在事物之上,与事物不相脱离,但又与具体事物相区别。理之所以能创造事物,在于先有各种事物的各种形式(即各种规定),如房屋的建筑必先有图样,然后才能与质料(即气)结合而成实际的事物。由于各个事物之则之性不同,才有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不同事物。因此,不同事物之理(即则、性)又是各个不同事物相互区别的标志。
陈普还指出,物与形出于气。他说:
故文公云:非有以离乎阴阳,明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言。盖形气以理为一,然形气须作形气说,道理须作道理说。既须各说,则须画个有形有气者在下,无声无臭者在上。形气是所为者,道理是所以为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然之理也。非独如此,道理本是作一处。②物皆理所当为,则物固小而理至大,物自沉而理至浮,物自后而理自先。这就是说,理是创造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本体者,所以生之谓也。”
陈普所谓则“须画个有形有气者在下,无声无臭者在上”,是指周敦颐所画的太极图:无形的理(太极)在上,有形的阴阳五行之气和人、万物在下。他通过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全面阐明了无极、太极、理、气、阴阳、五行、人、物等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其图最上圈是太极,不可以闻见,故曰无极而太极。意谓太极不可以形气言,虽无而实有。后之儒者将太极作一块混沌之气,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人知其为理而非气。理生阴阳五行之气。陈普说:
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阴阳二气,不可以太极言,但其圈之大之圆与上圈(按此“上圈”即指代表理或太极的那圈)同,则又见其不相离(按即理生气后理气不相离)之妙,中一小圈谓太极(按即作为本体的理),即在阴阳(按即指阴阳二气)中常生常死有常无,谓自中央一个分开作二个(按即指一理生阴阳二气),只是头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为主(按指理为气之主),非又别有一个小底。故文公云:中〇(按即上文讲的‘中一小圈谓太极’)者其本体也。本体即最上圈。本体大小不同,本非有异,亦犹五行下一个小圈,见二五之合为一者,又是大弥六合,小不满一掬之义,画出成此一个,亦是妙处,非有意为之也。①
陈普认为,理生阴阳五行之气,理与阴阳五行之气的精微凝合而成人与万物,以及两端(即男女、雌雄、牝牡)的胚胎。它们是繁殖人与万物的种子。他说:
图下二圈只是一体一太极。男女圈义深最当,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谓天地之生,气化之初,合下只有两端,一阴一阳,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兽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横渠(按张载字)所谓阴阳两端立天地之大义,亦此意也。②
陈普认为,人和万物两端的胚胎既成,就能繁衍无穷。究其最终的根源在于“理”,理是生物之本体。
在陈普看来,理不仅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本体,而且也是可以认识的。理思之可见,察之而得。但是,理只可以心见,而不可以耳闻。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理的产物或表现形式“形迹声臭”之“耳闻目睹”才能认识理,即通过感性知觉,然后进行理性分析,就能认识理。用陈普的话说,就是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不能光空谈大道理。陈普说:
先立其大则必略其小,而迷于下学上达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砺大节至其平居,则放言纵欲致犯清议者,此说开之也。③
“下学”是指日用寻常之学,“上达”是指天理、性命之学。陈普反对只空谈天理、性命。他又说:
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至,又不可骛于虚远而又不察切己之实。①
他认为,陆象山(九渊)的“先立乎其大”之说就是空谈大道理,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为切。陈普讲的由“察切己之实”而“求造道之极至”,即达到做圣贤的大目标。他在这里讲的虽是人的道德修养,而其讲的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方法应该是对的。
四 吴海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吴海(1322—1387年),字朝宗,因尊崇孔孟,自号鲁客,或叫鲁生;又因喜人规过,名其斋曰闻过,学者称闻过夫子。福建闽县下渡(今福州市)人。吴海誓不仕元朝,其朋友王翰任官元朝,吴海劝其死节,后果死节。明徐宗起指出,吴海“平生刚直,终身隐钓,未尝求知于人,然非其人则亦莫能知也”。②吴海一生过着清寒的教育和著述生活。
吴海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义愤,怀有亡国之恨,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是十分突出的。明人王称指出,“先生以刚明仁勇之资,充圣贤诚正修齐之学。不幸生非其时,视当时有不可为者,于是卓然长往终身不污一命。”③吴海的著作,言切而理当,气充而笔严,其于濂洛载道之言有益于世者皆得之。因此,吴海的人品和学识极得后人的称颂。明人张维康说:
刚直不偶,处于山林之下。味圣贤之中,学周程张朱之学,而独嗜为古文,其悲欢忧悦,感时愤事,未尝不寓之于此。故必关乎世教,而流涟光景之辞一不苟为,盖有意于圣贤之文者也。……闽自文公之后,复有如此之人,如此之文也。④
吴海的学说是醇正的朱子学。他研究学问皆据朱熹著作,认为“其寸纸片墨流落人间,自当为世所宝”。⑤有人认为,吴海是朱熹学说的真正继承者。清人蔡衍锟认为,吴海是闽学史上一个关键性人物。吴海学识醇正,所学皆周程张朱之道,故凡一言一行无非出于大中至正。蔡衍锟说:
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按指杨时),其盛也集于朱子,其末也振于西山(按指真德秀),又二百余年而始有剩夫陈氏、翠渠周氏、虚斋蔡氏。向非有先生(按指吴海)之辟邪崇正,傺然挺出于绝续之间,何以继已往而启将来哉!①
这就是说,吴海是朱子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人物。
吴海的著述结辑有《闻过斋集》、《闻过斋诗集》、《命本录》等,《丛书集成初编》、《元诗选》等有选录。
(二)道理读书论
吴海认为,“天不言所出者理”②,“理出于天而具于人之心”③。吴海还用道来释理,认为道是事物当然之理。他说:“道者人伦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乃天下古今人物共行之路。”④因吴海曾谓“天下古今治乱时世不同,而人心无不同者,理一而已”⑤,所以天下古今人物共同之路即是“一理”。吴海认为,理是事物的道理,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因此,人们必须依理而行才行。“安莫于理,理出于天而具于人心。物必有则,事必有宜。大而民生伦纪之间,细而日用动静之际。”⑥因此,顺理则安,逆理必危。
依理而行,就要知理,认识理。在认识论上,吴海很少讲格外物而致知,反复讲学(读书)以致知。他认为,学则致知,知则知所择。通过读书学习使知道的更多;但是要有选择,要选择所知中之正确的部分,加以牢固的掌握住。显然,这是唯理论的认识论。吴海说:
天下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正身修己之法,莫不昭然具在于书,必读之而后有以识事理之当然。……书不可不读,而读之固当有法。盖不读非圣之书,则异端邪说不得以乱吾之聪明,而志定虑专无他歧之惑,讽诵习熟循序渐进,则无欲速不达舍近求远之病,优游涵泳,沉潜玩索,则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实。朝夕孳孳无有间断,则温故知新而有日进之益,骤觉忽喜小得勿足,则人自己得而有必成之效。⑦
吴海的这种以读书(学)为认识起点的思想是以圣贤之书为绝对真理为前提的。他所谓圣贤之书,主要是指孔孟和程朱理学的著作。在吴海看来,除孔孟之外,就是程朱了。孔孟、程朱之道著于书,都是绝对真理。他说:
圣贤之道著于书,学者不能身体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传虽多无益。顾学者莫先于立志,志即定,然后即物以穷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曰孜孜无少间断,则入道有方,进德有序,圣贤可驯致,苟有一毫为利近名之心,则非己之学矣!①在这里,吴海把“格物穷理”改为“即物穷理”是个好提法。不过,吴海所谓“即物穷理”,实际上是由理及物。“力行以求至”,即要真正实践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
吴海特别强调学习要不断深化。不断深化的动力是由学知不足、由教而知困。他说:
为学之道,精知而力行之。知有不逮继可以进行,有所失则改之,以至于无可改,岂不为大善乎?②吴海认为,知之诚难,知之精在乎穷理而已。要日日改之“以至于无可改”。在吴海看来,“至于无可改”就是“知之精”、“致知穷理”了。当然,吴海所谓“至于无可改”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人的认识是矛盾发展的过程,是知与不知、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的过程,因此不可能达到“至于无可改”的。
吴海还指出教对知的重要性。上面已经引到,吴海提出“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此外,吴海还提出“教之身不以言,教者治之本。”③吴海又说:
教,治之本也?学校,风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产以立其业,教之礼仪以正其俗。……民知教则良心生,教立则善人众。大家既服,小民视之而化,风俗无不美。④
教之所以极端重要,就是因为教能出贤才,“小民视之而化”。贤才为政能立国,因此“教,治之本”,“事实无难者,顾难得其人”。⑤
(三)道德伦理观
吴海吸取先秦韩非关于“德者得于内”的观点,而又加入天命论。他说:
德非自外也,得之于天我固有之也。故自吾之爱亲慈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食而悯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无衣,己安而不忍人之危。若其恻隐之情出于天性,随寓而发,非以纳交要誉于人,求报冥冥于天也。然天道无感而不应,人道无施而不酬,顾为德者不可以是没心而已。……恩惠及人,德之余也;孝悌、忠信、仁爱、诚实蓄于身,德之本也。①
他还说“天降民德五常具全”。他把“孝悌、忠信、仁爱、诚实蓄于身”作为“德之本”。这种修养过程要求慎德。他还认为,“理出于天而具于人之心。至善而无恶、纯一而不杂者为吉德;肆情而荡、逐物而不返,暴逸败悖者为凶德。”“学则致知,知则知所择,慎得致确,确则任所守。此慎德之要也。”②吴海之前的一些学者中,一般释德为褒意,只有德与不德之分。吴海提出凶德,其内涵是指不德,即德之贼,是有新意的。
对于理学家所常讲的天理与人欲的矛盾,吴海以“惟德胜欲”加以解决。他认为,“有能洗心濯虑,使方寸湛然”,理义以为之主则道充,就是使德胜欲。③吴海说:
善,人所固有,生而莫不善。天地之性为性也,而为情也未始不善也。耳目鼻口累乎欲,视听言动出乎己。物我相行,万事相感,利害相权也,日用酬酢之间有不得其正焉,斯其为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于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④
此谓“善非取于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就是上引“德非自外也,得之于天我固有之也”。在吴海看来,人之本性是善的,因此应该完全是吉德;但是人的物欲为不善,是凶德。因此,人欲是与人的德性相矛盾的。欲多理则少,无欲理则全。吴海又说:“天下之福,恒生于无欲,而祸每起于贪,贪者无厌,无厌则不知止,不知止故祸必恒随之。然自古及今相接于目前而不戒,岂人情不安福乐得祸哉?由不能止其贪耳。”⑤
吴海进一步指出,由于人们贪得无厌,祸必恒随之。因此,对人们进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世学不明,风俗益薄,人之道将不立于天下,只有读书养心以成德。吴海十分强调社会风化教育,以使知道贪之有愧,与禽兽无异。吴海说:
唯君子能全其性分所有而无私欲之蔽,日用之间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来应之不穷,随寓而安。……观阴阳之变,万物之化,古今往来,治乱相寻,至人所以酬酢万变者(按即乐于道,依理而行)也。①
在吴海的伦理思想中还有父子、兄弟等的对等思想。他认为,古者宗法行于天下,宗族有所统一,人心有所一致。故孝悌隆而习俗美,先王之治容易。吴海说:
恩固赖于相成,而道实原于自致。子焉自致其孝,无怨乎父子不慈;父焉自致其慈,无疾乎子之不孝;兄焉自致其友,无责乎弟之不恭;弟焉自致其恭,无恤乎兄之不友。致于己而不望于人,则其道易成也。②
在吴海看来,伦理关系是双方的,若绝对服从一方,则协调的伦理关系就建立不起来。吴海强调伦理关系“原于自致”,即出于自觉而不能强制,是内在超越。这就讲到了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真谛。
五 陈真晟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真晟(1411—1473年),字晦德,又字晦夫,号剩夫,又自号布衣,学者称剩夫先生或陈布衣,福建镇海卫(今漳浦)人。曾任漳平县学教谕等。
陈真晟的著述有《程朱正学纂要》、《正教正考会通》、《陈剩夫粹言》等,结辑有《陈真晟布衣存稿》、《陈剩夫先生集》、《布衣陈先生集》、《陈剩夫集》等,《正谊堂全书》、《丛书集成》、《古今粹言》等有选录。
陈真晟出身贫苦,有谓其为“卖油佣”。据清初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西人)在其《观感录》中记载:陈真晟的“父为打银匠,携之执业,主人密为防。真晟年十一,语父曰:‘何业而蒙盗贼之防乎?’劝父捨之。问卖油有所得?曰:‘日余二壶。’喜曰:‘此足备养矣。’货油至书舍。闻讲有子孝悌章,大悦;明日又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益喜。入请其师曰:‘小人愿受学,日以余油为贽。’师曰:‘诺。’复告曰:‘我本以卖油代父之业,备日养耳;专一于学,则累我父,须每旦一受讲,日仍卖油。’师从之。逾年学大进。”可见是自学成才。陈真晟自号布衣,其出身是劳动人民家庭。
陈真晟的上祖陈安宓是黄榦高徒,宋末元初的朱子学家;高祖陈址幼是元代朱子学家。陈真晟早年从著名朱子学家唐泰(号东里,长泰人)学《易》。唐泰通晓“五经”,尤精于《易》,著《思诚斋易学》。陈真晟学习刻苦,卓有成就。他私淑明初著名的朱子学家胡居仁,得胡氏之穷理方法。明人周瑛说:
先生之学无师承,自读《中庸》、《大学》始。初读《中庸》,做存养省察功夫;继读《大学》,专从事于主敬穷理。先生本原徵澈,义理精明,有所本也。①
明陈琐称陈真晟之学为“全体大用之学”。“先生学业积力久,大有了悟。读《论语》则悟圣道一贯之旨;读《易通》则悟天地万物之本;读《西铭》则悟理一分殊之原。得存养于《中庸》。得扩充于《孟子》。得圣学始终之要于《大学》。乃以知行二字为用功之纲,以敬之一字为用功之要。静以此敬,涵养其心;动以此敬,持守其身;以此敬而立体,以此敬而致用:盖心身动静一于敬也。先生平生动必以礼,行必以义。不沽名而钓誉。当言则言,当为则为,无所顾虑。尝曰:‘宁自见毁于世俗,毋一得罪于圣贤。’”②在读书人热衷于科举仕官的社会风气中,陈真晟却一反潮流,“不以科举为事”③,“不图做官,安贫乐道,其所著书无非示人以朱学之梯航”④,遂成为明代福建著名的朱子学家。
陈真晟使福建朱子学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当时,朱子学的异端、明代心学的先驱者陈宪章,亦谓对“布衣先生余雅敬慕久矣”。⑤明人陈琐引述当时著名学者的评论说:“陈白沙(即陈宪章)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周畏斋以灵芝醴泉目之,程御史以世间出真儒目之。”⑥清代福建著名学者陈祚康在《全闽道学总纂》中称陈真晟为明代前期福建闽学学者之第一人。陈真晟在福建朱子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公认的。
学者们认为,陈真晟思想得程朱理学之真传。明人张元桢(东白)在《赠行诗》中说:“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彼吴(按指吴与弼)、许(按指许谦)二子盖亦有未是处。”陈真晟的论敌陈献章认为,其学为真正朱子学。陈献章在《诗赠陈剩夫先生》中说:“多谢泉南翁,神交愿倾倒。”“漳南陈先生曰布衣者,其学以子朱子为宗。”学者们认为,陈真晟对朱子学有很大的发展。清代著名的学者蓝鼎元说:
真晟学问纯粹。尝诣阙上书,请补正学,上《程朱正学纂要》,作《心学图》二,一著圣人心与天同运;次著学者法天之运,与周子《太极图说》相发明。又作《正教正考会通》,规制详密。①
明代理学家郑纪说:
今日程朱又几五百年矣。先生在戎伍之中,忧道学之计,以穷理为入门,以主敬为实地,指画心图,而阴阳动静之理明;敷陈王道而经邦济世之术著。闽之后生小子得以觉迷途而归正学者,先生之赐也。先生虽不得游夫程朱之门,亦可谓私淑其道者矣。②
一般认为,陈真晟把程朱之学概括为治心之学,以主敬贯穿于其学的始终,以笃行为学之目的,是其对朱子学的发展。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刘宗周说:
一者诚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独之说,诚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识慎独之义,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学有本领,故立言谛当如此。③陈真晟的闽学思想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教人以礼,感人以德”。④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陈真晟倡导朱熹《家礼》,而使社会风气始正;自陈真晟起,而儒风始正。明人黄直说:
先生之时,有康斋吴公倡道于江右,白沙陈公倡道于岭南。公皆与同时,未见公与之相师友以上下齐议论。则公之学术其渊源虽不可知,然公当海内竟趋功利之时,独能安于布衣从事躬行之学,卓然自立门户,为天下豪杰之所尊仰。则公诚可谓一世之高士也矣。⑤
由此可见,在同时代的诸学者中,陈真晟的思想具有领先的地位。
(二)思想体系
陈真晟一生用力于程朱理学的本源之地,即理、气、心、性等诸范畴的相互关系,使其形成为更加切实致用的严密思想体系。清人张伯行在《陈布衣文集·序》中说:“明布衣陈剩夫先生,奋起南服而有以得程朱正学之奥。盖其专用力于本源之地(按指理气心性)。今观二图及圣要四说,可以知其功力之所在。”此评至为切当。
陈真晟把程朱理学的本质概括为治心之学,是符合程朱理学的实际的,是非常准确的。这是陈真晟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发掘。陈真晟说:“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岂有外于《大学或问》所详居敬穷理之工夫乎!”①“居敬穷理”就是治心。朱子学就是适应宋元明各朝治人心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为了阐发朱子学即心学,陈真晟著《心学图说》,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多言心学。但是,陈真晟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学是不同的。心学派的心学是把心作为宇宙的本体,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源。陈真晟认为,天命之理具于人心,要存心致知笃行,即所谓本源之地。对于陈真晟的心学和心学派的心学之不同,清人张伯行有深刻的分析。他说:
或问余曰:陈布衣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之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尧舜以讫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迄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则为敬,在释氏言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②
可见陈真晟言心与心学派言心,字句相同而实质不同,正如孔子、老子皆言道德,其含义各异;子思、陆九渊皆言尊德性,其本质不同;韩愈、朱熹皆言道统,而途径背驰。总之,陈真晟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学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为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后者为本体论。
陈真晟的思想体系是以讲心为要。他说:
先讲求夫心要。心要既明则于圣学工夫已思过半矣,盖其心体是静坚固而能自立,则光明洞达作得主宰。所以一心有主,万事有纲,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之要得矣,然后可依节目补小学、大学工夫,而其尤急务则专在于致知诚意而已,皆不外乎一敬以为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功,则皆有自得之实矣。①
陈真晟认为,明白了心要,就会懂得把各个方面联系成为一个体系。他撰写《心学图说》,把自己的心学呈现出来。其思想体系是: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是谓之(善)性(五常之性);性为利欲所惑,“法天之当然是性之复”;复性需主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即知行,此即所谓一动一静在于理也。质言之,就是天理——善性、复性——敬(存心)、义(知行)。他认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二者为学《易》之要。以始学言之,存心致知之道亦在乎是。盖主敬即存心,择义即致知。道体极乎其大也,非存心则无以极其大;道体极乎其微也,非致知则无以尽其微。静而不能极夫道之大,动而不能择乎道之微。则虽曰学《易》,亦买椟还珠而已矣。静焉而涵养致知,动焉而慎独诚意,使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己,则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然则因外美而益充内美,发而为至美。
陈真晟的思想就是主敬存心(穷理)和知行并进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明人郑普在《布衣陈先生传》中把陈真晟的思想体系概括为“治心修身”四字,是十分确当的。陈真晟在《答耿斋周轸举人书》中认为,“治心修身”是程朱之学的要法,要以程朱之学为入门要道。
(三)主敬穷理和知行并进
陈真晟深刻地论述了要穷物之理,必须涵养此心,只有主敬才行。他认为,义理之聚于物,犹蚕丝之聚于茧,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绎使丝于茧之外,盖引其绪(指圣贤微言绪论)以出于外。于物理为难,实游其心以入于内。这是说非先养此心不可,使有刚锐精明纯一之气,入其微、步其精以诣其极,使其表里精粗之处无不到,而脱然尽得其妙于吾胸之中。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绎到八九分,则一二分绎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谓最精妙者。精妙既不能绎,则其所绎者八九分,皆其粗者。他说:
得其粗,昧其精,虽谓之全未紬绎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绎,则物物皆不能绎。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张模糊,则张张皆模糊。心粗之病,何以异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望深于道。殆难矣,矧道不惟精深,而为一广大者也。故不能析之极其精,则不能合之尽其大。所谓物有未格,则知有未至者此也。然之所以合之者,又须此心先有广大之量,然后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所谓敬者,岂非涵养此心,使动而穷夫理,则有刚锐精明纯一之气;静而合乎理,又有高明广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实工夫,做到至处,所谓圣学者。①
这就是说,认识事物,就像引蚕丝一样,把蚕丝引出来容易,而深入去了解其物理就不容易,因为把物理从物中拿出来,只有体察、思考才行。因此,要穷物理,必须首先涵养此心。只有“先养此心,使有刚锐精明纯一之气”,才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诣其极,随其表里精粗之处无不能,而脱然尽得其妙于吾胸中”;否则,只能得其现象(粗),得不到本质(精,精妙,即道、理)。在这里,陈真晟认识到思想理论对认识的指导作用,是有其合理因素的。但是,他把这种思想看成是主敬,就是所谓“涵养此心”,是从主观到客观的唯理论的认识论。
在陈真晟看来,主敬穷理修己乃圣学之要,是为学的根本。他说:
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发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为说焉。②
陈真晟提出主敬的内容有四个方面。清人张伯行说:“先生取圣要四说系于法天之图,曰主一无适,曰整齐严肃,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③其中所谓“常惺惺法”,就是时时警觉。此是陈真晟采用北宋谢良佐“主敬是常惺惺法”之说。谢良佐这种说法得到朱熹的赞赏。
这四点均合朱熹的说法。这四点的核心是“专用心于心”④。“专心克治”⑤,即把精力都集中至道德伦理关系上。对此,明人林雍有所解释。林雍认为,陈真晟读(朱熹)《大学或问》,见朱子博采主敬之说,及求之所以为敬;见程子以主一释敬,以无适释一,始于敬字见得亲切。下功夫推得此心之动静而务主于一。静而主于一,则动有所持而外诱不能夺。“意有善恶,若发于善而一守之,则所谓恶者退而听命。”⑥陈真晟的主敬境界就是“客念不复作”、“外诱不能夺”、“发于善(按即五常之善)而守之”。陈真晟说:
今之学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无主一无适之确,则是未尝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穷理,亦只是泛泛焉务读书多而无即事穷理之精,则是未尝穷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门安得观其堂奥,未噬其肉安得味其精髓。①
陈真晟提出以尊德性为穷理之本;道问学为尽心之功。陈真晟的这种用巨细相涵、动静交养的静坐养心之法以实现格物穷理,于朱子学是有所发挥的。
陈真晟在《心学图说》中认为,主敬的最大功用是复性。天心动静之本然是性之原。君子法天之当然即是性之复。圣人亦天心之自然者。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体之,以尽其法天之功效而有序。盖始则主敬,使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即致知诚意之事是圣学之要。自始至终则皆不离乎敬,如是则法天之功至。陈真晟的复性说是受唐人李翱的复性说的影响的。李翱认为,性是人先天的内在本质,是善的,外在的情欲蒙蔽了先天的善性,要用“勿虑勿失”、“寂然不动”的方法克服情欲,便可以复性。陈真晟的以主敬来复性,与李翱的以“勿虑勿失”、“寂然不动”来复性是相似的。②
陈真晟认为,主敬所穷之理和读书、即事所穷之理,此理是否是真理、真知,还必须验之以行。他认为,能行才算真知。明人林雍说:
先生又常语人曰:“人于此学,若真知之,则行在其中矣!”盖以知之真,则处善安、循理乐,其行甚顺。然而,气禀有偏胜,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顺而易者反为逆而难矣。此圣门论学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后,又加以笃行也。③
这就是说,知了并不等于能行,因为人的气禀有偏胜。清李颙在《观感录》中说:“陈真晟之学,以知行并进为宗旨。”在这里,可以说陈真晟知行并进论是后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先驱。
(四)社会政治思想
陈真晟基于其心学,提出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他在《正风教疏》中,以古鉴今,认为三代所以盛者,学校兴,师道立,心学正教倡明于天下。后世虽有学校之设,然专以科举俗学为教。陈真晟强调,当时虽有学校,“然专以科举俗学为教”,“则心学益废”,危害甚大。他说:“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育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现今)科举虽曰考理学以取贤才,而其实累贤才而妨正学,使后生晚进奔竞浮薄而士风大坏者,科举实为之也。”他认为,“科举不罢则正教不可得而行”。①因此,陈真晟提出当时学校教育必须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改革。
陈真晟基于其程朱理学即治心之学,提出学校必须真正进行程朱理学的教育。他曾向明英宗朱祁镇进呈他的《程朱正学纂要》,此书提出“所谓圣学者,程朱之学也”。当时学校虽用程朱之书,但是由于八股取士,而实际上没有进行治心的教育。此书还说:“士习不正,民风不淳,三代盛治未能全复。盖由学校虽用程朱之书,然不过使之勤记诵训诂攻举业而已,而于身心正学之教,则实未尝举行故也。”②
陈真晟指出的当时科举考试的弊病是对的,是有眼光的。他认为,宋元以来,学校虽用程朱之书,但是科举取士仍用隋唐旧制,这实际上是视圣贤正学为无用。圣贤之道自孟子以后千有余年晦而不明;自周、程、张、朱出,此学才大明;自朱熹死后,此学又复晦。因此,他提出科举要用程朱理学,圣贤之学才能由晦而复明。当他看到学校颁行敕谕教条有合程朱教法时,喜之曰:“此学校正教也”。③
陈真晟采取皇帝敕谕中的要语,参以程氏学制,以及朱熹吕氏乡约、贡举私议,作《正教正考会通》。他把考文与考德结合起来,而且认为考德比考文更为重要。这是极有见解的思想。他把考德与考文各分为几等。考德:上上等,即能主敬穷理修己者,就是已经自觉践履道德的;上中等,即能求以主敬穷理修己者,就是正在努力去践履道德伦理的;中上等,即性行端洁,居家孝悌、廉耻礼逊、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者;中中等,即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下上等,即能习经书(学而不实践)者;下中等,即惟记诵旧文、务口耳之学(道德品质极差、不务正学)者。考文:上等,考德名在下之中(下等),则考文虽上亦降;中等,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中等),则考文虽下必取,考德名在上之上(上等),则考文虽下必取,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下等,即为学不务修身),则专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选。陈真晟在教育问题上,始终重德教。这是符合朱熹思想的。④
在社会历史观上,陈真晟主张复古礼,亦即复先王古制。他说:
世人言执古贵乎通今,执古而不通今,犹执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谓古者,即先王之制著于礼经者是也。所谓今者何礼也。岂非流俗之弊习于性成者乎。姑以丧礼言之。古者以不饮酒食肉为礼,今人必以饮酒食肉为礼,如执古则不能以通今,通今则非所谓执古。岂一人真有两个口,其一则执古,又其一则通今乎?抑只是一个口,但遇酒食则通今,及醉饱之后则执古,斯谓可贵乎?愚意古礼用意着力执之犹不能及,多得罪于先王,况今乃以执古为非,以通今为是,则其伤礼败俗宜无不至,又岂可胜言乎!吁孔子执古释君而从下,犹为时之所讥;孟子行古礼尚为王欢所怒,况某以区区而欲执古孔孟之礼,其为所讥毁宜也。然则宁百见毁于世俗,不可一得罪于先王。①
陈真晟正确地认为古今制度不一,执古不能通今,通今不能执古。但是,他认为古者为好,今者为差,今不如古。他这种颂古非今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多数朱子学者共同的毛病。
六 周瑛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周瑛(1430—1518年),字梁石,初号蒙中子,别号翠渠,学者称翠渠先生,福建漳浦人(祖籍莆田,其先世于明洪武年间调戍漳浦,后定居,而周瑛仍自称莆田人)。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进士。曾任广德知州、南京礼部郎中,抚州、镇远知府,四川右布政使,等等。
周瑛一生为官多年,较能秉公办事。他自谓,“以理处物(按即事)是谓之义;以心(按指私心)处理是谓之利。”“求仁惟公为近。惟公之至,斯理之尽。”②周瑛认为,为官办事要公。公即理,亦即仁、义。周瑛所谓的“公”,是指社会国家的利益;而他所谓的“私”,是指某些人的利益。因此,他说要施仁义于君子,“以猛待小人”,即对危害和反对国家统治的人要进行镇压。他说:“晦翁谓此说未尽道理,因自谓欲以宽待君子,以猛待小人。瑛得其说而推行之。自入仕以来,奉以周旋。”③周瑛是根据朱熹的政治思想施政的。此外,周瑛认为,损害民族利益的官不能做,刘静修、吴草庐仕元是事夷狄,是不知《春秋》大义,学孔孟违孔孟之教;宋非桀纣之暴,元非汤武之仁,元灭宋是掠夺、非正义,为官不能助暴。①由于周瑛为官有一定原则,多有政绩,为时人所敬仰。
周瑛为学拜陈真晟为师,得朱子学真传。他尝以书抵剩夫,谓人有古今,心无古今,“平日颇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检于心,以求合于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人及知而暗于天,则恒自曰:此吾学之得也。”②周瑛所谓天命即理。“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周瑛学到了。因此,明冯具区在《科场备用》中谓,“周瑛为理学之精粹,朱学之名臣。”明人周志渠称其为“理学名臣”,谓“天不欲使紫阳道脉历再世而斩,故祖(按指周翠渠)得以续其传”。③周瑛的学问极为渊博。他“幼习举子业,即不安于俗学,自‘六经’、‘四子’(按指‘四书’),以及天文律历、字画、方外之书无所不究,辨析精微,以洞见本原为极致”。④周瑛还工翰墨,笔迹为艺林所珍重。
周瑛与心学家陈献章是多年的老朋友。周瑛谓,“瑛因献章得钞朱子语类书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门人退录其师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尽在是矣。”⑤但是陈献章心学是尊陆贬朱之学。周瑛极力反对陈献章的心学,批判他学术不正,是禅学,规劝其改过,并对其同僚和好友中信奉陈献章心学者,亦规劝其放弃而转向朱子学,致使陈献章极为不满。明代学者何乔远说:“其时白沙陈公之学盛行,名公卿咸为折节,翠渠周公辞而辟之。非白沙为禅学者,周翠渠也。”⑥此谓周瑛之学有心学倾向。
对于周瑛的学问、人品性格和施政之方,时人也有比较概括的评论。明代著名学者杨廉说:
读书以穷理而非务博,作文以明道而不专于求工。心朗徼而月霁,气舒畅以春融。其政事也,虽居今世而每有古意。其进修也,虽在眉寿而时有新功。想其寤寢之际,思维之中不龟山则豫章、非延平必晦翁。其所探也为甚远,其所得也为已丰。然第知其志之有在,而莫窥其学之所终。⑦
这些评价是公正的。
周瑛的著作有《字学纂要》(又名《书纂》,附《字学管钥》)、《政本正均》、《祠山杂录》、《教民杂录》(又名《广孝录》、《正德漳州府志》、《弘治兴化府志》、《莆阳拗史》等,结辑有《翠渠稿》(又名《翠渠诗文集》)、《翠渠摘稿》及《续稿》等。
(二)一本万殊的世界观
周瑛认为,形成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太极(理),由太极(理)产生气之阳动阴静而成天地。他说:
天地何始?曰:自太极生阴阳(两气),始阳动而阴静,阳清而阴浊。其动而清者日旋于外,积一万八百年而天成焉。天成,日月星辰备矣。其静而浊者月聚于内,积一万八百年而地成焉。地成,山岳河海备矣。①
天地形成后,天地又通过气产生万物。由于气化有“伸缩盈虚错综杂揉”之不同,便产生天地间形形色色的不同事物。他认为,“天地生物,气化不齐,伸缩盈虚错综杂揉,故其偏孜乖戾之甚,必生而为毒螫馋噬之物,盖非天地欲生此物也,气之所至不得不生也。”②天地生万物人为贵,故王者养万民亦以人为主,若夫水土之产、昆虫草木鳞介之属皆为人之用,不可与人论轻重。在周瑛看来,天地产生万物不是随意的,是要受气的制约的;天地所生万物之中包括人,人是万物之中最高贵者。在这里,周瑛把民为贵进一步解释为王者要以民为主,是具有进步性的思想。
周瑛基于其天地通过气产生物和人的思想,提出人死后复归气,复归天地,因此人死后是没有鬼神的。其《鬼神》谓,人之生,泊乎其气。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散而未尽而崇兴,是因气尽而死者,魂归于天,魄归于地,崇何从兴?气未尽而死,魂升而沉,魄降而滞。因此,“死而为怪,气未尽也。然则无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暂也。虽曰暂有终化而为无。君子谓之无鬼可也。”
由于周瑛没有鬼神思想,把自己的死看得非常淡薄,认为是自然现象,任其自为,不必悲观。他在生前就自撰圹志,深刻地论述了生死为气聚散,可以等闲生死。其曰:
气聚吾生兮,气散我死;聚散常事兮,吾何悲;人授吾地兮,壶山之颠;屹立万仞兮,摩于青天;中有灵湫兮,我其司汝;鞭笞灵物兮,为云为雨;愧无非泽兮,遍于八荒;愿借杯勺吟,以泽我故乡。③
在这里,周瑛愿自己死后其灵魂化气为青天,为云降雨露八方,泽于故乡。周瑛的这种思想境界是比较高的。
这种由太极(理)通过气产生物和人的宇宙生成论,周瑛概括为一本与万殊、体与用的关系。周瑛认为,理产生万物后,理在物中,是物之必然,物之当然之则;物之理隐蔽在物中,又能通过物表现出来。周瑛把这种关系就叫做体用一元。周瑛说:
求其理谓求其自然与当然,又以自然当然求其所以然。积累既多,自然融会通贯,而于所谓一本者或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学者所敢言,然闻之《中庸》有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又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此譬如谷种,虽曰块然,而根苗花实皆象于此。又如鸡卵,虽曰浑然,而羽毛嘴爪皆具于此,及其发见于行事。在圣人则体用一贯(按因圣人气质全正,行事全是天理),在学者未免差互,盖在己者有所拘蔽(按指气质有欠缺),故所施不无迁就之异。然而既见本原,则于处善亦安,循理亦乐,至于患难事变虽以死易生,亦甘心为之矣。此圣学之大略也。①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出周瑛的世界观。周瑛认为,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归为一本,就是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都离不开天理。就人来讲,圣人由于气质全正,行事全是天理;一般人由于气质有偏和物欲干扰,不能事事符合天理,但可以通过改造使之符合天理。这就是周瑛的体用一元论。
由于体用一元,理和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所谓无,不是如佛家的“真无”(什么也没有),而是“虽无而实有”。其说:
僧曰:吾所谓静与儒同,静无而动有也。予曰:是恶得同,儒于静言无,虽无而实有也。惟其实有,是以见诸用也。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不可改易。子谓无则真无耳。②
这就把儒与佛区分开来了。
周瑛基于其体用一元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天人为理一而已矣。人能顺理则合于天矣,人能顺理则天与之矣。故以人赉天而天无不应者,其几在此也。”③“几”是周瑛哲学中的一个范畴。周瑛说:
天下之事有几有势有形。几,善恶也;势,轻重也;形,治乱也,几动则势趋,势趋则形就。是故几动于善,则其势趋于善矣。④
由此可见,他把善看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或动力。周瑛认为,善能天人一致。周瑛说:
予少读书见史传论福庆于人必归于有德。如尝疑之,晚潜心世故,玩志天人,始知感应之理甚微(按指微妙,包含深意)。盖天人相去虽远,而其理未尝不一(按天道与人道皆出于一理),而其气未尝不相同。其理一而其气相通,而感应之机在我矣。包氏自其先世以来,皆积德行善至于乡邦。①
他认为,包氏行善,因果相应,其三子伯仲皆举甲科。“予观包氏福庆之隆,而知天人感应之机不爽也。诸君退省于其私,以为修德保家之惩劝。”②“天心好善而恶恶,人立心造行务须凑合天心。今日为善,明日为善,始终为善,与天同旋,则天与之矣。今日为恶,明日为恶,始终为恶,与天背驰,则天弃之矣。天之所与,其兴也勃然;天之所弃,其败也欻然。”“知其可畏,则不驱迫而趣于善矣。”③
周瑛讲的天人感应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有很大不同的。周瑛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新的解释。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人格神,天用谴告和灾异来处罚人事,是由天到人;而在周瑛这里则是强调人力可以感天,重视人为,是由人到天。如周瑛谓,“天下事常以贤者胜,以不贤者败。九折坡易破车而使王良卸之无虑,巫峡水善覆舟而使三老渡江必济。”④这就是强调事在人为。周瑛所谓天人感应,是一种顺天理(即事物道理)而从事的思想。人们做事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按事物的道理办事,才能成功。他又谓,“世固有直道事人而为人所弃者,有枉道事人而为人所取者。然为人所弃者,而天(按即周瑛的道德理想)喜之,为人所喜者而天厌之。一得天一得人,轻重何如耶!”⑤这就是说,要“直(按直即遵循)道事人”,“不能枉(按枉即违反)道事人”,要按照客观事物规律办事。在这里,含有某些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因素。
(三)认识论
周瑛的认识论是在与其老友心学家陈献章论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涉及了认识论的许多方面,使福建朱子学的认识论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首先,周瑛把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区分开来,并且肯定主体是可以认识客体的。周瑛激烈抨击主体自我认识的观点。他说:“今夫静坐(按即内省)不相与讲学穷理,果足以立天之大本乎?果足以行天下之大道乎?”这就是说,静坐是不能认识世界之本原的。他说: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此言人心无外也。不即物以穷理,其所静此心之体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纲常之大;自六经之奥,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求其理。①
这里周瑛引用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意为心(认识的主体)能认识事物之理(认识的客体),心外之物理皆可认识。心外之物诸如人之性惰食息、人和物之形骸、社会之纲常、“六经”之旨、天地之万物等,这些都是人的认识对象,这些对象之理都是可以认识的。因此,认识就是从客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以幻为真,也不能以真为幻。周瑛认为,“天下事有实体可据者是谓之真,无实体可据者是谓之幻。世有以幻为真者,亦有以真为幻者。以真为幻,此妙识(按指佛教之观点)也,妙识入于无,故不有其有;以幻为真,此俗识(按指世俗之见)也,俗识胶于有,故不知夫所谓无者。然此二者为说皆非也。”“君子之于天下也,不杂物以自高,不婴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应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这里“以天下之理应天下之事”是个很好的提法。②
其次,主体要认识客体,要先排除主观成见,以心虚照万物。用周瑛的话说,就是“明月照万物,而物无不照。”“月无客心焉;无客心,即所谓虚。虚者,天之道也。”③之所以要先排除主观成见,是因为“水不静则不能鉴物,心不静则不能烛理。盖静则虚,虚则明;动则挠,挠则暗,是静虚其义理之窟乎!动挠其义理之障乎!”④可见,周瑛的认识论是吸取了道家的“虚静”思想的。其曰:“气平则貌温,心虚则理明。自今以往吾当养吾气而使之平,庶不害于温,廓吾心而使之虚,庶不害于明。”⑤周瑛把这种虚心又叫做洗心。他说:
夫易天道也,其有迹可见者曰蓍曰卦曰爻。盖圆而神者蓍之德也,方而知者卦之德也,易以贞者六爻之义也。此三者洁净精微之至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盖寂焉而莫窥其体,有感焉而莫测其用,隐之至也。学者要必先有以探阴阳之蕴,通神明之德,窥见天下之至隐,以其洁净精微之教。洗吾秽浊杂乱之私,然后用神以合蓍,用知以辨卦,用易以贞以合六爻之变,而于天道无不合矣。是圣人所谓洗心者不待洗而洗也。学者洗心要必有以洗之而天道乃得也。①这里虽有天人合一论的神秘主义思想,而其主旨则是在说明只有排除主观成见才能认识事物。
再其次,在主体认识客体问题上,致知而穷理。周瑛提出许多方面,主要有下列几点:
(1)主敬。周瑛反对陈献章的主静说,认为学当以敬为主,居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他说:
始学之要,以收放心为先务。收放心,居敬是已。盖居敬则心存,聪明睿智由此出,然后可以穷理。穷理者非静此心而理自见也,盖亦推之以极其至焉耳。②
这就是说,学要以收放心为先务。收放心则是居敬。居敬则心存,聪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此就能穷理。其又说:
惟居敬则心常惺惺,始可以穷理;惟穷理则君子小人决择精审,而不至于混淆者。③
周瑛认为,只有居敬才能使心时常警觉,这样才能穷理。
(2)读书。周瑛十分强调读书穷理。他认为,天下事见于载籍而其理具于心,求诸心考诸载籍则体用备。其曰:
天道备于圣人,圣人心术于此,《易》、《诗》、《书》、《礼》、《乐》、《春秋》皆书之大者,读书则有以探圣人心术精微之蕴而天道可得,以是而亘三纲,以是而秩五常,以是而酬庶物。天地所以位,万物所以育,皆是物也,恶可不读书!④
在周瑛看来,读书致知即格物致知。他认为,读书将以穷理,将以修行,将以济时。读书而不穷理是自愚;穷理而不修行是自诬;可以仕而不仕是绝物;不可任而任是狗物。自愚非智,自诬非实,绝物非仁,狗物非义。凡此皆非所谓读书。⑤
(3)慎行。在周瑛看来,“《大学》论治国平天下之道本于正心诚意,而又本于格物致知,此所以明为纲领之道也。”①因此,穷理就是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但是道德修养要在平时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离开行为讲道德修养是空谈,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时时检点其身心。自虑念之微以达于事为之蓄,务合于道义,间有不合如被秽在躬,力祛去之乃止。“学不过欲得此心而已(按指学为了道德修养,使此心纯正),不可以外天理人事以求之也。处人事以合天理,则此心得矣。若厌人事而慕高虚,恶积累(按指道德修养要逐渐积累)而求超脱,皆非学也。”“古人书而诵读之,考其迹以求其心,涉于万以会于一,以此而毕圣贤体用之学。”穷理的标志要看其行为如何,“考其迹,以求其心”,“处人事以合天理,则此心得矣”。只有知行一致,才是“圣贤体用之学”。是有合理性的。②
周瑛还特别指出,所穷之理如不在行为中体验,就有可能把道义当成功利,走到邪路上去。他认为,“终生闭户探讨,出而与事接,往往抵牾,间有走四方习知天下事者,引而置诸烦剧皆有获。予始知人材虽俊美而学虽工,不历试诸难,终不足与理天下事也。”③又说:
子之为学亦慎其所趣哉。盖趣吾心于道义,则以道义归焉;趣吾心于功利,则于功利归焉。此二者王霸所自分也,而所以趣之者以志为主。然学之弗博,择之弗精,守之弗固,则此志不知所主,固有舍夫道义之正,而趣夫功利之私者矣。子其慎之乎!④
周瑛强调,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时时检点,即所谓谨独,就是在自己闲居独处之时也要谨慎地遵守道德原则。周瑛说:
张子(按指张载)谓达天德便可以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所谓天德者是理得于心,纯粹至善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独知之地不能致谨,则人欲间之矣,何可以语王道。王道是治道之至纯者也,由天德而出者也。⑤
他强调,人不能无过。过而得闻,闻而能改,则复于无过。无心失理为过,有心悖理为恶。处人之道不过于处己。处己之外无复处人之道。①周瑛的这种“闻过能改”、“改复无过”的命题,是一种既往不咎的思想,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积积意义的。
(4)由用及体、由体及用,一以贯之。此即今所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的认识方法。周瑛认为,致知穷理是循序渐进和反复无限的过程。他认为,“天下事即其小可以占其大,据其始可以据其终”②,“学者求之万,其一乃可至”③,此即由用及体,同时还由体及用。这种体用一贯、反复深化的思想,是有合理因素的。周瑛说:
人心无外,圣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动有以行天下之达道,由体及用,一以贯之。自余为学皆由博以及约。博古者万殊也,约者一本也。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既得一本则所谓万殊者,亦可推此以贯之矣。④
周瑛主张先由万殊至一本,是符合人的认识顺序的,因而是有合理因素的。
(四)社会政治思想
周瑛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几动则势趋,势趋则形就”,形就表现出治乱。天下之事有几有势有形。势趋于善,善重则恶轻,及其至也而治成;势趋于恶,恶重则善轻,及其至也而乱成。“夫治乱形也,然不生于形而生于势。轻重势也,然不生于势而生于几。有善恶是为形势之先,治乱之本也。当时群贤论事,或在治平之后,或在草昧之初,或在存亡危急之秋,其所言事虽有大小,要皆有以审夫几也。夫几动乎于心间不容发,非天下之大智不足以知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用此。故气运不我与,明良不相值,坐失此几者亦多矣。此君子以豪杰之士,又不能不叹其建功立业之为难也。”⑤在这里,周瑛提出几、势、形三个范畴,用以论述社会发展的关键和环节。他把“善”看做是社会治乱发展的关键,几是善恶的矛盾运动,历史的治乱就是由善恶的矛盾运动而决定的。治乱是形,治乱之形生于势;轻重之势生于几,几表现为善恶的矛盾运动,因此善恶之几为治乱之本。周瑛这种抛开社会的经济条件,以道德观念的善恶来作为社会治乱的决定因素,是不科学的。
在上引周瑛的这段论述中,他还提到“气运不我与”。周瑛认为,善恶之几也是气运问题。在他看来,以数百年之事功而成于一旦,十数人之集事同出于一心。谁之力也?御史之力。他认为,人事关于气运。“学校由气运而兴,则人才当应气运而出。”①在周瑛看来,事业的成败在于气运。他根据这种气运说,还用季节的变化和五行运行来解释社会现象。周瑛说:
天顺庚辰:正月一日,天薄雾日色微黄,有霰霏霏而下堂涂,檐瓦不受,而苑内诸树皆白,未几人告忠国公石亨反状。上收其从子定远侯彪斩之,继而亨亦下锦衣卫狱死。其说曰:皆木青也。木属少阳,贵臣之家。三阳之月,万物皆暖矣。木性反寒而阴协之,故霰下堂涂,檐瓦不受,而苑树皆白,此贵臣蒙显戳之象也。当时贵显莫如亨与彪,而取祸之道亦莫盛于亨与彪,是以当之。②
在这里,周瑛为论证自己的这种神秘主义观点所胡乱凑集的这一套,是歪曲事实的。
周瑛认为,救治当时社会腐败之道是复纲纪。他所谓纲纪,就是指当时朝廷应该施行的各种制度和臣民应服从的准则。他指出,天下之弊非一朝一夕之贮积。为天下谋者当思所以致弊之源,而拟听以救弊之道,然后可渐而理。致弊之源为失纪纲,救弊之道为复纪纲。纪纲存则弊消,天下治安;纪纲失则弊滋,天下病。“盖纪纲之于国家犹脉之于人也。人病而脉不病,可不药而愈;人不病而脉病,此华(佗)扁(鹊)所以却望而走焉者。今日纪纲何如哉?!盖其失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所以复之者亦岂一朝一夕所能哉!”③在这里,撇开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把上层建筑的东西作为决定社会治乱的根本,显然是错误的。
在周瑛看来,失纲纪主要是由于当时道德人伦败坏。他认为,“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后世教化不明,“一旦遇有变故,往往臣弃其君,子弃其父,纲常不立,人道大坏,使夫英雄豪杰之出,虽极力营救而不可收拾以归于尽。”④这是说圣学不明而纲常之道坏。“人道一失则夷狄矣,再失则禽兽矣。反夷狄禽兽以归人道。”①
那么,如何恢复纲纪或纲常呢?周瑛认为,要恢复人的善性。“五伦均出于天赋”,人要遵循社会道德伦理的原则才符合人性。②他说:“天道好善而恶恶,喜顺而恶逆。”“人性之中万善俱足,其近者曰孝曰友曰悌,此三善者皆自人性中来。而所以推行之者则孝又是友与悌之本也。予尝观夫世之人矣,凡爱父母深者于兄弟之情恒笃,爱父母浅者于兄弟之情恒薄,其有不知爱父母者则于兄弟漠如也。”③他认为,在道德人伦中最根本的是孝。其次,节、义也很重要。“节义者,人道之大闲也。节、义立,人道定矣。”④
因此,周瑛当时提出要加强道德教育,认为学校以风化为首,风化以节义为先。他说:
吾教兹土,不能使人重节义尚可置而不问乎!嗟夫世之为学校官者,不过集诸生于堂,序订其疑义,校其文字,使取科第以为成绩,至于人为善或为不善,孰问焉!君往矣,异日有怀念君者,必曰:是能助人为学者也,是能侃侃仗义而不属于细事者也。⑤
在这里,周瑛深刻地指出了当时科举取士的弊病,而推出学校应教书又要教人,智育和德育并重。周瑛所提出的德教,就是要培养无欲顺命的人。周瑛说:
龙可豢,麟可絷,凤凰可以网罗取,予尝求其故矣。盖麟凤与龙皆灵物也,然有形焉。有形则有欲,有欲则人得而制之矣。若夫有形而无欲,恶得而制之哉!⑥
他认为,孔子有形无欲,于富贵贫贱死生寿夭皆夷视之。非惟孔子,凡知为学而能自绝于欲者莫不皆然。能制物而不制于物,无欲即顺命。“高牙大纛坐立庙堂吾非薄此不为,也是有命焉,吾恶得而存之;箪瓢陋巷裘褐不完吾非爱此乐为,也是有命焉,吾恶得而去之。”⑦把无欲释为顺命,是欺人之谈。
七 蔡清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蔡清(1453—1508年),字介夫,因其为学主虚,匾其斋曰“虚”,遂号虚斋,学者称虚斋先生,福建晋江(今泉州市)人。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历官吏部稽勋主事、礼部祠祭主事、南京文选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职。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蔡清的著述有《易经蒙引》、《四书蒙引》、《艾言密箴》、《太极图解》(原名叫《看<太极图说>》)、《河洛私见》(原名叫《看河图洛书说》),今存目无书有《纲鉴随笔》、《考定大学传》、《天文略》、《虚斋至言》、《虚斋杂著》、《批点易经大全》等,结辑有《虚斋文集》、《蔡文庄公集》、《蔡虚斋粹言》、《虚斋三书》、《性理要解》等,《四库全书·经部》、《古今粹言》等有选录。
蔡清为官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有政绩,得到时人的称颂。蔡清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曾上书曰:
今士民之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宦官厕养至有宅舍拟于公侯,金银动以万计,此皆万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锱铢而取于民,以为士马之资者,多充牣于庸将之家,转运于权幸之门。于是兵弱不能卫民,虏骑一至而边民身家一扫空矣。①
蔡清在从政期间,反对豪强兼并土地和贪官污吏,要给国家和人民做出大事业。但是,蔡清仅活到50多岁就病逝了。他在临死时与亲友说:
吾平生志慕古人。古人如贾谊、诸葛孔明辈,皆年未四十,做出许多大事业。今吾年过五十,而功业不建,上负天地,中负朝廷,下负祖宗,此吾所以羞也。②
蔡清给自己提出做官的原则是:“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③他能有这种思想并提出这种原则,是难能可贵的。
蔡清平时直言行事,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趋炎附势。如曾载有蔡清任江西提学副使时的一件事:
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即不穿朝服而入),王积不悦。会王求复护卫,清有后言。王欲诬以底毁诏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许以女妻其子,竞力辞去。①蔡清认为,先朝王后朝文庙不合礼制;朝服是臣见君之礼,不能用于见王。因蔡清得罪于宁王宸濠,有一天宸濠宴诸司,蔡清亦与之。宸濠嘲笑蔡清“不能作诗”,而蔡清应之曰:“平生与人无私(诗)。”②此可见蔡清不畏权贵。
蔡清在从政期间,如任江西提学副使时,修《白鹿洞学规》,以德行道义教授学者;告病家居时,设讲堂于泉州水陆寺,学徒众多。据记载,蔡清的门人遍于全国,“有志之士,不远数千里从之,出其门者,皆能以理学名于时。”③像当时知名学者闽人陈琛、林希元、王宣、易时中、林同、蔡烈,赣人舒芬、夏良胜,鲁人赵录,等等,皆为蔡清门人。这些人《明史》均有传,皆是著名的朱子学者,有著述行于世。
蔡清一生大部分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其成就学者评价极高。明人林俊说:温陵(按指泉州)蔡介夫虚斋,“其学以‘六经’为正宗,‘四书’为嫡传,(宋)四儒(按指周程张朱)为真派。平生精力尽用之《易》、《四书》蒙引(按即《易经蒙引》、《四书蒙引》)之间,阐发幽秘,梓学宫而行天下。其于《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其有以见夫天下之赜象。”④蔡清的《蒙引》诸书很有学术价值。
蔡清的学术研究,是在朱熹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尝谓吾平生所学惟师文公而已。……吾为《蒙引》,合为文公者取之,异者斥之,使人观朱注,玲珑透彻,以归圣贤本旨而已”。⑤因此,蔡清的学说就是朱子学。对此,清人李光地评之曰:
虚斋先生崛起温陵,首以穷经析理为事,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说不讲。其于传注也,句读而字义,务得朱子当日所以发明之精意。盖有勉斋、北溪诸君子得之于口授而讹误者,而先生是订。故前辈遵岩王氏谓:自明兴以来,尽心于朱子之学者,虚斋先生一人而已。⑥把蔡清推为明代闽学学者之第一人,是明清两代学者公认的。明人林希元曾谓:入国朝来理学之工者蔡虚斋,“仆读虚斋之书老矣,但觉其汪洋渊澳,尚未得其门径。”①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朱子学学者。他不仅用力阐述朱子学,而且在与心学派论辩中有很大的发展,把朱子学说推进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蔡清的学说出现于朱子学的发展由独盛到稍衰的转变时刻。蔡清是在与明代前期心学派的论战中逐步形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清人蔡廷魁说:
文庄公崛起于明,远录坠绪,殚毕生心力,著《易》、《四书》蒙引,阐孔孟之微言,发明濂洛关闽之正学,刊学宫而播天下,至今学士确守其说毋变。钩深括奥,振落扶衰,文庄公岂非紫阳(即朱熹)功臣哉!②
在这里,蔡廷魁用“钩深括奥,振落扶衰”来评价蔡清学说的历史地位,甚为确当。蔡清的学说是福建朱子学前期发展的高峰和总结,在福建朱子学发展史上确实具有继往开来、振落扶衰的作用。
蔡清的学说是真正的朱子学。历代学者包括和蔡清同时代的学者在内,一般公认蔡清的学说“不悖于程朱”。后人读蔡清的《易》、《四书》蒙引二书,“亲炙私淑,尊崇之不异朱子”。③“朱熹有功于圣人,而(蔡)清则有功于朱氏”④。这是说,蔡清是朱熹后之第一人。
蔡清的生活年代,正是明代陈献章心学盛行之时。心学派把朱子学说视为异端邪说,极力攻击。在反击心学派的众多朱子学者中,蔡清最为突出。蔡清抓住当时心学派的两个要害进行驳斥。其一,心学派认为,心即理。万理具于吾心,吾心即是万理。陈献章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⑤蔡清认为,理在心外。他说:“尽六合皆气也。理则是此气之理耳。”“理以(心)虚而入。”⑥“理”从外而入于心。蔡清在这里明确地肯定了理不在心中而在心外。朱熹认为理在心外,心学派认为理在我心中。蔡清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了心学派,捍卫了朱熹的学说。
其二,陈献章认为,读书穷理不如静坐。蔡清针对陈献章提出的“学穷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①的命题,蔡清在《书戒五条》中批之曰:“前辈云:皋夔、稷契,何书可读?盖此数公者,虽未尝读书,亦未尝不穷理也。……使皋、契生今世,吾知其不能不读书。”②这是从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方法上批判心学派。蔡清强调读书穷理,反对静坐,维护了朱子学说。
蔡清不仅批评了心学派,还对当时及以往的朱子学者没有真正继承朱子学作了评论。他说:
文公折衷众说,以归功圣贤本旨。至宋末诸儒,割裂装缀,尽取伊洛遗言,以资科举;元儒许衡、吴澄、虞集辈,皆务张大其学术,自谓足继道统,其实名理不精,而失之疏略;本朝宋潜溪、王华川诸公,虽屡次辨其非文人,其实不脱文人习气,于经传鲜有究心。国家以经术取士,其意甚美,但命题各立主意,众说纷纭。太宗皇帝(按即明成祖朱棣)命诸儒集经书大全(按指《五经四书大全》),不分异同,混取成书,遂使群言无所折衷。③
这是蔡清对南宋末年以来朱子学发展过程的总结。蔡清谓宋末朱子学者“取伊洛遗言以资科举”,元代朱子学者“名理不精,失之疏略”,当时朱子学者“于经传鲜有究心”,等等,这些批评是公允的,抓住了以往朱子学者弊病的主要问题。
蔡清对朱子学的发展是全面的。蔡清把朱熹的基本思想“理先气后”说改为“理气一致”说,是有创见的。蔡清说:
朱子之说亦有未当者。忠恕不宜分贴一贯。曾子本意是谓忠恕一理贯天下之道而无余者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④
在此书信中,蔡清对于《大学》的看法,与朱子亦有所不同,他以为“知止”两节合下“听讼”一节,为释格物致知之义。并提出去掉朱熹所补格物传。蔡清认为,《大学》格物传混入经文之中,未失,不必补。蔡清对于《易经》的看法与朱子亦有所不同:如对《经》分上下经,朱熹认为,因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蔡清则认为,何不以三十二卦为上经?三十二卦为下经,而乃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也;用九见群龙无首,朱子云用九是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见群龙无首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词。蔡清则认为,孔子《象传》及《文言传》节节皆是主六爻皆用九者。而朱子《周易本义》却不主此说。蔡清又说若依朱子之说,则于用九下又当添六爻皆用九者;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朱子说上句知字重,下句终字重,蔡清则认为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岂偶然哉!岂姑以对上句而无所当哉!此外,蔡清对儒家道统的解释也和朱熹有所不同。蔡清说:
所谓道统之传者即《大学》之道也。所谓允执其中者亦止至善也。仁义礼智之性、道心之正,气质之禀不齐,所以人心惟危也;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者,格物致知也;一则守其平心之正而不离者。诚意正心修身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不过如此。是乃所以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者也。盖昔者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曾子,而及思孟,元(原)无二物也。①
朱熹释道统真传用十六字,即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②在这里蔡清不仅对“十六字诀”的解释与前人不同,并且还引进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
(二)理气无有先后
蔡清认为,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理生气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应该是理气合一,无有先后。蔡清认为,“尽六合皆气也。理则是此气之理耳。先儒(按指朱熹)必先有理而后有气,及理生气之说,愚实有未所详。”③在这里,蔡清暗指朱熹理先气后、理生气之说是出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误。这段话对研究蔡清的世界观颇为重要。蔡清就是以理气合一、无有先后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体系的。蔡清的世界观具有明显的二元论倾向。他所讲理的规定,认为实有是物,实有是气;实有是气,则实有是理。盈天地间一气耳。机之屈伸往来而不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在蔡清看来,实有(物)是气,气(即物)中“机之屈伸往来”就是理,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质言之,理是事物的道理。④事物和关于事物的道理是不能混淆的,前者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后者是关于客观存在的东西的观念。对此,蔡清讲的十分明白。他说: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其曰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耳。此正《易本义》所谓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盖阴阳非道,阴阳所有迭运之理,则道也,非他也。①《易本义》是朱熹的著作。这里“阴阳而指其本体”,是说从各种事物的阴阳关系中概括出来的共性(本体)就是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是说不要把“道”(即“理”)与各种事物的阴阳之气混同起来。阴阳是客观存在的气(事物),不是关于客观存在的气的道理,所以“阴阳非道”;“阴阳所以迭运之理是道”,就是说,理是气的道理;“非他”,即不是在气之外或之上还有一个先于气而独立存在的永恒的理。在这里,蔡清的分析是深刻的,其理论思维是有一定高度的。由于“盈天地间一气”,因此理“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大凡气之所在,理即随之”。②从这种意义上说,理是永恒的,“理之所在,万古不易。理既如此,予之笔亦不能不惟理之命。”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蔡清一方面要坚持理和气不能分割,在气之外或之上没有一个先于气而独立存在的永恒的理;而另一方面又不敢公开违反其祖师朱熹所提出的理是永恒的、“万古不易”的说法。蔡清提出所谓理是永恒的、“万古不易”的,是在“盈天地间一气(物)”、理“无物不在,无时不然”的意义上讲的。在这里,蔡清的理论更接近于气论。
由上所引“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理,可知蔡清把理和道看做具有相同的含义。那么,理和太极呢?他认为,太极者,只是理之尊号也。盖贯万理而一之,谓之大原。太极只是贯乎阴阳五行之中,而实超乎阴阳五行之表,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源。“阴阳动静之中有太极焉。此即所谓阴阳一太极也。所谓非有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者也。”太极者,其本体也。动生于静,静生于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此盖太极之本体也。是岂离于一阴一阳乎!抑岂杂于一阴一阳乎!所谓道之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倚于阴阳。”④蔡清认为,太极贯穿于阴阳五行之气当中,阴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即太极之本体。质言之,太极就是理的尊号。这就是说,太极就是阴阳五行之气的理或道理。
太极就是理,并不是说太极与理的含义未有不同。在蔡清看来,太极是最高最完整的理。他在《太极图解》中反复讲了这个问题。第一,太极是极至之理,所谓无极而太极。“曰无极,言初无个极也。曰而太极,言实则为莫大之极也。”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解释最有权威者是朱熹。朱熹认为,所谓“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蔡清却认为,太极是莫大之极,在太极之上无有极了,太极是理之极至。第二,太极是至广大、尽精微、最中正之理。极字所从来,本是指屋极。故极字从木。今以理之至极而借此以名之,犹道本是道路之义,今亦以此理为人之所当行而借名之耳。太字是大字加一点,盖大之有加焉者也。既曰极矣,而又加以大,盖以此理至广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正。一极字犹未足以尽之,故加太字于极之上,则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易》赞乾曰刚健中正纯粹精者,亦此意。彼则其词备,此则其词绚也。”蔡清关于太极是“理之至极”、“理至广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正”,这种对太极的解释甚为新颖、独到,前人未有此说。
跟理、道、太极分别相连的气、器、阴阳、五行等范畴,蔡清在《太极图解》中亦有深刻的论述。气在先秦是指一种极微的物质。蔡清认为,实有是物,则实有是气,盈天地间一气。可见气是物质。“理为精,气为粗,所谓形而上、形而下也。”“太极为本,二气为末也。”粗末都是指具体的有形迹的事物,是形而下的,人们可以感触到的东西。在蔡清看来,气的具体内容就是指阴阳五行,即所谓“二五(按指阴阳五行)均气”。蔡清说:
盖泥于器而不杂于器,乃所谓道也。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各适其用。形而上者谓之道,道者实妙其全。
蔡清认为,器是有形有象的东西。比如,器具是泥做,但泥并不等于器具。用泥做成的东西就是器,做器之理是道。在这里,蔡清的器和朱熹的器是有所不同的。朱熹认为,“凡有形有象者皆器”①;而蔡清则认为,作器的原料(如泥)不是器,器是制成品。就器是指有形有象的具体东西来讲,朱蔡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已有用阴阳概括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力量,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水、火、木、金、土五种具体物质力量(五行),来说明各种事物的起源。而蔡清直接把阴阳五行归结为气,作为产生世界万事万物的直接原因和元素。
在蔡清的世界观中,理与气、太极与阴阳五行、道与器的关系,相当于精①《朱子文集》卷三六《答陆子静二》。
神与物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分先后,是主体(本体)与用的关系。由于本体之为全体,兼有体用,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蔡清在《太极图解》中深刻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他说:
分理与气,则理为精,气为粗,所谓形而上、形而下也。太极者二气之本体,二气者太极之分支,是太极为本,二气为末也。所以无彼此者,盖精而本者,实包举乎粗而末者。其粗而末者,实皆精而本者之所在耳,故曰无彼此也。明阴阳一太极也。然五行一阴阳处,即便是阴阳一太极处。
二五均气,太极对阴阳则有理气之分。意即为“本体之为主体,兼有体用”。蔡清认为,理和气只是精粗、本末、体用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无彼此”之分的,是密切联系着的。在蔡清看来,这是研究理气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蔡清在《太极图解》中进一步指出,理是通过气表现为万物的,人、物借气而生。在蔡清看来,“盖天下之有不能以自有,而所谓无者有其有也”。不是无中生有,无本身就是有。他说:
水以澄而清,夫水本清也。初何浊之可澄,惟而挠之,或自动而所之者非其他,于是乎有浊耳,然使浊者复得片时之静,则浊滓自沉而还归于清矣。用是以观澄之方,其无出于静之者乎。
水之所以由浊而清,就是因为本来是清的。由此可推,所谓由无到有,也是因为“无者有其有也”,无也是有的一种状态。就理一分殊来说,所谓万物各具一太极。其实是“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各一其太极者,比如日月之光辉一也,或在水或在庭或在屋,同一日月之光辉也。以水得之而为水之光,庭户得之而为庭户之光,屋瓦得之而为屋瓦之光。要之则初无二光也,同受一日月之光。”具体来说,太极生阴阳五行之气,也是一种从有到有(即物到物)的过程。蔡清说:
木气布为春,万物以生;火气布为夏,万物以长;金气布为秋,万物以敛;水气布为冬,万物以藏;土气则寄旺于四序之间,万物之生长收藏者以成。……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
所谓“太极之本然”,就是说太极本来就是有,即太极本来就在物中。
此外,蔡清又在其《藏春窝记》中对理气与阴阳、动静、四时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认述。他说:
天地之所以造化万类者,春夏秋冬四时也,而究其所以为夏为秋为冬者,实一春之气贯通特有伸缩之异耳,元非可以判然异体观也。譬之水,春发其源也,夏秋冬则皆源之流行灌注异坎而同宗者也。由是言之,春之于造化其所职无限大乎!然人知夏秋冬之出于春,而不知春之所从出者冬也。夫冬其春之所藏也。呜呼!亦妙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向使天地之气一于发舒,而无冬以敛藏之,则元气将有时而竭,虽天地亦不能久。其所以为天地者矣,《传》(按指《易传》)不云乎?不专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发散。故太极之用所以行,则先阳动;太极之体所以立,则先阴静。①
这就是说,太极体现在气中,阴阳五行之气为动静和春夏秋冬的内在根据,一春之气贯通特有伸缩之异,各种自然现象就发生了。在这里,蔡清的说法尽管不是科学的,但他力图用物质现象来说明物质现象,是有其合理因素的。
蔡清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构成它们的阴阳五行之数多寡不同。他在《太极图解》中反复讲了这些问题。他认为,“古人欲分别阴阳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为言耳,自一至十之数特言奇偶之数多寡耳,非谓次第如此也。”至于人和物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人受天地之正气,而物则是受天地之偏气,前者为气之精美部分,后者则为气之渣滓部分。他说:
朱子曰: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鸟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此耳。又曰:只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之中渣滓者愚不肖。②
在这里,蔡清力图通过物质性的气产生人和物的表述,是合理的。蔡清还指出,构成人的有气和理。气生形,理生神(即性)。“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此人之所同也。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③
此外,蔡清基于其人和物皆借气以生的思想,在《与柴墟储静夫书》中提出“亡者所藏也在大气之内”的无神论命题。④蔡精的无神论含有物质不灭的思想。
朱熹之后的朱子学,基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朱子学的发源地福建(闽中)与全国的朱子学衍变和发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分开来论述。本章先论述闽中的朱子学(闽学)的传衍分化和派别,全国性的将在下面论述。
南宋王朝是与北方金朝的对峙而存在的。后来,蒙古族的元朝崛起于漠北,宋朝联蒙攻金,于1234年灭金;1270年蒙又灭宋。蒙灭宋后,其首领忽必烈任用汉化契丹人耶律楚材,并经宋降蒙的儒生窦默、姚枢、许衡、刘秉忠等人策划,取《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在元朝统一中国的90年(1280—1368年)中,利用儒家的政治制度来统治全国。由于蒙古族的经济、文化比宋、金落后,他们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尤其残酷,横征暴敛,赋役极重。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对汉人和南人仇视。福建是南人居住的主要地区之一,福建人受元朝的剥削压迫最为严重,反抗元朝统治也最为激烈。这种社会环境对福建朱子学具有深刻的影响。
蒙古贵族统治者在思想上利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宋朝遗留下来的一批儒学家,如窦默、许衡等都被请到朝廷,有的任国子监丞,专门传授儒学,他们被称为元代大儒。在儒学当中,蒙古族统治者又特别提倡程朱理学。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很快由福建地区发展到全国。清人皮锡瑞说:
朱学统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时,程学(按指二程洛学及其后继者朱子学)盛于南,苏学(按指宋时蜀学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姚枢、许衡、窦默、刘因辈翕然从之。①
朱子学原盛行于福建,在元初由闽而至江、浙、皖、赣、两湖、两广、冀、鲁、晋、豫、川、陕等。
至元仁宗时(1312—1320年),朱子学遍及全国。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义军推翻元朝,在南京称帝,国号为明。朱明王朝存在了270年之久,国势在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达到了顶点,到了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7年)由盛而衰,史家称为前期。从朱子学在明代的发展来看,与其相对立的王阳明学说兴起于嘉靖初年,此后朱子学在明代由独盛而稍衰,使明代朱子学形成为两个不同的时期。
元代全国朱子学盛行,相比之下似乎福建朱子学不如全国。当时闽籍朱子学的主要学者如熊禾、陈普、吴海等,没有居于全国地位。其实,从学术思想上看,当时福建的闽学并不落后于全国朱子学。一些主要的福建闽学学者之所以未居于全国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民族气节,不仅不肯仕宦于朝廷,有的还积极进行反抗,因而不仅得不到朝廷的褒扬,还受到诬蔑和打击。他们隐姓埋名,深居山林,从事于教育和学术活动,为士人所罕知。他们忠实于朱熹的思想,是真正的朱子学者。当时,福建闽学人才济济,除下面将要评述的熊禾、陈普、吴海等外,知名者还有丘葵(字吉甫,同安人)、韩信同(字伯循,宁德人)、欧阳光(字以大,长乐人)、张复(字伯阳,建瓯人)、黄镇成(字元定,邵武人)、刘有定(字能静,莆田人)、张复(字伯阳,建瓯人)、黄清老(字子肖,邵武人)、林广发(字明卿,龙溪人)、陈旅(字众仲,莆田人)、雷杭(字颜舟,建瓯人)、陈自新(字贡义,宁德人)、李应龙(字玉林,光泽人)、郭堂(字德基,长乐人)、郑仪孙(号翠屏,建瓯人)、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人)等。他们大都一生从事于朱子学,各自著作数种。
在明代前期,闽籍朱子学学者忠实地阐发朱熹学说。例如,林瀚(字亨大,闽县人),学术醇正,以朱子学为宗,在朝廷正直无私,不以皇帝和宰辅颜色行事,不计较利禄,为世所敬重;林玭(字廷珍,侯官人),以朱子《易》学倡教东南,学务穷理,笃于躬行;郑守道(字用行,侯官人),著《太极图说解》、《大学解》,旨精袐具,全是朱子学风格,有功于后学,等等。
宋元之际至明代中叶,福建朱子学与当时全国朱子学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或者叫做优点。
第一,这个时期福建的朱子学学者大多数坚持朱熹的民族气节论,不肯到朝廷做官为蒙古族统治者服务。熊禾、陈普在南宋末年曾任过地方官,入元后朝廷几次征召不出,甘受贫困,宁可饿死。郑仪孙在宋亡后隐居山林不仕。敖继公中进士后归里务农。邱葵力辞元官。吴海生活在元朝末年,也未曾出来仕元。
第二,福建朱子学学者务实学,强调“躬行”。他们认为,道并非超出于人事之外,道即在人事之中。他们讲学和著述的内容务实切近,反对好高骛远。他们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把“躬行”看成是精义理。他们激烈抨击当时一些空谈心性的理学学者,明确提出研究理学的目的是为了道德践履。他们把朱熹关于“知行相须互发”的观点发挥为要重视“躬行”的实学。
第三,这个时期福建朱子学学者大都潜心于“五经”、“四书”的注疏。他们视注疏“五经”为务本之学,多自幼即为之。由于他们不想仕元,不随流俗,因此他们所注疏的“五经”有自己的特点,以经注发挥朱子学思想,有功于后学。例如,熊禾是元朝的经学家,除《仪礼》外,他对《诗》、《书》、《易》、《春秋》、《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等皆有注疏。他采用集疏,以朱子之说为主,融合诸家之精华,阐发自己的朱子学观点。据不完全统计,元代福建朱子学学者有关经书的注疏达100多种。明代前期福建朱子学学者以精湛研究《易经》闻名全国。其著作有几百种,数量之多全国第一。仅晋江一地研究《易》著名者有数十家,著作达八九十种。明代全国研究《易》者首推晋江,而晋江以蔡(清)、陈(琛)、苏(浚)三家为最。蔡清著《易经蒙引》、陈琛著《易经通典》、苏浚著《易说》,皆为研究《易》学之杰作。蔡清之《易》精而密,陈琛之《易》高而朗,苏浚之《易》渊源蔡清,而其超广洞达,气象绝类陈琛。此三人之《易》学理论,相为表里。其共同的特点是羽翼和发挥朱子学。
第四,福建朱子学学者从不同方面阐发了朱子学。例如,陈普跟随朱熹推崇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通过讲解《太极图说》来说明自己的哲学观点,阐发了朱子学。熊禾在注疏儒家经典中,全面阐发了朱熹的思想。吴海对朱熹的“主敬”说有较深的研究,特别重视道德践履。明人朱衡说:
明以后诸儒,如元吴朝宗(按指吴海)……善守程朱门户,勿为异说所惑,是均有传道(按指朱子学)之功。①
吴海身体力行,凡朱熹之明体达用之学,修己治人之术,罔不一一体验于身心之间,而犹歉然不敢自持,乃颜其读书之室曰闻过斋。
第五,捍卫朱子学。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年),陈宪章、王阳明心学兴起,广泛传播。这时,福建朱子学者绝大部分不为异端所惑,挺身而出,奋起捍卫朱子学。例如,马森(字孔养,侯官人),提出理学必须以朱子学为宗,不可动摇,陆王心学非理学之正脉,不可接受;孔端仪(字子明,莆田人),著《考亭渊源录》,力排王学,言行举止一依朱熹;卢一诚(字诚之,福清人),坚持朱子立场,拒绝参加阳明学社;童世坚(字克刚,连城人),受业于王阳明,归而笃信朱子学,谓王学不若朱学有把握;杨道昭(号天游,建阳人),与王学学者王心斋、王龙溪等反复辩论,激烈抨击阳明学说,称颂朱子学;周瑛(字梁石,漳浦人),以朱熹居敬穷理之说批评王学先驱陈白沙心学;方良永(字寿卿,莆田人),谓言心学者不知其妄;等等。
下面我们选择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福建籍朱子学学者熊禾、陈普、吴海、陈真晟、周瑛、蔡清等加以评述,以窥一斑。
二 熊禾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熊禾(1247—1312年),字位辛,又字去非、退斋,号勿庵、勿轩,学者称勿轩先生,福建建阳人。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熊禾在宋官至汀州司户参军,多有政绩。入元后基于十分强烈的民族大义,誓不仕宦。他在元朝生活33年始终批元颂宋,特别是表彰宋儒,自称“宋之义士元之顽民”。熊禾隐居福建崇安武夷山,筑洪源书堂、武夷书堂,晚年主持建阳鳌峰书院,前后30多年,从事讲学、著述和刻书,研究传播朱子学和其他儒家典籍。
熊禾的著述有《易学图传》、《易经讲义》、《周易集疏》、《勿轩易学启蒙图传》、《春秋通义》、《春秋通解》、《三礼考略》、《四书标题》、《诗选正宗》、《勿轩诗集》、《小学句解》、《注解朱文公先生小学集注大成》、《文公要语》等,结辑有《勿轩集》等,《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正谊堂全书》、《元诗初选集》等有选录。
熊禾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即朱熹——辅广——刘敬堂——熊禾。熊禾在朱子学、经学和教育上卓有贡献,他不仅是元代著名的朱子学家,还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
熊禾竭力推崇朱熹,认为朱熹是孔子第二。他反复强调,“朱文公,百世之师,即今夫子。徽国公(即朱熹)千年之墓视昔孔林。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地。”①他说:
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朱子倡明斯道。……“四书”(按指朱熹《四书集注》)衍洙泗之传,《纲目》(按指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接《春秋》之笔。当今寰海数州之内,何人不读其书。①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人心无所为主。②
熊禾把朱熹章句集注“四书”和孔子整理“六经”并列,俨然视朱熹为孔子之后儒者第一人。熊禾这种评价,为尔后朱熹在儒家中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基础。历代至今公认为朱熹为孔子后儒学之第一人,应是熊禾首先倡导的。
熊禾认为,朱子学的中心思想是治国之大道。他说:
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仪礼、兵刑之具。……文公嘱之门人黄氏榦,且曰:“如用之,固当尽天地之变,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风气,损文就质以求其中可也。”③
他认为,朱子学足以为天地立心、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熊禾准确地认识到朱子学对社会国家的重大作用。不出熊禾所料,朱子学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
熊禾以继朱子学绝续为己任。他认为,“文公殁且百年,门人传习寖益失真,余以为文公之学不行,文公之道不传也。昔游浙中,尝因受业敬堂刘先生,得闻文公晚年所以与勉斋黄先生、潜室陈先生论学之要旨,然后乃知文公之学,其体全体,其用大用,与世之所言第以资诵说者固不同也。”④他又说:
考亭夫子集其大成,平生精力在《易》、《诗》、“四书”。《仪礼》未完书,开端而未竟,九峰蔡氏犹未大畅厥旨。“三礼”,虽有《通解》,而勉斋黄氏、信斋杨氏粗完《丧》、《祭》二书,其授受损益精意尚无能续。若《春秋》,则不过发其大义而已。余虽与君讲求十有七年,《易》、《诗》、《书》仅就绪,《春秋》更加重纂,则皇帝王霸之道亦或粗备。“三礼”乃文公与门人三世未竟之书,君当分任此责,以毕吾志。⑤
这是熊禾在其主持的螯峰书院内与其门人说的。熊禾还谓,这是朱熹“所俟于来学乎,当吾世不完,则亦愧负师训多矣!”①熊禾未食其言,他用二三十年的工夫,孜孜不倦致力于儒家经典。他为学以朱熹诸书是信是行。熊禾用朱子学阐释儒家经典,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
熊禾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是维护朱子学的。他“衍紫阳之正脉,作诗云:斯文一缕千钧日,我辈三经五典身。’其担当斯道为何如哉!”②熊禾不仅是在福建朱子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在全国朱子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二)人能胜天的世界观
熊禾吸取张载“太虚即气”的命题,认为天地间一气而已。他说:“生生而直遂者(按指充实的物)皆阳(气)也,而其虚处即阴(气)。”③在熊禾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太虚即气,因此天地间皆气。阳气生物,故曰实,而阴气为虚也。熊禾把这种虚直的世界观用于社会生活中。他认为,自己不仕元朝,甘于贫困,默默无闻的隐居山林,是虚;但自己著述讲学,有益于后世,却是实。
在熊禾看来,道或理不在事物之外,而在事物之中。因此,在熊禾哲学中,道或理似乎不具世界本原的含义。他认为,道或理是事物的自然规律,人能顺乎自然,其乐无穷。熊禾说:
宇宙间无一物非道,则亦无一处非可乐。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岂好游者,要其胸中自有乐地,故随其所寓,自然景与心会,趣与理融,无所不自适也。④
熊禾的道除了具有事物的自然规律的含义之外,还具有人生应行之路的含义。他把世界观和伦理道德观点结合起来,在《纪典议》中提出道具有立德、立功、立言的含义,认为此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学者言必根于理,文必称行。自然和社会都是有规律的,即皆有其自然之理,当行之路。圣贤是根据事物的规律立教养之法的,而未掺杂一毫私欲于其间。⑤
熊禾认为,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天道有往必复之几,地气无有不伸之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熊禾说:
“易”字从日从月。日中有一为奇,阳数也;月中有二为偶,阴数也。合日月为“易”。故观《图》(按指《河图》)、《书》(按指《洛书》)迭出,可见天地自然之“易”。“易”之作虽则乎《图》、《书》,而其为义,尤莫蓄于日月。盖易者阴阳之道,卦则阴阳之物,爻则阴阳之动也。然有交易、变易之义,在天则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所谓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是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所谓天地设位卑高以陈是也。在《易》书则一阴一阳各有定位,所谓刚柔立本、八卦相错是也。一刚一柔迭相推荡,所谓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是故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人事之吉凶悔吝,物类之得失忧虑。与夫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莫不于是乎尽矣。①
这里充分地表达出了熊禾的辩证法。
熊禾主张遵天命,尽人力。他认为,为君者有拨乱之志,为臣者有尽忠之节。人事既尽,能以天道为定命,故能臻兹大业。这是他强调人定胜天,命自我立。他说:
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孟子不谓命,又曰得之有命,然则将孰从?盖命有二,以性言则理一而已,以气言则分有万之不齐。智愚贤否一类也,富贵贫贱寿夭一类也。以理制数,以性御气,愚可明,柔可强,勤之可以不匮也,仁义之可以得天爵也,修养之可以延年也,为善之可以获福也,孰谓其不可变乎!是故君子但当言理,不当言数;但当论性,不当论命;当然在我,适于在天。敢问三代盛时,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阴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选,科目未兴,科甲之星夫何丽?②
熊禾是把天命看成理,不是人格神;理是事物之道理或规定性,只要人们按照事物之理或规定办事,如修养之可以延年,为善可以获福,愚可明,柔可强,勤之可以不匮。这就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的,自己的命运是自己掌握的。由此可见,熊禾先承认天命,其后又否认了天命。
(三)全体大用的认识修养论
熊禾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例如,天文历法不是天地产生前就有的,也不是天地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人们长期观察天地四时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黄帝颛顼虽云造历,盖未详也。至(尧)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时,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丽于天者,始则而象之岁分为四时,又分为十二月,又分为三百六十日,因其气盈朔虚又为置闰以应周天之度,于是天道可得成矣。这就是说,天文历法是人们根据日月星辰的变化而逐渐认识的,不是上天赐给或圣人头脑里空想出来的。这种讲法是符合科学思想的。熊禾由此推论出朱子学的体系是有体有用,而且体全用大。他说:
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载道之文也。言学而无见于道,则不足以为学;言道而无得乎道之全体,则亦不足以为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时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语之有关于世教亦可以为立言,而皆无见乎道体之全,则亦不足与乎道统之正矣。①
正是由于朱子学体全用大用,是致用之学,因此必须学用结合,即儒道与吏治为一,讲学与论政为一,德权与笃行为一。他反复强调,朱子学体全体、用大,为讲学论政之本。
熊禾基于其学以致用的思想,反对不关心社会国家的空谈,激烈抨击和蔑视不关心世事的儒生下士。熊禾遵循孔子、朱熹教导的“为己之学”,明确提出,研究理论的目的在有功于社会和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自己就是如此做的。熊禾说:
余弱冠读《大学》,玩索有得,始喟然叹曰:“学在是矣!”自此益穷研“四书”以及诸经,务为明体达用之学;每病今世之学者,议论徒多而践履益薄,词华虽工而事功益不竞。②
熊禾特别主张知行统一、实事求是。他说:
余壮而读书颇识《大学》知行之要,益求实事,不竞虚文。勉焉自力于躬行,切亦有志于世故。③他认为,若以敬为宅心之要,盖心存则众理具而万事之纲举,非心存之外别有所谓敬。圣贤之学不讲,人心失其主,理乖事谬,世道随之。“万事具万理,万理在万事,而其妙蓄于人心,一物不体则一理息,一理息则一事废。敬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也。”“心生生不穷者,道也;敬则生矣,生则恶可己也。怠焉则放,放则死矣。此千古圣贤传授心法之妙,学者深体而屡省之也。”④这就是说,只有敬才能生道,才能存道。因此,敬是学者特别要“深体而屡省之”的。
在践履道德伦理上,熊禾还宣扬无物欲而乐道的思想。他认为,“人生苟不以外物为累,则虽羹藜饭糗莫非珍馔,粗绘大布何异衮冕,而荜门圭窦又皆吞风吐月之大厦也。”①嵇山之隐,陋巷之居,虽以四海九州之富、钎朱怀金之贵,而不以易其所乐者哉!熊禾基于他的这种“不以外物为累”的思想,誓不仕元,甘受贫困,宁可饿死。因此,熊禾的无物欲而乐道的思想,并不完全都是禁欲主义的。
此外,熊禾还强调践履道德伦理要心悟躬践。他认为,凡病必有治,治必有要,不独医为然。人的思想病即道德上的欠缺也是可以医治的,而道德修养是有其要旨的。自治治人之道的宗旨在于,“药灵丸不大,棋妙子无多,心悟躬践”,即在于心中真正领悟和实行。②
三 陈普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普(1253—1325年),字尚德,所居有石堂山,自号石堂,学者称石堂先生,福建宁德人。他是朱熹四传弟子,即朱熹—辅广—刘敬堂—熊禾—陈普。陈普一生未做官,为阐发和传播朱子学而奋斗终身。他学问极为渊博,不仅精通朱子学,还对声律、天文、地理、算术等有很精湛的研究。
陈普的著述有《仪礼注释》、《孟子纂要》、《四书集解》、《石堂先生诗》、《朱子武夷棹歌注》等,结辑有《石堂先生遗集》等,《丛书集成初编》、《元诗选》等有选录。
陈普一生以讲学为务,反复强调朱子学的核心问题。陈普说:
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皆在“四书”、“六经”中,如斗极、列宿之在天,五岳、四渎之在地,舍此不求,更求何事?……普读书不多,于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里,姑据来示一二,则其于思孟程朱之大义已有胡越参辰(按指对立两端)之拟。……《诗》、《书》、《易》、《礼》、“四书”微周程朱,学者至于今犹夜行耳。……陆学多犯朱学明辨是非处。③
陈普认为,朱学和陆学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朱学正确而陆学错误,竭力伸朱排陆。在陈普看来,陆学违背儒家正统,是欺世盗名之学。
(二)哲学思想
陈普在论说世界本原的过程中,理学家们常用的无极、太极、道、则、性等都有提到。陈普认为,这些范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理的。
首先,陈普认为,理是事物道理之极至,故又叫做太极,而无极太极只是一个理。天下之物,其形体、性情、位分、度数,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当然。他说:
太极不过道理之总名尔。物有去来、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间,耿耿于人心目中。所以圣人提出,濂洛画出。其所提出画出,只是一个所以为物者而已。思之而见,察之而得。然则形迹声臭可以耳目闻者见,故谓之无极。无极太极只是一个,非有二也。①事物之理是不变的,应该如此,永远如此,是不能变易的,如对君永远要忠等。陈普强调,理之至极不可变易,就是为了说明三纲五常、人伦道德是永恒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其次,陈普认为,理是事物之则、之性。他指出,有物必有则,有形必有性。则,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极。物与形出于气,而则与性,即太极之各具于物者,与物未尝相离。物有去来生死,其则其性乃道理之本体无时而不在。故须别作一处,盖欲使之见其则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理是事物的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性)。理表现在物上则为性。事物之则之性在事物之上,与事物不相脱离,但又与具体事物相区别。理之所以能创造事物,在于先有各种事物的各种形式(即各种规定),如房屋的建筑必先有图样,然后才能与质料(即气)结合而成实际的事物。由于各个事物之则之性不同,才有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不同事物。因此,不同事物之理(即则、性)又是各个不同事物相互区别的标志。
陈普还指出,物与形出于气。他说:
故文公云:非有以离乎阴阳,明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言。盖形气以理为一,然形气须作形气说,道理须作道理说。既须各说,则须画个有形有气者在下,无声无臭者在上。形气是所为者,道理是所以为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然之理也。非独如此,道理本是作一处。②物皆理所当为,则物固小而理至大,物自沉而理至浮,物自后而理自先。这就是说,理是创造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本体者,所以生之谓也。”
陈普所谓则“须画个有形有气者在下,无声无臭者在上”,是指周敦颐所画的太极图:无形的理(太极)在上,有形的阴阳五行之气和人、万物在下。他通过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全面阐明了无极、太极、理、气、阴阳、五行、人、物等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其图最上圈是太极,不可以闻见,故曰无极而太极。意谓太极不可以形气言,虽无而实有。后之儒者将太极作一块混沌之气,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人知其为理而非气。理生阴阳五行之气。陈普说:
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阴阳二气,不可以太极言,但其圈之大之圆与上圈(按此“上圈”即指代表理或太极的那圈)同,则又见其不相离(按即理生气后理气不相离)之妙,中一小圈谓太极(按即作为本体的理),即在阴阳(按即指阴阳二气)中常生常死有常无,谓自中央一个分开作二个(按即指一理生阴阳二气),只是头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为主(按指理为气之主),非又别有一个小底。故文公云:中〇(按即上文讲的‘中一小圈谓太极’)者其本体也。本体即最上圈。本体大小不同,本非有异,亦犹五行下一个小圈,见二五之合为一者,又是大弥六合,小不满一掬之义,画出成此一个,亦是妙处,非有意为之也。①
陈普认为,理生阴阳五行之气,理与阴阳五行之气的精微凝合而成人与万物,以及两端(即男女、雌雄、牝牡)的胚胎。它们是繁殖人与万物的种子。他说:
图下二圈只是一体一太极。男女圈义深最当,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谓天地之生,气化之初,合下只有两端,一阴一阳,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兽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横渠(按张载字)所谓阴阳两端立天地之大义,亦此意也。②
陈普认为,人和万物两端的胚胎既成,就能繁衍无穷。究其最终的根源在于“理”,理是生物之本体。
在陈普看来,理不仅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本体,而且也是可以认识的。理思之可见,察之而得。但是,理只可以心见,而不可以耳闻。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理的产物或表现形式“形迹声臭”之“耳闻目睹”才能认识理,即通过感性知觉,然后进行理性分析,就能认识理。用陈普的话说,就是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不能光空谈大道理。陈普说:
先立其大则必略其小,而迷于下学上达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砺大节至其平居,则放言纵欲致犯清议者,此说开之也。③
“下学”是指日用寻常之学,“上达”是指天理、性命之学。陈普反对只空谈天理、性命。他又说:
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至,又不可骛于虚远而又不察切己之实。①
他认为,陆象山(九渊)的“先立乎其大”之说就是空谈大道理,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为切。陈普讲的由“察切己之实”而“求造道之极至”,即达到做圣贤的大目标。他在这里讲的虽是人的道德修养,而其讲的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方法应该是对的。
四 吴海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吴海(1322—1387年),字朝宗,因尊崇孔孟,自号鲁客,或叫鲁生;又因喜人规过,名其斋曰闻过,学者称闻过夫子。福建闽县下渡(今福州市)人。吴海誓不仕元朝,其朋友王翰任官元朝,吴海劝其死节,后果死节。明徐宗起指出,吴海“平生刚直,终身隐钓,未尝求知于人,然非其人则亦莫能知也”。②吴海一生过着清寒的教育和著述生活。
吴海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义愤,怀有亡国之恨,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是十分突出的。明人王称指出,“先生以刚明仁勇之资,充圣贤诚正修齐之学。不幸生非其时,视当时有不可为者,于是卓然长往终身不污一命。”③吴海的著作,言切而理当,气充而笔严,其于濂洛载道之言有益于世者皆得之。因此,吴海的人品和学识极得后人的称颂。明人张维康说:
刚直不偶,处于山林之下。味圣贤之中,学周程张朱之学,而独嗜为古文,其悲欢忧悦,感时愤事,未尝不寓之于此。故必关乎世教,而流涟光景之辞一不苟为,盖有意于圣贤之文者也。……闽自文公之后,复有如此之人,如此之文也。④
吴海的学说是醇正的朱子学。他研究学问皆据朱熹著作,认为“其寸纸片墨流落人间,自当为世所宝”。⑤有人认为,吴海是朱熹学说的真正继承者。清人蔡衍锟认为,吴海是闽学史上一个关键性人物。吴海学识醇正,所学皆周程张朱之道,故凡一言一行无非出于大中至正。蔡衍锟说:
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按指杨时),其盛也集于朱子,其末也振于西山(按指真德秀),又二百余年而始有剩夫陈氏、翠渠周氏、虚斋蔡氏。向非有先生(按指吴海)之辟邪崇正,傺然挺出于绝续之间,何以继已往而启将来哉!①
这就是说,吴海是朱子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人物。
吴海的著述结辑有《闻过斋集》、《闻过斋诗集》、《命本录》等,《丛书集成初编》、《元诗选》等有选录。
(二)道理读书论
吴海认为,“天不言所出者理”②,“理出于天而具于人之心”③。吴海还用道来释理,认为道是事物当然之理。他说:“道者人伦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乃天下古今人物共行之路。”④因吴海曾谓“天下古今治乱时世不同,而人心无不同者,理一而已”⑤,所以天下古今人物共同之路即是“一理”。吴海认为,理是事物的道理,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因此,人们必须依理而行才行。“安莫于理,理出于天而具于人心。物必有则,事必有宜。大而民生伦纪之间,细而日用动静之际。”⑥因此,顺理则安,逆理必危。
依理而行,就要知理,认识理。在认识论上,吴海很少讲格外物而致知,反复讲学(读书)以致知。他认为,学则致知,知则知所择。通过读书学习使知道的更多;但是要有选择,要选择所知中之正确的部分,加以牢固的掌握住。显然,这是唯理论的认识论。吴海说:
天下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正身修己之法,莫不昭然具在于书,必读之而后有以识事理之当然。……书不可不读,而读之固当有法。盖不读非圣之书,则异端邪说不得以乱吾之聪明,而志定虑专无他歧之惑,讽诵习熟循序渐进,则无欲速不达舍近求远之病,优游涵泳,沉潜玩索,则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实。朝夕孳孳无有间断,则温故知新而有日进之益,骤觉忽喜小得勿足,则人自己得而有必成之效。⑦
吴海的这种以读书(学)为认识起点的思想是以圣贤之书为绝对真理为前提的。他所谓圣贤之书,主要是指孔孟和程朱理学的著作。在吴海看来,除孔孟之外,就是程朱了。孔孟、程朱之道著于书,都是绝对真理。他说:
圣贤之道著于书,学者不能身体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传虽多无益。顾学者莫先于立志,志即定,然后即物以穷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曰孜孜无少间断,则入道有方,进德有序,圣贤可驯致,苟有一毫为利近名之心,则非己之学矣!①在这里,吴海把“格物穷理”改为“即物穷理”是个好提法。不过,吴海所谓“即物穷理”,实际上是由理及物。“力行以求至”,即要真正实践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
吴海特别强调学习要不断深化。不断深化的动力是由学知不足、由教而知困。他说:
为学之道,精知而力行之。知有不逮继可以进行,有所失则改之,以至于无可改,岂不为大善乎?②吴海认为,知之诚难,知之精在乎穷理而已。要日日改之“以至于无可改”。在吴海看来,“至于无可改”就是“知之精”、“致知穷理”了。当然,吴海所谓“至于无可改”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人的认识是矛盾发展的过程,是知与不知、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的过程,因此不可能达到“至于无可改”的。
吴海还指出教对知的重要性。上面已经引到,吴海提出“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此外,吴海还提出“教之身不以言,教者治之本。”③吴海又说:
教,治之本也?学校,风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产以立其业,教之礼仪以正其俗。……民知教则良心生,教立则善人众。大家既服,小民视之而化,风俗无不美。④
教之所以极端重要,就是因为教能出贤才,“小民视之而化”。贤才为政能立国,因此“教,治之本”,“事实无难者,顾难得其人”。⑤
(三)道德伦理观
吴海吸取先秦韩非关于“德者得于内”的观点,而又加入天命论。他说:
德非自外也,得之于天我固有之也。故自吾之爱亲慈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食而悯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无衣,己安而不忍人之危。若其恻隐之情出于天性,随寓而发,非以纳交要誉于人,求报冥冥于天也。然天道无感而不应,人道无施而不酬,顾为德者不可以是没心而已。……恩惠及人,德之余也;孝悌、忠信、仁爱、诚实蓄于身,德之本也。①
他还说“天降民德五常具全”。他把“孝悌、忠信、仁爱、诚实蓄于身”作为“德之本”。这种修养过程要求慎德。他还认为,“理出于天而具于人之心。至善而无恶、纯一而不杂者为吉德;肆情而荡、逐物而不返,暴逸败悖者为凶德。”“学则致知,知则知所择,慎得致确,确则任所守。此慎德之要也。”②吴海之前的一些学者中,一般释德为褒意,只有德与不德之分。吴海提出凶德,其内涵是指不德,即德之贼,是有新意的。
对于理学家所常讲的天理与人欲的矛盾,吴海以“惟德胜欲”加以解决。他认为,“有能洗心濯虑,使方寸湛然”,理义以为之主则道充,就是使德胜欲。③吴海说:
善,人所固有,生而莫不善。天地之性为性也,而为情也未始不善也。耳目鼻口累乎欲,视听言动出乎己。物我相行,万事相感,利害相权也,日用酬酢之间有不得其正焉,斯其为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于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④
此谓“善非取于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就是上引“德非自外也,得之于天我固有之也”。在吴海看来,人之本性是善的,因此应该完全是吉德;但是人的物欲为不善,是凶德。因此,人欲是与人的德性相矛盾的。欲多理则少,无欲理则全。吴海又说:“天下之福,恒生于无欲,而祸每起于贪,贪者无厌,无厌则不知止,不知止故祸必恒随之。然自古及今相接于目前而不戒,岂人情不安福乐得祸哉?由不能止其贪耳。”⑤
吴海进一步指出,由于人们贪得无厌,祸必恒随之。因此,对人们进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世学不明,风俗益薄,人之道将不立于天下,只有读书养心以成德。吴海十分强调社会风化教育,以使知道贪之有愧,与禽兽无异。吴海说:
唯君子能全其性分所有而无私欲之蔽,日用之间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来应之不穷,随寓而安。……观阴阳之变,万物之化,古今往来,治乱相寻,至人所以酬酢万变者(按即乐于道,依理而行)也。①
在吴海的伦理思想中还有父子、兄弟等的对等思想。他认为,古者宗法行于天下,宗族有所统一,人心有所一致。故孝悌隆而习俗美,先王之治容易。吴海说:
恩固赖于相成,而道实原于自致。子焉自致其孝,无怨乎父子不慈;父焉自致其慈,无疾乎子之不孝;兄焉自致其友,无责乎弟之不恭;弟焉自致其恭,无恤乎兄之不友。致于己而不望于人,则其道易成也。②
在吴海看来,伦理关系是双方的,若绝对服从一方,则协调的伦理关系就建立不起来。吴海强调伦理关系“原于自致”,即出于自觉而不能强制,是内在超越。这就讲到了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真谛。
五 陈真晟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真晟(1411—1473年),字晦德,又字晦夫,号剩夫,又自号布衣,学者称剩夫先生或陈布衣,福建镇海卫(今漳浦)人。曾任漳平县学教谕等。
陈真晟的著述有《程朱正学纂要》、《正教正考会通》、《陈剩夫粹言》等,结辑有《陈真晟布衣存稿》、《陈剩夫先生集》、《布衣陈先生集》、《陈剩夫集》等,《正谊堂全书》、《丛书集成》、《古今粹言》等有选录。
陈真晟出身贫苦,有谓其为“卖油佣”。据清初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西人)在其《观感录》中记载:陈真晟的“父为打银匠,携之执业,主人密为防。真晟年十一,语父曰:‘何业而蒙盗贼之防乎?’劝父捨之。问卖油有所得?曰:‘日余二壶。’喜曰:‘此足备养矣。’货油至书舍。闻讲有子孝悌章,大悦;明日又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益喜。入请其师曰:‘小人愿受学,日以余油为贽。’师曰:‘诺。’复告曰:‘我本以卖油代父之业,备日养耳;专一于学,则累我父,须每旦一受讲,日仍卖油。’师从之。逾年学大进。”可见是自学成才。陈真晟自号布衣,其出身是劳动人民家庭。
陈真晟的上祖陈安宓是黄榦高徒,宋末元初的朱子学家;高祖陈址幼是元代朱子学家。陈真晟早年从著名朱子学家唐泰(号东里,长泰人)学《易》。唐泰通晓“五经”,尤精于《易》,著《思诚斋易学》。陈真晟学习刻苦,卓有成就。他私淑明初著名的朱子学家胡居仁,得胡氏之穷理方法。明人周瑛说:
先生之学无师承,自读《中庸》、《大学》始。初读《中庸》,做存养省察功夫;继读《大学》,专从事于主敬穷理。先生本原徵澈,义理精明,有所本也。①
明陈琐称陈真晟之学为“全体大用之学”。“先生学业积力久,大有了悟。读《论语》则悟圣道一贯之旨;读《易通》则悟天地万物之本;读《西铭》则悟理一分殊之原。得存养于《中庸》。得扩充于《孟子》。得圣学始终之要于《大学》。乃以知行二字为用功之纲,以敬之一字为用功之要。静以此敬,涵养其心;动以此敬,持守其身;以此敬而立体,以此敬而致用:盖心身动静一于敬也。先生平生动必以礼,行必以义。不沽名而钓誉。当言则言,当为则为,无所顾虑。尝曰:‘宁自见毁于世俗,毋一得罪于圣贤。’”②在读书人热衷于科举仕官的社会风气中,陈真晟却一反潮流,“不以科举为事”③,“不图做官,安贫乐道,其所著书无非示人以朱学之梯航”④,遂成为明代福建著名的朱子学家。
陈真晟使福建朱子学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当时,朱子学的异端、明代心学的先驱者陈宪章,亦谓对“布衣先生余雅敬慕久矣”。⑤明人陈琐引述当时著名学者的评论说:“陈白沙(即陈宪章)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周畏斋以灵芝醴泉目之,程御史以世间出真儒目之。”⑥清代福建著名学者陈祚康在《全闽道学总纂》中称陈真晟为明代前期福建闽学学者之第一人。陈真晟在福建朱子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公认的。
学者们认为,陈真晟思想得程朱理学之真传。明人张元桢(东白)在《赠行诗》中说:“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彼吴(按指吴与弼)、许(按指许谦)二子盖亦有未是处。”陈真晟的论敌陈献章认为,其学为真正朱子学。陈献章在《诗赠陈剩夫先生》中说:“多谢泉南翁,神交愿倾倒。”“漳南陈先生曰布衣者,其学以子朱子为宗。”学者们认为,陈真晟对朱子学有很大的发展。清代著名的学者蓝鼎元说:
真晟学问纯粹。尝诣阙上书,请补正学,上《程朱正学纂要》,作《心学图》二,一著圣人心与天同运;次著学者法天之运,与周子《太极图说》相发明。又作《正教正考会通》,规制详密。①
明代理学家郑纪说:
今日程朱又几五百年矣。先生在戎伍之中,忧道学之计,以穷理为入门,以主敬为实地,指画心图,而阴阳动静之理明;敷陈王道而经邦济世之术著。闽之后生小子得以觉迷途而归正学者,先生之赐也。先生虽不得游夫程朱之门,亦可谓私淑其道者矣。②
一般认为,陈真晟把程朱之学概括为治心之学,以主敬贯穿于其学的始终,以笃行为学之目的,是其对朱子学的发展。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刘宗周说:
一者诚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独之说,诚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识慎独之义,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学有本领,故立言谛当如此。③陈真晟的闽学思想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教人以礼,感人以德”。④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陈真晟倡导朱熹《家礼》,而使社会风气始正;自陈真晟起,而儒风始正。明人黄直说:
先生之时,有康斋吴公倡道于江右,白沙陈公倡道于岭南。公皆与同时,未见公与之相师友以上下齐议论。则公之学术其渊源虽不可知,然公当海内竟趋功利之时,独能安于布衣从事躬行之学,卓然自立门户,为天下豪杰之所尊仰。则公诚可谓一世之高士也矣。⑤
由此可见,在同时代的诸学者中,陈真晟的思想具有领先的地位。
(二)思想体系
陈真晟一生用力于程朱理学的本源之地,即理、气、心、性等诸范畴的相互关系,使其形成为更加切实致用的严密思想体系。清人张伯行在《陈布衣文集·序》中说:“明布衣陈剩夫先生,奋起南服而有以得程朱正学之奥。盖其专用力于本源之地(按指理气心性)。今观二图及圣要四说,可以知其功力之所在。”此评至为切当。
陈真晟把程朱理学的本质概括为治心之学,是符合程朱理学的实际的,是非常准确的。这是陈真晟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发掘。陈真晟说:“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岂有外于《大学或问》所详居敬穷理之工夫乎!”①“居敬穷理”就是治心。朱子学就是适应宋元明各朝治人心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为了阐发朱子学即心学,陈真晟著《心学图说》,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多言心学。但是,陈真晟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学是不同的。心学派的心学是把心作为宇宙的本体,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源。陈真晟认为,天命之理具于人心,要存心致知笃行,即所谓本源之地。对于陈真晟的心学和心学派的心学之不同,清人张伯行有深刻的分析。他说:
或问余曰:陈布衣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之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尧舜以讫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迄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则为敬,在释氏言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②
可见陈真晟言心与心学派言心,字句相同而实质不同,正如孔子、老子皆言道德,其含义各异;子思、陆九渊皆言尊德性,其本质不同;韩愈、朱熹皆言道统,而途径背驰。总之,陈真晟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学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为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后者为本体论。
陈真晟的思想体系是以讲心为要。他说:
先讲求夫心要。心要既明则于圣学工夫已思过半矣,盖其心体是静坚固而能自立,则光明洞达作得主宰。所以一心有主,万事有纲,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之要得矣,然后可依节目补小学、大学工夫,而其尤急务则专在于致知诚意而已,皆不外乎一敬以为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功,则皆有自得之实矣。①
陈真晟认为,明白了心要,就会懂得把各个方面联系成为一个体系。他撰写《心学图说》,把自己的心学呈现出来。其思想体系是: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是谓之(善)性(五常之性);性为利欲所惑,“法天之当然是性之复”;复性需主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即知行,此即所谓一动一静在于理也。质言之,就是天理——善性、复性——敬(存心)、义(知行)。他认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二者为学《易》之要。以始学言之,存心致知之道亦在乎是。盖主敬即存心,择义即致知。道体极乎其大也,非存心则无以极其大;道体极乎其微也,非致知则无以尽其微。静而不能极夫道之大,动而不能择乎道之微。则虽曰学《易》,亦买椟还珠而已矣。静焉而涵养致知,动焉而慎独诚意,使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己,则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然则因外美而益充内美,发而为至美。
陈真晟的思想就是主敬存心(穷理)和知行并进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明人郑普在《布衣陈先生传》中把陈真晟的思想体系概括为“治心修身”四字,是十分确当的。陈真晟在《答耿斋周轸举人书》中认为,“治心修身”是程朱之学的要法,要以程朱之学为入门要道。
(三)主敬穷理和知行并进
陈真晟深刻地论述了要穷物之理,必须涵养此心,只有主敬才行。他认为,义理之聚于物,犹蚕丝之聚于茧,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绎使丝于茧之外,盖引其绪(指圣贤微言绪论)以出于外。于物理为难,实游其心以入于内。这是说非先养此心不可,使有刚锐精明纯一之气,入其微、步其精以诣其极,使其表里精粗之处无不到,而脱然尽得其妙于吾胸之中。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绎到八九分,则一二分绎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谓最精妙者。精妙既不能绎,则其所绎者八九分,皆其粗者。他说:
得其粗,昧其精,虽谓之全未紬绎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绎,则物物皆不能绎。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张模糊,则张张皆模糊。心粗之病,何以异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望深于道。殆难矣,矧道不惟精深,而为一广大者也。故不能析之极其精,则不能合之尽其大。所谓物有未格,则知有未至者此也。然之所以合之者,又须此心先有广大之量,然后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所谓敬者,岂非涵养此心,使动而穷夫理,则有刚锐精明纯一之气;静而合乎理,又有高明广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实工夫,做到至处,所谓圣学者。①
这就是说,认识事物,就像引蚕丝一样,把蚕丝引出来容易,而深入去了解其物理就不容易,因为把物理从物中拿出来,只有体察、思考才行。因此,要穷物理,必须首先涵养此心。只有“先养此心,使有刚锐精明纯一之气”,才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诣其极,随其表里精粗之处无不能,而脱然尽得其妙于吾胸中”;否则,只能得其现象(粗),得不到本质(精,精妙,即道、理)。在这里,陈真晟认识到思想理论对认识的指导作用,是有其合理因素的。但是,他把这种思想看成是主敬,就是所谓“涵养此心”,是从主观到客观的唯理论的认识论。
在陈真晟看来,主敬穷理修己乃圣学之要,是为学的根本。他说:
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发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为说焉。②
陈真晟提出主敬的内容有四个方面。清人张伯行说:“先生取圣要四说系于法天之图,曰主一无适,曰整齐严肃,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③其中所谓“常惺惺法”,就是时时警觉。此是陈真晟采用北宋谢良佐“主敬是常惺惺法”之说。谢良佐这种说法得到朱熹的赞赏。
这四点均合朱熹的说法。这四点的核心是“专用心于心”④。“专心克治”⑤,即把精力都集中至道德伦理关系上。对此,明人林雍有所解释。林雍认为,陈真晟读(朱熹)《大学或问》,见朱子博采主敬之说,及求之所以为敬;见程子以主一释敬,以无适释一,始于敬字见得亲切。下功夫推得此心之动静而务主于一。静而主于一,则动有所持而外诱不能夺。“意有善恶,若发于善而一守之,则所谓恶者退而听命。”⑥陈真晟的主敬境界就是“客念不复作”、“外诱不能夺”、“发于善(按即五常之善)而守之”。陈真晟说:
今之学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无主一无适之确,则是未尝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穷理,亦只是泛泛焉务读书多而无即事穷理之精,则是未尝穷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门安得观其堂奥,未噬其肉安得味其精髓。①
陈真晟提出以尊德性为穷理之本;道问学为尽心之功。陈真晟的这种用巨细相涵、动静交养的静坐养心之法以实现格物穷理,于朱子学是有所发挥的。
陈真晟在《心学图说》中认为,主敬的最大功用是复性。天心动静之本然是性之原。君子法天之当然即是性之复。圣人亦天心之自然者。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体之,以尽其法天之功效而有序。盖始则主敬,使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即致知诚意之事是圣学之要。自始至终则皆不离乎敬,如是则法天之功至。陈真晟的复性说是受唐人李翱的复性说的影响的。李翱认为,性是人先天的内在本质,是善的,外在的情欲蒙蔽了先天的善性,要用“勿虑勿失”、“寂然不动”的方法克服情欲,便可以复性。陈真晟的以主敬来复性,与李翱的以“勿虑勿失”、“寂然不动”来复性是相似的。②
陈真晟认为,主敬所穷之理和读书、即事所穷之理,此理是否是真理、真知,还必须验之以行。他认为,能行才算真知。明人林雍说:
先生又常语人曰:“人于此学,若真知之,则行在其中矣!”盖以知之真,则处善安、循理乐,其行甚顺。然而,气禀有偏胜,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顺而易者反为逆而难矣。此圣门论学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后,又加以笃行也。③
这就是说,知了并不等于能行,因为人的气禀有偏胜。清李颙在《观感录》中说:“陈真晟之学,以知行并进为宗旨。”在这里,可以说陈真晟知行并进论是后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先驱。
(四)社会政治思想
陈真晟基于其心学,提出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他在《正风教疏》中,以古鉴今,认为三代所以盛者,学校兴,师道立,心学正教倡明于天下。后世虽有学校之设,然专以科举俗学为教。陈真晟强调,当时虽有学校,“然专以科举俗学为教”,“则心学益废”,危害甚大。他说:“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育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现今)科举虽曰考理学以取贤才,而其实累贤才而妨正学,使后生晚进奔竞浮薄而士风大坏者,科举实为之也。”他认为,“科举不罢则正教不可得而行”。①因此,陈真晟提出当时学校教育必须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改革。
陈真晟基于其程朱理学即治心之学,提出学校必须真正进行程朱理学的教育。他曾向明英宗朱祁镇进呈他的《程朱正学纂要》,此书提出“所谓圣学者,程朱之学也”。当时学校虽用程朱之书,但是由于八股取士,而实际上没有进行治心的教育。此书还说:“士习不正,民风不淳,三代盛治未能全复。盖由学校虽用程朱之书,然不过使之勤记诵训诂攻举业而已,而于身心正学之教,则实未尝举行故也。”②
陈真晟指出的当时科举考试的弊病是对的,是有眼光的。他认为,宋元以来,学校虽用程朱之书,但是科举取士仍用隋唐旧制,这实际上是视圣贤正学为无用。圣贤之道自孟子以后千有余年晦而不明;自周、程、张、朱出,此学才大明;自朱熹死后,此学又复晦。因此,他提出科举要用程朱理学,圣贤之学才能由晦而复明。当他看到学校颁行敕谕教条有合程朱教法时,喜之曰:“此学校正教也”。③
陈真晟采取皇帝敕谕中的要语,参以程氏学制,以及朱熹吕氏乡约、贡举私议,作《正教正考会通》。他把考文与考德结合起来,而且认为考德比考文更为重要。这是极有见解的思想。他把考德与考文各分为几等。考德:上上等,即能主敬穷理修己者,就是已经自觉践履道德的;上中等,即能求以主敬穷理修己者,就是正在努力去践履道德伦理的;中上等,即性行端洁,居家孝悌、廉耻礼逊、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者;中中等,即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下上等,即能习经书(学而不实践)者;下中等,即惟记诵旧文、务口耳之学(道德品质极差、不务正学)者。考文:上等,考德名在下之中(下等),则考文虽上亦降;中等,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中等),则考文虽下必取,考德名在上之上(上等),则考文虽下必取,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下等,即为学不务修身),则专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选。陈真晟在教育问题上,始终重德教。这是符合朱熹思想的。④
在社会历史观上,陈真晟主张复古礼,亦即复先王古制。他说:
世人言执古贵乎通今,执古而不通今,犹执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谓古者,即先王之制著于礼经者是也。所谓今者何礼也。岂非流俗之弊习于性成者乎。姑以丧礼言之。古者以不饮酒食肉为礼,今人必以饮酒食肉为礼,如执古则不能以通今,通今则非所谓执古。岂一人真有两个口,其一则执古,又其一则通今乎?抑只是一个口,但遇酒食则通今,及醉饱之后则执古,斯谓可贵乎?愚意古礼用意着力执之犹不能及,多得罪于先王,况今乃以执古为非,以通今为是,则其伤礼败俗宜无不至,又岂可胜言乎!吁孔子执古释君而从下,犹为时之所讥;孟子行古礼尚为王欢所怒,况某以区区而欲执古孔孟之礼,其为所讥毁宜也。然则宁百见毁于世俗,不可一得罪于先王。①
陈真晟正确地认为古今制度不一,执古不能通今,通今不能执古。但是,他认为古者为好,今者为差,今不如古。他这种颂古非今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多数朱子学者共同的毛病。
六 周瑛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周瑛(1430—1518年),字梁石,初号蒙中子,别号翠渠,学者称翠渠先生,福建漳浦人(祖籍莆田,其先世于明洪武年间调戍漳浦,后定居,而周瑛仍自称莆田人)。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进士。曾任广德知州、南京礼部郎中,抚州、镇远知府,四川右布政使,等等。
周瑛一生为官多年,较能秉公办事。他自谓,“以理处物(按即事)是谓之义;以心(按指私心)处理是谓之利。”“求仁惟公为近。惟公之至,斯理之尽。”②周瑛认为,为官办事要公。公即理,亦即仁、义。周瑛所谓的“公”,是指社会国家的利益;而他所谓的“私”,是指某些人的利益。因此,他说要施仁义于君子,“以猛待小人”,即对危害和反对国家统治的人要进行镇压。他说:“晦翁谓此说未尽道理,因自谓欲以宽待君子,以猛待小人。瑛得其说而推行之。自入仕以来,奉以周旋。”③周瑛是根据朱熹的政治思想施政的。此外,周瑛认为,损害民族利益的官不能做,刘静修、吴草庐仕元是事夷狄,是不知《春秋》大义,学孔孟违孔孟之教;宋非桀纣之暴,元非汤武之仁,元灭宋是掠夺、非正义,为官不能助暴。①由于周瑛为官有一定原则,多有政绩,为时人所敬仰。
周瑛为学拜陈真晟为师,得朱子学真传。他尝以书抵剩夫,谓人有古今,心无古今,“平日颇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检于心,以求合于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人及知而暗于天,则恒自曰:此吾学之得也。”②周瑛所谓天命即理。“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周瑛学到了。因此,明冯具区在《科场备用》中谓,“周瑛为理学之精粹,朱学之名臣。”明人周志渠称其为“理学名臣”,谓“天不欲使紫阳道脉历再世而斩,故祖(按指周翠渠)得以续其传”。③周瑛的学问极为渊博。他“幼习举子业,即不安于俗学,自‘六经’、‘四子’(按指‘四书’),以及天文律历、字画、方外之书无所不究,辨析精微,以洞见本原为极致”。④周瑛还工翰墨,笔迹为艺林所珍重。
周瑛与心学家陈献章是多年的老朋友。周瑛谓,“瑛因献章得钞朱子语类书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门人退录其师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尽在是矣。”⑤但是陈献章心学是尊陆贬朱之学。周瑛极力反对陈献章的心学,批判他学术不正,是禅学,规劝其改过,并对其同僚和好友中信奉陈献章心学者,亦规劝其放弃而转向朱子学,致使陈献章极为不满。明代学者何乔远说:“其时白沙陈公之学盛行,名公卿咸为折节,翠渠周公辞而辟之。非白沙为禅学者,周翠渠也。”⑥此谓周瑛之学有心学倾向。
对于周瑛的学问、人品性格和施政之方,时人也有比较概括的评论。明代著名学者杨廉说:
读书以穷理而非务博,作文以明道而不专于求工。心朗徼而月霁,气舒畅以春融。其政事也,虽居今世而每有古意。其进修也,虽在眉寿而时有新功。想其寤寢之际,思维之中不龟山则豫章、非延平必晦翁。其所探也为甚远,其所得也为已丰。然第知其志之有在,而莫窥其学之所终。⑦
这些评价是公正的。
周瑛的著作有《字学纂要》(又名《书纂》,附《字学管钥》)、《政本正均》、《祠山杂录》、《教民杂录》(又名《广孝录》、《正德漳州府志》、《弘治兴化府志》、《莆阳拗史》等,结辑有《翠渠稿》(又名《翠渠诗文集》)、《翠渠摘稿》及《续稿》等。
(二)一本万殊的世界观
周瑛认为,形成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太极(理),由太极(理)产生气之阳动阴静而成天地。他说:
天地何始?曰:自太极生阴阳(两气),始阳动而阴静,阳清而阴浊。其动而清者日旋于外,积一万八百年而天成焉。天成,日月星辰备矣。其静而浊者月聚于内,积一万八百年而地成焉。地成,山岳河海备矣。①
天地形成后,天地又通过气产生万物。由于气化有“伸缩盈虚错综杂揉”之不同,便产生天地间形形色色的不同事物。他认为,“天地生物,气化不齐,伸缩盈虚错综杂揉,故其偏孜乖戾之甚,必生而为毒螫馋噬之物,盖非天地欲生此物也,气之所至不得不生也。”②天地生万物人为贵,故王者养万民亦以人为主,若夫水土之产、昆虫草木鳞介之属皆为人之用,不可与人论轻重。在周瑛看来,天地产生万物不是随意的,是要受气的制约的;天地所生万物之中包括人,人是万物之中最高贵者。在这里,周瑛把民为贵进一步解释为王者要以民为主,是具有进步性的思想。
周瑛基于其天地通过气产生物和人的思想,提出人死后复归气,复归天地,因此人死后是没有鬼神的。其《鬼神》谓,人之生,泊乎其气。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散而未尽而崇兴,是因气尽而死者,魂归于天,魄归于地,崇何从兴?气未尽而死,魂升而沉,魄降而滞。因此,“死而为怪,气未尽也。然则无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暂也。虽曰暂有终化而为无。君子谓之无鬼可也。”
由于周瑛没有鬼神思想,把自己的死看得非常淡薄,认为是自然现象,任其自为,不必悲观。他在生前就自撰圹志,深刻地论述了生死为气聚散,可以等闲生死。其曰:
气聚吾生兮,气散我死;聚散常事兮,吾何悲;人授吾地兮,壶山之颠;屹立万仞兮,摩于青天;中有灵湫兮,我其司汝;鞭笞灵物兮,为云为雨;愧无非泽兮,遍于八荒;愿借杯勺吟,以泽我故乡。③
在这里,周瑛愿自己死后其灵魂化气为青天,为云降雨露八方,泽于故乡。周瑛的这种思想境界是比较高的。
这种由太极(理)通过气产生物和人的宇宙生成论,周瑛概括为一本与万殊、体与用的关系。周瑛认为,理产生万物后,理在物中,是物之必然,物之当然之则;物之理隐蔽在物中,又能通过物表现出来。周瑛把这种关系就叫做体用一元。周瑛说:
求其理谓求其自然与当然,又以自然当然求其所以然。积累既多,自然融会通贯,而于所谓一本者或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学者所敢言,然闻之《中庸》有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又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此譬如谷种,虽曰块然,而根苗花实皆象于此。又如鸡卵,虽曰浑然,而羽毛嘴爪皆具于此,及其发见于行事。在圣人则体用一贯(按因圣人气质全正,行事全是天理),在学者未免差互,盖在己者有所拘蔽(按指气质有欠缺),故所施不无迁就之异。然而既见本原,则于处善亦安,循理亦乐,至于患难事变虽以死易生,亦甘心为之矣。此圣学之大略也。①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出周瑛的世界观。周瑛认为,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归为一本,就是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都离不开天理。就人来讲,圣人由于气质全正,行事全是天理;一般人由于气质有偏和物欲干扰,不能事事符合天理,但可以通过改造使之符合天理。这就是周瑛的体用一元论。
由于体用一元,理和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所谓无,不是如佛家的“真无”(什么也没有),而是“虽无而实有”。其说:
僧曰:吾所谓静与儒同,静无而动有也。予曰:是恶得同,儒于静言无,虽无而实有也。惟其实有,是以见诸用也。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不可改易。子谓无则真无耳。②
这就把儒与佛区分开来了。
周瑛基于其体用一元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天人为理一而已矣。人能顺理则合于天矣,人能顺理则天与之矣。故以人赉天而天无不应者,其几在此也。”③“几”是周瑛哲学中的一个范畴。周瑛说:
天下之事有几有势有形。几,善恶也;势,轻重也;形,治乱也,几动则势趋,势趋则形就。是故几动于善,则其势趋于善矣。④
由此可见,他把善看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或动力。周瑛认为,善能天人一致。周瑛说:
予少读书见史传论福庆于人必归于有德。如尝疑之,晚潜心世故,玩志天人,始知感应之理甚微(按指微妙,包含深意)。盖天人相去虽远,而其理未尝不一(按天道与人道皆出于一理),而其气未尝不相同。其理一而其气相通,而感应之机在我矣。包氏自其先世以来,皆积德行善至于乡邦。①
他认为,包氏行善,因果相应,其三子伯仲皆举甲科。“予观包氏福庆之隆,而知天人感应之机不爽也。诸君退省于其私,以为修德保家之惩劝。”②“天心好善而恶恶,人立心造行务须凑合天心。今日为善,明日为善,始终为善,与天同旋,则天与之矣。今日为恶,明日为恶,始终为恶,与天背驰,则天弃之矣。天之所与,其兴也勃然;天之所弃,其败也欻然。”“知其可畏,则不驱迫而趣于善矣。”③
周瑛讲的天人感应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有很大不同的。周瑛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新的解释。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人格神,天用谴告和灾异来处罚人事,是由天到人;而在周瑛这里则是强调人力可以感天,重视人为,是由人到天。如周瑛谓,“天下事常以贤者胜,以不贤者败。九折坡易破车而使王良卸之无虑,巫峡水善覆舟而使三老渡江必济。”④这就是强调事在人为。周瑛所谓天人感应,是一种顺天理(即事物道理)而从事的思想。人们做事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按事物的道理办事,才能成功。他又谓,“世固有直道事人而为人所弃者,有枉道事人而为人所取者。然为人所弃者,而天(按即周瑛的道德理想)喜之,为人所喜者而天厌之。一得天一得人,轻重何如耶!”⑤这就是说,要“直(按直即遵循)道事人”,“不能枉(按枉即违反)道事人”,要按照客观事物规律办事。在这里,含有某些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因素。
(三)认识论
周瑛的认识论是在与其老友心学家陈献章论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涉及了认识论的许多方面,使福建朱子学的认识论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首先,周瑛把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区分开来,并且肯定主体是可以认识客体的。周瑛激烈抨击主体自我认识的观点。他说:“今夫静坐(按即内省)不相与讲学穷理,果足以立天之大本乎?果足以行天下之大道乎?”这就是说,静坐是不能认识世界之本原的。他说: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此言人心无外也。不即物以穷理,其所静此心之体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纲常之大;自六经之奥,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求其理。①
这里周瑛引用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意为心(认识的主体)能认识事物之理(认识的客体),心外之物理皆可认识。心外之物诸如人之性惰食息、人和物之形骸、社会之纲常、“六经”之旨、天地之万物等,这些都是人的认识对象,这些对象之理都是可以认识的。因此,认识就是从客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以幻为真,也不能以真为幻。周瑛认为,“天下事有实体可据者是谓之真,无实体可据者是谓之幻。世有以幻为真者,亦有以真为幻者。以真为幻,此妙识(按指佛教之观点)也,妙识入于无,故不有其有;以幻为真,此俗识(按指世俗之见)也,俗识胶于有,故不知夫所谓无者。然此二者为说皆非也。”“君子之于天下也,不杂物以自高,不婴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应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这里“以天下之理应天下之事”是个很好的提法。②
其次,主体要认识客体,要先排除主观成见,以心虚照万物。用周瑛的话说,就是“明月照万物,而物无不照。”“月无客心焉;无客心,即所谓虚。虚者,天之道也。”③之所以要先排除主观成见,是因为“水不静则不能鉴物,心不静则不能烛理。盖静则虚,虚则明;动则挠,挠则暗,是静虚其义理之窟乎!动挠其义理之障乎!”④可见,周瑛的认识论是吸取了道家的“虚静”思想的。其曰:“气平则貌温,心虚则理明。自今以往吾当养吾气而使之平,庶不害于温,廓吾心而使之虚,庶不害于明。”⑤周瑛把这种虚心又叫做洗心。他说:
夫易天道也,其有迹可见者曰蓍曰卦曰爻。盖圆而神者蓍之德也,方而知者卦之德也,易以贞者六爻之义也。此三者洁净精微之至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盖寂焉而莫窥其体,有感焉而莫测其用,隐之至也。学者要必先有以探阴阳之蕴,通神明之德,窥见天下之至隐,以其洁净精微之教。洗吾秽浊杂乱之私,然后用神以合蓍,用知以辨卦,用易以贞以合六爻之变,而于天道无不合矣。是圣人所谓洗心者不待洗而洗也。学者洗心要必有以洗之而天道乃得也。①这里虽有天人合一论的神秘主义思想,而其主旨则是在说明只有排除主观成见才能认识事物。
再其次,在主体认识客体问题上,致知而穷理。周瑛提出许多方面,主要有下列几点:
(1)主敬。周瑛反对陈献章的主静说,认为学当以敬为主,居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他说:
始学之要,以收放心为先务。收放心,居敬是已。盖居敬则心存,聪明睿智由此出,然后可以穷理。穷理者非静此心而理自见也,盖亦推之以极其至焉耳。②
这就是说,学要以收放心为先务。收放心则是居敬。居敬则心存,聪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此就能穷理。其又说:
惟居敬则心常惺惺,始可以穷理;惟穷理则君子小人决择精审,而不至于混淆者。③
周瑛认为,只有居敬才能使心时常警觉,这样才能穷理。
(2)读书。周瑛十分强调读书穷理。他认为,天下事见于载籍而其理具于心,求诸心考诸载籍则体用备。其曰:
天道备于圣人,圣人心术于此,《易》、《诗》、《书》、《礼》、《乐》、《春秋》皆书之大者,读书则有以探圣人心术精微之蕴而天道可得,以是而亘三纲,以是而秩五常,以是而酬庶物。天地所以位,万物所以育,皆是物也,恶可不读书!④
在周瑛看来,读书致知即格物致知。他认为,读书将以穷理,将以修行,将以济时。读书而不穷理是自愚;穷理而不修行是自诬;可以仕而不仕是绝物;不可任而任是狗物。自愚非智,自诬非实,绝物非仁,狗物非义。凡此皆非所谓读书。⑤
(3)慎行。在周瑛看来,“《大学》论治国平天下之道本于正心诚意,而又本于格物致知,此所以明为纲领之道也。”①因此,穷理就是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但是道德修养要在平时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离开行为讲道德修养是空谈,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时时检点其身心。自虑念之微以达于事为之蓄,务合于道义,间有不合如被秽在躬,力祛去之乃止。“学不过欲得此心而已(按指学为了道德修养,使此心纯正),不可以外天理人事以求之也。处人事以合天理,则此心得矣。若厌人事而慕高虚,恶积累(按指道德修养要逐渐积累)而求超脱,皆非学也。”“古人书而诵读之,考其迹以求其心,涉于万以会于一,以此而毕圣贤体用之学。”穷理的标志要看其行为如何,“考其迹,以求其心”,“处人事以合天理,则此心得矣”。只有知行一致,才是“圣贤体用之学”。是有合理性的。②
周瑛还特别指出,所穷之理如不在行为中体验,就有可能把道义当成功利,走到邪路上去。他认为,“终生闭户探讨,出而与事接,往往抵牾,间有走四方习知天下事者,引而置诸烦剧皆有获。予始知人材虽俊美而学虽工,不历试诸难,终不足与理天下事也。”③又说:
子之为学亦慎其所趣哉。盖趣吾心于道义,则以道义归焉;趣吾心于功利,则于功利归焉。此二者王霸所自分也,而所以趣之者以志为主。然学之弗博,择之弗精,守之弗固,则此志不知所主,固有舍夫道义之正,而趣夫功利之私者矣。子其慎之乎!④
周瑛强调,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时时检点,即所谓谨独,就是在自己闲居独处之时也要谨慎地遵守道德原则。周瑛说:
张子(按指张载)谓达天德便可以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所谓天德者是理得于心,纯粹至善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独知之地不能致谨,则人欲间之矣,何可以语王道。王道是治道之至纯者也,由天德而出者也。⑤
他强调,人不能无过。过而得闻,闻而能改,则复于无过。无心失理为过,有心悖理为恶。处人之道不过于处己。处己之外无复处人之道。①周瑛的这种“闻过能改”、“改复无过”的命题,是一种既往不咎的思想,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积积意义的。
(4)由用及体、由体及用,一以贯之。此即今所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的认识方法。周瑛认为,致知穷理是循序渐进和反复无限的过程。他认为,“天下事即其小可以占其大,据其始可以据其终”②,“学者求之万,其一乃可至”③,此即由用及体,同时还由体及用。这种体用一贯、反复深化的思想,是有合理因素的。周瑛说:
人心无外,圣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动有以行天下之达道,由体及用,一以贯之。自余为学皆由博以及约。博古者万殊也,约者一本也。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既得一本则所谓万殊者,亦可推此以贯之矣。④
周瑛主张先由万殊至一本,是符合人的认识顺序的,因而是有合理因素的。
(四)社会政治思想
周瑛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几动则势趋,势趋则形就”,形就表现出治乱。天下之事有几有势有形。势趋于善,善重则恶轻,及其至也而治成;势趋于恶,恶重则善轻,及其至也而乱成。“夫治乱形也,然不生于形而生于势。轻重势也,然不生于势而生于几。有善恶是为形势之先,治乱之本也。当时群贤论事,或在治平之后,或在草昧之初,或在存亡危急之秋,其所言事虽有大小,要皆有以审夫几也。夫几动乎于心间不容发,非天下之大智不足以知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用此。故气运不我与,明良不相值,坐失此几者亦多矣。此君子以豪杰之士,又不能不叹其建功立业之为难也。”⑤在这里,周瑛提出几、势、形三个范畴,用以论述社会发展的关键和环节。他把“善”看做是社会治乱发展的关键,几是善恶的矛盾运动,历史的治乱就是由善恶的矛盾运动而决定的。治乱是形,治乱之形生于势;轻重之势生于几,几表现为善恶的矛盾运动,因此善恶之几为治乱之本。周瑛这种抛开社会的经济条件,以道德观念的善恶来作为社会治乱的决定因素,是不科学的。
在上引周瑛的这段论述中,他还提到“气运不我与”。周瑛认为,善恶之几也是气运问题。在他看来,以数百年之事功而成于一旦,十数人之集事同出于一心。谁之力也?御史之力。他认为,人事关于气运。“学校由气运而兴,则人才当应气运而出。”①在周瑛看来,事业的成败在于气运。他根据这种气运说,还用季节的变化和五行运行来解释社会现象。周瑛说:
天顺庚辰:正月一日,天薄雾日色微黄,有霰霏霏而下堂涂,檐瓦不受,而苑内诸树皆白,未几人告忠国公石亨反状。上收其从子定远侯彪斩之,继而亨亦下锦衣卫狱死。其说曰:皆木青也。木属少阳,贵臣之家。三阳之月,万物皆暖矣。木性反寒而阴协之,故霰下堂涂,檐瓦不受,而苑树皆白,此贵臣蒙显戳之象也。当时贵显莫如亨与彪,而取祸之道亦莫盛于亨与彪,是以当之。②
在这里,周瑛为论证自己的这种神秘主义观点所胡乱凑集的这一套,是歪曲事实的。
周瑛认为,救治当时社会腐败之道是复纲纪。他所谓纲纪,就是指当时朝廷应该施行的各种制度和臣民应服从的准则。他指出,天下之弊非一朝一夕之贮积。为天下谋者当思所以致弊之源,而拟听以救弊之道,然后可渐而理。致弊之源为失纪纲,救弊之道为复纪纲。纪纲存则弊消,天下治安;纪纲失则弊滋,天下病。“盖纪纲之于国家犹脉之于人也。人病而脉不病,可不药而愈;人不病而脉病,此华(佗)扁(鹊)所以却望而走焉者。今日纪纲何如哉?!盖其失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所以复之者亦岂一朝一夕所能哉!”③在这里,撇开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把上层建筑的东西作为决定社会治乱的根本,显然是错误的。
在周瑛看来,失纲纪主要是由于当时道德人伦败坏。他认为,“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后世教化不明,“一旦遇有变故,往往臣弃其君,子弃其父,纲常不立,人道大坏,使夫英雄豪杰之出,虽极力营救而不可收拾以归于尽。”④这是说圣学不明而纲常之道坏。“人道一失则夷狄矣,再失则禽兽矣。反夷狄禽兽以归人道。”①
那么,如何恢复纲纪或纲常呢?周瑛认为,要恢复人的善性。“五伦均出于天赋”,人要遵循社会道德伦理的原则才符合人性。②他说:“天道好善而恶恶,喜顺而恶逆。”“人性之中万善俱足,其近者曰孝曰友曰悌,此三善者皆自人性中来。而所以推行之者则孝又是友与悌之本也。予尝观夫世之人矣,凡爱父母深者于兄弟之情恒笃,爱父母浅者于兄弟之情恒薄,其有不知爱父母者则于兄弟漠如也。”③他认为,在道德人伦中最根本的是孝。其次,节、义也很重要。“节义者,人道之大闲也。节、义立,人道定矣。”④
因此,周瑛当时提出要加强道德教育,认为学校以风化为首,风化以节义为先。他说:
吾教兹土,不能使人重节义尚可置而不问乎!嗟夫世之为学校官者,不过集诸生于堂,序订其疑义,校其文字,使取科第以为成绩,至于人为善或为不善,孰问焉!君往矣,异日有怀念君者,必曰:是能助人为学者也,是能侃侃仗义而不属于细事者也。⑤
在这里,周瑛深刻地指出了当时科举取士的弊病,而推出学校应教书又要教人,智育和德育并重。周瑛所提出的德教,就是要培养无欲顺命的人。周瑛说:
龙可豢,麟可絷,凤凰可以网罗取,予尝求其故矣。盖麟凤与龙皆灵物也,然有形焉。有形则有欲,有欲则人得而制之矣。若夫有形而无欲,恶得而制之哉!⑥
他认为,孔子有形无欲,于富贵贫贱死生寿夭皆夷视之。非惟孔子,凡知为学而能自绝于欲者莫不皆然。能制物而不制于物,无欲即顺命。“高牙大纛坐立庙堂吾非薄此不为,也是有命焉,吾恶得而存之;箪瓢陋巷裘褐不完吾非爱此乐为,也是有命焉,吾恶得而去之。”⑦把无欲释为顺命,是欺人之谈。
七 蔡清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蔡清(1453—1508年),字介夫,因其为学主虚,匾其斋曰“虚”,遂号虚斋,学者称虚斋先生,福建晋江(今泉州市)人。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历官吏部稽勋主事、礼部祠祭主事、南京文选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职。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蔡清的著述有《易经蒙引》、《四书蒙引》、《艾言密箴》、《太极图解》(原名叫《看<太极图说>》)、《河洛私见》(原名叫《看河图洛书说》),今存目无书有《纲鉴随笔》、《考定大学传》、《天文略》、《虚斋至言》、《虚斋杂著》、《批点易经大全》等,结辑有《虚斋文集》、《蔡文庄公集》、《蔡虚斋粹言》、《虚斋三书》、《性理要解》等,《四库全书·经部》、《古今粹言》等有选录。
蔡清为官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有政绩,得到时人的称颂。蔡清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曾上书曰:
今士民之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宦官厕养至有宅舍拟于公侯,金银动以万计,此皆万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锱铢而取于民,以为士马之资者,多充牣于庸将之家,转运于权幸之门。于是兵弱不能卫民,虏骑一至而边民身家一扫空矣。①
蔡清在从政期间,反对豪强兼并土地和贪官污吏,要给国家和人民做出大事业。但是,蔡清仅活到50多岁就病逝了。他在临死时与亲友说:
吾平生志慕古人。古人如贾谊、诸葛孔明辈,皆年未四十,做出许多大事业。今吾年过五十,而功业不建,上负天地,中负朝廷,下负祖宗,此吾所以羞也。②
蔡清给自己提出做官的原则是:“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③他能有这种思想并提出这种原则,是难能可贵的。
蔡清平时直言行事,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趋炎附势。如曾载有蔡清任江西提学副使时的一件事:
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即不穿朝服而入),王积不悦。会王求复护卫,清有后言。王欲诬以底毁诏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许以女妻其子,竞力辞去。①蔡清认为,先朝王后朝文庙不合礼制;朝服是臣见君之礼,不能用于见王。因蔡清得罪于宁王宸濠,有一天宸濠宴诸司,蔡清亦与之。宸濠嘲笑蔡清“不能作诗”,而蔡清应之曰:“平生与人无私(诗)。”②此可见蔡清不畏权贵。
蔡清在从政期间,如任江西提学副使时,修《白鹿洞学规》,以德行道义教授学者;告病家居时,设讲堂于泉州水陆寺,学徒众多。据记载,蔡清的门人遍于全国,“有志之士,不远数千里从之,出其门者,皆能以理学名于时。”③像当时知名学者闽人陈琛、林希元、王宣、易时中、林同、蔡烈,赣人舒芬、夏良胜,鲁人赵录,等等,皆为蔡清门人。这些人《明史》均有传,皆是著名的朱子学者,有著述行于世。
蔡清一生大部分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其成就学者评价极高。明人林俊说:温陵(按指泉州)蔡介夫虚斋,“其学以‘六经’为正宗,‘四书’为嫡传,(宋)四儒(按指周程张朱)为真派。平生精力尽用之《易》、《四书》蒙引(按即《易经蒙引》、《四书蒙引》)之间,阐发幽秘,梓学宫而行天下。其于《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其有以见夫天下之赜象。”④蔡清的《蒙引》诸书很有学术价值。
蔡清的学术研究,是在朱熹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尝谓吾平生所学惟师文公而已。……吾为《蒙引》,合为文公者取之,异者斥之,使人观朱注,玲珑透彻,以归圣贤本旨而已”。⑤因此,蔡清的学说就是朱子学。对此,清人李光地评之曰:
虚斋先生崛起温陵,首以穷经析理为事,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说不讲。其于传注也,句读而字义,务得朱子当日所以发明之精意。盖有勉斋、北溪诸君子得之于口授而讹误者,而先生是订。故前辈遵岩王氏谓:自明兴以来,尽心于朱子之学者,虚斋先生一人而已。⑥把蔡清推为明代闽学学者之第一人,是明清两代学者公认的。明人林希元曾谓:入国朝来理学之工者蔡虚斋,“仆读虚斋之书老矣,但觉其汪洋渊澳,尚未得其门径。”①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朱子学学者。他不仅用力阐述朱子学,而且在与心学派论辩中有很大的发展,把朱子学说推进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蔡清的学说出现于朱子学的发展由独盛到稍衰的转变时刻。蔡清是在与明代前期心学派的论战中逐步形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清人蔡廷魁说:
文庄公崛起于明,远录坠绪,殚毕生心力,著《易》、《四书》蒙引,阐孔孟之微言,发明濂洛关闽之正学,刊学宫而播天下,至今学士确守其说毋变。钩深括奥,振落扶衰,文庄公岂非紫阳(即朱熹)功臣哉!②
在这里,蔡廷魁用“钩深括奥,振落扶衰”来评价蔡清学说的历史地位,甚为确当。蔡清的学说是福建朱子学前期发展的高峰和总结,在福建朱子学发展史上确实具有继往开来、振落扶衰的作用。
蔡清的学说是真正的朱子学。历代学者包括和蔡清同时代的学者在内,一般公认蔡清的学说“不悖于程朱”。后人读蔡清的《易》、《四书》蒙引二书,“亲炙私淑,尊崇之不异朱子”。③“朱熹有功于圣人,而(蔡)清则有功于朱氏”④。这是说,蔡清是朱熹后之第一人。
蔡清的生活年代,正是明代陈献章心学盛行之时。心学派把朱子学说视为异端邪说,极力攻击。在反击心学派的众多朱子学者中,蔡清最为突出。蔡清抓住当时心学派的两个要害进行驳斥。其一,心学派认为,心即理。万理具于吾心,吾心即是万理。陈献章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⑤蔡清认为,理在心外。他说:“尽六合皆气也。理则是此气之理耳。”“理以(心)虚而入。”⑥“理”从外而入于心。蔡清在这里明确地肯定了理不在心中而在心外。朱熹认为理在心外,心学派认为理在我心中。蔡清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了心学派,捍卫了朱熹的学说。
其二,陈献章认为,读书穷理不如静坐。蔡清针对陈献章提出的“学穷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①的命题,蔡清在《书戒五条》中批之曰:“前辈云:皋夔、稷契,何书可读?盖此数公者,虽未尝读书,亦未尝不穷理也。……使皋、契生今世,吾知其不能不读书。”②这是从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方法上批判心学派。蔡清强调读书穷理,反对静坐,维护了朱子学说。
蔡清不仅批评了心学派,还对当时及以往的朱子学者没有真正继承朱子学作了评论。他说:
文公折衷众说,以归功圣贤本旨。至宋末诸儒,割裂装缀,尽取伊洛遗言,以资科举;元儒许衡、吴澄、虞集辈,皆务张大其学术,自谓足继道统,其实名理不精,而失之疏略;本朝宋潜溪、王华川诸公,虽屡次辨其非文人,其实不脱文人习气,于经传鲜有究心。国家以经术取士,其意甚美,但命题各立主意,众说纷纭。太宗皇帝(按即明成祖朱棣)命诸儒集经书大全(按指《五经四书大全》),不分异同,混取成书,遂使群言无所折衷。③
这是蔡清对南宋末年以来朱子学发展过程的总结。蔡清谓宋末朱子学者“取伊洛遗言以资科举”,元代朱子学者“名理不精,失之疏略”,当时朱子学者“于经传鲜有究心”,等等,这些批评是公允的,抓住了以往朱子学者弊病的主要问题。
蔡清对朱子学的发展是全面的。蔡清把朱熹的基本思想“理先气后”说改为“理气一致”说,是有创见的。蔡清说:
朱子之说亦有未当者。忠恕不宜分贴一贯。曾子本意是谓忠恕一理贯天下之道而无余者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④
在此书信中,蔡清对于《大学》的看法,与朱子亦有所不同,他以为“知止”两节合下“听讼”一节,为释格物致知之义。并提出去掉朱熹所补格物传。蔡清认为,《大学》格物传混入经文之中,未失,不必补。蔡清对于《易经》的看法与朱子亦有所不同:如对《经》分上下经,朱熹认为,因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蔡清则认为,何不以三十二卦为上经?三十二卦为下经,而乃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也;用九见群龙无首,朱子云用九是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见群龙无首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词。蔡清则认为,孔子《象传》及《文言传》节节皆是主六爻皆用九者。而朱子《周易本义》却不主此说。蔡清又说若依朱子之说,则于用九下又当添六爻皆用九者;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朱子说上句知字重,下句终字重,蔡清则认为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岂偶然哉!岂姑以对上句而无所当哉!此外,蔡清对儒家道统的解释也和朱熹有所不同。蔡清说:
所谓道统之传者即《大学》之道也。所谓允执其中者亦止至善也。仁义礼智之性、道心之正,气质之禀不齐,所以人心惟危也;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者,格物致知也;一则守其平心之正而不离者。诚意正心修身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不过如此。是乃所以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者也。盖昔者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曾子,而及思孟,元(原)无二物也。①
朱熹释道统真传用十六字,即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②在这里蔡清不仅对“十六字诀”的解释与前人不同,并且还引进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
(二)理气无有先后
蔡清认为,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理生气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应该是理气合一,无有先后。蔡清认为,“尽六合皆气也。理则是此气之理耳。先儒(按指朱熹)必先有理而后有气,及理生气之说,愚实有未所详。”③在这里,蔡清暗指朱熹理先气后、理生气之说是出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误。这段话对研究蔡清的世界观颇为重要。蔡清就是以理气合一、无有先后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体系的。蔡清的世界观具有明显的二元论倾向。他所讲理的规定,认为实有是物,实有是气;实有是气,则实有是理。盈天地间一气耳。机之屈伸往来而不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在蔡清看来,实有(物)是气,气(即物)中“机之屈伸往来”就是理,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质言之,理是事物的道理。④事物和关于事物的道理是不能混淆的,前者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后者是关于客观存在的东西的观念。对此,蔡清讲的十分明白。他说: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其曰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耳。此正《易本义》所谓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盖阴阳非道,阴阳所有迭运之理,则道也,非他也。①《易本义》是朱熹的著作。这里“阴阳而指其本体”,是说从各种事物的阴阳关系中概括出来的共性(本体)就是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是说不要把“道”(即“理”)与各种事物的阴阳之气混同起来。阴阳是客观存在的气(事物),不是关于客观存在的气的道理,所以“阴阳非道”;“阴阳所以迭运之理是道”,就是说,理是气的道理;“非他”,即不是在气之外或之上还有一个先于气而独立存在的永恒的理。在这里,蔡清的分析是深刻的,其理论思维是有一定高度的。由于“盈天地间一气”,因此理“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大凡气之所在,理即随之”。②从这种意义上说,理是永恒的,“理之所在,万古不易。理既如此,予之笔亦不能不惟理之命。”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蔡清一方面要坚持理和气不能分割,在气之外或之上没有一个先于气而独立存在的永恒的理;而另一方面又不敢公开违反其祖师朱熹所提出的理是永恒的、“万古不易”的说法。蔡清提出所谓理是永恒的、“万古不易”的,是在“盈天地间一气(物)”、理“无物不在,无时不然”的意义上讲的。在这里,蔡清的理论更接近于气论。
由上所引“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理,可知蔡清把理和道看做具有相同的含义。那么,理和太极呢?他认为,太极者,只是理之尊号也。盖贯万理而一之,谓之大原。太极只是贯乎阴阳五行之中,而实超乎阴阳五行之表,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源。“阴阳动静之中有太极焉。此即所谓阴阳一太极也。所谓非有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者也。”太极者,其本体也。动生于静,静生于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此盖太极之本体也。是岂离于一阴一阳乎!抑岂杂于一阴一阳乎!所谓道之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倚于阴阳。”④蔡清认为,太极贯穿于阴阳五行之气当中,阴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即太极之本体。质言之,太极就是理的尊号。这就是说,太极就是阴阳五行之气的理或道理。
太极就是理,并不是说太极与理的含义未有不同。在蔡清看来,太极是最高最完整的理。他在《太极图解》中反复讲了这个问题。第一,太极是极至之理,所谓无极而太极。“曰无极,言初无个极也。曰而太极,言实则为莫大之极也。”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解释最有权威者是朱熹。朱熹认为,所谓“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蔡清却认为,太极是莫大之极,在太极之上无有极了,太极是理之极至。第二,太极是至广大、尽精微、最中正之理。极字所从来,本是指屋极。故极字从木。今以理之至极而借此以名之,犹道本是道路之义,今亦以此理为人之所当行而借名之耳。太字是大字加一点,盖大之有加焉者也。既曰极矣,而又加以大,盖以此理至广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正。一极字犹未足以尽之,故加太字于极之上,则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易》赞乾曰刚健中正纯粹精者,亦此意。彼则其词备,此则其词绚也。”蔡清关于太极是“理之至极”、“理至广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正”,这种对太极的解释甚为新颖、独到,前人未有此说。
跟理、道、太极分别相连的气、器、阴阳、五行等范畴,蔡清在《太极图解》中亦有深刻的论述。气在先秦是指一种极微的物质。蔡清认为,实有是物,则实有是气,盈天地间一气。可见气是物质。“理为精,气为粗,所谓形而上、形而下也。”“太极为本,二气为末也。”粗末都是指具体的有形迹的事物,是形而下的,人们可以感触到的东西。在蔡清看来,气的具体内容就是指阴阳五行,即所谓“二五(按指阴阳五行)均气”。蔡清说:
盖泥于器而不杂于器,乃所谓道也。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各适其用。形而上者谓之道,道者实妙其全。
蔡清认为,器是有形有象的东西。比如,器具是泥做,但泥并不等于器具。用泥做成的东西就是器,做器之理是道。在这里,蔡清的器和朱熹的器是有所不同的。朱熹认为,“凡有形有象者皆器”①;而蔡清则认为,作器的原料(如泥)不是器,器是制成品。就器是指有形有象的具体东西来讲,朱蔡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已有用阴阳概括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力量,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水、火、木、金、土五种具体物质力量(五行),来说明各种事物的起源。而蔡清直接把阴阳五行归结为气,作为产生世界万事万物的直接原因和元素。
在蔡清的世界观中,理与气、太极与阴阳五行、道与器的关系,相当于精①《朱子文集》卷三六《答陆子静二》。
神与物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分先后,是主体(本体)与用的关系。由于本体之为全体,兼有体用,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蔡清在《太极图解》中深刻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他说:
分理与气,则理为精,气为粗,所谓形而上、形而下也。太极者二气之本体,二气者太极之分支,是太极为本,二气为末也。所以无彼此者,盖精而本者,实包举乎粗而末者。其粗而末者,实皆精而本者之所在耳,故曰无彼此也。明阴阳一太极也。然五行一阴阳处,即便是阴阳一太极处。
二五均气,太极对阴阳则有理气之分。意即为“本体之为主体,兼有体用”。蔡清认为,理和气只是精粗、本末、体用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无彼此”之分的,是密切联系着的。在蔡清看来,这是研究理气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蔡清在《太极图解》中进一步指出,理是通过气表现为万物的,人、物借气而生。在蔡清看来,“盖天下之有不能以自有,而所谓无者有其有也”。不是无中生有,无本身就是有。他说:
水以澄而清,夫水本清也。初何浊之可澄,惟而挠之,或自动而所之者非其他,于是乎有浊耳,然使浊者复得片时之静,则浊滓自沉而还归于清矣。用是以观澄之方,其无出于静之者乎。
水之所以由浊而清,就是因为本来是清的。由此可推,所谓由无到有,也是因为“无者有其有也”,无也是有的一种状态。就理一分殊来说,所谓万物各具一太极。其实是“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各一其太极者,比如日月之光辉一也,或在水或在庭或在屋,同一日月之光辉也。以水得之而为水之光,庭户得之而为庭户之光,屋瓦得之而为屋瓦之光。要之则初无二光也,同受一日月之光。”具体来说,太极生阴阳五行之气,也是一种从有到有(即物到物)的过程。蔡清说:
木气布为春,万物以生;火气布为夏,万物以长;金气布为秋,万物以敛;水气布为冬,万物以藏;土气则寄旺于四序之间,万物之生长收藏者以成。……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
所谓“太极之本然”,就是说太极本来就是有,即太极本来就在物中。
此外,蔡清又在其《藏春窝记》中对理气与阴阳、动静、四时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认述。他说:
天地之所以造化万类者,春夏秋冬四时也,而究其所以为夏为秋为冬者,实一春之气贯通特有伸缩之异耳,元非可以判然异体观也。譬之水,春发其源也,夏秋冬则皆源之流行灌注异坎而同宗者也。由是言之,春之于造化其所职无限大乎!然人知夏秋冬之出于春,而不知春之所从出者冬也。夫冬其春之所藏也。呜呼!亦妙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向使天地之气一于发舒,而无冬以敛藏之,则元气将有时而竭,虽天地亦不能久。其所以为天地者矣,《传》(按指《易传》)不云乎?不专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发散。故太极之用所以行,则先阳动;太极之体所以立,则先阴静。①
这就是说,太极体现在气中,阴阳五行之气为动静和春夏秋冬的内在根据,一春之气贯通特有伸缩之异,各种自然现象就发生了。在这里,蔡清的说法尽管不是科学的,但他力图用物质现象来说明物质现象,是有其合理因素的。
蔡清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构成它们的阴阳五行之数多寡不同。他在《太极图解》中反复讲了这些问题。他认为,“古人欲分别阴阳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为言耳,自一至十之数特言奇偶之数多寡耳,非谓次第如此也。”至于人和物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人受天地之正气,而物则是受天地之偏气,前者为气之精美部分,后者则为气之渣滓部分。他说:
朱子曰: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鸟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此耳。又曰:只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之中渣滓者愚不肖。②
在这里,蔡清力图通过物质性的气产生人和物的表述,是合理的。蔡清还指出,构成人的有气和理。气生形,理生神(即性)。“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此人之所同也。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③
此外,蔡清基于其人和物皆借气以生的思想,在《与柴墟储静夫书》中提出“亡者所藏也在大气之内”的无神论命题。④蔡精的无神论含有物质不灭的思想。
附注
①《经学历史》第九章。
①《道南源委·凡例》。
①《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
①《重修武夷书院疏》。
②《考亭书院记》。
③《考亭书院记》。
④《送胡庭芳序》。
⑤《送胡庭芳后序》。
①《送胡庭芳后序》。
②[清]张伯行:《熊勿轩集序》。
③《虚直轩记》。
④《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诗卷》。
⑤参见《商鞅徙木之信论》。
①《易卦说》。
②《赠熊云岫挟星术远游序》。
①《祀典仪》。
②《谢乡举论学》。
③《谢贡举启》。
④《敬斋铭箴跋》。
①《曝背龛记》。
②以上见《四时治要方序》。
③《答上饶翁山书》。
①《答谢子祥无极太极书》。
②《答谢子祥无极太极书》。
①《答上饶游翁山书》。
②《闻过斋集·序》。
③《闻过斋集·序》。
④《闻过斋集·跋》。
⑤《跋罗源黄氏所臧朱文公手贴》。
①《闻过斋集·序》。
②《闻过斋集》卷五《祭关以弘文》。
③《闻过斋集》卷三《慎德斋记》。
④《闻过斋集》卷三《近道斋记》。
⑤《闻过斋集》卷二《送龙江书院山长序》。
⑥《闻过斋集》卷三《遗安堂记》。
⑦《闻过斋集》卷三《读书室记》。
①《闻过斋集》卷三《阜林乡学记》。
②《闻过斋集》卷三《改轩记》。
③《闻过斋集》卷二《赠闽县学教谕叙》。
④《闻过斋集》卷二《送宁化训导叙》。
⑤《闻过斋集》卷二《送王潮州序》。
①《闻过斋集》卷三《五德堂记》。
②《闻过斋集》卷三《慎德斋记》。
③《闻过斋集》卷三《淡轩记》。
④《闻过斋集》卷三《祠堂记》。
⑤《闻过斋集》卷三《知止轩记》。
①《闻过斋集》卷三《独乐千古轩记》。
②《闻过斋集》卷二《吴氏世谱序》。
①《周翠渠诗文集·祭布衣陈先生文》。
②[明]陈琐:《布衣陈先生行实》。
③[明]林雍:《陈真晟行实》。
④[清]雷鋐:《漳平县学朱子祠记》。
⑤《挽陈先生诗》。
⑥[明]陈琐:《布衣陈先生行实》。
①《上东学宪请补漳浦县学乡贤祠》。
②《祭布衣陈先生文》。
③《祭布衣陈先生文》。
④《祭布衣陈先生文》。
⑤《祭布衣陈先生文》。
①《上当道书》。
②《正谊堂文集》卷七《陈布衣文集序》。
①《二补正学》。
①《答耿斋周轸举人书》。
②《推朱子兼补之说》。
③《正谊堂文集》卷七《陈布衣文集序》。
④《一立明师》。
⑤《明史》卷一七〇《陈真晟传》。
⑥《林雍诗文集·陈真晟行实》。
①《覆宪副何乔新书》。
②[唐]李翱:《复性书》上。
③《陈真晟行实》。
①《程朱正学纂要·程氏学制》。
②《上程朱正学纂要疏》。
③《陈剩夫集·答周公载》。
④以上参见[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四《布衣陈剩夫先生真晟》。
①《执古辨》。
②《抚州府正义堂铭》。
③《复高都宪五宣翁书》。
①参见《读刘静修渡江赋》、《读吴草庐年谱》。
②《翠渠摘稿·自撰蒙中子圹志》。
③《翠渠摘稿序》。
④《漳浦县志·人物》。
⑤《上剩夫师书》。
⑥《名山藏·周翠渠》。
⑦《祭翠渠公文》。
①《天地说》。
②《柳子宥蝮蛇辨》。
③《自撰蒙中子圹志》。
①《题嘉鱼李氏义学》。
②《题嘉鱼李氏义学》。
③《题姜氏双槐堂》。
④《赤城论谏录序》。
①《贺包封君以六十受恩命序》。
②《贺包封君以六十受恩命序》。
③《题资善堂屏门》。
④《赠倪适瞻知怀庆府序》。
⑤《题如此轩》。
①《题嘉鱼李氏义学》。
②《壶中丘壑记》。
③《续骚亭记》。
④《自警说》。
⑤《温明堂记》。
①《洗心亭记》。
②《题嘉鱼李氏义学》。
③《考功司题署记》。
④《石堂书层记》。
⑤参见《莲溪书屋记》。
①《上王冢宰书》。
②《送林蒙庵序》。
③《送黄郎中还南都序》。
④《题族子最高勿斋册》。
⑤《杂说》。
①参见《复林孟和进士书》。
②《锦江赠别诗序》。
③《送陈白沙归南海》。
④《题嘉鱼李氏义学》。
⑤《赤城论谏录序》。
①《浦城辟群学记》。
②《五行类征说》。
③《壶山赠言序》。
④《赠张廷厚分教济宁序》。
①《徐氏贞节挽诗序》。
②《金兰真意序》。
③《棣怀春序》。
④《一室双贞涛序》。
⑤《赠王司训书满序》。
⑥《超然宴处诗序》。
⑦《超然宴处诗序》。
①《管见上堂尊》。
②转引自林次崖:《虚斋先生行略》。
③《艾庵密箴》。
①《明史》卷二四《蔡清传》。
②见林次崖:《虚斋先生行略》。
③嘉靖《泉州府志》卷二五。
④《虚斋先生文集序》。
⑤转引自林次崖:《虚斋先生行略》。
⑥《重修文庄公祠序》。
①《林次厓先生文集》卷三《与吴思斋书》。
②《蔡文庄公集序》。
③[清]杨瞿崃:《栖霞续稿》。
④[明]詹师庇:《咫亭詹先生请諡疏稿》。
⑤《白沙子全集》卷二。
⑥《太极图解》。
①《白沙子全集》卷三《与贺克恭黄门》。
②《蔡文庄公集》卷四。
③转引自林次崖:《虚斋先生行略》。
④《蔡文庄公集》卷二《与郭文博士书》。
①《蔡文庄公集》卷二《与黄德馨石仲殷书》。
②《书经·大禹谟》。
③《太极图解》。
④《四书蒙引》卷五。
①《太极图解》。
②《蔡文庄公集》卷二《寄梅一之书》。
③《蔡文庄公集》卷四《惠夫字说》。
④《太极图解》。
①《蔡文庄公集》卷六。
②《太极图解》。
③《太极图解》。
④《蔡文庄公集》卷二。
①《林次崖先生文集·送张净峰郡守提学浙江序》。
②《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①《重修文庄蔡先生祠序》。
②《紫峰文集序》。
③《粤大记》。
④《经笥堂文钞·林次崖先生文集序》。
①《林次崖先生文集序》。
②《紫峰文集序》。
③《明史》卷二八二《陈琛传》。
④[明]陈敦履、陈敦豫:《紫峰先生年谱》。①乾隆《泉州府志·明列传》。
②参见《明史》卷二八二《陈琛传》。
③《紫峰文集序》。
④《小山类稿选·江西提学佥事紫峰陈先生墓志铭》。
⑤《紫峰先生年谱》。
①《圣人所由惟一理》。
②《正学篇》。
③《赠江西少参陈柏崖先生序》。
④《正学篇》。
①《圣人所由惟一理》。
②《圣人所由惟一理》。
③《赠黄汝为序》。
①《圣人所由惟一理》。
②《正学编》。
③《正学编》。
①《赠太守易嘉言之重庆序》。
②《正学编》。
③《论语·颜渊》。
①《正学篇》。
②《寿武翁制师序》。
③《心如谷种》。
④《与张克轩大尹书》。
①《正学篇》。
②《隘轩记》。
③《圣人所由惟一理》。
④转引自[明]成子学:《紫峰文集序》。
⑤《正学篇》。
①《时轩文集序》。
②《赠叶仕尧尹新兴序》。
③《河桥清饯图诗序》。
①《正学篇》。
②《海云舒集》。
③乾隆《泉州府志·张岳传》。
④[明]吴文华:《苍梧重刻净峰文集选序》。
⑤[明]林希元:《赠张净峰郡守考绩序》。
①乾隆《泉州府志·张岳传》。
②《镇粤楼特祀碑》。
③《恭介奏议》。
④《与姚明山学士》。①《与黄泰泉书》。
②《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③《答聂双江》。
④《答聂双江》。
⑤《太玄集注序》。
①《与夏桂洲阁老》。
②《赠郑太学子荣还曲江序》。
③《与郭浅斋书》。
④《杂言》。
①《蔡文庄密箴序跋》。
②《传习录》中。
③《与黄泰泉书》。
④《草堂学则》。
⑤《答参赞司马张通川》。
⑥《杂言》。
①《与聂双江书》。
②《朱子语类》卷一五《大学二》。
③《与聂双江书》。
④《与聂双江书》。
⑤《与聂双江书》。
⑥《与聂双江书》。
①《杂言》。
②《一齐记》。
③《杂言》。
④《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①《答张甬川书》。
②《与黄泰泉书》。
③《学堂学则》。
④《答邵端峰提学》。
⑤《谏南巡疏》。
⑥《赠大参孙公毅庵序》。
①《江省人才疏》。
②《赠竹泉龚君之河南少参序》。
③[清]雷鋐:《林次崖先生文集序》。
④[明]蔡献臣:《林次崖先生文集序》。
①《林次崖先生文集序》。
②《赠掌教李拙修奖励序》。
③《改正经传以垂世训疏》。
④《复罗整庵冢宰书》。
①《与王蘖谷中丞书》。
②《重刊四书蒙引序》。
③《顺蒙四言》。
①《卡鹤臬荣寿编考》。
②《赠徐东溪三尹擢典宝序》。
③《送郡侯俞蒲山宪副河南序》。
①《贺潭瓶台邑侯祷雨有感序》。
②《贺分教玉田邓先生寿序》。
③《复彭城马宗孔同年书》。
①《和郡守方西川九咏》。
②《复彭城马宗孔同年书》。
③《季考诸生策问三道》。
①《与林国博论格物大学问疑书》。
②《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一》。
③《困知记序》。
④《重刊蔡虚斋先生批点四书程文序》。
⑤《与林国博论格物大学问难书》。
⑥《一田翁对》。
⑦《送举人邓池宪之教政和序》。
①《朱子全书序》。
②《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五十二年八月。
①《陆稼书文集》卷一《学术辨》上。
①[清]陈庚焕:《闽学源流说》。
②《拟重修福州文庙碑》。
③[清]陈庚焕:《闽学源流说》。
④《经笥堂文钞·平州试院与诸生论格致传义》。①《汉学师承记·评序》。
②《四书改错》卷一。
③[清]陈庚焕:《闽学源流说》。
④转引自[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兴时代》。
⑤《昔抱轩尺牍》卷五。
①转引自[清]唐鉴:《清学案小识》卷五。
①参见[清]全祖望:《鲒埼亭集·李文贞遗事》。
②钱穆:《中国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局1998年版,第157页。
③《清儒学案·安溪学案》。
④《清史稿》卷二六二《李光地传》。
①《清儒学案·安溪学案》。
②《榕村全书·诸儒》。
③《清史稿》卷二六二《李光地传》。
④《清儒学案·安溪学案》。
①《尊朱要旨》。
②《大学古本私记序》。
③《大学古本说》。
④《尊朱要旨》。
⑤《孟子篇》。
①以上见《尊朱要旨》。
①《通书篇》。
②《尊朱要旨》。
①《尊朱要旨》。
②转引自[清]雷鋐:《二希堂文集跋》。
③《二希堂文集·鳌峰讲义》。
①以上参见[清]张伯行:《与蔡闻之书》。
②转引自郑贞文:《闽贤事略·蔡世远》。
③《二希堂文集·居业录序》。
④《孟子·公孙丑上》。
⑤《二希堂文集·寄宁化五峰诸生书》。
⑥《二希堂文集·学规类编序》。①《二希堂文集·居业录序》。
②《正谊堂文集·答蔡闻之书》。
③《二希堂文集·学规类编序》。
④《二希堂文集·寄宁化五峰诸生书》。
①《二希堂文集·与李巨来同年书》。
②《二希堂文集·古文雅正序》。
③转引自[清]唐鉴:《清学案小识》卷五《翼道学案·漳浦蔡先生》。
④《漳平县朱子祠记》。
⑤《蔡梁村扪斋初集序》。
⑥《二希堂文集·历代名儒传序》。
①《鹿洲全集·初集》卷一《与张巡抚书》。此书各本文字差异甚大,今引从光绪刻本。
②《棉阳学准》。
①《经学考》。
②《上张巡抚书》。
③《棉阳学准》。
④《送谢古梅太史还闽序》。
①《历代历法考》。
②《棉阳学准》。
③《棉阳学准》。
④《棉阳学准》。
①《棉阳学准》。
②《棉阳学准》。
③《棉阳学准》。
①《棉阳学准》。
②《棉阳学准》。
③《棉阳学准》。
④《棉阳学准》。
①《棉阳学准》。
②《棉阳学准》。
③《朱子语类》卷四《论人物之性气质之性》。
④《与荆璞家兄论台变书》。
⑤《论南洋事宜书》。
①《论南洋事宜书》。
②《棉阳学准》。
③《棉阳学准》。
④《棉阳学准》。
①《棉阳学准》。
②《棉阳学准》。
③《与友人论浙尼书》。
①《冠豸山堂文集跋》。
②[清]唐鉴:《清学案小识》卷九。
③[清]雷鋐:《寒泉童先生慕志铭》。
④《朱陆渊源考》。
①《朱陆渊源考》。
②《太极辨微》。
③《太极辨微》。
④《子朱子为学次第考》。
①《子朱子为学次第考》。
②《中天河洛》。
③《答清流伍鹤声》。
④《乐律古义·候中气于地》。
⑤《太极辨微》。
①《朱陆渊源考》。
②以上见《朱陆渊源考》。
③《太极辨微》。
①如《老子》第16章。
②《老子略例》。
③《太极辨微》。
④《作讹成易论》。
①《中天河洛》。
②《周易剩义序》。
③《周易剩义序》。
④《中天河洛》。
①《周易剩义序》。
②《乐律古义·积数》。
③《乐律古义·积数》。
④《乐律古义·五音源于河图包洛书》。
①《理学疑问》。
②《理学疑问》。
③《理学疑问》。
④《格致录》。
⑤参见《约语追记》。
①以上见《理学疑问》。
②《理学疑问》。
①《与周抚军书》。
②《复陈榕门前辈》。
③《屯田说》。
④[清]唐鉴:《清学案小识》卷五。
⑤《竹山精舍记》。
⑥见[清]朱梅崖:《雷鋐文集序》。①《答朱梅崖》。
②《清学案小识》卷五《宁化雷先生》。
③《清史稿》卷二九〇《雷鋐传》。
④《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
⑤《胡敬斋先生文集居业录合刊序》。
⑥《雷鋐文集序》。
⑦《与长汀赵邑侯书》。
⑧《漳平县朱子祠记》。
①《阳明禅学考》。
②《阳明禅学考》。
③《与李贯之》。
①以上见《胡州试院与诸生论太极图说通书》。
②《金坛试院示诸生》。
③《真西山读书记序》。
①《湖州试院与诸生论太极图说通书》。
②《朱子语类》卷六二《中庸一》。
③《朱子文集》卷七六《中庸章句序》。
④《湖州试院与诸生论太极图说通书》。
⑤《江宁试院示诸生》。
①《理学疑问》。
②《子朱子学次第考》。
③《答平和曾为谦》。
④《答郑一志》。
⑤《中天河洛》。
①《朱子文集》卷四〇《答何叔京书五》、卷三二《答张敬夫书三》。
②《严州试院与诸生论格致传义》。
③《知行存养论》。
①《竹山精舍记》。
②《陆宣公全集笺注序》。
③《与李贯之》。
④《湖州试院与诸生论太极图说通书》。①《松溪县学记》。
②《书李生传后》。
③《送吴子涵碧游浙序》。
④《送伊子墨卿会试序》。
①《主一元适论》。
②《读陆稼书先生读朱随笔》。
③《重刻治心录序》。
①《重刻治心录序》。
②《礼敬策》。
③《礼敬策》。
①《重刻治心录序》。
②《松溪县学记》。
③《答王廷有书》。
①《经义治事策》。
②《送伊子墨卿会试序》。
③《读陆稼书先生读朱随笔》。
①《读陆稼书先生读朱随笔》。
②《主一无适论》。
①《四书拾遗自序》。
②《开辟传疑》。
③《开辟传疑序考》。
①《清史稿》卷四七九《孟超然传》。
②《瓜棚避暑录》。
③《诚是录》。
①《诚是录》。
②《诚是录》。
③《丧礼辑录序》。
④《诚是录》。
①《诚是录》。
②《瓜棚避暑录》。
③《瓜棚避暑录》。
④《求复录》。
⑤《晚闻录》。
⑥《克省录序》。
⑦《求复录》。
①《瓜棚避暑录》。
②《诚是录》。
③《晚闻录》。
④《焚香录》。
⑤《答郑云门书》。
⑥《求复录》。
①《克省录序》。
②《瓜棚避暑录》。
③《瓜棚避暑录》。
①[清]余潜士:《惕园全集序》。
②以上见《畅园全集·乡贤事实》。
③《性道图》。
①《五伦说》。
②《性道图》。
③《无恩而无不通为圣人论》。
④《性道图》。
①《性道图》。
②《性道图》。
③《气禀说》。
①《识警》。
②《好善伏于天下论》。
③《故纸随笔》。
①《约语追记》。
②《约语补录》。
③《虚仁李说》。
④《问学赘说》。
①《约语追记》。
②《与余耕顿茂才潜士书》。
③《问学赘说》。
④《永福余而遂七十寿序》。
⑤《与余耕邨才潜士书》。
⑥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
⑦《尽心近譬》。
⑧《故纸随笔》。
①《尽心近譬》。
②《谈五常》。
③《糖粿喻气质之性》。
④《气禀说》。
①《气禀说》。
②《童子摭谈》。
③《与陈茂坚书》。
④《与余耕顿茂才潜士书》。
①转引自[清]陈宗英:《惕园先生行述》。
②《约语补录》。
③《劝学刍言》。
④《劝学刍言》。
①《劝学刍言》。
②《与姚懋勤书》。
③《劝学刍言》。
④《立志说》。
①《劝学刍言》。
②《刘石湖制义跋》。
③《劝学刍言》。
①《尚书·大禹谟》。
②《劝学刍言》。
③《劝学刍言》。
④《劝学刍言》。
⑤《送五弟晓农之福清序》。
①《送五弟晓农之福清序》。
②《屺云楼文钞·复倪粹卿书》。
③《屺云楼文钞·复倪粹卿书》。
①《李梅生小芋香馆诗钞序》。
②《苏鳌石亦佳室诗文钞序》。
③道光《福建通志》总卷三八·分卷五。
④道光《福建通志》总卷三八·分卷五。
⑤《蒋慕生“易”说引》。
①《彭仲山无近名斋文钞序》。
②《籀经堂类稿序》。
③《郑云麓先生文集序》。
④《彭仲山无近名斋文钞序》。
①《吕西邨类稿序》。
②《吕西邨类稿序》。
③《蒋恭生易说引》。
④《易经儿说序》。
①《福州郭氏族谱序》。
②《郭榴山易录序》。
③《郭榴山易录序》。
④《张石洲烟雨归耕图序》。
①《宋元学案·勉斋学案》。
②《中庸总序说》。
①《北溪语录》。
②《竹林精舍语录》。
③《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
④[明]戴铣:《朱子实纪》卷首。
①[清]张伯行:《西山文钞序》。
②《西山问答》。
③《西山问答》。
④《四书标注》。
⑤[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一《邱公葵》。
⑥[韩]李退溪:《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增补退溪全书》第3册,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9年影印本,第496、520页。
①[韩]李退溪:《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增补退溪全书》第3册,第496、520页。
②[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一《方公权》。
③[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五《林公雍》。
④[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五《林公玭》。
⑤《尊朱要旨》。
⑥《朱子文集》卷八三《跋蔡神与绝笔》。
①《皇极经世全书解部论》。
②《答江功书》。
③《皇极经世指要》。
④[清]蓝鼎元:《棉阳学准》。
⑤转引自翁易:《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
①《太玄集注序》。
①《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训门人七》。
②《宋元学案》卷七七。
③《宋元学案》卷四九。
①《与舒国裳修撰书》。
②参见《疏天文稿》第二八种《林子》。
①《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237页。
②见《困知录》附录,《答林次崖佥宪》。
③《北溪语录》。
④《四书疑略》卷一。
①《周礼·夏官司马》。
②《史记·东越列傅》。
③以上参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673页;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福建学刊》1991年第2期。
④《欧阳行周集》卷三。
①参见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②[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五。
③[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卷二。
④第4卷第24期,1937年4月。
⑤《朱子文集》卷九七《皇考朱公行状》。
⑥《朱子文集·别集》卷六《与林择之六》。
⑦《答李仲久问目》,《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313页。
⑧参见《张南轩集》卷二一《致朱元晦》。
①《求可堂两世遗书》卷三方冀亨《求可家训》。
②民国《上杭县志》卷二三雷赞明《溟池遗训序》。
③《勉斋集》卷八《朱子行状》。
④台北《史学评论》1985年第9期。
①章廷泗:《对宋代闽北文化全盛的思考》,《福建学刊》,1989年第2期。
②乾隆《武夷山志》卷首史贻直《武夷山志序》。
③乾隆《武夷山志》卷首何瀚《武夷山志序》。
④《朱子文集》卷八〇。
①《宋史》卷四二〇《黄榦传》。
②淳熙《三山志》卷四〇《世俗类》。
③《宋史》卷四二〇《陈淳传》。
④康熙《南溪书院》卷一《朱子年谱》。
⑤《朱子文集》卷七七。
⑥[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七《书院》。
⑦民国《尤溪县志》卷四《祠庙》。
①雍正《崇安县志》卷六《科弟》。
②[民国]詹继良:《五夫子里志》卷一一《游寓》。
③康熙《建宁府志》卷一〇《书院》。
④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学校志》。
⑤民国《政和县志》卷三《名胜志》。
⑥康熙《建宁府志》卷五《山川》下。
①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元揭汯《重建湛庐书院记》。
②《夷坚志》。
③麻沙:《刘氏忠贤传》卷九。
④《朱子文集》卷八五、卷七五、卷七四《论诸职事》。
⑤[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1册卷三《历代褒典》。
⑥参见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303页。
⑦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三《学校·安溪县》。
①[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一《方域·泉州府·安溪县》。
②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六《学校·泉州府》。
③洪谷:《安海古镇》,《厦门日报》1984年1月16日。
①乾隆《晋江县志》卷四《学校·书院》。
②《朱子文集》卷五。
③嘉靖《安溪县志》卷七。
④民国《南平县志》卷一〇《学校》。
⑤民国《建阳县志》卷一〇《艺文》,《朱子文集》卷八七《祭何叔京知县文》。
⑥陈荣捷:《朱子门人》,第93页。
⑦[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1册卷三《历代褒典》。
①《朱子文集》卷七八《云谷记》、卷六;嘉靖《建宁府志》卷二〇《古迹》。
②《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
③转引自《式古堂书画汇考·画考》卷一三。
④《朱子语类》卷二《理气下》。
⑤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志》。
①康熙《建宁府志》卷四四[明]林雍:《星溪书院记》、卷一〇《书院志》。
②[明]戴铣:《朱子年谱》卷一。
③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
④《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自论为学工夫》。
⑤《朱子文集》卷七五。
⑥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一《祀典》。
⑦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四《学校志》。
⑧乾隆《古田县志》卷七《寓贤》。
①嘉庆《福鼎县志》卷六《流寓》。
②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五《学校》。
③《朱子文集》卷七七。
④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五《学校》。
⑤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四《学校志》。
⑥《闽书》卷三七《建置志·漳州府》。
⑦光绪《漳州府志》卷二四《官绩·朱熹》。
①光绪《龙溪县志》卷二四《艺文》。
②[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七。
③《闽书》卷三二《建置志》。
④民国《福建通志》卷一一《金石志》。
⑤《朱子文集》卷八四。
⑥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⑦《闽书》卷三二《建置志》。
⑧光绪《紫阳朱氏建安谱》。
⑨光绪《紫阳朱氏建安谱》。
①万历《建宁府志》卷三三《名宦志》。
②民国《建阳县志》卷一〇《艺文》。
③《朱子实纪》卷七《书院》。
④《朱子文集》卷九。
⑤乾隆《武夷山志》卷五《五曲》。
⑥民国《古田县志》卷二四《艺文》。
①乾隆《古田县志》卷四、八。
②民国《建阳县志》卷三《名胜》。
③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五《学校·建阳县》。
④[明]朱世泽:《考亭志》卷一《沧洲形胜·考亭图说》。
⑤乾隆《武夷山志》卷一六《名贤·理学》。
⑥《朱子遗迹访问记》,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2月号。
⑦《学规类编》。
①《朱子与书院》,台北《史学评论》1985年第9期。
②《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③《正谊堂文集》卷一二《蔡恭靖先生墓志铭》。
④《钱庵方公文集》卷二一。
①[宋]祝穆:《方舆胜览》。
②《朱子文集》卷七八。
③嘉靖《建阳县志》卷六、卷五。
④郑志路:《书灯田》,《清词锋》,第35页。
⑤《朱子文集》卷七八。
⑥《朱子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六四》。
①《新唐书》卷一八《百官志》。
②《朱子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二〇》。
③《朱子文集》卷三三。
④《朱子文集》卷四〇《答何叔京三》。
①《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卷首。
②《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卷首。
③孔传:《东家雜记》卷上《历代崇奉》。
④参见郎廷极:《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
①《四书疑略》卷一。
②以上参见笔者与友人陈其芳:《关于研究福建地方哲学的几个问题》,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学会1984年印。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