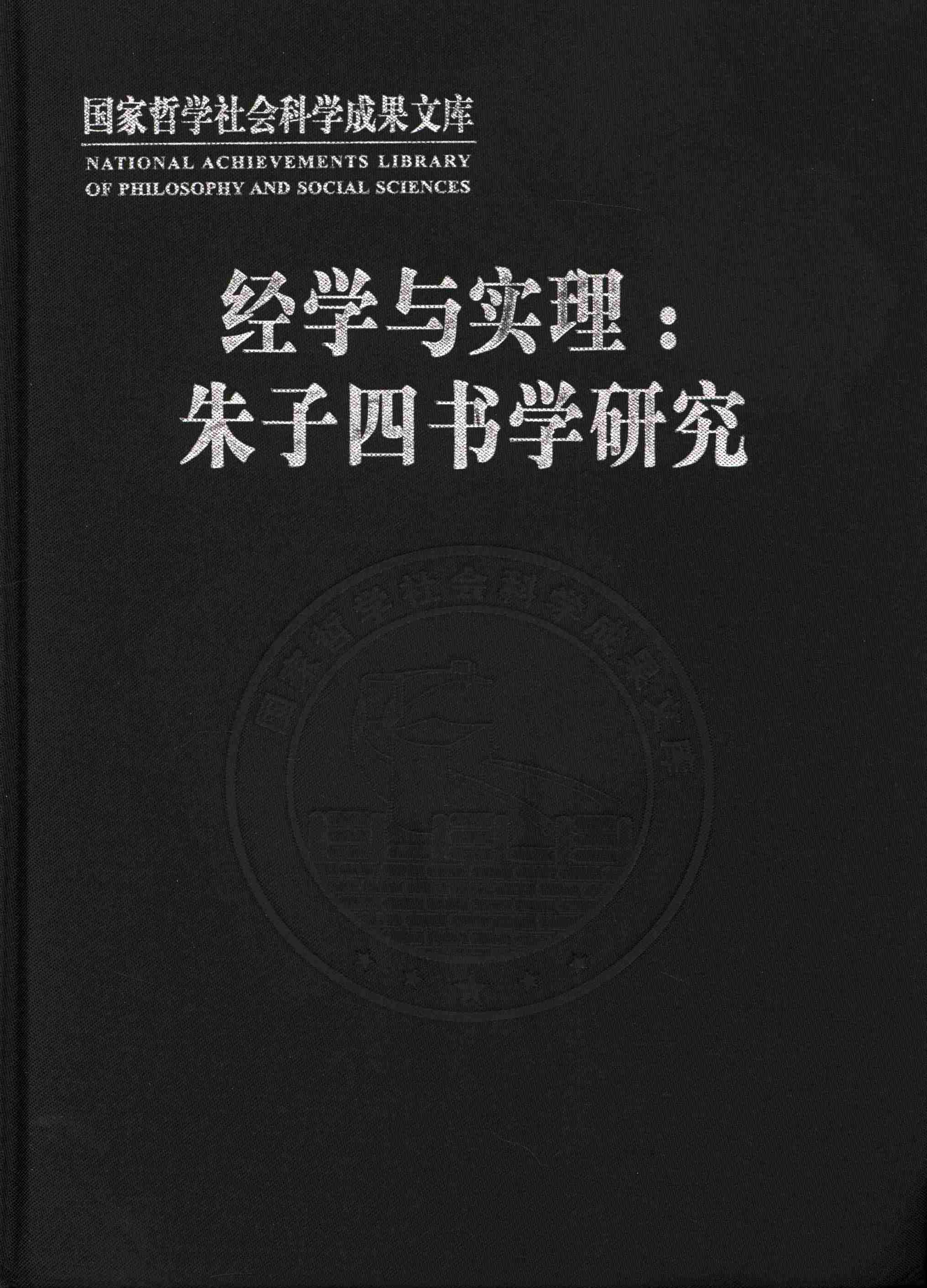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四节 朱子《四书》书信年代再考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902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朱子《四书》书信年代再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2 |
| 页码: | 503-524 |
| 摘要: | 这段文字考察了朱子书信的编辑方式,指出后人编定的《文集》和《语类》中可能存在书信的杂糅和重出。对于确定朱子书信年代的基础性意义在于审慎对待非朱子自定的材料,特别是对于涉及不同时期书信的混合和编辑问题,需要保持怀疑和审慎的态度。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编辑方式 |
内容
朱子书信年代的考察对于客观呈现朱子思想的复杂演变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然朱子思想形成历经多年,其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始终处于动态修改之中,对同一论题的看法在不同时期又常有差异。故对其书信年代的研究,必具历史变化之眼光方能有所收获。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新编》于此树立了典范。据朱子书信所蕴含的事实信息出发(指人名、地名、事件等)以定其年代的事实考察法无疑是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但朱子有不少书信并未蕴含明显的事实信息,而是纯粹的讨论学术问题,对这些书信我们就只能就其所透露的思想来确定年代。采用“思想”考察这一辅助方法的根据是:鉴于朱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朱子与门人之间通常就某一论题同时展开相互交流切磋的情况,可采用论题相互比照的方法,来大致推定其书信年代,其效用虽不如事实考察法有效,然“虽不中,亦不远矣。”
故本书拟将思想与事实考察方法相结合,重新考证数十封有关四书的书信年代,试图提出几个共性问题:一是《朱文公文集》虽为原始文献,然经后人之手,难免存在书信的杂糅、重出;二是《朱子语类》同样由后人删补而成,未可全据记录者来判定其年代;三是作为确定书信年代中心线索之一的朱子《四书》处于不断修改过程中,将其作为判定年代依据时当采取灵活、审慎态度;四是各书信之年代应保持相洽而无矛盾。
一 书信杂糅与重出
朱子传世著作甚多,但由其本人定稿的甚少,今人研究所惯用的《文集》、《语类》皆为后人所编,其中难免有混杂不清、甚至谬误之处。故对非朱子自定材料,皆须持一怀疑审慎之眼光,这对于确定朱子书信年代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一)书信杂糅
朱子《文集》书信编辑,采用以人系书的方式,时有不同年代书信杂糅为一的现象,甚或同一段书信而来自不同时期,在此情况下,其书信下注年代即不可据信。①如《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第5—8这四封长札皆是不同时期书信之混合。以《答蔡季通》八最为典型,该札题下小字注“癸丑(1193年)三月二十一日”,全文共9段,除首段小注标明实为癸丑外,其余段落内容应皆非此年书信,乃各期书信之混杂,故对各段皆须逐条考订。
1段:中间到宅。题下注:癸丑三月二十一日。②
2段:《启蒙》修了未?早欲得之。《通书》、《皇极例》等说,不知已下手否?……只欲得贤者一来,会语数日为幸。
按:此提及修《启蒙》、写《通书》、《皇极例》等,戴铣《朱子实纪年谱》载癸巳四月朱子“《太极图传》,《通书解》成”③。丙午1186年三月“《易学启蒙》成”④。据此讨论三书之撰写,以《通书解》完成为限,似在癸巳1173年前后。3段:所苦且喜向安……许见访,幸甚。……此行见上,褒予甚至。言虽狂妄,无仵色。
按:据此提及“此行见上,褒予甚至”,当为辛丑1181年末。据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载,辛丑十一月朱子“奏事延和殿。极陈灾异之由,与夫修德任人之说。上为动容悚听。十二月视事于西兴”①。黄榦《朱先生行状》亦言,“及对,卒言之。上委曲访问,悉从其请”②。
4段:伯谏来此已两三日……约左右一来相聚。……其所论极不争多,孤城悉拔,合并兵力,一鼓可克也。
按:“伯谏来此已两三日”与《答范伯崇》十书“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正相应,陈来先生考证《答范伯崇》十书为庚寅春夏,故此书亦当在此稍前,即庚寅1170年春夏。③
5段:中间报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说……《律说》少有碍处……《启蒙》所疑……《律说》幸早改定。
按:此提及《启蒙》与《律说》,朱子丙午作《易学启蒙序》、丁未作《律吕新书序》,该书应在丙午1186年、丁未1187年前。其反复提及《律说》,与《续集》《答蔡季通》第六书“律说幸早写寄”、第九十二书“律说幸写寄”相通。
6段:《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昨看此间写本,脱一“吾”字,烦一哥为看。如少,即添之。此虽不系义理,然亦觉少不得也。“费隐”之说,今日终日安排,终不能定。盖察乎天地,终是说做“隐”不得,百种计较,更说不来。且是所说“不知”、“不能”,“有憾”等句,虚无恍惚,如捕风系影,圣人平日之言,恐无是也。与“未之或知”、“不可能也”不同。不审看得如何?幸详以见喻也。
按:此段文字分别讨论《中庸序》与“费隐”说,实为不同时期书信的杂糅。前者讨论《中庸章句》序文及其刊刻,反映的应是朱子对《中庸》具有较为成熟看法的时期。目前确切关于《章句序》的文献,一为丙午1186年《答詹帅》,一为己酉1189年《中庸章句》,故可认为此处关于《中庸序》的一段似在丙午1186年后。后者则连“费隐”“不知”等文字义理尚处于恍惚捕捉状态,据《文集》相关文献可知,朱子已在壬辰、癸巳年间与张栻、吕祖谦等人反复讨论《中庸》的章句处理(如《答张敬夫论中庸章句》、《答张敬夫再论中庸章句》,与石子重商定《中庸集解》并作《中庸集解序》等),对“费隐”等文义的理解已不是问题。故可推出此段文字当为朱子早年思想之反映,应在壬辰1172年前。
7段:仁义之说……《中庸》、《诗传》,幸速修改示及,《中庸》更有数处,今并录呈。
按:此处提及《中庸章句》《诗集传》的修改,据朱子《诗集传序》(《文集》卷七十六),该书作于淳熙丁酉1177年,故此书当在丁酉年左右。
8段:西山之约……归来又得伯恭书。
按:吕祖谦亡于辛卯1181年,《朱子实纪年谱》第54页言,七月“东莱吕公讣至,为位哭之。”故该书当在辛卯前。
9段:公济、伯谏得书否?某归途过伯谏,见收公济书,大段手忙脚乱也。①
此段文字又重见《续集》《答蔡季通》101书第2段。笔者曾推测为甲申—庚寅年,束景南先生定为辛卯九月,可从。①
有些书信则需要据其所含之思想来推定年代。如《文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四十二书题下小字注“下《论语杂论》同戊午二月五日”,《四库》本无此数字。该书先讨论了四条历史问题,然后集中讨论了八九条《论语》,故题下注“《论语杂论》同”。考察《论语杂论》的具体内容,此书杂出痕迹甚明显。观朱子与子约全部通信,双方论学围绕《论语》与《中庸》展开,间涉太极。其特点是:早期论《论语》,晚期论《中庸》。如癸巳《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第四书讨论时习、巧言令色、三省、传习、父在观志等章,甲午《答吕子约》八—十二书,八书提出“专看《论语》”,九书讨论“三省”,十书讨论三省、传习、道千乘之国章,十二书讨论“时习”。此《答吕子约》四十二书与七书、十二书皆有对“时习”的讨论。故《论语杂论》似在癸巳甲午间更合理。
(二)书信重出
今存《朱文公文集》卷帙浩大,《正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存在些许重出情况,亦属正常。此重出情况多见于《续集》,故对书信系年时,当对此重出现象有所考虑,以免将同一书信系为不同年代之二书,导致考证结果相冲突。
1.书之重出、杂糅者。《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六书重见于第九十二书。第六书首句为“律说幸早为寄”,第九十二书为“律说幸写寄。”“为”、“早”字有别,但《朱子全书》本第6书下出校勘记云:“为”,“闽本、天顺本作“写”。《四库全书》本《晦庵集》仅收第六书而未收第九十二书,或是因此之故。
但九十二书较第六书多出一段,多出部分当为另一信札。现将其录于下:
《大学》等已令进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为致问。公济既平心和气以观义理之所在,则不患无邻矣。草绝交之书,似于禅学亦未得力也。观过之说竟未安,尝思之矣。①
《考证》第六书定为戊戌1178年,第九十二书定为辛卯1171年,所据是:“书尾云‘观过之说竟未安,尝思之矣’。当承上考第四十书等,亦在辛卯。”②《考证》将二书视为不同年代之书信,可见第九十二书为不同年代书信之杂糅。
此种重出情况在《答黄直卿》中亦有出现。如《文集》卷四十六《答黄直卿》第二书除首句多出“子春闻时相过,甚善”八字外,与《续集》卷一《答黄直卿》第十八书文字完全相同,实为重出。
2.据事实与思想出发得出不同年代,推出书信杂糅为一者。《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各书分合间有混杂,若不细加分辨,对其年代判定易造成冲突。《续集·答蔡季通》第五十五书言:
古乐之说…《启蒙》之名,本以为谦而反近于不逊,不知别有何字可改。幸更为思。费隐之说,若有所见,须子细写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见得上下察是隐处,须着力说教分明,方见归着。若只如此含糊约度,说得不济事。不惟人晓不得,自家亦晓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细,当时便合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以明至隐之义,不应却引“鸢飞鱼跃”至显之事而为言,却说翻了也。③
该书讨论了三个问题:古乐、《易学启蒙》、费隐。据其提及《启蒙》书名,当为丙午年。但似乎与朱子理解“费隐”之过程相冲突。就《答蔡季通》各书可知,“费、隐”之说为朱子与蔡季通早年讨论的重要论题。该札与上述《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第八书第六段所论“费隐”显然是前后关系,第6段云:“费隐之说,今日终日安排,终不能定”云云,朱子对“费隐”说无从理解的苦恼之情,跃然纸上。因为旧说以鸢飞鱼跃为隐,朱子对此难以理解。《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六十四书朱子亦提及费隐说:“三日来发热昏冒,……费隐之说,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终觉费力,强说不行。不免且仍旧耳。”①《四库全书》本则无“项平父”以下一段文字,《朱子全书》本则将“项平父”云云单列为一段,据此可推“项平父云云”显然为另一书。《续集》卷二《答蔡季通》有一处再次提及“费隐”说:“费隐尽有说,但日间稍得坐,又贪温卷工夫,不暇安排文义耳。”②此条不见于《四库》本,《朱子全书》本单独列为一段,其上一段文字则是关于《启蒙》之修订讨论。
考察朱子对“费隐”的处理,可知在壬辰、癸巳年间已然解决此问题,定“费”为“著见”。故上引《答蔡季通》诸书涉及“费隐”者,应在此之前,以戊戌至壬辰为佳,如癸巳《文集》卷四十九《答林子玉》已明确“察”不是“隐”而是“著见”,“察是著见之义,然须见其所著见者是何物始得。”己亥十一月五日《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第五书再次强调“察”的“显著”义,“此察字训‘著’不训‘到’。”因此,朱子与蔡季通涉及费隐讨论之书信当在壬辰之前为宜,而不大可能晚至《易学启蒙》完成的丙午1186年。在此之前,朱子对《中庸》的章句义理处理已近乎完成,不至如《蔡季通》诸书中所表现的茫然无主的初学状态。《启蒙》年代与“费隐”问题解决年代相冲突的情况,及《文集》不同版本所收文字分段之异同,皆启示我们应注意其中似乎存在不同书信杂糅为一的情况,如此理解,似可消除其中之矛盾。
据古书之体例,书信文字是否单独分段,可作为判定考虑书札是否有杂糅的因素之一。
如《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第一书重见于《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四十七书,但《文集》第一书与《续集》第四十七书存在两个差别:一是《文集》分为两段,自“《易说》三条”始另为一段。《续集》不分段。其次,《文集》较《续集》首尾各多出一句。首句多出文字:“昨日上状必已达,此人至,又辱书,三复感叹。不能自已。”结尾多出文字:“愚意如此,不审如何?”其余正文“所谓一剑两段者”等皆同。《文集》首句多出文字与《续集》《答蔡季通》第七十九书极为相应,该书云:“昨日亦尝上状,不知何故未达。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刘医,乃昨日遣书时所遗也。今想皆已到矣。”①故第一书较《续集》第四十七书多出之首句当为掺入。
二 《语类》记录者年代分析
《语录》大多数标明记录者,并列有所录大致年份。据此可以明了该条语录年代,对研究朱子思想演变甚为便利。但亦不应拘泥看待《语录》所提供的年代价值,因诸弟子所记往往跨有很长时期,若拘泥固守,则有将研究导入歧途之虞。②如《朱子语录姓氏》指出“廖德明癸巳以后所闻。”其实,廖德明所录绝非止于癸巳,辛亥、丁巳皆有之。如朱子丁巳与吕子约争论,廖德明有记录。“吕子约书来,争‘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只管衮作一段看。③又如《朱子语录姓氏》指出郑可学所录为“辛亥所闻。”亦并非完全如此。下文以《文集》、《语类》中郑子上、蔡季通、余大雅关于人心、道心之说的记录为例,从事实与思想两面证明对《语类》记录年代应持审慎态度。
郑子上与朱子关于人心道心的讨论甚多,先录《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二)》如下:
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发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尝直以形气之发尽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纯粹之时,如来谕之所疑也。①
《语类》卷六十二郑可学所录为:
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先生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气亦皆有善。’不知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②
郑可学所录并非皆在辛亥,举两点为证:一是郑可学记录王子合问朱子《中庸》:子合以书问:“《中庸》‘鸢飞鱼跃’处……”曰:“鸢飞鱼跃,只是言其发见耳。”③按理此条为郑可学所记,当在辛亥,但此条与丁未《答王子合》第七书相对应:“今书所论《中庸》,大旨盖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④二者皆讨论《中庸》“鸢飞鱼跃”,故当在丁未。二是陈荣捷《朱子门人》引田中谦二《朱子门人师事朱子考》指出,“可学记朱子淳熙十四年1187年吊陈魏公,又自云年三十七,即1188,则混入以前所闻。”田中考订可学师事朱子最早为1187春—1188年春。⑤并举可学所录《语类》为证: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中吊陈魏公,回途过雪峰,长老升堂说法……”可学。⑥
我们再对照《文集》卷五十六《答郑子上》相关书信:
今说如云“必有道心,然后可以用于人心”以下数语,亦未莹也。《答郑子上》三⑦
道心之说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为主,即人心自不能夺,而亦莫非道心之所为矣。然此处极难照管,须臾间断,即人欲便行矣。《答郑子上》四①
此心之灵,即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虚,则无所不知,而岂特知此数者而止耶。(朱子答):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答郑子上》十②
“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蒙喻此语,极有开发。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书》语未莹,不足据以为说。可学窃寻《中庸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今如所说,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可学窃疑向所闻“此心之灵”一段所见差谬。先生欲觉其愚迷,故直于本原处指示,使不走作。非谓形气无预,而皆出于心。愚意以为‘觉于理,则一本于性命而为道心;觉于欲,则涉于形气而为人心’。如此所见如何?
(朱子答):《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来喻大概亦已得之矣。《答郑子上》十一③
按:《答郑子上》第十、十一书显然前后相继,第十书朱子把郑子上的“此心之灵,即道心也”改成“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第十一书郑子上引朱子之答,并提出自己理解。《考证》据第十一书提及蔡季通而断定“答郑子上十、十一亦当在辛亥。”但《答郑子上》第十一书同时在余大雅所记语录中有更完整记录,而且加入了余大雅的讨论。谨录于下:
因郑子上书来问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按:此见于《答郑子上》第十书)可学窃寻《中庸序》,以“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盖觉于理谓性命,觉于欲谓形气”云云。(按:此见于《答郑子上》第十一书)可学近观《中庸序》所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来专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于形气,如何去得!然人于性命之理不明,而专为形气所使,则流于人欲矣。如其达性命之理,则虽人心之用,而无非道心,……可学以为‘必有道心,而后可以用人心,而于人心之中,又当识道心。若专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则固流入于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则是判性命为二物,而所谓道心者,空虚无有,将流于释老之学,而非虞书之所指者。”(按:此见于《答郑子上》第三书)大雅云:“前辈多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当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则须绝灭此身,而后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说道心,后说人心?”大雅云:“如此,则人心生于血气,道心生于天理;人心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而道心则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今郑子上之言都是,但于道心下,却一向说是个空虚无有之物,将流为释老之学。”大雅。
按:余大雅(正叔)所记为戊戌1178以后所闻。据陈文蔚(《克斋集》卷十二《余正叔墓碣》可知,余大雅卒于己酉十一月。故《答郑子上》、《答蔡季通》第二书关于人心道心的讨论不可能在辛亥1191年,只能在己酉1189年秋之前。因《中庸章句》序定于己酉三月,《答郑子上》、《蔡季通》书中“序”尚在紧密修改讨论,上引《答郑子上》提及《中庸序》与今本《中庸章句序》不同,故推出诸书当在己酉三月之前的戊申较合理。且与郑子上丁未戊申首次问学朱子时间亦相合。据此可知,郑子上与朱子关于人心道心的通信、郑子上有关人心道心的语录、《答蔡季通》第二书,应在戊申1188年左右为宜。
三 立论中心的再考察
朱子书信考察较为直接可靠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有确切年代的标志性事件,以之为中心发散开来,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典型者如据某些著作的完成年代,来推断书信年代。但由于朱子著作始终处在不断修订刊刻的动态过程中,故对作为中心的朱子著作年代应持有变化的观点。这里主要讨论己酉年1189年刊刻的《学庸章句》这一中心。《学庸章句》之形成修改,历经长期过程,在癸巳至丁酉年的形成初期,朱子即与吕子约、张栻等反复提及《章句》。在己酉序定《中庸章句》后,仍不废讨论修改《章句》,为其形成晚期。而己酉是否一定刊刻《学庸章句》也是可讨论的。通过细致的比照性考察《章句》论述的具体论题,来判定书信中提及的《章句》处于何种阶段是可以尝试的。尽管可以质疑此种尝试的“合法性”:同一论题难道不可以在不同时期讨论吗?但亦可反问,同样的论题相似的文字在不同问答对象中出现,其可能见诸同一年代的概率难道不是大于在不同时期吗?而且,朱子有时明确要求弟子应将他关于同一论题的答复在弟子间传阅,以达到相互学习的效果。再则,已有的考证成果,亦多利用朱子书信的“叠出”(即同样的论题、书信在不同弟子间传阅)来作推论的根据。故在没有明确事实材料的情况下,本部分试图采用此种“论题叠出相同”法作一推论,虽未必获得确论,然对于真实情况之探究当有所益。
(一)周舜弼、叶贺孙、李尧卿与朱子关于大学“格物”致知的讨论。《答周舜弼》第十书讨论了格物致知说,朱子在“知之者切”还是“知之者尽”,“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还是“无不到”之间有所反复。此时朱子与周、叶、李三位的讨论皆主张“知之者切”。
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后意无不诚,”……而所知者非复泛然无切于事理。……泛然而应,不得其当,是皆知之有未切也。补亡之章谓“用力之久而一旦廓然贯通焉,则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心之分别取舍无不切”。……则分别取舍于心当如何?《答周舜弼》十①
“尽”字固可兼得“切”意,恐“切”字却是“尽于内”之意。若只作“尽”字,须兼看得此意乃佳耳。辛亥《答李尧卿》四②叶贺孙所录《语类》卷十六朱子与李尧卿的讨论。
李问“吾之所知无不切。”曰:“某向说得较宽,又觉不切;今说较切,又少些宽舒意;所以又说道‘表里精粗无不尽’也。自见得‘切’字却约向里面。”①
朱子的意思是,“知切”是“切尽于内”之义,与“知尽”相比,语义更贴切恰当。“尽”固然有切之义,但意义过于宽泛外化,故若选择“尽”字,则须包含“切”义。为此,朱子亦主张“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正好与“吾之所知无不切”相应,以显示“切”的内在向里义。朱子承认在“知切”与“知尽”的选择上,自己在紧切与宽缓、外在与内在之间左右为难。朱子与周舜弼信中的看法同样见于《答李尧卿》和叶贺孙所录《语类》中,表明朱子对格物的理解处于同一时期,而李、叶的记录时间为辛亥年,则可推证《答周舜弼》第十书似亦在辛亥年。
(二)周舜弼、李守约、董铢与朱子关于“中和”的讨论。《答周舜弼》第十书还讨论了《中庸章句》的中和说,与《答李守约》第八书讨论的主题一致。先抄录相关文献:
致中和注云:自戒谨恐惧而守之,以至于无一息之不存,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谨其独而察之,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答周舜弼》十②
但致中和处,旧来看得皆未尽,要须兼表里而言。如致中则“欲其无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则欲其无少差谬而又能无适不然”,乃为尽其意耳。……近来看得此意稍精,旧说却不及此也。《答李守约》八③
致中和,须兼表里而言。致中,欲其无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则欲其无少差缪,而又能无适不然。铢。①
据所论而言,《答李守约》提出对中和旧说的修改,要求做到表里兼至,以无少偏倚、守之不失分别指致中的内外;无少差谬、无适不然分别指致和的内外,兼顾未发已发两面。今本《章句》言中和分别为“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二者仅个别表述之异。而反观《答周舜弼》,仅言“守之以至于无一息之不存”、“察之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皆侧重从外在已发角度言中和。显然为“旧说”。据此,《答周舜弼》第十书当在《答李守约》第八书前。中和新旧解为朱子晚年讨论的重要论题,朱子对中和“须兼表里”的思想极为重视。董铢所录(丙辰1196年以后)语类中亦有体现,其说法与今本《章句》完全相同,可证已经定型。故《答李守约》第八书当在丙辰左右为宜。
(三)周舜弼、董铢与朱子关于“必有事焉”的讨论。《答周舜弼》第十书讨论了“必有事焉”,其论同样见于《答董叔重》第八书及董铢所录《语类》。原文如下:
窃以为子思之言无非实理,而程夫子之说亦皆真见。今又得先生窜定此章……子思于是托鸢鱼以明此理之昭著……程子之论,无纤毫凝滞倚着之意。《答周舜弼》十②
铢详先生旧说,盖谓“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语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活泼泼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无所滞碍之妙。”……铢见得此说,似无可疑,而朋友间多主旧说,盖以程子文义观之,其曰“与”曰“同”,而又以“活泼泼地”四字为注云,则若此两句,皆是形容道体之语。然旧说诚不若今说之实,旧说读之不精,未免使人眩瞀迷惑,学者能实用力于今说,则于道之体用流行,当自有见。然又恐非程子当日之本意。
(朱子答):旧说固好,似涉安排,今说若见得破,则即此须臾之顷,此体便已洞然,不待说尽下句矣。《答董叔重》八①
问:先生旧说程先生论“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两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无凝滞倚着之意。今说却是将必有事焉作用功处说。(董铢丙辰1196以后所闻)②
周舜弼提出此章程子说“无纤毫凝滞倚着”,董铢提出朱子对程子的理解有新旧二说,旧说认为程子“必有事”与“活泼泼地”皆是形容道体流行发现“无所滞碍倚着”,今说则认为“必有事”指“心之存主处”,“活泼泼”地才是“形容天理流行无所滞碍之妙”。并指出今说较旧说更为实在,有用力处,而朱子弟子却多坚持旧说。朱子对董氏的理解表示认可。周舜弼所提出的程子说正为旧说。可证《答周舜弼》当在《答董铢》前。董、朱关于此处新旧解的讨论还见于董铢所录语类中,且与《中庸或问》观点相同,故《答董铢》当在晚年丙辰左右。当然,此处今说也非最后定说,今本《章句》删除了程子的“必有事焉”数位,全部言道体而不言工夫。
(四)以动态观点看待《学庸章句》成书,有助于重新考察《文集》卷五十八朱子与宋深之、容之兄弟的八封通信。《学庸章句》在己酉前有不少版本。如《答宋深之》第二书提到,“《大学》当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东刻本峥见为一编,恐勾仓尚在彼,可就求之”③。此处提及“合为一编”乃壬寅(1182年)朱子刊《学庸章句》于浙东任上。在己酉前,《大学》、《中庸》至少尚有德庆刻本、丙午改本。就《答宋深之》第四书来看,该书言,“格物功夫,前书已再录去,然亦未尽,旦夕当再写一本去也。前本千万且勿示人,看令有疑处,乃有进处耳”④。据其语气,《大学章句》并未定稿,还在不断讨论修改誊写之中,故朱子交代宋深之千万不要将前本示人。若此书信为《大学》己酉序成之时,则朱子是要将此书广为刊刻流传而非秘不示人了。再则,此《答宋深之》数封信内容与朱子丙午丁未间《答詹帅书》皆论及四书相关问题,如《大学》的修订刊刻,《中庸章句序》的道统问题等。
如前所引,朱子与《与詹帅书》明确提及《中庸章句序》之修改,至少可以证明《学庸章句》在己酉之前已经有序文,有刊刻了。故据《答宋深之》第二书提及“且附去《大学》《中庸》本,大小学序两篇”并不能断定该书信为己酉年,而据“《小学》成于丁未”之事实,可作为该书成于丁未年的佐证之一。而《答宋深之》第一、二书前后相承,皆言及“分别”。第一书言“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见。虽人事忽忽未得款语,然已足以自慰矣。”第二书言,“前日临歧,不胜忡怅。”《朱子门人》亦认为朱子与宋深之仅见一面,以后恐未有谋面。①可推一、二书当为相承。
又次,宋深之为四川成都人,与朱子通信时在湖南潭州跟随戴溪在石鼓书院问学。《答宋深之》第四书提及,“戴监庙久闻其名,讲学从容必有至论。季随、允升相聚,各有何说?”戴监庙为戴溪,1178年中进士,监潭州南岳庙,主持石鼓书院。胡季随(大壮)乃湖湘学派骨干成员。宋深之父宋若水此时任湖南提点刑狱公事,兄弟随父任读书,《答宋深之》第一书言“获闻比日侍奉佳庆”即言此事。据朱子撰《运判宋公墓志铭》(《晦庵集》卷93)可知,宋若水在湖南任上与刘清之(1186年四月上任潭州)一起修复石鼓书院,并聘请戴溪主持。至晚在丁未1187年末,宋若水调任江西,并于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年二月在江西任上去世。②兄弟扶柩而归,次年己酉年葬父,并请朱子撰铭。据其兄弟父子之活动,亦可佐证他们与朱子的通信当在丙午1186年4月至丁未1187年之间,当在己酉宋若水去世之前。
(五)如不为己酉序定刊刻《大学章句》说所束缚,当能有更多新的发现。如《文集》卷五十五《答邵叔义》第二书言:“《大学》鄙说旧本,纰陋不足观。近年屡加刋(删)订,似颇得圣贤之遗意。”①此书透露的信息是,朱子所解《大学》有新旧本之分,对近年来屡加修订的新本颇为满意,达到了获得圣贤本意的效果。今观旧本,问题颇多,不值得再看。但是无暇抄写新本(尚没有刊刻)给邵氏。该札书信开篇即透露了该书年代线索:
委喻《祠记》,深认不鄙。初以衰病之余,心力衰耗,兼前后欠人文字颇多,不敢率尔承当。又念题目甚佳,却欲附名其间,使后人知贤大夫用心之所在,但见有一二文字未竟,度须更数日方得下笔。九月间,更令一介往山间取之为幸。
此处所言《祠记》即《文集》卷七十九《衢州江山县学景行堂记》,朱子写于淳熙十有二年秋(乙卯1185)八月乙丑。其时邵浩(叔义)为知县,书中还提及《大学》“絜矩”说,与此信完全相应。
对《大学或问》年代的把握亦须小心。如《答黄商伯》一言,“心丧问大意甚善……恕说亦佳,但《大学》絜矩常在格物之后,……熹尝于《大学》治国平天下《或问》中极论此事”②。己酉前后,朱子对《学庸章句》、《或问》皆有反复修改,不可见书信中有《章句》、《或问》之名即据为己酉。此处“熹尝于云云”亦有过去曾经之意。《答黄商伯》第二、三书皆涉及丧礼,如“示喻向来丧服制度”“心丧”“丧礼”,此第一书开篇亦讨论“心丧”,三书显然皆围绕丧礼展开。《考证》定二、三书为“甲寅”,故第一书恐亦当在此年。
四 论题、材料的相洽
朱子书信与诸弟子友朋反复往来,常有数人讨论同一话题之情况,故在考察其书信年代时,应力求各材料间通贯无碍,应与同一论题、人物生平的讨论等相应。
(一)同一论题的关联照应。关于万正淳《中庸》说的讨论。《文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第4—6书皆提及万氏《中庸说》,第四书问目四十一条,几乎皆为《中庸》说,万氏评论甚多,朱子多以“得之”应之。第五书言“去岁尝读《中庸》,妄意辨析先儒之说,今春录以求教矣。”明确表明第四书在今春。第六书讨论较杂,但也讨论了几条《中庸》说。此三书与《答吴伯丰》第七书正好相应,朱子在该函中请吴必大转呈自己给万氏的回函,特别称赞万氏《中庸说》水平颇高。朱子于此提及“丧子之悲”,故推出当为辛亥(1191年)春,由此可见答万正淳四、五、六书亦当在辛亥春前后。
又如朱子与李晦叔、黄商伯、李孝述关于阴阳五行的讨论。《文集》卷六十二《答李晦叔》第六书言“《大学或问》中阴阳五行之说。先生答黄寺丞云:‘阴阳之为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辉尝推之云云。”①按:此书提及的“先生答黄寺丞”,指《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第四书:“阴阳之为五行,有分而言之,如木火阳,而金水阴也。有合而言之……”②而该书内容又见于胡泳戊午所录语录,《答黄商伯》第四书“必在戊午”,据此顺推,《答李晦叔》第六书亦应在戊午。此外《续集》卷十《答李孝述继善问目》第二书亦作于“戊午后”,该书亦提及“孝述又见先生答黄寺丞健顺仁义礼智之问”,更证实《答李晦叔》第六书当在戊午。主旨相同、文字有重合者的两封或以上书信,其年代应是大体相近的。《别集》卷四《答向伯元》一、二书皆论及就刘子澄处听闻书府有康节墨迹事,文字基本相同,年代亦应相近。《文集》卷五十二《答李叔文》一与《文集》卷四十四《答梁文叔》三主旨相同,且有文字极为相似者,皆讨论“孟子下文再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之言”之说,年应相同或相近。
(二)事实材料的关联一致。朱子与弟子之交往对于我们准确判定书信年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文集》卷五十九《答余正叔》第三书言,“熹一出无补,幸已还家,又幸奉祠遂请,且得杜门休息”③。按:此书当在己酉四月后。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载,“己酉春正月……,除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辞职名”①。朱子两次辞免方得成功,时间已在己酉四月后。《文集》卷二十二《辞免秘阁修撰状二》云:“右熹四月二十二日准尚书省札子,以熹辞免秘阁修撰恩命,奉圣旨不许辞免。”②又如《文集》卷五十九《答陈才卿》第三书提及“正叔在此,无日不讲说”③。而陈文蔚(字才卿)《克斋集》卷十二之《余正叔墓碣》言,“己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值正叔将归,语别武夷溪上,未两月而讣闻矣。寔十一月乙丑也。”正叔死于己酉十一月,故该书当在戊申己酉间。
《文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粹》四、五、十、十一诸书年代。第十书言:
示喻缕缕备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胜正理,便是确然可据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顾恐或未能耳。记《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诚如来喻,然其间亦不敢甚远其实,异时善读者当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获,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须旬月,复申前请耳。淳叟、国正想时相见,有何讲论?方丈计亦时会见也。④
该信提及的刘淳叟(刘尧夫),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死于己酉1189年,此书不可能在己酉后。其次,“衰病日侵,求去未获”当与相连下文“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等齐观,意指辞职未能获得批准,“求去”指辞去所授职而并非辞去已经担任的在位实职。朱子意为:在职有利于干造福生民之事的提醒不敢忘记,但对此不能必定得行。再过十天个把月,将再次申请辞职。朱子一生多有辞职,此处当指朱子丁未至戊申间多次辞江西提刑之职,详见《文集》卷二十二《辞免江西提刑状》一、《辞免江西提刑》札子一、二、三。更重要的是,第十书与《答滕德粹》第四、五、十一书紧密相关,为讨论方便,录三书如下:
四书: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亲炙诸贤,想亦有益。日用之间常更加持守讲习之功。①
五书:知官闲,颇得读书,……彼中朋友书来,多称德粹之贤……《溪堂杂文》久欲为作序,但以当时收拾得太少,诗篇四六之外,杂文仅有两篇,想亦未是当时着力处,未有意思可以发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着题底文字,以故迟迟至今。②
十一书: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其他事难预论。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熹所识者杨敬仲简,吕子约(监米仓),所闻者沈国正焕,袁和叔燮,到彼皆可从游也。③
十书首句告之“果能真使私情不胜正理,便是确然可据之地”,乃守身为官之法,与四、五、十一书为官之说相接。次句“记序之作”与五书“溪堂杂文久欲为作序”相应,指《文集》卷八十二《跋滕南夫溪堂集》,该跋言,“平生遗文在者不能什一。”“淳熙丁未其兄孙璘访予崇安,出其集与此传示予。九月丙辰,里人朱熹书”。④有力证实了此四封书信当在丁未(1187年)。十书末句提及“淳叟、国正想时相见,有何讲论?方丈计亦时会见也。”指刘尧夫(淳叟)、沈焕(国正),方谊(方宾王)。四书言,“亲炙诸贤”,五书言,“彼中朋友书来,多称德粹之贤”,十一书言,“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熹所识者”云云,语义相应。此外,《文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章》第四书亦提及,“示谕《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来病思昏愦,作文甚艰,又欠人债负颇多,须少暇乃可为耳”⑤。
《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诸书年代。《答方宾王》第一书“作于戊申夏归自临安途中”⑥。其余诸书似亦在戊申年间。其一,综合1—10书考虑,朱子戊申六月奏事,停留京城不到半月即离开,在路上接到方氏之书。1书言:“乃辱专人追路,惠以手书。”①2书言:“道旁客舍,草草布此。”②特别是第7书提及,“熹前日看所寄《易说》不子细,书中未敢察察言之。遣书后归故居,道间看得两册,始见其底蕴”③。此三书皆言及道间,可见三书时间相接,主题相同,《答方宾王》第3书与4书内容上颇多重复,显然一时。第4书:“近方略为刋订,欲因婺女便人,转以寄呈而临行适病,不能料理简书,令人检寻不复可得。”④此句“临行”与“适病”的主语非一人,临行是寄信的便人,病者是朱熹。似不可据此断定是朱子在临漳赴任前。第11书言拜祠辞职之事:“比虽已拜祠官之命,然辞职未报。尚此忧惧,万一未遂更须力请耳。”⑤戊申年朱子亦有反复拜祠辞职之请。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二书的年代。按:《答张敬夫》第二十七书依次讨论了五王之事、唐代牛李之事、《论语》何有于我哉、《孟子》恶知其非有章,正一一对应于《南轩集》卷二十二《答朱元晦》“《通鉴纲目》想见次第”书。该书提及南轩主持城南书院,托朱子写书楼大字,据此可知当在癸巳1173年也。
《答张敬夫》第二十八书,《南轩文集》卷二十二答朱子此书开篇言,“某守藩倏八阅朔矣”⑥。《南轩文集》卷十《尧山漓江二坛记》言,“淳熙二年之春,某来守桂”⑦。故二十八书正在岁末也。另《朱子全书》本该书校勘记提出浙本此书下注十一月。
《答张敬夫》三十二书即《答敬夫论中庸说》,该书与三十三书前后相承,亦当在丁酉1177年。二书之内容皆对应于《南轩文集》卷二十三答朱子“某新岁来即欲申前请”“此间归长沙一水甚便”前后二书。《答张敬夫》三十二书依次讨论了《中庸》、《大学》的“鸢飞鱼跃”“前知之义”“切磋琢磨”三章注解。与《南轩文集》答朱子“某新岁”书所言“《中庸》、《大学》中三义,复辱详示,今皆无疑。但截取程子之意”①说分明相应。
以上在前辈学者成果基础上,采用事实考辨与思想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对若干朱子书信年代提出了一些新的探讨,通过这些具体考证,试图表明其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窃以为对诸如朱子文集、语类、《四书》著作、人物交往等问题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警惕,无疑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朱子文献,从而客观的阐释其思想。
故本书拟将思想与事实考察方法相结合,重新考证数十封有关四书的书信年代,试图提出几个共性问题:一是《朱文公文集》虽为原始文献,然经后人之手,难免存在书信的杂糅、重出;二是《朱子语类》同样由后人删补而成,未可全据记录者来判定其年代;三是作为确定书信年代中心线索之一的朱子《四书》处于不断修改过程中,将其作为判定年代依据时当采取灵活、审慎态度;四是各书信之年代应保持相洽而无矛盾。
一 书信杂糅与重出
朱子传世著作甚多,但由其本人定稿的甚少,今人研究所惯用的《文集》、《语类》皆为后人所编,其中难免有混杂不清、甚至谬误之处。故对非朱子自定材料,皆须持一怀疑审慎之眼光,这对于确定朱子书信年代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一)书信杂糅
朱子《文集》书信编辑,采用以人系书的方式,时有不同年代书信杂糅为一的现象,甚或同一段书信而来自不同时期,在此情况下,其书信下注年代即不可据信。①如《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第5—8这四封长札皆是不同时期书信之混合。以《答蔡季通》八最为典型,该札题下小字注“癸丑(1193年)三月二十一日”,全文共9段,除首段小注标明实为癸丑外,其余段落内容应皆非此年书信,乃各期书信之混杂,故对各段皆须逐条考订。
1段:中间到宅。题下注:癸丑三月二十一日。②
2段:《启蒙》修了未?早欲得之。《通书》、《皇极例》等说,不知已下手否?……只欲得贤者一来,会语数日为幸。
按:此提及修《启蒙》、写《通书》、《皇极例》等,戴铣《朱子实纪年谱》载癸巳四月朱子“《太极图传》,《通书解》成”③。丙午1186年三月“《易学启蒙》成”④。据此讨论三书之撰写,以《通书解》完成为限,似在癸巳1173年前后。3段:所苦且喜向安……许见访,幸甚。……此行见上,褒予甚至。言虽狂妄,无仵色。
按:据此提及“此行见上,褒予甚至”,当为辛丑1181年末。据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载,辛丑十一月朱子“奏事延和殿。极陈灾异之由,与夫修德任人之说。上为动容悚听。十二月视事于西兴”①。黄榦《朱先生行状》亦言,“及对,卒言之。上委曲访问,悉从其请”②。
4段:伯谏来此已两三日……约左右一来相聚。……其所论极不争多,孤城悉拔,合并兵力,一鼓可克也。
按:“伯谏来此已两三日”与《答范伯崇》十书“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正相应,陈来先生考证《答范伯崇》十书为庚寅春夏,故此书亦当在此稍前,即庚寅1170年春夏。③
5段:中间报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说……《律说》少有碍处……《启蒙》所疑……《律说》幸早改定。
按:此提及《启蒙》与《律说》,朱子丙午作《易学启蒙序》、丁未作《律吕新书序》,该书应在丙午1186年、丁未1187年前。其反复提及《律说》,与《续集》《答蔡季通》第六书“律说幸早写寄”、第九十二书“律说幸写寄”相通。
6段:《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昨看此间写本,脱一“吾”字,烦一哥为看。如少,即添之。此虽不系义理,然亦觉少不得也。“费隐”之说,今日终日安排,终不能定。盖察乎天地,终是说做“隐”不得,百种计较,更说不来。且是所说“不知”、“不能”,“有憾”等句,虚无恍惚,如捕风系影,圣人平日之言,恐无是也。与“未之或知”、“不可能也”不同。不审看得如何?幸详以见喻也。
按:此段文字分别讨论《中庸序》与“费隐”说,实为不同时期书信的杂糅。前者讨论《中庸章句》序文及其刊刻,反映的应是朱子对《中庸》具有较为成熟看法的时期。目前确切关于《章句序》的文献,一为丙午1186年《答詹帅》,一为己酉1189年《中庸章句》,故可认为此处关于《中庸序》的一段似在丙午1186年后。后者则连“费隐”“不知”等文字义理尚处于恍惚捕捉状态,据《文集》相关文献可知,朱子已在壬辰、癸巳年间与张栻、吕祖谦等人反复讨论《中庸》的章句处理(如《答张敬夫论中庸章句》、《答张敬夫再论中庸章句》,与石子重商定《中庸集解》并作《中庸集解序》等),对“费隐”等文义的理解已不是问题。故可推出此段文字当为朱子早年思想之反映,应在壬辰1172年前。
7段:仁义之说……《中庸》、《诗传》,幸速修改示及,《中庸》更有数处,今并录呈。
按:此处提及《中庸章句》《诗集传》的修改,据朱子《诗集传序》(《文集》卷七十六),该书作于淳熙丁酉1177年,故此书当在丁酉年左右。
8段:西山之约……归来又得伯恭书。
按:吕祖谦亡于辛卯1181年,《朱子实纪年谱》第54页言,七月“东莱吕公讣至,为位哭之。”故该书当在辛卯前。
9段:公济、伯谏得书否?某归途过伯谏,见收公济书,大段手忙脚乱也。①
此段文字又重见《续集》《答蔡季通》101书第2段。笔者曾推测为甲申—庚寅年,束景南先生定为辛卯九月,可从。①
有些书信则需要据其所含之思想来推定年代。如《文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四十二书题下小字注“下《论语杂论》同戊午二月五日”,《四库》本无此数字。该书先讨论了四条历史问题,然后集中讨论了八九条《论语》,故题下注“《论语杂论》同”。考察《论语杂论》的具体内容,此书杂出痕迹甚明显。观朱子与子约全部通信,双方论学围绕《论语》与《中庸》展开,间涉太极。其特点是:早期论《论语》,晚期论《中庸》。如癸巳《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第四书讨论时习、巧言令色、三省、传习、父在观志等章,甲午《答吕子约》八—十二书,八书提出“专看《论语》”,九书讨论“三省”,十书讨论三省、传习、道千乘之国章,十二书讨论“时习”。此《答吕子约》四十二书与七书、十二书皆有对“时习”的讨论。故《论语杂论》似在癸巳甲午间更合理。
(二)书信重出
今存《朱文公文集》卷帙浩大,《正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存在些许重出情况,亦属正常。此重出情况多见于《续集》,故对书信系年时,当对此重出现象有所考虑,以免将同一书信系为不同年代之二书,导致考证结果相冲突。
1.书之重出、杂糅者。《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六书重见于第九十二书。第六书首句为“律说幸早为寄”,第九十二书为“律说幸写寄。”“为”、“早”字有别,但《朱子全书》本第6书下出校勘记云:“为”,“闽本、天顺本作“写”。《四库全书》本《晦庵集》仅收第六书而未收第九十二书,或是因此之故。
但九十二书较第六书多出一段,多出部分当为另一信札。现将其录于下:
《大学》等已令进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为致问。公济既平心和气以观义理之所在,则不患无邻矣。草绝交之书,似于禅学亦未得力也。观过之说竟未安,尝思之矣。①
《考证》第六书定为戊戌1178年,第九十二书定为辛卯1171年,所据是:“书尾云‘观过之说竟未安,尝思之矣’。当承上考第四十书等,亦在辛卯。”②《考证》将二书视为不同年代之书信,可见第九十二书为不同年代书信之杂糅。
此种重出情况在《答黄直卿》中亦有出现。如《文集》卷四十六《答黄直卿》第二书除首句多出“子春闻时相过,甚善”八字外,与《续集》卷一《答黄直卿》第十八书文字完全相同,实为重出。
2.据事实与思想出发得出不同年代,推出书信杂糅为一者。《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各书分合间有混杂,若不细加分辨,对其年代判定易造成冲突。《续集·答蔡季通》第五十五书言:
古乐之说…《启蒙》之名,本以为谦而反近于不逊,不知别有何字可改。幸更为思。费隐之说,若有所见,须子细写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见得上下察是隐处,须着力说教分明,方见归着。若只如此含糊约度,说得不济事。不惟人晓不得,自家亦晓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细,当时便合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以明至隐之义,不应却引“鸢飞鱼跃”至显之事而为言,却说翻了也。③
该书讨论了三个问题:古乐、《易学启蒙》、费隐。据其提及《启蒙》书名,当为丙午年。但似乎与朱子理解“费隐”之过程相冲突。就《答蔡季通》各书可知,“费、隐”之说为朱子与蔡季通早年讨论的重要论题。该札与上述《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第八书第六段所论“费隐”显然是前后关系,第6段云:“费隐之说,今日终日安排,终不能定”云云,朱子对“费隐”说无从理解的苦恼之情,跃然纸上。因为旧说以鸢飞鱼跃为隐,朱子对此难以理解。《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六十四书朱子亦提及费隐说:“三日来发热昏冒,……费隐之说,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终觉费力,强说不行。不免且仍旧耳。”①《四库全书》本则无“项平父”以下一段文字,《朱子全书》本则将“项平父”云云单列为一段,据此可推“项平父云云”显然为另一书。《续集》卷二《答蔡季通》有一处再次提及“费隐”说:“费隐尽有说,但日间稍得坐,又贪温卷工夫,不暇安排文义耳。”②此条不见于《四库》本,《朱子全书》本单独列为一段,其上一段文字则是关于《启蒙》之修订讨论。
考察朱子对“费隐”的处理,可知在壬辰、癸巳年间已然解决此问题,定“费”为“著见”。故上引《答蔡季通》诸书涉及“费隐”者,应在此之前,以戊戌至壬辰为佳,如癸巳《文集》卷四十九《答林子玉》已明确“察”不是“隐”而是“著见”,“察是著见之义,然须见其所著见者是何物始得。”己亥十一月五日《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第五书再次强调“察”的“显著”义,“此察字训‘著’不训‘到’。”因此,朱子与蔡季通涉及费隐讨论之书信当在壬辰之前为宜,而不大可能晚至《易学启蒙》完成的丙午1186年。在此之前,朱子对《中庸》的章句义理处理已近乎完成,不至如《蔡季通》诸书中所表现的茫然无主的初学状态。《启蒙》年代与“费隐”问题解决年代相冲突的情况,及《文集》不同版本所收文字分段之异同,皆启示我们应注意其中似乎存在不同书信杂糅为一的情况,如此理解,似可消除其中之矛盾。
据古书之体例,书信文字是否单独分段,可作为判定考虑书札是否有杂糅的因素之一。
如《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第一书重见于《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四十七书,但《文集》第一书与《续集》第四十七书存在两个差别:一是《文集》分为两段,自“《易说》三条”始另为一段。《续集》不分段。其次,《文集》较《续集》首尾各多出一句。首句多出文字:“昨日上状必已达,此人至,又辱书,三复感叹。不能自已。”结尾多出文字:“愚意如此,不审如何?”其余正文“所谓一剑两段者”等皆同。《文集》首句多出文字与《续集》《答蔡季通》第七十九书极为相应,该书云:“昨日亦尝上状,不知何故未达。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刘医,乃昨日遣书时所遗也。今想皆已到矣。”①故第一书较《续集》第四十七书多出之首句当为掺入。
二 《语类》记录者年代分析
《语录》大多数标明记录者,并列有所录大致年份。据此可以明了该条语录年代,对研究朱子思想演变甚为便利。但亦不应拘泥看待《语录》所提供的年代价值,因诸弟子所记往往跨有很长时期,若拘泥固守,则有将研究导入歧途之虞。②如《朱子语录姓氏》指出“廖德明癸巳以后所闻。”其实,廖德明所录绝非止于癸巳,辛亥、丁巳皆有之。如朱子丁巳与吕子约争论,廖德明有记录。“吕子约书来,争‘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只管衮作一段看。③又如《朱子语录姓氏》指出郑可学所录为“辛亥所闻。”亦并非完全如此。下文以《文集》、《语类》中郑子上、蔡季通、余大雅关于人心、道心之说的记录为例,从事实与思想两面证明对《语类》记录年代应持审慎态度。
郑子上与朱子关于人心道心的讨论甚多,先录《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二)》如下:
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发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尝直以形气之发尽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纯粹之时,如来谕之所疑也。①
《语类》卷六十二郑可学所录为:
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先生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气亦皆有善。’不知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②
郑可学所录并非皆在辛亥,举两点为证:一是郑可学记录王子合问朱子《中庸》:子合以书问:“《中庸》‘鸢飞鱼跃’处……”曰:“鸢飞鱼跃,只是言其发见耳。”③按理此条为郑可学所记,当在辛亥,但此条与丁未《答王子合》第七书相对应:“今书所论《中庸》,大旨盖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④二者皆讨论《中庸》“鸢飞鱼跃”,故当在丁未。二是陈荣捷《朱子门人》引田中谦二《朱子门人师事朱子考》指出,“可学记朱子淳熙十四年1187年吊陈魏公,又自云年三十七,即1188,则混入以前所闻。”田中考订可学师事朱子最早为1187春—1188年春。⑤并举可学所录《语类》为证: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中吊陈魏公,回途过雪峰,长老升堂说法……”可学。⑥
我们再对照《文集》卷五十六《答郑子上》相关书信:
今说如云“必有道心,然后可以用于人心”以下数语,亦未莹也。《答郑子上》三⑦
道心之说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为主,即人心自不能夺,而亦莫非道心之所为矣。然此处极难照管,须臾间断,即人欲便行矣。《答郑子上》四①
此心之灵,即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虚,则无所不知,而岂特知此数者而止耶。(朱子答):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答郑子上》十②
“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蒙喻此语,极有开发。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书》语未莹,不足据以为说。可学窃寻《中庸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今如所说,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可学窃疑向所闻“此心之灵”一段所见差谬。先生欲觉其愚迷,故直于本原处指示,使不走作。非谓形气无预,而皆出于心。愚意以为‘觉于理,则一本于性命而为道心;觉于欲,则涉于形气而为人心’。如此所见如何?
(朱子答):《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来喻大概亦已得之矣。《答郑子上》十一③
按:《答郑子上》第十、十一书显然前后相继,第十书朱子把郑子上的“此心之灵,即道心也”改成“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第十一书郑子上引朱子之答,并提出自己理解。《考证》据第十一书提及蔡季通而断定“答郑子上十、十一亦当在辛亥。”但《答郑子上》第十一书同时在余大雅所记语录中有更完整记录,而且加入了余大雅的讨论。谨录于下:
因郑子上书来问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按:此见于《答郑子上》第十书)可学窃寻《中庸序》,以“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盖觉于理谓性命,觉于欲谓形气”云云。(按:此见于《答郑子上》第十一书)可学近观《中庸序》所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来专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于形气,如何去得!然人于性命之理不明,而专为形气所使,则流于人欲矣。如其达性命之理,则虽人心之用,而无非道心,……可学以为‘必有道心,而后可以用人心,而于人心之中,又当识道心。若专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则固流入于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则是判性命为二物,而所谓道心者,空虚无有,将流于释老之学,而非虞书之所指者。”(按:此见于《答郑子上》第三书)大雅云:“前辈多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当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则须绝灭此身,而后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说道心,后说人心?”大雅云:“如此,则人心生于血气,道心生于天理;人心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而道心则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今郑子上之言都是,但于道心下,却一向说是个空虚无有之物,将流为释老之学。”大雅。
按:余大雅(正叔)所记为戊戌1178以后所闻。据陈文蔚(《克斋集》卷十二《余正叔墓碣》可知,余大雅卒于己酉十一月。故《答郑子上》、《答蔡季通》第二书关于人心道心的讨论不可能在辛亥1191年,只能在己酉1189年秋之前。因《中庸章句》序定于己酉三月,《答郑子上》、《蔡季通》书中“序”尚在紧密修改讨论,上引《答郑子上》提及《中庸序》与今本《中庸章句序》不同,故推出诸书当在己酉三月之前的戊申较合理。且与郑子上丁未戊申首次问学朱子时间亦相合。据此可知,郑子上与朱子关于人心道心的通信、郑子上有关人心道心的语录、《答蔡季通》第二书,应在戊申1188年左右为宜。
三 立论中心的再考察
朱子书信考察较为直接可靠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有确切年代的标志性事件,以之为中心发散开来,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典型者如据某些著作的完成年代,来推断书信年代。但由于朱子著作始终处在不断修订刊刻的动态过程中,故对作为中心的朱子著作年代应持有变化的观点。这里主要讨论己酉年1189年刊刻的《学庸章句》这一中心。《学庸章句》之形成修改,历经长期过程,在癸巳至丁酉年的形成初期,朱子即与吕子约、张栻等反复提及《章句》。在己酉序定《中庸章句》后,仍不废讨论修改《章句》,为其形成晚期。而己酉是否一定刊刻《学庸章句》也是可讨论的。通过细致的比照性考察《章句》论述的具体论题,来判定书信中提及的《章句》处于何种阶段是可以尝试的。尽管可以质疑此种尝试的“合法性”:同一论题难道不可以在不同时期讨论吗?但亦可反问,同样的论题相似的文字在不同问答对象中出现,其可能见诸同一年代的概率难道不是大于在不同时期吗?而且,朱子有时明确要求弟子应将他关于同一论题的答复在弟子间传阅,以达到相互学习的效果。再则,已有的考证成果,亦多利用朱子书信的“叠出”(即同样的论题、书信在不同弟子间传阅)来作推论的根据。故在没有明确事实材料的情况下,本部分试图采用此种“论题叠出相同”法作一推论,虽未必获得确论,然对于真实情况之探究当有所益。
(一)周舜弼、叶贺孙、李尧卿与朱子关于大学“格物”致知的讨论。《答周舜弼》第十书讨论了格物致知说,朱子在“知之者切”还是“知之者尽”,“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还是“无不到”之间有所反复。此时朱子与周、叶、李三位的讨论皆主张“知之者切”。
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后意无不诚,”……而所知者非复泛然无切于事理。……泛然而应,不得其当,是皆知之有未切也。补亡之章谓“用力之久而一旦廓然贯通焉,则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心之分别取舍无不切”。……则分别取舍于心当如何?《答周舜弼》十①
“尽”字固可兼得“切”意,恐“切”字却是“尽于内”之意。若只作“尽”字,须兼看得此意乃佳耳。辛亥《答李尧卿》四②叶贺孙所录《语类》卷十六朱子与李尧卿的讨论。
李问“吾之所知无不切。”曰:“某向说得较宽,又觉不切;今说较切,又少些宽舒意;所以又说道‘表里精粗无不尽’也。自见得‘切’字却约向里面。”①
朱子的意思是,“知切”是“切尽于内”之义,与“知尽”相比,语义更贴切恰当。“尽”固然有切之义,但意义过于宽泛外化,故若选择“尽”字,则须包含“切”义。为此,朱子亦主张“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正好与“吾之所知无不切”相应,以显示“切”的内在向里义。朱子承认在“知切”与“知尽”的选择上,自己在紧切与宽缓、外在与内在之间左右为难。朱子与周舜弼信中的看法同样见于《答李尧卿》和叶贺孙所录《语类》中,表明朱子对格物的理解处于同一时期,而李、叶的记录时间为辛亥年,则可推证《答周舜弼》第十书似亦在辛亥年。
(二)周舜弼、李守约、董铢与朱子关于“中和”的讨论。《答周舜弼》第十书还讨论了《中庸章句》的中和说,与《答李守约》第八书讨论的主题一致。先抄录相关文献:
致中和注云:自戒谨恐惧而守之,以至于无一息之不存,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谨其独而察之,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答周舜弼》十②
但致中和处,旧来看得皆未尽,要须兼表里而言。如致中则“欲其无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则欲其无少差谬而又能无适不然”,乃为尽其意耳。……近来看得此意稍精,旧说却不及此也。《答李守约》八③
致中和,须兼表里而言。致中,欲其无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则欲其无少差缪,而又能无适不然。铢。①
据所论而言,《答李守约》提出对中和旧说的修改,要求做到表里兼至,以无少偏倚、守之不失分别指致中的内外;无少差谬、无适不然分别指致和的内外,兼顾未发已发两面。今本《章句》言中和分别为“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二者仅个别表述之异。而反观《答周舜弼》,仅言“守之以至于无一息之不存”、“察之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皆侧重从外在已发角度言中和。显然为“旧说”。据此,《答周舜弼》第十书当在《答李守约》第八书前。中和新旧解为朱子晚年讨论的重要论题,朱子对中和“须兼表里”的思想极为重视。董铢所录(丙辰1196年以后)语类中亦有体现,其说法与今本《章句》完全相同,可证已经定型。故《答李守约》第八书当在丙辰左右为宜。
(三)周舜弼、董铢与朱子关于“必有事焉”的讨论。《答周舜弼》第十书讨论了“必有事焉”,其论同样见于《答董叔重》第八书及董铢所录《语类》。原文如下:
窃以为子思之言无非实理,而程夫子之说亦皆真见。今又得先生窜定此章……子思于是托鸢鱼以明此理之昭著……程子之论,无纤毫凝滞倚着之意。《答周舜弼》十②
铢详先生旧说,盖谓“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语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活泼泼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无所滞碍之妙。”……铢见得此说,似无可疑,而朋友间多主旧说,盖以程子文义观之,其曰“与”曰“同”,而又以“活泼泼地”四字为注云,则若此两句,皆是形容道体之语。然旧说诚不若今说之实,旧说读之不精,未免使人眩瞀迷惑,学者能实用力于今说,则于道之体用流行,当自有见。然又恐非程子当日之本意。
(朱子答):旧说固好,似涉安排,今说若见得破,则即此须臾之顷,此体便已洞然,不待说尽下句矣。《答董叔重》八①
问:先生旧说程先生论“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两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无凝滞倚着之意。今说却是将必有事焉作用功处说。(董铢丙辰1196以后所闻)②
周舜弼提出此章程子说“无纤毫凝滞倚着”,董铢提出朱子对程子的理解有新旧二说,旧说认为程子“必有事”与“活泼泼地”皆是形容道体流行发现“无所滞碍倚着”,今说则认为“必有事”指“心之存主处”,“活泼泼”地才是“形容天理流行无所滞碍之妙”。并指出今说较旧说更为实在,有用力处,而朱子弟子却多坚持旧说。朱子对董氏的理解表示认可。周舜弼所提出的程子说正为旧说。可证《答周舜弼》当在《答董铢》前。董、朱关于此处新旧解的讨论还见于董铢所录语类中,且与《中庸或问》观点相同,故《答董铢》当在晚年丙辰左右。当然,此处今说也非最后定说,今本《章句》删除了程子的“必有事焉”数位,全部言道体而不言工夫。
(四)以动态观点看待《学庸章句》成书,有助于重新考察《文集》卷五十八朱子与宋深之、容之兄弟的八封通信。《学庸章句》在己酉前有不少版本。如《答宋深之》第二书提到,“《大学》当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东刻本峥见为一编,恐勾仓尚在彼,可就求之”③。此处提及“合为一编”乃壬寅(1182年)朱子刊《学庸章句》于浙东任上。在己酉前,《大学》、《中庸》至少尚有德庆刻本、丙午改本。就《答宋深之》第四书来看,该书言,“格物功夫,前书已再录去,然亦未尽,旦夕当再写一本去也。前本千万且勿示人,看令有疑处,乃有进处耳”④。据其语气,《大学章句》并未定稿,还在不断讨论修改誊写之中,故朱子交代宋深之千万不要将前本示人。若此书信为《大学》己酉序成之时,则朱子是要将此书广为刊刻流传而非秘不示人了。再则,此《答宋深之》数封信内容与朱子丙午丁未间《答詹帅书》皆论及四书相关问题,如《大学》的修订刊刻,《中庸章句序》的道统问题等。
如前所引,朱子与《与詹帅书》明确提及《中庸章句序》之修改,至少可以证明《学庸章句》在己酉之前已经有序文,有刊刻了。故据《答宋深之》第二书提及“且附去《大学》《中庸》本,大小学序两篇”并不能断定该书信为己酉年,而据“《小学》成于丁未”之事实,可作为该书成于丁未年的佐证之一。而《答宋深之》第一、二书前后相承,皆言及“分别”。第一书言“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见。虽人事忽忽未得款语,然已足以自慰矣。”第二书言,“前日临歧,不胜忡怅。”《朱子门人》亦认为朱子与宋深之仅见一面,以后恐未有谋面。①可推一、二书当为相承。
又次,宋深之为四川成都人,与朱子通信时在湖南潭州跟随戴溪在石鼓书院问学。《答宋深之》第四书提及,“戴监庙久闻其名,讲学从容必有至论。季随、允升相聚,各有何说?”戴监庙为戴溪,1178年中进士,监潭州南岳庙,主持石鼓书院。胡季随(大壮)乃湖湘学派骨干成员。宋深之父宋若水此时任湖南提点刑狱公事,兄弟随父任读书,《答宋深之》第一书言“获闻比日侍奉佳庆”即言此事。据朱子撰《运判宋公墓志铭》(《晦庵集》卷93)可知,宋若水在湖南任上与刘清之(1186年四月上任潭州)一起修复石鼓书院,并聘请戴溪主持。至晚在丁未1187年末,宋若水调任江西,并于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年二月在江西任上去世。②兄弟扶柩而归,次年己酉年葬父,并请朱子撰铭。据其兄弟父子之活动,亦可佐证他们与朱子的通信当在丙午1186年4月至丁未1187年之间,当在己酉宋若水去世之前。
(五)如不为己酉序定刊刻《大学章句》说所束缚,当能有更多新的发现。如《文集》卷五十五《答邵叔义》第二书言:“《大学》鄙说旧本,纰陋不足观。近年屡加刋(删)订,似颇得圣贤之遗意。”①此书透露的信息是,朱子所解《大学》有新旧本之分,对近年来屡加修订的新本颇为满意,达到了获得圣贤本意的效果。今观旧本,问题颇多,不值得再看。但是无暇抄写新本(尚没有刊刻)给邵氏。该札书信开篇即透露了该书年代线索:
委喻《祠记》,深认不鄙。初以衰病之余,心力衰耗,兼前后欠人文字颇多,不敢率尔承当。又念题目甚佳,却欲附名其间,使后人知贤大夫用心之所在,但见有一二文字未竟,度须更数日方得下笔。九月间,更令一介往山间取之为幸。
此处所言《祠记》即《文集》卷七十九《衢州江山县学景行堂记》,朱子写于淳熙十有二年秋(乙卯1185)八月乙丑。其时邵浩(叔义)为知县,书中还提及《大学》“絜矩”说,与此信完全相应。
对《大学或问》年代的把握亦须小心。如《答黄商伯》一言,“心丧问大意甚善……恕说亦佳,但《大学》絜矩常在格物之后,……熹尝于《大学》治国平天下《或问》中极论此事”②。己酉前后,朱子对《学庸章句》、《或问》皆有反复修改,不可见书信中有《章句》、《或问》之名即据为己酉。此处“熹尝于云云”亦有过去曾经之意。《答黄商伯》第二、三书皆涉及丧礼,如“示喻向来丧服制度”“心丧”“丧礼”,此第一书开篇亦讨论“心丧”,三书显然皆围绕丧礼展开。《考证》定二、三书为“甲寅”,故第一书恐亦当在此年。
四 论题、材料的相洽
朱子书信与诸弟子友朋反复往来,常有数人讨论同一话题之情况,故在考察其书信年代时,应力求各材料间通贯无碍,应与同一论题、人物生平的讨论等相应。
(一)同一论题的关联照应。关于万正淳《中庸》说的讨论。《文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第4—6书皆提及万氏《中庸说》,第四书问目四十一条,几乎皆为《中庸》说,万氏评论甚多,朱子多以“得之”应之。第五书言“去岁尝读《中庸》,妄意辨析先儒之说,今春录以求教矣。”明确表明第四书在今春。第六书讨论较杂,但也讨论了几条《中庸》说。此三书与《答吴伯丰》第七书正好相应,朱子在该函中请吴必大转呈自己给万氏的回函,特别称赞万氏《中庸说》水平颇高。朱子于此提及“丧子之悲”,故推出当为辛亥(1191年)春,由此可见答万正淳四、五、六书亦当在辛亥春前后。
又如朱子与李晦叔、黄商伯、李孝述关于阴阳五行的讨论。《文集》卷六十二《答李晦叔》第六书言“《大学或问》中阴阳五行之说。先生答黄寺丞云:‘阴阳之为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辉尝推之云云。”①按:此书提及的“先生答黄寺丞”,指《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第四书:“阴阳之为五行,有分而言之,如木火阳,而金水阴也。有合而言之……”②而该书内容又见于胡泳戊午所录语录,《答黄商伯》第四书“必在戊午”,据此顺推,《答李晦叔》第六书亦应在戊午。此外《续集》卷十《答李孝述继善问目》第二书亦作于“戊午后”,该书亦提及“孝述又见先生答黄寺丞健顺仁义礼智之问”,更证实《答李晦叔》第六书当在戊午。主旨相同、文字有重合者的两封或以上书信,其年代应是大体相近的。《别集》卷四《答向伯元》一、二书皆论及就刘子澄处听闻书府有康节墨迹事,文字基本相同,年代亦应相近。《文集》卷五十二《答李叔文》一与《文集》卷四十四《答梁文叔》三主旨相同,且有文字极为相似者,皆讨论“孟子下文再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之言”之说,年应相同或相近。
(二)事实材料的关联一致。朱子与弟子之交往对于我们准确判定书信年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文集》卷五十九《答余正叔》第三书言,“熹一出无补,幸已还家,又幸奉祠遂请,且得杜门休息”③。按:此书当在己酉四月后。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载,“己酉春正月……,除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辞职名”①。朱子两次辞免方得成功,时间已在己酉四月后。《文集》卷二十二《辞免秘阁修撰状二》云:“右熹四月二十二日准尚书省札子,以熹辞免秘阁修撰恩命,奉圣旨不许辞免。”②又如《文集》卷五十九《答陈才卿》第三书提及“正叔在此,无日不讲说”③。而陈文蔚(字才卿)《克斋集》卷十二之《余正叔墓碣》言,“己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值正叔将归,语别武夷溪上,未两月而讣闻矣。寔十一月乙丑也。”正叔死于己酉十一月,故该书当在戊申己酉间。
《文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粹》四、五、十、十一诸书年代。第十书言:
示喻缕缕备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胜正理,便是确然可据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顾恐或未能耳。记《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诚如来喻,然其间亦不敢甚远其实,异时善读者当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获,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须旬月,复申前请耳。淳叟、国正想时相见,有何讲论?方丈计亦时会见也。④
该信提及的刘淳叟(刘尧夫),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死于己酉1189年,此书不可能在己酉后。其次,“衰病日侵,求去未获”当与相连下文“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等齐观,意指辞职未能获得批准,“求去”指辞去所授职而并非辞去已经担任的在位实职。朱子意为:在职有利于干造福生民之事的提醒不敢忘记,但对此不能必定得行。再过十天个把月,将再次申请辞职。朱子一生多有辞职,此处当指朱子丁未至戊申间多次辞江西提刑之职,详见《文集》卷二十二《辞免江西提刑状》一、《辞免江西提刑》札子一、二、三。更重要的是,第十书与《答滕德粹》第四、五、十一书紧密相关,为讨论方便,录三书如下:
四书: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亲炙诸贤,想亦有益。日用之间常更加持守讲习之功。①
五书:知官闲,颇得读书,……彼中朋友书来,多称德粹之贤……《溪堂杂文》久欲为作序,但以当时收拾得太少,诗篇四六之外,杂文仅有两篇,想亦未是当时着力处,未有意思可以发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着题底文字,以故迟迟至今。②
十一书: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其他事难预论。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熹所识者杨敬仲简,吕子约(监米仓),所闻者沈国正焕,袁和叔燮,到彼皆可从游也。③
十书首句告之“果能真使私情不胜正理,便是确然可据之地”,乃守身为官之法,与四、五、十一书为官之说相接。次句“记序之作”与五书“溪堂杂文久欲为作序”相应,指《文集》卷八十二《跋滕南夫溪堂集》,该跋言,“平生遗文在者不能什一。”“淳熙丁未其兄孙璘访予崇安,出其集与此传示予。九月丙辰,里人朱熹书”。④有力证实了此四封书信当在丁未(1187年)。十书末句提及“淳叟、国正想时相见,有何讲论?方丈计亦时会见也。”指刘尧夫(淳叟)、沈焕(国正),方谊(方宾王)。四书言,“亲炙诸贤”,五书言,“彼中朋友书来,多称德粹之贤”,十一书言,“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熹所识者”云云,语义相应。此外,《文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章》第四书亦提及,“示谕《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来病思昏愦,作文甚艰,又欠人债负颇多,须少暇乃可为耳”⑤。
《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诸书年代。《答方宾王》第一书“作于戊申夏归自临安途中”⑥。其余诸书似亦在戊申年间。其一,综合1—10书考虑,朱子戊申六月奏事,停留京城不到半月即离开,在路上接到方氏之书。1书言:“乃辱专人追路,惠以手书。”①2书言:“道旁客舍,草草布此。”②特别是第7书提及,“熹前日看所寄《易说》不子细,书中未敢察察言之。遣书后归故居,道间看得两册,始见其底蕴”③。此三书皆言及道间,可见三书时间相接,主题相同,《答方宾王》第3书与4书内容上颇多重复,显然一时。第4书:“近方略为刋订,欲因婺女便人,转以寄呈而临行适病,不能料理简书,令人检寻不复可得。”④此句“临行”与“适病”的主语非一人,临行是寄信的便人,病者是朱熹。似不可据此断定是朱子在临漳赴任前。第11书言拜祠辞职之事:“比虽已拜祠官之命,然辞职未报。尚此忧惧,万一未遂更须力请耳。”⑤戊申年朱子亦有反复拜祠辞职之请。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二书的年代。按:《答张敬夫》第二十七书依次讨论了五王之事、唐代牛李之事、《论语》何有于我哉、《孟子》恶知其非有章,正一一对应于《南轩集》卷二十二《答朱元晦》“《通鉴纲目》想见次第”书。该书提及南轩主持城南书院,托朱子写书楼大字,据此可知当在癸巳1173年也。
《答张敬夫》第二十八书,《南轩文集》卷二十二答朱子此书开篇言,“某守藩倏八阅朔矣”⑥。《南轩文集》卷十《尧山漓江二坛记》言,“淳熙二年之春,某来守桂”⑦。故二十八书正在岁末也。另《朱子全书》本该书校勘记提出浙本此书下注十一月。
《答张敬夫》三十二书即《答敬夫论中庸说》,该书与三十三书前后相承,亦当在丁酉1177年。二书之内容皆对应于《南轩文集》卷二十三答朱子“某新岁来即欲申前请”“此间归长沙一水甚便”前后二书。《答张敬夫》三十二书依次讨论了《中庸》、《大学》的“鸢飞鱼跃”“前知之义”“切磋琢磨”三章注解。与《南轩文集》答朱子“某新岁”书所言“《中庸》、《大学》中三义,复辱详示,今皆无疑。但截取程子之意”①说分明相应。
以上在前辈学者成果基础上,采用事实考辨与思想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对若干朱子书信年代提出了一些新的探讨,通过这些具体考证,试图表明其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窃以为对诸如朱子文集、语类、《四书》著作、人物交往等问题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警惕,无疑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朱子文献,从而客观的阐释其思想。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