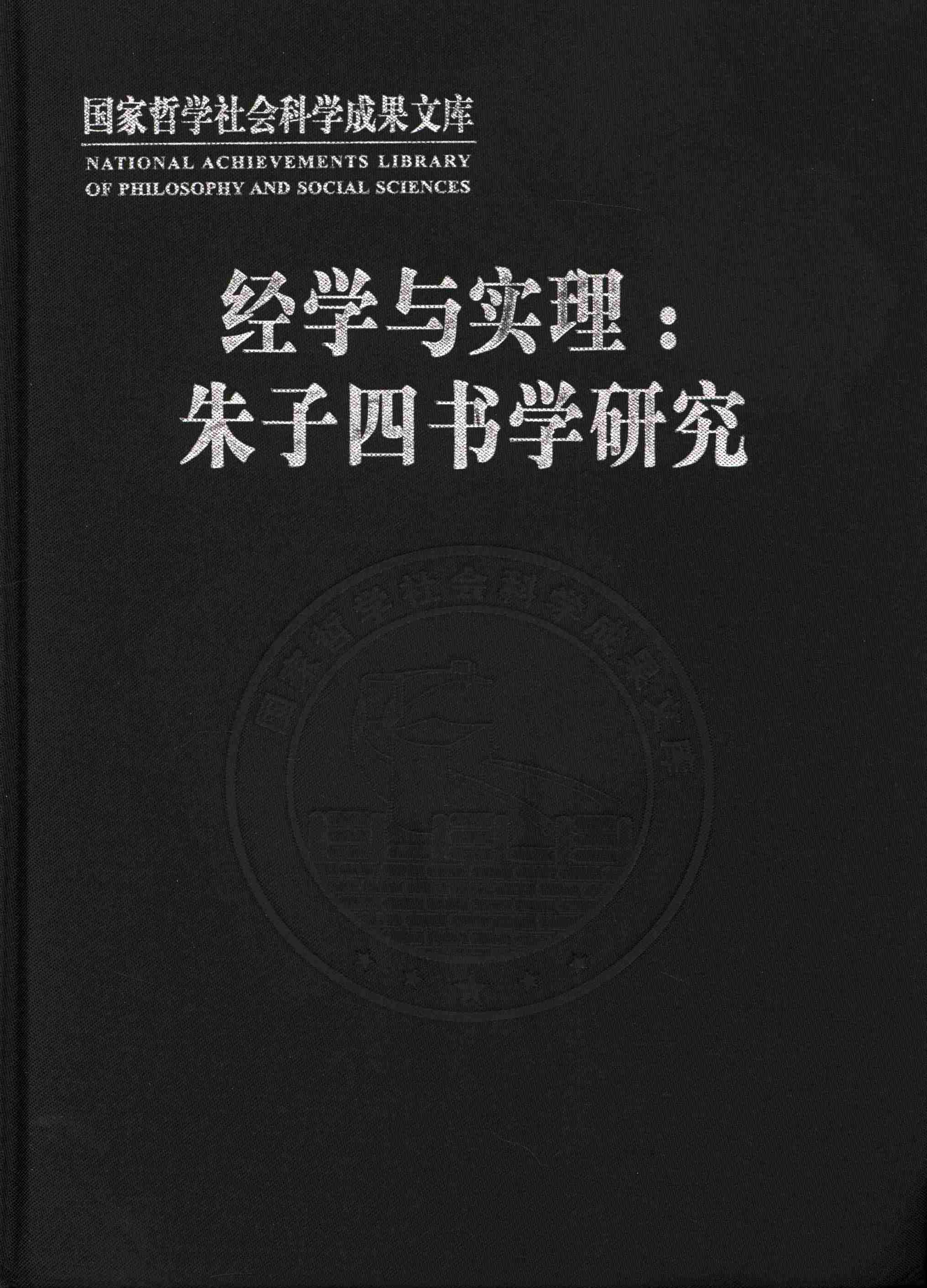二 “得于心而不失”与“行道而有得于心”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872 |
| 颗粒名称: | 二 “得于心而不失”与“行道而有得于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8 |
| 页码: | 440-447 |
| 摘要: | 这段文字讨论了《论语》中为政以德的“德”字的解释和朱注的修改过程。胡炳文和陈栎对此有不同看法。胡炳文认为“德”应该解释为“不失”,即得之于有生之初,不可失之于有生之后;昨日得之者,今日不可失之。而陈栎则认为胡炳文过于挑剔,并质疑其对朱子定本的判断。他认为“德”应该解释为“得于心而不失”,即得之于有生之初,不可失之于有生之后;昨日得之者,今日不可失之。总之,这是一个涉及文本版本、作者意图、文本意义和读者理解等问题的复杂讨论。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论语 |
内容
胡炳文指出,《论语》为政以德的“德”,朱注有过两次修改。《四书通》凡例三言:
祝氏以刊于兴国者为定本,今细考其文义,如为政以德,旧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本作“有得于心”,后本又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见也。按:桐原胡氏侍坐武夷亭。先生执扇而曰:“德字须用‘不失’训,如得人,此物可谓得矣,才失之则非得也。”此譬甚切。盖此句含两意:一谓得之于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于有生之后;一谓昨日得之者,今日不可失之也。今必以祝本为定,未必先曰“得于心而不失”,然后改曰“行道而有得于身”,末又改曰“行道而有得于心”。故今不以祝本为定。①
通曰:“不失”二字自有工夫在焉,《集注》改本之精也如此。①
朱子先是把“行道而有得于身”的“身”改为“心”,即变为“行道而有得于心”;在此基础上又改为“得于心而不失”,把“行道”去除,补充“不失”。胡炳文指出祝洙并未看到第二次改本,故停留于第一次改后的“行道而有得于心”。又以《语类》中朱子之说为证,朱子提出“德”当以“不失”解,并以扇子为譬,以德为先天所得而不可失于后天,为往昔实践所获而不可失于今日。“不失”之改反映了朱子重视工夫实践以砥砺德行的用意。如按祝本,则落入先“不失”而后“得于心”的逻辑颠倒之中,实不合情理。“不失”对于操守工夫的凸显显示了《集注》修改之精妙。
在胡炳文所持宋本与陈栎所主祝本的五处差异中,胡炳文仅就此说直接提出与陈栎交流,陈栎对此颇为不满。说:
胡仲虎《四书通》……最是不以祝本为定本,大不是。文公适孙鉴庚三总领题祝氏《附录》云:“后以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今乃不信其亲孙之言,而信外人之言。只看《中庸》首一节断语,诸本与祝本疏密天地悬隔,乃隐而不言,而专以为政篇“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一节来辨,谓“得于心而不失”为定本,而非“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说,“得于心”何必加以“而不失”?“得于心”是得何物?不比据德云,据德是“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因“据”字而下“不失”字耳。②
在认可《四书通》有可取之处的同时,陈栎批评该书过于挑剔,流于“鸡蛋里挑骨头”,最大缺陷在于未将祝本当作定本,不信朱子嫡孙之言而信外人之说。指出二本《中庸》首章按语差别巨大,炳文不以此辩论,却专挑为政以德来争辩,避重就轻。认为“得于心”后不必补“不失”,“为政以德”之德不同于“志道据德”之德,彼“德”为“不失”,乃是因“据”字而发。并指出胡炳文相交之初,甚为认可自家观点,如今却改变初衷,背离己说,显出对炳文讥讽态度。
倪士毅《四书辑释》详引师说,批评胡炳文根据《语录》“德字须用不失训”说断定以“不失”解“德”,并不可取。
祝氏《附录》本如此,他本作“得于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于心而不失”之说……先师谓此说纵使有之,亦必非末后定本。深思细玩,终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精当不可易也。……初作“得于身”,后改“得于心”。夫“道”字广,在天下所共由,“德”字亲切,吾心所独得。行道,行之于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于心,则躬行者始心得之,心与理为一,斯可谓之德。①
因此说并非朱子定见,实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精妙确当。朱子“德之为得”初作“得于身”,后改作“得于心”。行道得于心方可为德,盖道指天下共同遵循之路,所指广大普遍,不如“德”字专指一心所独得亲切。“有得于身”和“有得于心”有别,行道于身,未足言德,只有得道于心,躬行实践,心与理一者方可视为德。“行道而有得于心”的“行道”是实践工夫,“得于心”是工夫目标,二者次序分明而分工明确,精妙无比。“得于心而不失”说一则笼统,未指明“得于心”者为何,二则衍说此处所无的“不失”之意,不紧切。此外,“据于德”注之“不失”乃因“据”字而发,且紧接“行道而有得于心”来。此章如言“得于心而不失”则过于急促,且无所指向,徒为累赘。又《大学章句序》“本之躬行心得”与“行道而有得于心”相印合,“躬行”对应“行道”,“心得”对“得于心”,可证祝本为定本。
二本皆有“得于心”,差别仅在“行道”和“不失”二字。正如诚意解一样,《四书集编》《四书纂疏》等宋元本主“不失”,赵顺孙指出新旧本的修改是从“行道而有得于身”到“得于心而不失”,心较身更为紧切。但并未提及陈栎所主张的“行道而有得于心”说,或许他当时似并未见此说,此说于其时恐未甚流行。“愚案旧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今作‘得于心而不失’。不言身而言心,心切于身也。”①金履祥则明确指出“行道而得于心”为初说,“《集注》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于心,’其后改从此。盖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鲜可谓之有德者。”②他认为初说来自据于德注,后改为“得于心而不失”。作为公共的道为人心所同具,但作为个体修养的有德者则少,人常常暂有所悟而无法久存于心,或仅是知德而不能体之于身,故最终皆得而复失,而不足以为德。可见朱子改本强调“不失”二字用意深刻,德不难于得,而在于保持不失。吴程亦以陈栎说为初本,说“行道而有得于心”,乃朱子初改本。
元刘将孙《颜曾省身字说》对朱子“德”字注释修改之叙述,同于胡炳文说,由“得于身”到“得于心”,在易箦前方定为“得于心而不失”。由此推出身即心、心即身说为合理而有益,显出心在腔子里。“犹记往年见晦庵释‘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一语,初本‘心’作‘身’。盖易箦前数日,始定为‘得于心而不失’。故窃以为‘身即心,心即身’语为不悖而粗有益。”③
陈栎说在元代亦有所呼应。史伯璿大赞其“得于心者何物”说反驳有力,认为“不失”说未论及所得为何,有落空之疑,不如“行道有得”明确得于心者为道,正与《大学》明德解“得乎天”同例,可见所得真实不虚。且“不失”乃学者工夫,是就入德之人而言,不合经文大舜无为而治的圣人境界。史氏是从德之虚实及工夫境界之分而论,颇见新意。《四书大全》认可陈栎说,并引倪氏辩护语。
二说当以《发明》为是,其曰“得于心者何物乎”?此说极是。《大学》释明德,必曰“所得乎天”云云,便见所得之实处。今但曰“得于心”而不言所得之实,可乎?况“不失”二字为入德、进德者言之则有味。为政以德,无为而天下归之,正是舜无为而治之事,此盛德自然之应,“不失”不足以言之矣!①
但自元以来,主张胡炳文说的学者即大有人在。元许有壬认为朱子之德有两种解释,本然之德和修为之德,朱子虽以“行道而有得心”解此处之“德”,但却是从“修为以复德”的学者之工夫而论,不同于史伯璿主张的“盛德自然”境界义,史氏所论乃本然之德,是圣人所独有。许氏强调了得而不失的意义,天所降之理构成我所受之德,此即道得于心;然而有得则有失,只有得而不失于心,深造自得而保持持久者,方是真得其德。日月一至者,非得也。
德之本然,唯圣人为能;修为以复,则学者事也……天之所以与我,我所以为德者,故曰“行道而有得于心”。且得者,失之反也,“得于心而不失”,乃为真得。②
清汪武曹反驳史伯璿说,而认可“得于心而不失”说,一则据《语类》之意,二则就文本论。为政以德必须兼不失,若无“不失”,则得失无常,无法保证德之真实拥有。又据注文中程子的“为政以德,然后无为”,即朱子的“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推出以德和无为是两层意义,无为而民归之意实在下句“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中,不可完全由“为政以德”承担,此此反驳了史伯璿的“德”为舜无为而治之境界说。孙见龙对新旧说加以调和,认为本可相通,“得于心”是就正面论德,“不失”是从反面不足。
汪武曹曰:“得于心者何物”句,似亦驳得有理。但玩《语类》,终当以“得于心而不失”为定本。且讲“为政以德”,必须兼“不失”意乃足,否则方得之,遽失之。①
吴英在《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中亦对陈栎、史伯璿说加以反驳。首先指出据上下文,“得”是就“为政”而来,意指由心正而推出身正乃至天下正。“不失”则是指修身为政的态度,兢兢业业而不离法度,内含终始不懈、无已不息之义。就朱注言,在“德之为言得也”下顺接“得于心”极为顺畅,如作“行道”则语义中断、累赘。其次,就二说内涵论,“得于心”虽是对“得于身”之改进,但仍是沿用古注,未能自出新说,未能显出必得不失之义。反之,“不失”则已包含行道之义在内,故二者存在语义偏全之别。又反驳陈栎引《大学章句序》“躬行有得于心”为证,盖在序文中,“躬行”乃是据上下文言上下各色人物,皆不离躬行。而此处“为政”和“以德”之所为所以乃是同一回事,故无须再插入“行道”说。同理,“据于德”注之所以有“行道”字,盖此“德”是据上文“志于道”而来,德与道相对而论,而本章“为政以德”之德与政并非相对而是相承,故无须再添“行道”。进而驳史伯璿的“德”为圣人境界说,指出“不失”是对“得”的补充完善,如为邦章注引张子的“不谨”说,即证明“不失”并非仅指贤人工夫,亦可用之以言圣人盛德。针对史氏引《大学章句序》“人所得于天”证明无“行道而有得”则“得于心”者不明说,吴氏从区别两处“德”的普遍与特定意义反驳之,《序》强调德为人所普遍拥有而非大人所独具,突出德的公共普遍性;此处是特就圣人之德而论,其德生而有之,故无须言“行道有得”。批评倪氏未能择善而从而阿谀其师。②
学者还讨论了据于德之德与为政以德之德的异同,意见不一。如金履祥指出,尽管《集注》两处皆以“得于心而不失”解之,然为政以德解不如据于德精密,毕竟此处“据”与“不失”相通。“‘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旧本作‘行道而有得于心’,后改定从此。第二篇‘德’字虽改作‘得之于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①汪武曹则与金氏意见相反,认为正因为政以德章无“据”字,故以“不失”解政可包“据”字。而据于德章之据,已是不失之意,则不应再以“不失”解,而当作“行道而有得于心”。此是从避免语义重复的角度考虑。注文总论中的“得于心”指“德”,“不失”指“据”。
汪武曹曰:“愚谓此处与为政以德不同。彼但举‘德’字,故应兼‘不失’言之,乃是包此章‘据’字在内。若此章既有‘据’字,是不失之意,则‘德’字之解应如今本作‘行道而有得于心’矣。”②
按:朱子与弟子明确论及“得于身”与“得于心”,“行道有得”与“得而不失”的新旧本关系。
问:“《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也。’后改‘身’作‘心’,如何?”曰:“所谓‘得’者,谓其行之熟,而心安于此也。”义刚。
“行道而有得于身”,“身”当改作“心”。诸经注皆如此。僩。
旧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今作“得于心而不失”。诸书未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于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于身’。”曰:“如此较牢固,真个是得而不失了。”义刚。③
朱子指出,改“身”为“心”,突出了行德非勉强偶尔之举,而是对道德自觉认同的为己之行,以便在反复实践中达到内心的安然,“行之熟,而心安于此”,如此才有心悦诚服之效。且“身”当作“心”,亦符合经注通例,合乎“德”的造字本意,“德”字中间为“心”,意味着“德”是“得于心”者也。故改“身”为“心”更加亲切,更合文意。陈淳提出朱子把旧说“行道而有得于身”改为“得于心而不失”(陈淳似未注意“得于心”之说),“不失”可以包含“行道”说,朱子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如此方显出德性之牢固。可见“不失”强调内心德性拥有之牢固。
祝氏以刊于兴国者为定本,今细考其文义,如为政以德,旧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本作“有得于心”,后本又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见也。按:桐原胡氏侍坐武夷亭。先生执扇而曰:“德字须用‘不失’训,如得人,此物可谓得矣,才失之则非得也。”此譬甚切。盖此句含两意:一谓得之于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于有生之后;一谓昨日得之者,今日不可失之也。今必以祝本为定,未必先曰“得于心而不失”,然后改曰“行道而有得于身”,末又改曰“行道而有得于心”。故今不以祝本为定。①
通曰:“不失”二字自有工夫在焉,《集注》改本之精也如此。①
朱子先是把“行道而有得于身”的“身”改为“心”,即变为“行道而有得于心”;在此基础上又改为“得于心而不失”,把“行道”去除,补充“不失”。胡炳文指出祝洙并未看到第二次改本,故停留于第一次改后的“行道而有得于心”。又以《语类》中朱子之说为证,朱子提出“德”当以“不失”解,并以扇子为譬,以德为先天所得而不可失于后天,为往昔实践所获而不可失于今日。“不失”之改反映了朱子重视工夫实践以砥砺德行的用意。如按祝本,则落入先“不失”而后“得于心”的逻辑颠倒之中,实不合情理。“不失”对于操守工夫的凸显显示了《集注》修改之精妙。
在胡炳文所持宋本与陈栎所主祝本的五处差异中,胡炳文仅就此说直接提出与陈栎交流,陈栎对此颇为不满。说:
胡仲虎《四书通》……最是不以祝本为定本,大不是。文公适孙鉴庚三总领题祝氏《附录》云:“后以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今乃不信其亲孙之言,而信外人之言。只看《中庸》首一节断语,诸本与祝本疏密天地悬隔,乃隐而不言,而专以为政篇“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一节来辨,谓“得于心而不失”为定本,而非“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说,“得于心”何必加以“而不失”?“得于心”是得何物?不比据德云,据德是“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因“据”字而下“不失”字耳。②
在认可《四书通》有可取之处的同时,陈栎批评该书过于挑剔,流于“鸡蛋里挑骨头”,最大缺陷在于未将祝本当作定本,不信朱子嫡孙之言而信外人之说。指出二本《中庸》首章按语差别巨大,炳文不以此辩论,却专挑为政以德来争辩,避重就轻。认为“得于心”后不必补“不失”,“为政以德”之德不同于“志道据德”之德,彼“德”为“不失”,乃是因“据”字而发。并指出胡炳文相交之初,甚为认可自家观点,如今却改变初衷,背离己说,显出对炳文讥讽态度。
倪士毅《四书辑释》详引师说,批评胡炳文根据《语录》“德字须用不失训”说断定以“不失”解“德”,并不可取。
祝氏《附录》本如此,他本作“得于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于心而不失”之说……先师谓此说纵使有之,亦必非末后定本。深思细玩,终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精当不可易也。……初作“得于身”,后改“得于心”。夫“道”字广,在天下所共由,“德”字亲切,吾心所独得。行道,行之于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于心,则躬行者始心得之,心与理为一,斯可谓之德。①
因此说并非朱子定见,实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精妙确当。朱子“德之为得”初作“得于身”,后改作“得于心”。行道得于心方可为德,盖道指天下共同遵循之路,所指广大普遍,不如“德”字专指一心所独得亲切。“有得于身”和“有得于心”有别,行道于身,未足言德,只有得道于心,躬行实践,心与理一者方可视为德。“行道而有得于心”的“行道”是实践工夫,“得于心”是工夫目标,二者次序分明而分工明确,精妙无比。“得于心而不失”说一则笼统,未指明“得于心”者为何,二则衍说此处所无的“不失”之意,不紧切。此外,“据于德”注之“不失”乃因“据”字而发,且紧接“行道而有得于心”来。此章如言“得于心而不失”则过于急促,且无所指向,徒为累赘。又《大学章句序》“本之躬行心得”与“行道而有得于心”相印合,“躬行”对应“行道”,“心得”对“得于心”,可证祝本为定本。
二本皆有“得于心”,差别仅在“行道”和“不失”二字。正如诚意解一样,《四书集编》《四书纂疏》等宋元本主“不失”,赵顺孙指出新旧本的修改是从“行道而有得于身”到“得于心而不失”,心较身更为紧切。但并未提及陈栎所主张的“行道而有得于心”说,或许他当时似并未见此说,此说于其时恐未甚流行。“愚案旧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今作‘得于心而不失’。不言身而言心,心切于身也。”①金履祥则明确指出“行道而得于心”为初说,“《集注》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于心,’其后改从此。盖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鲜可谓之有德者。”②他认为初说来自据于德注,后改为“得于心而不失”。作为公共的道为人心所同具,但作为个体修养的有德者则少,人常常暂有所悟而无法久存于心,或仅是知德而不能体之于身,故最终皆得而复失,而不足以为德。可见朱子改本强调“不失”二字用意深刻,德不难于得,而在于保持不失。吴程亦以陈栎说为初本,说“行道而有得于心”,乃朱子初改本。
元刘将孙《颜曾省身字说》对朱子“德”字注释修改之叙述,同于胡炳文说,由“得于身”到“得于心”,在易箦前方定为“得于心而不失”。由此推出身即心、心即身说为合理而有益,显出心在腔子里。“犹记往年见晦庵释‘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一语,初本‘心’作‘身’。盖易箦前数日,始定为‘得于心而不失’。故窃以为‘身即心,心即身’语为不悖而粗有益。”③
陈栎说在元代亦有所呼应。史伯璿大赞其“得于心者何物”说反驳有力,认为“不失”说未论及所得为何,有落空之疑,不如“行道有得”明确得于心者为道,正与《大学》明德解“得乎天”同例,可见所得真实不虚。且“不失”乃学者工夫,是就入德之人而言,不合经文大舜无为而治的圣人境界。史氏是从德之虚实及工夫境界之分而论,颇见新意。《四书大全》认可陈栎说,并引倪氏辩护语。
二说当以《发明》为是,其曰“得于心者何物乎”?此说极是。《大学》释明德,必曰“所得乎天”云云,便见所得之实处。今但曰“得于心”而不言所得之实,可乎?况“不失”二字为入德、进德者言之则有味。为政以德,无为而天下归之,正是舜无为而治之事,此盛德自然之应,“不失”不足以言之矣!①
但自元以来,主张胡炳文说的学者即大有人在。元许有壬认为朱子之德有两种解释,本然之德和修为之德,朱子虽以“行道而有得心”解此处之“德”,但却是从“修为以复德”的学者之工夫而论,不同于史伯璿主张的“盛德自然”境界义,史氏所论乃本然之德,是圣人所独有。许氏强调了得而不失的意义,天所降之理构成我所受之德,此即道得于心;然而有得则有失,只有得而不失于心,深造自得而保持持久者,方是真得其德。日月一至者,非得也。
德之本然,唯圣人为能;修为以复,则学者事也……天之所以与我,我所以为德者,故曰“行道而有得于心”。且得者,失之反也,“得于心而不失”,乃为真得。②
清汪武曹反驳史伯璿说,而认可“得于心而不失”说,一则据《语类》之意,二则就文本论。为政以德必须兼不失,若无“不失”,则得失无常,无法保证德之真实拥有。又据注文中程子的“为政以德,然后无为”,即朱子的“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推出以德和无为是两层意义,无为而民归之意实在下句“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中,不可完全由“为政以德”承担,此此反驳了史伯璿的“德”为舜无为而治之境界说。孙见龙对新旧说加以调和,认为本可相通,“得于心”是就正面论德,“不失”是从反面不足。
汪武曹曰:“得于心者何物”句,似亦驳得有理。但玩《语类》,终当以“得于心而不失”为定本。且讲“为政以德”,必须兼“不失”意乃足,否则方得之,遽失之。①
吴英在《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中亦对陈栎、史伯璿说加以反驳。首先指出据上下文,“得”是就“为政”而来,意指由心正而推出身正乃至天下正。“不失”则是指修身为政的态度,兢兢业业而不离法度,内含终始不懈、无已不息之义。就朱注言,在“德之为言得也”下顺接“得于心”极为顺畅,如作“行道”则语义中断、累赘。其次,就二说内涵论,“得于心”虽是对“得于身”之改进,但仍是沿用古注,未能自出新说,未能显出必得不失之义。反之,“不失”则已包含行道之义在内,故二者存在语义偏全之别。又反驳陈栎引《大学章句序》“躬行有得于心”为证,盖在序文中,“躬行”乃是据上下文言上下各色人物,皆不离躬行。而此处“为政”和“以德”之所为所以乃是同一回事,故无须再插入“行道”说。同理,“据于德”注之所以有“行道”字,盖此“德”是据上文“志于道”而来,德与道相对而论,而本章“为政以德”之德与政并非相对而是相承,故无须再添“行道”。进而驳史伯璿的“德”为圣人境界说,指出“不失”是对“得”的补充完善,如为邦章注引张子的“不谨”说,即证明“不失”并非仅指贤人工夫,亦可用之以言圣人盛德。针对史氏引《大学章句序》“人所得于天”证明无“行道而有得”则“得于心”者不明说,吴氏从区别两处“德”的普遍与特定意义反驳之,《序》强调德为人所普遍拥有而非大人所独具,突出德的公共普遍性;此处是特就圣人之德而论,其德生而有之,故无须言“行道有得”。批评倪氏未能择善而从而阿谀其师。②
学者还讨论了据于德之德与为政以德之德的异同,意见不一。如金履祥指出,尽管《集注》两处皆以“得于心而不失”解之,然为政以德解不如据于德精密,毕竟此处“据”与“不失”相通。“‘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旧本作‘行道而有得于心’,后改定从此。第二篇‘德’字虽改作‘得之于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①汪武曹则与金氏意见相反,认为正因为政以德章无“据”字,故以“不失”解政可包“据”字。而据于德章之据,已是不失之意,则不应再以“不失”解,而当作“行道而有得于心”。此是从避免语义重复的角度考虑。注文总论中的“得于心”指“德”,“不失”指“据”。
汪武曹曰:“愚谓此处与为政以德不同。彼但举‘德’字,故应兼‘不失’言之,乃是包此章‘据’字在内。若此章既有‘据’字,是不失之意,则‘德’字之解应如今本作‘行道而有得于心’矣。”②
按:朱子与弟子明确论及“得于身”与“得于心”,“行道有得”与“得而不失”的新旧本关系。
问:“《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也。’后改‘身’作‘心’,如何?”曰:“所谓‘得’者,谓其行之熟,而心安于此也。”义刚。
“行道而有得于身”,“身”当改作“心”。诸经注皆如此。僩。
旧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今作“得于心而不失”。诸书未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于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于身’。”曰:“如此较牢固,真个是得而不失了。”义刚。③
朱子指出,改“身”为“心”,突出了行德非勉强偶尔之举,而是对道德自觉认同的为己之行,以便在反复实践中达到内心的安然,“行之熟,而心安于此”,如此才有心悦诚服之效。且“身”当作“心”,亦符合经注通例,合乎“德”的造字本意,“德”字中间为“心”,意味着“德”是“得于心”者也。故改“身”为“心”更加亲切,更合文意。陈淳提出朱子把旧说“行道而有得于身”改为“得于心而不失”(陈淳似未注意“得于心”之说),“不失”可以包含“行道”说,朱子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如此方显出德性之牢固。可见“不失”强调内心德性拥有之牢固。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