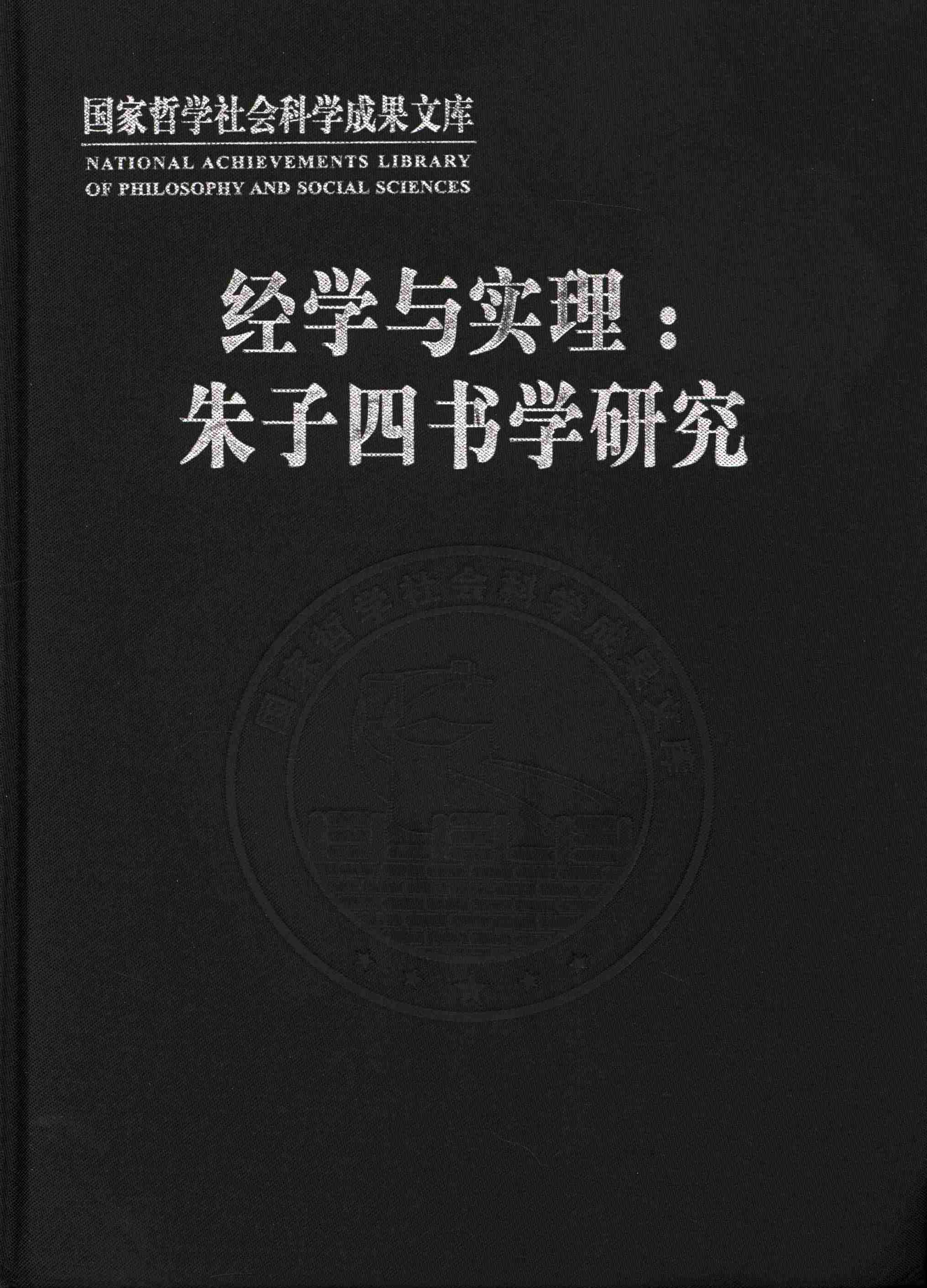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六节 “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朱子四书学的转化与超越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862 |
| 颗粒名称: | 第六节 “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朱子四书学的转化与超越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7 |
| 页码: | 420-436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从学术史的视野出发,将朱子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前朱子学、朱子之学和后朱子学三个阶段。其中,朱子对程门思想的批判和自我否定成为其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朱子去世后,朱门后学对朱子思想进行了新的批判性诠释,试图消除其矛盾和不足。清儒对朱子的批评也是基于朱子后学对朱子考据学的补偏纠缪。因此,本文试图立足于朱子学的批判继承精神,来考察朱子及其后学的自我更新和转化。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学术史 |
内容
从学术史的视野来看,广义的朱子学似可包含以北宋道学为主的前朱子学、构成朱子学主体的朱子之学、传承发展朱子之学的后朱子学。在此波澜壮阔的朱子学发展历程中,善于传承、勇于批判的精神成为其自我革新的不竭动力。朱子丁酉初成的《论孟或问》,以辨析《论孟精义》所收程门之说为主,充分显示了朱子对程门由“不敢疑”之尊崇至怀疑批判的转变,反映了朱子由依傍程门到自出手眼,独立门户的转变,实现了对自我的否定和超越,堪称朱子思想之“独立宣言”。朱子于该书实现了两个相辅相成的目的:辨程门诸说得失,明《集注》去取用心。但朱子思想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或问》之解“原多未定之论”,晚年《集注》对此作了很大修订,体现了朱子自我批判的彻底性和长期性。朱子去世后,朱门后学亦因应时代变化和朱学演变的实际情况,对朱子思想从训诂、义理两面加以新的批判性诠释,试图消除朱子的矛盾与不足,勉斋学派于此尤为显著,如北山学派之考据、双峰学派之义理皆立足于此。故从朱子后学对朱子的批判继承这一视阈来看,阳明学未尝不可谓之朱子学的修正者。至于清儒以朴学批朱,如毛西河以考据对朱子加以纠缪与“改错”,本不足为奇,实为朱子后学对朱子考据学补偏纠缪之发展,并未逸出朱子学之藩篱。故本书试图立足于朱子学的批判继承精神,来考察朱子对二程学派、对自我、朱子后学对朱子前后相续的三重批判,以管窥八百年朱子学自我更新与转化之一斑。
一 《或问》之“辨析毫厘”与“明所以去取”
(一)《或问》:朱子思想独立之宣言
朱子毕生殚精竭虑于《四书》,完成了一个由《精义》、《或问》、《集注》构成的四书系列著作。在三者之中,《或问》是一具有特殊地位而相对被轻忽的著作,它起着承接《精义》与《集注》的枢纽作用,不仅是研读二者不可或缺的辅助之书,且具有独立价值,标志着朱子思想的初步成熟,显示了朱子与程门的某种“决裂”,所用设问问答的“或问体”亦成为影响后世经典诠释的一种重要题材。
《或问》为朱子多年研读《精义》的一次深度全面反思,二书关系极为紧密,如同靶与箭之关系,无《精义》之靶,则《或问》成无的之矢。①朱子给弟子示范了如何比较辨析《精义》各说,特别提到对各说皆应抱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不可先入为主,迷信程子权威,尽管在比较验证之后,通常是程子之说“多是”,门人之说“多非”,但在面对文本之前,不可先怀是此非彼之心。盖门人之说亦“多有好处”。朱子强调,最难辨“似是而非”之论,只有对诸家是非得失有了恰当认识,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看法,自身才能实有所得,“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②。
《或问》对《精义》的反思成为理解《集注》的必要参考。因《论孟或问》代表了中年朱子的思想,可作为考察朱子思想演变的重要桥梁。《集注》由于受到注释题材的限制,非常讲究文字精简,力求达到无一字闲的地步,《或问》则是论辩题材,抒写自由,论说详尽。如说《集注》是论题之结论,那么《或问》则是论题的论证,清晰展开对各说得失的取舍辨正,非常有助于学者理解《集注》。朱子甚为忧虑学人未能理解《集注》良苦用心,引杜甫诗“良工心独苦”自明心迹,言“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③。《或问》最充分流露了朱子的用心,可谓“吐心”之作。尽管朱子貌似对《或问》有“不须看”之言辞,但此仅是特就其与《集注》相较不可作为定论而言的,朱子并未否定该书价值。简言之,该书在继承程门说之同时,体现了一破一立的特点:破程门之瑕疵,立自家之新意。一则尽显朱子与程门在义理与方法上之差异,可窥朱子之独立与自信;二则可察朱子诠释《集注》下笔之良苦用心;三则可动观朱子思想异同之演变。古今学者对《或问》皆给予高度评价,真德秀《读书记》卷三十一赞为“辨析毫厘无微不显,真读书之龟鉴也。”《四库提要》就其与《集注》关系之分合两面论其价值,中其肯綮,“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于折衷众说之由;其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①。今有学者认为其价值犹在《集注》之上。
因《或问》批判锋芒太过锐利,朱子对其“轻诋前贤”所可能造成不良影响亦有所顾忌。《答吕子约》言,“但掎摭前贤,深负不韪之罪耳”②。真德秀《读书记》认为朱子不欲以该书示人,亦与担心其可能造成学风轻薄有关。“恐学者转而趋薄,故《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③此仅为《或问》之一面,然该书实为朱子辨误说、明正学的“不得已”之作,它实质上是对程门思想的清算之作,书中对程门的批评可谓体无完肤,划清了与程门淫于佛老、脱离文义之界限;以毫无隐晦的态度,锱铢必较之精神对程门之说逐字逐句加以辨析,在充分表达自身见解用心之时,显示了思想独立的应有自信。
(二)“辨析毫厘无微不显”
《或问》对诸家说的解析,体现了朱子特别重视解经方法和严辨儒佛的特点,显示了他与二程学派在解经理念、方法上的诸多差异④,朱子反思曾信奉达二十年之久的一味发挥己意,自作文字,不切文本的自我阐发型解经风格,强调回归意从文出、贴切本意、注重训诂的传统解经风格。他对借经典发挥一家之言的宋学解经风格之弊加以反思批判,而力图以注重文本之义、阐明圣贤原意的汉学解经风格矫正之,从而实现两种解释方法的统一。这个反思早在丁酉《或问》之前已开始,癸巳左右给南轩书信中已深切反思“自作一片文字”的风格,强调要回归汉儒经注合一,注仆经主的诠释态度,改变二程学派经仆注主、以经文强就己意的做法,提出虚心发明经意的原则。
批评“不叛圣贤而兼取老佛”的儒佛合流论,严辨掺杂佛老的思想,注重内部清理。朱子认为,佛老对儒学的侵蚀冲击,要害不在崇信佛老者,而在淫于佛老的儒家内部人士,尤在以佛老思想解释儒家经典,造成儒佛不分,以紫乱朱之混乱。朱子《杂学辨》将“阳儒阴释”的程门后学张九成斥责为“洪水猛兽”。《中庸章句序》公开指责程门“倍于师说,淫于佛老”。《或问》对亲学于二程诸高弟的儒佛不辨,以佛老解儒表达了极度失望、愤懑、痛惜、不解之情。“(游、杨)二公学于程氏之门,号称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晓也已。”①朱子以对屡空的解释为证,批评程门采用何晏老庄之解而不能辨之,亦不能辨别颜子不远复与佛教止念之别。“何晏始以为虚中受道,盖出老庄之说,非圣言本意也。诸先生亦或从之,误矣。……夫《易》所谓‘不远复’者,岂若佛氏觉速念止之云哉。”②朱子认为,以佛老解儒和以儒解佛老是同一事情的两面,相互影响渗透,导致儒与佛老愈加纠缠难辨。真正要做的是正本清源,切割二者联系,以儒解佛者将不同体系之思想强加扭捏,极为可笑。
空、无、忘、乐等与儒家境界相通之概念易于儒佛混流。儒家并非不讲无,只是此无须建立在“无私欲”之后自然呈现的无我之上,而非佛老刻意造作所追求者。“夫谓无私心而自无物我之间可也。若有意会物而又必于己焉,则是物我未忘。”③在带有本体意义的论题如性、理等上,朱子严别儒佛。一方面批评学者在突出理的形上意义之时,未能兼顾其与形下的贯通,导致“遗物”“外物”。如批评杨时理不可言即老佛之意。盖理即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本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中,非在日用彝伦之外别有一空悬之理存在。于“朝闻道”章强调儒道以五伦为实理,佛道则以五伦为幻妄绝灭之物,而以清净寂灭为终极追求,二者根本不同。另一方面又批评其说“遗理”,如批评游氏道本无名,感物而生,方有善名;因物而生,方有性名说乃佛老言,割裂了道、善、性的一体,而分裂为三物。
朱子判定程门流于佛老有以下情形:一是直接采用“老佛之正论”,引佛老之语,此为直接证据。如谢氏“引老聃知我者希,则我贵以为说者”。④二是化其语而师其意,常以“老佛之余论”“老佛之绪论”称之。如批评“游氏念念不忘之说善矣……则恐其未免于老佛之余也”①。此是由朱子判定而出,其说服力不如第一种。三是因语意不精、用语过度而“流于老佛之弊”。如指出“无隐”之解,“谢、杨氏为说……恐其过而流于老佛之意也”②。四是儒佛“一毫之间”者,其论与佛说相差几微,极其值得警惕。如指出程子“‘得此义理’一条尤为卓绝。然读者亦当深造以道而自得之,一毫之差,则入于老佛之门矣”③。五是着重从治学风格判定异端祸害,以正学风。异端之学表现为幽深、恍惚、高远、虚空、怪诞,措心文字之外,崇新奇尚简易。凡用语传达好高轻下、喜内忽外之意者,朱子多纳入于习于佛老,试图希望对此风气的扭转促使学风回归平实。如批评在格物的理解上存在此种倾向:“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而欲藏形匿景,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絶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言论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后可以得之,则是近世佛学诐淫邪遁之尤者。”④
“傍缘假借,最释经之大病”。此是朱子对程门解经弊病的根本概括。《或问》在揭示程门解经内容不妥之时,尤重反思解经方法。从解经方法上详尽揭示程门欠缺,清算程门不切文本,以己意解经的诠释风气,强调解经应切当文意,是《或问》批判的另一重心所在。批评程门“不附经文而直述己意”的做法完全无视经文本意,对此等说“虽美不取”。如《论语》谁毁谁誉章指出,“诸说之于此章,其意则皆美矣……类皆不附经文而直述己意,使人读之,但见义理粲然,曲有条贯而莫知其果欲置经文本意于何许也?……是以不得而取耳”⑤。比照一下伊川之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⑥。其摆脱文本束缚,直抒大意的说法,恰与朱子相对照。朱子对此有明确自觉,提出程子与己解经的差别在于置理于解语中还是经文内。朱子于学而章对程门解经得失及其弊病作了纲领式的阐述。将其症状总结为七类:文同旨异;意似实殊;以难释易;以有形无;亲者反疏;明者反暗;俱昧欲明,循环无决;取信于外,无真实见。此对各家解经弊病的批评,乃是朱子解经的实践之谈。如在对忠恕的理解上,程门常将《中庸》“忠恕违道不远”与《论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引用互证,两种不同含义的忠恕相互矛盾,导致混乱。
(三)文本、义理与实践兼具的取舍原则
《集注》用语“浑然犹经”,貌似多采成说,实则创新极多。朱子担心学者不能明其用意所在,故于《或问》阐明之。自述宁冒轻诋前贤之恶名,而决意于《或问》直析前辈各家得失,阐明自家取舍标准与用心。在表述上,《或问》皆是先立后破,先表达朱子见解,再剖析各说得失所在,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采用问答体这一问题导向鲜明的体裁,《或问》可谓一部问题诠释的经典之作。以皆自设问答的方式,精准解答之,典型的表达方式是:“或问……何也?”如《大学或问》开篇,依次问答“大人之学”,小子之学,小学与大学,以敬补小学,敬之为学之始终意义等论题,以1300余字的篇幅阐明《大学》三纲之理气、心性、工夫论含义,一气呵成,实可谓朱子哲学之提纲。二是进一步阐明《集注》观点,如关于程子改“亲”为“新”之根据,《大学》章句文本的调整及缘由等皆有充分说明,达到了解疑释惑的目的。三是详尽呈现朱子取舍之根据、理念,如指出《集注》“三年无改”章所引尹、游二说分指孝子之心与孝子之事,二说相须,不可或缺,道出《集注》用心所在,二说各自意义及其关系,“盖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说相须,为不可易”①。这种解释方法对朱子后学《四书》解释影响甚大。
《或问》辨析极为细致,贯穿了读音与字义,文义与本旨,文本与现实,提出了取舍的多项原则。一是文义优先于义理原则。某说虽发明道理甚美,若不契合文义,则不取。“又有谓施为施刑之施,……其意美矣,然‘施’字之说,则恐过深。”②文字训释不仅是为义理服务的小学工夫,而是决定义理理解的根基之学。《或问》充分体现了此点。如《中庸》“违道不远”的“违”非“离开”,而是距离之意,诸说不解文义而强加解说,扦格不通。“违道不远,如齐师违谷七里之违,非背而去之之谓。愚固已言之矣,诸说于此多所未合,则不察文义而强为之说之过也。”①他以“恕”字解为例,突出此字义解释偏差将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极大祸害。“恕”当正解为“如心”,而非苟且姑息之义,只可对人,不可于己,于己则当“严于自治”,批评范纯仁“恕己之心恕人”说虽心存厚道,为世所称,其实不合本义,后果严重。批评郅恽对光武帝的“恕己”解将引发逢君之恶、贼君之罪的恶劣后果,发出“一字之义不明而其祸乃至于此,可不谨哉”的感慨。②
与把握文义密切相关,常为前辈所疏忽的读音、句读、章句之学则为朱子所极重视,他视此为与前辈治学的重要区别。“诸说多误,盖由音读之学不明”。朱子指出程门解经之误多源于缺乏音读之学,认为“文字音读之学岂可忽哉”!《或问》特别注意从音韵的角度解释字义,将音义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如论证“望道而未之见”的“而”与“如”古字音义通用,诸家之误即在于无“文字音读之学”。指出“古今为说,迂回赘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于圣人之心,又不能有所发明,由不察乎此而已。然则文字音读之学岂可忽哉”。③《或问》关于音读解义有极精彩之例,如批评诸家对“无适无莫”的误解源于以“适”为“子适卫”之适故也。
《或问》进一步提出章句之学的重要,主张义理与章句融为一体,批评程门解经之误多源于“看不成句”的章句之差。言“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典型者如《中庸》道不远人章“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四句之断句,应在“子、臣、弟、友”后绝句,前辈如张九成等以“父、君、兄、之”断句既不通文意,亦不当文理,批评“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①。《或问》对程门句读点评甚多。或批评其新句读之新解不合文义。如《论语》4.5不以其道章,程氏主“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说;《论语》礼让为国章主“能以礼让”断句等。朱子有时亦反对各家采用旧注点读而自出新说。如批评各家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循旧注“心”后断句,读“从”为“纵”,音、读皆误,不合文义、本旨。然于“至大至刚以直”则宁用近世俗师之见,以“至大至刚”为断,批评程子循赵岐说以“直”断,体现了朱子当仁不让、公平正大的批判精神。朱子对《四书》章节之分颇有创获,如《论语》9.29“可与共学”章,9.30“唐棣之华”章自出新解,批评程门(范氏在外)因循汉儒合章之说有误,强调章句之差非无关紧要之误,它直接决定义理得失,提出章句之学不可忽视。“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说之弊,遂至于此。章句之学,其亦岂可忽哉。”②
本意(本旨)优先于义理原则。朱子认为,解经在平实释义的基础上,以阐明经文本意、挖掘圣贤本旨为目标。故是否准确阐发经文本旨,是决定《集注》取舍的根本原则。《或问》亦多次提出,某说虽美而不合本旨,故未取。如批评程子以“斯言可师”解“温故而知新”章,义理虽优美却无关文意,“程子恶夫气象之狭而为斯言,可师之说,美则美矣,其无乃非本文之意乎!”③
药病救失的工夫实践原则。朱子认为,经典诠释除切合文意之外,更要重视对学者践履工夫的指导和为学弊病的矫正,如能做到此点,虽有不合文意之处,亦当取之。此是从工夫实践角度确定的原则。《或问》特别注意提示此点,如指出吕氏不可使知之章“起机心”说虽非圣人本意,然确有切中时弊之益。“此非圣言之本意,然亦颇中近世学者之病矣。”④有时否定谢氏之说不合圣人气象之时,又赞其确有激发学者立志向学之处,故取之。“谢氏之说粗厉感奋,若不近圣贤气象者而吾独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①
逻辑一致原则。朱子据逻辑一致原则批评程门“语意倒置”之误。《或问》多处揭示程门在解说经典时,常颠倒语义,反映出逻辑次序混乱。程子即被多次点出此种“倒置”倾向。基于朱子自身理解,判定他们对文义、概念、工夫、效用等先后、本末关系处理有误,体现了重视逻辑分析的特点。如批评程子《论语》末章“第三说谓有诸己然后知言,则能格物穷理。语意倒置,亦不可晓”②。《孟子》尽心首章范氏颠倒穷理与尽心的关系,“至谓尽心所以穷理,则又倒置矣”③。
“本文气象”原则。“本文气象”指文本内在传达着与某种人格(含被诠释者与诠释者)相对应的一种精神气质,如典雅、雍容、洒脱、敬畏、粗暴、高远、平实等,体现了朱子经典诠释始终以塑造人的精神为指归的特点。朱子指出程门之解虽文意无误,但却不合乎文意所传达的人物精神气质,如《论语》“惟天为大”章杨氏说解释详密,但气象狭窄,不合本文气象,故《集注》不取,“杨氏说虽密,然气象反狭,与本文气象不相似也”④。朱子始终以圣贤气象为中心,如批评侯氏对夫子心怀重重顾虑之论说,完全不合圣人从容中道之气息,还指出解经文字所显示的气象恰是作为解释主体自身气象的映现,所谓“文如其人”也,学者诠释之差异偏颇,正是各自气象修养偏颇之显露。如《论语》“鲁人为长府”章谢氏“不必改”、杨氏“无意改”皆是各自性情气象所偏之体现。
公平正大原则。《或问》还从诠释态度批评程门之误,未能做到是非分明、公平正大、不虚美,不隐恶,其避嫌之论,远离圣贤公平正直的本来宗旨,体现了强烈的实事求是的反权威精神。《或问》批评“齐一变”章各家存在避嫌思想,不欲就太公、周公优劣加以比较,不欲正视鲁国以侯王而行天子之事的事实,正因有如此之避讳,故其说难免存在有意之私,而不合乎公平正大如实的圣人本旨。此直接影响诠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又有避嫌之病,益使其说不得不有所遗。如避周公、太公优劣之嫌……避鲁以侯国而行王道……此其说虽似美,然恐其不免于有意之私,而非圣言公平正实之本旨也。”①在“宰我问三年之丧”章、“犬马有养”章,《或问》皆批评诸家用心不公,多有维护宰我的文过之言,强调三年之丧“非有难明之理”,圣人明斥宰我为不仁而不应曲讳。“为已死之人,文不可赎之过。”②
二 “当日原多未定之论”
《论孟或问》作为处于壬辰《精义》与晚年《集注》之间反映朱子丁酉时期思想的作品,与二者皆有距离,尤其是与《集注》颇多差异,“多未定之论”,故其解不可据为定论,此似为其价值之限,然正因其与《集注》之差异,正可由此真实窥探朱子思想前后之演进,体现了朱子自我批判精神。即以简单的分章为例,《或问》受前人影响曾将雍也可使南面章分为两章,“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句单独一章。又如恭而无礼则劳章《集注》引吴氏说,主张“君子”以下单独分章,《或问》未提吴氏说,可知此意乃《或问》之后所增。义理方面,更是与《集注》差距颇多,存在“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的对反情况,即被《或问》所肯定者为《集注》所否定;被《或问》所否定者为《集注》所肯定。如大哉尧之为君章《或问》大赞程子解,但《集注》并未取,而是取尹说。如《或问》批评《精义》诸家“免而无耻”之“苟免”解不合文意,应是真心革面、不敢为非之意,但今《集注》正是“苟免刑罚”,又折回《或问》所否定的程门说。大体来说,朱子之见,在前《或问》时代,常采用程门说;《或问》时代,则通过扬弃程门而自出己说;《集注》时代,则是成熟的定见。《集注》对《论孟或问》之说,或删除或增补。如《或问》把学而章全章分为学之始、中、终,《集注》无此。《集注》第二章仁之解较《或问》“爱之理”补充了“心之德”说。鉴于《论孟或问》与《集注》存在的客观异同,使用该书时应对其得失和价值有一理性中道的认识,置其于具体语境中,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方能尽其底蕴,为我所用。
三 后学批评:“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
朱子学既形成于朱子对程门的批判和自我修正中,亦离不开门人后学对之展开的批判、传承与转化。黄榦及其开出的双峰学派、北山学派对朱子学展开了有力批判,成为后世朱子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从朱子学的批判接受史来看,明代阳明学的出现正是对朱子学批判修正的结果。清代朴学之兴起及对朱子的批评,并未越出朱子学之藩篱。概言之,朱子之后宋元明清之思想学术,实可谓“朱子学之注脚”,以下拟从批判性继承朱子学的角度论之。
朱子后学之义理批判。勉斋被朱子赞为“会看文字”,他弘扬乃师“取予在己”、入室操戈之精神,直接指出《集注》之不足。《复叶味道书》言:“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如在《论语》首章学而不愠与君子关系上,勉斋认同程子不愠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说,反对朱子君子才能不愠说,前者从工夫言,后者就成德言。指出《集注》“人而无信”章、“志道据德依仁”章之不足,修正《集注》“十五志学”章夫子所言进学次第乃虚说之观点,认为当是夫子为学境地之实说。勉斋有意彰显心的本体意义,提出“心便是性”“心便是仁”等心性为一思想,指出“点检身心”“求放心”“反身一念”等身心之学较之讲学穷理,更为根本,是道之传承与否的关键所在,显示出对“心学”的包容与工夫的内转。勉斋对朱子之批判,为弟子饶鲁所继承光大。如在《孟子》“仁人心也”章,师徒就心的属性提出与朱子不同看法。认为人心、放其心、求放心的三个“心”脉络相连,皆是指仁,指义理之心。《集注》视后者为知觉之心,与前文不相应。在《中庸》理解上,勉斋、双峰、草庐更体现了对朱子学继承突破的接力性,勉斋将《中庸》分为三十四章六大节,以道之体用为全书主线,戒惧慎独、知仁勇、诚为工夫论系统,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二,突出“诚”的地位。弟子饶双峰、双峰再传吴草庐对此作了新的继承阐发。在章的划分上,双峰与勉斋有所不同。草庐则干脆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四,并独立为一节,认为其主旨为“论治国之道在人以行其教”而非诚。双峰对朱子的批判、突破有明确的自觉,提出怀疑朱子格物诸说的原因在于朱子格物解过于阔大空洞而不切实际,“反之于身,自觉未有亲切要约受用处”。主张“诚意”章“乃《大学》一篇紧要处”。批评朱子忠恕之道解仅突出了忠恕的道体义而忽视了工夫义,犯了“主一而废一”的毛病。有学者由此提出朱、饶分开的观点:“后学当以朱子四书自作朱子四书看,饶氏四书自作饶氏四书看”。①元程钜夫《书何安子四书后》肯定了勉斋、双峰师徒对朱子的突破创新。“而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双峰之说,又有勉斋所未及者。”②
朱门后学之考证辨析。承继勉斋的北山学派着重对《集注》的缺失展开知识性的考证,突出了朱子学中考据的一面。金履祥《论语孟子集注考证》为其代表,《四库提要》认为该书于《集注》“事迹典故考订尤多……于朱子深为有功”。金履祥表白了对《集注》修正的忠臣态度和纠偏的客观事实。其言颇有意味:“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③史家多将刊于1337年的金氏之书视为考辨《集注》最早、最要之作,其实不然。如赵惪《四书笺义》纯以考证《集注》史实训诂为主,与《论孟集注》为同一类型著作,刊于1328年④。胡炳文(1253—1333年)之《四书通》刊于1329年,该书虽重义理,然于训诂亦多所校正。另元詹道传《四书纂笺》亦与《论孟集注》为同类型的纯训诂著作,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音、明义、考制、辨名等方面考察,该书广引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许谦《详说》、赵悳《四书笺义》,较三者晚出。然《四库提要》对此四书评价颇异,赞誉金履祥《考证》勇于批判之精神,却屡贬低其他三书对朱子之维护曲从。导致四书馆臣产生此种偏差的原因,与其不熟悉三书而带有先入之见有关。以下随举数例以较此四书对《集注》之批评:
据表可见,其一,对《集注》的考辨不始于金履祥,实始于朱子门人勉斋、辅广等,朱子门人并未因维护朱子而讳言其失,只是较含蓄而已。其二,朱子门人后学对《集注》缺失的考察基于其他朱子文献和朱子漫长的学术空间,常采取以晚年之朱攻早年之朱的方法,但在判定孰为早晚、何为朱子晚年定见时不无可商。如《诗集传》、《书集注》是否必晚于《集注》?金履祥的“《辨证》朱子晚笔,则《集注》未及改耳”说是否可信?盖《集注》朱子至死仍在修改,不好断定《集注》必在后。其三,诸书指出《集注》之“误”表现在引史实、古注、古书等,包括记忆之误,可见《集注》即便存在某些失误,亦是有根底之误,非朱子自造之误。其四,学者判定《集注》之“误”乃是基于各自理解,未必妥当。如金履祥站在王柏立场,认为《诗》并不可靠,针对《诗》之郑卫情况,提出“今之三百篇岂尽夫子之三百篇乎”①?
明代心学、清代朴学对朱子学之批判顺承。清儒对《集注》之辩证,虽引证范围更广、论证更精密,然其旨趣并未越出朱子《四书》之范围,不过是其中“小学”一面之发展而已。即以攻朱甚烈的毛奇龄《四书改错》为例,该书除夹杂争强好胜意气成分外,其余关于人名、地名等处,一则反驳立论非皆有定据,二则以朱子放弃之说以攻朱,了无新意。如以朱子已放弃的程子等采用的“传不习”旧注,攻击朱子新说。其对《集注》相关内容之驳正,大半朱子后学早已陆续开展之,毛氏所驳殊无可奇之处。如对朱子后学相关考辨作进一步搜寻,毛氏所论当基本包括。故该书不过是无意中将朱子后学对朱子考据批评之一面,集中罗列批评而已,所论实未能逸朱子学之藩篱。颇惊奇者,清人及近人予此书过誉之评,恐受《四库提要》误导,仅见朱子后学对朱子维护羽翼之一面,而未睹其批判修正之工作。②
阳明学常被视为朱子学之“反动”,然唐君毅、陈荣捷等先生则视为朱子学之修正。①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皆是在与朱子学长期的学习对话中展开。他自述曾对朱子之说“奉若神明”;刊刻《朱子晚年定论》以示并未偏离朱子,而是契合如一,本意并非“摘议晦庵”,其所不满者,乃是朱子心理为二所导致的外在格物之学、支离之学。其实阳明学之起点和终点大体同于朱子,千学万学,无非是“去人欲,存天理,成圣贤”。差别在实现“去欲存理”的理论基础和路径,阳明肯定心理即一,良知内在,天理内在,故工夫主内在推扩,逐步致良知于外;朱子则认为心理虽先天为一,理具于心,理不外心,但现实中因气禀私欲之遮蔽,心理为二,实现心理为一之境,须经由向外格物穷理,以光明心之体用。元儒评价饶双峰之《四书》不同于朱子者“十之八九”,阳明喜以“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来形容与朱子之别,不同于朱子者不至于“十之八九”,其思想之论域并未越出朱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更内在化、收缩化了,跳过了朱子学第一层的理、物存在问题,而始终着眼于心与理、心与物的意义显现问题,其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之“无”,并非存在之没有,而是于心之“未显”,可以说朱子注重存在“实现”,阳明关切意义“显现”。阳明特别重视理学之体用,以此处理良知与发用。在工夫问题上,阳明固不重主敬,但颇重克己(克治)、主静、立志,此与朱子亦一致。《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开启阳明学与朱子学内在沟通的可能性和连贯性,通过重新“发现朱子”,论证朱子“晚年之悔”来印证彼此的关联一体性。故自勉斋开始,朱子后学即逐步存在一“内转”倾向,此正如孔门后学之内转,至孟子而显其成;亦可说朱子学之内转,至阳明而终其成。阳明批朱的“话头”多有与朱子后学同声相应之处。如批评朱子之理由之一是无法自得其学于心,此与双峰反思朱子格物之说未有亲切受用极其相似。阳明对朱子之批评,多以“先儒”等语含蓄表达之,且始终保有尊重附和之意,认为己心实同朱子之心,称赞朱子解义有不可改易之处。“然吾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①勉斋学派对朱子批评之用语,较阳明甚至更为直白,如双峰言:“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于前人语意尤看得未尽如此。”②阳明阐发之问题,在朱子后学中不乏知音在。如对朱子《大学》改本之不满,重视诚意等;即如“心即理”“心外无理”之命题,元代朱子学者胡炳文亦提出“心外无理”“理外无事”说,言“心外无理,理外无事,即事以穷理,明明德第一功夫也”③。固然,勉斋、双峰、云峰等所提出的命题,与阳明之内在思想意涵当然不同。但如摆脱朱、王对立之视角,从朱子学绵延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此差异自可视为朱子学内部问题。基于朱子后学对朱子考据之学的批判,可视毛西河《四书改错》为朱子学发展之自然结果;基于朱子后学对朱子学义理之批判,可视阳明学为朱子后学从义理上对朱子批判继承所获得的最重要成果。这对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朱子后学与阳明学都是有意义的。套用怀特海评价柏拉图的一句名言,可以说南宋朱子以下儒家思想学术史,实皆可视为朱子学之注脚。这也可视为从批判继承角度论朱子学的三重批判,所见八百余年朱子学的自我转化及其超越所在。
一 《或问》之“辨析毫厘”与“明所以去取”
(一)《或问》:朱子思想独立之宣言
朱子毕生殚精竭虑于《四书》,完成了一个由《精义》、《或问》、《集注》构成的四书系列著作。在三者之中,《或问》是一具有特殊地位而相对被轻忽的著作,它起着承接《精义》与《集注》的枢纽作用,不仅是研读二者不可或缺的辅助之书,且具有独立价值,标志着朱子思想的初步成熟,显示了朱子与程门的某种“决裂”,所用设问问答的“或问体”亦成为影响后世经典诠释的一种重要题材。
《或问》为朱子多年研读《精义》的一次深度全面反思,二书关系极为紧密,如同靶与箭之关系,无《精义》之靶,则《或问》成无的之矢。①朱子给弟子示范了如何比较辨析《精义》各说,特别提到对各说皆应抱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不可先入为主,迷信程子权威,尽管在比较验证之后,通常是程子之说“多是”,门人之说“多非”,但在面对文本之前,不可先怀是此非彼之心。盖门人之说亦“多有好处”。朱子强调,最难辨“似是而非”之论,只有对诸家是非得失有了恰当认识,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看法,自身才能实有所得,“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②。
《或问》对《精义》的反思成为理解《集注》的必要参考。因《论孟或问》代表了中年朱子的思想,可作为考察朱子思想演变的重要桥梁。《集注》由于受到注释题材的限制,非常讲究文字精简,力求达到无一字闲的地步,《或问》则是论辩题材,抒写自由,论说详尽。如说《集注》是论题之结论,那么《或问》则是论题的论证,清晰展开对各说得失的取舍辨正,非常有助于学者理解《集注》。朱子甚为忧虑学人未能理解《集注》良苦用心,引杜甫诗“良工心独苦”自明心迹,言“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③。《或问》最充分流露了朱子的用心,可谓“吐心”之作。尽管朱子貌似对《或问》有“不须看”之言辞,但此仅是特就其与《集注》相较不可作为定论而言的,朱子并未否定该书价值。简言之,该书在继承程门说之同时,体现了一破一立的特点:破程门之瑕疵,立自家之新意。一则尽显朱子与程门在义理与方法上之差异,可窥朱子之独立与自信;二则可察朱子诠释《集注》下笔之良苦用心;三则可动观朱子思想异同之演变。古今学者对《或问》皆给予高度评价,真德秀《读书记》卷三十一赞为“辨析毫厘无微不显,真读书之龟鉴也。”《四库提要》就其与《集注》关系之分合两面论其价值,中其肯綮,“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于折衷众说之由;其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①。今有学者认为其价值犹在《集注》之上。
因《或问》批判锋芒太过锐利,朱子对其“轻诋前贤”所可能造成不良影响亦有所顾忌。《答吕子约》言,“但掎摭前贤,深负不韪之罪耳”②。真德秀《读书记》认为朱子不欲以该书示人,亦与担心其可能造成学风轻薄有关。“恐学者转而趋薄,故《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③此仅为《或问》之一面,然该书实为朱子辨误说、明正学的“不得已”之作,它实质上是对程门思想的清算之作,书中对程门的批评可谓体无完肤,划清了与程门淫于佛老、脱离文义之界限;以毫无隐晦的态度,锱铢必较之精神对程门之说逐字逐句加以辨析,在充分表达自身见解用心之时,显示了思想独立的应有自信。
(二)“辨析毫厘无微不显”
《或问》对诸家说的解析,体现了朱子特别重视解经方法和严辨儒佛的特点,显示了他与二程学派在解经理念、方法上的诸多差异④,朱子反思曾信奉达二十年之久的一味发挥己意,自作文字,不切文本的自我阐发型解经风格,强调回归意从文出、贴切本意、注重训诂的传统解经风格。他对借经典发挥一家之言的宋学解经风格之弊加以反思批判,而力图以注重文本之义、阐明圣贤原意的汉学解经风格矫正之,从而实现两种解释方法的统一。这个反思早在丁酉《或问》之前已开始,癸巳左右给南轩书信中已深切反思“自作一片文字”的风格,强调要回归汉儒经注合一,注仆经主的诠释态度,改变二程学派经仆注主、以经文强就己意的做法,提出虚心发明经意的原则。
批评“不叛圣贤而兼取老佛”的儒佛合流论,严辨掺杂佛老的思想,注重内部清理。朱子认为,佛老对儒学的侵蚀冲击,要害不在崇信佛老者,而在淫于佛老的儒家内部人士,尤在以佛老思想解释儒家经典,造成儒佛不分,以紫乱朱之混乱。朱子《杂学辨》将“阳儒阴释”的程门后学张九成斥责为“洪水猛兽”。《中庸章句序》公开指责程门“倍于师说,淫于佛老”。《或问》对亲学于二程诸高弟的儒佛不辨,以佛老解儒表达了极度失望、愤懑、痛惜、不解之情。“(游、杨)二公学于程氏之门,号称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晓也已。”①朱子以对屡空的解释为证,批评程门采用何晏老庄之解而不能辨之,亦不能辨别颜子不远复与佛教止念之别。“何晏始以为虚中受道,盖出老庄之说,非圣言本意也。诸先生亦或从之,误矣。……夫《易》所谓‘不远复’者,岂若佛氏觉速念止之云哉。”②朱子认为,以佛老解儒和以儒解佛老是同一事情的两面,相互影响渗透,导致儒与佛老愈加纠缠难辨。真正要做的是正本清源,切割二者联系,以儒解佛者将不同体系之思想强加扭捏,极为可笑。
空、无、忘、乐等与儒家境界相通之概念易于儒佛混流。儒家并非不讲无,只是此无须建立在“无私欲”之后自然呈现的无我之上,而非佛老刻意造作所追求者。“夫谓无私心而自无物我之间可也。若有意会物而又必于己焉,则是物我未忘。”③在带有本体意义的论题如性、理等上,朱子严别儒佛。一方面批评学者在突出理的形上意义之时,未能兼顾其与形下的贯通,导致“遗物”“外物”。如批评杨时理不可言即老佛之意。盖理即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本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中,非在日用彝伦之外别有一空悬之理存在。于“朝闻道”章强调儒道以五伦为实理,佛道则以五伦为幻妄绝灭之物,而以清净寂灭为终极追求,二者根本不同。另一方面又批评其说“遗理”,如批评游氏道本无名,感物而生,方有善名;因物而生,方有性名说乃佛老言,割裂了道、善、性的一体,而分裂为三物。
朱子判定程门流于佛老有以下情形:一是直接采用“老佛之正论”,引佛老之语,此为直接证据。如谢氏“引老聃知我者希,则我贵以为说者”。④二是化其语而师其意,常以“老佛之余论”“老佛之绪论”称之。如批评“游氏念念不忘之说善矣……则恐其未免于老佛之余也”①。此是由朱子判定而出,其说服力不如第一种。三是因语意不精、用语过度而“流于老佛之弊”。如指出“无隐”之解,“谢、杨氏为说……恐其过而流于老佛之意也”②。四是儒佛“一毫之间”者,其论与佛说相差几微,极其值得警惕。如指出程子“‘得此义理’一条尤为卓绝。然读者亦当深造以道而自得之,一毫之差,则入于老佛之门矣”③。五是着重从治学风格判定异端祸害,以正学风。异端之学表现为幽深、恍惚、高远、虚空、怪诞,措心文字之外,崇新奇尚简易。凡用语传达好高轻下、喜内忽外之意者,朱子多纳入于习于佛老,试图希望对此风气的扭转促使学风回归平实。如批评在格物的理解上存在此种倾向:“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而欲藏形匿景,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絶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言论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后可以得之,则是近世佛学诐淫邪遁之尤者。”④
“傍缘假借,最释经之大病”。此是朱子对程门解经弊病的根本概括。《或问》在揭示程门解经内容不妥之时,尤重反思解经方法。从解经方法上详尽揭示程门欠缺,清算程门不切文本,以己意解经的诠释风气,强调解经应切当文意,是《或问》批判的另一重心所在。批评程门“不附经文而直述己意”的做法完全无视经文本意,对此等说“虽美不取”。如《论语》谁毁谁誉章指出,“诸说之于此章,其意则皆美矣……类皆不附经文而直述己意,使人读之,但见义理粲然,曲有条贯而莫知其果欲置经文本意于何许也?……是以不得而取耳”⑤。比照一下伊川之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⑥。其摆脱文本束缚,直抒大意的说法,恰与朱子相对照。朱子对此有明确自觉,提出程子与己解经的差别在于置理于解语中还是经文内。朱子于学而章对程门解经得失及其弊病作了纲领式的阐述。将其症状总结为七类:文同旨异;意似实殊;以难释易;以有形无;亲者反疏;明者反暗;俱昧欲明,循环无决;取信于外,无真实见。此对各家解经弊病的批评,乃是朱子解经的实践之谈。如在对忠恕的理解上,程门常将《中庸》“忠恕违道不远”与《论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引用互证,两种不同含义的忠恕相互矛盾,导致混乱。
(三)文本、义理与实践兼具的取舍原则
《集注》用语“浑然犹经”,貌似多采成说,实则创新极多。朱子担心学者不能明其用意所在,故于《或问》阐明之。自述宁冒轻诋前贤之恶名,而决意于《或问》直析前辈各家得失,阐明自家取舍标准与用心。在表述上,《或问》皆是先立后破,先表达朱子见解,再剖析各说得失所在,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采用问答体这一问题导向鲜明的体裁,《或问》可谓一部问题诠释的经典之作。以皆自设问答的方式,精准解答之,典型的表达方式是:“或问……何也?”如《大学或问》开篇,依次问答“大人之学”,小子之学,小学与大学,以敬补小学,敬之为学之始终意义等论题,以1300余字的篇幅阐明《大学》三纲之理气、心性、工夫论含义,一气呵成,实可谓朱子哲学之提纲。二是进一步阐明《集注》观点,如关于程子改“亲”为“新”之根据,《大学》章句文本的调整及缘由等皆有充分说明,达到了解疑释惑的目的。三是详尽呈现朱子取舍之根据、理念,如指出《集注》“三年无改”章所引尹、游二说分指孝子之心与孝子之事,二说相须,不可或缺,道出《集注》用心所在,二说各自意义及其关系,“盖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说相须,为不可易”①。这种解释方法对朱子后学《四书》解释影响甚大。
《或问》辨析极为细致,贯穿了读音与字义,文义与本旨,文本与现实,提出了取舍的多项原则。一是文义优先于义理原则。某说虽发明道理甚美,若不契合文义,则不取。“又有谓施为施刑之施,……其意美矣,然‘施’字之说,则恐过深。”②文字训释不仅是为义理服务的小学工夫,而是决定义理理解的根基之学。《或问》充分体现了此点。如《中庸》“违道不远”的“违”非“离开”,而是距离之意,诸说不解文义而强加解说,扦格不通。“违道不远,如齐师违谷七里之违,非背而去之之谓。愚固已言之矣,诸说于此多所未合,则不察文义而强为之说之过也。”①他以“恕”字解为例,突出此字义解释偏差将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极大祸害。“恕”当正解为“如心”,而非苟且姑息之义,只可对人,不可于己,于己则当“严于自治”,批评范纯仁“恕己之心恕人”说虽心存厚道,为世所称,其实不合本义,后果严重。批评郅恽对光武帝的“恕己”解将引发逢君之恶、贼君之罪的恶劣后果,发出“一字之义不明而其祸乃至于此,可不谨哉”的感慨。②
与把握文义密切相关,常为前辈所疏忽的读音、句读、章句之学则为朱子所极重视,他视此为与前辈治学的重要区别。“诸说多误,盖由音读之学不明”。朱子指出程门解经之误多源于缺乏音读之学,认为“文字音读之学岂可忽哉”!《或问》特别注意从音韵的角度解释字义,将音义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如论证“望道而未之见”的“而”与“如”古字音义通用,诸家之误即在于无“文字音读之学”。指出“古今为说,迂回赘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于圣人之心,又不能有所发明,由不察乎此而已。然则文字音读之学岂可忽哉”。③《或问》关于音读解义有极精彩之例,如批评诸家对“无适无莫”的误解源于以“适”为“子适卫”之适故也。
《或问》进一步提出章句之学的重要,主张义理与章句融为一体,批评程门解经之误多源于“看不成句”的章句之差。言“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典型者如《中庸》道不远人章“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四句之断句,应在“子、臣、弟、友”后绝句,前辈如张九成等以“父、君、兄、之”断句既不通文意,亦不当文理,批评“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①。《或问》对程门句读点评甚多。或批评其新句读之新解不合文义。如《论语》4.5不以其道章,程氏主“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说;《论语》礼让为国章主“能以礼让”断句等。朱子有时亦反对各家采用旧注点读而自出新说。如批评各家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循旧注“心”后断句,读“从”为“纵”,音、读皆误,不合文义、本旨。然于“至大至刚以直”则宁用近世俗师之见,以“至大至刚”为断,批评程子循赵岐说以“直”断,体现了朱子当仁不让、公平正大的批判精神。朱子对《四书》章节之分颇有创获,如《论语》9.29“可与共学”章,9.30“唐棣之华”章自出新解,批评程门(范氏在外)因循汉儒合章之说有误,强调章句之差非无关紧要之误,它直接决定义理得失,提出章句之学不可忽视。“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说之弊,遂至于此。章句之学,其亦岂可忽哉。”②
本意(本旨)优先于义理原则。朱子认为,解经在平实释义的基础上,以阐明经文本意、挖掘圣贤本旨为目标。故是否准确阐发经文本旨,是决定《集注》取舍的根本原则。《或问》亦多次提出,某说虽美而不合本旨,故未取。如批评程子以“斯言可师”解“温故而知新”章,义理虽优美却无关文意,“程子恶夫气象之狭而为斯言,可师之说,美则美矣,其无乃非本文之意乎!”③
药病救失的工夫实践原则。朱子认为,经典诠释除切合文意之外,更要重视对学者践履工夫的指导和为学弊病的矫正,如能做到此点,虽有不合文意之处,亦当取之。此是从工夫实践角度确定的原则。《或问》特别注意提示此点,如指出吕氏不可使知之章“起机心”说虽非圣人本意,然确有切中时弊之益。“此非圣言之本意,然亦颇中近世学者之病矣。”④有时否定谢氏之说不合圣人气象之时,又赞其确有激发学者立志向学之处,故取之。“谢氏之说粗厉感奋,若不近圣贤气象者而吾独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①
逻辑一致原则。朱子据逻辑一致原则批评程门“语意倒置”之误。《或问》多处揭示程门在解说经典时,常颠倒语义,反映出逻辑次序混乱。程子即被多次点出此种“倒置”倾向。基于朱子自身理解,判定他们对文义、概念、工夫、效用等先后、本末关系处理有误,体现了重视逻辑分析的特点。如批评程子《论语》末章“第三说谓有诸己然后知言,则能格物穷理。语意倒置,亦不可晓”②。《孟子》尽心首章范氏颠倒穷理与尽心的关系,“至谓尽心所以穷理,则又倒置矣”③。
“本文气象”原则。“本文气象”指文本内在传达着与某种人格(含被诠释者与诠释者)相对应的一种精神气质,如典雅、雍容、洒脱、敬畏、粗暴、高远、平实等,体现了朱子经典诠释始终以塑造人的精神为指归的特点。朱子指出程门之解虽文意无误,但却不合乎文意所传达的人物精神气质,如《论语》“惟天为大”章杨氏说解释详密,但气象狭窄,不合本文气象,故《集注》不取,“杨氏说虽密,然气象反狭,与本文气象不相似也”④。朱子始终以圣贤气象为中心,如批评侯氏对夫子心怀重重顾虑之论说,完全不合圣人从容中道之气息,还指出解经文字所显示的气象恰是作为解释主体自身气象的映现,所谓“文如其人”也,学者诠释之差异偏颇,正是各自气象修养偏颇之显露。如《论语》“鲁人为长府”章谢氏“不必改”、杨氏“无意改”皆是各自性情气象所偏之体现。
公平正大原则。《或问》还从诠释态度批评程门之误,未能做到是非分明、公平正大、不虚美,不隐恶,其避嫌之论,远离圣贤公平正直的本来宗旨,体现了强烈的实事求是的反权威精神。《或问》批评“齐一变”章各家存在避嫌思想,不欲就太公、周公优劣加以比较,不欲正视鲁国以侯王而行天子之事的事实,正因有如此之避讳,故其说难免存在有意之私,而不合乎公平正大如实的圣人本旨。此直接影响诠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又有避嫌之病,益使其说不得不有所遗。如避周公、太公优劣之嫌……避鲁以侯国而行王道……此其说虽似美,然恐其不免于有意之私,而非圣言公平正实之本旨也。”①在“宰我问三年之丧”章、“犬马有养”章,《或问》皆批评诸家用心不公,多有维护宰我的文过之言,强调三年之丧“非有难明之理”,圣人明斥宰我为不仁而不应曲讳。“为已死之人,文不可赎之过。”②
二 “当日原多未定之论”
《论孟或问》作为处于壬辰《精义》与晚年《集注》之间反映朱子丁酉时期思想的作品,与二者皆有距离,尤其是与《集注》颇多差异,“多未定之论”,故其解不可据为定论,此似为其价值之限,然正因其与《集注》之差异,正可由此真实窥探朱子思想前后之演进,体现了朱子自我批判精神。即以简单的分章为例,《或问》受前人影响曾将雍也可使南面章分为两章,“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句单独一章。又如恭而无礼则劳章《集注》引吴氏说,主张“君子”以下单独分章,《或问》未提吴氏说,可知此意乃《或问》之后所增。义理方面,更是与《集注》差距颇多,存在“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的对反情况,即被《或问》所肯定者为《集注》所否定;被《或问》所否定者为《集注》所肯定。如大哉尧之为君章《或问》大赞程子解,但《集注》并未取,而是取尹说。如《或问》批评《精义》诸家“免而无耻”之“苟免”解不合文意,应是真心革面、不敢为非之意,但今《集注》正是“苟免刑罚”,又折回《或问》所否定的程门说。大体来说,朱子之见,在前《或问》时代,常采用程门说;《或问》时代,则通过扬弃程门而自出己说;《集注》时代,则是成熟的定见。《集注》对《论孟或问》之说,或删除或增补。如《或问》把学而章全章分为学之始、中、终,《集注》无此。《集注》第二章仁之解较《或问》“爱之理”补充了“心之德”说。鉴于《论孟或问》与《集注》存在的客观异同,使用该书时应对其得失和价值有一理性中道的认识,置其于具体语境中,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方能尽其底蕴,为我所用。
三 后学批评:“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
朱子学既形成于朱子对程门的批判和自我修正中,亦离不开门人后学对之展开的批判、传承与转化。黄榦及其开出的双峰学派、北山学派对朱子学展开了有力批判,成为后世朱子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从朱子学的批判接受史来看,明代阳明学的出现正是对朱子学批判修正的结果。清代朴学之兴起及对朱子的批评,并未越出朱子学之藩篱。概言之,朱子之后宋元明清之思想学术,实可谓“朱子学之注脚”,以下拟从批判性继承朱子学的角度论之。
朱子后学之义理批判。勉斋被朱子赞为“会看文字”,他弘扬乃师“取予在己”、入室操戈之精神,直接指出《集注》之不足。《复叶味道书》言:“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如在《论语》首章学而不愠与君子关系上,勉斋认同程子不愠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说,反对朱子君子才能不愠说,前者从工夫言,后者就成德言。指出《集注》“人而无信”章、“志道据德依仁”章之不足,修正《集注》“十五志学”章夫子所言进学次第乃虚说之观点,认为当是夫子为学境地之实说。勉斋有意彰显心的本体意义,提出“心便是性”“心便是仁”等心性为一思想,指出“点检身心”“求放心”“反身一念”等身心之学较之讲学穷理,更为根本,是道之传承与否的关键所在,显示出对“心学”的包容与工夫的内转。勉斋对朱子之批判,为弟子饶鲁所继承光大。如在《孟子》“仁人心也”章,师徒就心的属性提出与朱子不同看法。认为人心、放其心、求放心的三个“心”脉络相连,皆是指仁,指义理之心。《集注》视后者为知觉之心,与前文不相应。在《中庸》理解上,勉斋、双峰、草庐更体现了对朱子学继承突破的接力性,勉斋将《中庸》分为三十四章六大节,以道之体用为全书主线,戒惧慎独、知仁勇、诚为工夫论系统,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二,突出“诚”的地位。弟子饶双峰、双峰再传吴草庐对此作了新的继承阐发。在章的划分上,双峰与勉斋有所不同。草庐则干脆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四,并独立为一节,认为其主旨为“论治国之道在人以行其教”而非诚。双峰对朱子的批判、突破有明确的自觉,提出怀疑朱子格物诸说的原因在于朱子格物解过于阔大空洞而不切实际,“反之于身,自觉未有亲切要约受用处”。主张“诚意”章“乃《大学》一篇紧要处”。批评朱子忠恕之道解仅突出了忠恕的道体义而忽视了工夫义,犯了“主一而废一”的毛病。有学者由此提出朱、饶分开的观点:“后学当以朱子四书自作朱子四书看,饶氏四书自作饶氏四书看”。①元程钜夫《书何安子四书后》肯定了勉斋、双峰师徒对朱子的突破创新。“而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双峰之说,又有勉斋所未及者。”②
朱门后学之考证辨析。承继勉斋的北山学派着重对《集注》的缺失展开知识性的考证,突出了朱子学中考据的一面。金履祥《论语孟子集注考证》为其代表,《四库提要》认为该书于《集注》“事迹典故考订尤多……于朱子深为有功”。金履祥表白了对《集注》修正的忠臣态度和纠偏的客观事实。其言颇有意味:“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③史家多将刊于1337年的金氏之书视为考辨《集注》最早、最要之作,其实不然。如赵惪《四书笺义》纯以考证《集注》史实训诂为主,与《论孟集注》为同一类型著作,刊于1328年④。胡炳文(1253—1333年)之《四书通》刊于1329年,该书虽重义理,然于训诂亦多所校正。另元詹道传《四书纂笺》亦与《论孟集注》为同类型的纯训诂著作,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音、明义、考制、辨名等方面考察,该书广引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许谦《详说》、赵悳《四书笺义》,较三者晚出。然《四库提要》对此四书评价颇异,赞誉金履祥《考证》勇于批判之精神,却屡贬低其他三书对朱子之维护曲从。导致四书馆臣产生此种偏差的原因,与其不熟悉三书而带有先入之见有关。以下随举数例以较此四书对《集注》之批评:
据表可见,其一,对《集注》的考辨不始于金履祥,实始于朱子门人勉斋、辅广等,朱子门人并未因维护朱子而讳言其失,只是较含蓄而已。其二,朱子门人后学对《集注》缺失的考察基于其他朱子文献和朱子漫长的学术空间,常采取以晚年之朱攻早年之朱的方法,但在判定孰为早晚、何为朱子晚年定见时不无可商。如《诗集传》、《书集注》是否必晚于《集注》?金履祥的“《辨证》朱子晚笔,则《集注》未及改耳”说是否可信?盖《集注》朱子至死仍在修改,不好断定《集注》必在后。其三,诸书指出《集注》之“误”表现在引史实、古注、古书等,包括记忆之误,可见《集注》即便存在某些失误,亦是有根底之误,非朱子自造之误。其四,学者判定《集注》之“误”乃是基于各自理解,未必妥当。如金履祥站在王柏立场,认为《诗》并不可靠,针对《诗》之郑卫情况,提出“今之三百篇岂尽夫子之三百篇乎”①?
明代心学、清代朴学对朱子学之批判顺承。清儒对《集注》之辩证,虽引证范围更广、论证更精密,然其旨趣并未越出朱子《四书》之范围,不过是其中“小学”一面之发展而已。即以攻朱甚烈的毛奇龄《四书改错》为例,该书除夹杂争强好胜意气成分外,其余关于人名、地名等处,一则反驳立论非皆有定据,二则以朱子放弃之说以攻朱,了无新意。如以朱子已放弃的程子等采用的“传不习”旧注,攻击朱子新说。其对《集注》相关内容之驳正,大半朱子后学早已陆续开展之,毛氏所驳殊无可奇之处。如对朱子后学相关考辨作进一步搜寻,毛氏所论当基本包括。故该书不过是无意中将朱子后学对朱子考据批评之一面,集中罗列批评而已,所论实未能逸朱子学之藩篱。颇惊奇者,清人及近人予此书过誉之评,恐受《四库提要》误导,仅见朱子后学对朱子维护羽翼之一面,而未睹其批判修正之工作。②
阳明学常被视为朱子学之“反动”,然唐君毅、陈荣捷等先生则视为朱子学之修正。①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皆是在与朱子学长期的学习对话中展开。他自述曾对朱子之说“奉若神明”;刊刻《朱子晚年定论》以示并未偏离朱子,而是契合如一,本意并非“摘议晦庵”,其所不满者,乃是朱子心理为二所导致的外在格物之学、支离之学。其实阳明学之起点和终点大体同于朱子,千学万学,无非是“去人欲,存天理,成圣贤”。差别在实现“去欲存理”的理论基础和路径,阳明肯定心理即一,良知内在,天理内在,故工夫主内在推扩,逐步致良知于外;朱子则认为心理虽先天为一,理具于心,理不外心,但现实中因气禀私欲之遮蔽,心理为二,实现心理为一之境,须经由向外格物穷理,以光明心之体用。元儒评价饶双峰之《四书》不同于朱子者“十之八九”,阳明喜以“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来形容与朱子之别,不同于朱子者不至于“十之八九”,其思想之论域并未越出朱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更内在化、收缩化了,跳过了朱子学第一层的理、物存在问题,而始终着眼于心与理、心与物的意义显现问题,其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之“无”,并非存在之没有,而是于心之“未显”,可以说朱子注重存在“实现”,阳明关切意义“显现”。阳明特别重视理学之体用,以此处理良知与发用。在工夫问题上,阳明固不重主敬,但颇重克己(克治)、主静、立志,此与朱子亦一致。《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开启阳明学与朱子学内在沟通的可能性和连贯性,通过重新“发现朱子”,论证朱子“晚年之悔”来印证彼此的关联一体性。故自勉斋开始,朱子后学即逐步存在一“内转”倾向,此正如孔门后学之内转,至孟子而显其成;亦可说朱子学之内转,至阳明而终其成。阳明批朱的“话头”多有与朱子后学同声相应之处。如批评朱子之理由之一是无法自得其学于心,此与双峰反思朱子格物之说未有亲切受用极其相似。阳明对朱子之批评,多以“先儒”等语含蓄表达之,且始终保有尊重附和之意,认为己心实同朱子之心,称赞朱子解义有不可改易之处。“然吾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①勉斋学派对朱子批评之用语,较阳明甚至更为直白,如双峰言:“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于前人语意尤看得未尽如此。”②阳明阐发之问题,在朱子后学中不乏知音在。如对朱子《大学》改本之不满,重视诚意等;即如“心即理”“心外无理”之命题,元代朱子学者胡炳文亦提出“心外无理”“理外无事”说,言“心外无理,理外无事,即事以穷理,明明德第一功夫也”③。固然,勉斋、双峰、云峰等所提出的命题,与阳明之内在思想意涵当然不同。但如摆脱朱、王对立之视角,从朱子学绵延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此差异自可视为朱子学内部问题。基于朱子后学对朱子考据之学的批判,可视毛西河《四书改错》为朱子学发展之自然结果;基于朱子后学对朱子学义理之批判,可视阳明学为朱子后学从义理上对朱子批判继承所获得的最重要成果。这对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朱子后学与阳明学都是有意义的。套用怀特海评价柏拉图的一句名言,可以说南宋朱子以下儒家思想学术史,实皆可视为朱子学之注脚。这也可视为从批判继承角度论朱子学的三重批判,所见八百余年朱子学的自我转化及其超越所在。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