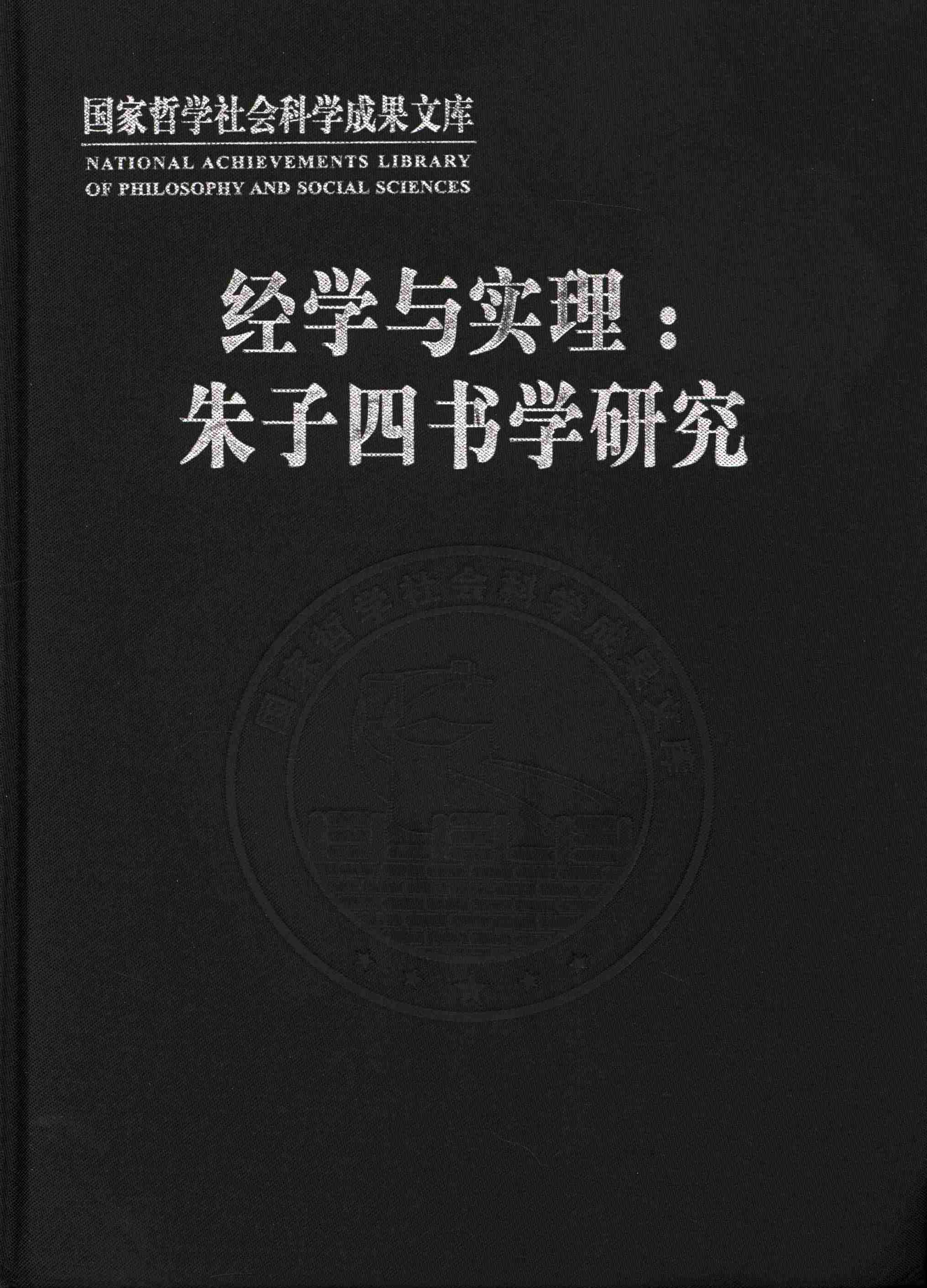二 “寓作于述”:易其文而改其意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828 |
| 颗粒名称: | 二 “寓作于述”:易其文而改其意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9 |
| 页码: | 349-357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上述《集注》对引文的处理,皆是不改变引文思想,对文本做出的规范、简要、典雅、精密处理,盖其说大体属于“无(大)病”者。但朱子还对认为“其说有病”者径直加以“增损改易”,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文之意,而表达了朱子之意。这种处理着眼点不是形式的规整,而是思想的改变。但因朱子采用局部修改而非全盘否定方式,且处理极为隐微,不经比对,实难察觉其用心之苦,故朱子曾发出“良工心独苦”之感慨。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上述《集注》对引文的处理,皆是不改变引文思想,对文本做出的规范、简要、典雅、精密处理,盖其说大体属于“无(大)病”者。但朱子还对认为“其说有病”者径直加以“增损改易”,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文之意,而表达了朱子之意。这种处理着眼点不是形式的规整,而是思想的改变。但因朱子采用局部修改而非全盘否定方式,且处理极为隐微,不经比对,实难察觉其用心之苦,故朱子曾发出“良工心独苦”之感慨。①
(一)概念改易
《集注》极重“字义”辨析,对引文个别概念的改易颇能显示朱子思想关注所在。涉及人与民、心与意、命与天命、道与道学、忘我与无我、知与行等。
人与民。“人”、“民”问题曾是《论语》研究的热点。二者含义本来有别,人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泛指,常与禽兽相对,“民”显然带有政治色彩,常与君(官)相对。《集注》于此有意区分之。如《论语集注》1.5引杨氏曰:“故爱(人)【民】必先于节用。”②《论语集注》8.9引伊川“若曰圣人不使(人)【民】知”。③以上易“人”为“民”,既与上下文保持对应,亦强调了民与官对的政治意义。《论语集注》2.19引伊川:“则(民)【人】心服。”则改“民”为“人”,突出普遍性。
心与意。心、意是朱子学中联系密切而又有差别的一组概念,朱子特别注意区分二者,如《论语集注》5.25引伊川说:“【未免】出于有(心)【意】也。”《孟子集注》3.2引程子说,“一为私(心)【意】所蔽”。《孟子集注》12.6引杨氏说,“即有伐桀之(意)【心】。”在朱子看来,意是“心之所发”,指更内在深沉的意识,它比心所指更小,“心大意小”,心是“身之所主”,然“意”的作用较“心”更直接,犹如船舵。三条所改皆有其用意。朱子有时亦把“心”改为“志”或“身”。如《孟子集注》14.34引赵氏,“(心舒意展)【志意舒展】”,突出了内在意识的状态。《孟子集注》14.25引张子说,“诚善于(心)【身】之谓信。”改“心”为“身”,盖经文是“有诸己之谓善”。命与天命。朱子认为命包括理命与气命两种,天命相当于义理之命。《论语集注》11.18改范氏“安命”为“安受天命”,强调当安于义理之命。《孟子集注》2.10改张子“命未绝”为“天命未绝”。明确了命的义理性与神圣性。《集注》还注意天命与天道的区别,如《中庸章句》二十六章改程子“天命”为“天道”,突出它的流行不已。道与道学。《论语集注》8.8改程子“道不明于天下”为“特以道学不明”,“道”与“道学”,把客观的“道”改为特指二程一派的“道学”,突出了道学在教化人才中的意义。又如《论语集注》9.26删谢氏“学道者”为“学者”,扩大了所指范围。忘我与无我。《论语集注》8.5以尹氏“非几于无我者不能也”替换所引谢氏“惟忘物我者能之”,体现了朱子严辨儒佛之别,忌惮“忘我”,接纳“无我”的态度。①欺与罔。《论语集注》14.33改杨氏“卒为小人所欺”的“欺”为“罔”。朱子指出欺、罔的区别在于“欺,诳之以理之所有。罔,昧之以理之所无。”故君子受小人合乎情理之欺骗是正常的,被“罔”则不应该。知与行。如《论语集注》11.24引范氏:“读而(求)【知】之……【然后能行】。”改“求”为“知”,与“行”构成“知—行”对应。
(二)逐字称等之精密改易
《集注》精心调整引文,使其合乎己意而更准确。如改“为”成“惟”。《论语集注》7.19改尹氏“非为勉人”的“为”为“惟”,语义有别。《论语集注》14.2改伊川“为仁者能之”的“为”成“惟”,所指由学习仁者变成仁者。《集注》之改有时出于纠偏。如《论语集注》6.2改伊川“三千子”为“七十子”,符合《史记》“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说。改“喜怒哀乐”的“乐”为“惧”,乃《礼记·礼运》说。改“觉者”为“学者”更合好学主题,改“养”为“往”,与下文“力行”一致。《论语集注》9.29改伊川“(人)【汉儒】(多)以反经合道为权”的“人”为“汉儒”,所指更精确。如《论语集注》7.10用舍行藏章改尹氏“(因其)所遇”的“因其”为“安于”,突出颜子境界。《集注》改写以示区分。《论语集注》4.15引程子说:“‘忠恕违道不远’,斯【乃】下学上达之义。”于“忠恕违道不远”前补“《中庸》所谓”四字,强调《中庸》“忠恕”义与此不同。《论语集注》8.8改程子“晓其义”为“知其说”,符合闾里童稚的认识程度。《论语集注》18.4改范氏“贤人”为“仁贤”。《孟子集注》12.7引赵氏解,“周文(王)”后特意补充“武王”,以求语义精备。《论语集注》5.8改胡氏“故(称)之如此”的“称”为“喻”,《论语集注》6.18改尹氏“(安)之”的“安”为“乐”,改后更契文意。《论语集注》5.23改伊川“而害则大”为“害直为大”,突出“直”的章旨,体现了朱子之创造。
《集注》调整使其语义轻重、感情色彩迥然有别而准确达意。如以“著”“叹”“谓”替换“讥”。《论语集注》3.2改伊川“著之”的“著”为“讥”,《论语集注》5.6改伊川“讥【伤】天下……而(谓)【讥】其不能”的“讥”为“伤”,“谓”为“讥”,鲜明准确传达了圣人的情感态度。又如《孟子集注》7.21改吕氏“(妄)得誉”的“妄”为“偶”,《论语集注》11.24引范氏“故夫子(以为)佞”的“以为”为“恶其”,皆改变了原文态度。又如《论语集注》11.23引尹氏说:“季氏(执国命)……可谓(备数之臣而已)。”改“执国命”为贬义的“专权僭窃”,改贬义“备数之臣而已(去除文字底色)”为中性的“具臣矣”。《孟子集注》9.7改《史记·殷本纪》贬义的“奸汤”为褒义之“行道以致君”。《孟子集注》9.6改赵岐说太丁“薨”的“薨”为“死”,更合其“未立”身份。《孟子集注》10.2改明道的“曲为之辞”为“句为之解”,改《论语集注》6.2伊川“(去)四凶”的“去”为“诛”,皆是对用语情感色彩的调整。
朱子增改虚词工夫非常了得,如补“专”“深”“反”“大”等字。《论语集注》1.2谢氏“【专】用心于内”前补“专”字,突出曾子工夫专一于内。《孟子集注》8.26改伊川“皆为”为“专为”,突出论智之章旨。《论语集注》17.20引明道“教”前补“深”,突出教诲用意之深。《论语集注》5.9删范氏“深责”的“深”,减弱责备语义。《论语集注》3.5引伊川说补“反”字,突出不满之意。《论语集注》9.26于谢氏说“病”前补“大”字,突出病之重。近义词替换亦显朱子用心深密。如《论语集注》4.12改伊川的“损”为“害”,程度更深。《论语集注》15.2改尹氏“先发其(问)”的“问”为“疑”。《论语集注》19.16改范氏的“唯”为“宁”。
改末句以显豁主题。汉唐《论》、《孟》注解,常以“章旨”形式概括本章大意,《集注》亦通过对引文末句调整来体现一章章旨。或解释原因,如《论语集注》3.10于所引谢氏说后补末句“孔子所以深叹也”。《论语集注》5.1于伊川说后补末句“盖厚于兄而薄于己也”。或点明主旨,如《论语集注》6.12改杨氏末句为“而其正大之情可见矣”,突出章旨是见“正大之情”。《论语集注》15.2引尹氏补“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判定章旨是境界论。或突出工夫教化意义。《孟子集注》12.16引尹说末补“无非教”三字,突出夫子对弟子无处不在的教化。《论语集注》2.19引谢说末句补“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突出了居敬穷理的工夫意义。
(三)因不满而增删改易
此类最鲜明体现了朱子改文的创作性。
概念有误。朱子认为所引之说对概念理解不当而改之。如认为杨氏对仁与心关系理解有误。《论语集注》14.7引谢氏说:“心不在焉,【则未免为】不仁也。(然未害为君子)。”①删末句“未害为君子”,不仁如何未害为君子?朱子还在“心”与“不仁”之间补“则未免为”,把心、仁的语义等同关系转化为条件关系。这是朱子一贯理解,因为心有多重属性,不可与作为理的仁直接等同。《或问》对此有详细讨论,既称赞谢说之善,又批评以心训仁不安,当补充“则”字,指出“未害为君子”说将造成学者功夫“自恕”的弊病,体现了朱子时刻着眼现实教化的立场。批评杨氏对“中”理解有误。《论语集注》3.16改杨氏“(容节)可以(习)”的“容节”为“中”,认为此方合乎论射之义,且与“力”相应。并与门人反复讨论之,指出“容节”非中非射。
沿袭旧说而误。如《论语集注》1.2改谢氏“(九流)皆出于圣人”的“九流”为“诸子之学”。盖“九流”非皆出自圣人。引文与章旨冲突。如《论语集注》15.19引范氏说,“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扬雄曰:‘名誉以崇之’。《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名者实之宾也。)”朱子认为章旨强调没世名不称的原因在于无实,范氏所引扬雄说则意在求名,不对。或强调手段—目的关系,违背尽己无为原则。批评范氏“所以”之说多如此,如《论语集注》18.7删范氏“所以扶世立教”说,《论语集注》15.41删范氏“所以教人”说,皆因与圣人自然无为说矛盾。用词不当而自相矛盾。如《论语集注》4.14引伊川:“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无所立)【而已矣】。”朱子以“而已矣”取代“故患身无所立”,盖其与“求其在己”相矛盾。《论语集注》10.11引谢氏:“马非不爱也……故捐情于此。”改“捐情”为“不暇问”,盖前者与“马非不爱也”相矛盾。《论语集注》6.20引伊川说:“人多(敬)【信】鬼神者,(只是)惑。”改“敬”为“信”,盖敬并非惑,信之方易惑。《论语集注》3.14引尹氏:“三代【之】礼(文),至周大备。”删“礼文”之“文”,“文”是周代文化特性,故与“三代”和“至周大备”相冲突。不合圣人境界。《论语集注》7.10删谢氏“(始可谓真知物我之分者也”,此不适合形容圣人。字义理解有误。《论语集注》7.13引范氏说删“夫子不意学乐至如是之美,故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盖为乐乃是指舜创作此乐,非指夫子学乐。或不合文义而删。如《论语集注》6.25删明道“未及知之也”说,一则不合学文守礼并重的章旨,二则过于突出“知”的地位。或不合礼制而误。删《论语集注》17.21“此为中人而言”,盖三年之丧乃天下通丧。兼取他说改之。《论语集注》9.26引谢氏说有“则几于小成者”,今以杨氏“则非所以进于日新也,故激而进之”改之,突出工夫教化意义。改为引注对立面。如《论语集注》20.1引孔安国《尚书》注认为“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改“少”为“多”,改变了孔氏之意。《论语集注》2.4改伊川“纵心”为“从心所欲不逾矩”,完全与伊川意异。“从心”而非“纵心”是朱子异于程门一大新解。朱子据文本及《经典释文》,指出读“纵”是近代习俗流传的误读。就义理言,“纵”亦不合乎圣天为一的境界。
(四)“良工心独苦”
朱子《论语集注》常有经过一番修改却回归旧说之情况,实不易察忽。如《论语集注》16.7引范氏说:“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异于人者,志气也。”按:《集注》曾删除“血气”的“血”和“志气”的“气”,变成“圣人同于人者,气也。异于人者,志也。”突出圣凡之别在于志、气,后觉不妥又改回原说。①又如《论语集注》14.33引杨氏说,“君子一于诚而已,(惟至诚可以前知)。”改“至诚前知”句为“然未有诚而不明者”,兼顾本章兼论诚、觉的主旨。《或问》详尽交代改定经过,本以吕氏“烛乎事几之先”替换之,后又觉其说偏于“明”,故终改诚而明说。②
朱子对《中庸》第十三章费隐章所引明道说的处理尤彰显了其用心之苦。
所引明道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节】,子思喫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③
此处删改看似简易,实则大费周章,关乎朱子对本章主旨理解的变化。朱子引程子说非关文义,而是帮助读者加深对义理的体会涵泳。朱子对“察”的理解历经反复,壬辰前将“察”释为“隐”,“盖察乎天地,终是说做‘隐’字不得”④。丁未《答王子合》7则明确提出“其察”是指道体流行、昭著显露,批评谢、杨的观察说。“‘其’者指道体而言,‘察’者昭著之义,言道体之流行发见,昭著如此也。谢、杨之意似皆以为观察之察。”①但“观察”更合《诗经》本意。朱子亦自觉此处之“察”与《诗经》“审察”本意已不同,是借以形容道体流行遍在,而与禅宗佛性无处不在说极似。鸢飞鱼跃言道体呈现而近乎佛学真如遍在说,但据儒家“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的定分说,则由此鸢必戾天,鱼必跃渊可把握儒佛之异。对此当从两面把握,故明道有“会得与不会得”的警示。“恰似禅家云‘青青绿竹,莫匪真如;粲粲黄花,无非般若’之语。”②
在明确了“察”为“昭著”而非“审察”义基础上,朱子对所引程子说尚有三次修改。
修改之一:道体流行无凝滞。认同程子说,为分别其“必有事”中立不倚。但此为旧说。《答周舜弼》已明确了“察”的昭著义,与“活泼泼”,认为皆言道体自然无滞,
程夫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与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泼泼地”。……程子之论无纤毫凝滞倚着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③
修改二,心之存主与天理流行。此为新说。己酉《答董叔重》八指出朱子今说改变此前把程子必有事、活泼泼皆解为道体流行之意的看法,而主张分别二者,“必有事”为心之存养,“活泼泼”才是天理流行。董铢批评友朋尚多坚持朱子旧说,亦客观指出今说并不合程子本意,而是朱子新解。朱子认可董铢理解,强调今说更自然简易,如能把握存养工夫,则自然洞见道体。
铢详先生旧说,盖谓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语,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活泼泼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无所滞碍之妙。”……而朋友间多主旧说。(朱子):“旧说固好,似涉安排。今说若见得破,则即此须臾之顷,此体便已洞然。”①
修改之三,删除“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句,放弃存主工夫说,不再牵引孟子说,而专一于道体流行的“活泼泼地”,但保留的“子思吃紧为人处”说,亦是对工夫的暗示,不过采取了引而不发的方式,如此既做到了工夫引导,同时又坚持了阐明本意而不多说的原则。
朱子如此慎重地反复修改本章,盖关乎儒佛虚实、理事之辨这一重要问题。本章主旨言道体流行,与佛学真如遍在观极相似,“易说得近禅”。如程子末句“会得与不会得”说乃是就儒佛之辨言,然朱子觉此毕竟偏离本意,故终删之。朱子从道体与工夫角度,立足儒佛虚实、理事之辨,强调了见道与行道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践道工夫与本体流行应是统一的,可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但若过于执着工夫,“太以事为重”,则恐固执不化,拘泥于事,见理不透。故在践道之时应保有“不着”之心,“勿正心”。朱子继承二程理之实有与空虚之分来分辨儒佛大旨。佛学虽亦标榜“不遗一事”,然其所行之“事”无关人伦之道,家国治理,故仍只是虚说。根源于其所谓理,乃是脱离具体事物的空理。但就实际修行而言,佛之理虽空而修行实,儒之理虽实却修行空,故儒者践行反不如佛门落实。此“实理之空”与“空理之实”导致儒学于世道人心之影响反不如佛学。故儒家在修养工夫的落实上应向佛教学习,否则无法体现儒学之高明。
以上对朱子《集注》“增损改易注文”这一重要而又罕见讨论情况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集注》这一经典“成品”的修改制作过程,显示了朱子思想早晚异同之变及与二程之差异,阐明了朱子自我修正的良苦用心,对准确把握《集注》注释,体会朱子思想的发展变化应有所裨益。《集注》最大特点是“浑然简易”,乃朱子耗毕生心血、经千锤百炼而铸成,实不可轻易读之。本文正印证了朱子之学“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直是下得工夫”的特点,而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的论断恰于《集注》前后修改中体现得最鲜明。钱穆亦曾指出《集注》之易简恰是朱子反复艰苦打磨用功之结果。“后人读朱子《论孟集注》,岂不爱其易简,然朱子当时所用功夫,则自不易简中来也。”并指出辨析朱子前后异同反复之说,乃是颇为重要而困难之工作。“辨程朱异说已不易。辨朱子一人之说之先后相异,而又必究其孰失孰得,则更不易也。”①
《集注》对所引二程学的“增损改易”,既有出于表达需要而做出文字调整的“述而不作”型,又有出于思想差异而做出意义修改的“寓作于述”型。二者显示了朱子对二程学派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程、朱异同。这种细微实则重要之差异,不经过仔细对照文本和深入分析,几乎不可能察觉出来。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诠释的理念、态度、方法,亦关乎经文意义的理解、取舍,还涉及工夫教化等立场。故本书所分析朱子于程门的“增损改易”,正可有效提醒我们在采用“程朱之学”这种一体性的表述时,亦应清晰意识到程朱之异的客观存在及对此后理学发展的影响。
《集注》通过“增损改易”程门之说等做法,在思想建构与诠释方法上形成了融经学与理学、考据与义理为一体的四书经学新范式。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课题颇具启示意义。如今日中国思想之创作,是否必定抛弃传统的经典注疏形式?从理学来看,朱子最典型的采用了注疏“旧瓶”承载理学“新酒”的形式,而心学一系则放弃之。现代中国哲学的开拓者则主要采用了以西学思想解释传统资料的方式,放弃了传统的经注形式。但同样引发了其诠释成果似乎不那么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质疑。而且文史领域对经典注释这一传统学术主要传承形式似仍有所延续,哲学领域则似不认同之。又如,《集注》是典型的寓创新于继承之作,那么在强调创新的当下,如何把握述、作之度,区分二者同一与差异的界限,从而延续经典的述和作?《集注》可谓是经学与哲学合一的经学哲学的典范,是对朱子“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学术理念的充分落实。但经学与哲学之关系,颇为复杂,《集注》对程门取舍的反复斟酌,其关键就在于朱子对二者关系的判定。故《集注》文本形成即内涵之诸多精微处,实值得深入挖掘,从而为激发当下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创作,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一)概念改易
《集注》极重“字义”辨析,对引文个别概念的改易颇能显示朱子思想关注所在。涉及人与民、心与意、命与天命、道与道学、忘我与无我、知与行等。
人与民。“人”、“民”问题曾是《论语》研究的热点。二者含义本来有别,人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泛指,常与禽兽相对,“民”显然带有政治色彩,常与君(官)相对。《集注》于此有意区分之。如《论语集注》1.5引杨氏曰:“故爱(人)【民】必先于节用。”②《论语集注》8.9引伊川“若曰圣人不使(人)【民】知”。③以上易“人”为“民”,既与上下文保持对应,亦强调了民与官对的政治意义。《论语集注》2.19引伊川:“则(民)【人】心服。”则改“民”为“人”,突出普遍性。
心与意。心、意是朱子学中联系密切而又有差别的一组概念,朱子特别注意区分二者,如《论语集注》5.25引伊川说:“【未免】出于有(心)【意】也。”《孟子集注》3.2引程子说,“一为私(心)【意】所蔽”。《孟子集注》12.6引杨氏说,“即有伐桀之(意)【心】。”在朱子看来,意是“心之所发”,指更内在深沉的意识,它比心所指更小,“心大意小”,心是“身之所主”,然“意”的作用较“心”更直接,犹如船舵。三条所改皆有其用意。朱子有时亦把“心”改为“志”或“身”。如《孟子集注》14.34引赵氏,“(心舒意展)【志意舒展】”,突出了内在意识的状态。《孟子集注》14.25引张子说,“诚善于(心)【身】之谓信。”改“心”为“身”,盖经文是“有诸己之谓善”。命与天命。朱子认为命包括理命与气命两种,天命相当于义理之命。《论语集注》11.18改范氏“安命”为“安受天命”,强调当安于义理之命。《孟子集注》2.10改张子“命未绝”为“天命未绝”。明确了命的义理性与神圣性。《集注》还注意天命与天道的区别,如《中庸章句》二十六章改程子“天命”为“天道”,突出它的流行不已。道与道学。《论语集注》8.8改程子“道不明于天下”为“特以道学不明”,“道”与“道学”,把客观的“道”改为特指二程一派的“道学”,突出了道学在教化人才中的意义。又如《论语集注》9.26删谢氏“学道者”为“学者”,扩大了所指范围。忘我与无我。《论语集注》8.5以尹氏“非几于无我者不能也”替换所引谢氏“惟忘物我者能之”,体现了朱子严辨儒佛之别,忌惮“忘我”,接纳“无我”的态度。①欺与罔。《论语集注》14.33改杨氏“卒为小人所欺”的“欺”为“罔”。朱子指出欺、罔的区别在于“欺,诳之以理之所有。罔,昧之以理之所无。”故君子受小人合乎情理之欺骗是正常的,被“罔”则不应该。知与行。如《论语集注》11.24引范氏:“读而(求)【知】之……【然后能行】。”改“求”为“知”,与“行”构成“知—行”对应。
(二)逐字称等之精密改易
《集注》精心调整引文,使其合乎己意而更准确。如改“为”成“惟”。《论语集注》7.19改尹氏“非为勉人”的“为”为“惟”,语义有别。《论语集注》14.2改伊川“为仁者能之”的“为”成“惟”,所指由学习仁者变成仁者。《集注》之改有时出于纠偏。如《论语集注》6.2改伊川“三千子”为“七十子”,符合《史记》“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说。改“喜怒哀乐”的“乐”为“惧”,乃《礼记·礼运》说。改“觉者”为“学者”更合好学主题,改“养”为“往”,与下文“力行”一致。《论语集注》9.29改伊川“(人)【汉儒】(多)以反经合道为权”的“人”为“汉儒”,所指更精确。如《论语集注》7.10用舍行藏章改尹氏“(因其)所遇”的“因其”为“安于”,突出颜子境界。《集注》改写以示区分。《论语集注》4.15引程子说:“‘忠恕违道不远’,斯【乃】下学上达之义。”于“忠恕违道不远”前补“《中庸》所谓”四字,强调《中庸》“忠恕”义与此不同。《论语集注》8.8改程子“晓其义”为“知其说”,符合闾里童稚的认识程度。《论语集注》18.4改范氏“贤人”为“仁贤”。《孟子集注》12.7引赵氏解,“周文(王)”后特意补充“武王”,以求语义精备。《论语集注》5.8改胡氏“故(称)之如此”的“称”为“喻”,《论语集注》6.18改尹氏“(安)之”的“安”为“乐”,改后更契文意。《论语集注》5.23改伊川“而害则大”为“害直为大”,突出“直”的章旨,体现了朱子之创造。
《集注》调整使其语义轻重、感情色彩迥然有别而准确达意。如以“著”“叹”“谓”替换“讥”。《论语集注》3.2改伊川“著之”的“著”为“讥”,《论语集注》5.6改伊川“讥【伤】天下……而(谓)【讥】其不能”的“讥”为“伤”,“谓”为“讥”,鲜明准确传达了圣人的情感态度。又如《孟子集注》7.21改吕氏“(妄)得誉”的“妄”为“偶”,《论语集注》11.24引范氏“故夫子(以为)佞”的“以为”为“恶其”,皆改变了原文态度。又如《论语集注》11.23引尹氏说:“季氏(执国命)……可谓(备数之臣而已)。”改“执国命”为贬义的“专权僭窃”,改贬义“备数之臣而已(去除文字底色)”为中性的“具臣矣”。《孟子集注》9.7改《史记·殷本纪》贬义的“奸汤”为褒义之“行道以致君”。《孟子集注》9.6改赵岐说太丁“薨”的“薨”为“死”,更合其“未立”身份。《孟子集注》10.2改明道的“曲为之辞”为“句为之解”,改《论语集注》6.2伊川“(去)四凶”的“去”为“诛”,皆是对用语情感色彩的调整。
朱子增改虚词工夫非常了得,如补“专”“深”“反”“大”等字。《论语集注》1.2谢氏“【专】用心于内”前补“专”字,突出曾子工夫专一于内。《孟子集注》8.26改伊川“皆为”为“专为”,突出论智之章旨。《论语集注》17.20引明道“教”前补“深”,突出教诲用意之深。《论语集注》5.9删范氏“深责”的“深”,减弱责备语义。《论语集注》3.5引伊川说补“反”字,突出不满之意。《论语集注》9.26于谢氏说“病”前补“大”字,突出病之重。近义词替换亦显朱子用心深密。如《论语集注》4.12改伊川的“损”为“害”,程度更深。《论语集注》15.2改尹氏“先发其(问)”的“问”为“疑”。《论语集注》19.16改范氏的“唯”为“宁”。
改末句以显豁主题。汉唐《论》、《孟》注解,常以“章旨”形式概括本章大意,《集注》亦通过对引文末句调整来体现一章章旨。或解释原因,如《论语集注》3.10于所引谢氏说后补末句“孔子所以深叹也”。《论语集注》5.1于伊川说后补末句“盖厚于兄而薄于己也”。或点明主旨,如《论语集注》6.12改杨氏末句为“而其正大之情可见矣”,突出章旨是见“正大之情”。《论语集注》15.2引尹氏补“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判定章旨是境界论。或突出工夫教化意义。《孟子集注》12.16引尹说末补“无非教”三字,突出夫子对弟子无处不在的教化。《论语集注》2.19引谢说末句补“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突出了居敬穷理的工夫意义。
(三)因不满而增删改易
此类最鲜明体现了朱子改文的创作性。
概念有误。朱子认为所引之说对概念理解不当而改之。如认为杨氏对仁与心关系理解有误。《论语集注》14.7引谢氏说:“心不在焉,【则未免为】不仁也。(然未害为君子)。”①删末句“未害为君子”,不仁如何未害为君子?朱子还在“心”与“不仁”之间补“则未免为”,把心、仁的语义等同关系转化为条件关系。这是朱子一贯理解,因为心有多重属性,不可与作为理的仁直接等同。《或问》对此有详细讨论,既称赞谢说之善,又批评以心训仁不安,当补充“则”字,指出“未害为君子”说将造成学者功夫“自恕”的弊病,体现了朱子时刻着眼现实教化的立场。批评杨氏对“中”理解有误。《论语集注》3.16改杨氏“(容节)可以(习)”的“容节”为“中”,认为此方合乎论射之义,且与“力”相应。并与门人反复讨论之,指出“容节”非中非射。
沿袭旧说而误。如《论语集注》1.2改谢氏“(九流)皆出于圣人”的“九流”为“诸子之学”。盖“九流”非皆出自圣人。引文与章旨冲突。如《论语集注》15.19引范氏说,“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扬雄曰:‘名誉以崇之’。《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名者实之宾也。)”朱子认为章旨强调没世名不称的原因在于无实,范氏所引扬雄说则意在求名,不对。或强调手段—目的关系,违背尽己无为原则。批评范氏“所以”之说多如此,如《论语集注》18.7删范氏“所以扶世立教”说,《论语集注》15.41删范氏“所以教人”说,皆因与圣人自然无为说矛盾。用词不当而自相矛盾。如《论语集注》4.14引伊川:“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无所立)【而已矣】。”朱子以“而已矣”取代“故患身无所立”,盖其与“求其在己”相矛盾。《论语集注》10.11引谢氏:“马非不爱也……故捐情于此。”改“捐情”为“不暇问”,盖前者与“马非不爱也”相矛盾。《论语集注》6.20引伊川说:“人多(敬)【信】鬼神者,(只是)惑。”改“敬”为“信”,盖敬并非惑,信之方易惑。《论语集注》3.14引尹氏:“三代【之】礼(文),至周大备。”删“礼文”之“文”,“文”是周代文化特性,故与“三代”和“至周大备”相冲突。不合圣人境界。《论语集注》7.10删谢氏“(始可谓真知物我之分者也”,此不适合形容圣人。字义理解有误。《论语集注》7.13引范氏说删“夫子不意学乐至如是之美,故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盖为乐乃是指舜创作此乐,非指夫子学乐。或不合文义而删。如《论语集注》6.25删明道“未及知之也”说,一则不合学文守礼并重的章旨,二则过于突出“知”的地位。或不合礼制而误。删《论语集注》17.21“此为中人而言”,盖三年之丧乃天下通丧。兼取他说改之。《论语集注》9.26引谢氏说有“则几于小成者”,今以杨氏“则非所以进于日新也,故激而进之”改之,突出工夫教化意义。改为引注对立面。如《论语集注》20.1引孔安国《尚书》注认为“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改“少”为“多”,改变了孔氏之意。《论语集注》2.4改伊川“纵心”为“从心所欲不逾矩”,完全与伊川意异。“从心”而非“纵心”是朱子异于程门一大新解。朱子据文本及《经典释文》,指出读“纵”是近代习俗流传的误读。就义理言,“纵”亦不合乎圣天为一的境界。
(四)“良工心独苦”
朱子《论语集注》常有经过一番修改却回归旧说之情况,实不易察忽。如《论语集注》16.7引范氏说:“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异于人者,志气也。”按:《集注》曾删除“血气”的“血”和“志气”的“气”,变成“圣人同于人者,气也。异于人者,志也。”突出圣凡之别在于志、气,后觉不妥又改回原说。①又如《论语集注》14.33引杨氏说,“君子一于诚而已,(惟至诚可以前知)。”改“至诚前知”句为“然未有诚而不明者”,兼顾本章兼论诚、觉的主旨。《或问》详尽交代改定经过,本以吕氏“烛乎事几之先”替换之,后又觉其说偏于“明”,故终改诚而明说。②
朱子对《中庸》第十三章费隐章所引明道说的处理尤彰显了其用心之苦。
所引明道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节】,子思喫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③
此处删改看似简易,实则大费周章,关乎朱子对本章主旨理解的变化。朱子引程子说非关文义,而是帮助读者加深对义理的体会涵泳。朱子对“察”的理解历经反复,壬辰前将“察”释为“隐”,“盖察乎天地,终是说做‘隐’字不得”④。丁未《答王子合》7则明确提出“其察”是指道体流行、昭著显露,批评谢、杨的观察说。“‘其’者指道体而言,‘察’者昭著之义,言道体之流行发见,昭著如此也。谢、杨之意似皆以为观察之察。”①但“观察”更合《诗经》本意。朱子亦自觉此处之“察”与《诗经》“审察”本意已不同,是借以形容道体流行遍在,而与禅宗佛性无处不在说极似。鸢飞鱼跃言道体呈现而近乎佛学真如遍在说,但据儒家“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的定分说,则由此鸢必戾天,鱼必跃渊可把握儒佛之异。对此当从两面把握,故明道有“会得与不会得”的警示。“恰似禅家云‘青青绿竹,莫匪真如;粲粲黄花,无非般若’之语。”②
在明确了“察”为“昭著”而非“审察”义基础上,朱子对所引程子说尚有三次修改。
修改之一:道体流行无凝滞。认同程子说,为分别其“必有事”中立不倚。但此为旧说。《答周舜弼》已明确了“察”的昭著义,与“活泼泼”,认为皆言道体自然无滞,
程夫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与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泼泼地”。……程子之论无纤毫凝滞倚着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③
修改二,心之存主与天理流行。此为新说。己酉《答董叔重》八指出朱子今说改变此前把程子必有事、活泼泼皆解为道体流行之意的看法,而主张分别二者,“必有事”为心之存养,“活泼泼”才是天理流行。董铢批评友朋尚多坚持朱子旧说,亦客观指出今说并不合程子本意,而是朱子新解。朱子认可董铢理解,强调今说更自然简易,如能把握存养工夫,则自然洞见道体。
铢详先生旧说,盖谓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语,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活泼泼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无所滞碍之妙。”……而朋友间多主旧说。(朱子):“旧说固好,似涉安排。今说若见得破,则即此须臾之顷,此体便已洞然。”①
修改之三,删除“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句,放弃存主工夫说,不再牵引孟子说,而专一于道体流行的“活泼泼地”,但保留的“子思吃紧为人处”说,亦是对工夫的暗示,不过采取了引而不发的方式,如此既做到了工夫引导,同时又坚持了阐明本意而不多说的原则。
朱子如此慎重地反复修改本章,盖关乎儒佛虚实、理事之辨这一重要问题。本章主旨言道体流行,与佛学真如遍在观极相似,“易说得近禅”。如程子末句“会得与不会得”说乃是就儒佛之辨言,然朱子觉此毕竟偏离本意,故终删之。朱子从道体与工夫角度,立足儒佛虚实、理事之辨,强调了见道与行道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践道工夫与本体流行应是统一的,可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但若过于执着工夫,“太以事为重”,则恐固执不化,拘泥于事,见理不透。故在践道之时应保有“不着”之心,“勿正心”。朱子继承二程理之实有与空虚之分来分辨儒佛大旨。佛学虽亦标榜“不遗一事”,然其所行之“事”无关人伦之道,家国治理,故仍只是虚说。根源于其所谓理,乃是脱离具体事物的空理。但就实际修行而言,佛之理虽空而修行实,儒之理虽实却修行空,故儒者践行反不如佛门落实。此“实理之空”与“空理之实”导致儒学于世道人心之影响反不如佛学。故儒家在修养工夫的落实上应向佛教学习,否则无法体现儒学之高明。
以上对朱子《集注》“增损改易注文”这一重要而又罕见讨论情况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集注》这一经典“成品”的修改制作过程,显示了朱子思想早晚异同之变及与二程之差异,阐明了朱子自我修正的良苦用心,对准确把握《集注》注释,体会朱子思想的发展变化应有所裨益。《集注》最大特点是“浑然简易”,乃朱子耗毕生心血、经千锤百炼而铸成,实不可轻易读之。本文正印证了朱子之学“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直是下得工夫”的特点,而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的论断恰于《集注》前后修改中体现得最鲜明。钱穆亦曾指出《集注》之易简恰是朱子反复艰苦打磨用功之结果。“后人读朱子《论孟集注》,岂不爱其易简,然朱子当时所用功夫,则自不易简中来也。”并指出辨析朱子前后异同反复之说,乃是颇为重要而困难之工作。“辨程朱异说已不易。辨朱子一人之说之先后相异,而又必究其孰失孰得,则更不易也。”①
《集注》对所引二程学的“增损改易”,既有出于表达需要而做出文字调整的“述而不作”型,又有出于思想差异而做出意义修改的“寓作于述”型。二者显示了朱子对二程学派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程、朱异同。这种细微实则重要之差异,不经过仔细对照文本和深入分析,几乎不可能察觉出来。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诠释的理念、态度、方法,亦关乎经文意义的理解、取舍,还涉及工夫教化等立场。故本书所分析朱子于程门的“增损改易”,正可有效提醒我们在采用“程朱之学”这种一体性的表述时,亦应清晰意识到程朱之异的客观存在及对此后理学发展的影响。
《集注》通过“增损改易”程门之说等做法,在思想建构与诠释方法上形成了融经学与理学、考据与义理为一体的四书经学新范式。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课题颇具启示意义。如今日中国思想之创作,是否必定抛弃传统的经典注疏形式?从理学来看,朱子最典型的采用了注疏“旧瓶”承载理学“新酒”的形式,而心学一系则放弃之。现代中国哲学的开拓者则主要采用了以西学思想解释传统资料的方式,放弃了传统的经注形式。但同样引发了其诠释成果似乎不那么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质疑。而且文史领域对经典注释这一传统学术主要传承形式似仍有所延续,哲学领域则似不认同之。又如,《集注》是典型的寓创新于继承之作,那么在强调创新的当下,如何把握述、作之度,区分二者同一与差异的界限,从而延续经典的述和作?《集注》可谓是经学与哲学合一的经学哲学的典范,是对朱子“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学术理念的充分落实。但经学与哲学之关系,颇为复杂,《集注》对程门取舍的反复斟酌,其关键就在于朱子对二者关系的判定。故《集注》文本形成即内涵之诸多精微处,实值得深入挖掘,从而为激发当下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创作,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