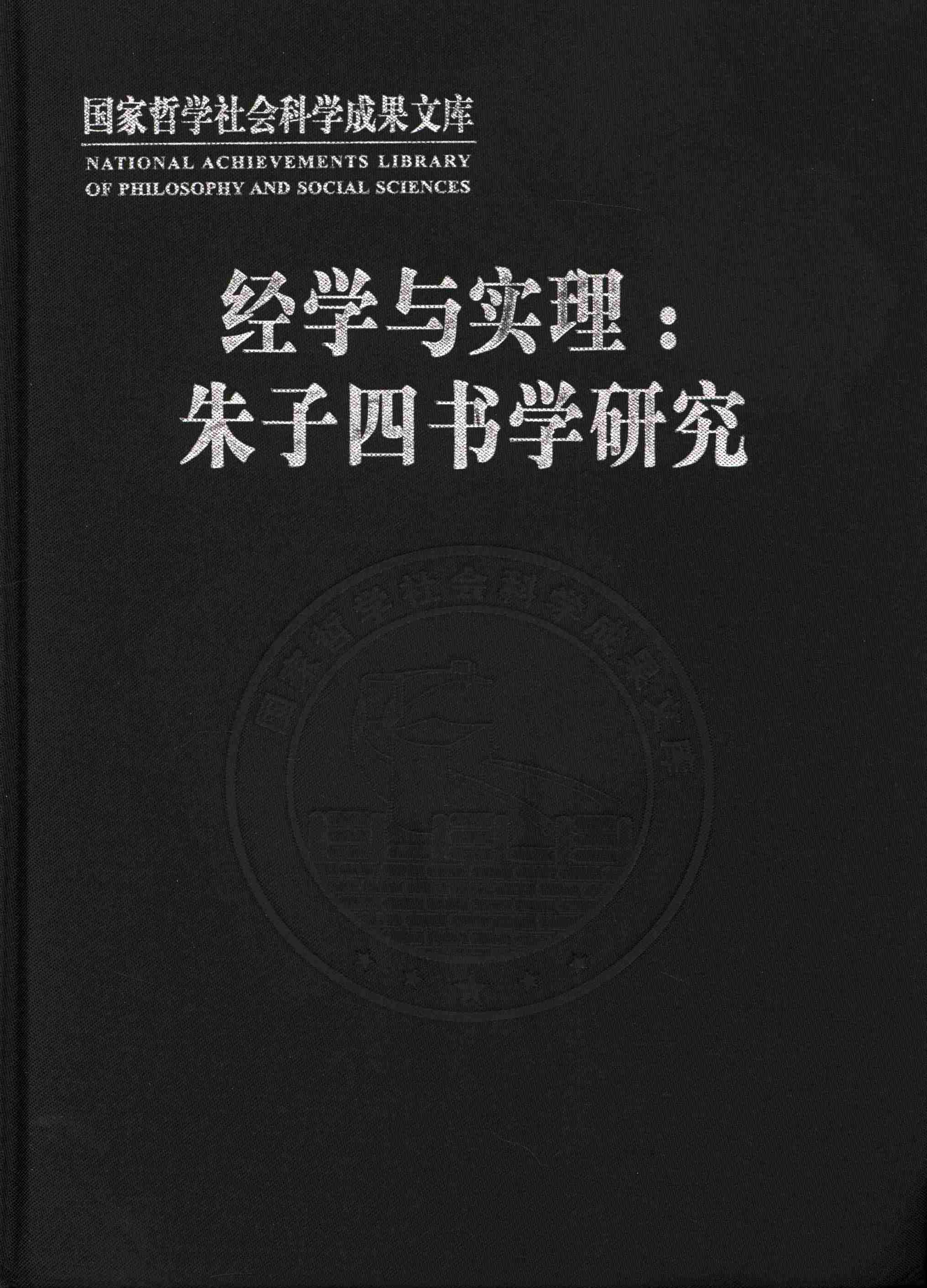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二节 “察病救失”:孔门弟子之评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810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察病救失”:孔门弟子之评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311-322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居于理学立场,根据针砭学弊,“察病救失”的工夫论诠释原则,在《论语集注》中对孔门自颜、曾以下多给予否定性评价,这一《论语》诠释史上的重大变化,颠覆了一贯仰视孔门弟子的看法,形成了新的孔门弟子观念,展现了理学的成就与自信,得到了理学学者的广泛认可,但也遭到后世汉学者的反驳。尤其是清代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专门辟有“贬抑圣门”两卷,举出朱子否定孔门弟子四十七条逐一驳斥,认为“若《集注》贬抑,节节有之,名为补救而实所以显正夫子之失。”①虽毛氏对朱子攻击多牵强附会,但其批判确揭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朱子是否在贬抑圣门?其“察病救失”出于何等立场?采用了什么方法?取得了怎样效果?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把握朱子的理学思想与经典诠释,认识孔门弟子在理学时代形象的颠覆皆具有启发意义。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孔门弟子 |
内容
朱子居于理学立场,根据针砭学弊,“察病救失”的工夫论诠释原则,在《论语集注》中对孔门自颜、曾以下多给予否定性评价,这一《论语》诠释史上的重大变化,颠覆了一贯仰视孔门弟子的看法,形成了新的孔门弟子观念,展现了理学的成就与自信,得到了理学学者的广泛认可,但也遭到后世汉学者的反驳。尤其是清代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专门辟有“贬抑圣门”两卷,举出朱子否定孔门弟子四十七条逐一驳斥,认为“若《集注》贬抑,节节有之,名为补救而实所以显正夫子之失。”①虽毛氏对朱子攻击多牵强附会,但其批判确揭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朱子是否在贬抑圣门?其“察病救失”出于何等立场?采用了什么方法?取得了怎样效果?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把握朱子的理学思想与经典诠释,认识孔门弟子在理学时代形象的颠覆皆具有启发意义。
一 “造道之极致”
儒家向来注重对人格成就层次的品评判定,认为学者在为学境地上存在先后高低之别本是成道进程中应有之事实,能否正视自身为学得失,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自知之明,亦是为学进步之关键。故孔子很注意点评弟子为学得失与境地高下,以促其反省进步。孟子亦注重区别人格层次,通过圣圣之间的相较,彰显了孔子“大成之圣”的崇高地位,确定了“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的为学目标,而且提出了节次分明的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之说。理学开创者周、程继承此风并发扬之,他们辨析孔门弟子高下得失,将其划分为两大层次:闻道传道的颜子、曾子与其他未能传道弟子,特别凸显颜子的独特性,树起“学颜子之所学”的理学旗帜,通过辨析颜、孟高下之分,突出颜子“学以至圣”的品质,以建立纯正的为学之方。同时抬尊曾子,确立了他在儒家道统中传道地位。故朱子在《集注》中批评孔门弟子的做法,乃是继承理学家风,《集注》批评孔门弟子的说法多数引自前辈学者即是明证。事实上,在疑经解经风潮涌起的宋代,对孔门弟子高下扬抑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宋儒多倡导以义理解经之模式,主张经典诠释应从个人理性出发进行批判性阐发,以达到针砭工夫弊病的效果。如《集注》对樊迟多有微词,其实北宋苏轼早有此说。朱子在《论语或问》中曾引用并称赞苏氏说:“苏氏曰:孔子之言,常中弟子之过,樊迟问崇德,孔子答以‘先事后得’,则须也有苟得之意也欤?其问知也,‘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教之以专修人事而不求侥幸之福也。其问仁也,曰‘仁者先难而后获’,教之以修德进业而不贪无故之利也。”①
除受前辈影响外,朱子对孔门弟子的批判诠释主要出于自身理学思想。毛氏认为朱子对孔门弟子横加挑剔,导致“圣门无完行”,制造了“圣门冤狱”。殊不知当朱子以至善、中庸,“造道之极致”作为评判孔门弟子的尺度时,“圣门无完行”之义自可成立。朱子对《大学》“至善”这一概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认为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也”,在三纲八目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明德、亲民皆须止于至善,“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②。从格致诚正修身的内圣一直通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皆须达于至善,有一处未到,即不能算至善。人在道德的修炼中,始终行走在追求至善的道路上。中庸是朱子极其看重的另一概念,朱子指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①中庸就是要求在日用常行中实现事事合宜,此是极难之事,乃儒家至德所在。当朱子以“造道之极致”的至善、中庸来衡量孔门高弟时,故难免见其到处是“病”了。如学而篇“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章注,朱子指出孔子和子贡境界高下在其问答中已彰显无遗,带给学者的教训是不能安于小成,固步自封,而应当追寻道德的最高境界。“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②若就孔门高弟所达境地成就,与常人相较,自然难以企及,令人景仰了。但若从“造道之极致”角度来看,不能不承认孔门高弟仍有不足。
人之为学自然存在境界高下,孔门弟子亦不能外。朱子对孔门弟子境界从上下、平行、前后三个层次进行高下浅深的比较,其意是为了树立为学典范。首先,通过夫子与弟子上下层次间的比较,揭示弟子和孔子境界上的差异,既突出了圣人境界的高远,同时又给学者以警示,促其谦虚反省。如子路篇“仲弓为季氏宰”章注,朱子引程子说指出仲弓心量与圣人存在大小之别,暗示仲弓还须在此方面努力用功。“程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③其次,朱子更重视弟子之间的平行比较,以见其高下,此意也是顺《论语》中夫子对弟子点评而发。夫子评价弟子,是为了检查他们的修行程度,以发现问题进行纠正。基于确定学习典范的考虑,朱子认为孔门弟子境界大致可分为三等,此等级决定了《集注》的诠释视角。颜子、曾子属于闻道一级,对儒家道统传扬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了圣贤之学,《集注》对之极力推崇褒扬。如《学而》篇“吾日三省”章,《集注》引谢氏说指出,孔门诸子虽然皆与闻夫子之道,除颜子外真正能够传承夫子之道者唯有曾子,其他诸子有所得亦有所失,夫子之学在其他学派中流传愈远,流弊愈多,已经失去了夫子学的真谛。只有曾子获得真传,并毫无流弊地传给子思、孟子,保持维护了儒家道统的延续,在孔门中居功甚伟,故此对其言语当用心体会。并强调曾子学圣人无弊,对于其流传下来的言语论说当倍加珍惜,可见对曾子之重视。“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①此说与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确定“曾氏独得其传”的传道地位一致。子贡、子路、子夏、子游、子张等学有所成的弟子为次一级,他们为学有得有失,得多于失,《集注》对之褒贬相间,但他们之间也存在高下之分。其中,子贡、闵子骞境界仅次于颜、曾,要高于其他弟子。《集注》中对子贡批评之辞不少,最终还是肯定子贡仅次颜、曾而终闻夫子之道。《卫灵公》篇“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章注朱子特加按语指出,据《论语》所载夫子与子贡对话之内容和频率,颜、曾以下,当属子贡。朱子之辞虽为推测,要之亦有一定道理。“愚按: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②闵子骞境界与颜子相似,要高于子张。《为政》篇“子张学干禄”章注引程子说:“子张学干禄,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为利禄动,若颜、闵则无此问矣。”③以樊迟、司马牛为代表的弟子则属于更下一级,他们为学失多于得,《集注》对之多加贬斥,以为后学者鉴。再次,朱子在诠释中非常注重学者境界的前后变化,以动态观看待孔门弟子为学变化。他认为学者境界总是在不断提升变化中,修道成德变化气质本为一生命历练的动态过程。这就向后学表明,孔门弟子高明境界亦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对成圣成贤之学应当保有信心。朱子根据夫子与弟子的问答,断定处于何种阶段,对颜子、子贡、樊迟,子路等皆有判定,如《阳货》篇“君子尚勇乎”章注引胡氏说指出此问答反映出子路初学时状态:“疑此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也。”④《先进》篇“回也其庶乎”注引程子说同样指出该问答是子贡年少问学时事,后来已经得闻性与天道之学,自然不会有此问题,“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①。
二 “圣门冤狱”
朱子以“造道之极致”为镜子,照出孔门弟子存在境界高下浅深之别,更照出孔门弟子为学病痛。从为后学树立正确为学之方的角度考虑,朱子非常尖锐苛刻地揭露了这些病痛,用毛氏的话说,简直是制造“圣门冤狱”。真相如何呢?我们具体探究一下所谓“圣门冤狱”。
首先,朱子对孔门弟子并非一味贬斥,而是抱褒贬分明各得其所的态度。尽管在“造道之极致”的标准下孔门弟子显出不足,朱子仍充分赞扬了孔门弟子各自所获得的成就,褒其已成足为后学者师,贬其不足引为后学者鉴。孔门弟子虽未得夫子道全,然得夫子之道之一偏一体,其成就足以为后世之师,远非后人所能达到。如对曾点高明气象、子贡颖悟才质、子路信勇卓著,子夏笃实工夫皆极其肯定。即以对子路评价为例,朱子多次赞其豪迈刚勇,重信轻财,气象高远,学者应以之为师。如《先进》篇“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章注强调子路境界已达到正大高明地步,只是在精微之处有所不足而已,堪为学者百世师而不可轻视之,“言子路之学,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②。
其次,朱子从理学概念出发,将孔门弟子诠释为理学概念的化身,把他们与理学概念紧密相连并类型化之,朱子对孔门弟子的评论其实表达的是对理学概念的认识,目的是增进学者对理学概念和为学境界的理解,以为己鉴。客观而论,朱子评论孔门弟子,除对颜、曾倍加维护赞颂外,于其他弟子似乎更侧重指出过失,其目的是阐述他“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的为学理念。正是以“求造道之极致”为标准,故《集注》详加挑剔孔门弟子病痛,几乎达到了吹毛求疵地步。然条目挑剔虽多,其义多为重复。在朱子看来,孔门弟子之病痛皆可以类型论之,如子路之信勇而乏义理,子夏之严谨笃厚而气度狭隘,子张之意态高远而无诚实,子贡之聪明博学而务外。朱子对于他们的批评,皆以此类型套而论之,简直成了数学公式。即以子路为例,批评他的用语大致如下:
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为政》篇“由诲女知之乎”章)
程子曰:“故夫子美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公冶长》篇“乘桴浮于海”章)
吴氏曰:“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子路》篇“子路问政”章)
胡氏曰:“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子路》篇“卫君待子而为政”章)
尹氏曰:“义以为尚,则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阳货》篇“君子尚勇乎”章)
范氏曰:“子路勇于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学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阳货》篇“女闻六言六蔽”章)
显然,朱子对子路的评价总体为具信勇而乏义理,如此诠释的效果是把诠释对象子路固定为轻财守信意气用事的侠客形象①,此一类型化形象又套用涉及于子路的所有方面。《集注》关于子张、子夏等弟子的评论皆是如此。不难看出,朱子实际是在有意以一套理学概念诠释孔门弟子,使孔门弟子成为理学概念的符号和代言人。这种概念化、符号化、抽象脸谱化的诠释凸显了孔门弟子气质中真实本质一面,使学者容易把握其特质,如子路成为勇信的符号化身,子张是高远阔大的化身,子夏是谨慎笃厚的化身。该诠释的主观色彩非常明显,朱子在进入文本之前,对诠释对象已有了很强的诠释成见,文本不过是强化、印证了他的成见而已。朱子这种先入为主,以人物特质、理学范畴为中心的诠释手法得到《论语》中因材施教法的支撑。该诠释法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直具有人物性格脸谱化的传统,典型者如《三国演义》中关羽塑造为“忠义”的化身,曹操为“奸诈”的化身,近如对革命英雄人物的塑造,“高干大”形象的出现等,人物皆成为叙述者的理念符号。在朱子诠释中,孔门弟子成为表达其理学概念的符号,孔门弟子所体现的优缺点皆具有了普遍意义,朱子通过扬其优长,揭其缺失这种褒贬分明的揭示对照,达到了给学者树立正确为学之方的目的。
再次,朱子批评孔门弟子,是要求学者“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①基于这一原则,朱子认为孔门师生之交流多具有指点弟子病痛的意味,其言谈“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集注》评论孔子门人时数十次使用“病”这个词,强调成圣之学首要工夫就是反省自身气质工夫的真实病痛。学者先天资质禀赋总是有所缺失,应由后天工夫来消除弊病以变化气质。首要工夫是发现病痛,但人自知甚难,其病痛往往需经他人指点揭示。朱子认为孔子与弟子言谈,就是根据诸弟子资质、工夫、境界,把脉开方,对症下药,其药因人病痛而异,但皆符合“切己”这一原则,如此方能收到效果。如子张有“过高之病”,开出药方是“笃实”。《颜渊》篇“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章注引尹氏说指出,“子张之学,病在乎不务实。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②子贡也有类似毛病,夫子告之近处下手之方。雍也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章注引吕氏说,“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③在“司马牛问仁”章,朱子特意揭示了孔门之教“切己”特点。他指出,因司马牛病痛与子贡等人不同,故当其问仁时,夫子并不是随便给予答复,而是根据其为学气质病痛,针对性开出适合他的“言忍”这一处方。夫子对学生虽然指点不一,但皆是为帮助弟子认识自身病痛所在,找到修身进德的途径要领,学者对此应深思自考。《颜渊》篇“司马牛问仁”章注,“愚谓牛之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为仁之大概语之,则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终无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读者其致思焉。”①再如对孔子称赞樊迟“善哉问”,朱子注为,“善其切于为己。”皆是点出切己在为学中的重要意义。在《先进》篇“柴愚参鲁师辟由喭”章,朱子引杨时说指出夫子指点四者气质偏颇处,希望他们知道各自病痛,从而针对性地下手用工以克服之,“四者性之偏,语之使知自励也。”②朱子这一诠释定式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要求学者以“察切己之实病”的方法作为现实工夫指导,在学习《论语》过程中,应将孔子对弟子教导一一自我对照,视为对自身教导并应用到日常实践中,克除自我气质病痛,这即是理学的工夫要义。在“克己复礼”章,朱子引用谢良佐“克己须从性偏处克去”说,提出克己工夫应从气质最偏颇处用工,方能变化气质。谢氏本人也正是由此下手用工,伊川与上蔡别后一年再见,问他做何工夫。谢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点头称赞,“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③
最后,朱子诠释夫子对弟子的教导时常采用“救失”之说。如“樊迟问知”章注,“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章注,“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子张学干禄”章注,“言此以救子张之失而进之也”“子张问明”章注,“此亦必因子张之失而告之”等。朱子认为,孔子与弟子问答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尤其是多处“问同答异”,更证实了长善救失的问答特点。如关于问孝,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所问相同而夫子所答不同,“子夏问孝”章注引程子说指出,夫子根据弟子自身材质、病痛不同而指点不同,“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④孔子的教导指点,带有帮助弟子改正为学进程中缺失不足,使其工夫境界得到完善进步的意味。“救失”和“发病”语义相似,皆是指出弟子不足病痛,前者语气较后者缓和,程度较轻,劝告意味重,多指出问题;后者则语气严厉,带有斥责强调意味,直接点出病痛根源所在。朱子根据孔子与弟子问答之辞,就问题严重与否作出“药病”还是“救失”的判定。
此外,朱子也采用“警告”之说,表明夫子之言虽不一定针对个人病痛而发,但具有普遍警告意义,学者须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可轻易放过。“警告”说和“药病”“救失”又略有不同,其程度更轻,所指范围更大,警告可指事先提醒,而药病、救失则显然针对事后而行的。就诠释根据来看,警告说也是最牵强猜测的一种。故朱子用词语气也最弱,泛指意味强而贬抑批评意味薄,其意为即便自身无此病痛,亦可以因之提高警惕,此亦反映出朱子诠释的良苦用心。朱子在“子路使门人为臣”章引胡氏说指出,孔子严厉批评子路,目的是警告所有学者,要成为君子就应谨小慎微,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不可懈怠细微之事,否则陷于不义而不知也。“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是以陷于行诈,罪至欺天。君子之于言动,虽微不可不谨。夫子深惩子路,所以警学者也。”①在“子游问孝”章,朱子指出孔子之言是警告子游敬对于孝的不可或缺性,并引胡氏说强调孔子之言虽不一定针对子游病痛而发,但在敬和爱的关系处理上,对子游及其他学者皆具警告意味。“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②再如“宰予昼寝”章亦引胡氏说指出夫子对宰予的批评是为了立定教法,警告弟子谨言敏行,言行一致。“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③
三 理论与工夫
朱子所谓贬抑圣门的说法其实出于自身理论建构和指点为学工夫的需要,其意是借评点孔门弟子来揭示学者为学病痛过失,确定为学典范,阐发理学概念,以为现实工夫做一参照,充分体现了朱子诠释经典以工夫为中心的立场。为了增加诠释的客观可信,朱子还尽力提出一些方法证据来支持论述,其主要方法大概为以下三种:
其一,根据学者造道境界、气质特征,采用对号入座法,推出学者应当有某种毛病,将概念类型化的诠释方法贯穿全书。朱子在诠释孔门弟子言论时,形成一个诠释循环,即“根据境界断定其言辞,根据言辞证实其境界”,境界与言辞紧密一体,相互印证,以此达到诠释前后一致。但这种诠释是建立在言行、德言相互对应前提下的,并不可以普遍绝对化。孔子就曾指出德言、言行不一致的情况,个人思想境地与个别言论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朱子据某人气质有某病痛,因而指出其所有言辞无一例外显示此病痛的诠释方法过于绝对简单,容有牵强不合情理处。事实上,孔子之教也常泛论儒家价值为学工夫,本无特别针砭意。
其二,尽量列举史实为证,以增强诠释的可信度。但因可用史实太少,无法普遍展开,故朱子此法只是运用到少数几条注释中。如“人皆有兄弟”章引胡氏说,以子夏自身哭子丧明这一事实为据,指出子夏在实践中未能处理好“爱与理”的关系,没有做到理论与修为的一致。“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广司马牛之意,意圆而语滞者也,惟圣人则无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践其言尔。”但朱子举事实佐证的可信度也遭到质疑,如关于“柴也愚”的注释不惜大段引用《家语》之说以证实其愚笨特点。“愚者,知不足而厚有余。《家语》记其‘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避难而行,不径不窦’。可以见其为人矣。”①虽然此类事实仅仅起辅助作用,但表明朱子很希望找到客观事实来印证自己观点。
其三,据夫子“因材施教”“问同答异”的特点,由因病发药、针砭学弊的诠释原则出发,与其理学思想相结合,实行有病推定。“针砭学弊”乃朱子经典诠释主要原则,其重要性还高于他一贯倡导的“求本义”原则,在二者相冲突时,朱子常选择前者。①该做法虽有一定可信度,但过于强调一致性,亦是主观牵强成分多,并不足以服人。夫子即便因材施教,并不代表指责弟子病痛,其中存在多种可能,如理论解惑等。朱子评论孔门诸子,本来就是要从中找出可以为学者“警示”的材料,提供一部为学警示录而不是功德谱,以为现实工夫之鉴。据弟子与孔子对话,弟子自身言行所推出的病痛,皆取决于诠释者本人的眼光,体现了朱子的理学思想,实为朱子理学思想之投射。如多处病痛皆与朱子的理一分殊、本末轻重思想有关,若抽出此理学思想,则病痛自无矣。理一分殊思想在《集注》中多有反映,由此判定弟子言语病痛最典型者,莫过于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章的诠释。朱子在此引胡氏观点指出子夏之言其意在于宽司马牛之忧虑,但其言语本身多“皆兄弟”三字,违背了理一分殊,爱有差等的原则,就变成无差等之爱的二本了。兄弟之爱乃血亲之爱,与他人之爱天然有别,可由此及彼,不可由彼及此。“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广司马牛之意,意圆而语滞者也,惟圣人则无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践其言尔。”朱子的本末观在判定孔门弟子病痛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学而》篇“子夏曰贤贤易色”章,朱子引吴氏说指出子夏在本末轻重之间虽然抓住了根本,但过于强调实践而忽视了学文,有重本轻末的偏颇之病,“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为无弊也。”②在《颜渊》篇“君子质而已矣”章朱子同样指出,子贡“文犹质也”说虽针对子成有本无末说以救其偏弊,然自身之言亦犯下了无本末轻重之别的毛病,“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③在《子张》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朱子引尹氏说强调君子应务学以成其道,并加按语指出子夏与尹焞之言各有所偏得,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语义才完备无瑕,“二说相须,其义始备。”④皆是本本有别、相须不离观点的反映。
可见朱子“贬抑圣门”的做法,根本是为学者“察病救失”服务的,其中贯穿了他的道统思想、理学观念,并以针砭学弊的诠释原则主导之。“察病救失”这一诠释手法承载的是朱子的理学思想,体现了对汉学解经模式的颠覆,是宋学义理解经模式的继承总结,表明儒学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贬抑圣门”的做法绝非朱子一家私见,乃宋代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宋学这一新的时代精神的显现。朱子通过这一诠释手法,颠覆了孔门弟子的形象,将新的时代思想注入古老经典,强调了经典与现实,理论与工夫的关联,赋予了儒家经典前所未有的魅力,确立了经典诠释的新典范,体现了宋学解释经典所获得的成功,表示新经学诠释时代的到来。它对经典诠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于今天儒学的发展亦具有深刻借鉴意义。朱子的做法表明儒学的发展不能离开自身资源,特别是经学。朱子正是通过对四书的成功诠释才建构起他的理学体系,并借助四书使理学思想广泛传播,扎根社会人心,真正做到了阐新知于旧闻。它同样表明思想、方法的创造与超越必须建立在足够深厚的思想资源基础上。朱子的思想即建立在前代学人深厚丰富的资源之上,体现出海纳百川包容并举的气势,由此建构了新的经学体系。当下儒学的发展,应投入更大精力于古代经典的再诠,使之与接引外来学术思想相互融合,为儒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创造条件。
一 “造道之极致”
儒家向来注重对人格成就层次的品评判定,认为学者在为学境地上存在先后高低之别本是成道进程中应有之事实,能否正视自身为学得失,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自知之明,亦是为学进步之关键。故孔子很注意点评弟子为学得失与境地高下,以促其反省进步。孟子亦注重区别人格层次,通过圣圣之间的相较,彰显了孔子“大成之圣”的崇高地位,确定了“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的为学目标,而且提出了节次分明的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之说。理学开创者周、程继承此风并发扬之,他们辨析孔门弟子高下得失,将其划分为两大层次:闻道传道的颜子、曾子与其他未能传道弟子,特别凸显颜子的独特性,树起“学颜子之所学”的理学旗帜,通过辨析颜、孟高下之分,突出颜子“学以至圣”的品质,以建立纯正的为学之方。同时抬尊曾子,确立了他在儒家道统中传道地位。故朱子在《集注》中批评孔门弟子的做法,乃是继承理学家风,《集注》批评孔门弟子的说法多数引自前辈学者即是明证。事实上,在疑经解经风潮涌起的宋代,对孔门弟子高下扬抑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宋儒多倡导以义理解经之模式,主张经典诠释应从个人理性出发进行批判性阐发,以达到针砭工夫弊病的效果。如《集注》对樊迟多有微词,其实北宋苏轼早有此说。朱子在《论语或问》中曾引用并称赞苏氏说:“苏氏曰:孔子之言,常中弟子之过,樊迟问崇德,孔子答以‘先事后得’,则须也有苟得之意也欤?其问知也,‘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教之以专修人事而不求侥幸之福也。其问仁也,曰‘仁者先难而后获’,教之以修德进业而不贪无故之利也。”①
除受前辈影响外,朱子对孔门弟子的批判诠释主要出于自身理学思想。毛氏认为朱子对孔门弟子横加挑剔,导致“圣门无完行”,制造了“圣门冤狱”。殊不知当朱子以至善、中庸,“造道之极致”作为评判孔门弟子的尺度时,“圣门无完行”之义自可成立。朱子对《大学》“至善”这一概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认为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也”,在三纲八目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明德、亲民皆须止于至善,“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②。从格致诚正修身的内圣一直通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皆须达于至善,有一处未到,即不能算至善。人在道德的修炼中,始终行走在追求至善的道路上。中庸是朱子极其看重的另一概念,朱子指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①中庸就是要求在日用常行中实现事事合宜,此是极难之事,乃儒家至德所在。当朱子以“造道之极致”的至善、中庸来衡量孔门高弟时,故难免见其到处是“病”了。如学而篇“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章注,朱子指出孔子和子贡境界高下在其问答中已彰显无遗,带给学者的教训是不能安于小成,固步自封,而应当追寻道德的最高境界。“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②若就孔门高弟所达境地成就,与常人相较,自然难以企及,令人景仰了。但若从“造道之极致”角度来看,不能不承认孔门高弟仍有不足。
人之为学自然存在境界高下,孔门弟子亦不能外。朱子对孔门弟子境界从上下、平行、前后三个层次进行高下浅深的比较,其意是为了树立为学典范。首先,通过夫子与弟子上下层次间的比较,揭示弟子和孔子境界上的差异,既突出了圣人境界的高远,同时又给学者以警示,促其谦虚反省。如子路篇“仲弓为季氏宰”章注,朱子引程子说指出仲弓心量与圣人存在大小之别,暗示仲弓还须在此方面努力用功。“程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③其次,朱子更重视弟子之间的平行比较,以见其高下,此意也是顺《论语》中夫子对弟子点评而发。夫子评价弟子,是为了检查他们的修行程度,以发现问题进行纠正。基于确定学习典范的考虑,朱子认为孔门弟子境界大致可分为三等,此等级决定了《集注》的诠释视角。颜子、曾子属于闻道一级,对儒家道统传扬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了圣贤之学,《集注》对之极力推崇褒扬。如《学而》篇“吾日三省”章,《集注》引谢氏说指出,孔门诸子虽然皆与闻夫子之道,除颜子外真正能够传承夫子之道者唯有曾子,其他诸子有所得亦有所失,夫子之学在其他学派中流传愈远,流弊愈多,已经失去了夫子学的真谛。只有曾子获得真传,并毫无流弊地传给子思、孟子,保持维护了儒家道统的延续,在孔门中居功甚伟,故此对其言语当用心体会。并强调曾子学圣人无弊,对于其流传下来的言语论说当倍加珍惜,可见对曾子之重视。“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①此说与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确定“曾氏独得其传”的传道地位一致。子贡、子路、子夏、子游、子张等学有所成的弟子为次一级,他们为学有得有失,得多于失,《集注》对之褒贬相间,但他们之间也存在高下之分。其中,子贡、闵子骞境界仅次于颜、曾,要高于其他弟子。《集注》中对子贡批评之辞不少,最终还是肯定子贡仅次颜、曾而终闻夫子之道。《卫灵公》篇“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章注朱子特加按语指出,据《论语》所载夫子与子贡对话之内容和频率,颜、曾以下,当属子贡。朱子之辞虽为推测,要之亦有一定道理。“愚按: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②闵子骞境界与颜子相似,要高于子张。《为政》篇“子张学干禄”章注引程子说:“子张学干禄,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为利禄动,若颜、闵则无此问矣。”③以樊迟、司马牛为代表的弟子则属于更下一级,他们为学失多于得,《集注》对之多加贬斥,以为后学者鉴。再次,朱子在诠释中非常注重学者境界的前后变化,以动态观看待孔门弟子为学变化。他认为学者境界总是在不断提升变化中,修道成德变化气质本为一生命历练的动态过程。这就向后学表明,孔门弟子高明境界亦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对成圣成贤之学应当保有信心。朱子根据夫子与弟子的问答,断定处于何种阶段,对颜子、子贡、樊迟,子路等皆有判定,如《阳货》篇“君子尚勇乎”章注引胡氏说指出此问答反映出子路初学时状态:“疑此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也。”④《先进》篇“回也其庶乎”注引程子说同样指出该问答是子贡年少问学时事,后来已经得闻性与天道之学,自然不会有此问题,“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①。
二 “圣门冤狱”
朱子以“造道之极致”为镜子,照出孔门弟子存在境界高下浅深之别,更照出孔门弟子为学病痛。从为后学树立正确为学之方的角度考虑,朱子非常尖锐苛刻地揭露了这些病痛,用毛氏的话说,简直是制造“圣门冤狱”。真相如何呢?我们具体探究一下所谓“圣门冤狱”。
首先,朱子对孔门弟子并非一味贬斥,而是抱褒贬分明各得其所的态度。尽管在“造道之极致”的标准下孔门弟子显出不足,朱子仍充分赞扬了孔门弟子各自所获得的成就,褒其已成足为后学者师,贬其不足引为后学者鉴。孔门弟子虽未得夫子道全,然得夫子之道之一偏一体,其成就足以为后世之师,远非后人所能达到。如对曾点高明气象、子贡颖悟才质、子路信勇卓著,子夏笃实工夫皆极其肯定。即以对子路评价为例,朱子多次赞其豪迈刚勇,重信轻财,气象高远,学者应以之为师。如《先进》篇“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章注强调子路境界已达到正大高明地步,只是在精微之处有所不足而已,堪为学者百世师而不可轻视之,“言子路之学,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②。
其次,朱子从理学概念出发,将孔门弟子诠释为理学概念的化身,把他们与理学概念紧密相连并类型化之,朱子对孔门弟子的评论其实表达的是对理学概念的认识,目的是增进学者对理学概念和为学境界的理解,以为己鉴。客观而论,朱子评论孔门弟子,除对颜、曾倍加维护赞颂外,于其他弟子似乎更侧重指出过失,其目的是阐述他“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的为学理念。正是以“求造道之极致”为标准,故《集注》详加挑剔孔门弟子病痛,几乎达到了吹毛求疵地步。然条目挑剔虽多,其义多为重复。在朱子看来,孔门弟子之病痛皆可以类型论之,如子路之信勇而乏义理,子夏之严谨笃厚而气度狭隘,子张之意态高远而无诚实,子贡之聪明博学而务外。朱子对于他们的批评,皆以此类型套而论之,简直成了数学公式。即以子路为例,批评他的用语大致如下:
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为政》篇“由诲女知之乎”章)
程子曰:“故夫子美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公冶长》篇“乘桴浮于海”章)
吴氏曰:“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子路》篇“子路问政”章)
胡氏曰:“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子路》篇“卫君待子而为政”章)
尹氏曰:“义以为尚,则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阳货》篇“君子尚勇乎”章)
范氏曰:“子路勇于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学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阳货》篇“女闻六言六蔽”章)
显然,朱子对子路的评价总体为具信勇而乏义理,如此诠释的效果是把诠释对象子路固定为轻财守信意气用事的侠客形象①,此一类型化形象又套用涉及于子路的所有方面。《集注》关于子张、子夏等弟子的评论皆是如此。不难看出,朱子实际是在有意以一套理学概念诠释孔门弟子,使孔门弟子成为理学概念的符号和代言人。这种概念化、符号化、抽象脸谱化的诠释凸显了孔门弟子气质中真实本质一面,使学者容易把握其特质,如子路成为勇信的符号化身,子张是高远阔大的化身,子夏是谨慎笃厚的化身。该诠释的主观色彩非常明显,朱子在进入文本之前,对诠释对象已有了很强的诠释成见,文本不过是强化、印证了他的成见而已。朱子这种先入为主,以人物特质、理学范畴为中心的诠释手法得到《论语》中因材施教法的支撑。该诠释法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直具有人物性格脸谱化的传统,典型者如《三国演义》中关羽塑造为“忠义”的化身,曹操为“奸诈”的化身,近如对革命英雄人物的塑造,“高干大”形象的出现等,人物皆成为叙述者的理念符号。在朱子诠释中,孔门弟子成为表达其理学概念的符号,孔门弟子所体现的优缺点皆具有了普遍意义,朱子通过扬其优长,揭其缺失这种褒贬分明的揭示对照,达到了给学者树立正确为学之方的目的。
再次,朱子批评孔门弟子,是要求学者“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①基于这一原则,朱子认为孔门师生之交流多具有指点弟子病痛的意味,其言谈“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集注》评论孔子门人时数十次使用“病”这个词,强调成圣之学首要工夫就是反省自身气质工夫的真实病痛。学者先天资质禀赋总是有所缺失,应由后天工夫来消除弊病以变化气质。首要工夫是发现病痛,但人自知甚难,其病痛往往需经他人指点揭示。朱子认为孔子与弟子言谈,就是根据诸弟子资质、工夫、境界,把脉开方,对症下药,其药因人病痛而异,但皆符合“切己”这一原则,如此方能收到效果。如子张有“过高之病”,开出药方是“笃实”。《颜渊》篇“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章注引尹氏说指出,“子张之学,病在乎不务实。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②子贡也有类似毛病,夫子告之近处下手之方。雍也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章注引吕氏说,“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③在“司马牛问仁”章,朱子特意揭示了孔门之教“切己”特点。他指出,因司马牛病痛与子贡等人不同,故当其问仁时,夫子并不是随便给予答复,而是根据其为学气质病痛,针对性开出适合他的“言忍”这一处方。夫子对学生虽然指点不一,但皆是为帮助弟子认识自身病痛所在,找到修身进德的途径要领,学者对此应深思自考。《颜渊》篇“司马牛问仁”章注,“愚谓牛之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为仁之大概语之,则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终无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读者其致思焉。”①再如对孔子称赞樊迟“善哉问”,朱子注为,“善其切于为己。”皆是点出切己在为学中的重要意义。在《先进》篇“柴愚参鲁师辟由喭”章,朱子引杨时说指出夫子指点四者气质偏颇处,希望他们知道各自病痛,从而针对性地下手用工以克服之,“四者性之偏,语之使知自励也。”②朱子这一诠释定式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要求学者以“察切己之实病”的方法作为现实工夫指导,在学习《论语》过程中,应将孔子对弟子教导一一自我对照,视为对自身教导并应用到日常实践中,克除自我气质病痛,这即是理学的工夫要义。在“克己复礼”章,朱子引用谢良佐“克己须从性偏处克去”说,提出克己工夫应从气质最偏颇处用工,方能变化气质。谢氏本人也正是由此下手用工,伊川与上蔡别后一年再见,问他做何工夫。谢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点头称赞,“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③
最后,朱子诠释夫子对弟子的教导时常采用“救失”之说。如“樊迟问知”章注,“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章注,“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子张学干禄”章注,“言此以救子张之失而进之也”“子张问明”章注,“此亦必因子张之失而告之”等。朱子认为,孔子与弟子问答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尤其是多处“问同答异”,更证实了长善救失的问答特点。如关于问孝,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所问相同而夫子所答不同,“子夏问孝”章注引程子说指出,夫子根据弟子自身材质、病痛不同而指点不同,“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④孔子的教导指点,带有帮助弟子改正为学进程中缺失不足,使其工夫境界得到完善进步的意味。“救失”和“发病”语义相似,皆是指出弟子不足病痛,前者语气较后者缓和,程度较轻,劝告意味重,多指出问题;后者则语气严厉,带有斥责强调意味,直接点出病痛根源所在。朱子根据孔子与弟子问答之辞,就问题严重与否作出“药病”还是“救失”的判定。
此外,朱子也采用“警告”之说,表明夫子之言虽不一定针对个人病痛而发,但具有普遍警告意义,学者须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可轻易放过。“警告”说和“药病”“救失”又略有不同,其程度更轻,所指范围更大,警告可指事先提醒,而药病、救失则显然针对事后而行的。就诠释根据来看,警告说也是最牵强猜测的一种。故朱子用词语气也最弱,泛指意味强而贬抑批评意味薄,其意为即便自身无此病痛,亦可以因之提高警惕,此亦反映出朱子诠释的良苦用心。朱子在“子路使门人为臣”章引胡氏说指出,孔子严厉批评子路,目的是警告所有学者,要成为君子就应谨小慎微,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不可懈怠细微之事,否则陷于不义而不知也。“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是以陷于行诈,罪至欺天。君子之于言动,虽微不可不谨。夫子深惩子路,所以警学者也。”①在“子游问孝”章,朱子指出孔子之言是警告子游敬对于孝的不可或缺性,并引胡氏说强调孔子之言虽不一定针对子游病痛而发,但在敬和爱的关系处理上,对子游及其他学者皆具警告意味。“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②再如“宰予昼寝”章亦引胡氏说指出夫子对宰予的批评是为了立定教法,警告弟子谨言敏行,言行一致。“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③
三 理论与工夫
朱子所谓贬抑圣门的说法其实出于自身理论建构和指点为学工夫的需要,其意是借评点孔门弟子来揭示学者为学病痛过失,确定为学典范,阐发理学概念,以为现实工夫做一参照,充分体现了朱子诠释经典以工夫为中心的立场。为了增加诠释的客观可信,朱子还尽力提出一些方法证据来支持论述,其主要方法大概为以下三种:
其一,根据学者造道境界、气质特征,采用对号入座法,推出学者应当有某种毛病,将概念类型化的诠释方法贯穿全书。朱子在诠释孔门弟子言论时,形成一个诠释循环,即“根据境界断定其言辞,根据言辞证实其境界”,境界与言辞紧密一体,相互印证,以此达到诠释前后一致。但这种诠释是建立在言行、德言相互对应前提下的,并不可以普遍绝对化。孔子就曾指出德言、言行不一致的情况,个人思想境地与个别言论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朱子据某人气质有某病痛,因而指出其所有言辞无一例外显示此病痛的诠释方法过于绝对简单,容有牵强不合情理处。事实上,孔子之教也常泛论儒家价值为学工夫,本无特别针砭意。
其二,尽量列举史实为证,以增强诠释的可信度。但因可用史实太少,无法普遍展开,故朱子此法只是运用到少数几条注释中。如“人皆有兄弟”章引胡氏说,以子夏自身哭子丧明这一事实为据,指出子夏在实践中未能处理好“爱与理”的关系,没有做到理论与修为的一致。“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广司马牛之意,意圆而语滞者也,惟圣人则无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践其言尔。”但朱子举事实佐证的可信度也遭到质疑,如关于“柴也愚”的注释不惜大段引用《家语》之说以证实其愚笨特点。“愚者,知不足而厚有余。《家语》记其‘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避难而行,不径不窦’。可以见其为人矣。”①虽然此类事实仅仅起辅助作用,但表明朱子很希望找到客观事实来印证自己观点。
其三,据夫子“因材施教”“问同答异”的特点,由因病发药、针砭学弊的诠释原则出发,与其理学思想相结合,实行有病推定。“针砭学弊”乃朱子经典诠释主要原则,其重要性还高于他一贯倡导的“求本义”原则,在二者相冲突时,朱子常选择前者。①该做法虽有一定可信度,但过于强调一致性,亦是主观牵强成分多,并不足以服人。夫子即便因材施教,并不代表指责弟子病痛,其中存在多种可能,如理论解惑等。朱子评论孔门诸子,本来就是要从中找出可以为学者“警示”的材料,提供一部为学警示录而不是功德谱,以为现实工夫之鉴。据弟子与孔子对话,弟子自身言行所推出的病痛,皆取决于诠释者本人的眼光,体现了朱子的理学思想,实为朱子理学思想之投射。如多处病痛皆与朱子的理一分殊、本末轻重思想有关,若抽出此理学思想,则病痛自无矣。理一分殊思想在《集注》中多有反映,由此判定弟子言语病痛最典型者,莫过于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章的诠释。朱子在此引胡氏观点指出子夏之言其意在于宽司马牛之忧虑,但其言语本身多“皆兄弟”三字,违背了理一分殊,爱有差等的原则,就变成无差等之爱的二本了。兄弟之爱乃血亲之爱,与他人之爱天然有别,可由此及彼,不可由彼及此。“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广司马牛之意,意圆而语滞者也,惟圣人则无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践其言尔。”朱子的本末观在判定孔门弟子病痛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学而》篇“子夏曰贤贤易色”章,朱子引吴氏说指出子夏在本末轻重之间虽然抓住了根本,但过于强调实践而忽视了学文,有重本轻末的偏颇之病,“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为无弊也。”②在《颜渊》篇“君子质而已矣”章朱子同样指出,子贡“文犹质也”说虽针对子成有本无末说以救其偏弊,然自身之言亦犯下了无本末轻重之别的毛病,“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③在《子张》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朱子引尹氏说强调君子应务学以成其道,并加按语指出子夏与尹焞之言各有所偏得,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语义才完备无瑕,“二说相须,其义始备。”④皆是本本有别、相须不离观点的反映。
可见朱子“贬抑圣门”的做法,根本是为学者“察病救失”服务的,其中贯穿了他的道统思想、理学观念,并以针砭学弊的诠释原则主导之。“察病救失”这一诠释手法承载的是朱子的理学思想,体现了对汉学解经模式的颠覆,是宋学义理解经模式的继承总结,表明儒学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贬抑圣门”的做法绝非朱子一家私见,乃宋代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宋学这一新的时代精神的显现。朱子通过这一诠释手法,颠覆了孔门弟子的形象,将新的时代思想注入古老经典,强调了经典与现实,理论与工夫的关联,赋予了儒家经典前所未有的魅力,确立了经典诠释的新典范,体现了宋学解释经典所获得的成功,表示新经学诠释时代的到来。它对经典诠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于今天儒学的发展亦具有深刻借鉴意义。朱子的做法表明儒学的发展不能离开自身资源,特别是经学。朱子正是通过对四书的成功诠释才建构起他的理学体系,并借助四书使理学思想广泛传播,扎根社会人心,真正做到了阐新知于旧闻。它同样表明思想、方法的创造与超越必须建立在足够深厚的思想资源基础上。朱子的思想即建立在前代学人深厚丰富的资源之上,体现出海纳百川包容并举的气势,由此建构了新的经学体系。当下儒学的发展,应投入更大精力于古代经典的再诠,使之与接引外来学术思想相互融合,为儒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创造条件。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