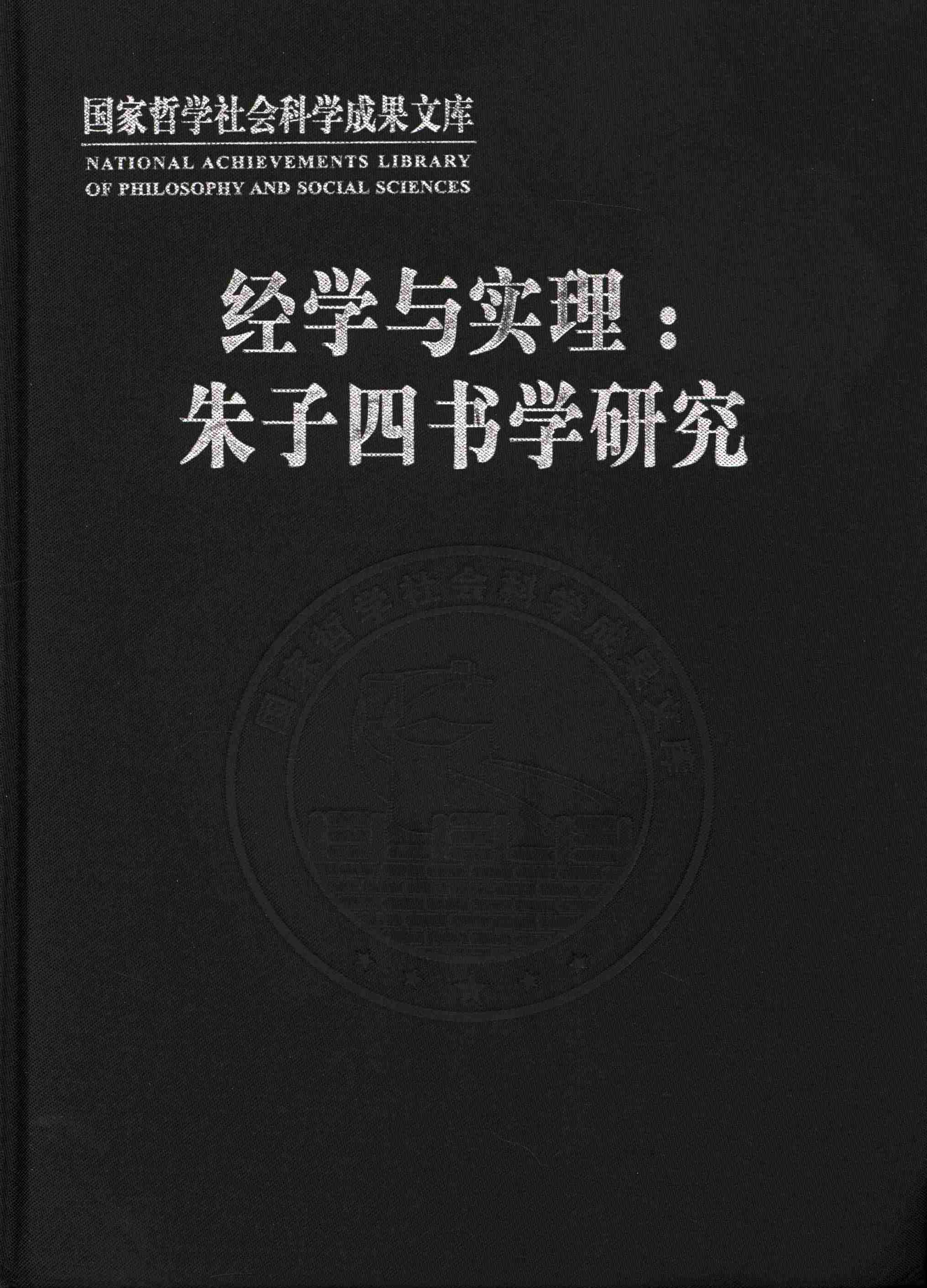四 圣圣之别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808 |
| 颗粒名称: | 四 圣圣之别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7 |
| 页码: | 303-309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在理学上对孟子的圣人观进行了深化和扩展。他认为圣人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分为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伯夷、伊尹、柳下惠等圣人属于偏至之圣,因其气质或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而表现出清、任、和等单一特质,但未达到中庸的标准。朱子将圣人概念泛化,认为只要在德性某一方面的成就达到极至即可称之为圣。同时,孔子作为集大成之圣,其特质是集众圣之长而为一大圣,具有全面性和中庸性。朱子强调孔子在儒家道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远胜于尧舜等先代圣人。总之,朱子的理论构建在强调圣人的多元性和现实性的同时,也维护了儒家道统的连续性和权威性。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从理论上论述人人皆可以为圣,使理想中的圣人有了成为生活常态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泛化了圣人。针对孟子泛化和现实化圣人的倾向,朱子在理学的立场上予以推进,将圣人明确划分为两等: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判别标准在于是否从容中道不勉而至,或者说是仁智兼具还是仁而欠智。同时从性之与反之的角度,将尧舜与汤武分为两等,这样既坚持了圣的高远理想性,又俯就了圣的现实可行性,但同时亦使得偏圣与大贤之区别变得模糊。
圣之别:清、任、和的偏至之圣。《孟子·万章下》“集大成”章揭示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四圣的特点分别为清、任、和、时。这既是由圣人自身气质所造成的圣之类型差异,其中又存在大小偏全的层次差别。朱子首先指出四位圣人虽然存在类型上的差别,然而却有其作为圣的根本一致处,即于人伦道德的安而行之,自然从容而至其极至。“圣只是做到极至处,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谓之圣。”①他引用张载对清、和、任的解释,提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者各因其气质,在清、和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与孔子同为极至。“张子曰:无所杂者清之极,无所异者和之极。勉而清,非圣人之清;勉而和,非圣人之和。所谓圣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其次,朱子强调三者虽然为圣,但这种圣非中和通全之圣,而是一偏之圣,因为三者气质偏颇而不中正,各以其一节为圣,是在某一端力行至极,达到了无私欲、纯天理之不可企及境界,然于总体境界而言,则偏而不中,执而不通,任而不化,专而不全,不如孔子大成之圣的纯全中正,巧力皆备。“愚谓孔子仕、止、久、速,各当其可。盖兼三子之所以圣者而时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处合乎孔子,而不得为圣之时,何也?程子曰:‘终是任底意思在。’”(《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明确将圣和中分开,肯定这种偏圣并不是中,并没有达到中庸之境,“三子之德,但各至于一偏之极,不可谓之中。……圣,非中之谓也”①。尽管这种圣存在偏颇之处,但符合圣德性纯粹、纯乎天理、无有私欲的标准。“某问:既是如此,何以为圣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无驳杂。虽是过当,直是无纤豪查滓。”②朱子进一步指出伯夷等圣人造行虽极高,但却有“隘与不恭”的偏颇流弊,故不可以为学之矩范。“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孟子集注·公孙丑上》)朱子分析三圣偏而未中的原因在于天生气禀有所限制,同时在后天之知上亦有所不足,故未能达到通化之圣的地步。“厚之问:三圣事,是当初如此,是后来如此?”曰:“是知之不至。”③
朱子一方面既把伯夷等看作圣,同时又指出他们自身德性存在偏颇,不够完满,这就将圣之标准降低,由一种全体完美,尽善尽美,转化为凡在德性某一方面做到极至者。再由一种人格道德概念,转化延伸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凡是某一方面做得极好者,故有书圣、茶圣、诗圣之说,这是圣概念的普泛化。
金声玉振:孔子集大成之圣。孟子不满意伯夷等偏至之圣,而心仪于孔子的集大成之圣,给予了孔子最崇高的评价。可以说,孟子提出伯夷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衬托孔子的大成之圣。朱子同样突出了孔子的重要性,在儒家道统谱系中给予孔子远迈尧舜的至高定位。他指出在儒学道统中,在政统和道统分化之时,孔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延续道统,开创学统的作用,其功劳远胜于尧舜。“圣人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垂于世。”①孟子以金声玉振比喻孔子之集大成,朱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孔子大成之圣和三子偏至之圣的差别:孔子集三圣之长而为一大成之圣,无所不备、无所不通,三子乃偏于小成。夫子和三子,恰如太和元气流行于春夏秋冬之四时也。“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批评前辈学者为维护圣人权威而回避圣人之间优劣之分,指出应认真面对这一客观事实。他以具体事例指出伯夷等本来即存在欠缺不足,其弊病与生俱来,非末流所至,避嫌之论应当取消。或问:“如伯夷之清而‘不念旧恶’,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之清、圣之和也,但其流弊则有隘与不恭之失。”曰:“这也是诸先生恐伤触二子,所以说流弊。今以圣人观二子,则二子多有欠阙处;才有欠阙处,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说他‘隘与不恭’,不曾说其末流如此。如‘不念旧恶’、‘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处。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处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说得。大率前辈之论多是如此。”②朱子认为三子和孔子之别在于知上。三子之偏,源于缺少知上工夫,其初始即看得道理有偏差,所以其终之行亦止于偏至。孔子高明处在于知上已经无所不尽,故于行上能赅括包容,知行始终圆融无缺。“见孔子巧力俱全,而圣智兼备,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尽。”(《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将智圣分开,认为各自代表知德一面。圣并不能包含智;反之,智倒有包含圣之意味,如真知即包含行,并再三强调大圣即是德智双修,巧力兼全。“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朱子根据知先行后说,认为知是行之源头,行是知之落实,一旦作为源头的知上有偏,则行上亦必然有所不足。孔子作为大成之圣,关键在于知上明了事理。“功夫紧要处,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极于一偏,缘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终之成也亦各至于一偏之极。孔子合下尽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无所不尽,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该毕备,而无一德一行之或阙。”①朱子指出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的差别还在于是否时中。孟子以射箭为喻,说明三子与夫子之差别,在于未能做到巧力兼具,至而且中。朱子认为孔子具有中正、时中、中和的大圣气象,时时刻刻皆处于中正之位。三子在偏处达到圣,至而不中,大圣则在全和中之统一上达到和谐。三子极其一偏,如四时之一季,音乐之一成;大圣则是大成之音,太和元气之流行,遍布于四时中。②“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圣之至与至于圣:性之与反之。在圣人层次上,除了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外,还有尧舜与汤武之间的性之与反之的差别。孟子对同为圣人的尧舜和汤武数次提出性之、反之的高下评价。朱子对此作了具体分析,肯定圣人之至与至于圣人的客观差别。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朱子注:“性者,得全于天,无所污坏,不假修为,圣之至也。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语,盖自孟子发之。’吕氏曰:‘无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于无意,复性者也。尧舜不失其性,汤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则一也。’”(《孟子集注·尽心下》)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朱子注:“尧舜天性浑全,不假修习。汤武修身体道,以复其性。尹氏曰:“性之者,与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则一也。”(《孟子集注·尽心上》)
朱子认为“性之”“身之”用以突出尧舜与汤武之分别,关键在于是否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性者”直下保全天赐性理,不受外界污损破坏,顺其自然而不需人为努力,这是圣人中的极品,圣之至也。“反之”则需要人为努力来消除后天所沾染之不完善,以恢复其天性,最终达到圣的境界。二者之别,其实即是无意安行之顺性还是有意利行之复性。“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①程颢认为孟子对尧舜汤武作出高下之分,指出二者区别,是前所未有之开创性思想。“性、反”差距体现在工夫上:性之自然无意,挥洒自如,安行而不涉人力;反之则需勉强复性之功,以返乎本性,当然二者在最终成就上皆为圣人。朱子还据史实指出尧舜与汤武是常与变、经与权的差别,汤武之放伐尽管变而合乎中道,然终究不如尧舜之禅让自然合理,二者存在等差,“如尧舜与汤武真个争分数,有等级”②。批评学者对此理解不够,有意回避尧舜汤武高下之别。圣人与常人自然不在一个道德层次上,但是圣圣相较,天然存在一个优劣之分,而且孔子“尽善尽美”之别已有此意,“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分明有优劣不同,却要都回护教一般,少间便说不行。且如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若是以常人去比圣贤,则说是与不是不得;若以圣贤比圣贤,则自有是与不是处,须与他分个优劣。今若隐避回互不说,亦不可”③。除肯定尧舜与汤武的差别外,朱子还对同为反之的汤武区别出高低,认为汤在修为工夫上又较胜于武。“‘汤武反之’,其反之虽同,然细看来,武王终是疏略,成汤却孜孜向进。”“汤反之之工恐更精密。”①
圣、贤、君子之别。圣、贤、君子皆是儒家之理想人格,三者之间有同有异,朱子在处理三者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由偏圣这一概念引起与大贤、君子概念的紊乱。
圣与贤的异同。朱子在诠释《论》、《孟》时,多数地方并不分别圣贤,常把“圣贤”当作一词组连用,如“圣贤亦何所用心哉”“圣贤之心”等,这强调了圣贤相同的一面。但朱子有时又特意区分圣贤,剖析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讨论孔孟之异。朱子指出孔孟一为圣一为贤,二者存在客观差别。这种圣贤之别显露于答问言辞等诸多方面,如孟子言语时常露出锋芒,孔子则浑然无迹,透过言语即见出修为之高低。朱子在“孟子告齐宣王”章注中引潘兴嗣说:“孟子告齐王之言,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孟子集注·离娄》下)在“孟子曰说大人”章注中引杨氏说:“孟子此章,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孟子集注·尽心下》)朱子引用杨时的话,批评孟子言语之间极为明显的用己之长,较人之短的意图,显得粗率狂妄,不符合圣人气象。如在对待大人态度上,孔孟截然相反,孔子畏敬,孟子藐视。这些都见出圣贤有别。
但朱子提出偏圣说,造成偏圣与贤人层次区分上的模糊。一方面只有至圣才是性之安之,偏圣与贤人一样,皆须反之复性工夫,如此一来,偏圣与贤人就难以区别了。而且,在朱子看来,作为大贤的颜子在修为上(如巧和中)有超过伯夷等偏圣处,“颜子优于汤武”,②只是在行上不够充足,力有未至而已。另一大贤孟子与偏圣之高低,亦不好评论,这就造成贤与圣的层次上的混乱。正是有见于伯夷等偏圣存在不完善处,故程子提出将他们从圣人位置上降下来,以解决与大贤之间的矛盾,提出伯夷柳下惠并非圣人说,“人皆称柳下惠为圣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语,非自见。”又曰:“夷、惠圣人,传者之误。”①但朱子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坚持偏圣的存在,强调圣人以所至而论,不以是否大全中正通化为准。并以药为譬指出偏方之药有时效果胜于中和之药,夷惠对世道人心教化作用甚为明显,有时还甚于至圣孔子。可见,朱子更侧重从客观教化效果来着眼。“未必误也。彼曰圣之清也、圣之和,则固不思不勉而从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于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备,所以不得班于孔子耳。……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圣而易能,有迹而易见,且世人之贪懦鄙薄者众,一闻其风而兴起焉,则其为效也速,而所及者广,譬如姜桂大黄之剂,虽非中和,然(文渊阁本有“其”字)于去病之功为捷。”②
圣人与君子。朱子将君子视为圣人的通称。“君子,圣人之通称也。”(《孟子集注·尽心上》)这样一来,君子就包含了圣人,也就意味着圣人可以视为君子的一种,即圣人君子,与通常概念下的君子相对照。但是圣人自身又有偏圣和至圣的区别,当圣人和君子相提并论时,君子就包含了偏圣,圣就特指至圣。如在“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章的注释中,朱子强调圣人(专指至圣)立法出命,性之安之,君子(包含偏圣)则需要行法俟命,反之复性。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圣与君子概念的紊乱。“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祸福有所不计,盖虽未至于自然,而已非有所为而为矣。此反之之事。吕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圣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圣人性之,君子所以复其性也。’”(《孟子集注·尽心下》)
圣之别:清、任、和的偏至之圣。《孟子·万章下》“集大成”章揭示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四圣的特点分别为清、任、和、时。这既是由圣人自身气质所造成的圣之类型差异,其中又存在大小偏全的层次差别。朱子首先指出四位圣人虽然存在类型上的差别,然而却有其作为圣的根本一致处,即于人伦道德的安而行之,自然从容而至其极至。“圣只是做到极至处,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谓之圣。”①他引用张载对清、和、任的解释,提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者各因其气质,在清、和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与孔子同为极至。“张子曰:无所杂者清之极,无所异者和之极。勉而清,非圣人之清;勉而和,非圣人之和。所谓圣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其次,朱子强调三者虽然为圣,但这种圣非中和通全之圣,而是一偏之圣,因为三者气质偏颇而不中正,各以其一节为圣,是在某一端力行至极,达到了无私欲、纯天理之不可企及境界,然于总体境界而言,则偏而不中,执而不通,任而不化,专而不全,不如孔子大成之圣的纯全中正,巧力皆备。“愚谓孔子仕、止、久、速,各当其可。盖兼三子之所以圣者而时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处合乎孔子,而不得为圣之时,何也?程子曰:‘终是任底意思在。’”(《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明确将圣和中分开,肯定这种偏圣并不是中,并没有达到中庸之境,“三子之德,但各至于一偏之极,不可谓之中。……圣,非中之谓也”①。尽管这种圣存在偏颇之处,但符合圣德性纯粹、纯乎天理、无有私欲的标准。“某问:既是如此,何以为圣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无驳杂。虽是过当,直是无纤豪查滓。”②朱子进一步指出伯夷等圣人造行虽极高,但却有“隘与不恭”的偏颇流弊,故不可以为学之矩范。“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孟子集注·公孙丑上》)朱子分析三圣偏而未中的原因在于天生气禀有所限制,同时在后天之知上亦有所不足,故未能达到通化之圣的地步。“厚之问:三圣事,是当初如此,是后来如此?”曰:“是知之不至。”③
朱子一方面既把伯夷等看作圣,同时又指出他们自身德性存在偏颇,不够完满,这就将圣之标准降低,由一种全体完美,尽善尽美,转化为凡在德性某一方面做到极至者。再由一种人格道德概念,转化延伸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凡是某一方面做得极好者,故有书圣、茶圣、诗圣之说,这是圣概念的普泛化。
金声玉振:孔子集大成之圣。孟子不满意伯夷等偏至之圣,而心仪于孔子的集大成之圣,给予了孔子最崇高的评价。可以说,孟子提出伯夷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衬托孔子的大成之圣。朱子同样突出了孔子的重要性,在儒家道统谱系中给予孔子远迈尧舜的至高定位。他指出在儒学道统中,在政统和道统分化之时,孔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延续道统,开创学统的作用,其功劳远胜于尧舜。“圣人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垂于世。”①孟子以金声玉振比喻孔子之集大成,朱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孔子大成之圣和三子偏至之圣的差别:孔子集三圣之长而为一大成之圣,无所不备、无所不通,三子乃偏于小成。夫子和三子,恰如太和元气流行于春夏秋冬之四时也。“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批评前辈学者为维护圣人权威而回避圣人之间优劣之分,指出应认真面对这一客观事实。他以具体事例指出伯夷等本来即存在欠缺不足,其弊病与生俱来,非末流所至,避嫌之论应当取消。或问:“如伯夷之清而‘不念旧恶’,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之清、圣之和也,但其流弊则有隘与不恭之失。”曰:“这也是诸先生恐伤触二子,所以说流弊。今以圣人观二子,则二子多有欠阙处;才有欠阙处,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说他‘隘与不恭’,不曾说其末流如此。如‘不念旧恶’、‘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处。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处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说得。大率前辈之论多是如此。”②朱子认为三子和孔子之别在于知上。三子之偏,源于缺少知上工夫,其初始即看得道理有偏差,所以其终之行亦止于偏至。孔子高明处在于知上已经无所不尽,故于行上能赅括包容,知行始终圆融无缺。“见孔子巧力俱全,而圣智兼备,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尽。”(《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将智圣分开,认为各自代表知德一面。圣并不能包含智;反之,智倒有包含圣之意味,如真知即包含行,并再三强调大圣即是德智双修,巧力兼全。“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朱子根据知先行后说,认为知是行之源头,行是知之落实,一旦作为源头的知上有偏,则行上亦必然有所不足。孔子作为大成之圣,关键在于知上明了事理。“功夫紧要处,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极于一偏,缘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终之成也亦各至于一偏之极。孔子合下尽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无所不尽,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该毕备,而无一德一行之或阙。”①朱子指出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的差别还在于是否时中。孟子以射箭为喻,说明三子与夫子之差别,在于未能做到巧力兼具,至而且中。朱子认为孔子具有中正、时中、中和的大圣气象,时时刻刻皆处于中正之位。三子在偏处达到圣,至而不中,大圣则在全和中之统一上达到和谐。三子极其一偏,如四时之一季,音乐之一成;大圣则是大成之音,太和元气之流行,遍布于四时中。②“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圣之至与至于圣:性之与反之。在圣人层次上,除了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外,还有尧舜与汤武之间的性之与反之的差别。孟子对同为圣人的尧舜和汤武数次提出性之、反之的高下评价。朱子对此作了具体分析,肯定圣人之至与至于圣人的客观差别。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朱子注:“性者,得全于天,无所污坏,不假修为,圣之至也。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语,盖自孟子发之。’吕氏曰:‘无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于无意,复性者也。尧舜不失其性,汤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则一也。’”(《孟子集注·尽心下》)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朱子注:“尧舜天性浑全,不假修习。汤武修身体道,以复其性。尹氏曰:“性之者,与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则一也。”(《孟子集注·尽心上》)
朱子认为“性之”“身之”用以突出尧舜与汤武之分别,关键在于是否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性者”直下保全天赐性理,不受外界污损破坏,顺其自然而不需人为努力,这是圣人中的极品,圣之至也。“反之”则需要人为努力来消除后天所沾染之不完善,以恢复其天性,最终达到圣的境界。二者之别,其实即是无意安行之顺性还是有意利行之复性。“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①程颢认为孟子对尧舜汤武作出高下之分,指出二者区别,是前所未有之开创性思想。“性、反”差距体现在工夫上:性之自然无意,挥洒自如,安行而不涉人力;反之则需勉强复性之功,以返乎本性,当然二者在最终成就上皆为圣人。朱子还据史实指出尧舜与汤武是常与变、经与权的差别,汤武之放伐尽管变而合乎中道,然终究不如尧舜之禅让自然合理,二者存在等差,“如尧舜与汤武真个争分数,有等级”②。批评学者对此理解不够,有意回避尧舜汤武高下之别。圣人与常人自然不在一个道德层次上,但是圣圣相较,天然存在一个优劣之分,而且孔子“尽善尽美”之别已有此意,“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分明有优劣不同,却要都回护教一般,少间便说不行。且如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若是以常人去比圣贤,则说是与不是不得;若以圣贤比圣贤,则自有是与不是处,须与他分个优劣。今若隐避回互不说,亦不可”③。除肯定尧舜与汤武的差别外,朱子还对同为反之的汤武区别出高低,认为汤在修为工夫上又较胜于武。“‘汤武反之’,其反之虽同,然细看来,武王终是疏略,成汤却孜孜向进。”“汤反之之工恐更精密。”①
圣、贤、君子之别。圣、贤、君子皆是儒家之理想人格,三者之间有同有异,朱子在处理三者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由偏圣这一概念引起与大贤、君子概念的紊乱。
圣与贤的异同。朱子在诠释《论》、《孟》时,多数地方并不分别圣贤,常把“圣贤”当作一词组连用,如“圣贤亦何所用心哉”“圣贤之心”等,这强调了圣贤相同的一面。但朱子有时又特意区分圣贤,剖析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讨论孔孟之异。朱子指出孔孟一为圣一为贤,二者存在客观差别。这种圣贤之别显露于答问言辞等诸多方面,如孟子言语时常露出锋芒,孔子则浑然无迹,透过言语即见出修为之高低。朱子在“孟子告齐宣王”章注中引潘兴嗣说:“孟子告齐王之言,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孟子集注·离娄》下)在“孟子曰说大人”章注中引杨氏说:“孟子此章,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孟子集注·尽心下》)朱子引用杨时的话,批评孟子言语之间极为明显的用己之长,较人之短的意图,显得粗率狂妄,不符合圣人气象。如在对待大人态度上,孔孟截然相反,孔子畏敬,孟子藐视。这些都见出圣贤有别。
但朱子提出偏圣说,造成偏圣与贤人层次区分上的模糊。一方面只有至圣才是性之安之,偏圣与贤人一样,皆须反之复性工夫,如此一来,偏圣与贤人就难以区别了。而且,在朱子看来,作为大贤的颜子在修为上(如巧和中)有超过伯夷等偏圣处,“颜子优于汤武”,②只是在行上不够充足,力有未至而已。另一大贤孟子与偏圣之高低,亦不好评论,这就造成贤与圣的层次上的混乱。正是有见于伯夷等偏圣存在不完善处,故程子提出将他们从圣人位置上降下来,以解决与大贤之间的矛盾,提出伯夷柳下惠并非圣人说,“人皆称柳下惠为圣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语,非自见。”又曰:“夷、惠圣人,传者之误。”①但朱子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坚持偏圣的存在,强调圣人以所至而论,不以是否大全中正通化为准。并以药为譬指出偏方之药有时效果胜于中和之药,夷惠对世道人心教化作用甚为明显,有时还甚于至圣孔子。可见,朱子更侧重从客观教化效果来着眼。“未必误也。彼曰圣之清也、圣之和,则固不思不勉而从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于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备,所以不得班于孔子耳。……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圣而易能,有迹而易见,且世人之贪懦鄙薄者众,一闻其风而兴起焉,则其为效也速,而所及者广,譬如姜桂大黄之剂,虽非中和,然(文渊阁本有“其”字)于去病之功为捷。”②
圣人与君子。朱子将君子视为圣人的通称。“君子,圣人之通称也。”(《孟子集注·尽心上》)这样一来,君子就包含了圣人,也就意味着圣人可以视为君子的一种,即圣人君子,与通常概念下的君子相对照。但是圣人自身又有偏圣和至圣的区别,当圣人和君子相提并论时,君子就包含了偏圣,圣就特指至圣。如在“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章的注释中,朱子强调圣人(专指至圣)立法出命,性之安之,君子(包含偏圣)则需要行法俟命,反之复性。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圣与君子概念的紊乱。“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祸福有所不计,盖虽未至于自然,而已非有所为而为矣。此反之之事。吕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圣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圣人性之,君子所以复其性也。’”(《孟子集注·尽心下》)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