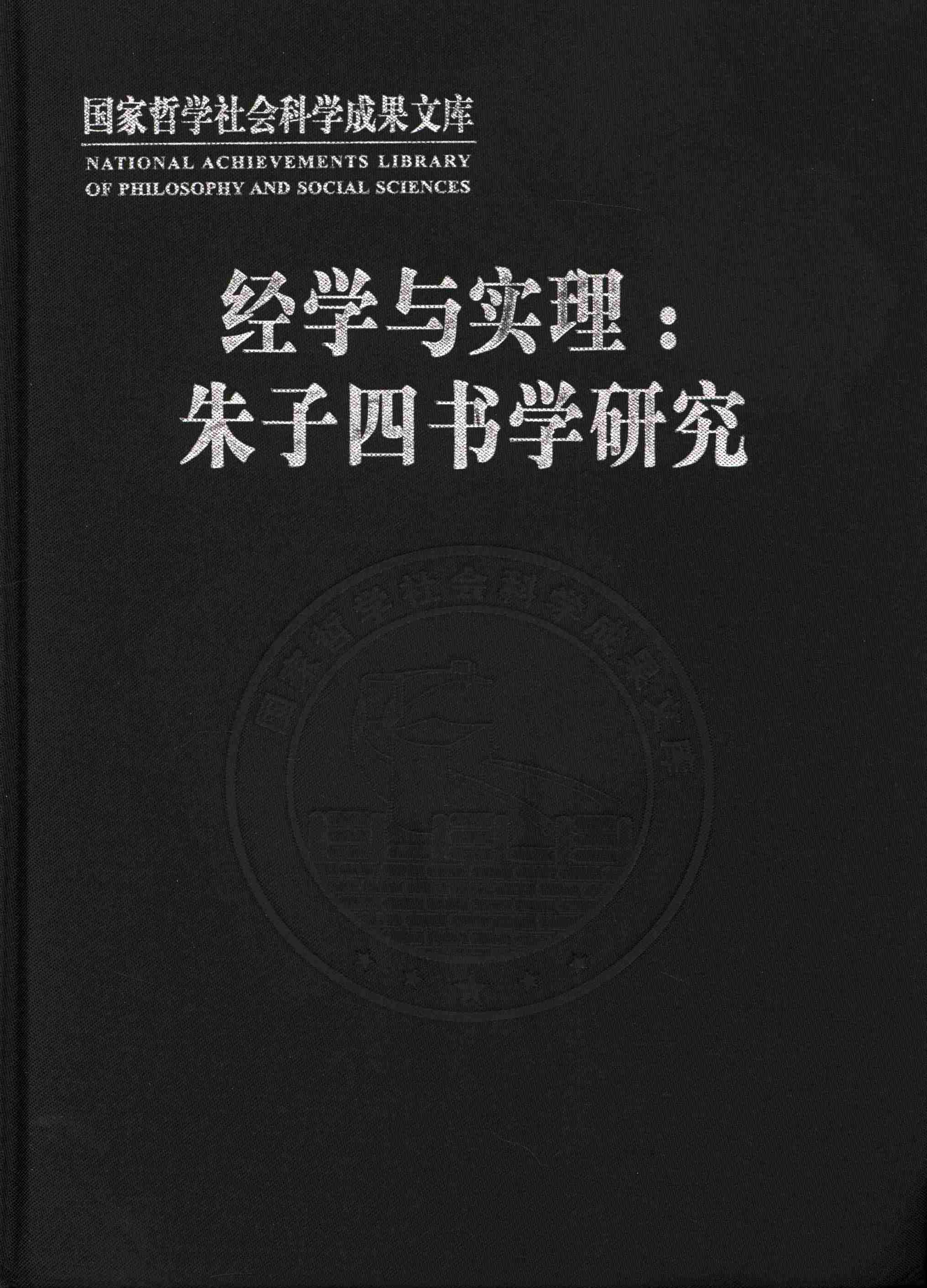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一节 超凡与入俗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804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超凡与入俗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296-311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圣人人格是儒家理想人格,实现这一人格乃儒学作为内圣之学的应有之义。在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的朱子看来,重新诠释圣人这一理想人格,对于端正学子为学方向,树立正确的人格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朱子四书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在接续理学前辈周、程等对圣人看法基础上,详尽分析了圣人人格超凡和入俗两个向度的特质,创造性提出至圣和偏圣的差别,并剖析了圣王、圣师、圣徒人格,是儒家圣人思想的一次总结,深刻影响了后世圣人观。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圣人人格是儒家理想人格,实现这一人格乃儒学作为内圣之学的应有之义。在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的朱子看来,重新诠释圣人这一理想人格,对于端正学子为学方向,树立正确的人格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朱子四书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在接续理学前辈周、程等对圣人看法基础上,详尽分析了圣人人格超凡和入俗两个向度的特质,创造性提出至圣和偏圣的差别,并剖析了圣王、圣师、圣徒人格,是儒家圣人思想的一次总结,深刻影响了后世圣人观。
一 周、程论圣
儒学本质上是一种教化之学,特别强调先知先觉的指引之功,故树立一种人格鹄的于为学之功就必不可少。圣人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其中,孔子居于集诸圣之大成的地位。孔子本人阐发最多者乃君子人格,于圣人论述甚少,后学孟子对圣人则多有阐发,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说,降低了圣人与常人的距离。宋儒接续孟子提出的圣人说,予以新的阐发,首发其轫者是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周敦颐提出并回答了“圣可学乎?”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他在《通书》中采用诚、性、神、公、仁义、天等概念对圣人人格做了突出说明。指出圣人根本特质在于诚,诚是圣人之本,圣人最大限度实现了诚,“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①“圣,诚而已。”(《通书·诚下》)他还从心性道德角度论圣,指出圣人就是尽乎本性,安乎本性者,“性焉安焉之谓圣。”(《通书·诚几德》)就圣人所为之道而言,又不离仁义中正而大公无私,“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通书·道》)“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通书·公》)圣人所至境界,与神、几相通,变化无方,见微知著;与天相通,深奥莫测,浩瀚无穷,“诚、神、几曰圣人。”(《通书·圣》)“圣同天,不亦深乎!”(《通书·圣蕴》)周敦颐强调了孔圣道德教化与天地四时相并的效用,“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通书·孔子下》)且进一步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的人格成就层次。
二程曾受学于周敦颐,教之寻求“孔颜乐处”境界,如何成圣乃二程理学所探求之核心问题。与周敦颐相比,二程除善于形容圣人境界效用外,尤为关注如何学以至圣。故离孔圣境界最为接近的颜子,就成为他们推尊的人物。如程颢说,“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二程集》卷一)①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对圣人之道作了详尽说明:他首先从天地宇宙之道入手,阐发人性善的源头。指出作为自然一员的人,和其他生物本无差异,但由于秉承了阴阳五行之秀气,故为万物灵长。然后从心性情的角度,说明人心在没有和外物接触处于未发状态时,就已经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本性。当人与外物相接触而感动内心时,就发出喜怒哀乐等七情,若不对此情感进行调控,任其发展,则将会变得泛滥无边,难以收拾,最终会湮没遮蔽本性,失去自我。故需要对情感加以控制约束,使其合乎中庸之道,无过不及。此工夫根本在于端正本心,保养本性。其前提是使本心保持澄明,知所趋向,然后再一一落实践履。程颐肯定了颜子好学之笃,学以至道的光辉成就,以此反驳世人所谓圣为生知,非学所至说,批判以此为由放弃对圣人人格追求的做法,斥责耽于记诵文辞之学的做法,认为和颜子之学相左,违背了圣学精神。程子的圣人之说甫一提出即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它道出了儒学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学为圣人。
宋儒不仅注重理论上阐发圣人这一理想人格,而且以极认真的态度探索如何在实践层面实现这一人格。他们对理想人格的深入探讨,其实既是自身所达到境界之反映,亦受到佛学刺激。佛学终极目的是立地成佛,它宣称佛是一个可以现之于世的鲜活肉身,是面向众生的人人皆可达到的目标。儒家在对此作出回应时,亦须证明圣人同样是人人皆可成就的。朱子早在从师延平时,即深知此一问题的重大意义,曾与之就圣贤气象展开过细致探讨。在四书注释中,朱子对孔子的圣人形象做了深入论述,尤其是揭示出圣人之所以为圣的超凡和入俗两个向度。
二 圣人之圣
朱子的《四书》注释,首次清楚揭示出圣人之所以为圣的特质。
圣人是天理、天道之化身,与天理合一无间,为道体之呈现。“圣人则表里精粗无不昭彻,其形骸虽是人,其实只是一团天理。”①“故人终不知,独有个天理与圣人相契耳。”②朱子从本体之理出发,论证圣人浑是天理,其作用处置万事万物,皆从天理上自然流出,无不中道合宜,犹如天地之诚实不伪,生生不息,虽有精粗远近之别而事物各得其宜。“吾道一以贯之章”注,“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里仁》)“饭疏食饮水章”注,“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论语集注·述而》)圣人是天理流行之实,为天理之客观呈现,举手投足,动静语默,皆合乎天理,中乎法度,无须勉强,乃天道精义之自然显现。“予欲无言”章注,“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著者。……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论语集注·阳货》)
圣人之大全。圣人周全无遗,道大德全,如天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备,始终本末精粗动静,皆为一致。在一切行为事物上皆体现出理之完善,不存在丝毫的疏漏和瑕疵。“达巷党人”章注,“尹氏曰:圣人道全而德备,不可以偏长目之也。”(《论语集注·子罕》)“子见南子章”注,“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论语集注·雍也》)这些皆强调圣人在道德上的纯全完备,达到了无往不可的地步,“圣人万善皆备,有一豪之失,此不足为圣人”①。
圣人形象与天地相通,如太极之一体浑然而备阴阳正气,于外在容貌间呈露中和气象,显示其与天合一之境界。②“子温而厉”章注,“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论语集注·泰伯》)圣人与天地化育相通的天地气象自然展露,时刻皆以道示人,无有丝毫隐藏。圣人之大全与其创生特质相联系,于生生不息,连续持久上显出圣之道大。圣人是如天地乾坤般的最大全体,是一至高至极至善的存在;如天道般流转不已,不可窥测。“发愤忘食”章注:“然深味之,则见其全体至极,纯亦不已之妙,有非圣人不能及者。”(《论语集注·子罕》)
圣人之通。“圣”从字义上讲,与听觉有着紧密关联,为“通”义。《说文》:“圣,通也。从耳,呈声。段注:《周礼》:‘六德教万民,智仁圣义忠和’。注云:‘圣,通而先识。《洪范》曰:‘睿作圣’,凡一事精通亦得为之圣。’《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按:声、圣字古相假借。”③朱子亦突出圣人通达无碍无有限量的特质,指出圣人无论在处己修德还是外在应物上,皆无所不通。这种通,亦是学习之结果。“固天纵之将圣”章注,“圣无不通,多能乃其余事。”(《论语集注·子罕》)圣人之通还表现在因革损益、鉴往知来的变通上。圣人对事物客观规律和演进态势有着准确把握,能够鉴往知来,如对于三代礼乐之因革损益,皆能辨析其变与不变之成分,由其不变之本质推出将来之发展,而其通变则非汉代所谓“谶纬术数之学”可比。“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注:“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非若后世谶纬术数之学也。”(《论语集注·为政》)朱子认为只有圣人的通变才能达至经权之中,故从圣人之体经用权上亦能见出圣人之通。“佛肸召”章注,“张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闻,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圣人体道之大权也。”(《论语集注·阳货》)
圣人之“神明不测、大而化之”。朱子指出圣人乃神奇明彻变化无端之称号,这是圣人之功效作用。圣人与君子、士之区别在于,同样的行为不仅做得完美无暇,更在于自然从容,毫不费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未能达此境者,则事事勉强费力,未能尽善尽美。“圣人,神明不测之号。”(《论语集注·述而》)“圣者,大而化之。”(《论语集注·述而》)“颜渊、季路侍”章的注释中,朱子充分诠释了圣人裁成辅相天地之道的化功,指出孔子志向即是安顿天下百姓,使各个阶层的民众皆有所养,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其施为则如天地一般,顺万物之自然,因其本性而点化,不假丝毫人为之力,实具天地无心成化之神奇效果。“至于夫子,则如天地之化工,付与万物而己不劳焉,此圣人之所为也。今夫羁靮以御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羁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羁靮之生由于马,圣人之化,亦犹是也。”(《论语集注·公冶长》)
圣人之化亦有变化无息之义。圣人与道体为一,其心如天地之创生变化,如时序之循环运转,无有停息,纯亦不已,乃天德王道。这种化的一个特点是造道极高而自然无为,圣人道德深厚,于民之治教皆顺其自然,无须有所作为,而自化成天下,泽被四海。尽管呈现出来的作用自然而然,但其心体之变化则神妙莫测。“无为而治者”章注,“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论语集注·卫灵公》)圣人之化上通于天,下达于地,周流遍布,难以预测,如天地一般,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人观其教化之功,而莫测其神奇之体。这种化功往往于圣人威仪举止间显现,对学者产生观感而化,化人于无形之效果。故朱子在“夫子至于是邦也”章引谢氏说:“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今去圣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尚能使人兴起,而况于亲炙之者乎!”(《论语集注·学而》)揭示了圣人内在德性所至显透于外,对他人心灵所产生的感化效果。以物质为喻,圣人好比一种无形的香味,与其接触之物,必默然不觉染上其味,受其感化。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有事实经验根据的。圣人之化,还体现在它不拘泥固执于某一点,随心所欲而皆一一合乎中道,达到无可无不可之化境。
三 圣人之常
浑然天理、道大德全、圣无不通、大而化之是朱子对圣人高明处的典型概括,但朱子并没有拔高、神化圣人。在突出其高明难及之时,又尽量将其从高悬的云端拉向平实的地面,强调圣人扎根于普通百姓中的庸常世俗一面。
常人之性情。朱子肯定圣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从普通人的情感来阐发圣人。圣人与常人之异在于得“情性之正”,无过不及。与佛道耶诸家超越之神相比,儒家圣人最亲切可感。与汉代神秘化、外在化、乃至粗俗化圣人不同,朱子将圣人平常化、内在化而不失其高明。朱子提出当从日常情性生活上识别圣人,从真实的性情入手见出圣人之可亲可感,并以之为入圣之门。如“子食于有丧者之侧”章注:“谢氏曰:‘学者于此二者,可见圣人情性之正也。能识圣人之情性,然后可以学道。’”(《论语集注·述而》)朱子提出,应从反映孔子平常仪容神态的《乡党》一篇寻求圣人之道,从圣人之日常举止言行中来求做圣人,他特意在《乡党篇》章目下分别引杨时和尹焞说以强调此点,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尹氏曰:“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论语集注·乡党》)
常人之学习。朱子尽管肯定圣人生而知之,但仍强调学习在成就圣人中不可或缺之作用。朱子认为圣人乃仁智双修的人格,孔子在知性上的成就,完全是学习的结果。圣人天生气质清明,生知者是义理分明,所学则是具体制度事件,即知性一面,这和学者并无不同。“十室之邑”章注,“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论语集注·公冶长》)朱子极为强调圣人之博学多能,认为“孔子天地间甚事不理会过!”①孔子自述其学习过程每一为学层次的升高,其实即是知性层面的提升,分别为知明、知精、知之至,由无所守、无所惑,达到无所思,是一个义理和知性双向并进过程。
常人之入世。朱子指出,圣人并非遁世独居的自修者,而是积极入世的济世者,是社群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圣人必定要在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在一个相互合作与奉献的世界里存在。圣人反对隐者脱离世俗责任而隐居独善,无论何时何地皆不忘其在世使命。因为圣人之心广大包容,博爱万物,故抱汲汲乎救世之志而不能忘怀,所以孔子才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之叹。(《论语集注·微子》)朱子在其他章的注释中亦屡屡突出此点,如“子路宿于石门”章注引胡氏说,“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论语集注·宪问》)“子击磬于卫”章注,“圣人心同天地,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不能一日忘也。”(《论语集注·宪问》)
常人之伦道。孟子提出“圣人,人伦之至也”说,首先揭示出圣人乃人伦规矩之至,并推崇舜在孝悌人伦之道上的垂范意义。尧舜作为圣人,是人伦的典范和标尺,是为道实存的体现,二人分别在君道和臣道上树立了楷模。《孟子·离娄上》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朱子注,“规矩尽所以为方员之理,犹圣人尽所以为人之道。”与常人相比,圣人能够尽性尽伦,尽其人道。凡圣之别在于尽性尽伦的程度而非性质,圣人超凡处在于能够尽性之至,“惟圣人都尽,无一豪之不尽,故为人伦之至”①。其次,圣人是性善的实存体现。朱子认为道性善和称尧舜有种内在关联,“‘道性善’与‘称尧舜’二句正相表里”,②乃抽象之理和具体实相之关系。“性善者,以理言之?称尧舜者,质其事以实之,所以互相发也。”③朱子指出,在先天性善上,人与尧舜相同,皆具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达成圣贤之可能,但由于私欲对本性的遮蔽,导致丧失本性之善。尧舜最大特点是能充扩其本性,尽其本原先天性善,成为性善的化身,为学者树立起一个向善的人伦标准、法则。朱子在《孟子·滕文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章注中称,“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汨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
再次,圣人尽人伦的方式极为自然。圣人存心天理,安行仁义,践形尽性,以达到形色天性的一体,常人则将形色天性分为两撅。朱子认为,真正尽性尽伦非常困难,要求处理好公私之间关系,兼顾家庭人伦和国家公义,舜于此做得极好。在圣人的价值谱系中,人伦之道居于最高位置,即便“遭人伦之变”也“不失天理之常也。”朱子在“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章引吴氏说:“言圣人不以公义废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义。舜之于象,仁之至,义之尽也。”(《孟子集注·万章上》)
四 圣圣之别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从理论上论述人人皆可以为圣,使理想中的圣人有了成为生活常态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泛化了圣人。针对孟子泛化和现实化圣人的倾向,朱子在理学的立场上予以推进,将圣人明确划分为两等: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判别标准在于是否从容中道不勉而至,或者说是仁智兼具还是仁而欠智。同时从性之与反之的角度,将尧舜与汤武分为两等,这样既坚持了圣的高远理想性,又俯就了圣的现实可行性,但同时亦使得偏圣与大贤之区别变得模糊。
圣之别:清、任、和的偏至之圣。《孟子·万章下》“集大成”章揭示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四圣的特点分别为清、任、和、时。这既是由圣人自身气质所造成的圣之类型差异,其中又存在大小偏全的层次差别。朱子首先指出四位圣人虽然存在类型上的差别,然而却有其作为圣的根本一致处,即于人伦道德的安而行之,自然从容而至其极至。“圣只是做到极至处,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谓之圣。”①他引用张载对清、和、任的解释,提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者各因其气质,在清、和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与孔子同为极至。“张子曰:无所杂者清之极,无所异者和之极。勉而清,非圣人之清;勉而和,非圣人之和。所谓圣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其次,朱子强调三者虽然为圣,但这种圣非中和通全之圣,而是一偏之圣,因为三者气质偏颇而不中正,各以其一节为圣,是在某一端力行至极,达到了无私欲、纯天理之不可企及境界,然于总体境界而言,则偏而不中,执而不通,任而不化,专而不全,不如孔子大成之圣的纯全中正,巧力皆备。“愚谓孔子仕、止、久、速,各当其可。盖兼三子之所以圣者而时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处合乎孔子,而不得为圣之时,何也?程子曰:‘终是任底意思在。’”(《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明确将圣和中分开,肯定这种偏圣并不是中,并没有达到中庸之境,“三子之德,但各至于一偏之极,不可谓之中。……圣,非中之谓也”①。尽管这种圣存在偏颇之处,但符合圣德性纯粹、纯乎天理、无有私欲的标准。“某问:既是如此,何以为圣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无驳杂。虽是过当,直是无纤豪查滓。”②朱子进一步指出伯夷等圣人造行虽极高,但却有“隘与不恭”的偏颇流弊,故不可以为学之矩范。“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孟子集注·公孙丑上》)朱子分析三圣偏而未中的原因在于天生气禀有所限制,同时在后天之知上亦有所不足,故未能达到通化之圣的地步。“厚之问:三圣事,是当初如此,是后来如此?”曰:“是知之不至。”③
朱子一方面既把伯夷等看作圣,同时又指出他们自身德性存在偏颇,不够完满,这就将圣之标准降低,由一种全体完美,尽善尽美,转化为凡在德性某一方面做到极至者。再由一种人格道德概念,转化延伸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凡是某一方面做得极好者,故有书圣、茶圣、诗圣之说,这是圣概念的普泛化。
金声玉振:孔子集大成之圣。孟子不满意伯夷等偏至之圣,而心仪于孔子的集大成之圣,给予了孔子最崇高的评价。可以说,孟子提出伯夷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衬托孔子的大成之圣。朱子同样突出了孔子的重要性,在儒家道统谱系中给予孔子远迈尧舜的至高定位。他指出在儒学道统中,在政统和道统分化之时,孔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延续道统,开创学统的作用,其功劳远胜于尧舜。“圣人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垂于世。”①孟子以金声玉振比喻孔子之集大成,朱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孔子大成之圣和三子偏至之圣的差别:孔子集三圣之长而为一大成之圣,无所不备、无所不通,三子乃偏于小成。夫子和三子,恰如太和元气流行于春夏秋冬之四时也。“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批评前辈学者为维护圣人权威而回避圣人之间优劣之分,指出应认真面对这一客观事实。他以具体事例指出伯夷等本来即存在欠缺不足,其弊病与生俱来,非末流所至,避嫌之论应当取消。或问:“如伯夷之清而‘不念旧恶’,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之清、圣之和也,但其流弊则有隘与不恭之失。”曰:“这也是诸先生恐伤触二子,所以说流弊。今以圣人观二子,则二子多有欠阙处;才有欠阙处,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说他‘隘与不恭’,不曾说其末流如此。如‘不念旧恶’、‘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处。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处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说得。大率前辈之论多是如此。”②朱子认为三子和孔子之别在于知上。三子之偏,源于缺少知上工夫,其初始即看得道理有偏差,所以其终之行亦止于偏至。孔子高明处在于知上已经无所不尽,故于行上能赅括包容,知行始终圆融无缺。“见孔子巧力俱全,而圣智兼备,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尽。”(《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将智圣分开,认为各自代表知德一面。圣并不能包含智;反之,智倒有包含圣之意味,如真知即包含行,并再三强调大圣即是德智双修,巧力兼全。“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朱子根据知先行后说,认为知是行之源头,行是知之落实,一旦作为源头的知上有偏,则行上亦必然有所不足。孔子作为大成之圣,关键在于知上明了事理。“功夫紧要处,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极于一偏,缘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终之成也亦各至于一偏之极。孔子合下尽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无所不尽,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该毕备,而无一德一行之或阙。”①朱子指出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的差别还在于是否时中。孟子以射箭为喻,说明三子与夫子之差别,在于未能做到巧力兼具,至而且中。朱子认为孔子具有中正、时中、中和的大圣气象,时时刻刻皆处于中正之位。三子在偏处达到圣,至而不中,大圣则在全和中之统一上达到和谐。三子极其一偏,如四时之一季,音乐之一成;大圣则是大成之音,太和元气之流行,遍布于四时中。②“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圣之至与至于圣:性之与反之。在圣人层次上,除了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外,还有尧舜与汤武之间的性之与反之的差别。孟子对同为圣人的尧舜和汤武数次提出性之、反之的高下评价。朱子对此作了具体分析,肯定圣人之至与至于圣人的客观差别。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朱子注:“性者,得全于天,无所污坏,不假修为,圣之至也。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语,盖自孟子发之。’吕氏曰:‘无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于无意,复性者也。尧舜不失其性,汤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则一也。’”(《孟子集注·尽心下》)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朱子注:“尧舜天性浑全,不假修习。汤武修身体道,以复其性。尹氏曰:“性之者,与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则一也。”(《孟子集注·尽心上》)
朱子认为“性之”“身之”用以突出尧舜与汤武之分别,关键在于是否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性者”直下保全天赐性理,不受外界污损破坏,顺其自然而不需人为努力,这是圣人中的极品,圣之至也。“反之”则需要人为努力来消除后天所沾染之不完善,以恢复其天性,最终达到圣的境界。二者之别,其实即是无意安行之顺性还是有意利行之复性。“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①程颢认为孟子对尧舜汤武作出高下之分,指出二者区别,是前所未有之开创性思想。“性、反”差距体现在工夫上:性之自然无意,挥洒自如,安行而不涉人力;反之则需勉强复性之功,以返乎本性,当然二者在最终成就上皆为圣人。朱子还据史实指出尧舜与汤武是常与变、经与权的差别,汤武之放伐尽管变而合乎中道,然终究不如尧舜之禅让自然合理,二者存在等差,“如尧舜与汤武真个争分数,有等级”②。批评学者对此理解不够,有意回避尧舜汤武高下之别。圣人与常人自然不在一个道德层次上,但是圣圣相较,天然存在一个优劣之分,而且孔子“尽善尽美”之别已有此意,“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分明有优劣不同,却要都回护教一般,少间便说不行。且如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若是以常人去比圣贤,则说是与不是不得;若以圣贤比圣贤,则自有是与不是处,须与他分个优劣。今若隐避回互不说,亦不可”③。除肯定尧舜与汤武的差别外,朱子还对同为反之的汤武区别出高低,认为汤在修为工夫上又较胜于武。“‘汤武反之’,其反之虽同,然细看来,武王终是疏略,成汤却孜孜向进。”“汤反之之工恐更精密。”①
圣、贤、君子之别。圣、贤、君子皆是儒家之理想人格,三者之间有同有异,朱子在处理三者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由偏圣这一概念引起与大贤、君子概念的紊乱。
圣与贤的异同。朱子在诠释《论》、《孟》时,多数地方并不分别圣贤,常把“圣贤”当作一词组连用,如“圣贤亦何所用心哉”“圣贤之心”等,这强调了圣贤相同的一面。但朱子有时又特意区分圣贤,剖析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讨论孔孟之异。朱子指出孔孟一为圣一为贤,二者存在客观差别。这种圣贤之别显露于答问言辞等诸多方面,如孟子言语时常露出锋芒,孔子则浑然无迹,透过言语即见出修为之高低。朱子在“孟子告齐宣王”章注中引潘兴嗣说:“孟子告齐王之言,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孟子集注·离娄》下)在“孟子曰说大人”章注中引杨氏说:“孟子此章,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孟子集注·尽心下》)朱子引用杨时的话,批评孟子言语之间极为明显的用己之长,较人之短的意图,显得粗率狂妄,不符合圣人气象。如在对待大人态度上,孔孟截然相反,孔子畏敬,孟子藐视。这些都见出圣贤有别。
但朱子提出偏圣说,造成偏圣与贤人层次区分上的模糊。一方面只有至圣才是性之安之,偏圣与贤人一样,皆须反之复性工夫,如此一来,偏圣与贤人就难以区别了。而且,在朱子看来,作为大贤的颜子在修为上(如巧和中)有超过伯夷等偏圣处,“颜子优于汤武”,②只是在行上不够充足,力有未至而已。另一大贤孟子与偏圣之高低,亦不好评论,这就造成贤与圣的层次上的混乱。正是有见于伯夷等偏圣存在不完善处,故程子提出将他们从圣人位置上降下来,以解决与大贤之间的矛盾,提出伯夷柳下惠并非圣人说,“人皆称柳下惠为圣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语,非自见。”又曰:“夷、惠圣人,传者之误。”①但朱子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坚持偏圣的存在,强调圣人以所至而论,不以是否大全中正通化为准。并以药为譬指出偏方之药有时效果胜于中和之药,夷惠对世道人心教化作用甚为明显,有时还甚于至圣孔子。可见,朱子更侧重从客观教化效果来着眼。“未必误也。彼曰圣之清也、圣之和,则固不思不勉而从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于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备,所以不得班于孔子耳。……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圣而易能,有迹而易见,且世人之贪懦鄙薄者众,一闻其风而兴起焉,则其为效也速,而所及者广,譬如姜桂大黄之剂,虽非中和,然(文渊阁本有“其”字)于去病之功为捷。”②
圣人与君子。朱子将君子视为圣人的通称。“君子,圣人之通称也。”(《孟子集注·尽心上》)这样一来,君子就包含了圣人,也就意味着圣人可以视为君子的一种,即圣人君子,与通常概念下的君子相对照。但是圣人自身又有偏圣和至圣的区别,当圣人和君子相提并论时,君子就包含了偏圣,圣就特指至圣。如在“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章的注释中,朱子强调圣人(专指至圣)立法出命,性之安之,君子(包含偏圣)则需要行法俟命,反之复性。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圣与君子概念的紊乱。“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祸福有所不计,盖虽未至于自然,而已非有所为而为矣。此反之之事。吕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圣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圣人性之,君子所以复其性也。’”(《孟子集注·尽心下》)
五圣人之衍
孟子对圣人的论述较为全面,除圣人外,还论述了圣王理想、圣师愿望、圣徒使命。朱子在此基础上,阐发了由圣衍生出的圣王、圣师、圣徒,强调了圣王、圣师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圣人之徒捍卫、传承儒学,辟除邪说的护教传道。
圣王。在对圣的论述中,孟子很重视圣兼具外王的一面。他痛心于尧舜之道既衰而圣王不起所造成的社会混乱状况,故周游诸国,劝说君王行王道之事,希望能有圣而王者出现,以收拾霸而王之局面。朱子亦非常注意揭示圣而王的特点,要求圣者必须具有王者的政治才能,这样他的仁者之功才会受益广大,并以舜、孔为例,指出圣人过化存神妙用无边,自然妥帖,与天地化生陶冶万物异曲同工,体现出王道效果之广大久远,神奇莫测,远胜霸道。“君子,圣人之通称也。所过者化,身所经历之处,即人无不化,如舜之耕历山而田者逊畔,陶河滨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处便神妙不测,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绥斯来、动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业之盛,乃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举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补塞其罅漏而已。此则王道之所以为大,而学者所当尽心也。”(《孟子集注·尽心上》)朱子注“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亦突出孔子之事功,认为“圣人无不盛”,在任何事上都能做得很好,于外王上也不例外,自然有其神功妙化。
圣师。自周公后,圣王传统已经断绝,此后再也没有赓续上。故藉内圣修为而为圣师,成为儒家学者更切近现实的追求。儒家学者希望以内圣之功为基础,通过自身的率先垂范成为道德导师,以此影响整个社会风俗人伦,以实现外王之功。孟子提出“圣人百世之师也”,通过圣师这一新的定位宣扬了儒者功业之深远,同时又给予了儒者很好的自我定位。朱子认为,圣人居于王者师的地位,虽然不据有天下,但是其功业恩泽同样能广被天下,圣师并不以个人一己得失为念,而是以天下之公利为人生目标,至公无我。“滕国褊小,虽行仁政,未必能兴王业;然为王者师,则虽不有天下,而其泽亦足以及天下矣。”(《孟子集注·滕文公上》)
圣徒。孟子周流一生,并未能够获得圣师之地位。退而求其次,认为能够传扬圣人学说,捍卫圣人思想,抗击异端学说者,亦可为圣门中人,即圣人之徒也,这是孟子对儒者的又一定位。“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下》)孟子提出严拒杨墨异端,捍卫儒家学说的态度决心,获得身处同一境地中的宋儒极大共鸣。“盖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弒之祸,故孟子深惧而力救之。”(《孟子集注·滕文公下》)朱子在对孟子此段思想的阐发中,特别强调了异端邪说对人心的冲击破坏,比之为洪水猛兽、夷狄篡弒。称赞凡是能够起而辟之者,即使未能知道,但为学趋向已经走上正路,可以视为圣门中人。孳孳为善者,即是行走在圣人之道上的圣徒。“言苟有能为此距杨墨之说者,则其所趋正矣,虽未必知道,是亦圣人之徒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下》)
总之,朱子对圣人观念的细加辨析,突出了孔子作为至圣的完满性,反映出儒家“止于至善”的人格理念。同时不惜反对程子之说,宁冒混淆人格层次之弊,坚持降低一等的偏圣说,是在承认偏圣人格有所不足的基础上,强调他们所实际具有的教化效果,表明了成就圣人的现实可行性。朱子在继承前辈学者理论基础上,对儒家圣人说作出了创造性理解,对后世的圣人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学习、探究朱子的圣人思想,对理解儒家理学人格,增进个人修养实践皆具有重要意义。
一 周、程论圣
儒学本质上是一种教化之学,特别强调先知先觉的指引之功,故树立一种人格鹄的于为学之功就必不可少。圣人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其中,孔子居于集诸圣之大成的地位。孔子本人阐发最多者乃君子人格,于圣人论述甚少,后学孟子对圣人则多有阐发,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说,降低了圣人与常人的距离。宋儒接续孟子提出的圣人说,予以新的阐发,首发其轫者是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周敦颐提出并回答了“圣可学乎?”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他在《通书》中采用诚、性、神、公、仁义、天等概念对圣人人格做了突出说明。指出圣人根本特质在于诚,诚是圣人之本,圣人最大限度实现了诚,“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①“圣,诚而已。”(《通书·诚下》)他还从心性道德角度论圣,指出圣人就是尽乎本性,安乎本性者,“性焉安焉之谓圣。”(《通书·诚几德》)就圣人所为之道而言,又不离仁义中正而大公无私,“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通书·道》)“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通书·公》)圣人所至境界,与神、几相通,变化无方,见微知著;与天相通,深奥莫测,浩瀚无穷,“诚、神、几曰圣人。”(《通书·圣》)“圣同天,不亦深乎!”(《通书·圣蕴》)周敦颐强调了孔圣道德教化与天地四时相并的效用,“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通书·孔子下》)且进一步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的人格成就层次。
二程曾受学于周敦颐,教之寻求“孔颜乐处”境界,如何成圣乃二程理学所探求之核心问题。与周敦颐相比,二程除善于形容圣人境界效用外,尤为关注如何学以至圣。故离孔圣境界最为接近的颜子,就成为他们推尊的人物。如程颢说,“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二程集》卷一)①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对圣人之道作了详尽说明:他首先从天地宇宙之道入手,阐发人性善的源头。指出作为自然一员的人,和其他生物本无差异,但由于秉承了阴阳五行之秀气,故为万物灵长。然后从心性情的角度,说明人心在没有和外物接触处于未发状态时,就已经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本性。当人与外物相接触而感动内心时,就发出喜怒哀乐等七情,若不对此情感进行调控,任其发展,则将会变得泛滥无边,难以收拾,最终会湮没遮蔽本性,失去自我。故需要对情感加以控制约束,使其合乎中庸之道,无过不及。此工夫根本在于端正本心,保养本性。其前提是使本心保持澄明,知所趋向,然后再一一落实践履。程颐肯定了颜子好学之笃,学以至道的光辉成就,以此反驳世人所谓圣为生知,非学所至说,批判以此为由放弃对圣人人格追求的做法,斥责耽于记诵文辞之学的做法,认为和颜子之学相左,违背了圣学精神。程子的圣人之说甫一提出即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它道出了儒学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学为圣人。
宋儒不仅注重理论上阐发圣人这一理想人格,而且以极认真的态度探索如何在实践层面实现这一人格。他们对理想人格的深入探讨,其实既是自身所达到境界之反映,亦受到佛学刺激。佛学终极目的是立地成佛,它宣称佛是一个可以现之于世的鲜活肉身,是面向众生的人人皆可达到的目标。儒家在对此作出回应时,亦须证明圣人同样是人人皆可成就的。朱子早在从师延平时,即深知此一问题的重大意义,曾与之就圣贤气象展开过细致探讨。在四书注释中,朱子对孔子的圣人形象做了深入论述,尤其是揭示出圣人之所以为圣的超凡和入俗两个向度。
二 圣人之圣
朱子的《四书》注释,首次清楚揭示出圣人之所以为圣的特质。
圣人是天理、天道之化身,与天理合一无间,为道体之呈现。“圣人则表里精粗无不昭彻,其形骸虽是人,其实只是一团天理。”①“故人终不知,独有个天理与圣人相契耳。”②朱子从本体之理出发,论证圣人浑是天理,其作用处置万事万物,皆从天理上自然流出,无不中道合宜,犹如天地之诚实不伪,生生不息,虽有精粗远近之别而事物各得其宜。“吾道一以贯之章”注,“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里仁》)“饭疏食饮水章”注,“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论语集注·述而》)圣人是天理流行之实,为天理之客观呈现,举手投足,动静语默,皆合乎天理,中乎法度,无须勉强,乃天道精义之自然显现。“予欲无言”章注,“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著者。……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论语集注·阳货》)
圣人之大全。圣人周全无遗,道大德全,如天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备,始终本末精粗动静,皆为一致。在一切行为事物上皆体现出理之完善,不存在丝毫的疏漏和瑕疵。“达巷党人”章注,“尹氏曰:圣人道全而德备,不可以偏长目之也。”(《论语集注·子罕》)“子见南子章”注,“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论语集注·雍也》)这些皆强调圣人在道德上的纯全完备,达到了无往不可的地步,“圣人万善皆备,有一豪之失,此不足为圣人”①。
圣人形象与天地相通,如太极之一体浑然而备阴阳正气,于外在容貌间呈露中和气象,显示其与天合一之境界。②“子温而厉”章注,“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论语集注·泰伯》)圣人与天地化育相通的天地气象自然展露,时刻皆以道示人,无有丝毫隐藏。圣人之大全与其创生特质相联系,于生生不息,连续持久上显出圣之道大。圣人是如天地乾坤般的最大全体,是一至高至极至善的存在;如天道般流转不已,不可窥测。“发愤忘食”章注:“然深味之,则见其全体至极,纯亦不已之妙,有非圣人不能及者。”(《论语集注·子罕》)
圣人之通。“圣”从字义上讲,与听觉有着紧密关联,为“通”义。《说文》:“圣,通也。从耳,呈声。段注:《周礼》:‘六德教万民,智仁圣义忠和’。注云:‘圣,通而先识。《洪范》曰:‘睿作圣’,凡一事精通亦得为之圣。’《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按:声、圣字古相假借。”③朱子亦突出圣人通达无碍无有限量的特质,指出圣人无论在处己修德还是外在应物上,皆无所不通。这种通,亦是学习之结果。“固天纵之将圣”章注,“圣无不通,多能乃其余事。”(《论语集注·子罕》)圣人之通还表现在因革损益、鉴往知来的变通上。圣人对事物客观规律和演进态势有着准确把握,能够鉴往知来,如对于三代礼乐之因革损益,皆能辨析其变与不变之成分,由其不变之本质推出将来之发展,而其通变则非汉代所谓“谶纬术数之学”可比。“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注:“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非若后世谶纬术数之学也。”(《论语集注·为政》)朱子认为只有圣人的通变才能达至经权之中,故从圣人之体经用权上亦能见出圣人之通。“佛肸召”章注,“张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闻,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圣人体道之大权也。”(《论语集注·阳货》)
圣人之“神明不测、大而化之”。朱子指出圣人乃神奇明彻变化无端之称号,这是圣人之功效作用。圣人与君子、士之区别在于,同样的行为不仅做得完美无暇,更在于自然从容,毫不费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未能达此境者,则事事勉强费力,未能尽善尽美。“圣人,神明不测之号。”(《论语集注·述而》)“圣者,大而化之。”(《论语集注·述而》)“颜渊、季路侍”章的注释中,朱子充分诠释了圣人裁成辅相天地之道的化功,指出孔子志向即是安顿天下百姓,使各个阶层的民众皆有所养,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其施为则如天地一般,顺万物之自然,因其本性而点化,不假丝毫人为之力,实具天地无心成化之神奇效果。“至于夫子,则如天地之化工,付与万物而己不劳焉,此圣人之所为也。今夫羁靮以御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羁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羁靮之生由于马,圣人之化,亦犹是也。”(《论语集注·公冶长》)
圣人之化亦有变化无息之义。圣人与道体为一,其心如天地之创生变化,如时序之循环运转,无有停息,纯亦不已,乃天德王道。这种化的一个特点是造道极高而自然无为,圣人道德深厚,于民之治教皆顺其自然,无须有所作为,而自化成天下,泽被四海。尽管呈现出来的作用自然而然,但其心体之变化则神妙莫测。“无为而治者”章注,“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论语集注·卫灵公》)圣人之化上通于天,下达于地,周流遍布,难以预测,如天地一般,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人观其教化之功,而莫测其神奇之体。这种化功往往于圣人威仪举止间显现,对学者产生观感而化,化人于无形之效果。故朱子在“夫子至于是邦也”章引谢氏说:“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今去圣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尚能使人兴起,而况于亲炙之者乎!”(《论语集注·学而》)揭示了圣人内在德性所至显透于外,对他人心灵所产生的感化效果。以物质为喻,圣人好比一种无形的香味,与其接触之物,必默然不觉染上其味,受其感化。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有事实经验根据的。圣人之化,还体现在它不拘泥固执于某一点,随心所欲而皆一一合乎中道,达到无可无不可之化境。
三 圣人之常
浑然天理、道大德全、圣无不通、大而化之是朱子对圣人高明处的典型概括,但朱子并没有拔高、神化圣人。在突出其高明难及之时,又尽量将其从高悬的云端拉向平实的地面,强调圣人扎根于普通百姓中的庸常世俗一面。
常人之性情。朱子肯定圣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从普通人的情感来阐发圣人。圣人与常人之异在于得“情性之正”,无过不及。与佛道耶诸家超越之神相比,儒家圣人最亲切可感。与汉代神秘化、外在化、乃至粗俗化圣人不同,朱子将圣人平常化、内在化而不失其高明。朱子提出当从日常情性生活上识别圣人,从真实的性情入手见出圣人之可亲可感,并以之为入圣之门。如“子食于有丧者之侧”章注:“谢氏曰:‘学者于此二者,可见圣人情性之正也。能识圣人之情性,然后可以学道。’”(《论语集注·述而》)朱子提出,应从反映孔子平常仪容神态的《乡党》一篇寻求圣人之道,从圣人之日常举止言行中来求做圣人,他特意在《乡党篇》章目下分别引杨时和尹焞说以强调此点,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尹氏曰:“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论语集注·乡党》)
常人之学习。朱子尽管肯定圣人生而知之,但仍强调学习在成就圣人中不可或缺之作用。朱子认为圣人乃仁智双修的人格,孔子在知性上的成就,完全是学习的结果。圣人天生气质清明,生知者是义理分明,所学则是具体制度事件,即知性一面,这和学者并无不同。“十室之邑”章注,“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论语集注·公冶长》)朱子极为强调圣人之博学多能,认为“孔子天地间甚事不理会过!”①孔子自述其学习过程每一为学层次的升高,其实即是知性层面的提升,分别为知明、知精、知之至,由无所守、无所惑,达到无所思,是一个义理和知性双向并进过程。
常人之入世。朱子指出,圣人并非遁世独居的自修者,而是积极入世的济世者,是社群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圣人必定要在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在一个相互合作与奉献的世界里存在。圣人反对隐者脱离世俗责任而隐居独善,无论何时何地皆不忘其在世使命。因为圣人之心广大包容,博爱万物,故抱汲汲乎救世之志而不能忘怀,所以孔子才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之叹。(《论语集注·微子》)朱子在其他章的注释中亦屡屡突出此点,如“子路宿于石门”章注引胡氏说,“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论语集注·宪问》)“子击磬于卫”章注,“圣人心同天地,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不能一日忘也。”(《论语集注·宪问》)
常人之伦道。孟子提出“圣人,人伦之至也”说,首先揭示出圣人乃人伦规矩之至,并推崇舜在孝悌人伦之道上的垂范意义。尧舜作为圣人,是人伦的典范和标尺,是为道实存的体现,二人分别在君道和臣道上树立了楷模。《孟子·离娄上》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朱子注,“规矩尽所以为方员之理,犹圣人尽所以为人之道。”与常人相比,圣人能够尽性尽伦,尽其人道。凡圣之别在于尽性尽伦的程度而非性质,圣人超凡处在于能够尽性之至,“惟圣人都尽,无一豪之不尽,故为人伦之至”①。其次,圣人是性善的实存体现。朱子认为道性善和称尧舜有种内在关联,“‘道性善’与‘称尧舜’二句正相表里”,②乃抽象之理和具体实相之关系。“性善者,以理言之?称尧舜者,质其事以实之,所以互相发也。”③朱子指出,在先天性善上,人与尧舜相同,皆具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达成圣贤之可能,但由于私欲对本性的遮蔽,导致丧失本性之善。尧舜最大特点是能充扩其本性,尽其本原先天性善,成为性善的化身,为学者树立起一个向善的人伦标准、法则。朱子在《孟子·滕文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章注中称,“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汨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
再次,圣人尽人伦的方式极为自然。圣人存心天理,安行仁义,践形尽性,以达到形色天性的一体,常人则将形色天性分为两撅。朱子认为,真正尽性尽伦非常困难,要求处理好公私之间关系,兼顾家庭人伦和国家公义,舜于此做得极好。在圣人的价值谱系中,人伦之道居于最高位置,即便“遭人伦之变”也“不失天理之常也。”朱子在“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章引吴氏说:“言圣人不以公义废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义。舜之于象,仁之至,义之尽也。”(《孟子集注·万章上》)
四 圣圣之别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从理论上论述人人皆可以为圣,使理想中的圣人有了成为生活常态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泛化了圣人。针对孟子泛化和现实化圣人的倾向,朱子在理学的立场上予以推进,将圣人明确划分为两等: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判别标准在于是否从容中道不勉而至,或者说是仁智兼具还是仁而欠智。同时从性之与反之的角度,将尧舜与汤武分为两等,这样既坚持了圣的高远理想性,又俯就了圣的现实可行性,但同时亦使得偏圣与大贤之区别变得模糊。
圣之别:清、任、和的偏至之圣。《孟子·万章下》“集大成”章揭示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四圣的特点分别为清、任、和、时。这既是由圣人自身气质所造成的圣之类型差异,其中又存在大小偏全的层次差别。朱子首先指出四位圣人虽然存在类型上的差别,然而却有其作为圣的根本一致处,即于人伦道德的安而行之,自然从容而至其极至。“圣只是做到极至处,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谓之圣。”①他引用张载对清、和、任的解释,提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者各因其气质,在清、和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与孔子同为极至。“张子曰:无所杂者清之极,无所异者和之极。勉而清,非圣人之清;勉而和,非圣人之和。所谓圣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其次,朱子强调三者虽然为圣,但这种圣非中和通全之圣,而是一偏之圣,因为三者气质偏颇而不中正,各以其一节为圣,是在某一端力行至极,达到了无私欲、纯天理之不可企及境界,然于总体境界而言,则偏而不中,执而不通,任而不化,专而不全,不如孔子大成之圣的纯全中正,巧力皆备。“愚谓孔子仕、止、久、速,各当其可。盖兼三子之所以圣者而时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处合乎孔子,而不得为圣之时,何也?程子曰:‘终是任底意思在。’”(《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明确将圣和中分开,肯定这种偏圣并不是中,并没有达到中庸之境,“三子之德,但各至于一偏之极,不可谓之中。……圣,非中之谓也”①。尽管这种圣存在偏颇之处,但符合圣德性纯粹、纯乎天理、无有私欲的标准。“某问:既是如此,何以为圣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无驳杂。虽是过当,直是无纤豪查滓。”②朱子进一步指出伯夷等圣人造行虽极高,但却有“隘与不恭”的偏颇流弊,故不可以为学之矩范。“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孟子集注·公孙丑上》)朱子分析三圣偏而未中的原因在于天生气禀有所限制,同时在后天之知上亦有所不足,故未能达到通化之圣的地步。“厚之问:三圣事,是当初如此,是后来如此?”曰:“是知之不至。”③
朱子一方面既把伯夷等看作圣,同时又指出他们自身德性存在偏颇,不够完满,这就将圣之标准降低,由一种全体完美,尽善尽美,转化为凡在德性某一方面做到极至者。再由一种人格道德概念,转化延伸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凡是某一方面做得极好者,故有书圣、茶圣、诗圣之说,这是圣概念的普泛化。
金声玉振:孔子集大成之圣。孟子不满意伯夷等偏至之圣,而心仪于孔子的集大成之圣,给予了孔子最崇高的评价。可以说,孟子提出伯夷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衬托孔子的大成之圣。朱子同样突出了孔子的重要性,在儒家道统谱系中给予孔子远迈尧舜的至高定位。他指出在儒学道统中,在政统和道统分化之时,孔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延续道统,开创学统的作用,其功劳远胜于尧舜。“圣人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垂于世。”①孟子以金声玉振比喻孔子之集大成,朱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孔子大成之圣和三子偏至之圣的差别:孔子集三圣之长而为一大成之圣,无所不备、无所不通,三子乃偏于小成。夫子和三子,恰如太和元气流行于春夏秋冬之四时也。“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批评前辈学者为维护圣人权威而回避圣人之间优劣之分,指出应认真面对这一客观事实。他以具体事例指出伯夷等本来即存在欠缺不足,其弊病与生俱来,非末流所至,避嫌之论应当取消。或问:“如伯夷之清而‘不念旧恶’,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之清、圣之和也,但其流弊则有隘与不恭之失。”曰:“这也是诸先生恐伤触二子,所以说流弊。今以圣人观二子,则二子多有欠阙处;才有欠阙处,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说他‘隘与不恭’,不曾说其末流如此。如‘不念旧恶’、‘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处。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处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说得。大率前辈之论多是如此。”②朱子认为三子和孔子之别在于知上。三子之偏,源于缺少知上工夫,其初始即看得道理有偏差,所以其终之行亦止于偏至。孔子高明处在于知上已经无所不尽,故于行上能赅括包容,知行始终圆融无缺。“见孔子巧力俱全,而圣智兼备,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尽。”(《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朱子将智圣分开,认为各自代表知德一面。圣并不能包含智;反之,智倒有包含圣之意味,如真知即包含行,并再三强调大圣即是德智双修,巧力兼全。“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朱子根据知先行后说,认为知是行之源头,行是知之落实,一旦作为源头的知上有偏,则行上亦必然有所不足。孔子作为大成之圣,关键在于知上明了事理。“功夫紧要处,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极于一偏,缘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终之成也亦各至于一偏之极。孔子合下尽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无所不尽,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该毕备,而无一德一行之或阙。”①朱子指出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的差别还在于是否时中。孟子以射箭为喻,说明三子与夫子之差别,在于未能做到巧力兼具,至而且中。朱子认为孔子具有中正、时中、中和的大圣气象,时时刻刻皆处于中正之位。三子在偏处达到圣,至而不中,大圣则在全和中之统一上达到和谐。三子极其一偏,如四时之一季,音乐之一成;大圣则是大成之音,太和元气之流行,遍布于四时中。②“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孟子集注·集大成章》)
圣之至与至于圣:性之与反之。在圣人层次上,除了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外,还有尧舜与汤武之间的性之与反之的差别。孟子对同为圣人的尧舜和汤武数次提出性之、反之的高下评价。朱子对此作了具体分析,肯定圣人之至与至于圣人的客观差别。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朱子注:“性者,得全于天,无所污坏,不假修为,圣之至也。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语,盖自孟子发之。’吕氏曰:‘无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于无意,复性者也。尧舜不失其性,汤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则一也。’”(《孟子集注·尽心下》)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朱子注:“尧舜天性浑全,不假修习。汤武修身体道,以复其性。尹氏曰:“性之者,与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则一也。”(《孟子集注·尽心上》)
朱子认为“性之”“身之”用以突出尧舜与汤武之分别,关键在于是否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性者”直下保全天赐性理,不受外界污损破坏,顺其自然而不需人为努力,这是圣人中的极品,圣之至也。“反之”则需要人为努力来消除后天所沾染之不完善,以恢复其天性,最终达到圣的境界。二者之别,其实即是无意安行之顺性还是有意利行之复性。“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①程颢认为孟子对尧舜汤武作出高下之分,指出二者区别,是前所未有之开创性思想。“性、反”差距体现在工夫上:性之自然无意,挥洒自如,安行而不涉人力;反之则需勉强复性之功,以返乎本性,当然二者在最终成就上皆为圣人。朱子还据史实指出尧舜与汤武是常与变、经与权的差别,汤武之放伐尽管变而合乎中道,然终究不如尧舜之禅让自然合理,二者存在等差,“如尧舜与汤武真个争分数,有等级”②。批评学者对此理解不够,有意回避尧舜汤武高下之别。圣人与常人自然不在一个道德层次上,但是圣圣相较,天然存在一个优劣之分,而且孔子“尽善尽美”之别已有此意,“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分明有优劣不同,却要都回护教一般,少间便说不行。且如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若是以常人去比圣贤,则说是与不是不得;若以圣贤比圣贤,则自有是与不是处,须与他分个优劣。今若隐避回互不说,亦不可”③。除肯定尧舜与汤武的差别外,朱子还对同为反之的汤武区别出高低,认为汤在修为工夫上又较胜于武。“‘汤武反之’,其反之虽同,然细看来,武王终是疏略,成汤却孜孜向进。”“汤反之之工恐更精密。”①
圣、贤、君子之别。圣、贤、君子皆是儒家之理想人格,三者之间有同有异,朱子在处理三者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由偏圣这一概念引起与大贤、君子概念的紊乱。
圣与贤的异同。朱子在诠释《论》、《孟》时,多数地方并不分别圣贤,常把“圣贤”当作一词组连用,如“圣贤亦何所用心哉”“圣贤之心”等,这强调了圣贤相同的一面。但朱子有时又特意区分圣贤,剖析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讨论孔孟之异。朱子指出孔孟一为圣一为贤,二者存在客观差别。这种圣贤之别显露于答问言辞等诸多方面,如孟子言语时常露出锋芒,孔子则浑然无迹,透过言语即见出修为之高低。朱子在“孟子告齐宣王”章注中引潘兴嗣说:“孟子告齐王之言,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孟子集注·离娄》下)在“孟子曰说大人”章注中引杨氏说:“孟子此章,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孟子集注·尽心下》)朱子引用杨时的话,批评孟子言语之间极为明显的用己之长,较人之短的意图,显得粗率狂妄,不符合圣人气象。如在对待大人态度上,孔孟截然相反,孔子畏敬,孟子藐视。这些都见出圣贤有别。
但朱子提出偏圣说,造成偏圣与贤人层次区分上的模糊。一方面只有至圣才是性之安之,偏圣与贤人一样,皆须反之复性工夫,如此一来,偏圣与贤人就难以区别了。而且,在朱子看来,作为大贤的颜子在修为上(如巧和中)有超过伯夷等偏圣处,“颜子优于汤武”,②只是在行上不够充足,力有未至而已。另一大贤孟子与偏圣之高低,亦不好评论,这就造成贤与圣的层次上的混乱。正是有见于伯夷等偏圣存在不完善处,故程子提出将他们从圣人位置上降下来,以解决与大贤之间的矛盾,提出伯夷柳下惠并非圣人说,“人皆称柳下惠为圣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语,非自见。”又曰:“夷、惠圣人,传者之误。”①但朱子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坚持偏圣的存在,强调圣人以所至而论,不以是否大全中正通化为准。并以药为譬指出偏方之药有时效果胜于中和之药,夷惠对世道人心教化作用甚为明显,有时还甚于至圣孔子。可见,朱子更侧重从客观教化效果来着眼。“未必误也。彼曰圣之清也、圣之和,则固不思不勉而从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于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备,所以不得班于孔子耳。……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圣而易能,有迹而易见,且世人之贪懦鄙薄者众,一闻其风而兴起焉,则其为效也速,而所及者广,譬如姜桂大黄之剂,虽非中和,然(文渊阁本有“其”字)于去病之功为捷。”②
圣人与君子。朱子将君子视为圣人的通称。“君子,圣人之通称也。”(《孟子集注·尽心上》)这样一来,君子就包含了圣人,也就意味着圣人可以视为君子的一种,即圣人君子,与通常概念下的君子相对照。但是圣人自身又有偏圣和至圣的区别,当圣人和君子相提并论时,君子就包含了偏圣,圣就特指至圣。如在“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章的注释中,朱子强调圣人(专指至圣)立法出命,性之安之,君子(包含偏圣)则需要行法俟命,反之复性。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圣与君子概念的紊乱。“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祸福有所不计,盖虽未至于自然,而已非有所为而为矣。此反之之事。吕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圣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圣人性之,君子所以复其性也。’”(《孟子集注·尽心下》)
五圣人之衍
孟子对圣人的论述较为全面,除圣人外,还论述了圣王理想、圣师愿望、圣徒使命。朱子在此基础上,阐发了由圣衍生出的圣王、圣师、圣徒,强调了圣王、圣师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圣人之徒捍卫、传承儒学,辟除邪说的护教传道。
圣王。在对圣的论述中,孟子很重视圣兼具外王的一面。他痛心于尧舜之道既衰而圣王不起所造成的社会混乱状况,故周游诸国,劝说君王行王道之事,希望能有圣而王者出现,以收拾霸而王之局面。朱子亦非常注意揭示圣而王的特点,要求圣者必须具有王者的政治才能,这样他的仁者之功才会受益广大,并以舜、孔为例,指出圣人过化存神妙用无边,自然妥帖,与天地化生陶冶万物异曲同工,体现出王道效果之广大久远,神奇莫测,远胜霸道。“君子,圣人之通称也。所过者化,身所经历之处,即人无不化,如舜之耕历山而田者逊畔,陶河滨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处便神妙不测,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绥斯来、动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业之盛,乃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举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补塞其罅漏而已。此则王道之所以为大,而学者所当尽心也。”(《孟子集注·尽心上》)朱子注“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亦突出孔子之事功,认为“圣人无不盛”,在任何事上都能做得很好,于外王上也不例外,自然有其神功妙化。
圣师。自周公后,圣王传统已经断绝,此后再也没有赓续上。故藉内圣修为而为圣师,成为儒家学者更切近现实的追求。儒家学者希望以内圣之功为基础,通过自身的率先垂范成为道德导师,以此影响整个社会风俗人伦,以实现外王之功。孟子提出“圣人百世之师也”,通过圣师这一新的定位宣扬了儒者功业之深远,同时又给予了儒者很好的自我定位。朱子认为,圣人居于王者师的地位,虽然不据有天下,但是其功业恩泽同样能广被天下,圣师并不以个人一己得失为念,而是以天下之公利为人生目标,至公无我。“滕国褊小,虽行仁政,未必能兴王业;然为王者师,则虽不有天下,而其泽亦足以及天下矣。”(《孟子集注·滕文公上》)
圣徒。孟子周流一生,并未能够获得圣师之地位。退而求其次,认为能够传扬圣人学说,捍卫圣人思想,抗击异端学说者,亦可为圣门中人,即圣人之徒也,这是孟子对儒者的又一定位。“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下》)孟子提出严拒杨墨异端,捍卫儒家学说的态度决心,获得身处同一境地中的宋儒极大共鸣。“盖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弒之祸,故孟子深惧而力救之。”(《孟子集注·滕文公下》)朱子在对孟子此段思想的阐发中,特别强调了异端邪说对人心的冲击破坏,比之为洪水猛兽、夷狄篡弒。称赞凡是能够起而辟之者,即使未能知道,但为学趋向已经走上正路,可以视为圣门中人。孳孳为善者,即是行走在圣人之道上的圣徒。“言苟有能为此距杨墨之说者,则其所趋正矣,虽未必知道,是亦圣人之徒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下》)
总之,朱子对圣人观念的细加辨析,突出了孔子作为至圣的完满性,反映出儒家“止于至善”的人格理念。同时不惜反对程子之说,宁冒混淆人格层次之弊,坚持降低一等的偏圣说,是在承认偏圣人格有所不足的基础上,强调他们所实际具有的教化效果,表明了成就圣人的现实可行性。朱子在继承前辈学者理论基础上,对儒家圣人说作出了创造性理解,对后世的圣人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学习、探究朱子的圣人思想,对理解儒家理学人格,增进个人修养实践皆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