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为多维关系
| 内容出处: |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668 |
| 颗粒名称: | 三、“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为多维关系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8 |
| 页码: | 251-258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熹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儒家学者,他对于“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主张仁和礼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上都是相通的,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克尽己私、复礼的工夫,人们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这种理解对于我们深入探究中国哲学中的仁学和礼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
| 关键词: | 朱熹 克己复礼 哲学思想 |
内容
在梳理完朱熹论“克己”与“复礼”、“克己复礼”与“为仁”的关系后,我们再来考察其仁礼关系。前文已指出,关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关系的讨论历来十分热烈,⑤主要有四类,一是仁先礼后说,二是礼先仁后说,三是仁礼统一说,四是仁礼分疏说。这些讨论主要是以单一的模式和理路来诠释仁礼关系,事实上,仁礼关系始终是多维度、多面向的,单一模式和理路很难全面概括仁礼关系涉及和蕴含的全部意义。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关系的论述即颇具代表性和启示性。出于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和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远远不同于孔子的理解,他试图从多重维度来诠释和呈现“克己复礼为仁”中仁礼关系的复杂性,具体来看,可概括为仁礼相通、仁包含礼等多层意涵。
其一,仁礼相通:为性为理兼体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仁礼相通之关系,我们不妨在前文对朱熹“复礼”“为仁”诠释的已有讨论之基础上,再对照比较《论语集注》中“克己复礼为仁”之“礼”“仁”诠释。朱熹《论语集注》释“克己复礼为仁”之“礼”“仁”分别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仁者,本心之全德”①。这两个诠释皆以“者”字来表示定义和停顿,具有相同的句式特征,而且在内涵上两者也有诸多相通之处。
不难发现,朱熹释“礼”,一端伸向形而上的本体“天理”,释“礼”为“天理”、为“体”“性”;一端指向形而下的“节文”,释“礼”为“节文”、为用。在朱熹看来,“礼”本身兼备体用,释“礼”为“天理”,突出的是“礼”的本体性,视“礼”为合当底;释“礼”为“节文”,突出的是“礼”之践履、“礼”之下学工夫。张载释“礼”兼体用,二程释“礼”侧重理与礼的关系,朱熹释“礼”亦兼亦分,融通和发展了张载、二程的“礼”之诠释。
朱熹释“仁”,一端指向“本心”,另一端指向“全德”,以“本心”修饰“全德”,释“仁”之“德”兼性情、体用。在朱熹看来,“仁”本身兼备体用,释“仁”为“本心”突出的是“仁”的本体性,释“仁”为“全德”,突出“仁”是包四德、包四端之“性情之德”“有体有用之德”,突出的是“仁”兼具众德、包容遍覆、纯粹无私、同于天理。孟子释“仁”兼体用,二程释“仁”分别体用,朱熹释“仁”亦分亦兼,融通并发展了孟子、二程的“仁”之诠释。
通过上述仁礼诠释对照分析,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朱熹的仁礼相通思想。
首先,仁礼皆为性。朱熹释“仁”为性、释“礼”为性,而且还常常并提并释“仁义礼智”为“性”。“仁是性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①“在人,仁义礼智,性也。”②“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③“仁义礼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炉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时,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昼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万叶,千条万绪,都是这四者做出来。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许多般样。”④在朱熹看来,仁、礼与义、智一样,自天生成人,本来便有,不是从外部给予的,仁、礼皆是天生、本有的四件之一,仁义礼智就好比火炉之四角、天之四时、地之四方、日之昼夜昏旦。
其次,仁礼皆为理。朱熹释“仁”为“理”、释“礼”为“理”,释“仁”“礼”等性之德目与宇宙的终极本体“理”等同。“须知仁、义、礼、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无所为而然者。”⑤“当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体,故仁义礼智为体。”⑥“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⑦在朱熹看来,仁礼均是天然本有之理。
此外,仁礼皆兼体用。“天理”是体,“节文”是用,用以释“礼”的“天理之节文”兼具体用;“全德”兼体用,用以释“仁”的“本心之全德”兼具体用。
朱熹主张仁礼相通,是对二程诠释的继承和发展。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①可见,程颢释礼同于仁,遗憾的是,这里对仁礼关系只做了隐含的表述。相比之下,程颐的诠释则更为清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②程颐明确交代仁与礼没有什么不同,仁就是礼。有人曾问及程颐为何以“克己复礼”为“仁”,他回答说:“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③程颐的这一回答显然反映出其仁礼同一的主张。朱熹并不是盲目地遵循二程之诠。即便对于“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这一句话的理解,朱熹亦有所发展。《论语或问》指出,该句话意为“言能复于礼,则仁心自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与礼为一物也”④。《朱子语类》指出,“一于礼之谓仁。只是仁在内,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复礼乃见仁。仁、礼非是二物”⑤。朱熹从两个角度深度诠释仁与礼“非为一物”“非是二物”,就工夫论而言,“复礼”工夫到,“仁”心自存,正所谓德盛仁熟,工夫至、自然成;就性情观而言,在内的仁,容易被私欲这一层外膜遮蔽,克去己私,自然能复礼见仁。可见,朱熹释仁礼相通是对二程诠释的反复思考和发展。
其二,仁包含礼:为大为先为“骨子”。
朱熹虽常并提仁、义、礼、智四者,视这四者相通,但在这四者之中,他又特别重视仁,视仁大于礼,仁先于礼、主导礼,仁包含礼。
首先,仁大于礼。“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⑥就范围而言,朱熹认为,仁为大,包含仁义礼智四德。《仁说》言:“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①朱熹认为,心有四德,仁无不包,是至大的。《朱子语类》载:“‘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②;“便是包四者”③;“仁专言‘心之德’,所统又大”④。朱熹从“专言”“偏言”的角度强调,仁是“专言”,“所统又大”,包含礼等四者。
朱熹《克斋记》言: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着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⑤
在朱熹看来,“仁”是用来命名无所不备的“性情之德”的,是天地生物之心,未发之前,它统包仁、义、礼、智四德,已发之际,它显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仁自然包含礼。
其次,仁先于礼。“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⑥朱熹指出:“性是统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礼是右手,义是左脚,智是右脚。……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⑦这里释“仁”为“左手”,手在足之先,左在右之先,突出“仁”为先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朱子所说的“先”是一种逻辑上的先。显然,这一思想来源于孔子。因为在孔子那里,虽然“礼”是历史上西周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即时间上在先),但已居于次要地位,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他所提倡的“仁”(即逻辑上在先的)。
再次,仁是“骨子”。《朱子语类》载:“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须是仁做始得。凡言体,便是他那骨子”①;“理者物之体,仁者事之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仁则不可行”②。朱熹强调仁是“始”,是体,是“骨子”,礼离不开仁,离开仁,则“礼仪”“威仪”均不可行。针对此言,钱穆指出,“仁见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上,此乃体见于用上,犹如骨在里不可见,所见是外面皮肉也。然非理则事不成,非仁则礼不立,非体则用不有,犹之非骨则皮肉无所依附也”③。“骨子”是皮肉的依靠,仁是礼的主心骨。从程颢的相关表述中,我们能更明白地理解这一点。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④;“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⑤。程颢从“万物之生意”的角度,强调仁具有“元者善之长”之特别重要的地位,仁是头,“仁义礼智”是手足,作为大脑之仁主导着作为手足之礼,仁主导礼。
朱熹《仁说》言: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⑥
朱熹认为,在天地之心的四德元亨利贞之中,元无不统,相仿,在人心之四德仁义礼智之中,仁无不统,发用之时,恻隐之心贯通爱恭宜别四情,就如春夏秋冬四季之序,春生之气贯通其间,无所不通。由“元”统“元亨利贞”四德、“春生之气”通“春夏秋冬”,可以比附推言仁统包“仁义礼智”四德,“恻隐之心”贯通“爱恭宜别”之情。
朱子关于仁包含礼的思想无疑是对程颐以“专言则包四者”释“仁”、释“仁”为“全体”、“仁包含礼”之诠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程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①这里强调“仁”是全体,“仁义礼智信”是性,“仁”这个全体包含“仁义礼智”四者。可见,在二程看来,仁不同于礼,包含礼。较之二程,朱熹提出了“全德”概念以代替二程的“全体”概念,并进而发展提出“仁”包“四德”、“恻隐之心”包“四端”等,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学诠释体系,比二程单纯以“全体”释“仁”,显得更为精致、严密和丰富。可以说,朱子对“仁”是全德的这种理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充实。蔡仁厚先生与陈荣捷先生都曾指出,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整体的、普遍的德行,综摄一切德目,是一种全德。②
1195年,朱熹《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③
朱熹直接引用程颐“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又以春夏秋冬同出乎春为比附,强调春夏秋冬为春之生、长、成、藏,强调仁贯通仁、义、礼、智四性,强调仁礼义智分别为仁之本体、节文、断制、分别。从仁这一贯通仁、义、礼、智之义,不难理解朱熹释仁包含礼的真正意涵了。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从多重维度来诠释仁礼关系,各个维度之间是什么关联?有矛盾吗?朱熹是怎么解决这种矛盾的?就“仁礼相通”“仁包含礼”这两者来说,朱熹是通过“理一分殊”理论来建立这种关联并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朱熹认为,仁是“理一”,仁义礼智是“分殊之理”,作为分殊之仁与分殊之礼是相通的,因而“仁礼相通”;作为理一之仁为先、为大、为生意贯通,因而包了四德,“仁包含礼”。
其一,仁礼相通:为性为理兼体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仁礼相通之关系,我们不妨在前文对朱熹“复礼”“为仁”诠释的已有讨论之基础上,再对照比较《论语集注》中“克己复礼为仁”之“礼”“仁”诠释。朱熹《论语集注》释“克己复礼为仁”之“礼”“仁”分别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仁者,本心之全德”①。这两个诠释皆以“者”字来表示定义和停顿,具有相同的句式特征,而且在内涵上两者也有诸多相通之处。
不难发现,朱熹释“礼”,一端伸向形而上的本体“天理”,释“礼”为“天理”、为“体”“性”;一端指向形而下的“节文”,释“礼”为“节文”、为用。在朱熹看来,“礼”本身兼备体用,释“礼”为“天理”,突出的是“礼”的本体性,视“礼”为合当底;释“礼”为“节文”,突出的是“礼”之践履、“礼”之下学工夫。张载释“礼”兼体用,二程释“礼”侧重理与礼的关系,朱熹释“礼”亦兼亦分,融通和发展了张载、二程的“礼”之诠释。
朱熹释“仁”,一端指向“本心”,另一端指向“全德”,以“本心”修饰“全德”,释“仁”之“德”兼性情、体用。在朱熹看来,“仁”本身兼备体用,释“仁”为“本心”突出的是“仁”的本体性,释“仁”为“全德”,突出“仁”是包四德、包四端之“性情之德”“有体有用之德”,突出的是“仁”兼具众德、包容遍覆、纯粹无私、同于天理。孟子释“仁”兼体用,二程释“仁”分别体用,朱熹释“仁”亦分亦兼,融通并发展了孟子、二程的“仁”之诠释。
通过上述仁礼诠释对照分析,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朱熹的仁礼相通思想。
首先,仁礼皆为性。朱熹释“仁”为性、释“礼”为性,而且还常常并提并释“仁义礼智”为“性”。“仁是性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①“在人,仁义礼智,性也。”②“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③“仁义礼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炉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时,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昼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万叶,千条万绪,都是这四者做出来。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许多般样。”④在朱熹看来,仁、礼与义、智一样,自天生成人,本来便有,不是从外部给予的,仁、礼皆是天生、本有的四件之一,仁义礼智就好比火炉之四角、天之四时、地之四方、日之昼夜昏旦。
其次,仁礼皆为理。朱熹释“仁”为“理”、释“礼”为“理”,释“仁”“礼”等性之德目与宇宙的终极本体“理”等同。“须知仁、义、礼、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无所为而然者。”⑤“当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体,故仁义礼智为体。”⑥“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⑦在朱熹看来,仁礼均是天然本有之理。
此外,仁礼皆兼体用。“天理”是体,“节文”是用,用以释“礼”的“天理之节文”兼具体用;“全德”兼体用,用以释“仁”的“本心之全德”兼具体用。
朱熹主张仁礼相通,是对二程诠释的继承和发展。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①可见,程颢释礼同于仁,遗憾的是,这里对仁礼关系只做了隐含的表述。相比之下,程颐的诠释则更为清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②程颐明确交代仁与礼没有什么不同,仁就是礼。有人曾问及程颐为何以“克己复礼”为“仁”,他回答说:“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③程颐的这一回答显然反映出其仁礼同一的主张。朱熹并不是盲目地遵循二程之诠。即便对于“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这一句话的理解,朱熹亦有所发展。《论语或问》指出,该句话意为“言能复于礼,则仁心自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与礼为一物也”④。《朱子语类》指出,“一于礼之谓仁。只是仁在内,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复礼乃见仁。仁、礼非是二物”⑤。朱熹从两个角度深度诠释仁与礼“非为一物”“非是二物”,就工夫论而言,“复礼”工夫到,“仁”心自存,正所谓德盛仁熟,工夫至、自然成;就性情观而言,在内的仁,容易被私欲这一层外膜遮蔽,克去己私,自然能复礼见仁。可见,朱熹释仁礼相通是对二程诠释的反复思考和发展。
其二,仁包含礼:为大为先为“骨子”。
朱熹虽常并提仁、义、礼、智四者,视这四者相通,但在这四者之中,他又特别重视仁,视仁大于礼,仁先于礼、主导礼,仁包含礼。
首先,仁大于礼。“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⑥就范围而言,朱熹认为,仁为大,包含仁义礼智四德。《仁说》言:“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①朱熹认为,心有四德,仁无不包,是至大的。《朱子语类》载:“‘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②;“便是包四者”③;“仁专言‘心之德’,所统又大”④。朱熹从“专言”“偏言”的角度强调,仁是“专言”,“所统又大”,包含礼等四者。
朱熹《克斋记》言: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着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⑤
在朱熹看来,“仁”是用来命名无所不备的“性情之德”的,是天地生物之心,未发之前,它统包仁、义、礼、智四德,已发之际,它显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仁自然包含礼。
其次,仁先于礼。“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⑥朱熹指出:“性是统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礼是右手,义是左脚,智是右脚。……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⑦这里释“仁”为“左手”,手在足之先,左在右之先,突出“仁”为先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朱子所说的“先”是一种逻辑上的先。显然,这一思想来源于孔子。因为在孔子那里,虽然“礼”是历史上西周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即时间上在先),但已居于次要地位,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他所提倡的“仁”(即逻辑上在先的)。
再次,仁是“骨子”。《朱子语类》载:“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须是仁做始得。凡言体,便是他那骨子”①;“理者物之体,仁者事之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仁则不可行”②。朱熹强调仁是“始”,是体,是“骨子”,礼离不开仁,离开仁,则“礼仪”“威仪”均不可行。针对此言,钱穆指出,“仁见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上,此乃体见于用上,犹如骨在里不可见,所见是外面皮肉也。然非理则事不成,非仁则礼不立,非体则用不有,犹之非骨则皮肉无所依附也”③。“骨子”是皮肉的依靠,仁是礼的主心骨。从程颢的相关表述中,我们能更明白地理解这一点。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④;“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⑤。程颢从“万物之生意”的角度,强调仁具有“元者善之长”之特别重要的地位,仁是头,“仁义礼智”是手足,作为大脑之仁主导着作为手足之礼,仁主导礼。
朱熹《仁说》言: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⑥
朱熹认为,在天地之心的四德元亨利贞之中,元无不统,相仿,在人心之四德仁义礼智之中,仁无不统,发用之时,恻隐之心贯通爱恭宜别四情,就如春夏秋冬四季之序,春生之气贯通其间,无所不通。由“元”统“元亨利贞”四德、“春生之气”通“春夏秋冬”,可以比附推言仁统包“仁义礼智”四德,“恻隐之心”贯通“爱恭宜别”之情。
朱子关于仁包含礼的思想无疑是对程颐以“专言则包四者”释“仁”、释“仁”为“全体”、“仁包含礼”之诠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程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①这里强调“仁”是全体,“仁义礼智信”是性,“仁”这个全体包含“仁义礼智”四者。可见,在二程看来,仁不同于礼,包含礼。较之二程,朱熹提出了“全德”概念以代替二程的“全体”概念,并进而发展提出“仁”包“四德”、“恻隐之心”包“四端”等,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学诠释体系,比二程单纯以“全体”释“仁”,显得更为精致、严密和丰富。可以说,朱子对“仁”是全德的这种理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充实。蔡仁厚先生与陈荣捷先生都曾指出,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整体的、普遍的德行,综摄一切德目,是一种全德。②
1195年,朱熹《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③
朱熹直接引用程颐“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又以春夏秋冬同出乎春为比附,强调春夏秋冬为春之生、长、成、藏,强调仁贯通仁、义、礼、智四性,强调仁礼义智分别为仁之本体、节文、断制、分别。从仁这一贯通仁、义、礼、智之义,不难理解朱熹释仁包含礼的真正意涵了。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从多重维度来诠释仁礼关系,各个维度之间是什么关联?有矛盾吗?朱熹是怎么解决这种矛盾的?就“仁礼相通”“仁包含礼”这两者来说,朱熹是通过“理一分殊”理论来建立这种关联并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朱熹认为,仁是“理一”,仁义礼智是“分殊之理”,作为分殊之仁与分殊之礼是相通的,因而“仁礼相通”;作为理一之仁为先、为大、为生意贯通,因而包了四德,“仁包含礼”。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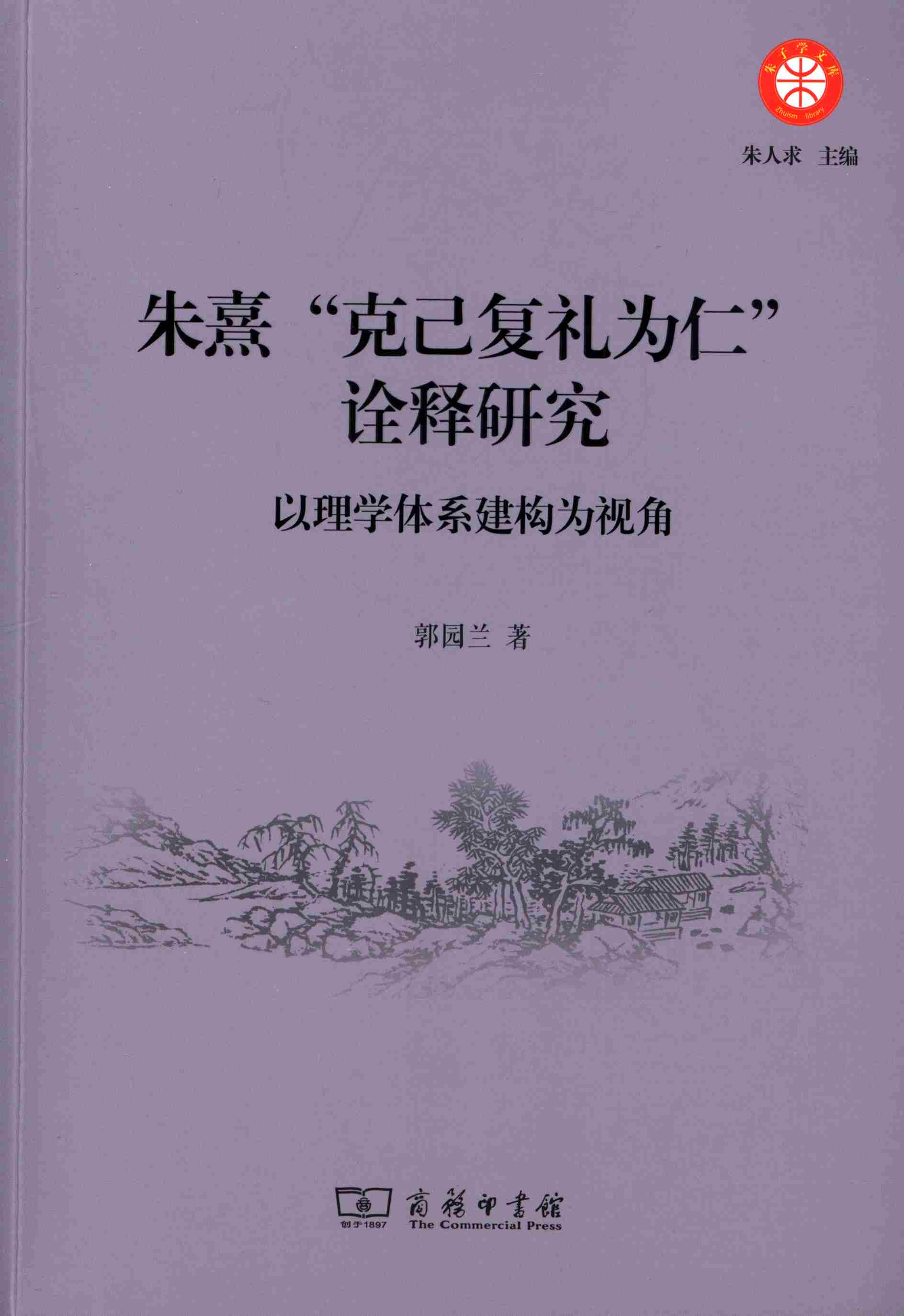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以宋代佛道挑战、清代汉宋之争为背景,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研究,挖掘朱熹克己、复礼、为仁及三者关系的诠释意涵,揭示其诠释的理学化、阶段性、发展性、矛盾性特征及其成因,彰显了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与深远影响。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