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儒学史上“无极太极”论辩
| 内容出处: |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549 |
| 颗粒名称: | 韩国儒学史上“无极太极”论辩 |
| 其他题名: | 以李彦迪和曹汉辅为中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3 |
| 页码: | 257-269 |
| 摘要: | 本次论辩是韩国性理学者李彦迪和曹汉辅对“无极太极”问题的辩论,源于孙叔暾与曹汉辅对周濂溪《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的讨论。李彦迪认为孙、曹二人的论辩源于陆象山,而曹汉辅则以周濂溪的“无极太极”为宗旨进行回应。这次辩论涉及对朱子学的深入理解和发挥,对儒、佛思想的不同也有恰当的理解,展现了韩国性理学的发展。 |
| 关键词: | 无极太极 儒家文化 朱熹 |
内容
韩国性理学者李彦迪和曹汉辅有关“无极太极”问题的论辩,虽不及后来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端七情”论辩、南塘与巍岩的“湖洛争论”,在韩国儒学史上牵涉人物之多,但是,此次论辩显示了韩儒对朱子学有很深入的掌握和发挥,对儒、佛思想的不同,也有恰当的理解,很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发展。
一、“无极太极”论辩的理论渊源
这次辩论之缘起是孙叔暾(号忘斋)与曹汉辅(号忘机堂)讨论周濂溪《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的意义。李彦迪(号晦斋)看到孙、曹二人的论辩文章后,写出《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一文。他评论曹汉铺、孙叔暾二人的论辩说:
谨案忘斋无极太极辨,其说盖出于陆象山,而昔日朱子辨之详矣,愚不敢容赘。若忘机堂之答书,则犹本于濂溪之旨,而其论甚高,其见又甚远矣。其语中庸之理,亦颇深奥开广,得其领要,可谓甚似而几矣。①
李彦迪言孙忘斋之说出于陆象山,认为他的“无极太极辨”是太极由无极所生;对曹汉铺之说认为是“犹本于濂溪之旨”,以无极太极为一。曹氏看到这篇文章后,作出了回应。于是,李、曹两人书信往来数次进行论辩。遗憾的是,曹汉铺和孙叔暾论辩的有关书信,曹汉補和李彦迪论辩,曹氏的原信都已失传,现对曹汉補的见解只能从李晦斋书信中征引,来讨论其思想。为了弄清李彦迪和曹汉辅对朱子学的理解,我们先从朱熹与陆九渊“无极太极”论辩谈起。
朱熹曾与陆九渊有“无极太极”论辩,这是关于周濂溪《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应如何解释的问题。陆九渊认为周敦颐此句有如老子“有生于无”,即太极是由无极而来。他主要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理解,认为“易”之“太极”即是“中”,即是本源;在“太极”之上再加“无极”,是“叠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①朱熹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认为非“太极”之外复有一“无极”,两者本一,“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但分解地说,“无极”是有中说无,“太极”是无中说有。故朱喜说“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②这也就是说,“无极”之“无”非没有之意,即不是不存在,而是无形无状却实有此理之意。它也是存在,只是无形、无状、无名、无限而已。但它却是“太极”之所以为“太极”的存在依据。③
朱熹和陆九渊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各有所据。陆氏之所以会从生成论角度理解这一命题:一是与传统的思维进路有关;二是与《太极图说》的版本有关,因为当时《太极图说》的《国史》本,此句为:“自无极而为太极”。九江本是“无极而生太极”。这两个版本都是“以无为本”、“有生于无”的观点。朱熹不取其说,而作出上面的理解,就在于周敦颐之《通书·动静》章。因为按《太极图说》所言“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如陆氏的生成论之理解,即顺序地从“无极”到“太极”到“阴阳”到“五行”。这里隐含着一个时间的流变过程。
朱熹对“无极而太极”所取周氏《动静》章言:“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①按周氏之意,“物”仅仅执“动”或“静”之一端,要么“动”,要么“静”,非此即彼,故为“不通”。而神则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是超乎动静的。对这种形而上的动静,朱熹说:“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②作为形而上之“神”的动静是变化无穷的。它是能神妙万物的,是动静之理。它跳出了生成流变的过程,消解了时间因子,成为动和静之所以能够动静的原因。“神”是无形无状的,但却又是实有的存在,它可以“妙万物”。“妙万物”是指神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内在本性和变化生生的微妙功能。这个神,实质上是说“无极”和“太极”本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实无先后上下之分。如果硬要说“无极”先于“太极”,那也只能理解为是逻辑在先。③朱熹把周敦颐讲的“太极”解释为“理”,对“太极”本体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二、曹汉辅“无极太极”论
曹汉辅对“太极无极”的理解,主要是从本体和工夫两个方面来阐述。他认为“太极即无极”,故《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中说:“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也。……岂有论有论无,分内分外,滞于名数之末。’”曹汉辅从无极的意义来体会太极,即可进入一浑然无分别之境界,而有无、内外等分别便可消泯。他对“太极无极”本体的规定是“虚而灵,寂而妙,灵妙之体,充满太虚,处处呈露”④。此说认为本体为虚寂灵妙。对此虚灵之本体,曹汉辅又用“寂灭”来规定:“太虚之体,本来寂灭。”⑤大概曹汉辅重视太极之“无极”性格,从虚无处体会本体。他对本体的规定还进一步说:“无则不无,而灵源独立;有则不有,而还归澌尽。”⑥这就是说,本体不落于有无之相对说中,即说有说无皆不可。曹汉辅以“虚灵”来说本体,应是受北宋理学家张载思想的影响。张载云:“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又云:“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①曹汉辅认为,太虚之体虚灵寂灭,为气之本,万化皆会澌尽,而虚灵之体独立恒存。这样理解本体,与张载之意还是有距离的。张载虽言太虚是气之本体,及气散而适得吾体,但亦强调太虚即气,并非至万化澌尽时,方可见本体之存在。而曹汉辅所谓的“寂灭”,是从万化终归于尽,聚而必散上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曹汉辅说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但并不强调“灭”之意,只是说本体虚灵寂妙,充满太虚。如此说,则本体亦是实理,并不是佛教之“寂灭”之意。
在工夫论上,曹汉辅主张“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万物朝宗于我,而运用无滞。”②又说:“游心于无极之真,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③这里所说的“万物朝宗于我”,即天地万物以我为中心;“运用无滞”,即表示本心呈现,理便呈现,而事物之来,皆能恰当回应之;而“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从本体之形而上的性格,作为契悟本心的入路而言。曹汉辅从“无极”意契入道体,由此而有“万物朝宗于我,运用无滞”之境。曹汉辅藉着对本体是虚灵无极之体会,使生命能进入一种与日常生活不同之境界,这是一种类似主张“顿悟”的工夫。李彦迪认为,曹氏此一“顿悟”功夫是违反了儒家下学上达之程序,并大加反对。
在李彦迪的论难下,曹汉辅将工夫论修正为“主敬存心,而上达天理”④,并以“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言主敬,便加强了此工夫中的道德意识。但李彦迪认为,此中仍缺乏“下学人事”的工夫,不从下学人事入手,上达天理是不可能的。曹汉辅则认为“下学”工夫是初学的工夫,他说:“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⑤所以,他说:“先立其体,然后下学人事。”⑥依曹汉辅之意,“下学人事”的工夫须在“先立其体”之后。
曹汉辅还认为“体既立,则运用万变,纯乎一理之正”。在曹氏看来,“先立其体”是较“静涵动察”更为高一层的工夫。此更高一层之工夫,依孟子是求其放心,就是逆觉本心的工夫。如果说“先立其体然后下学”,即在逆觉其本心后,是可以作存养省察之工夫的,而且使工夫更为有效果。但曹汉辅以“主敬存心”来“先立其体”,则未能显示逆觉本心之意。所以,李彦迪很容易便往朱子的“静涵动察,而敬赅动静”的工夫处理解。他说:“下学人事时固当常常主敬存心,安有断除人事,独守其心,然后可以下学?”①在此工夫论辩中,曹汉辅表现了孟子、陆九渊之说的特色。依孟、陆确可当下明本心,先立其大者。所以,李彦迪和曹汉辅之论辩,亦多少表现了朱陆之争的意义。
三、李彦迪“无极太极”论
李彦迪在评论曹汉铺和孙叔暾有关“无极太极”问题的论争后,并在与曹汉铺就本体和工夫的辩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本体论上,李彦迪主要依据朱子的“理气不离”及“理一分殊”说,来强调道至高至妙,又至近至实,道只是人事之理,形而上者必即于形而下者。李彦迪在对太极这一本体之体会时说:
然其间不能无过于高远,而有背于吾儒之说者,愚请言之;夫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抵也。是乃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来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哉!②
从文句来看,这段多採自朱熹答陆子静书之意来论说。③这对朱子“理气不离”之说作了很好的诠释。
李彦迪在补充说明“无极”之意义时说:“此理虽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实体之所以寓,则又至近而至实,若欲讲明此理,而徒鹜于窅冥虚远之地,不复求之至近至实之处,则未有不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矣。”①这就是说,太极之理,虽是至高至妙,而须用无极来形容。但此理之所存在处,是至近至实的。所谓至近至实,是指日用伦常而言。人不能因为天理是形而上的,便专从虚无飘渺,远离人生处想象追寻。这体现了李彦迪重视伦常实践之特色。
李彦迪认为无极是对太极之形容,太极可以言空寂,但乃是寂而感、虚而有,他说:
所以谓之无极者,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非若老氏之出无入有,释氏之所谓空也。”……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风雷之所以变,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也。②
李彦迪还从朱熹中和说之心性关系来论证道体并非寂灭。他说在情绪未发时,性体浑然在中,此可说是寂。但在情绪已发而心感通应物时,此性便表现其作用,故性体之寂,是“寂而感”的。这与佛教的“寂而灭”是不同的。对“中和”之义,李氏说:
其八曰:致中和。……盖天命之性,纯粹至善,而具于人心。方其未发,浑然在中而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及其发而品节不差,无所乖戾,故谓之和。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天下之理皆由是出,故曰天下之大本。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达道。此乃人心寂感自然之理,体用之全。③
这就是说,从未发已发,见理从中而和,有体有用,故并非枯寂无用之体。但李彦迪对《中庸》所说的“中和”之理解,是遵从朱熹之说,即是在“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架构下所说的。理之作用乃是由情之未发至已发,心之由寂然而感通,而显出的。即理挂搭在气上,由气之活动显出理之作用,使理由浑然而粲然。
李彦迪还认为,须正视世间之差别,不能浑然无别。由于理不离气,理必即于形器而存在,故理必有分殊之表现。人反身而于至切近处践履以求明道,必须注意存在事物之差别性、多样性。从李彦迪反对曹汉辅所主张的“一理太虚”①、“物我无间”②来看,李氏对“理一分殊”是十分重视的。他强调不同之存在物皆有其所以如此之理,故物各有不同之司职。他又认为理虽浑然一致,但其中粲然,可知李彦迪意在肯定世间存在事物之差别性。由于肯定分殊,便会相应于各存在物之不同而成就之。由于承认差别,就必须使分殊之个别存在,皆实现自身之价值,必见到在各分殊中皆显出天理,方可见天理之全,在浑然之天理中,存在着无限丰富的内容。这一观点显示了朱子思想中对“致广大而尽精微”境界之向往,亦充分表达了儒家“人文化成”的精神。
在工夫论上,李彦迪对朱子“静涵动察”、“敬贯动静”之工夫,有很深的体会。他说:
圣门之教,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齐其外以养其内,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严然肃然,深省密察,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动直,中一外融,则可以驯致乎不勉不思,从容中道之极矣。两件工夫不可偏废明矣。③
在这里,李彦迪是按照朱子所倡导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④来说,认为持敬省察久了,方可达到“静虚动直,中一外融”之境界。
李彦迪主张“静涵动察”、“敬义夹持”的工夫。他认为须于动、静,未发、已发之时各有工夫,方能使心依理而行。这是在心、理为二时,由于心不即理,故须用敬以夹持,使心合理。依朱子及李彦迪之言,只有存养以立大本的工夫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动时之省察。就是说,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本心之呈现并不易得,大多都处在受感性情绪影响的状况中。这时的动时之省察工夫,就显得尤为重要。故李氏在其诗中云:“中和虽似有宾主,动静周流无定辰。体察工夫终是宾,空虚论说竟非真。”①他所说的省察是对自己任何细微的生命活动皆须反省。在心发为意,意或善或恶之际作工夫;在处事接物时省察体验,而言顾行,行顾言,“制于外以养其中”。这种对动时省察的强调,隐含着他对现实生命的有限性、缺陷性有深切的体会。人的生命充满私欲习气,必须着实下苦功对治,方可有纯洁化之可能。而人在应事接物而动时,其生命问题才会显示出来,此时才好做工夫。而若只是静时涵养之工夫,则不易见生命之毛病。此亦如王龙溪所说:“欲根潜藏,非对境则不易发”②之意。这是修养之实在工夫。
李彦迪认为“主敬存心,下学人事,方能上达天理”。他说:
夫道只是人事之理耳。离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于空虚之境,而非吾儒之实学矣。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者人事也,则者天理也。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安得不先于下学之实务,而驰神空荡之地,可以为上达乎?天理不离于人事,人事之尽,而足目俱到,以臻于贯通之极,则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浑全,酬酢万变,左右逢原,无非为我之贯用矣。故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又曰:“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巨不信欤?③
这就是说,超越的天理,必须从人事的实践中才能体悟。人事实践至尽,便是天理。若离人事而求道,没有不蹈于空虚之境。李彦迪以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体会。李氏此论,有如当代儒学的“道德的形上学”,或“实践的形上学”之论,即形上之道体,是只有藉道德实践才能体证到的,并非思辨可知。故形上理论,须以道德实践为进路来建立。
由上可知,李彦迪的“无极太极”论,对本体和功夫问题的理解,多得自朱子。所以,李退溪在《晦斋李先生行状》中说:
而其精诣之见,独得之妙,最在于与曹忘机汉辅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也。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即朱子)为尤多也。①
退溪认为,李彦迪之论,是合于朱子义理的,并说彦迪此一论辩在其著作中最有“精诣之见,独得之妙”。可见,李彦迪对“无极太极”的阐释,得到后来李退溪的赞赏。
四、李彦迪与曹汉辅“无极太极”论之异
李彦迪与曹汉辅遵从朱子之说,都认为“太极即无极”。李氏说:“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则是也。”②而两人之争论,是对此无极之本体,应如何规定,及如何方能体会、掌握之问题。前者是属本体问题,后者是属工夫问题。李、曹对“无极太极”理解之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在对“道体”的规定性上产生歧义
曹汉辅认为,道体是“太虚之体,本来寂灭”。李彦迪则认为曹汉辅对朱子之本体理解不恰当。他说:
大抵忘机堂平生学术之误,病于空虚。而其病根之所在,则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以灭字说太虚体,是断非吾儒之说矣。谓之寂可也,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谓“於穆不已”者存焉。……此心本然之体,而谓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则喜怒哀乐发皆中节,而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谓“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灭,则是枯木死灰而已,其得不至于灭天性乎?③
李彦迪认为,“寂灭”是佛教之说,用寂灭来形容道体,不合儒家义。若以“寂”形容道体是可以的,但在至寂中,有“於穆不已者存焉”,即道体是既寂而又生生不已的,不能以虚无寂灭来说。在这里,李彦迪对“寂灭”与“寂感”作了区分,显示了他对儒佛之别有恰当的理解。
曹汉辅对李彦迪之意见,有接受,但对自己的见解,亦有坚持。他说:
至如寂灭之说,生于前书粗辩矣,未蒙允。今又举虚灭无极之真,乃曰“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是未免于借儒言而文异端之说,小子之感滋甚。先儒于此四字盖尝析之曰:“此之虚,虚而有;彼之虚,虚而无。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灭。”然则彼此之虚寂同,而其归绝异,固不容不辨。而至于无极之云,只是形容此理之妙,无影响声臭之耳,非如彼之所谓无也。故朱子曰:“老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讵不信欤?①
曹汉辅以“寂灭”来形容道体,又认无极之真,其虚灵无极,即是寂灭。李彦迪对曹氏之论,又引丽末鲜初著名性理学者郑道传《儒释同异之辨》来作说明。郑氏说:
先儒谓儒释之道句句同而事事异。今且因是而推广之。此曰虚,彼亦曰虚;此曰寂,彼亦曰寂。……此曰知行,彼曰悟修;此之知,知万物之理具于吾心也;彼之悟,悟此心本空无一物也。此之行,循万物之理而行之无所违失也;彼之修,绝去万物而不为吾心之累也。此曰心具众理,彼曰心生万法。所谓具众理者,心中原有此理,方其静也至寂,而此理之体具焉;及其动也感通,而此理之用行焉,其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所谓生万法者,心中本无法也,对外境而后法生焉。②
郑道传之说,本朱子之意而推衍,而李彦迪之说,大抵依郑氏。儒家所说之道体,虽亦可用虚、寂来形容,但一定是虚而有,寂而感,决不能说虚而无,寂而灭。按朱子之意,寂感应都从心上说。在情绪未发而心寂然处,理浑然而在;在情绪发时,心感而遂通,在心之感通时,理亦粲然地表现其内容(显为四德)。心之寂然感通,虽具理在其中,但寂感是从心之活动上说,理是不能说寂感。郑道传和李彦迪对寂感之理解,应是上述之意,而并非认为太极是即寂即感的。
曹汉辅对于所以要坚持用“寂灭”来形容道体,有自己的说明。他说:“为破世人执幻形为坚实,故曰寂灭。”③对此说,李彦迪反驳说:
此语又甚害理。盖人之有此形体,莫非天之所赋,而至理寓焉。是以圣门之教,每于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尽夫天之所以赋我之则,而保守其虚灵明德之本体,岂流于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岂可以此为幻妄,必使人断除外相,独守虚灵之体,而乃可以为道乎?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此寂灭之教所以陷于空虚诞谩之境,而无所逃其违天灭理之罪者。①
在这里,李彦迪进一步肯定了一切形器存在之真实性。他认为形而上者必即于形而下者存在,故形而下者必有天理为其存在之根据。形而下者,就形器本身之存在状况来说,当然是聚散变化,生灭不已的,不会永恒不变地存在。但在形器之变化过程中,都有实理贯串其中,都显现了理的意义,故虽聚散变化,但形器本身并非虚幻而无意义。李氏肯定形器,并非只就形器说,而是由“道不离于形器”来说。道不孤悬,必即于形器;而器亦不只是器,必有其所以然之理。李彦迪这一说法,可以说是对朱子“理气论”作了很好的诠释。由于理气不离,故天理不离形器,一切事物皆有其道,一切存在皆有其存在之客观根据,并不是偶然而虚忘的。又由于理不杂于气,故人必须努力探索践履,于形器中体会其形上根据,于事物上了解其当然之则。
2.在对“道体”的体会之工夫上有不同见解
曹汉辅对“道体”的体会,主张“主敬存心,上达天理”②。李彦迪对此说:
此语固善,然于上达天理,却欠下学人事四字,于圣门之教有异。天理不离于人事,下学人事,自然上达天理;若不存下学工夫,直欲上达,则是释氏觉之之说,乌可讳哉?盖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则天理之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便是上达境界。从事于斯积久贯通,可以达夫浑然之极矣。而至于穷神如化之妙,亦不过是而驯致耳。③
在这里,李彦迪藉朱子“理气不离”之义,来说明形而上之道,不离形而下之器。而若形而上者不离形而下者,则人欲知天理,便只有在形而下之存在处寻求;舍此而外,别无他途。他认为不下学人事,是不能上达天理的。“下学人事,方能上达天理”之说,实含有“理必不离人事”,能于人事中表达出来的,方是道德之理。如果单靠心的虚明,是不能表现道德之理的。
曹汉辅以“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为工夫,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是以无极太虚之体作为心之主,是体证本心的工夫,未必是静以涵养心中之理,即未必是在心与理为二之下存养工夫。李彦迪认为,曹汉辅此一工夫有所偏。他说:
来教有曰:“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则固存养之谓矣,而于静时工夫则有矣;若夫顿除下学之务,略无体验省察之为,则于动时工夫,盖未之及焉。是以其于求道之功,疏荡不实,而未免流为异端空虚之说。伏睹日用酬酢之际,不能无人欲之累,而或失于喜怒之际,未能全其虚灵之本体者有矣。岂非虽粗有敬以直内工夫,而无此义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体道不能精密,而或于此乎?①
李彦迪认为曹汉辅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有差失,正是因为只有静时的“敬以直内”之工夫,而欠缺动时的“义以方外”工夫所致。若不能以本心即理,则心是现实的经验义之心,对于此一意义之心,确实需要这种静涵动察,敬义夹持的工夫。但若曹汉辅所说的“顾諟天之明命”,是让炯然不昧之本心作为人生命之主宰,则是另一种功夫,并不可以套在“静涵动察”之工夫系统下。所以,李彦迪说曹忘辅只有主敬存养之静时的工夫,而缺乏已发时省察之动时的工夫。
李彦迪非常强调动时工夫的重要,他说:
昔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子继之曰;“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然则圣门工夫,虽曰主于静以立其本,亦必于其动处深加省察。盖不如是,则无以克己复礼,而保固其中心之所以存矣。故曰“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未有不制其外而能安其中也。愚前所云“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顾行,行顾言”者,此之谓也。安有遗其心官,随声逐色,失其本源之弊哉!……若未到从容中道之地,而都遗却择善省察工夫,但执虚灵之识,不假修为,而可以克己复礼,可以酬酢万变云,则譬如不出门而欲适千里,不举足而欲登泰山,其不能必矣。①
按朱子来说心,是经验义的心,故必须以静涵动察,敬义夹持为工夫,这两方面下功夫是必须的。所以,李彦迪以曹汉辅的工夫为有所偏。
李彦迪以曹汉辅之言工夫,是如不出门而欲适千里,是不可能达到目的之工夫。这是纯依朱子来说,此一批评是值得商榷的。若是本心呈现,理便存在,而且离开实践行动之源,何以不能克己复礼?曹汉辅之说,是先立本以为人生命活动之主宰。他批评李氏所倡导之工夫是“遗其心官,随声逐色,失其本源”②,是“姑舍其体而先学其用”③。李彦迪要“制外以养中”④,当不会随外物而转,但从曹氏的批评,可见曹汉辅对“先立本”是十分强调的。曹氏认为他自己所倡导的是“立纲领”的功夫,即他所说的“衣必有领而百衣顺,纲必有纲而万目张”⑤。
以上对李彦迪与曹汉辅的“无极太极”论辩作了疏释,从本体及工夫两方面,分析了李、曹二人的辩论内容。从中可看出,李彦迪对朱子思想有较深入的理解,表现出朱子学重视道德实践,强调下学的特色。而曹汉辅的思想中,则具有陆王之学的某些特征。
(原刊于《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
一、“无极太极”论辩的理论渊源
这次辩论之缘起是孙叔暾(号忘斋)与曹汉辅(号忘机堂)讨论周濂溪《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的意义。李彦迪(号晦斋)看到孙、曹二人的论辩文章后,写出《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一文。他评论曹汉铺、孙叔暾二人的论辩说:
谨案忘斋无极太极辨,其说盖出于陆象山,而昔日朱子辨之详矣,愚不敢容赘。若忘机堂之答书,则犹本于濂溪之旨,而其论甚高,其见又甚远矣。其语中庸之理,亦颇深奥开广,得其领要,可谓甚似而几矣。①
李彦迪言孙忘斋之说出于陆象山,认为他的“无极太极辨”是太极由无极所生;对曹汉铺之说认为是“犹本于濂溪之旨”,以无极太极为一。曹氏看到这篇文章后,作出了回应。于是,李、曹两人书信往来数次进行论辩。遗憾的是,曹汉铺和孙叔暾论辩的有关书信,曹汉補和李彦迪论辩,曹氏的原信都已失传,现对曹汉補的见解只能从李晦斋书信中征引,来讨论其思想。为了弄清李彦迪和曹汉辅对朱子学的理解,我们先从朱熹与陆九渊“无极太极”论辩谈起。
朱熹曾与陆九渊有“无极太极”论辩,这是关于周濂溪《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应如何解释的问题。陆九渊认为周敦颐此句有如老子“有生于无”,即太极是由无极而来。他主要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理解,认为“易”之“太极”即是“中”,即是本源;在“太极”之上再加“无极”,是“叠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①朱熹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认为非“太极”之外复有一“无极”,两者本一,“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但分解地说,“无极”是有中说无,“太极”是无中说有。故朱喜说“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②这也就是说,“无极”之“无”非没有之意,即不是不存在,而是无形无状却实有此理之意。它也是存在,只是无形、无状、无名、无限而已。但它却是“太极”之所以为“太极”的存在依据。③
朱熹和陆九渊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各有所据。陆氏之所以会从生成论角度理解这一命题:一是与传统的思维进路有关;二是与《太极图说》的版本有关,因为当时《太极图说》的《国史》本,此句为:“自无极而为太极”。九江本是“无极而生太极”。这两个版本都是“以无为本”、“有生于无”的观点。朱熹不取其说,而作出上面的理解,就在于周敦颐之《通书·动静》章。因为按《太极图说》所言“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如陆氏的生成论之理解,即顺序地从“无极”到“太极”到“阴阳”到“五行”。这里隐含着一个时间的流变过程。
朱熹对“无极而太极”所取周氏《动静》章言:“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①按周氏之意,“物”仅仅执“动”或“静”之一端,要么“动”,要么“静”,非此即彼,故为“不通”。而神则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是超乎动静的。对这种形而上的动静,朱熹说:“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②作为形而上之“神”的动静是变化无穷的。它是能神妙万物的,是动静之理。它跳出了生成流变的过程,消解了时间因子,成为动和静之所以能够动静的原因。“神”是无形无状的,但却又是实有的存在,它可以“妙万物”。“妙万物”是指神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内在本性和变化生生的微妙功能。这个神,实质上是说“无极”和“太极”本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实无先后上下之分。如果硬要说“无极”先于“太极”,那也只能理解为是逻辑在先。③朱熹把周敦颐讲的“太极”解释为“理”,对“太极”本体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二、曹汉辅“无极太极”论
曹汉辅对“太极无极”的理解,主要是从本体和工夫两个方面来阐述。他认为“太极即无极”,故《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中说:“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也。……岂有论有论无,分内分外,滞于名数之末。’”曹汉辅从无极的意义来体会太极,即可进入一浑然无分别之境界,而有无、内外等分别便可消泯。他对“太极无极”本体的规定是“虚而灵,寂而妙,灵妙之体,充满太虚,处处呈露”④。此说认为本体为虚寂灵妙。对此虚灵之本体,曹汉辅又用“寂灭”来规定:“太虚之体,本来寂灭。”⑤大概曹汉辅重视太极之“无极”性格,从虚无处体会本体。他对本体的规定还进一步说:“无则不无,而灵源独立;有则不有,而还归澌尽。”⑥这就是说,本体不落于有无之相对说中,即说有说无皆不可。曹汉辅以“虚灵”来说本体,应是受北宋理学家张载思想的影响。张载云:“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又云:“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①曹汉辅认为,太虚之体虚灵寂灭,为气之本,万化皆会澌尽,而虚灵之体独立恒存。这样理解本体,与张载之意还是有距离的。张载虽言太虚是气之本体,及气散而适得吾体,但亦强调太虚即气,并非至万化澌尽时,方可见本体之存在。而曹汉辅所谓的“寂灭”,是从万化终归于尽,聚而必散上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曹汉辅说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但并不强调“灭”之意,只是说本体虚灵寂妙,充满太虚。如此说,则本体亦是实理,并不是佛教之“寂灭”之意。
在工夫论上,曹汉辅主张“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万物朝宗于我,而运用无滞。”②又说:“游心于无极之真,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③这里所说的“万物朝宗于我”,即天地万物以我为中心;“运用无滞”,即表示本心呈现,理便呈现,而事物之来,皆能恰当回应之;而“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则是从本体之形而上的性格,作为契悟本心的入路而言。曹汉辅从“无极”意契入道体,由此而有“万物朝宗于我,运用无滞”之境。曹汉辅藉着对本体是虚灵无极之体会,使生命能进入一种与日常生活不同之境界,这是一种类似主张“顿悟”的工夫。李彦迪认为,曹氏此一“顿悟”功夫是违反了儒家下学上达之程序,并大加反对。
在李彦迪的论难下,曹汉辅将工夫论修正为“主敬存心,而上达天理”④,并以“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言主敬,便加强了此工夫中的道德意识。但李彦迪认为,此中仍缺乏“下学人事”的工夫,不从下学人事入手,上达天理是不可能的。曹汉辅则认为“下学”工夫是初学的工夫,他说:“下学上达,乃指示童蒙初学之士,豪杰之士不如是。”⑤所以,他说:“先立其体,然后下学人事。”⑥依曹汉辅之意,“下学人事”的工夫须在“先立其体”之后。
曹汉辅还认为“体既立,则运用万变,纯乎一理之正”。在曹氏看来,“先立其体”是较“静涵动察”更为高一层的工夫。此更高一层之工夫,依孟子是求其放心,就是逆觉本心的工夫。如果说“先立其体然后下学”,即在逆觉其本心后,是可以作存养省察之工夫的,而且使工夫更为有效果。但曹汉辅以“主敬存心”来“先立其体”,则未能显示逆觉本心之意。所以,李彦迪很容易便往朱子的“静涵动察,而敬赅动静”的工夫处理解。他说:“下学人事时固当常常主敬存心,安有断除人事,独守其心,然后可以下学?”①在此工夫论辩中,曹汉辅表现了孟子、陆九渊之说的特色。依孟、陆确可当下明本心,先立其大者。所以,李彦迪和曹汉辅之论辩,亦多少表现了朱陆之争的意义。
三、李彦迪“无极太极”论
李彦迪在评论曹汉铺和孙叔暾有关“无极太极”问题的论争后,并在与曹汉铺就本体和工夫的辩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本体论上,李彦迪主要依据朱子的“理气不离”及“理一分殊”说,来强调道至高至妙,又至近至实,道只是人事之理,形而上者必即于形而下者。李彦迪在对太极这一本体之体会时说:
然其间不能无过于高远,而有背于吾儒之说者,愚请言之;夫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抵也。是乃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来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哉!②
从文句来看,这段多採自朱熹答陆子静书之意来论说。③这对朱子“理气不离”之说作了很好的诠释。
李彦迪在补充说明“无极”之意义时说:“此理虽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实体之所以寓,则又至近而至实,若欲讲明此理,而徒鹜于窅冥虚远之地,不复求之至近至实之处,则未有不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矣。”①这就是说,太极之理,虽是至高至妙,而须用无极来形容。但此理之所存在处,是至近至实的。所谓至近至实,是指日用伦常而言。人不能因为天理是形而上的,便专从虚无飘渺,远离人生处想象追寻。这体现了李彦迪重视伦常实践之特色。
李彦迪认为无极是对太极之形容,太极可以言空寂,但乃是寂而感、虚而有,他说:
所以谓之无极者,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非若老氏之出无入有,释氏之所谓空也。”……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风雷之所以变,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也。②
李彦迪还从朱熹中和说之心性关系来论证道体并非寂灭。他说在情绪未发时,性体浑然在中,此可说是寂。但在情绪已发而心感通应物时,此性便表现其作用,故性体之寂,是“寂而感”的。这与佛教的“寂而灭”是不同的。对“中和”之义,李氏说:
其八曰:致中和。……盖天命之性,纯粹至善,而具于人心。方其未发,浑然在中而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及其发而品节不差,无所乖戾,故谓之和。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天下之理皆由是出,故曰天下之大本。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达道。此乃人心寂感自然之理,体用之全。③
这就是说,从未发已发,见理从中而和,有体有用,故并非枯寂无用之体。但李彦迪对《中庸》所说的“中和”之理解,是遵从朱熹之说,即是在“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架构下所说的。理之作用乃是由情之未发至已发,心之由寂然而感通,而显出的。即理挂搭在气上,由气之活动显出理之作用,使理由浑然而粲然。
李彦迪还认为,须正视世间之差别,不能浑然无别。由于理不离气,理必即于形器而存在,故理必有分殊之表现。人反身而于至切近处践履以求明道,必须注意存在事物之差别性、多样性。从李彦迪反对曹汉辅所主张的“一理太虚”①、“物我无间”②来看,李氏对“理一分殊”是十分重视的。他强调不同之存在物皆有其所以如此之理,故物各有不同之司职。他又认为理虽浑然一致,但其中粲然,可知李彦迪意在肯定世间存在事物之差别性。由于肯定分殊,便会相应于各存在物之不同而成就之。由于承认差别,就必须使分殊之个别存在,皆实现自身之价值,必见到在各分殊中皆显出天理,方可见天理之全,在浑然之天理中,存在着无限丰富的内容。这一观点显示了朱子思想中对“致广大而尽精微”境界之向往,亦充分表达了儒家“人文化成”的精神。
在工夫论上,李彦迪对朱子“静涵动察”、“敬贯动静”之工夫,有很深的体会。他说:
圣门之教,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齐其外以养其内,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严然肃然,深省密察,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动直,中一外融,则可以驯致乎不勉不思,从容中道之极矣。两件工夫不可偏废明矣。③
在这里,李彦迪是按照朱子所倡导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④来说,认为持敬省察久了,方可达到“静虚动直,中一外融”之境界。
李彦迪主张“静涵动察”、“敬义夹持”的工夫。他认为须于动、静,未发、已发之时各有工夫,方能使心依理而行。这是在心、理为二时,由于心不即理,故须用敬以夹持,使心合理。依朱子及李彦迪之言,只有存养以立大本的工夫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动时之省察。就是说,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本心之呈现并不易得,大多都处在受感性情绪影响的状况中。这时的动时之省察工夫,就显得尤为重要。故李氏在其诗中云:“中和虽似有宾主,动静周流无定辰。体察工夫终是宾,空虚论说竟非真。”①他所说的省察是对自己任何细微的生命活动皆须反省。在心发为意,意或善或恶之际作工夫;在处事接物时省察体验,而言顾行,行顾言,“制于外以养其中”。这种对动时省察的强调,隐含着他对现实生命的有限性、缺陷性有深切的体会。人的生命充满私欲习气,必须着实下苦功对治,方可有纯洁化之可能。而人在应事接物而动时,其生命问题才会显示出来,此时才好做工夫。而若只是静时涵养之工夫,则不易见生命之毛病。此亦如王龙溪所说:“欲根潜藏,非对境则不易发”②之意。这是修养之实在工夫。
李彦迪认为“主敬存心,下学人事,方能上达天理”。他说:
夫道只是人事之理耳。离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于空虚之境,而非吾儒之实学矣。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者人事也,则者天理也。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安得不先于下学之实务,而驰神空荡之地,可以为上达乎?天理不离于人事,人事之尽,而足目俱到,以臻于贯通之极,则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浑全,酬酢万变,左右逢原,无非为我之贯用矣。故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又曰:“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巨不信欤?③
这就是说,超越的天理,必须从人事的实践中才能体悟。人事实践至尽,便是天理。若离人事而求道,没有不蹈于空虚之境。李彦迪以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体会。李氏此论,有如当代儒学的“道德的形上学”,或“实践的形上学”之论,即形上之道体,是只有藉道德实践才能体证到的,并非思辨可知。故形上理论,须以道德实践为进路来建立。
由上可知,李彦迪的“无极太极”论,对本体和功夫问题的理解,多得自朱子。所以,李退溪在《晦斋李先生行状》中说:
而其精诣之见,独得之妙,最在于与曹忘机汉辅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也。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即朱子)为尤多也。①
退溪认为,李彦迪之论,是合于朱子义理的,并说彦迪此一论辩在其著作中最有“精诣之见,独得之妙”。可见,李彦迪对“无极太极”的阐释,得到后来李退溪的赞赏。
四、李彦迪与曹汉辅“无极太极”论之异
李彦迪与曹汉辅遵从朱子之说,都认为“太极即无极”。李氏说:“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则是也。”②而两人之争论,是对此无极之本体,应如何规定,及如何方能体会、掌握之问题。前者是属本体问题,后者是属工夫问题。李、曹对“无极太极”理解之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在对“道体”的规定性上产生歧义
曹汉辅认为,道体是“太虚之体,本来寂灭”。李彦迪则认为曹汉辅对朱子之本体理解不恰当。他说:
大抵忘机堂平生学术之误,病于空虚。而其病根之所在,则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以灭字说太虚体,是断非吾儒之说矣。谓之寂可也,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谓“於穆不已”者存焉。……此心本然之体,而谓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则喜怒哀乐发皆中节,而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谓“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灭,则是枯木死灰而已,其得不至于灭天性乎?③
李彦迪认为,“寂灭”是佛教之说,用寂灭来形容道体,不合儒家义。若以“寂”形容道体是可以的,但在至寂中,有“於穆不已者存焉”,即道体是既寂而又生生不已的,不能以虚无寂灭来说。在这里,李彦迪对“寂灭”与“寂感”作了区分,显示了他对儒佛之别有恰当的理解。
曹汉辅对李彦迪之意见,有接受,但对自己的见解,亦有坚持。他说:
至如寂灭之说,生于前书粗辩矣,未蒙允。今又举虚灭无极之真,乃曰“虚无即寂灭,寂灭即虚无”,是未免于借儒言而文异端之说,小子之感滋甚。先儒于此四字盖尝析之曰:“此之虚,虚而有;彼之虚,虚而无。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灭。”然则彼此之虚寂同,而其归绝异,固不容不辨。而至于无极之云,只是形容此理之妙,无影响声臭之耳,非如彼之所谓无也。故朱子曰:“老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讵不信欤?①
曹汉辅以“寂灭”来形容道体,又认无极之真,其虚灵无极,即是寂灭。李彦迪对曹氏之论,又引丽末鲜初著名性理学者郑道传《儒释同异之辨》来作说明。郑氏说:
先儒谓儒释之道句句同而事事异。今且因是而推广之。此曰虚,彼亦曰虚;此曰寂,彼亦曰寂。……此曰知行,彼曰悟修;此之知,知万物之理具于吾心也;彼之悟,悟此心本空无一物也。此之行,循万物之理而行之无所违失也;彼之修,绝去万物而不为吾心之累也。此曰心具众理,彼曰心生万法。所谓具众理者,心中原有此理,方其静也至寂,而此理之体具焉;及其动也感通,而此理之用行焉,其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所谓生万法者,心中本无法也,对外境而后法生焉。②
郑道传之说,本朱子之意而推衍,而李彦迪之说,大抵依郑氏。儒家所说之道体,虽亦可用虚、寂来形容,但一定是虚而有,寂而感,决不能说虚而无,寂而灭。按朱子之意,寂感应都从心上说。在情绪未发而心寂然处,理浑然而在;在情绪发时,心感而遂通,在心之感通时,理亦粲然地表现其内容(显为四德)。心之寂然感通,虽具理在其中,但寂感是从心之活动上说,理是不能说寂感。郑道传和李彦迪对寂感之理解,应是上述之意,而并非认为太极是即寂即感的。
曹汉辅对于所以要坚持用“寂灭”来形容道体,有自己的说明。他说:“为破世人执幻形为坚实,故曰寂灭。”③对此说,李彦迪反驳说:
此语又甚害理。盖人之有此形体,莫非天之所赋,而至理寓焉。是以圣门之教,每于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尽夫天之所以赋我之则,而保守其虚灵明德之本体,岂流于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岂可以此为幻妄,必使人断除外相,独守虚灵之体,而乃可以为道乎?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此寂灭之教所以陷于空虚诞谩之境,而无所逃其违天灭理之罪者。①
在这里,李彦迪进一步肯定了一切形器存在之真实性。他认为形而上者必即于形而下者存在,故形而下者必有天理为其存在之根据。形而下者,就形器本身之存在状况来说,当然是聚散变化,生灭不已的,不会永恒不变地存在。但在形器之变化过程中,都有实理贯串其中,都显现了理的意义,故虽聚散变化,但形器本身并非虚幻而无意义。李氏肯定形器,并非只就形器说,而是由“道不离于形器”来说。道不孤悬,必即于形器;而器亦不只是器,必有其所以然之理。李彦迪这一说法,可以说是对朱子“理气论”作了很好的诠释。由于理气不离,故天理不离形器,一切事物皆有其道,一切存在皆有其存在之客观根据,并不是偶然而虚忘的。又由于理不杂于气,故人必须努力探索践履,于形器中体会其形上根据,于事物上了解其当然之则。
2.在对“道体”的体会之工夫上有不同见解
曹汉辅对“道体”的体会,主张“主敬存心,上达天理”②。李彦迪对此说:
此语固善,然于上达天理,却欠下学人事四字,于圣门之教有异。天理不离于人事,下学人事,自然上达天理;若不存下学工夫,直欲上达,则是释氏觉之之说,乌可讳哉?盖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则天理之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便是上达境界。从事于斯积久贯通,可以达夫浑然之极矣。而至于穷神如化之妙,亦不过是而驯致耳。③
在这里,李彦迪藉朱子“理气不离”之义,来说明形而上之道,不离形而下之器。而若形而上者不离形而下者,则人欲知天理,便只有在形而下之存在处寻求;舍此而外,别无他途。他认为不下学人事,是不能上达天理的。“下学人事,方能上达天理”之说,实含有“理必不离人事”,能于人事中表达出来的,方是道德之理。如果单靠心的虚明,是不能表现道德之理的。
曹汉辅以“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为工夫,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是以无极太虚之体作为心之主,是体证本心的工夫,未必是静以涵养心中之理,即未必是在心与理为二之下存养工夫。李彦迪认为,曹汉辅此一工夫有所偏。他说:
来教有曰:“敬以直内,顾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坚定不易。”则固存养之谓矣,而于静时工夫则有矣;若夫顿除下学之务,略无体验省察之为,则于动时工夫,盖未之及焉。是以其于求道之功,疏荡不实,而未免流为异端空虚之说。伏睹日用酬酢之际,不能无人欲之累,而或失于喜怒之际,未能全其虚灵之本体者有矣。岂非虽粗有敬以直内工夫,而无此义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体道不能精密,而或于此乎?①
李彦迪认为曹汉辅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有差失,正是因为只有静时的“敬以直内”之工夫,而欠缺动时的“义以方外”工夫所致。若不能以本心即理,则心是现实的经验义之心,对于此一意义之心,确实需要这种静涵动察,敬义夹持的工夫。但若曹汉辅所说的“顾諟天之明命”,是让炯然不昧之本心作为人生命之主宰,则是另一种功夫,并不可以套在“静涵动察”之工夫系统下。所以,李彦迪说曹忘辅只有主敬存养之静时的工夫,而缺乏已发时省察之动时的工夫。
李彦迪非常强调动时工夫的重要,他说:
昔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子继之曰;“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然则圣门工夫,虽曰主于静以立其本,亦必于其动处深加省察。盖不如是,则无以克己复礼,而保固其中心之所以存矣。故曰“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未有不制其外而能安其中也。愚前所云“存省体验于日用事物之际,而言顾行,行顾言”者,此之谓也。安有遗其心官,随声逐色,失其本源之弊哉!……若未到从容中道之地,而都遗却择善省察工夫,但执虚灵之识,不假修为,而可以克己复礼,可以酬酢万变云,则譬如不出门而欲适千里,不举足而欲登泰山,其不能必矣。①
按朱子来说心,是经验义的心,故必须以静涵动察,敬义夹持为工夫,这两方面下功夫是必须的。所以,李彦迪以曹汉辅的工夫为有所偏。
李彦迪以曹汉辅之言工夫,是如不出门而欲适千里,是不可能达到目的之工夫。这是纯依朱子来说,此一批评是值得商榷的。若是本心呈现,理便存在,而且离开实践行动之源,何以不能克己复礼?曹汉辅之说,是先立本以为人生命活动之主宰。他批评李氏所倡导之工夫是“遗其心官,随声逐色,失其本源”②,是“姑舍其体而先学其用”③。李彦迪要“制外以养中”④,当不会随外物而转,但从曹氏的批评,可见曹汉辅对“先立本”是十分强调的。曹氏认为他自己所倡导的是“立纲领”的功夫,即他所说的“衣必有领而百衣顺,纲必有纲而万目张”⑤。
以上对李彦迪与曹汉辅的“无极太极”论辩作了疏释,从本体及工夫两方面,分析了李、曹二人的辩论内容。从中可看出,李彦迪对朱子思想有较深入的理解,表现出朱子学重视道德实践,强调下学的特色。而曹汉辅的思想中,则具有陆王之学的某些特征。
(原刊于《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
附注
①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载《韩国文集从刊》第24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①陆九渊:《与朱元晦》,载《陆九渊集》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7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陆子美书》,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60页。
③徐洪兴:《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关系考》,《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①《通书·动静第十六》。
②《朱子语类》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03页。
③徐洪兴:《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关系考》,《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④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晦斋集》卷五。
⑤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晦斋集》卷五。
⑥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晦斋集》卷五。
①《正蒙·太和篇》。
②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晦斋集》卷五。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晦斋集》卷五。
④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晦斋集》卷五。
⑤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晦斋集》卷五。
⑥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晦斋集》卷五。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晦斋集》卷五。
②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晦斋集》卷五。
③见《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68页。
①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晦斋集》卷五。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晦斋集》卷五。
③李彦迪:《进修八规》,《晦斋集》卷八。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晦斋集》卷五。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晦斋集》卷五。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晦斋集》卷五。
④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76页。
①李彦迪:《次忘机堂韵》五首之二,《晦斋集》卷四。
②王龙溪:《三山丽泽录》,载《王龙溪语录》卷一,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第8页。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一书》,《晦斋集》卷五。
①退溪学研究院编:《陶山全书(三)》,首尔:高丽书籍株式会社,1988年,第393页。
②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晦斋集》卷五。
③李彦迪:《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晦斋集》卷五。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晦斋集》卷五。
②郑道传:《三峰集》卷九,载《韩国儒学资料集成(上)》,首尔:延世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晦斋集》卷五。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晦斋集》卷五。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晦斋集》卷五。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二书》,《晦斋集》卷五。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晦斋集》卷五。
①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晦斋集》卷五。
②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晦斋集》卷五。
③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晦斋集》卷五。
④李彦迪:《答忘机堂第三书》,《晦斋集》卷五。
⑤李彦迪:《答忘机堂第四书》,《晦斋集》卷五。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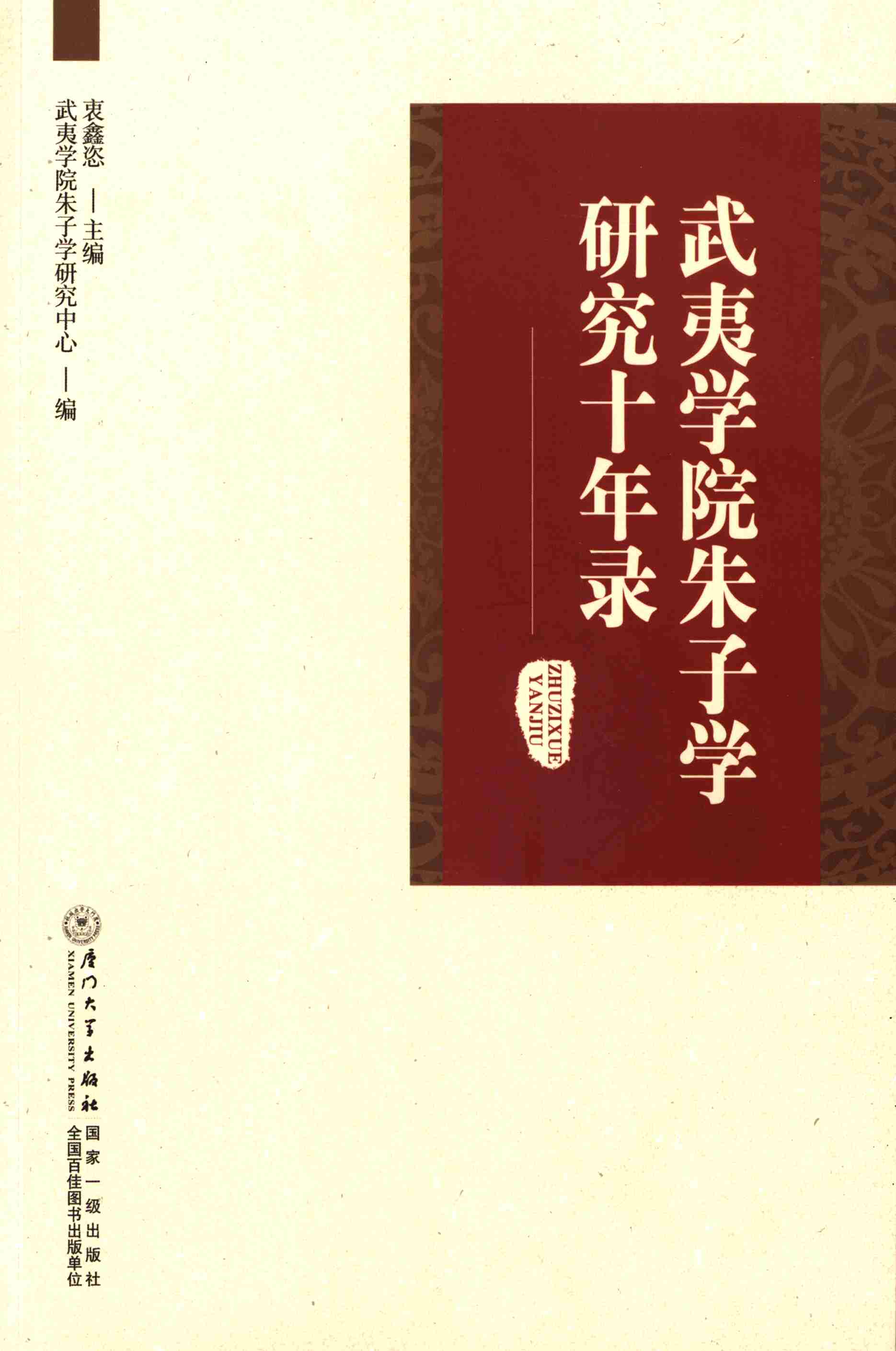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2008-2018年公开发表的朱子学研究论文37篇,按文章内容分成了朱子与理学、朱子与社会、朱子与教育、朱子与当代、朱子与东亚、朱子与闽台等几组。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