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风流与儒者气象
| 内容出处: |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472 |
| 颗粒名称: | 才子风流与儒者气象 |
| 其他题名: | 柳永与朱熹文化人格比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87-97 |
| 摘要: | 这段文字探讨了柳永和朱熹在宋代的武夷山地区的文化活动和影响。柳永和朱熹都出生在当地的世家,但他们的个人追求和人生格调却截然不同。柳永追求感官享乐和爱情体验,表现出潇洒自如的生命格调,而朱熹则追求道德理想,注重生命情调。这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追求,也影响了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和认知。 |
| 关键词: | 教育 儒家文化 朱熹 |
内容
有宋一代,武夷山人文荟萃,碧水丹山不仅孕育出风流才子柳永,还滋养出辉映当时、泽及后代的一代大儒朱熹。柳永(987—1057)出生于北宋盛世的崇安县五夫里,在家乡度过他的少年时代,青年时期离开崇安就再也没有回来;朱熹(1130—1200)出生于南剑尤溪,14岁丧父,居五夫里,师事武夷三先生,中举后除几年外出做官,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度过。柳永和朱熹,一个是北宋盛世困顿科场的“白衣卿相”,一个是南宋衰微之际传道民间的学术素王,他们皆仕途偃蹇,而死后地位却截然不同:朱熹被历代统治者逐渐神化为圣人,朱子之学也被认定为官方学说;而柳永,由于历代文人围绕其词雅俗之争对其人品、词品颇有微词,一直是见弃于正统文化之外的浪子形象。
两人在生命格调和精神风貌方面迥异其趣,代表了中国士人文化人格截然不同的两方面,影响着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行为方式、精神追求和生命底蕴。南怀瑾在《易经杂说》中认为:“人生最大的哲学是在‘存亡’、‘进退’、‘得失’这六个字。”①从出处行藏作为切入点可以很好地考察、比较其文化人格的不同。
一、薄于操行的风流浪子与克己自律的道学家
柳永和朱熹皆有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学背景,少年时皆颖悟好学,在理智上都信奉修齐治平、积极济世的儒家思想。但柳永的儒家思想更多世俗功利色彩,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原始儒学已经蜕化为士人藉以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成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柳永也未脱樊篱,少年时即作《劝学文》自勉:“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①其内心深处一直有无法割舍的仕宦情结,代表了封建社会一般读书人的普遍愿望。
青年时代的柳永离开家乡来到汴京,立刻被繁华的都市文化所吸引,接受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享乐思想,“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②并很快投入艳情词创作,成为风靡词坛的都市流行歌词作者。柳永在歌坛上赢得了无限风光,却也为以后的仕途埋下了隐患,第一次进士考试即被仁宗以“薄于操行”之由而黜落。世俗功利欲望受挫后必然产生强烈的逆反,自视甚高的柳永《鹤冲天》高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自称“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走向正统文化的对立面。“白衣卿相”一词足见柳永思想深处的矛盾:既不甘作一介平民久居人下,渴望高官厚禄,又怨恨统治者埋没人才而自甘堕落。作为负气带性之人的一种反抗,柳永更加放纵地投身于绮罗香泽、声色享乐之中,走向及时行乐和玩味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从此,在他的处世心态和人生哲学里,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的儒家积极入世精神消退成为潜在的思想,而彰显一种佯狂、玩世不恭的叛逆行径,一种非中庸的极端形态,通过自我堕落,以对通行价值观的挑战姿态来表现其对生存状态的不满,成为徘徊于正统文化之外的边缘人。
柳永将生命的砝码移向了男女私情,更无顾忌地投入词的创作,表现出潇洒自如的生命格调。与儒者比较,文人注重生命情调,词人更重感性经验,尤其是情感体验,成为其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词更适于表现人性的真实存在,充满世俗生活气息,本来就志短情长,“不再以紧张的政治观念或者沉重的理性原则压抑自我的生命自由和感性享乐。”①词放弃传统写作模式对于道德和教化的守护,抒写的是感性生命的忧伤与欢乐,甚至可以写正统文学不宜言说的男女色欲之大防。柳永为世所诟病皆因其“好为俳体,词多媟黩”②。柳词重感性,沉醉于感官的放纵和欲望的满足中,展现的是真实、活泼的人性,带有明显的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倾向。
柳永的人生态度和词作具有明显的离经叛道性质,带有追求个人适意和精神自由而反社会、反权威、反主流价值的倾向,统治者发现传统儒家道德戒律在柳永身上已失去约束力,进而有可能使儒家那一套的纲常名教失去维系社会稳定的力量,因此封建统治阶层和士大夫将柳永作为“小有才而无德”的鉴戒,视之为传统道德的破坏者而深恶痛绝。可以说柳永是风流才子的典型,是正统儒家的叛臣逆子,具有有悖于士大夫传统文化品格的另类人格。
不同于柳永的追求感官享乐和爱情体验,儒者追求道德理想。朱熹对文学也很在行,但自命二程道学传人、追求德性圆满自足的儒者立场,常使他有感于作文害道,认为诗人的生活多崇尚感觉,作诗须有情感体验,难免流为人欲之私,因此放弃了当文人的念头,立志做读书穷理的儒者。从朱熹开始文人与儒者之间逐渐形成很深的夙怨:“文人多视理学家为迂阔不通人情的腐儒,泥古不化而空谈性理;儒者多认为文人是不拘礼节的轻薄之士,难免有蔑视权威而犯上作乱之嫌。”③在以醇儒自居的理学家看来,一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理性规范的言行都属于“玩物丧志”的表现,朱熹就曾批评欧阳修、苏轼等人:“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作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④朱熹对柳永只字未提,或许是不屑一顾,因为朱熹是极力反对时文俗曲的,而柳永艳情词是典型的时文俗曲。而朱熹的老师刘子翬对柳永却评价极高:“屯田词,考功诗,白水之白钟此奇。钩章棘句凌万象,逸兴高情俱一时”⑤认为柳永是武夷山后生俊秀效仿的榜样。刘子翬是诗人中的理学家,其理学思想既有家学渊源,也有对名重一时的胡安国、杨时等理学家的师承,可见在刘子翬理学家和文人并非决然对立无法相融。朱熹参与了《屏山集》祖本的校编,还撰写了《屏山集原跋》,不可能不知其师对柳永的评价,之所以不作评价大概出于朱熹向来对吟诗作词的矛盾心理,或许是出于对其师刘子翬的尊重。
朱熹一生清贫,过着晦居山林的淡泊生活,清心寡欲,甘于读书穷理和思想改造之苦,探求圣人之道,执着地把“立德”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立身严谨,其言行举止不仅有不苟言笑、严于律己的严肃,也有嫉恶如仇、正义凛然的庄重。朱熹弟子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说,朱熹常常终日俨然,端坐一室,晚睡早起,连走路都是整步徐行,“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事事表现出整齐严肃的态度,生活近乎刻板。朱熹在为自己画像作的《写照铭》这样形容自己:“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共终。操有要,保无穷。”他确实做到了立身端正、自我检点、坚持操守,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晚年曾亲自抄录程颐所言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的“四箴”贴在墙上,作为修身养性的座右铭。
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亲近女色,怕溺于情而伤害义理。《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诗云:“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从奏劾风流贪官唐仲友一案中可以看出朱熹对人欲泛滥的深恶痛绝和对端人正士品行和良好社会风化的崇尚。他是从事道德教化的布道者,贯穿朱子一生的正心诚意之说、知行统一精神和体现他教育思想的《朱子家书》、白鹿洞书院学规等,无不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精髓。
作为以“醇儒”自居的理学家,朱熹具有强烈的道学忧患意识,于南宋社会危机中发现了封建社会的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认为国家的衰落、政治的腐败与社会人心的道德堕落和信仰危机紧密相连,所以将二程理学作为拯救南宋衰败的精神力量,试图通过振兴儒学教育来改变世道人心。朱熹为弘扬儒家失落的实践理性,深入到文化思想的深层结构,由传统儒学注重纲常伦理的政教意蕴转移到如何做人的心性修养上,建立起一种实践的儒家仁学,使传统儒学成为士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在道德需求,把儒学作为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据,要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注重操持涵养心性,以培养严肃整齐的道德人格。他的五经学和四书学标志儒学思辨化历史进程的完成,树立了为适应大一统王权政治需要的儒家正统学说的思想权威。“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①,是要有赖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和养心存性。严肃、庄重的理性精神使朱熹具有持敬、克己工夫,于内始终保持道德的自律,于外事事都要符合理的法度和规范,往往克制自我情感欲望而入世苦行,因此必然带有否定自我、压抑个性的倾向。
柳永和朱熹,一个是薄于操行的风流浪子,一个是克己自律的道学家;一个偏重感性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超越,易流于浅薄轻浮,一个偏重于严肃、庄重的理性反思,易流于艰奥深沉;一个代表了人类文化中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一个代表了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他们的矛盾,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两种对立的典型文化人格,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内部的深刻矛盾。
二、歌功颂德的干谒者与狷介刚直的道学诤臣
柳永和朱熹的文化人格可以从他们对功名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进行比较。
柳永屡试不第,表面佯狂,骨子里却放不下功名利禄,曾多次寻找机会干谒权贵以求引荐,可以说,柳永是北宋创作干谒词第一人也是最多的一个。据《后山诗话》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骩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会改京官,乃以无行黜之。后改名永,仕至屯田员外郎。”②为得到赏识和重用,柳永可谓费尽心机,不仅向内官请求援引,也曾干谒当朝宰相晏殊,不料被晏殊数落了几句,说他没有作为官员应有的文化品格,只好尴尬地无言而退。柳永很多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真实地再现了北宋繁华富庶的盛世图景,但不可否认一些作品有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嫌。如《玉楼春》有三首写皇家庆典,皆是谀美应景之作。柳永还有意创作了不少投献之作,如《送征衣》《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永遇乐》(薰风解愠),据薛瑞生《乐章集校注》考证,都是为宋仁宗祝寿而作。又有《早梅芳》词是投献给杭州知府孙沔的,《一寸金》(井络天开)为投献益州太守蒋堂所作,《永遇乐》(天阁英游)为投献苏州太守而作,大都刻意歌颂主人的事功人品,含蓄地表达了希望主人纳贤好客、提携自己的愿望。这些应酬文字都暴露了柳永强烈的功名意识、摆脱低微社会地位的渴望。及第被黜,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打击,既愤愤不平,又不失时机到处干谒请托,进而形成依附人格和从众心理,随俗浮沉,足见其人格的矛盾性。
但柳永毕竟不同于功名利禄之徒,干谒求官主要是为了实现他少年时代的儒家理想,作为文人他还是有一定的操守。他不时在词中表达对这种奔波竞走生涯的冷静反思和厌恶:“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①黄氏在《蓼园词评》里评说:“趋炎附热、势利薰灼、狗苟蝇营之辈,可以‘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二语尽之。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是耆卿虽才士,想亦不喜奔竞者,故所言若此。此词实令触热者读之,如冷水浇背矣。意不过为‘衣冠冒炎暑’五字下针砭,而凌空结撰,成一篇奇文。”②在经受上层社会的冷眼、饱受羁旅奔波之苦后,柳永清醒地认识到“名缰利锁”对生命的剥离,思想上还有作为文人独立的人格和自尊,但传统和现实的压力迫使他无法割舍功名,因此柳永的人格是矛盾的。
由于柳永长期困顿科场、流连情场,景祐元年(1034年)50岁进士及第后,至多只做了屯田员外郎这类小官,终其一生无政绩可考。柳永只是北宋盛世一个风流才子的典型,在政治、学术上几乎无所建树。
与柳永人格的游离不同,朱熹具有一种顺境退守、逆境进取的道学性格,难进易退,不肯唱颂歌,却专好唱丧曲,天生有一副逞强好辩的性格。
这种狷介刚直的道学性格首先表现在对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南宋衰微之际,统治者战和不定,由于隆兴北伐的失败,朝廷笼罩着苟安主和退守的氛围。朱熹一变多年来上状辞免的态度,慨然入京奏事,总结北伐失败的原因,指出当时国家根本之忧不在边境而在庙堂,对奸邪误国、近习小人的结党弄权进行严厉的批评。历经人世忧患的朱熹称得上是封建衰世以倡道救世为己任的匡世之才,他的三大政治主张是由安民—治官—正君构成的更革弊政体系,施仁政、宽民力、打击贪官近习和要皇帝正心诚意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对大病沉疴的南宋社会所下的一贴救世良方。朱熹不断地犯颜直谏,其庚子封事、延和奏事对皇帝赵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戊申封事洋洋万余言:“可以称得上南渡以来第一篇奏疏文字,是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的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解剖,也是理学家用正心诚意之学解决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著名的范例。……在愤激慷慨与理智冷静交织的陈词中,搏动着哲人的明智博大与庸人的昏聩渺小,帝王放臣的忠肝披露与道学铮骨的桀骜犯上,衰世大厦将倾的忧焚如火与拯民水火的真诚呼喊。”①“这些放肆无忌的攻击是需要有极大的近于迂气的胆量的。”②
朱熹是强毅威严、雷厉风行的治才,更是体恤民情、拯民水火的仁者。朱熹一生出仕的时间并不长,却不断在现实中实践理学拯人心、挽世道的力量。综观朱熹一生政绩,他治世刚决,敢于向腐败的官僚制度开刀,打击豪强、贪官、滑吏向来不手软,有着非凡的政绩。朱熹不仅有“法治”一手,还有“礼治”、“文治”的一手,不愧为革除弊政的改革家。由于各种邪恶势力的阻挠,朱熹的改革大都付之东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移风易俗、振厉士风、震慑贪官酷吏的成效,表现出一代儒宗直面现实、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
昏君、庸相、叛臣、近习权幸、主和派,构成南宋小朝廷反道学的政治核心,对朱熹等道学家频频施以残酷的打击,但朱熹铮铮傲骨,从未屈服。他一次次触怒最高统治者,一次次被迫请辞归隐于武夷山。归隐后朱熹毫不退缩,不断反思和批判封建文化,埋头铸造理学之剑。垂暮之年,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成为帝王师,入侍经筵仅四十六日,因提出防止帝王独断与近习预权之法,招致这位表面上从善如流、有志行道的“贤君”的憎恶,赵扩借助外戚与近习剪除道学清议势力,将朱熹打入伪籍并斥为逆党之魁。晚年的朱熹在文化专制的炼狱中备受煎熬,但精神上没有停止求索,转而投入《楚辞集注》和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新的探索中,将世上疮痍化为笔底波澜,最终怀着“吾道不孤”的信念在党禁的阴影中去世。“这也许是他那个苟安腐朽的封建衰世社会在他身上逆反塑造出来的一种特殊进取心态和性格。”③
朱熹的道学性格还表现在对自己思想进行自我反省、在论辩中不断辨析兼取他人思想的怀疑与求实精神。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同形形色色的人与学派进行无休止的讲学论战,其理学思想是在与各种不同论见不断论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论战成了进行传统反思和现实批判的独特方式。著名的有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白鹿洞之会、与浙东学派的角逐、与陈亮等人的义利王霸之辩、与陆九渊的太极论战等,每一次论战都给朱熹思想上带来一次升华,先后完成了对生平学问的三次总结,建立了离经叛道的新经学体系和人本主义的四书学体系,最终集理学之大成。这种特殊的人格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学人格,是一种体道弘道的崇高人格。
有意味的是,柳永作为传统儒学的叛臣逆子,却经常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朱熹作为克己自律的旷世大儒,却屡屡犯颜直谏,时时不忘革除弊政,极力挽救封建衰世。二人皆触及最高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而不被接纳。
三、进退失据的词人与淡泊自守的晦翁
柳永和朱熹都饱经忧患,但化解人生忧患的方式迥然不同。
柳永热衷功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求仕,直到中年,在仕途上仍毫无进展,内心非常失望:“干名利禄终无益。”①失意时沮丧、愤激,得意时又忘乎所以,如进士及第后所作《透碧霄》言语夸饰,颇露志得意满之情。入仕后久困选调,“游宦成羁旅”的困顿奔波生涯又使他陷入更大的仕宦与归隐的矛盾冲突中,产生对功名的怀疑:“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②并油然而生一种人生无常的感受。他认识到传统价值观对人性的剥离,在很多羁旅词中表达对“名宦拘检”的动荡人生的厌倦,更倾向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去生活。柳永幼时居住的武夷山是道教名山,受道家影响很深,有记载称其道骨仙风。精神上无所托庇的空虚迫使他对隐逸生活充满向往:“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试图遁入道家寻找精神避难所。
然而柳永抵挡不住繁华市井和歌妓舞女的诱惑,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了爱情和市井,以爱情的温馨和市井的放纵对抗上流社会的拒斥,弥补功名无望的憾恨,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大隐、中隐、小隐的归隐之路,即以爱情为归隐的方式,追求世俗物欲、情欲的感官享受成为他解脱人生苦闷的主要方式。
柳永在仕途与爱情的追求中表现出明显的进退去就之间的矛盾,往往陷入轩冕与山林不可得兼、个体需求与人生责任不能统一的矛盾之中。这种思想矛盾与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标榜的“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人格理想不同,他受世俗束缚太多而无法做到进退自如。他所体会到的理性世界是有限的,始终无法解决思想深处厌倦现实与执着人生的矛盾,“他只是一个懂得爱情、珍惜爱情,懂得享受生活与温情的世俗才子,不是超凡入圣的圣人,他的道行被滚滚红尘、被和着胭脂的眼泪湮没,不能‘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达不到‘以道家精神来从事儒家的业绩’的‘天地境界’(冯友兰《新原人》)。他还达不到哲人的层次,不能以哲人的思辨精神来看待人生,不能以圣贤的勇力和智慧独立承担人世的艰难。”①其道骨仙风只是一种外在的风度与表象,灵魂深处缺乏真正超然自适的精神。“他所追求的全是外向的,是‘有待’……所以,柳永的一生是两边都落空了。当年他听歌看舞的这种感情生活落空了,用世的志意也落空了。”②由于局限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和感官享乐,他的艳情词和羁旅词充分展示出升平时代失意士人既向往功名利禄又渴望官能享受而不可兼得的矛盾苦闷心态,进退失据,往往陷入求仕而事业无成、求爱而情感无依的两难困境之中,始终无法战胜自我,做自己心灵的主宰。因此,柳永是软弱的,只能作为封建社会俗艳文化的代表而见斥于正统文化之外。
朱熹一生官多禄少,屡起屡扑,纵观其一生,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了积极济世的道学家淡泊自守的另一面。朱熹不仅有二程理学的头脑,还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把佛老作为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方法和途径。朱熹对道教和道家思想学说有十分深入的了解,有着长达十余年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青年时在建阳云谷隐居即自号“晦庵”,准备隐遁山林自晦终老,从壮年建筑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到晚年卜居考亭、沧州精舍,始终埋头著述讲学,过着寂寞清寒的生活,行为上是真正的隐士。旷世大儒的声誉给朱熹带来很多次做官的机会,但朱熹并不贪恋富贵显达,多次受朝廷征召皆上书请辞。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晦居山林的淡然生活,清心寡欲,以著述讲学为独善其身的方式。
儒者的道骨仙风常常隐藏在其灵魂深处,时隐时现,难以捉摸,不像文人那样任性直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朱熹学道不过是“在人生境界和精神修养方面吸收佛道的生存智慧以超越自我,使儒学重新起到全面指导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用,成为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①哲人的思辨精神使他超越于佛道而援佛道入儒,顺应了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而成为一代理学宗师,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大代表。与魏晋名士徜徉山水是为了逃避现实不同,朱熹对现实有着清醒的批判意识,敢于直面现实,与衰朽的上层统治者作艰苦的抗争。“吾道付沧洲”②并不是去做功成名就的隐逸高士,而是要做传道民间的学术素王,他不能身在朝廷建功济世,却可以退居山林倡道拯心。朱熹始终未尝忘怀尘世苍生,“退居山林讲学著述不过是他历来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③一旦时机成熟,便立刻出山,努力在实践中“见儒者之效”和“反振民功”。
朱熹从容地进退于仕宦与归隐之间,“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始终是自己的主宰,从未象柳永那样心为形役,既享受了山水林泉的宁静恬适、超然无碍,又无个体价值的失落感,用则进,废则退,每次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后更是收敛身心、韬光养晦,力戒躁进之病,做一个平和、冲淡、闲适的真正的“晦翁”。
朱熹是真正的“‘人中之龙’,一个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宗,进退于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有一个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住的傲魂,不为统治者所屈,不为衰世所用,也不为俗人所理解。”④正如他称赞周敦颐那样,“风月无边,庭草交翠”⑤,朱熹胸次浩然,具有一种“超然于个人名利富贵等私欲束缚而与天地合德的快乐……一种经过持敬存养的长期修炼后所具有的德性圆满而内心充实的心境。”⑥这就是所谓能洞悉天地万物本体而胸中洒落、天人合一的圣贤气象,是千百年来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贤境界,惟有朱熹等极少数人达到了这一境界。
结论
柳永是北宋升平时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导致人欲膨胀并进而影响文人阶层所产生的风流才子的代表,而朱熹是南宋封建衰世内外交困、文化道德全面衰退时期试图以理学为武器对封建文化做一次全面总结和振兴的旷世大儒。柳永重感性体验,以审美活动为生命的最高形式,柳词蕴含着封建社会见斥于正统文化之外的浪子才人对生活的体会和特殊的文化心理,放浪有余而严肃不足,因而政治上难有作为。柳永经历了由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转入享乐主义再转入对道家出世思想的向往,且一直在矛盾中徘徊的过程,作为封建传统文化的另类——风流才子形象为中下层文人和市民阶层所喜爱,成为俗艳文化的代表。朱熹是读书穷理的儒者,是道德教化的布道者,经历的是一个出入佛老而归宗于儒学的蜕变过程,重视的是理性,以道德人格的涵养作为拯救封建衰世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的利剑,严肃有余而豁达不足,他建立起的理学文化大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精神支柱,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大代表和后世景仰的圣人。柳永词心放旷,追求个人价值和审美价值;朱熹道心为微,强调伦理价值和群体价值。两人代表了中国士人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追求,反映了传统文化中个性价值和群体价值的深刻矛盾,在这矛盾不断的对立统一和扬弃过程中影响了中国士人的文化人格。
(原刊于《武夷学院学报》第33卷第4期,2014年8月)
两人在生命格调和精神风貌方面迥异其趣,代表了中国士人文化人格截然不同的两方面,影响着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行为方式、精神追求和生命底蕴。南怀瑾在《易经杂说》中认为:“人生最大的哲学是在‘存亡’、‘进退’、‘得失’这六个字。”①从出处行藏作为切入点可以很好地考察、比较其文化人格的不同。
一、薄于操行的风流浪子与克己自律的道学家
柳永和朱熹皆有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学背景,少年时皆颖悟好学,在理智上都信奉修齐治平、积极济世的儒家思想。但柳永的儒家思想更多世俗功利色彩,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原始儒学已经蜕化为士人藉以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成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柳永也未脱樊篱,少年时即作《劝学文》自勉:“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①其内心深处一直有无法割舍的仕宦情结,代表了封建社会一般读书人的普遍愿望。
青年时代的柳永离开家乡来到汴京,立刻被繁华的都市文化所吸引,接受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享乐思想,“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②并很快投入艳情词创作,成为风靡词坛的都市流行歌词作者。柳永在歌坛上赢得了无限风光,却也为以后的仕途埋下了隐患,第一次进士考试即被仁宗以“薄于操行”之由而黜落。世俗功利欲望受挫后必然产生强烈的逆反,自视甚高的柳永《鹤冲天》高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自称“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走向正统文化的对立面。“白衣卿相”一词足见柳永思想深处的矛盾:既不甘作一介平民久居人下,渴望高官厚禄,又怨恨统治者埋没人才而自甘堕落。作为负气带性之人的一种反抗,柳永更加放纵地投身于绮罗香泽、声色享乐之中,走向及时行乐和玩味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从此,在他的处世心态和人生哲学里,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的儒家积极入世精神消退成为潜在的思想,而彰显一种佯狂、玩世不恭的叛逆行径,一种非中庸的极端形态,通过自我堕落,以对通行价值观的挑战姿态来表现其对生存状态的不满,成为徘徊于正统文化之外的边缘人。
柳永将生命的砝码移向了男女私情,更无顾忌地投入词的创作,表现出潇洒自如的生命格调。与儒者比较,文人注重生命情调,词人更重感性经验,尤其是情感体验,成为其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词更适于表现人性的真实存在,充满世俗生活气息,本来就志短情长,“不再以紧张的政治观念或者沉重的理性原则压抑自我的生命自由和感性享乐。”①词放弃传统写作模式对于道德和教化的守护,抒写的是感性生命的忧伤与欢乐,甚至可以写正统文学不宜言说的男女色欲之大防。柳永为世所诟病皆因其“好为俳体,词多媟黩”②。柳词重感性,沉醉于感官的放纵和欲望的满足中,展现的是真实、活泼的人性,带有明显的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倾向。
柳永的人生态度和词作具有明显的离经叛道性质,带有追求个人适意和精神自由而反社会、反权威、反主流价值的倾向,统治者发现传统儒家道德戒律在柳永身上已失去约束力,进而有可能使儒家那一套的纲常名教失去维系社会稳定的力量,因此封建统治阶层和士大夫将柳永作为“小有才而无德”的鉴戒,视之为传统道德的破坏者而深恶痛绝。可以说柳永是风流才子的典型,是正统儒家的叛臣逆子,具有有悖于士大夫传统文化品格的另类人格。
不同于柳永的追求感官享乐和爱情体验,儒者追求道德理想。朱熹对文学也很在行,但自命二程道学传人、追求德性圆满自足的儒者立场,常使他有感于作文害道,认为诗人的生活多崇尚感觉,作诗须有情感体验,难免流为人欲之私,因此放弃了当文人的念头,立志做读书穷理的儒者。从朱熹开始文人与儒者之间逐渐形成很深的夙怨:“文人多视理学家为迂阔不通人情的腐儒,泥古不化而空谈性理;儒者多认为文人是不拘礼节的轻薄之士,难免有蔑视权威而犯上作乱之嫌。”③在以醇儒自居的理学家看来,一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理性规范的言行都属于“玩物丧志”的表现,朱熹就曾批评欧阳修、苏轼等人:“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作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④朱熹对柳永只字未提,或许是不屑一顾,因为朱熹是极力反对时文俗曲的,而柳永艳情词是典型的时文俗曲。而朱熹的老师刘子翬对柳永却评价极高:“屯田词,考功诗,白水之白钟此奇。钩章棘句凌万象,逸兴高情俱一时”⑤认为柳永是武夷山后生俊秀效仿的榜样。刘子翬是诗人中的理学家,其理学思想既有家学渊源,也有对名重一时的胡安国、杨时等理学家的师承,可见在刘子翬理学家和文人并非决然对立无法相融。朱熹参与了《屏山集》祖本的校编,还撰写了《屏山集原跋》,不可能不知其师对柳永的评价,之所以不作评价大概出于朱熹向来对吟诗作词的矛盾心理,或许是出于对其师刘子翬的尊重。
朱熹一生清贫,过着晦居山林的淡泊生活,清心寡欲,甘于读书穷理和思想改造之苦,探求圣人之道,执着地把“立德”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立身严谨,其言行举止不仅有不苟言笑、严于律己的严肃,也有嫉恶如仇、正义凛然的庄重。朱熹弟子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说,朱熹常常终日俨然,端坐一室,晚睡早起,连走路都是整步徐行,“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事事表现出整齐严肃的态度,生活近乎刻板。朱熹在为自己画像作的《写照铭》这样形容自己:“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共终。操有要,保无穷。”他确实做到了立身端正、自我检点、坚持操守,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晚年曾亲自抄录程颐所言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的“四箴”贴在墙上,作为修身养性的座右铭。
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亲近女色,怕溺于情而伤害义理。《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诗云:“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从奏劾风流贪官唐仲友一案中可以看出朱熹对人欲泛滥的深恶痛绝和对端人正士品行和良好社会风化的崇尚。他是从事道德教化的布道者,贯穿朱子一生的正心诚意之说、知行统一精神和体现他教育思想的《朱子家书》、白鹿洞书院学规等,无不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精髓。
作为以“醇儒”自居的理学家,朱熹具有强烈的道学忧患意识,于南宋社会危机中发现了封建社会的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认为国家的衰落、政治的腐败与社会人心的道德堕落和信仰危机紧密相连,所以将二程理学作为拯救南宋衰败的精神力量,试图通过振兴儒学教育来改变世道人心。朱熹为弘扬儒家失落的实践理性,深入到文化思想的深层结构,由传统儒学注重纲常伦理的政教意蕴转移到如何做人的心性修养上,建立起一种实践的儒家仁学,使传统儒学成为士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在道德需求,把儒学作为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据,要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注重操持涵养心性,以培养严肃整齐的道德人格。他的五经学和四书学标志儒学思辨化历史进程的完成,树立了为适应大一统王权政治需要的儒家正统学说的思想权威。“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①,是要有赖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和养心存性。严肃、庄重的理性精神使朱熹具有持敬、克己工夫,于内始终保持道德的自律,于外事事都要符合理的法度和规范,往往克制自我情感欲望而入世苦行,因此必然带有否定自我、压抑个性的倾向。
柳永和朱熹,一个是薄于操行的风流浪子,一个是克己自律的道学家;一个偏重感性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超越,易流于浅薄轻浮,一个偏重于严肃、庄重的理性反思,易流于艰奥深沉;一个代表了人类文化中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一个代表了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他们的矛盾,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两种对立的典型文化人格,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内部的深刻矛盾。
二、歌功颂德的干谒者与狷介刚直的道学诤臣
柳永和朱熹的文化人格可以从他们对功名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进行比较。
柳永屡试不第,表面佯狂,骨子里却放不下功名利禄,曾多次寻找机会干谒权贵以求引荐,可以说,柳永是北宋创作干谒词第一人也是最多的一个。据《后山诗话》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骩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会改京官,乃以无行黜之。后改名永,仕至屯田员外郎。”②为得到赏识和重用,柳永可谓费尽心机,不仅向内官请求援引,也曾干谒当朝宰相晏殊,不料被晏殊数落了几句,说他没有作为官员应有的文化品格,只好尴尬地无言而退。柳永很多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真实地再现了北宋繁华富庶的盛世图景,但不可否认一些作品有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嫌。如《玉楼春》有三首写皇家庆典,皆是谀美应景之作。柳永还有意创作了不少投献之作,如《送征衣》《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永遇乐》(薰风解愠),据薛瑞生《乐章集校注》考证,都是为宋仁宗祝寿而作。又有《早梅芳》词是投献给杭州知府孙沔的,《一寸金》(井络天开)为投献益州太守蒋堂所作,《永遇乐》(天阁英游)为投献苏州太守而作,大都刻意歌颂主人的事功人品,含蓄地表达了希望主人纳贤好客、提携自己的愿望。这些应酬文字都暴露了柳永强烈的功名意识、摆脱低微社会地位的渴望。及第被黜,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打击,既愤愤不平,又不失时机到处干谒请托,进而形成依附人格和从众心理,随俗浮沉,足见其人格的矛盾性。
但柳永毕竟不同于功名利禄之徒,干谒求官主要是为了实现他少年时代的儒家理想,作为文人他还是有一定的操守。他不时在词中表达对这种奔波竞走生涯的冷静反思和厌恶:“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①黄氏在《蓼园词评》里评说:“趋炎附热、势利薰灼、狗苟蝇营之辈,可以‘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二语尽之。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是耆卿虽才士,想亦不喜奔竞者,故所言若此。此词实令触热者读之,如冷水浇背矣。意不过为‘衣冠冒炎暑’五字下针砭,而凌空结撰,成一篇奇文。”②在经受上层社会的冷眼、饱受羁旅奔波之苦后,柳永清醒地认识到“名缰利锁”对生命的剥离,思想上还有作为文人独立的人格和自尊,但传统和现实的压力迫使他无法割舍功名,因此柳永的人格是矛盾的。
由于柳永长期困顿科场、流连情场,景祐元年(1034年)50岁进士及第后,至多只做了屯田员外郎这类小官,终其一生无政绩可考。柳永只是北宋盛世一个风流才子的典型,在政治、学术上几乎无所建树。
与柳永人格的游离不同,朱熹具有一种顺境退守、逆境进取的道学性格,难进易退,不肯唱颂歌,却专好唱丧曲,天生有一副逞强好辩的性格。
这种狷介刚直的道学性格首先表现在对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南宋衰微之际,统治者战和不定,由于隆兴北伐的失败,朝廷笼罩着苟安主和退守的氛围。朱熹一变多年来上状辞免的态度,慨然入京奏事,总结北伐失败的原因,指出当时国家根本之忧不在边境而在庙堂,对奸邪误国、近习小人的结党弄权进行严厉的批评。历经人世忧患的朱熹称得上是封建衰世以倡道救世为己任的匡世之才,他的三大政治主张是由安民—治官—正君构成的更革弊政体系,施仁政、宽民力、打击贪官近习和要皇帝正心诚意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对大病沉疴的南宋社会所下的一贴救世良方。朱熹不断地犯颜直谏,其庚子封事、延和奏事对皇帝赵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戊申封事洋洋万余言:“可以称得上南渡以来第一篇奏疏文字,是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的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解剖,也是理学家用正心诚意之学解决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著名的范例。……在愤激慷慨与理智冷静交织的陈词中,搏动着哲人的明智博大与庸人的昏聩渺小,帝王放臣的忠肝披露与道学铮骨的桀骜犯上,衰世大厦将倾的忧焚如火与拯民水火的真诚呼喊。”①“这些放肆无忌的攻击是需要有极大的近于迂气的胆量的。”②
朱熹是强毅威严、雷厉风行的治才,更是体恤民情、拯民水火的仁者。朱熹一生出仕的时间并不长,却不断在现实中实践理学拯人心、挽世道的力量。综观朱熹一生政绩,他治世刚决,敢于向腐败的官僚制度开刀,打击豪强、贪官、滑吏向来不手软,有着非凡的政绩。朱熹不仅有“法治”一手,还有“礼治”、“文治”的一手,不愧为革除弊政的改革家。由于各种邪恶势力的阻挠,朱熹的改革大都付之东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移风易俗、振厉士风、震慑贪官酷吏的成效,表现出一代儒宗直面现实、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
昏君、庸相、叛臣、近习权幸、主和派,构成南宋小朝廷反道学的政治核心,对朱熹等道学家频频施以残酷的打击,但朱熹铮铮傲骨,从未屈服。他一次次触怒最高统治者,一次次被迫请辞归隐于武夷山。归隐后朱熹毫不退缩,不断反思和批判封建文化,埋头铸造理学之剑。垂暮之年,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成为帝王师,入侍经筵仅四十六日,因提出防止帝王独断与近习预权之法,招致这位表面上从善如流、有志行道的“贤君”的憎恶,赵扩借助外戚与近习剪除道学清议势力,将朱熹打入伪籍并斥为逆党之魁。晚年的朱熹在文化专制的炼狱中备受煎熬,但精神上没有停止求索,转而投入《楚辞集注》和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新的探索中,将世上疮痍化为笔底波澜,最终怀着“吾道不孤”的信念在党禁的阴影中去世。“这也许是他那个苟安腐朽的封建衰世社会在他身上逆反塑造出来的一种特殊进取心态和性格。”③
朱熹的道学性格还表现在对自己思想进行自我反省、在论辩中不断辨析兼取他人思想的怀疑与求实精神。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同形形色色的人与学派进行无休止的讲学论战,其理学思想是在与各种不同论见不断论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论战成了进行传统反思和现实批判的独特方式。著名的有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白鹿洞之会、与浙东学派的角逐、与陈亮等人的义利王霸之辩、与陆九渊的太极论战等,每一次论战都给朱熹思想上带来一次升华,先后完成了对生平学问的三次总结,建立了离经叛道的新经学体系和人本主义的四书学体系,最终集理学之大成。这种特殊的人格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学人格,是一种体道弘道的崇高人格。
有意味的是,柳永作为传统儒学的叛臣逆子,却经常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朱熹作为克己自律的旷世大儒,却屡屡犯颜直谏,时时不忘革除弊政,极力挽救封建衰世。二人皆触及最高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而不被接纳。
三、进退失据的词人与淡泊自守的晦翁
柳永和朱熹都饱经忧患,但化解人生忧患的方式迥然不同。
柳永热衷功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求仕,直到中年,在仕途上仍毫无进展,内心非常失望:“干名利禄终无益。”①失意时沮丧、愤激,得意时又忘乎所以,如进士及第后所作《透碧霄》言语夸饰,颇露志得意满之情。入仕后久困选调,“游宦成羁旅”的困顿奔波生涯又使他陷入更大的仕宦与归隐的矛盾冲突中,产生对功名的怀疑:“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②并油然而生一种人生无常的感受。他认识到传统价值观对人性的剥离,在很多羁旅词中表达对“名宦拘检”的动荡人生的厌倦,更倾向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去生活。柳永幼时居住的武夷山是道教名山,受道家影响很深,有记载称其道骨仙风。精神上无所托庇的空虚迫使他对隐逸生活充满向往:“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试图遁入道家寻找精神避难所。
然而柳永抵挡不住繁华市井和歌妓舞女的诱惑,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了爱情和市井,以爱情的温馨和市井的放纵对抗上流社会的拒斥,弥补功名无望的憾恨,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大隐、中隐、小隐的归隐之路,即以爱情为归隐的方式,追求世俗物欲、情欲的感官享受成为他解脱人生苦闷的主要方式。
柳永在仕途与爱情的追求中表现出明显的进退去就之间的矛盾,往往陷入轩冕与山林不可得兼、个体需求与人生责任不能统一的矛盾之中。这种思想矛盾与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标榜的“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人格理想不同,他受世俗束缚太多而无法做到进退自如。他所体会到的理性世界是有限的,始终无法解决思想深处厌倦现实与执着人生的矛盾,“他只是一个懂得爱情、珍惜爱情,懂得享受生活与温情的世俗才子,不是超凡入圣的圣人,他的道行被滚滚红尘、被和着胭脂的眼泪湮没,不能‘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达不到‘以道家精神来从事儒家的业绩’的‘天地境界’(冯友兰《新原人》)。他还达不到哲人的层次,不能以哲人的思辨精神来看待人生,不能以圣贤的勇力和智慧独立承担人世的艰难。”①其道骨仙风只是一种外在的风度与表象,灵魂深处缺乏真正超然自适的精神。“他所追求的全是外向的,是‘有待’……所以,柳永的一生是两边都落空了。当年他听歌看舞的这种感情生活落空了,用世的志意也落空了。”②由于局限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和感官享乐,他的艳情词和羁旅词充分展示出升平时代失意士人既向往功名利禄又渴望官能享受而不可兼得的矛盾苦闷心态,进退失据,往往陷入求仕而事业无成、求爱而情感无依的两难困境之中,始终无法战胜自我,做自己心灵的主宰。因此,柳永是软弱的,只能作为封建社会俗艳文化的代表而见斥于正统文化之外。
朱熹一生官多禄少,屡起屡扑,纵观其一生,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了积极济世的道学家淡泊自守的另一面。朱熹不仅有二程理学的头脑,还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把佛老作为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方法和途径。朱熹对道教和道家思想学说有十分深入的了解,有着长达十余年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青年时在建阳云谷隐居即自号“晦庵”,准备隐遁山林自晦终老,从壮年建筑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到晚年卜居考亭、沧州精舍,始终埋头著述讲学,过着寂寞清寒的生活,行为上是真正的隐士。旷世大儒的声誉给朱熹带来很多次做官的机会,但朱熹并不贪恋富贵显达,多次受朝廷征召皆上书请辞。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晦居山林的淡然生活,清心寡欲,以著述讲学为独善其身的方式。
儒者的道骨仙风常常隐藏在其灵魂深处,时隐时现,难以捉摸,不像文人那样任性直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朱熹学道不过是“在人生境界和精神修养方面吸收佛道的生存智慧以超越自我,使儒学重新起到全面指导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用,成为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①哲人的思辨精神使他超越于佛道而援佛道入儒,顺应了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而成为一代理学宗师,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大代表。与魏晋名士徜徉山水是为了逃避现实不同,朱熹对现实有着清醒的批判意识,敢于直面现实,与衰朽的上层统治者作艰苦的抗争。“吾道付沧洲”②并不是去做功成名就的隐逸高士,而是要做传道民间的学术素王,他不能身在朝廷建功济世,却可以退居山林倡道拯心。朱熹始终未尝忘怀尘世苍生,“退居山林讲学著述不过是他历来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③一旦时机成熟,便立刻出山,努力在实践中“见儒者之效”和“反振民功”。
朱熹从容地进退于仕宦与归隐之间,“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始终是自己的主宰,从未象柳永那样心为形役,既享受了山水林泉的宁静恬适、超然无碍,又无个体价值的失落感,用则进,废则退,每次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后更是收敛身心、韬光养晦,力戒躁进之病,做一个平和、冲淡、闲适的真正的“晦翁”。
朱熹是真正的“‘人中之龙’,一个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宗,进退于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有一个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住的傲魂,不为统治者所屈,不为衰世所用,也不为俗人所理解。”④正如他称赞周敦颐那样,“风月无边,庭草交翠”⑤,朱熹胸次浩然,具有一种“超然于个人名利富贵等私欲束缚而与天地合德的快乐……一种经过持敬存养的长期修炼后所具有的德性圆满而内心充实的心境。”⑥这就是所谓能洞悉天地万物本体而胸中洒落、天人合一的圣贤气象,是千百年来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贤境界,惟有朱熹等极少数人达到了这一境界。
结论
柳永是北宋升平时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导致人欲膨胀并进而影响文人阶层所产生的风流才子的代表,而朱熹是南宋封建衰世内外交困、文化道德全面衰退时期试图以理学为武器对封建文化做一次全面总结和振兴的旷世大儒。柳永重感性体验,以审美活动为生命的最高形式,柳词蕴含着封建社会见斥于正统文化之外的浪子才人对生活的体会和特殊的文化心理,放浪有余而严肃不足,因而政治上难有作为。柳永经历了由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转入享乐主义再转入对道家出世思想的向往,且一直在矛盾中徘徊的过程,作为封建传统文化的另类——风流才子形象为中下层文人和市民阶层所喜爱,成为俗艳文化的代表。朱熹是读书穷理的儒者,是道德教化的布道者,经历的是一个出入佛老而归宗于儒学的蜕变过程,重视的是理性,以道德人格的涵养作为拯救封建衰世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的利剑,严肃有余而豁达不足,他建立起的理学文化大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精神支柱,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大代表和后世景仰的圣人。柳永词心放旷,追求个人价值和审美价值;朱熹道心为微,强调伦理价值和群体价值。两人代表了中国士人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追求,反映了传统文化中个性价值和群体价值的深刻矛盾,在这矛盾不断的对立统一和扬弃过程中影响了中国士人的文化人格。
(原刊于《武夷学院学报》第33卷第4期,2014年8月)
附注
①南怀瑾:《易经杂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①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五八〇,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236页。
②严有翼:《艺苑雌黄》,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9页。
①颜翔林:《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②冯煦:《蒿庵论词》,见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85页。
③张毅:《苏轼与朱熹》,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④《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96页。
⑤《莱孙歌》,见杨国学:《屏山集校注与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①黄榦:《朱子行状》。
②胡仔:《苕溪渔隐词话》,见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页。
①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8页。
②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61页。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61页。
②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3页。
③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75页。
①《轮台子》,见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3页。
②《凤归云》,见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05页。
①程荣:《柳永的两难处境与儒道思想》,《武夷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②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6页。
②《水调歌头》,《朱子文集》卷一〇。
③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61页。
④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13页。
⑤《濂溪象赞》。
⑥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9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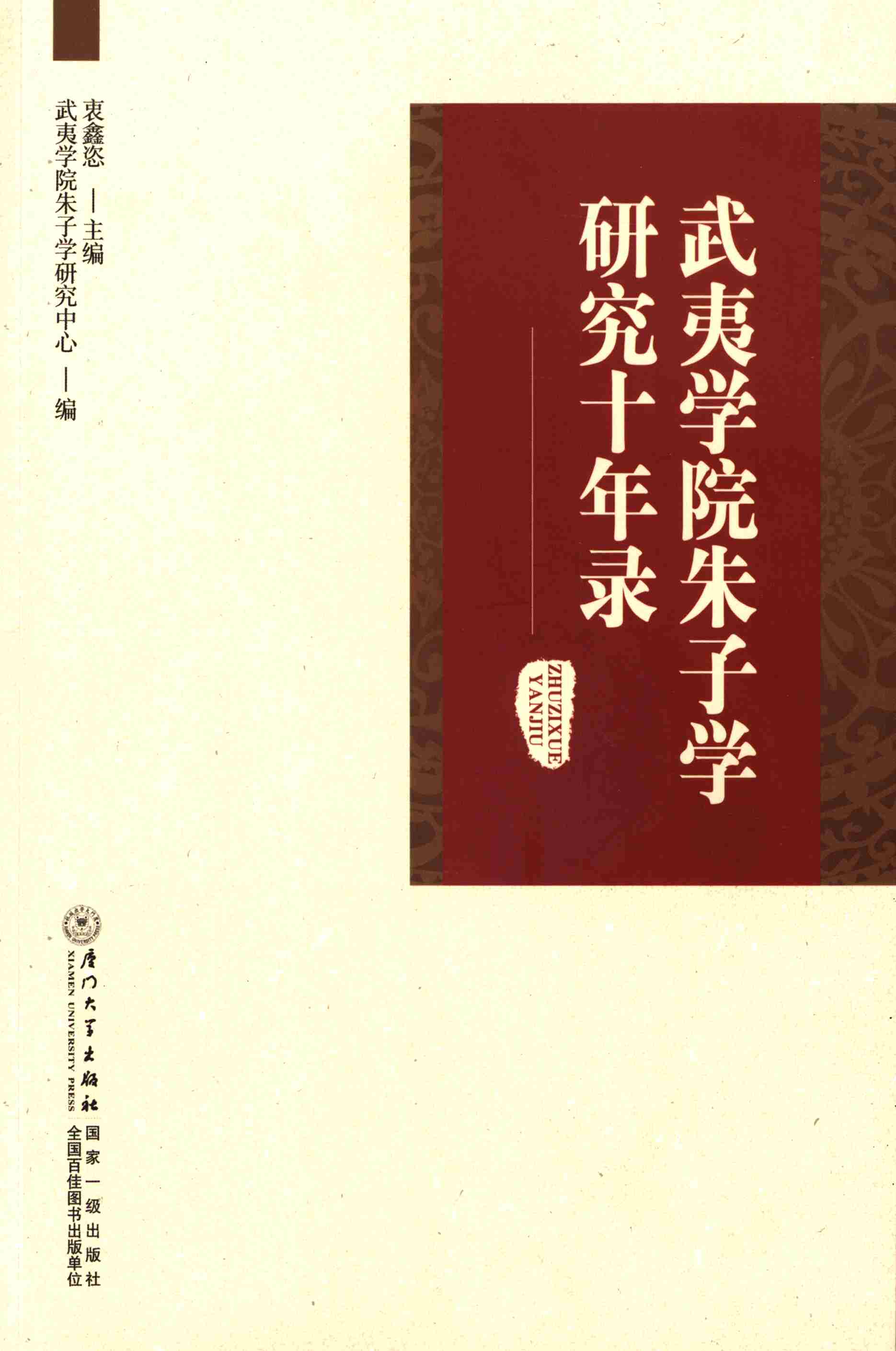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2008-2018年公开发表的朱子学研究论文37篇,按文章内容分成了朱子与理学、朱子与社会、朱子与教育、朱子与当代、朱子与东亚、朱子与闽台等几组。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