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蔡世远的实学研究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412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蔡世远的实学研究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9 |
| 页码: | 646-654 |
| 摘要: | 本文主要内容是关于蔡世远义理思想中的实学因素。蔡世远认为儒学的基本内涵包括道学、经济、文章、气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了儒学的核心。他坚决反驳了一些学者对于理学空谈、无裨实用的批评,强调理学乃是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之学,只有根本深厚、真实无妄的理学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出经济、文章和气节的作用,对世界有重要的影响。蔡世远本人也以治平天下为目标,注重内圣与外王的兼顾,将理学与实践相结合。因此,他的朱子学被认为是一种实学。本文探讨了蔡世远义理思想中的实学因素。 |
| 关键词: | 清初 朱子学 实学思想 |
内容
关于儒学的内涵,不同学者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回答。在蔡世远看来,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相互联系,未尝相离,共同构成了儒学的基本内涵,儒学即“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合而为一者也”④。这既是蔡世远对于杨时学术的总结与褒扬,亦可视作其对自己的期许。针对某些学者对于理学与理学家空谈心性、论多迂疏、无裨实用的批评,蔡世远亦做了坚决的反驳。他说:“夫学贵有本,无本之学,纵修饰补苴,无用于世。有本之学,其根沃者其叶茂。本圣贤所以出治者发而见之事业,是则莫大之经济也;与师友讲明而论著,罔非载道之书,是则莫大之文章也;可死可辱,而浩然之气刚大常伸,是则莫大之气节也。”①换言之,理学乃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之学,唯其根本深厚,真实无妄,故能发为经济、文章、气节之用,实有大用于世。他又以宋、元、明三代之治乱兴衰为例,认为“使程朱得大用于世,隆古之治可复也。宋季指为伪学,国随以微。鲁斋之在元,略见施用,有经邦定国之功。明初正学昌明,成弘之际,风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后,人不遵朱,学术漓而政纪亦坏,非其明效大验欤?”②而蔡世远本人治学亦注重内圣与外王兼顾,以治平天下为归依。在谈及自己的理想与志向时,他说:“学问未敢望朱文公,庶几其真希元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庶几其范希文乎?”③可见其理解与追求的朱子学确实是一种实学。
一 蔡世远义理思想中的实学因素
根据蔡世远的理解,作为本体的天理即是一种生生之理,其最主要的性质是善。“生生之理,善之长也。己与物之所共也,贵与贱之所同也。”④这种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善恶之善,而是最高的至善,既赋予天地万物生命与本质,又构成了万事万物一体相通的基础。至于气,则是万物身体形质的来源,其在生生之理的主宰下通过不断的运动、变化产生天地万物。由于气直接与人的身体、欲望相关,故其往往与生生之理发生冲突,遮蔽了人的本性,阻隔了万物之间的一体相通。“人之心本有是天地生生之理,牿于气、囿于习而善心之遏绝者多矣。”①因此,学者为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恢复本然的善性。
蔡世远的理气论思想较为简单,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复性说提供理论前提。事实上,蔡世远很少直接讨论理、气、心、性等形上问题,亦不注重抽象的哲学思辨,其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朱子学的认识论、工夫论方面,即所谓的实学与实行。蔡世远认为,朱子学以复性为宗旨,主要有三大要点,即主敬、穷理与力行。“不主敬,则无私之体何以澄之?不穷理,则天下古今当然之则何以考之?不力行,则所谓道听途说而已,何由有以复其性之本然哉?”②在他看来,学者只有将主敬、穷理、力行三者结合起来,“纯主敬之功,穷理、力行,以复其性之本然”③,才能革除学术的虚浮、势利之病,复兴程朱之实学。
关于主敬,蔡世远强调其为彻始彻终工夫,须与立志、躬行相结合,贯穿于知行、动静之中,“谨几以审于将发,慎动以持于已发”④,方能避免“失之宽”或“失之严”之弊。故曰:“程子论学之功,莫要于主敬。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又曰:‘只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然此际加功最难,过于矜持则苦而难久,稍宽缓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坚,躬行又力,用谢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敛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体不至昏怠。以此穷理,心极清明,以此克己,气极勇决,更日加涵养,自然德成而学就,所谓彻始彻终工夫也。”⑤
关于穷理,蔡世远特别重视读书的作用。他说:“由明以求诚之方,惟读书为最要。朱子曰:‘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学者率此以读天下之书,则义理浸灌,致用宏裕。”①他还将读书视作力行的基础和前提,提出:“要其加功用力之始,专在读书。若读一书而近里著己,以身体之,以心契之,虽未知果能力行与否,然方其开卷绎诵时,谁无激励与愧耻之心?激励愧耻之心日进不已,则力行而至于古人之涂径也。”②
关于力行,蔡世远将其视为立志与穷理的完成和实现。若知而不行,则流为空谈,无益身心,故称“力行为贵”③。在他看来,“凡讲学不在辨别异同,贵能自得师,知得一事,便行一事。……徒讲解剖判,皆肤词也”④,又谓:“不加体察躬行之功,徒夸闳博雕镂之用,先儒之所羞称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远,亦大雅之所弗尚也”⑤,可见其对力行的重视。
由于当时学者常有好高骛远、厌弃卑近之病,不问具体切近之实事,专求虚玄高妙之空理,故蔡世远论学亦注重下学上达、由博至约之序,强调笃实与晓事之难,要求学者多于此处用功。他说:“学者患于无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笃实;笃实矣,又苦不能晓事。以陈北溪之贤,受业漳州,与闻至道,越十年,往见朱子于竹林精舍,犹谓其尚少下学之功,勉之曰:‘当学曾子之所谓贯,勿遽求曾子之所谓一;当学颜子之博约,勿遽求颜子之卓尔。’北溪自此精进有加。盖笃实之难也。以司马温公之学识,一代宁有几人?明道犹谓君实不晓事。使明道得大用于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温公,自是不侔。然温公尚未足当晓事之称,由是言之,学之进境,岂有涯哉!”①
二 蔡世远的经世之学
作为一位理学名臣,蔡世远屡次批评当时的学者与士子多不知读书为学的目的,“以记诵、词章为止境,以科名、爵位为可毕一生能事”②。在他看来,读书并不是为了记诵、词章,而是为了学为圣人,使万物各得其所,安顿天下秩序;谋求科名、爵位亦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禄,而是为了施展抱负,学以致用,“可以见一生之品节、经济,不至泯没以终耳”③。因此,蔡世远十分重视经世之学,自言:“自年十二三时,涉猎经史诸书,便讲气节,喜作古文,谈经济”④,而方苞亦称其“夙尚气节,敦行孝弟,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议论慷慨,自为诸生,即以民物为己任。及从清恪公游,吏疵民病,言无不尽,政行众服,而莫知其自公”,即便私下所论,“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类之邪正,无一语及身家浅事者”。⑤正因为如此,故其经世思想能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颇多可观之处。
关于为政之道,蔡世远特别强调恳恻与条理两方面因素。恳恻关乎体,条理关乎用,二者不可偏废。他说:“恳恻者,仁也,即《易》所谓‘元者,善之长’,程子所谓‘满腔皆恻隐之心’,张子所谓‘乾父坤母’‘民胞物与’者是也。有条理者,本平日读书穷理之功,措则正而施则行也。无恳恻则立体不宏,无条理则致用不裕。”⑥蔡世远指出,为政者的恳恻并非出于后天功利的考虑,而是源自先天的仁心,“从本原之地流出”,故能“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尽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职分所当为”①,从而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前提与基础,亦是分辨王道与霸道的根本标准。如管仲治齐,虽亦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义示信,极有条理,但其动机在于追求国家富强,而非出于本心之恳恻,故只是霸道而非王道。
在恳恻的基础上,为了妥善地应对和解决现实治理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蔡世远亦很注重为政之条理。“所谓恳恻者无尽,而条理者无穷。事变繁多,土俗各别,所谓条理者,尤难之又难。”②与传统政治思想所提倡的“有治人,无治法”不同,蔡世远较为重视法的作用,主张廉法结合、以法济廉。因为在他看来,“大臣能廉,仅得其半,非廉无以行法,非法无以佐廉。使一己廉静而属员奸贪,或限于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牵制而不能决去,犹是独善其身,岂称开府之治哉?”③同时,蔡世远还很赞赏薛瑄所说的“立法贵在必行,法立而不行,则法为虚文,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主张通过严格的奉法与执法来树立法令的权威性,以此维护民众的利益。蔡世远特别指出,当时地方上以“蠹役与健讼之徒最为民害。蠹役朘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骄横已极,陵绅士如草芥。……健讼者指无为有,饬毫末之事以为滔天,上官不知,辄为听理,小民身家荡散无余”④。故其主张依法严厉打击蠹役与健讼之徒,“摘其尤者,宁确无滥,宁重无轻,惩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务也”⑤。
关于治术,蔡世远并未简单以权术视之,而是将其建立在身心性命之学的基础上,主张“治术关于学术,经济通于性命”⑥。因此,当谈及大臣所应具备的素质时,蔡世远认为其应兼具五方面的综合素质:“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恺恻之怀,有明通之识,有强毅之概,有儆惧之心。无公清之操,则不免有宠利之疾矣。无恺恻之怀,则不能有纳沟之耻矣。无明通之识,则胶执而鲜通矣。无强毅之概,则虽知其然,发之不勇,守之不固矣。无儆惧之心,则自信太过,祸且随之矣。”①这一概括同时兼顾了官员的德行、能力与性格、心态等各方面要素,颇为全面,值得所有官员对照反思,引为鉴戒。
县令作为国家的基层官员,直接与民众相接触,负责管理地方上的日常事务,具体执行国家的法令政策,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纽带。蔡世远就相当重视县令的作用,称其为“亲民之官”,认为“欲天下之均平,人被尧舜之泽,非亲民之官不可”②。根据蔡世远的理解,县令的工作无非三项要点,即息讼、薄赋与兴教。而要做好这三件事,就必须做到“民以事至县者,胥役不扰,无守候之劳,分其曲直,惩其诬黠,诲谕之,又加详焉,则讼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为案实立限,使自封投柜,主以信。使投毕,躬自称平之,榜列明示,归其有余,使补其不足,如期至,则民自不欺,输将恐后矣。择士民之秀者聚之于学,课文饬行,月三四至,又于暇日适山村里闾,言孝弟农桑之事。其有家门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访其家以荣之,而教道兴矣”③。在此基础上,他又告诫即将出任县令的弟子,须淡泊自守,爱民如子,积极为民兴利除害,“事上贵恭不贵屈,驭民以诚不以术”④,如此方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县令。
对于县令与学政二官的职责特点,蔡世远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今之持论者,皆曰外官惟县令与学使最难供职。世远窃谓此二者为最易。夫县令者,朝行一政则夕及于民,兴政立教无耳目不周之处,无中隔之患,古人所谓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学使无刑名、钱谷之繁,惟以衡文劝学、广励学官、振饬士子为职业,草偃风行,比地方职守者尤易。或又以为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谓掣肘者,多由于自掣,非尽人掣之也。夫布衣则古称先,自强不懈,人犹称其严毅清苦,力行可畏,况居官哉?但气不可胜,事不可激,当谨确完养以合乎中耳。”①在此,蔡世远表面上是在强调县令与学政之官易做,实则蕴含了其对这两种官员的重视与期许,希望他们能够善用手中的权力,勤勉于公事,不受外界的掣肘和私心的干扰,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爆发朱一贵事变,震动全台,声势极大,清政府派遣闽浙总督满保督师入台平乱。蔡世远与满保交好,对于征台一事亦十分关注,曾为此数次致信满保,对征台用兵及后续的治台事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建议多被满保采纳施行,对于台湾的安定、治理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蔡世远看来,此次起事者只是一群草窃小寇、乌合之众,与当年的郑氏政权不可同日而语,故讨平叛乱不足为虑。其最担心的是用兵过程中造成的杀掠之祸。蔡世远强调,台湾乃吾故土,台民为吾同胞,大部分从乱者只不过是为人所裹胁驱使,并非有意反叛朝廷,故希望满保能够“严饬将士,并移檄施、蓝二公,约以入台之日,不妄杀一人”②。后事变果然被迅速平定,对于台湾社会亦未造成太大的破坏。但蔡世远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着眼于台湾的长治久安,进一步提出了“平台匪易,而安台实难”③的观点。在他看来,台湾之所以难治易乱,固然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人口结构等客观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地官员的治理不善。他说:“台湾五方杂处,骄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哄聚,风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传舍之意,隔膜之视,所以致乱之由。”④又说:“夫台湾鲜土著之民,耕凿流落,多闽粤无赖子弟,土广而民杂,至难治也。为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爱之,而因以为利。夫杂而不教,则日至于侈靡荡逸而不自禁;不爱而利之,则下与上无相维系之情。为将校者,所属之兵平居不能训练而又骄之。夫不能训练,则万一有事不能以备御;骄之,则恣睢侵轶于百姓。夫聚数十万无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荡逸,无相维系之情,又视彼不能备御之兵,而有恣睢侵轶之举,欲其帖然无事也难矣。”①为了解决台湾的治理难题,蔡世远主张须对台湾民众“教而爱之”,趁此平乱更革之际,彻底整顿吏治,完善管理,与民休息,推行教化。他向满保建议:“文武之官,必须慎选洁介严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兴教化以美风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内地遗亲之民,不许有司擅给过台执照,恐长其助乱之心。新垦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编粮,恐扰其乐生之计。三县县治,不萃一处,则教养更周。南北宽阔,酌添将领,则控驭愈密。”②显然,蔡世远的这些看法与主张是符合当时台湾的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台湾的安定和发展的。
第四节 蓝鼎元的实学研究
蓝鼎元论学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笃守朱子之学而不稍改,力辟释、道、心学等异端;一是注重实用,留心实际,强调有体有用之学,力戒无用之空谈。这两点相辅相成,皆以“实”为根本,体现于其一生行事之中,共同成就了蓝鼎元“经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的美誉。
一 蓝鼎元义理思想中的实学因素
在讨论理学的基本范畴“道”时,蓝鼎元说道:
圣贤之道,原非高远,不外纲常伦纪、日用常行之事。③
一 蔡世远义理思想中的实学因素
根据蔡世远的理解,作为本体的天理即是一种生生之理,其最主要的性质是善。“生生之理,善之长也。己与物之所共也,贵与贱之所同也。”④这种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善恶之善,而是最高的至善,既赋予天地万物生命与本质,又构成了万事万物一体相通的基础。至于气,则是万物身体形质的来源,其在生生之理的主宰下通过不断的运动、变化产生天地万物。由于气直接与人的身体、欲望相关,故其往往与生生之理发生冲突,遮蔽了人的本性,阻隔了万物之间的一体相通。“人之心本有是天地生生之理,牿于气、囿于习而善心之遏绝者多矣。”①因此,学者为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恢复本然的善性。
蔡世远的理气论思想较为简单,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复性说提供理论前提。事实上,蔡世远很少直接讨论理、气、心、性等形上问题,亦不注重抽象的哲学思辨,其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朱子学的认识论、工夫论方面,即所谓的实学与实行。蔡世远认为,朱子学以复性为宗旨,主要有三大要点,即主敬、穷理与力行。“不主敬,则无私之体何以澄之?不穷理,则天下古今当然之则何以考之?不力行,则所谓道听途说而已,何由有以复其性之本然哉?”②在他看来,学者只有将主敬、穷理、力行三者结合起来,“纯主敬之功,穷理、力行,以复其性之本然”③,才能革除学术的虚浮、势利之病,复兴程朱之实学。
关于主敬,蔡世远强调其为彻始彻终工夫,须与立志、躬行相结合,贯穿于知行、动静之中,“谨几以审于将发,慎动以持于已发”④,方能避免“失之宽”或“失之严”之弊。故曰:“程子论学之功,莫要于主敬。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又曰:‘只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然此际加功最难,过于矜持则苦而难久,稍宽缓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坚,躬行又力,用谢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敛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体不至昏怠。以此穷理,心极清明,以此克己,气极勇决,更日加涵养,自然德成而学就,所谓彻始彻终工夫也。”⑤
关于穷理,蔡世远特别重视读书的作用。他说:“由明以求诚之方,惟读书为最要。朱子曰:‘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学者率此以读天下之书,则义理浸灌,致用宏裕。”①他还将读书视作力行的基础和前提,提出:“要其加功用力之始,专在读书。若读一书而近里著己,以身体之,以心契之,虽未知果能力行与否,然方其开卷绎诵时,谁无激励与愧耻之心?激励愧耻之心日进不已,则力行而至于古人之涂径也。”②
关于力行,蔡世远将其视为立志与穷理的完成和实现。若知而不行,则流为空谈,无益身心,故称“力行为贵”③。在他看来,“凡讲学不在辨别异同,贵能自得师,知得一事,便行一事。……徒讲解剖判,皆肤词也”④,又谓:“不加体察躬行之功,徒夸闳博雕镂之用,先儒之所羞称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远,亦大雅之所弗尚也”⑤,可见其对力行的重视。
由于当时学者常有好高骛远、厌弃卑近之病,不问具体切近之实事,专求虚玄高妙之空理,故蔡世远论学亦注重下学上达、由博至约之序,强调笃实与晓事之难,要求学者多于此处用功。他说:“学者患于无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笃实;笃实矣,又苦不能晓事。以陈北溪之贤,受业漳州,与闻至道,越十年,往见朱子于竹林精舍,犹谓其尚少下学之功,勉之曰:‘当学曾子之所谓贯,勿遽求曾子之所谓一;当学颜子之博约,勿遽求颜子之卓尔。’北溪自此精进有加。盖笃实之难也。以司马温公之学识,一代宁有几人?明道犹谓君实不晓事。使明道得大用于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温公,自是不侔。然温公尚未足当晓事之称,由是言之,学之进境,岂有涯哉!”①
二 蔡世远的经世之学
作为一位理学名臣,蔡世远屡次批评当时的学者与士子多不知读书为学的目的,“以记诵、词章为止境,以科名、爵位为可毕一生能事”②。在他看来,读书并不是为了记诵、词章,而是为了学为圣人,使万物各得其所,安顿天下秩序;谋求科名、爵位亦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禄,而是为了施展抱负,学以致用,“可以见一生之品节、经济,不至泯没以终耳”③。因此,蔡世远十分重视经世之学,自言:“自年十二三时,涉猎经史诸书,便讲气节,喜作古文,谈经济”④,而方苞亦称其“夙尚气节,敦行孝弟,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议论慷慨,自为诸生,即以民物为己任。及从清恪公游,吏疵民病,言无不尽,政行众服,而莫知其自公”,即便私下所论,“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类之邪正,无一语及身家浅事者”。⑤正因为如此,故其经世思想能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颇多可观之处。
关于为政之道,蔡世远特别强调恳恻与条理两方面因素。恳恻关乎体,条理关乎用,二者不可偏废。他说:“恳恻者,仁也,即《易》所谓‘元者,善之长’,程子所谓‘满腔皆恻隐之心’,张子所谓‘乾父坤母’‘民胞物与’者是也。有条理者,本平日读书穷理之功,措则正而施则行也。无恳恻则立体不宏,无条理则致用不裕。”⑥蔡世远指出,为政者的恳恻并非出于后天功利的考虑,而是源自先天的仁心,“从本原之地流出”,故能“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尽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职分所当为”①,从而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前提与基础,亦是分辨王道与霸道的根本标准。如管仲治齐,虽亦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义示信,极有条理,但其动机在于追求国家富强,而非出于本心之恳恻,故只是霸道而非王道。
在恳恻的基础上,为了妥善地应对和解决现实治理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蔡世远亦很注重为政之条理。“所谓恳恻者无尽,而条理者无穷。事变繁多,土俗各别,所谓条理者,尤难之又难。”②与传统政治思想所提倡的“有治人,无治法”不同,蔡世远较为重视法的作用,主张廉法结合、以法济廉。因为在他看来,“大臣能廉,仅得其半,非廉无以行法,非法无以佐廉。使一己廉静而属员奸贪,或限于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牵制而不能决去,犹是独善其身,岂称开府之治哉?”③同时,蔡世远还很赞赏薛瑄所说的“立法贵在必行,法立而不行,则法为虚文,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主张通过严格的奉法与执法来树立法令的权威性,以此维护民众的利益。蔡世远特别指出,当时地方上以“蠹役与健讼之徒最为民害。蠹役朘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骄横已极,陵绅士如草芥。……健讼者指无为有,饬毫末之事以为滔天,上官不知,辄为听理,小民身家荡散无余”④。故其主张依法严厉打击蠹役与健讼之徒,“摘其尤者,宁确无滥,宁重无轻,惩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务也”⑤。
关于治术,蔡世远并未简单以权术视之,而是将其建立在身心性命之学的基础上,主张“治术关于学术,经济通于性命”⑥。因此,当谈及大臣所应具备的素质时,蔡世远认为其应兼具五方面的综合素质:“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恺恻之怀,有明通之识,有强毅之概,有儆惧之心。无公清之操,则不免有宠利之疾矣。无恺恻之怀,则不能有纳沟之耻矣。无明通之识,则胶执而鲜通矣。无强毅之概,则虽知其然,发之不勇,守之不固矣。无儆惧之心,则自信太过,祸且随之矣。”①这一概括同时兼顾了官员的德行、能力与性格、心态等各方面要素,颇为全面,值得所有官员对照反思,引为鉴戒。
县令作为国家的基层官员,直接与民众相接触,负责管理地方上的日常事务,具体执行国家的法令政策,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纽带。蔡世远就相当重视县令的作用,称其为“亲民之官”,认为“欲天下之均平,人被尧舜之泽,非亲民之官不可”②。根据蔡世远的理解,县令的工作无非三项要点,即息讼、薄赋与兴教。而要做好这三件事,就必须做到“民以事至县者,胥役不扰,无守候之劳,分其曲直,惩其诬黠,诲谕之,又加详焉,则讼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为案实立限,使自封投柜,主以信。使投毕,躬自称平之,榜列明示,归其有余,使补其不足,如期至,则民自不欺,输将恐后矣。择士民之秀者聚之于学,课文饬行,月三四至,又于暇日适山村里闾,言孝弟农桑之事。其有家门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访其家以荣之,而教道兴矣”③。在此基础上,他又告诫即将出任县令的弟子,须淡泊自守,爱民如子,积极为民兴利除害,“事上贵恭不贵屈,驭民以诚不以术”④,如此方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县令。
对于县令与学政二官的职责特点,蔡世远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今之持论者,皆曰外官惟县令与学使最难供职。世远窃谓此二者为最易。夫县令者,朝行一政则夕及于民,兴政立教无耳目不周之处,无中隔之患,古人所谓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学使无刑名、钱谷之繁,惟以衡文劝学、广励学官、振饬士子为职业,草偃风行,比地方职守者尤易。或又以为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谓掣肘者,多由于自掣,非尽人掣之也。夫布衣则古称先,自强不懈,人犹称其严毅清苦,力行可畏,况居官哉?但气不可胜,事不可激,当谨确完养以合乎中耳。”①在此,蔡世远表面上是在强调县令与学政之官易做,实则蕴含了其对这两种官员的重视与期许,希望他们能够善用手中的权力,勤勉于公事,不受外界的掣肘和私心的干扰,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爆发朱一贵事变,震动全台,声势极大,清政府派遣闽浙总督满保督师入台平乱。蔡世远与满保交好,对于征台一事亦十分关注,曾为此数次致信满保,对征台用兵及后续的治台事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建议多被满保采纳施行,对于台湾的安定、治理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蔡世远看来,此次起事者只是一群草窃小寇、乌合之众,与当年的郑氏政权不可同日而语,故讨平叛乱不足为虑。其最担心的是用兵过程中造成的杀掠之祸。蔡世远强调,台湾乃吾故土,台民为吾同胞,大部分从乱者只不过是为人所裹胁驱使,并非有意反叛朝廷,故希望满保能够“严饬将士,并移檄施、蓝二公,约以入台之日,不妄杀一人”②。后事变果然被迅速平定,对于台湾社会亦未造成太大的破坏。但蔡世远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着眼于台湾的长治久安,进一步提出了“平台匪易,而安台实难”③的观点。在他看来,台湾之所以难治易乱,固然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人口结构等客观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地官员的治理不善。他说:“台湾五方杂处,骄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哄聚,风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传舍之意,隔膜之视,所以致乱之由。”④又说:“夫台湾鲜土著之民,耕凿流落,多闽粤无赖子弟,土广而民杂,至难治也。为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爱之,而因以为利。夫杂而不教,则日至于侈靡荡逸而不自禁;不爱而利之,则下与上无相维系之情。为将校者,所属之兵平居不能训练而又骄之。夫不能训练,则万一有事不能以备御;骄之,则恣睢侵轶于百姓。夫聚数十万无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荡逸,无相维系之情,又视彼不能备御之兵,而有恣睢侵轶之举,欲其帖然无事也难矣。”①为了解决台湾的治理难题,蔡世远主张须对台湾民众“教而爱之”,趁此平乱更革之际,彻底整顿吏治,完善管理,与民休息,推行教化。他向满保建议:“文武之官,必须慎选洁介严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兴教化以美风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内地遗亲之民,不许有司擅给过台执照,恐长其助乱之心。新垦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编粮,恐扰其乐生之计。三县县治,不萃一处,则教养更周。南北宽阔,酌添将领,则控驭愈密。”②显然,蔡世远的这些看法与主张是符合当时台湾的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台湾的安定和发展的。
第四节 蓝鼎元的实学研究
蓝鼎元论学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笃守朱子之学而不稍改,力辟释、道、心学等异端;一是注重实用,留心实际,强调有体有用之学,力戒无用之空谈。这两点相辅相成,皆以“实”为根本,体现于其一生行事之中,共同成就了蓝鼎元“经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的美誉。
一 蓝鼎元义理思想中的实学因素
在讨论理学的基本范畴“道”时,蓝鼎元说道:
圣贤之道,原非高远,不外纲常伦纪、日用常行之事。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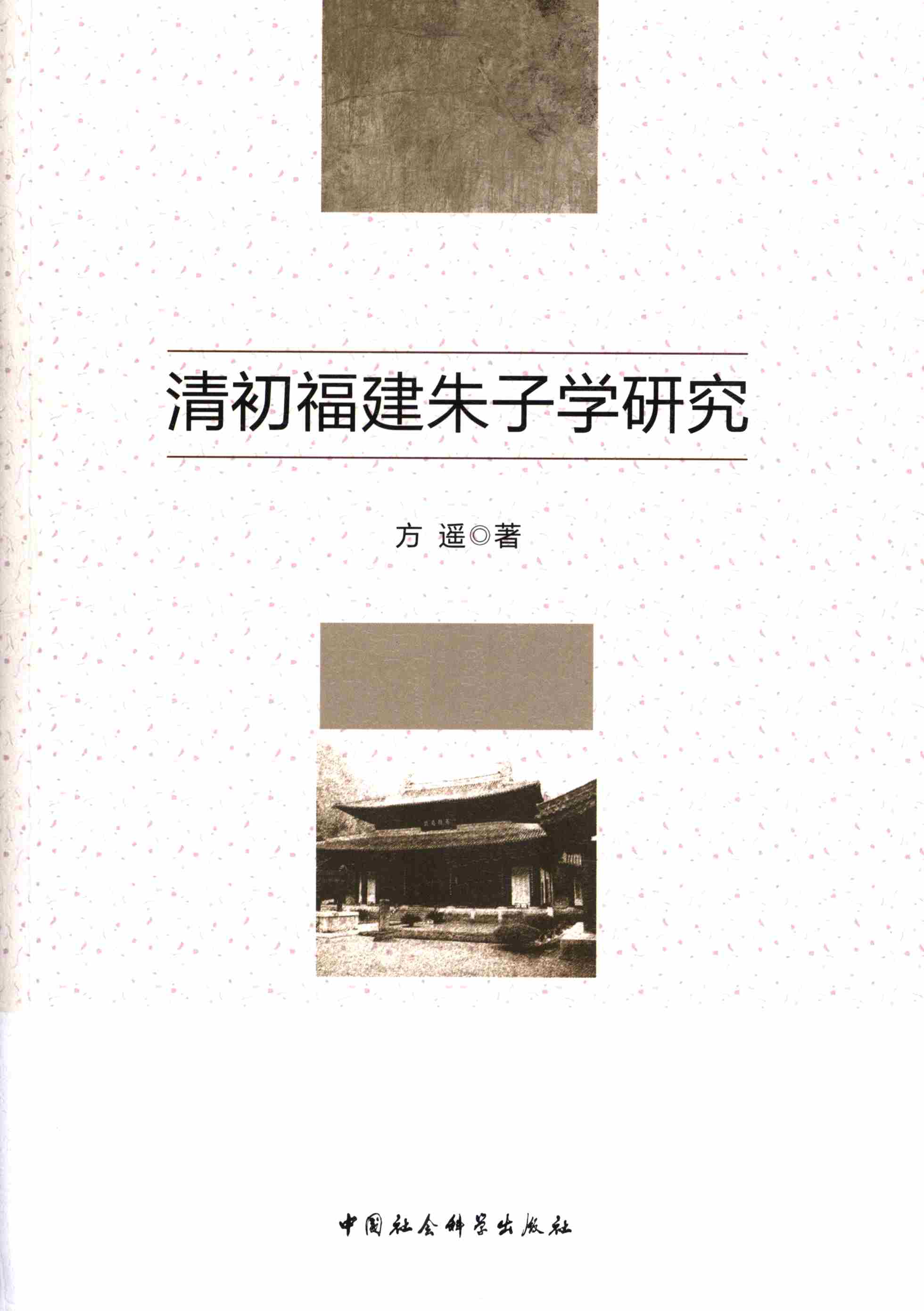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