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光地的六艺、格物之学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410 |
| 颗粒名称: | 三 李光地的六艺、格物之学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8 |
| 页码: | 608-625 |
| 摘要: | 本文主要介绍清代学者李光地对六艺学的重视与研究。六艺学是实学的基本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李光地认为这些学问都是经世致用的重要事务,必须加以关注和学习。他特别强调了礼、乐、书、数的重要性,并反驳了将六艺与心性学分隔开来的观点。李光地在音乐、兵法、历算等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它们的实际应用和教化作用进行了探讨。他还提出了关于调与声、诗与调、现实乐教等问题的看法。李光地的研究与努力推动了清代实学的发展。 |
| 关键词: | 清初 朱子学 格物之学 |
内容
除了六经之学外,六艺之学亦被不少清初学者视作实学的基本形式和重要代表。如颜元即云:“我夫子承周末文胜之际,洞见道之不兴,不在文之不详而在实之不修,奋笔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经书,取足以明道,而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①又谓:“如朱、陆两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学之成法,而身习夫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属而精之。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兵农,某也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则及门皆通儒。……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虚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实得其用,天下必实被其泽,人才既兴,王道次举,异端可靖,太平可期。”②李塨亦言:“先王三物之教,六德六行,其实事只在六艺”③,“六艺为圣贤学习实事,孔子习礼学乐,执射执御,笔削会计,无不精当”④。又言:“人之参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见乎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艺也。……夫德行之实事,皆在六艺。艺失则德行俱失。”⑤潘耒则说:“古之君子不为无用之学。六艺次乎德行,皆实学,足以经世者也。”⑥
而李光地亦相当重视六艺之学,提出:
六经外,六艺皆当留心。文武既分途,射、御暂可不讲,至礼、乐、书、数,实要紧事。⑦
六艺真是要紧事。礼乐不消说,射不可不知,但今之架式,要弯身才好,看古人却云“外体直”。至于御,今已无之,骑马即御也。古时太守领兵,文武未始分,若是一旦朝廷以武事命之,不能骑射,如何使得?大将尚可,偏裨岂不殆哉!至书算,试看岂可阙得。本朝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①
显然,在李光地看来,六艺之学各有实用,皆为经世之要紧事,皆须讲求。特别是礼、乐、书、数,应当成为每个士子必须学习与掌握的基本技能。针对那些轻视六艺,甚至将六艺之学与心性之学割裂、对立,分属于小学与大学的观点,李光地亦进行了批驳:
今人动言,小学只习礼、乐、射、御、书、数,到入大学,便专讲心性。从来无此说。不想扫洒、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节”“文”二字作何解?节是童子不知登降周旋所以然之故,但习其节目;文是童子不知礼、乐、射、御、书、数所以然之理,但诵其文词。到后来成人时,便已熟惯而知其用,日用而益明,精义入神,下学上达,不离乎此。非大学后便不提起六艺之事也。②
根据李光地的理解,六艺之事作为实学的基本内容,贯穿于人的一生,并不以年龄为限。小学时习六艺之节文,大学时明六艺之道理。且知性明理必须建立在不断实行、实践的基础之上,日用而理益明,理明而行益笃,二者不可割裂,并非明理后便不须实践。
以六艺之学为核心,李光地对于音韵、兵法、音乐、天文、历算等各种实用知识与学问皆抱有广泛的兴趣,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培养、影响、带动了一大批清初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从而推动了清初实学的发展。分而言之,在音韵方面,李光地主要受到顾炎武的影响,编撰有《音韵阐微》《榕村韵书》《韵笺》《等韵便览》《等韵辨疑》等著作,其基本观点上文已有述及。
在兵法方面,李光地主要撰有《握奇经注》等。在古代众多阵法中,李光地尤其重视武侯八阵与李卫公五花阵,以其内容有所根底。在他看来,“五花原于乡遂之兵,八阵原于都鄙之兵。乡遂之兵,以十为数,起于五;都鄙之兵,以八为数,起于井田之八家。自五家,以至于万二千五百家,皆以五相叠,故出兵自五人,以至于万二千五百人,亦如之。自八家,以至五百一十二家,皆以八相叠”①。而在《握奇经注》中,李光地简要地解释了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的布阵、变化之法,以及游兵与正兵的配合方法,清晰地阐述了《握奇经》“以正合,以奇胜”的军事思想。关于排兵布阵中正、奇配合的基本方式,李光地总结道:“天、地、风、云者,正也;龙、虎、鸟、蛇者,奇也。正者,连营布阵之法,至于应敌决胜,则变为四奇。奇即正之变,非在正之外也。八者之外,尚有奇兵焉,则谓之握机。言其或前或后,望敌设伏,虽不在八阵之中,而实握其机,故曰握机也。”②但是,正与奇的内容亦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随着战场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以天、地、风、云为正,则龙、虎、鸟、蛇为奇;以天、地为正,则风、云为奇;以龙、虎为正,则鸟、蛇为奇也。以前列之八阵为正,则后队之游军为奇也。揔而言之,则凡正阵、游军皆为正,而时静时动、变变化化、不可测度皆为奇也。”③相较于八阵之中的正与奇,李光地更为重视正兵与奇兵即游军的相互配合。关于正兵与游军各自的作用与特点,李光地总结道:“正兵者,利戈矛弓戟之用,习金鼓旌麾之节,闲步伐进退之方,识高下向背之地。其教养之素,至于如手足之相捍卫;其节制之重,至于如山丘之不可顿撼。如是,则正兵之用尽矣。若夫侦间以得敌情,窥望以审敌势,未遇而致师,既阵而蹑敌,方合而出其傍,绕其后,我退而设之伏,示之疑,变强弱之形,移彼己之利,若此者,非游军不足以备其用,济其机也。”①显然,李光地将游军视作战场上出奇制胜的关键因素。故曰:“养游军之禄可数倍于养兵,驭游军之权或更甚于驭将,此握奇之号所以或专属之游兵,以为设奇制胜专在此也。”②
在音乐方面,李光地撰有《古乐经传》《大司乐释义》《乐书纂》等著作。对于六经中唯独《乐经》无文的原因,李光地解释道:“经具于《春官》之属,记具于戴氏之编,二者皆传于窦公。窦公者,与子夏同时,同事魏文侯,而申礼乐之事。其传止于此,则以其官器神明大略备也。若声气微妙,则不可写,故曰乐崩。”③因此,李光地以《周礼·春官》中的《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乐》之经,以《礼记·乐记》为《乐》之传,又杂取《周易》《诗经》《尚书》、三礼、《孟子》《左传》《国语》《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汉书》《后汉书》《通典》《文献通考》等书论乐之文附之,较为细致地考察、辨正、阐释了古代传统音乐的乐仪、乐器、乐律、乐理、乐教与乐用。
譬如,关于乐律,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冬至郊天之乐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夏至祭地之乐以“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祭祀宗庙之乐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李光地认为此天、地、人三乐乃上文祭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六乐合二为一而成,并且指出先儒之所以没有发现这一点,正是由于未能分别“声”与“调”的不同所致。他说:“调与声不同。……且以黄钟之五调论,则所谓黄钟宫调者,用黄钟所生之七律,而以黄钟起调,黄钟毕曲也。所谓黄钟商调、黄钟角调、黄钟徵调、黄钟羽调者,则亦用黄钟所生之七律,而或以太簇,或以姑洗,或以林钟、南吕起调毕曲也。所以然者,黄钟以太簇为商,以姑洗为角,以林钟为徵,以南吕为羽,如此节用黄钟为角调,则必以其所生之角声起调毕曲,自然之理也。故如黄钟之为角声也,则必曰夷则角,而不曰黄钟角;如太簇之为徵声也,则必曰林钟徵,而不曰太簇徵;如姑洗之为羽声也。则必曰林钟羽,而不曰姑洗羽。汉魏以来,乐部未之有改,然则黄钟为角之为角调而用姑洗,太簇为徵之为徵调而用南吕,姑洗为羽之为羽调而用大吕,无疑也。”①
据此,李光地认为郊天之乐的“圜钟为宫”与祭祀宗庙之乐的“黄钟为宫”存在错互,即前者当作“黄钟为宫”,而后者当作“圜钟为宫”,且以黄钟一律宫、角两用并不构成重复。李光地引用祀天神、四望之律解释郊天之乐道:“黄钟为宫,则黄钟宫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即以黄钟。黄钟为角,则黄钟角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则以姑洗。太簇为徵,则太簇徵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则以南吕。姑洗为羽,则姑洗羽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则以大吕。此四律者,皆前所祀天神、四望之乐,故此大祀则合而用之,至下二乐莫不皆然。”②他又引班固《汉书·律历志》以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太簇为人统之说,认为“黄钟当为天宫,林钟当为地宫,明矣”,故郊天当以黄钟为宫,而“太簇虽属人统,然前文既与应钟合而为祭地之乐,则施之宗庙之宫义有未允。而夹钟者,前文所用以享于先祖者也。盖天气始于子,地气始于午,人事始于卯者,阴阳昼夜之正也。地退一位而始于未,则避南方之正阳也。人进一位而始于寅,则重民事之蚤作也。然则宗庙之祭以圜钟为宫,既合享祖之文,又著人事之始,比于援引星辰,舍经证纬,不亦善乎?”③此外,李光地还提出:“祭祀之大者废商,故调止于四。而地乐中有太簇,本黄钟之商声,人乐中有无射,乃西方之穷律,缘去商调之义,故此二律有应为起调毕曲者则并去之。盖蕤宾与太簇同类,南吕与无射同方,故其乐可以相代也。”④
李光地认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不仅与句字相关,而且与韵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说:“凡人声之发于喉者,宫也;其入于鼻者,商也;其转于舌者,角也;其抵于齿者,徵也;其收于唇者,羽也。喉之声,深以厚;鼻之声,铿以轰;舌之声,流以畅;齿之声,细以详;唇之声,闭以藏。人之声必自喉始,交于舌齿之间,上于鼻而下于唇,至唇之闭,则又息于喉而复生矣。是故古之知音者必辨韵部,未有韵部之不审,句字之不清,而可以言歌者也。”①又说:“作诗用韵脚,若是喜庆事,用宫音,便洪亮;发扬感激事,用商音;述平常事,用角音;可骇愕事,用徴音;悲恻事,用羽音。”②但李光地同时指出,五音的形成较为复杂,韵部仅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单纯依靠唇、齿、舌、喉之声确定宫、商、角、徵、羽。“因其调之抑扬高下而叶之,因其言之缓急轻重而命之,因其情之刚柔吐茹而形之,夫然后口与心相应也,响与籁相追也。故韵部者,音乐之助而犹非音乐之本也。”③
李光地对于音乐的思想内涵与教化作用亦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五音有声有调,而调始于人心,反映人的性情之德,故较之声更为基本。“宫调深厚,于人为信之德,而其发则和也。角调明畅,于人为仁之德,而其发则喜也。商调清厉,于人为义之德,而其发则威也。徵调繁喧,于人为礼之德,而其发则乐也。羽调丛聚,于人为智之德,而其发则思也。是数者生于心,故形于言,言之有发敛、轻重、长短、疾徐,故又寓于歌。《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者此也。圣人因是制为五者之调以仿之。”④因此,音乐便具备了教化人心、陶冶性情的功能。“闻宫音使人和厚而忠诚,闻角音使人欢喜而慈爱,闻商音使人奋发而好义,闻徵音使人乐业而兴功,闻羽音使人节约而虑远。”⑤五者之调形成后,圣人又制六律以为其发敛、轻重、长短、疾徐之节,则调中之五音具焉。从五音产生的这一过程来看,“仁义礼智信者五音之本也。喜怒哀乐者五音之动也。调者,五音之体制,而声者,五音之句字也”①。因此,音乐演奏必须先定调,而后以声从之。若先设声,而后以调从之,则将导致性情之失,背离了音乐的本质。
至于诗、调、声三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李光地认为应以诗为根本,调次之,声最后。因为诗与性情之德的联系最为密切,所谓“不知调者,不可与言声;不知诗者,不可与言调;不知性情之德者,不可与言诗。可与言诗,而乐思过半矣”②。据此,李光地批评后代的雅乐形式大于内容,“声有高下而无疾徐,纵其应律,亦所谓知声而不知调者也,知调而不知诗者也”,因而主张学习与创作音乐“必先教诗,教诗者,必先以六德为之本,使其性情之发无有不得其平而不由其诚者,则二者之患亡矣。然后以六律为之音,盖亦简易而不难也”。③
李光地进一步指出,音乐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人民,故推行乐教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变通,使今人喜闻乐见,而不能将今乐与古乐简单地对立起来,一味追求复古。在他看来,三代以下礼乐不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儒者的礼乐思想迂大繁难、流于空谈而不切实际、无关日用。“礼则必其周公之制,乐则必其伶伦之律,微论其说无一是之归,纵使得之,亦止于郊庙朝廷之事,而所谓移风易俗,无有议及之者,又岂圣人礼云乐云之意哉?”④“若只郊庙中作乐,就是《云门》《咸池》《韶濩》《大武》,亦只天地鬼神闻之,如何天下风俗就会移易?自然是人人见闻,才能移风易俗。”⑤加之社会风俗变迁,民众习尚日非,即便勉强推行古乐,亦不过是“强其所不乐,举其所不行,则莫之从而不能久,非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者也”①。因此,李光地极称孟子所说的“今之乐,由古之乐”,主张从实用出发,借鉴古乐的精神与形式来改良、整理今日之戏曲,“去其淫辞新声,及其节目之荒诞无实者,而一均之和音,被以雅曲,实之以忠孝廉贞节义之事,亦庶几乎可以语,可以道古者,未必非风俗之一助也”②。同时,还应改变俗乐的冗长繁衍,戏以四出为则,并使歌、舞分离,做到“舞以动其容,虽貌肖而口不言也;歌以咏其事,虽赞叹之而亦非其自言也。听其歌,观其容,而其人可知。……则至善矣”③。
在天文、历法方面,李光地主要受到梅文鼎与康熙帝的影响,编撰有《历象要义》《历象本要》④《星历考原》等著作。在某些学者眼中,天文、历法乃畴人、星官的专门职守,非儒者之所当务,故学者不必于此用心。而李光地则指出,天文、历法之学不仅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直接指导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适于日用,所需尤大”⑤,而且其关于宇宙、天地的生成、演化、运动等诸问题的研究亦与儒学义理直接关联,构成了儒家学说的重要知识背景与思想基础。所以他说:
圣人作历,为顺天以授时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时,而寒暑四时运于不可见,于是而纪诸日月星辰之行。是故察日之出没,而昼夜明焉;察月之盈虚,而朔晦明焉;察日之发敛,而冬夏明焉。《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寒暑昼夜者,天道之纲,民用之本。⑥
又说:
乾坤,父母也,继志述事者,不离乎动静、居息、色笑之间,故《书》始历象,《诗》咏时物,《礼》分方设官,《春秋》以时纪事,《易》观于阴阳而立卦,合乎岁闰以生蓍,其所谓秩序、命讨、好恶、美刺、治教、兵刑、朝会、搂伐,建侯迁国之大,涉川畜牝之细,根而本之,则始于太乙,而殽于阴阳。日星以为纪,月以为量,四时以为柄,鬼神以为徒,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①
在李光地看来,天地不仅是万事万理的根本,而且是万事万理的起点,构成了实学的真正基础。故“孔子从不曾说到天地之先。……都是从天地说起。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无稽之言,无复证据者,圣人便不言”②。又谓:“圣人万古之师,一切幽渺荒唐之说,删去净尽。说理气只从天地说起,又只说现在的,至天地以前,天地之终,都不说。删《书》断自唐虞,以前就有文字,孔子都不存。不似他家从混沌之始,悬空揣度,以启后来编通鉴者荒唐幽怪之谬。”③因此,李光地的天文、历法研究既注重实际、实用,不为幽渺荒唐之说,又时常将其与理学思想进行结合,互相印证,故而往往给人留下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
譬如,关于宇宙的结构,李光地其实已经接受了西方天文学的“地圆说”,提出:“地至圆,无有上下,周遭人皆戴天履地,无有偏侧倒置”④,“天地如鸡卵,古人虽有其说而未竟其论。唐之淳风、一行,宋之尧夫,元之郭太史、许鲁斋,明之刘伯温,皆聪明绝世,而皆不知天地之俱为圆体。自西人利玛窦辈入中国,言地原无上下,无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中国人争笑之,岂知自彼国至中国,几于绕地一周,此事乃彼所目见,并非浪词”①。但在同时,李光地亦未彻底否定传统的“天圆地方”说,而是对其加以转化,以动静之理进行解释。如南怀仁曾深诋天圆地方之说,李光地即回应道:“天地无分于方圆,无分于动静乎?盖动者,其机必圆;静者,其本必方。如是则天虽不圆,不害于圆;地虽不方,不害于方也。”②此后,他又多次提及“‘天圆地方’之说,盖以动静体性言之。实则形气浑沦相周,古人卵中黄之喻是已”③,“天圆地方者,言其动静之性耳。实则地亦圆体,如卵里黄,上下周围与天度相应”④。显然,李光地并非当真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是借用《大戴礼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道曰方圆耳,非形也”⑤的思想,以天道动、地道静来解释“天圆地方”说。
类似地,李光地既然承认地圆说,那么自然知道中国并非位于大地的中心,甚至根本不存在某一特定的“地中”。譬如他说:“夫至顺极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浑沦旁薄者,地之本体然也。其南北两端,以去日远近为寒暑之差;东西以见日早晚为昼夜之度。东之夜乃西之昼,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则东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极为中,或以赤道为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⑥但是,当南怀仁以赤道为地中,批评“中国”之名时,李光地又反驳道:“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⑦关于地中的含义与判断标准,李光地还提出:“西法称赤道之下,二分午表无景,是冬夏数均也。昔人有至外国者,熟一羊头而夜已曙,是昼数常赢也。今法南方四时昼刻每多于北,又况乎其九州之外者乎?昼夜不均,非所语中,然一岁之内,绝无短永,阴阳消息,其序靡显,揆之于理,亦未为中也。如此,则惟中国之地,晷刻赢缩,与四时进退,二至相除,毫无余欠,而洛又其中之中,谓之中土,理宜不诬。以是知经所言天地四时之所交合,阴阳风雨之所和会,信乎其为至理,而非虚说也”①,又谓:“中国不可言地之中,惟可言得天地之中气。当黄道下处,日直到顶上,其热太剧。当赤道下处,一岁两春夏秋冬,立春、春分为春夏,立夏、夏至为秋冬,立秋、秋分又为春夏,立冬、冬至又为秋冬。惟中国寒暑昼夜适均而不过,所以形骸端整,文物盛备。”②如此,李光地就将原先表示地理位置的“中”转化为合理、中理的意思,并将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昼夜寒暑变化规律视为理的标准,即所谓“正理”,从而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提供合理性依据。
由上可知,李光地并未在客观事实的层面上否定地圆说,反而一再对其予以肯定和宣传,但他同时又努力从义理的层面上对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和“中国”说进行解释和辩护,以此维护这些作为传统文化思想、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知识背景与思想前提的基础性观念,使其能够继续为上层建筑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持,尽量缓解来自西方知识与思想的冲击。有趣的是,当初利玛窦在向中国介绍和引进地圆说时,为了淡化与中国传统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以减轻西方知识、思想传播的阻力,亦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如利玛窦在解释《坤舆万国全图》时就曾表示:“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德静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③而他在绘制世界地图时,亦有意将中国安排在靠近中心的位置,以适应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若从这一角度观察,则李光地对于传统观念的维护及其对中西学说的调和或许也带有某种辅助西学传播的意味,尽管这并非其主要目的。
此外,李光地还结合西方古典天文学知识与《周髀算经》中的传统天文理论,以太阳的运动来解释四季变化、极昼、极夜等现象,以及寒暑五带的形成原因。他说:“《周髀》言:‘北极之下,有朝生而暮获者’,人指为谩。赵氏注之云:‘以北极之下,有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者故也。’此语忒煞聪明。盖北极下,日在天腰,其在上半盘绕时全是昼,及旋到下半,便全是夜。此理甚确。”①又说:“其地气寒暑,则以去日远近为差。赤道之下,正与日对,其地最热,其景则四时常均,无冬夏短永。两极之下,取日最远,其地最寒,其景则短者极短,长者极长。正当两极之处,常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惟二极与赤道相去之间,当日南北轨之外,起二十三度,至四十度许,其地不寒不热,温和可居,其景则与冬夏进退,长短之极,皆无过十之七。”②李光地还据此批评《绎史》“天地之精华为四时,有四时而后有五行。水之精为月,火之精为日”的观点“大可笑”,指出:“四时乃因日而有,日傍近气温为春,在头上大热为夏,稍远便凉为秋,大远便冷为冬。据《周髀经》及西洋人说,则半年寒、半年暑者有之,一年有两春夏秋冬者有之。与中国对过的地方,中国的南极,是他的北极,中国的北极,是他的南极。中国寒,他却暑,中国暑,他却寒。”③
在算学方面,李光地主要亦受到梅文鼎与康熙帝的影响。据李光地自述,其早年曾问算学于潘耒,可惜教学不甚得法,故所得不多。直到后来与梅文鼎结交,其算学水平才得到较大提升。④而康熙帝亦时常与李光地探讨算学问题,还曾亲赐对数表与《几何原本》《算法原本》等算学书籍给李光地,对其算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引导与促进作用。
李光地治算学同样注重中西、新旧之法的融合与会通。在他看来,古代六艺之学中的所谓“九数”皆与实际、实用相关,皆为经世之实学,故能极数之用。“然古人精密之法不传,而后世所用,悉皆疏率。故所谓径一围三、径五斜七云者,不过约略之算,而其方圆相求,三分进益,虚加实退,皆非真数也。”①相比之下,当时传入的西洋新法却十分精密,“于方圆、围径、幂积之算不爽纤毫”②,故应积极学习、借鉴西洋新法以补本国旧法之未备。关于西洋算学的学习与运用,李光地提出:“欲通新法者,必于几何求其原,以三角定其度,较之以八线,算之以三率,则大而测量天地,小而度物计数,无所求而不得矣。”③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李光地对几何学与《几何原本》特别重视,将点、线、面、体视为算学的基础,即“万数之宗”。他说:“点引而成线,线联而成面,面积而成体。自此而物之多寡、长短、方圆、广狭、大小、厚薄、轻重,悉无遁形;自此而物之比例、参求、变化、附会,悉无遁理。”④他又将几何原理与儒学义理结合起来,提出:“凡数起于点,当初止有一点,引而长之则为线,将此线四围而周方之则为面,又复叠之教高则成体。‘直方大’,即是此意。直即线,方即面,大即体。惟直而后可方,惟方而后能大,故《象》曰‘直以方也’。直了才能方,既直方自然大,故曰‘敬义立而德不孤’”⑤,试图以客观、具体、精密的西洋算学来解释、论证道德性的儒学义理。
此外,李光地还主张“算法重三角形”⑥,故对我国古代的勾股法与西洋的三角、八线、三率法之间的异同做了比较。他说:“古所谓勾股者,举中之法耳。今三角法,即勾股也,然而有直角,有锐角,有钝角。又其算也,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而角度对之,故量角之度以为起数之根。然则勾股有直而无锐钝,其数起于边而不起于角,岂非有待于新法以补其所未备者乎?其用之,则以八线之表。八线者,亦古人所谓勾股弦也。今则变勾而曰矢,且有正矢焉,有余矢焉;变股而曰弦,且有正弦焉,有余弦焉;其在圆外之股则曰切,且有正切焉,有余切焉;变弦而曰割,且有正割焉,有余割焉。八线相求,互为正余,故举一则可以反三,穷三则可以知一。举一反三,穷三知一者,则今之三率法是也。三率之法,即古者异乘同除之法,而其立法加妙,用之加广,则非古人之所及也。”①显然,李光地承认西洋数学要比我国的传统算学在方法上更为完备、精妙与准确。
综上可知,作为一位重视实学的理学家,李光地对于当时大量传入的西学事实上抱持着一种较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李光地对于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与实用器物持较为开放与开明的接受态度,特别是对其研究方法的完备、精密,及其对自然事物的解释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十分肯定和推崇,所以他屡次称赞西洋历法“甚精密……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②,“西士天学可称烂熟,简平仪取适用,而天之体不外乎是。前儒《浑天象七政图》,却失本来面目”③,“自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说多矣,至于今日西历之家,其说弥详”④,又表彰西洋数学“立法加妙,用之加广,则非古人之所及也”⑤,还为西洋的机械、仪器等正名与辩护,提出:“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觿、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①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地有时还会借助西方的科学知识来解释、论证儒学的观点与义理,如以几何学原理解释《周易》所说的“直以方”和“敬义立而德不孤”,又谓:“看天似无心,然从事事物物体贴来,觉得处处都似算计过一番。如黄道、赤道不同极,常疑何不同极,省得步算多少周折。细想,若同一极,必有百年只见半日、半月之处,惟略一差异,便隐见盈亏都均齐矣”②,可见其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准确性的信任和重视。李光地不仅自身积极学习、研究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运用其知识编撰相关著作,如阮元即称李光地“所著书皆欧罗巴之学。其言均轮次轮之理,黄赤同升、日食三差诸解,旁引曲喻,推阐无遗,并图五纬视行之轨迹,尤多前人所未发”③,而且延揽、培养、提携了一大批天文、历算人才,资助梅文鼎等人刊刻出版最新的天文、历算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天文、历算之学的繁荣兴盛,以及相关西学知识的传播扩散。
但在另一方面,李光地对于西学的传播、流行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可能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与威胁亦表示深刻的忧虑。为此,他对西方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思想学说持批评与排斥的态度,认为“西人学甚荒唐”④,而对西方的科技知识则主要将其限制在实用的范围之内,尽量避免其与传统思想发生直接冲突,同时更多地采取所谓“古已有之”的应对策略,通过发掘自身固有的学术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可与之对应的内容与材料,以此证明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与合理性,起码在与西学的比较中并不显得落后。譬如,李光地受梅文鼎的影响,特别重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古代天文、历算典籍,大力发掘、阐释其中埋没已久的学术内涵,提出:
天圆而地亦圆,四方上下皆人物所居,各以戴天为上,履地为下也,其说与《周髀》合。且浑天之术本谓如卵裹黄,乌有卵圆而黄不圆者乎?……天有九重,最近者月天也,稍远则日天与金、水天,又远则火星天,又远则木星天,又远则土星天,最远则恒星天,其外则宗动天也。《楚辞·天问》曰:“天有九重,孰营度之?”然则九重之说旧矣。……惟宗动天行有常度,不独日月五星右行,恒星天亦右行也。其说则历代岁差之说是也。①
新历以地为圆体,南北东西,随处转移,故南北则望极有高下,东西则见日有早暮。望极有高下,而节气之寒暑因之矣;见日有早暮,而节气之先后因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其变,其说与《周髀》合。②
天地如鸡卵,古人虽有其说而未竟其论。……自西人利玛窦辈入中国,言地原无上下,无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中国人争笑之,岂知自彼国至中国,几于绕地一周,此事乃彼所目见,并非浪词。至梅定九出,始发明《周髀经》,以为原如此说,何必西学。③
夫至顺极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浑沦旁薄者,地之本体然也。其南北两端,以去日远近为寒暑之差;东西以见日早晚为昼夜之度。东之夜乃西之昼,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则东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极为中,或以赤道为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此理《周髀》言之至悉,而汉氏以下莫有知者。近新历之家,侈为独得,历诋前说,几数万言。惜乎无以《髀》盖之术告之者。④这些带有浓厚附会色彩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有些自大和可笑,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士人内心的紧张,在客观上有助于那些刚刚接触西学的士人以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情去理解和接受西方的新知识与新思想,未必一无是处。
关于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差异,李光地还提出过这样一种说法:
西人历算,比中国自觉细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如古人说日变修德,月变修刑,西人便说日月交食,五星凌犯,乃运行定数,无关灾异。不知天于人君,犹父母也,父母或有病,饮食不进,岂不是风寒燥湿所感,自然有的。但为子孙者,自应忧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反于身,或是己有不是处,触怒致然,否则亦是我有调理不周而致然。因为彷徨求医,断无有说疾病人所时有,不须管他之理。无论天子,即督抚于一省,知府于一郡,知县于一邑,皆有社稷人民之责,皆当修省。即士庶虽至卑贱,似不足以召天变,然据理亦当修省。如父母怒别个儿子时,凡为儿子者俱当畏惧,父母断不因其畏惧,而谓我本怒他,于尔无与,而反增其怒者。通天地人之谓儒,扬雄谓:“知天而不知人则技。”西人此等说话,直是阴助人无忌惮,天变不足畏之说。①
对于李光地的这一说法,不少学者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其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以愚昧落后的天人感应和星占术数迷信观念来诋斥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反映了其对西学的浅薄和无知。这一批评虽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起码有简单化的嫌疑。其实,若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李光地在这里虽然借用了某种天人感应的表达形式,但其目的并非为了宣扬天人感应学说,也不能因此认定李光地相信自然现象是由人事所引起,因为这明显不符合李光地的天文学思想。而他之所以要这么说,主要是希望借此提醒人君与各级官员须对天地自然,特别是天地自然背后的天理保持敬畏之心,时时因外部世界的改变而反省自己的行为,进而修明政治,改过迁善。所以李光地以父母子女比喻天人关系,认为虽然父母因风寒燥湿所感而生病是自然有的,但作为子女仍须首先自我反省,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然后为父母求医治病,“断无有说疾病人所时有,不须管他之理”。更进一步,在李光地看来,一门学问必须贯通天人,能够从具体的事物之理提升到普遍之理,并且对从天道到人事的所有问题都给出连贯、统一的解释,才能称得上最好的学问。所以他强调“通天地人之谓儒”,“知天而不知人则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的天文、历算之学恰好可以为这种“天人相通之理”提供相关的知识背景与思想基础,进而满足人们关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知识与价值的需要,而注重客观、专门的西方天文、历算之学显然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光地认为中学优于西学,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纵然精密,但亦无法彻底取代中国的传统学问。
而李光地亦相当重视六艺之学,提出:
六经外,六艺皆当留心。文武既分途,射、御暂可不讲,至礼、乐、书、数,实要紧事。⑦
六艺真是要紧事。礼乐不消说,射不可不知,但今之架式,要弯身才好,看古人却云“外体直”。至于御,今已无之,骑马即御也。古时太守领兵,文武未始分,若是一旦朝廷以武事命之,不能骑射,如何使得?大将尚可,偏裨岂不殆哉!至书算,试看岂可阙得。本朝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①
显然,在李光地看来,六艺之学各有实用,皆为经世之要紧事,皆须讲求。特别是礼、乐、书、数,应当成为每个士子必须学习与掌握的基本技能。针对那些轻视六艺,甚至将六艺之学与心性之学割裂、对立,分属于小学与大学的观点,李光地亦进行了批驳:
今人动言,小学只习礼、乐、射、御、书、数,到入大学,便专讲心性。从来无此说。不想扫洒、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节”“文”二字作何解?节是童子不知登降周旋所以然之故,但习其节目;文是童子不知礼、乐、射、御、书、数所以然之理,但诵其文词。到后来成人时,便已熟惯而知其用,日用而益明,精义入神,下学上达,不离乎此。非大学后便不提起六艺之事也。②
根据李光地的理解,六艺之事作为实学的基本内容,贯穿于人的一生,并不以年龄为限。小学时习六艺之节文,大学时明六艺之道理。且知性明理必须建立在不断实行、实践的基础之上,日用而理益明,理明而行益笃,二者不可割裂,并非明理后便不须实践。
以六艺之学为核心,李光地对于音韵、兵法、音乐、天文、历算等各种实用知识与学问皆抱有广泛的兴趣,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培养、影响、带动了一大批清初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从而推动了清初实学的发展。分而言之,在音韵方面,李光地主要受到顾炎武的影响,编撰有《音韵阐微》《榕村韵书》《韵笺》《等韵便览》《等韵辨疑》等著作,其基本观点上文已有述及。
在兵法方面,李光地主要撰有《握奇经注》等。在古代众多阵法中,李光地尤其重视武侯八阵与李卫公五花阵,以其内容有所根底。在他看来,“五花原于乡遂之兵,八阵原于都鄙之兵。乡遂之兵,以十为数,起于五;都鄙之兵,以八为数,起于井田之八家。自五家,以至于万二千五百家,皆以五相叠,故出兵自五人,以至于万二千五百人,亦如之。自八家,以至五百一十二家,皆以八相叠”①。而在《握奇经注》中,李光地简要地解释了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的布阵、变化之法,以及游兵与正兵的配合方法,清晰地阐述了《握奇经》“以正合,以奇胜”的军事思想。关于排兵布阵中正、奇配合的基本方式,李光地总结道:“天、地、风、云者,正也;龙、虎、鸟、蛇者,奇也。正者,连营布阵之法,至于应敌决胜,则变为四奇。奇即正之变,非在正之外也。八者之外,尚有奇兵焉,则谓之握机。言其或前或后,望敌设伏,虽不在八阵之中,而实握其机,故曰握机也。”②但是,正与奇的内容亦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随着战场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以天、地、风、云为正,则龙、虎、鸟、蛇为奇;以天、地为正,则风、云为奇;以龙、虎为正,则鸟、蛇为奇也。以前列之八阵为正,则后队之游军为奇也。揔而言之,则凡正阵、游军皆为正,而时静时动、变变化化、不可测度皆为奇也。”③相较于八阵之中的正与奇,李光地更为重视正兵与奇兵即游军的相互配合。关于正兵与游军各自的作用与特点,李光地总结道:“正兵者,利戈矛弓戟之用,习金鼓旌麾之节,闲步伐进退之方,识高下向背之地。其教养之素,至于如手足之相捍卫;其节制之重,至于如山丘之不可顿撼。如是,则正兵之用尽矣。若夫侦间以得敌情,窥望以审敌势,未遇而致师,既阵而蹑敌,方合而出其傍,绕其后,我退而设之伏,示之疑,变强弱之形,移彼己之利,若此者,非游军不足以备其用,济其机也。”①显然,李光地将游军视作战场上出奇制胜的关键因素。故曰:“养游军之禄可数倍于养兵,驭游军之权或更甚于驭将,此握奇之号所以或专属之游兵,以为设奇制胜专在此也。”②
在音乐方面,李光地撰有《古乐经传》《大司乐释义》《乐书纂》等著作。对于六经中唯独《乐经》无文的原因,李光地解释道:“经具于《春官》之属,记具于戴氏之编,二者皆传于窦公。窦公者,与子夏同时,同事魏文侯,而申礼乐之事。其传止于此,则以其官器神明大略备也。若声气微妙,则不可写,故曰乐崩。”③因此,李光地以《周礼·春官》中的《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乐》之经,以《礼记·乐记》为《乐》之传,又杂取《周易》《诗经》《尚书》、三礼、《孟子》《左传》《国语》《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汉书》《后汉书》《通典》《文献通考》等书论乐之文附之,较为细致地考察、辨正、阐释了古代传统音乐的乐仪、乐器、乐律、乐理、乐教与乐用。
譬如,关于乐律,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冬至郊天之乐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夏至祭地之乐以“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祭祀宗庙之乐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李光地认为此天、地、人三乐乃上文祭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六乐合二为一而成,并且指出先儒之所以没有发现这一点,正是由于未能分别“声”与“调”的不同所致。他说:“调与声不同。……且以黄钟之五调论,则所谓黄钟宫调者,用黄钟所生之七律,而以黄钟起调,黄钟毕曲也。所谓黄钟商调、黄钟角调、黄钟徵调、黄钟羽调者,则亦用黄钟所生之七律,而或以太簇,或以姑洗,或以林钟、南吕起调毕曲也。所以然者,黄钟以太簇为商,以姑洗为角,以林钟为徵,以南吕为羽,如此节用黄钟为角调,则必以其所生之角声起调毕曲,自然之理也。故如黄钟之为角声也,则必曰夷则角,而不曰黄钟角;如太簇之为徵声也,则必曰林钟徵,而不曰太簇徵;如姑洗之为羽声也。则必曰林钟羽,而不曰姑洗羽。汉魏以来,乐部未之有改,然则黄钟为角之为角调而用姑洗,太簇为徵之为徵调而用南吕,姑洗为羽之为羽调而用大吕,无疑也。”①
据此,李光地认为郊天之乐的“圜钟为宫”与祭祀宗庙之乐的“黄钟为宫”存在错互,即前者当作“黄钟为宫”,而后者当作“圜钟为宫”,且以黄钟一律宫、角两用并不构成重复。李光地引用祀天神、四望之律解释郊天之乐道:“黄钟为宫,则黄钟宫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即以黄钟。黄钟为角,则黄钟角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则以姑洗。太簇为徵,则太簇徵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则以南吕。姑洗为羽,则姑洗羽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则以大吕。此四律者,皆前所祀天神、四望之乐,故此大祀则合而用之,至下二乐莫不皆然。”②他又引班固《汉书·律历志》以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太簇为人统之说,认为“黄钟当为天宫,林钟当为地宫,明矣”,故郊天当以黄钟为宫,而“太簇虽属人统,然前文既与应钟合而为祭地之乐,则施之宗庙之宫义有未允。而夹钟者,前文所用以享于先祖者也。盖天气始于子,地气始于午,人事始于卯者,阴阳昼夜之正也。地退一位而始于未,则避南方之正阳也。人进一位而始于寅,则重民事之蚤作也。然则宗庙之祭以圜钟为宫,既合享祖之文,又著人事之始,比于援引星辰,舍经证纬,不亦善乎?”③此外,李光地还提出:“祭祀之大者废商,故调止于四。而地乐中有太簇,本黄钟之商声,人乐中有无射,乃西方之穷律,缘去商调之义,故此二律有应为起调毕曲者则并去之。盖蕤宾与太簇同类,南吕与无射同方,故其乐可以相代也。”④
李光地认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不仅与句字相关,而且与韵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说:“凡人声之发于喉者,宫也;其入于鼻者,商也;其转于舌者,角也;其抵于齿者,徵也;其收于唇者,羽也。喉之声,深以厚;鼻之声,铿以轰;舌之声,流以畅;齿之声,细以详;唇之声,闭以藏。人之声必自喉始,交于舌齿之间,上于鼻而下于唇,至唇之闭,则又息于喉而复生矣。是故古之知音者必辨韵部,未有韵部之不审,句字之不清,而可以言歌者也。”①又说:“作诗用韵脚,若是喜庆事,用宫音,便洪亮;发扬感激事,用商音;述平常事,用角音;可骇愕事,用徴音;悲恻事,用羽音。”②但李光地同时指出,五音的形成较为复杂,韵部仅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单纯依靠唇、齿、舌、喉之声确定宫、商、角、徵、羽。“因其调之抑扬高下而叶之,因其言之缓急轻重而命之,因其情之刚柔吐茹而形之,夫然后口与心相应也,响与籁相追也。故韵部者,音乐之助而犹非音乐之本也。”③
李光地对于音乐的思想内涵与教化作用亦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五音有声有调,而调始于人心,反映人的性情之德,故较之声更为基本。“宫调深厚,于人为信之德,而其发则和也。角调明畅,于人为仁之德,而其发则喜也。商调清厉,于人为义之德,而其发则威也。徵调繁喧,于人为礼之德,而其发则乐也。羽调丛聚,于人为智之德,而其发则思也。是数者生于心,故形于言,言之有发敛、轻重、长短、疾徐,故又寓于歌。《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者此也。圣人因是制为五者之调以仿之。”④因此,音乐便具备了教化人心、陶冶性情的功能。“闻宫音使人和厚而忠诚,闻角音使人欢喜而慈爱,闻商音使人奋发而好义,闻徵音使人乐业而兴功,闻羽音使人节约而虑远。”⑤五者之调形成后,圣人又制六律以为其发敛、轻重、长短、疾徐之节,则调中之五音具焉。从五音产生的这一过程来看,“仁义礼智信者五音之本也。喜怒哀乐者五音之动也。调者,五音之体制,而声者,五音之句字也”①。因此,音乐演奏必须先定调,而后以声从之。若先设声,而后以调从之,则将导致性情之失,背离了音乐的本质。
至于诗、调、声三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李光地认为应以诗为根本,调次之,声最后。因为诗与性情之德的联系最为密切,所谓“不知调者,不可与言声;不知诗者,不可与言调;不知性情之德者,不可与言诗。可与言诗,而乐思过半矣”②。据此,李光地批评后代的雅乐形式大于内容,“声有高下而无疾徐,纵其应律,亦所谓知声而不知调者也,知调而不知诗者也”,因而主张学习与创作音乐“必先教诗,教诗者,必先以六德为之本,使其性情之发无有不得其平而不由其诚者,则二者之患亡矣。然后以六律为之音,盖亦简易而不难也”。③
李光地进一步指出,音乐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人民,故推行乐教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变通,使今人喜闻乐见,而不能将今乐与古乐简单地对立起来,一味追求复古。在他看来,三代以下礼乐不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儒者的礼乐思想迂大繁难、流于空谈而不切实际、无关日用。“礼则必其周公之制,乐则必其伶伦之律,微论其说无一是之归,纵使得之,亦止于郊庙朝廷之事,而所谓移风易俗,无有议及之者,又岂圣人礼云乐云之意哉?”④“若只郊庙中作乐,就是《云门》《咸池》《韶濩》《大武》,亦只天地鬼神闻之,如何天下风俗就会移易?自然是人人见闻,才能移风易俗。”⑤加之社会风俗变迁,民众习尚日非,即便勉强推行古乐,亦不过是“强其所不乐,举其所不行,则莫之从而不能久,非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者也”①。因此,李光地极称孟子所说的“今之乐,由古之乐”,主张从实用出发,借鉴古乐的精神与形式来改良、整理今日之戏曲,“去其淫辞新声,及其节目之荒诞无实者,而一均之和音,被以雅曲,实之以忠孝廉贞节义之事,亦庶几乎可以语,可以道古者,未必非风俗之一助也”②。同时,还应改变俗乐的冗长繁衍,戏以四出为则,并使歌、舞分离,做到“舞以动其容,虽貌肖而口不言也;歌以咏其事,虽赞叹之而亦非其自言也。听其歌,观其容,而其人可知。……则至善矣”③。
在天文、历法方面,李光地主要受到梅文鼎与康熙帝的影响,编撰有《历象要义》《历象本要》④《星历考原》等著作。在某些学者眼中,天文、历法乃畴人、星官的专门职守,非儒者之所当务,故学者不必于此用心。而李光地则指出,天文、历法之学不仅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直接指导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适于日用,所需尤大”⑤,而且其关于宇宙、天地的生成、演化、运动等诸问题的研究亦与儒学义理直接关联,构成了儒家学说的重要知识背景与思想基础。所以他说:
圣人作历,为顺天以授时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时,而寒暑四时运于不可见,于是而纪诸日月星辰之行。是故察日之出没,而昼夜明焉;察月之盈虚,而朔晦明焉;察日之发敛,而冬夏明焉。《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寒暑昼夜者,天道之纲,民用之本。⑥
又说:
乾坤,父母也,继志述事者,不离乎动静、居息、色笑之间,故《书》始历象,《诗》咏时物,《礼》分方设官,《春秋》以时纪事,《易》观于阴阳而立卦,合乎岁闰以生蓍,其所谓秩序、命讨、好恶、美刺、治教、兵刑、朝会、搂伐,建侯迁国之大,涉川畜牝之细,根而本之,则始于太乙,而殽于阴阳。日星以为纪,月以为量,四时以为柄,鬼神以为徒,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①
在李光地看来,天地不仅是万事万理的根本,而且是万事万理的起点,构成了实学的真正基础。故“孔子从不曾说到天地之先。……都是从天地说起。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无稽之言,无复证据者,圣人便不言”②。又谓:“圣人万古之师,一切幽渺荒唐之说,删去净尽。说理气只从天地说起,又只说现在的,至天地以前,天地之终,都不说。删《书》断自唐虞,以前就有文字,孔子都不存。不似他家从混沌之始,悬空揣度,以启后来编通鉴者荒唐幽怪之谬。”③因此,李光地的天文、历法研究既注重实际、实用,不为幽渺荒唐之说,又时常将其与理学思想进行结合,互相印证,故而往往给人留下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
譬如,关于宇宙的结构,李光地其实已经接受了西方天文学的“地圆说”,提出:“地至圆,无有上下,周遭人皆戴天履地,无有偏侧倒置”④,“天地如鸡卵,古人虽有其说而未竟其论。唐之淳风、一行,宋之尧夫,元之郭太史、许鲁斋,明之刘伯温,皆聪明绝世,而皆不知天地之俱为圆体。自西人利玛窦辈入中国,言地原无上下,无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中国人争笑之,岂知自彼国至中国,几于绕地一周,此事乃彼所目见,并非浪词”①。但在同时,李光地亦未彻底否定传统的“天圆地方”说,而是对其加以转化,以动静之理进行解释。如南怀仁曾深诋天圆地方之说,李光地即回应道:“天地无分于方圆,无分于动静乎?盖动者,其机必圆;静者,其本必方。如是则天虽不圆,不害于圆;地虽不方,不害于方也。”②此后,他又多次提及“‘天圆地方’之说,盖以动静体性言之。实则形气浑沦相周,古人卵中黄之喻是已”③,“天圆地方者,言其动静之性耳。实则地亦圆体,如卵里黄,上下周围与天度相应”④。显然,李光地并非当真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是借用《大戴礼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道曰方圆耳,非形也”⑤的思想,以天道动、地道静来解释“天圆地方”说。
类似地,李光地既然承认地圆说,那么自然知道中国并非位于大地的中心,甚至根本不存在某一特定的“地中”。譬如他说:“夫至顺极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浑沦旁薄者,地之本体然也。其南北两端,以去日远近为寒暑之差;东西以见日早晚为昼夜之度。东之夜乃西之昼,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则东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极为中,或以赤道为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⑥但是,当南怀仁以赤道为地中,批评“中国”之名时,李光地又反驳道:“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⑦关于地中的含义与判断标准,李光地还提出:“西法称赤道之下,二分午表无景,是冬夏数均也。昔人有至外国者,熟一羊头而夜已曙,是昼数常赢也。今法南方四时昼刻每多于北,又况乎其九州之外者乎?昼夜不均,非所语中,然一岁之内,绝无短永,阴阳消息,其序靡显,揆之于理,亦未为中也。如此,则惟中国之地,晷刻赢缩,与四时进退,二至相除,毫无余欠,而洛又其中之中,谓之中土,理宜不诬。以是知经所言天地四时之所交合,阴阳风雨之所和会,信乎其为至理,而非虚说也”①,又谓:“中国不可言地之中,惟可言得天地之中气。当黄道下处,日直到顶上,其热太剧。当赤道下处,一岁两春夏秋冬,立春、春分为春夏,立夏、夏至为秋冬,立秋、秋分又为春夏,立冬、冬至又为秋冬。惟中国寒暑昼夜适均而不过,所以形骸端整,文物盛备。”②如此,李光地就将原先表示地理位置的“中”转化为合理、中理的意思,并将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昼夜寒暑变化规律视为理的标准,即所谓“正理”,从而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提供合理性依据。
由上可知,李光地并未在客观事实的层面上否定地圆说,反而一再对其予以肯定和宣传,但他同时又努力从义理的层面上对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和“中国”说进行解释和辩护,以此维护这些作为传统文化思想、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知识背景与思想前提的基础性观念,使其能够继续为上层建筑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持,尽量缓解来自西方知识与思想的冲击。有趣的是,当初利玛窦在向中国介绍和引进地圆说时,为了淡化与中国传统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以减轻西方知识、思想传播的阻力,亦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如利玛窦在解释《坤舆万国全图》时就曾表示:“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德静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③而他在绘制世界地图时,亦有意将中国安排在靠近中心的位置,以适应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若从这一角度观察,则李光地对于传统观念的维护及其对中西学说的调和或许也带有某种辅助西学传播的意味,尽管这并非其主要目的。
此外,李光地还结合西方古典天文学知识与《周髀算经》中的传统天文理论,以太阳的运动来解释四季变化、极昼、极夜等现象,以及寒暑五带的形成原因。他说:“《周髀》言:‘北极之下,有朝生而暮获者’,人指为谩。赵氏注之云:‘以北极之下,有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者故也。’此语忒煞聪明。盖北极下,日在天腰,其在上半盘绕时全是昼,及旋到下半,便全是夜。此理甚确。”①又说:“其地气寒暑,则以去日远近为差。赤道之下,正与日对,其地最热,其景则四时常均,无冬夏短永。两极之下,取日最远,其地最寒,其景则短者极短,长者极长。正当两极之处,常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惟二极与赤道相去之间,当日南北轨之外,起二十三度,至四十度许,其地不寒不热,温和可居,其景则与冬夏进退,长短之极,皆无过十之七。”②李光地还据此批评《绎史》“天地之精华为四时,有四时而后有五行。水之精为月,火之精为日”的观点“大可笑”,指出:“四时乃因日而有,日傍近气温为春,在头上大热为夏,稍远便凉为秋,大远便冷为冬。据《周髀经》及西洋人说,则半年寒、半年暑者有之,一年有两春夏秋冬者有之。与中国对过的地方,中国的南极,是他的北极,中国的北极,是他的南极。中国寒,他却暑,中国暑,他却寒。”③
在算学方面,李光地主要亦受到梅文鼎与康熙帝的影响。据李光地自述,其早年曾问算学于潘耒,可惜教学不甚得法,故所得不多。直到后来与梅文鼎结交,其算学水平才得到较大提升。④而康熙帝亦时常与李光地探讨算学问题,还曾亲赐对数表与《几何原本》《算法原本》等算学书籍给李光地,对其算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引导与促进作用。
李光地治算学同样注重中西、新旧之法的融合与会通。在他看来,古代六艺之学中的所谓“九数”皆与实际、实用相关,皆为经世之实学,故能极数之用。“然古人精密之法不传,而后世所用,悉皆疏率。故所谓径一围三、径五斜七云者,不过约略之算,而其方圆相求,三分进益,虚加实退,皆非真数也。”①相比之下,当时传入的西洋新法却十分精密,“于方圆、围径、幂积之算不爽纤毫”②,故应积极学习、借鉴西洋新法以补本国旧法之未备。关于西洋算学的学习与运用,李光地提出:“欲通新法者,必于几何求其原,以三角定其度,较之以八线,算之以三率,则大而测量天地,小而度物计数,无所求而不得矣。”③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李光地对几何学与《几何原本》特别重视,将点、线、面、体视为算学的基础,即“万数之宗”。他说:“点引而成线,线联而成面,面积而成体。自此而物之多寡、长短、方圆、广狭、大小、厚薄、轻重,悉无遁形;自此而物之比例、参求、变化、附会,悉无遁理。”④他又将几何原理与儒学义理结合起来,提出:“凡数起于点,当初止有一点,引而长之则为线,将此线四围而周方之则为面,又复叠之教高则成体。‘直方大’,即是此意。直即线,方即面,大即体。惟直而后可方,惟方而后能大,故《象》曰‘直以方也’。直了才能方,既直方自然大,故曰‘敬义立而德不孤’”⑤,试图以客观、具体、精密的西洋算学来解释、论证道德性的儒学义理。
此外,李光地还主张“算法重三角形”⑥,故对我国古代的勾股法与西洋的三角、八线、三率法之间的异同做了比较。他说:“古所谓勾股者,举中之法耳。今三角法,即勾股也,然而有直角,有锐角,有钝角。又其算也,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而角度对之,故量角之度以为起数之根。然则勾股有直而无锐钝,其数起于边而不起于角,岂非有待于新法以补其所未备者乎?其用之,则以八线之表。八线者,亦古人所谓勾股弦也。今则变勾而曰矢,且有正矢焉,有余矢焉;变股而曰弦,且有正弦焉,有余弦焉;其在圆外之股则曰切,且有正切焉,有余切焉;变弦而曰割,且有正割焉,有余割焉。八线相求,互为正余,故举一则可以反三,穷三则可以知一。举一反三,穷三知一者,则今之三率法是也。三率之法,即古者异乘同除之法,而其立法加妙,用之加广,则非古人之所及也。”①显然,李光地承认西洋数学要比我国的传统算学在方法上更为完备、精妙与准确。
综上可知,作为一位重视实学的理学家,李光地对于当时大量传入的西学事实上抱持着一种较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李光地对于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与实用器物持较为开放与开明的接受态度,特别是对其研究方法的完备、精密,及其对自然事物的解释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十分肯定和推崇,所以他屡次称赞西洋历法“甚精密……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②,“西士天学可称烂熟,简平仪取适用,而天之体不外乎是。前儒《浑天象七政图》,却失本来面目”③,“自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说多矣,至于今日西历之家,其说弥详”④,又表彰西洋数学“立法加妙,用之加广,则非古人之所及也”⑤,还为西洋的机械、仪器等正名与辩护,提出:“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觿、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①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地有时还会借助西方的科学知识来解释、论证儒学的观点与义理,如以几何学原理解释《周易》所说的“直以方”和“敬义立而德不孤”,又谓:“看天似无心,然从事事物物体贴来,觉得处处都似算计过一番。如黄道、赤道不同极,常疑何不同极,省得步算多少周折。细想,若同一极,必有百年只见半日、半月之处,惟略一差异,便隐见盈亏都均齐矣”②,可见其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准确性的信任和重视。李光地不仅自身积极学习、研究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运用其知识编撰相关著作,如阮元即称李光地“所著书皆欧罗巴之学。其言均轮次轮之理,黄赤同升、日食三差诸解,旁引曲喻,推阐无遗,并图五纬视行之轨迹,尤多前人所未发”③,而且延揽、培养、提携了一大批天文、历算人才,资助梅文鼎等人刊刻出版最新的天文、历算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天文、历算之学的繁荣兴盛,以及相关西学知识的传播扩散。
但在另一方面,李光地对于西学的传播、流行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可能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与威胁亦表示深刻的忧虑。为此,他对西方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思想学说持批评与排斥的态度,认为“西人学甚荒唐”④,而对西方的科技知识则主要将其限制在实用的范围之内,尽量避免其与传统思想发生直接冲突,同时更多地采取所谓“古已有之”的应对策略,通过发掘自身固有的学术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可与之对应的内容与材料,以此证明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与合理性,起码在与西学的比较中并不显得落后。譬如,李光地受梅文鼎的影响,特别重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古代天文、历算典籍,大力发掘、阐释其中埋没已久的学术内涵,提出:
天圆而地亦圆,四方上下皆人物所居,各以戴天为上,履地为下也,其说与《周髀》合。且浑天之术本谓如卵裹黄,乌有卵圆而黄不圆者乎?……天有九重,最近者月天也,稍远则日天与金、水天,又远则火星天,又远则木星天,又远则土星天,最远则恒星天,其外则宗动天也。《楚辞·天问》曰:“天有九重,孰营度之?”然则九重之说旧矣。……惟宗动天行有常度,不独日月五星右行,恒星天亦右行也。其说则历代岁差之说是也。①
新历以地为圆体,南北东西,随处转移,故南北则望极有高下,东西则见日有早暮。望极有高下,而节气之寒暑因之矣;见日有早暮,而节气之先后因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其变,其说与《周髀》合。②
天地如鸡卵,古人虽有其说而未竟其论。……自西人利玛窦辈入中国,言地原无上下,无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中国人争笑之,岂知自彼国至中国,几于绕地一周,此事乃彼所目见,并非浪词。至梅定九出,始发明《周髀经》,以为原如此说,何必西学。③
夫至顺极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浑沦旁薄者,地之本体然也。其南北两端,以去日远近为寒暑之差;东西以见日早晚为昼夜之度。东之夜乃西之昼,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则东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极为中,或以赤道为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此理《周髀》言之至悉,而汉氏以下莫有知者。近新历之家,侈为独得,历诋前说,几数万言。惜乎无以《髀》盖之术告之者。④这些带有浓厚附会色彩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有些自大和可笑,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士人内心的紧张,在客观上有助于那些刚刚接触西学的士人以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情去理解和接受西方的新知识与新思想,未必一无是处。
关于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差异,李光地还提出过这样一种说法:
西人历算,比中国自觉细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如古人说日变修德,月变修刑,西人便说日月交食,五星凌犯,乃运行定数,无关灾异。不知天于人君,犹父母也,父母或有病,饮食不进,岂不是风寒燥湿所感,自然有的。但为子孙者,自应忧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反于身,或是己有不是处,触怒致然,否则亦是我有调理不周而致然。因为彷徨求医,断无有说疾病人所时有,不须管他之理。无论天子,即督抚于一省,知府于一郡,知县于一邑,皆有社稷人民之责,皆当修省。即士庶虽至卑贱,似不足以召天变,然据理亦当修省。如父母怒别个儿子时,凡为儿子者俱当畏惧,父母断不因其畏惧,而谓我本怒他,于尔无与,而反增其怒者。通天地人之谓儒,扬雄谓:“知天而不知人则技。”西人此等说话,直是阴助人无忌惮,天变不足畏之说。①
对于李光地的这一说法,不少学者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其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以愚昧落后的天人感应和星占术数迷信观念来诋斥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反映了其对西学的浅薄和无知。这一批评虽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起码有简单化的嫌疑。其实,若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李光地在这里虽然借用了某种天人感应的表达形式,但其目的并非为了宣扬天人感应学说,也不能因此认定李光地相信自然现象是由人事所引起,因为这明显不符合李光地的天文学思想。而他之所以要这么说,主要是希望借此提醒人君与各级官员须对天地自然,特别是天地自然背后的天理保持敬畏之心,时时因外部世界的改变而反省自己的行为,进而修明政治,改过迁善。所以李光地以父母子女比喻天人关系,认为虽然父母因风寒燥湿所感而生病是自然有的,但作为子女仍须首先自我反省,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然后为父母求医治病,“断无有说疾病人所时有,不须管他之理”。更进一步,在李光地看来,一门学问必须贯通天人,能够从具体的事物之理提升到普遍之理,并且对从天道到人事的所有问题都给出连贯、统一的解释,才能称得上最好的学问。所以他强调“通天地人之谓儒”,“知天而不知人则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的天文、历算之学恰好可以为这种“天人相通之理”提供相关的知识背景与思想基础,进而满足人们关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知识与价值的需要,而注重客观、专门的西方天文、历算之学显然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光地认为中学优于西学,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纵然精密,但亦无法彻底取代中国的传统学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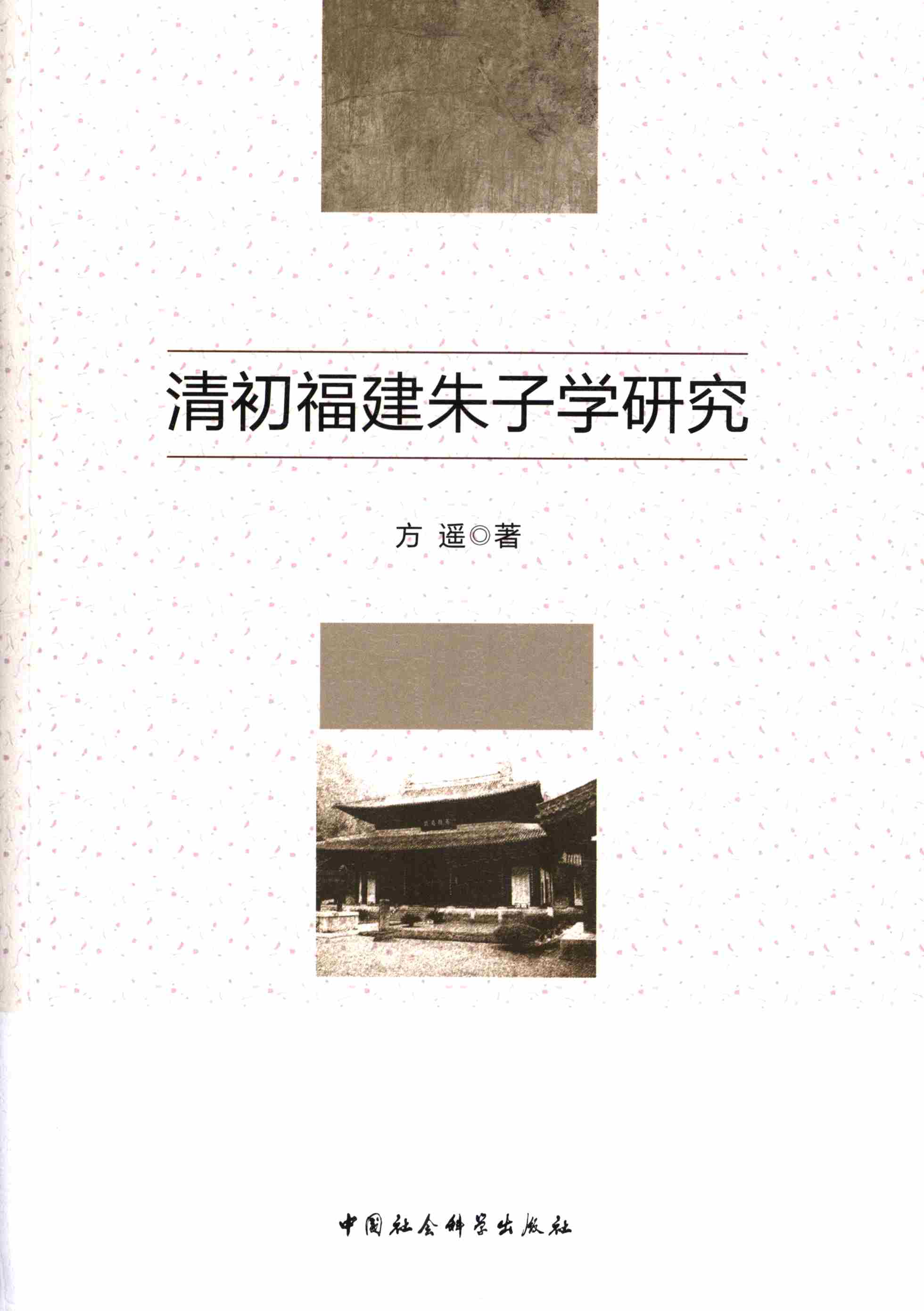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
相关人物
李光地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