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道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400 |
| 颗粒名称: | (一)治道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0 |
| 页码: | 553-562 |
| 摘要: | 本文主要介绍了朱熹关于治道的主张。朱熹认为治道应当以正君心、修君德为大本,同时还应建立起纲纪,使君臣、百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他强调了正君心的重要性,认为纲纪的确立需要依靠人君心术公平正大,并选贤任能以共治天下。朱熹还批评了过去一味追求宽政的现象,主张在严政的基础上予以宽济。此外,朱熹还提出了“论治须识体”的思想,强调官员应当根据职位的要求与设立之意来了解并履行自己的责任。 |
| 关键词: | 清初 朱子学 治道 |
内容
关于治道,朱熹提出应当首重正君心,修君德,以此为治道之大本。他说:
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⑤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个根本。⑥
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①
因此,朱熹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首次应诏上封事时即昌言“人心道心”之旨:
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尧、舜、禹皆大圣人也,生而知之,宜无事于学矣。而犹曰精,犹曰一,犹曰执者,明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也。……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②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事延和殿时又言: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舜、禹相传,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正谓此也。①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所上封事中再次强调正君心的重要性:
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盖不惟其赏之所劝、刑之所威,各随所向,势有不能已者,而其观感之间,风动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②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朱熹又拟对新皇帝说道:
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为本。然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然所谓学,则又有邪正之别焉。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学之正也。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反之身则无实,措之事则无当者,学之邪也。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故讲学虽所以为正心之要,而学之邪正,其系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审者又如此。①由此可见,朱熹不仅对于正君心、修君德特别重视,而且针对当时流行的“以佛治心”之说,着意将正心与理学的心性论和工夫论紧密捆绑在一起,强调必由格物、致知,方能诚意、正心而应天下之务。而朱熹之所以始终执着于此,既是出于理学家提倡尊德性与价值优先的基本立场,又是基于朱熹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尽管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下,唯有彻底说服皇帝相信自己的思想主张,取得皇帝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才能合法而顺利地推动政治变革。所谓“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②。若从这一意义上看,朱熹强调的正君心与得君心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不过在现实中,真要皇帝以理学的方式正心、修德亦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须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一步步做起,其中光是格物一项便繁复无比,在外人看来不免迂阔。因此,当有人问及“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修起?必有其要”时,朱熹即答以去私心、任贤人为要,认为“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③,从而将人君的修养与国家的治理用最简洁的方式连接起来,既避免了单纯道德说教的抽象性,又将君与臣的作用恰当地结合起来,使人君知其要领。既然治国须“搜求正人用之”,那么正心、修德、明理就不能仅仅被看作人君的个人责任,而应该成为所有官员、士大夫的首要任务。“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明,自做得尧、舜许多事业。若要一一理会,则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①反过来说,则“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说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我自不消得用此”②。其实不唯当时,在朱熹看来,宋代以来的历次变法之所以皆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士大夫不明义理所致。
除了正君心、修君德这个大根本外,在治理国家的各个具体方面与具体领域亦有其切要处即小根本需要讲求。“如理财以养民为本,治兵以择将为本。”③“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④显然,朱熹对于治国理政的各项基本原则与措施要点皆有清楚的认识,并未因重视道德修养而对实际事务有所忽略和排斥。只不过在他看来,人君的道德修养构成了这一切的基础与保障,若人君心术不正,再好的政策都无法落实。故曰:“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矣。”⑤
正君心之后还须立纲纪,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朱熹在淳熙七年(1180)所上封事中指出: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纵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①
由此可见,若君心不正,则纲纪无由立;若纲纪不立,而曰君心正,亦无是理。朱熹进一步指出,纲纪虽由乡、县总于宰相、天子,但其要者在于“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②,故欲立纲纪,必由天子及其家人、近臣而推及朝廷、天下。所谓“明于内,然后有以齐乎外;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③。人君若为小人环伺,耳闻目睹无非不公不正之事,自然无法秉公执政,是以纪纲不能无挠败。相反,“若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退朝之后,从容燕息,贵戚近臣、携仆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戴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纪纲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④。而这亦体现出理学家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政治思想。
树立纲纪的另一重点便是君臣、百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而互不扰乱。在朱熹看来,人君虽以制命为职,拥有最高的权力,但亦无法以一人之身独任天下,故须选贤任能以共治天下。凡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必须由君臣共同商议决定,使其出于公议,而非皇帝一人的独断。因此,对于宁宗即位之初,在未与大臣商议的情况下即擅自“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的举动,朱熹就不客气地以朝廷纲纪的名义提出了批评:
朝廷纪纲,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①
在此,朱熹反复强调“公议”的重要性,将君臣共商朝政视作“古今之常理”“祖宗之家法”,甚至认为即便人君独断之事符合道理,其行为亦不合治体,显然都是出于对君权过度集中的担忧。朱熹十分清楚,若君权过度集中而不受制约,必将使权力的授予与运行逸出理性的制度法规之外,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从而损害朝廷纲纪,助长不正之风,破坏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正是鉴于当时纲纪紊乱、风俗颓敝、奸佞当道、豪强横行的状况,朱熹主张为政须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朱子语类》载:
或问:“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曰:“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曲礼》谓‘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①
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②
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宽”字。③朱熹指出,由于过去一味提倡为政以宽,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其仁民爱物的本意,不但百姓未蒙其惠,反而造成了事无统纪、法令不行、权力旁落、奸豪得志的恶果,故须以严政矫之,确保令行禁止,方能逐渐过渡到宽严相济的合理状态。同时,由于对宽政理解的偏差,还导致官员因循苟且、不问政事的风气迅速蔓延,使国家、百姓皆深受其害。所以朱熹批评“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抚循为知体。……如此风俗议论至十年,国家事都无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风大害事”④。又谓:“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排,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予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⑤
由此亦可看出,朱熹并未盲目迷信过去的政策、制度与成法,而是主张在继承祖宗立法之意的基础上,因时制宜,因事制宜,而加以变通和更张,甚至将此视为后人应尽的职责。故曰:“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①事实上,朱熹在孝宗即位之初所上的第一道封事中就明确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由于担心遭到守旧官僚集团以更改“祖宗之法”的借口加以反对和阻挠,朱熹特别强调高宗“用人造事,皆因时循理以应事变,未尝胶于一定之说。先后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变,相反以成岁功,存神过化,而无有毫发私意凝滞于其间”,又引尧舜相承为例,指出“舜承尧禅,二十有八年之间,其于礼乐刑政,更张多矣。其大者,举十六相,皆尧之所未举;去四凶,皆尧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为嫌,尧不以为罪,天下之人不以为非,载在《虞书》,孔子录之以为大典,垂万世法”,以此论证其改革主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批评守旧者“顾欲守一时偶然之迹一二以循之,以是为太上皇帝之本心,则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语天地变化之神也,岂不误哉!”②
尽管从表面上看,朱熹对于改革与变法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哄然成纷扰,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③,但若考虑到朱熹对当时政治“其法无一不弊”④的激烈批评,则其改革政治的意图和决心无疑是很明显的,甚至不惜要“一切重铸”⑤。而其政治改革除了要求变革旧法外,最终仍归结到正人心、去私欲上。所谓“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祐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⑥。显然,朱熹的这一改革思路是在反思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指示了理学家关注内圣之学的原因与意义所在。
此外,朱熹还提出了“论治须识体”的思想。根据朱熹的解释,“体”便是事理合当做处,是当务之急,因而亦是某一事物成立和存在的原因。“凡事皆有个体,皆有个当然处。”①以治理国家而论,则为朝廷有朝廷之体,为一国有一国之体,为州县有州县之体,相互之间不可紊乱。故官员处于不同的职位,就应根据这一职位的客观要求与设立之意来了解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如作州县,便合治告讦,除盗贼,劝农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须开言路,通下情,消朋党;如为大吏,便须求贤才,去脏吏,除暴敛,均力役,这个都是定底格局,合当如此做。”②反之,若是官员不务正业,颠倒主次,专以小事为急,便损害了那个“体”,于治道大有害。“如为天子近臣,合当謇谔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处乡里,合当闭门自守,躬廉退之节,又却向前要做事,这个便都伤了那大体。”③据此,朱熹批评当时的官员“合当举贤才而不举,而曰我远权势;合当去奸恶而不去,而曰不为已甚。且如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却曰休兵息民,兼爱南北!正使真个能如此,犹不是,况为此说者,其实只是懒计而已!”④
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⑤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个根本。⑥
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①
因此,朱熹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首次应诏上封事时即昌言“人心道心”之旨:
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尧、舜、禹皆大圣人也,生而知之,宜无事于学矣。而犹曰精,犹曰一,犹曰执者,明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也。……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②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事延和殿时又言: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舜、禹相传,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正谓此也。①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所上封事中再次强调正君心的重要性:
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盖不惟其赏之所劝、刑之所威,各随所向,势有不能已者,而其观感之间,风动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②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朱熹又拟对新皇帝说道:
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为本。然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然所谓学,则又有邪正之别焉。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学之正也。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反之身则无实,措之事则无当者,学之邪也。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故讲学虽所以为正心之要,而学之邪正,其系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审者又如此。①由此可见,朱熹不仅对于正君心、修君德特别重视,而且针对当时流行的“以佛治心”之说,着意将正心与理学的心性论和工夫论紧密捆绑在一起,强调必由格物、致知,方能诚意、正心而应天下之务。而朱熹之所以始终执着于此,既是出于理学家提倡尊德性与价值优先的基本立场,又是基于朱熹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尽管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下,唯有彻底说服皇帝相信自己的思想主张,取得皇帝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才能合法而顺利地推动政治变革。所谓“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②。若从这一意义上看,朱熹强调的正君心与得君心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不过在现实中,真要皇帝以理学的方式正心、修德亦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须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一步步做起,其中光是格物一项便繁复无比,在外人看来不免迂阔。因此,当有人问及“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修起?必有其要”时,朱熹即答以去私心、任贤人为要,认为“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③,从而将人君的修养与国家的治理用最简洁的方式连接起来,既避免了单纯道德说教的抽象性,又将君与臣的作用恰当地结合起来,使人君知其要领。既然治国须“搜求正人用之”,那么正心、修德、明理就不能仅仅被看作人君的个人责任,而应该成为所有官员、士大夫的首要任务。“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明,自做得尧、舜许多事业。若要一一理会,则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①反过来说,则“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说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我自不消得用此”②。其实不唯当时,在朱熹看来,宋代以来的历次变法之所以皆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士大夫不明义理所致。
除了正君心、修君德这个大根本外,在治理国家的各个具体方面与具体领域亦有其切要处即小根本需要讲求。“如理财以养民为本,治兵以择将为本。”③“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④显然,朱熹对于治国理政的各项基本原则与措施要点皆有清楚的认识,并未因重视道德修养而对实际事务有所忽略和排斥。只不过在他看来,人君的道德修养构成了这一切的基础与保障,若人君心术不正,再好的政策都无法落实。故曰:“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矣。”⑤
正君心之后还须立纲纪,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朱熹在淳熙七年(1180)所上封事中指出: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纵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①
由此可见,若君心不正,则纲纪无由立;若纲纪不立,而曰君心正,亦无是理。朱熹进一步指出,纲纪虽由乡、县总于宰相、天子,但其要者在于“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②,故欲立纲纪,必由天子及其家人、近臣而推及朝廷、天下。所谓“明于内,然后有以齐乎外;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③。人君若为小人环伺,耳闻目睹无非不公不正之事,自然无法秉公执政,是以纪纲不能无挠败。相反,“若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退朝之后,从容燕息,贵戚近臣、携仆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戴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纪纲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④。而这亦体现出理学家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政治思想。
树立纲纪的另一重点便是君臣、百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而互不扰乱。在朱熹看来,人君虽以制命为职,拥有最高的权力,但亦无法以一人之身独任天下,故须选贤任能以共治天下。凡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必须由君臣共同商议决定,使其出于公议,而非皇帝一人的独断。因此,对于宁宗即位之初,在未与大臣商议的情况下即擅自“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的举动,朱熹就不客气地以朝廷纲纪的名义提出了批评:
朝廷纪纲,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①
在此,朱熹反复强调“公议”的重要性,将君臣共商朝政视作“古今之常理”“祖宗之家法”,甚至认为即便人君独断之事符合道理,其行为亦不合治体,显然都是出于对君权过度集中的担忧。朱熹十分清楚,若君权过度集中而不受制约,必将使权力的授予与运行逸出理性的制度法规之外,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从而损害朝廷纲纪,助长不正之风,破坏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正是鉴于当时纲纪紊乱、风俗颓敝、奸佞当道、豪强横行的状况,朱熹主张为政须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朱子语类》载:
或问:“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曰:“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曲礼》谓‘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①
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②
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宽”字。③朱熹指出,由于过去一味提倡为政以宽,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其仁民爱物的本意,不但百姓未蒙其惠,反而造成了事无统纪、法令不行、权力旁落、奸豪得志的恶果,故须以严政矫之,确保令行禁止,方能逐渐过渡到宽严相济的合理状态。同时,由于对宽政理解的偏差,还导致官员因循苟且、不问政事的风气迅速蔓延,使国家、百姓皆深受其害。所以朱熹批评“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抚循为知体。……如此风俗议论至十年,国家事都无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风大害事”④。又谓:“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排,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予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⑤
由此亦可看出,朱熹并未盲目迷信过去的政策、制度与成法,而是主张在继承祖宗立法之意的基础上,因时制宜,因事制宜,而加以变通和更张,甚至将此视为后人应尽的职责。故曰:“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①事实上,朱熹在孝宗即位之初所上的第一道封事中就明确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由于担心遭到守旧官僚集团以更改“祖宗之法”的借口加以反对和阻挠,朱熹特别强调高宗“用人造事,皆因时循理以应事变,未尝胶于一定之说。先后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变,相反以成岁功,存神过化,而无有毫发私意凝滞于其间”,又引尧舜相承为例,指出“舜承尧禅,二十有八年之间,其于礼乐刑政,更张多矣。其大者,举十六相,皆尧之所未举;去四凶,皆尧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为嫌,尧不以为罪,天下之人不以为非,载在《虞书》,孔子录之以为大典,垂万世法”,以此论证其改革主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批评守旧者“顾欲守一时偶然之迹一二以循之,以是为太上皇帝之本心,则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语天地变化之神也,岂不误哉!”②
尽管从表面上看,朱熹对于改革与变法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哄然成纷扰,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③,但若考虑到朱熹对当时政治“其法无一不弊”④的激烈批评,则其改革政治的意图和决心无疑是很明显的,甚至不惜要“一切重铸”⑤。而其政治改革除了要求变革旧法外,最终仍归结到正人心、去私欲上。所谓“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祐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⑥。显然,朱熹的这一改革思路是在反思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指示了理学家关注内圣之学的原因与意义所在。
此外,朱熹还提出了“论治须识体”的思想。根据朱熹的解释,“体”便是事理合当做处,是当务之急,因而亦是某一事物成立和存在的原因。“凡事皆有个体,皆有个当然处。”①以治理国家而论,则为朝廷有朝廷之体,为一国有一国之体,为州县有州县之体,相互之间不可紊乱。故官员处于不同的职位,就应根据这一职位的客观要求与设立之意来了解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如作州县,便合治告讦,除盗贼,劝农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须开言路,通下情,消朋党;如为大吏,便须求贤才,去脏吏,除暴敛,均力役,这个都是定底格局,合当如此做。”②反之,若是官员不务正业,颠倒主次,专以小事为急,便损害了那个“体”,于治道大有害。“如为天子近臣,合当謇谔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处乡里,合当闭门自守,躬廉退之节,又却向前要做事,这个便都伤了那大体。”③据此,朱熹批评当时的官员“合当举贤才而不举,而曰我远权势;合当去奸恶而不去,而曰不为已甚。且如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却曰休兵息民,兼爱南北!正使真个能如此,犹不是,况为此说者,其实只是懒计而已!”④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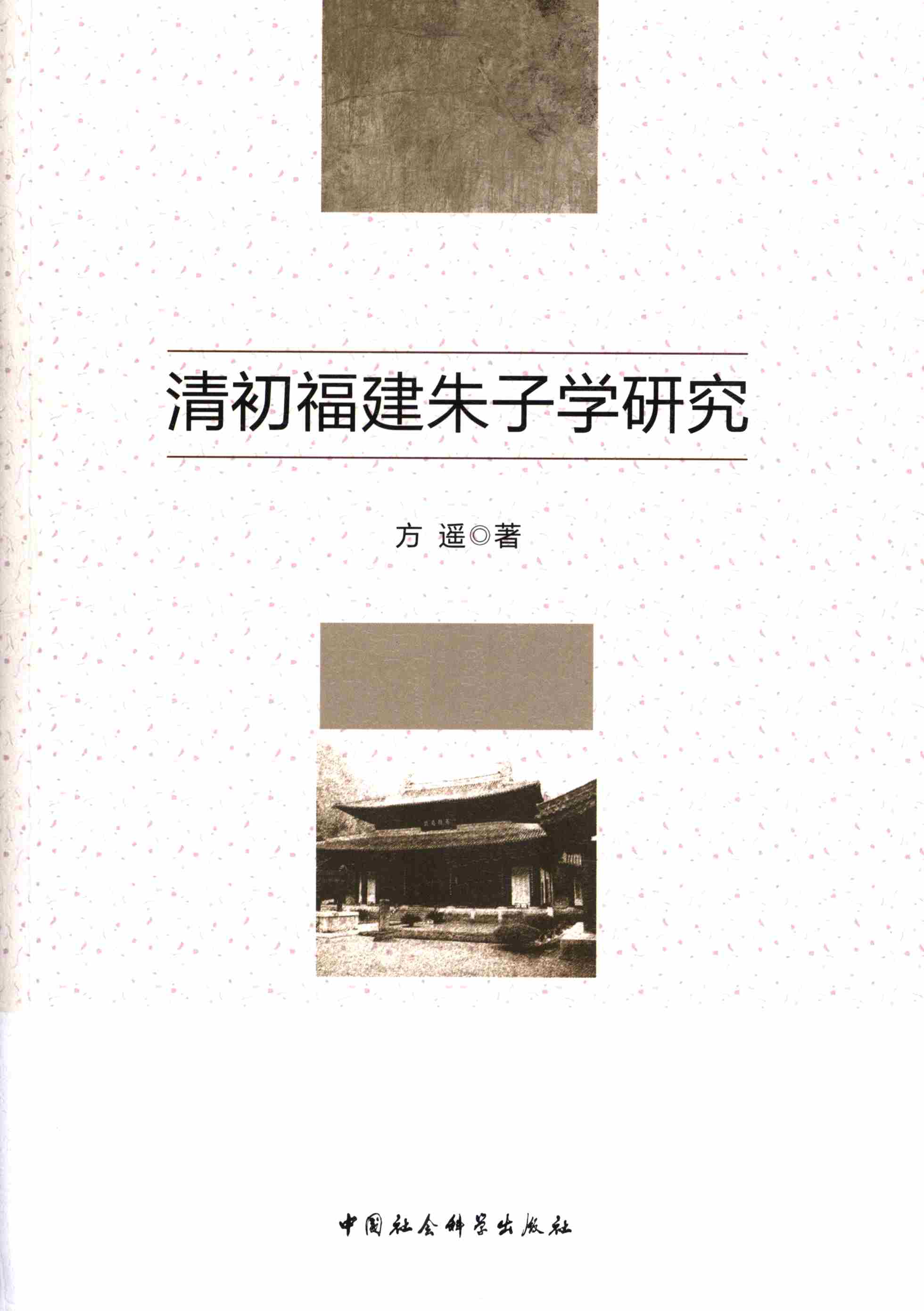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