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子学的为学方法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98 |
| 颗粒名称: | 三 朱子学的为学方法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3 |
| 页码: | 540-552 |
| 摘要: |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强调重实践、重经验,在具体事物中去寻找道理,并将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他主张通过实践来验证和完善知识,强调知行相辅相成,要将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实践能力。这种实学思想对后世的儒家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 关键词: | 清初 朱子学 为学方法 |
内容
毫无疑问,“格物致知”是朱子学中最为核心与重要,也最具特色和价值的一项为学方法。按照朱熹的理解,“格物”指的是即物穷理,“致知”主要指知识的扩充。格物与致知并非两种相互独立的为学方法,而是同一个求知穷理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致知虽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但作为一种为学方法来说,其本身已蕴含于格物穷理之中,并借助格物的过程得以实现。
对于格物穷理,朱熹十分注重“即事即物”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穷理工夫不可脱离具体事物而凭空进行。譬如他说:“圣人不令人悬空穷理,须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见得道理破,便实”②,“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③。在朱熹看来,《大学》之所以不直说穷理而只言格物,亦是为了避免学者离物言理、空谈穷理。“人多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④“《大学》所以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所以只说格物。”①
根据《大学》指示的“八条目”的先后次第,朱熹明确将格物致知视作学者为学的基本工夫和实下手处。他说:
须先致知而后涵养。②
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③
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④
圣贤所言为学之序例如此,须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处把捉扶竖起来,不如今人动便说正心诚意,却打入无形影、无稽考处去也。⑤
同时,朱熹虽然承认人自身的德性、情感、思维、念虑等也在格物的范围之内,但并不主张将其作为格物的主要内容与首要对象,更反对将格物仅仅理解为格心、明心。他说:
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己,亦恐见有错处,不可执一。⑥
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于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①
人之有是身也,则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则必有是理。若仁、义、礼、智之为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为用,是则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铄我也。然圣人之所以教,不使学者收视反听,一以反求诸心为事,而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盖理虽在我,而或蔽于气禀物欲之私,则不能以自见。学虽在外,然皆所以讲乎此理之实,及其浃洽贯通而自得之,则又初无内外精粗之间也。②
总之,朱熹之所以强调格物须以具体事物为主,为学必以格物为先,都是为了确保理的客观真实性。在朱熹看来,虽然心具万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心在即物穷理之前便已先天地具备对于所有知识与道理的完整认识。事实上,若不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践履,人就无法获得各种具体的知识与道理,并将潜在的道德原则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所谓“万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③。同时,现实中的人总是不免受到气质与欲望的干扰和障蔽,其心中本具之理往往难以觉察、实现与扩充,所以必须借助对外在事物的考察、研究来发明义理,从而使义理建立在一个客观、确实的基础之上。从这一意义上看,格物致知不仅能够扩充人的知识,还能为人的道德行为指示明确的方向,提供可靠的内容。因此,朱熹要批评陆九渊“大抵其学于心地工夫不为无所见,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穷理细密功夫,卒并与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觉,而高谈大论,以为天理尽在是也,则其所谓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①
关于格物致知的具体手段与途径,朱熹说道:
穷理格物,如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②
如读书而求其义,处事而求其当,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③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④由此可见,朱熹所主张的格物手段还是较为丰富的,由内到外,由静至动,从主观到客观,几乎都已囊括在内。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理学学术范式的影响,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实际上仍以读书为基本内容。就读书而言,朱熹可谓宋明理学家中最为重视读书价值的学者之一,并且为此建立起一整套的读书方法。其读书法以虚心平气、平实周密、循序渐进为最大特色,反对好高骛远、穿凿附会、空谈义理,完全可以实学之名当之。譬如他说:
读书大抵只就事上理会,看他语意如何,不必过为深昧之说,却失圣贤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于支离怪僻之域,所害不细矣。切宜戒之,只就平易慤实处理会也。⑤
圣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闲看过。直须是置心平淡慤实之地,玩味探索而虚恬省事以养之,迟久不懈,当自觉其益;切不可以轻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虚度光阴也。①
大概如此看,更须从浅近平易处理会、应用切身处体察,渐次接续,勿令间断,久之自然意味浃洽,伦类贯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厌常喜新,专拣一等难理会、无形影底言语暗中想象,杜撰穿凿,枉用心神,空费日力。②
奉劝诸公,且子细读书。书不曾读,不见义理,乘虚接渺,指摘一二句来问人,又有涨开其说来问,又有牵甲证乙来问,皆是不曾有志朴实头读书。若是有志朴实头读书,真个逐些理会将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己无益,只是一场闲说话尔,济得甚事?且如读此一般书,只就此一般书上穷究,册子外一个字且莫兜揽来炒。将来理明,却将已晓得者去解得未晓者。如今学者将未能解说者却去参解说不得者,鹘突好笑。③
据此,朱熹自然要批评陆九渊一派为学“不肯随人后,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烦如此逐些理会,须要立个高论笼罩将去。譬如读书,不肯从上至下逐字读去,只要从东至西一抹横说。乍看虽似新巧,压得人过,然横拗粗疏,不成义理,全然不是圣贤当来本说之意,则于己分究竟成得何事?”④又谓:“近世有人为学,专要说空说妙,不肯就实,却说是悟。此是不知学,学问无此法。才说一‘悟’字,便不可穷诘,不可研究,不可与论是非,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①显然,在朱熹眼中,其与陆氏之学的差别就是实学与虚谈的差别。
朱熹虽然十分重视读书的作用与价值,但并未排斥或否定其他更为直接的格物方法。当有学生问及“明明德之功,是否以读书为要”时,朱熹既肯定“固是要读书”,又补充道:“然书上有底,便可就书理会;若书上无底,便着就事上理会;若古时无底,便着就而今理会”,②显示出一种通达、实际的为学态度。事实上,在格物致知这项庞大的事业中,朱熹始终都未停止使用观察、实验、实测等手段来认识、研究各种事物的知识、性质与规律。譬如,为了研究、验证《周礼》所载“土圭测土深”之法,朱熹曾请弟子林择之以“竹尺一枚,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示及”③。为了考证《仪礼》所载士庙之制,朱熹认为光凭纸面上的考据和想象并不足够,还须还原现场,实地模拟以验其实。他在给黄榦的信中说道:“所论士庙之制……堂上前为三间、后为二间者,似有证据。但假设尺寸大小,无以见其深广之实,须稍展样,以四五尺以上为一架,方可分画许多地头、安顿许多物色。而中间更容升降、坐立、拜起之处,净扫一片空地,以灰画定,而实周旋俯仰于其间,庶几见得通与不通,有端的之验耳。”④又如,朱熹十分重视天象的观测,对于各种天文仪器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家中不仅拥有一台浑仪⑤,可用来观测天象,而且还试图制作一台浑象以供天文研究之用。在给蔡渊的一封信中,朱熹曾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计划制作浑象的原因与方法:“《天经》之说,今日所论乃中其病,然亦未尽。彼论之失,正坐以天形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间随人所望固有少不同处,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弹圆之下以望之,南极虽高,而北极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极,决不至反入地下而移过南方也。(但入弹圆下者自不看见耳。)盖图虽古所创,然终不似天体,孰若一大圆象,钻穴为星,而虚其当隐之规,以为瓮口,乃设短轴于北极之外,以缀而运之,又设短柱于南极之北,以承瓮口,遂自瓮口设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为地平,使可仰窥而不失浑体耶?”①此后,朱熹在与蔡渊的信中又提及制作浑象之事,曰:“浑象之说,古人已虑及此,但不说如何运转。今当作一小者,粗见其形制,但难得车匠耳”②,可见其用心之深,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在致知与力行的关系上,朱熹从认识论的角度始终坚持知先行后的观点③,强调“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未能识得,涵养个甚”,④但他亦没有因此而忽视“行”的作用,而是从工夫论的角度主张知行相须,知行互发,不可偏废。譬如他说: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⑤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⑥又说: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①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②
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谨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③
由此可见,朱熹认为致知与力行作为两项基本的为学工夫,在学者为学的整个动态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虽说知先于行,但在事实上,不可能要求某人先达到物格知至的境界再去专意践行。因为“知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便穷毕生之功也未必能够实现,若一定要等到致知完成、知无不尽之后才去力行,势必导致力行流于空谈,或成为人们逃避力行的借口。同时,知有深浅,行有大小,真知的实现也有赖于行的推动,人往往需要通过实行来检验、加深对既有知识的认识。因此,人在略知所当然之后便当去行,在行中不断完善知,反过来又不断促进行,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与共同进步。“故《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履践而直从事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但以为必知之至,然后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尽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俟其至而后行哉?”①
但是,若硬要在知与行中分出一个先后轻重来,那么朱熹的答案亦是十分明确的,即“知为先,行为重”。②因为从儒者为学的逻辑次序与追求的终极目标来看,格物致知只是为学的起点,是于事事物物皆知其所以然与所当然,此后还须力行所知,修养德性,经世济民,由内圣推出外王,最终实现治平天下、成圣成贤的伟大目标。所谓“见无虚实,行有虚实。见只是见,见了后却有行,有不行”③,说明是否能够将所知所见付诸实行亦是衡量、判断学术虚实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此意义上,朱熹亦对行的价值作了极大的肯定与张扬: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④既涵养,又须致知;既致知,又须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与不知同。①
既知得,若不真实去做,那个道理也只悬空在这里,无个安泊处。②
为学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觉有窒碍,方好商量。今未尝举足而坐谈远想,非惟无益,窃恐徒长浮薄之气,非所以变化旧习而趋于诚实也。③
据此,朱熹批评当时学者多将进学致知与力行践履割裂开来,各主一偏,或知之不行,或行而不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固,与彼区区口耳之间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④。而之所以会出现“知之不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之不深、知之未至造成的。因为在朱熹看来,凡真知者必能循理而行,高度的道德意识必将产生自觉的道德行为,故“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⑤,不可能存在真知而不行的现象。既然真知必能行,那么反过来看,是否能够实行也就成为检验、判断知之深浅的一个重要标准。故曰:“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于己,岂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⑥,“人于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尽耳”⑦,“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⑧。此外,为了提倡躬行践履,力矫空谈之弊,朱熹还发挥了《尚书》“知易行难”的思想,指出践行义理要比谈论、讲说义理困难得多。他说:“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①又说:“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敱无能底人矣。恐不然也”②,“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③。显然,以上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朱熹所主张的“行重于知”的原因与根据。
主敬涵养作为一项基本的为学、修养工夫与“行”的重要内容,亦与格物致知保持着互发并进的关系。钱穆曾将朱熹所说的“主敬”的具体含义归纳为畏、收敛其心不容一物、随事专一(即主一)、随事点检、常惺惺、整齐严肃等六个主要方面。④其中既包含了未发主敬,也包含了已发主敬。在朱熹看来,“主敬”与“主静”有所不同。一方面,敬是静的前提,静是敬的表现,故曰:“敬则虚静,不可把虚静唤作敬”⑤,“敬则自然静,不可将静来唤做敬”⑥;另一方面,主敬贯穿动静、内外、始终,作用于从格物致知到治平天下的每一个环节中,并不仅限于未发涵养或主静工夫,故曰:“‘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⑦,“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⑧,“但看圣贤说‘行笃敬’‘执事敬’,则敬字本不为默然无为时设,须向难处力加持守,庶几动静如一耳”①。
因此,虽然朱熹所运用的居敬涵养工夫亦包含了静坐等偏向于静的内容,但与释、道二教或陆氏心学提倡的枯木死灰、块然独坐的主静工夫仍有着显著的区别。其静坐只是为了收敛身心,养得心地湛然虚明,则邪思妄念自然不作,随事而应皆得其当,而非为了于静中发明本心,求得顿悟,亦非遗弃事物而一味求静。故曰:
如静也不是闭门独坐,块然自守,事物来都不应。若事物来,亦须应,既应了,此心便又静。心既静,虚明洞彻,无一豪之累,便从这里应将去,应得便彻,便不难,便是“安而后能虑”。②
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及其有事,则随事而应;事已,则复湛然矣。③
人也有静坐无思念底时节,也有思量道理底时节,岂可画为两涂,说静坐时与读书时工夫迥然不同。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今人之病,正在于静坐读书时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④
对于修养工夫上的这一区别,朱门高弟陈淳亦曾做了明确的阐释与辨析,并将其视为分判正统与异端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所谓终日兀坐,与坐禅无异,而前辈又喜人静坐之说,此正异端与吾儒极相似而绝不同处,不可不讲,其所以为邪正之辨。道、佛二家,皆于坐中做工夫而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卧则精神莽董,行动则劳形揺精,故终日夜专以打坐为功,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游心于冲漠,以通仙灵而为长生计尔。佛家以睡卧则心灵颠倒,行动则心灵走失,故终日夜专以坐禅为功,只是欲空百念,绝万想,以常存其千万亿劫不死不灭底心灵神识,使不至于迷错个轮回超生路头尔。此其所主,皆未免意欲为利之私,且违阴阳之经,咈人理之常,非所谓大中至正之道也。若圣贤之所谓静坐者,盖持敬之道,所以敛容体,息思虑,收放心,涵养本原而为酬酢之地尔,固不终日役役,与事物相追逐。前辈所以喜人静坐,必叹其为善学者以此。然亦未尝终日偏靠于此,无事则静坐,事至则应接。”①以此标准衡量,故陈淳批评陆氏之学“不读书,不穷理,只终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坐禅之说,非吾儒所宜言。在初学者,未能有得,则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可须臾忘也,安得终日兀坐而无为?如理未明,识未精,徒然终日兀坐而无为,是乃槁木死灰,其将何用?”②
对于格物穷理,朱熹十分注重“即事即物”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穷理工夫不可脱离具体事物而凭空进行。譬如他说:“圣人不令人悬空穷理,须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见得道理破,便实”②,“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③。在朱熹看来,《大学》之所以不直说穷理而只言格物,亦是为了避免学者离物言理、空谈穷理。“人多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④“《大学》所以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所以只说格物。”①
根据《大学》指示的“八条目”的先后次第,朱熹明确将格物致知视作学者为学的基本工夫和实下手处。他说:
须先致知而后涵养。②
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③
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④
圣贤所言为学之序例如此,须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处把捉扶竖起来,不如今人动便说正心诚意,却打入无形影、无稽考处去也。⑤
同时,朱熹虽然承认人自身的德性、情感、思维、念虑等也在格物的范围之内,但并不主张将其作为格物的主要内容与首要对象,更反对将格物仅仅理解为格心、明心。他说:
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己,亦恐见有错处,不可执一。⑥
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于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①
人之有是身也,则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则必有是理。若仁、义、礼、智之为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为用,是则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铄我也。然圣人之所以教,不使学者收视反听,一以反求诸心为事,而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盖理虽在我,而或蔽于气禀物欲之私,则不能以自见。学虽在外,然皆所以讲乎此理之实,及其浃洽贯通而自得之,则又初无内外精粗之间也。②
总之,朱熹之所以强调格物须以具体事物为主,为学必以格物为先,都是为了确保理的客观真实性。在朱熹看来,虽然心具万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心在即物穷理之前便已先天地具备对于所有知识与道理的完整认识。事实上,若不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践履,人就无法获得各种具体的知识与道理,并将潜在的道德原则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所谓“万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③。同时,现实中的人总是不免受到气质与欲望的干扰和障蔽,其心中本具之理往往难以觉察、实现与扩充,所以必须借助对外在事物的考察、研究来发明义理,从而使义理建立在一个客观、确实的基础之上。从这一意义上看,格物致知不仅能够扩充人的知识,还能为人的道德行为指示明确的方向,提供可靠的内容。因此,朱熹要批评陆九渊“大抵其学于心地工夫不为无所见,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穷理细密功夫,卒并与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觉,而高谈大论,以为天理尽在是也,则其所谓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①
关于格物致知的具体手段与途径,朱熹说道:
穷理格物,如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②
如读书而求其义,处事而求其当,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③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④由此可见,朱熹所主张的格物手段还是较为丰富的,由内到外,由静至动,从主观到客观,几乎都已囊括在内。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理学学术范式的影响,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实际上仍以读书为基本内容。就读书而言,朱熹可谓宋明理学家中最为重视读书价值的学者之一,并且为此建立起一整套的读书方法。其读书法以虚心平气、平实周密、循序渐进为最大特色,反对好高骛远、穿凿附会、空谈义理,完全可以实学之名当之。譬如他说:
读书大抵只就事上理会,看他语意如何,不必过为深昧之说,却失圣贤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于支离怪僻之域,所害不细矣。切宜戒之,只就平易慤实处理会也。⑤
圣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闲看过。直须是置心平淡慤实之地,玩味探索而虚恬省事以养之,迟久不懈,当自觉其益;切不可以轻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虚度光阴也。①
大概如此看,更须从浅近平易处理会、应用切身处体察,渐次接续,勿令间断,久之自然意味浃洽,伦类贯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厌常喜新,专拣一等难理会、无形影底言语暗中想象,杜撰穿凿,枉用心神,空费日力。②
奉劝诸公,且子细读书。书不曾读,不见义理,乘虚接渺,指摘一二句来问人,又有涨开其说来问,又有牵甲证乙来问,皆是不曾有志朴实头读书。若是有志朴实头读书,真个逐些理会将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己无益,只是一场闲说话尔,济得甚事?且如读此一般书,只就此一般书上穷究,册子外一个字且莫兜揽来炒。将来理明,却将已晓得者去解得未晓者。如今学者将未能解说者却去参解说不得者,鹘突好笑。③
据此,朱熹自然要批评陆九渊一派为学“不肯随人后,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烦如此逐些理会,须要立个高论笼罩将去。譬如读书,不肯从上至下逐字读去,只要从东至西一抹横说。乍看虽似新巧,压得人过,然横拗粗疏,不成义理,全然不是圣贤当来本说之意,则于己分究竟成得何事?”④又谓:“近世有人为学,专要说空说妙,不肯就实,却说是悟。此是不知学,学问无此法。才说一‘悟’字,便不可穷诘,不可研究,不可与论是非,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①显然,在朱熹眼中,其与陆氏之学的差别就是实学与虚谈的差别。
朱熹虽然十分重视读书的作用与价值,但并未排斥或否定其他更为直接的格物方法。当有学生问及“明明德之功,是否以读书为要”时,朱熹既肯定“固是要读书”,又补充道:“然书上有底,便可就书理会;若书上无底,便着就事上理会;若古时无底,便着就而今理会”,②显示出一种通达、实际的为学态度。事实上,在格物致知这项庞大的事业中,朱熹始终都未停止使用观察、实验、实测等手段来认识、研究各种事物的知识、性质与规律。譬如,为了研究、验证《周礼》所载“土圭测土深”之法,朱熹曾请弟子林择之以“竹尺一枚,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示及”③。为了考证《仪礼》所载士庙之制,朱熹认为光凭纸面上的考据和想象并不足够,还须还原现场,实地模拟以验其实。他在给黄榦的信中说道:“所论士庙之制……堂上前为三间、后为二间者,似有证据。但假设尺寸大小,无以见其深广之实,须稍展样,以四五尺以上为一架,方可分画许多地头、安顿许多物色。而中间更容升降、坐立、拜起之处,净扫一片空地,以灰画定,而实周旋俯仰于其间,庶几见得通与不通,有端的之验耳。”④又如,朱熹十分重视天象的观测,对于各种天文仪器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家中不仅拥有一台浑仪⑤,可用来观测天象,而且还试图制作一台浑象以供天文研究之用。在给蔡渊的一封信中,朱熹曾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计划制作浑象的原因与方法:“《天经》之说,今日所论乃中其病,然亦未尽。彼论之失,正坐以天形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间随人所望固有少不同处,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弹圆之下以望之,南极虽高,而北极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极,决不至反入地下而移过南方也。(但入弹圆下者自不看见耳。)盖图虽古所创,然终不似天体,孰若一大圆象,钻穴为星,而虚其当隐之规,以为瓮口,乃设短轴于北极之外,以缀而运之,又设短柱于南极之北,以承瓮口,遂自瓮口设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为地平,使可仰窥而不失浑体耶?”①此后,朱熹在与蔡渊的信中又提及制作浑象之事,曰:“浑象之说,古人已虑及此,但不说如何运转。今当作一小者,粗见其形制,但难得车匠耳”②,可见其用心之深,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在致知与力行的关系上,朱熹从认识论的角度始终坚持知先行后的观点③,强调“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未能识得,涵养个甚”,④但他亦没有因此而忽视“行”的作用,而是从工夫论的角度主张知行相须,知行互发,不可偏废。譬如他说: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⑤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⑥又说: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①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②
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谨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③
由此可见,朱熹认为致知与力行作为两项基本的为学工夫,在学者为学的整个动态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虽说知先于行,但在事实上,不可能要求某人先达到物格知至的境界再去专意践行。因为“知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便穷毕生之功也未必能够实现,若一定要等到致知完成、知无不尽之后才去力行,势必导致力行流于空谈,或成为人们逃避力行的借口。同时,知有深浅,行有大小,真知的实现也有赖于行的推动,人往往需要通过实行来检验、加深对既有知识的认识。因此,人在略知所当然之后便当去行,在行中不断完善知,反过来又不断促进行,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与共同进步。“故《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履践而直从事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但以为必知之至,然后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尽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俟其至而后行哉?”①
但是,若硬要在知与行中分出一个先后轻重来,那么朱熹的答案亦是十分明确的,即“知为先,行为重”。②因为从儒者为学的逻辑次序与追求的终极目标来看,格物致知只是为学的起点,是于事事物物皆知其所以然与所当然,此后还须力行所知,修养德性,经世济民,由内圣推出外王,最终实现治平天下、成圣成贤的伟大目标。所谓“见无虚实,行有虚实。见只是见,见了后却有行,有不行”③,说明是否能够将所知所见付诸实行亦是衡量、判断学术虚实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此意义上,朱熹亦对行的价值作了极大的肯定与张扬: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④既涵养,又须致知;既致知,又须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与不知同。①
既知得,若不真实去做,那个道理也只悬空在这里,无个安泊处。②
为学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觉有窒碍,方好商量。今未尝举足而坐谈远想,非惟无益,窃恐徒长浮薄之气,非所以变化旧习而趋于诚实也。③
据此,朱熹批评当时学者多将进学致知与力行践履割裂开来,各主一偏,或知之不行,或行而不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固,与彼区区口耳之间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④。而之所以会出现“知之不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之不深、知之未至造成的。因为在朱熹看来,凡真知者必能循理而行,高度的道德意识必将产生自觉的道德行为,故“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⑤,不可能存在真知而不行的现象。既然真知必能行,那么反过来看,是否能够实行也就成为检验、判断知之深浅的一个重要标准。故曰:“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于己,岂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⑥,“人于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尽耳”⑦,“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⑧。此外,为了提倡躬行践履,力矫空谈之弊,朱熹还发挥了《尚书》“知易行难”的思想,指出践行义理要比谈论、讲说义理困难得多。他说:“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①又说:“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敱无能底人矣。恐不然也”②,“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③。显然,以上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朱熹所主张的“行重于知”的原因与根据。
主敬涵养作为一项基本的为学、修养工夫与“行”的重要内容,亦与格物致知保持着互发并进的关系。钱穆曾将朱熹所说的“主敬”的具体含义归纳为畏、收敛其心不容一物、随事专一(即主一)、随事点检、常惺惺、整齐严肃等六个主要方面。④其中既包含了未发主敬,也包含了已发主敬。在朱熹看来,“主敬”与“主静”有所不同。一方面,敬是静的前提,静是敬的表现,故曰:“敬则虚静,不可把虚静唤作敬”⑤,“敬则自然静,不可将静来唤做敬”⑥;另一方面,主敬贯穿动静、内外、始终,作用于从格物致知到治平天下的每一个环节中,并不仅限于未发涵养或主静工夫,故曰:“‘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⑦,“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⑧,“但看圣贤说‘行笃敬’‘执事敬’,则敬字本不为默然无为时设,须向难处力加持守,庶几动静如一耳”①。
因此,虽然朱熹所运用的居敬涵养工夫亦包含了静坐等偏向于静的内容,但与释、道二教或陆氏心学提倡的枯木死灰、块然独坐的主静工夫仍有着显著的区别。其静坐只是为了收敛身心,养得心地湛然虚明,则邪思妄念自然不作,随事而应皆得其当,而非为了于静中发明本心,求得顿悟,亦非遗弃事物而一味求静。故曰:
如静也不是闭门独坐,块然自守,事物来都不应。若事物来,亦须应,既应了,此心便又静。心既静,虚明洞彻,无一豪之累,便从这里应将去,应得便彻,便不难,便是“安而后能虑”。②
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及其有事,则随事而应;事已,则复湛然矣。③
人也有静坐无思念底时节,也有思量道理底时节,岂可画为两涂,说静坐时与读书时工夫迥然不同。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今人之病,正在于静坐读书时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④
对于修养工夫上的这一区别,朱门高弟陈淳亦曾做了明确的阐释与辨析,并将其视为分判正统与异端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所谓终日兀坐,与坐禅无异,而前辈又喜人静坐之说,此正异端与吾儒极相似而绝不同处,不可不讲,其所以为邪正之辨。道、佛二家,皆于坐中做工夫而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卧则精神莽董,行动则劳形揺精,故终日夜专以打坐为功,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游心于冲漠,以通仙灵而为长生计尔。佛家以睡卧则心灵颠倒,行动则心灵走失,故终日夜专以坐禅为功,只是欲空百念,绝万想,以常存其千万亿劫不死不灭底心灵神识,使不至于迷错个轮回超生路头尔。此其所主,皆未免意欲为利之私,且违阴阳之经,咈人理之常,非所谓大中至正之道也。若圣贤之所谓静坐者,盖持敬之道,所以敛容体,息思虑,收放心,涵养本原而为酬酢之地尔,固不终日役役,与事物相追逐。前辈所以喜人静坐,必叹其为善学者以此。然亦未尝终日偏靠于此,无事则静坐,事至则应接。”①以此标准衡量,故陈淳批评陆氏之学“不读书,不穷理,只终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坐禅之说,非吾儒所宜言。在初学者,未能有得,则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可须臾忘也,安得终日兀坐而无为?如理未明,识未精,徒然终日兀坐而无为,是乃槁木死灰,其将何用?”②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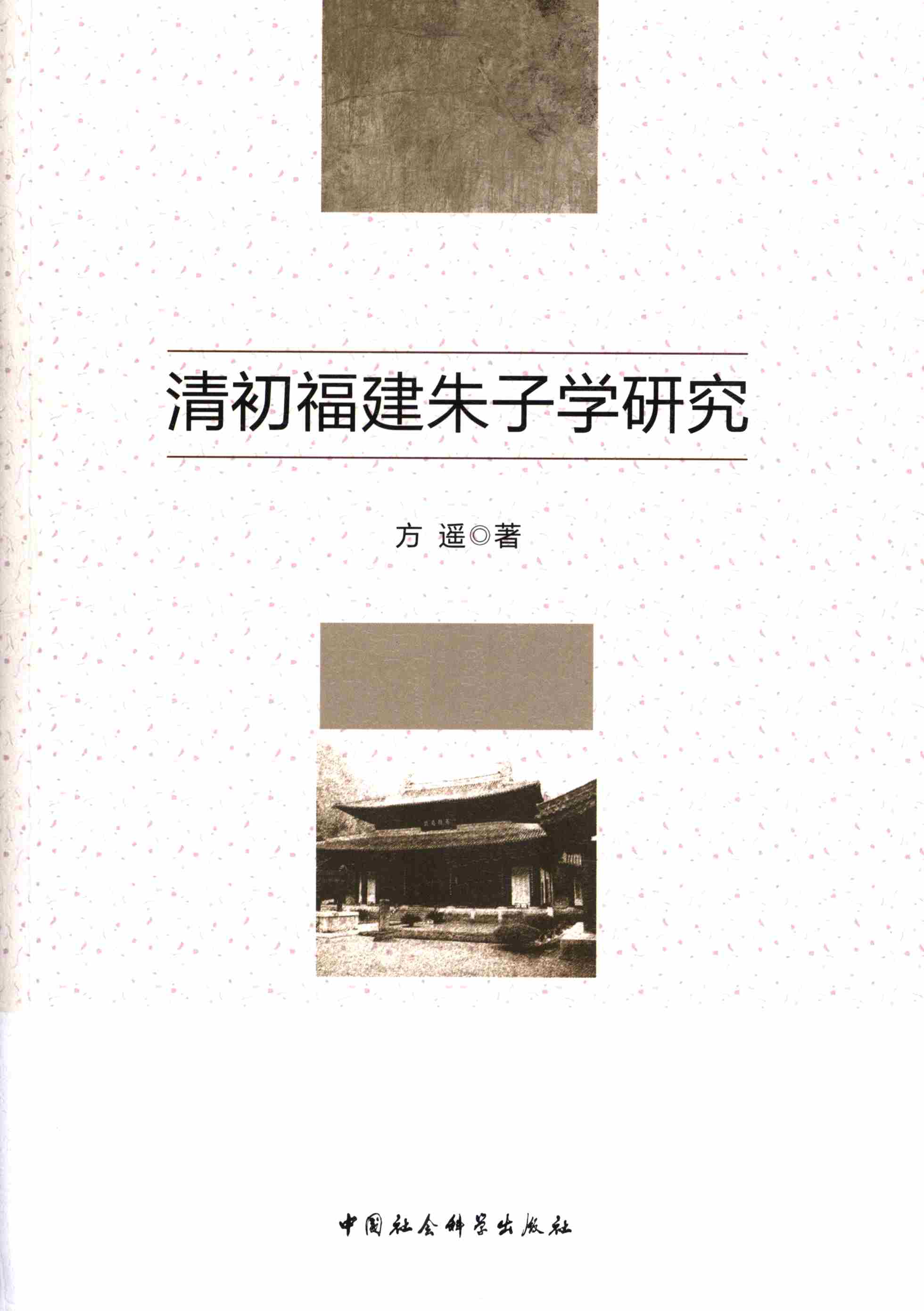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