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朱子学的研究对象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97 |
| 颗粒名称: | 二 朱子学的研究对象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7 |
| 页码: | 524-540 |
| 摘要: | 本文主要介绍了朱熹对儒家实学的理解和对道、理、人性的解析。朱熹认为儒家是实在的学说,强调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因此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儒家学习的对象。他对经典的研究也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训诂考据,而是强调要理解其中的道理,并将其运用于实践中。朱熹将道理理解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强调理与人伦日常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理是真实不欺的,是最真实和实在的存在。另外,朱熹还解析了理与人性的关系,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人性是实有的,不是空洞的。朱熹的实学思想强调重实用、重实体,将理用于实践之中。 |
| 关键词: | 清初 朱子学 草木 |
内容
朱熹认为,有物必有则,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所以从理论上说,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朱子学的研究对象。譬如他说: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③
一身之中是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与夫耳目手足视听言动,皆所当理会。至若万物之荣悴与夫动植小大,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皆所当理会。④
虽一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①
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如所谓“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自家知得这个道理,处之而各得其当便是。且如鸟兽之情,莫不好生而恶杀,自家知得是恁地,便须“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远,由粗以至精。②又说:
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这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须是“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圣人虽是生知,然也事事理会过,无一之不讲。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件上理会去。凡事虽未理会得详密,亦有个大要处,纵详密处未晓得,而大要处已被自家见了。①
由此可见,朱熹所理解的研究对象是十分广泛而实际的,从自然事物、历史规律,到人类的活动事为、典章制度,再到个体的思维念虑、道德本性,无论精粗、远近、大小、贵贱,通通包括在内。即便是圣人,也必须经过广博的学习,事事都要理会。而研究的次序,则须从粗处、浅处、近处、分明处入手,由粗以至精,由近以及远,以免好高骛远,遗漏了实际事物。同时,朱熹指出:“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③。因此,学者不仅需要把握事物中蕴含的道德原则,还需要广泛地学习、研究有关各类事物的性质、规律、原理的具体知识,才算是真正的穷理。
譬如,朱熹对于经史之书中记载的名物度数、典章制度、历史事变、治乱兴亡之道等皆十分留意,主张通经致用、史学经世。他说:“且如读《尧舜典》‘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礼五玉’之类,《禹贡》山川、《洪范》九畴,须一一理会令透。又如《礼书》冠、昏、丧、祭、王朝、邦国许多制度,逐一讲究。”④又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⑤,“三代以下书,古今世变治乱存亡,皆当理会”⑥。在朱熹看来,掌握这些知识正是一位儒者的分内之事,亦是成圣成贤的必要条件。若非如此,则何以承担治平天下的重任?故曰:“若论为学,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艺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其与玩意于空言,以校工拙于篇牍之间者,其损益相万万矣。”①
尽管从总体上看,朱熹对于道德规范与政治、社会、历史领域的知识更为重视,但他并未因此而忽略、排斥有关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的客观知识。甚至可以说,朱熹对于自然事物与科学技术的关注和兴趣在宋明理学家中是少有人及的。我们在朱熹的文集、语录甚至经史著作中,都可以发现其对天文、历象、地理、地质、气象、气候、生物、医药等知识与学问的思考、研究和讨论。
(一)天文、历象
在天文、历象方面,朱熹主要以阴阳二气的运动来解释天地、日月、星辰的生成原因。他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查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②换言之,阴阳二气的旋转运动,相互摩擦碰撞,产生了最初的物质颗粒,混杂在气中间。又由于气的运动,气之轻清者逐渐跑到外层,形成不断旋转运行的天与日月星辰,重浊者则聚在中央,结成不动的大地。据此,朱熹认为地不在天之下,而在天之中。“地却是有空阙处。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阙,逼塞满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气无不通。恁地看来,浑只是天了。”③而地之所以能够凝聚、保持在天的中央而不散不坠,正是由于天极速运转的力量。“天运不息,昼夜辊转,故地榷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查滓在中间。”④若以比喻言之,“天地之形,如人以两碗相合,贮水于内。以手常常掉开,则水在内不出;稍住手,则水漏矣”①。
关于宇宙的结构,朱熹不仅修正了传统的浑天说,认为天圆如弹丸,地悬于天之气中,而非浮于水上,所谓“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故地榷在中间,隤然不动”②,而且对“九天”之说进行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九天”并不是指九个天,亦非九方之天,而是指天有九个层次,且每层都因天的运转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特点。“《离骚》有九天之说,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据某观之,只是九重。盖天运行有许多重数。里面重教较软,至外面则渐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壳相似,那里转得又愈紧矣。”③
关于天体运行,朱熹赞同张载之说,认为“天道与日月五星皆是左旋”④。他进一步指出,传统历家之所以多主张日月右旋,是由于天与日月的旋转运行速度不同,若以运行最快的天为标准,则运行较慢的日月便仿佛逆行右旋。“天最健,一日一周而过一度。日之健次于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缓,比天为退十三度有奇。但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说,其实非右行也。横渠曰:‘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矣。’此说最好。”⑤朱熹又根据古今“地中”位置的不同,推测地亦处于运动之中,会随天而转。“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⑥此外,朱熹既以北极为天之枢轴,居中不动,众星环绕其旋转,又补充道:“北辰无星,缘是人要取此为极,不可无个记认,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谓之极星。……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如那射糖盘子样,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极星便是近椿底点子,虽也随那盘子转,却近那椿子,转得不觉。”①
关于天象,朱熹认为“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②,月球本身并不发光,只是反射它所受到的日光。同时,月本身亦无圆缺盈亏,只是由于其受日光照射的部分不同,才使地上的人们产生月有圆缺盈亏的感觉。故曰:“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边明,人在这边望,只见在弦光。十五六则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边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③又说:“日月相会时,日在月上,不是无光,光都载在上面一边,故地上无光。到得日月渐渐相远时,渐擦挫,月光渐渐见于下。到得望时,月光浑在下面一边。望后又渐渐光向上去。”④对于月中黑影,朱熹认为是日光被地遮蔽而产生的阴影。“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伴更无亏欠;唯中心有少黡翳处,是地有影蔽者尔。”⑤“如镜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见也。盖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间地是一块实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晕也。”⑥对于日食,朱熹认为是由于日月相合时,日光被月遮蔽所致,故日食只发生在朔日。“日食是为月所掩”⑦,“日所以蚀于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会,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蚀”⑧。但朔日并不必然发生日食,这是因为“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者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①。对于月食,朱熹的态度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认为日为阳,月为阴,故“月食是与日争敌”②,“月蚀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谓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盖阴盛亢阳,而不少让阳故也”③。另一方面,朱熹又以日月相掩来解释月食的成因,认为“日月薄蚀,只是二者交会处,二者紧合,所以其光淹没,在朔则为日食,在望则为月食。……如自东而西,渐次相近,或日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蚀。唯月行日外而掩日于内,则为日蚀;日行月外而掩月于内,则为月蚀。所蚀分数,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④。此外,朱熹还假设日光被地遮蔽而形成了一块暗处,即“暗虚”,当望日月球经过暗虚时,因照射不到日光便出现月食。故曰:“望时月蚀,固是阴敢与阳敌,然历家又谓之暗虚。盖火日外影,其中实暗,到望时恰当着其中暗处,故月蚀”⑤,“至明中有暗处,其暗至微。望之时,月与之正对,无分豪相差,月为暗处所射,故蚀”⑥。不论如何,在朱熹看来,日食与月食都是可以预测的自然现象,而非灾异。
(二)气候、气象
在气候、气象方面,朱熹往往以阴阳之气的运动来解释四季气候的变化与各种天气现象。譬如他说:“天地间只是一个气,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气周匝。把来折做两截时,前面底便是阳,后面底便是阴。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时。天地间只有六层,阳气到地面上时,地下便冷了。只是这六位,阳长到那第六位时极了,无去处,上面只是渐次消了。上面消了些个时,下面便生了些个,那便是阴。”①又说:“看来天地中间,此气升降上下,当分为六层。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层生起,直到第六层,上极至天,是为四月。阳气既生足,便消,下面阴气便生。只是这一气升降,循环不已,往来乎六层之中也。”②同时,天的运转速度的变化所造成的气的变化亦会影响四季的气候。“想得春夏间天转稍慢,故气候缓散昏昏然,而南方为尤甚。至秋冬,则天转益急,故气候清明,宇宙澄旷。所以说天高气清,以其转急而气紧也。”③
关于局部地区的气候,朱熹认为既受到当地地形的影响,又与阴阳之气的盛衰有关。他说:“闽中之山多自北来,水皆东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来,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热。”④又说:“如海边诸郡风极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东风,夏必南风,不如此间之无定。盖土地旷阔,无高山之限,故风各以方至。……如西北边多阴,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阳气到彼处衰谢。盖日到彼方午,则彼已甚晚,不久则落,故西边不甚见日。”⑤
关于云、雨、雷、电、风、霾等现象的产生,朱熹多采张载之说,以阴阳二气的运动加以解释。他说:“横渠云:‘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阳气正升,忽遇阴气,则相持而下为雨。盖阳气轻,阴气重,故阳气为阴气压坠而下也。‘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阴气正升,忽遇阳气,则助之飞腾而上为云也。‘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气伏于阴气之内不得出,故爆开而为雷也。‘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阴气凝结于内,阳气欲入不得,故旋绕其外不已而为风,至吹散阴气尽乃已也。‘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噎霾。’戾气,飞雹之类;曀霾,黄雾之类,皆阴阳邪恶不正之气,所以雹水秽浊,或青黑色。”①但是,朱熹又对张载的一些观点做了补充与修正。譬如,朱熹认为天之气的旋转也会形成风,并说:“风随阳气生,日方升则阳气生,至午则阳气盛,午后则阳气微,故风亦随而盛衰。”②又如,关于雨的成因,朱熹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凡雨者,皆是阴气盛,凝结得密,方湿润下降为雨。且如饭甑,盖得密了,气郁不通,四畔方有温汗。”③显然,朱熹的这些说法更为接近实情。关于霜与雪的成因,朱熹则说:“霜只是露结成,雪只是雨结成。古人说露是星月之气,不然。今高山顶上虽晴亦无露。露只是自下蒸上。”④至于高山上无霜露,却有雪的原因,朱熹解释道:“上面气渐清,风渐紧,虽微有雾气,都吹散了,所以不结。若雪,则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处雪先结也。”⑤此外,朱熹还对露与霜、雪与霜、雨与露、雾与露之间的区别做了细致的分析。“露与霜之气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杀物也。又雪霜亦有异:霜则杀物,雪不能杀物也。雨与露亦不同:雨气昏,露气清。气蒸而为雨,如饭甑盖之,其气蒸郁而汗下淋漓;气蒸而为雾,如饭甑不盖,其气散而不收。雾与露亦微有异,露气肃,而雾气昏也。”⑥
关于虹的现象,朱熹有时以阴阳之气相交解释,谓:“蝃蝀,虹也。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⑦;有时又以日照之影解释,谓:“蝃蝀本只是薄雨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气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气了”①。关于潮汐的现象,朱熹注意到其与月球位置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阴阳之气的更替加以解释。他说:“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时,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②,“大抵天地之间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故子午卯酉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进退以月至此位为节耳。以气之消息言之,则子者阴之极而阳之始,午者阳之极而阴之始,卯为阳中,酉为阴中也”③。关于庐山的“佛灯”现象,朱熹推测“此是气盛而有光,又恐是宝气,又恐是腐叶飞虫之光”④。关于峨眉山的“佛光”现象,朱熹认为“今所在有石,号‘菩萨石’者,如水精状,于日中照之,便有圆光。想是彼处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见其影圆,而映人影如佛影耳”⑤。关于“大雪兆丰年”之说,朱熹认为“雪非丰年,盖为凝结得阳气在地,来年发达生长万物”⑥。此外,朱熹对于一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亦观察入微。譬如,朱熹不仅注意到雪花皆呈六角形的有趣现象,而且将其与玄精石的六棱联系起来,以“数”的思想加以解释。他说:“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灒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⑦
(三)地理
在地理方面,朱熹指出山与水往往并行,因而可以通过江河来判断山脉的分支与走向。“大凡两山夹行,中间必有水;两水夹行,中间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夹江两岸而行,那边一支去为陇,这边一支为湖南。又一支为建康,又一支为两浙,而余气为福建、二广。”①关于山与水的关系,朱熹又提出“水随山行”的观点,认为“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间底水在脊上行”,又说:“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脉。”②关于中国的整体地形,朱熹说道:“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③关于地理位置与环境对建都的影响,朱熹既肯定“河东地形极好,乃尧、舜、禹故都……左右多山,黄河绕之,嵩、华列其前”,又指出平阳、蒲坂“其地硗瘠不生物,人民朴陋俭啬,故惟尧、舜能都之。后世侈泰,如何都得”。④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朱熹曾说:“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来便要硬做”⑤,又说:“某观诸处习俗不同,见得山川之气甚牢。且如建州七县,县县人物各自是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长短小大清浊皆不同,都改变不得,岂不是山川之气甚牢?”⑥关于地图的制作要领,朱熹提出“要作地理图三个样子:一写州名,一写县名,一写山川名。仍作图时,须用逐州正邪、长短、阔狭如其地厚,糊纸叶子以剪”⑦。他还主张讨论地理须首重大形势,再由大及小,故批评薛常州的《九域图》“其书细碎,不是著书手段”⑧。在朱熹看来,“‘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圣人做事便有大纲领,先决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爬疏小水,令至川。学者亦先识个大形势,如江、河、淮先合识得,渭水入河,上面漆、沮、泾等又入渭,皆是第二重事”。①
同时,朱熹对于《禹贡》所载地理亦做了部分的考据与辨正,客观地指出了其中不少难以理解或与现实不合之处。譬如他说:“《禹贡》济水,今皆变尽了。又江水无沲,又不至澧。九江亦无寻处,后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数千里不说一句,及到江州,数千里间连说数处,此皆不可晓者。”②又说:“《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目见者,皆有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③由于朱熹曾知南康军,故能亲履九江、彭蠡、庐山等地考察,目睹其山川形势之实,复与《禹贡》之文相核,发现殊不相应,遂作《九江彭蠡辨》以辨《禹贡》之非。《禹贡》所载乃九州之山川,如今仅荆扬一地可见之谬误已如此,朱熹更有理由怀疑“耳目见闻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当几何”④。据此,加之古今地理的变迁,朱熹认为若仅就地理本身而言,《禹贡》并不值得学者特别重视与信赖。“《禹贡》地理,不须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如今地理。”⑤他进一步指出,后世学者在注解《禹贡》的过程中,多是一味迷信经典与书本,非但不能考辨、订正其中的错误,反而牵强附会,曲为解说,文过饰非,遂使其学错上加错。所以他批评“古今读者皆以为是既出于圣人之手,则固不容复有讹谬,万世之下,但当尊信诵习,传之无穷,亦无以核其事实是否为也。是以为之说者,不过随文解义,以就章句”⑥,又谓学者所论地理“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历,故其说亦难尽据,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著明耳”①。由此可见朱熹在地理研究上注重客观实际与实地考察的科学精神。
(四)地质
在地质方面,朱熹被认为是最早认识化石的学者之一,并且能够初步以地质变迁的观点来解释化石的生成。他说:“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②又说:“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③关于山脉与大地的最初形成,朱熹认为是由于浑浊的水的沉积作用,因而存在一个由软到硬的变化过程。“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④此外,朱熹还注意到流水对山的侵蚀作用,提出“山上之土为水漂流下来,山便瘦,泽便高”⑤。
(五)生物
在生物方面,朱熹对于各种动植物的性状、特点亦多有留意。譬如,朱熹认为不同植物的花期长短与季节之令有关。他说:“冬间花难谢。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蜡梅,皆然。至春花则易谢。若夏间花,则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开得一日。必竟冬时其气贞固,故难得谢。若春夏间,才发便发尽了,故不能久。”⑥关于兰、蕙、荼、堇等植物的区别与联系,朱熹考证道:“《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说兰、蕙殊不分明。盖古人所说似泽兰者,非今之兰,(泽兰此中有之,尖叶方茎紫节,正如洪庆善说。若兰草似此,则决非今之兰矣。)自刘次庄以下所说,乃今之兰而非古之兰也。……又所谓蕙,以兰推之,则古之蕙恐当如陈藏器说乃是。若山谷说,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荼,恐是蓼属,(见《诗》疏《载芟》篇。)故诗人与堇并称。堇乃乌头,非先苦而后甘也。又云荼毒,盖荼有毒,今人用以药溪取鱼,堇是其类,则宜亦有毒而不得为苦苣矣。”①关于松柏不凋的现象,朱熹认为“松柏非是叶不凋,但旧叶凋时新叶已生。木犀亦然”②。关于《诗经》所说的“关雎”,朱熹说道:“古说关雎为王雎,挚而有别,居水中,善捕鱼。说得来可畏,当是鹰鹘之类,做得勇武气象,恐后妃不然。某见人说,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虽两两相随,然相离每远,此说却与《列女传》所引义合。”③又说:“王鸠,尝见淮上人说,淮上有之,状如此间之鸠,差小而长,常是雌雄二个不相失。虽然二个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处,须是隔丈来地,所谓‘挚而有别’也。‘人未尝见其匹居而乘处’,乘处,谓四个同处也。只是二个相随,既不失其偶,又未尝近而相狎,所以为贵也。”④关于蚁封,朱熹解释道:“蚁垤也,北方谓之‘蚁楼’,如小山子,乃蚁穴地,其泥坟起如丘垤,中间屈曲如小巷道。古语云‘乘马折旋于蚁封之间’,言蚁封之间巷路屈曲狭小,而能乘马折旋于其间,不失其驰骤之节,所以为难也。‘鹳鸣于垤’,垤即蚁封也。天阴雨下则蚁出,故鹳鸣于垤,以俟蚁之出而啄食之也。”⑤
(六)医药
在医药方面,关于药物之理,朱熹说道:“今医者定魄药多用虎睛,助魂药多用龙骨。魄属金,金西方,主肺与魄。虎是阴属之最强者,故其魄最盛。魂属木,木东方,主肝与魂。龙是阳属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强。龙能驾云飞腾,便是与气合。虎啸则风生,便是与魄合。”①关于诊脉之法,朱熹认为《难经》首篇所载“寸关尺之法为最要”,而以丁德用的密排三指之法为未备。他说:“夫《难经》则至矣,至于德用之法,则予窃意诊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长短,以是相求,或未得为定论也。盖尝细考经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关而前却,以距乎鱼际尺泽,是则所谓关者必有一定之处,亦若鱼际尺泽之可以外见而先识也。然今诸书皆无的然之论,唯《千金》以为寸口之处,其骨自高,而关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则其言之先后、位之进退,若与经文不合。独俗间所传《脉诀》五七言韵语者,词最鄙浅,非叔和本书明甚,乃能直指高骨为关,而分其前后,以为寸尺阴阳之位,似得《难经》本指。”②此外,朱熹还曾请李伯谏“烦为寻访庞安常《难经说》,及闻别有论医文字颇多,得并为访问,传得一本示及为幸”③,可见其对医药之学的关注。
诚然,朱熹关于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的这些说法与解释,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或许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的认识与标准,不仅仍带有较强的哲学思辨色彩,而且多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直接推理,还显得较为直观与粗糙,但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与科技条件下,这几乎已是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作为一位影响巨大的理学家,朱熹始终对于各种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且试图以自然的、物质性的原理对其加以解释,还能够利用观察、实验、实测等手段,亲自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充分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崭新的、具有前瞻性与启发性的创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亦对我国日后的科技研究和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与示范效应。
朱熹之所以如此重视包括社会、历史、自然等各方面知识与规律的学习和研究,并能取得如此多的成绩,除了个人兴趣与性格方面的因素外,主要还是由于其“理一分殊”的基本思想,使得这方面的内容成为其建构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朱熹的理解,一方面,若就统一的、作为万事万物根本依据的天理而言,万事万物皆禀受此理以为性,彼此之间并无分别。“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①,“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②。从这一意义上说,“物理即道理,天下初无二理”③,“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④,“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⑤。因此,万物之理可相互推知而无不通,研究、发明客观事物中蕴含的理,有利于更准确把握人心中的理。另一方面,若就分殊的、作为具体事物特定规律的物理而言,则不同事物的理又是相互区别的,是统一的普遍规律的不同部分与不同表现。因此,学者必须广泛、具体地研究各种事物中分殊的物理,并加以积累、融汇和贯通,才有可能最终把握完整的天理。故曰:“这事自有这个道理,那事自有那个道理。各理会得透,则万事各成万个道理。四面凑合来,便只是一个浑沦道理”⑥,“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百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只是空想象”①。因此,虽然朱熹亦承认价值优先的原则,并不以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或知识的学习作为最终目的,但其理学思想体系内实际上已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与要求,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道问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使得朱子学呈现出明显的理性色彩与知识取向,并且能够为各种专门知识与学问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合法性依据。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③
一身之中是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与夫耳目手足视听言动,皆所当理会。至若万物之荣悴与夫动植小大,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皆所当理会。④
虽一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①
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如所谓“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自家知得这个道理,处之而各得其当便是。且如鸟兽之情,莫不好生而恶杀,自家知得是恁地,便须“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远,由粗以至精。②又说:
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这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须是“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圣人虽是生知,然也事事理会过,无一之不讲。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件上理会去。凡事虽未理会得详密,亦有个大要处,纵详密处未晓得,而大要处已被自家见了。①
由此可见,朱熹所理解的研究对象是十分广泛而实际的,从自然事物、历史规律,到人类的活动事为、典章制度,再到个体的思维念虑、道德本性,无论精粗、远近、大小、贵贱,通通包括在内。即便是圣人,也必须经过广博的学习,事事都要理会。而研究的次序,则须从粗处、浅处、近处、分明处入手,由粗以至精,由近以及远,以免好高骛远,遗漏了实际事物。同时,朱熹指出:“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③。因此,学者不仅需要把握事物中蕴含的道德原则,还需要广泛地学习、研究有关各类事物的性质、规律、原理的具体知识,才算是真正的穷理。
譬如,朱熹对于经史之书中记载的名物度数、典章制度、历史事变、治乱兴亡之道等皆十分留意,主张通经致用、史学经世。他说:“且如读《尧舜典》‘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礼五玉’之类,《禹贡》山川、《洪范》九畴,须一一理会令透。又如《礼书》冠、昏、丧、祭、王朝、邦国许多制度,逐一讲究。”④又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⑤,“三代以下书,古今世变治乱存亡,皆当理会”⑥。在朱熹看来,掌握这些知识正是一位儒者的分内之事,亦是成圣成贤的必要条件。若非如此,则何以承担治平天下的重任?故曰:“若论为学,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艺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其与玩意于空言,以校工拙于篇牍之间者,其损益相万万矣。”①
尽管从总体上看,朱熹对于道德规范与政治、社会、历史领域的知识更为重视,但他并未因此而忽略、排斥有关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的客观知识。甚至可以说,朱熹对于自然事物与科学技术的关注和兴趣在宋明理学家中是少有人及的。我们在朱熹的文集、语录甚至经史著作中,都可以发现其对天文、历象、地理、地质、气象、气候、生物、医药等知识与学问的思考、研究和讨论。
(一)天文、历象
在天文、历象方面,朱熹主要以阴阳二气的运动来解释天地、日月、星辰的生成原因。他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查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②换言之,阴阳二气的旋转运动,相互摩擦碰撞,产生了最初的物质颗粒,混杂在气中间。又由于气的运动,气之轻清者逐渐跑到外层,形成不断旋转运行的天与日月星辰,重浊者则聚在中央,结成不动的大地。据此,朱熹认为地不在天之下,而在天之中。“地却是有空阙处。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阙,逼塞满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气无不通。恁地看来,浑只是天了。”③而地之所以能够凝聚、保持在天的中央而不散不坠,正是由于天极速运转的力量。“天运不息,昼夜辊转,故地榷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查滓在中间。”④若以比喻言之,“天地之形,如人以两碗相合,贮水于内。以手常常掉开,则水在内不出;稍住手,则水漏矣”①。
关于宇宙的结构,朱熹不仅修正了传统的浑天说,认为天圆如弹丸,地悬于天之气中,而非浮于水上,所谓“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故地榷在中间,隤然不动”②,而且对“九天”之说进行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九天”并不是指九个天,亦非九方之天,而是指天有九个层次,且每层都因天的运转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特点。“《离骚》有九天之说,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据某观之,只是九重。盖天运行有许多重数。里面重教较软,至外面则渐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壳相似,那里转得又愈紧矣。”③
关于天体运行,朱熹赞同张载之说,认为“天道与日月五星皆是左旋”④。他进一步指出,传统历家之所以多主张日月右旋,是由于天与日月的旋转运行速度不同,若以运行最快的天为标准,则运行较慢的日月便仿佛逆行右旋。“天最健,一日一周而过一度。日之健次于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缓,比天为退十三度有奇。但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说,其实非右行也。横渠曰:‘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矣。’此说最好。”⑤朱熹又根据古今“地中”位置的不同,推测地亦处于运动之中,会随天而转。“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⑥此外,朱熹既以北极为天之枢轴,居中不动,众星环绕其旋转,又补充道:“北辰无星,缘是人要取此为极,不可无个记认,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谓之极星。……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如那射糖盘子样,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极星便是近椿底点子,虽也随那盘子转,却近那椿子,转得不觉。”①
关于天象,朱熹认为“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②,月球本身并不发光,只是反射它所受到的日光。同时,月本身亦无圆缺盈亏,只是由于其受日光照射的部分不同,才使地上的人们产生月有圆缺盈亏的感觉。故曰:“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边明,人在这边望,只见在弦光。十五六则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边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③又说:“日月相会时,日在月上,不是无光,光都载在上面一边,故地上无光。到得日月渐渐相远时,渐擦挫,月光渐渐见于下。到得望时,月光浑在下面一边。望后又渐渐光向上去。”④对于月中黑影,朱熹认为是日光被地遮蔽而产生的阴影。“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伴更无亏欠;唯中心有少黡翳处,是地有影蔽者尔。”⑤“如镜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见也。盖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间地是一块实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晕也。”⑥对于日食,朱熹认为是由于日月相合时,日光被月遮蔽所致,故日食只发生在朔日。“日食是为月所掩”⑦,“日所以蚀于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会,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蚀”⑧。但朔日并不必然发生日食,这是因为“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者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①。对于月食,朱熹的态度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认为日为阳,月为阴,故“月食是与日争敌”②,“月蚀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谓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盖阴盛亢阳,而不少让阳故也”③。另一方面,朱熹又以日月相掩来解释月食的成因,认为“日月薄蚀,只是二者交会处,二者紧合,所以其光淹没,在朔则为日食,在望则为月食。……如自东而西,渐次相近,或日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蚀。唯月行日外而掩日于内,则为日蚀;日行月外而掩月于内,则为月蚀。所蚀分数,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④。此外,朱熹还假设日光被地遮蔽而形成了一块暗处,即“暗虚”,当望日月球经过暗虚时,因照射不到日光便出现月食。故曰:“望时月蚀,固是阴敢与阳敌,然历家又谓之暗虚。盖火日外影,其中实暗,到望时恰当着其中暗处,故月蚀”⑤,“至明中有暗处,其暗至微。望之时,月与之正对,无分豪相差,月为暗处所射,故蚀”⑥。不论如何,在朱熹看来,日食与月食都是可以预测的自然现象,而非灾异。
(二)气候、气象
在气候、气象方面,朱熹往往以阴阳之气的运动来解释四季气候的变化与各种天气现象。譬如他说:“天地间只是一个气,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气周匝。把来折做两截时,前面底便是阳,后面底便是阴。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时。天地间只有六层,阳气到地面上时,地下便冷了。只是这六位,阳长到那第六位时极了,无去处,上面只是渐次消了。上面消了些个时,下面便生了些个,那便是阴。”①又说:“看来天地中间,此气升降上下,当分为六层。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层生起,直到第六层,上极至天,是为四月。阳气既生足,便消,下面阴气便生。只是这一气升降,循环不已,往来乎六层之中也。”②同时,天的运转速度的变化所造成的气的变化亦会影响四季的气候。“想得春夏间天转稍慢,故气候缓散昏昏然,而南方为尤甚。至秋冬,则天转益急,故气候清明,宇宙澄旷。所以说天高气清,以其转急而气紧也。”③
关于局部地区的气候,朱熹认为既受到当地地形的影响,又与阴阳之气的盛衰有关。他说:“闽中之山多自北来,水皆东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来,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热。”④又说:“如海边诸郡风极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东风,夏必南风,不如此间之无定。盖土地旷阔,无高山之限,故风各以方至。……如西北边多阴,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阳气到彼处衰谢。盖日到彼方午,则彼已甚晚,不久则落,故西边不甚见日。”⑤
关于云、雨、雷、电、风、霾等现象的产生,朱熹多采张载之说,以阴阳二气的运动加以解释。他说:“横渠云:‘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阳气正升,忽遇阴气,则相持而下为雨。盖阳气轻,阴气重,故阳气为阴气压坠而下也。‘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阴气正升,忽遇阳气,则助之飞腾而上为云也。‘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气伏于阴气之内不得出,故爆开而为雷也。‘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阴气凝结于内,阳气欲入不得,故旋绕其外不已而为风,至吹散阴气尽乃已也。‘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噎霾。’戾气,飞雹之类;曀霾,黄雾之类,皆阴阳邪恶不正之气,所以雹水秽浊,或青黑色。”①但是,朱熹又对张载的一些观点做了补充与修正。譬如,朱熹认为天之气的旋转也会形成风,并说:“风随阳气生,日方升则阳气生,至午则阳气盛,午后则阳气微,故风亦随而盛衰。”②又如,关于雨的成因,朱熹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凡雨者,皆是阴气盛,凝结得密,方湿润下降为雨。且如饭甑,盖得密了,气郁不通,四畔方有温汗。”③显然,朱熹的这些说法更为接近实情。关于霜与雪的成因,朱熹则说:“霜只是露结成,雪只是雨结成。古人说露是星月之气,不然。今高山顶上虽晴亦无露。露只是自下蒸上。”④至于高山上无霜露,却有雪的原因,朱熹解释道:“上面气渐清,风渐紧,虽微有雾气,都吹散了,所以不结。若雪,则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处雪先结也。”⑤此外,朱熹还对露与霜、雪与霜、雨与露、雾与露之间的区别做了细致的分析。“露与霜之气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杀物也。又雪霜亦有异:霜则杀物,雪不能杀物也。雨与露亦不同:雨气昏,露气清。气蒸而为雨,如饭甑盖之,其气蒸郁而汗下淋漓;气蒸而为雾,如饭甑不盖,其气散而不收。雾与露亦微有异,露气肃,而雾气昏也。”⑥
关于虹的现象,朱熹有时以阴阳之气相交解释,谓:“蝃蝀,虹也。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⑦;有时又以日照之影解释,谓:“蝃蝀本只是薄雨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气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气了”①。关于潮汐的现象,朱熹注意到其与月球位置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阴阳之气的更替加以解释。他说:“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时,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②,“大抵天地之间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故子午卯酉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进退以月至此位为节耳。以气之消息言之,则子者阴之极而阳之始,午者阳之极而阴之始,卯为阳中,酉为阴中也”③。关于庐山的“佛灯”现象,朱熹推测“此是气盛而有光,又恐是宝气,又恐是腐叶飞虫之光”④。关于峨眉山的“佛光”现象,朱熹认为“今所在有石,号‘菩萨石’者,如水精状,于日中照之,便有圆光。想是彼处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见其影圆,而映人影如佛影耳”⑤。关于“大雪兆丰年”之说,朱熹认为“雪非丰年,盖为凝结得阳气在地,来年发达生长万物”⑥。此外,朱熹对于一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亦观察入微。譬如,朱熹不仅注意到雪花皆呈六角形的有趣现象,而且将其与玄精石的六棱联系起来,以“数”的思想加以解释。他说:“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灒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⑦
(三)地理
在地理方面,朱熹指出山与水往往并行,因而可以通过江河来判断山脉的分支与走向。“大凡两山夹行,中间必有水;两水夹行,中间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夹江两岸而行,那边一支去为陇,这边一支为湖南。又一支为建康,又一支为两浙,而余气为福建、二广。”①关于山与水的关系,朱熹又提出“水随山行”的观点,认为“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间底水在脊上行”,又说:“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脉。”②关于中国的整体地形,朱熹说道:“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③关于地理位置与环境对建都的影响,朱熹既肯定“河东地形极好,乃尧、舜、禹故都……左右多山,黄河绕之,嵩、华列其前”,又指出平阳、蒲坂“其地硗瘠不生物,人民朴陋俭啬,故惟尧、舜能都之。后世侈泰,如何都得”。④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朱熹曾说:“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来便要硬做”⑤,又说:“某观诸处习俗不同,见得山川之气甚牢。且如建州七县,县县人物各自是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长短小大清浊皆不同,都改变不得,岂不是山川之气甚牢?”⑥关于地图的制作要领,朱熹提出“要作地理图三个样子:一写州名,一写县名,一写山川名。仍作图时,须用逐州正邪、长短、阔狭如其地厚,糊纸叶子以剪”⑦。他还主张讨论地理须首重大形势,再由大及小,故批评薛常州的《九域图》“其书细碎,不是著书手段”⑧。在朱熹看来,“‘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圣人做事便有大纲领,先决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爬疏小水,令至川。学者亦先识个大形势,如江、河、淮先合识得,渭水入河,上面漆、沮、泾等又入渭,皆是第二重事”。①
同时,朱熹对于《禹贡》所载地理亦做了部分的考据与辨正,客观地指出了其中不少难以理解或与现实不合之处。譬如他说:“《禹贡》济水,今皆变尽了。又江水无沲,又不至澧。九江亦无寻处,后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数千里不说一句,及到江州,数千里间连说数处,此皆不可晓者。”②又说:“《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目见者,皆有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③由于朱熹曾知南康军,故能亲履九江、彭蠡、庐山等地考察,目睹其山川形势之实,复与《禹贡》之文相核,发现殊不相应,遂作《九江彭蠡辨》以辨《禹贡》之非。《禹贡》所载乃九州之山川,如今仅荆扬一地可见之谬误已如此,朱熹更有理由怀疑“耳目见闻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当几何”④。据此,加之古今地理的变迁,朱熹认为若仅就地理本身而言,《禹贡》并不值得学者特别重视与信赖。“《禹贡》地理,不须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如今地理。”⑤他进一步指出,后世学者在注解《禹贡》的过程中,多是一味迷信经典与书本,非但不能考辨、订正其中的错误,反而牵强附会,曲为解说,文过饰非,遂使其学错上加错。所以他批评“古今读者皆以为是既出于圣人之手,则固不容复有讹谬,万世之下,但当尊信诵习,传之无穷,亦无以核其事实是否为也。是以为之说者,不过随文解义,以就章句”⑥,又谓学者所论地理“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历,故其说亦难尽据,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著明耳”①。由此可见朱熹在地理研究上注重客观实际与实地考察的科学精神。
(四)地质
在地质方面,朱熹被认为是最早认识化石的学者之一,并且能够初步以地质变迁的观点来解释化石的生成。他说:“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②又说:“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③关于山脉与大地的最初形成,朱熹认为是由于浑浊的水的沉积作用,因而存在一个由软到硬的变化过程。“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④此外,朱熹还注意到流水对山的侵蚀作用,提出“山上之土为水漂流下来,山便瘦,泽便高”⑤。
(五)生物
在生物方面,朱熹对于各种动植物的性状、特点亦多有留意。譬如,朱熹认为不同植物的花期长短与季节之令有关。他说:“冬间花难谢。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蜡梅,皆然。至春花则易谢。若夏间花,则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开得一日。必竟冬时其气贞固,故难得谢。若春夏间,才发便发尽了,故不能久。”⑥关于兰、蕙、荼、堇等植物的区别与联系,朱熹考证道:“《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说兰、蕙殊不分明。盖古人所说似泽兰者,非今之兰,(泽兰此中有之,尖叶方茎紫节,正如洪庆善说。若兰草似此,则决非今之兰矣。)自刘次庄以下所说,乃今之兰而非古之兰也。……又所谓蕙,以兰推之,则古之蕙恐当如陈藏器说乃是。若山谷说,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荼,恐是蓼属,(见《诗》疏《载芟》篇。)故诗人与堇并称。堇乃乌头,非先苦而后甘也。又云荼毒,盖荼有毒,今人用以药溪取鱼,堇是其类,则宜亦有毒而不得为苦苣矣。”①关于松柏不凋的现象,朱熹认为“松柏非是叶不凋,但旧叶凋时新叶已生。木犀亦然”②。关于《诗经》所说的“关雎”,朱熹说道:“古说关雎为王雎,挚而有别,居水中,善捕鱼。说得来可畏,当是鹰鹘之类,做得勇武气象,恐后妃不然。某见人说,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虽两两相随,然相离每远,此说却与《列女传》所引义合。”③又说:“王鸠,尝见淮上人说,淮上有之,状如此间之鸠,差小而长,常是雌雄二个不相失。虽然二个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处,须是隔丈来地,所谓‘挚而有别’也。‘人未尝见其匹居而乘处’,乘处,谓四个同处也。只是二个相随,既不失其偶,又未尝近而相狎,所以为贵也。”④关于蚁封,朱熹解释道:“蚁垤也,北方谓之‘蚁楼’,如小山子,乃蚁穴地,其泥坟起如丘垤,中间屈曲如小巷道。古语云‘乘马折旋于蚁封之间’,言蚁封之间巷路屈曲狭小,而能乘马折旋于其间,不失其驰骤之节,所以为难也。‘鹳鸣于垤’,垤即蚁封也。天阴雨下则蚁出,故鹳鸣于垤,以俟蚁之出而啄食之也。”⑤
(六)医药
在医药方面,关于药物之理,朱熹说道:“今医者定魄药多用虎睛,助魂药多用龙骨。魄属金,金西方,主肺与魄。虎是阴属之最强者,故其魄最盛。魂属木,木东方,主肝与魂。龙是阳属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强。龙能驾云飞腾,便是与气合。虎啸则风生,便是与魄合。”①关于诊脉之法,朱熹认为《难经》首篇所载“寸关尺之法为最要”,而以丁德用的密排三指之法为未备。他说:“夫《难经》则至矣,至于德用之法,则予窃意诊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长短,以是相求,或未得为定论也。盖尝细考经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关而前却,以距乎鱼际尺泽,是则所谓关者必有一定之处,亦若鱼际尺泽之可以外见而先识也。然今诸书皆无的然之论,唯《千金》以为寸口之处,其骨自高,而关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则其言之先后、位之进退,若与经文不合。独俗间所传《脉诀》五七言韵语者,词最鄙浅,非叔和本书明甚,乃能直指高骨为关,而分其前后,以为寸尺阴阳之位,似得《难经》本指。”②此外,朱熹还曾请李伯谏“烦为寻访庞安常《难经说》,及闻别有论医文字颇多,得并为访问,传得一本示及为幸”③,可见其对医药之学的关注。
诚然,朱熹关于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的这些说法与解释,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或许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的认识与标准,不仅仍带有较强的哲学思辨色彩,而且多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直接推理,还显得较为直观与粗糙,但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与科技条件下,这几乎已是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作为一位影响巨大的理学家,朱熹始终对于各种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且试图以自然的、物质性的原理对其加以解释,还能够利用观察、实验、实测等手段,亲自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充分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崭新的、具有前瞻性与启发性的创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亦对我国日后的科技研究和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与示范效应。
朱熹之所以如此重视包括社会、历史、自然等各方面知识与规律的学习和研究,并能取得如此多的成绩,除了个人兴趣与性格方面的因素外,主要还是由于其“理一分殊”的基本思想,使得这方面的内容成为其建构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朱熹的理解,一方面,若就统一的、作为万事万物根本依据的天理而言,万事万物皆禀受此理以为性,彼此之间并无分别。“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①,“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②。从这一意义上说,“物理即道理,天下初无二理”③,“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④,“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⑤。因此,万物之理可相互推知而无不通,研究、发明客观事物中蕴含的理,有利于更准确把握人心中的理。另一方面,若就分殊的、作为具体事物特定规律的物理而言,则不同事物的理又是相互区别的,是统一的普遍规律的不同部分与不同表现。因此,学者必须广泛、具体地研究各种事物中分殊的物理,并加以积累、融汇和贯通,才有可能最终把握完整的天理。故曰:“这事自有这个道理,那事自有那个道理。各理会得透,则万事各成万个道理。四面凑合来,便只是一个浑沦道理”⑥,“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百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只是空想象”①。因此,虽然朱熹亦承认价值优先的原则,并不以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或知识的学习作为最终目的,但其理学思想体系内实际上已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与要求,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道问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使得朱子学呈现出明显的理性色彩与知识取向,并且能够为各种专门知识与学问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合法性依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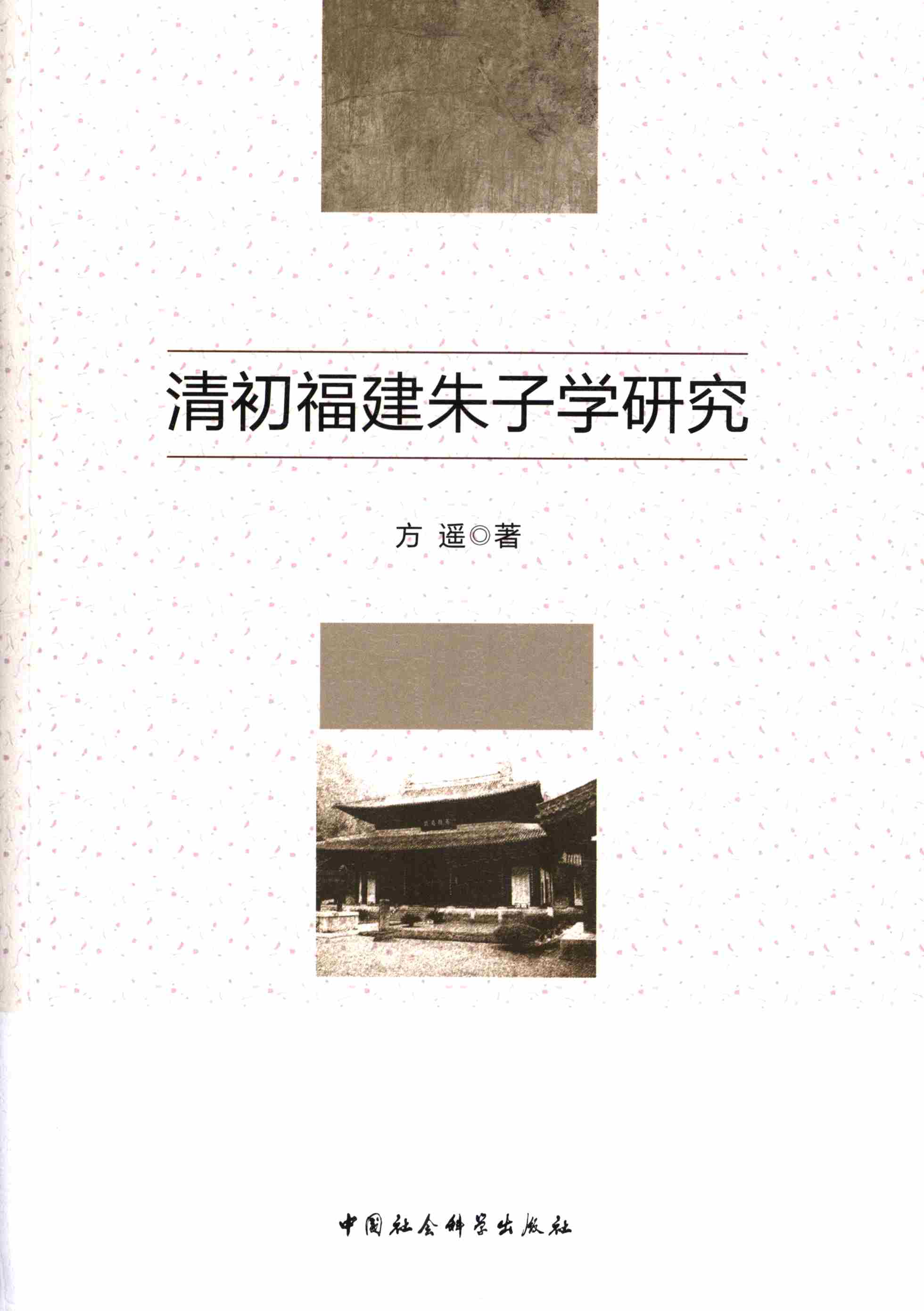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