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科举考试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92 |
| 颗粒名称: | 二 改革科举考试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503-513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科举制度与经学、士风的关系及李光地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与改革建议。 |
| 关键词: | 科举制度 经学 士风 |
内容
尽管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福建朱子学者门下多通经之士,亦取得了不少经学研究成果,但若要大量培养经史实学方面的人才,扭转空疏不学的士风,仅靠若干学者的个人努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须从教育、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上加以变革。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之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便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奋斗目标,而考试的科目内容、评判标准和参考教材对于士子的读书、治学无疑起到了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标准既受到一时学术思潮与学术风气的影响,反过来又有力地巩固和推动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潮与学术风气。可以说,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社会后期始终维持其官方思想的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与科举制度的密切联系,始终被奉为科举程式而得以保障的。
自元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以后,科举制度逐渐规范定型。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首重四书,而五经仅须专一经应试。四书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五经亦多用程朱派理学家的传注。元代时,五经尚可参用汉唐诸儒的注疏,至明代颁行《四书五经大全》,专用宋元理学家的传注,则古注疏皆废。这一举动虽然进一步巩固了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但也导致了士人对经学原典与汉唐注疏的轻视和忽略,甚至只读《大全》、语录与各种时文讲章,而将经典弃之不顾,加剧了经学的衰落。故皮锡瑞称:“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全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经义考》所目为兔园册子者。故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①而这种情况在清初仍未发生明显改变。“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顺治)二年,颁《科场条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①
科举制度的这种弊端,及其对学术与士风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不满和抗议。如杨慎说:
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②
曹安云:
《周易》,人多读《本义》,不读《传》,不知《传》义不可阙;《书》,读《禹贡》节要;《诗》,不读变《风》《雅》;《春秋》,不详崩薨卒葬;《礼记》,《丧服》《大记》等多不考;《学》《庸》多不读《或问》;《论》《孟》多不读《序说》。经有节文,史有略本,百家诸氏之书,皆有纂集,以为一切目前苟且速成之诗。父兄以是夸子弟,师儒以是训学徒。近时书房,又刊时文,以炫末学,不使义理淹贯,可胜叹哉!③
黄宗羲亦言:
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冗,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障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①顾炎武则谓:
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与?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②
李光地显然也意识到了科举制度的这一弊病,故激烈批评道:“八股取士弊坏极矣,离却四书、五经不可”③,“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浮词填胸,千里一轨。遇题目相近,剽剥不让,公然相袭,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间或理致及典实题样,与所习相左,则荒疏杜撰,无一语中肯綮者”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光地主张将“汉、唐、宋试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专经义,守师说”⑤,提高经典内容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与重要性。譬如他说:,《周礼》经也,《公》《谷》于孔子为近,与《左氏》当列于学宫。首场试经说五篇,令学者述先儒之异同,而析其孰为是,孰为非。皆所不可,则自出己意。四书说三,经说二。只此,足觇穷经,多则敝士子之精力,无谓也。二场论二篇,《孝经》虽圣人之经,卷帙最少,不如易以《性理》《通鉴》。表判可去,恐声病之学遂废,兼采唐制,试诗二首。三场策三道。……又以五年试大科,俾兼通数经,习三《春秋》、三礼者,得殚所长。登斯选者,授以馆职,如殿一甲之例,亦不过数人而已。即以其年试天文、律历,专门名家,分别录用。如此,则士皆务实学。①
在李光地看来,科举考试“使士子传注是遵,格式是守,非固束天下之心思才智,而使之不得逞也”,而是为了“率天下尊经学古,游于圣贤之路”。②因此,他虽然仍旧注重在科举考试中考察有关程朱理学的内容,但也要求提高经典在科举考试中所占的分量,以培养尊经学古的风气。自元代以后,科举于三礼中仅试《礼记》一经,《周礼》与《仪礼》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清顺治二年(1645)颁布的《科场条例》规定,《春秋》主胡安国《传》,传统的《春秋》三传亦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对此,李光地不以为然,主张将《周礼》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列学宫,重新纳入学校的教授范围。他又提出,科举首场应试经说五篇,令考生就所给题目论述先儒注疏之异同,辨析其是非,并且允许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同时设立专门的经学考试,五年举行一次,考生须兼通数经,重点考察三礼与《春秋》“三传”,通过考试者授以翰林院官职。此外,还应设立有关天文、律历的考试,选拔专门人才,分别录用,以弘扬实学。
同时,李光地还主张将制义与经学结合起来,使其发挥羽翼经传的作用。在他看来,制义与经学本就相互关联,不应分割。“制举之文……其原盖出于义疏之流,而稍叶以俳俪者也。其法虽起于熙宁之新学,然观洛闽以来,训义讲说,用其体者多矣。盖穷经之学,以剖析为功,故谭经之文,亦不以栉比为病也。由是观之,制举而能有发于圣贤之意,有助于儒先之说,虽与义疏注解佐佑六经可也。”①因此,学者若欲在举业中学有所得,“则制义之根本六经也,其门户先儒也,讲诵而思索之,固即汉宋所谓专经之艺,穷理之功也,与习为浮艳而卒与古背驰者,不犹远乎?”②李光地认为,优秀的制义之文不仅足以佐佑六经,其至者甚至“语皆如经”。“如顾亭林‘且比化者’一节文,直驾守溪而上。盖字字有来历,精于经学,而其辞又能补经之所未备,而不悖于经,亦可为经矣。”③据此,李光地强调“吾所为汲汲焉勉子弟以制举业者,欲其借此以通经焉尔,循是以辨理焉耳”④。
科举不但与一时的学术、士风相关,而且是选拔政府官员的基本制度。在这方面,李光地亦积极肯定了以科举昌明经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强化了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意义。他说:“经尊而理明,则人心淳而世道泰,历世之科目为有用,而平日之占毕为有施矣。”⑤又说:“汉、唐、宋、明之盛,未有不泽于经术,使其文雅驯者也。故大为斯世之休征,上为国家之和应,然要不出于经明行修,则文不期醇而自醇。”⑥
因此,当李光地提督顺天学政时,便十分注意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培养经学人才。据《文贞公年谱》记载,当时“北方侵寻学废,公教以则古通经。有能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辞多者,稍成文,辄录以示劝,为之背诵至漏下二三鼓不倦。试日发题,先为解剥经旨,而后答义,极力起衰”⑦。《榕村谱录合考》亦载:“畿辅固多英俊,但沿俗学之弊,不习经书古文。公预示生童,有能背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百篇以上者,稍有文义,并拔擢之,以风励实学。日坐绛纱,生童有质问经义者,为之从容剖析,发蒙解惑,然后人知向学于古,不为俗儒曲说所诱。覆试或至十余次,文体一轨于正,非真才无得幸。”①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下诏,命李光地、郭琇等人就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各抒己见,提出解决方案。李光地于是上《条议学校科场疏》,提出了“学臣宜经考试”“教职宜稍清汰”“士习宜正”“经学宜崇”四项建议。其中,与科举考试内容直接相关的“经学宜崇”条说道:
皇上表章经术,以正学养天下士。而迩来学臣,率多苟且从事,以致士子荒经蔑古,自四书本经,不能记忆成诵。其能者,不过读时文百篇,剿习雷同,侥幸终身,殊非国家作养成就之意。前岁皇上旨下学臣,使童子入学兼用小学论一篇。其时幼稚见闻一新,胸中顿明古义,此则以正学诱人之明验也。然书不熟记,终非己得。宜令学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将经书、小学讲诵精熟者,文理粗成,便与录取。如更能成诵三经以至五经者,仍与补廪,以示鼓励。庶几人崇经学,稍助圣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通习小学,以端幼志,生员及科场论题似当兼命《性理》《纲目》,以励弘通。今《孝经》题目至少,以致每年科场论题重复雷同,似宜通变。②
在此,李光地的提议与其一贯的教育主张相一致,即在重视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高经学与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以培养通经学古的良好风气。而康熙帝亦对李光地的这一提议表示认可。是年十一月,朝廷根据郭琇、李光地等人的奏议,宣布:“嗣后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子弟,俱编入官字号,另入号房考试,各照定额。……童生内,有将经书、小学真能精熟,及能成诵三经、五经者,该学臣酌量优录。论题,将《性理》中《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书一并命题。”①
蔡世远作为一位拥有丰富书院教学经验,并长期在朝为官的朱子学者,亦对当时科举考试忽视经学而导致的空疏学风深为不满,批评“士子荒经久矣,剿袭撮摘,以涂有司之目,侮圣人之言,莫此为甚”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蔡世远对担负着选拔人才重任的学政一职寄予了特别关注,提出“学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风而变士习”③,希望通过学政的实际工作,培养、选拔通经学古、品行优良的人才,以扭转空疏放逸的学风士习。至于具体的措施与标准,蔡世远则主张借鉴汉唐的取士方法,经术与品行并重。他说:“昔两汉之选博士弟子员也,以好文学、敬长上、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为称选,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异等者以为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纵不能荐之于朝,私自褒扬,亦学政之大者。唐时有帖经墨义之科,今亦仿此意施之,使士子无荒经之患,于学者大有裨益。”④据此,蔡世远提议,学政到任伊始,即颁令于当地的县令、学官,要求“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闻,并上所实行;有能通经学古、奇才异能者以名闻,并上所论著。行之各属,揭之通衢”,并且“本之以诚心,加之以询访,择其真者而奖励之,或誉之于发落诸生之时,或荐之督抚,或表宅以优之。试竣,或延而面叩之,从容讲论,以验其所长。有行检不饬者,摘其尤而重黜责之。如是而士习不变者,未之有也”。⑤
同时,蔡世远亦认识到,学子荒废经学多是由于科举考试内容的不合理而造成,故提议学政“于岁科未试之先,通行于各学,曰:书艺二篇之外,不出经题,但依所限,抄录本经,多不过五行,少不过三行。不者,文虽佳,岁试降等,科试不录。科举至期,牌示曰:某经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各书于卷后。夫勒写数行本经,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诵,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场中又牌示曰:能成诵四经、五经者,庠生给饩禀,童子青其衿”①。如此,自然能敦促、引导广大学子重视经典,研习经学。
从康熙后期起,由李光地、蔡世远及其他学者共同提倡和推动的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譬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乡试,顺天南皿监生庄令舆、俞长策在考试第一场中,除了本经之外,兼作四书、五经文二十三篇,虽然违式,但仍奉旨授为举人,并旋著为令,即所谓“五经中式”。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先是,顺治二年,以士子博雅不在多篇,停五经中式。至康熙三十六年京闱乡试②,有五经二卷,特旨授为举人,后不为例。至是,礼部议,本年乡试,监生庄令舆、俞长策,试卷作五经文字,与例不合。奉谕旨,五经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当取中,若能切题旨,文理明顺,一日书写二万余字,实为难得。庄令舆、俞长策俱着授为举人,准其会试。嗣后作五经文字,不必禁止。作何定例,着九卿、詹事、科道议奏。寻议,嗣后乡、会试作五经文字者,应于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果多,另行题明酌夺。五经文字草稿不全,免其贴出。二场于论、表、判外添诏、诰各一道。头场备多页长卷,有愿作五经者,许本生禀明,给发从之。”③
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定乡、会试“五经中式”例,恢复“五经中式”之后,学子习五经者益众。在直隶、陕西等省的考试中,甚至出现以五经卷抡元者。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又增加“五经中式”名额,外省乡试增加一名,顺天增加二名,会试增加三名。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经中式”曾一度停止。雍正二年(1724)又再次恢复,规定“顺天皿字号中四名,各省每额九名加中一名。大省人多文佳,额外量取副榜三四名。四年丙午,诏是科以五经中副榜者,准作举人,一体会试,尤为特异”①。陆廷灿谓此为“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矣”②。
由于科举考试是传统社会中一项关乎无数读书人命运与各方面重大利益的基本制度,因而对其进行的任何改革与调整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其中必然充满了反复与曲折。同样,清初出现的要求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也是直到乾嘉时代才逐渐确定与巩固下来。譬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认为“设科立法程材,无取繁文虚饰”,而“今士子论、表、判、策,不过雷同剿说,而阅卷者亦止以书艺为重,即经文已不甚留意”,故下诏曰:“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如此,则士子闱中,不得复诿之于日力不给,而主试者亦可从容尽心详校,无鱼目碔砆之混。且乡试第二场止经文四篇,斯潦草完篇者,当在所黜。专经之士,得抒夙学,而浅陋者亦知所奋励,去浮文而求实效。”③这样,就将五经从四书附庸的位置独立出来,成为第二场考试的核心,取得了与四书约略同等的地位,有利于精通经学的考生取得更好的成绩,从而促使士子更加注重经学的学习。同时,艾尔曼指出,清代科举考试中“论”的科目与程朱宋学紧密相关,当时官员们关于论题去留的争论“说明了论题之删除,部分原因是乾隆年间(1736—1795年)更古的五经在汉学学者间普遍得到偏好”④。
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又因“士子束发授书,原应五经全读,向来止就本经按额取中,应试各生只知专治一经,揣摩诵习,而他经并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故规定自明年戊申乡试开始,乡、会试二场改用五经出题,先于五科内将五经依次轮试一周,然后再以五经并试,“既可令士子潜心经学,又可以杜绝场内关节弊端,而衡文取中,复不至限于经额,致佳卷被遗”。①如此,五经在科举中的重要性与考试要求显然又大大提高了。
此外,由于科举考试第一场与第二场的考查科目、命题方式、答题格式与评判标准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个人因素难以发挥过多的影响,故乾嘉时代拥有考据学背景的考官们往往还会利用第三场经史时务策的命题来表达自己的学术偏好,从而出现了许多经史考据类的策论试题。据艾尔曼考证,从18世纪晚期起,在北京、江南、山东、四川、陕西各地都出现了“乡试及会试考官在第三场的策论题中开始测验原先国家规定科目以外的技术性的考证题目”。据此他指出:“在乡试与会试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策论题,开始反映出操纵儒学科举的学术脉络之改变。虽然在乡试及会试的第一、二场所考的四书五经引文大多未曾改变且受制于正统程朱派解释,汉学趋势及考证问题仍能经由第三场的策论题渗入科举。”②而冯建民则指出,乾嘉时期由具有汉学背景的官员充任的乡、会试考官在评阅考卷时,往往会改变过去特重首场四书文的取士倾向,而是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后两场,尤其是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上。“这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对策最能反映出举子的学识水平。”③
诚然,不论是实行“五经中式”,还是增加科举考试中的经典内容,若是抽离出来孤立地看,都未必与经学研究的发展繁荣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若将李光地、蔡世远等学者提倡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放在清初经学复兴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与观照,则不难看出科举考试与学术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的密切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李光地、蔡世远等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扭转空疏学风、推动经学复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亦反映了当时理学与经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关系。
自元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以后,科举制度逐渐规范定型。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首重四书,而五经仅须专一经应试。四书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五经亦多用程朱派理学家的传注。元代时,五经尚可参用汉唐诸儒的注疏,至明代颁行《四书五经大全》,专用宋元理学家的传注,则古注疏皆废。这一举动虽然进一步巩固了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但也导致了士人对经学原典与汉唐注疏的轻视和忽略,甚至只读《大全》、语录与各种时文讲章,而将经典弃之不顾,加剧了经学的衰落。故皮锡瑞称:“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全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经义考》所目为兔园册子者。故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①而这种情况在清初仍未发生明显改变。“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顺治)二年,颁《科场条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①
科举制度的这种弊端,及其对学术与士风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不满和抗议。如杨慎说:
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②
曹安云:
《周易》,人多读《本义》,不读《传》,不知《传》义不可阙;《书》,读《禹贡》节要;《诗》,不读变《风》《雅》;《春秋》,不详崩薨卒葬;《礼记》,《丧服》《大记》等多不考;《学》《庸》多不读《或问》;《论》《孟》多不读《序说》。经有节文,史有略本,百家诸氏之书,皆有纂集,以为一切目前苟且速成之诗。父兄以是夸子弟,师儒以是训学徒。近时书房,又刊时文,以炫末学,不使义理淹贯,可胜叹哉!③
黄宗羲亦言:
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冗,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障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①顾炎武则谓:
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与?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②
李光地显然也意识到了科举制度的这一弊病,故激烈批评道:“八股取士弊坏极矣,离却四书、五经不可”③,“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浮词填胸,千里一轨。遇题目相近,剽剥不让,公然相袭,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间或理致及典实题样,与所习相左,则荒疏杜撰,无一语中肯綮者”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光地主张将“汉、唐、宋试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专经义,守师说”⑤,提高经典内容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与重要性。譬如他说:,《周礼》经也,《公》《谷》于孔子为近,与《左氏》当列于学宫。首场试经说五篇,令学者述先儒之异同,而析其孰为是,孰为非。皆所不可,则自出己意。四书说三,经说二。只此,足觇穷经,多则敝士子之精力,无谓也。二场论二篇,《孝经》虽圣人之经,卷帙最少,不如易以《性理》《通鉴》。表判可去,恐声病之学遂废,兼采唐制,试诗二首。三场策三道。……又以五年试大科,俾兼通数经,习三《春秋》、三礼者,得殚所长。登斯选者,授以馆职,如殿一甲之例,亦不过数人而已。即以其年试天文、律历,专门名家,分别录用。如此,则士皆务实学。①
在李光地看来,科举考试“使士子传注是遵,格式是守,非固束天下之心思才智,而使之不得逞也”,而是为了“率天下尊经学古,游于圣贤之路”。②因此,他虽然仍旧注重在科举考试中考察有关程朱理学的内容,但也要求提高经典在科举考试中所占的分量,以培养尊经学古的风气。自元代以后,科举于三礼中仅试《礼记》一经,《周礼》与《仪礼》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清顺治二年(1645)颁布的《科场条例》规定,《春秋》主胡安国《传》,传统的《春秋》三传亦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对此,李光地不以为然,主张将《周礼》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列学宫,重新纳入学校的教授范围。他又提出,科举首场应试经说五篇,令考生就所给题目论述先儒注疏之异同,辨析其是非,并且允许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同时设立专门的经学考试,五年举行一次,考生须兼通数经,重点考察三礼与《春秋》“三传”,通过考试者授以翰林院官职。此外,还应设立有关天文、律历的考试,选拔专门人才,分别录用,以弘扬实学。
同时,李光地还主张将制义与经学结合起来,使其发挥羽翼经传的作用。在他看来,制义与经学本就相互关联,不应分割。“制举之文……其原盖出于义疏之流,而稍叶以俳俪者也。其法虽起于熙宁之新学,然观洛闽以来,训义讲说,用其体者多矣。盖穷经之学,以剖析为功,故谭经之文,亦不以栉比为病也。由是观之,制举而能有发于圣贤之意,有助于儒先之说,虽与义疏注解佐佑六经可也。”①因此,学者若欲在举业中学有所得,“则制义之根本六经也,其门户先儒也,讲诵而思索之,固即汉宋所谓专经之艺,穷理之功也,与习为浮艳而卒与古背驰者,不犹远乎?”②李光地认为,优秀的制义之文不仅足以佐佑六经,其至者甚至“语皆如经”。“如顾亭林‘且比化者’一节文,直驾守溪而上。盖字字有来历,精于经学,而其辞又能补经之所未备,而不悖于经,亦可为经矣。”③据此,李光地强调“吾所为汲汲焉勉子弟以制举业者,欲其借此以通经焉尔,循是以辨理焉耳”④。
科举不但与一时的学术、士风相关,而且是选拔政府官员的基本制度。在这方面,李光地亦积极肯定了以科举昌明经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强化了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意义。他说:“经尊而理明,则人心淳而世道泰,历世之科目为有用,而平日之占毕为有施矣。”⑤又说:“汉、唐、宋、明之盛,未有不泽于经术,使其文雅驯者也。故大为斯世之休征,上为国家之和应,然要不出于经明行修,则文不期醇而自醇。”⑥
因此,当李光地提督顺天学政时,便十分注意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培养经学人才。据《文贞公年谱》记载,当时“北方侵寻学废,公教以则古通经。有能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辞多者,稍成文,辄录以示劝,为之背诵至漏下二三鼓不倦。试日发题,先为解剥经旨,而后答义,极力起衰”⑦。《榕村谱录合考》亦载:“畿辅固多英俊,但沿俗学之弊,不习经书古文。公预示生童,有能背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百篇以上者,稍有文义,并拔擢之,以风励实学。日坐绛纱,生童有质问经义者,为之从容剖析,发蒙解惑,然后人知向学于古,不为俗儒曲说所诱。覆试或至十余次,文体一轨于正,非真才无得幸。”①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下诏,命李光地、郭琇等人就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各抒己见,提出解决方案。李光地于是上《条议学校科场疏》,提出了“学臣宜经考试”“教职宜稍清汰”“士习宜正”“经学宜崇”四项建议。其中,与科举考试内容直接相关的“经学宜崇”条说道:
皇上表章经术,以正学养天下士。而迩来学臣,率多苟且从事,以致士子荒经蔑古,自四书本经,不能记忆成诵。其能者,不过读时文百篇,剿习雷同,侥幸终身,殊非国家作养成就之意。前岁皇上旨下学臣,使童子入学兼用小学论一篇。其时幼稚见闻一新,胸中顿明古义,此则以正学诱人之明验也。然书不熟记,终非己得。宜令学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将经书、小学讲诵精熟者,文理粗成,便与录取。如更能成诵三经以至五经者,仍与补廪,以示鼓励。庶几人崇经学,稍助圣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通习小学,以端幼志,生员及科场论题似当兼命《性理》《纲目》,以励弘通。今《孝经》题目至少,以致每年科场论题重复雷同,似宜通变。②
在此,李光地的提议与其一贯的教育主张相一致,即在重视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高经学与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以培养通经学古的良好风气。而康熙帝亦对李光地的这一提议表示认可。是年十一月,朝廷根据郭琇、李光地等人的奏议,宣布:“嗣后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子弟,俱编入官字号,另入号房考试,各照定额。……童生内,有将经书、小学真能精熟,及能成诵三经、五经者,该学臣酌量优录。论题,将《性理》中《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书一并命题。”①
蔡世远作为一位拥有丰富书院教学经验,并长期在朝为官的朱子学者,亦对当时科举考试忽视经学而导致的空疏学风深为不满,批评“士子荒经久矣,剿袭撮摘,以涂有司之目,侮圣人之言,莫此为甚”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蔡世远对担负着选拔人才重任的学政一职寄予了特别关注,提出“学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风而变士习”③,希望通过学政的实际工作,培养、选拔通经学古、品行优良的人才,以扭转空疏放逸的学风士习。至于具体的措施与标准,蔡世远则主张借鉴汉唐的取士方法,经术与品行并重。他说:“昔两汉之选博士弟子员也,以好文学、敬长上、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为称选,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异等者以为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纵不能荐之于朝,私自褒扬,亦学政之大者。唐时有帖经墨义之科,今亦仿此意施之,使士子无荒经之患,于学者大有裨益。”④据此,蔡世远提议,学政到任伊始,即颁令于当地的县令、学官,要求“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闻,并上所实行;有能通经学古、奇才异能者以名闻,并上所论著。行之各属,揭之通衢”,并且“本之以诚心,加之以询访,择其真者而奖励之,或誉之于发落诸生之时,或荐之督抚,或表宅以优之。试竣,或延而面叩之,从容讲论,以验其所长。有行检不饬者,摘其尤而重黜责之。如是而士习不变者,未之有也”。⑤
同时,蔡世远亦认识到,学子荒废经学多是由于科举考试内容的不合理而造成,故提议学政“于岁科未试之先,通行于各学,曰:书艺二篇之外,不出经题,但依所限,抄录本经,多不过五行,少不过三行。不者,文虽佳,岁试降等,科试不录。科举至期,牌示曰:某经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各书于卷后。夫勒写数行本经,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诵,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场中又牌示曰:能成诵四经、五经者,庠生给饩禀,童子青其衿”①。如此,自然能敦促、引导广大学子重视经典,研习经学。
从康熙后期起,由李光地、蔡世远及其他学者共同提倡和推动的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譬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乡试,顺天南皿监生庄令舆、俞长策在考试第一场中,除了本经之外,兼作四书、五经文二十三篇,虽然违式,但仍奉旨授为举人,并旋著为令,即所谓“五经中式”。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先是,顺治二年,以士子博雅不在多篇,停五经中式。至康熙三十六年京闱乡试②,有五经二卷,特旨授为举人,后不为例。至是,礼部议,本年乡试,监生庄令舆、俞长策,试卷作五经文字,与例不合。奉谕旨,五经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当取中,若能切题旨,文理明顺,一日书写二万余字,实为难得。庄令舆、俞长策俱着授为举人,准其会试。嗣后作五经文字,不必禁止。作何定例,着九卿、詹事、科道议奏。寻议,嗣后乡、会试作五经文字者,应于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果多,另行题明酌夺。五经文字草稿不全,免其贴出。二场于论、表、判外添诏、诰各一道。头场备多页长卷,有愿作五经者,许本生禀明,给发从之。”③
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定乡、会试“五经中式”例,恢复“五经中式”之后,学子习五经者益众。在直隶、陕西等省的考试中,甚至出现以五经卷抡元者。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又增加“五经中式”名额,外省乡试增加一名,顺天增加二名,会试增加三名。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经中式”曾一度停止。雍正二年(1724)又再次恢复,规定“顺天皿字号中四名,各省每额九名加中一名。大省人多文佳,额外量取副榜三四名。四年丙午,诏是科以五经中副榜者,准作举人,一体会试,尤为特异”①。陆廷灿谓此为“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矣”②。
由于科举考试是传统社会中一项关乎无数读书人命运与各方面重大利益的基本制度,因而对其进行的任何改革与调整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其中必然充满了反复与曲折。同样,清初出现的要求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也是直到乾嘉时代才逐渐确定与巩固下来。譬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认为“设科立法程材,无取繁文虚饰”,而“今士子论、表、判、策,不过雷同剿说,而阅卷者亦止以书艺为重,即经文已不甚留意”,故下诏曰:“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如此,则士子闱中,不得复诿之于日力不给,而主试者亦可从容尽心详校,无鱼目碔砆之混。且乡试第二场止经文四篇,斯潦草完篇者,当在所黜。专经之士,得抒夙学,而浅陋者亦知所奋励,去浮文而求实效。”③这样,就将五经从四书附庸的位置独立出来,成为第二场考试的核心,取得了与四书约略同等的地位,有利于精通经学的考生取得更好的成绩,从而促使士子更加注重经学的学习。同时,艾尔曼指出,清代科举考试中“论”的科目与程朱宋学紧密相关,当时官员们关于论题去留的争论“说明了论题之删除,部分原因是乾隆年间(1736—1795年)更古的五经在汉学学者间普遍得到偏好”④。
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又因“士子束发授书,原应五经全读,向来止就本经按额取中,应试各生只知专治一经,揣摩诵习,而他经并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故规定自明年戊申乡试开始,乡、会试二场改用五经出题,先于五科内将五经依次轮试一周,然后再以五经并试,“既可令士子潜心经学,又可以杜绝场内关节弊端,而衡文取中,复不至限于经额,致佳卷被遗”。①如此,五经在科举中的重要性与考试要求显然又大大提高了。
此外,由于科举考试第一场与第二场的考查科目、命题方式、答题格式与评判标准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个人因素难以发挥过多的影响,故乾嘉时代拥有考据学背景的考官们往往还会利用第三场经史时务策的命题来表达自己的学术偏好,从而出现了许多经史考据类的策论试题。据艾尔曼考证,从18世纪晚期起,在北京、江南、山东、四川、陕西各地都出现了“乡试及会试考官在第三场的策论题中开始测验原先国家规定科目以外的技术性的考证题目”。据此他指出:“在乡试与会试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策论题,开始反映出操纵儒学科举的学术脉络之改变。虽然在乡试及会试的第一、二场所考的四书五经引文大多未曾改变且受制于正统程朱派解释,汉学趋势及考证问题仍能经由第三场的策论题渗入科举。”②而冯建民则指出,乾嘉时期由具有汉学背景的官员充任的乡、会试考官在评阅考卷时,往往会改变过去特重首场四书文的取士倾向,而是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后两场,尤其是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上。“这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对策最能反映出举子的学识水平。”③
诚然,不论是实行“五经中式”,还是增加科举考试中的经典内容,若是抽离出来孤立地看,都未必与经学研究的发展繁荣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若将李光地、蔡世远等学者提倡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放在清初经学复兴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与观照,则不难看出科举考试与学术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的密切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李光地、蔡世远等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扭转空疏学风、推动经学复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亦反映了当时理学与经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关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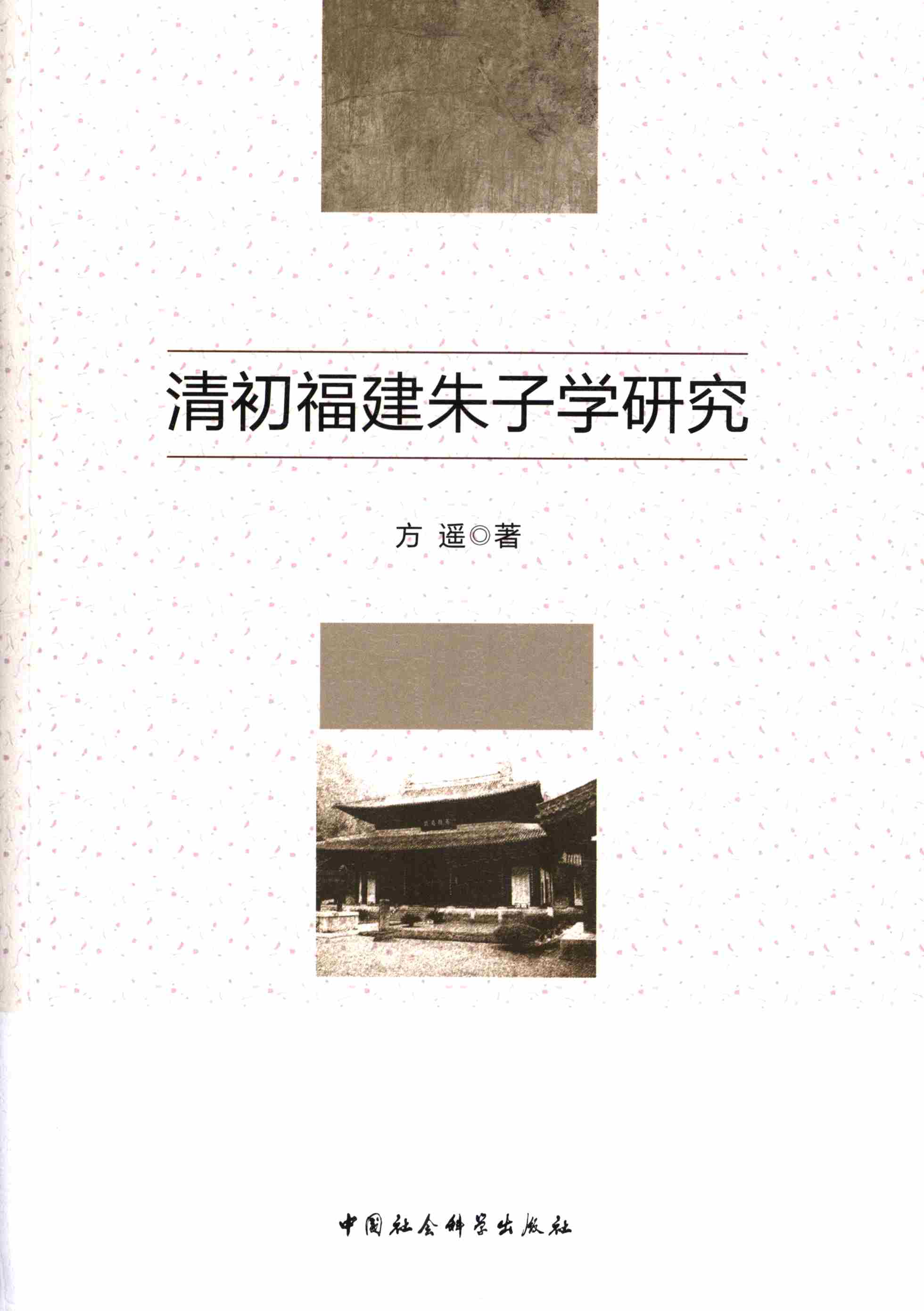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