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对清初经学复兴的影响与推动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90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对清初经学复兴的影响与推动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6 |
| 页码: | 491-516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李光地门下治经学较有成就的学者杨名时、惠士奇、冉觐祖等人。详细描述了杨名时对《易经》和《诗经》的治学成就,以及他在《易经》中阐发义理、重视图书之学,对《诗经》中淫诗的观点等。同时,介绍了惠士奇对象数和礼学的主张,以及他对《易经》和《礼经》的解释方法。 |
| 关键词: | 惠士奇 治学成就 易经 |
内容
一 培养、奖掖经学人才
李光地身为清初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又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十
①(清)李光坡:《仪礼述注》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四库馆臣指出:“今考贾前《疏》云:‘酒浆皆以酳口’,谓二饮本并设以待宾用也。后《疏》云:‘浆以酳口,不用酒’,谓二饮虽并设,其实宾止用浆耳。前后一义相承,并无抵牾。杨氏殊未解《疏》意。至于郑《注》‘优宾’之义,亦谓宾酳口止用浆,而主人仍特设酒,故曰‘优宾’。下文之祭饮酒,乃宾加敬以报酳礼之优,与他篇献酬之酒、祭酒不同。观郑上《注》,明云饮酒非献酬之酒,则为饭后洁口之物可知。杨氏以设饮酒为优宾,而谓饮酒非以酳口,于郑《注》‘优宾’之义亦为未明。且考《周礼·酒人》曰:‘共宾客之礼酒,饮酒而奉之。’《注》:‘礼酒,飨燕之酒。饮酒,食之酒。’贾《疏》:‘饮酒,食之酒者,《曲礼》曰,酒浆处右,此非献酬之酒,是酳口之酒。’则杨氏谓饮酒非酳口之物,与《酒人》经注皆相矛盾矣。”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经部·礼类二》“仪礼述注”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页。
分热心于作育贤才,培植国本,门下名士硕学众多。诚如彭绍升所称,李光地“门下士杨名时、李绂、陈鹏年、赵申乔、冉觐祖、蔡世远并以德望重于时,它若张昺、张瑗、惠士奇、秦道然、王兰生、何焯、庄亨阳之徒,类有清节,通经能文章。故本朝诸巨公称善育材者,必以公为首焉”①。李光地曾指出:“今之学者,大抵搜华撷卉,为文辞之用而已。至于字义故实,书文形声,尚未有留意讲考于其间者。若大者为遗经源流,礼典同异,细而地名山川,史载人物,真赝是非之迹,则岂徒以朴学置之,抑其恶赜就简,而自恬于讹陋。呜呼!文武之道,岂有小大哉?万一朝廷举行石渠之典,吾知众籍罗凑,而莫之措辞,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②故其较为注重发掘、培养经学方面的人才,门下多通经学古与汉宋兼采之士,影响及于一时风气,推动了清初经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李光地门下治经学较有成就的学者主要有杨名时、惠士奇、冉觐祖等人。杨名时,字宾实,号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出李光地门。其学识深受李光地器重,故从李光地受经学。后因李光地举荐,得到康熙帝召对,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四十一年(1702),又因李光地的推荐,提督顺天学政,寻迁侍讲学士。康熙五十二年(1713),入直南书房,参与修校李光地主持的《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后累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云南巡抚、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吏部尚书等职。乾隆二年(1737)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杨名时治学范围较广,于诸经皆有讲义,尤重《周易》《诗经》,著有《周易劄记》《诗经劄记》《四书劄记》《经书言学指要》等。《清儒学案》称其“于《易》《诗》多本安溪之说,亦自有考订折衷,不尽附和”③。
杨名时治《易》以阐发义理为主,多采《周易折中》与《周易观彖》之说,在继承程朱《易》说和李光地《易》说的同时,亦有所发挥和修正,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杨名时治《易》还很重视图书之学,试图以阴阳消长与体用关系来说明《先后天图》的合理性。他说:“先后天之学,其道同归,而其说并行不悖者也。愚谓康节之学见疑于世,使是图而康节所自为,亦所谓先圣后圣,如合符节者矣。况证之以《大传》,参之以自汉而下儒伎诸书,阴阳消息进退之所,确然可据,则其学之有传,又岂可诬乎?”①四库馆臣称其《周易劄记》“多得之光地。虽《说卦传》及附论《启蒙》之类,颇推衍先天诸图,尚不至于支离附会。至其诠解经传,则纯以义理为宗,不涉象数。大抵于程朱之义,不为苟异,亦不为苟同,在宋学之中,可谓明白而笃实矣”②。
杨名时治《诗经》以李光地《诗》说为宗,并斟酌于《诗序》与朱熹《诗集传》之间。譬如,杨名时对《大序》十分赞赏,认为“读《大序》则知《诗》之教是从人之心志上养其善端,消其邪恶,以为美政教之本”③。论及《关雎》,杨名时亦取《小序》言后妃之德之说,提出:“大臣之职,莫大于求贤才,以佐朝廷之治。后妃之职,莫大于与贤淑,共成宫阃之化。后妃求淑女,此德之所以为至。味此诗,殆后妃所自作欤?”④关于《诗经》中的淫诗问题,杨名时则根据诗意与诗人作诗之动机判断《诗经》中存在淫诗。“今观《桑中》《同车》及《丰》之诗,皆似其人自作,非有刺讥之意,安得不谓之淫诗?且人之作诗,或美或刺,或述怀见志。若如旧说,是专有美刺,而无述怀见志之诗也,于理亦觉难通。”⑤而孔子之所以要在《诗经》中保存淫诗,是为了使读者引为鉴戒,“盖以著其风俗之恶,使人知卫所以亡,郑所以乱也”⑥。杨名时进一步指出,“郑声淫”即“郑诗淫”,“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有源有流,不相假易,安有诗言正而声律淫者乎”,又谓:“要之心中有哀,而以哀词填入哀调;心中有乐,而以乐词填入乐调,是哀乐仍生于心也。决无欲抒写好贤乐善、劝德规过之心,而用庄雅之词填入淫靡之调者。可见诗不淫而声淫,无是理也。”①但他同时强调,“郑声淫”主要指孔子未删《诗》时,郑、卫淫诗不可胜数。在孔子删《诗》之后,淫诗已去十之八九,只存十之一二,故郑诗亦多非淫诗。关于“思无邪”的解释,杨名时则从李光地自得之说,认为“‘邪’音‘余’,与‘余’同,《史记》历书‘归邪于终’,注:‘邪,余分也,终闰月也。’”
杨名时在《诗经》的训诂考据方面亦颇有可取之处。譬如,李光地认为,东周列国之《风》鲁国无备,故季札观乐所陈多为西周之诗。而杨名时则提出,东周之《风》列国具备,“东迁后,列国名卿学士辈留心礼乐典章,兼通当世之务者,类不乏人。平日则互相咨访,以广见闻;及出使,则赋诗赠答以见志,《左传》所称纪者甚繁。晋、宋、齐、郑皆然,不独鲁也。鲁秉周礼,崇文教为诸国望,于文章风雅之事必尤备焉。采辑所得,存之史氏,掌之太师,由来旧矣”,其又据“变《风》终于陈灵,陈灵弑于宣公十年,又越五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九年,而季札观乐”,推测“季札观乐即今所载各国《风》也”。③又如,《小雅·常棣》云:“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说者多谓此诗乃周公作于成王时,“死丧之威”指管叔、蔡叔叛乱之事,杨名时对此并不认同。他借鉴孔颖达等人的意见,④引《左传》富辰谏襄王之言“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认为周公封建既以管叔、蔡叔为首,则“二叔”当指夏、商之叔世,并非管、蔡二人,又引孔氏《毛诗正义》“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认为召穆公乃诵周公之诗,其目的在于“厉王时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诗,以亲之耳”。根据上述周人之说,及其对《常棣》诗意的理解,“且管、蔡所谓悖理乱常,公诛之出于万不得已,上伤文考宁王之心,下为终身莫释之憾,乃以此施于燕同姓兄弟之时,定为乐章,咏歌不置,揆诸情理之安,益多未协”,故杨名时坚持此诗乃周公作于文武之世,反对将“死丧之威”理解为管、蔡之事。①《召南·小星》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杨名时引《礼记》“三五而盈”,《古诗》“三五明月满”,认为“三五”指每月十五日月望之时,故此句之意是“月望时,月光满则星光为之夺。今小星嘒然在东,是不为月掩矣”②。《大雅·棫朴》云:“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朱熹认为此言祭宗庙之礼。而杨名时则引《周礼》所载,祭天地以苍璧、黄琮及珪,祀日月星辰以珪璧,礼四方以圭璋琥璜,认为祭天地三辰亦有奉圭璋之礼,“奉璋”并非专指祭宗庙之礼。《大雅·皇矣》云:“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杨名时引《集韵》“嗜”字注与《礼记·月令》“节耆欲”,认为“耆”通“嗜”字,并解“上帝耆之”为“嗜好出于性情,圣人性与天合,故帝耆之也”③。《诗经》中的《大雅》《鲁颂》只称姜嫄,杨名时据《周礼·大司乐》叙“享先妣”于“享先祖”之上,认为周代郊稷专禘姜嫄,《诗经》之说与《周礼》相合。另《左传》载,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大夫叔孙婼到宋国聘问,宋公设宴款待,席间宋公赋《新宫》,叔孙婼赋《车辖》。后《新宫》失传,或以为《新宫》即《小雅·斯干》。杨名时据《仪礼》有言“下管《新宫》”,认为《仪礼》成于周之盛时,而《斯干》乃宣王之诗,故《新宫》不可能是《斯干》。诸如此类,四库馆臣称赞其《诗经劄记》“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皆具有考据,于其师说,可谓有所发明矣”①。
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江苏吴县人,惠栋之父。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改庶吉士,出李光地门。散馆授编修,后提督广东学政,官至侍读学士。惠士奇盛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于经学,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惠士奇之经学后为其子惠栋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形成乾嘉考据学中的吴派,推动清代考据学进入全盛时期。
惠士奇治《易》以象数为主,专宗汉学,征引极博,力矫王弼以来虚谈义理之弊。他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牺,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②惠士奇治《易》宗旨虽与李光地有所不同,但在解《易》的某些方面又有相似之处,或许亦曾受到李光地易学的影响。
惠士奇治礼学亦带有强烈的信古精神,以郑玄为宗,并旁求于周秦诸子,力图借此发明《周礼》的古盲古义乃周代典制之原貌。他说:“《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①四库馆臣称其《礼说》“于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底”②。
惠士奇治《春秋》以周礼为纲领,主要据“三传”立论。他说:“《春秋》三传,事莫详于《左氏》,论莫正于《谷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本周礼以记事也。《左氏》褒贬,皆春秋诸儒之论,故纪事皆实,而论或未公。《公羊》不信国史,惟笃信其师说,师所未言,则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诸国史,《公》《谷》得之师承,虽互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王通者,好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传作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赵匡之徒争攻三传,以伸其异说。夫《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然如坐暗室之中矣。《公》《谷》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也。后之学者当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若徒据《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力排而痛诋之,吾恐三传废而《春秋》亦随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学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无可疑,惑之甚者也。”③四库馆臣称其《春秋说》“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于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谷》。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大致出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门目,不设凡例。其引据证佐,则尤较二家为典核。虽其中灾异之类,反复辨诘,务申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未免过信汉儒,物而不化。然全书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元元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④。
冉觐祖,字永光,号蟫庵,河南中牟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改庶吉士,出李光地门。散馆授检讨,寻告归,曾主讲嵩阳书院与仪封请见书院。冉觐祖学通经史,兼采汉宋,而以朱子为归,著有《易经详说》《书经详说》《诗经详说》《礼记详说》《春秋详说》《孝经详说》《四书玩注详说》《性理纂要》《阳明疑案》《正蒙补训》等。康熙晚年敕令大臣纂修五经时,李光地曾以冉觐祖所著《五经详说》上闻,康熙帝命取其书以供采择。
冉觐祖治《易》以程朱为宗,折中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之说,辅以蔡清《易经蒙引》与林希元《易经存疑》,并博采诸儒之说足以羽翼程朱者。其易学兼顾义理与象数,注重卦辞的研究。在他看来,程颐《易传》以辞言理,而朱熹《周易本义》于卦爻言象占,于《彖传》往往言卦之变,例究之,亦不离乎辞。关于卦爻之象,冉觐祖肯定其出自圣人化工之笔,应认真推求取象之意,但其中有可解、有不可解者,若必欲穷究其取象何意,则不免陷于穿凿附会。冉觐祖亦主图书之学,认为《河图》《洛书》与《先后天图》皆与经旨有关,但图外生图,变化多端,则多经中用不及者。四库馆臣称其《易经详说》“兼用程《传》《本义》,谓朱子分象占,程《传》说理,二书不可偏废,故兼取二家之说,低一格以别于经。又采诸儒之说互相发明者,再低一格,以别于二家。觐祖时有所见,亦附著焉。其中亦间有与朱子异者。如朱子谓《左传》穆姜筮遇《艮》之八法,宜以‘系小子,失丈夫’为占,而史妄引彖辞为非。觐祖则谓《艮》卦只二不变,当为《随》,既以二为八,则非六二矣,当以彖辞为是,史非妄也。又谓文王八卦方位,未必分配父母男女,较量卦画阴阳,朱子从后推论,未必是文王当日之意。又不取卦变之说。盖大旨不出程朱,而小节则兼采诸论也”①。
冉觐祖治《尚书》以朱子学为宗,重在阐发义理。根据他的理解,“钦”字为《尚书》五十八篇之纲要。《尚书》所言之“钦”,即后世所言之“敬”。他举例道,《尚书》所言“敬修可愿”“敬哉有土”“懋敬厥德”“敬用五事”“王敬作所”“敬迓天威”,皆显言敬也;其言“克艰”“敬戒”“兢业”“同寅协恭”“慎乃在位”“祗台德先”“栗栗危惧”“克自抑畏”“不遑暇食”“夙夜不怠”,皆与“敬”文异而意同;而禹之戒傲,虺之戒满,尹之戒欲,召公之戒玩,周公之戒逸,则皆“敬”之反也。四库馆臣称其《书经详说》“以蔡《传》为主,旁引孔《传》、孔《疏》及宋元以下诸家之说以释之。虽引证颇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据诸说,而终以蔡《传》为主”①。
冉觐祖治《诗经》亦宗朱熹,多取朱熹《诗集传》与《朱子语类》之说,并旁采诸家讲义与《诗集传》相互发明。其于《诗序》之说亦未全盘否定,能够在阐释诗意时有所取舍。四库馆臣称其《诗经详说》“以朱子《集传》为主,仍采毛、郑、孔及宋元以下诸儒之说,附录于下。每章《小序》与《集传》并列,盖欲尊《集传》,而又不能尽弃《序》说;欲从《小序》,而又不敢显悖《传》文,故其案语,率依文讲解,往往模棱,间有自出新义者”②。
冉觐祖治《春秋》主“三传”及程颐《春秋传》与胡安国《春秋传》,博采杜预、何休、范宁、孔颖达、徐彦、杨士勋等人注疏,并加以阐明驳正。四库馆臣称其《春秋详说》“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采其邪心而成之。觐祖则谓父之令可行于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于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于非之说。于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征引诸家,颇伤芜漫,又略于考证,而详于议论”③。
冉觐祖治《礼记》主张汉宋兼采,认为仅读陈澔《礼记集说》而不睹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终属管窥之见,不能无扦格于其间。故其《礼记详说》于每篇经文后先举陈澔《集说》之解,再分列各家之说于后,主要取郑《注》、孔《疏》,汰其烦冗,录十之五六,兼采卫湜《礼记集说》、吴澄《礼记纂言》、郝敬《礼记通解》及坊本诸讲可取者,与陈澔《礼记集说》相互发明,以补陈澔之不足。若有辞义未尽者,则以己意为之申明。冉觐祖还提出,《礼记》虽是《仪礼》之传,但若专用《仪礼》,则不免徒存仪文器数而使习礼者终于茫昧,必须结合《礼记》,才能得探本穷源之论。而他之所以要使用这种采摭群言的“详说”形式,则是为了对治当时学者的空疏之弊,使得读者可以由详而得约,不欲其舍详而径约。
李光地门下,以王兰生最能传其音韵之学。王兰生,字振声,一字信芳,号坦斋,直隶交河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李光地督顺天学政,王兰生应童子试,为李光地所赏识,遂拔为第一,补县学生。后李光地升任直隶巡抚,又将王兰生录入保定莲池书院肄业,教以治经,旁及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光地拜文渊阁大学士,携王兰生进京,协助编纂《朱子全书》。后经李光地举荐,入直内廷,校勘《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又入蒙养斋分校《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卜筮精蕴》,并奉旨纂修《音韵阐微》。康熙六十年(1721),王兰生应会试落第,康熙帝以其久直内廷,学问优长,特赐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改庶吉士,校对《钦若历书》。次年,奉旨充武英殿总裁,纂修《骈字类篇》《子史精华》诸书。后授翰林院编修,署理国子监司业,提督浙江、安徽、陕西学政,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任三礼馆副总裁,补授刑部右侍郎,兼管礼部侍郎事。
王兰生的音韵学正是授自李光地。在他看来,当世所传等韵书清浊未分,元声不辨,而邵雍的《皇极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亦未能尽善尽美。其在李光地的主持下具体负责《音韵阐微》的编纂工作,贯彻、运用李光地的合声反切法,以满文五字类为声音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兼取各家之长,编成了当时最为完备的韵书,推动了清代音韵学的发展和完善,对后世的汉字标音工作亦影响甚大。同时,王兰生对四书五经亦颇有研究。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于武英殿召见王兰生,命讲《周易》之《乾》《坤》两卦,其能“抉疑释滞,精奥畅达”①。雍正三年(1725),王兰生署理国子监司业时,“期年讲《中庸》一部,《孟子》数大章,悉本李文贞公之指而畅之,衍为《太学讲义》二卷”②。
除此之外,李光地门下何焯、蔡世远、王之锐等人皆学兼汉宋,重视经学,于经义多有阐发。而蔡世远门下高弟雷鋐、官献瑶亦通经学。雷鋐既是清代中期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精擅理学,又能吸收考据学之长,注重考订经史疑义,辨析思想源流,于易学、礼学多有阐发。所著《读书偶记》多读经之札记,其中有近半篇幅在讨论易学。官献瑶为学主张治经以治身,教人于经中求道。其治《周易》《诗经》主李光地,治《尚书》主蔡沈、金履祥,治《周礼》主方苞,治《仪礼》主郑玄、敖继公、吴绂,学术视野较为宽广,并能斟酌众家,择其粹要,尤邃于礼学。著有《读易偶记》《尚书偶记》《尚书讲稿》《读诗偶记》《周官偶记》《仪礼读》《丧服私钞》《春秋传习录》《孝经刊误》等。
李光地从弟李光墺、李光型亦受业于光地,二人皆精研性理,兼治经学。李光墺,字广卿,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充《一统志》《八旗人物志》纂修官。后提督山东学政,奏请《春秋》四传宜并习,不宜独宗胡《传》;四氏学宜遍习,不得专习《毛诗》,均得旨允行。寻擢国子监司业,充三礼馆纂修官。著有《考工发明》等。李光型,字仪卿,雍正十一年(1733)以理学荐,特赐进士,授彰德府同知。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寻擢刑部主事,充三礼馆律吕纂修官。著有《易通正》《洪范解》《诗六义说》《文王世子解》《天问解》等。二人还合著有《二李经说》。
李光地之子钟伦、孙清植受学于光地、光坡,治经学皆有成就。李钟伦,字世得,李光地长子。康熙三十六年(1693)举人,尤嗜礼学,著有《周礼纂训》。其治《周礼》,从李光坡之法,列郑玄《注》、贾公彦《疏》于前,而以己意训之于后,多发前人所未发者。四库馆臣称其《周礼纂训》“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于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然如辨禘袷、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钟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于五人,讫于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于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余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①。
李清植,字立侯,号穆亭,李光地三子钟佐子。雍正二年(172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八年(1730),补右春坊中允,寻迁侍讲学士,提督浙江学政。乾隆七年(1742),奉旨分纂《仪礼》。次年,迁右庶子,擢詹事府詹事,充三礼馆副总裁,又升内阁学士,充武英殿总裁,兼理经史馆事,主持校刊《十三经》《二十四史》。乾隆九年(1744),升礼部左侍郎,寻病卒。李清植少时好《周易》,晚岁专攻礼学,著有《仪礼纂录》。其治《仪礼》,亦本李光坡之法,以郑《注》、贾《疏》为主,于经文下引录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与敖继公《仪礼集说》之语。于《注疏》未安之处,则别下己意以折中之,颇能驳正《注疏》之失。
李光坡表侄邓启元,受业于光坡,亦精通三礼。雍正五年(1727)获进士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纂修官,曾参与编纂三礼,著有《周官考注》《礼记注》等。
二 改革科举考试
尽管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福建朱子学者门下多通经之士,亦取得了不少经学研究成果,但若要大量培养经史实学方面的人才,扭转空疏不学的士风,仅靠若干学者的个人努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须从教育、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上加以变革。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之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便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奋斗目标,而考试的科目内容、评判标准和参考教材对于士子的读书、治学无疑起到了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标准既受到一时学术思潮与学术风气的影响,反过来又有力地巩固和推动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潮与学术风气。可以说,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社会后期始终维持其官方思想的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与科举制度的密切联系,始终被奉为科举程式而得以保障的。
自元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以后,科举制度逐渐规范定型。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首重四书,而五经仅须专一经应试。四书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五经亦多用程朱派理学家的传注。元代时,五经尚可参用汉唐诸儒的注疏,至明代颁行《四书五经大全》,专用宋元理学家的传注,则古注疏皆废。这一举动虽然进一步巩固了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但也导致了士人对经学原典与汉唐注疏的轻视和忽略,甚至只读《大全》、语录与各种时文讲章,而将经典弃之不顾,加剧了经学的衰落。故皮锡瑞称:“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全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经义考》所目为兔园册子者。故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①而这种情况在清初仍未发生明显改变。“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顺治)二年,颁《科场条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①
科举制度的这种弊端,及其对学术与士风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不满和抗议。如杨慎说:
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②
曹安云:
《周易》,人多读《本义》,不读《传》,不知《传》义不可阙;《书》,读《禹贡》节要;《诗》,不读变《风》《雅》;《春秋》,不详崩薨卒葬;《礼记》,《丧服》《大记》等多不考;《学》《庸》多不读《或问》;《论》《孟》多不读《序说》。经有节文,史有略本,百家诸氏之书,皆有纂集,以为一切目前苟且速成之诗。父兄以是夸子弟,师儒以是训学徒。近时书房,又刊时文,以炫末学,不使义理淹贯,可胜叹哉!③
黄宗羲亦言:
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冗,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障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①顾炎武则谓:
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与?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②
李光地显然也意识到了科举制度的这一弊病,故激烈批评道:“八股取士弊坏极矣,离却四书、五经不可”③,“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浮词填胸,千里一轨。遇题目相近,剽剥不让,公然相袭,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间或理致及典实题样,与所习相左,则荒疏杜撰,无一语中肯綮者”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光地主张将“汉、唐、宋试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专经义,守师说”⑤,提高经典内容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与重要性。譬如他说:,《周礼》经也,《公》《谷》于孔子为近,与《左氏》当列于学宫。首场试经说五篇,令学者述先儒之异同,而析其孰为是,孰为非。皆所不可,则自出己意。四书说三,经说二。只此,足觇穷经,多则敝士子之精力,无谓也。二场论二篇,《孝经》虽圣人之经,卷帙最少,不如易以《性理》《通鉴》。表判可去,恐声病之学遂废,兼采唐制,试诗二首。三场策三道。……又以五年试大科,俾兼通数经,习三《春秋》、三礼者,得殚所长。登斯选者,授以馆职,如殿一甲之例,亦不过数人而已。即以其年试天文、律历,专门名家,分别录用。如此,则士皆务实学。①
在李光地看来,科举考试“使士子传注是遵,格式是守,非固束天下之心思才智,而使之不得逞也”,而是为了“率天下尊经学古,游于圣贤之路”。②因此,他虽然仍旧注重在科举考试中考察有关程朱理学的内容,但也要求提高经典在科举考试中所占的分量,以培养尊经学古的风气。自元代以后,科举于三礼中仅试《礼记》一经,《周礼》与《仪礼》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清顺治二年(1645)颁布的《科场条例》规定,《春秋》主胡安国《传》,传统的《春秋》三传亦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对此,李光地不以为然,主张将《周礼》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列学宫,重新纳入学校的教授范围。他又提出,科举首场应试经说五篇,令考生就所给题目论述先儒注疏之异同,辨析其是非,并且允许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同时设立专门的经学考试,五年举行一次,考生须兼通数经,重点考察三礼与《春秋》“三传”,通过考试者授以翰林院官职。此外,还应设立有关天文、律历的考试,选拔专门人才,分别录用,以弘扬实学。
同时,李光地还主张将制义与经学结合起来,使其发挥羽翼经传的作用。在他看来,制义与经学本就相互关联,不应分割。“制举之文……其原盖出于义疏之流,而稍叶以俳俪者也。其法虽起于熙宁之新学,然观洛闽以来,训义讲说,用其体者多矣。盖穷经之学,以剖析为功,故谭经之文,亦不以栉比为病也。由是观之,制举而能有发于圣贤之意,有助于儒先之说,虽与义疏注解佐佑六经可也。”①因此,学者若欲在举业中学有所得,“则制义之根本六经也,其门户先儒也,讲诵而思索之,固即汉宋所谓专经之艺,穷理之功也,与习为浮艳而卒与古背驰者,不犹远乎?”②李光地认为,优秀的制义之文不仅足以佐佑六经,其至者甚至“语皆如经”。“如顾亭林‘且比化者’一节文,直驾守溪而上。盖字字有来历,精于经学,而其辞又能补经之所未备,而不悖于经,亦可为经矣。”③据此,李光地强调“吾所为汲汲焉勉子弟以制举业者,欲其借此以通经焉尔,循是以辨理焉耳”④。
科举不但与一时的学术、士风相关,而且是选拔政府官员的基本制度。在这方面,李光地亦积极肯定了以科举昌明经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强化了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意义。他说:“经尊而理明,则人心淳而世道泰,历世之科目为有用,而平日之占毕为有施矣。”⑤又说:“汉、唐、宋、明之盛,未有不泽于经术,使其文雅驯者也。故大为斯世之休征,上为国家之和应,然要不出于经明行修,则文不期醇而自醇。”⑥
因此,当李光地提督顺天学政时,便十分注意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培养经学人才。据《文贞公年谱》记载,当时“北方侵寻学废,公教以则古通经。有能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辞多者,稍成文,辄录以示劝,为之背诵至漏下二三鼓不倦。试日发题,先为解剥经旨,而后答义,极力起衰”⑦。《榕村谱录合考》亦载:“畿辅固多英俊,但沿俗学之弊,不习经书古文。公预示生童,有能背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百篇以上者,稍有文义,并拔擢之,以风励实学。日坐绛纱,生童有质问经义者,为之从容剖析,发蒙解惑,然后人知向学于古,不为俗儒曲说所诱。覆试或至十余次,文体一轨于正,非真才无得幸。”①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下诏,命李光地、郭琇等人就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各抒己见,提出解决方案。李光地于是上《条议学校科场疏》,提出了“学臣宜经考试”“教职宜稍清汰”“士习宜正”“经学宜崇”四项建议。其中,与科举考试内容直接相关的“经学宜崇”条说道:
皇上表章经术,以正学养天下士。而迩来学臣,率多苟且从事,以致士子荒经蔑古,自四书本经,不能记忆成诵。其能者,不过读时文百篇,剿习雷同,侥幸终身,殊非国家作养成就之意。前岁皇上旨下学臣,使童子入学兼用小学论一篇。其时幼稚见闻一新,胸中顿明古义,此则以正学诱人之明验也。然书不熟记,终非己得。宜令学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将经书、小学讲诵精熟者,文理粗成,便与录取。如更能成诵三经以至五经者,仍与补廪,以示鼓励。庶几人崇经学,稍助圣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通习小学,以端幼志,生员及科场论题似当兼命《性理》《纲目》,以励弘通。今《孝经》题目至少,以致每年科场论题重复雷同,似宜通变。②
在此,李光地的提议与其一贯的教育主张相一致,即在重视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高经学与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以培养通经学古的良好风气。而康熙帝亦对李光地的这一提议表示认可。是年十一月,朝廷根据郭琇、李光地等人的奏议,宣布:“嗣后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子弟,俱编入官字号,另入号房考试,各照定额。……童生内,有将经书、小学真能精熟,及能成诵三经、五经者,该学臣酌量优录。论题,将《性理》中《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书一并命题。”①
蔡世远作为一位拥有丰富书院教学经验,并长期在朝为官的朱子学者,亦对当时科举考试忽视经学而导致的空疏学风深为不满,批评“士子荒经久矣,剿袭撮摘,以涂有司之目,侮圣人之言,莫此为甚”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蔡世远对担负着选拔人才重任的学政一职寄予了特别关注,提出“学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风而变士习”③,希望通过学政的实际工作,培养、选拔通经学古、品行优良的人才,以扭转空疏放逸的学风士习。至于具体的措施与标准,蔡世远则主张借鉴汉唐的取士方法,经术与品行并重。他说:“昔两汉之选博士弟子员也,以好文学、敬长上、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为称选,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异等者以为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纵不能荐之于朝,私自褒扬,亦学政之大者。唐时有帖经墨义之科,今亦仿此意施之,使士子无荒经之患,于学者大有裨益。”④据此,蔡世远提议,学政到任伊始,即颁令于当地的县令、学官,要求“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闻,并上所实行;有能通经学古、奇才异能者以名闻,并上所论著。行之各属,揭之通衢”,并且“本之以诚心,加之以询访,择其真者而奖励之,或誉之于发落诸生之时,或荐之督抚,或表宅以优之。试竣,或延而面叩之,从容讲论,以验其所长。有行检不饬者,摘其尤而重黜责之。如是而士习不变者,未之有也”。⑤
同时,蔡世远亦认识到,学子荒废经学多是由于科举考试内容的不合理而造成,故提议学政“于岁科未试之先,通行于各学,曰:书艺二篇之外,不出经题,但依所限,抄录本经,多不过五行,少不过三行。不者,文虽佳,岁试降等,科试不录。科举至期,牌示曰:某经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各书于卷后。夫勒写数行本经,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诵,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场中又牌示曰:能成诵四经、五经者,庠生给饩禀,童子青其衿”①。如此,自然能敦促、引导广大学子重视经典,研习经学。
从康熙后期起,由李光地、蔡世远及其他学者共同提倡和推动的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譬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乡试,顺天南皿监生庄令舆、俞长策在考试第一场中,除了本经之外,兼作四书、五经文二十三篇,虽然违式,但仍奉旨授为举人,并旋著为令,即所谓“五经中式”。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先是,顺治二年,以士子博雅不在多篇,停五经中式。至康熙三十六年京闱乡试②,有五经二卷,特旨授为举人,后不为例。至是,礼部议,本年乡试,监生庄令舆、俞长策,试卷作五经文字,与例不合。奉谕旨,五经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当取中,若能切题旨,文理明顺,一日书写二万余字,实为难得。庄令舆、俞长策俱着授为举人,准其会试。嗣后作五经文字,不必禁止。作何定例,着九卿、詹事、科道议奏。寻议,嗣后乡、会试作五经文字者,应于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果多,另行题明酌夺。五经文字草稿不全,免其贴出。二场于论、表、判外添诏、诰各一道。头场备多页长卷,有愿作五经者,许本生禀明,给发从之。”③
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定乡、会试“五经中式”例,恢复“五经中式”之后,学子习五经者益众。在直隶、陕西等省的考试中,甚至出现以五经卷抡元者。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又增加“五经中式”名额,外省乡试增加一名,顺天增加二名,会试增加三名。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经中式”曾一度停止。雍正二年(1724)又再次恢复,规定“顺天皿字号中四名,各省每额九名加中一名。大省人多文佳,额外量取副榜三四名。四年丙午,诏是科以五经中副榜者,准作举人,一体会试,尤为特异”①。陆廷灿谓此为“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矣”②。
由于科举考试是传统社会中一项关乎无数读书人命运与各方面重大利益的基本制度,因而对其进行的任何改革与调整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其中必然充满了反复与曲折。同样,清初出现的要求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也是直到乾嘉时代才逐渐确定与巩固下来。譬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认为“设科立法程材,无取繁文虚饰”,而“今士子论、表、判、策,不过雷同剿说,而阅卷者亦止以书艺为重,即经文已不甚留意”,故下诏曰:“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如此,则士子闱中,不得复诿之于日力不给,而主试者亦可从容尽心详校,无鱼目碔砆之混。且乡试第二场止经文四篇,斯潦草完篇者,当在所黜。专经之士,得抒夙学,而浅陋者亦知所奋励,去浮文而求实效。”③这样,就将五经从四书附庸的位置独立出来,成为第二场考试的核心,取得了与四书约略同等的地位,有利于精通经学的考生取得更好的成绩,从而促使士子更加注重经学的学习。同时,艾尔曼指出,清代科举考试中“论”的科目与程朱宋学紧密相关,当时官员们关于论题去留的争论“说明了论题之删除,部分原因是乾隆年间(1736—1795年)更古的五经在汉学学者间普遍得到偏好”④。
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又因“士子束发授书,原应五经全读,向来止就本经按额取中,应试各生只知专治一经,揣摩诵习,而他经并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故规定自明年戊申乡试开始,乡、会试二场改用五经出题,先于五科内将五经依次轮试一周,然后再以五经并试,“既可令士子潜心经学,又可以杜绝场内关节弊端,而衡文取中,复不至限于经额,致佳卷被遗”。①如此,五经在科举中的重要性与考试要求显然又大大提高了。
此外,由于科举考试第一场与第二场的考查科目、命题方式、答题格式与评判标准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个人因素难以发挥过多的影响,故乾嘉时代拥有考据学背景的考官们往往还会利用第三场经史时务策的命题来表达自己的学术偏好,从而出现了许多经史考据类的策论试题。据艾尔曼考证,从18世纪晚期起,在北京、江南、山东、四川、陕西各地都出现了“乡试及会试考官在第三场的策论题中开始测验原先国家规定科目以外的技术性的考证题目”。据此他指出:“在乡试与会试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策论题,开始反映出操纵儒学科举的学术脉络之改变。虽然在乡试及会试的第一、二场所考的四书五经引文大多未曾改变且受制于正统程朱派解释,汉学趋势及考证问题仍能经由第三场的策论题渗入科举。”②而冯建民则指出,乾嘉时期由具有汉学背景的官员充任的乡、会试考官在评阅考卷时,往往会改变过去特重首场四书文的取士倾向,而是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后两场,尤其是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上。“这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对策最能反映出举子的学识水平。”③
诚然,不论是实行“五经中式”,还是增加科举考试中的经典内容,若是抽离出来孤立地看,都未必与经学研究的发展繁荣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若将李光地、蔡世远等学者提倡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放在清初经学复兴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与观照,则不难看出科举考试与学术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的密切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李光地、蔡世远等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扭转空疏学风、推动经学复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亦反映了当时理学与经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关系。
三 搜集、编纂、刊印经学典籍
清初福建朱子学者除了自身撰有各种经学著作之外,还以官方、团体或个人的身份整理、编纂、刊印了不少经学原典与经学研究著作,从而推动了清初经典编纂与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李光地为例,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光地奉旨承修《周易折中》一书。据《文贞公年谱》记载:“先是,上以《易》为六经之源,欲成一书,以惠万世,而郑重其事,未知所委。至是,屡出图象,命公采择,依义条答,与上意合,乃下谕曰:‘卿留心《河》《洛》久矣,见来书,愈知理明识远,此事非卿,万不能辨其是非。’遂命修之。”①其书“荟萃自汉迄明诸儒之说凡三百余家,采撷精纯,刊取领要,镕铸百氏,陶冶千载,《易》之道于是大备”②。而四库馆臣亦赞其“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谶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于伊川、紫阳,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惟一切支离幻渺之说,咸斥不录,不使溷四圣之遗文。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数千年画卦系辞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③。
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光地曾向皇帝进言:“秦汉以后,礼坏乐崩,六经虽经宋儒阐明,然永乐间所修《大全》未免芜杂疏漏,宜大征天下知学之士,搜罗群言,讨论编纂,以至礼乐制度,亦稽古论定,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诚千载一时也。”④康熙五十三年(1714),李光地又借向皇帝汇报《周易折中》编纂进展之机,“频言经学隆污,有关世运”,希望皇帝修明经学。而康熙帝亦认可李光地的提议,“遂分简大臣修纂《诗》《书》《春秋》,又别纂《律吕正义》,厘定韵学之书,皆命就公是正焉”①。就在其去世前一年,李光地仍“奉命勘阅大学士王掞等所纂《春秋传说》”②。应该说,康熙晚年敕令诸大臣纂修的这一套御纂诸经,上承唐代《五经正义》与明代《五经大全》,特别是在《五经大全》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增删,又参考了许多汇总性质的经学著作,收罗极为广泛,在当时发挥了引领学术风气与思想潮流的作用,在官修经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亦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中间,李光地的作用与贡献自然是功不可没的。正如清代中期福建著名经学家陈寿祺所言:“安溪李文贞公……博综群书,与顾亭林、梅定九二先生游,通律算、音韵之学,洞性命天人之旨,陶冶百氏,刊滌千载。尝奉敕纂《周易折中》《性理精义》《音韵阐微》《朱子全书》,以为非公莫能为,而《书诗春秋传说》《律吕正义》,分简诸大臣编纂,皆命就公是正,次第进御,颁行学官。盖康熙朝经术修明,自圣祖成之,自公发之,而后雍正、乾隆间继述众经,圣教由是大显。”③
同时,李光地个人亦搜集、刊印或协助他人刊印了一批重要的经学研究著作。其中,自然以李光地保护、抢救顾炎武《音学五书》刻版之事最为典型。在顾炎武生前,其开创性的古音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和推崇,但从更广的范围来观察,其古音学理论仍是知之者鲜,并不为当时的一般学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清初,从事古音学研究的也并非仅有顾氏一家,还包括毛奇龄、柴绍炳、毛先舒、邵长衡、李因笃、熊士伯等人,且大都有著作行世。如柴绍炳著有《古韵通》,毛先舒著有《韵学通指》,邵长衡著有《古今韵略》,李因笃著有《古今韵考》,熊士伯著有《古音正义》,但皆未采顾炎武的古音说。特别是毛奇龄的《古今通韵》,有意排斥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创为古韵通转说,因其获得官方的认可,由康熙帝诏付史馆刊印,故在当时拥有很强的权威性。
从顾炎武这方面来看,其《音学五书》竣稿之后,于康熙六年(1667)交由淮安山阳县好友张弨刊刻。对此,顾炎武曾自述道:“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①由于《音学五书》内容浩繁,刊刻难度较大,其间又经过顾炎武的反复修改,故刊刻工作时断时续,直到其去世前仍未全部刊出。对于先期刊出的部分,顾炎武亦厚自宝秘,不愿轻易示人,以其“为一生之独得……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②,并自言“五十年后乃有知我者耳”③,故希望将刻版藏之名山,以待后之信古者。由此可以推断,《音学五书》在最初仅有少量的出版印行,流传不广。而在顾炎武与张弨相继去世之后,张弨之子因为家贫,又将《音学五书》的刻版质于他人,遂流入坊间,不知所踪。
康熙四十六年(1707),李光地得知《音学五书》的刻版位于扬州坊间,且即将被毁坏,遂花费重金将书版赎出,并印行出版。《文贞公年谱》记载此事道:“顾氏是书既成,厚自珍秘,世无知者。顾氏既没,其版沉埋于扬州坊贾间。坊贾将削其版以镌它文,适有见者,以告公。公为赎归,传于世。”①正是由于李光地的及时抢救、保护与宣扬,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才能够在日后大行于世,并作为清学的开山之作受人敬仰,放射出莫大的光芒,否则这一传世之作很可能就此绝版而湮没无闻,后人也就无法在其基础上继续顾氏的古音学研究,取得如此多的成绩。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光地对于清代的古音学研究,甚至经学与考据学研究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清初福建朱子学者或奉朝廷之命,参与官方的经典编纂工程,或应书院、个人之邀,协助整理、编刻各类经典与经学研究著作,共同推动了清初经学的复兴与发展。
综上所述,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对于经典与经学研究还是普遍较为重视的。这既根源于朱子学本身的经学传统,又受到明末清初经学复兴运动的深刻影响,反映了当时学术潮流的变迁。清初福建朱子学者虽然并不认同汉儒以烦琐的训诂、考据、注疏为主要内容与手段的经学形态,甚至指责其未明圣贤之道,但亦不因此否认汉代经学的长处与价值,不仅表彰了汉儒的注经、传经之功,而且积极参考、借鉴其治经方法与治经成果来为自己的经学和理学研究服务。因此,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在治经中往往主张汉宋兼采,不立门户,将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结合起来,既为原本烦琐、庞杂的经学研究指引了方向,又可避免唯以己意解经的弊病,为日益流于虚妄的理学重新构筑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群体中,以李光地的经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成就亦最大。其不仅对于诸部经典都有较为细致的研究与讨论,而且影响和带动了一批学者从事经学研究,围绕其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尤其在易学与三礼学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清初福建朱子学者不但自身撰写了不少经学著作,而且在培养、奖掖经学人才,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搜集、编纂、刊印经学典籍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从而推动了清初经学的复兴与发展。
李光地身为清初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又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十
①(清)李光坡:《仪礼述注》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四库馆臣指出:“今考贾前《疏》云:‘酒浆皆以酳口’,谓二饮本并设以待宾用也。后《疏》云:‘浆以酳口,不用酒’,谓二饮虽并设,其实宾止用浆耳。前后一义相承,并无抵牾。杨氏殊未解《疏》意。至于郑《注》‘优宾’之义,亦谓宾酳口止用浆,而主人仍特设酒,故曰‘优宾’。下文之祭饮酒,乃宾加敬以报酳礼之优,与他篇献酬之酒、祭酒不同。观郑上《注》,明云饮酒非献酬之酒,则为饭后洁口之物可知。杨氏以设饮酒为优宾,而谓饮酒非以酳口,于郑《注》‘优宾’之义亦为未明。且考《周礼·酒人》曰:‘共宾客之礼酒,饮酒而奉之。’《注》:‘礼酒,飨燕之酒。饮酒,食之酒。’贾《疏》:‘饮酒,食之酒者,《曲礼》曰,酒浆处右,此非献酬之酒,是酳口之酒。’则杨氏谓饮酒非酳口之物,与《酒人》经注皆相矛盾矣。”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经部·礼类二》“仪礼述注”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页。
分热心于作育贤才,培植国本,门下名士硕学众多。诚如彭绍升所称,李光地“门下士杨名时、李绂、陈鹏年、赵申乔、冉觐祖、蔡世远并以德望重于时,它若张昺、张瑗、惠士奇、秦道然、王兰生、何焯、庄亨阳之徒,类有清节,通经能文章。故本朝诸巨公称善育材者,必以公为首焉”①。李光地曾指出:“今之学者,大抵搜华撷卉,为文辞之用而已。至于字义故实,书文形声,尚未有留意讲考于其间者。若大者为遗经源流,礼典同异,细而地名山川,史载人物,真赝是非之迹,则岂徒以朴学置之,抑其恶赜就简,而自恬于讹陋。呜呼!文武之道,岂有小大哉?万一朝廷举行石渠之典,吾知众籍罗凑,而莫之措辞,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②故其较为注重发掘、培养经学方面的人才,门下多通经学古与汉宋兼采之士,影响及于一时风气,推动了清初经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李光地门下治经学较有成就的学者主要有杨名时、惠士奇、冉觐祖等人。杨名时,字宾实,号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出李光地门。其学识深受李光地器重,故从李光地受经学。后因李光地举荐,得到康熙帝召对,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四十一年(1702),又因李光地的推荐,提督顺天学政,寻迁侍讲学士。康熙五十二年(1713),入直南书房,参与修校李光地主持的《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后累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云南巡抚、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吏部尚书等职。乾隆二年(1737)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杨名时治学范围较广,于诸经皆有讲义,尤重《周易》《诗经》,著有《周易劄记》《诗经劄记》《四书劄记》《经书言学指要》等。《清儒学案》称其“于《易》《诗》多本安溪之说,亦自有考订折衷,不尽附和”③。
杨名时治《易》以阐发义理为主,多采《周易折中》与《周易观彖》之说,在继承程朱《易》说和李光地《易》说的同时,亦有所发挥和修正,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杨名时治《易》还很重视图书之学,试图以阴阳消长与体用关系来说明《先后天图》的合理性。他说:“先后天之学,其道同归,而其说并行不悖者也。愚谓康节之学见疑于世,使是图而康节所自为,亦所谓先圣后圣,如合符节者矣。况证之以《大传》,参之以自汉而下儒伎诸书,阴阳消息进退之所,确然可据,则其学之有传,又岂可诬乎?”①四库馆臣称其《周易劄记》“多得之光地。虽《说卦传》及附论《启蒙》之类,颇推衍先天诸图,尚不至于支离附会。至其诠解经传,则纯以义理为宗,不涉象数。大抵于程朱之义,不为苟异,亦不为苟同,在宋学之中,可谓明白而笃实矣”②。
杨名时治《诗经》以李光地《诗》说为宗,并斟酌于《诗序》与朱熹《诗集传》之间。譬如,杨名时对《大序》十分赞赏,认为“读《大序》则知《诗》之教是从人之心志上养其善端,消其邪恶,以为美政教之本”③。论及《关雎》,杨名时亦取《小序》言后妃之德之说,提出:“大臣之职,莫大于求贤才,以佐朝廷之治。后妃之职,莫大于与贤淑,共成宫阃之化。后妃求淑女,此德之所以为至。味此诗,殆后妃所自作欤?”④关于《诗经》中的淫诗问题,杨名时则根据诗意与诗人作诗之动机判断《诗经》中存在淫诗。“今观《桑中》《同车》及《丰》之诗,皆似其人自作,非有刺讥之意,安得不谓之淫诗?且人之作诗,或美或刺,或述怀见志。若如旧说,是专有美刺,而无述怀见志之诗也,于理亦觉难通。”⑤而孔子之所以要在《诗经》中保存淫诗,是为了使读者引为鉴戒,“盖以著其风俗之恶,使人知卫所以亡,郑所以乱也”⑥。杨名时进一步指出,“郑声淫”即“郑诗淫”,“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有源有流,不相假易,安有诗言正而声律淫者乎”,又谓:“要之心中有哀,而以哀词填入哀调;心中有乐,而以乐词填入乐调,是哀乐仍生于心也。决无欲抒写好贤乐善、劝德规过之心,而用庄雅之词填入淫靡之调者。可见诗不淫而声淫,无是理也。”①但他同时强调,“郑声淫”主要指孔子未删《诗》时,郑、卫淫诗不可胜数。在孔子删《诗》之后,淫诗已去十之八九,只存十之一二,故郑诗亦多非淫诗。关于“思无邪”的解释,杨名时则从李光地自得之说,认为“‘邪’音‘余’,与‘余’同,《史记》历书‘归邪于终’,注:‘邪,余分也,终闰月也。’”
杨名时在《诗经》的训诂考据方面亦颇有可取之处。譬如,李光地认为,东周列国之《风》鲁国无备,故季札观乐所陈多为西周之诗。而杨名时则提出,东周之《风》列国具备,“东迁后,列国名卿学士辈留心礼乐典章,兼通当世之务者,类不乏人。平日则互相咨访,以广见闻;及出使,则赋诗赠答以见志,《左传》所称纪者甚繁。晋、宋、齐、郑皆然,不独鲁也。鲁秉周礼,崇文教为诸国望,于文章风雅之事必尤备焉。采辑所得,存之史氏,掌之太师,由来旧矣”,其又据“变《风》终于陈灵,陈灵弑于宣公十年,又越五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九年,而季札观乐”,推测“季札观乐即今所载各国《风》也”。③又如,《小雅·常棣》云:“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说者多谓此诗乃周公作于成王时,“死丧之威”指管叔、蔡叔叛乱之事,杨名时对此并不认同。他借鉴孔颖达等人的意见,④引《左传》富辰谏襄王之言“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认为周公封建既以管叔、蔡叔为首,则“二叔”当指夏、商之叔世,并非管、蔡二人,又引孔氏《毛诗正义》“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认为召穆公乃诵周公之诗,其目的在于“厉王时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诗,以亲之耳”。根据上述周人之说,及其对《常棣》诗意的理解,“且管、蔡所谓悖理乱常,公诛之出于万不得已,上伤文考宁王之心,下为终身莫释之憾,乃以此施于燕同姓兄弟之时,定为乐章,咏歌不置,揆诸情理之安,益多未协”,故杨名时坚持此诗乃周公作于文武之世,反对将“死丧之威”理解为管、蔡之事。①《召南·小星》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杨名时引《礼记》“三五而盈”,《古诗》“三五明月满”,认为“三五”指每月十五日月望之时,故此句之意是“月望时,月光满则星光为之夺。今小星嘒然在东,是不为月掩矣”②。《大雅·棫朴》云:“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朱熹认为此言祭宗庙之礼。而杨名时则引《周礼》所载,祭天地以苍璧、黄琮及珪,祀日月星辰以珪璧,礼四方以圭璋琥璜,认为祭天地三辰亦有奉圭璋之礼,“奉璋”并非专指祭宗庙之礼。《大雅·皇矣》云:“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杨名时引《集韵》“嗜”字注与《礼记·月令》“节耆欲”,认为“耆”通“嗜”字,并解“上帝耆之”为“嗜好出于性情,圣人性与天合,故帝耆之也”③。《诗经》中的《大雅》《鲁颂》只称姜嫄,杨名时据《周礼·大司乐》叙“享先妣”于“享先祖”之上,认为周代郊稷专禘姜嫄,《诗经》之说与《周礼》相合。另《左传》载,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大夫叔孙婼到宋国聘问,宋公设宴款待,席间宋公赋《新宫》,叔孙婼赋《车辖》。后《新宫》失传,或以为《新宫》即《小雅·斯干》。杨名时据《仪礼》有言“下管《新宫》”,认为《仪礼》成于周之盛时,而《斯干》乃宣王之诗,故《新宫》不可能是《斯干》。诸如此类,四库馆臣称赞其《诗经劄记》“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皆具有考据,于其师说,可谓有所发明矣”①。
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江苏吴县人,惠栋之父。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改庶吉士,出李光地门。散馆授编修,后提督广东学政,官至侍读学士。惠士奇盛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于经学,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惠士奇之经学后为其子惠栋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形成乾嘉考据学中的吴派,推动清代考据学进入全盛时期。
惠士奇治《易》以象数为主,专宗汉学,征引极博,力矫王弼以来虚谈义理之弊。他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牺,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②惠士奇治《易》宗旨虽与李光地有所不同,但在解《易》的某些方面又有相似之处,或许亦曾受到李光地易学的影响。
惠士奇治礼学亦带有强烈的信古精神,以郑玄为宗,并旁求于周秦诸子,力图借此发明《周礼》的古盲古义乃周代典制之原貌。他说:“《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①四库馆臣称其《礼说》“于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底”②。
惠士奇治《春秋》以周礼为纲领,主要据“三传”立论。他说:“《春秋》三传,事莫详于《左氏》,论莫正于《谷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本周礼以记事也。《左氏》褒贬,皆春秋诸儒之论,故纪事皆实,而论或未公。《公羊》不信国史,惟笃信其师说,师所未言,则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诸国史,《公》《谷》得之师承,虽互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王通者,好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传作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赵匡之徒争攻三传,以伸其异说。夫《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然如坐暗室之中矣。《公》《谷》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也。后之学者当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若徒据《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力排而痛诋之,吾恐三传废而《春秋》亦随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学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无可疑,惑之甚者也。”③四库馆臣称其《春秋说》“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于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谷》。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大致出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门目,不设凡例。其引据证佐,则尤较二家为典核。虽其中灾异之类,反复辨诘,务申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未免过信汉儒,物而不化。然全书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元元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④。
冉觐祖,字永光,号蟫庵,河南中牟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改庶吉士,出李光地门。散馆授检讨,寻告归,曾主讲嵩阳书院与仪封请见书院。冉觐祖学通经史,兼采汉宋,而以朱子为归,著有《易经详说》《书经详说》《诗经详说》《礼记详说》《春秋详说》《孝经详说》《四书玩注详说》《性理纂要》《阳明疑案》《正蒙补训》等。康熙晚年敕令大臣纂修五经时,李光地曾以冉觐祖所著《五经详说》上闻,康熙帝命取其书以供采择。
冉觐祖治《易》以程朱为宗,折中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之说,辅以蔡清《易经蒙引》与林希元《易经存疑》,并博采诸儒之说足以羽翼程朱者。其易学兼顾义理与象数,注重卦辞的研究。在他看来,程颐《易传》以辞言理,而朱熹《周易本义》于卦爻言象占,于《彖传》往往言卦之变,例究之,亦不离乎辞。关于卦爻之象,冉觐祖肯定其出自圣人化工之笔,应认真推求取象之意,但其中有可解、有不可解者,若必欲穷究其取象何意,则不免陷于穿凿附会。冉觐祖亦主图书之学,认为《河图》《洛书》与《先后天图》皆与经旨有关,但图外生图,变化多端,则多经中用不及者。四库馆臣称其《易经详说》“兼用程《传》《本义》,谓朱子分象占,程《传》说理,二书不可偏废,故兼取二家之说,低一格以别于经。又采诸儒之说互相发明者,再低一格,以别于二家。觐祖时有所见,亦附著焉。其中亦间有与朱子异者。如朱子谓《左传》穆姜筮遇《艮》之八法,宜以‘系小子,失丈夫’为占,而史妄引彖辞为非。觐祖则谓《艮》卦只二不变,当为《随》,既以二为八,则非六二矣,当以彖辞为是,史非妄也。又谓文王八卦方位,未必分配父母男女,较量卦画阴阳,朱子从后推论,未必是文王当日之意。又不取卦变之说。盖大旨不出程朱,而小节则兼采诸论也”①。
冉觐祖治《尚书》以朱子学为宗,重在阐发义理。根据他的理解,“钦”字为《尚书》五十八篇之纲要。《尚书》所言之“钦”,即后世所言之“敬”。他举例道,《尚书》所言“敬修可愿”“敬哉有土”“懋敬厥德”“敬用五事”“王敬作所”“敬迓天威”,皆显言敬也;其言“克艰”“敬戒”“兢业”“同寅协恭”“慎乃在位”“祗台德先”“栗栗危惧”“克自抑畏”“不遑暇食”“夙夜不怠”,皆与“敬”文异而意同;而禹之戒傲,虺之戒满,尹之戒欲,召公之戒玩,周公之戒逸,则皆“敬”之反也。四库馆臣称其《书经详说》“以蔡《传》为主,旁引孔《传》、孔《疏》及宋元以下诸家之说以释之。虽引证颇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据诸说,而终以蔡《传》为主”①。
冉觐祖治《诗经》亦宗朱熹,多取朱熹《诗集传》与《朱子语类》之说,并旁采诸家讲义与《诗集传》相互发明。其于《诗序》之说亦未全盘否定,能够在阐释诗意时有所取舍。四库馆臣称其《诗经详说》“以朱子《集传》为主,仍采毛、郑、孔及宋元以下诸儒之说,附录于下。每章《小序》与《集传》并列,盖欲尊《集传》,而又不能尽弃《序》说;欲从《小序》,而又不敢显悖《传》文,故其案语,率依文讲解,往往模棱,间有自出新义者”②。
冉觐祖治《春秋》主“三传”及程颐《春秋传》与胡安国《春秋传》,博采杜预、何休、范宁、孔颖达、徐彦、杨士勋等人注疏,并加以阐明驳正。四库馆臣称其《春秋详说》“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采其邪心而成之。觐祖则谓父之令可行于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于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于非之说。于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征引诸家,颇伤芜漫,又略于考证,而详于议论”③。
冉觐祖治《礼记》主张汉宋兼采,认为仅读陈澔《礼记集说》而不睹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终属管窥之见,不能无扦格于其间。故其《礼记详说》于每篇经文后先举陈澔《集说》之解,再分列各家之说于后,主要取郑《注》、孔《疏》,汰其烦冗,录十之五六,兼采卫湜《礼记集说》、吴澄《礼记纂言》、郝敬《礼记通解》及坊本诸讲可取者,与陈澔《礼记集说》相互发明,以补陈澔之不足。若有辞义未尽者,则以己意为之申明。冉觐祖还提出,《礼记》虽是《仪礼》之传,但若专用《仪礼》,则不免徒存仪文器数而使习礼者终于茫昧,必须结合《礼记》,才能得探本穷源之论。而他之所以要使用这种采摭群言的“详说”形式,则是为了对治当时学者的空疏之弊,使得读者可以由详而得约,不欲其舍详而径约。
李光地门下,以王兰生最能传其音韵之学。王兰生,字振声,一字信芳,号坦斋,直隶交河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李光地督顺天学政,王兰生应童子试,为李光地所赏识,遂拔为第一,补县学生。后李光地升任直隶巡抚,又将王兰生录入保定莲池书院肄业,教以治经,旁及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光地拜文渊阁大学士,携王兰生进京,协助编纂《朱子全书》。后经李光地举荐,入直内廷,校勘《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又入蒙养斋分校《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卜筮精蕴》,并奉旨纂修《音韵阐微》。康熙六十年(1721),王兰生应会试落第,康熙帝以其久直内廷,学问优长,特赐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改庶吉士,校对《钦若历书》。次年,奉旨充武英殿总裁,纂修《骈字类篇》《子史精华》诸书。后授翰林院编修,署理国子监司业,提督浙江、安徽、陕西学政,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任三礼馆副总裁,补授刑部右侍郎,兼管礼部侍郎事。
王兰生的音韵学正是授自李光地。在他看来,当世所传等韵书清浊未分,元声不辨,而邵雍的《皇极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亦未能尽善尽美。其在李光地的主持下具体负责《音韵阐微》的编纂工作,贯彻、运用李光地的合声反切法,以满文五字类为声音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兼取各家之长,编成了当时最为完备的韵书,推动了清代音韵学的发展和完善,对后世的汉字标音工作亦影响甚大。同时,王兰生对四书五经亦颇有研究。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于武英殿召见王兰生,命讲《周易》之《乾》《坤》两卦,其能“抉疑释滞,精奥畅达”①。雍正三年(1725),王兰生署理国子监司业时,“期年讲《中庸》一部,《孟子》数大章,悉本李文贞公之指而畅之,衍为《太学讲义》二卷”②。
除此之外,李光地门下何焯、蔡世远、王之锐等人皆学兼汉宋,重视经学,于经义多有阐发。而蔡世远门下高弟雷鋐、官献瑶亦通经学。雷鋐既是清代中期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精擅理学,又能吸收考据学之长,注重考订经史疑义,辨析思想源流,于易学、礼学多有阐发。所著《读书偶记》多读经之札记,其中有近半篇幅在讨论易学。官献瑶为学主张治经以治身,教人于经中求道。其治《周易》《诗经》主李光地,治《尚书》主蔡沈、金履祥,治《周礼》主方苞,治《仪礼》主郑玄、敖继公、吴绂,学术视野较为宽广,并能斟酌众家,择其粹要,尤邃于礼学。著有《读易偶记》《尚书偶记》《尚书讲稿》《读诗偶记》《周官偶记》《仪礼读》《丧服私钞》《春秋传习录》《孝经刊误》等。
李光地从弟李光墺、李光型亦受业于光地,二人皆精研性理,兼治经学。李光墺,字广卿,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充《一统志》《八旗人物志》纂修官。后提督山东学政,奏请《春秋》四传宜并习,不宜独宗胡《传》;四氏学宜遍习,不得专习《毛诗》,均得旨允行。寻擢国子监司业,充三礼馆纂修官。著有《考工发明》等。李光型,字仪卿,雍正十一年(1733)以理学荐,特赐进士,授彰德府同知。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寻擢刑部主事,充三礼馆律吕纂修官。著有《易通正》《洪范解》《诗六义说》《文王世子解》《天问解》等。二人还合著有《二李经说》。
李光地之子钟伦、孙清植受学于光地、光坡,治经学皆有成就。李钟伦,字世得,李光地长子。康熙三十六年(1693)举人,尤嗜礼学,著有《周礼纂训》。其治《周礼》,从李光坡之法,列郑玄《注》、贾公彦《疏》于前,而以己意训之于后,多发前人所未发者。四库馆臣称其《周礼纂训》“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于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然如辨禘袷、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钟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于五人,讫于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于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余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①。
李清植,字立侯,号穆亭,李光地三子钟佐子。雍正二年(172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八年(1730),补右春坊中允,寻迁侍讲学士,提督浙江学政。乾隆七年(1742),奉旨分纂《仪礼》。次年,迁右庶子,擢詹事府詹事,充三礼馆副总裁,又升内阁学士,充武英殿总裁,兼理经史馆事,主持校刊《十三经》《二十四史》。乾隆九年(1744),升礼部左侍郎,寻病卒。李清植少时好《周易》,晚岁专攻礼学,著有《仪礼纂录》。其治《仪礼》,亦本李光坡之法,以郑《注》、贾《疏》为主,于经文下引录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与敖继公《仪礼集说》之语。于《注疏》未安之处,则别下己意以折中之,颇能驳正《注疏》之失。
李光坡表侄邓启元,受业于光坡,亦精通三礼。雍正五年(1727)获进士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纂修官,曾参与编纂三礼,著有《周官考注》《礼记注》等。
二 改革科举考试
尽管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福建朱子学者门下多通经之士,亦取得了不少经学研究成果,但若要大量培养经史实学方面的人才,扭转空疏不学的士风,仅靠若干学者的个人努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须从教育、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上加以变革。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之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便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奋斗目标,而考试的科目内容、评判标准和参考教材对于士子的读书、治学无疑起到了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标准既受到一时学术思潮与学术风气的影响,反过来又有力地巩固和推动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潮与学术风气。可以说,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社会后期始终维持其官方思想的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与科举制度的密切联系,始终被奉为科举程式而得以保障的。
自元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以后,科举制度逐渐规范定型。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首重四书,而五经仅须专一经应试。四书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五经亦多用程朱派理学家的传注。元代时,五经尚可参用汉唐诸儒的注疏,至明代颁行《四书五经大全》,专用宋元理学家的传注,则古注疏皆废。这一举动虽然进一步巩固了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但也导致了士人对经学原典与汉唐注疏的轻视和忽略,甚至只读《大全》、语录与各种时文讲章,而将经典弃之不顾,加剧了经学的衰落。故皮锡瑞称:“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全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经义考》所目为兔园册子者。故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①而这种情况在清初仍未发生明显改变。“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顺治)二年,颁《科场条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①
科举制度的这种弊端,及其对学术与士风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不满和抗议。如杨慎说:
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②
曹安云:
《周易》,人多读《本义》,不读《传》,不知《传》义不可阙;《书》,读《禹贡》节要;《诗》,不读变《风》《雅》;《春秋》,不详崩薨卒葬;《礼记》,《丧服》《大记》等多不考;《学》《庸》多不读《或问》;《论》《孟》多不读《序说》。经有节文,史有略本,百家诸氏之书,皆有纂集,以为一切目前苟且速成之诗。父兄以是夸子弟,师儒以是训学徒。近时书房,又刊时文,以炫末学,不使义理淹贯,可胜叹哉!③
黄宗羲亦言:
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冗,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障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①顾炎武则谓:
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与?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②
李光地显然也意识到了科举制度的这一弊病,故激烈批评道:“八股取士弊坏极矣,离却四书、五经不可”③,“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浮词填胸,千里一轨。遇题目相近,剽剥不让,公然相袭,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间或理致及典实题样,与所习相左,则荒疏杜撰,无一语中肯綮者”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光地主张将“汉、唐、宋试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专经义,守师说”⑤,提高经典内容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与重要性。譬如他说:,《周礼》经也,《公》《谷》于孔子为近,与《左氏》当列于学宫。首场试经说五篇,令学者述先儒之异同,而析其孰为是,孰为非。皆所不可,则自出己意。四书说三,经说二。只此,足觇穷经,多则敝士子之精力,无谓也。二场论二篇,《孝经》虽圣人之经,卷帙最少,不如易以《性理》《通鉴》。表判可去,恐声病之学遂废,兼采唐制,试诗二首。三场策三道。……又以五年试大科,俾兼通数经,习三《春秋》、三礼者,得殚所长。登斯选者,授以馆职,如殿一甲之例,亦不过数人而已。即以其年试天文、律历,专门名家,分别录用。如此,则士皆务实学。①
在李光地看来,科举考试“使士子传注是遵,格式是守,非固束天下之心思才智,而使之不得逞也”,而是为了“率天下尊经学古,游于圣贤之路”。②因此,他虽然仍旧注重在科举考试中考察有关程朱理学的内容,但也要求提高经典在科举考试中所占的分量,以培养尊经学古的风气。自元代以后,科举于三礼中仅试《礼记》一经,《周礼》与《仪礼》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清顺治二年(1645)颁布的《科场条例》规定,《春秋》主胡安国《传》,传统的《春秋》三传亦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对此,李光地不以为然,主张将《周礼》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列学宫,重新纳入学校的教授范围。他又提出,科举首场应试经说五篇,令考生就所给题目论述先儒注疏之异同,辨析其是非,并且允许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同时设立专门的经学考试,五年举行一次,考生须兼通数经,重点考察三礼与《春秋》“三传”,通过考试者授以翰林院官职。此外,还应设立有关天文、律历的考试,选拔专门人才,分别录用,以弘扬实学。
同时,李光地还主张将制义与经学结合起来,使其发挥羽翼经传的作用。在他看来,制义与经学本就相互关联,不应分割。“制举之文……其原盖出于义疏之流,而稍叶以俳俪者也。其法虽起于熙宁之新学,然观洛闽以来,训义讲说,用其体者多矣。盖穷经之学,以剖析为功,故谭经之文,亦不以栉比为病也。由是观之,制举而能有发于圣贤之意,有助于儒先之说,虽与义疏注解佐佑六经可也。”①因此,学者若欲在举业中学有所得,“则制义之根本六经也,其门户先儒也,讲诵而思索之,固即汉宋所谓专经之艺,穷理之功也,与习为浮艳而卒与古背驰者,不犹远乎?”②李光地认为,优秀的制义之文不仅足以佐佑六经,其至者甚至“语皆如经”。“如顾亭林‘且比化者’一节文,直驾守溪而上。盖字字有来历,精于经学,而其辞又能补经之所未备,而不悖于经,亦可为经矣。”③据此,李光地强调“吾所为汲汲焉勉子弟以制举业者,欲其借此以通经焉尔,循是以辨理焉耳”④。
科举不但与一时的学术、士风相关,而且是选拔政府官员的基本制度。在这方面,李光地亦积极肯定了以科举昌明经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强化了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意义。他说:“经尊而理明,则人心淳而世道泰,历世之科目为有用,而平日之占毕为有施矣。”⑤又说:“汉、唐、宋、明之盛,未有不泽于经术,使其文雅驯者也。故大为斯世之休征,上为国家之和应,然要不出于经明行修,则文不期醇而自醇。”⑥
因此,当李光地提督顺天学政时,便十分注意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培养经学人才。据《文贞公年谱》记载,当时“北方侵寻学废,公教以则古通经。有能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辞多者,稍成文,辄录以示劝,为之背诵至漏下二三鼓不倦。试日发题,先为解剥经旨,而后答义,极力起衰”⑦。《榕村谱录合考》亦载:“畿辅固多英俊,但沿俗学之弊,不习经书古文。公预示生童,有能背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百篇以上者,稍有文义,并拔擢之,以风励实学。日坐绛纱,生童有质问经义者,为之从容剖析,发蒙解惑,然后人知向学于古,不为俗儒曲说所诱。覆试或至十余次,文体一轨于正,非真才无得幸。”①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下诏,命李光地、郭琇等人就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各抒己见,提出解决方案。李光地于是上《条议学校科场疏》,提出了“学臣宜经考试”“教职宜稍清汰”“士习宜正”“经学宜崇”四项建议。其中,与科举考试内容直接相关的“经学宜崇”条说道:
皇上表章经术,以正学养天下士。而迩来学臣,率多苟且从事,以致士子荒经蔑古,自四书本经,不能记忆成诵。其能者,不过读时文百篇,剿习雷同,侥幸终身,殊非国家作养成就之意。前岁皇上旨下学臣,使童子入学兼用小学论一篇。其时幼稚见闻一新,胸中顿明古义,此则以正学诱人之明验也。然书不熟记,终非己得。宜令学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将经书、小学讲诵精熟者,文理粗成,便与录取。如更能成诵三经以至五经者,仍与补廪,以示鼓励。庶几人崇经学,稍助圣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通习小学,以端幼志,生员及科场论题似当兼命《性理》《纲目》,以励弘通。今《孝经》题目至少,以致每年科场论题重复雷同,似宜通变。②
在此,李光地的提议与其一贯的教育主张相一致,即在重视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高经学与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以培养通经学古的良好风气。而康熙帝亦对李光地的这一提议表示认可。是年十一月,朝廷根据郭琇、李光地等人的奏议,宣布:“嗣后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子弟,俱编入官字号,另入号房考试,各照定额。……童生内,有将经书、小学真能精熟,及能成诵三经、五经者,该学臣酌量优录。论题,将《性理》中《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书一并命题。”①
蔡世远作为一位拥有丰富书院教学经验,并长期在朝为官的朱子学者,亦对当时科举考试忽视经学而导致的空疏学风深为不满,批评“士子荒经久矣,剿袭撮摘,以涂有司之目,侮圣人之言,莫此为甚”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蔡世远对担负着选拔人才重任的学政一职寄予了特别关注,提出“学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风而变士习”③,希望通过学政的实际工作,培养、选拔通经学古、品行优良的人才,以扭转空疏放逸的学风士习。至于具体的措施与标准,蔡世远则主张借鉴汉唐的取士方法,经术与品行并重。他说:“昔两汉之选博士弟子员也,以好文学、敬长上、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为称选,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异等者以为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纵不能荐之于朝,私自褒扬,亦学政之大者。唐时有帖经墨义之科,今亦仿此意施之,使士子无荒经之患,于学者大有裨益。”④据此,蔡世远提议,学政到任伊始,即颁令于当地的县令、学官,要求“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闻,并上所实行;有能通经学古、奇才异能者以名闻,并上所论著。行之各属,揭之通衢”,并且“本之以诚心,加之以询访,择其真者而奖励之,或誉之于发落诸生之时,或荐之督抚,或表宅以优之。试竣,或延而面叩之,从容讲论,以验其所长。有行检不饬者,摘其尤而重黜责之。如是而士习不变者,未之有也”。⑤
同时,蔡世远亦认识到,学子荒废经学多是由于科举考试内容的不合理而造成,故提议学政“于岁科未试之先,通行于各学,曰:书艺二篇之外,不出经题,但依所限,抄录本经,多不过五行,少不过三行。不者,文虽佳,岁试降等,科试不录。科举至期,牌示曰:某经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各书于卷后。夫勒写数行本经,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诵,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场中又牌示曰:能成诵四经、五经者,庠生给饩禀,童子青其衿”①。如此,自然能敦促、引导广大学子重视经典,研习经学。
从康熙后期起,由李光地、蔡世远及其他学者共同提倡和推动的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譬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乡试,顺天南皿监生庄令舆、俞长策在考试第一场中,除了本经之外,兼作四书、五经文二十三篇,虽然违式,但仍奉旨授为举人,并旋著为令,即所谓“五经中式”。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先是,顺治二年,以士子博雅不在多篇,停五经中式。至康熙三十六年京闱乡试②,有五经二卷,特旨授为举人,后不为例。至是,礼部议,本年乡试,监生庄令舆、俞长策,试卷作五经文字,与例不合。奉谕旨,五经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当取中,若能切题旨,文理明顺,一日书写二万余字,实为难得。庄令舆、俞长策俱着授为举人,准其会试。嗣后作五经文字,不必禁止。作何定例,着九卿、詹事、科道议奏。寻议,嗣后乡、会试作五经文字者,应于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果多,另行题明酌夺。五经文字草稿不全,免其贴出。二场于论、表、判外添诏、诰各一道。头场备多页长卷,有愿作五经者,许本生禀明,给发从之。”③
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定乡、会试“五经中式”例,恢复“五经中式”之后,学子习五经者益众。在直隶、陕西等省的考试中,甚至出现以五经卷抡元者。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又增加“五经中式”名额,外省乡试增加一名,顺天增加二名,会试增加三名。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经中式”曾一度停止。雍正二年(1724)又再次恢复,规定“顺天皿字号中四名,各省每额九名加中一名。大省人多文佳,额外量取副榜三四名。四年丙午,诏是科以五经中副榜者,准作举人,一体会试,尤为特异”①。陆廷灿谓此为“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矣”②。
由于科举考试是传统社会中一项关乎无数读书人命运与各方面重大利益的基本制度,因而对其进行的任何改革与调整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其中必然充满了反复与曲折。同样,清初出现的要求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也是直到乾嘉时代才逐渐确定与巩固下来。譬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认为“设科立法程材,无取繁文虚饰”,而“今士子论、表、判、策,不过雷同剿说,而阅卷者亦止以书艺为重,即经文已不甚留意”,故下诏曰:“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如此,则士子闱中,不得复诿之于日力不给,而主试者亦可从容尽心详校,无鱼目碔砆之混。且乡试第二场止经文四篇,斯潦草完篇者,当在所黜。专经之士,得抒夙学,而浅陋者亦知所奋励,去浮文而求实效。”③这样,就将五经从四书附庸的位置独立出来,成为第二场考试的核心,取得了与四书约略同等的地位,有利于精通经学的考生取得更好的成绩,从而促使士子更加注重经学的学习。同时,艾尔曼指出,清代科举考试中“论”的科目与程朱宋学紧密相关,当时官员们关于论题去留的争论“说明了论题之删除,部分原因是乾隆年间(1736—1795年)更古的五经在汉学学者间普遍得到偏好”④。
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又因“士子束发授书,原应五经全读,向来止就本经按额取中,应试各生只知专治一经,揣摩诵习,而他经并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故规定自明年戊申乡试开始,乡、会试二场改用五经出题,先于五科内将五经依次轮试一周,然后再以五经并试,“既可令士子潜心经学,又可以杜绝场内关节弊端,而衡文取中,复不至限于经额,致佳卷被遗”。①如此,五经在科举中的重要性与考试要求显然又大大提高了。
此外,由于科举考试第一场与第二场的考查科目、命题方式、答题格式与评判标准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个人因素难以发挥过多的影响,故乾嘉时代拥有考据学背景的考官们往往还会利用第三场经史时务策的命题来表达自己的学术偏好,从而出现了许多经史考据类的策论试题。据艾尔曼考证,从18世纪晚期起,在北京、江南、山东、四川、陕西各地都出现了“乡试及会试考官在第三场的策论题中开始测验原先国家规定科目以外的技术性的考证题目”。据此他指出:“在乡试与会试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策论题,开始反映出操纵儒学科举的学术脉络之改变。虽然在乡试及会试的第一、二场所考的四书五经引文大多未曾改变且受制于正统程朱派解释,汉学趋势及考证问题仍能经由第三场的策论题渗入科举。”②而冯建民则指出,乾嘉时期由具有汉学背景的官员充任的乡、会试考官在评阅考卷时,往往会改变过去特重首场四书文的取士倾向,而是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后两场,尤其是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上。“这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对策最能反映出举子的学识水平。”③
诚然,不论是实行“五经中式”,还是增加科举考试中的经典内容,若是抽离出来孤立地看,都未必与经学研究的发展繁荣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若将李光地、蔡世远等学者提倡重视经学的科举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放在清初经学复兴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与观照,则不难看出科举考试与学术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的密切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李光地、蔡世远等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扭转空疏学风、推动经学复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亦反映了当时理学与经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关系。
三 搜集、编纂、刊印经学典籍
清初福建朱子学者除了自身撰有各种经学著作之外,还以官方、团体或个人的身份整理、编纂、刊印了不少经学原典与经学研究著作,从而推动了清初经典编纂与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李光地为例,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光地奉旨承修《周易折中》一书。据《文贞公年谱》记载:“先是,上以《易》为六经之源,欲成一书,以惠万世,而郑重其事,未知所委。至是,屡出图象,命公采择,依义条答,与上意合,乃下谕曰:‘卿留心《河》《洛》久矣,见来书,愈知理明识远,此事非卿,万不能辨其是非。’遂命修之。”①其书“荟萃自汉迄明诸儒之说凡三百余家,采撷精纯,刊取领要,镕铸百氏,陶冶千载,《易》之道于是大备”②。而四库馆臣亦赞其“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谶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于伊川、紫阳,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惟一切支离幻渺之说,咸斥不录,不使溷四圣之遗文。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数千年画卦系辞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③。
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光地曾向皇帝进言:“秦汉以后,礼坏乐崩,六经虽经宋儒阐明,然永乐间所修《大全》未免芜杂疏漏,宜大征天下知学之士,搜罗群言,讨论编纂,以至礼乐制度,亦稽古论定,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诚千载一时也。”④康熙五十三年(1714),李光地又借向皇帝汇报《周易折中》编纂进展之机,“频言经学隆污,有关世运”,希望皇帝修明经学。而康熙帝亦认可李光地的提议,“遂分简大臣修纂《诗》《书》《春秋》,又别纂《律吕正义》,厘定韵学之书,皆命就公是正焉”①。就在其去世前一年,李光地仍“奉命勘阅大学士王掞等所纂《春秋传说》”②。应该说,康熙晚年敕令诸大臣纂修的这一套御纂诸经,上承唐代《五经正义》与明代《五经大全》,特别是在《五经大全》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增删,又参考了许多汇总性质的经学著作,收罗极为广泛,在当时发挥了引领学术风气与思想潮流的作用,在官修经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亦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中间,李光地的作用与贡献自然是功不可没的。正如清代中期福建著名经学家陈寿祺所言:“安溪李文贞公……博综群书,与顾亭林、梅定九二先生游,通律算、音韵之学,洞性命天人之旨,陶冶百氏,刊滌千载。尝奉敕纂《周易折中》《性理精义》《音韵阐微》《朱子全书》,以为非公莫能为,而《书诗春秋传说》《律吕正义》,分简诸大臣编纂,皆命就公是正,次第进御,颁行学官。盖康熙朝经术修明,自圣祖成之,自公发之,而后雍正、乾隆间继述众经,圣教由是大显。”③
同时,李光地个人亦搜集、刊印或协助他人刊印了一批重要的经学研究著作。其中,自然以李光地保护、抢救顾炎武《音学五书》刻版之事最为典型。在顾炎武生前,其开创性的古音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和推崇,但从更广的范围来观察,其古音学理论仍是知之者鲜,并不为当时的一般学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清初,从事古音学研究的也并非仅有顾氏一家,还包括毛奇龄、柴绍炳、毛先舒、邵长衡、李因笃、熊士伯等人,且大都有著作行世。如柴绍炳著有《古韵通》,毛先舒著有《韵学通指》,邵长衡著有《古今韵略》,李因笃著有《古今韵考》,熊士伯著有《古音正义》,但皆未采顾炎武的古音说。特别是毛奇龄的《古今通韵》,有意排斥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创为古韵通转说,因其获得官方的认可,由康熙帝诏付史馆刊印,故在当时拥有很强的权威性。
从顾炎武这方面来看,其《音学五书》竣稿之后,于康熙六年(1667)交由淮安山阳县好友张弨刊刻。对此,顾炎武曾自述道:“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①由于《音学五书》内容浩繁,刊刻难度较大,其间又经过顾炎武的反复修改,故刊刻工作时断时续,直到其去世前仍未全部刊出。对于先期刊出的部分,顾炎武亦厚自宝秘,不愿轻易示人,以其“为一生之独得……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②,并自言“五十年后乃有知我者耳”③,故希望将刻版藏之名山,以待后之信古者。由此可以推断,《音学五书》在最初仅有少量的出版印行,流传不广。而在顾炎武与张弨相继去世之后,张弨之子因为家贫,又将《音学五书》的刻版质于他人,遂流入坊间,不知所踪。
康熙四十六年(1707),李光地得知《音学五书》的刻版位于扬州坊间,且即将被毁坏,遂花费重金将书版赎出,并印行出版。《文贞公年谱》记载此事道:“顾氏是书既成,厚自珍秘,世无知者。顾氏既没,其版沉埋于扬州坊贾间。坊贾将削其版以镌它文,适有见者,以告公。公为赎归,传于世。”①正是由于李光地的及时抢救、保护与宣扬,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才能够在日后大行于世,并作为清学的开山之作受人敬仰,放射出莫大的光芒,否则这一传世之作很可能就此绝版而湮没无闻,后人也就无法在其基础上继续顾氏的古音学研究,取得如此多的成绩。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光地对于清代的古音学研究,甚至经学与考据学研究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清初福建朱子学者或奉朝廷之命,参与官方的经典编纂工程,或应书院、个人之邀,协助整理、编刻各类经典与经学研究著作,共同推动了清初经学的复兴与发展。
综上所述,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对于经典与经学研究还是普遍较为重视的。这既根源于朱子学本身的经学传统,又受到明末清初经学复兴运动的深刻影响,反映了当时学术潮流的变迁。清初福建朱子学者虽然并不认同汉儒以烦琐的训诂、考据、注疏为主要内容与手段的经学形态,甚至指责其未明圣贤之道,但亦不因此否认汉代经学的长处与价值,不仅表彰了汉儒的注经、传经之功,而且积极参考、借鉴其治经方法与治经成果来为自己的经学和理学研究服务。因此,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在治经中往往主张汉宋兼采,不立门户,将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结合起来,既为原本烦琐、庞杂的经学研究指引了方向,又可避免唯以己意解经的弊病,为日益流于虚妄的理学重新构筑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群体中,以李光地的经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成就亦最大。其不仅对于诸部经典都有较为细致的研究与讨论,而且影响和带动了一批学者从事经学研究,围绕其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尤其在易学与三礼学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清初福建朱子学者不但自身撰写了不少经学著作,而且在培养、奖掖经学人才,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搜集、编纂、刊印经学典籍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从而推动了清初经学的复兴与发展。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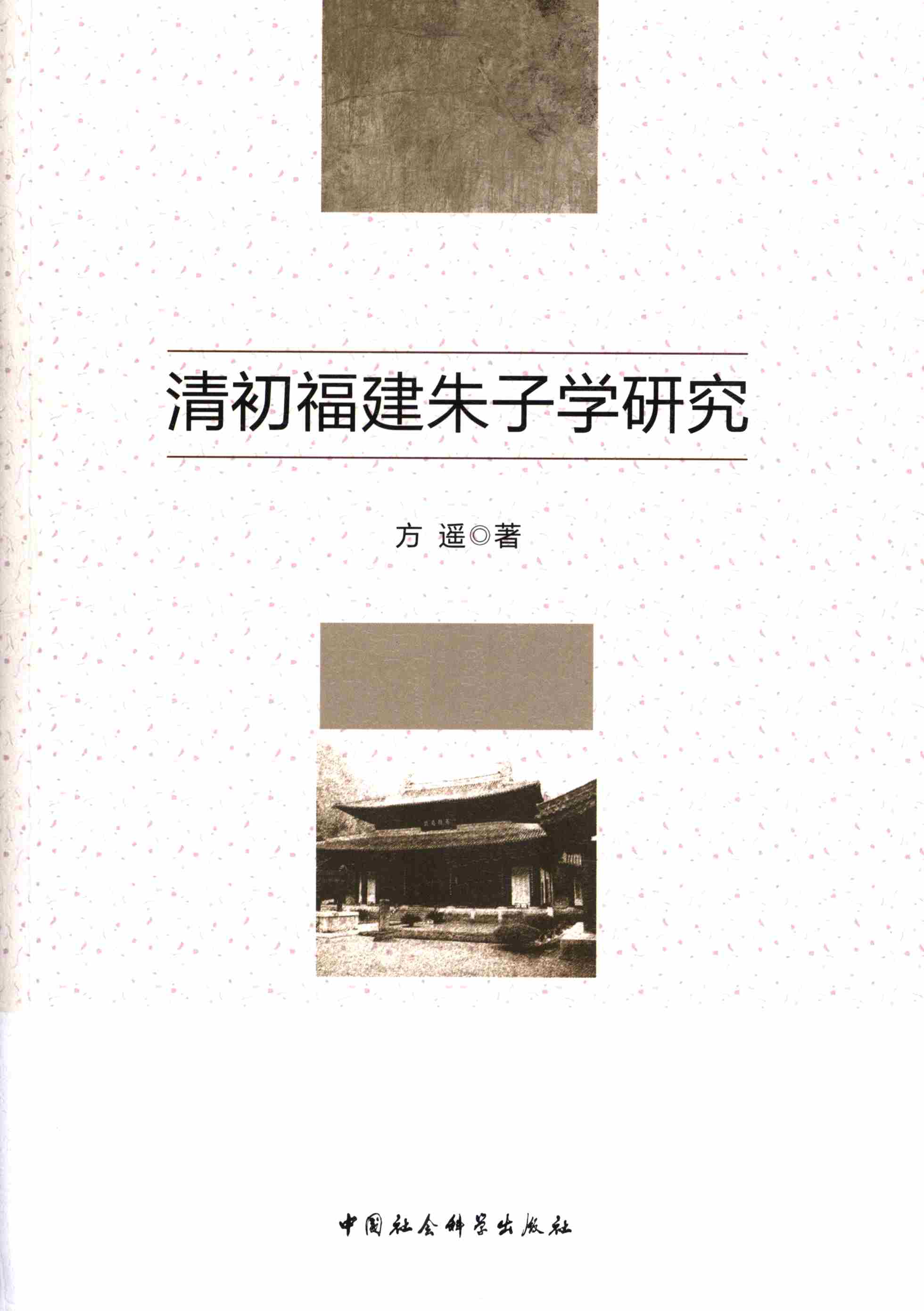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