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李光坡与《三礼述注》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89 |
| 颗粒名称: | 六 李光坡与《三礼述注》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481-491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清代经学以及儒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礼与礼学研究的重视和强调。特别是清代中期之后,一批清代学者(如戴震、段玉裁、任大椿、程瑶田、凌廷堪、焦循等)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三礼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校勘、整理、考辨、注解和阐发,并提出了“以礼代理”的思想主张。 |
| 关键词: | 清代经学 礼学 以礼代理 |
内容
清代经学以至于清代儒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对于礼与礼学研究的重视和强调。特别是清代中期之后,以戴震、段玉裁、任大椿、程瑶田、凌廷堪、焦循等皖派考据学家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三礼做了细致而深入的校勘、整理、考辨、注解和阐发,“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①,进而提出了“以礼代理”的思想主张。如凌廷堪曾说:“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如曰舍礼而可以复性也,必如释氏之幽深微眇而后可,若犹是圣人之道也,则舍礼奚由哉!盖性至隐也,而礼则见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礼则显焉者也。”②又说:“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知其然也,制礼以节之,自少壮以至耆耄,无一日不囿于礼,而莫之敢越也;制礼以防之,自冠昏以逮饮射,无一事不依乎礼,而莫之敢溃也。然后优柔厌饫,徐以复性,而至乎道。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别无所谓性道也。”③
其实,早在清初,以李光地、李光坡等安溪李氏学者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并用力于礼学的研究。他们虽未主张“以礼代理”之说,但亦对礼与礼学的意义和价值十分重视,在礼义、礼制、礼仪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李光坡积四十年之功所成的《三礼述注》最为突出。李光坡治三礼学不拘门户,择善而从,既大量借鉴、吸收以郑玄、孔颖达、贾公彦为代表的汉唐经学家的治经成果,又受到宋代以后儒者的礼学思想影响,与李光地的礼学研究相互呼应。兄弟二人经常就各种礼学问题展开讨论,《榕村语录》卷十四“三礼”部分的不少观点为李光坡所录,同时亦见于李光坡的《三礼述注》中,可视为二人共同的礼学思想成果。
《周礼述注》是李光坡完成的第一部三礼学著作,始撰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先后历时近二十年,修改八九次,终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成书。关于《周礼述注》的撰写缘由,李光坡自述道:“坡昔者年及壮始治《周礼》,患其难读,因求解于今人之所为注者,亦复惘然,后受《注疏》以卒业,得能成诵,而于诂释圣言之法,且微测其端绪”①,遂在李光地的鼓励之下,开始撰写《周礼述注》。其治《周礼》的基本方法是“本述《注疏》,搜索儒先,以相发明,更以愚见次其先后”②,即主要利用郑玄、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并搜集、参考其他先辈儒者的观点、解释,使其相互发明,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李光坡还将《周礼》与《仪礼》等经典相互参校,以确保经文“颇少舛讹”,并于“诸儒讲解,随所见到,亦多采摭”③,故能博采众长,而成一家之言。《周礼述注》卷首列有其所征引的诸儒姓氏,计有汉代孔安国、刘歆、杜子春、贾逵、郑众、马融、郑玄七家,唐代贾公彦、韩愈两家,宋代刘敞、王安石、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吕祖谦、张栻、黄榦等四十家,元代吴澄、毛应龙、邱葵三家,明代何乔新、魏校、徐常吉、王应电四家,清代顾景范、李光地、李钟伦三家,另有不详朝代名号者八家,总计六十七家。④由此可见其搜讨之广、用功之勤,亦略可窥见其研治《周礼》的大体思路与宗尚所在。
关于《周礼》一书,历代争论极多,或以为非出于圣人之手,或以为存在讹舛错简,故多遭学者改窜。对此,李光坡多不以为然。他批评道:“众说纷罗,或疑信相参,肆其触排,以为非圣之书;或借其大意,敷陈上下,如射策之文;或分割诸官,隶属颠倒。求其切实训诂,开解支条,自信于心,示信于人者,盖鲜欤。”①在李光坡看来,《周礼》确为圣人所作,其中蕴含了上古圣王之义理与大经大法。义理虽可由心传,礼法虽贵乎通变,但学者若欲明礼制之因革渊源与根本准则,则不可不求之于《周礼》。故曰:“唐虞之书,根底数语,夏商之礼,荒略无征。然明物察伦,所因所革,圣圣相授,远有渊源,则求观二帝三王所以反本修教之道者,舍是书何适乎?传其心者,虽存乎人,酌其通者,虽存乎变,而其正大之情,周密之义,如身焉,其血气之顺逆,至于一毛之拔,皆关于心;如治室焉,数计之书录之细大幽显,皆经于意,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虽百世而见之也,若揭焉。”②
李光坡进一步指出,礼与道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六经之书言道者,所以崇其知;言礼者,所以卑其行。知崇礼卑,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者都不可偏废。”③礼虽以形上之道作为根据,但又具有特定的外在形式,故“道之大原出于天,有废兴而无存亡”,而“礼乐制度一不讲学则扫地无余矣”④。因此,孔子、朱熹等历代圣贤都很注重礼的讲习与礼书的整理编纂,所谓“断简残编,依违顾惜,先圣后圣,为万世虑至深远也”,而李光坡治三礼亦坚持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原则,主张“缘其文,求其义,去其师心武断……原本先圣所以顾惜之意,固不必卑视训诂,妄指康成为支离已”。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制作之义。虽于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辞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又谓:“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恒多。又鉴于熙宁之新法,故恒牵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于注疏多所攻击,议论盛而经义反淆。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于说经之家,亦可谓适中之道矣。”①对于《周礼述注》的特点把握较为准确,可谓持平之论。
继《周礼述注》之后,李光坡又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完成《礼记述注》一书。关于《礼记述注》的撰写缘由,李光坡说道:
诸经注疏,共最《礼记》。朱子教学者看注看疏自好,然文字浩汗,班史谓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者,盖汉唐讲师之体尔也。……宋末有陈氏《集说》,学者喜其便,祧《注疏》而崇焉。明初为之《大全》,裒然列于太学。坡始受之,窃病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它说,以为可恨。夫祖谶莫过于《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郊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缕列,不特此也。考之全经,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与?又《礼器》篇斥后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预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解。时而指《注疏》为旧说,旧说似矣,时而著郑氏曰,《疏》曰,至著郑曰,《疏》曰,盎有德色,若不遗葑菲者。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后生,何以示诚乎?……至《大全》所集,尤为狼藉,未论其它,彼陈氏方恨孔惟郑从,不载它说,而其首例云一以《集说》为宗,不合者不取,何自悖也。②
李光坡指出,汉唐经师注解《礼记》虽然广博详核,但失之烦琐,不便阅读,故陈㵆所著《礼记集说》一经问世,便以其浅显简便的特点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欢迎。明初,《礼记集说》更被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永乐年间,胡广奉旨编修《五经大全》,《礼记》亦以陈澔《集说》为主,其他古注疏皆废。而李光坡却对《礼记集说》极为不满,既病其说未尽,又疑其心不诚。在他看来,《礼记集说》不仅在注解经文上不能令人满意,且对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的批评亦属无的放矢,错漏百出。更为严重的是,《礼记集说》对待郑《注》、孔《疏》的态度十分恶劣,既对其大肆批判,指为旧说,而其本身亦多约取《注疏》而成,了无新意,甚至有意通过对郑《注》、孔《疏》的征引来夸耀自己的广博与大度,可谓“抵冒前人”“欺负后生”的不诚之行。而《礼记大全》既从陈澔之说,批评孔《疏》惟郑《注》是从,而它自身又标榜一以陈澔《礼记集说》为宗,凡不合《集说》者皆弃而不取,可谓自相矛盾。
因此,与《周礼述注》类似,李光坡研治《礼记》亦采用“本述《注疏》”的方法,扬弃《礼记集说》与《礼记大全》,重新回到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的基本立场上,既充分思考、发掘郑《注》、孔《疏》的合理内容,又积极借鉴其注经方法。譬如,他曾称赞郑玄、孔颖达“注疏训说,正当脉络分明,真解经之体也。如陈氏所引,欲深反浅,欲切反泛”①1。同时,他还反对学者随意讥讽“汉唐儒者说理如梦”的风气,认为这是程朱为了“进人以知本”而说的,非程朱之大贤不能道,不能以此否定汉唐儒者在注经上的优点与贡献。对于陈澔杂合《注疏》与诸儒之说所成的《礼记集说》,李光坡亦未全盘否定,而是主张“或仍之,或以《注疏》增其未备,损其枝辞,标‘《集说》曰’,从其实也。凡诸篇皆妄,次第为之条理”②,使读者能够自行判断选择。
在此基础上,李光坡进一步提出了研究《礼记》的几条方法与原则。首先,李光坡认为应尊重《礼记》的权威性,认真理会其文义脉络,从中把握经典本义,而不应随意怀疑、贬低经典之文,或一味离经言理,务为新论。因此,他批评学者“今于《礼运》则轻其出于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其他整篇完文,多指为汉儒之傅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轶前人,恐未得其退舍也”①。李光坡相信,《礼记》中记载的孔子之言皆有其来源,并非出于后儒臆造,只不过由于记录者个人资质与理解的不同,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礼运》《乐记》,或云非洙泗微文,私心则疑不惟此也。凡此经及史、子之拾遗掇逸,谓是子言,意皆有自来,但至者有浅深,故所录有完阙耳。”②因此,对于《礼记》中存有疑问的内容,李光坡主张“随分尽心,至有厚薄醇醨之异,则存所疑,以质师友。公然妄骂,窃恐未能信人,徒先失己也”③。其次,李光坡主张《礼记》多为孔门弟子所作,而孔子家传之礼为殷礼,故《礼记》所述多是殷礼。若此,郑玄注解《礼记》多以殷礼为说便有其合理性,学者于此“当推寻究竟,未可遽斥臆说也”④。再次,李光坡主张“解经惟当求意义之合”⑤,不应将不同经文随意牵合比较,以避免出现朱熹所说的“彼此迷暗,互相连累”之弊。最后,李光坡指出,汉唐儒者去古未远,学识广博,在经学上有其长处,故后人治经须尊重汉唐儒者的传经、注经之功,避免“侈口经纬”“广张质文”的弊病。他说:“经文不解,指为傅会,《注疏》曲折,指为支离。然傅会者世近于古,支离者学多于吾,不顾理之是非,而漫为指斥,则将何所承受取信也?”⑥
由此不难看出,李光坡的《礼记述注》受到了汉学与朱子学的双重影响,并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所以他既强调“本述《注疏》”,又认为这是“朱子之教”。同时,李光坡在引用郑《注》、孔《疏》时,往往对其原文进行删节和取舍,或利用自己的语言加以重新阐述,从而使注解更为简洁易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①。
《仪礼述注》是李光坡《三礼述注》中的最后一部,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成书,标志着其三礼学研究的最终完成。其时距李光坡逝世亦仅有一年时间。《仪礼》一书主要记载周代士大夫的礼仪度数,名物繁富,文义古奥,又多讹脱衍倒之处,故于三礼中最称难读。“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注其书者,寥寥数家。即郝敬《完解》之类,稍著于世者,亦大抵影响揣摩,横生臆见。盖《周礼》犹可谈王谈霸,《礼记》犹可言敬言诚,《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避而不道也。”②为此,李光坡注解《仪礼》用功甚勤,以至“《仪礼》十七篇可以全文暗倍”③。
李光坡认为,《仪礼》所载之礼有“俭”“节”“均”三大要点。从其基本精神上看,《仪礼》“取其备物,不美其财贿,适其中节,不贵其多仪,贵者不重,贱者不虚,又为之摈相以诏之,成礼以及之,等级相役以授之,故国不费而礼常行,节不越而分各得,终事逮下,皆足不余”④。就其具体内容而言,“《仪礼》十七篇,冠、昏、相见、饮、射、聘、觐、丧、虞、馈食,所著其上下。衣服、冕服、丝衣、朝服、布衣、瓦尊、漆器、绤幂、萑席、牲狗、羊豕体、骨肉仪、黍稷、葅醢,乃定上下位著。室堂、帘阶、东西、门庭、坐立、远近、升降、裼袭、君父报礼、臣子拜伏,有数有度,乃及均惠。冠昏、媵御、饮射之钟人、阍人,馈食之私臣,有司皆与献酬,自尊及卑,次第以至,吉无止怠,凶无陵节,信俭矣,节矣,均矣”①。乍看之下,这些仪节度数似乎“至繁而非便”,其实“条理而精简”,故能使“敬意嘉于神人,欢心美于大小”②。另一方面,李光坡又提醒人们,切忌因其杂碎细小而轻视了这些仪节度数,以为无关紧要。因为“杂也,小也,正圣人所谓卑也。礼愈卑,则业愈广”③。何况这些礼仪背后的依据正是至大至善的天理与本性,所谓“大道依之,以为实体,精爽会之,以为守气”④。若要真正将其贯彻实行,“非节欲强力者,不足以终其事;非心存无放者,不足以纪其数;非忠厚惨怛者,不足以致其情”⑤,君子可不慎乎?
李光坡进一步指出,古礼于后世失落已久,遽复不易。若要复礼,则必须立定志向,并从“俭”“节”“均”三方面致力。“由今之礼,师古之意,服食用器,靡而朴之,俭可复也。上骄下谄,酌而通之,节可复也。尊者成礼,而后及次,贵者成礼,而后及贱,均可复也。文不相袭,道则不变,人自不复,非复之无由也。”⑥至于礼仪节文历来聚讼不休,无法统一的问题,李光坡认为这是由于“诸儒不分经传之失也”⑦。在他看来,《周礼》《仪礼》为经,其中集中保存了三代之礼,而《礼记》与《春秋》三传,以及子、史中谈及礼的内容都是传,是对经的解释、说明和补充。因此,议礼者须以经为主,以传为辅,“以传博经之详略,以经正传之是非。扬子谓,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圣存则人,圣亡则书,其统一也。知其统一,何聚讼之二乎?”⑧他举例道:“如郊社,《左氏》《公羊》《曲礼》皆言不卜,《谷梁》言卜,而《冢宰》有卜日则言卜,得矣。《晏子春秋》言四时祭祀皆用孟月,而《大司马》明著四仲则仲月,得矣。”①
由于《仪礼》主要记载的是具体的礼仪节文、名物度数,所以注解《仪礼》十分考验学者的训诂考据工夫。李光坡治《仪礼》虽然亦主要采用郑玄、贾公彦的《仪礼注疏》,总撮大义而节取其词,并间取诸家异同之说附于后,但在采择取舍之间仍不免瑕瑜互见。譬如,关于《士冠礼》中的“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李光坡解释道:“‘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妇人于丈夫皆侠拜,于子亦然,非先拜子也。”②四库馆臣称“其义最允”③。关于《丧服》中的“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万斯同以此为嫂叔有服之证,而李光坡则表示反对,亦不认同贾公彦“夫之从母”之说,主张这里的“兄弟”应指姊妹。他引《仪礼注疏·丧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妇,报”的注释“夫之姑、姊妹,夫为之期,妻降一等,出嫁小功,因恩疏,略从降,故在室及嫁同小功”,认为“兄弟盖指姊妹女兄弟也。季野失检,当再详之”④。对此,四库馆臣亦称赞其“深有抉择”⑤。
同时,四库馆臣对于《仪礼述注》亦有所批评,认为其书在征引郑《注》、贾《疏》时存在删削不当的问题,而旁采诸家之言亦有未审之处。譬如,《士冠礼》云:“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加柶,覆之,面叶。”郑玄注曰:“洗盥而洗爵者。《昏礼》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东隅,篚在洗东,北面盥。侧酌者,言无为之荐者。面,前也。叶,柶大端。赞酌者,宾尊,不入房。”①而李光坡在征引时删去了“侧酌者,言无为之荐者”与“赞酌者,宾尊,不入房”两句。四库馆臣认为“光坡节此二句,则宾不自酌而用赞者,义遂不明,为删所不应删矣”②。《士丧礼》云:“设决,丽于掔,自饭持之。设握,乃连掔。”郑玄注曰:“丽,施也。掔,手后节中也。饭,大擘指本也。决,以韦为之,籍有彄。彄内端为纽,外端有横带,设之,以纽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横带贯纽,结于掔之表也。设握者,以綦系钩中指,由手表与决带之余连结之。此谓右手也。古文丽亦为连,掔作捥。”③而李光坡在征引时删去了“古文丽亦为连,掔作捥”一句。对此,四库馆臣指出:“《注》载古文、今文,最关经义。如《士丧礼》‘设决,丽于掔’,《注》引古文‘掔’作‘捥’。考《管子·弟子职》‘饭必捧掔,羹不以手’;《吕览·本味篇》‘述荡之掔’,高诱注曰:‘掔,古手捥之字也。’据此,则以古文之‘捥’,证今文之‘掔’,义更明晰。而光坡概节之,亦为太简。”④
又如,《公食大夫礼》云:“饮酒、浆饮,俟于东房。”李光坡引“《注》曰:‘饮酒,清酒也。浆饮,酨浆也。其俟,奠于丰上也。饮酒先言饮,明非献酬之酒也。浆饮先言浆,别于六饮也。’《疏》曰:‘酨之言载,以其汁滓相载,故云酨。饮酒先言饮,此拟酳口,异于献酬酒。六饮为渴而饮,此浆为酳口,故异之’”⑤《公食大夫礼》又云:“宰夫右执觯,左执丰,进设于豆东。”李光坡先引“《注》曰:‘食有酒者,优宾也。设于豆东,不举也。《燕礼》记曰:凡奠者于左。’《疏》曰:‘按下文宰夫执浆饮,宾兴受。唯用浆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犹设之,是优宾也。此酒不用,故奠于豆东’”,后又引杨孚之说曰:“按上文‘饮酒、浆饮,俟于东房’,《疏》云‘酒浆皆以酳口’,此又云‘浆以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犹设之,所以优宾’,两说抵牾不同。又按下文‘祭饮酒于上豆之间,鱼腊酱湆不祭’。夫鱼腊酱湆不祭,而祭饮酒,则知酒以优宾,但宾不举尔,岂酳口之物哉?当以优宾之义为正。”①由此可见,李光坡倾向于杨孚的观点,认为此处设酒是为了表示优宾之义,并非酳口之物。而四库馆臣则以杨孚之说为非,批评“光坡取之,实未深考”②。
诚如陈祖武所言:“李光坡萃毕生心力于《三礼》学研究。他在这一领域中所留下的三部著述,虽然只是历代经学家研究所得的汇集,并没有提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创见,但是,不为汉、宋学门户之争所拘囿,‘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为后来的《三礼》学研究者,也确实提供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料。”③
其实,早在清初,以李光地、李光坡等安溪李氏学者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并用力于礼学的研究。他们虽未主张“以礼代理”之说,但亦对礼与礼学的意义和价值十分重视,在礼义、礼制、礼仪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李光坡积四十年之功所成的《三礼述注》最为突出。李光坡治三礼学不拘门户,择善而从,既大量借鉴、吸收以郑玄、孔颖达、贾公彦为代表的汉唐经学家的治经成果,又受到宋代以后儒者的礼学思想影响,与李光地的礼学研究相互呼应。兄弟二人经常就各种礼学问题展开讨论,《榕村语录》卷十四“三礼”部分的不少观点为李光坡所录,同时亦见于李光坡的《三礼述注》中,可视为二人共同的礼学思想成果。
《周礼述注》是李光坡完成的第一部三礼学著作,始撰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先后历时近二十年,修改八九次,终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成书。关于《周礼述注》的撰写缘由,李光坡自述道:“坡昔者年及壮始治《周礼》,患其难读,因求解于今人之所为注者,亦复惘然,后受《注疏》以卒业,得能成诵,而于诂释圣言之法,且微测其端绪”①,遂在李光地的鼓励之下,开始撰写《周礼述注》。其治《周礼》的基本方法是“本述《注疏》,搜索儒先,以相发明,更以愚见次其先后”②,即主要利用郑玄、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并搜集、参考其他先辈儒者的观点、解释,使其相互发明,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李光坡还将《周礼》与《仪礼》等经典相互参校,以确保经文“颇少舛讹”,并于“诸儒讲解,随所见到,亦多采摭”③,故能博采众长,而成一家之言。《周礼述注》卷首列有其所征引的诸儒姓氏,计有汉代孔安国、刘歆、杜子春、贾逵、郑众、马融、郑玄七家,唐代贾公彦、韩愈两家,宋代刘敞、王安石、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吕祖谦、张栻、黄榦等四十家,元代吴澄、毛应龙、邱葵三家,明代何乔新、魏校、徐常吉、王应电四家,清代顾景范、李光地、李钟伦三家,另有不详朝代名号者八家,总计六十七家。④由此可见其搜讨之广、用功之勤,亦略可窥见其研治《周礼》的大体思路与宗尚所在。
关于《周礼》一书,历代争论极多,或以为非出于圣人之手,或以为存在讹舛错简,故多遭学者改窜。对此,李光坡多不以为然。他批评道:“众说纷罗,或疑信相参,肆其触排,以为非圣之书;或借其大意,敷陈上下,如射策之文;或分割诸官,隶属颠倒。求其切实训诂,开解支条,自信于心,示信于人者,盖鲜欤。”①在李光坡看来,《周礼》确为圣人所作,其中蕴含了上古圣王之义理与大经大法。义理虽可由心传,礼法虽贵乎通变,但学者若欲明礼制之因革渊源与根本准则,则不可不求之于《周礼》。故曰:“唐虞之书,根底数语,夏商之礼,荒略无征。然明物察伦,所因所革,圣圣相授,远有渊源,则求观二帝三王所以反本修教之道者,舍是书何适乎?传其心者,虽存乎人,酌其通者,虽存乎变,而其正大之情,周密之义,如身焉,其血气之顺逆,至于一毛之拔,皆关于心;如治室焉,数计之书录之细大幽显,皆经于意,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虽百世而见之也,若揭焉。”②
李光坡进一步指出,礼与道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六经之书言道者,所以崇其知;言礼者,所以卑其行。知崇礼卑,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者都不可偏废。”③礼虽以形上之道作为根据,但又具有特定的外在形式,故“道之大原出于天,有废兴而无存亡”,而“礼乐制度一不讲学则扫地无余矣”④。因此,孔子、朱熹等历代圣贤都很注重礼的讲习与礼书的整理编纂,所谓“断简残编,依违顾惜,先圣后圣,为万世虑至深远也”,而李光坡治三礼亦坚持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原则,主张“缘其文,求其义,去其师心武断……原本先圣所以顾惜之意,固不必卑视训诂,妄指康成为支离已”。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制作之义。虽于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辞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又谓:“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恒多。又鉴于熙宁之新法,故恒牵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于注疏多所攻击,议论盛而经义反淆。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于说经之家,亦可谓适中之道矣。”①对于《周礼述注》的特点把握较为准确,可谓持平之论。
继《周礼述注》之后,李光坡又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完成《礼记述注》一书。关于《礼记述注》的撰写缘由,李光坡说道:
诸经注疏,共最《礼记》。朱子教学者看注看疏自好,然文字浩汗,班史谓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者,盖汉唐讲师之体尔也。……宋末有陈氏《集说》,学者喜其便,祧《注疏》而崇焉。明初为之《大全》,裒然列于太学。坡始受之,窃病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它说,以为可恨。夫祖谶莫过于《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郊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缕列,不特此也。考之全经,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与?又《礼器》篇斥后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预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解。时而指《注疏》为旧说,旧说似矣,时而著郑氏曰,《疏》曰,至著郑曰,《疏》曰,盎有德色,若不遗葑菲者。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后生,何以示诚乎?……至《大全》所集,尤为狼藉,未论其它,彼陈氏方恨孔惟郑从,不载它说,而其首例云一以《集说》为宗,不合者不取,何自悖也。②
李光坡指出,汉唐经师注解《礼记》虽然广博详核,但失之烦琐,不便阅读,故陈㵆所著《礼记集说》一经问世,便以其浅显简便的特点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欢迎。明初,《礼记集说》更被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永乐年间,胡广奉旨编修《五经大全》,《礼记》亦以陈澔《集说》为主,其他古注疏皆废。而李光坡却对《礼记集说》极为不满,既病其说未尽,又疑其心不诚。在他看来,《礼记集说》不仅在注解经文上不能令人满意,且对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的批评亦属无的放矢,错漏百出。更为严重的是,《礼记集说》对待郑《注》、孔《疏》的态度十分恶劣,既对其大肆批判,指为旧说,而其本身亦多约取《注疏》而成,了无新意,甚至有意通过对郑《注》、孔《疏》的征引来夸耀自己的广博与大度,可谓“抵冒前人”“欺负后生”的不诚之行。而《礼记大全》既从陈澔之说,批评孔《疏》惟郑《注》是从,而它自身又标榜一以陈澔《礼记集说》为宗,凡不合《集说》者皆弃而不取,可谓自相矛盾。
因此,与《周礼述注》类似,李光坡研治《礼记》亦采用“本述《注疏》”的方法,扬弃《礼记集说》与《礼记大全》,重新回到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的基本立场上,既充分思考、发掘郑《注》、孔《疏》的合理内容,又积极借鉴其注经方法。譬如,他曾称赞郑玄、孔颖达“注疏训说,正当脉络分明,真解经之体也。如陈氏所引,欲深反浅,欲切反泛”①1。同时,他还反对学者随意讥讽“汉唐儒者说理如梦”的风气,认为这是程朱为了“进人以知本”而说的,非程朱之大贤不能道,不能以此否定汉唐儒者在注经上的优点与贡献。对于陈澔杂合《注疏》与诸儒之说所成的《礼记集说》,李光坡亦未全盘否定,而是主张“或仍之,或以《注疏》增其未备,损其枝辞,标‘《集说》曰’,从其实也。凡诸篇皆妄,次第为之条理”②,使读者能够自行判断选择。
在此基础上,李光坡进一步提出了研究《礼记》的几条方法与原则。首先,李光坡认为应尊重《礼记》的权威性,认真理会其文义脉络,从中把握经典本义,而不应随意怀疑、贬低经典之文,或一味离经言理,务为新论。因此,他批评学者“今于《礼运》则轻其出于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其他整篇完文,多指为汉儒之傅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轶前人,恐未得其退舍也”①。李光坡相信,《礼记》中记载的孔子之言皆有其来源,并非出于后儒臆造,只不过由于记录者个人资质与理解的不同,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礼运》《乐记》,或云非洙泗微文,私心则疑不惟此也。凡此经及史、子之拾遗掇逸,谓是子言,意皆有自来,但至者有浅深,故所录有完阙耳。”②因此,对于《礼记》中存有疑问的内容,李光坡主张“随分尽心,至有厚薄醇醨之异,则存所疑,以质师友。公然妄骂,窃恐未能信人,徒先失己也”③。其次,李光坡主张《礼记》多为孔门弟子所作,而孔子家传之礼为殷礼,故《礼记》所述多是殷礼。若此,郑玄注解《礼记》多以殷礼为说便有其合理性,学者于此“当推寻究竟,未可遽斥臆说也”④。再次,李光坡主张“解经惟当求意义之合”⑤,不应将不同经文随意牵合比较,以避免出现朱熹所说的“彼此迷暗,互相连累”之弊。最后,李光坡指出,汉唐儒者去古未远,学识广博,在经学上有其长处,故后人治经须尊重汉唐儒者的传经、注经之功,避免“侈口经纬”“广张质文”的弊病。他说:“经文不解,指为傅会,《注疏》曲折,指为支离。然傅会者世近于古,支离者学多于吾,不顾理之是非,而漫为指斥,则将何所承受取信也?”⑥
由此不难看出,李光坡的《礼记述注》受到了汉学与朱子学的双重影响,并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所以他既强调“本述《注疏》”,又认为这是“朱子之教”。同时,李光坡在引用郑《注》、孔《疏》时,往往对其原文进行删节和取舍,或利用自己的语言加以重新阐述,从而使注解更为简洁易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①。
《仪礼述注》是李光坡《三礼述注》中的最后一部,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成书,标志着其三礼学研究的最终完成。其时距李光坡逝世亦仅有一年时间。《仪礼》一书主要记载周代士大夫的礼仪度数,名物繁富,文义古奥,又多讹脱衍倒之处,故于三礼中最称难读。“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注其书者,寥寥数家。即郝敬《完解》之类,稍著于世者,亦大抵影响揣摩,横生臆见。盖《周礼》犹可谈王谈霸,《礼记》犹可言敬言诚,《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避而不道也。”②为此,李光坡注解《仪礼》用功甚勤,以至“《仪礼》十七篇可以全文暗倍”③。
李光坡认为,《仪礼》所载之礼有“俭”“节”“均”三大要点。从其基本精神上看,《仪礼》“取其备物,不美其财贿,适其中节,不贵其多仪,贵者不重,贱者不虚,又为之摈相以诏之,成礼以及之,等级相役以授之,故国不费而礼常行,节不越而分各得,终事逮下,皆足不余”④。就其具体内容而言,“《仪礼》十七篇,冠、昏、相见、饮、射、聘、觐、丧、虞、馈食,所著其上下。衣服、冕服、丝衣、朝服、布衣、瓦尊、漆器、绤幂、萑席、牲狗、羊豕体、骨肉仪、黍稷、葅醢,乃定上下位著。室堂、帘阶、东西、门庭、坐立、远近、升降、裼袭、君父报礼、臣子拜伏,有数有度,乃及均惠。冠昏、媵御、饮射之钟人、阍人,馈食之私臣,有司皆与献酬,自尊及卑,次第以至,吉无止怠,凶无陵节,信俭矣,节矣,均矣”①。乍看之下,这些仪节度数似乎“至繁而非便”,其实“条理而精简”,故能使“敬意嘉于神人,欢心美于大小”②。另一方面,李光坡又提醒人们,切忌因其杂碎细小而轻视了这些仪节度数,以为无关紧要。因为“杂也,小也,正圣人所谓卑也。礼愈卑,则业愈广”③。何况这些礼仪背后的依据正是至大至善的天理与本性,所谓“大道依之,以为实体,精爽会之,以为守气”④。若要真正将其贯彻实行,“非节欲强力者,不足以终其事;非心存无放者,不足以纪其数;非忠厚惨怛者,不足以致其情”⑤,君子可不慎乎?
李光坡进一步指出,古礼于后世失落已久,遽复不易。若要复礼,则必须立定志向,并从“俭”“节”“均”三方面致力。“由今之礼,师古之意,服食用器,靡而朴之,俭可复也。上骄下谄,酌而通之,节可复也。尊者成礼,而后及次,贵者成礼,而后及贱,均可复也。文不相袭,道则不变,人自不复,非复之无由也。”⑥至于礼仪节文历来聚讼不休,无法统一的问题,李光坡认为这是由于“诸儒不分经传之失也”⑦。在他看来,《周礼》《仪礼》为经,其中集中保存了三代之礼,而《礼记》与《春秋》三传,以及子、史中谈及礼的内容都是传,是对经的解释、说明和补充。因此,议礼者须以经为主,以传为辅,“以传博经之详略,以经正传之是非。扬子谓,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圣存则人,圣亡则书,其统一也。知其统一,何聚讼之二乎?”⑧他举例道:“如郊社,《左氏》《公羊》《曲礼》皆言不卜,《谷梁》言卜,而《冢宰》有卜日则言卜,得矣。《晏子春秋》言四时祭祀皆用孟月,而《大司马》明著四仲则仲月,得矣。”①
由于《仪礼》主要记载的是具体的礼仪节文、名物度数,所以注解《仪礼》十分考验学者的训诂考据工夫。李光坡治《仪礼》虽然亦主要采用郑玄、贾公彦的《仪礼注疏》,总撮大义而节取其词,并间取诸家异同之说附于后,但在采择取舍之间仍不免瑕瑜互见。譬如,关于《士冠礼》中的“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李光坡解释道:“‘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妇人于丈夫皆侠拜,于子亦然,非先拜子也。”②四库馆臣称“其义最允”③。关于《丧服》中的“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万斯同以此为嫂叔有服之证,而李光坡则表示反对,亦不认同贾公彦“夫之从母”之说,主张这里的“兄弟”应指姊妹。他引《仪礼注疏·丧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妇,报”的注释“夫之姑、姊妹,夫为之期,妻降一等,出嫁小功,因恩疏,略从降,故在室及嫁同小功”,认为“兄弟盖指姊妹女兄弟也。季野失检,当再详之”④。对此,四库馆臣亦称赞其“深有抉择”⑤。
同时,四库馆臣对于《仪礼述注》亦有所批评,认为其书在征引郑《注》、贾《疏》时存在删削不当的问题,而旁采诸家之言亦有未审之处。譬如,《士冠礼》云:“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加柶,覆之,面叶。”郑玄注曰:“洗盥而洗爵者。《昏礼》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东隅,篚在洗东,北面盥。侧酌者,言无为之荐者。面,前也。叶,柶大端。赞酌者,宾尊,不入房。”①而李光坡在征引时删去了“侧酌者,言无为之荐者”与“赞酌者,宾尊,不入房”两句。四库馆臣认为“光坡节此二句,则宾不自酌而用赞者,义遂不明,为删所不应删矣”②。《士丧礼》云:“设决,丽于掔,自饭持之。设握,乃连掔。”郑玄注曰:“丽,施也。掔,手后节中也。饭,大擘指本也。决,以韦为之,籍有彄。彄内端为纽,外端有横带,设之,以纽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横带贯纽,结于掔之表也。设握者,以綦系钩中指,由手表与决带之余连结之。此谓右手也。古文丽亦为连,掔作捥。”③而李光坡在征引时删去了“古文丽亦为连,掔作捥”一句。对此,四库馆臣指出:“《注》载古文、今文,最关经义。如《士丧礼》‘设决,丽于掔’,《注》引古文‘掔’作‘捥’。考《管子·弟子职》‘饭必捧掔,羹不以手’;《吕览·本味篇》‘述荡之掔’,高诱注曰:‘掔,古手捥之字也。’据此,则以古文之‘捥’,证今文之‘掔’,义更明晰。而光坡概节之,亦为太简。”④
又如,《公食大夫礼》云:“饮酒、浆饮,俟于东房。”李光坡引“《注》曰:‘饮酒,清酒也。浆饮,酨浆也。其俟,奠于丰上也。饮酒先言饮,明非献酬之酒也。浆饮先言浆,别于六饮也。’《疏》曰:‘酨之言载,以其汁滓相载,故云酨。饮酒先言饮,此拟酳口,异于献酬酒。六饮为渴而饮,此浆为酳口,故异之’”⑤《公食大夫礼》又云:“宰夫右执觯,左执丰,进设于豆东。”李光坡先引“《注》曰:‘食有酒者,优宾也。设于豆东,不举也。《燕礼》记曰:凡奠者于左。’《疏》曰:‘按下文宰夫执浆饮,宾兴受。唯用浆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犹设之,是优宾也。此酒不用,故奠于豆东’”,后又引杨孚之说曰:“按上文‘饮酒、浆饮,俟于东房’,《疏》云‘酒浆皆以酳口’,此又云‘浆以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犹设之,所以优宾’,两说抵牾不同。又按下文‘祭饮酒于上豆之间,鱼腊酱湆不祭’。夫鱼腊酱湆不祭,而祭饮酒,则知酒以优宾,但宾不举尔,岂酳口之物哉?当以优宾之义为正。”①由此可见,李光坡倾向于杨孚的观点,认为此处设酒是为了表示优宾之义,并非酳口之物。而四库馆臣则以杨孚之说为非,批评“光坡取之,实未深考”②。
诚如陈祖武所言:“李光坡萃毕生心力于《三礼》学研究。他在这一领域中所留下的三部著述,虽然只是历代经学家研究所得的汇集,并没有提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创见,但是,不为汉、宋学门户之争所拘囿,‘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为后来的《三礼》学研究者,也确实提供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料。”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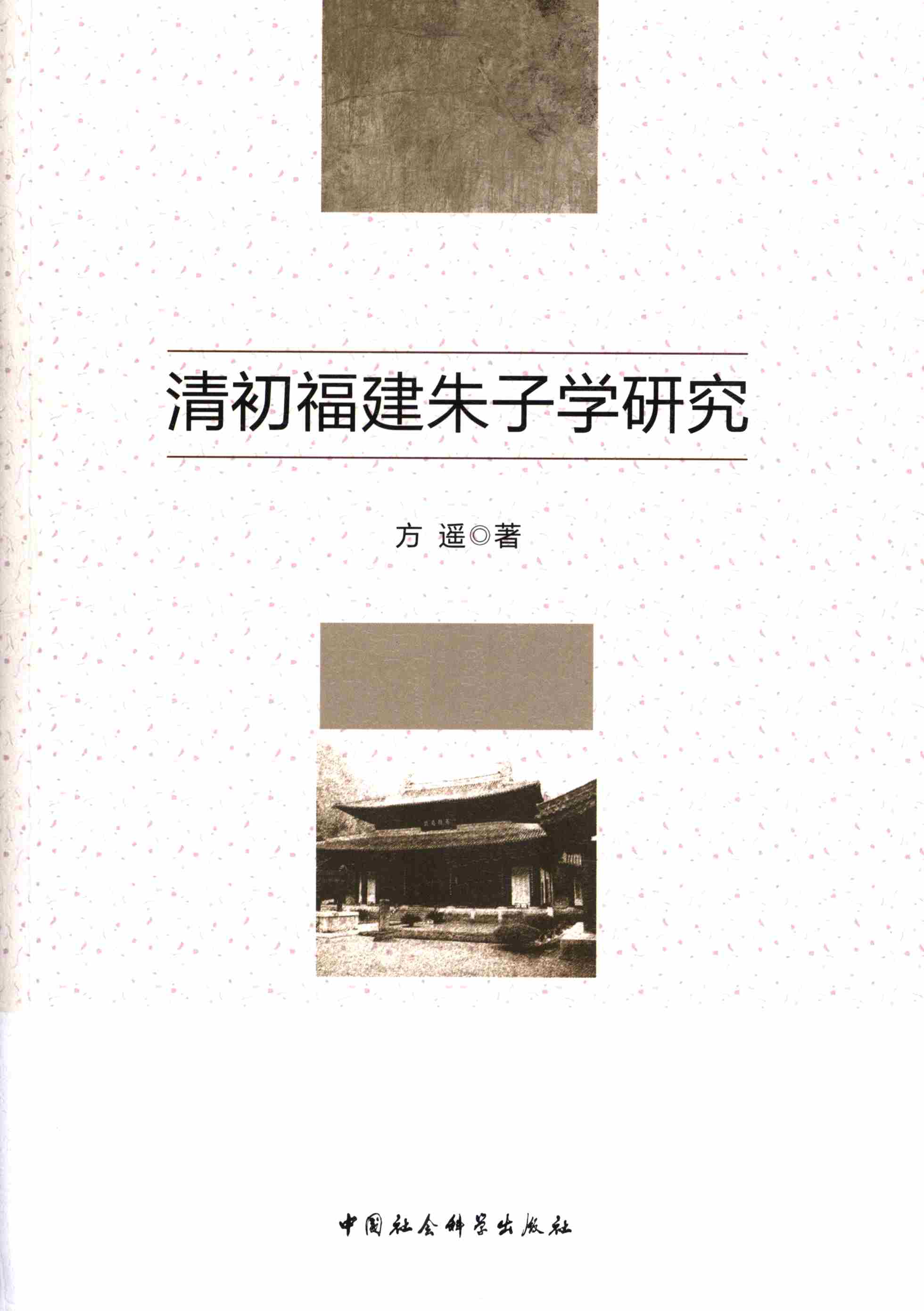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
相关人物
戴震
相关人物
段玉裁
相关人物
任大椿
相关人物
程瑶田
相关人物
凌廷堪
相关人物
焦循
相关人物
李光坡
相关人物
郑玄
相关人物
孔颖达
相关人物
陈㵆
相关人物
刘敞
相关人物
王安石
相关人物
周敦颐
相关人物
张载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
吕祖谦
相关人物
张栻
相关人物
黄榦
相关人物
吴澄
相关人物
毛应龙
相关人物
邱葵
相关人物
何乔新
相关人物
魏校
相关人物
徐常吉
相关人物
王应电
相关人物
顾景范
相关人物
李光地
相关人物
李钟伦
相关人物
孔安国
相关人物
刘歆
相关人物
杜子春
相关人物
贾逵
相关人物
郑众
相关人物
马融
相关人物
郑玄
相关人物
贾公彦
相关人物
韩愈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