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光地的三礼学研究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87 |
| 颗粒名称: | 四 李光地的三礼学研究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437-152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李光地重视礼学义理的阐发,注重将礼学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他认为礼的根本特征是“中”与“和”,与乐在本质上相通。他强调礼与道德人伦规范的实现紧密相关。对于《周礼》,他相信其为周公所作,赞扬其中的制度规定,并认为其应成为天下万世取法的依据。他反对将《周礼》视为刘歆伪作,认为其文字与义理精妙。对于《周礼》多次遭到改窜的观点,他指出是由于《冬官》一章阙失所致。 |
| 关键词: | 李光地 礼学义理 《周礼》 |
内容
李光地治三礼之学,既注重礼学义理的阐发,也兼顾对古代仪法制度的考释,同时还力求将礼学落实到现实生活层面,讲求礼在日常生活、社会政治中的运用。关于礼的本质,李光地认为,性是礼的来源与最终依据,礼则是性的外在表现,礼的根本特征是“中”与“和”。从这一点上看,礼与乐在本质上亦是相通的,“礼乐是一件……盖礼之和乐处,即是乐也”①。所以他说:“吾性之中即礼,吾性之和即乐。”②又说:“以今日用礼者言之,必以和,行之乃可贵也。先王之道,斯为美。以昔日制礼者言之,惟其和,所以为美也。”③
另一方面,李光地又强调:“礼者,纪人伦者也。有冠昬,而夫妇之别严;有丧祭,而父子之恩笃;有乡射,而长幼之序明;有朝聘,而君臣之义肃。”④也就是说,礼仪节文有助于道德人伦规范的实现。因此,研究礼学与研究其他经典之学的方法有所不同,务必与实践相结合,边学边行,使其落实贯彻到日用常行之中。而这亦成为孔门教学的一大特点。所谓“《诗》《书》可以讲诵,而《礼》必须习。故夫子与门弟子率之习礼,而雅言于《礼》必曰‘执’。朱子谓:‘讲求数日不能通晓记忆者,如其法习之,半日即熟。’春秋时,《礼》《乐》崩坏,《诗》《书》废阙,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使门弟子琴瑟歌舞,习《礼》不辍,使身心性命之学,与《诗》《书》、六艺之义,一以贯之,灿然具备”①。
具体而言,关于《周礼》一书,李光地相信其为周公所作。《榕村语录》载:
问:“周家制度,是周公手定,孔子却说文王之文,何也?”曰:“想是文王已有成模,所以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丕显哉,文王谟’。周公守其家学而修之耳。”②
《周礼》看来无可疑,我深信之,确有以见其为周公之书也。③
胡五峰以《周礼》为刘歆伪作,说太宰岂有管米盐醯酱之事之理。不知男女饮食,自外言之,即治国平天下之要;自内言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要。日用间更有何事?④
《考工记》文字最妙,岂刘歆所能到?人不信《周礼》,遂将此书推与刘歆。近如阎百诗、黄梨洲辈,并将《周礼》亦推与刘歆。卑《周礼》失其平,不觉尊刘歆过其分矣。⑤
李光地认为,《周礼》确是周公自作,而其制度规模于文王时便已粗具。胡宏等人因《周礼》以冢宰为首,而冢宰所管多为男女饮食、米盐酱醋之类的宫闱琐细,故疑《周礼》为伪。对此,李光地指出,冢宰所司正是国君修身齐家之要事,乃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与前提,《周礼》由修身齐家说起,进而推出治平天下,反映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合乎义理,不能以此判断《周礼》为伪。故曰:“修身齐家,平治之本,冢宰之司,修齐之事也。……道造端夫妇,而始于居处服食之间,冢宰之职,其义不亦深乎?末学疑端,以是为首,是乌知礼意哉?”①又说:“天者,君也;官犹司也,冢宰所司者,君之事,故曰‘天官’。宰者,调和膳羞之名;冢,大也。君德者,万化之本;而饮食尽道者,又君德之本也。冢宰掌王饮食男女之事,使皆有节度,此体信之道,其为宰也大矣。君正而推以均四海,不过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而万物自育,天地自位。是调和膳羞,其事至小而实大,其义至近而实远,以此名官,非喻也,深哉!”②可见其对冢宰一职的特别重视。至于以《周礼》为刘歆伪作的观点,李光地亦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周礼》文字、义理精妙,绝非刘歆辈所能伪造。以《周礼》为刘歆所作,既贬低了《周礼》,又高看了刘歆,与实情不符。
对于《周礼》多遭学者改窜一事,李光地说道:
《周礼》一书,为近代诸儒改易窜置,真赝相乱。自吴幼清、方逊志之贤,皆不能免。要其疑端,皆生于《冬官》之阙,而地官所掌,乃邦土之事。故或则曰《地官》阙而《冬官》未尝阙也,或曰《冬官》错于《地官》之中也。然以愚考之,大司徒之职,及其所属之官,虽所掌邦土,而要归于教,其非《冬官》之误明甚。且大小司徒之章,文意相从,所属自乡遂以下,官职相序,亦绝不类他官搀入。然则诸儒之所改易窜置者,其可信乎?是则何说而可?曰:自虞夏之间,而司空之职率先于司徒旧矣。《舜典》伯禹作司空,稷播百谷,然后契继敷教,其在后世,则播谷亦司空职也。《洪范》序八政,四曰司空,五曰司徒。《礼记·王制》,说者以为夏殷之书。其文曰:“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此皆司空、司徒二官阜教相成之证也。周监历代,损益厥礼,董正治官,六典斯备。其列司空于五官之末者,盖别有深意焉。然《周礼》者,周公未成之书也。故其叙司徒之篇,犹首以司空之事,合养教而备厥职。惜乎司空未作,而成书不可见矣。学者无由尽知周公之意,又未尝深考沿革之由,私疑臆决,穿凿附会,遇不可通,则悉以为汉儒变乱之罪,岂不过哉?然则司徒之篇,杂以司空之事,此周公之旧,而非所谓误与错也。盖周公初革官制,其犹未能变古若此。①
在他看来,《周礼》之所以多遭学者改窜变乱,主要是由于《冬官》一章阙失。据《尚书·周官》记载,“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而今传《周礼》中的地官亦掌邦土之事,所以宋代以来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冬官》并未亡佚,而是《地官》亡佚,今传《周礼》中的《地官》一章即是《冬官》;或认为《冬官》被割裂错杂于《地官》之中。对此,李光地认为,地官司徒及其所属职官虽然也掌邦土之事,但其要归于教民,与冬官司空不同,所以《地官》绝非《冬官》之误。且《地官》一章,文意顺畅,司徒所属诸官,自乡遂以下,官职相序,亦不可能由他官搀入。李光地进一步指出,根据《尚书》中的《舜典》《洪范》与《礼记·王制》的记载,地官司徒与冬官司空的职守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官阜教相成,且古制中司空之职先于司徒。这是由于司徒主于教民,司空主于养民,“故司空之职,虞夏最先,养先于教也”②。因此,《周礼》中的《地官》一章先叙冬官司空之事,是“合养教而备厥职”之意。且周公借鉴、损益古代制度,制礼作乐,改革官制,初时尚未完全变更古法,故《地官》中仍夹杂有冬官之事,正是周公旧文,并非后人所说的讹误与错简。至于《周礼》中为何不见《冬官》,李光地的解释是《周礼》并未成书,故《冬官》一章未作。
周公之所以将司空改列于五官之后,李光地认为别有深意,“非后也,以终为始,建子之义也”①。具体来说,“冢宰掌天,司徒掌地,兼总条贯,是二官者,包乎上下。其外春夏秋冬,各司一事。宗伯以礼乐教,而实由司空之富邦国,生万民,而后教化行。则自冬而春,贞下起元之义也。礼以节之,乐以和之,政以行之,刑以防之,极其效,不过欲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黎民不饥不寒,矜寡孤独废疾者有养而已。则春生、夏长、秋收以至冬藏之义也。以此为终,而实王道之始;以此为始,而要其成何以加兹?深哉!周公之意,岂有异于尧、舜、禹、汤之心乎!”②换言之,冬官司空所掌养民之事,是春、夏、秋三官之职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而其他三官所行礼乐刑政之事,其最终目的亦是为了民有所养。因此,以司空为终,其实也是王道之始;以司空为始,其最终成就亦不外乎此。可见周公之意与尧、舜、禹、汤无异。另一方面,李光地又提出,周代当“三代以后,水土事平,度地居民,经画颇易”③,所以司空与执掌礼乐兵刑的诸官轻重易次,反映了商周制度的变化。
由于李光地相信《周礼》为周公所作,故对其中所述制度十分重视,倍加称赞,以为足资天下万世取法。譬如,关于《周礼》中的赋税制度,李光地说道:
邦都之赋,以待祭祀;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关市之赋,以待膳服,皆赋之最多者也。邦县之赋,以待币帛;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皆赋之次多者也。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币余之赋,以待赐予,皆赋之差少者也。盖邦中以外,其地渐远渐大,自甸、稍、县、都以内,其赋渐近渐轻。至于关市、山泽、币余,皆逐末趋利者,故又增重赋焉。然王城之内,人民聚集,故赋虽轻而得亦多。……历观《周官》之职,凡祭祀、宾客、丧纪诸大事,自邦中以至郊野,莫敢不供。然则某赋以待某事者,计其所出,约略足以供之耳。读《周礼》者宜善观之。①
在他看来,《周礼》中规定的这一套赋税制度不仅能够根据征收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赋税的多寡轻重,而且能将不同来源的赋税分别用于特定的事项上,以便根据该项的支出来决定征收的数额,从而既保证了祭祀、宾客、丧纪等大事皆有足够的物品与费用,又使不同地区、职业的民众都能负担得起,值得后世借鉴。又如《周礼》中的乡遂制度,李光地认为“乡遂兵多,隐然有强本之意。圣人作事,多少意思都包在内”②。诸如此类,使李光地不禁赞叹道:“《周礼》一书,幸而存,必有发用之时。汉武帝直谓是战国黩乱不经之书,其后尊信《周礼》数人皆败事,所以人益不信。北魏文帝、周武帝、唐太宗略仿佛行之,如均田、府兵之类,皆有其意。文中子之子福畤,记唐太宗欲行《周礼》,魏郑公曰:‘非君不能行,顾臣无素业耳。’此未必确。纵不精熟,如考起来,何至全无头绪?欲治天下,断非此书不可。”③与此同时,李光地还意识到,即便有了好的制度,也须用贤得人,合乎实际,才能保证制度顺利推行,达到好的效果。而《周礼》在制定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故其法仅行于王畿一州之内。他解释道:“不得其人,未有不弊之法。如《周官》一书,但立王畿千里一州之法,他八州置之不问,正是此意。那时王畿之地,有周、召、毕、芮盈于朝宁,恁甚详密之法,无不可行。至外诸侯,若强之行,有必不能者,但立一榜样于此,有能彷而行者,天子未尝不嘉与之。不然亦止五年之间,察其土地人民,风俗贞淫,在位贤否而已。这是圣人识大体处,若使九州尽如《周官》,虽圣人有所不能。”④
李光地还利用自己精通天文、历算之学的优势,修正了前人注解《周礼》时出现的一些错误。譬如,《周礼》中记载有所谓“土圭之法”测土深,曰:“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对此,郑玄注解道:“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郑司农云,测土深,谓南北东西之深也。日南,谓立表处大南,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大北,远日也。景夕,谓日昳景乃中,立表处大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大西,远日也。玄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阴阳,审其南北。景短于土圭,谓之日南,是地于日为近南也。景长于土圭,谓之日北,是地于日为近北也。东于土圭,谓之日东,是地于日为近东也。西于土圭,谓之日西,是地于日为近西也。如是,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树,树木沟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①
李光地指出,若以郑玄所说的立八尺之表,于洛阳、阳城得影一尺五寸,每千里差一寸,阳城以北影渐长,阳城以南影渐短推算,最后短至广州须一万五千里,方才表影全无。但“今考洛阳出北极二十三度有奇,广州出极三十五度,以成数要之,只差十一度。以今所制营造尺量之,每二百里差一度,止得二千二百里。即以古尺二百五十里差一度算之,亦止得二千七百五十里。安得一万五千里耶?”②对于郑玄的日影千里差一寸之说,李光地还批评道:“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弧背九度余。夏至日道,下直衡岳,晷无影。从嵩高至衡岳,夏至日道圜天之弧背,以弧矢术求弦,得衡岳脱地中弦径,约九度余。从阳城至衡岳,地平鸟道,相去约二千五百里。夫止二千五百里,而一则尺五寸,一则无影。是百六十余里,景已差一寸矣。则郑注所云千里而差一寸,恐未然也。又郑注谓景短者,中表之南,千里景短一寸;景长者,中表之北,千里景长一寸。如此,则日下无景,当在极南,万五千里之外,而衡岳之远阳城,不能万五千里昭昭矣。”①据李光地的测算,日影差一寸约略相当于一百六十余里之地,绝不可能如郑玄所说的千里之远。
对于郑玄所引郑众之言“景夕,谓日昳景乃中,立表处大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大西,远日也”,李光地亦不赞同。他根据“地圆说”反驳道:“如此,则极东之地,日出方及三五寻丈,日景已中;极西之地,日入未及三五寻丈,日景方中。若果地体方平,四际弥天,则信如所云矣。不然如鸡子裹黄之喻,地在天中,不过成形之大耳。弹丸浮寄,四际距天至远,四际距天之远若一也,则去日安能有远近之殊乎?虽日之出也,极东先见,及其入也,极西先昏,然随其处,各有晓午昏暮。安知日东者,不以吾为景朝乎?日西者,不以吾为景夕乎?且此尺有五寸,东西直北一带中,日景皆如是也。何以定其为东西之中乎?”②
在此基础上,李光地提出了自己对于“土圭之法”的解释:
吾谓日南则景短多暑,谓从此中表而南之地,则当景短之时,盛暑不堪。若今广州夏时,炎赫倍于他州。盖景短即夏至,非短于尺有五寸之谓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者,谓从此中表而北之地,则当景长之时,隆寒不堪。若今塞外冬时,凛栗亦倍。盖景长即冬至,非长于尺有五寸之谓也。日东则景夕多风者,谓从此中表而东之地,则景夕之时多风。盖东地多水,多水则多风。若吾州,午后即海风扬也。风起于夕,故以景夕言之。日西则景朝多阴者,谓从此中表而西之地,则景朝之时多阴。盖西地多山,多山则云气盛。若柳子厚所谓“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是也。阴霾于朝,故以景朝言之。如此,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天地之所合者,地中与天中气合也。
合则四时交,而无多暑、多寒之患;合则风雨会,而无多风;合则阴阳和,而无多阴。何以定之?以验寒暑阴风于五土,而知惟此为不偏也。然特就中国九州,而奠其四方之中耳。若论大地之中,当在南戴赤道下之国,则未知其何如也。然则冲和所会,无水旱昆虫之灾,无凶饥妖孽之疾,兆民之众,含生之类,莫不阜安,是乃王者之都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者,非谓必日景尺有五寸,乃为地中,是言地中之处,其景尺有五寸。盖用以为标识也。①
李光地认为,《周礼》所说的“景短”指夏至,而非日影短于一尺五寸。当景短之时,中表以南之地盛暑不堪。“景长”指冬至,而非日影长于一尺五寸。当景长之时,中表以北之地隆寒不堪。“日东则景夕多风”是由于中表以东之地多水,多水则多风。因为风多起于夕,故言景夕。“日西则景朝多阴”是由于中表以西之地多山,多山则云气盛。因为阴霾多起于朝,故言景朝。不论偏南、偏北,还是偏东、偏西,气候皆偏而不和,故不符合建都的要求。建都须择天地之气相合处,合则四时交、风雨会、阴阳和,而无多暑、多寒、多风、多阴之患。而此处即中国九州之地中,以验寒暑阴风于五土,便知唯此处不偏。李光地最后强调,“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并不是说只要夏至正午日影一尺五寸之处便为地中,而是指地中之处夏至正午日影一尺五寸,故以此作为标志。
关于《仪礼》与《礼记》,李光地从朱熹之说,认为“礼有经有传。《仪礼》,礼之经也;《礼记》,礼之传也”②。又说:“《仪礼》虽非圣作,但在仪节上讲,何尝不是道德性命所发见,毕竟略隔一层。《礼记》中圣人议论亦多,但大半出自汉人,不尽是圣人之笔”③,亦与朱熹看法相近。李光地接着指出,上古文、武、周公之道未坠于地者,赖有《仪礼》《礼记》二书流传,但“《仪礼》缺而不完,《礼记》乱而无序。自朱子欲以经传相从,成为礼书,然犹苦于体大,未究厥业”①,使得后之欲为礼学者益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李光地便“择其大者要者,略依经传之体,别为四际八篇,以记礼之纲焉”②,撰为《礼学四际约言》。所谓的“四际”,指的是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而之所以要列此四际八篇,李光地解释道:
《易》曰:“有天地万物,而后有男女夫妇;有男女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上下君臣,而礼义有所措也。”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有冠昏,而夫妇别矣;有丧祭,而父子亲矣;有乡射,而长幼序矣;有朝聘,而君臣严矣。夫妇别而后父子亲,父子亲而后长幼序,长幼序而后君臣严。由闺门而乡党,由乡党而邦国朝廷,盖不可以一日废也。……有冠昏而夫妇别,夫妇别然后智可求也;有丧祭而父子亲,父子亲而后仁可守也;有乡射而长幼序,长幼序而后礼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严,君臣严而后义可正也。③
在他看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即是礼中的大者、要者。因为这四者分别对应夫妇、父子、长幼、君臣四对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皆根源于人的本性,符合天地万物发展的规律,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后先相继的礼法体系,进而保证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和人的本质的实现。而这亦是先王先圣制礼设教的根本目的。故“学者,学此者也。洒扫进退而非粗也,尽性至命而非远也。小学以始之,大学以终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书也,虽未能该先王之典,庶几求礼之门户者,得其端焉”④。
此外,李光地又病《礼记》“冗而无序”,“繁且乱,记识之难熟,讲贯之弗理”,认为其“既非周鲁之旧,当日采辑,其于章句文义亦择焉而弗精,苟为之详论条理,成一家言,抑犹作者未竟之绪”,①故将《礼记》之文加以整理,分为内、外二篇,并重定篇次,撰为《礼记纂编》。其内篇篇目依次为:《曲礼》《少仪》《内则》《冠义》《昏义》《丧大记》《丧服小记》《间传》《问丧》《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奔丧》《檀弓》《曾子问》《杂记》《祭法》《祭义》《祭统》《郊特牲》《乡饮义》《投壶》《射义》《大传》《明堂位》《燕义》《聘义》《深衣》《玉藻》,外篇篇目依次为:《礼运》《礼器》《经解》《坊记》《表记》《儒行》《缁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文王世子》《王制》《月令》《学记》《乐记》。
对于这样安排篇次的用意,李光地解释道:
夫古者小学之教,成人之始,故先之《曲礼》《少仪》《内则》三篇。人道莫首于冠昏,故《冠义》《昏义》次之。慎终追远,民行之大,故丧祭又次之。言丧者,凡八篇,而《檀弓》《曾子问》《杂记》附焉。言祭者,凡三篇,而《郊特牲》附焉。由是而达于乡党州间,则《乡饮酒》《投壶》《射义》次之。由是而达于朝廷、邦国,则《大传》《明堂位》《燕义》《聘义》次之。由是而周于衣冠冕珮之制,与夫行礼之容仪,则《深衣》《玉藻》又次之。自《曲礼》至此,为《礼记》内篇。《礼运》《礼器》以下,《学记》《乐记》以上,或通论礼意,或泛设杂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陈王者政教之务,要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靡所不讲,为《礼记》外篇。②
在内篇中,李光地以小学之礼为开端,并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四际”为纲领对《礼记》诸篇进行整理、分类和排序,与其《礼学四际约言》中阐述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体现了朱子学者由小学至于大学,由修身齐家推及治平天下的循循有序的为学工夫与教育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外篇之后,李光地还附录了《大戴礼记》四篇:《武王践祚》《曾子大孝》《曾子疾病》《曾子天圆》,可谓清代较早关注《大戴礼记》的学者之一。惜乎其书不存,后人已无由窥见其详。
由于李光地本人对于乐律的兴趣,他对《仪礼》中有关古乐的记载亦颇为关注,并对其内容和形式做了一些考证与阐发。譬如,关于古乐的篇章结构,李光地说道:“周乐是四节:一、升歌三终,堂上人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用琴瑟和之,无他声;二、笙入三终,堂下笙《南陔》《白华》《华黍》,亦无他声;三、间歌三终,堂上歌《鱼丽》毕,堂下笙《由庚》,又堂上歌《嘉鱼》毕,堂下笙《崇丘》,又堂上歌《有台》毕,堂下笙《由仪》;四、合乐三终,堂上歌《关雎》《葛覃》《卷耳》,堂下笙《鹊巢》《采蘩》《采苹》,众乐器齐作,舞亦在此时,而乐终矣。”①他还举《尚书·益稷》中的“戛击鸣球”一节为例,认为“搏拊琴瑟以咏”便是第一节升歌,“下管鼗鼓”是第二节笙入,“笙镛以间”是第三节间歌,“合止柷敔”“箫韶九成”是第四节合乐。
关于古乐开始时的演奏次序,朱熹认为是“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②,而李光地则认为此说无据,且与经文不合。他说:“观‘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及‘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反似磬在先。盖堂上堂下,皆用钟磬节之,如今曲中之用板。与歌相应者,曰颂钟、颂磬;与笙相应者,曰笙钟、笙磬也。”③
关于乐舞的演奏时间,经中并无明文,李光地推测应在合乐之时,譬如“箫韶九成”。他以《大武》为例,描述其情状道:“如《大武》‘始而北出’,一人‘总干而山立’,‘夹振驷伐’,但作此象,不知此为何人。旁或歌‘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之章,则人知其为武王大正于商,俟天休命也。‘再成而灭商’,一人‘发扬蹈厉’,又不知为何人。旁或歌‘维兹尚父,时维鹰扬’之章,则人知为太公也。‘三成而南’,所谓‘济河而西,马归之华山之阳,牛放之桃林之野’,使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四成而南国是疆’,所谓‘列爵惟五,分土维三’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陕而治’也。‘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所谓‘垂拱而天下治’也。由此推之,则韶之九成,想见舜之功德,征庸、在位、齐政、巡守、命官、殛罪、封山、浚川诸事,遂至九成也。”①
由于《仪礼》所载多为士大夫之礼,天子、诸侯所用礼乐皆不传,故李光地还由士大夫之乐推测当时天子、诸侯所用之乐。譬如,他根据士大夫之乐四节皆三终,而《鹿鸣》《四牡》《皇华》,《文王》《大明》《绵》与《清庙》《维天》《维清》皆为三诗,推测天子、诸侯之乐大概亦是三终。又根据《诗经·商颂·那》“嘒嘒管声”,《尚书·益稷》“下管鼗鼓”,《礼记·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和《仪礼·燕礼》“下管新宫”等描述推测,天子、诸侯之乐的第二节笙入不用笙,而用管。又谓天子、诸侯之乐虽于笙入时用管,但至间歌、合乐时仍用笙,不用管。
论及《礼记》,李光地特重《王制》《乐记》两篇。关于《王制》,李光地说道:
《王制》一篇,先儒谓多举历代之典,盖不尽周制也。然其本末次第,井有条贯,则非苟然编次者。盖首言封建、井田、爵禄之制,乃王道之本也。次言巡狩、朝觐、班锡、田猎之制,王者所以治诸侯也。次及冢宰、司空、司徒、乐正、司马、司寇、市官之职,而以告成受质终焉,王者所以理庶官也。然后及于养老、恤穷之典,使天下无不得其所者,则又所以逮万民也。庶官理于内,诸侯顺于外,万民得所于下,而王道备矣。然必自封建、井田始,故二事不还,则三代终不可得而复也。②
《王制》一篇主要记载古代的封国、爵禄、职官、祭祀、巡狩、养老等制度。由于其中所述制度多与《周礼》不合,故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汉文帝博士所作,或秦汉间学者所作,乃杂取圣贤经传中所载历代制度斟酌损益而成。而李光地则从文章的内在理路分析,认为《王制》先论王道之本,后依次言王者所以治诸侯、理庶官、逮万民之法,使庶官理于内,诸侯顺于外,万民得所于下,而王道备矣。其本末次第,井井有条,合乎义理,并非出于后人缀辑,而是周代旧文。至于《王制》所载多非周制的问题,李光地解释道:
《王制》当是殷制,故其通篇次叙,恰与《洪范》“八政”相符。想禹当年锡洛叙畴之后,一切规模制度,都从此出,所以《禹贡》中山川田赋,数皆用九。殷人承之,因于夏礼所谓“缵禹旧服”者也。则夏制疑亦仿此。直至文王演《易》,画出《后天图》来,其后周家六官,遂从天地四时起义,非复“八政”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之序矣。然宾、师二者,《洪范》次于后,而《王制》居前。《王制》所以定立国规模,非《洪范》立教垂训之比。宾、师乃国事之尤大者,故先之。①
禹之《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今观《王制》,自冢宰制国以下至司寇,其序正合。盖冢宰所司,食、货、祀三者备矣。然后以司空定民之居,然后以司徒兴民之德。至于乐正、司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以附于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终焉。宾、师二者,《洪范》次于后,《王制》叙于前。盖《洪范》言其切于民生之先后缓急,则柔远安邦之事宜居养教之后;《王制》言其关于建国之规模纲纪,则礼乐征伐之柄必在庶政之先,义各有所当也。此书上比《虞典》,既微有不同,下视周制,又甚相悬绝,独与《洪范》,则其暗合若此。②
郑玄注解《王制》,多以殷制为说。李光地借鉴了郑玄的这一思路,亦主张《王制》是殷制,并进一步指出其制度规模与基本框架源自于禹所作的“洪范九畴”中的“八政”。他的依据是《王制》中由冢宰至司寇的职官次序恰与《洪范》“八政”相符。唯一的不同在于,宾、师二者在《洪范》中次于后,而在《王制》中居于前。宾是掌诸侯朝觐之官,师是掌军旅之官,李光地认为二者乃国事之尤大者。只不过因为《洪范》切于民生立教,而《王制》重于建国规模,故《洪范》以宾、师次后,而《王制》以宾、师居前。由于殷承夏制,而周代则由文王、周公据《易经》之义重订制度,故《王制》虽作于周,却与周制不同。
《乐记》有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①这段话提出天理、人欲之分,又暗含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历来为理学家所特别重视,反复征引阐发,成为理学心性论最重要的经典依据之一。李光地亦赞叹道:“《乐记》‘人生而静’一段,真是千圣传心之要典,与虞廷十六字同。‘人心’‘道心’四字,浑含精微;‘天理’‘人欲’四字,刻画透露。”②
李光地还将《乐记》一篇划分为若干段落,并逐段概括其大意。他首先将《乐记》开头至“魏文侯问于子夏”这一部分分为八段,提出:“自‘凡音之起’至‘而出治道也’为第一段,自‘凡音者’至‘德者得也’为第二段。此二段言乐之生于人心而关乎政治也。自‘乐之隆’至‘则礼行矣’为第三段,言先王作乐,感人心之效。自‘大乐与天地同和’至‘故圣人曰礼乐云’为第四段,又推其制作之原,极其神化之妙,其精微所存,有不在区区器数声容之间者矣。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善则行象德矣’为五段,申乐之关乎政也。自‘夫豢豕为酒’至‘可以观德矣’为六段,申乐之生乎人心,而感通之效也。自‘德者性之端也’至‘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为第七段,又以申其制作之精,神化之盛,诚不在气数声容之间也。”①李光地认为,这一部分构成了《乐记》全篇的核心内容,揭示了其主旨。“盖统乐之本末而论之,则生于人心者,还足以感乎人心;成乎风俗者,还足以变乎风俗;本于天地者,还足以通乎天地。是以终篇反复推明,而大旨不过如此而已。”②他又将“君子曰”至“礼乐可谓盛矣”归为一段,视作乐之总论,认为应当依据《史记》附于上述第七段之后。至于其余部分,李光地认为“魏文侯”一节言声,“宾牟贾”一节言舞,而“子贡”一节则言声容之本。分析完全篇之后,李光地再次强调:“戴氏之编,自《学》《庸》外,未有若是之精神者也。留心礼乐者,其可不致思焉?”③
另一方面,李光地又强调:“礼者,纪人伦者也。有冠昬,而夫妇之别严;有丧祭,而父子之恩笃;有乡射,而长幼之序明;有朝聘,而君臣之义肃。”④也就是说,礼仪节文有助于道德人伦规范的实现。因此,研究礼学与研究其他经典之学的方法有所不同,务必与实践相结合,边学边行,使其落实贯彻到日用常行之中。而这亦成为孔门教学的一大特点。所谓“《诗》《书》可以讲诵,而《礼》必须习。故夫子与门弟子率之习礼,而雅言于《礼》必曰‘执’。朱子谓:‘讲求数日不能通晓记忆者,如其法习之,半日即熟。’春秋时,《礼》《乐》崩坏,《诗》《书》废阙,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使门弟子琴瑟歌舞,习《礼》不辍,使身心性命之学,与《诗》《书》、六艺之义,一以贯之,灿然具备”①。
具体而言,关于《周礼》一书,李光地相信其为周公所作。《榕村语录》载:
问:“周家制度,是周公手定,孔子却说文王之文,何也?”曰:“想是文王已有成模,所以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丕显哉,文王谟’。周公守其家学而修之耳。”②
《周礼》看来无可疑,我深信之,确有以见其为周公之书也。③
胡五峰以《周礼》为刘歆伪作,说太宰岂有管米盐醯酱之事之理。不知男女饮食,自外言之,即治国平天下之要;自内言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要。日用间更有何事?④
《考工记》文字最妙,岂刘歆所能到?人不信《周礼》,遂将此书推与刘歆。近如阎百诗、黄梨洲辈,并将《周礼》亦推与刘歆。卑《周礼》失其平,不觉尊刘歆过其分矣。⑤
李光地认为,《周礼》确是周公自作,而其制度规模于文王时便已粗具。胡宏等人因《周礼》以冢宰为首,而冢宰所管多为男女饮食、米盐酱醋之类的宫闱琐细,故疑《周礼》为伪。对此,李光地指出,冢宰所司正是国君修身齐家之要事,乃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与前提,《周礼》由修身齐家说起,进而推出治平天下,反映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合乎义理,不能以此判断《周礼》为伪。故曰:“修身齐家,平治之本,冢宰之司,修齐之事也。……道造端夫妇,而始于居处服食之间,冢宰之职,其义不亦深乎?末学疑端,以是为首,是乌知礼意哉?”①又说:“天者,君也;官犹司也,冢宰所司者,君之事,故曰‘天官’。宰者,调和膳羞之名;冢,大也。君德者,万化之本;而饮食尽道者,又君德之本也。冢宰掌王饮食男女之事,使皆有节度,此体信之道,其为宰也大矣。君正而推以均四海,不过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而万物自育,天地自位。是调和膳羞,其事至小而实大,其义至近而实远,以此名官,非喻也,深哉!”②可见其对冢宰一职的特别重视。至于以《周礼》为刘歆伪作的观点,李光地亦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周礼》文字、义理精妙,绝非刘歆辈所能伪造。以《周礼》为刘歆所作,既贬低了《周礼》,又高看了刘歆,与实情不符。
对于《周礼》多遭学者改窜一事,李光地说道:
《周礼》一书,为近代诸儒改易窜置,真赝相乱。自吴幼清、方逊志之贤,皆不能免。要其疑端,皆生于《冬官》之阙,而地官所掌,乃邦土之事。故或则曰《地官》阙而《冬官》未尝阙也,或曰《冬官》错于《地官》之中也。然以愚考之,大司徒之职,及其所属之官,虽所掌邦土,而要归于教,其非《冬官》之误明甚。且大小司徒之章,文意相从,所属自乡遂以下,官职相序,亦绝不类他官搀入。然则诸儒之所改易窜置者,其可信乎?是则何说而可?曰:自虞夏之间,而司空之职率先于司徒旧矣。《舜典》伯禹作司空,稷播百谷,然后契继敷教,其在后世,则播谷亦司空职也。《洪范》序八政,四曰司空,五曰司徒。《礼记·王制》,说者以为夏殷之书。其文曰:“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此皆司空、司徒二官阜教相成之证也。周监历代,损益厥礼,董正治官,六典斯备。其列司空于五官之末者,盖别有深意焉。然《周礼》者,周公未成之书也。故其叙司徒之篇,犹首以司空之事,合养教而备厥职。惜乎司空未作,而成书不可见矣。学者无由尽知周公之意,又未尝深考沿革之由,私疑臆决,穿凿附会,遇不可通,则悉以为汉儒变乱之罪,岂不过哉?然则司徒之篇,杂以司空之事,此周公之旧,而非所谓误与错也。盖周公初革官制,其犹未能变古若此。①
在他看来,《周礼》之所以多遭学者改窜变乱,主要是由于《冬官》一章阙失。据《尚书·周官》记载,“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而今传《周礼》中的地官亦掌邦土之事,所以宋代以来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冬官》并未亡佚,而是《地官》亡佚,今传《周礼》中的《地官》一章即是《冬官》;或认为《冬官》被割裂错杂于《地官》之中。对此,李光地认为,地官司徒及其所属职官虽然也掌邦土之事,但其要归于教民,与冬官司空不同,所以《地官》绝非《冬官》之误。且《地官》一章,文意顺畅,司徒所属诸官,自乡遂以下,官职相序,亦不可能由他官搀入。李光地进一步指出,根据《尚书》中的《舜典》《洪范》与《礼记·王制》的记载,地官司徒与冬官司空的职守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官阜教相成,且古制中司空之职先于司徒。这是由于司徒主于教民,司空主于养民,“故司空之职,虞夏最先,养先于教也”②。因此,《周礼》中的《地官》一章先叙冬官司空之事,是“合养教而备厥职”之意。且周公借鉴、损益古代制度,制礼作乐,改革官制,初时尚未完全变更古法,故《地官》中仍夹杂有冬官之事,正是周公旧文,并非后人所说的讹误与错简。至于《周礼》中为何不见《冬官》,李光地的解释是《周礼》并未成书,故《冬官》一章未作。
周公之所以将司空改列于五官之后,李光地认为别有深意,“非后也,以终为始,建子之义也”①。具体来说,“冢宰掌天,司徒掌地,兼总条贯,是二官者,包乎上下。其外春夏秋冬,各司一事。宗伯以礼乐教,而实由司空之富邦国,生万民,而后教化行。则自冬而春,贞下起元之义也。礼以节之,乐以和之,政以行之,刑以防之,极其效,不过欲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黎民不饥不寒,矜寡孤独废疾者有养而已。则春生、夏长、秋收以至冬藏之义也。以此为终,而实王道之始;以此为始,而要其成何以加兹?深哉!周公之意,岂有异于尧、舜、禹、汤之心乎!”②换言之,冬官司空所掌养民之事,是春、夏、秋三官之职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而其他三官所行礼乐刑政之事,其最终目的亦是为了民有所养。因此,以司空为终,其实也是王道之始;以司空为始,其最终成就亦不外乎此。可见周公之意与尧、舜、禹、汤无异。另一方面,李光地又提出,周代当“三代以后,水土事平,度地居民,经画颇易”③,所以司空与执掌礼乐兵刑的诸官轻重易次,反映了商周制度的变化。
由于李光地相信《周礼》为周公所作,故对其中所述制度十分重视,倍加称赞,以为足资天下万世取法。譬如,关于《周礼》中的赋税制度,李光地说道:
邦都之赋,以待祭祀;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关市之赋,以待膳服,皆赋之最多者也。邦县之赋,以待币帛;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皆赋之次多者也。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币余之赋,以待赐予,皆赋之差少者也。盖邦中以外,其地渐远渐大,自甸、稍、县、都以内,其赋渐近渐轻。至于关市、山泽、币余,皆逐末趋利者,故又增重赋焉。然王城之内,人民聚集,故赋虽轻而得亦多。……历观《周官》之职,凡祭祀、宾客、丧纪诸大事,自邦中以至郊野,莫敢不供。然则某赋以待某事者,计其所出,约略足以供之耳。读《周礼》者宜善观之。①
在他看来,《周礼》中规定的这一套赋税制度不仅能够根据征收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赋税的多寡轻重,而且能将不同来源的赋税分别用于特定的事项上,以便根据该项的支出来决定征收的数额,从而既保证了祭祀、宾客、丧纪等大事皆有足够的物品与费用,又使不同地区、职业的民众都能负担得起,值得后世借鉴。又如《周礼》中的乡遂制度,李光地认为“乡遂兵多,隐然有强本之意。圣人作事,多少意思都包在内”②。诸如此类,使李光地不禁赞叹道:“《周礼》一书,幸而存,必有发用之时。汉武帝直谓是战国黩乱不经之书,其后尊信《周礼》数人皆败事,所以人益不信。北魏文帝、周武帝、唐太宗略仿佛行之,如均田、府兵之类,皆有其意。文中子之子福畤,记唐太宗欲行《周礼》,魏郑公曰:‘非君不能行,顾臣无素业耳。’此未必确。纵不精熟,如考起来,何至全无头绪?欲治天下,断非此书不可。”③与此同时,李光地还意识到,即便有了好的制度,也须用贤得人,合乎实际,才能保证制度顺利推行,达到好的效果。而《周礼》在制定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故其法仅行于王畿一州之内。他解释道:“不得其人,未有不弊之法。如《周官》一书,但立王畿千里一州之法,他八州置之不问,正是此意。那时王畿之地,有周、召、毕、芮盈于朝宁,恁甚详密之法,无不可行。至外诸侯,若强之行,有必不能者,但立一榜样于此,有能彷而行者,天子未尝不嘉与之。不然亦止五年之间,察其土地人民,风俗贞淫,在位贤否而已。这是圣人识大体处,若使九州尽如《周官》,虽圣人有所不能。”④
李光地还利用自己精通天文、历算之学的优势,修正了前人注解《周礼》时出现的一些错误。譬如,《周礼》中记载有所谓“土圭之法”测土深,曰:“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对此,郑玄注解道:“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郑司农云,测土深,谓南北东西之深也。日南,谓立表处大南,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大北,远日也。景夕,谓日昳景乃中,立表处大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大西,远日也。玄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阴阳,审其南北。景短于土圭,谓之日南,是地于日为近南也。景长于土圭,谓之日北,是地于日为近北也。东于土圭,谓之日东,是地于日为近东也。西于土圭,谓之日西,是地于日为近西也。如是,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树,树木沟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①
李光地指出,若以郑玄所说的立八尺之表,于洛阳、阳城得影一尺五寸,每千里差一寸,阳城以北影渐长,阳城以南影渐短推算,最后短至广州须一万五千里,方才表影全无。但“今考洛阳出北极二十三度有奇,广州出极三十五度,以成数要之,只差十一度。以今所制营造尺量之,每二百里差一度,止得二千二百里。即以古尺二百五十里差一度算之,亦止得二千七百五十里。安得一万五千里耶?”②对于郑玄的日影千里差一寸之说,李光地还批评道:“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弧背九度余。夏至日道,下直衡岳,晷无影。从嵩高至衡岳,夏至日道圜天之弧背,以弧矢术求弦,得衡岳脱地中弦径,约九度余。从阳城至衡岳,地平鸟道,相去约二千五百里。夫止二千五百里,而一则尺五寸,一则无影。是百六十余里,景已差一寸矣。则郑注所云千里而差一寸,恐未然也。又郑注谓景短者,中表之南,千里景短一寸;景长者,中表之北,千里景长一寸。如此,则日下无景,当在极南,万五千里之外,而衡岳之远阳城,不能万五千里昭昭矣。”①据李光地的测算,日影差一寸约略相当于一百六十余里之地,绝不可能如郑玄所说的千里之远。
对于郑玄所引郑众之言“景夕,谓日昳景乃中,立表处大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大西,远日也”,李光地亦不赞同。他根据“地圆说”反驳道:“如此,则极东之地,日出方及三五寻丈,日景已中;极西之地,日入未及三五寻丈,日景方中。若果地体方平,四际弥天,则信如所云矣。不然如鸡子裹黄之喻,地在天中,不过成形之大耳。弹丸浮寄,四际距天至远,四际距天之远若一也,则去日安能有远近之殊乎?虽日之出也,极东先见,及其入也,极西先昏,然随其处,各有晓午昏暮。安知日东者,不以吾为景朝乎?日西者,不以吾为景夕乎?且此尺有五寸,东西直北一带中,日景皆如是也。何以定其为东西之中乎?”②
在此基础上,李光地提出了自己对于“土圭之法”的解释:
吾谓日南则景短多暑,谓从此中表而南之地,则当景短之时,盛暑不堪。若今广州夏时,炎赫倍于他州。盖景短即夏至,非短于尺有五寸之谓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者,谓从此中表而北之地,则当景长之时,隆寒不堪。若今塞外冬时,凛栗亦倍。盖景长即冬至,非长于尺有五寸之谓也。日东则景夕多风者,谓从此中表而东之地,则景夕之时多风。盖东地多水,多水则多风。若吾州,午后即海风扬也。风起于夕,故以景夕言之。日西则景朝多阴者,谓从此中表而西之地,则景朝之时多阴。盖西地多山,多山则云气盛。若柳子厚所谓“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是也。阴霾于朝,故以景朝言之。如此,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天地之所合者,地中与天中气合也。
合则四时交,而无多暑、多寒之患;合则风雨会,而无多风;合则阴阳和,而无多阴。何以定之?以验寒暑阴风于五土,而知惟此为不偏也。然特就中国九州,而奠其四方之中耳。若论大地之中,当在南戴赤道下之国,则未知其何如也。然则冲和所会,无水旱昆虫之灾,无凶饥妖孽之疾,兆民之众,含生之类,莫不阜安,是乃王者之都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者,非谓必日景尺有五寸,乃为地中,是言地中之处,其景尺有五寸。盖用以为标识也。①
李光地认为,《周礼》所说的“景短”指夏至,而非日影短于一尺五寸。当景短之时,中表以南之地盛暑不堪。“景长”指冬至,而非日影长于一尺五寸。当景长之时,中表以北之地隆寒不堪。“日东则景夕多风”是由于中表以东之地多水,多水则多风。因为风多起于夕,故言景夕。“日西则景朝多阴”是由于中表以西之地多山,多山则云气盛。因为阴霾多起于朝,故言景朝。不论偏南、偏北,还是偏东、偏西,气候皆偏而不和,故不符合建都的要求。建都须择天地之气相合处,合则四时交、风雨会、阴阳和,而无多暑、多寒、多风、多阴之患。而此处即中国九州之地中,以验寒暑阴风于五土,便知唯此处不偏。李光地最后强调,“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并不是说只要夏至正午日影一尺五寸之处便为地中,而是指地中之处夏至正午日影一尺五寸,故以此作为标志。
关于《仪礼》与《礼记》,李光地从朱熹之说,认为“礼有经有传。《仪礼》,礼之经也;《礼记》,礼之传也”②。又说:“《仪礼》虽非圣作,但在仪节上讲,何尝不是道德性命所发见,毕竟略隔一层。《礼记》中圣人议论亦多,但大半出自汉人,不尽是圣人之笔”③,亦与朱熹看法相近。李光地接着指出,上古文、武、周公之道未坠于地者,赖有《仪礼》《礼记》二书流传,但“《仪礼》缺而不完,《礼记》乱而无序。自朱子欲以经传相从,成为礼书,然犹苦于体大,未究厥业”①,使得后之欲为礼学者益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李光地便“择其大者要者,略依经传之体,别为四际八篇,以记礼之纲焉”②,撰为《礼学四际约言》。所谓的“四际”,指的是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而之所以要列此四际八篇,李光地解释道:
《易》曰:“有天地万物,而后有男女夫妇;有男女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上下君臣,而礼义有所措也。”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有冠昏,而夫妇别矣;有丧祭,而父子亲矣;有乡射,而长幼序矣;有朝聘,而君臣严矣。夫妇别而后父子亲,父子亲而后长幼序,长幼序而后君臣严。由闺门而乡党,由乡党而邦国朝廷,盖不可以一日废也。……有冠昏而夫妇别,夫妇别然后智可求也;有丧祭而父子亲,父子亲而后仁可守也;有乡射而长幼序,长幼序而后礼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严,君臣严而后义可正也。③
在他看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即是礼中的大者、要者。因为这四者分别对应夫妇、父子、长幼、君臣四对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皆根源于人的本性,符合天地万物发展的规律,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后先相继的礼法体系,进而保证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和人的本质的实现。而这亦是先王先圣制礼设教的根本目的。故“学者,学此者也。洒扫进退而非粗也,尽性至命而非远也。小学以始之,大学以终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书也,虽未能该先王之典,庶几求礼之门户者,得其端焉”④。
此外,李光地又病《礼记》“冗而无序”,“繁且乱,记识之难熟,讲贯之弗理”,认为其“既非周鲁之旧,当日采辑,其于章句文义亦择焉而弗精,苟为之详论条理,成一家言,抑犹作者未竟之绪”,①故将《礼记》之文加以整理,分为内、外二篇,并重定篇次,撰为《礼记纂编》。其内篇篇目依次为:《曲礼》《少仪》《内则》《冠义》《昏义》《丧大记》《丧服小记》《间传》《问丧》《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奔丧》《檀弓》《曾子问》《杂记》《祭法》《祭义》《祭统》《郊特牲》《乡饮义》《投壶》《射义》《大传》《明堂位》《燕义》《聘义》《深衣》《玉藻》,外篇篇目依次为:《礼运》《礼器》《经解》《坊记》《表记》《儒行》《缁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文王世子》《王制》《月令》《学记》《乐记》。
对于这样安排篇次的用意,李光地解释道:
夫古者小学之教,成人之始,故先之《曲礼》《少仪》《内则》三篇。人道莫首于冠昏,故《冠义》《昏义》次之。慎终追远,民行之大,故丧祭又次之。言丧者,凡八篇,而《檀弓》《曾子问》《杂记》附焉。言祭者,凡三篇,而《郊特牲》附焉。由是而达于乡党州间,则《乡饮酒》《投壶》《射义》次之。由是而达于朝廷、邦国,则《大传》《明堂位》《燕义》《聘义》次之。由是而周于衣冠冕珮之制,与夫行礼之容仪,则《深衣》《玉藻》又次之。自《曲礼》至此,为《礼记》内篇。《礼运》《礼器》以下,《学记》《乐记》以上,或通论礼意,或泛设杂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陈王者政教之务,要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靡所不讲,为《礼记》外篇。②
在内篇中,李光地以小学之礼为开端,并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四际”为纲领对《礼记》诸篇进行整理、分类和排序,与其《礼学四际约言》中阐述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体现了朱子学者由小学至于大学,由修身齐家推及治平天下的循循有序的为学工夫与教育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外篇之后,李光地还附录了《大戴礼记》四篇:《武王践祚》《曾子大孝》《曾子疾病》《曾子天圆》,可谓清代较早关注《大戴礼记》的学者之一。惜乎其书不存,后人已无由窥见其详。
由于李光地本人对于乐律的兴趣,他对《仪礼》中有关古乐的记载亦颇为关注,并对其内容和形式做了一些考证与阐发。譬如,关于古乐的篇章结构,李光地说道:“周乐是四节:一、升歌三终,堂上人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用琴瑟和之,无他声;二、笙入三终,堂下笙《南陔》《白华》《华黍》,亦无他声;三、间歌三终,堂上歌《鱼丽》毕,堂下笙《由庚》,又堂上歌《嘉鱼》毕,堂下笙《崇丘》,又堂上歌《有台》毕,堂下笙《由仪》;四、合乐三终,堂上歌《关雎》《葛覃》《卷耳》,堂下笙《鹊巢》《采蘩》《采苹》,众乐器齐作,舞亦在此时,而乐终矣。”①他还举《尚书·益稷》中的“戛击鸣球”一节为例,认为“搏拊琴瑟以咏”便是第一节升歌,“下管鼗鼓”是第二节笙入,“笙镛以间”是第三节间歌,“合止柷敔”“箫韶九成”是第四节合乐。
关于古乐开始时的演奏次序,朱熹认为是“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②,而李光地则认为此说无据,且与经文不合。他说:“观‘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及‘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反似磬在先。盖堂上堂下,皆用钟磬节之,如今曲中之用板。与歌相应者,曰颂钟、颂磬;与笙相应者,曰笙钟、笙磬也。”③
关于乐舞的演奏时间,经中并无明文,李光地推测应在合乐之时,譬如“箫韶九成”。他以《大武》为例,描述其情状道:“如《大武》‘始而北出’,一人‘总干而山立’,‘夹振驷伐’,但作此象,不知此为何人。旁或歌‘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之章,则人知其为武王大正于商,俟天休命也。‘再成而灭商’,一人‘发扬蹈厉’,又不知为何人。旁或歌‘维兹尚父,时维鹰扬’之章,则人知为太公也。‘三成而南’,所谓‘济河而西,马归之华山之阳,牛放之桃林之野’,使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四成而南国是疆’,所谓‘列爵惟五,分土维三’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陕而治’也。‘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所谓‘垂拱而天下治’也。由此推之,则韶之九成,想见舜之功德,征庸、在位、齐政、巡守、命官、殛罪、封山、浚川诸事,遂至九成也。”①
由于《仪礼》所载多为士大夫之礼,天子、诸侯所用礼乐皆不传,故李光地还由士大夫之乐推测当时天子、诸侯所用之乐。譬如,他根据士大夫之乐四节皆三终,而《鹿鸣》《四牡》《皇华》,《文王》《大明》《绵》与《清庙》《维天》《维清》皆为三诗,推测天子、诸侯之乐大概亦是三终。又根据《诗经·商颂·那》“嘒嘒管声”,《尚书·益稷》“下管鼗鼓”,《礼记·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和《仪礼·燕礼》“下管新宫”等描述推测,天子、诸侯之乐的第二节笙入不用笙,而用管。又谓天子、诸侯之乐虽于笙入时用管,但至间歌、合乐时仍用笙,不用管。
论及《礼记》,李光地特重《王制》《乐记》两篇。关于《王制》,李光地说道:
《王制》一篇,先儒谓多举历代之典,盖不尽周制也。然其本末次第,井有条贯,则非苟然编次者。盖首言封建、井田、爵禄之制,乃王道之本也。次言巡狩、朝觐、班锡、田猎之制,王者所以治诸侯也。次及冢宰、司空、司徒、乐正、司马、司寇、市官之职,而以告成受质终焉,王者所以理庶官也。然后及于养老、恤穷之典,使天下无不得其所者,则又所以逮万民也。庶官理于内,诸侯顺于外,万民得所于下,而王道备矣。然必自封建、井田始,故二事不还,则三代终不可得而复也。②
《王制》一篇主要记载古代的封国、爵禄、职官、祭祀、巡狩、养老等制度。由于其中所述制度多与《周礼》不合,故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汉文帝博士所作,或秦汉间学者所作,乃杂取圣贤经传中所载历代制度斟酌损益而成。而李光地则从文章的内在理路分析,认为《王制》先论王道之本,后依次言王者所以治诸侯、理庶官、逮万民之法,使庶官理于内,诸侯顺于外,万民得所于下,而王道备矣。其本末次第,井井有条,合乎义理,并非出于后人缀辑,而是周代旧文。至于《王制》所载多非周制的问题,李光地解释道:
《王制》当是殷制,故其通篇次叙,恰与《洪范》“八政”相符。想禹当年锡洛叙畴之后,一切规模制度,都从此出,所以《禹贡》中山川田赋,数皆用九。殷人承之,因于夏礼所谓“缵禹旧服”者也。则夏制疑亦仿此。直至文王演《易》,画出《后天图》来,其后周家六官,遂从天地四时起义,非复“八政”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之序矣。然宾、师二者,《洪范》次于后,而《王制》居前。《王制》所以定立国规模,非《洪范》立教垂训之比。宾、师乃国事之尤大者,故先之。①
禹之《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今观《王制》,自冢宰制国以下至司寇,其序正合。盖冢宰所司,食、货、祀三者备矣。然后以司空定民之居,然后以司徒兴民之德。至于乐正、司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以附于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终焉。宾、师二者,《洪范》次于后,《王制》叙于前。盖《洪范》言其切于民生之先后缓急,则柔远安邦之事宜居养教之后;《王制》言其关于建国之规模纲纪,则礼乐征伐之柄必在庶政之先,义各有所当也。此书上比《虞典》,既微有不同,下视周制,又甚相悬绝,独与《洪范》,则其暗合若此。②
郑玄注解《王制》,多以殷制为说。李光地借鉴了郑玄的这一思路,亦主张《王制》是殷制,并进一步指出其制度规模与基本框架源自于禹所作的“洪范九畴”中的“八政”。他的依据是《王制》中由冢宰至司寇的职官次序恰与《洪范》“八政”相符。唯一的不同在于,宾、师二者在《洪范》中次于后,而在《王制》中居于前。宾是掌诸侯朝觐之官,师是掌军旅之官,李光地认为二者乃国事之尤大者。只不过因为《洪范》切于民生立教,而《王制》重于建国规模,故《洪范》以宾、师次后,而《王制》以宾、师居前。由于殷承夏制,而周代则由文王、周公据《易经》之义重订制度,故《王制》虽作于周,却与周制不同。
《乐记》有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①这段话提出天理、人欲之分,又暗含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历来为理学家所特别重视,反复征引阐发,成为理学心性论最重要的经典依据之一。李光地亦赞叹道:“《乐记》‘人生而静’一段,真是千圣传心之要典,与虞廷十六字同。‘人心’‘道心’四字,浑含精微;‘天理’‘人欲’四字,刻画透露。”②
李光地还将《乐记》一篇划分为若干段落,并逐段概括其大意。他首先将《乐记》开头至“魏文侯问于子夏”这一部分分为八段,提出:“自‘凡音之起’至‘而出治道也’为第一段,自‘凡音者’至‘德者得也’为第二段。此二段言乐之生于人心而关乎政治也。自‘乐之隆’至‘则礼行矣’为第三段,言先王作乐,感人心之效。自‘大乐与天地同和’至‘故圣人曰礼乐云’为第四段,又推其制作之原,极其神化之妙,其精微所存,有不在区区器数声容之间者矣。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善则行象德矣’为五段,申乐之关乎政也。自‘夫豢豕为酒’至‘可以观德矣’为六段,申乐之生乎人心,而感通之效也。自‘德者性之端也’至‘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为第七段,又以申其制作之精,神化之盛,诚不在气数声容之间也。”①李光地认为,这一部分构成了《乐记》全篇的核心内容,揭示了其主旨。“盖统乐之本末而论之,则生于人心者,还足以感乎人心;成乎风俗者,还足以变乎风俗;本于天地者,还足以通乎天地。是以终篇反复推明,而大旨不过如此而已。”②他又将“君子曰”至“礼乐可谓盛矣”归为一段,视作乐之总论,认为应当依据《史记》附于上述第七段之后。至于其余部分,李光地认为“魏文侯”一节言声,“宾牟贾”一节言舞,而“子贡”一节则言声容之本。分析完全篇之后,李光地再次强调:“戴氏之编,自《学》《庸》外,未有若是之精神者也。留心礼乐者,其可不致思焉?”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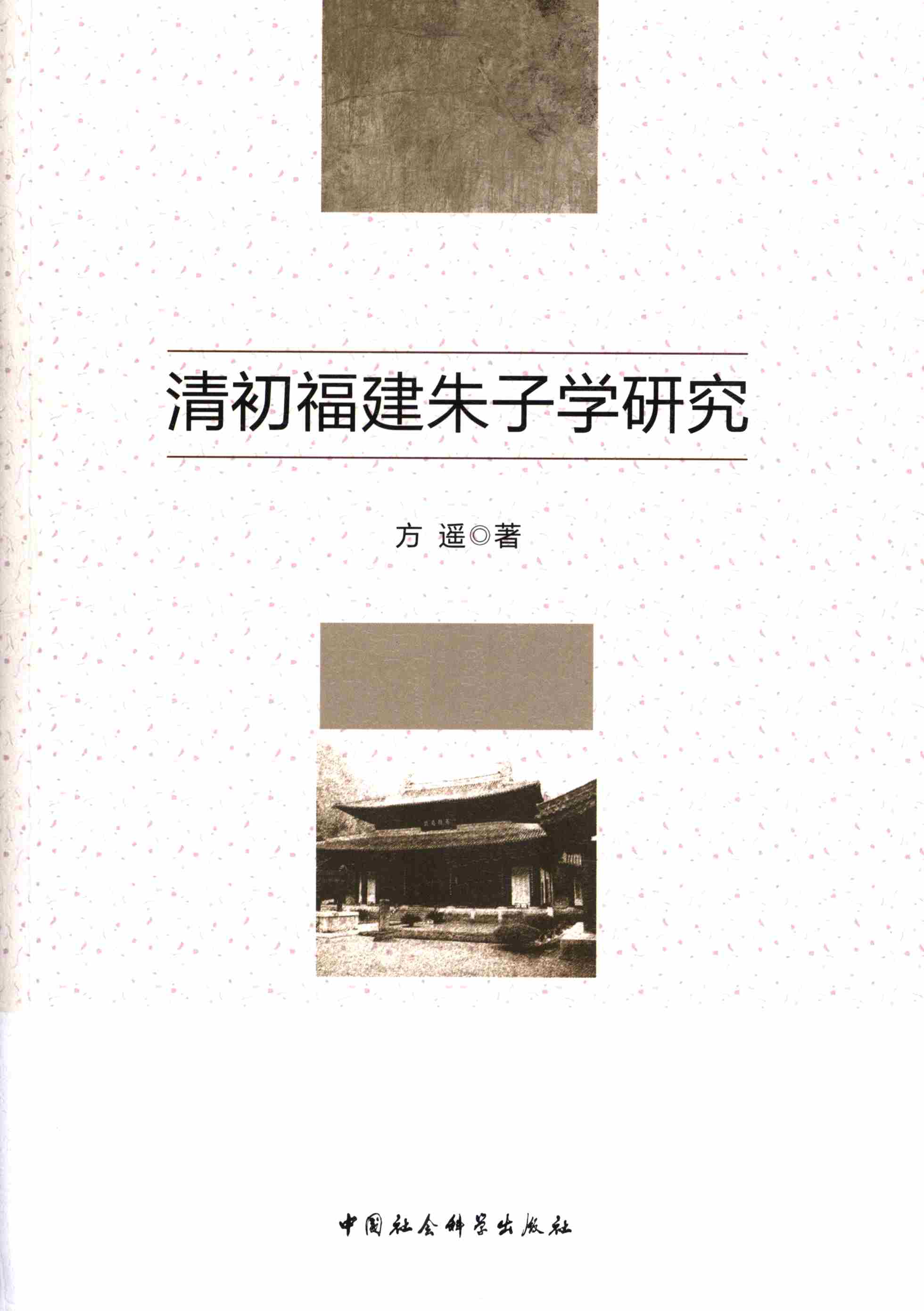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
相关人物
李光地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