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光地的《诗经》学研究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85 |
| 颗粒名称: | 二 李光地的《诗经》学研究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412-427 |
| 关键词: | 李光地 易学 《周易》 |
内容
李光地在概论《诗经》之学时,往往会提及所谓的“《雅》《郑》之辨”,并将其作为朱熹《诗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与成果加以表彰。简单来说,朱熹认为《诗经》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淫奔之诗”,而这些淫诗主要集中在《郑风》《邶风》《鄘风》《卫风》中,尤以《郑风》为多,且淫乱之意最甚。郑、卫之诗即为“郑、卫之音”,郑诗便是孔子所说的“郑声淫”“放郑声”中的“郑声”。对于朱熹的这一观点,李光地十分赞同,表示“朱子《易》《诗》卜筮、雅郑之说,吾所笃信也”②,又说:“孔子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然则《雅》《郑》之判久矣。汉儒以为三百之篇皆圣人所删定,可以存为训戒,被之弦歌,故《序》于淫诗悉归之刺者之作。然实有不可通者,朱子之辨明矣。当日论难,以为郑声则淫,非诗淫也,朱子答以‘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至哉斯言!虽孔子复生,何以易此?”①
对于《诗经》,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不少尊信《诗序》的学者便以此为据,主张《诗经》中并无淫诗,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而朱熹既然认为《诗经》中存在淫诗,自然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他解释道:
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③
非言作诗之人“思无邪”也。盖谓三百篇之诗,所美者皆可以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为戒,读之者“思无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无邪”乎?只是要正人心。④
“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某《诗传》去《小序》,以为此汉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类,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诗人作此以讥刺其人也。圣人存之,以见风俗如此不好。至于做出此诗来,使读者有所愧耻而以为戒耳。⑤
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①
朱熹认为,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并不是指整部《诗经》的所有篇章都无邪,也不是指作诗者所思无邪,而是说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诗经》达到内心“思无邪”的目的与效用。《诗经》本身的内容固然美恶邪正夹杂,但其美者皆可以为法,恶者皆可以为戒,“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②,故有正人心之效。而圣人之所以要保存那些淫诗,亦是为了使读者有所警惧愧耻而引以为戒。
李光地基本同意朱熹对于“思无邪”的这种理解,并进一步就《诗经》中何以存有淫诗这一问题给出了解答:
“《诗》三百”章,依朱子说,则当以“无”字与“毋”通,禁止辞也。言《诗》之为教,归于使人禁止其邪思,故虽有三百之多,而《鲁颂》一言,可以蔽其指也。……其词意显然不可掩覆,如《桑中》《洧外》,乃为淫词无疑。圣人所以存而不删,正以见一国之俗化如此,而其间尚有特立独行之人,不以风雨辍其音,不以如云乱其志,则民彝之不泯可见,而欲矫世行义者可以兴。此圣人之意也。……是故郑人之诗,“思无邪”者仅耳,而其皎然有志操者,则以淫俗而愈彰。故曰:“举世浑浊,贞士乃见。”郑、卫之存淫诗,乃与“思无邪”之义相反而相明,盖变例也。③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非言作诗之人性情无邪,亦非言诗之辞义无邪。盖言《诗》之为教,所以禁止人邪心而已。“无”字亦当与“毋”通。夫子言《诗》三百篇,而其为教则可以一言蔽其义,不过禁止人之邪心而已。夫先王之教,《诗》《书》《礼》《乐》,孰非所以收放心、养徳性之具?然至于讽咏优游,感发兴起,使人之邪慝自消,则未若《诗》教之切。《诗》之为教,人事洽于下,天道备于上。然其要,所以道性情,使人以劝以戒,则蔽其义者,未若“思无邪”一语之精也。此“思无邪”三字与“毋不敬”语气相似,皆当作戒词看,则文意自然明白。①
“无”者,犹“毋”也,禁止之也。《诗》教如此,非概《诗》辞也。……俗化之不知,则劝戒之不明。有《桑中》《洧外》之人,则《东门》《风雨》所以贵也。今欲旌显幽节,必先列强暴者之罪状。此数诗,罪状也。其俗如此,而犹有王泽民彝在焉,如晦而不辍其音,如云而不乱其意,此所以为性情之正,而可以观,可以兴者,此也。②
李光地认为,“思无邪”的“无”字通“毋”字,“思无邪”即“思毋邪”,与“毋不敬”语气类似,乃禁止、告诫之辞。因此,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说作诗之人性情无邪,也不是说诗之辞义皆无邪,而是表示《诗经》的立教宗旨是为了劝善惩恶,防止人们的邪心、邪思。简言之,“思无邪”指的是《诗》教,而非《诗》辞。另一方面,李光地认为,郑、卫之诗中虽然存在淫诗,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卫之诗皆是淫诗。事实上,即便其国俗化如此,郑、卫之诗尚有正诗,郑、卫之地仍有善人。圣人之所以要在《郑风》《卫风》等篇中保存这些淫诗、恶事,正是为了公布其罪状,并与其地的善人、善行相对照,以此突出和表彰善人、善行之可贵,显示王道人伦之不可泯灭,使读者可以明辨善恶,为善去恶。李光地还指出,《诗经》中不仅郑、卫之诗有邪思,其他一些诗篇中亦包含邪思、恶事。“岂独《郑》《卫》尔?《二南》之篇,亦以邪正而相形也。江汉之女,有求之者矣;怀春之女,有诱之者矣;行露之女,有速之狱讼者矣。”①“《汉广》之游女,有求之者矣;《行路》《野麕》之贞人,有诱之者矣,幸而求之诱之无传诗耳。设其有之而兼载焉,固所以形恶而彰善,而又何讳乎?”②此处所要表达的亦是所谓“形恶而彰善”的意思。若从这一角度来看,则圣人之存淫诗恰好与“思无邪”之义相反而相明。
李光地虽然在“思无邪”的问题上基本认同朱熹之说,但他亦未完全否定吕祖谦等人以作诗之人为无邪思的看法。譬如他说:
然谓作诗之人自无邪思者,亦不为无理。盖《诗》为夫子所删,则黜弃者多矣,其存者必其醇者也。虽有郑、卫淫佚之诗,较之全编,殆不能什之一,则从其多者而谓之“思无邪”也可矣。就《郑》《卫》之中,亦有未必淫诗而朱子姑意之者,《风雨》《青矜》之类是也。③
《雅》《郑》之辨,正矣。虽然,谓《诗》之无邪者,未可尽非也。圣人之以一言蔽者,概言《诗》之正者多而已矣。列国之诗,俗化而声变,《郑》《卫》之荡也,《齐》《秦》之夸也,圣人间存焉,以为泯其失,无以彰其得也;不极乎民心之流,不足以显民彝之真也。郑政之昏也,如风雨之晦;秦法之厉也,如霜露之零。于是喈喈者不辍其音,苍苍者不改其色,故以为礼义之在人心也,若王化之行,而又何征乎?④
在李光地看来,《诗经》中虽然确有淫诗存在,但其数量极少,所占比例亦极低,而朱熹对于《诗经》中淫诗数量的估计不免过高,以至于将一些并非淫诗的诗也当作淫诗看待。如《郑风》中的《风雨》与《子衿》二诗,朱熹谓其词意轻佻儇薄,皆以淫诗视之,而李光地却认为《风雨》之意,“《序》谓思君子者可从。盖以‘风雨’‘鸡鸣’为兴也。鸡之知时,或有东方微濛之景,则感之而鸣。然风雨冥晦,且无星月之光,而鸡鸣之节不改也。郑俗昏乱,而犹有心知礼义,独为言行,而不失其操者,是以同道者见而喜之”,又谓《子矜》“《序》谓刺学校,朱《传》谓淫奔者,详诗意俱无显证,或亦朋友相思念之辞尔”。①因此,从整体上看,《诗经》中绝大部分内容皆为正诗,若要笼统地说作诗之人无邪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同时,若以李光地提出的“形恶而彰善”“以王泽民彝之犹在察其无邪焉”②的观点来理解淫诗的存在与意义,则极少数淫诗不仅不会妨碍读者对于《诗》无邪的总体判断,而且有助于无邪之《诗》教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与吕祖谦等人主张的《诗》皆无邪之说相通。
李光地在讨论、分析了朱、吕两派“思无邪”说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自己对于“思无邪”的另一种理解:
“邪”字,古多作“余”解,《史记》《汉书》尚如此。“思无邪”,恐是言思之周尽而无余也。观上“无疆”“无期”“无斁”,都是说思之深的意思。《邶》之《北风》,亦作“余”解。古人历法拙,闰月必定在十二月,故曰“闰者,岁之余;虚者,朔虚也”。言冬月将尽,而岁余亦将终,比北风、雨雪又急矣。但“思无邪”,从来都说是“邪正”之邪,故《诗所》亦姑依之,不欲破尽旧解。其实他经说道理学问,至世事人情,容有搜求未尽者,惟《诗》穷尽事物曲折,情伪变幻,无有遗余,故曰“思无邪”也。③
李光地参考《史记》《汉书》以及《诗经》本文等资料,将“思无邪”的“邪”字解作“余”字,认为“思无邪”是指《诗经》之思周尽而无余的意思。在他看来,虽然各部经典中都包含丰富的义理,但其他经典所言道理学问,乃至世事人情,仍不免有搜求未尽者,唯有《诗经》一书穷尽事物曲折与情伪变幻,无有遗余,所以孔子才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此一来,则“思无邪”一语便与《诗经》中是否存在淫诗的争论脱离了关系,亦不失为对《诗经》淫诗问题的一种辩护与解答。当然,李光地的这一解释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但他能够大胆超出长久以来以“邪正”之“邪”来理解“思无邪”的传统思路,另辟蹊径,自圆其说,既反映了其独立思考、不囿旧说的学术特点,也为后人重新理解“思无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可能。
《雅》《郑》之辨中还附带包含了一个如何理解“郑诗”与“郑声”的关系问题。吕祖谦认为,郑声不等于郑诗,故郑声淫并非郑诗淫。朱熹则主张郑声即郑诗,“‘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①,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而李光地则在遵从朱熹《诗》说的基本前提下,对于郑诗与郑声的关系,以及孔子对待二者的不同态度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以修正、完善朱熹的《诗》学理论。他说:
东莱以为“《诗》无邪”,焉得有淫风?朱子以“放郑声”诘之,吕云:“郑声淫,非郑诗淫也。”朱子曰:“未有诗淫而声不淫者。”本末源流,已一句说尽,但却亦要知诗自诗,声自声,不然《虞书》何为说“诗言志”,又说“声依永”?夫子何为说“兴于诗”,又说“成于乐”?不淫诗亦可以淫声歌之,淫诗亦可以不淫声歌之,如旦曲以净唱,净曲以旦唱,只是不合情事耳。何以“放郑声”,不放郑诗?这却易知。丑行恶状,采风者存为鉴戒,见得淫风便至乱亡。若播之于乐,要人感动此心,却是何为?如商臣陈恒等,寻常说话时,何妨举为灭伦乱理之戒?若被之管弦,摹写他如何举动,是甚意思?圣人之权衡精矣。①
彼谓夫子“放郑声”,则不宜录此者,似已。然朱子谓乐教与《诗》教不同,放其声者乐也,存其篇者《诗》也。声入于耳,感于心,则不可以无放。若夫考其俗以究治乱之本,极其弊以察是非之心,篇可不存乎?是故郑人之诗,“思无邪”者仅耳,而其皎然有志操者,则以淫俗而愈彰。②
孔子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然则《雅》《郑》之判久矣。……当日论难,以为郑声则淫,非诗淫也,朱子答以“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至哉斯言!虽孔子复生,何以易此?然声与诗亦有不可不辨者。论其合,则自“言志”至于“和声”一也,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未有本末乖离者也。论其分,则诗直述情事,而乐被以音容,故曰“兴于诗,成于乐”。郑诗可存也,而郑声必放。以为道情事者,人能辨其非,饰之音容,则惑焉者众矣。然则圣人何不并其诗而放之?曰:“是于乐中论其声,况又有《鸡鸣》《风雨》《东门》之篇错出其间,苟没其诗,无以知其善。放郑声,则犹之远佞人也;存郑诗,则犹之知佞人之情状,见而能辨,辨而知恶者也。”③
事实上,朱熹虽然坚持郑声淫即郑诗淫,但他为了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何孔子既主张“放郑声”,却又存郑诗的问题,亦初步注意到了郑声与郑诗之间的某些差别。譬如他说:“吕伯恭以为‘放郑声’矣,则其诗必不存。某以为放是放其声,不用之郊庙宾客耳,其诗则固存也。如《周礼》有官以掌四夷之乐,盖不以为用,亦存之而已。”④又说:“放者,放其乐耳;取者,取其诗以为戒。今所谓郑卫乐,乃诗之所载。”①这也就是李光地所说的“朱子谓乐教与《诗》教不同”。而他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的这一思路,同时借鉴吕祖谦等人关于“诗”“声”不同的主张,从而得出了“声与诗亦有不可不辨者”的观点。
具体来说,李光地认为,“诗”与“声”、“诗”与“乐”之间既有相合的一面,又有相分的一面。自其合者言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之始终条理备矣。诗所以言志,而诗之言,必抑扬高下,歌之而后可听。其诗之和平广大者,以宫声歌之;清扬激发,慷慨悲壮者,以商声歌之;欢忻流畅者,以角声歌之;急疾清促者,以徵声歌之;繁碎嘈杂者,以羽声歌之。然五声无节,不能中和,则以律和之。由律而写其声于八音之中,至于克谐,无相夺伦,则神人以和矣”②。简言之,即诗、歌、声、律四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在乐中合而为一,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未有本末乖离者。自其分者言之,诗属于直述情事,而乐则有音韵、节奏等外在形式,遂有“诗言志”与“声依永”、“兴于诗”与“成于乐”之间的区别。故“不淫诗亦可以淫声歌之,淫诗亦可以不淫声歌之”。尽管这样做未免有违常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李光地进一步指出,与诗相比,声、乐较为感性,更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所以郑诗可存为鉴戒,使人知其丑行恶状,读者亦不难明辨其非,而郑声必放,以免蛊惑人心,败坏风俗。总之,在李光地看来,“诗”与“声”、“诗”与“乐”二者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而郑诗与郑声在内容上或许有许多重合之处,但在表现形式、影响效果和目的作用等方面皆有所不同,不宜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综上亦可发现,李光地对于《雅》《郑》之辨的理解与论述主要是以朱熹《诗》学为基础,折中、融会朱、吕二家《诗》说而形成的,从中体现出其不立门户、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故曰:“朱子《易》《诗》卜筮、雅郑之说,吾所笃信也。程谓随时以从道,吕谓作诗之无邪,吾则兼取焉,以为与朱子之说相备而不相悖也。盖执其两端,则中者出矣,穷理之要也。”①
根据传统看法,《诗经》曾经孔子删削,这一观点在唐代之前几乎无人提出异议。如最早提出删《诗》说的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②班固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采鲁,凡三百五篇。”③郑玄说:“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圣贤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④陆德明则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⑤
至唐代时,孔颖达提出:“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⑥,始对孔子删《诗》说提出怀疑。朱熹等人既然认定《诗经》中存在淫诗,那么孔子删《诗》的旧命题就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如果孔子确曾删《诗》,为何当存者不存,反而保留了许多淫诗?对于《诗经》中的淫诗问题,朱熹虽以“惩恶”“鉴戒”之说加以解释,但他却并未因此承认孔子删《诗》。他说:“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圣人当来刊定,好底诗便要吟咏,兴发人之善心;不好底诗便要起人羞恶之心,皆要人‘思无邪’。”①又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②,“论来不知所谓删者,果是有删否?要之,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到孔子时已经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如云:‘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则是还其旧位”③。由此可见,朱熹显然不以孔子删《诗》之说为然,只承认孔子曾整理、刊定《诗经》而已。
与朱熹的看法不同,李光地相信孔子删《诗》之说,屡言“圣人删《诗》最妙”④,“《诗》三百亦删后之诗”⑤,“《诗》为夫子所删,则黜弃者多矣,其存者必其醇者也”⑥,并且对孔子删《诗》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可算作对传统删《诗》说的一种补充。
关于孔子删《诗》的具体内容及其原因,李光地说道:
圣人删《诗》之意,当就《论语》中求之。如“素以为绚”句,某意即在《硕人》之诗,而夫子去之。素自素,绚自绚,如人天资自天资,学问自学问,岂可说天资高便不用学问不成?正如“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又如“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一般。“绘事后素”,亦言绘事必继素后耳。“礼后乎”,亦言礼必继忠信之后乎?皆言绚不可抹杀也。推此可以见删《诗》之意。⑦
《关雎》之诗,夫子明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自非淫诗。……天下惟此乐不淫,哀不伤,外此未有不淫伤者。《唐棣》之诗孔子删之,以其无此意也。①
李光地认为,根据《论语》之文推断,孔子曾删去《卫风·硕人》中的“素以为绚”一句。《论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②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即出自《诗经》的《卫风·硕人》。在李光地看来,“素以为绚”的“素”代表人的天资,“绚”代表人的学问,素自素,绚自绚,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决定关系,不能说天资可当学问,天资高的人便不用后天的学习。而孔子亦言“绘事后素”,肯定了“质”与“文”之间的区别,主张天资好的人也须加以后天的问学之功,外在的礼仪必须接续在内在的忠信之后。可见“素以为绚”之说不合道理,故为孔子所删。同样,李光地又据《论语》断定《诗经》中的《唐棣》之诗也经过孔子的删削。《论语·子罕》载有“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历代学者多将其视为逸诗。李光地认为此言不符合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所以孔子删之。除此之外,李光地还说:“齐桓、晋文之事,艳于天下,而皆无诗焉。或者夸美之过,而夫子删之矣。”③怀疑《诗经》中原有记载齐桓、晋文之事的诗篇,或许由于过度夸美,有悖理义,遭到了孔子的删削。
在此基础上,李光地进一步考察了《论语》中有关孔子论《诗》的记载,虚心体会圣人之意,归纳、概括出孔子删《诗》的六条凡例:“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为《二南》,便正墙面;不学《诗》,便无以言;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思无邪;皆是删《诗》凡例。”①在他看来,这六条便是孔子论《诗》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凡是符合这六条原则的诗便为孔子所保留,凡是违背这六条原则的诗必为孔子所删削。至于李光地为何在承认《诗经》中包含淫诗的同时,又将“思无邪”列为孔子删《诗》的凡例之一,上文在讨论“思无邪”说的时候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处恕不赘述。
浏览李光地文集、语录中记载的论《诗》之言不难发现,其对于《诗经》中各诗的时代、世次等问题特别关注,并且提出了不少异于前人的看法。譬如,历代学者多受郑玄等人的影响,认为《诗经》中的《雅》《颂》多为西周之诗,而《国风》多为东周之诗。李光地则提出:“以愚论之,十五国之诗,必也东、西周具有焉,而后可通也。不独《风》尔,《大小雅》之诗,亦必东、西周具有焉,而后可通也”②,认为《风》《雅》《颂》中都同时包含东、西周时期的诗。具体来说:
如《郑》《卫》之武公,《秦》之襄公,如《序》者之说,固非尽东周矣。《小雅》之篇,所谓“周宗既灭,靡所底戾”,“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亦岂西周之词哉?惟《豳风》之为周公可信。若《颂》则有“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不显成康”者,既足以明其非尽周公之作,而《鲁颂》则僖公诗也,亦不得谓东迁之后无《颂》也。且以事理揆之,《风》者,天子命太史陈诗而得者也。西周之盛,巡狩庆让之典行,故风谣达焉。及其既东,则天子不巡狩,太师不采风也旧矣。今乃西京之采,乐府之藏,无一篇在者,而尽出于东迁之后乎?则其诗又孰采之,而孰收之也?如谓夫子周游所得,则季札观乐于鲁,而其篇什既备矣。鲁存六代礼乐,故自《韶箾》《夏濩》以下皆具。曾谓昭代乐府,列国之诗,太史之所掌者尽皆亡轶,而反取东迁以后不隶于乐府,莫之采而莫之收者,以与《易》象、《春秋》并藏,而与《韶》《夏濩》《武》《雅》《颂》迭奏,必不然矣。①
某谓畿内之地,亦有风谣,虽西周盛时,岂能无《风》。王朝卿士贤人,闵时念乱,虽既东之后,岂尽无《雅》。只可以正、变分治乱,不可以《风》《雅》为盛衰也。观《二雅》体制,不进于《颂》,东迁后,犹有《鲁颂》,况《雅》乎!然西周不见所谓《风》,东周亦复无《雅》者,意畿内醇美之诗,悉附于《二南》以为正《风》,而衰乱之《风》,则别为《王风》而为变;至《雅》之无东,则序《诗》者失之也。今观所谓“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周宗既灭”;“今也日蹙国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风》,东迁有变《雅》之证,而说《诗》者穿凿以就其例。此正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缘说者谓皆周公制礼作乐时诗,遂以为非二王,而别为解释耳。其可信乎?此三百一大义,不敢附和先儒而不阙所疑也。②
《大雅》章什,世次最明。《文王》以下皆周盛时诗也,《民劳》以下则厉王诗,《云汉》以下则宣王诗,《瞻印》以下则幽王或东迁以后诗。《小雅》则《鹿鸣》以下为盛时诗,《六月》以下为宣王以后诗,《节南山》《正月》以下为幽王及东迁以后诗,叙亦甚明。独《楚茨》诸篇之叙田功,《瞻彼洛矣》诸篇之叙朝会,皆不类幽王以后事,且有“王在在镐”之文,则又非东迁可知。③
李光地指出,从诗的内容上看,《郑风》《卫风》涉及武公,《秦风》涉及襄公,说明《国风》并非都是东周之诗。《大雅》部分,自《瞻印》以下为周幽王或东迁以后诗;《小雅》部分,自《节南山》《正月》以下,除《楚茨》《瞻彼洛矣》等篇外,亦为周幽王及东迁以后诗。《鲁颂》四篇为鲁僖公诗,证明东周时期仍然有《颂》。他特别提到,《小雅·正月》明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雨无正》明言“周宗既灭,靡所底戾”,《大雅·召旻》明言“今也日蹙国百里”,显然皆是东周之诗;《国风·召南·何彼秾矣》则言“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证明王畿有正《风》。从道理上看,《风》诗乃天子命采诗之官所采,待天子巡守时陈诗以观民风,没有西周兴盛时所采之诗一无所存,而东周既衰之后的诗反而大量保留的道理。若说《风》诗是孔子周游时所得,则当时鲁国六代礼乐皆存,亦没有只记录东周时不隶于乐府,不知何人所采、何人所收的诗,而不记录保存完备、来历清晰的西周之诗的道理。另一方面,《风》《雅》《颂》的体制是相对固定的,三者同时并存而不会互相取代。《雅》诗既不会因西周兴盛而进于《颂》,也不会因东周衰乱而降为《风》。且《二雅》的体制低于《颂》,东周时即便衰乱,尚且有《鲁颂》,不可能完全没有《雅》诗。因此,李光地不同意《诗经》中无西周之《风》与东周之《雅》的观点。在他看来,学者之所以会误以为西周不见《风》,主要是由于西周畿内之诗为正《风》,已附于《二南》之中,故与东周之变《风》不同,而学者之所以会误以为东周无《雅》,则是由于《诗序》作者对《二雅》年代的误判和错置。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光地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诗》亡说:
《诗》亡之说何如?曰:“殆谓正《风》、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子举巡狩之典,陈诗观风,于是庆让行焉;诸侯修述职之礼,朝会雅歌,于是劝戒继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劝惩明也。及周之东,天子不巡狩,则太师无采也,故谓之《风》亡。其有《风》者,列国讴谣相为传播者耳。诸侯不述职,则朝会无闻也,故谓之《雅》亡。其有《雅》者,贤人君子思古念乱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劝惩不明,诸侯僭,大夫叛,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其所由来者渐矣。是故《春秋》之褒贬,所以申王事之劝惩也。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①
李光地认为,孟子所说的“《诗》亡”是指东周时期的正《风》、正《雅》亡。因为《风》源自于天子巡狩时,采风视俗以行庆让之典。东周之后,天子不巡狩,太师不采风,庆让之典亦废,所以说《风》亡。如今《诗经》中所保存的东周之《风》,乃列国间自己流传的歌谣,非太师所采,只能称作变《风》。而《雅》则源自于诸侯述职时的朝会雅歌。东周之后,周王室衰微,诸侯不再行述职之礼,所以说《雅》亡。如今《诗经》中所保存的东周之《雅》,乃贤人君子思古念乱、忧虑时俗所作,只能称作变《雅》。孔子正是看到当时王道不行、功罪劝惩不明、礼崩乐坏的混乱状况,才作《春秋》而寓之褒贬,以申明王事之劝惩。所以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
对于《诗经》,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不少尊信《诗序》的学者便以此为据,主张《诗经》中并无淫诗,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而朱熹既然认为《诗经》中存在淫诗,自然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他解释道:
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③
非言作诗之人“思无邪”也。盖谓三百篇之诗,所美者皆可以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为戒,读之者“思无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无邪”乎?只是要正人心。④
“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某《诗传》去《小序》,以为此汉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类,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诗人作此以讥刺其人也。圣人存之,以见风俗如此不好。至于做出此诗来,使读者有所愧耻而以为戒耳。⑤
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①
朱熹认为,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并不是指整部《诗经》的所有篇章都无邪,也不是指作诗者所思无邪,而是说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诗经》达到内心“思无邪”的目的与效用。《诗经》本身的内容固然美恶邪正夹杂,但其美者皆可以为法,恶者皆可以为戒,“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②,故有正人心之效。而圣人之所以要保存那些淫诗,亦是为了使读者有所警惧愧耻而引以为戒。
李光地基本同意朱熹对于“思无邪”的这种理解,并进一步就《诗经》中何以存有淫诗这一问题给出了解答:
“《诗》三百”章,依朱子说,则当以“无”字与“毋”通,禁止辞也。言《诗》之为教,归于使人禁止其邪思,故虽有三百之多,而《鲁颂》一言,可以蔽其指也。……其词意显然不可掩覆,如《桑中》《洧外》,乃为淫词无疑。圣人所以存而不删,正以见一国之俗化如此,而其间尚有特立独行之人,不以风雨辍其音,不以如云乱其志,则民彝之不泯可见,而欲矫世行义者可以兴。此圣人之意也。……是故郑人之诗,“思无邪”者仅耳,而其皎然有志操者,则以淫俗而愈彰。故曰:“举世浑浊,贞士乃见。”郑、卫之存淫诗,乃与“思无邪”之义相反而相明,盖变例也。③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非言作诗之人性情无邪,亦非言诗之辞义无邪。盖言《诗》之为教,所以禁止人邪心而已。“无”字亦当与“毋”通。夫子言《诗》三百篇,而其为教则可以一言蔽其义,不过禁止人之邪心而已。夫先王之教,《诗》《书》《礼》《乐》,孰非所以收放心、养徳性之具?然至于讽咏优游,感发兴起,使人之邪慝自消,则未若《诗》教之切。《诗》之为教,人事洽于下,天道备于上。然其要,所以道性情,使人以劝以戒,则蔽其义者,未若“思无邪”一语之精也。此“思无邪”三字与“毋不敬”语气相似,皆当作戒词看,则文意自然明白。①
“无”者,犹“毋”也,禁止之也。《诗》教如此,非概《诗》辞也。……俗化之不知,则劝戒之不明。有《桑中》《洧外》之人,则《东门》《风雨》所以贵也。今欲旌显幽节,必先列强暴者之罪状。此数诗,罪状也。其俗如此,而犹有王泽民彝在焉,如晦而不辍其音,如云而不乱其意,此所以为性情之正,而可以观,可以兴者,此也。②
李光地认为,“思无邪”的“无”字通“毋”字,“思无邪”即“思毋邪”,与“毋不敬”语气类似,乃禁止、告诫之辞。因此,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说作诗之人性情无邪,也不是说诗之辞义皆无邪,而是表示《诗经》的立教宗旨是为了劝善惩恶,防止人们的邪心、邪思。简言之,“思无邪”指的是《诗》教,而非《诗》辞。另一方面,李光地认为,郑、卫之诗中虽然存在淫诗,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卫之诗皆是淫诗。事实上,即便其国俗化如此,郑、卫之诗尚有正诗,郑、卫之地仍有善人。圣人之所以要在《郑风》《卫风》等篇中保存这些淫诗、恶事,正是为了公布其罪状,并与其地的善人、善行相对照,以此突出和表彰善人、善行之可贵,显示王道人伦之不可泯灭,使读者可以明辨善恶,为善去恶。李光地还指出,《诗经》中不仅郑、卫之诗有邪思,其他一些诗篇中亦包含邪思、恶事。“岂独《郑》《卫》尔?《二南》之篇,亦以邪正而相形也。江汉之女,有求之者矣;怀春之女,有诱之者矣;行露之女,有速之狱讼者矣。”①“《汉广》之游女,有求之者矣;《行路》《野麕》之贞人,有诱之者矣,幸而求之诱之无传诗耳。设其有之而兼载焉,固所以形恶而彰善,而又何讳乎?”②此处所要表达的亦是所谓“形恶而彰善”的意思。若从这一角度来看,则圣人之存淫诗恰好与“思无邪”之义相反而相明。
李光地虽然在“思无邪”的问题上基本认同朱熹之说,但他亦未完全否定吕祖谦等人以作诗之人为无邪思的看法。譬如他说:
然谓作诗之人自无邪思者,亦不为无理。盖《诗》为夫子所删,则黜弃者多矣,其存者必其醇者也。虽有郑、卫淫佚之诗,较之全编,殆不能什之一,则从其多者而谓之“思无邪”也可矣。就《郑》《卫》之中,亦有未必淫诗而朱子姑意之者,《风雨》《青矜》之类是也。③
《雅》《郑》之辨,正矣。虽然,谓《诗》之无邪者,未可尽非也。圣人之以一言蔽者,概言《诗》之正者多而已矣。列国之诗,俗化而声变,《郑》《卫》之荡也,《齐》《秦》之夸也,圣人间存焉,以为泯其失,无以彰其得也;不极乎民心之流,不足以显民彝之真也。郑政之昏也,如风雨之晦;秦法之厉也,如霜露之零。于是喈喈者不辍其音,苍苍者不改其色,故以为礼义之在人心也,若王化之行,而又何征乎?④
在李光地看来,《诗经》中虽然确有淫诗存在,但其数量极少,所占比例亦极低,而朱熹对于《诗经》中淫诗数量的估计不免过高,以至于将一些并非淫诗的诗也当作淫诗看待。如《郑风》中的《风雨》与《子衿》二诗,朱熹谓其词意轻佻儇薄,皆以淫诗视之,而李光地却认为《风雨》之意,“《序》谓思君子者可从。盖以‘风雨’‘鸡鸣’为兴也。鸡之知时,或有东方微濛之景,则感之而鸣。然风雨冥晦,且无星月之光,而鸡鸣之节不改也。郑俗昏乱,而犹有心知礼义,独为言行,而不失其操者,是以同道者见而喜之”,又谓《子矜》“《序》谓刺学校,朱《传》谓淫奔者,详诗意俱无显证,或亦朋友相思念之辞尔”。①因此,从整体上看,《诗经》中绝大部分内容皆为正诗,若要笼统地说作诗之人无邪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同时,若以李光地提出的“形恶而彰善”“以王泽民彝之犹在察其无邪焉”②的观点来理解淫诗的存在与意义,则极少数淫诗不仅不会妨碍读者对于《诗》无邪的总体判断,而且有助于无邪之《诗》教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与吕祖谦等人主张的《诗》皆无邪之说相通。
李光地在讨论、分析了朱、吕两派“思无邪”说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自己对于“思无邪”的另一种理解:
“邪”字,古多作“余”解,《史记》《汉书》尚如此。“思无邪”,恐是言思之周尽而无余也。观上“无疆”“无期”“无斁”,都是说思之深的意思。《邶》之《北风》,亦作“余”解。古人历法拙,闰月必定在十二月,故曰“闰者,岁之余;虚者,朔虚也”。言冬月将尽,而岁余亦将终,比北风、雨雪又急矣。但“思无邪”,从来都说是“邪正”之邪,故《诗所》亦姑依之,不欲破尽旧解。其实他经说道理学问,至世事人情,容有搜求未尽者,惟《诗》穷尽事物曲折,情伪变幻,无有遗余,故曰“思无邪”也。③
李光地参考《史记》《汉书》以及《诗经》本文等资料,将“思无邪”的“邪”字解作“余”字,认为“思无邪”是指《诗经》之思周尽而无余的意思。在他看来,虽然各部经典中都包含丰富的义理,但其他经典所言道理学问,乃至世事人情,仍不免有搜求未尽者,唯有《诗经》一书穷尽事物曲折与情伪变幻,无有遗余,所以孔子才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此一来,则“思无邪”一语便与《诗经》中是否存在淫诗的争论脱离了关系,亦不失为对《诗经》淫诗问题的一种辩护与解答。当然,李光地的这一解释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但他能够大胆超出长久以来以“邪正”之“邪”来理解“思无邪”的传统思路,另辟蹊径,自圆其说,既反映了其独立思考、不囿旧说的学术特点,也为后人重新理解“思无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可能。
《雅》《郑》之辨中还附带包含了一个如何理解“郑诗”与“郑声”的关系问题。吕祖谦认为,郑声不等于郑诗,故郑声淫并非郑诗淫。朱熹则主张郑声即郑诗,“‘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①,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而李光地则在遵从朱熹《诗》说的基本前提下,对于郑诗与郑声的关系,以及孔子对待二者的不同态度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以修正、完善朱熹的《诗》学理论。他说:
东莱以为“《诗》无邪”,焉得有淫风?朱子以“放郑声”诘之,吕云:“郑声淫,非郑诗淫也。”朱子曰:“未有诗淫而声不淫者。”本末源流,已一句说尽,但却亦要知诗自诗,声自声,不然《虞书》何为说“诗言志”,又说“声依永”?夫子何为说“兴于诗”,又说“成于乐”?不淫诗亦可以淫声歌之,淫诗亦可以不淫声歌之,如旦曲以净唱,净曲以旦唱,只是不合情事耳。何以“放郑声”,不放郑诗?这却易知。丑行恶状,采风者存为鉴戒,见得淫风便至乱亡。若播之于乐,要人感动此心,却是何为?如商臣陈恒等,寻常说话时,何妨举为灭伦乱理之戒?若被之管弦,摹写他如何举动,是甚意思?圣人之权衡精矣。①
彼谓夫子“放郑声”,则不宜录此者,似已。然朱子谓乐教与《诗》教不同,放其声者乐也,存其篇者《诗》也。声入于耳,感于心,则不可以无放。若夫考其俗以究治乱之本,极其弊以察是非之心,篇可不存乎?是故郑人之诗,“思无邪”者仅耳,而其皎然有志操者,则以淫俗而愈彰。②
孔子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然则《雅》《郑》之判久矣。……当日论难,以为郑声则淫,非诗淫也,朱子答以“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至哉斯言!虽孔子复生,何以易此?然声与诗亦有不可不辨者。论其合,则自“言志”至于“和声”一也,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未有本末乖离者也。论其分,则诗直述情事,而乐被以音容,故曰“兴于诗,成于乐”。郑诗可存也,而郑声必放。以为道情事者,人能辨其非,饰之音容,则惑焉者众矣。然则圣人何不并其诗而放之?曰:“是于乐中论其声,况又有《鸡鸣》《风雨》《东门》之篇错出其间,苟没其诗,无以知其善。放郑声,则犹之远佞人也;存郑诗,则犹之知佞人之情状,见而能辨,辨而知恶者也。”③
事实上,朱熹虽然坚持郑声淫即郑诗淫,但他为了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何孔子既主张“放郑声”,却又存郑诗的问题,亦初步注意到了郑声与郑诗之间的某些差别。譬如他说:“吕伯恭以为‘放郑声’矣,则其诗必不存。某以为放是放其声,不用之郊庙宾客耳,其诗则固存也。如《周礼》有官以掌四夷之乐,盖不以为用,亦存之而已。”④又说:“放者,放其乐耳;取者,取其诗以为戒。今所谓郑卫乐,乃诗之所载。”①这也就是李光地所说的“朱子谓乐教与《诗》教不同”。而他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的这一思路,同时借鉴吕祖谦等人关于“诗”“声”不同的主张,从而得出了“声与诗亦有不可不辨者”的观点。
具体来说,李光地认为,“诗”与“声”、“诗”与“乐”之间既有相合的一面,又有相分的一面。自其合者言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之始终条理备矣。诗所以言志,而诗之言,必抑扬高下,歌之而后可听。其诗之和平广大者,以宫声歌之;清扬激发,慷慨悲壮者,以商声歌之;欢忻流畅者,以角声歌之;急疾清促者,以徵声歌之;繁碎嘈杂者,以羽声歌之。然五声无节,不能中和,则以律和之。由律而写其声于八音之中,至于克谐,无相夺伦,则神人以和矣”②。简言之,即诗、歌、声、律四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在乐中合而为一,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未有本末乖离者。自其分者言之,诗属于直述情事,而乐则有音韵、节奏等外在形式,遂有“诗言志”与“声依永”、“兴于诗”与“成于乐”之间的区别。故“不淫诗亦可以淫声歌之,淫诗亦可以不淫声歌之”。尽管这样做未免有违常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李光地进一步指出,与诗相比,声、乐较为感性,更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所以郑诗可存为鉴戒,使人知其丑行恶状,读者亦不难明辨其非,而郑声必放,以免蛊惑人心,败坏风俗。总之,在李光地看来,“诗”与“声”、“诗”与“乐”二者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而郑诗与郑声在内容上或许有许多重合之处,但在表现形式、影响效果和目的作用等方面皆有所不同,不宜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综上亦可发现,李光地对于《雅》《郑》之辨的理解与论述主要是以朱熹《诗》学为基础,折中、融会朱、吕二家《诗》说而形成的,从中体现出其不立门户、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故曰:“朱子《易》《诗》卜筮、雅郑之说,吾所笃信也。程谓随时以从道,吕谓作诗之无邪,吾则兼取焉,以为与朱子之说相备而不相悖也。盖执其两端,则中者出矣,穷理之要也。”①
根据传统看法,《诗经》曾经孔子删削,这一观点在唐代之前几乎无人提出异议。如最早提出删《诗》说的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②班固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采鲁,凡三百五篇。”③郑玄说:“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圣贤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④陆德明则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⑤
至唐代时,孔颖达提出:“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⑥,始对孔子删《诗》说提出怀疑。朱熹等人既然认定《诗经》中存在淫诗,那么孔子删《诗》的旧命题就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如果孔子确曾删《诗》,为何当存者不存,反而保留了许多淫诗?对于《诗经》中的淫诗问题,朱熹虽以“惩恶”“鉴戒”之说加以解释,但他却并未因此承认孔子删《诗》。他说:“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圣人当来刊定,好底诗便要吟咏,兴发人之善心;不好底诗便要起人羞恶之心,皆要人‘思无邪’。”①又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②,“论来不知所谓删者,果是有删否?要之,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到孔子时已经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如云:‘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则是还其旧位”③。由此可见,朱熹显然不以孔子删《诗》之说为然,只承认孔子曾整理、刊定《诗经》而已。
与朱熹的看法不同,李光地相信孔子删《诗》之说,屡言“圣人删《诗》最妙”④,“《诗》三百亦删后之诗”⑤,“《诗》为夫子所删,则黜弃者多矣,其存者必其醇者也”⑥,并且对孔子删《诗》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可算作对传统删《诗》说的一种补充。
关于孔子删《诗》的具体内容及其原因,李光地说道:
圣人删《诗》之意,当就《论语》中求之。如“素以为绚”句,某意即在《硕人》之诗,而夫子去之。素自素,绚自绚,如人天资自天资,学问自学问,岂可说天资高便不用学问不成?正如“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又如“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一般。“绘事后素”,亦言绘事必继素后耳。“礼后乎”,亦言礼必继忠信之后乎?皆言绚不可抹杀也。推此可以见删《诗》之意。⑦
《关雎》之诗,夫子明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自非淫诗。……天下惟此乐不淫,哀不伤,外此未有不淫伤者。《唐棣》之诗孔子删之,以其无此意也。①
李光地认为,根据《论语》之文推断,孔子曾删去《卫风·硕人》中的“素以为绚”一句。《论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②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即出自《诗经》的《卫风·硕人》。在李光地看来,“素以为绚”的“素”代表人的天资,“绚”代表人的学问,素自素,绚自绚,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决定关系,不能说天资可当学问,天资高的人便不用后天的学习。而孔子亦言“绘事后素”,肯定了“质”与“文”之间的区别,主张天资好的人也须加以后天的问学之功,外在的礼仪必须接续在内在的忠信之后。可见“素以为绚”之说不合道理,故为孔子所删。同样,李光地又据《论语》断定《诗经》中的《唐棣》之诗也经过孔子的删削。《论语·子罕》载有“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历代学者多将其视为逸诗。李光地认为此言不符合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所以孔子删之。除此之外,李光地还说:“齐桓、晋文之事,艳于天下,而皆无诗焉。或者夸美之过,而夫子删之矣。”③怀疑《诗经》中原有记载齐桓、晋文之事的诗篇,或许由于过度夸美,有悖理义,遭到了孔子的删削。
在此基础上,李光地进一步考察了《论语》中有关孔子论《诗》的记载,虚心体会圣人之意,归纳、概括出孔子删《诗》的六条凡例:“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为《二南》,便正墙面;不学《诗》,便无以言;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思无邪;皆是删《诗》凡例。”①在他看来,这六条便是孔子论《诗》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凡是符合这六条原则的诗便为孔子所保留,凡是违背这六条原则的诗必为孔子所删削。至于李光地为何在承认《诗经》中包含淫诗的同时,又将“思无邪”列为孔子删《诗》的凡例之一,上文在讨论“思无邪”说的时候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处恕不赘述。
浏览李光地文集、语录中记载的论《诗》之言不难发现,其对于《诗经》中各诗的时代、世次等问题特别关注,并且提出了不少异于前人的看法。譬如,历代学者多受郑玄等人的影响,认为《诗经》中的《雅》《颂》多为西周之诗,而《国风》多为东周之诗。李光地则提出:“以愚论之,十五国之诗,必也东、西周具有焉,而后可通也。不独《风》尔,《大小雅》之诗,亦必东、西周具有焉,而后可通也”②,认为《风》《雅》《颂》中都同时包含东、西周时期的诗。具体来说:
如《郑》《卫》之武公,《秦》之襄公,如《序》者之说,固非尽东周矣。《小雅》之篇,所谓“周宗既灭,靡所底戾”,“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亦岂西周之词哉?惟《豳风》之为周公可信。若《颂》则有“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不显成康”者,既足以明其非尽周公之作,而《鲁颂》则僖公诗也,亦不得谓东迁之后无《颂》也。且以事理揆之,《风》者,天子命太史陈诗而得者也。西周之盛,巡狩庆让之典行,故风谣达焉。及其既东,则天子不巡狩,太师不采风也旧矣。今乃西京之采,乐府之藏,无一篇在者,而尽出于东迁之后乎?则其诗又孰采之,而孰收之也?如谓夫子周游所得,则季札观乐于鲁,而其篇什既备矣。鲁存六代礼乐,故自《韶箾》《夏濩》以下皆具。曾谓昭代乐府,列国之诗,太史之所掌者尽皆亡轶,而反取东迁以后不隶于乐府,莫之采而莫之收者,以与《易》象、《春秋》并藏,而与《韶》《夏濩》《武》《雅》《颂》迭奏,必不然矣。①
某谓畿内之地,亦有风谣,虽西周盛时,岂能无《风》。王朝卿士贤人,闵时念乱,虽既东之后,岂尽无《雅》。只可以正、变分治乱,不可以《风》《雅》为盛衰也。观《二雅》体制,不进于《颂》,东迁后,犹有《鲁颂》,况《雅》乎!然西周不见所谓《风》,东周亦复无《雅》者,意畿内醇美之诗,悉附于《二南》以为正《风》,而衰乱之《风》,则别为《王风》而为变;至《雅》之无东,则序《诗》者失之也。今观所谓“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周宗既灭”;“今也日蹙国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风》,东迁有变《雅》之证,而说《诗》者穿凿以就其例。此正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缘说者谓皆周公制礼作乐时诗,遂以为非二王,而别为解释耳。其可信乎?此三百一大义,不敢附和先儒而不阙所疑也。②
《大雅》章什,世次最明。《文王》以下皆周盛时诗也,《民劳》以下则厉王诗,《云汉》以下则宣王诗,《瞻印》以下则幽王或东迁以后诗。《小雅》则《鹿鸣》以下为盛时诗,《六月》以下为宣王以后诗,《节南山》《正月》以下为幽王及东迁以后诗,叙亦甚明。独《楚茨》诸篇之叙田功,《瞻彼洛矣》诸篇之叙朝会,皆不类幽王以后事,且有“王在在镐”之文,则又非东迁可知。③
李光地指出,从诗的内容上看,《郑风》《卫风》涉及武公,《秦风》涉及襄公,说明《国风》并非都是东周之诗。《大雅》部分,自《瞻印》以下为周幽王或东迁以后诗;《小雅》部分,自《节南山》《正月》以下,除《楚茨》《瞻彼洛矣》等篇外,亦为周幽王及东迁以后诗。《鲁颂》四篇为鲁僖公诗,证明东周时期仍然有《颂》。他特别提到,《小雅·正月》明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雨无正》明言“周宗既灭,靡所底戾”,《大雅·召旻》明言“今也日蹙国百里”,显然皆是东周之诗;《国风·召南·何彼秾矣》则言“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证明王畿有正《风》。从道理上看,《风》诗乃天子命采诗之官所采,待天子巡守时陈诗以观民风,没有西周兴盛时所采之诗一无所存,而东周既衰之后的诗反而大量保留的道理。若说《风》诗是孔子周游时所得,则当时鲁国六代礼乐皆存,亦没有只记录东周时不隶于乐府,不知何人所采、何人所收的诗,而不记录保存完备、来历清晰的西周之诗的道理。另一方面,《风》《雅》《颂》的体制是相对固定的,三者同时并存而不会互相取代。《雅》诗既不会因西周兴盛而进于《颂》,也不会因东周衰乱而降为《风》。且《二雅》的体制低于《颂》,东周时即便衰乱,尚且有《鲁颂》,不可能完全没有《雅》诗。因此,李光地不同意《诗经》中无西周之《风》与东周之《雅》的观点。在他看来,学者之所以会误以为西周不见《风》,主要是由于西周畿内之诗为正《风》,已附于《二南》之中,故与东周之变《风》不同,而学者之所以会误以为东周无《雅》,则是由于《诗序》作者对《二雅》年代的误判和错置。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光地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诗》亡说:
《诗》亡之说何如?曰:“殆谓正《风》、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子举巡狩之典,陈诗观风,于是庆让行焉;诸侯修述职之礼,朝会雅歌,于是劝戒继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劝惩明也。及周之东,天子不巡狩,则太师无采也,故谓之《风》亡。其有《风》者,列国讴谣相为传播者耳。诸侯不述职,则朝会无闻也,故谓之《雅》亡。其有《雅》者,贤人君子思古念乱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劝惩不明,诸侯僭,大夫叛,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其所由来者渐矣。是故《春秋》之褒贬,所以申王事之劝惩也。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①
李光地认为,孟子所说的“《诗》亡”是指东周时期的正《风》、正《雅》亡。因为《风》源自于天子巡狩时,采风视俗以行庆让之典。东周之后,天子不巡狩,太师不采风,庆让之典亦废,所以说《风》亡。如今《诗经》中所保存的东周之《风》,乃列国间自己流传的歌谣,非太师所采,只能称作变《风》。而《雅》则源自于诸侯述职时的朝会雅歌。东周之后,周王室衰微,诸侯不再行述职之礼,所以说《雅》亡。如今《诗经》中所保存的东周之《雅》,乃贤人君子思古念乱、忧虑时俗所作,只能称作变《雅》。孔子正是看到当时王道不行、功罪劝惩不明、礼崩乐坏的混乱状况,才作《春秋》而寓之褒贬,以申明王事之劝惩。所以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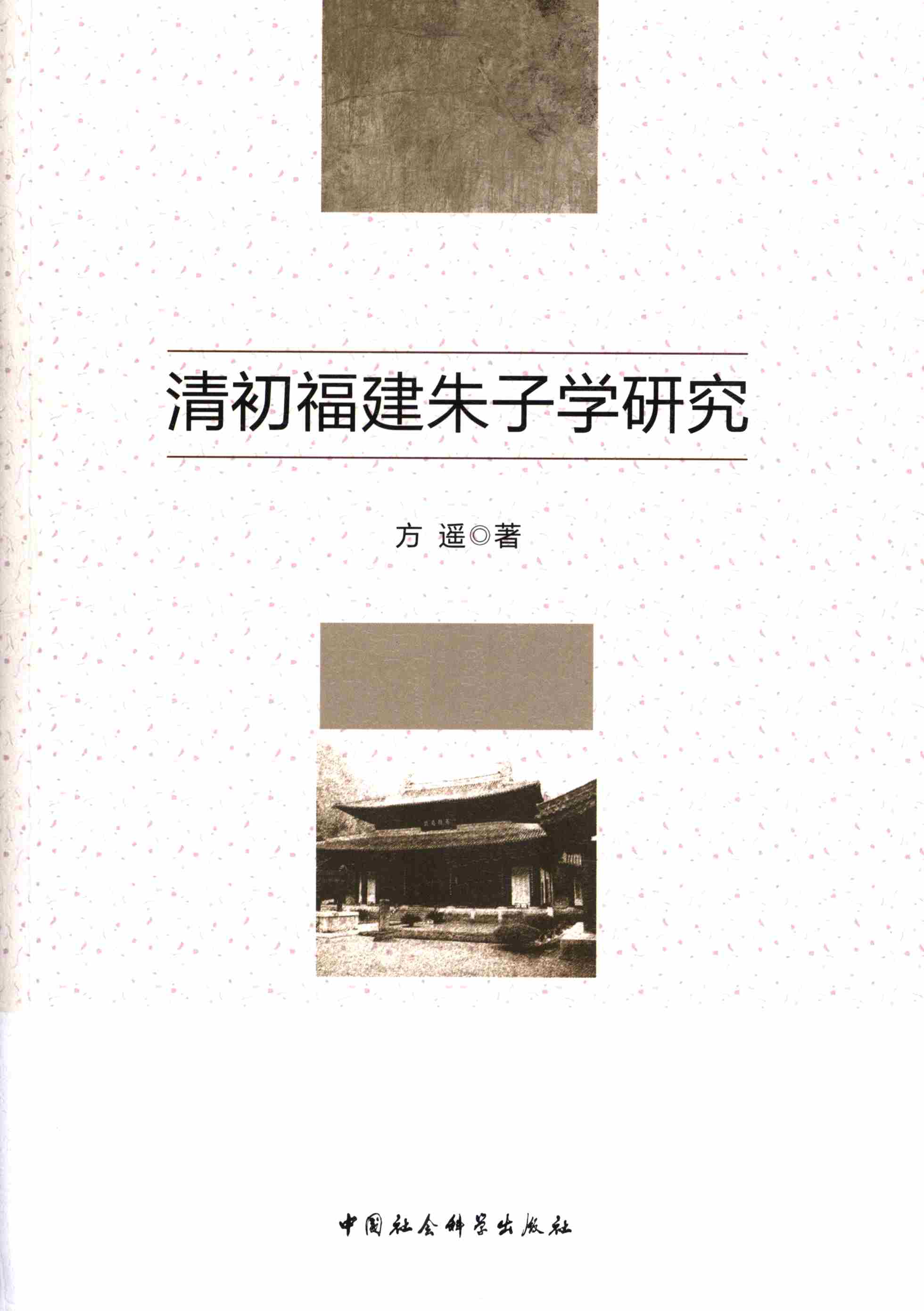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