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光地的易学研究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84 |
| 颗粒名称: | 一 李光地的易学研究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5 |
| 页码: | 388-412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李光地对《周易》的研究及其易学思想。李光地用功深入研究《易经》,将朱熹易学作为基础,吸收前辈福建理学家的成果,并与《参同契》等典籍相互参证,构成了清代易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赞同朱熹的卜筮观点,将《易经》视为卜筮之书,强调象数与义理的结合,同时注重《易传》与《易经》的相合。在研究方法上,李光地注重从象数和卦爻辞中推阐义理,强调卦象的取象与卦名的命名方式。 |
| 关键词: | 李光地 易学 《周易》 |
内容
在六经之学中,李光地对《周易》的研究可谓用力最多,用功最深,而所得与影响亦最大。对于自己的易学研究,李光地曾说:“某治《易》,虽不能刻刻穷研,但无时去怀,每见一家解必看。今四十七年矣,觉得道理深广,无穷无尽。”②据《文贞公年谱》记载,李光地自十八岁即玩心于《易》,二十岁便纂《周易解》一部,颇能“于诸家同异,条分缕析,用为熟研覃思之地”①,至七十一、七十二岁撰成《周易通论》与《周易观彖大指》,并奉旨承修《周易折中》,七十三岁最终撰成《周易观彖》,“前后凡易稿数十次”,七十四岁修《周易折中》成,“荟萃自汉迄明诸儒之说凡三百余家,采撷精纯,刊取领要,镕铸百氏,陶冶千载,《易》之道于是大备”②,可谓终身用力于易学。李光地的易学思想以朱熹易学为基础,较多地参考、吸收了蔡清、林希元、黄道周等前辈福建理学家的易学成果,又能博采众家,折中义理、象数两派易学之长,并与《参同契》等典籍相互参证,最终以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加以发挥创造,故能取得较大的成就,构成了清代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忽视的发展环节。
关于《易经》的制作本意,李光地赞同朱熹的卜筮之说,并将其视为朱熹易学最重大的发明之一,揭示了《易经》的本质。他说:
《易》不是为上智立言,却是为百姓日用,使之即占筮中,顺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本义》象数宗邵,道理尊程,不复自立说,惟断为占筮而作。提出此意,觉一部《易经》字字活动。朱子亦自得意,以为“天牖其衷”。③
朱子说《易》,亦不必逐段是。如赞《先天图》,以《易》为卜筮之书,皆有大功于《易》。④
朱子崇重《先天图》,得《易》之本原,明为占筮之书,得《易》之本义。⑤
李光地认为,“三代学术所尊,《诗》《书》《礼》《乐》四者而已。《易》之籍掌于太卜,非学者所务也。是以秦汉之间,齿于种树医药,其流为风雨占候。盖去古未远,相为习沿若此”,后孔子虽于其中阐发性命之理,但亦未尝“离卜筮之指而空言设教”。①因此,李光地特别强调:“《易》之用以卜筮而益周,《易》之道以卜筮而益妙,而凡经之象数辞义,皆以卜筮观之而后可通”②,从而将明卜筮之本义视为理解一部《易经》的关键所在。
关于《周易》的形成历史与发展阶段,李光地亦从朱熹之说,承认《周易》存在伏羲之《易》、文周之《易》与孔子之《易》的区别。“设为八卦而观其象,伏羲之《易》也。系之彖爻辞以明示吉凶,文周之《易》也。”③“圣人之精,画卦以示,伏羲之《易》是也。圣人之蕴,因卦以发,文周之《易》是也。”④李光地进一步指出,自孔子作“十翼”之后,汉易多淫于象数之末而离其宗,王弼虽以义理说《易》,但其学不纯,惟“周子穷天人之源;邵子明象数自然之理;程子一一体察之于人事,步步踏实;朱子提出占筮,平正、活动、的确。故《易经》一书,前有四圣,后有四贤”⑤,从而建构了易学发展史上四圣四贤后先相继的传递系统。
但是,与朱熹提倡经传相分,将《易传》整体附于《易经》之后,以复《周易》古本的做法不同,除了具有官方色彩的《周易折中》外,李光地在其他易学著作中,基本都是采用援传于经、经传合编的王弼本,而非朱熹的《周易本义》本。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朱子既复经传次序,今不遵之,而从王弼旧本,何也?曰:“朱子之复古经传也,虑四圣之书之混而为一也。今之仍旧本也,虑四圣之意之离而为二也。盖后世之注经也,文义训诂而已,而又未必其得,故善读经者,且涵泳乎经文,使之浃洽,然后参以注解,未失也。若四圣之书,先后如一人之所为,互发相备,必合之而后识化工之神,则未可以离异观也。”①
不可以文周之《易》为伏羲之《易》,不可以孔子之《易》为文周之《易》,朱子之说也,信乎?曰:“朱子有为言之也,为夫拘文而忘象,凿理而弃占者尔。象涵于虚,辞指于实,占其本教,理其源出,混之则不知赓续缉熙之功也,离之则不知道法揆合之神也。故其赞曰:‘恭惟三古,四圣一心。’”②
其言四圣之《易》各有不同,固是。然又须晓得伏羲之《易》,即文、周之《易》,文、周之《易》,即孔子之《易》,划然看作各样,又不是。故朱子又曰:“恭惟三古,四圣一心。”③
由此可见,与朱熹强调经传相分相比,李光地显然更为注重经传相合。李光地指出,朱熹之所以分别经传,是为了揭示《易经》的卜筮本义,纠正时人治《易》“拘文而忘象,凿理而弃占”的弊病,而他主张经传相合则是为了彰显四圣《易》的一脉相承之处,使其互相发明,避免学者将《易经》与《易传》作离异观。同时,李光地治《易》以宋易义理之学为基础,故其强调《易传》与《易经》之间的同一性,认为《易经》的卦爻辞之义须借《易传》方明,“《彖传》为卦爻之枢要”④,亦是为了突出《易传》所确立的以义理解《易》的传统与思路。
李光地治《易》虽以义理为主,但亦不废象数,其易学正是由象数、图书之学而入门的。“某少时好看难书,如乐书、历书之类。即看《易》,亦是将图画来画去,求其变化巧合处。于《太极图》,不看其上下三空圈,却拣那有黑有白、相交相系处,东扯西牵,配搭得来,便得意。”①在李光地看来,《周易》实根于象数而作,六十四卦本身就是象数的表现。“然其为书,始于卜筮之教,而根于阴阳之道,故玩辞必本于观象而不为苟言,占事必由于极数而不为苟用。非徒以象数为先也,象数而理义在焉。”②“此经所言,固皆道德性命之奥,然其渊源实起于图书,苟象数未能精通,则义理亦无根据。”③故言理必根于象数,不可离象数而言理。而他之所以推崇朱熹易学,亦是因为朱熹易学最能将义理与象数结合起来,集宋代易学之大成。故曰:“言数始于焦贡、京房,言理始于王弼,但王弼已中了老庄之说,故其学不纯。六朝、唐浮华相尚,未见有深于经学者。直至邵雍传先天之图,立象尽意,其功极大。程颐《易传》,义理醇正。朱某折中二家之学,理数俱极其归,而易学始定于一。”④
因此,李光地治《易》既注重从《易》的象数与卦爻辞中推阐、论证理学的宇宙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义理思想,又十分强调象数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以象数来解释《易经》。譬如他说:
象也者,像也。故或其卦取于物象而爻当之,则遂以其义之吉凶断,而爻德犹其次也。如《屯》所以为屯者,以其雷在下而未起也,初为《震》主当之,故曰“磐桓”,又以其云在上而未下也,五为《坎》主当之,故曰“屯膏”。《需》所以为需,以其云上于天也,九五《坎》主当之,故为饮食宴乐也。《履》之六三,说而承《乾》,本卦之主,然因彖言“咥人”,而三适当兑口之缺,有受咥之象,故其《传》曰“位不当也”,言其直口之位为不当也。《颐》之初九,本有刚德,能自守者也。以其与上共为《颐》象,而《颐》之为物,其动在下,故曰“朵颐”,而得凶也。《咸》《艮》以人身取象,故《咸》二虽中正,以直腓位而凶;《艮》四虽不中正,以直背位而无咎。《归妹》之凶,以女少而自归故也。初九适当娣象,则不嫌于少且自归矣;六五适当帝女之象,则亦不嫌于自归矣,故皆得吉也。《节》取泽与水为通塞,九二适在泽中,则塞之至也,故虽有刚德而凶也。凡若此类,以爻德比应求之,多所不通,惟明于象像之理,则得之。①
李光地以《屯》《需》《履》《颐》《咸》《艮》《归妹》《节》等卦为例,说明卦象取自物象而爻象当之,故其吉凶主要由爻象的吉凶决定,而非首先取决于爻德或比应。同时,爻象的取象亦与爻义直接相关,取象会因爻义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有一卦六爻,专取一事一物为象,而或一爻别取者,则其义因以异矣。如《需》诸爻皆取沙、泥、郊、穴之象,而五独曰‘需于酒食’,则以五为《需》之主,有《需》之德,而所《需》之安也。《蛊》诸爻皆象父母,而上独曰‘不事王侯’,则以上九居卦之上,无复承于父母之象,人未有不事父母者,故曰‘不事王侯’也。《咸》诸爻皆取身象,惟四不取者,四直心位,因之以论心之感应,而所该者广也。《大壮》诸爻取羊者三,其曰‘壮趾’,曰‘藩决’,亦羊象也。惟二不取者,有中德而居下体,不任壮者也。《蹇》诸爻皆取往来为象,惟二、五不言者,五尊位,二王臣之位,义不避难,无往来者也。《艮》诸爻亦取身象,惟上不取者,九三虽亦《艮》主而直心位,然止未极也,至上而后止极,则尽止之道者也。若此之类,皆其权于义者精,故其取于象者审也。”②
李光地还指出,《易经》的重卦之名亦多由卦象而来。他说:卦之名不尽取于象也,然而取于象者多矣。是故夫子之以《彖传》释卦也,卦象、卦德、爻义盖兼取焉,而又专立一传,特揭两象以明卦意。《易》者,象也,本天道以言人事,此夫子特揭之指也。约之则有三例。有卦名所以取者。地天为《泰》,天地为《否》,火地为《晋》,地火为《明夷》,泽水为《困》,水泽为《节》,水火为《既济》,火水为《未济》之类是也。有卦名虽别取,而象意亦甚切者。一阳统众,所以为《师》,而地中有水亦似之;一阳御下,所以为《比》,而地上有水亦似之;一阳来反,所以为《复》,而地中有雷亦其时也;一阴始生,所以为《姤》,而天下有风亦其候也,此类皆是也。有卦名别取,象意本不甚切,而理亦可通者。《随》之为随,刚来下柔也,泽中有雷,阳气下伏,亦有其象焉;《蛊》之为蛊,刚上柔下也,山下有风,阴气下行,亦有其象焉;四阳居中,则为《大过》,泽之灭木,亦气盛而《大过》之象也;四阴居外,则为《小过》,山上有雷,亦气微而《小过》之象也,此类皆是也。①
李光地将《易经》重卦与卦象有关的命名方式归纳为三种:一是以象直接命名,如《泰》《否》《晋》《明夷》《困》《节》《既济》《未济》诸卦;二是以象的含义来间接命名,如《师》《比》《复》《姤》诸卦;三是以象中所包含的道理来间接命名,如《随》《蛊》《大过》《小过》诸卦。由此可见,卦象与卦名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密切且多层面的,认识、理解卦象对于准确把握卦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容轻忽。
除了卦象与爻象之外,李光地对于《易经》中的数亦很重视。他说:
天地之间,阴阳而已。《河图》之奇耦者,所以纪阴阳之数,仿阴阳之象,而尽阴阳之理也。一奇为阳数,二耦为阴数。其余凡奇者,皆从一而为阳也;凡耦者,皆从二而为阴也。其位则节于四,备于五,而加于十。四者,天地之气分司于四方,迭王于四时之用数也。五者,兼其中之体数也。十者,倍五而成,在四方四时,则阴阳互藏互根之数;在中央,则阴阳混一和会之数也。①
圣人之则《图》作《易》也,非规规于点画之似,方位之配也。其理之一者,有以默启圣人之心而已。《图》所列之数如此,其所涵之象又如此。今以《易》卦观之,天一地二,数之源也,则圣人所取以定两仪者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象之成也,则圣人所取以定四象、八卦者也。何则?一、二之数起,则凡三、五、七、九皆一之变矣,四、六、八、十皆二之变矣,故奇耦之画由此而定也。相得有合之象列,则阴阳之宾主辨,而交易之妙具矣;阴阳之消息序,而变易之机行矣,故四象、八卦之设由此而定也。②
李光地继承了宋儒的图书之学,认为《河图》中包含了阴阳之数、阴阳之象与阴阳之理,圣人依据《河图》画卦作《易》,《易经》中的象数即来源于《河图》中的象数。《河图》中的天一地二之数是数之本源,《易》之两仪、四象、八卦皆由此而定,而《易》之交易、变易亦由其变化、组合、搭配而生。
在天一地二之数外,李光地还很重视《易经》中的天三地二之数。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
天一地二者,数之本也,而曰“参天两地而倚数”,何也?曰:“此《河图》《洛书》所以相为表里也。盖以理言之,天之数常兼乎地之数,故以天一并地二而为三也。以算言之,一一相乘,其数不行,二二而后有四,三三而后有九,故天数起于三,地数起于二也。以象言之,天圆地方,凡圆者,皆以三而成,故设三点于此,无论疏密斜正,求其交会之心而规运之,皆可作圆也;方者,皆以二而成,故设二点于此,亦无论疏密斜正,直其折连之角而矩度之,皆可作方也。
三者殊途同归,皆会于中极之五数。何则?天三地二,合之则五,此所谓阴阳之会,天地之心也。一、三、九、七相乘无穷,二、四、八、六亦相乘无穷,而五者自相乘,此所谓不动之枢,运化之本也。圆之成也三,方之成也四,三四之积,适足以当五之积,此所谓兼体之实,等量之功也。是故《洛书》缘此以起天地人之义也。至于《易》中七、八、九、六之数,盖亦有三者之符焉。参两相加,以三为节,故三三则九矣,三二则六矣,二二一三则七矣,二三一二则八矣。天数相乘,极于九而还于七;地数相乘,极于八而还于六。极者,其进也;还者,其退也。阳主进,阴主退,故阳以九为父,阴以六为母也。凡物圆者,皆以六而包一,实其中则七也,虚其中则六也。凡物方者,皆以八而包一,实其中则九也,虚其中则八也。阳实阴虚,故九、七为阳,六、八为阴。然阴阳之盛者,独七、八耳。九阳之老,而积方之所成,则阳已将变而为阴;六阴之老,而积圆之所得,则阴又将变而为阳矣。是故始于一、二、三、四,而成于六、七、八、九,万理万象万数备矣,莫不自参天两地而来,故曰‘参天两地而倚数’。”①
李光地指出,天三地二之数中包含天一地二,体现了《河图》《洛书》互相统一、互为表里。以理言之,天之数常兼地之数,所以天一加地二而为三。以算言之,一一相乘,其数不行,二二得四,三三得九,所以天数起于三,地数起于二。以象言之,天圆地方,凡圆皆以三而成,凡方皆以二而成,所以同样是天三地二。天三地二之数合而为五,乃阴阳之会,天地之心,亦是《洛书》天地人之义的根据与由来。天三地二相加、相乘又有七、八、九、六之数,于理、于算、于象三方面推衍变化,便可产生万理、万数、万象。此外,李光地对于《先天图》与《后天图》中的象数亦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论述,支持、维护并完善了朱熹的图书学理论。
由于李光地治《易》兼顾义理与象数,强调由卜筮以明义理,故其易学的一大特色便是对于《易经》卜筮之辞的重视与研究。他说:
读《易》先要知道“元亨利贞”四字。文王本意,只说大通而利于正,孔子却作四件说,朱子谓并行不悖,亦未言其故。孔子读书细,亨而谓之大,毕竟亨前有个大;利于正,毕竟正前有个利。元,大也,始也,凡物之始者便大。如唐虞是何等事业,洙泗是何等学问,然须知是尧舜之心胸,孔子之志愿,其初便大不可言。范文正作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程明道方成童,便以圣贤自期。这却在事功、学问之先。赤子之心大人不失者,赤子之心,最初之心,无所为而为,不自私也。不自私便大,大则统率群物。长子曰元子,以能统率众子也;天子曰元后,以能统率诸侯也;长妻曰元妃,以能统率群御也。大而亨,不必既亨始见其大,元自在亨之前。如孔孟终身不得行道,其大自在。我实有此大,不必问其亨不亨也。利而贞,不必既贞始见其利,利自在贞之前。亨便当收回来,宜收而收,便有利益。利本训宜,宜便利。如人君手致太平,便宜兢兢业业,持盈保泰,这是利。至于社稷巩固,则贞也。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成”字意,“利”字中已有。贞乃是坚实凝固之谓。①
李光地指出,正确理解“元、亨、利、贞”及其相互关系是读懂一部《周易》的前提和基础。四者之中,“元”即大,是“亨”的基础,“亨”即蕴含于“元”中,不必到“亨”始见其大;“利”即宜,是“贞”的前提,“贞”即蕴含于“利”中,不必到“贞”始见其利。而“元”又是四者的统帅与头脑,“亨、利、贞”皆从属于“元”。因为“元”奠定了万事万物初始的规模,规模大则学问、事业方大。其在人身上又表现为不自私的赤子之心,不自私便大,大则能统率群物。因此,事物始于大便能亨通,亨通便当回收、持守,依道理而行,最终便可致万物之成。
李光地又云:
孔子将“元亨利贞”作四件说,其理最精。且以为六十四卦占辞之权舆。占辞有仅曰“亨”者,有曰“小亨”者,是亨不必皆大也。不必皆大,而独系以“元亨”,则是未有亨,先有大也。如农之倍收,贾之获利,亦可言亨,而不可以言大,以其先所谋者原小故也。若士希贤,贤希圣,其勋业功用,直可以充塞天壤。岂不以先有斯大,故亨得来亦大耶?以此例之,则“亨”不如“元亨”,“小亨”又不如“亨”矣。占辞有曰“贞吝”“贞厉”者,有曰“不可贞”者,有曰“贞凶”者,是贞不必皆利也。不必皆利,而独系以利贞,则是未有贞,先有利也。如事之不可常者,以为正而固守之,则必致凶厉矣,何利之有?以此例之,则凡“贞吝”“贞厉”者,必其微有不宜也;其曰“贞凶”者,必其大有不宜也。故以“元亨利贞”作占辞看,似“元”字、“利”字是虚字,“亨”字、“贞”字是实字。被孔子细心读破,“元”字、“利”字却是实际字,“亨”字、“贞”字反是现成字。①
在此,他将“元、亨、利、贞”视作六十四卦占辞之权舆,以这四者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判断、衡量占辞轻重的重要标准。譬如,“亨”“小亨”“元亨”不同,“小亨”不如“亨”,“亨”又不如“元亨”,其结果取决于初始之规模不同。“贞吝”“贞厉”“贞凶”亦不同,“贞吝”“贞厉”者微有不宜,“贞凶”者则大有不宜,其结果取决于是否依理而为。由此亦可看出,“元、亨、利、贞”作为占辞,“元”与“利”是实际字,“亨”与“贞”是现成字,“元”“利”对于占筮结果的解读往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故比“亨”“贞”更为重要。
《易经》的占辞除了“元、亨、利、贞”之外,还有“吉、凶、悔、吝、无咎”等。关于后者的解释,李光地说道:
彖爻之辞,为筮而设,故吉、凶、悔、吝、无咎者,断占之凡例也。吉凶者,失得之象,故辞之吉凶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忧虞之象,故辞之悔吝言乎其小疵也。无咎则行乎四者之间,盖内省不疚,以消悔吝之萌,反己无愆,而顺吉凶之至,乃人心之得其正,而人事之得其平者。故辞之无咎,善乎其补过也。①
李光地以得失言“吉凶”,以小疵言“悔吝”,以善补过言“无咎”。对于这几种状态,李光地反对一味地追求趋吉避凶,而是以无咎为尚。他指出:“人无日不在吉、凶、悔、吝之中,亦无日不欲避凶而趋吉者。然避凶之心胜,必至于害而苟免;趋吉之心胜,必至于利而幸邀。惟君子之心则不然,曰:‘吾求无咎而已。’求无咎者,修其可吉之道而无心于获吉,至于既吉,而其惴惴于无咎之心常在也;去其取凶之道而亦无意于避凶,不幸而凶,而其怛怛于无咎之心常安也。”②因为吉凶是以个人的得失为依据,若以趋吉避凶作为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利己之心便会战胜理义之心,必将导致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故君子只需循道而行,求无咎而使心常在、常安,便是最佳的状态。“悔而无咎,则可以至于吉矣。吉而无咎,则不至于可吝矣。吝而无咎,则必不至于凶矣。凶而无咎,则亦无所可悔矣。故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③而欲达到“无咎”的状态,就必须善于补过,必须能知“悔”。“悔吝则小疵方形,必有其几微之介焉。圣人往往于此而预为之忧,曰如是则有悔,如是则有吝,所以使人谨于几先,不待乎著明而后觉也。无咎虽行乎四者之间,而其机皆在于悔。盖悔而后能补过,能补过而后无咎。其所以一转而为吉者,此也。以是处吉,则必惕然有以保其吉,而不至于吝;以是处吝,则必翻然有以消其吝,而不至于凶矣。故凡《易》之震动人以无咎者,必于悔而发其机焉。”①由此可见,“悔”在占辞中亦极为重要。圣人往往通过“悔”来提醒、告诫人们,在错误或灾祸刚刚萌发、显露的时候,就必须预先有所警觉和防范,并尽早改过或弥补,使其不至于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悔”而后能补过,能补过而后“无咎”,“无咎”方可一转而为“吉”。因此,不论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状态,心中都需要时常保持“悔”的心态。
关于“元、亨、利、贞”与“吉、凶、悔、吝”等占辞在卦爻辞中出现和使用的一些特点与规律,李光地亦有所考究。譬如他注意到,爻辞中无“元亨”,最多只用到“元吉”“大吉”,而卦辞中无“吝”,“悔”亦仅见于《革》卦而已。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元、亨、利、贞者,天道之常,而贯乎人事者也。吉、凶、悔、吝者,人事之致,而通乎天道者也。卦本乎天道,而元亨者,天道之大者也,故爻不得而用之也。爻主乎人事,而悔吝者,人事之细者也,故卦不得而及之也。且元亨之为大也,不独爻无用焉,而见于卦者亦少。②
在他看来,“元、亨、利、贞”属于天道,“吉、凶、悔、吝”则属于人事。卦本乎天道,故“元亨”只可用于卦辞,不可用于爻辞;爻主乎人事,故“悔吝”只可用于爻辞,基本不用于卦辞。“元亨”“利贞”之义若要用于爻辞,则须变“元亨”为“元吉”“大吉”,变“利贞”为“贞吉”。这是因为“卦之义全,爻则偏指一事而言,故变其文以别之也”③。同时,“元亨”所言甚大,不仅不用于爻辞,连卦辞中亦很罕见,除《乾》《坤》二卦之外,仅见于《屯》《革》《随》《临》《无妄》《蛊》《大有》《升》《鼎》诸卦中。这些卦辞或言天人之大者,或以养贤、进贤取义,皆是《易经》最为重视的内容。
李光地还指出,“元吉”与“大吉”意虽相近,但在爻辞的使用中仍略有区别。除了《坤》五、《离》二、《履》上、《复》初四爻以德之纯言“元吉”外,“凡言‘元吉’者,多指吉之在天下者也;凡言‘大吉’者,多指吉之在一人者也”①,故“元”重于“大”。类似地,“利”与“用”、“不利”与“勿用”在彖爻辞中亦属于意相近而辞不同。一方面,“言‘利’‘不利’者,以占者当卦爻谓如此之德、如此之时位,则其利、不利如此也;言‘用’‘不用’者,谓卦爻之德之时如此,占者可用以如此、不可用以如此也”②。简言之,即占筮者与卦爻辞之间的主客关系不同。另一方面,“凡言‘利’者,皆其事后之利。……凡言‘用’者,则即今而可用。……凡言‘不利’者,事无可为之称。……凡言‘勿用’者,暂且勿用之意”③。因此,“利”与“不利”、“用”与“勿用”之间又有缓急之不同。“利”缓于“不利”,“用”又急于“勿用”。“通事后而论之,则‘利’者犹在后也,故缓;‘不利’者终无可为也,故急。即当事而论之,则‘用’者即今可用也,故急;‘勿用’者惟此时勿用而已,故缓。若夫虚言‘无不利’‘无攸利’者,亦包当事、事后之辞也;虚言‘勿用’者,亦是且就其时断之之辞也。”④
此外,李光地在解读卦爻辞时还很强调整体解读的原则,反对将卦爻割裂开来,各自成义,并因此对程颐等人的治《易》方法提出批评。他说:
卦包乎爻而举其纲,爻析乎卦而穷其分。爻不立,无以发卦之缊,而冒天下之道。是故卦爻者,相为表里,相为经纬者也。此文周之书所为二而一者也。①
六爻皆从卦系辞,故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把卦爻看得各自成义,便不融洽。又系得初爻,余爻便可一笔写下,故曰:“初辞拟之,卒成之终。”把各爻看得各自成义,亦不是。②
伊川治《易》,逐爻去看他道理事情。后来尹和靖得伊川之传,教人看《易》,一日只看一爻。朱子便说《易》是联片的,如何一日只看一爻?问:“初学可以逐爻看起否?”曰:“使不得。每一爻如投词人,是个原告、被告,必须会同邻佑、乡保、证佐,四面逼紧审问,方得实情。不然虽审得是,亦不敢自信。不通六爻全看,虽一月看一爻,亦无用。”③由此可见,卦辞与爻辞之间,以及同卦六爻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必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方确实。如《大壮》九四云:“贞吉,悔亡,藩绝不羸,壮于大舆之輹。”有人不免产生疑问,谓:“《泰》之三则有戒词,《壮》至四阳极矣,何以反无戒词而决其往也?”对此,李光地答道:“凡卦诸爻,皆相备为义。《泰》前有拔茅冯河之象矣,故于三戒之。此卦初三既以壮趾触藩为凶厉,二又贞固自守而已,苟非有壮于进者,乘时之义安在乎?卦之为壮,进其义也,要在于贞而已。”④这说明了卦中诸爻的意义是相互影响、先后呼应的,要正确理解卦中某爻的爻辞,就需要联系卦辞及上下爻的爻辞进行整体解读。不同卦中同一位置的爻义往往不同,故不可对爻辞进行抽象、孤立的解读。
《周易》与其他儒家经典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其拥有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学者一般认为这一套相互配合的符号与文字系统中存在某种规律,这便是所谓的“义例”。而发现、认识并掌握这种“义例”就成为准确理解《周易》的重要前提和有效途径。李光地对《周易》中的义例亦极为关注,不仅在《周易折中》中撰有《义例》一篇,在《周易通论》中也对各种义例多有讨论,还特别强调:“至尊最得意《折中》中《义例》一篇,《启蒙附论》道理非不是,却不似《义例》是经中正大切要处。如治天下,《义例》是田赋、学校、官法、兵制、刑狱之类,日日要用,切于实事,《附论》则如王府中所藏‘关石和钧’,本来是道理根源,但终日拿这个来治天下,却不能”①,对于义例在治《易》中的作用可谓推崇备至。从李光地的易学实践来看,他在总结前人义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加以批判性的吸收和创造,主要从卦爻的时、位、德、比应及卦主等方面对《周易》义例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发展、完善了《周易》的义例理论,从而构成了李光地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时”,李光地说道:
王仲淹曰:“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其说善矣。然趋时之义,不可不辨也。近代说《易》,所谓时者,皆似有一时于此,而众人趋之尔。故其象君臣者皆若同朝,象上下者皆若同事。其为时也,既局于一而不通;其趋时也,又以互相牵合而说义多不贯。此则讲解之大患也。夫时也者,六位莫不有焉,各立其位,以指其时,非必如并生一世,并营一事者也。……盖必其所谓时者,广设而周于事,所谓动而趋时者,随所处而尽其理,然后有以得圣人贞一群动之心,而于辞也几矣。是故一世之治乱穷通时也,一身之行止动静亦时也,因其人因其事各有时焉,而各趋之云尔。不然,则何以曰冒天下之道而百姓与能乎?②
王弼曾说:“卦以存时,爻以示变”①,“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②,认为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卦时,即其特定的背景,而事物在这一特定背景下的运动、变化、发展则通过六爻展示、表现出来。这种卦时说曾为一般学者所普遍接受。至隋朝时,王仲淹提出“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的观点,修正了王弼的卦时说。而李光地则在王仲淹的基础上,进一步批驳了王弼的理论,反对每一卦仅有一种特定的背景,而六爻都趋向于同一背景。因为这样将导致卦时“局于一而不通”,而趋时“又以互相牵合而说义多不贯”。在李光地看来,“时”并非特定不动的,不仅卦有“时”,六爻亦各有其“时”,且六爻之“时”因其“位”而各有所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既不必与卦时相同,也不必与其他爻时相同。因此,动而趋时者就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具体情境去把握和理解“时”,这样才能领会圣人贞一群动之心。而关于“时”的内容与种类,李光地提出一世之治乱穷通是时,一身之行止动静是时,因其人因其事各有时;又说:“消息盈虚之谓时,《泰》《否》《剥》《复》之类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讼》《师》《噬嗑》《颐》之类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谦》《咸》《恒》之类是也。又有以象言者,《井》《鼎》之类是也。四者皆谓之时。”③这就极大地丰富、扩展了“时”的内涵,避免了人们对“时”的单一化与抽象化理解。
关于“位”,李光地说道:
贵贱上下之谓“位”。王弼谓中四爻有位,而初上两爻无位,非谓无阴阳之位也,乃谓爵位之位耳。五,君位也。四,近臣之位也。三虽非近,而位亦尊者也。二虽不如三、四之尊,而与五为正应者也。此四爻皆当时用事,故谓之有位。初上则但以时之始终论者为多,若以位论之,则初为始进而未当事之人,上为既退而在事外之人也,故谓之无位。然此但言其正例耳。若论变例,则如《屯》《泰》《复》《临》之初,《大有》《观》《大畜》《颐》之上,皆得时而用事,盖以其为卦主故也。五亦有时不以君位言者,则又以其卦义所取者臣道,不及于君故也。故朱子云:常可类求,变非例测。①
一般认为,《周易》每卦六爻各有其阴阳本位,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为“当位”,否则称“失位”。在王弼看来,一卦的初爻与上爻皆无确定的阴阳本位,故不当论位。而李光地则认为,初、上两爻无位,说的是无爵位,而非无阴阳之位。因为初爻象征始进而未当事之人,上爻象征既退而在事外之人,所以说这两爻无爵位。但是,由于《屯》《泰》《复》《临》四卦的初爻与《大有》《观》《大畜》《颐》四卦的上爻皆为卦主,所以也得时用事,拥有爵位。而某卦的卦义若取臣道,则其五爻亦不为君位。这些都是论“位”时的变例。
关于六爻之“位”的特点,李光地进一步说道:
考《象传》,凡言位当、不当者,独三、四、五三爻尔,初、二皆无之。盖所谓位者,虽以爻位言,然实借以明分位之义。初居卦下,上处卦外,无位者也。二虽有位,而未高者也。惟五居尊,而三、四皆当高位,故言位当、不当者,独此三爻详焉。……《大传》曰“列贵贱者存乎位”,则知爻位有六,而贵者惟此三爻矣。以《象传》之言位当、不当者施于此三爻而不及其它,故知借爻位以明分位之义也。②
在此,李光地再次强调了以爵位论“位”的观点,除了重复初、上两爻无位之外,还指出了二爻亦不言位的现象。而这不免令人疑惑,“二虽未高,然亦有位焉,何以不言也?”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据《大传》“其柔危,其刚胜邪”,“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则三、五宜刚者也,四宜柔者也,二反宜刚者也。三、四、五以当为善,不当为不善,二则反以不当为善,故当、不当之义不得而施于此爻也。①
这就是说,根据《系辞传》所说的“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与“柔之为道,不利远者”的原则,三爻、五爻为刚居阳位,四爻为柔居阴位时,既当位,又是善的;而二爻为柔居阴位时,虽当位,但因其远离五爻,不利于柔,故为不善,所以二爻便不言当位与否了。
接着,李光地还利用这一思路说明了为何“三爻只有言不当,而未有言当;四爻只有言当,而未有言正当;惟五爻多言正当,只有《大壮》五言不当,且反以不当为善”的问题。他说:“盖三,危位也,以柔居之固不当,以刚居之,亦未必当也,此其所以多凶也。四,近位也,以刚居之固不当,以柔居之,亦仅止于当而已,此其所以多惧也。五,尊位也,以刚居之为正当,以柔居之,有柔之善焉,虽不当,犹当也,此其所以多功也。”②
关于“德”,李光地说道:
刚柔、中正、不中正之谓“德”。刚柔各有善不善,时当用刚,则以刚为善也;时当用柔,则以柔为善也。唯中与正,则无有不善者。然正尤不如中之善,故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以此故尔。③
何以谓之德也?有根于卦者焉,健顺、动止、明说之类是也;有生于爻者焉,刚柔、中正之类是也。德无常善,适时为善。故健顺、动止、明说之德,失其节则悖矣;刚柔之道,逆其施则拂矣。……惟中也,正也,则无不宜也,而中为尤善。何也?《易》之义莫重于贞,然亦有贞凶者矣,有贞吝、贞厉者矣,其事未必不是也,而逆其时而不知变,且以为正而固守焉,则凶危之道也。中则义之精而用之妙,凡所谓健顺、动止、明说、刚柔之施,于是取裁焉。先儒所谓“中则无不正”者,此也。①
李光地认为,“德”可分为卦德与爻德两大类。卦德主要指健顺、动止、明说等特性,爻德主要指刚柔、中正等特性。德无常善,适时则为善。如当用刚时,刚便为善;当用柔时,柔便为善。唯有中与正,则无有不善,而中为尤善。这是因为正虽为善,但如果善事与时相逆,却仍以为正而固守,就会导致凶险与危难,而中则是义之精与用之妙,是健顺、动止、明说、刚柔的取裁标准,所以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譬如,除《乾》《坤》二卦外,“其余卦之诸爻,居得正者多矣,而亦鲜以正许之者。惟二与五得其正者,固曰以中正也,或不得其正者,亦曰中以行正也。是则中道之大,而《易》教之至也”②。
既然中道为《易》教之至,比正更为重要,为何“《易》之卦爻于贞盖谆谆焉,其于中行仅数四见而已”?对此,李光地解释道:“正理可识,而中体难明,非深于道者不能知,是故难以察察言也。存其义而没其名,则圣教之精也。”③也就是说,正比较容易被人认识,而中则难以言传,只有深明义理者方能意会,故圣人存其义而没其名,恰好体现出圣人之教的精妙。最后,李光地还强调中与正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正”代表道义的准则,具有外在的客观性,中则是正的实质,中必须通过正表现出来,故须求正以明中道,否则便易流为依违两可,混同无辨。“正非中,则正之实未至;中非正,则中之名亦易差。圣人所以尊中之道而略其名,精求乎正之实,而必广其教者,此也。”①
关于“比”“应”,李光地说道:
“应”者,上下体相对应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连之爻也。《易》中比应之义,唯四与五比,二与五应为最重。盖以五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远而应之也。……凡比与应,必一阴一阳,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刚应刚,以柔应柔,则谓之“无应”。以刚比刚,以柔比柔,则亦无相求相得之情矣。②
自王辅嗣说《易》,多取应爻为义,历代因之。考之夫子《彖象传》,言应者盖有之,然亦观爻之一义尔。若逐爻必以应言,恐非周公之意,亦非孔子所以释经之旨也。以经传之例观之,上下两体,阴阳相求,固其正矣。然《彖传》有以众爻应一爻者,亦有以一爻应众爻者,乃不拘于两体二爻之对。《比》《小畜》《同人》《大有》《豫》之类皆是也。有时义所宜,以阴应阴而吉,以阳应阳而吉者,又不拘于阴阳之偶。《晋》《小过》之王母、祖妣,《睽》《丰》之元夫、夷主之类,皆是也。有以承乘之爻为重者,则虽有应爻而不取。如《观》之观光,《蹇》之来硕,《姤》之包鱼,《鼎》之金铉,而《随》则有失丈夫之失,《观》则有窥观之丑,《姤》则有无鱼之凶,此类皆是也。其余但就其爻之时位才德起义,而不系于应者不可胜数,而欲一一以应义傅会之,则凿矣。③
承乘者谓之比。凡比爻,惟上体所取最多。盖四承五,则如人臣之得君;五承上,则如人主之尊贤。主于五,故其近之者,皆多所取也。然四之承五,惟六四、九五当之;五之承上,惟六五、上九当之。非然者,则亦无得君尊贤之义。……下体三爻所取比义至少,初与二,二与三,间有相从者,随其时义,或吉或否。至三与四,则隔体无相比之情矣。①
“应”指上卦三爻与下卦三爻之间的两两对应关系,包括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上爻相应。一般认为,“应”必须是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其情乃相求而相得。故阴阳、刚柔相应则吉,若以阳应阳,以阴应阴,或以刚应刚,以柔应柔,皆为凶。自王弼以应爻说《易》以来,这一观点为历代学者所普遍接受。而李光地则指出,孔子说《易》虽然确曾言“应”,但只是将其作为观爻之一义,若每爻都硬要以“应”来解释,则非周公、孔子之意。“应”除了“上下两体,阴阳相求”的正例之外,还存在不少变例。譬如,《比》《小畜》《同人》《大有》《豫》等卦就出现以众爻应一爻或以一爻应众爻的情况,而不拘于两体二爻对应;《晋》《小过》《睽》《丰》等卦则有以阴应阴而吉,以阳应阳而吉的现象,而不拘于阴阳相应得吉;《观》《蹇》《姤》《鼎》《随》等卦则以承乘之爻为重,而不取应爻。此外,以爻之时位才德起义的情况尚不可胜数,若欲一一以“应”的关系来解释,必然陷于穿凿附会。总之,使用“应”来解《易》须有限制,不可滥用。
至于“比”,则指相邻两爻比连并列,包含承与乘两种情况。比爻多用于上卦,而下卦较少,介于上下卦之间的三爻与四爻则基本没有相比的情况。
李光地认为,《周易》中的比应关系唯四与五比,二与五应为最吉。因为五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远而应之。加之二与五皆有中德,又各居当时之位,所以二与五应最吉。关于相应关系的吉凶,李光地还提出了“《易》之道,阴暗求于阳明,不以阳求阴也;上位求于下位,不以下求上也”②的原则。即符合以阴求阳、以上求下原则的相应二爻便为吉,否则皆为凶。此外,若三爻与上爻相应,则皆非吉,惟《剥》《损》《益》三卦例外。
关于“卦主”,李光地说道:
凡所谓卦主者,有成卦之主焉,有主卦之主焉。成卦之主,则卦之所由以成者。无论位之高下,德之善恶,若卦义因之而起,则皆得为卦主也。主卦之主,必皆德之善,而得时、得位者为之。故取于五位者为多,而它爻亦间取焉。其成卦之主,即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之善,而兼得时位者也。其成卦之主,不得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与时位,参错而不相当者也。①
圣人系彖之时,虽通观其卦象、卦德,以定名辞之义,然于爻位尤致详焉。盖有因爻位以名卦者,《师》《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谦》《豫》《剥》《复》《夬》《姤》之类是也。有名虽别取,而爻位之义发于辞者,《屯》《蒙》之“建侯”“求我”指初二,《讼》《蹇》《萃》《巽》之“大人”指九五之类是也。是二者皆谓论卦之主爻。但就文王之名辞观之,有包涵其意而未明者矣。至六爻之系,则辞有吉凶,义有轻重,而名辞之意,因以可见。……盖爻之意虽根于卦而后可明,而卦之意亦参于爻而后可知。卦爻相求,则所谓主爻者得矣。主爻者得,则其余爻之或吉或凶因是可推。何则?凡卦义善者,爻能合德则吉,反之则凶也;卦义不善者,爻能反之则吉,合德则凶也。故《师》《比》《谦》《豫》之类,主爻之吉者也,以其德与时适也。若其当与时反者,则为主者反不得吉。如《讼》之上九,则终讼者也;《履》之六三,则咥人者也;《明夷》上六,则明所以夷也;《归妹》上六,则妹所以归也。主爻吉,则余爻之吉者,必其德与主爻类者也。非然,则其比应也,而反是者则凶。主爻凶,则余爻之凶者,必其德与主爻类者也。非然,则其比应也,而反是者则吉。②所谓“卦主”,即一卦之主爻。李光地认为,卦主可分为“成卦之主”与“主卦之主”两种。其中,“成卦之主”是与卦名、卦辞由来直接相关的爻位,而“主卦之主”则是爻德为善,且得时、得位的爻位,故取于五位者为多。就前者来说,只要某爻是卦名或卦辞的来源,不论其爻位高下,爻德善恶,皆为此卦之卦主。因此,卦名、卦辞与爻意之间便可互相发明。学者既能利用卦名与卦辞来确定主爻,亦可通过主爻之意来理解卦名与卦辞的含义。同时,通过主爻的吉凶还可推断出其余爻的吉凶。主爻之德与时相适便是吉,主爻之德与时相反便是凶。确定主爻的吉凶之后,若主爻为吉,则余爻之德与主爻相类,或与主爻相比应的便是吉,反之则凶;若主爻为凶,则余爻之德与主爻相类,或与主爻相比应的便是凶,反之则吉。
李光地进一步说道:
若其卦成卦之主,即主卦之主,则是一主也。若其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则两爻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爻,则两爻又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象,则两象之两爻,又皆为卦主矣。①
主爻不拘于一,如《蒙》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以“童蒙”应之,则亦主爻也;《师》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使“长子帅师”,则亦主爻也;《履》之六三固主爻矣,九四有虎尾之象,则亦主爻也;《泰》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为下交之主,则亦主爻也。又如《临》之初、二,《观》之五、上,《坎》《离》之二、五,《萃》《升》之四、五,则皆自卦义而定,不妨两为卦主也。又如《震》有两主,而其重在初;《艮》有两主,而其重在上;《既济》二、五得中,而其重在二;《未济》二、五得中,而其重在五,此则因卦义而变者。《履》之三、四象虎尾,而其吉在四;《颐》之初、上象颐,而其凶在初;《大过》三、四象栋,而其吉在四;《小过》初、上象鸟,而其尤凶在初,此则又因物象而变者。若此之类,推说难尽,姑举其概,各随卦义、爻才而观之可也。凡卦有无主者,则以其义甚大,而爻德不足以配。如“同人于野”之义至大,六二之吝固不足以当之矣,惟上九居卦外,有野之象,而其德非中正,故仅止于郊而已;“恒久”之义至大,六五之贞固不足以当之矣,惟九二刚中,有久中之德,然位失其正,故止于悔亡而已。是二卦者,无主爻也。①
李光地指出,一卦并非只能有一个主爻,也可能存在两个或多个主爻。若一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抑或成卦兼取两爻或两象,那么一卦便有两个卦主。当一卦存在两个或多个卦主时,其中往往还有主次轻重之分,而其判断方法则随各卦的卦义与爻才而定。所谓“卦有无主者”,指的是主卦之主。由于主卦之主必须兼顾爻德与时、位,所以当卦义甚大,而爻德不足以配,或位失其正时,此卦便无主卦之主。至于成卦之主,则每卦皆有,故不存在无主的情况。
关于《易经》的制作本意,李光地赞同朱熹的卜筮之说,并将其视为朱熹易学最重大的发明之一,揭示了《易经》的本质。他说:
《易》不是为上智立言,却是为百姓日用,使之即占筮中,顺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本义》象数宗邵,道理尊程,不复自立说,惟断为占筮而作。提出此意,觉一部《易经》字字活动。朱子亦自得意,以为“天牖其衷”。③
朱子说《易》,亦不必逐段是。如赞《先天图》,以《易》为卜筮之书,皆有大功于《易》。④
朱子崇重《先天图》,得《易》之本原,明为占筮之书,得《易》之本义。⑤
李光地认为,“三代学术所尊,《诗》《书》《礼》《乐》四者而已。《易》之籍掌于太卜,非学者所务也。是以秦汉之间,齿于种树医药,其流为风雨占候。盖去古未远,相为习沿若此”,后孔子虽于其中阐发性命之理,但亦未尝“离卜筮之指而空言设教”。①因此,李光地特别强调:“《易》之用以卜筮而益周,《易》之道以卜筮而益妙,而凡经之象数辞义,皆以卜筮观之而后可通”②,从而将明卜筮之本义视为理解一部《易经》的关键所在。
关于《周易》的形成历史与发展阶段,李光地亦从朱熹之说,承认《周易》存在伏羲之《易》、文周之《易》与孔子之《易》的区别。“设为八卦而观其象,伏羲之《易》也。系之彖爻辞以明示吉凶,文周之《易》也。”③“圣人之精,画卦以示,伏羲之《易》是也。圣人之蕴,因卦以发,文周之《易》是也。”④李光地进一步指出,自孔子作“十翼”之后,汉易多淫于象数之末而离其宗,王弼虽以义理说《易》,但其学不纯,惟“周子穷天人之源;邵子明象数自然之理;程子一一体察之于人事,步步踏实;朱子提出占筮,平正、活动、的确。故《易经》一书,前有四圣,后有四贤”⑤,从而建构了易学发展史上四圣四贤后先相继的传递系统。
但是,与朱熹提倡经传相分,将《易传》整体附于《易经》之后,以复《周易》古本的做法不同,除了具有官方色彩的《周易折中》外,李光地在其他易学著作中,基本都是采用援传于经、经传合编的王弼本,而非朱熹的《周易本义》本。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朱子既复经传次序,今不遵之,而从王弼旧本,何也?曰:“朱子之复古经传也,虑四圣之书之混而为一也。今之仍旧本也,虑四圣之意之离而为二也。盖后世之注经也,文义训诂而已,而又未必其得,故善读经者,且涵泳乎经文,使之浃洽,然后参以注解,未失也。若四圣之书,先后如一人之所为,互发相备,必合之而后识化工之神,则未可以离异观也。”①
不可以文周之《易》为伏羲之《易》,不可以孔子之《易》为文周之《易》,朱子之说也,信乎?曰:“朱子有为言之也,为夫拘文而忘象,凿理而弃占者尔。象涵于虚,辞指于实,占其本教,理其源出,混之则不知赓续缉熙之功也,离之则不知道法揆合之神也。故其赞曰:‘恭惟三古,四圣一心。’”②
其言四圣之《易》各有不同,固是。然又须晓得伏羲之《易》,即文、周之《易》,文、周之《易》,即孔子之《易》,划然看作各样,又不是。故朱子又曰:“恭惟三古,四圣一心。”③
由此可见,与朱熹强调经传相分相比,李光地显然更为注重经传相合。李光地指出,朱熹之所以分别经传,是为了揭示《易经》的卜筮本义,纠正时人治《易》“拘文而忘象,凿理而弃占”的弊病,而他主张经传相合则是为了彰显四圣《易》的一脉相承之处,使其互相发明,避免学者将《易经》与《易传》作离异观。同时,李光地治《易》以宋易义理之学为基础,故其强调《易传》与《易经》之间的同一性,认为《易经》的卦爻辞之义须借《易传》方明,“《彖传》为卦爻之枢要”④,亦是为了突出《易传》所确立的以义理解《易》的传统与思路。
李光地治《易》虽以义理为主,但亦不废象数,其易学正是由象数、图书之学而入门的。“某少时好看难书,如乐书、历书之类。即看《易》,亦是将图画来画去,求其变化巧合处。于《太极图》,不看其上下三空圈,却拣那有黑有白、相交相系处,东扯西牵,配搭得来,便得意。”①在李光地看来,《周易》实根于象数而作,六十四卦本身就是象数的表现。“然其为书,始于卜筮之教,而根于阴阳之道,故玩辞必本于观象而不为苟言,占事必由于极数而不为苟用。非徒以象数为先也,象数而理义在焉。”②“此经所言,固皆道德性命之奥,然其渊源实起于图书,苟象数未能精通,则义理亦无根据。”③故言理必根于象数,不可离象数而言理。而他之所以推崇朱熹易学,亦是因为朱熹易学最能将义理与象数结合起来,集宋代易学之大成。故曰:“言数始于焦贡、京房,言理始于王弼,但王弼已中了老庄之说,故其学不纯。六朝、唐浮华相尚,未见有深于经学者。直至邵雍传先天之图,立象尽意,其功极大。程颐《易传》,义理醇正。朱某折中二家之学,理数俱极其归,而易学始定于一。”④
因此,李光地治《易》既注重从《易》的象数与卦爻辞中推阐、论证理学的宇宙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义理思想,又十分强调象数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以象数来解释《易经》。譬如他说:
象也者,像也。故或其卦取于物象而爻当之,则遂以其义之吉凶断,而爻德犹其次也。如《屯》所以为屯者,以其雷在下而未起也,初为《震》主当之,故曰“磐桓”,又以其云在上而未下也,五为《坎》主当之,故曰“屯膏”。《需》所以为需,以其云上于天也,九五《坎》主当之,故为饮食宴乐也。《履》之六三,说而承《乾》,本卦之主,然因彖言“咥人”,而三适当兑口之缺,有受咥之象,故其《传》曰“位不当也”,言其直口之位为不当也。《颐》之初九,本有刚德,能自守者也。以其与上共为《颐》象,而《颐》之为物,其动在下,故曰“朵颐”,而得凶也。《咸》《艮》以人身取象,故《咸》二虽中正,以直腓位而凶;《艮》四虽不中正,以直背位而无咎。《归妹》之凶,以女少而自归故也。初九适当娣象,则不嫌于少且自归矣;六五适当帝女之象,则亦不嫌于自归矣,故皆得吉也。《节》取泽与水为通塞,九二适在泽中,则塞之至也,故虽有刚德而凶也。凡若此类,以爻德比应求之,多所不通,惟明于象像之理,则得之。①
李光地以《屯》《需》《履》《颐》《咸》《艮》《归妹》《节》等卦为例,说明卦象取自物象而爻象当之,故其吉凶主要由爻象的吉凶决定,而非首先取决于爻德或比应。同时,爻象的取象亦与爻义直接相关,取象会因爻义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有一卦六爻,专取一事一物为象,而或一爻别取者,则其义因以异矣。如《需》诸爻皆取沙、泥、郊、穴之象,而五独曰‘需于酒食’,则以五为《需》之主,有《需》之德,而所《需》之安也。《蛊》诸爻皆象父母,而上独曰‘不事王侯’,则以上九居卦之上,无复承于父母之象,人未有不事父母者,故曰‘不事王侯’也。《咸》诸爻皆取身象,惟四不取者,四直心位,因之以论心之感应,而所该者广也。《大壮》诸爻取羊者三,其曰‘壮趾’,曰‘藩决’,亦羊象也。惟二不取者,有中德而居下体,不任壮者也。《蹇》诸爻皆取往来为象,惟二、五不言者,五尊位,二王臣之位,义不避难,无往来者也。《艮》诸爻亦取身象,惟上不取者,九三虽亦《艮》主而直心位,然止未极也,至上而后止极,则尽止之道者也。若此之类,皆其权于义者精,故其取于象者审也。”②
李光地还指出,《易经》的重卦之名亦多由卦象而来。他说:卦之名不尽取于象也,然而取于象者多矣。是故夫子之以《彖传》释卦也,卦象、卦德、爻义盖兼取焉,而又专立一传,特揭两象以明卦意。《易》者,象也,本天道以言人事,此夫子特揭之指也。约之则有三例。有卦名所以取者。地天为《泰》,天地为《否》,火地为《晋》,地火为《明夷》,泽水为《困》,水泽为《节》,水火为《既济》,火水为《未济》之类是也。有卦名虽别取,而象意亦甚切者。一阳统众,所以为《师》,而地中有水亦似之;一阳御下,所以为《比》,而地上有水亦似之;一阳来反,所以为《复》,而地中有雷亦其时也;一阴始生,所以为《姤》,而天下有风亦其候也,此类皆是也。有卦名别取,象意本不甚切,而理亦可通者。《随》之为随,刚来下柔也,泽中有雷,阳气下伏,亦有其象焉;《蛊》之为蛊,刚上柔下也,山下有风,阴气下行,亦有其象焉;四阳居中,则为《大过》,泽之灭木,亦气盛而《大过》之象也;四阴居外,则为《小过》,山上有雷,亦气微而《小过》之象也,此类皆是也。①
李光地将《易经》重卦与卦象有关的命名方式归纳为三种:一是以象直接命名,如《泰》《否》《晋》《明夷》《困》《节》《既济》《未济》诸卦;二是以象的含义来间接命名,如《师》《比》《复》《姤》诸卦;三是以象中所包含的道理来间接命名,如《随》《蛊》《大过》《小过》诸卦。由此可见,卦象与卦名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密切且多层面的,认识、理解卦象对于准确把握卦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容轻忽。
除了卦象与爻象之外,李光地对于《易经》中的数亦很重视。他说:
天地之间,阴阳而已。《河图》之奇耦者,所以纪阴阳之数,仿阴阳之象,而尽阴阳之理也。一奇为阳数,二耦为阴数。其余凡奇者,皆从一而为阳也;凡耦者,皆从二而为阴也。其位则节于四,备于五,而加于十。四者,天地之气分司于四方,迭王于四时之用数也。五者,兼其中之体数也。十者,倍五而成,在四方四时,则阴阳互藏互根之数;在中央,则阴阳混一和会之数也。①
圣人之则《图》作《易》也,非规规于点画之似,方位之配也。其理之一者,有以默启圣人之心而已。《图》所列之数如此,其所涵之象又如此。今以《易》卦观之,天一地二,数之源也,则圣人所取以定两仪者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象之成也,则圣人所取以定四象、八卦者也。何则?一、二之数起,则凡三、五、七、九皆一之变矣,四、六、八、十皆二之变矣,故奇耦之画由此而定也。相得有合之象列,则阴阳之宾主辨,而交易之妙具矣;阴阳之消息序,而变易之机行矣,故四象、八卦之设由此而定也。②
李光地继承了宋儒的图书之学,认为《河图》中包含了阴阳之数、阴阳之象与阴阳之理,圣人依据《河图》画卦作《易》,《易经》中的象数即来源于《河图》中的象数。《河图》中的天一地二之数是数之本源,《易》之两仪、四象、八卦皆由此而定,而《易》之交易、变易亦由其变化、组合、搭配而生。
在天一地二之数外,李光地还很重视《易经》中的天三地二之数。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
天一地二者,数之本也,而曰“参天两地而倚数”,何也?曰:“此《河图》《洛书》所以相为表里也。盖以理言之,天之数常兼乎地之数,故以天一并地二而为三也。以算言之,一一相乘,其数不行,二二而后有四,三三而后有九,故天数起于三,地数起于二也。以象言之,天圆地方,凡圆者,皆以三而成,故设三点于此,无论疏密斜正,求其交会之心而规运之,皆可作圆也;方者,皆以二而成,故设二点于此,亦无论疏密斜正,直其折连之角而矩度之,皆可作方也。
三者殊途同归,皆会于中极之五数。何则?天三地二,合之则五,此所谓阴阳之会,天地之心也。一、三、九、七相乘无穷,二、四、八、六亦相乘无穷,而五者自相乘,此所谓不动之枢,运化之本也。圆之成也三,方之成也四,三四之积,适足以当五之积,此所谓兼体之实,等量之功也。是故《洛书》缘此以起天地人之义也。至于《易》中七、八、九、六之数,盖亦有三者之符焉。参两相加,以三为节,故三三则九矣,三二则六矣,二二一三则七矣,二三一二则八矣。天数相乘,极于九而还于七;地数相乘,极于八而还于六。极者,其进也;还者,其退也。阳主进,阴主退,故阳以九为父,阴以六为母也。凡物圆者,皆以六而包一,实其中则七也,虚其中则六也。凡物方者,皆以八而包一,实其中则九也,虚其中则八也。阳实阴虚,故九、七为阳,六、八为阴。然阴阳之盛者,独七、八耳。九阳之老,而积方之所成,则阳已将变而为阴;六阴之老,而积圆之所得,则阴又将变而为阳矣。是故始于一、二、三、四,而成于六、七、八、九,万理万象万数备矣,莫不自参天两地而来,故曰‘参天两地而倚数’。”①
李光地指出,天三地二之数中包含天一地二,体现了《河图》《洛书》互相统一、互为表里。以理言之,天之数常兼地之数,所以天一加地二而为三。以算言之,一一相乘,其数不行,二二得四,三三得九,所以天数起于三,地数起于二。以象言之,天圆地方,凡圆皆以三而成,凡方皆以二而成,所以同样是天三地二。天三地二之数合而为五,乃阴阳之会,天地之心,亦是《洛书》天地人之义的根据与由来。天三地二相加、相乘又有七、八、九、六之数,于理、于算、于象三方面推衍变化,便可产生万理、万数、万象。此外,李光地对于《先天图》与《后天图》中的象数亦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论述,支持、维护并完善了朱熹的图书学理论。
由于李光地治《易》兼顾义理与象数,强调由卜筮以明义理,故其易学的一大特色便是对于《易经》卜筮之辞的重视与研究。他说:
读《易》先要知道“元亨利贞”四字。文王本意,只说大通而利于正,孔子却作四件说,朱子谓并行不悖,亦未言其故。孔子读书细,亨而谓之大,毕竟亨前有个大;利于正,毕竟正前有个利。元,大也,始也,凡物之始者便大。如唐虞是何等事业,洙泗是何等学问,然须知是尧舜之心胸,孔子之志愿,其初便大不可言。范文正作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程明道方成童,便以圣贤自期。这却在事功、学问之先。赤子之心大人不失者,赤子之心,最初之心,无所为而为,不自私也。不自私便大,大则统率群物。长子曰元子,以能统率众子也;天子曰元后,以能统率诸侯也;长妻曰元妃,以能统率群御也。大而亨,不必既亨始见其大,元自在亨之前。如孔孟终身不得行道,其大自在。我实有此大,不必问其亨不亨也。利而贞,不必既贞始见其利,利自在贞之前。亨便当收回来,宜收而收,便有利益。利本训宜,宜便利。如人君手致太平,便宜兢兢业业,持盈保泰,这是利。至于社稷巩固,则贞也。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成”字意,“利”字中已有。贞乃是坚实凝固之谓。①
李光地指出,正确理解“元、亨、利、贞”及其相互关系是读懂一部《周易》的前提和基础。四者之中,“元”即大,是“亨”的基础,“亨”即蕴含于“元”中,不必到“亨”始见其大;“利”即宜,是“贞”的前提,“贞”即蕴含于“利”中,不必到“贞”始见其利。而“元”又是四者的统帅与头脑,“亨、利、贞”皆从属于“元”。因为“元”奠定了万事万物初始的规模,规模大则学问、事业方大。其在人身上又表现为不自私的赤子之心,不自私便大,大则能统率群物。因此,事物始于大便能亨通,亨通便当回收、持守,依道理而行,最终便可致万物之成。
李光地又云:
孔子将“元亨利贞”作四件说,其理最精。且以为六十四卦占辞之权舆。占辞有仅曰“亨”者,有曰“小亨”者,是亨不必皆大也。不必皆大,而独系以“元亨”,则是未有亨,先有大也。如农之倍收,贾之获利,亦可言亨,而不可以言大,以其先所谋者原小故也。若士希贤,贤希圣,其勋业功用,直可以充塞天壤。岂不以先有斯大,故亨得来亦大耶?以此例之,则“亨”不如“元亨”,“小亨”又不如“亨”矣。占辞有曰“贞吝”“贞厉”者,有曰“不可贞”者,有曰“贞凶”者,是贞不必皆利也。不必皆利,而独系以利贞,则是未有贞,先有利也。如事之不可常者,以为正而固守之,则必致凶厉矣,何利之有?以此例之,则凡“贞吝”“贞厉”者,必其微有不宜也;其曰“贞凶”者,必其大有不宜也。故以“元亨利贞”作占辞看,似“元”字、“利”字是虚字,“亨”字、“贞”字是实字。被孔子细心读破,“元”字、“利”字却是实际字,“亨”字、“贞”字反是现成字。①
在此,他将“元、亨、利、贞”视作六十四卦占辞之权舆,以这四者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判断、衡量占辞轻重的重要标准。譬如,“亨”“小亨”“元亨”不同,“小亨”不如“亨”,“亨”又不如“元亨”,其结果取决于初始之规模不同。“贞吝”“贞厉”“贞凶”亦不同,“贞吝”“贞厉”者微有不宜,“贞凶”者则大有不宜,其结果取决于是否依理而为。由此亦可看出,“元、亨、利、贞”作为占辞,“元”与“利”是实际字,“亨”与“贞”是现成字,“元”“利”对于占筮结果的解读往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故比“亨”“贞”更为重要。
《易经》的占辞除了“元、亨、利、贞”之外,还有“吉、凶、悔、吝、无咎”等。关于后者的解释,李光地说道:
彖爻之辞,为筮而设,故吉、凶、悔、吝、无咎者,断占之凡例也。吉凶者,失得之象,故辞之吉凶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忧虞之象,故辞之悔吝言乎其小疵也。无咎则行乎四者之间,盖内省不疚,以消悔吝之萌,反己无愆,而顺吉凶之至,乃人心之得其正,而人事之得其平者。故辞之无咎,善乎其补过也。①
李光地以得失言“吉凶”,以小疵言“悔吝”,以善补过言“无咎”。对于这几种状态,李光地反对一味地追求趋吉避凶,而是以无咎为尚。他指出:“人无日不在吉、凶、悔、吝之中,亦无日不欲避凶而趋吉者。然避凶之心胜,必至于害而苟免;趋吉之心胜,必至于利而幸邀。惟君子之心则不然,曰:‘吾求无咎而已。’求无咎者,修其可吉之道而无心于获吉,至于既吉,而其惴惴于无咎之心常在也;去其取凶之道而亦无意于避凶,不幸而凶,而其怛怛于无咎之心常安也。”②因为吉凶是以个人的得失为依据,若以趋吉避凶作为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利己之心便会战胜理义之心,必将导致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故君子只需循道而行,求无咎而使心常在、常安,便是最佳的状态。“悔而无咎,则可以至于吉矣。吉而无咎,则不至于可吝矣。吝而无咎,则必不至于凶矣。凶而无咎,则亦无所可悔矣。故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③而欲达到“无咎”的状态,就必须善于补过,必须能知“悔”。“悔吝则小疵方形,必有其几微之介焉。圣人往往于此而预为之忧,曰如是则有悔,如是则有吝,所以使人谨于几先,不待乎著明而后觉也。无咎虽行乎四者之间,而其机皆在于悔。盖悔而后能补过,能补过而后无咎。其所以一转而为吉者,此也。以是处吉,则必惕然有以保其吉,而不至于吝;以是处吝,则必翻然有以消其吝,而不至于凶矣。故凡《易》之震动人以无咎者,必于悔而发其机焉。”①由此可见,“悔”在占辞中亦极为重要。圣人往往通过“悔”来提醒、告诫人们,在错误或灾祸刚刚萌发、显露的时候,就必须预先有所警觉和防范,并尽早改过或弥补,使其不至于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悔”而后能补过,能补过而后“无咎”,“无咎”方可一转而为“吉”。因此,不论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状态,心中都需要时常保持“悔”的心态。
关于“元、亨、利、贞”与“吉、凶、悔、吝”等占辞在卦爻辞中出现和使用的一些特点与规律,李光地亦有所考究。譬如他注意到,爻辞中无“元亨”,最多只用到“元吉”“大吉”,而卦辞中无“吝”,“悔”亦仅见于《革》卦而已。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元、亨、利、贞者,天道之常,而贯乎人事者也。吉、凶、悔、吝者,人事之致,而通乎天道者也。卦本乎天道,而元亨者,天道之大者也,故爻不得而用之也。爻主乎人事,而悔吝者,人事之细者也,故卦不得而及之也。且元亨之为大也,不独爻无用焉,而见于卦者亦少。②
在他看来,“元、亨、利、贞”属于天道,“吉、凶、悔、吝”则属于人事。卦本乎天道,故“元亨”只可用于卦辞,不可用于爻辞;爻主乎人事,故“悔吝”只可用于爻辞,基本不用于卦辞。“元亨”“利贞”之义若要用于爻辞,则须变“元亨”为“元吉”“大吉”,变“利贞”为“贞吉”。这是因为“卦之义全,爻则偏指一事而言,故变其文以别之也”③。同时,“元亨”所言甚大,不仅不用于爻辞,连卦辞中亦很罕见,除《乾》《坤》二卦之外,仅见于《屯》《革》《随》《临》《无妄》《蛊》《大有》《升》《鼎》诸卦中。这些卦辞或言天人之大者,或以养贤、进贤取义,皆是《易经》最为重视的内容。
李光地还指出,“元吉”与“大吉”意虽相近,但在爻辞的使用中仍略有区别。除了《坤》五、《离》二、《履》上、《复》初四爻以德之纯言“元吉”外,“凡言‘元吉’者,多指吉之在天下者也;凡言‘大吉’者,多指吉之在一人者也”①,故“元”重于“大”。类似地,“利”与“用”、“不利”与“勿用”在彖爻辞中亦属于意相近而辞不同。一方面,“言‘利’‘不利’者,以占者当卦爻谓如此之德、如此之时位,则其利、不利如此也;言‘用’‘不用’者,谓卦爻之德之时如此,占者可用以如此、不可用以如此也”②。简言之,即占筮者与卦爻辞之间的主客关系不同。另一方面,“凡言‘利’者,皆其事后之利。……凡言‘用’者,则即今而可用。……凡言‘不利’者,事无可为之称。……凡言‘勿用’者,暂且勿用之意”③。因此,“利”与“不利”、“用”与“勿用”之间又有缓急之不同。“利”缓于“不利”,“用”又急于“勿用”。“通事后而论之,则‘利’者犹在后也,故缓;‘不利’者终无可为也,故急。即当事而论之,则‘用’者即今可用也,故急;‘勿用’者惟此时勿用而已,故缓。若夫虚言‘无不利’‘无攸利’者,亦包当事、事后之辞也;虚言‘勿用’者,亦是且就其时断之之辞也。”④
此外,李光地在解读卦爻辞时还很强调整体解读的原则,反对将卦爻割裂开来,各自成义,并因此对程颐等人的治《易》方法提出批评。他说:
卦包乎爻而举其纲,爻析乎卦而穷其分。爻不立,无以发卦之缊,而冒天下之道。是故卦爻者,相为表里,相为经纬者也。此文周之书所为二而一者也。①
六爻皆从卦系辞,故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把卦爻看得各自成义,便不融洽。又系得初爻,余爻便可一笔写下,故曰:“初辞拟之,卒成之终。”把各爻看得各自成义,亦不是。②
伊川治《易》,逐爻去看他道理事情。后来尹和靖得伊川之传,教人看《易》,一日只看一爻。朱子便说《易》是联片的,如何一日只看一爻?问:“初学可以逐爻看起否?”曰:“使不得。每一爻如投词人,是个原告、被告,必须会同邻佑、乡保、证佐,四面逼紧审问,方得实情。不然虽审得是,亦不敢自信。不通六爻全看,虽一月看一爻,亦无用。”③由此可见,卦辞与爻辞之间,以及同卦六爻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必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方确实。如《大壮》九四云:“贞吉,悔亡,藩绝不羸,壮于大舆之輹。”有人不免产生疑问,谓:“《泰》之三则有戒词,《壮》至四阳极矣,何以反无戒词而决其往也?”对此,李光地答道:“凡卦诸爻,皆相备为义。《泰》前有拔茅冯河之象矣,故于三戒之。此卦初三既以壮趾触藩为凶厉,二又贞固自守而已,苟非有壮于进者,乘时之义安在乎?卦之为壮,进其义也,要在于贞而已。”④这说明了卦中诸爻的意义是相互影响、先后呼应的,要正确理解卦中某爻的爻辞,就需要联系卦辞及上下爻的爻辞进行整体解读。不同卦中同一位置的爻义往往不同,故不可对爻辞进行抽象、孤立的解读。
《周易》与其他儒家经典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其拥有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学者一般认为这一套相互配合的符号与文字系统中存在某种规律,这便是所谓的“义例”。而发现、认识并掌握这种“义例”就成为准确理解《周易》的重要前提和有效途径。李光地对《周易》中的义例亦极为关注,不仅在《周易折中》中撰有《义例》一篇,在《周易通论》中也对各种义例多有讨论,还特别强调:“至尊最得意《折中》中《义例》一篇,《启蒙附论》道理非不是,却不似《义例》是经中正大切要处。如治天下,《义例》是田赋、学校、官法、兵制、刑狱之类,日日要用,切于实事,《附论》则如王府中所藏‘关石和钧’,本来是道理根源,但终日拿这个来治天下,却不能”①,对于义例在治《易》中的作用可谓推崇备至。从李光地的易学实践来看,他在总结前人义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加以批判性的吸收和创造,主要从卦爻的时、位、德、比应及卦主等方面对《周易》义例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发展、完善了《周易》的义例理论,从而构成了李光地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时”,李光地说道:
王仲淹曰:“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其说善矣。然趋时之义,不可不辨也。近代说《易》,所谓时者,皆似有一时于此,而众人趋之尔。故其象君臣者皆若同朝,象上下者皆若同事。其为时也,既局于一而不通;其趋时也,又以互相牵合而说义多不贯。此则讲解之大患也。夫时也者,六位莫不有焉,各立其位,以指其时,非必如并生一世,并营一事者也。……盖必其所谓时者,广设而周于事,所谓动而趋时者,随所处而尽其理,然后有以得圣人贞一群动之心,而于辞也几矣。是故一世之治乱穷通时也,一身之行止动静亦时也,因其人因其事各有时焉,而各趋之云尔。不然,则何以曰冒天下之道而百姓与能乎?②
王弼曾说:“卦以存时,爻以示变”①,“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②,认为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卦时,即其特定的背景,而事物在这一特定背景下的运动、变化、发展则通过六爻展示、表现出来。这种卦时说曾为一般学者所普遍接受。至隋朝时,王仲淹提出“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的观点,修正了王弼的卦时说。而李光地则在王仲淹的基础上,进一步批驳了王弼的理论,反对每一卦仅有一种特定的背景,而六爻都趋向于同一背景。因为这样将导致卦时“局于一而不通”,而趋时“又以互相牵合而说义多不贯”。在李光地看来,“时”并非特定不动的,不仅卦有“时”,六爻亦各有其“时”,且六爻之“时”因其“位”而各有所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既不必与卦时相同,也不必与其他爻时相同。因此,动而趋时者就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具体情境去把握和理解“时”,这样才能领会圣人贞一群动之心。而关于“时”的内容与种类,李光地提出一世之治乱穷通是时,一身之行止动静是时,因其人因其事各有时;又说:“消息盈虚之谓时,《泰》《否》《剥》《复》之类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讼》《师》《噬嗑》《颐》之类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谦》《咸》《恒》之类是也。又有以象言者,《井》《鼎》之类是也。四者皆谓之时。”③这就极大地丰富、扩展了“时”的内涵,避免了人们对“时”的单一化与抽象化理解。
关于“位”,李光地说道:
贵贱上下之谓“位”。王弼谓中四爻有位,而初上两爻无位,非谓无阴阳之位也,乃谓爵位之位耳。五,君位也。四,近臣之位也。三虽非近,而位亦尊者也。二虽不如三、四之尊,而与五为正应者也。此四爻皆当时用事,故谓之有位。初上则但以时之始终论者为多,若以位论之,则初为始进而未当事之人,上为既退而在事外之人也,故谓之无位。然此但言其正例耳。若论变例,则如《屯》《泰》《复》《临》之初,《大有》《观》《大畜》《颐》之上,皆得时而用事,盖以其为卦主故也。五亦有时不以君位言者,则又以其卦义所取者臣道,不及于君故也。故朱子云:常可类求,变非例测。①
一般认为,《周易》每卦六爻各有其阴阳本位,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为“当位”,否则称“失位”。在王弼看来,一卦的初爻与上爻皆无确定的阴阳本位,故不当论位。而李光地则认为,初、上两爻无位,说的是无爵位,而非无阴阳之位。因为初爻象征始进而未当事之人,上爻象征既退而在事外之人,所以说这两爻无爵位。但是,由于《屯》《泰》《复》《临》四卦的初爻与《大有》《观》《大畜》《颐》四卦的上爻皆为卦主,所以也得时用事,拥有爵位。而某卦的卦义若取臣道,则其五爻亦不为君位。这些都是论“位”时的变例。
关于六爻之“位”的特点,李光地进一步说道:
考《象传》,凡言位当、不当者,独三、四、五三爻尔,初、二皆无之。盖所谓位者,虽以爻位言,然实借以明分位之义。初居卦下,上处卦外,无位者也。二虽有位,而未高者也。惟五居尊,而三、四皆当高位,故言位当、不当者,独此三爻详焉。……《大传》曰“列贵贱者存乎位”,则知爻位有六,而贵者惟此三爻矣。以《象传》之言位当、不当者施于此三爻而不及其它,故知借爻位以明分位之义也。②
在此,李光地再次强调了以爵位论“位”的观点,除了重复初、上两爻无位之外,还指出了二爻亦不言位的现象。而这不免令人疑惑,“二虽未高,然亦有位焉,何以不言也?”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据《大传》“其柔危,其刚胜邪”,“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则三、五宜刚者也,四宜柔者也,二反宜刚者也。三、四、五以当为善,不当为不善,二则反以不当为善,故当、不当之义不得而施于此爻也。①
这就是说,根据《系辞传》所说的“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与“柔之为道,不利远者”的原则,三爻、五爻为刚居阳位,四爻为柔居阴位时,既当位,又是善的;而二爻为柔居阴位时,虽当位,但因其远离五爻,不利于柔,故为不善,所以二爻便不言当位与否了。
接着,李光地还利用这一思路说明了为何“三爻只有言不当,而未有言当;四爻只有言当,而未有言正当;惟五爻多言正当,只有《大壮》五言不当,且反以不当为善”的问题。他说:“盖三,危位也,以柔居之固不当,以刚居之,亦未必当也,此其所以多凶也。四,近位也,以刚居之固不当,以柔居之,亦仅止于当而已,此其所以多惧也。五,尊位也,以刚居之为正当,以柔居之,有柔之善焉,虽不当,犹当也,此其所以多功也。”②
关于“德”,李光地说道:
刚柔、中正、不中正之谓“德”。刚柔各有善不善,时当用刚,则以刚为善也;时当用柔,则以柔为善也。唯中与正,则无有不善者。然正尤不如中之善,故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以此故尔。③
何以谓之德也?有根于卦者焉,健顺、动止、明说之类是也;有生于爻者焉,刚柔、中正之类是也。德无常善,适时为善。故健顺、动止、明说之德,失其节则悖矣;刚柔之道,逆其施则拂矣。……惟中也,正也,则无不宜也,而中为尤善。何也?《易》之义莫重于贞,然亦有贞凶者矣,有贞吝、贞厉者矣,其事未必不是也,而逆其时而不知变,且以为正而固守焉,则凶危之道也。中则义之精而用之妙,凡所谓健顺、动止、明说、刚柔之施,于是取裁焉。先儒所谓“中则无不正”者,此也。①
李光地认为,“德”可分为卦德与爻德两大类。卦德主要指健顺、动止、明说等特性,爻德主要指刚柔、中正等特性。德无常善,适时则为善。如当用刚时,刚便为善;当用柔时,柔便为善。唯有中与正,则无有不善,而中为尤善。这是因为正虽为善,但如果善事与时相逆,却仍以为正而固守,就会导致凶险与危难,而中则是义之精与用之妙,是健顺、动止、明说、刚柔的取裁标准,所以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譬如,除《乾》《坤》二卦外,“其余卦之诸爻,居得正者多矣,而亦鲜以正许之者。惟二与五得其正者,固曰以中正也,或不得其正者,亦曰中以行正也。是则中道之大,而《易》教之至也”②。
既然中道为《易》教之至,比正更为重要,为何“《易》之卦爻于贞盖谆谆焉,其于中行仅数四见而已”?对此,李光地解释道:“正理可识,而中体难明,非深于道者不能知,是故难以察察言也。存其义而没其名,则圣教之精也。”③也就是说,正比较容易被人认识,而中则难以言传,只有深明义理者方能意会,故圣人存其义而没其名,恰好体现出圣人之教的精妙。最后,李光地还强调中与正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正”代表道义的准则,具有外在的客观性,中则是正的实质,中必须通过正表现出来,故须求正以明中道,否则便易流为依违两可,混同无辨。“正非中,则正之实未至;中非正,则中之名亦易差。圣人所以尊中之道而略其名,精求乎正之实,而必广其教者,此也。”①
关于“比”“应”,李光地说道:
“应”者,上下体相对应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连之爻也。《易》中比应之义,唯四与五比,二与五应为最重。盖以五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远而应之也。……凡比与应,必一阴一阳,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刚应刚,以柔应柔,则谓之“无应”。以刚比刚,以柔比柔,则亦无相求相得之情矣。②
自王辅嗣说《易》,多取应爻为义,历代因之。考之夫子《彖象传》,言应者盖有之,然亦观爻之一义尔。若逐爻必以应言,恐非周公之意,亦非孔子所以释经之旨也。以经传之例观之,上下两体,阴阳相求,固其正矣。然《彖传》有以众爻应一爻者,亦有以一爻应众爻者,乃不拘于两体二爻之对。《比》《小畜》《同人》《大有》《豫》之类皆是也。有时义所宜,以阴应阴而吉,以阳应阳而吉者,又不拘于阴阳之偶。《晋》《小过》之王母、祖妣,《睽》《丰》之元夫、夷主之类,皆是也。有以承乘之爻为重者,则虽有应爻而不取。如《观》之观光,《蹇》之来硕,《姤》之包鱼,《鼎》之金铉,而《随》则有失丈夫之失,《观》则有窥观之丑,《姤》则有无鱼之凶,此类皆是也。其余但就其爻之时位才德起义,而不系于应者不可胜数,而欲一一以应义傅会之,则凿矣。③
承乘者谓之比。凡比爻,惟上体所取最多。盖四承五,则如人臣之得君;五承上,则如人主之尊贤。主于五,故其近之者,皆多所取也。然四之承五,惟六四、九五当之;五之承上,惟六五、上九当之。非然者,则亦无得君尊贤之义。……下体三爻所取比义至少,初与二,二与三,间有相从者,随其时义,或吉或否。至三与四,则隔体无相比之情矣。①
“应”指上卦三爻与下卦三爻之间的两两对应关系,包括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上爻相应。一般认为,“应”必须是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其情乃相求而相得。故阴阳、刚柔相应则吉,若以阳应阳,以阴应阴,或以刚应刚,以柔应柔,皆为凶。自王弼以应爻说《易》以来,这一观点为历代学者所普遍接受。而李光地则指出,孔子说《易》虽然确曾言“应”,但只是将其作为观爻之一义,若每爻都硬要以“应”来解释,则非周公、孔子之意。“应”除了“上下两体,阴阳相求”的正例之外,还存在不少变例。譬如,《比》《小畜》《同人》《大有》《豫》等卦就出现以众爻应一爻或以一爻应众爻的情况,而不拘于两体二爻对应;《晋》《小过》《睽》《丰》等卦则有以阴应阴而吉,以阳应阳而吉的现象,而不拘于阴阳相应得吉;《观》《蹇》《姤》《鼎》《随》等卦则以承乘之爻为重,而不取应爻。此外,以爻之时位才德起义的情况尚不可胜数,若欲一一以“应”的关系来解释,必然陷于穿凿附会。总之,使用“应”来解《易》须有限制,不可滥用。
至于“比”,则指相邻两爻比连并列,包含承与乘两种情况。比爻多用于上卦,而下卦较少,介于上下卦之间的三爻与四爻则基本没有相比的情况。
李光地认为,《周易》中的比应关系唯四与五比,二与五应为最吉。因为五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远而应之。加之二与五皆有中德,又各居当时之位,所以二与五应最吉。关于相应关系的吉凶,李光地还提出了“《易》之道,阴暗求于阳明,不以阳求阴也;上位求于下位,不以下求上也”②的原则。即符合以阴求阳、以上求下原则的相应二爻便为吉,否则皆为凶。此外,若三爻与上爻相应,则皆非吉,惟《剥》《损》《益》三卦例外。
关于“卦主”,李光地说道:
凡所谓卦主者,有成卦之主焉,有主卦之主焉。成卦之主,则卦之所由以成者。无论位之高下,德之善恶,若卦义因之而起,则皆得为卦主也。主卦之主,必皆德之善,而得时、得位者为之。故取于五位者为多,而它爻亦间取焉。其成卦之主,即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之善,而兼得时位者也。其成卦之主,不得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与时位,参错而不相当者也。①
圣人系彖之时,虽通观其卦象、卦德,以定名辞之义,然于爻位尤致详焉。盖有因爻位以名卦者,《师》《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谦》《豫》《剥》《复》《夬》《姤》之类是也。有名虽别取,而爻位之义发于辞者,《屯》《蒙》之“建侯”“求我”指初二,《讼》《蹇》《萃》《巽》之“大人”指九五之类是也。是二者皆谓论卦之主爻。但就文王之名辞观之,有包涵其意而未明者矣。至六爻之系,则辞有吉凶,义有轻重,而名辞之意,因以可见。……盖爻之意虽根于卦而后可明,而卦之意亦参于爻而后可知。卦爻相求,则所谓主爻者得矣。主爻者得,则其余爻之或吉或凶因是可推。何则?凡卦义善者,爻能合德则吉,反之则凶也;卦义不善者,爻能反之则吉,合德则凶也。故《师》《比》《谦》《豫》之类,主爻之吉者也,以其德与时适也。若其当与时反者,则为主者反不得吉。如《讼》之上九,则终讼者也;《履》之六三,则咥人者也;《明夷》上六,则明所以夷也;《归妹》上六,则妹所以归也。主爻吉,则余爻之吉者,必其德与主爻类者也。非然,则其比应也,而反是者则凶。主爻凶,则余爻之凶者,必其德与主爻类者也。非然,则其比应也,而反是者则吉。②所谓“卦主”,即一卦之主爻。李光地认为,卦主可分为“成卦之主”与“主卦之主”两种。其中,“成卦之主”是与卦名、卦辞由来直接相关的爻位,而“主卦之主”则是爻德为善,且得时、得位的爻位,故取于五位者为多。就前者来说,只要某爻是卦名或卦辞的来源,不论其爻位高下,爻德善恶,皆为此卦之卦主。因此,卦名、卦辞与爻意之间便可互相发明。学者既能利用卦名与卦辞来确定主爻,亦可通过主爻之意来理解卦名与卦辞的含义。同时,通过主爻的吉凶还可推断出其余爻的吉凶。主爻之德与时相适便是吉,主爻之德与时相反便是凶。确定主爻的吉凶之后,若主爻为吉,则余爻之德与主爻相类,或与主爻相比应的便是吉,反之则凶;若主爻为凶,则余爻之德与主爻相类,或与主爻相比应的便是凶,反之则吉。
李光地进一步说道:
若其卦成卦之主,即主卦之主,则是一主也。若其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则两爻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爻,则两爻又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象,则两象之两爻,又皆为卦主矣。①
主爻不拘于一,如《蒙》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以“童蒙”应之,则亦主爻也;《师》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使“长子帅师”,则亦主爻也;《履》之六三固主爻矣,九四有虎尾之象,则亦主爻也;《泰》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为下交之主,则亦主爻也。又如《临》之初、二,《观》之五、上,《坎》《离》之二、五,《萃》《升》之四、五,则皆自卦义而定,不妨两为卦主也。又如《震》有两主,而其重在初;《艮》有两主,而其重在上;《既济》二、五得中,而其重在二;《未济》二、五得中,而其重在五,此则因卦义而变者。《履》之三、四象虎尾,而其吉在四;《颐》之初、上象颐,而其凶在初;《大过》三、四象栋,而其吉在四;《小过》初、上象鸟,而其尤凶在初,此则又因物象而变者。若此之类,推说难尽,姑举其概,各随卦义、爻才而观之可也。凡卦有无主者,则以其义甚大,而爻德不足以配。如“同人于野”之义至大,六二之吝固不足以当之矣,惟上九居卦外,有野之象,而其德非中正,故仅止于郊而已;“恒久”之义至大,六五之贞固不足以当之矣,惟九二刚中,有久中之德,然位失其正,故止于悔亡而已。是二卦者,无主爻也。①
李光地指出,一卦并非只能有一个主爻,也可能存在两个或多个主爻。若一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抑或成卦兼取两爻或两象,那么一卦便有两个卦主。当一卦存在两个或多个卦主时,其中往往还有主次轻重之分,而其判断方法则随各卦的卦义与爻才而定。所谓“卦有无主者”,指的是主卦之主。由于主卦之主必须兼顾爻德与时、位,所以当卦义甚大,而爻德不足以配,或位失其正时,此卦便无主卦之主。至于成卦之主,则每卦皆有,故不存在无主的情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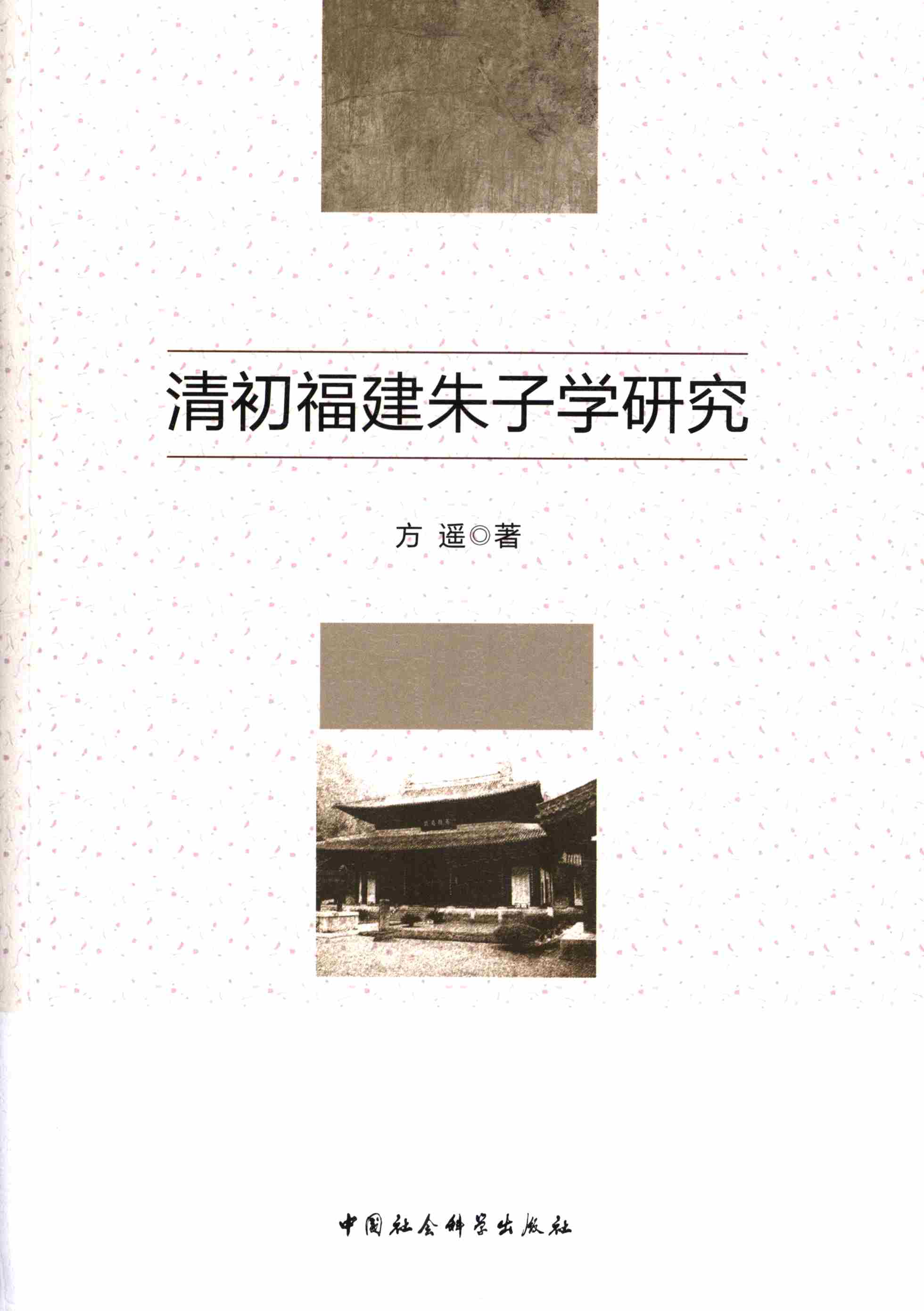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