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怀疑辨伪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81 |
| 颗粒名称: | (七)怀疑辨伪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9 |
| 页码: | 346-364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熹主张怀疑与辨伪精神,对经典进行审视与辨析。他根据流传情况、文体风格、字词用法、出现时间及思想义理等方面,提出了多种经学辨伪方法。 |
| 关键词: | 怀疑精神 辨伪 经学 |
内容
朱熹治经、治学历来提倡怀疑精神,将怀疑视作学者读书的必要方法与必经阶段,这也是宋代经学区别于汉唐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说: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⑥
看讲解,不可专徇他说,不求是非,便道前贤言语皆的当。如《遗书》中语,岂无过当失实处,亦有说不及处。⑦
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①
大率观书但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②
在朱熹看来,不但包括二程在内的前辈学者关于经典的传注疏释需要经过理性的怀疑与重新审视,甚至被视为圣贤之言的经典本身也可以加以怀疑。读书有疑方可立论,有疑方是有得,无疑则是怠惰。而怀疑与判断的基本标准则是“义理之所当否”与“左验之异同”,即思想逻辑与事实证据两大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治经提倡怀疑精神与其主张虚心切己并不必然构成矛盾,因为后者乃是前者的必要前提与基础。朱熹曾说:
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旧日看《论语》,合下便有疑。盖自有一样事,被诸先生说成数样,所以便着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间或有说不通处,自见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③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④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举所疑,与朋友讲论。假无朋友,久之,自能自见得。盖蓄积多者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此所谓“何天之衢亨”也。盖蓄极则通,须是蓄之极,则通。①
朱熹认为,怀疑须是在虚心熟读、深造自得的基础上自然有疑,不能故意立异,为怀疑而怀疑。若能真正做到虚心熟读,切己体认,自然会发现文本中的窒碍不通处,由此产生的怀疑便是合理的、有价值的怀疑。同时,也只有首先通过虚心切己的工夫积累了足够的知识与能力,才能在疑问产生后顺利将其解决,使学问更近一层,最终把握圣贤本意。
有所怀疑自然要有所辨伪。朱熹除了提倡怀疑精神之外,更在广泛借鉴、吸收前人辨疑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学实践与思考,择善而从,自立新说,做了大量的经典辨伪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绩。仅据白寿彝《朱熹辨伪书语》所辑录的资料来看,朱熹所辨疑的文献典籍就有四十余种,可谓宋代辨伪学的集大成者。其中,与儒家经典有关,且较为重要、具有较大影响者主要包括对《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孝经》等经典及其传注的辨伪。
对于《诗经》,朱熹指出《大序》与《小序》皆非孔子、子夏等圣贤所作,而是出于后人之手。“《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②“《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③“《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④
对于《尚书》,朱熹指出《孔序》《孔传》皆非西汉孔安国所作,而是出于后人伪托;《书序》(即《小序》)亦非孔子所作,乃周秦间人所作。“《尚书》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国所作。盖文字善困,不类西汉人文章,亦非后汉之文。”①“《书小序》亦非孔子作,与《诗小序》同。”②“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③同时,朱熹还对《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认为与《今文尚书》比较,“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④。且《古文尚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⑤。此外,朱熹对《今文尚书》中的某些篇章亦有所怀疑,认为其内容有不合常理处,多不可晓。
对于《礼记》,朱熹指出:“今只有《周礼》《仪礼》可全信。《礼记》有信不得处”⑥,“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⑦。又说:“《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⑧,“若《曲礼》《玉藻》诸篇,皆战国士人及汉儒所裒集”⑨,“《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恐未必得其真也”⑩,“《保傅》中说‘秦无道之暴’,此等语必非古书,乃后人采贾谊策为之,亦有《孝昭冠辞》”⑪。此外,朱熹还认为《礼运》“不是圣人书”⑫,《冠义》《昏义》《乡饮酒义》《乡射义》等篇皆系汉儒所造。
对于《左传》,朱熹认为并非春秋末年左丘明所作。“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较详。……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①
对于《孝经》,朱熹指出:“《孝经》,疑非圣人之言”②,“《孝经》亦是凑合之书,不可尽信”③,“据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④。因此,朱熹将《孝经》区分为经与传两部分,认为经是曾子门人所记,而传则是战国或汉初时人据《左传》《国语》等史传文字凑合缀辑而成,并非出于孔子或曾子之手。
朱熹之所以能在经典辨伪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对多部经典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还在于他总结、创造、使用了多种重要的经学辨伪方法,具有承上启下之功,为考据辨伪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试将朱熹所使用的辨伪方法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条:
(1)根据典籍的流传情况推断。譬如:
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⑤
《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大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①
朱熹认为,由伏生背诵口传的《今文尚书》文字艰涩难读,出于孔壁、以科斗文书写的《古文尚书》反而平易易晓,不符合典籍流传的一般情况与常理,故十分可疑。同时,出于孔壁的《古文尚书》历经数百年动荡却能完好无缺,不讹损一字,亦值得怀疑。
(2)根据典籍的文体风格推断。譬如: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如《书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②
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③
《尚书序》不似孔安国作,其文软弱,不似西汉人文,西汉文粗豪。也不似东汉人文,东汉人文有骨肋。也不似东晋人文,东晋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太段弱,读来却宛顺,是做《孔丛子》底人一手做。看《孔丛子》撰许多说话,极是陋。④
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验,古文自是庄重。至如孔安国《书序》并注中语,多非安国所作。盖西汉文章虽粗亦劲,今《书序》只是六朝软慢文体。因举《史记》所载《汤诰》并武王伐纣言辞不典,不知是甚底齐东野人之语也。⑤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①
朱熹认为,《尚书》的《孔序》与《孔传》文字软慢无气,不似西汉文章粗犷厚重的风格,且《孔传》的训释方法与西汉传注文字高简、有疑则阙的特征不符,证明《孔序》与《孔传》非西汉孔安国所作,系后人伪托。同时,朱熹含蓄地表示,《尚书》中的《汤诰》与武王伐纣等内容虽见于《史记》,但其言辞不典,亦值得怀疑。
(3)根据典籍所用字词推断。譬如:
(《舜典》)“玄德”难晓,书传中亦无言“玄”者。②
(《书大序》)“传之子孙,以贻后代。”汉时无这般文章。③
“《序》云‘聪明文思’,经作‘钦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问:“恐是作《序》者见经中有‘钦明文思’,遂改换‘钦’字作‘聪’字否?”曰:“然。”④
朱熹认为,《尚书·舜典》篇首的“玄德”之意难晓,且“玄”字未见于书传中,值得怀疑;《书大序》中“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的说法为汉代所无,亦值得怀疑。同时,朱熹认为《书小序》中所言“聪明文思”袭自经书中的“钦明文思”,有故意模仿作伪之嫌。
又如:《保傅》中说“秦无道之暴”,此等语必非古书,乃后人采贾谊策为之,亦有《孝昭冠辞》。①1
朱熹认为,《大戴礼记·保傅》中的“秦无道之暴”等语为先秦古书所无,乃后人杂取贾谊策论与《孝昭冠辞》等文字伪造。
(4)根据典籍的出现时间推断。譬如:《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②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③某尝疑《书注》非孔安国作,盖此传不应是东晋方出。④
朱熹认为,《书小序》于伏生时未见,今本《古文尚书》及《孔传》至东晋时方才出现,此前学者皆未见及,故十分可疑。
(5)根据典籍中体现的思想、义理推断。譬如:《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⑤《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煞有碍义理误人处。⑥
朱熹认为,《诗经》的《大序》与《小序》中皆有不符合儒家义理处,显然不可能是孔子、子夏等圣贤所作,而是出于后人杜撰。
又如: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①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②
朱熹认为,《左传》体现出纵横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不合儒家义理,其作者不可能是孔子所称赞的正直儒者左丘明。
又如:
据此书(指《孝经》),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如下面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岂不害理!倘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尽孝道也,岂不启人僭乱之心!③
朱熹认为,《孝经》所说的“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剥夺了一般人尽孝道的可能,不但不符合儒家义理,而且会引发人们的僭越作乱之心,故这部分内容绝不可能是孔子、曾子所作。
(6)根据典籍内容的不合理处推断。譬如:
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风,禾尽起”,也是差异。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启金滕之书?然当周公纳策于匮中,岂但二公知之?《盘庚》更没道理。从古相传来,如经传所引用,皆此书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说得都无头。且如今要告谕民间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只说道要迁,更不说道自家如何要迁,如何不可以不迁。万民因甚不要迁?要得人迁,也须说出利害,今更不说。《吕刑》一篇,如何穆王说得散漫,直从苗民蚩尤为始作乱说起?①
《康诰》以下三篇,更难理会。如《酒诰》却是戒饮酒,乃曰“肇牵车牛远服贾”,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亦多可疑处。②
朱熹认为,《尚书》的《金縢》《盘庚》《吕刑》《酒诰》《梓材》等篇中都存在不合人情事理、难以常理测度的内容,若说是出于圣贤之手,不免令人怀疑。
又如:
《蟋蟀》一篇,本其风俗勤俭,其民终岁勤劳,不得少休,及岁之暮,方且相与燕乐;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无已大康。”盖谓今虽不可以不为乐,然不已过于乐乎!其忧深思远固如此。……而序《蟋蟀》者则曰:“刺晋僖公俭不中礼。”盖风俗之变,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礼,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必无是理也。③
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④
朱熹认为,风俗的变化,必然是由社会上层传至下层民众。《诗小序》将《唐风·蟋蟀》一诗解释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不但与诗人原意不合,而且会导致君主过于勤俭而失礼,而民众犹知用礼的情况出现,有悖常理,故非圣贤所作。同时,朱熹指出,古人作诗的动机与今人一样,多是因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作,不可能每首诗都是为了赞美或讥刺他人而作。而《诗小序》作者将每篇诗歌都套用美刺说加以解说,显然有悖情理,绝非圣贤所为。
(7)根据经、序内容不合推断。譬如:
《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难”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①
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于让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难”,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②
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③
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汉书·艺文志》以为孔子纂《书》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于见存之篇虽颇依文立义,而亦无所发明。其间如《康诰》《酒诰》《梓材》之属,则与经文又有相戾者;其于已亡之篇,则伊阿简略,尤无所补,其非孔子所作明甚。④
诚有可疑。且如《康诰》,第述文王,不曾说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之词。然则《康诰》是武王诰康叔明矣。但缘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处,遂使序者以为成王时事。此岂可信。⑤
《书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诰》等篇,决是武王时书,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错处数简,遂误以为成王时书。然其词以康叔为弟而自称寡兄,追诵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文时语的甚。至于《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词,而亦误以为周公诰康叔而不之正也。①
朱熹认为,《书小序》对于《尧典》《舜典》《康诰》《酒诰》《梓材》等篇的解说皆与经文本义不合,对其所述时代、事件亦多误解,往往望文生义,证明作《序》者对《尚书》的内容与圣人作经之意并不了解,绝非孔子所作。
又如:
他做《小序》,不会宽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寻得着底,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底,要就《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诗》。②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见葛而思归宁,序得却如此!③
《大序》亦有末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④
《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⑤
《小序》……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昵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会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①
《诗序》实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诗》中数处皆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说。……《昊天有成命》中说“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会,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说了,又几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说,后来遂生一场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说“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说着地,如何说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说及后土。如汉诸郊诗,祭某神便说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说天,不说地。①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说,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庄姜》之诗,却以为刺卫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考者,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如《汉广》之《序》言“德广所及”,此语最乱道。诗人言“汉之广矣”,其言已分晓。②
看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事是当。如《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不知而今做义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
某谓此诗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读了。①
朱熹认为,《诗小序》刻意以美刺说解诗,多与《诗经》本义不合。譬如,《小序》对于《蟋蟀》《山有枢》《行苇》《卷耳》《桃夭》《有女同车》《抑》《昊天有成命》等篇的解说多是就诗中采摭言语,望文生义,又为了迁就美刺说,不惜穿凿附会,杜撰相关的人物、事实,不但不能发明诗之大旨,而且妨碍、干扰读者对于《诗经》的理解,显然不可能是圣贤所作。同时,朱熹指出《诗经》的《郑风》《卫风》《邶风》《鄘风》中多有淫诗,所以《诗大序》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并不能概括整部《诗经》的宗旨,证明其亦非圣贤所作。
(8)根据典籍所述内容后于成书年代推断。譬如: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②
左氏是三晋之后,不知是甚么人。看他说魏毕万之后必大,如说陈氏代齐之类,皆是后来设为豫定之言。③
子升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篡齐以后之书。”④
朱熹认为,《左传》中预言了三家分晋、陈氏代齐等事,证明其作者不可能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
(9)根据典籍所述内容与历史事实不符推断。譬如:《诗》,才说得密,便说他不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说自分晓。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须说。①
朱熹认为,据《周礼》《礼记》《左传》等书记载,周代史官并不掌诗,而《诗大序》却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证明其并非圣贤所作。
(10)根据典籍所载制度与时代不符推断。譬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②
朱熹认为,秦代开始才有腊祭的制度,而《左传》却说“虞不腊矣”,显然是在秦代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说法与意识,故作者不可能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
(11)根据典籍内容的取材来源推断。譬如:
棐,本木名,而借为“匪”字。颜师古注《汉书》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匪忱”,犹曰天难谋尔。孔传训作“辅”字,殊无义理。尝疑今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未必真安国所作,只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小尔雅》也。③
朱熹认为,《孔传》对于《尚书》的训解多出自《孔丛子》中的《小尔雅》,其言亦与《孔丛子》多相表里,因而怀疑《尚书孔传》与《孔丛子》是同一人伪作。
又如:
(《孝经》)“其中煞有《左传》及《国语》中言语。”或问:“莫是左氏引《孝经》中言语否?”曰:“不然。其言在《左氏传》《国语》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经》中却不成文理。见程沙随说,向时汪端明亦尝疑此书是后人伪为者。”①
古文《孝经》亦有可疑处。自《天子章》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与曾子说底通为一段。只逐章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一段文义都活。自此后,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多是《左传》中语。如“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季文子之辞。却云“虽得之,君子所不贵”,不知论孝却得个甚底,全无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②
朱熹认为,《孝经》中有不少言语与《左传》《国语》相似,且这些言语在《左传》《国语》中文理通贯,而在《孝经》中则不成文理,由此可以判断是《孝经》抄袭《左传》《国语》,证明《孝经》乃后人杂凑而成。
(12)根据与作者的其他著作或言论比较推断。譬如:
《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着,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③
朱熹认为,《孝经》说孝多未说到切要处,与《论语》说孝亲切有味不同,显然并非孔子之言,乃出于后人伪作。
诚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朱熹对于儒家经典的考证与辨伪仍显得较为简单零散,多散见于各种语录、书信、传注中,较少做深入、专门的讨论,有时证据不够充足,仅凭一两条理由就做出判断,不免过于轻率,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辨伪理论体系。同时,朱熹所使用的辨伪方法也存在一些不够科学、严谨的地方。比如,以典籍的文体风格、表达方式或思想义理等作为判断其作者、时代与真伪的标准,有时难免偏于个人主观的意见,而缺乏足够的客观性。又如,朱熹往往将圣贤之言预设为绝对正确、没有矛盾、绝对合乎义理的,认为圣贤对于经典的理解与解释必然完全符合经典本义,并且将此作为辨别经典及其传注真伪的基本前提,显然也有失武断,未必符合历史的真相。此外,朱熹在利用古代典籍互相比较、参证时,有时容易忽略不同典籍的成书年代与真伪情况,难保不会出现以晚证早、以伪驳真的情况。但是,正如白寿彝所指出的,朱熹辨伪学中的种种不足之处“是和后来考证学发达起来时的情形比较而言的。在当时能提出一种辨伪书的具体方案,并能应用这样多的方法的人,恐怕还是要推朱熹为第一人了。他辨伪书的话虽大半过于简单,但在简单的话里,颇有一些精彩的见解,给后来辨伪书的人不少的刺激”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对于儒家经典的怀疑与辨伪始终是以尊经卫道为基本前提和根本目的,并且与其理学思想的阐发、建构紧密关联。在朱熹看来,圣贤所作的经典本是完美无缺、尽善尽美、清楚明白、相互贯通的,只是由于后人的附会、增益、改窜、伪造,以及流传过程中遭到的毁坏,才使得经典文本出现残缺、错讹等各种问题以及阅读、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只有彻底清除这些后人附加上去的东西,恢复经典的原貌,才能更准确地接近、把握圣贤之道。同时,朱熹认为,正是由于后儒对于经典本义的误解与扭曲,才导致了圣贤之道的失真与失传,进而引发儒学地位的不断衰落。因此,必须扫除这些伪托、附会在圣贤身上的、有悖于义理的经典与传注,以符合圣贤相传之心的理学思想重新对儒家经典加以诠释,才能恢复、巩固儒学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一方面积极从事儒家经典的辨伪考证工作,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并将此作为经典辨伪的底线,最终实现了儒学的思想重建与全面复兴。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⑥
看讲解,不可专徇他说,不求是非,便道前贤言语皆的当。如《遗书》中语,岂无过当失实处,亦有说不及处。⑦
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①
大率观书但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②
在朱熹看来,不但包括二程在内的前辈学者关于经典的传注疏释需要经过理性的怀疑与重新审视,甚至被视为圣贤之言的经典本身也可以加以怀疑。读书有疑方可立论,有疑方是有得,无疑则是怠惰。而怀疑与判断的基本标准则是“义理之所当否”与“左验之异同”,即思想逻辑与事实证据两大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治经提倡怀疑精神与其主张虚心切己并不必然构成矛盾,因为后者乃是前者的必要前提与基础。朱熹曾说:
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旧日看《论语》,合下便有疑。盖自有一样事,被诸先生说成数样,所以便着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间或有说不通处,自见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③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④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举所疑,与朋友讲论。假无朋友,久之,自能自见得。盖蓄积多者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此所谓“何天之衢亨”也。盖蓄极则通,须是蓄之极,则通。①
朱熹认为,怀疑须是在虚心熟读、深造自得的基础上自然有疑,不能故意立异,为怀疑而怀疑。若能真正做到虚心熟读,切己体认,自然会发现文本中的窒碍不通处,由此产生的怀疑便是合理的、有价值的怀疑。同时,也只有首先通过虚心切己的工夫积累了足够的知识与能力,才能在疑问产生后顺利将其解决,使学问更近一层,最终把握圣贤本意。
有所怀疑自然要有所辨伪。朱熹除了提倡怀疑精神之外,更在广泛借鉴、吸收前人辨疑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学实践与思考,择善而从,自立新说,做了大量的经典辨伪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绩。仅据白寿彝《朱熹辨伪书语》所辑录的资料来看,朱熹所辨疑的文献典籍就有四十余种,可谓宋代辨伪学的集大成者。其中,与儒家经典有关,且较为重要、具有较大影响者主要包括对《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孝经》等经典及其传注的辨伪。
对于《诗经》,朱熹指出《大序》与《小序》皆非孔子、子夏等圣贤所作,而是出于后人之手。“《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②“《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③“《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④
对于《尚书》,朱熹指出《孔序》《孔传》皆非西汉孔安国所作,而是出于后人伪托;《书序》(即《小序》)亦非孔子所作,乃周秦间人所作。“《尚书》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国所作。盖文字善困,不类西汉人文章,亦非后汉之文。”①“《书小序》亦非孔子作,与《诗小序》同。”②“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③同时,朱熹还对《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认为与《今文尚书》比较,“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④。且《古文尚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⑤。此外,朱熹对《今文尚书》中的某些篇章亦有所怀疑,认为其内容有不合常理处,多不可晓。
对于《礼记》,朱熹指出:“今只有《周礼》《仪礼》可全信。《礼记》有信不得处”⑥,“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⑦。又说:“《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⑧,“若《曲礼》《玉藻》诸篇,皆战国士人及汉儒所裒集”⑨,“《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恐未必得其真也”⑩,“《保傅》中说‘秦无道之暴’,此等语必非古书,乃后人采贾谊策为之,亦有《孝昭冠辞》”⑪。此外,朱熹还认为《礼运》“不是圣人书”⑫,《冠义》《昏义》《乡饮酒义》《乡射义》等篇皆系汉儒所造。
对于《左传》,朱熹认为并非春秋末年左丘明所作。“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较详。……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①
对于《孝经》,朱熹指出:“《孝经》,疑非圣人之言”②,“《孝经》亦是凑合之书,不可尽信”③,“据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④。因此,朱熹将《孝经》区分为经与传两部分,认为经是曾子门人所记,而传则是战国或汉初时人据《左传》《国语》等史传文字凑合缀辑而成,并非出于孔子或曾子之手。
朱熹之所以能在经典辨伪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对多部经典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还在于他总结、创造、使用了多种重要的经学辨伪方法,具有承上启下之功,为考据辨伪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试将朱熹所使用的辨伪方法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条:
(1)根据典籍的流传情况推断。譬如:
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⑤
《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大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①
朱熹认为,由伏生背诵口传的《今文尚书》文字艰涩难读,出于孔壁、以科斗文书写的《古文尚书》反而平易易晓,不符合典籍流传的一般情况与常理,故十分可疑。同时,出于孔壁的《古文尚书》历经数百年动荡却能完好无缺,不讹损一字,亦值得怀疑。
(2)根据典籍的文体风格推断。譬如: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如《书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②
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③
《尚书序》不似孔安国作,其文软弱,不似西汉人文,西汉文粗豪。也不似东汉人文,东汉人文有骨肋。也不似东晋人文,东晋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太段弱,读来却宛顺,是做《孔丛子》底人一手做。看《孔丛子》撰许多说话,极是陋。④
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验,古文自是庄重。至如孔安国《书序》并注中语,多非安国所作。盖西汉文章虽粗亦劲,今《书序》只是六朝软慢文体。因举《史记》所载《汤诰》并武王伐纣言辞不典,不知是甚底齐东野人之语也。⑤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①
朱熹认为,《尚书》的《孔序》与《孔传》文字软慢无气,不似西汉文章粗犷厚重的风格,且《孔传》的训释方法与西汉传注文字高简、有疑则阙的特征不符,证明《孔序》与《孔传》非西汉孔安国所作,系后人伪托。同时,朱熹含蓄地表示,《尚书》中的《汤诰》与武王伐纣等内容虽见于《史记》,但其言辞不典,亦值得怀疑。
(3)根据典籍所用字词推断。譬如:
(《舜典》)“玄德”难晓,书传中亦无言“玄”者。②
(《书大序》)“传之子孙,以贻后代。”汉时无这般文章。③
“《序》云‘聪明文思’,经作‘钦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问:“恐是作《序》者见经中有‘钦明文思’,遂改换‘钦’字作‘聪’字否?”曰:“然。”④
朱熹认为,《尚书·舜典》篇首的“玄德”之意难晓,且“玄”字未见于书传中,值得怀疑;《书大序》中“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的说法为汉代所无,亦值得怀疑。同时,朱熹认为《书小序》中所言“聪明文思”袭自经书中的“钦明文思”,有故意模仿作伪之嫌。
又如:《保傅》中说“秦无道之暴”,此等语必非古书,乃后人采贾谊策为之,亦有《孝昭冠辞》。①1
朱熹认为,《大戴礼记·保傅》中的“秦无道之暴”等语为先秦古书所无,乃后人杂取贾谊策论与《孝昭冠辞》等文字伪造。
(4)根据典籍的出现时间推断。譬如:《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②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③某尝疑《书注》非孔安国作,盖此传不应是东晋方出。④
朱熹认为,《书小序》于伏生时未见,今本《古文尚书》及《孔传》至东晋时方才出现,此前学者皆未见及,故十分可疑。
(5)根据典籍中体现的思想、义理推断。譬如:《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⑤《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煞有碍义理误人处。⑥
朱熹认为,《诗经》的《大序》与《小序》中皆有不符合儒家义理处,显然不可能是孔子、子夏等圣贤所作,而是出于后人杜撰。
又如: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①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②
朱熹认为,《左传》体现出纵横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不合儒家义理,其作者不可能是孔子所称赞的正直儒者左丘明。
又如:
据此书(指《孝经》),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如下面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岂不害理!倘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尽孝道也,岂不启人僭乱之心!③
朱熹认为,《孝经》所说的“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剥夺了一般人尽孝道的可能,不但不符合儒家义理,而且会引发人们的僭越作乱之心,故这部分内容绝不可能是孔子、曾子所作。
(6)根据典籍内容的不合理处推断。譬如:
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风,禾尽起”,也是差异。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启金滕之书?然当周公纳策于匮中,岂但二公知之?《盘庚》更没道理。从古相传来,如经传所引用,皆此书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说得都无头。且如今要告谕民间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只说道要迁,更不说道自家如何要迁,如何不可以不迁。万民因甚不要迁?要得人迁,也须说出利害,今更不说。《吕刑》一篇,如何穆王说得散漫,直从苗民蚩尤为始作乱说起?①
《康诰》以下三篇,更难理会。如《酒诰》却是戒饮酒,乃曰“肇牵车牛远服贾”,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亦多可疑处。②
朱熹认为,《尚书》的《金縢》《盘庚》《吕刑》《酒诰》《梓材》等篇中都存在不合人情事理、难以常理测度的内容,若说是出于圣贤之手,不免令人怀疑。
又如:
《蟋蟀》一篇,本其风俗勤俭,其民终岁勤劳,不得少休,及岁之暮,方且相与燕乐;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无已大康。”盖谓今虽不可以不为乐,然不已过于乐乎!其忧深思远固如此。……而序《蟋蟀》者则曰:“刺晋僖公俭不中礼。”盖风俗之变,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礼,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必无是理也。③
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④
朱熹认为,风俗的变化,必然是由社会上层传至下层民众。《诗小序》将《唐风·蟋蟀》一诗解释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不但与诗人原意不合,而且会导致君主过于勤俭而失礼,而民众犹知用礼的情况出现,有悖常理,故非圣贤所作。同时,朱熹指出,古人作诗的动机与今人一样,多是因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作,不可能每首诗都是为了赞美或讥刺他人而作。而《诗小序》作者将每篇诗歌都套用美刺说加以解说,显然有悖情理,绝非圣贤所为。
(7)根据经、序内容不合推断。譬如:
《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难”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①
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于让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难”,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②
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③
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汉书·艺文志》以为孔子纂《书》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于见存之篇虽颇依文立义,而亦无所发明。其间如《康诰》《酒诰》《梓材》之属,则与经文又有相戾者;其于已亡之篇,则伊阿简略,尤无所补,其非孔子所作明甚。④
诚有可疑。且如《康诰》,第述文王,不曾说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之词。然则《康诰》是武王诰康叔明矣。但缘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处,遂使序者以为成王时事。此岂可信。⑤
《书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诰》等篇,决是武王时书,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错处数简,遂误以为成王时书。然其词以康叔为弟而自称寡兄,追诵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文时语的甚。至于《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词,而亦误以为周公诰康叔而不之正也。①
朱熹认为,《书小序》对于《尧典》《舜典》《康诰》《酒诰》《梓材》等篇的解说皆与经文本义不合,对其所述时代、事件亦多误解,往往望文生义,证明作《序》者对《尚书》的内容与圣人作经之意并不了解,绝非孔子所作。
又如:
他做《小序》,不会宽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寻得着底,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底,要就《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诗》。②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见葛而思归宁,序得却如此!③
《大序》亦有末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④
《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⑤
《小序》……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昵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会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①
《诗序》实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诗》中数处皆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说。……《昊天有成命》中说“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会,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说了,又几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说,后来遂生一场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说“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说着地,如何说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说及后土。如汉诸郊诗,祭某神便说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说天,不说地。①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说,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庄姜》之诗,却以为刺卫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考者,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如《汉广》之《序》言“德广所及”,此语最乱道。诗人言“汉之广矣”,其言已分晓。②
看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事是当。如《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不知而今做义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
某谓此诗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读了。①
朱熹认为,《诗小序》刻意以美刺说解诗,多与《诗经》本义不合。譬如,《小序》对于《蟋蟀》《山有枢》《行苇》《卷耳》《桃夭》《有女同车》《抑》《昊天有成命》等篇的解说多是就诗中采摭言语,望文生义,又为了迁就美刺说,不惜穿凿附会,杜撰相关的人物、事实,不但不能发明诗之大旨,而且妨碍、干扰读者对于《诗经》的理解,显然不可能是圣贤所作。同时,朱熹指出《诗经》的《郑风》《卫风》《邶风》《鄘风》中多有淫诗,所以《诗大序》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并不能概括整部《诗经》的宗旨,证明其亦非圣贤所作。
(8)根据典籍所述内容后于成书年代推断。譬如: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②
左氏是三晋之后,不知是甚么人。看他说魏毕万之后必大,如说陈氏代齐之类,皆是后来设为豫定之言。③
子升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篡齐以后之书。”④
朱熹认为,《左传》中预言了三家分晋、陈氏代齐等事,证明其作者不可能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
(9)根据典籍所述内容与历史事实不符推断。譬如:《诗》,才说得密,便说他不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说自分晓。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须说。①
朱熹认为,据《周礼》《礼记》《左传》等书记载,周代史官并不掌诗,而《诗大序》却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证明其并非圣贤所作。
(10)根据典籍所载制度与时代不符推断。譬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②
朱熹认为,秦代开始才有腊祭的制度,而《左传》却说“虞不腊矣”,显然是在秦代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说法与意识,故作者不可能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
(11)根据典籍内容的取材来源推断。譬如:
棐,本木名,而借为“匪”字。颜师古注《汉书》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匪忱”,犹曰天难谋尔。孔传训作“辅”字,殊无义理。尝疑今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未必真安国所作,只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小尔雅》也。③
朱熹认为,《孔传》对于《尚书》的训解多出自《孔丛子》中的《小尔雅》,其言亦与《孔丛子》多相表里,因而怀疑《尚书孔传》与《孔丛子》是同一人伪作。
又如:
(《孝经》)“其中煞有《左传》及《国语》中言语。”或问:“莫是左氏引《孝经》中言语否?”曰:“不然。其言在《左氏传》《国语》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经》中却不成文理。见程沙随说,向时汪端明亦尝疑此书是后人伪为者。”①
古文《孝经》亦有可疑处。自《天子章》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与曾子说底通为一段。只逐章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一段文义都活。自此后,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多是《左传》中语。如“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季文子之辞。却云“虽得之,君子所不贵”,不知论孝却得个甚底,全无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②
朱熹认为,《孝经》中有不少言语与《左传》《国语》相似,且这些言语在《左传》《国语》中文理通贯,而在《孝经》中则不成文理,由此可以判断是《孝经》抄袭《左传》《国语》,证明《孝经》乃后人杂凑而成。
(12)根据与作者的其他著作或言论比较推断。譬如:
《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着,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③
朱熹认为,《孝经》说孝多未说到切要处,与《论语》说孝亲切有味不同,显然并非孔子之言,乃出于后人伪作。
诚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朱熹对于儒家经典的考证与辨伪仍显得较为简单零散,多散见于各种语录、书信、传注中,较少做深入、专门的讨论,有时证据不够充足,仅凭一两条理由就做出判断,不免过于轻率,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辨伪理论体系。同时,朱熹所使用的辨伪方法也存在一些不够科学、严谨的地方。比如,以典籍的文体风格、表达方式或思想义理等作为判断其作者、时代与真伪的标准,有时难免偏于个人主观的意见,而缺乏足够的客观性。又如,朱熹往往将圣贤之言预设为绝对正确、没有矛盾、绝对合乎义理的,认为圣贤对于经典的理解与解释必然完全符合经典本义,并且将此作为辨别经典及其传注真伪的基本前提,显然也有失武断,未必符合历史的真相。此外,朱熹在利用古代典籍互相比较、参证时,有时容易忽略不同典籍的成书年代与真伪情况,难保不会出现以晚证早、以伪驳真的情况。但是,正如白寿彝所指出的,朱熹辨伪学中的种种不足之处“是和后来考证学发达起来时的情形比较而言的。在当时能提出一种辨伪书的具体方案,并能应用这样多的方法的人,恐怕还是要推朱熹为第一人了。他辨伪书的话虽大半过于简单,但在简单的话里,颇有一些精彩的见解,给后来辨伪书的人不少的刺激”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对于儒家经典的怀疑与辨伪始终是以尊经卫道为基本前提和根本目的,并且与其理学思想的阐发、建构紧密关联。在朱熹看来,圣贤所作的经典本是完美无缺、尽善尽美、清楚明白、相互贯通的,只是由于后人的附会、增益、改窜、伪造,以及流传过程中遭到的毁坏,才使得经典文本出现残缺、错讹等各种问题以及阅读、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只有彻底清除这些后人附加上去的东西,恢复经典的原貌,才能更准确地接近、把握圣贤之道。同时,朱熹认为,正是由于后儒对于经典本义的误解与扭曲,才导致了圣贤之道的失真与失传,进而引发儒学地位的不断衰落。因此,必须扫除这些伪托、附会在圣贤身上的、有悖于义理的经典与传注,以符合圣贤相传之心的理学思想重新对儒家经典加以诠释,才能恢复、巩固儒学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一方面积极从事儒家经典的辨伪考证工作,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并将此作为经典辨伪的底线,最终实现了儒学的思想重建与全面复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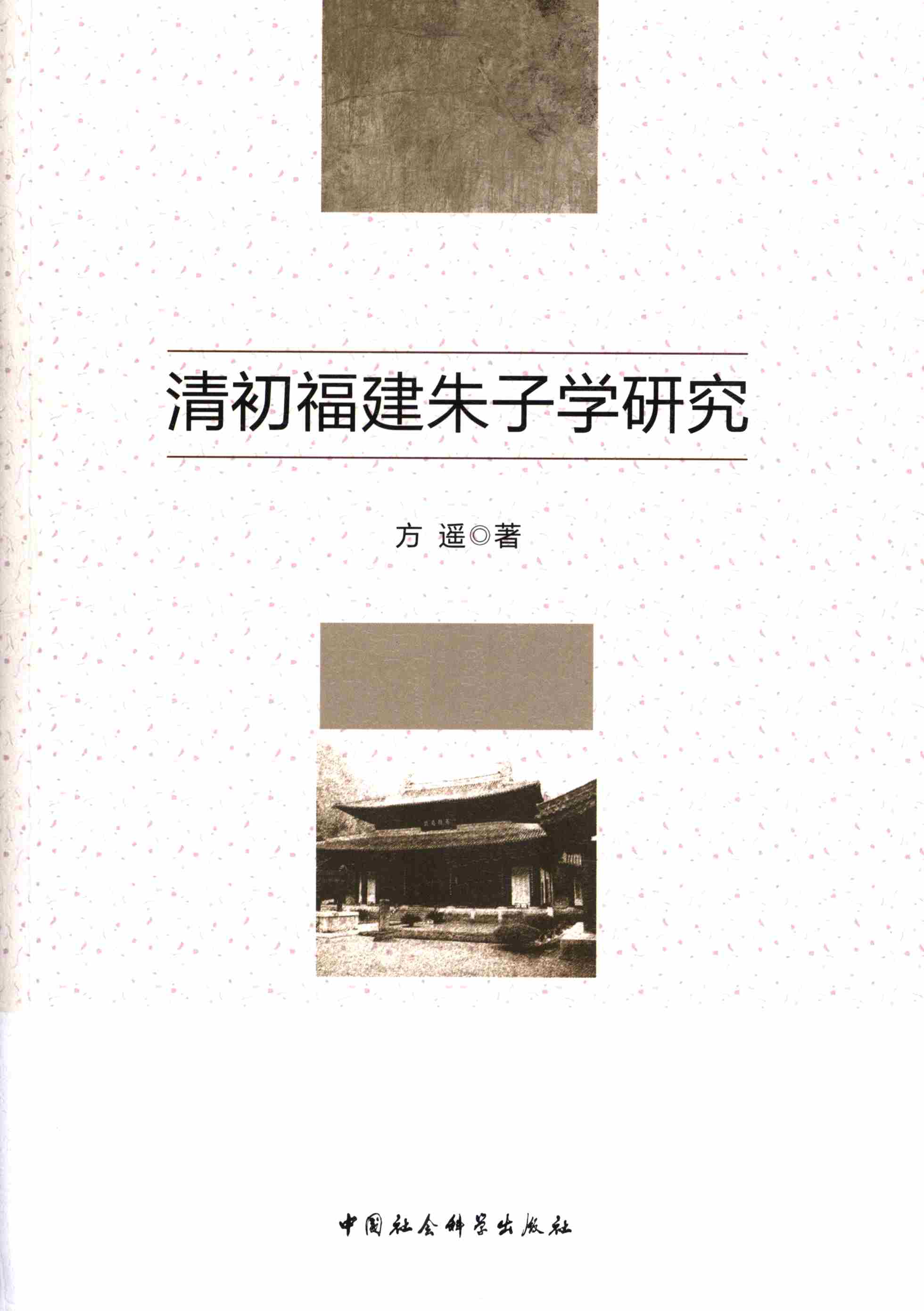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