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四书”代“五经”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72 |
| 颗粒名称: | (二)以“四书”代“五经”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5 |
| 页码: | 299-313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熹的经学特色和重大成就之一是提倡以“四书”代替“五经”,并建构了以四书为核心的新儒学经典体系。这一变革深刻地影响了儒家经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式,使儒学在宋代恢复了思想主导地位。朱熹通过对《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等四书的解读和注释,强调它们在阐发义理方面的重要性。他认为四书直接阐发义理,文字浅显易懂,是初学者理解儒家思想的良好入门。朱熹自己也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四书的研究上,编撰了多部与四书相关的著作。 |
| 关键词: | 朱熹 四书 五经 |
内容
提倡以“四书”代“五经”,建构以四书为核心的新儒学经典体系,亦是朱熹经学的基本特征和重大成就,深刻地影响、塑造了此后儒家经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式。从四书之学的形成过程来看,对于四书的发掘与提倡固然不始于朱熹,但最后却是由朱熹总其成的。可以说,四书的集成与四书学的确立是继西汉董仲舒表彰六经之后,儒学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通过对六经的推尊,使五经立于学官,从而借助政治权力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而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则通过对四书的表彰,使四书取代了五经的地位,成为儒学的基本典籍。这一典据变动,不仅有力地支撑、推动了传统儒学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转换,而且使儒学找到了新的思想基点,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成功地维护了儒学在传统社会后期的思想主导地位。
从学术思想史上看,在宋代以前,四书的地位与影响远远无法与五经相提并论。尤其是在中唐之前,《孟子》《大学》《中庸》基本上处于被忽视与埋没的状态。其中,《孟子》只是一部子书,而《大学》《中庸》还是《礼记》中的两篇文字,《中庸》虽曾有过单行本,但皆未得到学者的特别重视。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论语》,在汉代也仅附于五经之后,主要作为教育儿童的幼学之书,而唐代用以设科取士的“九经”中亦不包括《论语》。至中唐时,韩愈、李翱等学者开始表彰四书,方才正式开启了所谓“四书升格运动”的序幕。譬如,韩愈对孟子特别推崇,将孟子纳入其建构的儒学道统之中,认为列圣相传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①,并强调“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②。同时,韩愈在《原道》中引用《大学》思想,李翱作《复性书》阐发《中庸》中的性命之道,二人皆借《大学》《中庸》发挥儒家固有之义理,抵御佛教的扩张,从而赋予了这两篇文字较高的地位和意义。
入宋之后,宋儒又沿着韩愈、李翱开辟的这一思路继续前进。如范仲淹就曾借用《中庸》思想言“道”,提出:“诚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让乎圣贤,蟠极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于心,而后可言焉。”③更多学者发挥尊孟思想,如柳开认为,孔子之后,“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①,欧阳修谓:“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②,孙复则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③,石介亦云:“孔子既没,微言遂绝,杨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讵诐行,放淫辞,劝齐宣、梁惠七国之君以行仁义”④,皆衍韩愈道统之说。稍后,二程、张载、王安石等重要思想家亦表示尊孟,并着重从《孟子》中发掘儒家的心性思想与修养理论。特别是二程,不仅指出“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⑤,“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⑥,而且常将《孟子》与《论语》并列,认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⑦,“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⑧,隐然将原本附于五经之后的《论语》《孟子》置于五经之先,作为经学之本。此外,二程还大力表彰《大学》《中庸》,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极大地彰显了二书的重要性。正是在北宋诸儒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由子入经,《论语》的地位愈加尊崇,“孔孟之道”逐渐取代了“周孔之道”“孔颜之道”,而《大学》《中庸》亦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典据。据章权才研究,“从宋初到朱熹前,有关《论语》的著作不下七十部;有关《孟子》的著作不下四十部;有关《大学》的著作不下十部;有关《中庸》的著作不下二十部”①。这些学术成果为四书系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但在朱熹之前,宋代学者关于《孟子》一书的质疑与非议一直没有间断,“尊孟”与“贬孟”的争论持续百年,而“四书”一词亦未被正式提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经典还未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②据束景南考证,直到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婺州浙东提举任上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才正式出现,并首次作为一个整体结集出版。③此后,朱熹又反复修订、完善《四书章句集注》,不断将自己在理学思想上的新观点、新体悟融入四书的解释之中,最终使得以四书为核心的新儒学经典体系宣告成立。对于朱熹集注四书的重大意义,朱熹门人李方子曾做了明确的揭示:“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据依循守,以入于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语》《孟》二书,世所诵习,为之说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释言未备。《大学》《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学》次序不伦,阙遗未补,《中庸》虽为完篇,而章句浑沦,读者亦莫知其条理之灿然也。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①此后,朱注四书又被历代统治者悬为科举功令,四书义理之学遂取代五经训诂之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主流与核心。
关于四书与五经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朱熹说道: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
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③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④
《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切不可忙。⑤
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①
在朱熹看来,五经与四书之间存在着难易、远近、大小的差别。五经时代久远,文辞古奥,讲诵失传,其中的象数名物、训诂凡例多有难以确知者。加之在流传过程中屡遭散佚、窜乱,又“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②,故五经难看难解,非初学者所能把握。相比之下,四书则多直说日用眼前事,内容明白易晓,文字也较为浅显。根据朱熹提倡的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认识规律与学习方法,自然四书先于五经。
更为关键的是,四书以阐发义理为主要目的,是圣贤为了“言义理以晓人”而作,故说理最为直接、完整、系统,理学家最为重视的那些范畴、概念与命题亦多来源于四书之中。而五经的制作本意则非为了直接阐发义理,其与义理至多只有间接的关系。例如朱熹认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③,“《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④;《诗经》多是诗人为了“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作,故“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⑤,“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⑥;《仪礼》主要记载古代的仪节、名物、度数;而《春秋》则近史书,“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①,读《春秋》“且当看史功夫,未要便穿凿说褒贬道理”②。故曰:“《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因此,从理学家以义理解经的立场来看,自然四书重于五经。学者为学当以发明四书义理为先、为主,而五经转非所急。当然,朱熹并不否认五经中存在义理,也不反对学者从五经的文字中推衍、引申出义理,但这毕竟与圣人本意隔了几层,同样会导致所谓“工夫多,得效少”的问题。难怪朱熹也要无奈地感叹:“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③
而就朱熹本人的经学实践来看,其亦于四书之学上用功最勤,用力最多,可谓穷毕生精力以治之。朱熹编撰的与四书有关的著述即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四书音训》《论孟精义》《论语集解》《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要略》《孟子问辨》《孟子集解》《中庸辑略》《中庸详说》《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等。故黄榦谓:“先生著述虽多,于《语》《孟》《中庸》《大学》尤所加意。若《大学》《论语》,则更定数四,以至垂没。《大学》‘诚意’一章,乃其绝笔也。”④另据钱穆统计,《朱子语类》全书共一百四十卷,四书部分即占五十一卷,当全书篇幅三分之一以上;五经部分二十六卷,仅约四书部分篇幅的一半。其他各卷中,涉及四书的内容亦远胜其涉及五经的内容。⑤钱穆还指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作“乃是效法汉儒经学工夫而以之移用于语孟,逐字逐句,训诂考据,无所不用其极,而发挥义理则更为深至”,故称“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①因此可以说,朱熹的四书学集中体现了其建构的以阐发义理为主,融理学与经学为一炉的新学术范式。②
对于自己倾注了大半生心力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亦表现出特别的自信与重视。他说:
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③
《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④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⑤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那个无紧要闲底字,越要看。自家意里说是闲字,那个正是紧要字。⑥
陈淳亦云:
文公四书,一生精力在是,至属纩而后绝笔,为义极精矣。凡立语下字,端端的的,如逐字秤过一般,无一字苟且过。……注文与经文字字元自照应,有一字当数十字者,有一字当数千百字者,不可草草率略,皮肤上走过。⑦
由此可以想见朱熹注解四书之详慎与用心。因此,朱熹反复告诫门人弟子“《集注》且须熟读,记得”,“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如看得透,存养熟,可谓甚生气质”,①又说:“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故《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只把这个熟看,自然晓得,莫枉费心去外面思量。”②
相较之下,朱熹对于五经的态度就显得比较复杂。他一方面仍然肯定五经的价值,要求学者认真理会,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其中某些内容并非十分重要,或根本无法理解,因而不需要像研治四书那样逐字逐句推求阐释,以至于连一个闲字也不放过。譬如,对于《诗经》,朱熹提出“看《诗》,且看他大意。如《卫》诸诗,其中有说时事者,固当细考。如《郑》之淫乱底诗,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③,“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④。对于《尚书》,朱熹认为其“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⑤,又谓“《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着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⑥,“如《盘庚》之类,非特不可晓,便晓了亦要何用?如周《诰》诸篇,周公不过是说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⑦。对于礼书,朱熹认为“而今考得礼子细,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随俗不碍理底行去”⑧。对于《春秋》,朱熹则屡谓“《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①,“《春秋》难看,平生所以不敢说着”②,“《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尽教它是《鲁史》旧文,圣人笔削,又干我何事耶?”③由此亦可看出朱熹对待四书、五经的不同态度与研究方法。
此外,朱熹表彰四书,重建儒学经典体系,还是为了与其建构儒学道统的行为相互呼应和配合。④当时,由韩愈首先提出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一圣人之道的传授谱系,经过二程等人的继承与发扬,已逐渐成为宋代儒者的一种共识。而朱熹的历史意识和教学观念,使其特别重视经典与道之间的关系,强调经典是圣贤之道赖以传承的基础,始终致力于发掘和阐释相关的经典来支撑、论证和完善儒家的道统体系。因此,朱熹选择将四书与道统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道统的论述中。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道:
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⑤又说: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①
在朱熹所厘定的这一道统体系中,以人言,则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书言,则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如此,不仅填补了孔子与孟子之间的道统传授环节,而且使得经典与圣贤在道统中形成一种同构关系。而四书最初亦被称为“四子书”,表明其既代表了经典,也代表了圣贤。由此可以推断,朱熹之所以要将《大学》归之于曾子,将《中庸》归之于子思,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出于建构孔孟间道统的需要。反过来说,四书的提出亦清理、明确了孔子以下道统与道学的传承谱系,即便是孔门中地位最高、最受孔子青睐的颜子,虽然有时仍出现在朱熹的道统论述中,但由于他没有留下经典,并不在“四书”或“四子”的范围之内,因而亦逐渐消失在后人的道统谱系中。
圣贤之人与圣贤之道因经典而显,亦因经典而传。从这一意义上看,朱熹结撰《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发明、建构道统的需要,也表明了自己以道统自任的意愿与雄心。而这一点在朱熹自己的话语中亦可以得到印证。譬如,朱熹曾自述其撰写《大学章句》的缘由道: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①又述撰写《中庸章句》的缘由曰:
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后之君子。②
其言虽极谦虚,但其身任道统、当仁不让的态度亦极明显。
与此同时,唐宋儒者建立道统的一个重要目的还在于回应释、道二教在思想上的挑战。儒家的道统既有模仿佛家传灯系统的意味,又是对释、道异统的抗衡与否定。而朱熹通过对四书的表彰和重新诠释,不仅充实、巩固了儒家的道统理论,而且从中充分发掘了儒家自身固有的心性论、认识论、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建立了一套体用兼备、内外兼顾、可与释、道二教相匹敌的哲学形上学体系,并以入室操戈的方式对释、道二教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批判,从而成功地回应了释、道二教的挑战,重新夺回了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说,“朱熹的《四书集注》又是他从逃禅归儒以来不断批判佛老的一个总结,《四书集注》包含了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排佛思想体系”③。
当然,朱熹主张以四书代五经并不是要取消或否定五经的经典地位与学术价值,而是从理学的立场和需要出发,试图调整并重新定义四书与五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集注四书等一系列努力,朱熹成功地以四书取代了五经在经学中原有的核心与基础地位,形成了先四书后五经、以四书统率五经的全新经典体系与治学模式。众所周知,朱熹论学最重次第程序,要求学者通过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对圣人之道的完整把握,切不可急迫以求、妄意躐等。而为学次第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读书之序,读书之序其实正反映出朱熹所理解的入道之序。朱熹主张学者通过先治说理较为直接、系统、详细的四书,初步认识并正确理解圣人之道的大旨后,再去理会艰涩、繁杂的五经,以发明其中的义理与事实,把握圣人之学的全体。
朱熹对读书之序的讲求亦体现在其建构的四书学体系中。关于研治四书的次序,朱熹并未简单地按照四书作者的时代顺序进行排列,而是根据四书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性质特点,得出了以《大学》为先,《论语》《孟子》次之,《中庸》为末的治学次序。他说: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①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②
某说个读书之序:须是且著力去看《大学》,又著力去看《论语》,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书了,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问人,只略略恁看过。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难底。③
对此,黄榦亦云: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①
陈淳则曰:
圣门事业浩博无疆,而用功有节目,读书有次序。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此书见得古人规模节序,在诸书中为提纲振领处,必先从事于此,而《论》《孟》次之,《中庸》又次之。四书皆通,然后胸中权衡尺度分明,轻重长短毫发不差,乃可以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于是乎井井绳绳,莫不各有条理而不紊矣。②
李方子也说:
先生……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③
由此可见,《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学者的读书之序与入道之序,必然得到了朱熹的特别强调,已成为朱门中的不刊之论。而朱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先后次序,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从难易程度上看,《大学》“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虽“只说实事”①1,但由于“言语散见,初看亦难”,故在《大学》之后;《孟子》“多言理义大体”,又“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②故更难一些;《中庸》则“多说无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参’等类,说得高,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③,最难,故置于最后。另一方面,从逻辑、作用上看,《大学》总论“三纲领”“八条目”,为四书乃至整个儒学的纲领与基础;《论语》《孟子》则是对圣人之道的进一步展开和论述;《中庸》作为“孔门传授心法”,说理最为精微,为“造道之阃奥”④。因此,朱熹主张学者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圣人之微妙处,由此领会圣人之道,进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则可无往而不利。
从学术思想史上看,在宋代以前,四书的地位与影响远远无法与五经相提并论。尤其是在中唐之前,《孟子》《大学》《中庸》基本上处于被忽视与埋没的状态。其中,《孟子》只是一部子书,而《大学》《中庸》还是《礼记》中的两篇文字,《中庸》虽曾有过单行本,但皆未得到学者的特别重视。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论语》,在汉代也仅附于五经之后,主要作为教育儿童的幼学之书,而唐代用以设科取士的“九经”中亦不包括《论语》。至中唐时,韩愈、李翱等学者开始表彰四书,方才正式开启了所谓“四书升格运动”的序幕。譬如,韩愈对孟子特别推崇,将孟子纳入其建构的儒学道统之中,认为列圣相传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①,并强调“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②。同时,韩愈在《原道》中引用《大学》思想,李翱作《复性书》阐发《中庸》中的性命之道,二人皆借《大学》《中庸》发挥儒家固有之义理,抵御佛教的扩张,从而赋予了这两篇文字较高的地位和意义。
入宋之后,宋儒又沿着韩愈、李翱开辟的这一思路继续前进。如范仲淹就曾借用《中庸》思想言“道”,提出:“诚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让乎圣贤,蟠极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于心,而后可言焉。”③更多学者发挥尊孟思想,如柳开认为,孔子之后,“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①,欧阳修谓:“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②,孙复则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③,石介亦云:“孔子既没,微言遂绝,杨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讵诐行,放淫辞,劝齐宣、梁惠七国之君以行仁义”④,皆衍韩愈道统之说。稍后,二程、张载、王安石等重要思想家亦表示尊孟,并着重从《孟子》中发掘儒家的心性思想与修养理论。特别是二程,不仅指出“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⑤,“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⑥,而且常将《孟子》与《论语》并列,认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⑦,“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⑧,隐然将原本附于五经之后的《论语》《孟子》置于五经之先,作为经学之本。此外,二程还大力表彰《大学》《中庸》,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极大地彰显了二书的重要性。正是在北宋诸儒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由子入经,《论语》的地位愈加尊崇,“孔孟之道”逐渐取代了“周孔之道”“孔颜之道”,而《大学》《中庸》亦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典据。据章权才研究,“从宋初到朱熹前,有关《论语》的著作不下七十部;有关《孟子》的著作不下四十部;有关《大学》的著作不下十部;有关《中庸》的著作不下二十部”①。这些学术成果为四书系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但在朱熹之前,宋代学者关于《孟子》一书的质疑与非议一直没有间断,“尊孟”与“贬孟”的争论持续百年,而“四书”一词亦未被正式提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经典还未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②据束景南考证,直到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婺州浙东提举任上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才正式出现,并首次作为一个整体结集出版。③此后,朱熹又反复修订、完善《四书章句集注》,不断将自己在理学思想上的新观点、新体悟融入四书的解释之中,最终使得以四书为核心的新儒学经典体系宣告成立。对于朱熹集注四书的重大意义,朱熹门人李方子曾做了明确的揭示:“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据依循守,以入于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语》《孟》二书,世所诵习,为之说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释言未备。《大学》《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学》次序不伦,阙遗未补,《中庸》虽为完篇,而章句浑沦,读者亦莫知其条理之灿然也。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①此后,朱注四书又被历代统治者悬为科举功令,四书义理之学遂取代五经训诂之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主流与核心。
关于四书与五经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朱熹说道: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
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③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④
《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切不可忙。⑤
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①
在朱熹看来,五经与四书之间存在着难易、远近、大小的差别。五经时代久远,文辞古奥,讲诵失传,其中的象数名物、训诂凡例多有难以确知者。加之在流传过程中屡遭散佚、窜乱,又“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②,故五经难看难解,非初学者所能把握。相比之下,四书则多直说日用眼前事,内容明白易晓,文字也较为浅显。根据朱熹提倡的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认识规律与学习方法,自然四书先于五经。
更为关键的是,四书以阐发义理为主要目的,是圣贤为了“言义理以晓人”而作,故说理最为直接、完整、系统,理学家最为重视的那些范畴、概念与命题亦多来源于四书之中。而五经的制作本意则非为了直接阐发义理,其与义理至多只有间接的关系。例如朱熹认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③,“《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④;《诗经》多是诗人为了“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作,故“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⑤,“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⑥;《仪礼》主要记载古代的仪节、名物、度数;而《春秋》则近史书,“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①,读《春秋》“且当看史功夫,未要便穿凿说褒贬道理”②。故曰:“《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因此,从理学家以义理解经的立场来看,自然四书重于五经。学者为学当以发明四书义理为先、为主,而五经转非所急。当然,朱熹并不否认五经中存在义理,也不反对学者从五经的文字中推衍、引申出义理,但这毕竟与圣人本意隔了几层,同样会导致所谓“工夫多,得效少”的问题。难怪朱熹也要无奈地感叹:“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③
而就朱熹本人的经学实践来看,其亦于四书之学上用功最勤,用力最多,可谓穷毕生精力以治之。朱熹编撰的与四书有关的著述即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四书音训》《论孟精义》《论语集解》《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要略》《孟子问辨》《孟子集解》《中庸辑略》《中庸详说》《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等。故黄榦谓:“先生著述虽多,于《语》《孟》《中庸》《大学》尤所加意。若《大学》《论语》,则更定数四,以至垂没。《大学》‘诚意’一章,乃其绝笔也。”④另据钱穆统计,《朱子语类》全书共一百四十卷,四书部分即占五十一卷,当全书篇幅三分之一以上;五经部分二十六卷,仅约四书部分篇幅的一半。其他各卷中,涉及四书的内容亦远胜其涉及五经的内容。⑤钱穆还指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作“乃是效法汉儒经学工夫而以之移用于语孟,逐字逐句,训诂考据,无所不用其极,而发挥义理则更为深至”,故称“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①因此可以说,朱熹的四书学集中体现了其建构的以阐发义理为主,融理学与经学为一炉的新学术范式。②
对于自己倾注了大半生心力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亦表现出特别的自信与重视。他说:
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③
《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④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⑤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那个无紧要闲底字,越要看。自家意里说是闲字,那个正是紧要字。⑥
陈淳亦云:
文公四书,一生精力在是,至属纩而后绝笔,为义极精矣。凡立语下字,端端的的,如逐字秤过一般,无一字苟且过。……注文与经文字字元自照应,有一字当数十字者,有一字当数千百字者,不可草草率略,皮肤上走过。⑦
由此可以想见朱熹注解四书之详慎与用心。因此,朱熹反复告诫门人弟子“《集注》且须熟读,记得”,“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如看得透,存养熟,可谓甚生气质”,①又说:“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故《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只把这个熟看,自然晓得,莫枉费心去外面思量。”②
相较之下,朱熹对于五经的态度就显得比较复杂。他一方面仍然肯定五经的价值,要求学者认真理会,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其中某些内容并非十分重要,或根本无法理解,因而不需要像研治四书那样逐字逐句推求阐释,以至于连一个闲字也不放过。譬如,对于《诗经》,朱熹提出“看《诗》,且看他大意。如《卫》诸诗,其中有说时事者,固当细考。如《郑》之淫乱底诗,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③,“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④。对于《尚书》,朱熹认为其“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⑤,又谓“《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着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⑥,“如《盘庚》之类,非特不可晓,便晓了亦要何用?如周《诰》诸篇,周公不过是说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⑦。对于礼书,朱熹认为“而今考得礼子细,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随俗不碍理底行去”⑧。对于《春秋》,朱熹则屡谓“《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①,“《春秋》难看,平生所以不敢说着”②,“《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尽教它是《鲁史》旧文,圣人笔削,又干我何事耶?”③由此亦可看出朱熹对待四书、五经的不同态度与研究方法。
此外,朱熹表彰四书,重建儒学经典体系,还是为了与其建构儒学道统的行为相互呼应和配合。④当时,由韩愈首先提出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一圣人之道的传授谱系,经过二程等人的继承与发扬,已逐渐成为宋代儒者的一种共识。而朱熹的历史意识和教学观念,使其特别重视经典与道之间的关系,强调经典是圣贤之道赖以传承的基础,始终致力于发掘和阐释相关的经典来支撑、论证和完善儒家的道统体系。因此,朱熹选择将四书与道统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道统的论述中。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道:
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⑤又说: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①
在朱熹所厘定的这一道统体系中,以人言,则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书言,则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如此,不仅填补了孔子与孟子之间的道统传授环节,而且使得经典与圣贤在道统中形成一种同构关系。而四书最初亦被称为“四子书”,表明其既代表了经典,也代表了圣贤。由此可以推断,朱熹之所以要将《大学》归之于曾子,将《中庸》归之于子思,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出于建构孔孟间道统的需要。反过来说,四书的提出亦清理、明确了孔子以下道统与道学的传承谱系,即便是孔门中地位最高、最受孔子青睐的颜子,虽然有时仍出现在朱熹的道统论述中,但由于他没有留下经典,并不在“四书”或“四子”的范围之内,因而亦逐渐消失在后人的道统谱系中。
圣贤之人与圣贤之道因经典而显,亦因经典而传。从这一意义上看,朱熹结撰《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发明、建构道统的需要,也表明了自己以道统自任的意愿与雄心。而这一点在朱熹自己的话语中亦可以得到印证。譬如,朱熹曾自述其撰写《大学章句》的缘由道: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①又述撰写《中庸章句》的缘由曰:
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后之君子。②
其言虽极谦虚,但其身任道统、当仁不让的态度亦极明显。
与此同时,唐宋儒者建立道统的一个重要目的还在于回应释、道二教在思想上的挑战。儒家的道统既有模仿佛家传灯系统的意味,又是对释、道异统的抗衡与否定。而朱熹通过对四书的表彰和重新诠释,不仅充实、巩固了儒家的道统理论,而且从中充分发掘了儒家自身固有的心性论、认识论、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建立了一套体用兼备、内外兼顾、可与释、道二教相匹敌的哲学形上学体系,并以入室操戈的方式对释、道二教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批判,从而成功地回应了释、道二教的挑战,重新夺回了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说,“朱熹的《四书集注》又是他从逃禅归儒以来不断批判佛老的一个总结,《四书集注》包含了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排佛思想体系”③。
当然,朱熹主张以四书代五经并不是要取消或否定五经的经典地位与学术价值,而是从理学的立场和需要出发,试图调整并重新定义四书与五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集注四书等一系列努力,朱熹成功地以四书取代了五经在经学中原有的核心与基础地位,形成了先四书后五经、以四书统率五经的全新经典体系与治学模式。众所周知,朱熹论学最重次第程序,要求学者通过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对圣人之道的完整把握,切不可急迫以求、妄意躐等。而为学次第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读书之序,读书之序其实正反映出朱熹所理解的入道之序。朱熹主张学者通过先治说理较为直接、系统、详细的四书,初步认识并正确理解圣人之道的大旨后,再去理会艰涩、繁杂的五经,以发明其中的义理与事实,把握圣人之学的全体。
朱熹对读书之序的讲求亦体现在其建构的四书学体系中。关于研治四书的次序,朱熹并未简单地按照四书作者的时代顺序进行排列,而是根据四书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性质特点,得出了以《大学》为先,《论语》《孟子》次之,《中庸》为末的治学次序。他说: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①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②
某说个读书之序:须是且著力去看《大学》,又著力去看《论语》,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书了,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问人,只略略恁看过。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难底。③
对此,黄榦亦云: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①
陈淳则曰:
圣门事业浩博无疆,而用功有节目,读书有次序。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此书见得古人规模节序,在诸书中为提纲振领处,必先从事于此,而《论》《孟》次之,《中庸》又次之。四书皆通,然后胸中权衡尺度分明,轻重长短毫发不差,乃可以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于是乎井井绳绳,莫不各有条理而不紊矣。②
李方子也说:
先生……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③
由此可见,《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学者的读书之序与入道之序,必然得到了朱熹的特别强调,已成为朱门中的不刊之论。而朱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先后次序,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从难易程度上看,《大学》“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虽“只说实事”①1,但由于“言语散见,初看亦难”,故在《大学》之后;《孟子》“多言理义大体”,又“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②故更难一些;《中庸》则“多说无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参’等类,说得高,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③,最难,故置于最后。另一方面,从逻辑、作用上看,《大学》总论“三纲领”“八条目”,为四书乃至整个儒学的纲领与基础;《论语》《孟子》则是对圣人之道的进一步展开和论述;《中庸》作为“孔门传授心法”,说理最为精微,为“造道之阃奥”④。因此,朱熹主张学者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圣人之微妙处,由此领会圣人之道,进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则可无往而不利。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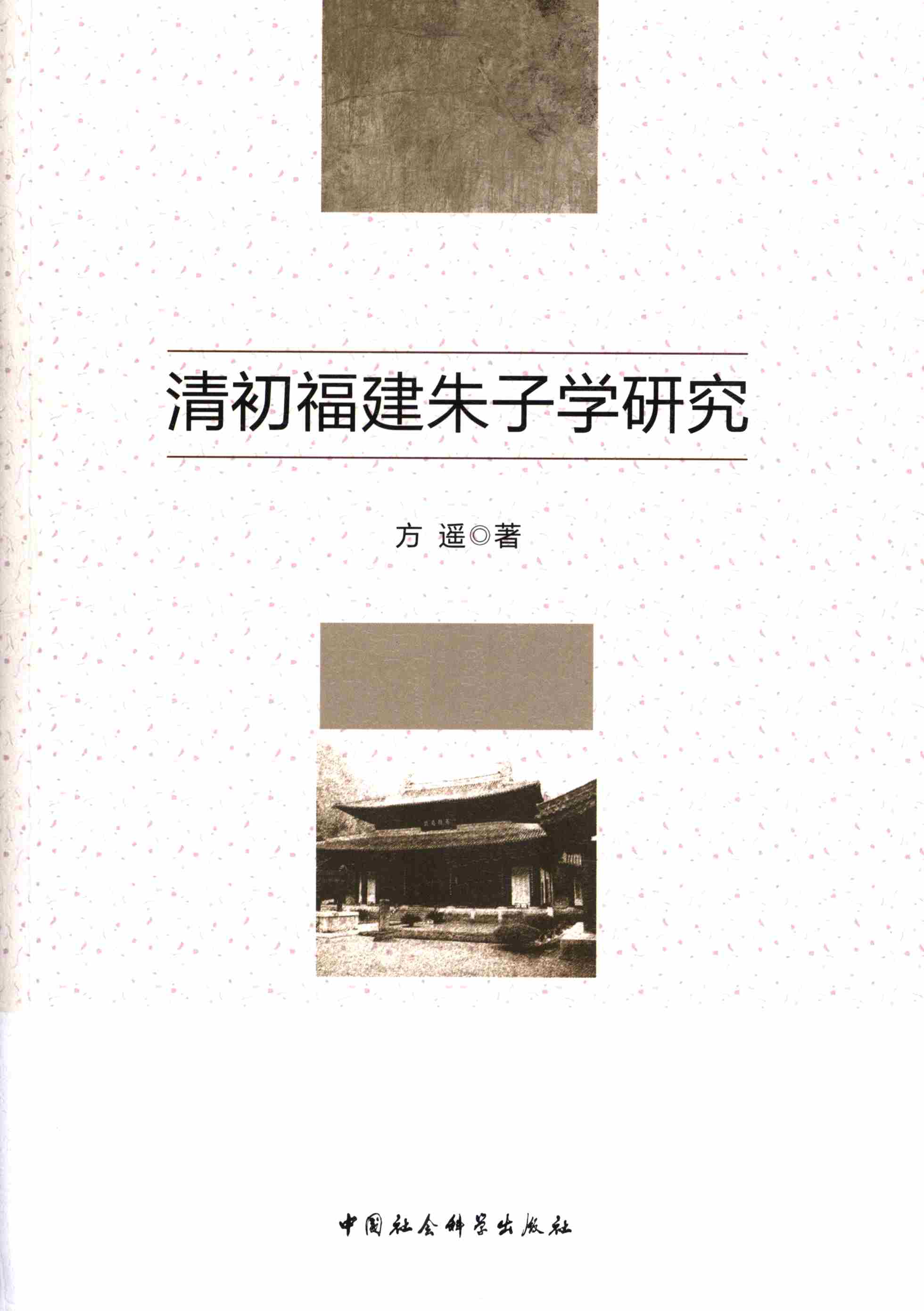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