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传相分,直求本义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71 |
| 颗粒名称: | (一)经传相分,直求本义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288-299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熹对于经学的特色之一是提倡“经传相分”,即将经书和传注分开阐释。他对《诗经》、《周易》、《三礼》、《尚书》和《春秋》等经典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经文和传注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和重点,应该分别对待。此外,朱熹还批评了一些传注的伪作和误解,并努力恢复经典本义的研究。 |
| 关键词: | 经传相分 经学特色 经文 |
内容
(一)经传相分,直求本义
提倡“经传相分”是朱熹经学的一项显著特色。束景南就将“经传相分,就经求经”视为朱熹确立的新的解经方法论原则之一。④蔡方鹿亦指出:“经传相分作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原则,贯穿在朱熹经学思想的各个方面。”⑤具体而论,对于《诗经》,朱熹主张将《毛传》与经区分开来,分别对待,以经解经,以《诗》说《诗》。他说:
《诗》疏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而《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亦与经别。及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而就经为注。”据此,则古之经、传本皆自为一书。①
朱熹指出,“经传相分”本是一项古代旧有的原则,“古之经、传本皆自为一书”。如在《汉书·艺文志》中,《毛诗经》与《毛诗诂训传》就是分开著录的,二者并不相连。直到东汉以后,才出现“就经为注”的现象,而《诗经》亦“引经附传”,人为地将经传合并在一起,使后人难以认识经传的原貌。且后世所传,又仅毛传郑笺一家而已,学者“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故只有突破解《诗》尽宗毛氏的旧传统,“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②
对于《周易》,朱熹主张将其分为《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并在《周易本义》中把“十翼”从经文中分离出来,列于上下经之后,使其不相扰乱。他说: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袠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③
朱熹指出,《周易》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最初由伏羲画卦,未有文字,后文王、周公依卦作卦爻辞,形诸文字,这部分即为《易经》。再后来,孔子作“十翼”,以义理释经,则为《易传》。《易经》以卜筮为主,《易传》以说理为主,二者各有侧重,应区分开来,各自阐释,而不能混为一谈。
在考察了古《易》的版本之后,朱熹进一步指出:
《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则《彖》《象》《文言》《系辞》始附卦爻而传于汉欤?先儒谓费直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其初费氏不列学官,惟行民间。至汉末,陈元、郑康成之徒学费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颖达又谓,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则费氏初变乱古制时,犹若今《乾》卦《彖》《象》系卦之末欤?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惜哉!①
朱熹举《汉书·艺文志》为证,认为在西汉费直之前,《易经》与《易传》尚是独立的。费直始将《彖》《象》《文言》等传文杂入卦中,其学经陈元、郑玄等人的传承,到王弼时更将经传合一,以老庄之理释《易》,造成了以传解经、以义理释《易》的解《易》原则的流行,掩盖了经文的本义。而王弼的这一思路又为程颐所继承和发扬,以理学义理释《易》,并著为《易传》,成为宋代易学义理派的代表。对此,身为理学家的朱熹却颇为不满,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②。其又指出程氏《易传》“义理精……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③,甚至批评程颐“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①,“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②。在朱熹看来,既然《周易》在客观上包含经、传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在历史发展中又形成了以象数或义理解经两种不同的传统,就应该将二者区别开来,分清《易经》的本义与引申义,立足于《易经》的本文来解释《易经》,以恢复其作为卜筮之书的原貌,并使义理的阐发能够有所依据,不悖经义。故曰:
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方得。③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④
对于三礼,朱熹主张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领。他说:
《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⑤
《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今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故不能见其本末。①又说:
《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故臣顷在山林,尝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②
朱熹认为,《仪礼》乃礼之本经,而《礼记》则是秦、汉前后诸儒解释《仪礼》之书,故礼学应以《仪礼》为根本。因此,他批评王安石废罢《仪礼》,以《礼记》取而代之的做法是“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同时,朱熹也指出了《礼记》与《仪礼》之间的相关性,主张将《礼记》等传注附在《仪礼》经文之后,一方面帮助学者理解经文,以解决《仪礼》难读的问题;另一方面使《礼记》所述之理建立在《仪礼》所载之事的基础上,则理、事不相分离,避免离事言理。
对于《尚书》,朱熹明确指出历来被视为解《书》正宗的《孔安国尚书传》与《孔安国尚书序》(即《大序》)皆非西汉孔安国所撰,而出于后人的伪托。他说:
《尚书》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国所作。盖文字善困,不类西汉人文章,亦非后汉之文。①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如《书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②
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百千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③
朱熹不仅根据文体风格、注解方法、出现时间等因素判定《尚书》的《孔传》与《孔序》皆伪,而且批评“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④,从而主张黜退《孔传》《孔序》,使学者能够从《孔传》《孔序》的障蔽与束缚中解脱出来,直接探求《尚书》的本义。
同时,朱熹还认为系于《尚书》各篇之前的《书序》(即《小序》)非孔子所作,乃出于周秦间经师之手。他说:《小序》断不是孔子做。⑤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⑥《书序》恐只是经师所作,然亦无证可考,但决非夫子之言耳。⑦
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汉书·艺文志》以为孔子纂《书》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于见存之篇虽颇依文立义,而亦无所发明。其间如《康诰》《酒诰》《梓材》之属,则与经文又有相戾者;其于已亡之篇,则伊阿简略,尤无所补,其非孔子所作明甚。①
在朱熹看来,《书序》只是依傍《尚书》经文而作,不但对经文无所发明,而且颇有与经文之意不合者,从中亦无法了解《尚书》亡佚篇章的真相,所以绝不可能是孔子所作。由于《书序》“相承已久”,朱熹对其并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有鉴于当时学者不顾《尚书》经文,而只理会《书序》的弊病,朱熹在漳州刊刻《尚书》时,“一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合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不乱乎诸儒之说”②。
对于《春秋》,朱熹亦指出《春秋》本经与“三传”之说有所区别,而“三传”之间又各具特色,互有长短,不能单纯以传解经。他说: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③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④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⑤《朱子语类》又载: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①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②
在朱熹看来,《左传》是史学,长于记事而蔽于说理,多世俗功利之见,而《公羊传》《谷梁传》是经学,长于义理而记事多误,且所说之理亦有非圣人原意者,故“三传”皆有所未备。他进一步指出,《春秋》主要应作为史书来看,所谓的《春秋》大义即见于史事之中,所以学者解读《春秋》时应于史事中直见圣人之意,避免陷于穿凿附会。故曰:“《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③,“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④
对于《大学》,朱熹将其分为经一章与传十章两个部分。其中,开首一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为经,提出“三纲领”“八条目”,被认为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而经以下的部分为传,是逐条对“三纲领”“八条目”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说与论证,被认为是曾子之意,门人记之。如此,则理解“三纲领”“八条目”便成为注解《大学》的关键所在。
对于《孝经》,朱熹亦将其分为经一章与传十四章两个部分。其中,原《孝经》的前六章,即“仲尼闲居,曾子侍坐。……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为经,被认为是孔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记之;经以下的部分为传,被认为是后人据《左传》《国语》等史传文字缀辑而成,用以解释经文。在朱熹看来,《孝经》经文虽“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但“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①而传文则属拼凑,且多附会、害理之言,故不应与经文相混杂。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经、传之外,每部儒家经典背后都有各种传注疏释存在。一般来说,经由圣人所作,或记圣人之言,拥有最高的权威性与真理性。而传注则比较复杂,既有出于先圣先贤者,但更多的则是后儒所作。特别是某些后儒对经典的注解与诠释,仅为一家之言却托之于圣人,难免驳杂不纯,不可尽信。若将其与经文相混杂,往往会导致经文本义的扭曲与淆乱。即便是先圣先贤所作之传,也应与经文有所区别,各究其义,使经传之旨各明。在朱熹看来,经典本身构成了经学研究的核心与根本,传注仅是经文的附庸,是使人们认识经文本义的工具与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容颠倒。所谓“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②。因此,朱熹既批评了汉唐诸儒只重章句训诂,援传入经,以传代经,甚至“宁言周孔误,不道郑服非”的弊病,也批评了宋儒脱离经典本义而空谈义理的不良学术风气。相较之下,朱熹作为南宋时人,不但不讳言后一种弊病的存在,反而因其现实性而对其危害认识更深,批评也较多。譬如他说:
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圣贤已死,它看你如何说,他又不会出来与你争,只是非圣贤之意。他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如何。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恐人捉他,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并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说而已,何尝真实得圣人之意?却是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①
大抵近世说经者,多不虚心以求经之本意,而务极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间略有缝罅,如可钩索,略有形影,如可执搏,则遂极笔模写,以附于经,而谓经之为说本如是也。其亦误矣。②
近见学者多是先立己见,不问经文向背之势,而横以义理加之。其说虽不悖理,然非经文本意也。如此则但据己见自为一书亦可,何必读古圣贤之书哉?所以读书,政恐吾之所见未必是,而求正于彼耳。惟其阙文断简、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则无可奈何,其他在义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须字字句句反复消详,不可草草说过也。③
朱熹指出,学者之所以要读经,正是因为不知自己的思想、见解是否正确,故以圣贤之言为标准,而取正于经书。因此,注经、解经必须以经文本身为基础,特别是将其中与义理有关的重要内容“字字句句反复消详”,完整掌握经典的本旨,然后再从中推说义理。若一以己意为是,甚至硬将己意加诸经典,挟经自重,强经以同己,则丧失了经学的本来目的,即便道理说得再好,也与圣人之意无关。同样,正因为有大量这样唯以己意解经的传注存在,学者治经亦须注意经传相分,超越先儒的传注,以经典本文为最终依据,而不能一味地以传解经、因循旧说。正如朱熹告诫学者:“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会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却将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而强饮食之,终无益也。”①
而在朱熹对于经典本义的强调中,实际上又包含了探求经典“文义”与经典“本意”两层含义。简言之,经典文义主要指经文的字面意思,而经典本意则指圣人作经之意图。因此,探求经典文义侧重于对语言文字、名物度数的注解与考释,要求注解者本人尽量不出现,略相当于“解释”;而探求经典本意则强调对隐藏于经文背后的圣人之意的领悟,是经典解释的进一步深化,更加突出解释者个人的思想因素与作用,略相当于“理解”或“诠释”。相对而言,“解释”是局部的、直接的、分析的,而“理解”或“诠释”则是整体的、间接的、综合的。
关于探求圣人本意的意义,朱熹说道:
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不得其意,则从那处推得出来?②
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③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不特《诗》也,他书皆然。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义,兴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台》序云:“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盖为见《诗》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才如此说定,便局了一诗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虽如此说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圣人《系辞》之意,便横说竖说都得。今断以一义解定,《易》便不活。④根据宋明理学的基本预设,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与天地同德,圣人的言行、思虑即是天理的体现,所谓“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①,“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②。因此,对圣人之意的追求即是对天理的追求。而朱熹作为宋代理学家的主要代表,其经学研究以义理阐释为主,自然要将对圣人本意的追求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由于圣人本意往往具有一定的内在性和复杂性,并非如字面意思那般直观可见,甚至可能与字面意思有所不合。因此,对经典文义的了解往往不能直接实现对圣人本意的把握,学者在掌握经典文义的基础上,还须更求圣人作经之本意。在朱熹看来,对圣人本意的探求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义理的阐发,因为圣人作经的原意并不都是为了直接说理,但对圣人思想意图的领悟却是推究、引申、阐发经典义理的必要前提与基础。若能先得圣人本意,则意味着获得了极大的诠释自由,“便横说竖说都得”。当然,由于思想观念的表达要以文本为载体,所以经典“文义”与“本意”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一致性,在实际的经学研究中要将二者截然区分开是很困难的。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学者对于圣人思想意图的领悟往往有赖于对文本字面意思的准确把握,而对圣人思想意图的领悟反过来又将促进学者对文本字面意思的正确解读,因而二者也不应该被割裂、对立。总之,不论是对于经典文义还是圣人本意的关注和强调,都是紧紧围绕着“圣人—经典”这个中心,都清楚地反映出朱熹对于经典解释的直接性与客观性的重视和追求。
提倡“经传相分”是朱熹经学的一项显著特色。束景南就将“经传相分,就经求经”视为朱熹确立的新的解经方法论原则之一。④蔡方鹿亦指出:“经传相分作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原则,贯穿在朱熹经学思想的各个方面。”⑤具体而论,对于《诗经》,朱熹主张将《毛传》与经区分开来,分别对待,以经解经,以《诗》说《诗》。他说:
《诗》疏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而《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亦与经别。及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而就经为注。”据此,则古之经、传本皆自为一书。①
朱熹指出,“经传相分”本是一项古代旧有的原则,“古之经、传本皆自为一书”。如在《汉书·艺文志》中,《毛诗经》与《毛诗诂训传》就是分开著录的,二者并不相连。直到东汉以后,才出现“就经为注”的现象,而《诗经》亦“引经附传”,人为地将经传合并在一起,使后人难以认识经传的原貌。且后世所传,又仅毛传郑笺一家而已,学者“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故只有突破解《诗》尽宗毛氏的旧传统,“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②
对于《周易》,朱熹主张将其分为《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并在《周易本义》中把“十翼”从经文中分离出来,列于上下经之后,使其不相扰乱。他说: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袠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③
朱熹指出,《周易》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最初由伏羲画卦,未有文字,后文王、周公依卦作卦爻辞,形诸文字,这部分即为《易经》。再后来,孔子作“十翼”,以义理释经,则为《易传》。《易经》以卜筮为主,《易传》以说理为主,二者各有侧重,应区分开来,各自阐释,而不能混为一谈。
在考察了古《易》的版本之后,朱熹进一步指出:
《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则《彖》《象》《文言》《系辞》始附卦爻而传于汉欤?先儒谓费直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其初费氏不列学官,惟行民间。至汉末,陈元、郑康成之徒学费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颖达又谓,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则费氏初变乱古制时,犹若今《乾》卦《彖》《象》系卦之末欤?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惜哉!①
朱熹举《汉书·艺文志》为证,认为在西汉费直之前,《易经》与《易传》尚是独立的。费直始将《彖》《象》《文言》等传文杂入卦中,其学经陈元、郑玄等人的传承,到王弼时更将经传合一,以老庄之理释《易》,造成了以传解经、以义理释《易》的解《易》原则的流行,掩盖了经文的本义。而王弼的这一思路又为程颐所继承和发扬,以理学义理释《易》,并著为《易传》,成为宋代易学义理派的代表。对此,身为理学家的朱熹却颇为不满,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②。其又指出程氏《易传》“义理精……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③,甚至批评程颐“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①,“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②。在朱熹看来,既然《周易》在客观上包含经、传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在历史发展中又形成了以象数或义理解经两种不同的传统,就应该将二者区别开来,分清《易经》的本义与引申义,立足于《易经》的本文来解释《易经》,以恢复其作为卜筮之书的原貌,并使义理的阐发能够有所依据,不悖经义。故曰:
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方得。③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④
对于三礼,朱熹主张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领。他说:
《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⑤
《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今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故不能见其本末。①又说:
《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故臣顷在山林,尝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②
朱熹认为,《仪礼》乃礼之本经,而《礼记》则是秦、汉前后诸儒解释《仪礼》之书,故礼学应以《仪礼》为根本。因此,他批评王安石废罢《仪礼》,以《礼记》取而代之的做法是“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同时,朱熹也指出了《礼记》与《仪礼》之间的相关性,主张将《礼记》等传注附在《仪礼》经文之后,一方面帮助学者理解经文,以解决《仪礼》难读的问题;另一方面使《礼记》所述之理建立在《仪礼》所载之事的基础上,则理、事不相分离,避免离事言理。
对于《尚书》,朱熹明确指出历来被视为解《书》正宗的《孔安国尚书传》与《孔安国尚书序》(即《大序》)皆非西汉孔安国所撰,而出于后人的伪托。他说:
《尚书》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国所作。盖文字善困,不类西汉人文章,亦非后汉之文。①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如《书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②
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百千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③
朱熹不仅根据文体风格、注解方法、出现时间等因素判定《尚书》的《孔传》与《孔序》皆伪,而且批评“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④,从而主张黜退《孔传》《孔序》,使学者能够从《孔传》《孔序》的障蔽与束缚中解脱出来,直接探求《尚书》的本义。
同时,朱熹还认为系于《尚书》各篇之前的《书序》(即《小序》)非孔子所作,乃出于周秦间经师之手。他说:《小序》断不是孔子做。⑤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⑥《书序》恐只是经师所作,然亦无证可考,但决非夫子之言耳。⑦
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汉书·艺文志》以为孔子纂《书》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于见存之篇虽颇依文立义,而亦无所发明。其间如《康诰》《酒诰》《梓材》之属,则与经文又有相戾者;其于已亡之篇,则伊阿简略,尤无所补,其非孔子所作明甚。①
在朱熹看来,《书序》只是依傍《尚书》经文而作,不但对经文无所发明,而且颇有与经文之意不合者,从中亦无法了解《尚书》亡佚篇章的真相,所以绝不可能是孔子所作。由于《书序》“相承已久”,朱熹对其并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有鉴于当时学者不顾《尚书》经文,而只理会《书序》的弊病,朱熹在漳州刊刻《尚书》时,“一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合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不乱乎诸儒之说”②。
对于《春秋》,朱熹亦指出《春秋》本经与“三传”之说有所区别,而“三传”之间又各具特色,互有长短,不能单纯以传解经。他说: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③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④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⑤《朱子语类》又载: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①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②
在朱熹看来,《左传》是史学,长于记事而蔽于说理,多世俗功利之见,而《公羊传》《谷梁传》是经学,长于义理而记事多误,且所说之理亦有非圣人原意者,故“三传”皆有所未备。他进一步指出,《春秋》主要应作为史书来看,所谓的《春秋》大义即见于史事之中,所以学者解读《春秋》时应于史事中直见圣人之意,避免陷于穿凿附会。故曰:“《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③,“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④
对于《大学》,朱熹将其分为经一章与传十章两个部分。其中,开首一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为经,提出“三纲领”“八条目”,被认为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而经以下的部分为传,是逐条对“三纲领”“八条目”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说与论证,被认为是曾子之意,门人记之。如此,则理解“三纲领”“八条目”便成为注解《大学》的关键所在。
对于《孝经》,朱熹亦将其分为经一章与传十四章两个部分。其中,原《孝经》的前六章,即“仲尼闲居,曾子侍坐。……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为经,被认为是孔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记之;经以下的部分为传,被认为是后人据《左传》《国语》等史传文字缀辑而成,用以解释经文。在朱熹看来,《孝经》经文虽“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但“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①而传文则属拼凑,且多附会、害理之言,故不应与经文相混杂。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经、传之外,每部儒家经典背后都有各种传注疏释存在。一般来说,经由圣人所作,或记圣人之言,拥有最高的权威性与真理性。而传注则比较复杂,既有出于先圣先贤者,但更多的则是后儒所作。特别是某些后儒对经典的注解与诠释,仅为一家之言却托之于圣人,难免驳杂不纯,不可尽信。若将其与经文相混杂,往往会导致经文本义的扭曲与淆乱。即便是先圣先贤所作之传,也应与经文有所区别,各究其义,使经传之旨各明。在朱熹看来,经典本身构成了经学研究的核心与根本,传注仅是经文的附庸,是使人们认识经文本义的工具与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容颠倒。所谓“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②。因此,朱熹既批评了汉唐诸儒只重章句训诂,援传入经,以传代经,甚至“宁言周孔误,不道郑服非”的弊病,也批评了宋儒脱离经典本义而空谈义理的不良学术风气。相较之下,朱熹作为南宋时人,不但不讳言后一种弊病的存在,反而因其现实性而对其危害认识更深,批评也较多。譬如他说:
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圣贤已死,它看你如何说,他又不会出来与你争,只是非圣贤之意。他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如何。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恐人捉他,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并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说而已,何尝真实得圣人之意?却是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①
大抵近世说经者,多不虚心以求经之本意,而务极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间略有缝罅,如可钩索,略有形影,如可执搏,则遂极笔模写,以附于经,而谓经之为说本如是也。其亦误矣。②
近见学者多是先立己见,不问经文向背之势,而横以义理加之。其说虽不悖理,然非经文本意也。如此则但据己见自为一书亦可,何必读古圣贤之书哉?所以读书,政恐吾之所见未必是,而求正于彼耳。惟其阙文断简、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则无可奈何,其他在义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须字字句句反复消详,不可草草说过也。③
朱熹指出,学者之所以要读经,正是因为不知自己的思想、见解是否正确,故以圣贤之言为标准,而取正于经书。因此,注经、解经必须以经文本身为基础,特别是将其中与义理有关的重要内容“字字句句反复消详”,完整掌握经典的本旨,然后再从中推说义理。若一以己意为是,甚至硬将己意加诸经典,挟经自重,强经以同己,则丧失了经学的本来目的,即便道理说得再好,也与圣人之意无关。同样,正因为有大量这样唯以己意解经的传注存在,学者治经亦须注意经传相分,超越先儒的传注,以经典本文为最终依据,而不能一味地以传解经、因循旧说。正如朱熹告诫学者:“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会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却将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而强饮食之,终无益也。”①
而在朱熹对于经典本义的强调中,实际上又包含了探求经典“文义”与经典“本意”两层含义。简言之,经典文义主要指经文的字面意思,而经典本意则指圣人作经之意图。因此,探求经典文义侧重于对语言文字、名物度数的注解与考释,要求注解者本人尽量不出现,略相当于“解释”;而探求经典本意则强调对隐藏于经文背后的圣人之意的领悟,是经典解释的进一步深化,更加突出解释者个人的思想因素与作用,略相当于“理解”或“诠释”。相对而言,“解释”是局部的、直接的、分析的,而“理解”或“诠释”则是整体的、间接的、综合的。
关于探求圣人本意的意义,朱熹说道:
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不得其意,则从那处推得出来?②
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③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不特《诗》也,他书皆然。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义,兴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台》序云:“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盖为见《诗》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才如此说定,便局了一诗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虽如此说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圣人《系辞》之意,便横说竖说都得。今断以一义解定,《易》便不活。④根据宋明理学的基本预设,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与天地同德,圣人的言行、思虑即是天理的体现,所谓“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①,“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②。因此,对圣人之意的追求即是对天理的追求。而朱熹作为宋代理学家的主要代表,其经学研究以义理阐释为主,自然要将对圣人本意的追求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由于圣人本意往往具有一定的内在性和复杂性,并非如字面意思那般直观可见,甚至可能与字面意思有所不合。因此,对经典文义的了解往往不能直接实现对圣人本意的把握,学者在掌握经典文义的基础上,还须更求圣人作经之本意。在朱熹看来,对圣人本意的探求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义理的阐发,因为圣人作经的原意并不都是为了直接说理,但对圣人思想意图的领悟却是推究、引申、阐发经典义理的必要前提与基础。若能先得圣人本意,则意味着获得了极大的诠释自由,“便横说竖说都得”。当然,由于思想观念的表达要以文本为载体,所以经典“文义”与“本意”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一致性,在实际的经学研究中要将二者截然区分开是很困难的。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学者对于圣人思想意图的领悟往往有赖于对文本字面意思的准确把握,而对圣人思想意图的领悟反过来又将促进学者对文本字面意思的正确解读,因而二者也不应该被割裂、对立。总之,不论是对于经典文义还是圣人本意的关注和强调,都是紧紧围绕着“圣人—经典”这个中心,都清楚地反映出朱熹对于经典解释的直接性与客观性的重视和追求。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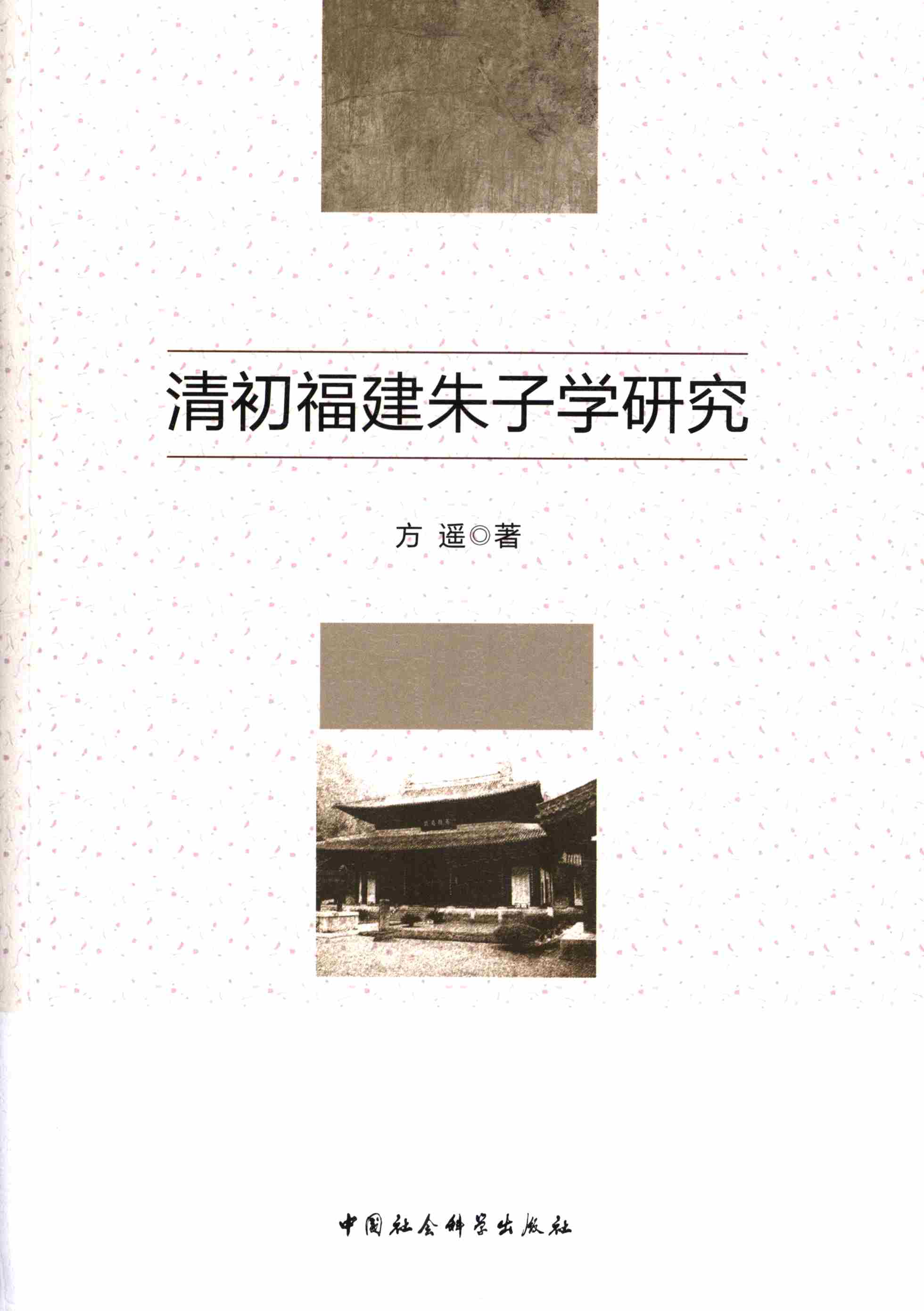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