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格物致知”与“知性明善”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65 |
| 颗粒名称: | 四 “格物致知”与“知性明善”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244-255 |
| 摘要: | 本文主要讨论了“格物致知”与“知性明善”的理论。作者首先介绍了李光地对于格物论的态度与观点,他认为自宋以来的格物论无不源自程朱之说,但在具体内容上,李光地认为自己与朱熹并无本质区别,同时也融摄了陆王格致论的思想。其次,作者详细分析了李光地与朱熹在格物致知论上的不同之处,朱熹主要以即物穷理言格致,而李光地偏重于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这种理解受到陆王心学的影响,体现了折中程朱、陆王思想的意图。文章还提到了王艮的“淮南格物论”,认为李光地的格物论与王艮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最后,文章指出李光地对于格物致知问题的看法与朱熹的观点存在一定的抵牾,反映了其在心学思想上的吸收与借鉴。整体来说,本文重点介绍了李光地在格物致知问题上的独特见解,以及他与朱熹、王艮等思想家在此问题上的关系和差异。 |
| 关键词: | 格物致知 朱子学 知性明善 |
内容
格物致知论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与基础性理论,既是李光地理学思想中富有特色与创造性的一个部分,亦是其融摄陆王之学的主要方面与典型表现之一。对于各家各派的格致论,李光地虽然多次表示“格物之说……自然是程朱说得确实”②,“自宋以来,格物之说纷然。……程朱之说至矣”③,“程朱以格物为穷理,当矣”④,并强调自己关于格物致知的理解与朱熹并无本质区别,但只要考察其格致论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李光地在朱子理学基础上对于陆王格致论的融摄是深刻且多方面的。
从表面上看,李光地格致论与朱熹格致论之间最明显的一点差异在于,朱熹主要以即物穷理言格致,而李光地则偏重于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李光地的这种理解显然受到了陆王心学的影响,表现出一种折中程朱、陆王的思想意图。他说:
陆象山《答赵咏道书》,引《大学》从“物有本末”起,至“格物”止,引得极精。两“物”字便是一个,把物之本末,事之终始讲究明白,便知所先后。未有知本末终始,而尚倒置从事者。知所先后,便有下手处,岂不近道。故下便接先后说去。……知所先后,即知本,知本,便是知之至。①
格物之说,至程朱而精,然“物有本末”一节,即是引起此意。物,事即物也;本末终始,即物中之理也。格之,则知所先后,而自诚意一下,一以贯之矣。象山陆子看得融洽,未可以同异忽之。②
《大学》古文曰“物有本末”,即物也;“知所先后”,即格也;“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即物有本末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即知所先后,物格而后知至也。象山陆氏引“物有本末”至“致知格物”为一意,以证为学讲明先于践履之事,其指固如此。陆谭经诚非朱伦,独此一义,愚窃以为甚精。③
虽然,程子之说,则真圣门穷理之要矣,而施之《大学》,则文意犹隔。盖《大学》所谓格物者,知本而已。物有本末,而贵乎格之而知其本。……象山陆氏之言曰:“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讲明也;修身正心,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又曰:“学问固无穷止,然端绪得失则当早辩,是非向背可以立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其端绪知之不至,悉精毕力求多于末,沟浍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终,本末俱失。”愚谓陆子之意,盖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后,连格物致知以成文,其于古人之旨既合,而警学之理尤极深切,视之诸家,似乎最优,未可以平日议论异于朱子而忽之也。就诸家中,则龟山之说独为浑全。盖虽稍失《大学》浅近示人之意,而实圣门一贯之传也。①
考之《大学》本文,其中并无“穷理”之说,程朱将“格物”解释为“穷理”,显系一种发挥创造。李光地认为,程朱以穷理言格物固然大体不差,但却未能突出格物工夫的核心与关键,故与《大学》文意犹隔。若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节来解释格物之义,则直截了当,无须假借,既符合圣人之旨,又可收警示学者之效。他进一步指出,物即事,本末始终即物中之理,所以格物穷理就是要知其本末始终。只要将事物的本末始终讲究明白,便可知所先后,使言行有所准则,从而避免在实践活动中犯错。知所先后亦即是知本。若能知本,便是达到了知至的境界。在此意义上,李光地表彰了陆九渊将“格物致知”与“知所先后”沟通融合的说法,认为其说“视之诸家,似乎最优”。
此外,李光地还附带肯定了杨时的格物说,认为其说虽有失浅近,但于诸家中“独为浑全”,“实圣门一贯之传”。按照李光地的理解,杨时格物论的要点在于“天下之物不可胜穷也,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反身而诚,则天地万物之理在我”,并引朱熹之言赞曰:“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卓其绪,龟山是承。”②但在事实上,杨时主张的这种“反身而诚”的格物论因与心学将格物理解为格心的基本思路相似,恰恰受到了朱熹的明确反对与批评。朱熹指出:“惟杨氏反身之说为未安耳。盖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于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①李光地既然表彰陆九渊与杨时的格物论,便不能不与朱熹之说有所抵牾,这正反映出其在格物致知问题上对于心学思想的吸收与借鉴。
关于事物的“本末始终”,李光地进一步解释道:
心身、家国、天下,是物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事也。本,即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始,即齐家,《书》曰:“始于家邦,终于四海。”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②
何谓知至?知本之谓也。盖家国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虽庶人亦有家,本乱则末乱,厚者薄则无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谓知本,能知乎此之谓知之至也。③
物有本末,而贵乎格之而知其本。末者,天下国家也;本者,身也。知天下国家不外于吾身之谓知本,知本则能务本矣。此古人言学之要,《大学》之首章,《学记》之卒章,其致一也。④
李光地的这种以身为本,以天下国家为末,认为天下国家不外于吾身的格物思想显然与泰州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存在相通之处。在对格物问题的理解上,王艮同样以“格物”之“物”为“物有本末”之“物”,认为格物就是要知本,知本就是知之至。他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以下数句,是释“格物致知”之义。“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即继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①
“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后“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至“此谓知之至也”一节,乃是释“格物致知”之义。②
严格说来,陆九渊只是将“物有本末”一节与“格物致知”合说,以此论证讲明先于践履,又以“物有本末”一节说明应当早辨端绪得失,先立乎其大者,并未直接以知本、知所先后来解释格物。而王艮则明确提出应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至“此谓知之至也”一节来解释“格物致知”之义,“格物”之“物”即是“物有本末”之“物”,故物格而后知本,知本即知之至。
关于“物有本末”与“格物”的具体含义,王艮进一步说道:
“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挈矩是“格”也。③
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挈度也,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④
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知身之为本,是以“明明德”而“亲民”也。①
《大学》曰“物有本末”,是吾身为天地万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后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②
在王艮看来,“格”即挈度、挈矩之义,“物”即身与天下国家。从万物一体的观点来看,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身与天下国家亦为一物,但其中又有本末先后的差别。身即是本,天下国家即是末。因此,格物首先不是某种具体的认识或修养工夫,而是一种“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所先后的见解与识度,即通过“比则推度”来确定事物之间的本末、主次关系。格物的目的就是要确认“身”作为“天下国家”之本的地位与价值,进而通过反己修身、正身的方法来正天下国家。
同时,王艮还由“以身为本”的格物论引申出尊身、安身、爱身、保身的思想。在他看来,个体的存在与生命是最根本的,甚至拥有与“道”同等的地位。“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③因此,安身和保身便成为良知良能的基本意义,无间于凡圣,具有最高的价值。只有安身、保身,才能成己成物,治平天下。“‘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身未安,本不立也。……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④“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①由此亦可看出,王艮虽提倡明哲保身,但并未将其导向一种极端利己主义,而是根据其“本末一物”的“淮南格物论”,始终将“本”与“末”、“身”与“天下国家”联系在一起,试图以个体存在为标准与尺度,去重新塑造一套合理的天下秩序。
阳明之后,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可谓王门中最具特色的格物学说之一。赵贞吉曾说:“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车两轮,实贯一毂。后有作者,来登此车,无以未觉,而空著书”②,将王艮的“淮南格物”与阳明的良知学说相提并论,共同作为王学的思想基础,可见其在当时思想界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后世学者对“淮南格物论”的评价则褒贬不一。一些学者对其颇为不满,批评王艮“别立说以为教,苟非门户之私,则亦未免意见之殊耳”③,但也有不少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其深得《大学》之旨,甚至将其视作王艮最重要的理论创造。譬如,虽对王学左派多有批评的刘宗周就曾称赞道:“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曰:‘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④而全祖望亦云:“七十二家格物之说,令末学穷老绝气不能尽举其异同。至于以‘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说最明了。盖物有本末,先其本,则不逐其末,后其末,则亦不遗其末,可谓尽善之说”,“心斋是说,乃其自得之言。……盖语物而返身,至于心、意、知,即身而推,至于家国天下,更何一物之遗者?而况先格其本,后格其末,则自无驰心荒远,与夫一切玩物丧志之病。……故心斋论学,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则最不可易。”⑤以李光地学识之广博,不可能不了解王艮的“淮南格物论”。由此可以推断,李光地以“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以“知本”“知所先后”言格物的格物论很有可能受到了王艮“淮南格物论”的启发与影响。李光地虽未特别讨论有关安身、保身的问题,但亦不反对明哲保身的思想。他还有意将明哲保身与人的道德本性联系起来,主张“明哲保身,道之用也”①,并为遭受误解的“明哲保身”正名、辩护,提出《诗经》“‘既明且哲’四句,承‘王躬是保’。自己不能保身,焉能保王躬?‘明哲保身’,非如世俗所谓趋利避害也。《孝经》言守富、守贵、保禄位,都说与道德学问是一事,何况保身?”②
诚然,由于双方在思想基础与理论背景上的差异,李光地的格物论与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在细节上仍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不能将其简单地等而视之。特别是李光地并未如王艮那样,由格物知本引申出对于个体存在的生命价值与意志作用的极度高扬,而是强调:“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犹人之性,人之性犹我之性,知其性善之同而尽之之本在我,此所以为知性明善也,此所以为知本也”③,从而将格物的重心转移到知性明善上。从这一点来看,李光地的格物论显然更接近传统理学的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李光地将格物理解为知本、知性明善,并不必然与朱熹所说的即物穷理相冲突。因为二者所指涉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主要说的是格物的目的,而后者则偏重于格物的方法。事实上,朱熹亦以知性明善为格物穷理的根本目的,而李光地也未否认即物穷理的作用与意义,仍将其作为格物的一项基本方法。李光地格物论与朱熹格物论的关键区别在于,朱熹在主张通过格物把握道德原则、提高道德修养的同时,亦注重研究各类具体事物的性质、规律,并将穷究物理作为知性明善的重要前提与基础;而李光地由于受到笼罩明代思想界的心学尤其是王学思潮迅速发展所导致的理学内向化的刺激与影响,在格致论上更加明确和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忽视和抑制了其对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
在朱熹看来,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①,因而格物穷理的范围与对象是极其广泛的。“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②这明显展现出朱熹格物论的知识取向,及其对于人的认识能力的乐观与自信态度。但是,过于强调知识的讲求,而又缺乏具体、可行的研究物理的方法,往往使学者流于训诂讲说一途而忽略了身心的修养,迷失了对于德性的根本追求。这一弊端在明代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与忧虑。如阳明即云:“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③而李光地同样意识到,朱熹在知识研究上的这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知识与道理是无穷的,而个人的时间、精力与能力等条件都有限,要想做到物无不格、理无不穷、知无不尽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自然事物之理与人的道德法则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穷理求知的过程并不必然会与人的道德修养发生直接关系。即便能够穷尽自然事物之理,读遍古今之书,亦难以直接、自发地实现知性明善的根本目的。因此,李光地特别突出格物穷理的伦理意涵,反复强调朱熹格物论“原以身心性情居首,并非教人于没要紧处用心”④,又谓朱熹《中庸章句》“注云:‘物之所以自成。’‘物’是君臣父子之类,即是‘道’字,莫认做万物之物。……‘物之终始’‘物’字亦然”⑤,从而将格物的主要对象限定在与道德性命有关的方面,而将与此无关的各种具体知识排除在格物的范围之外。
朱熹以“至”训“格”,“至”有“极至”之意,故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①李光地虽然接受朱熹训“格”为“至”的解释,但又特别指出:
极,如“皇极”“太极”之极,是中间透顶处,不是四旁到边处。“极”字,亦有作边际训者,如“四极”“八极”之类,但非此注“极”字之义。②
朱子说“极”字,即是“本”字,一物皆有一物之极,即此一物之原本。今人说“极”字,像四面都到的一般,非也。③
结合朱熹格物论的具体论述来看,朱熹所说的“极”字显然是兼括极点与边际两义的。但李光地仅取极点之义,而排斥边际之义,便是为了否定格物须格尽天下之物的观点,从而突出其以知本言格物的思想。在李光地看来,“极”即是“本”,穷极事物之理就是知本,而这个“本”便是人之善性。所以他说:
《语类》中,“穷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一段,说格物甚精。王阳明因格竹子致病,遂疑朱子之说,岂知朱子原未尝教人于没要紧处枉用心思也。人与物本同一性,禽兽真心发现处,与人一样。或止一节,比人更专笃,这个是万物一源的,所谓本也。子思、孟子不说格物,而曰明善,曰知性,正是《大学》知本之意。说到性与善,则程朱之说愈显然明白,而包括无余矣。④朱熹诚然说过“说穷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无别物事”⑤,但这主要是为了说明仁义礼智为理之根源,以及格物穷理应从切己处下手,并非朱熹格物论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相反,即物穷理才是朱熹格物论的真正重点所在。而李光地偏偏要从皇皇的《朱子语类》中挑出这句话来表彰,正是为了强调在自家身上知性明善的意义。当然,“在自家身上求之”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格心、正心,但起码与心学的内向格物说拥有较多的相似性。在李光地看来,万物一源,同出于善,人与物本同一性,所以只要能于身心性情之德上穷本极源,则人伦日用、天地鬼神、禽兽草木之理皆不外乎是。
同时,朱熹还很强调积累与贯通在格物致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朱熹认为,只要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工夫,用力既久,自然有豁然贯通处,最终可以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对此,李光地亦有不同看法:
学问全要知本,知本之学,所学皆归于一本。格物之说……自然是程朱说得确实,但细思之,亦有未尽。如云格物也,不是物物都要格尽,也不是格一物便知天下之物。积累多时,自有贯通处。这个说话,便似子夏之答子游。子游讥门人小子,“本之则无”,子夏只应答以洒扫、应对、进退,正是培养他根本处。人之初生,天性未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使之入孝出弟,一切谨愿。后来盛德大业,都从此出,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子夏却说成君子之道,毕竟先末而后本。子游、子夏都将本字看得太高妙。即如“一贯”章,都说零碎工夫尽做到了,只不晓得本源,故经夫子点化,便洞然无疑。若其初不晓得本源,日用之间如何用功?果然如此,多学而识正是用功处,夫子何以截断曰“非也”?特其初要将一去贯,终乃贯于一耳。以此起头,以此煞尾,圣贤学问都是如此。离了本便无末,但不可云只要本不须末耳。①
在他看来,日常的积累之功固不可少,但格物最重要的不是积累,而是知本。若不知本,则一切具体的工夫都无根基。这个“本”并不高妙,即人人固有之善性,亦即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一”。儒者为学既以知本为根基,最后又回复到本源上,始终都要以“本”来贯穿,不是仅仅通过今日格、明日格的零碎积累便可自发达到贯通的结果。
至于即物穷理的内容与作用,李光地还说道:“程朱以格物为穷理,当矣,然亦须就要紧处格将去。如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人伦中平庸无奇,何可思索?不知就上须大段与他思索一番,方得透彻。子孝臣忠,如何方是孝,如何方是忠,大有事在。物物各有一性,性即理也,物性犹吾性也。物各有牝牡雌雄,是其夫妇之性。海燕哺雏,雌雄代至,饮食之恩也;羽毛稍长,引雏习飞,教诲之义也,是其母子之性。同巢鸟兽,无不相倡相和,是其兄弟之性。类聚群分,是其朋友之性。就中必有为之雄长者,是其君臣之性。盖物虽殊,而性则一。此处穷尽,便见得万物一体,廓然有民胞物与之意。而所谓生之有道,取之有节,此心自不容已。至如草木臭味,种种各别,此则医家之所宜悉,而非儒者急务。……《大学》所谓格物,《中庸》又谓之明善,《孟子》又谓之知性。盖格物只是明个善,明善只是知个性。”①由此可见,李光地所理解的即物穷理的主要内容仍是思索、认识事物中包含的伦理原则与道德属性,以此来发现、印证人自身固有的善性,进而领悟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之意,并使自己的行为自觉符合天理、天性的要求。在李光地看来,这样的即物穷理才是知本的重要方式。
从表面上看,李光地格致论与朱熹格致论之间最明显的一点差异在于,朱熹主要以即物穷理言格致,而李光地则偏重于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李光地的这种理解显然受到了陆王心学的影响,表现出一种折中程朱、陆王的思想意图。他说:
陆象山《答赵咏道书》,引《大学》从“物有本末”起,至“格物”止,引得极精。两“物”字便是一个,把物之本末,事之终始讲究明白,便知所先后。未有知本末终始,而尚倒置从事者。知所先后,便有下手处,岂不近道。故下便接先后说去。……知所先后,即知本,知本,便是知之至。①
格物之说,至程朱而精,然“物有本末”一节,即是引起此意。物,事即物也;本末终始,即物中之理也。格之,则知所先后,而自诚意一下,一以贯之矣。象山陆子看得融洽,未可以同异忽之。②
《大学》古文曰“物有本末”,即物也;“知所先后”,即格也;“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即物有本末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即知所先后,物格而后知至也。象山陆氏引“物有本末”至“致知格物”为一意,以证为学讲明先于践履之事,其指固如此。陆谭经诚非朱伦,独此一义,愚窃以为甚精。③
虽然,程子之说,则真圣门穷理之要矣,而施之《大学》,则文意犹隔。盖《大学》所谓格物者,知本而已。物有本末,而贵乎格之而知其本。……象山陆氏之言曰:“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讲明也;修身正心,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又曰:“学问固无穷止,然端绪得失则当早辩,是非向背可以立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其端绪知之不至,悉精毕力求多于末,沟浍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终,本末俱失。”愚谓陆子之意,盖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后,连格物致知以成文,其于古人之旨既合,而警学之理尤极深切,视之诸家,似乎最优,未可以平日议论异于朱子而忽之也。就诸家中,则龟山之说独为浑全。盖虽稍失《大学》浅近示人之意,而实圣门一贯之传也。①
考之《大学》本文,其中并无“穷理”之说,程朱将“格物”解释为“穷理”,显系一种发挥创造。李光地认为,程朱以穷理言格物固然大体不差,但却未能突出格物工夫的核心与关键,故与《大学》文意犹隔。若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节来解释格物之义,则直截了当,无须假借,既符合圣人之旨,又可收警示学者之效。他进一步指出,物即事,本末始终即物中之理,所以格物穷理就是要知其本末始终。只要将事物的本末始终讲究明白,便可知所先后,使言行有所准则,从而避免在实践活动中犯错。知所先后亦即是知本。若能知本,便是达到了知至的境界。在此意义上,李光地表彰了陆九渊将“格物致知”与“知所先后”沟通融合的说法,认为其说“视之诸家,似乎最优”。
此外,李光地还附带肯定了杨时的格物说,认为其说虽有失浅近,但于诸家中“独为浑全”,“实圣门一贯之传”。按照李光地的理解,杨时格物论的要点在于“天下之物不可胜穷也,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反身而诚,则天地万物之理在我”,并引朱熹之言赞曰:“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卓其绪,龟山是承。”②但在事实上,杨时主张的这种“反身而诚”的格物论因与心学将格物理解为格心的基本思路相似,恰恰受到了朱熹的明确反对与批评。朱熹指出:“惟杨氏反身之说为未安耳。盖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于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①李光地既然表彰陆九渊与杨时的格物论,便不能不与朱熹之说有所抵牾,这正反映出其在格物致知问题上对于心学思想的吸收与借鉴。
关于事物的“本末始终”,李光地进一步解释道:
心身、家国、天下,是物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事也。本,即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始,即齐家,《书》曰:“始于家邦,终于四海。”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②
何谓知至?知本之谓也。盖家国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虽庶人亦有家,本乱则末乱,厚者薄则无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谓知本,能知乎此之谓知之至也。③
物有本末,而贵乎格之而知其本。末者,天下国家也;本者,身也。知天下国家不外于吾身之谓知本,知本则能务本矣。此古人言学之要,《大学》之首章,《学记》之卒章,其致一也。④
李光地的这种以身为本,以天下国家为末,认为天下国家不外于吾身的格物思想显然与泰州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存在相通之处。在对格物问题的理解上,王艮同样以“格物”之“物”为“物有本末”之“物”,认为格物就是要知本,知本就是知之至。他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以下数句,是释“格物致知”之义。“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即继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①
“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后“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至“此谓知之至也”一节,乃是释“格物致知”之义。②
严格说来,陆九渊只是将“物有本末”一节与“格物致知”合说,以此论证讲明先于践履,又以“物有本末”一节说明应当早辨端绪得失,先立乎其大者,并未直接以知本、知所先后来解释格物。而王艮则明确提出应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至“此谓知之至也”一节来解释“格物致知”之义,“格物”之“物”即是“物有本末”之“物”,故物格而后知本,知本即知之至。
关于“物有本末”与“格物”的具体含义,王艮进一步说道:
“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挈矩是“格”也。③
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挈度也,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④
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知身之为本,是以“明明德”而“亲民”也。①
《大学》曰“物有本末”,是吾身为天地万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后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②
在王艮看来,“格”即挈度、挈矩之义,“物”即身与天下国家。从万物一体的观点来看,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身与天下国家亦为一物,但其中又有本末先后的差别。身即是本,天下国家即是末。因此,格物首先不是某种具体的认识或修养工夫,而是一种“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所先后的见解与识度,即通过“比则推度”来确定事物之间的本末、主次关系。格物的目的就是要确认“身”作为“天下国家”之本的地位与价值,进而通过反己修身、正身的方法来正天下国家。
同时,王艮还由“以身为本”的格物论引申出尊身、安身、爱身、保身的思想。在他看来,个体的存在与生命是最根本的,甚至拥有与“道”同等的地位。“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③因此,安身和保身便成为良知良能的基本意义,无间于凡圣,具有最高的价值。只有安身、保身,才能成己成物,治平天下。“‘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身未安,本不立也。……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④“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①由此亦可看出,王艮虽提倡明哲保身,但并未将其导向一种极端利己主义,而是根据其“本末一物”的“淮南格物论”,始终将“本”与“末”、“身”与“天下国家”联系在一起,试图以个体存在为标准与尺度,去重新塑造一套合理的天下秩序。
阳明之后,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可谓王门中最具特色的格物学说之一。赵贞吉曾说:“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车两轮,实贯一毂。后有作者,来登此车,无以未觉,而空著书”②,将王艮的“淮南格物”与阳明的良知学说相提并论,共同作为王学的思想基础,可见其在当时思想界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后世学者对“淮南格物论”的评价则褒贬不一。一些学者对其颇为不满,批评王艮“别立说以为教,苟非门户之私,则亦未免意见之殊耳”③,但也有不少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其深得《大学》之旨,甚至将其视作王艮最重要的理论创造。譬如,虽对王学左派多有批评的刘宗周就曾称赞道:“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曰:‘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④而全祖望亦云:“七十二家格物之说,令末学穷老绝气不能尽举其异同。至于以‘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说最明了。盖物有本末,先其本,则不逐其末,后其末,则亦不遗其末,可谓尽善之说”,“心斋是说,乃其自得之言。……盖语物而返身,至于心、意、知,即身而推,至于家国天下,更何一物之遗者?而况先格其本,后格其末,则自无驰心荒远,与夫一切玩物丧志之病。……故心斋论学,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则最不可易。”⑤以李光地学识之广博,不可能不了解王艮的“淮南格物论”。由此可以推断,李光地以“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以“知本”“知所先后”言格物的格物论很有可能受到了王艮“淮南格物论”的启发与影响。李光地虽未特别讨论有关安身、保身的问题,但亦不反对明哲保身的思想。他还有意将明哲保身与人的道德本性联系起来,主张“明哲保身,道之用也”①,并为遭受误解的“明哲保身”正名、辩护,提出《诗经》“‘既明且哲’四句,承‘王躬是保’。自己不能保身,焉能保王躬?‘明哲保身’,非如世俗所谓趋利避害也。《孝经》言守富、守贵、保禄位,都说与道德学问是一事,何况保身?”②
诚然,由于双方在思想基础与理论背景上的差异,李光地的格物论与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在细节上仍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不能将其简单地等而视之。特别是李光地并未如王艮那样,由格物知本引申出对于个体存在的生命价值与意志作用的极度高扬,而是强调:“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犹人之性,人之性犹我之性,知其性善之同而尽之之本在我,此所以为知性明善也,此所以为知本也”③,从而将格物的重心转移到知性明善上。从这一点来看,李光地的格物论显然更接近传统理学的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李光地将格物理解为知本、知性明善,并不必然与朱熹所说的即物穷理相冲突。因为二者所指涉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主要说的是格物的目的,而后者则偏重于格物的方法。事实上,朱熹亦以知性明善为格物穷理的根本目的,而李光地也未否认即物穷理的作用与意义,仍将其作为格物的一项基本方法。李光地格物论与朱熹格物论的关键区别在于,朱熹在主张通过格物把握道德原则、提高道德修养的同时,亦注重研究各类具体事物的性质、规律,并将穷究物理作为知性明善的重要前提与基础;而李光地由于受到笼罩明代思想界的心学尤其是王学思潮迅速发展所导致的理学内向化的刺激与影响,在格致论上更加明确和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忽视和抑制了其对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
在朱熹看来,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①,因而格物穷理的范围与对象是极其广泛的。“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②这明显展现出朱熹格物论的知识取向,及其对于人的认识能力的乐观与自信态度。但是,过于强调知识的讲求,而又缺乏具体、可行的研究物理的方法,往往使学者流于训诂讲说一途而忽略了身心的修养,迷失了对于德性的根本追求。这一弊端在明代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与忧虑。如阳明即云:“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③而李光地同样意识到,朱熹在知识研究上的这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知识与道理是无穷的,而个人的时间、精力与能力等条件都有限,要想做到物无不格、理无不穷、知无不尽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自然事物之理与人的道德法则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穷理求知的过程并不必然会与人的道德修养发生直接关系。即便能够穷尽自然事物之理,读遍古今之书,亦难以直接、自发地实现知性明善的根本目的。因此,李光地特别突出格物穷理的伦理意涵,反复强调朱熹格物论“原以身心性情居首,并非教人于没要紧处用心”④,又谓朱熹《中庸章句》“注云:‘物之所以自成。’‘物’是君臣父子之类,即是‘道’字,莫认做万物之物。……‘物之终始’‘物’字亦然”⑤,从而将格物的主要对象限定在与道德性命有关的方面,而将与此无关的各种具体知识排除在格物的范围之外。
朱熹以“至”训“格”,“至”有“极至”之意,故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①李光地虽然接受朱熹训“格”为“至”的解释,但又特别指出:
极,如“皇极”“太极”之极,是中间透顶处,不是四旁到边处。“极”字,亦有作边际训者,如“四极”“八极”之类,但非此注“极”字之义。②
朱子说“极”字,即是“本”字,一物皆有一物之极,即此一物之原本。今人说“极”字,像四面都到的一般,非也。③
结合朱熹格物论的具体论述来看,朱熹所说的“极”字显然是兼括极点与边际两义的。但李光地仅取极点之义,而排斥边际之义,便是为了否定格物须格尽天下之物的观点,从而突出其以知本言格物的思想。在李光地看来,“极”即是“本”,穷极事物之理就是知本,而这个“本”便是人之善性。所以他说:
《语类》中,“穷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一段,说格物甚精。王阳明因格竹子致病,遂疑朱子之说,岂知朱子原未尝教人于没要紧处枉用心思也。人与物本同一性,禽兽真心发现处,与人一样。或止一节,比人更专笃,这个是万物一源的,所谓本也。子思、孟子不说格物,而曰明善,曰知性,正是《大学》知本之意。说到性与善,则程朱之说愈显然明白,而包括无余矣。④朱熹诚然说过“说穷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无别物事”⑤,但这主要是为了说明仁义礼智为理之根源,以及格物穷理应从切己处下手,并非朱熹格物论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相反,即物穷理才是朱熹格物论的真正重点所在。而李光地偏偏要从皇皇的《朱子语类》中挑出这句话来表彰,正是为了强调在自家身上知性明善的意义。当然,“在自家身上求之”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格心、正心,但起码与心学的内向格物说拥有较多的相似性。在李光地看来,万物一源,同出于善,人与物本同一性,所以只要能于身心性情之德上穷本极源,则人伦日用、天地鬼神、禽兽草木之理皆不外乎是。
同时,朱熹还很强调积累与贯通在格物致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朱熹认为,只要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工夫,用力既久,自然有豁然贯通处,最终可以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对此,李光地亦有不同看法:
学问全要知本,知本之学,所学皆归于一本。格物之说……自然是程朱说得确实,但细思之,亦有未尽。如云格物也,不是物物都要格尽,也不是格一物便知天下之物。积累多时,自有贯通处。这个说话,便似子夏之答子游。子游讥门人小子,“本之则无”,子夏只应答以洒扫、应对、进退,正是培养他根本处。人之初生,天性未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使之入孝出弟,一切谨愿。后来盛德大业,都从此出,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子夏却说成君子之道,毕竟先末而后本。子游、子夏都将本字看得太高妙。即如“一贯”章,都说零碎工夫尽做到了,只不晓得本源,故经夫子点化,便洞然无疑。若其初不晓得本源,日用之间如何用功?果然如此,多学而识正是用功处,夫子何以截断曰“非也”?特其初要将一去贯,终乃贯于一耳。以此起头,以此煞尾,圣贤学问都是如此。离了本便无末,但不可云只要本不须末耳。①
在他看来,日常的积累之功固不可少,但格物最重要的不是积累,而是知本。若不知本,则一切具体的工夫都无根基。这个“本”并不高妙,即人人固有之善性,亦即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一”。儒者为学既以知本为根基,最后又回复到本源上,始终都要以“本”来贯穿,不是仅仅通过今日格、明日格的零碎积累便可自发达到贯通的结果。
至于即物穷理的内容与作用,李光地还说道:“程朱以格物为穷理,当矣,然亦须就要紧处格将去。如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人伦中平庸无奇,何可思索?不知就上须大段与他思索一番,方得透彻。子孝臣忠,如何方是孝,如何方是忠,大有事在。物物各有一性,性即理也,物性犹吾性也。物各有牝牡雌雄,是其夫妇之性。海燕哺雏,雌雄代至,饮食之恩也;羽毛稍长,引雏习飞,教诲之义也,是其母子之性。同巢鸟兽,无不相倡相和,是其兄弟之性。类聚群分,是其朋友之性。就中必有为之雄长者,是其君臣之性。盖物虽殊,而性则一。此处穷尽,便见得万物一体,廓然有民胞物与之意。而所谓生之有道,取之有节,此心自不容已。至如草木臭味,种种各别,此则医家之所宜悉,而非儒者急务。……《大学》所谓格物,《中庸》又谓之明善,《孟子》又谓之知性。盖格物只是明个善,明善只是知个性。”①由此可见,李光地所理解的即物穷理的主要内容仍是思索、认识事物中包含的伦理原则与道德属性,以此来发现、印证人自身固有的善性,进而领悟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之意,并使自己的行为自觉符合天理、天性的要求。在李光地看来,这样的即物穷理才是知本的重要方式。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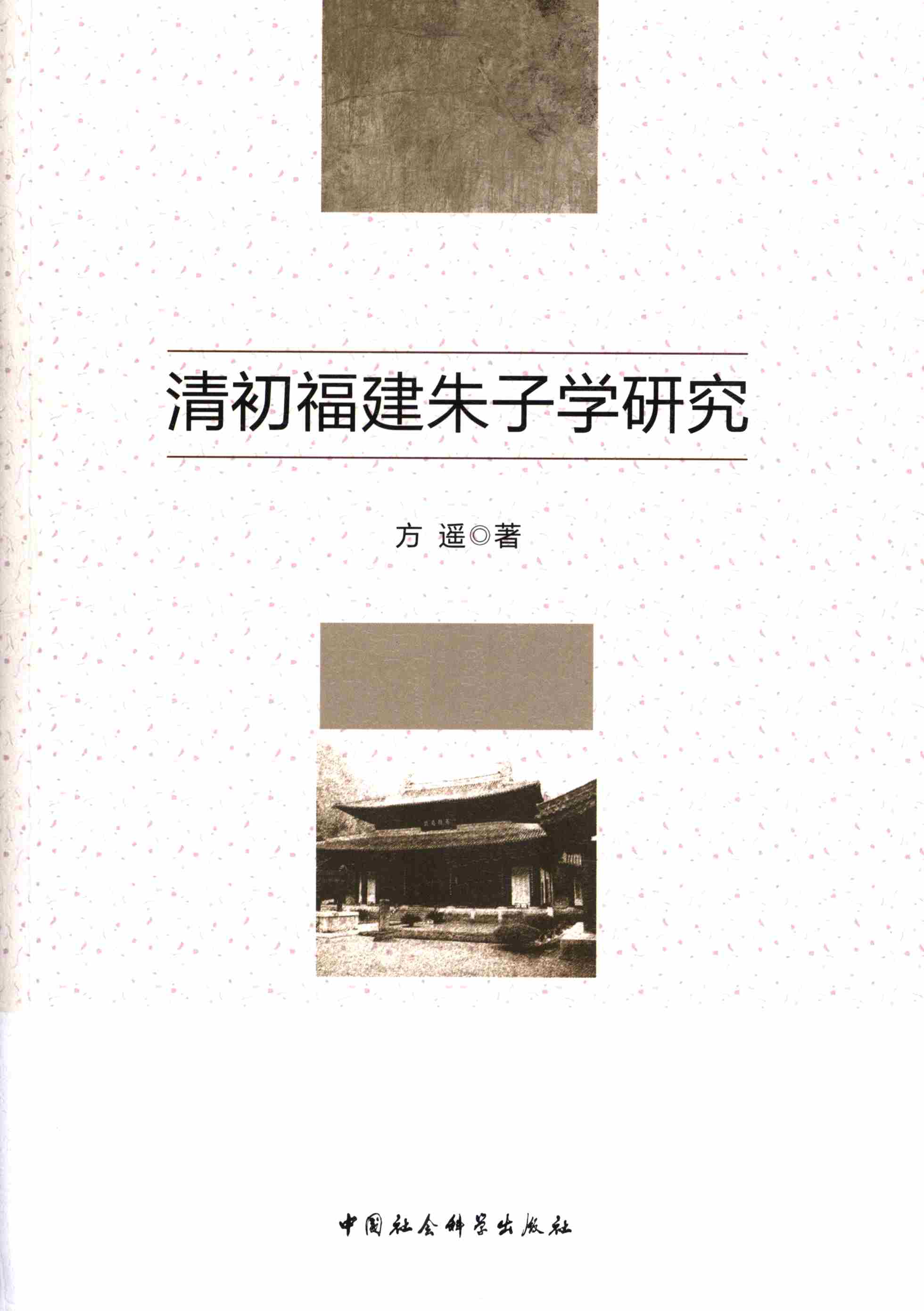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