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性即理”与“心即理”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58 |
| 颗粒名称: | 一 “性即理”与“心即理”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34 |
| 页码: | 88-122 |
| 摘要: | 本文主要介绍了清初福建朱子学对王学的纠驳。在朱子学者对王学的批判中,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是"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差异。朱熹认为,人性即是天理的体现,人所受之天命即为性之本体。他强调性善的根源在于天道的纯善,而人的真性表现为仁义礼智的本性。他将心理解为知觉,认为心具有知觉的能力,以及对事物的主宰作用。朱熹强调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认为心所具有的理即是性的体现。总的来说,朱熹的观点是,性即是理,本然之性即是天理的体现,而心则是具有知觉和主宰作用的能力。 |
| 关键词: | 朱子学 宋明理学 宇宙观 |
内容
众所周知,心性论作为宋明理学中最受关注、最具特色亦最富成果的理论议题之一,构成了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与基石。李泽厚即提出宋明理学的主题在于“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不是宇宙观、认识论而是人性论才是宋明理学的体系核心”。⑤心性论作为传统儒家内圣之学的重要内容,其发端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在秦汉之后却相对衰落,长期沉寂,直接导致了儒学在思想领域中的权威与影响力渐为释、道二教所侵夺,甚至威胁到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理学家通过吸收、借鉴释、道二教中有益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模式,重新发掘、阐释先秦儒家经典中可与之对应的思想内容,使得儒家的心性理论在两宋时期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发展与飞跃,重塑了儒学的面貌与内涵,成功回应了释、道二教的挑战,从而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由于心性论之于宋明理学的重要意义,朱子学与陆学或王学之间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差异和争论,也就不只是简单的一字之差或对个别概念的不同理解,而是突出地代表了两家思想在心性论领域的整体差异,从而构成了“朱陆之辨”或“朱王之辨”的要点之一。
在宋代之前,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一种性一元论,往往难以圆融地解释人性中善恶混杂所造成的种种复杂问题。而其他各种性无善恶论、性善恶混论等理论,或流于浅显粗糙,难以自圆其说,或不合于儒家主流伦理观念,都不能令学者普遍满足和信服。至北宋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二元论的理论倾向,主张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天地之性亦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人若是希望为善去恶、成圣成贤,就必须通过学习、修养等方法变化气质,以回复本然的天地之性。这种人性论肇始于周、张、二程等北宋理学家,直到南宋朱熹处方才发展到完善与成熟的阶段。
朱熹认为,世界由理和气构成,人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即“天命之性”,又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而“天命之性”落入气质形体中便有了“气质之性”,故极称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①之语,主张论性与论气兼备。他说:
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①
须是合性与气观之然后尽。②
由于理与气不离不杂,所以天命与气质亦是不离不杂的关系。一方面,“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③;另一方面,“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相夹杂”④。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说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非平行并立的两种性。前者作为后者的本体与根据,存在于后者中。故曰:“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性即太极之全体。但论气质之性,则此全体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⑤
在现实世界中,理必须安顿在一定的形气之中才能成为人性,故而一切现实的人性皆非性之本体,而是气质之性。“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也。”⑥因此,朱熹亦将人性中先天具有的恶的因素归因于气质。天命之性来源于天理,自然是纯善无恶的,而气质则有清浊昏明之不齐。天命之性经过气质的熏染、障蔽,所呈现出来的现实的人性,即气质之性,便是有善有恶的。所以朱熹说: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①
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②
以上即为朱熹人性论思想之大概。由此可知,朱熹所说的“性即理”之“性”并非具体、现实的人性,而只能是天命之性,亦即性之本体。所以“性即理”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便是性之本体是理,本然之性是理。程颐尝言:“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③此语极为朱熹所赞赏,以为“如‘性即理也’一语,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④,“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⑤。
为了进一步说明性善的根源,朱熹发挥《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想,指出: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⑥
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⑦
这就是说,理在天地间只是一个总的道理,为人所禀则表现为仁义礼智之本性。如果说程颐所说的“性即理”主要还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人性的本质内容与天理相互符合,那么朱熹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的本性与天理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从而将宇宙论与人性论贯穿起来。所以钱穆说:“伊川性即理也之语,主要在发挥孟子性善义,只就人生界立论,而朱子则用来上通之于宇宙界。亦可谓朱子乃就其自所创立有关宇宙界之理气论而来阐申伊川此语之义。”①
而“心”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意义之一便是知觉。朱熹认为,性属未发,故不能知觉,心含已发,方能知觉。故曰:
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便是那知觉底。②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运用处,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③
由于人心具有十分伟大的认识、思维能力,所以朱熹常常称赞心的虚灵与神妙:
此心至灵,细入豪芒纤芥之间,便知便觉,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到那里;下而方来又不知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也到那里。这个神明不测,至虚至灵,是甚次第。④与心的知觉能力相关联的便是心的主宰作用。所谓“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①。朱熹提出:
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②
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至动时方有主宰也。③
这就是说,心是人身唯一的主宰,不论语默动静,人的言语、行动、情感、思维等一切行为都受到心的控制与支配,并对知觉到的事物做出适当的反应,从而体现出高度的能动性。但是,由于朱熹在论述心的主宰作用时间或使用“命万物”“宰万物”等说法,便有学者据此认为朱熹所说的心就是万物的本体或万物的主宰者。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解,陈来先生已辨之。因为朱熹“心为主宰的思想主要是把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来考察心在个体实践活动中的作用”④,所以心并不能直接主宰万物,而是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支配来实现“命万物”与“宰万物”。
对于心与性的关系,朱熹强调“心具众理”⑤,这个“理”便是人的本性,亦即人先天内在的道德本质。故曰:
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虚,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⑥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①
可以说,心以性作为其内容与依据,性则通过心的知觉与主宰作用将自己表现出来。“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②
此外,朱熹极称张载“心统性情”之说,亦经常以“心统性情”的模式来分析心性关系。诚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在朱熹那里,“心统性情”这一命题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心兼赅性、情:
“心统性情”,统,犹兼也。③
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④
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⑤
朱熹认为,性静情动,性是心之体,是心所得于天的原理,情是心之用,是心感于物而发的功用,而心则是兼赅动静体用的知觉意识活动的总体。“心统性情”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心主宰性、情:
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统是主宰,如统百万军。⑥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①
在朱熹看来,心不仅兼赅性情,而且统率、管摄性情。心不仅需要在已发的状态下以理智和德性主导、宰制各种情感、欲望、念虑,还需要在未发之时主敬涵养、提撕警觉,使心处于平静、中和的状态,以此保证性对意识活动的支配作用不受干扰。故曰:“未发而知觉不昧者,岂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发而品节不差者,岂非心之主乎情者乎?”②
与通过天命与气质的划分来解释人性中善恶的来源这一方式类似,朱熹亦将心区别为“道心”与“人心”,以此来解释心所表现出来的善恶邪正。朱熹提出:
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
心者……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④
由此可见,道心根源于天理,是纯善的,亦是隐微难明的,而人心则来源于情欲与气质,是可善可恶的,若缺乏主宰、制约则极易流为不善。他进一步指出: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①
换言之,人只有一个心,所谓的道心、人心并不是真的有两个心存在,只是心的两个不同方面或两种思想内容而已。故曰:
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②
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非有两个心,道心、人心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③
在朱熹看来,由于人皆具有本性与形体,本性表现为道德意识,形体产生情感欲望,所以每个人都必然兼具道心与人心,圣人亦不能外。可以说,人心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因而朱熹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认为人心所包含的各种生理欲望只是“危”的,并不就是“恶”的,反对将人心等同于需要摒除的“人欲”或“私欲”。所以他说:
人心,尧舜不能无;道心,桀纣不能无。盖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则直是丧乱,岂止危而已哉?只饥食渴饮、目视耳听之类是也,易流故危。④
人心是知觉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说做人欲,则属恶了,何用说危?⑤
但是,由于人心易动,出入无时,莫知其向,若不加以引导、控制,则易流于不善,故仍须以道心统率、支配人心,“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①。正因为如此,朱熹虽然承认道心、人心只是一个心,但确认和凸显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明确道心代表天理,以道心主宰人心,方能在不消灭人心的条件下,使人的情欲念虑自觉以道德理性为指导,从而在实践上使人的一切行为、思想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为主,即人心自不能夺,而亦莫非道心之所为矣。”②
综上可见朱子理学心性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备,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也正因为如此,朱熹对于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性”与“心”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讨论与辨析,既肯定了性与心存在着密切关系,不容割裂,又明确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差异极为关键,不容混淆。“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处,又有析而言处。须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③简言之,性是心之体,是心的知觉、思维、主宰作用的原则与依据。“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于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发见处。四者之萌皆出于心,而其所以然者,则是此性之理所在也。”④同时,性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而心则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故曰:“心与性自有分别。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便是那知觉底。”⑤更为重要的是,性是纯粹至善的,心则是理与气合的产物,可分为道心和人心,是有善有恶的,故心之知觉不可能完全合乎理的要求。若以心为性,便是以知觉为性,乃佛家“作用是性”与告子“生之谓性”之说,必将导致以气质为天理,认人心做道心的结果。“此心固是圣贤本领,然学未讲、理未明,亦有错认人欲作天理处,不可不察。”①
此外,针对某些学者将朱熹所说的“性”混同于其他学者所说的“本心”的观点,陈来先生特别指出,作为心之本体的性“只是一个标志意识系统本质的范畴,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赋予任何心的功能”,而朱熹所说的“心体”则指未发之心,即意识过程的原始状态,因而“在朱熹哲学的结构中并不需要‘本心’这一类概念”。②在朱熹看来,不论是未发之心还是已发之心,操存之心还是舍亡之心,皆是同一层次上的心,即同一个心,而没有本体之心与发用之心的区别。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朱子理学的立场上都只能说“性即理”,而决不能承认“心即理”。
显然,朱熹对于心性概念的这种细致辨析在陆学与王学一系的学者那里被视为烦琐、支离,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导致了心与理的分离。王阳明在论学时便不愿区分心与性,认为心、性、理、知、命只是一件事,更不必分别,故而直接主张“心即理”:
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③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④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⑤
在阳明那里,“心体”“心之本体”指的都是心的本然状态、本来面目,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朱子学者所说的“性”。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心外无理”的思想: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①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②
对于王阳明这一明显背离正统朱子理学的思想,不少学者表示困惑与怀疑。其弟子徐爱就曾问道:“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对此,阳明答道:
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③
由此可见,在阳明看来,心不仅是知觉器官,更是天理的完整体现,而这个天理在阳明的理解中主要指道德法则。显然,道德法则不可能存在于道德行为的对象上,只能存在于道德主体心中,由道德主体通过道德实践自然而然地实现出来。若是认为理在事事物物上,进而即物穷理,便是离心求理,南辕北辙。所以他批评朱熹“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④。同样在此意义上,阳明指出: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学问思辨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①
也就是说,理是人心中固有的条理,而心则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源。道德法则必须依靠心之条理作用于事事物物上方能实现,因而不可外心以求理。
在对心的含义的理解上,与朱熹相同的是,王阳明亦将心解释为知觉: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②
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③同时,阳明亦以心为身之主宰:
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④
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⑤
王阳明和朱熹虽然都认同心具有知觉与主宰的作用,但在具体论述心的过程中,朱熹往往将其置于心性关系的结构中进行讨论,明辨心性之间的异同与相互作用,并最终归结为理或性对心的规定与制约,而阳明则倾向于将心、性、理视为一物,甚至抛开性的概念,直接以心说理。因此,阳明可以说那能视听言动的便是性,便是天理,而朱熹就绝对不能如此说。对此,杨国荣认为,朱熹“在心性关系上表现为以性说心,这一思路更多地将心的先验性与超验性联系起来,而对心的经验内容未予以应有的注意。与此不同……王阳明在肯定心体具有先天的普遍必然之理的同时,又将其与经验内容与感性存在联系起来”①。所以王阳明既肯定了“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②,又以“恻怛”之情释“仁”,谓:“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③,还以“乐”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心体染上了明显的感性色彩。在阳明看来,“‘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④。也就是说,作为心之本体的乐,虽不是单纯感性的七情之乐,但亦包含了某种类似的情感形式和情感体验,而不同于抽象的道德理性。这种本体之乐作为心的本然状态,是人所共有、无时不存、无间于凡圣的,亦是心性修养所欲达到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王阳明所说的心体既以理为本及形式结构(心之条理),又与身相联系而内含着感性之维。……以理为本(以性为体)决定了心的先天性(先验性),与感性存在的联系则使心无法隔绝于经验之外。这样,心体在总体上便表现为先天形式与经验内容、理性与非理性的交融”①。
而王阳明之所以要在程朱所说的“性即理”之外特别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或许亦可在此意义上得到一种理解。朱熹虽然也承认作为性的理先天地内在于人的心中,但由于其对理所采取的实体化的诠释方式,以及对带有明显超验色彩和普遍规范意义的性的突出与强化,特别是对于性规范、宰制心的作用的强调,使得性与理很容易被理解为外在于人的、异己的纯客观原则,如戴震所批评的“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②,从而与人的情感、意志等主观因素发生对立。而在实践中,朱子理学也确实表现出比较注重外在规范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的强制性等特点。相较之下,王阳明则更加强调理内在于心中,突出心、性、理的一致性,取消了心与理之间的各种中介因素,希望以此避免心与理的割裂和对立。可以说,阳明之所以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心之条理即理”等命题,都是为了保证作为道德法则的理内化于道德主体心中,与心相互融合,而使外在的道德行为皆为心中之理的外化与实现。如此,“一方面,普遍之理不再仅仅表现为与主体相对的超验存在,另一方面,个体意识则开始获得了普遍性的品格”③,从而使得普遍的道德法则能够顺利转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为人的行为提供理性范导与内在动力。
关于人性,王阳明虽然亦在一般的意义上承认天理“赋于人也谓之性”④,与程朱派理学家的理解相近,但在具体论述时,他又往往倾向于以气质论性,不提倡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他说: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①
王门高弟邹守益亦谓:
天性与气质,更无二件。人此身都是气质用事,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气质,天性从此处流行。先师有曰:“恻隐之心,气质之性也。”正与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谓“浩然之气,塞天地,配道义”,气质与天性,一滚出来,如何说得“论性不论气”。后儒说两件,反更不明。除却气质,何处求天地之性?②
由此可见,阳明虽不否认有“性之本原”,但他所关注的显然不是不容说的“性之本原”,而是现实的人性,即气质之性。因为性本身是不显现的,性与性之善只有通过气质才能表现出来。人的一切行动思虑皆是气质用事,人之天性亦从此处流行,四端即是性善的表现。若无气质,亦无性善可见。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心的本然状态,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一般规定。朱熹将四端称为情,阳明则将其视为气、气质之性、性之表德。在阳明看来,气质不仅与性相伴而生,而且是性的完整体现,故曰:“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由此可见,王阳明所说的性既是先天的普遍之理,也与人的情感、意识等经验内容和感性因素相互联系,同样体现了普遍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他之所以不提倡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恐怕亦是为了避免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此后,王阳明的这一思想经过王门后学的继承和发挥,逐渐发展为一种气质之性的性一元论,与明代中后期整个理学思维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打破了程朱理学性二元论的垄断地位。其中,刘宗周关于心性的看法即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
凡言性者,皆指气质而言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如曰“气质之理”即是,岂可曰“义理之理”乎?①
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为心也。性只有气质之性,而义理之性者,气质之所以为性也。②
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发之旨也。③
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④
在刘宗周看来,气是第一性的,理只是气之理,不在气先,亦不在气外。同样的道理,性也只是气质的性,并不存在独立于气质之外的性,所谓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此外别无义理之性,因而极力反对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刘宗周进一步指出,正如人只有一个性一样,人亦只有一个心,即人心。道心不是与人心并列对立的另一个心,只是人心的本然状态、人之所以为心的根据而已。若无人心则无道心,道心只能从人心中看出来。
自明代之后,以“性即理”与“心即理”为代表的心性论领域的思想差异就逐渐被一些学者提炼、归纳出来,作为朱陆之辨或朱王之辨的要点之一。如罗钦顺即言:“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辨之!”①而清初福建朱子学者亦主要站在“性即理”的立场上,以正统朱子理学为武器,对王学进行批判。
例如,李光地②指出,朱子学与陆王之学从表面上看既有不少相似的内容,又有一些明显的表达与方法差异,但其根本分歧则在于心性之辨。故曰:“夫告、孟之差也,朱、陆之异也,在乎心性之源不合,仁义之实不著,非夫功之偏而不举,说之略而不全云尔”③,“象山之学,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讲明,亦言践履,所谓与朱子异者,心性之辩耳。”④
对于心性之辨,李光地说道:
知心性之说,则知天命、气质之说。何以故?曰:知人则知天。夫性无不善,而及夫心焉,则过也,不及也,杂糅不齐,于是乎善恶生焉。天命无不善,而及夫气焉,则过也,不及也,杂糅不齐,于是乎善恶生焉。⑤
主于天,曰理也,气也;主于人,曰性也,心也。一也。之二者之在天人,又一也。一则不离,一而二则不杂。⑥在他看来,心、性之间的差别与天命、气质的差别相同,且来源于天命、气质的差别。因为人禀受天地之理与气而生,知人则知天。人之本性与天命之性属理,是纯粹至善的,而心则包含气质的因素,有过与不及,杂糅不齐,从而产生善恶,且心与性是不离不杂的关系,故心不同于理明矣。
从作用来看,李光地认为,性是生物之本,形是物生之迹,心则既非性,亦非形,“居形性之间,形性妙合,而心为之主”①。从心性关系来看,一方面,心具众理,“心者性之郛廓。心如物之皮壳,性是皮壳中包裹的”②;另一方面,性是心的本体与根据,“心亦性之所生也。及有此心,则性具于中,感物而动,而情生焉”③,“谓心乃能生者。心之所以能生,是之谓性焉尔”④。而心之所以具有无比强大的认识能力,能够周物而不遗,也是由于其以至大无外、无所不该的性作为根据。李光地特别强调性对于心的先在性与根源意义,故提醒学者:“‘心统性情’,形生神发后,便著如此说。若论自来,须先说性,而后及心,心亦性之所生也。”⑤
此外,心又有道心、人心之别。人心兼具善恶,由于“形气之用,徇之可以流而为恶,而失心之正,然亦不得谓之非心也”⑥,故曰“人心惟危”。“果心之即性,则何危之有与?”⑦据此,李光地批评王阳明以心为性,便是混淆了道心、人心之别。“姚江以一段灵明者为性,虽少近里,然所见乃心而非性也。心便有别,但看声色臭味,平时多少耽著,至遇疾病,便生厌恶;遇患难,便不复思想。惟孝弟忠信,则坎壈之中,转见诚笃。至于生死利害,更生精采。故知人心、道心,确然两个。”①综上可见,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不加限定地主张“心即性”“心即理”显然是不合适的。
李光地追根溯源,指出“心即性”“心即理”之说来源于释氏,不但与程朱之学相背,亦不合于孔孟之道。他分析道:
孔子所谓“仁者,人也”,心性之合也。孟子所谓“仁,人心也”,心性之合也。然且有不仁之人,有不仁之心,是心不与性合也。心不与性合,而曰即心即性,可与?不可与?是知孔子所谓人者,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非谓人为仁也。孟子所谓心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非谓心为性也。②
此处,李光地其实亦是借用理学中的心性之辨来阐释孔孟之言。仁义之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培养人的终极目标,而仁义之人与仁义之心便是心与性的完美结合。但是,现实中的人却并不总是表现为仁,有不仁之人,有不仁之心,因而证明现实的人心并不总是与性理相合。同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只是仁义之端,若此善端不能加以护持、扩充,人心亦将流而为恶,故不能以心为性。
在揭露“心即理”说的错误之后,李光地又进一步批判了王阳明“心无善恶”的思想:
象山谓即心即理,故其论《太极图说》也,谓阴阳便是形而上者,此则几微毫忽之差,而其究卒如凿枘之不相入也。近日姚江之学,其根源亦如此,故平生于心、理二字往往混而为一。《答顾东桥书》引《虞书》,断自“道心惟微”以下,而截去上一语,晚岁遂有心无善恶之说。①
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曾说:“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②可见李光地所说的“断自‘道心惟微’以下,而截去上一语”指的便是王阳明故意截去“十六字心传”中的“人心惟危”四字,欲以此隐藏危殆的人心,以便证明“心即理”,进而得出“心无善恶”的结论。
严格说来,王阳明其实并未直接主张心无善恶。其“四句教”中的首句乃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无善无恶所指称的显然是心之本体,而不是笼统地说人心无善无恶。那么,如果明确地说心体无善无恶,或本心即性,李光地是否就能同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面对诸如“姚江之说,谓心自仁,心自义,心自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其不然者,非本心也。以是谓即心即性,殆可与”之类的问题时,李光地回答道:
其言似,其意非。奚不曰仁义之心,道心也;其不然者,人心之流也,则心性之辩明矣。彼丽于孔孟而为是言也,其意则谓心之体如是妙也,故以觉为道。以觉为道,必以无为宗。以无为宗者,道亦无矣。故无善无恶心之体,姚江晚年之说也。其异于孔孟之旨,又奚匿焉?③
又曰:
王说之病,其源在“心之即理”。故其体察之也,体察乎心之妙也,不体察夫理之实也。心之妙在于虚,虚之极至于无,故谓无善无恶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谓心自仁义,心自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本趣也。①
由此可见,李光地对于王阳明“心无善恶”的批评并非完全出于误解。在他看来,所谓心之本体仍是具有知觉作用的心,而不能等同于性。即便阳明将“心即理”“心无善恶”中的“心”解释为本心,也是为了混淆心与性的差别,打着孔孟的招牌,实则强调心性本体虚无、玄妙的特质,从而达到援释入儒的目的。
关于心体的善恶问题,阳明本人的论述并非十分清晰、毫无疑义,其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往往存在互异的表述,而所谓“无善无恶”的确切含义亦是复杂难解。无善无恶究竟是否等同于至善?是没有善恶,还是可善可恶?抑或所说的根本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善与恶?这一系列问题历来争论不休,见仁见智,这里无法一一复述。简单说来,我认为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思想显然吸收、借鉴了佛家特别是禅宗的相关思想,认为心之本体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相对的、具体的善恶,而将其视为一种绝对待、不思议的先天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被称为“至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所说的纯善无恶的至善。它既带有传统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恶意涵,又非伦理学所能完全范围。这一点需要略加说明。
陈来先生曾详细考察了王阳明于不同时期所做的可与“无善无恶心之体”相互印证的各种表述,指出“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一命题强调的是心体所具有的纯粹的无滞性与无执着性,并以此作为个人实现理想的自在境界的内在依据。②应该说,陈来先生的这一论断思路独到,阐发入微,实发人之所未发,但似乎亦不必然要排斥“无善无恶”同时兼具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含义。首先,“四句教”乃阳明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晚年定论,若“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确实不具有任何伦理上的意涵,以阳明之大贤,为何一定要选择使用“善”“恶”这样带有浓厚伦理意味的语词与表达方式,而无视其必然引发的巨大误解与非议?其次,“四句教”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首句与后三句之间应有层层递进、一以贯之的一面,若将首句分割开来单独讨论似乎有所未备。如王门高弟王畿即谓:“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①又言:“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②由此可见,王畿认为心与意、知、物之间乃是体用关系,若心体是无善无恶的,则意、知、物自然也应是无善无恶的。反过来说,针对意、知、物三者所说的善恶显然是指伦理上的善恶,那么心体的无善无恶也应该相应具有伦理的含义。若针对心体所说的无善无恶仅指无滞性、无执着性,那就完全无法得出意、知、物三者皆无善无恶的结论。王畿所理解的“四无”说虽然与阳明的原版有所出入,未必能完全反映其本意,但阳明也并未反对王畿的“四无”说,反而特别赞赏王畿基于首句的理解与阐发,谓:“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又谓:“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③由此可见,阳明所谓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确实具有伦理方面的意涵与目的,从而与正统儒学的性善论产生了巨大乃至根本性的差异。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何当王畿道出他的想法时,会给阳明带来如此大的冲击与惊喜,又是“传心秘藏”“含蓄到今”,又是“天机发泄”“岂容复秘”,并且郑重其事,反复告诫。相较之下,所谓心体的无滞性、无执着性,或者说“无心”“无念”的思想,起码在宋代就已经得到儒者的关注与阐发,恐怕算不上什么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见解。不但程颢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①的说法,就连南宋前期并不以理学闻名的宰相留正亦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天之所以能成造化之功者,以其无容心也。是以生育肃杀自然有至理寓乎其间。夫圣人之心亦如是而已。举天下之事,是非利害杂然至乎其前,而吾一概以无心处之,方寸湛然,处处洞彻,天下之事焉往而不得其当哉!”②由此不难看出,当时这一思想起码在接近理学的士人群体中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同。若阳明所说的心无善恶只是指心体的无滞性、无执着性,又何至于如此隐秘而慎重?
应当说,正是由于王阳明这一思想的模糊性与复杂性,使其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不同目的、立场的学者误解或曲解为心无善恶,从而对王学进行激烈批判,或是彻底倒向自然主义,以此作为放纵身心、肆意妄为的借口。从这一意义上看,李光地虽未直接对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思想内容做详尽的辨析,也未必完全理解其复杂内涵,但又确实抓住了其中的某些要点。一方面,他始终坚持朱子理学关于心性之辨的基本立场,指责阳明在心性问题上故意回避了道心、人心的关键差别;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阳明的这一思想别有授受,乃根源于佛家以知觉作用为性,认心性为虚无的思想,并非出自孔孟本旨。若对这一点不加察觉,以非为是,终将导致一切道德规范与道德法则虚无化的严重后果。也正因为王学的心性思想更多地吸纳了佛教的智慧,而又证以孔孟之言,在正统的朱子学者看来不免似是而非,离经叛道,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与危害性,故李光地要极力辨之。
综上,李光地指出,陆王之学“心性之原既差,则志其所志,养其所养,讲其所讲,行其所行,二本殊归,其道使然。今言陆王之学者,不谓其偏于德性而缺学问,则谓重在诚意而轻格物,此亦朱子论近世攻禅,若唐檄句骊守险者类也。……然则陆王二子之弊其应辨析者,固在心性人道本原之际,不在讲学持守、知行先后之间也”①。在李光地看来,心性乃人之本原,心性论则是学术之源。王学固然存在“偏于德性而缺学问”“重在诚意而轻格物”等问题,但这些都不是要害所在,其谬误根源在于错认心性,故所志、所养、所讲、所行不免皆错。若要彻底辩驳王学之弊,恢复孔孟之真,就不能光在为学方法、修养工夫等处用力,而应该釜底抽薪,于心性大本大原处讨个分晓。
李光坡②的心性思想与李光地相近。根据他的理解,“心”即“神”,主要表现为知觉、运用与主宰能力,而“性”则是内在于知觉的原则与本体,二者紧密关联却并不等同,其根本差别在于性实心虚,存在虚实之不同。故曰:
人身有神有性。神者,灵觉也,视性则微有迹,方诸魂魄精气则妙矣。以其内足以运夫仁义秉彝之良,而外以管乎四支百骸之用,动静由己,变化无方,几几乎性之事,惟有虚实之分耳。③
据此,李光坡指出,心学的主要错误便是将虚灵的知觉混同于作为本质的实理与实性,从而落入释氏“作用是性”之见而不自知。所谓“见云为之际皆明觉为之宰,不复体其所觉之实,而但以所为灵者当之,此守溪‘性至虚至灵,如鉴之悬,物来则照,物去不留’之言。阳明表而出之,而不悟其仍于释氏之见”④。而这一思想的危害则在于将道德原则置于人心之外,进而导致“仁义礼智由外铄我”的结论,“使小慧之徒高者逃于幽禅,卑者至于狂悖”①。李光坡同时指出,心性之辨还与理气之别有关。性即是理,心虽不专是气,但包含气的因素。必先有知觉之理,后理与气合,心方能知觉。因此,若能明白“理气合而成觉”的道理,则知心不是性,亦不当以无善无恶名心。
综上,李光坡总结道:“能觉者,心之灵也;所觉者,性之理也。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嘑尔蹴尔而羞恶。知恻隐、知羞恶者,神也。伤之切,痛之深,无所为而为;羞之甚,恶之挚,宁身死而不受,是专虚灵之神乎,抑有实然之性乎?是自外照乎,抑由中出乎?是理在气中发见乎,抑超于气上而为之主乎?然则必有是性为所知所觉之实际而不沦于虚,为能静能动之本体而不杂于气也,明矣。”②
童能灵③亦站在朱子理学的立场上,对心性问题做了较为集中、系统的剖析与论述,批判了陆王的心性思想。童能灵认为,“天地之间,止此理、气二者而已,此即古今学术之辨所由分也”④,因而主要从理气论的角度来理解和阐述心、性概念及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于性,他认同程朱“性即理”之说,特别强调性与人之间的亲切关系。故曰:
以理言之,则为当然之则,所谓“有物必有则”是也。其具于人心,即在人之则,而为性者也。⑤
性固是天理,然必就人生所禀言之,乃见性之所以得名也。不然,何以不即谓天理,必别之曰性耶?谓之性,则如云水性寒、火性热之性。盖人但知有此生则有此性,不知须有此性始有此生也。如水必须有寒之性方凝而成水,火则必须有热之性方发而成火,人则必须有生之性方有此生而为人也。①
性固是理,但须看到理之在人最为亲切,方见其为人之性也。盖人之生,气聚而生也。气之所以聚而生,则理为之也。②
在童能灵看来,人由气聚而生,但气不能自生,也不能自行,气的聚散变化皆理为之。理为气之主宰,亦为气之所以然者,因而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与基本前提,“须有此性始有此生”。理又根植于气之中,气为理之载体。天理须为人所禀,内在于人心之中,方成其为人性。所以说性是于人最为亲切之理。
而心对于童能灵来说,则是一个属于气的概念,属形而下者,其特性为虚灵不测、神明之妙。他说:
以气言之,则气之粗者凝而为形,其精爽则为心。心之精爽至于神明,故其体虚而无物,其用灵而不测。③
盖(心)只是气也。气之粗者,凝而为形,其精爽则为心。气之精爽,自能摄气,此心所以宰乎一身也。且既曰精爽,则亦无气之迹,而妙于气矣。顾只是气之精爽,非形而上之理也。④
由此可见,在童能灵的理解中,性属理,属形而上之道,心属气,属形而下之器,故心不能为性,心不能为理明矣。同时,心之虚灵亦表现为一种主宰、运用、知觉的能力。童能灵认为,人得至精至灵之生气以为魂魄,魂为阳之神,魄为阴之神,魂魄之合为心,便有主宰运用、知觉记当的作用。因此,心本身虽无声无臭,却能觉声觉臭,认识各种事物与义理,主宰一身而运用之,而性则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显然不具备任何运用与知觉能力,这也说明心不能为性,心不能为理。所以他说:“性无为而心有觉,觉即精爽之所为也。性则是理,虽所觉者亦是理,而理初无觉也。此形而上下之分。”①
童能灵认为,心所具有的神明之妙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一曰神通,贯幽明,通远近,无所隔碍也;一曰神变,应事接物,变化不测也。然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变二者而已。通与变是其神处,而明在其中矣。②
心之所以能通、能变,是由于心乃气之精爽,“清之极矣,无粗浊,自无渣滓昏隔,如何不通”,“精极则变,无粗浊,故无滞碍也,如何不变”。③据此,童能灵提出,心虽属气,而其精爽之至却可通极于性,故胡宏谓“心妙性情之德”,朱熹言“心妙众理”。“不然,性即理也,理寓于心,岂不反为心所昏隔耶?”④若心与性相互隔绝,不能相通,则心中之理亦将为心所遮蔽阻隔,无法发而为用。正因为心具有如此的神明之妙,又可通极于性,故而许多学者便容易将心性混为一谈。对此,童能灵强调:“此又须知心之为物,只是气之精爽,其受气之浊者,亦有昏隔时。”⑤这就是说,心虽非形气之粗,但毕竟属气,不免有时要为气之粗浊者所遮蔽障碍,不能如性一般纯粹至善。心以性为体,其气之精爽可通极于性而有神明之妙,但不能因此认定心即是性,心即是理。
对于人性,童能灵进一步指出:“人者,天地之生而万物之灵,故其性无所不绾。所谓万物备于我者,非独备其影象也,即万物之所以为物者绾于此焉。”①由于天理包罗万有,万分具足,而人作为万物之灵,禀受天理之全体以为性,人性就不仅是人自身的根据与规定,也应该包括万物之所以为物的根据与规定。同时,人性之所以能够感物而动,发而为情,亦是因为人性中包含物理,性理与物理只是同一天理。“性所以感物而动者,性在内,物在外,然在内之性不是别物,只是理也。所谓理,便是在外之物之理也。舍物理,无以为吾之性矣。物理即吾性之理,此天下所以无性外之物也。”②因此,人性与性理中显然包含了物理、事理、情理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并不只局限于道德规定与道德准则等伦理范畴。故曰:
凡天地之道,圣人之蕴,措之为礼乐刑政,垂之为《诗》《书》《易》象者,皆是理之所蟠际,即皆是性之所充周。而日用彝伦、视听言动之间,须臾而离之,则是自失其则而不诚无物矣。是以圣人之教,必使择之精而执之固,有以完其所以为性者焉。此其学固非可以一朝顿悟而一悟无余者矣。③
又曰:
吾性之理即物理。天下之物理多矣,大而天地,细而昆虫草木,皆各有理。自人言之,大而五伦,细而三百三千,各有一理,千条万派,用各不同,而皆具于吾性之内。……万理只一理,故性具万理,无头项杂凑之嫌。但性只一理者,正指未发之前,内无感触,端绪未见,条理未分,浑然而一理耳。……当此之时,气不用事,心理为一,本难分别,故于所谓正而不偏、亭亭当当者,理固宜然,而心亦如是也。学者于此时实难见得亲切,不若即理之万分、散于事物者一一穷之,辨其万分者之不出一理,庶几心有把握,而涵泳之久,涣然释,怡然顺矣。①
这里所说的“一朝顿悟而一悟无余者”,以及只求“一理”而不顾“万分”的为学方法,显然都是针对被目为禅学的陆王之学。
对于陆王心学一派的学者所宣称的种种神秘的顿悟体验,童能灵并不否认这种体验本身的真实性,而是通过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指出其只不过是来源于心体虚灵不测、神明之妙的特性。他说:
心之精爽至于神明,故其体虚而无物,其用灵而不测。方其未用也,寂然而虚;及其既用也,亦寂然而虚,则其方用之际,亦谓必有常虚常寂者存于其中,而不得以心思求之,恐心思之有着而非虚也;不得以言语求之,恐言语之外喧而非寂也。②
正是由于心体虚灵不测,难以迹求,人们在追求心中存在的“常虚常寂者”时,便不能使用语言文字、逻辑思维等日常手段,因而往往容易陷入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境界之中。“心思路绝,言语道断,惟静惟默之际,而其为神明之本体,静极当动,敛极当发,介然有顷之间而偶尔感触,光明呈露,自觉自知,遂诧为神奇,得未曾有他人不见,师友莫与,而惟我独自得之者矣。……又有一种,静默之久,神明未瞑,亦未发用,迷离惝恍,虚实之间,有影象参差呈露于前,如睡初觉,如梦中见,原非实有,则遂以此为万物皆备之象呈于我矣。”③童能灵认为,这种神秘体验至多只是心体在极端静默状态下的一时呈露,而被偶尔感触,甚至是一种虚实之间迷离惝恍、真伪莫辨的幻觉、幻象,并非对于性理的完整、客观认识,自然也不具备他们所宣称的唯我独得、一朝顿悟、一悟无余的意义。
据此,童能灵指出,不论是陆九渊闻鼓声振动窗棂而豁然有觉,还是王阳明龙场中夜悟道,抑或徐仲试镜中看花,杨慈湖鉴中见象,“自穷理者观之,此皆心之神明不得循其寂感动静之常,而束于空寂,为之变现光影如此。既已自为之眩而不自知,遂欲保以终身,惟恐或失。此正朱子所谓禅家作弄精神,到死不肯舍放者也。嗟夫!以心为理,此势必眩于心而一于虚寂之见者,必不得与事相操持,泛应之际,涉而不有,日用彝伦之地,皆归之于浮薄不可止矣。……且夫虚寂之体,岂得不以礼法为束缚而废弃之哉?”①在他看来,陆王之学之所以将主静、顿悟作为最重要的为学方法与修养工夫,其根源还是在于误认心性,以心为理。若以心为理,一味地追求心之神明,必然会扰乱心性本身寂感动静的常态,陷入虚空寂灭的状态之中,从而执着、迷惑于心中闪现的虚幻光影,将其认作世界的实相或本质,并冀图保任终身。童能灵认为,这实际上正是禅家在主观上作弄精神的把戏,而非对于天理之实实有所得,学者若满足、沉溺于这种虚无高妙的境界之中,必将使心与现实事物相割裂,甚至以万事万物为虚幻,从而导致对日常的躬行践履、应事接物、日用彝伦等道德行为与道德规范的忽视和荒废。
此外,对于心与理的关系,以及心之神明的来源问题,童能灵主张心本于理,但心非即理。在他看来,人之一身止理、神、气、形四者而已。推其所由生,则“理生神,神生气,气生形,一以贯之也。……理生神,即所谓精爽也”②。理生心之神明,而其本身即寓于神明之中,故曰心具众理。前面曾经提到,心所具有的神通、神变等神明之妙是由于气的至清、至精、至灵,而追根溯源,又皆根源于理。理一分殊,就“理一”观之,“非独一身之内只此一个心……天地人物止此一个神明。原只一个,如何不通?原只一个,呼应自灵”③;就“分殊”观之,理一而散万心、应万心,心如何不通?理一而万、万而一,心如何不变?故曰:“神明之妙本于理。”①童能灵又以动静言心之神,而以理为所以动静者。有所以动静之理,方有动静之心,而心之动静又主宰形体之动静。童能灵指出,朱熹论《太极图》,以动静为心,以太极为性,性具于心,性与心本无先后可言,但据《太极图》推之,太极为动静之根底,性则当为心之根底,亦可证心之妙本于理。若从反面来看,世间虽有假仁假义之心,但这并非仁义之理本身为假,而是人在理解、运用上出现了偏差。所谓“假仁者不仁,苟无仁,彼安所假耶?假义者不义,苟无义,彼又安所假耶?……盗跖之不仁甚矣,不义亦甚矣,然尝以分均出后为仁义矣。假令跖不为盗,而以其分均者行赏,出后者居殿,谁得拒之仁义之外哉?乃知人心只是此理也,小人外是亦无以行其恶。故曰心本于理”②。
综上可见,童能灵虽然非常重视心的主宰、知觉的作用与能力,认为“天地之大,古今之远,心之所存,应念即至,乃知天地人物止此一个神明。……此心神明便是天之神明也”③,但却能始终恪守朱熹“性即理”的基本原则,强调心以理为本,理为心之神明之根基,从而明辨心性理气之异同,有力地批驳了陆王“心即理”的心性思想。
同样,蓝鼎元④亦认为,陆王之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根本差别并不在于是否讨论心,或者是否重视心,而在于对心性的不同理解。他说:
圣贤所以别于异端,其惟心学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千载心学之祖也。圣贤以道心为人心之主,异学养人心而弃其道心。故虽皆以心学为名,而是非邪正,相似而实不同者在此。①
蓝鼎元这里所说的异端,除了释、道二教之外,显然也包括陆王之学在内。蓝鼎元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句是义理之源、心学之祖,因而也是判断学问、义理是非真伪的根本标准。在他看来,朱子学明辨道心、人心,主张以道心主宰、制约人心,而陆王之学则忽视乃至泯灭道心、人心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分歧,从而导致养人心而弃道心。因此,二者虽然都以心学为名,但其中却隐含着是非邪正的根本区别,言相似而实不同,只有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正统儒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心学。
蓝鼎元进一步指出,人心以虚灵为特点,根源于知觉,而道心则根源于虚灵知觉之义理,故道心主宰人心。朱子学言心注重心的义理层面,故能以道心统率人心,培养心中的仁义礼智,使心的知觉作用能够符合道德法则的要求。而佛老与陆王之学则仅以知觉作用言心,舍性理而专言知觉,故不学不虑,不假修为,于一切事物都不理会,终日只是完养其精神魂魄,希望完全摒除心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知识与事物,必然导致以人心作道心。故曰:
主于义理者,惟恐义理不明,或有非理之视听言动,则失其所以为心。故必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而涵养省察,不敢有一息之或间。由是而为圣为贤为豪杰,皆此道心为之也。主于知觉者,则止欲全其知觉,惟恐心泊一事,思一理,或扰其昭灵寂静之神,故不顾善恶是非,不立语言文字。若老氏之无视无听,抱神以静,佛氏之净智妙圆,识心见性,象山之瞑目静坐,收拾精神,白沙之虚灵万象,阳明之良知,皆误以人心为道心者也。②由于陆九渊和王阳明都标榜自己的学术直承孟子而来,而孟子又特别关注心性问题,于儒学心性论多有开辟、发明之功,所以便不免有人产生疑问,认为陆王的心性思想皆本于孟子,似乎不应以异学视之。对于这一观点,蓝鼎元明确表示反对。他说:
孟子所言,仁义之心也;陆子所言,昭昭灵灵之心也。孟子求放心,必曰学问之道是教人读书穷理,主敬求仁者也。陆子以闭目静坐为求放心,是教人屏事物,绝思虑,废语言文字意见,即心是道,明心见性者也。言似同而旨不同,恶可以诬孟子。①
在蓝鼎元看来,孟子所说的心是主于义理的仁义之心,而陆王所说的心则是主于知觉的虚灵之心。孟子以读书穷理、主敬求仁为学问之道,注重内外交修并进,以此求放逸之心,而陆王则以闭目静坐为求放心的工夫,欲使人摒除事物,断绝思虑,以心为理,取消一切读书讲论与经典注疏,显然是佛老一路的思想,从而与孟子之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由此不难发现,蓝鼎元和其他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大都清楚地认识到,性与心、道心与人心的区分和差异在朱子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以心为理,以人心为道心正是陆王之学心性论与朱子学心性论之间的根本差异,也是陆王之学之所以错误的根源所在。若是否认性与心、道心与人心之间的区别,必然以个体的情感、欲望、意见为天理,从而导致是非善恶的混淆与道德秩序的崩溃。只有坚持以义理规范心,以道心统率人心,才能为善去恶,将人从世俗的功利境界提升到超越境界。
在宋代之前,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一种性一元论,往往难以圆融地解释人性中善恶混杂所造成的种种复杂问题。而其他各种性无善恶论、性善恶混论等理论,或流于浅显粗糙,难以自圆其说,或不合于儒家主流伦理观念,都不能令学者普遍满足和信服。至北宋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二元论的理论倾向,主张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天地之性亦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人若是希望为善去恶、成圣成贤,就必须通过学习、修养等方法变化气质,以回复本然的天地之性。这种人性论肇始于周、张、二程等北宋理学家,直到南宋朱熹处方才发展到完善与成熟的阶段。
朱熹认为,世界由理和气构成,人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即“天命之性”,又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而“天命之性”落入气质形体中便有了“气质之性”,故极称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①之语,主张论性与论气兼备。他说:
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①
须是合性与气观之然后尽。②
由于理与气不离不杂,所以天命与气质亦是不离不杂的关系。一方面,“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③;另一方面,“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相夹杂”④。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说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非平行并立的两种性。前者作为后者的本体与根据,存在于后者中。故曰:“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性即太极之全体。但论气质之性,则此全体堕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⑤
在现实世界中,理必须安顿在一定的形气之中才能成为人性,故而一切现实的人性皆非性之本体,而是气质之性。“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也。”⑥因此,朱熹亦将人性中先天具有的恶的因素归因于气质。天命之性来源于天理,自然是纯善无恶的,而气质则有清浊昏明之不齐。天命之性经过气质的熏染、障蔽,所呈现出来的现实的人性,即气质之性,便是有善有恶的。所以朱熹说: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①
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②
以上即为朱熹人性论思想之大概。由此可知,朱熹所说的“性即理”之“性”并非具体、现实的人性,而只能是天命之性,亦即性之本体。所以“性即理”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便是性之本体是理,本然之性是理。程颐尝言:“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③此语极为朱熹所赞赏,以为“如‘性即理也’一语,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④,“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⑤。
为了进一步说明性善的根源,朱熹发挥《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想,指出: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⑥
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⑦
这就是说,理在天地间只是一个总的道理,为人所禀则表现为仁义礼智之本性。如果说程颐所说的“性即理”主要还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人性的本质内容与天理相互符合,那么朱熹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的本性与天理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从而将宇宙论与人性论贯穿起来。所以钱穆说:“伊川性即理也之语,主要在发挥孟子性善义,只就人生界立论,而朱子则用来上通之于宇宙界。亦可谓朱子乃就其自所创立有关宇宙界之理气论而来阐申伊川此语之义。”①
而“心”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意义之一便是知觉。朱熹认为,性属未发,故不能知觉,心含已发,方能知觉。故曰:
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便是那知觉底。②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运用处,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③
由于人心具有十分伟大的认识、思维能力,所以朱熹常常称赞心的虚灵与神妙:
此心至灵,细入豪芒纤芥之间,便知便觉,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到那里;下而方来又不知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也到那里。这个神明不测,至虚至灵,是甚次第。④与心的知觉能力相关联的便是心的主宰作用。所谓“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①。朱熹提出:
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②
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至动时方有主宰也。③
这就是说,心是人身唯一的主宰,不论语默动静,人的言语、行动、情感、思维等一切行为都受到心的控制与支配,并对知觉到的事物做出适当的反应,从而体现出高度的能动性。但是,由于朱熹在论述心的主宰作用时间或使用“命万物”“宰万物”等说法,便有学者据此认为朱熹所说的心就是万物的本体或万物的主宰者。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解,陈来先生已辨之。因为朱熹“心为主宰的思想主要是把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来考察心在个体实践活动中的作用”④,所以心并不能直接主宰万物,而是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支配来实现“命万物”与“宰万物”。
对于心与性的关系,朱熹强调“心具众理”⑤,这个“理”便是人的本性,亦即人先天内在的道德本质。故曰:
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虚,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⑥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①
可以说,心以性作为其内容与依据,性则通过心的知觉与主宰作用将自己表现出来。“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②
此外,朱熹极称张载“心统性情”之说,亦经常以“心统性情”的模式来分析心性关系。诚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在朱熹那里,“心统性情”这一命题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心兼赅性、情:
“心统性情”,统,犹兼也。③
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④
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⑤
朱熹认为,性静情动,性是心之体,是心所得于天的原理,情是心之用,是心感于物而发的功用,而心则是兼赅动静体用的知觉意识活动的总体。“心统性情”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心主宰性、情:
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统是主宰,如统百万军。⑥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①
在朱熹看来,心不仅兼赅性情,而且统率、管摄性情。心不仅需要在已发的状态下以理智和德性主导、宰制各种情感、欲望、念虑,还需要在未发之时主敬涵养、提撕警觉,使心处于平静、中和的状态,以此保证性对意识活动的支配作用不受干扰。故曰:“未发而知觉不昧者,岂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发而品节不差者,岂非心之主乎情者乎?”②
与通过天命与气质的划分来解释人性中善恶的来源这一方式类似,朱熹亦将心区别为“道心”与“人心”,以此来解释心所表现出来的善恶邪正。朱熹提出:
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
心者……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④
由此可见,道心根源于天理,是纯善的,亦是隐微难明的,而人心则来源于情欲与气质,是可善可恶的,若缺乏主宰、制约则极易流为不善。他进一步指出: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①
换言之,人只有一个心,所谓的道心、人心并不是真的有两个心存在,只是心的两个不同方面或两种思想内容而已。故曰:
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②
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非有两个心,道心、人心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③
在朱熹看来,由于人皆具有本性与形体,本性表现为道德意识,形体产生情感欲望,所以每个人都必然兼具道心与人心,圣人亦不能外。可以说,人心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因而朱熹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认为人心所包含的各种生理欲望只是“危”的,并不就是“恶”的,反对将人心等同于需要摒除的“人欲”或“私欲”。所以他说:
人心,尧舜不能无;道心,桀纣不能无。盖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则直是丧乱,岂止危而已哉?只饥食渴饮、目视耳听之类是也,易流故危。④
人心是知觉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说做人欲,则属恶了,何用说危?⑤
但是,由于人心易动,出入无时,莫知其向,若不加以引导、控制,则易流于不善,故仍须以道心统率、支配人心,“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①。正因为如此,朱熹虽然承认道心、人心只是一个心,但确认和凸显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明确道心代表天理,以道心主宰人心,方能在不消灭人心的条件下,使人的情欲念虑自觉以道德理性为指导,从而在实践上使人的一切行为、思想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为主,即人心自不能夺,而亦莫非道心之所为矣。”②
综上可见朱子理学心性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备,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也正因为如此,朱熹对于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性”与“心”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讨论与辨析,既肯定了性与心存在着密切关系,不容割裂,又明确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差异极为关键,不容混淆。“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处,又有析而言处。须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③简言之,性是心之体,是心的知觉、思维、主宰作用的原则与依据。“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于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发见处。四者之萌皆出于心,而其所以然者,则是此性之理所在也。”④同时,性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而心则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故曰:“心与性自有分别。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便是那知觉底。”⑤更为重要的是,性是纯粹至善的,心则是理与气合的产物,可分为道心和人心,是有善有恶的,故心之知觉不可能完全合乎理的要求。若以心为性,便是以知觉为性,乃佛家“作用是性”与告子“生之谓性”之说,必将导致以气质为天理,认人心做道心的结果。“此心固是圣贤本领,然学未讲、理未明,亦有错认人欲作天理处,不可不察。”①
此外,针对某些学者将朱熹所说的“性”混同于其他学者所说的“本心”的观点,陈来先生特别指出,作为心之本体的性“只是一个标志意识系统本质的范畴,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赋予任何心的功能”,而朱熹所说的“心体”则指未发之心,即意识过程的原始状态,因而“在朱熹哲学的结构中并不需要‘本心’这一类概念”。②在朱熹看来,不论是未发之心还是已发之心,操存之心还是舍亡之心,皆是同一层次上的心,即同一个心,而没有本体之心与发用之心的区别。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朱子理学的立场上都只能说“性即理”,而决不能承认“心即理”。
显然,朱熹对于心性概念的这种细致辨析在陆学与王学一系的学者那里被视为烦琐、支离,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导致了心与理的分离。王阳明在论学时便不愿区分心与性,认为心、性、理、知、命只是一件事,更不必分别,故而直接主张“心即理”:
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③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④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⑤
在阳明那里,“心体”“心之本体”指的都是心的本然状态、本来面目,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朱子学者所说的“性”。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心外无理”的思想: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①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②
对于王阳明这一明显背离正统朱子理学的思想,不少学者表示困惑与怀疑。其弟子徐爱就曾问道:“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对此,阳明答道:
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③
由此可见,在阳明看来,心不仅是知觉器官,更是天理的完整体现,而这个天理在阳明的理解中主要指道德法则。显然,道德法则不可能存在于道德行为的对象上,只能存在于道德主体心中,由道德主体通过道德实践自然而然地实现出来。若是认为理在事事物物上,进而即物穷理,便是离心求理,南辕北辙。所以他批评朱熹“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④。同样在此意义上,阳明指出: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学问思辨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①
也就是说,理是人心中固有的条理,而心则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源。道德法则必须依靠心之条理作用于事事物物上方能实现,因而不可外心以求理。
在对心的含义的理解上,与朱熹相同的是,王阳明亦将心解释为知觉: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②
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③同时,阳明亦以心为身之主宰:
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④
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⑤
王阳明和朱熹虽然都认同心具有知觉与主宰的作用,但在具体论述心的过程中,朱熹往往将其置于心性关系的结构中进行讨论,明辨心性之间的异同与相互作用,并最终归结为理或性对心的规定与制约,而阳明则倾向于将心、性、理视为一物,甚至抛开性的概念,直接以心说理。因此,阳明可以说那能视听言动的便是性,便是天理,而朱熹就绝对不能如此说。对此,杨国荣认为,朱熹“在心性关系上表现为以性说心,这一思路更多地将心的先验性与超验性联系起来,而对心的经验内容未予以应有的注意。与此不同……王阳明在肯定心体具有先天的普遍必然之理的同时,又将其与经验内容与感性存在联系起来”①。所以王阳明既肯定了“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②,又以“恻怛”之情释“仁”,谓:“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③,还以“乐”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心体染上了明显的感性色彩。在阳明看来,“‘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④。也就是说,作为心之本体的乐,虽不是单纯感性的七情之乐,但亦包含了某种类似的情感形式和情感体验,而不同于抽象的道德理性。这种本体之乐作为心的本然状态,是人所共有、无时不存、无间于凡圣的,亦是心性修养所欲达到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王阳明所说的心体既以理为本及形式结构(心之条理),又与身相联系而内含着感性之维。……以理为本(以性为体)决定了心的先天性(先验性),与感性存在的联系则使心无法隔绝于经验之外。这样,心体在总体上便表现为先天形式与经验内容、理性与非理性的交融”①。
而王阳明之所以要在程朱所说的“性即理”之外特别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或许亦可在此意义上得到一种理解。朱熹虽然也承认作为性的理先天地内在于人的心中,但由于其对理所采取的实体化的诠释方式,以及对带有明显超验色彩和普遍规范意义的性的突出与强化,特别是对于性规范、宰制心的作用的强调,使得性与理很容易被理解为外在于人的、异己的纯客观原则,如戴震所批评的“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②,从而与人的情感、意志等主观因素发生对立。而在实践中,朱子理学也确实表现出比较注重外在规范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的强制性等特点。相较之下,王阳明则更加强调理内在于心中,突出心、性、理的一致性,取消了心与理之间的各种中介因素,希望以此避免心与理的割裂和对立。可以说,阳明之所以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心之条理即理”等命题,都是为了保证作为道德法则的理内化于道德主体心中,与心相互融合,而使外在的道德行为皆为心中之理的外化与实现。如此,“一方面,普遍之理不再仅仅表现为与主体相对的超验存在,另一方面,个体意识则开始获得了普遍性的品格”③,从而使得普遍的道德法则能够顺利转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为人的行为提供理性范导与内在动力。
关于人性,王阳明虽然亦在一般的意义上承认天理“赋于人也谓之性”④,与程朱派理学家的理解相近,但在具体论述时,他又往往倾向于以气质论性,不提倡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他说: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①
王门高弟邹守益亦谓:
天性与气质,更无二件。人此身都是气质用事,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气质,天性从此处流行。先师有曰:“恻隐之心,气质之性也。”正与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谓“浩然之气,塞天地,配道义”,气质与天性,一滚出来,如何说得“论性不论气”。后儒说两件,反更不明。除却气质,何处求天地之性?②
由此可见,阳明虽不否认有“性之本原”,但他所关注的显然不是不容说的“性之本原”,而是现实的人性,即气质之性。因为性本身是不显现的,性与性之善只有通过气质才能表现出来。人的一切行动思虑皆是气质用事,人之天性亦从此处流行,四端即是性善的表现。若无气质,亦无性善可见。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心的本然状态,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一般规定。朱熹将四端称为情,阳明则将其视为气、气质之性、性之表德。在阳明看来,气质不仅与性相伴而生,而且是性的完整体现,故曰:“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由此可见,王阳明所说的性既是先天的普遍之理,也与人的情感、意识等经验内容和感性因素相互联系,同样体现了普遍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他之所以不提倡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恐怕亦是为了避免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此后,王阳明的这一思想经过王门后学的继承和发挥,逐渐发展为一种气质之性的性一元论,与明代中后期整个理学思维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打破了程朱理学性二元论的垄断地位。其中,刘宗周关于心性的看法即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
凡言性者,皆指气质而言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如曰“气质之理”即是,岂可曰“义理之理”乎?①
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为心也。性只有气质之性,而义理之性者,气质之所以为性也。②
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发之旨也。③
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④
在刘宗周看来,气是第一性的,理只是气之理,不在气先,亦不在气外。同样的道理,性也只是气质的性,并不存在独立于气质之外的性,所谓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此外别无义理之性,因而极力反对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刘宗周进一步指出,正如人只有一个性一样,人亦只有一个心,即人心。道心不是与人心并列对立的另一个心,只是人心的本然状态、人之所以为心的根据而已。若无人心则无道心,道心只能从人心中看出来。
自明代之后,以“性即理”与“心即理”为代表的心性论领域的思想差异就逐渐被一些学者提炼、归纳出来,作为朱陆之辨或朱王之辨的要点之一。如罗钦顺即言:“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辨之!”①而清初福建朱子学者亦主要站在“性即理”的立场上,以正统朱子理学为武器,对王学进行批判。
例如,李光地②指出,朱子学与陆王之学从表面上看既有不少相似的内容,又有一些明显的表达与方法差异,但其根本分歧则在于心性之辨。故曰:“夫告、孟之差也,朱、陆之异也,在乎心性之源不合,仁义之实不著,非夫功之偏而不举,说之略而不全云尔”③,“象山之学,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讲明,亦言践履,所谓与朱子异者,心性之辩耳。”④
对于心性之辨,李光地说道:
知心性之说,则知天命、气质之说。何以故?曰:知人则知天。夫性无不善,而及夫心焉,则过也,不及也,杂糅不齐,于是乎善恶生焉。天命无不善,而及夫气焉,则过也,不及也,杂糅不齐,于是乎善恶生焉。⑤
主于天,曰理也,气也;主于人,曰性也,心也。一也。之二者之在天人,又一也。一则不离,一而二则不杂。⑥在他看来,心、性之间的差别与天命、气质的差别相同,且来源于天命、气质的差别。因为人禀受天地之理与气而生,知人则知天。人之本性与天命之性属理,是纯粹至善的,而心则包含气质的因素,有过与不及,杂糅不齐,从而产生善恶,且心与性是不离不杂的关系,故心不同于理明矣。
从作用来看,李光地认为,性是生物之本,形是物生之迹,心则既非性,亦非形,“居形性之间,形性妙合,而心为之主”①。从心性关系来看,一方面,心具众理,“心者性之郛廓。心如物之皮壳,性是皮壳中包裹的”②;另一方面,性是心的本体与根据,“心亦性之所生也。及有此心,则性具于中,感物而动,而情生焉”③,“谓心乃能生者。心之所以能生,是之谓性焉尔”④。而心之所以具有无比强大的认识能力,能够周物而不遗,也是由于其以至大无外、无所不该的性作为根据。李光地特别强调性对于心的先在性与根源意义,故提醒学者:“‘心统性情’,形生神发后,便著如此说。若论自来,须先说性,而后及心,心亦性之所生也。”⑤
此外,心又有道心、人心之别。人心兼具善恶,由于“形气之用,徇之可以流而为恶,而失心之正,然亦不得谓之非心也”⑥,故曰“人心惟危”。“果心之即性,则何危之有与?”⑦据此,李光地批评王阳明以心为性,便是混淆了道心、人心之别。“姚江以一段灵明者为性,虽少近里,然所见乃心而非性也。心便有别,但看声色臭味,平时多少耽著,至遇疾病,便生厌恶;遇患难,便不复思想。惟孝弟忠信,则坎壈之中,转见诚笃。至于生死利害,更生精采。故知人心、道心,确然两个。”①综上可见,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不加限定地主张“心即性”“心即理”显然是不合适的。
李光地追根溯源,指出“心即性”“心即理”之说来源于释氏,不但与程朱之学相背,亦不合于孔孟之道。他分析道:
孔子所谓“仁者,人也”,心性之合也。孟子所谓“仁,人心也”,心性之合也。然且有不仁之人,有不仁之心,是心不与性合也。心不与性合,而曰即心即性,可与?不可与?是知孔子所谓人者,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非谓人为仁也。孟子所谓心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非谓心为性也。②
此处,李光地其实亦是借用理学中的心性之辨来阐释孔孟之言。仁义之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培养人的终极目标,而仁义之人与仁义之心便是心与性的完美结合。但是,现实中的人却并不总是表现为仁,有不仁之人,有不仁之心,因而证明现实的人心并不总是与性理相合。同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只是仁义之端,若此善端不能加以护持、扩充,人心亦将流而为恶,故不能以心为性。
在揭露“心即理”说的错误之后,李光地又进一步批判了王阳明“心无善恶”的思想:
象山谓即心即理,故其论《太极图说》也,谓阴阳便是形而上者,此则几微毫忽之差,而其究卒如凿枘之不相入也。近日姚江之学,其根源亦如此,故平生于心、理二字往往混而为一。《答顾东桥书》引《虞书》,断自“道心惟微”以下,而截去上一语,晚岁遂有心无善恶之说。①
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曾说:“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②可见李光地所说的“断自‘道心惟微’以下,而截去上一语”指的便是王阳明故意截去“十六字心传”中的“人心惟危”四字,欲以此隐藏危殆的人心,以便证明“心即理”,进而得出“心无善恶”的结论。
严格说来,王阳明其实并未直接主张心无善恶。其“四句教”中的首句乃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无善无恶所指称的显然是心之本体,而不是笼统地说人心无善无恶。那么,如果明确地说心体无善无恶,或本心即性,李光地是否就能同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面对诸如“姚江之说,谓心自仁,心自义,心自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其不然者,非本心也。以是谓即心即性,殆可与”之类的问题时,李光地回答道:
其言似,其意非。奚不曰仁义之心,道心也;其不然者,人心之流也,则心性之辩明矣。彼丽于孔孟而为是言也,其意则谓心之体如是妙也,故以觉为道。以觉为道,必以无为宗。以无为宗者,道亦无矣。故无善无恶心之体,姚江晚年之说也。其异于孔孟之旨,又奚匿焉?③
又曰:
王说之病,其源在“心之即理”。故其体察之也,体察乎心之妙也,不体察夫理之实也。心之妙在于虚,虚之极至于无,故谓无善无恶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谓心自仁义,心自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本趣也。①
由此可见,李光地对于王阳明“心无善恶”的批评并非完全出于误解。在他看来,所谓心之本体仍是具有知觉作用的心,而不能等同于性。即便阳明将“心即理”“心无善恶”中的“心”解释为本心,也是为了混淆心与性的差别,打着孔孟的招牌,实则强调心性本体虚无、玄妙的特质,从而达到援释入儒的目的。
关于心体的善恶问题,阳明本人的论述并非十分清晰、毫无疑义,其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往往存在互异的表述,而所谓“无善无恶”的确切含义亦是复杂难解。无善无恶究竟是否等同于至善?是没有善恶,还是可善可恶?抑或所说的根本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善与恶?这一系列问题历来争论不休,见仁见智,这里无法一一复述。简单说来,我认为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思想显然吸收、借鉴了佛家特别是禅宗的相关思想,认为心之本体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相对的、具体的善恶,而将其视为一种绝对待、不思议的先天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被称为“至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所说的纯善无恶的至善。它既带有传统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恶意涵,又非伦理学所能完全范围。这一点需要略加说明。
陈来先生曾详细考察了王阳明于不同时期所做的可与“无善无恶心之体”相互印证的各种表述,指出“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一命题强调的是心体所具有的纯粹的无滞性与无执着性,并以此作为个人实现理想的自在境界的内在依据。②应该说,陈来先生的这一论断思路独到,阐发入微,实发人之所未发,但似乎亦不必然要排斥“无善无恶”同时兼具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含义。首先,“四句教”乃阳明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晚年定论,若“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确实不具有任何伦理上的意涵,以阳明之大贤,为何一定要选择使用“善”“恶”这样带有浓厚伦理意味的语词与表达方式,而无视其必然引发的巨大误解与非议?其次,“四句教”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首句与后三句之间应有层层递进、一以贯之的一面,若将首句分割开来单独讨论似乎有所未备。如王门高弟王畿即谓:“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①又言:“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②由此可见,王畿认为心与意、知、物之间乃是体用关系,若心体是无善无恶的,则意、知、物自然也应是无善无恶的。反过来说,针对意、知、物三者所说的善恶显然是指伦理上的善恶,那么心体的无善无恶也应该相应具有伦理的含义。若针对心体所说的无善无恶仅指无滞性、无执着性,那就完全无法得出意、知、物三者皆无善无恶的结论。王畿所理解的“四无”说虽然与阳明的原版有所出入,未必能完全反映其本意,但阳明也并未反对王畿的“四无”说,反而特别赞赏王畿基于首句的理解与阐发,谓:“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又谓:“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③由此可见,阳明所谓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确实具有伦理方面的意涵与目的,从而与正统儒学的性善论产生了巨大乃至根本性的差异。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何当王畿道出他的想法时,会给阳明带来如此大的冲击与惊喜,又是“传心秘藏”“含蓄到今”,又是“天机发泄”“岂容复秘”,并且郑重其事,反复告诫。相较之下,所谓心体的无滞性、无执着性,或者说“无心”“无念”的思想,起码在宋代就已经得到儒者的关注与阐发,恐怕算不上什么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见解。不但程颢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①的说法,就连南宋前期并不以理学闻名的宰相留正亦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天之所以能成造化之功者,以其无容心也。是以生育肃杀自然有至理寓乎其间。夫圣人之心亦如是而已。举天下之事,是非利害杂然至乎其前,而吾一概以无心处之,方寸湛然,处处洞彻,天下之事焉往而不得其当哉!”②由此不难看出,当时这一思想起码在接近理学的士人群体中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同。若阳明所说的心无善恶只是指心体的无滞性、无执着性,又何至于如此隐秘而慎重?
应当说,正是由于王阳明这一思想的模糊性与复杂性,使其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不同目的、立场的学者误解或曲解为心无善恶,从而对王学进行激烈批判,或是彻底倒向自然主义,以此作为放纵身心、肆意妄为的借口。从这一意义上看,李光地虽未直接对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思想内容做详尽的辨析,也未必完全理解其复杂内涵,但又确实抓住了其中的某些要点。一方面,他始终坚持朱子理学关于心性之辨的基本立场,指责阳明在心性问题上故意回避了道心、人心的关键差别;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阳明的这一思想别有授受,乃根源于佛家以知觉作用为性,认心性为虚无的思想,并非出自孔孟本旨。若对这一点不加察觉,以非为是,终将导致一切道德规范与道德法则虚无化的严重后果。也正因为王学的心性思想更多地吸纳了佛教的智慧,而又证以孔孟之言,在正统的朱子学者看来不免似是而非,离经叛道,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与危害性,故李光地要极力辨之。
综上,李光地指出,陆王之学“心性之原既差,则志其所志,养其所养,讲其所讲,行其所行,二本殊归,其道使然。今言陆王之学者,不谓其偏于德性而缺学问,则谓重在诚意而轻格物,此亦朱子论近世攻禅,若唐檄句骊守险者类也。……然则陆王二子之弊其应辨析者,固在心性人道本原之际,不在讲学持守、知行先后之间也”①。在李光地看来,心性乃人之本原,心性论则是学术之源。王学固然存在“偏于德性而缺学问”“重在诚意而轻格物”等问题,但这些都不是要害所在,其谬误根源在于错认心性,故所志、所养、所讲、所行不免皆错。若要彻底辩驳王学之弊,恢复孔孟之真,就不能光在为学方法、修养工夫等处用力,而应该釜底抽薪,于心性大本大原处讨个分晓。
李光坡②的心性思想与李光地相近。根据他的理解,“心”即“神”,主要表现为知觉、运用与主宰能力,而“性”则是内在于知觉的原则与本体,二者紧密关联却并不等同,其根本差别在于性实心虚,存在虚实之不同。故曰:
人身有神有性。神者,灵觉也,视性则微有迹,方诸魂魄精气则妙矣。以其内足以运夫仁义秉彝之良,而外以管乎四支百骸之用,动静由己,变化无方,几几乎性之事,惟有虚实之分耳。③
据此,李光坡指出,心学的主要错误便是将虚灵的知觉混同于作为本质的实理与实性,从而落入释氏“作用是性”之见而不自知。所谓“见云为之际皆明觉为之宰,不复体其所觉之实,而但以所为灵者当之,此守溪‘性至虚至灵,如鉴之悬,物来则照,物去不留’之言。阳明表而出之,而不悟其仍于释氏之见”④。而这一思想的危害则在于将道德原则置于人心之外,进而导致“仁义礼智由外铄我”的结论,“使小慧之徒高者逃于幽禅,卑者至于狂悖”①。李光坡同时指出,心性之辨还与理气之别有关。性即是理,心虽不专是气,但包含气的因素。必先有知觉之理,后理与气合,心方能知觉。因此,若能明白“理气合而成觉”的道理,则知心不是性,亦不当以无善无恶名心。
综上,李光坡总结道:“能觉者,心之灵也;所觉者,性之理也。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嘑尔蹴尔而羞恶。知恻隐、知羞恶者,神也。伤之切,痛之深,无所为而为;羞之甚,恶之挚,宁身死而不受,是专虚灵之神乎,抑有实然之性乎?是自外照乎,抑由中出乎?是理在气中发见乎,抑超于气上而为之主乎?然则必有是性为所知所觉之实际而不沦于虚,为能静能动之本体而不杂于气也,明矣。”②
童能灵③亦站在朱子理学的立场上,对心性问题做了较为集中、系统的剖析与论述,批判了陆王的心性思想。童能灵认为,“天地之间,止此理、气二者而已,此即古今学术之辨所由分也”④,因而主要从理气论的角度来理解和阐述心、性概念及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于性,他认同程朱“性即理”之说,特别强调性与人之间的亲切关系。故曰:
以理言之,则为当然之则,所谓“有物必有则”是也。其具于人心,即在人之则,而为性者也。⑤
性固是天理,然必就人生所禀言之,乃见性之所以得名也。不然,何以不即谓天理,必别之曰性耶?谓之性,则如云水性寒、火性热之性。盖人但知有此生则有此性,不知须有此性始有此生也。如水必须有寒之性方凝而成水,火则必须有热之性方发而成火,人则必须有生之性方有此生而为人也。①
性固是理,但须看到理之在人最为亲切,方见其为人之性也。盖人之生,气聚而生也。气之所以聚而生,则理为之也。②
在童能灵看来,人由气聚而生,但气不能自生,也不能自行,气的聚散变化皆理为之。理为气之主宰,亦为气之所以然者,因而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与基本前提,“须有此性始有此生”。理又根植于气之中,气为理之载体。天理须为人所禀,内在于人心之中,方成其为人性。所以说性是于人最为亲切之理。
而心对于童能灵来说,则是一个属于气的概念,属形而下者,其特性为虚灵不测、神明之妙。他说:
以气言之,则气之粗者凝而为形,其精爽则为心。心之精爽至于神明,故其体虚而无物,其用灵而不测。③
盖(心)只是气也。气之粗者,凝而为形,其精爽则为心。气之精爽,自能摄气,此心所以宰乎一身也。且既曰精爽,则亦无气之迹,而妙于气矣。顾只是气之精爽,非形而上之理也。④
由此可见,在童能灵的理解中,性属理,属形而上之道,心属气,属形而下之器,故心不能为性,心不能为理明矣。同时,心之虚灵亦表现为一种主宰、运用、知觉的能力。童能灵认为,人得至精至灵之生气以为魂魄,魂为阳之神,魄为阴之神,魂魄之合为心,便有主宰运用、知觉记当的作用。因此,心本身虽无声无臭,却能觉声觉臭,认识各种事物与义理,主宰一身而运用之,而性则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显然不具备任何运用与知觉能力,这也说明心不能为性,心不能为理。所以他说:“性无为而心有觉,觉即精爽之所为也。性则是理,虽所觉者亦是理,而理初无觉也。此形而上下之分。”①
童能灵认为,心所具有的神明之妙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一曰神通,贯幽明,通远近,无所隔碍也;一曰神变,应事接物,变化不测也。然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变二者而已。通与变是其神处,而明在其中矣。②
心之所以能通、能变,是由于心乃气之精爽,“清之极矣,无粗浊,自无渣滓昏隔,如何不通”,“精极则变,无粗浊,故无滞碍也,如何不变”。③据此,童能灵提出,心虽属气,而其精爽之至却可通极于性,故胡宏谓“心妙性情之德”,朱熹言“心妙众理”。“不然,性即理也,理寓于心,岂不反为心所昏隔耶?”④若心与性相互隔绝,不能相通,则心中之理亦将为心所遮蔽阻隔,无法发而为用。正因为心具有如此的神明之妙,又可通极于性,故而许多学者便容易将心性混为一谈。对此,童能灵强调:“此又须知心之为物,只是气之精爽,其受气之浊者,亦有昏隔时。”⑤这就是说,心虽非形气之粗,但毕竟属气,不免有时要为气之粗浊者所遮蔽障碍,不能如性一般纯粹至善。心以性为体,其气之精爽可通极于性而有神明之妙,但不能因此认定心即是性,心即是理。
对于人性,童能灵进一步指出:“人者,天地之生而万物之灵,故其性无所不绾。所谓万物备于我者,非独备其影象也,即万物之所以为物者绾于此焉。”①由于天理包罗万有,万分具足,而人作为万物之灵,禀受天理之全体以为性,人性就不仅是人自身的根据与规定,也应该包括万物之所以为物的根据与规定。同时,人性之所以能够感物而动,发而为情,亦是因为人性中包含物理,性理与物理只是同一天理。“性所以感物而动者,性在内,物在外,然在内之性不是别物,只是理也。所谓理,便是在外之物之理也。舍物理,无以为吾之性矣。物理即吾性之理,此天下所以无性外之物也。”②因此,人性与性理中显然包含了物理、事理、情理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并不只局限于道德规定与道德准则等伦理范畴。故曰:
凡天地之道,圣人之蕴,措之为礼乐刑政,垂之为《诗》《书》《易》象者,皆是理之所蟠际,即皆是性之所充周。而日用彝伦、视听言动之间,须臾而离之,则是自失其则而不诚无物矣。是以圣人之教,必使择之精而执之固,有以完其所以为性者焉。此其学固非可以一朝顿悟而一悟无余者矣。③
又曰:
吾性之理即物理。天下之物理多矣,大而天地,细而昆虫草木,皆各有理。自人言之,大而五伦,细而三百三千,各有一理,千条万派,用各不同,而皆具于吾性之内。……万理只一理,故性具万理,无头项杂凑之嫌。但性只一理者,正指未发之前,内无感触,端绪未见,条理未分,浑然而一理耳。……当此之时,气不用事,心理为一,本难分别,故于所谓正而不偏、亭亭当当者,理固宜然,而心亦如是也。学者于此时实难见得亲切,不若即理之万分、散于事物者一一穷之,辨其万分者之不出一理,庶几心有把握,而涵泳之久,涣然释,怡然顺矣。①
这里所说的“一朝顿悟而一悟无余者”,以及只求“一理”而不顾“万分”的为学方法,显然都是针对被目为禅学的陆王之学。
对于陆王心学一派的学者所宣称的种种神秘的顿悟体验,童能灵并不否认这种体验本身的真实性,而是通过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指出其只不过是来源于心体虚灵不测、神明之妙的特性。他说:
心之精爽至于神明,故其体虚而无物,其用灵而不测。方其未用也,寂然而虚;及其既用也,亦寂然而虚,则其方用之际,亦谓必有常虚常寂者存于其中,而不得以心思求之,恐心思之有着而非虚也;不得以言语求之,恐言语之外喧而非寂也。②
正是由于心体虚灵不测,难以迹求,人们在追求心中存在的“常虚常寂者”时,便不能使用语言文字、逻辑思维等日常手段,因而往往容易陷入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境界之中。“心思路绝,言语道断,惟静惟默之际,而其为神明之本体,静极当动,敛极当发,介然有顷之间而偶尔感触,光明呈露,自觉自知,遂诧为神奇,得未曾有他人不见,师友莫与,而惟我独自得之者矣。……又有一种,静默之久,神明未瞑,亦未发用,迷离惝恍,虚实之间,有影象参差呈露于前,如睡初觉,如梦中见,原非实有,则遂以此为万物皆备之象呈于我矣。”③童能灵认为,这种神秘体验至多只是心体在极端静默状态下的一时呈露,而被偶尔感触,甚至是一种虚实之间迷离惝恍、真伪莫辨的幻觉、幻象,并非对于性理的完整、客观认识,自然也不具备他们所宣称的唯我独得、一朝顿悟、一悟无余的意义。
据此,童能灵指出,不论是陆九渊闻鼓声振动窗棂而豁然有觉,还是王阳明龙场中夜悟道,抑或徐仲试镜中看花,杨慈湖鉴中见象,“自穷理者观之,此皆心之神明不得循其寂感动静之常,而束于空寂,为之变现光影如此。既已自为之眩而不自知,遂欲保以终身,惟恐或失。此正朱子所谓禅家作弄精神,到死不肯舍放者也。嗟夫!以心为理,此势必眩于心而一于虚寂之见者,必不得与事相操持,泛应之际,涉而不有,日用彝伦之地,皆归之于浮薄不可止矣。……且夫虚寂之体,岂得不以礼法为束缚而废弃之哉?”①在他看来,陆王之学之所以将主静、顿悟作为最重要的为学方法与修养工夫,其根源还是在于误认心性,以心为理。若以心为理,一味地追求心之神明,必然会扰乱心性本身寂感动静的常态,陷入虚空寂灭的状态之中,从而执着、迷惑于心中闪现的虚幻光影,将其认作世界的实相或本质,并冀图保任终身。童能灵认为,这实际上正是禅家在主观上作弄精神的把戏,而非对于天理之实实有所得,学者若满足、沉溺于这种虚无高妙的境界之中,必将使心与现实事物相割裂,甚至以万事万物为虚幻,从而导致对日常的躬行践履、应事接物、日用彝伦等道德行为与道德规范的忽视和荒废。
此外,对于心与理的关系,以及心之神明的来源问题,童能灵主张心本于理,但心非即理。在他看来,人之一身止理、神、气、形四者而已。推其所由生,则“理生神,神生气,气生形,一以贯之也。……理生神,即所谓精爽也”②。理生心之神明,而其本身即寓于神明之中,故曰心具众理。前面曾经提到,心所具有的神通、神变等神明之妙是由于气的至清、至精、至灵,而追根溯源,又皆根源于理。理一分殊,就“理一”观之,“非独一身之内只此一个心……天地人物止此一个神明。原只一个,如何不通?原只一个,呼应自灵”③;就“分殊”观之,理一而散万心、应万心,心如何不通?理一而万、万而一,心如何不变?故曰:“神明之妙本于理。”①童能灵又以动静言心之神,而以理为所以动静者。有所以动静之理,方有动静之心,而心之动静又主宰形体之动静。童能灵指出,朱熹论《太极图》,以动静为心,以太极为性,性具于心,性与心本无先后可言,但据《太极图》推之,太极为动静之根底,性则当为心之根底,亦可证心之妙本于理。若从反面来看,世间虽有假仁假义之心,但这并非仁义之理本身为假,而是人在理解、运用上出现了偏差。所谓“假仁者不仁,苟无仁,彼安所假耶?假义者不义,苟无义,彼又安所假耶?……盗跖之不仁甚矣,不义亦甚矣,然尝以分均出后为仁义矣。假令跖不为盗,而以其分均者行赏,出后者居殿,谁得拒之仁义之外哉?乃知人心只是此理也,小人外是亦无以行其恶。故曰心本于理”②。
综上可见,童能灵虽然非常重视心的主宰、知觉的作用与能力,认为“天地之大,古今之远,心之所存,应念即至,乃知天地人物止此一个神明。……此心神明便是天之神明也”③,但却能始终恪守朱熹“性即理”的基本原则,强调心以理为本,理为心之神明之根基,从而明辨心性理气之异同,有力地批驳了陆王“心即理”的心性思想。
同样,蓝鼎元④亦认为,陆王之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根本差别并不在于是否讨论心,或者是否重视心,而在于对心性的不同理解。他说:
圣贤所以别于异端,其惟心学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千载心学之祖也。圣贤以道心为人心之主,异学养人心而弃其道心。故虽皆以心学为名,而是非邪正,相似而实不同者在此。①
蓝鼎元这里所说的异端,除了释、道二教之外,显然也包括陆王之学在内。蓝鼎元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句是义理之源、心学之祖,因而也是判断学问、义理是非真伪的根本标准。在他看来,朱子学明辨道心、人心,主张以道心主宰、制约人心,而陆王之学则忽视乃至泯灭道心、人心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分歧,从而导致养人心而弃道心。因此,二者虽然都以心学为名,但其中却隐含着是非邪正的根本区别,言相似而实不同,只有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正统儒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心学。
蓝鼎元进一步指出,人心以虚灵为特点,根源于知觉,而道心则根源于虚灵知觉之义理,故道心主宰人心。朱子学言心注重心的义理层面,故能以道心统率人心,培养心中的仁义礼智,使心的知觉作用能够符合道德法则的要求。而佛老与陆王之学则仅以知觉作用言心,舍性理而专言知觉,故不学不虑,不假修为,于一切事物都不理会,终日只是完养其精神魂魄,希望完全摒除心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知识与事物,必然导致以人心作道心。故曰:
主于义理者,惟恐义理不明,或有非理之视听言动,则失其所以为心。故必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而涵养省察,不敢有一息之或间。由是而为圣为贤为豪杰,皆此道心为之也。主于知觉者,则止欲全其知觉,惟恐心泊一事,思一理,或扰其昭灵寂静之神,故不顾善恶是非,不立语言文字。若老氏之无视无听,抱神以静,佛氏之净智妙圆,识心见性,象山之瞑目静坐,收拾精神,白沙之虚灵万象,阳明之良知,皆误以人心为道心者也。②由于陆九渊和王阳明都标榜自己的学术直承孟子而来,而孟子又特别关注心性问题,于儒学心性论多有开辟、发明之功,所以便不免有人产生疑问,认为陆王的心性思想皆本于孟子,似乎不应以异学视之。对于这一观点,蓝鼎元明确表示反对。他说:
孟子所言,仁义之心也;陆子所言,昭昭灵灵之心也。孟子求放心,必曰学问之道是教人读书穷理,主敬求仁者也。陆子以闭目静坐为求放心,是教人屏事物,绝思虑,废语言文字意见,即心是道,明心见性者也。言似同而旨不同,恶可以诬孟子。①
在蓝鼎元看来,孟子所说的心是主于义理的仁义之心,而陆王所说的心则是主于知觉的虚灵之心。孟子以读书穷理、主敬求仁为学问之道,注重内外交修并进,以此求放逸之心,而陆王则以闭目静坐为求放心的工夫,欲使人摒除事物,断绝思虑,以心为理,取消一切读书讲论与经典注疏,显然是佛老一路的思想,从而与孟子之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由此不难发现,蓝鼎元和其他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大都清楚地认识到,性与心、道心与人心的区分和差异在朱子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以心为理,以人心为道心正是陆王之学心性论与朱子学心性论之间的根本差异,也是陆王之学之所以错误的根源所在。若是否认性与心、道心与人心之间的区别,必然以个体的情感、欲望、意见为天理,从而导致是非善恶的混淆与道德秩序的崩溃。只有坚持以义理规范心,以道心统率人心,才能为善去恶,将人从世俗的功利境界提升到超越境界。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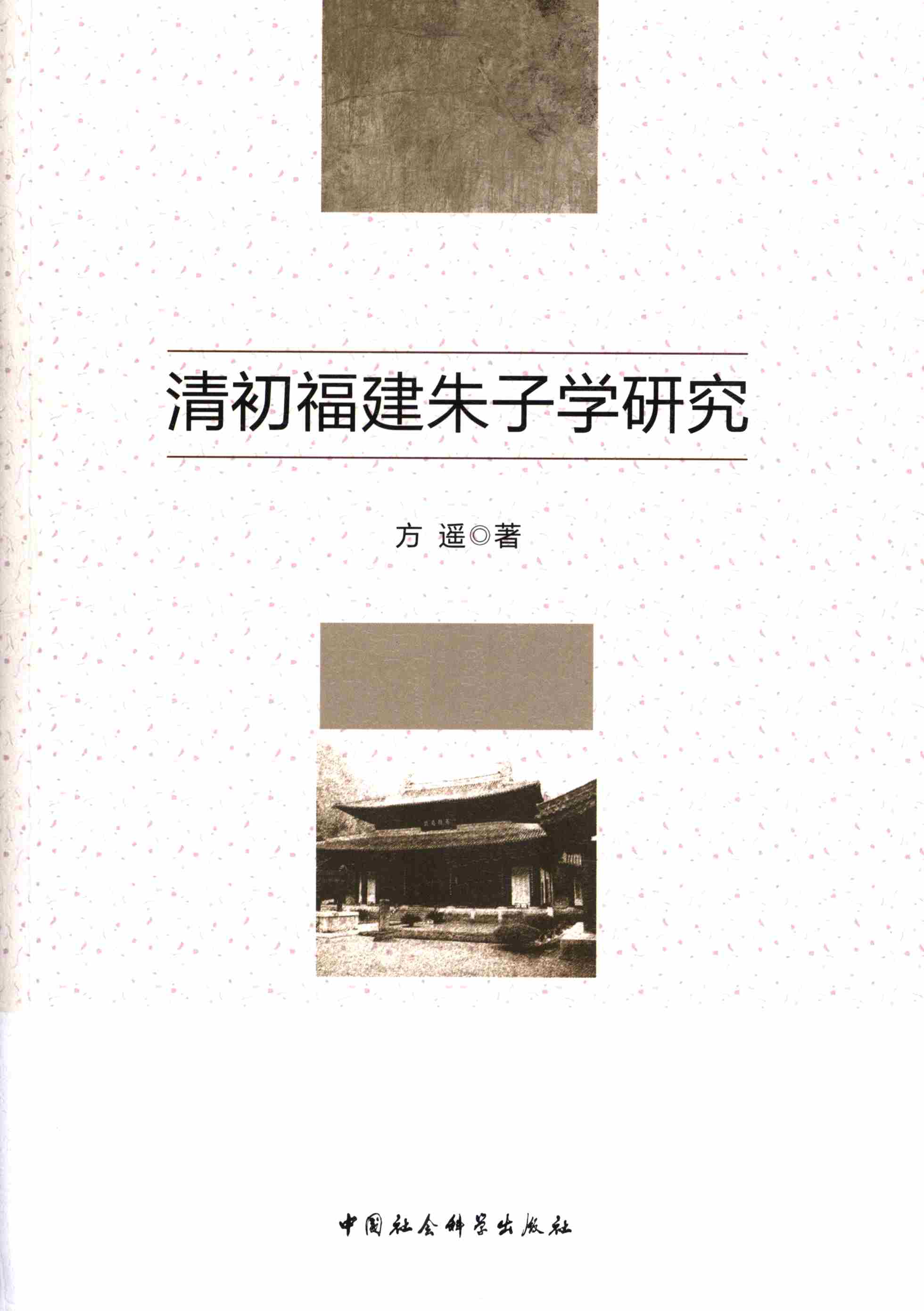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