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疑录》质疑《论语集注》述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93 |
| 颗粒名称: | 二、《我疑录》质疑《论语集注》述评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165-175 |
| 摘要: | 本文主要探讨了《论语》中关于文质关系的问题,并对朱熹的《论语集注》进行了质疑和探讨。其中涉及了对《论语》中某些章句的断句和释义的异议,以及对文质关系中本末轻重之分的辨析。 |
| 关键词: | 清代 陈德调 基层学者 |
内容
《我疑录》一卷,所疑者唯朱熹《论语集注》,书中针对朱熹关于“贤贤易色”“退而省其私”“哀公问社章”“君子怀德(四句)”“孟武伯问子路章”“伯夷叔齐不念旧恶”“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井有人焉章”“子见南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子行三军则谁与”“三以天下让”“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季氏富于周公章”“同也其庶乎屡空”“子畏于匡章(注阳虎曾暴于匡故匡人围之)”“莫春者至末节”“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樊迟请学稼”“宪问耻节”“晋文公谲而不正章”“如其仁如其仁”“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道不同不相为谋”“师冕见”“有攸不为臣东征(周公无诛管蔡之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节”等29条的解释,逐一质疑,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论语集注》断句提出异议
《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朱子《集注》云:“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坏也。憾,恨也。”陈德调曰:
按:此句读之错也。以“与朋友共”成句,“敝之而无憾”成句。敝之属友,则憾字自应改作恨字。不知无憾是自快然心慰,与“愤”“恨”字全不相假,且如此亦不过一豪侠行径耳,与圣贤心事何与?愚意当读“与朋友共敝之”成句,“而无憾”成句。言愿有此车马、轻裘与朋友久共直至敝之,而此心始快然无憾。敝之,不属己,亦不属友,极言其志同道合,愿与久处,以辅吾仁。
关于《论语》此章的断句,历来有两种意见。其中朱熹《集注》的断句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是“敝之”前属。后一种断句,最早见于《白虎通·纲纪篇》引《论语》子路云:“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张载《论语说》:“仲由乐善,故车马衣裘与贤者共敝。从‘愿’字至‘敝之’字为句。”陈德调认为,朱熹《集注》断句所表达的意思,充其量不过一豪侠行径,而后者断句则表示未敝之时已有共敝之意,语意直接,尤得圣贤气象。比较而言,陈德调的意见似更能体现仲由本意。唐宋人诗歌中,亦多取“共敝之”之意,如唐马戴《边馆逢贺秀才诗》云“鹿裘共敝同为客”,张文昌《赠殷山人诗》云“同袍还共敝”,苏轼《戏周正儒坠马诗》“故人共敝亦常情”,可见“共敝”是一种为大家普遍认同且具有圣贤气象的解释。
(二)对《论语集注》释义提出异议
《论语·里仁》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集注》云:“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陈德调则曰:
圣人下字,各有攸当,非若文士之变易求新也。如他处言怀居,此变易怀土。他处言放利喻利,此变言怀惠。夫怀土非怀居比也,怀居者有纵逸自安之意,土则人之所赖以生。先王别五土之宜以利民,故曰“厥心臧”,惟土物爱,怀之不为过分。怀惠又非贪利比也,贪利者有非分争夺之思,惠则人自与我,或出于君上之恩施,或出于朋友之馈遗,怀之,岂尽丧廉?且变惠言利,而以为小人怀利可也,若变怀言贪,而以为君子贪刑,不大笑话乎?盖此君子小人以分位言,犹如士农之别。言君子当怀德,不可如小人之仅怀土也。君子当怀刑,不可如小人之仅怀惠也。德与土皆我之所固有者,刑与惠皆人之加诸我者,故相对成文。
比较而言,朱熹《论语集注》简洁明了,释义到位,而陈德调的解说似乎透进一层,也更细腻,但未必够得上疑朱,其实是对朱熹诠释的一种引申,起到丰富、补充与发挥作用。
《论语·颜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朱子《集注》:“言文质等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陈德调曰:
文质两件,自是对待物事可以相胜言,不可以轻重本末言。大抵文一而已,而质有三样:一是质直之质。主内心而言,文质之所从出者也。此是大本,非此不但文有伪,即质亦有伪,《记》所谓“忠信之人可与学礼”是也。一是质干之质。主植基于事先者而言,文质之所由附者也。一是质朴之质。主措施于事物者而言,虽亦从大本而出,然可与文对言,不可与末对言者也。假以一人之身为质干,而文质二者从此附焉。有不衫不履者,有整齐修饰者,不可以不衫不履者为本,整齐修饰者为末也。又以画之粉地为质干,而文质二者从此附焉。有轻描淡写者,有着色渲染者,不可以轻描淡写者为本,着色渲染者为末也。草野之间多简略,冠裳之会盛繁华,不可以草野之间为本,冠裳之会为末也。礼或多之为贵、少之为贵,不可谓少者为本,多者为末也。又有同是礼文之中,而又质之为贵、文之为贵,不可谓贵本而贵末也。以两朝之规模气象言,商尚质,周尚文,不可谓商尚本,周尚末也。以一朝之规模气象言,郁郁乎文哉,不可谓郁郁乎末哉也。其轻重之说,亦即仿是。至若在天为云霞,在地为草木,在人物为须发毛羽,此天然之文质,又是一种。
文质先后之分则有之,而后者较重于前。草衣卉服,衣之始也,今人可以供曳娄乎?茹毛饮血,食之始也,今人可以给饔飱乎?至于明堂清庙之间,太羹玄酒,大辂越席,不过略存一二,以昭原始,其它冠裳带舄、尊斝笾豆、羽籥琴瑟,非极情致文不足以将诚敬而鬼神亦不之享,由此观之,文重乎,质重乎?
陈德调此论,仍是从毛奇龄而来。《四书改错》云:“《礼》凡言文质,只是质朴与文饰两相对待之辞,并无曰质是本,文是末者。……向使质是忠信,则文不当胜忠信;文是礼,则质又不当胜礼。相胜且不可,何况相去?朱氏既引杨说,于《质胜章》疑为质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错,而此竟直称质为本,文为末,则错认假逢丑父为真齐顷公矣。”陈德调说:“文质两件,自是对待物事可以相胜言,不可以轻重本末言。”这显然是对毛奇龄的继承,但他通过对“质有三样”的类型分析,然后再来谈文质之关系,却是《论语》诠释史上能够把这个老问题讲清楚的人。
《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朱熹《集注》云:“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盖圣人于此,非作意而为之,但尽其道而已。尹氏曰:‘圣人处己为人,其心一致,无不尽其诚故也。有志于学者,求圣人之心,于斯亦可见矣。’范氏曰:‘圣人不侮鳏寡,不虐无告,可见于此。推之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矣。’”陈德调曰:
师冕,瞽者,非能贸贸然升夫子之阶,登夫子之席也。其自未入门以前,一路便有相者,何待升阶入席而始赖夫子之告?如谓相者告之,夫子又从而告之,则一堂嘈杂,成何体统。抑知瞽目之人,每到一处,惴惴然惟恐其失仪,夫子曲体之,故于其及阶也,不待相者之告而遽告之,曰:“阶也。”其及席也,不待相者之告而遽告之,曰:“席也。”其一片肫诚,俱在无意中流出。迨闻子张问,又不便明言其故,姑应之曰:“固相师之道也。”然而斯道也,非夫子则莫能尽矣。
陈德调的理解,相对而言更能设身处地,还原当时实际情景。尤其是说孔子每到一处,抢在相者之前而遽告之,这等诚敬之心,自然让人感慕于千载之上。当子张问起“与师言之道与”?孔子不过轻描淡写回以“固相师之道也”。其平常自然如此。陈德调对此章的体味,既合乎人之常情,又贴近圣人之心,较之前注,可谓略胜一层。
(三)对《论语集注》古今人物评价提出异议
《论语·公冶长》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朱熹《集注》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称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其介如此,宜若无所容矣;然其所恶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陈德调则曰:
此当与孟子之言参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其言皆从恶恶正面极力形容。圣人却把他不见有恶时翻转一看,觉更清到极处。“怨是用希”,为不善学夷、齐者进一良方,其实夷、齐意中一概不计。“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窃谓群圣皆可以量言,惟夷、齐不可以量言。盖夷、齐心头譬如一面实镜,本无尘滓,自然些子难容,及既脱去,仍是一片空明,含容宽恕,概无所用。
朱熹对《孟子》的引用,重在一个“介”字,但即使如夷、齐有如此之介,仍对所恶之人,保持适度的宽容,因此别人对他们也“怨是用希”。朱熹对“怨是用希”的解释,立足于他人对夷、齐之态度与评价,着眼于日常层面,从人之常情道来。而陈德调对《孟子》的引用,则重在一个“清”字,立足于圣人的自我完善,意若对旧恶,一概不计,则我之心中自无怨恨可言。陈德调此处发明,其实是对明代林希元之说的发挥。旧恶,就是夙怨。不念旧恶,就是不念旧仇。林希元《四书存疑》中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盖所恶者,恶其恶也,非恶其人也。因其自取,非出于有心也。若恶其人而出于有心,则追念不忘矣。”陈德调所谓“夷、齐心头譬如一面实镜”,与林希元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似乎相同,所不同者陈德调比林希元对圣人明心见性的发挥更为彻底。林希元的圣人心如明镜止水,其恶虽出于无心,但仍是有恶的;而陈德调的圣人之心“本无尘滓,自然些子难容,及既脱去,仍是一片空明,含容宽恕,概无所用”。本来无怨,何生怨心?干净彻底,不落一点尘埃。
《论语·宪问》:“如其仁,如其仁。”朱子《集注》:“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陈德调曰:
按:夫子满口许管仲之仁。《注》言:“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则是在外者一仁,而在内者又一仁也。然则有大不仁者于此曰:“吾虽无仁人之事,而固有仁人之心矣。”可乎?
照陈德调理解,仁无分内外,故不可将仁心与事功折解。如果说管仲未得为仁人,则其事功就未必合乎仁道。管仲为霸者之佐,自始至终事业不过以力借仁而已。孔子所言“如其仁”可能就不是朱熹《集注》说的“深许之”之意了。《论语》其他地方涉及管仲,孔子但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按陈德调的意思,《集注》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与事功为二,这是很容易产生逻辑上漏洞的。
(四)对《论语集注》释礼提出异议
《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朱子《集注》云:“南子,卫灵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卫,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故不悦。矢,誓也。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谓不合于礼,不由其道也。厌,弃绝也。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陈德调曰:
《注》:“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毛西河谓其于礼文无据,而究未明子路所以不说之故。盖此与主颜仇由为一时事。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孔子曰:“有命。”进以礼,退以义。今又去见南子,则仍是非礼之进,与主弥子何异?故子路不说,而非谓小君无可见之礼也。“否”字,亦跟弥子来,盖主弥子,夫子之所否者。今见南子,人亦疑夫子为否,故誓言以明之。“予所否者”,古者誓词多用所字打头,如“所不与舅氏者”之类。“天厌之,天厌之”,言若予所否者,则天应早绝我,复何能行道于天下哉?从古宵小多托名流以自重。弥子不得于已则假南子以要之,南子之请见,亦必挟君命先之,故不得不见。要之,圣人道大德宏,其所见者即是圣人之礼,何必于礼外求礼哉?
在《论语》里,子见南子是一件很令后儒困惑的事情,也是《论语》里获得注释最多的章节之一。前人注释归纳起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子见南子是否合礼,二是子路为何不悦,三是孔子解释表达了什么。朱熹之前,何晏《集解》综合孔安国等的意思,认为孔子之见南子,乃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欲因而说灵公使行治道”。“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个比较合乎常情的解释。朱熹《集注》所言“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引来清初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的反驳,他说:“古并无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遍考诸《礼》文及汉晋唐诸儒言礼者,亦并无此说,惊怪甚久。及观《大全》载朱氏《或问》,竟自言是于《礼》无所见,则明白杜撰矣。”但朱熹用一“盖”字,有推测之意,不可作定论。而陈德调的意思是,对于孔子之见南子一事,应与子见弥子一事作同样看待,且二者之间还有联系。他认为子见南子一事乃因弥子引起,弥子假南子以要之,南子又挟君命以先之,孔子不得不见。既是不得不见,则与合礼或不合礼无涉,故不必于礼外求礼。言下之意,子路不悦者,其实是凭己之力来衡量圣人的“道大德宏”,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要之,这其实不就是朱熹所谓“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吗?当然,陈德调最终要表达的是,朱熹完全用不着虚构一个合乎古礼来为孔子开脱,因为圣人怎么着都是有其道理的。
(五)对《论语集注》道学之论提出异议
《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朱子《集注》云:“尹氏曰:‘用舍无与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颜子几于圣人,故亦能之。’”陈德调曰:
不是用则行,舍则藏。不是用我则行,舍我则藏。两“之”字,俱有真实经济。以颜子言之,定是四代礼乐言用之,则把许多经济一齐展布出去而行之,不是空行。舍之,则把许多经济敛藏有待而藏之,不是空藏。这个本领,惟我许尔有是夫。与,犹许也。惟之为言独也。独我许尔,言他人不能知也。子路疑颜子文事有余而武备不足,故以行军为问。岂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正惟颜子优为。乃知平日所藏,无所不有也。前后三“与”字,一气相应。
自来对“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解释,认为惟孔子和颜渊可以做到,而能做到者便是圣人。圣人的标准是知进退存亡,乐天知命。但陈德调则立足于两“之”字内涵分析,认为“俱有真实经济”,不是空行,也不是空藏,即是说圣人也有真本领,而非只会玩假动作。前者解释是心性之学范畴,后者则是事功之学了。所以,接下来针对朱熹引谢氏语,陈德调更是以事功之学直接来驳心性之学了。
《论语·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朱子《集注》曰:“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谢氏曰:‘圣人于行藏之间,无意无必。其行非贪位,其藏非独善也。若有欲心,则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颜子可以与于此。子路虽非有欲心者,然未能无固必也,至以行三军为问,则其论益卑矣。’”而陈德调曰:
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呜呼!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子论政,足食兼以足兵;朝廷设官司徒,不废司马;禹敷文命,而有三苗之征;惟师尚父,而膺燮伐之任,岂尽卑耶?且孔子不与子路,则所与者,必仍属颜子。岂颜子亦卑耶?嗟乎!南宋之蹙,已甚矣!忠贞百战者,斧锧一时;高谈游食者,俎豆千古,则其谓之卑也,亦宜。
朱熹引“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陈德调举南宋困厄之例,反问“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并将谢氏之论斥之为“高谈游食”之言。关于此章的解释,概括而言,也有三种意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心性派,二是以毛奇龄为代表的事功派,三是以周宗建为代表的折中派。毛奇龄说:“行三军非细事,自神农伐补遂,黄帝伐蚩尤而后,行军皆圣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于《师卦》曰:‘开国承家。’又曰:‘可以王矣。’未尝卑也。况临事而惧,正夫子慎战之意。好谋而成,正夫子我战则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语,并不贬抑,而读其书者反从而鄙夷之,可乎?”显然,陈德调的意见是从毛奇龄而来。第三种折中派意见,周宗建《论语商》云:“大抵圣贤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不作两橛,故以此出处则舒卷无心,绝不著些豪意见。以此任事,则锋镝消除,绝不露一豪气。子路三军一问,色相炽然,故夫子把经世大机局点化之,亦正欲其体认到里面去也。临事二语,此是千古圣人兢兢业业之心肠。”如此看来,周宗建是能把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综合加以解说的学者。
《论语·先进》“莫春者”至末节,朱子《集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乎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者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陈德调曰:
此节内外,《注》直说到天地同流、尧舜气象上去。窃以为,圣学不空言气象也。且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点盖谓三子各有用世之撰矣,既究竟知我何人,用我何日,点则不预言,撰亦并不待人知。现在春服可服则服之,童冠可与则与之,舞雩沂水可风浴则风浴之。倘异日知我有人,亦且再作理会,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然已不觉将夫子不怨不尤心事信口道破,故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若夫以泉石啸傲为清高,贤劳鞅掌为多事,此西晋祖尚玄虚之习,为吾儒所痛疾者,岂圣人所乐与哉?又以为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迥不侔矣,尤所未晓。……说此章者,能将开首“不吾知也”及“如或知尔”句,眼光牢注,便是善读书人。点虽狂士,既受夫子之裁,何至一味空狂毫无实际。“不吾知也”,自必数点于诸贤之中;“如或知尔”,岂能推点于诸贤之外?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首节记诸贤之侍坐,如许多才而使之邱壑终老,为诸贤惜,正为自身惜也。“则何以哉”,不是忧其无具,正欲把各色珍宝大家展玩一番。吾故谓此章,头一个悲者夫子,第二个悲者曾点,第三个悲者子路。
《论语·先进》此章,历来解释基本上也是两种意见。一是以朱熹《集注》为代表,从圣人气象上去说。当然,朱熹《集注》实际上也是承皇《疏》、韩愈、程子而来,并有所取。二是以黄震、杨慎为代表,从“答问之正”角度去说。黄震《黄氏日抄》云:“三子言为国之事,皆答问之正也。曾皙,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之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归咏之言,若有触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晳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黄震还批评有些学者过度诠释孔子的意思,他说:“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以曾晳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晳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谈禅”已经是很严重的用词了。明代杨慎《升庵全集》也说:“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语,《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后来陈澧《东塾读书记》亦云:“此则程、朱之说亦有未安。”顺着黄震的思路,而陈德调甚至干脆说:“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但他说曾点之言,“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则又多少有些误解了。可是,他从心理学角度说:“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仍为体贴之言。
(一)对《论语集注》断句提出异议
《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朱子《集注》云:“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坏也。憾,恨也。”陈德调曰:
按:此句读之错也。以“与朋友共”成句,“敝之而无憾”成句。敝之属友,则憾字自应改作恨字。不知无憾是自快然心慰,与“愤”“恨”字全不相假,且如此亦不过一豪侠行径耳,与圣贤心事何与?愚意当读“与朋友共敝之”成句,“而无憾”成句。言愿有此车马、轻裘与朋友久共直至敝之,而此心始快然无憾。敝之,不属己,亦不属友,极言其志同道合,愿与久处,以辅吾仁。
关于《论语》此章的断句,历来有两种意见。其中朱熹《集注》的断句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是“敝之”前属。后一种断句,最早见于《白虎通·纲纪篇》引《论语》子路云:“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张载《论语说》:“仲由乐善,故车马衣裘与贤者共敝。从‘愿’字至‘敝之’字为句。”陈德调认为,朱熹《集注》断句所表达的意思,充其量不过一豪侠行径,而后者断句则表示未敝之时已有共敝之意,语意直接,尤得圣贤气象。比较而言,陈德调的意见似更能体现仲由本意。唐宋人诗歌中,亦多取“共敝之”之意,如唐马戴《边馆逢贺秀才诗》云“鹿裘共敝同为客”,张文昌《赠殷山人诗》云“同袍还共敝”,苏轼《戏周正儒坠马诗》“故人共敝亦常情”,可见“共敝”是一种为大家普遍认同且具有圣贤气象的解释。
(二)对《论语集注》释义提出异议
《论语·里仁》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集注》云:“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陈德调则曰:
圣人下字,各有攸当,非若文士之变易求新也。如他处言怀居,此变易怀土。他处言放利喻利,此变言怀惠。夫怀土非怀居比也,怀居者有纵逸自安之意,土则人之所赖以生。先王别五土之宜以利民,故曰“厥心臧”,惟土物爱,怀之不为过分。怀惠又非贪利比也,贪利者有非分争夺之思,惠则人自与我,或出于君上之恩施,或出于朋友之馈遗,怀之,岂尽丧廉?且变惠言利,而以为小人怀利可也,若变怀言贪,而以为君子贪刑,不大笑话乎?盖此君子小人以分位言,犹如士农之别。言君子当怀德,不可如小人之仅怀土也。君子当怀刑,不可如小人之仅怀惠也。德与土皆我之所固有者,刑与惠皆人之加诸我者,故相对成文。
比较而言,朱熹《论语集注》简洁明了,释义到位,而陈德调的解说似乎透进一层,也更细腻,但未必够得上疑朱,其实是对朱熹诠释的一种引申,起到丰富、补充与发挥作用。
《论语·颜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朱子《集注》:“言文质等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陈德调曰:
文质两件,自是对待物事可以相胜言,不可以轻重本末言。大抵文一而已,而质有三样:一是质直之质。主内心而言,文质之所从出者也。此是大本,非此不但文有伪,即质亦有伪,《记》所谓“忠信之人可与学礼”是也。一是质干之质。主植基于事先者而言,文质之所由附者也。一是质朴之质。主措施于事物者而言,虽亦从大本而出,然可与文对言,不可与末对言者也。假以一人之身为质干,而文质二者从此附焉。有不衫不履者,有整齐修饰者,不可以不衫不履者为本,整齐修饰者为末也。又以画之粉地为质干,而文质二者从此附焉。有轻描淡写者,有着色渲染者,不可以轻描淡写者为本,着色渲染者为末也。草野之间多简略,冠裳之会盛繁华,不可以草野之间为本,冠裳之会为末也。礼或多之为贵、少之为贵,不可谓少者为本,多者为末也。又有同是礼文之中,而又质之为贵、文之为贵,不可谓贵本而贵末也。以两朝之规模气象言,商尚质,周尚文,不可谓商尚本,周尚末也。以一朝之规模气象言,郁郁乎文哉,不可谓郁郁乎末哉也。其轻重之说,亦即仿是。至若在天为云霞,在地为草木,在人物为须发毛羽,此天然之文质,又是一种。
文质先后之分则有之,而后者较重于前。草衣卉服,衣之始也,今人可以供曳娄乎?茹毛饮血,食之始也,今人可以给饔飱乎?至于明堂清庙之间,太羹玄酒,大辂越席,不过略存一二,以昭原始,其它冠裳带舄、尊斝笾豆、羽籥琴瑟,非极情致文不足以将诚敬而鬼神亦不之享,由此观之,文重乎,质重乎?
陈德调此论,仍是从毛奇龄而来。《四书改错》云:“《礼》凡言文质,只是质朴与文饰两相对待之辞,并无曰质是本,文是末者。……向使质是忠信,则文不当胜忠信;文是礼,则质又不当胜礼。相胜且不可,何况相去?朱氏既引杨说,于《质胜章》疑为质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错,而此竟直称质为本,文为末,则错认假逢丑父为真齐顷公矣。”陈德调说:“文质两件,自是对待物事可以相胜言,不可以轻重本末言。”这显然是对毛奇龄的继承,但他通过对“质有三样”的类型分析,然后再来谈文质之关系,却是《论语》诠释史上能够把这个老问题讲清楚的人。
《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朱熹《集注》云:“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盖圣人于此,非作意而为之,但尽其道而已。尹氏曰:‘圣人处己为人,其心一致,无不尽其诚故也。有志于学者,求圣人之心,于斯亦可见矣。’范氏曰:‘圣人不侮鳏寡,不虐无告,可见于此。推之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矣。’”陈德调曰:
师冕,瞽者,非能贸贸然升夫子之阶,登夫子之席也。其自未入门以前,一路便有相者,何待升阶入席而始赖夫子之告?如谓相者告之,夫子又从而告之,则一堂嘈杂,成何体统。抑知瞽目之人,每到一处,惴惴然惟恐其失仪,夫子曲体之,故于其及阶也,不待相者之告而遽告之,曰:“阶也。”其及席也,不待相者之告而遽告之,曰:“席也。”其一片肫诚,俱在无意中流出。迨闻子张问,又不便明言其故,姑应之曰:“固相师之道也。”然而斯道也,非夫子则莫能尽矣。
陈德调的理解,相对而言更能设身处地,还原当时实际情景。尤其是说孔子每到一处,抢在相者之前而遽告之,这等诚敬之心,自然让人感慕于千载之上。当子张问起“与师言之道与”?孔子不过轻描淡写回以“固相师之道也”。其平常自然如此。陈德调对此章的体味,既合乎人之常情,又贴近圣人之心,较之前注,可谓略胜一层。
(三)对《论语集注》古今人物评价提出异议
《论语·公冶长》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朱熹《集注》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称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其介如此,宜若无所容矣;然其所恶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陈德调则曰:
此当与孟子之言参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其言皆从恶恶正面极力形容。圣人却把他不见有恶时翻转一看,觉更清到极处。“怨是用希”,为不善学夷、齐者进一良方,其实夷、齐意中一概不计。“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窃谓群圣皆可以量言,惟夷、齐不可以量言。盖夷、齐心头譬如一面实镜,本无尘滓,自然些子难容,及既脱去,仍是一片空明,含容宽恕,概无所用。
朱熹对《孟子》的引用,重在一个“介”字,但即使如夷、齐有如此之介,仍对所恶之人,保持适度的宽容,因此别人对他们也“怨是用希”。朱熹对“怨是用希”的解释,立足于他人对夷、齐之态度与评价,着眼于日常层面,从人之常情道来。而陈德调对《孟子》的引用,则重在一个“清”字,立足于圣人的自我完善,意若对旧恶,一概不计,则我之心中自无怨恨可言。陈德调此处发明,其实是对明代林希元之说的发挥。旧恶,就是夙怨。不念旧恶,就是不念旧仇。林希元《四书存疑》中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盖所恶者,恶其恶也,非恶其人也。因其自取,非出于有心也。若恶其人而出于有心,则追念不忘矣。”陈德调所谓“夷、齐心头譬如一面实镜”,与林希元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似乎相同,所不同者陈德调比林希元对圣人明心见性的发挥更为彻底。林希元的圣人心如明镜止水,其恶虽出于无心,但仍是有恶的;而陈德调的圣人之心“本无尘滓,自然些子难容,及既脱去,仍是一片空明,含容宽恕,概无所用”。本来无怨,何生怨心?干净彻底,不落一点尘埃。
《论语·宪问》:“如其仁,如其仁。”朱子《集注》:“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陈德调曰:
按:夫子满口许管仲之仁。《注》言:“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则是在外者一仁,而在内者又一仁也。然则有大不仁者于此曰:“吾虽无仁人之事,而固有仁人之心矣。”可乎?
照陈德调理解,仁无分内外,故不可将仁心与事功折解。如果说管仲未得为仁人,则其事功就未必合乎仁道。管仲为霸者之佐,自始至终事业不过以力借仁而已。孔子所言“如其仁”可能就不是朱熹《集注》说的“深许之”之意了。《论语》其他地方涉及管仲,孔子但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按陈德调的意思,《集注》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与事功为二,这是很容易产生逻辑上漏洞的。
(四)对《论语集注》释礼提出异议
《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朱子《集注》云:“南子,卫灵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卫,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故不悦。矢,誓也。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谓不合于礼,不由其道也。厌,弃绝也。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陈德调曰:
《注》:“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毛西河谓其于礼文无据,而究未明子路所以不说之故。盖此与主颜仇由为一时事。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孔子曰:“有命。”进以礼,退以义。今又去见南子,则仍是非礼之进,与主弥子何异?故子路不说,而非谓小君无可见之礼也。“否”字,亦跟弥子来,盖主弥子,夫子之所否者。今见南子,人亦疑夫子为否,故誓言以明之。“予所否者”,古者誓词多用所字打头,如“所不与舅氏者”之类。“天厌之,天厌之”,言若予所否者,则天应早绝我,复何能行道于天下哉?从古宵小多托名流以自重。弥子不得于已则假南子以要之,南子之请见,亦必挟君命先之,故不得不见。要之,圣人道大德宏,其所见者即是圣人之礼,何必于礼外求礼哉?
在《论语》里,子见南子是一件很令后儒困惑的事情,也是《论语》里获得注释最多的章节之一。前人注释归纳起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子见南子是否合礼,二是子路为何不悦,三是孔子解释表达了什么。朱熹之前,何晏《集解》综合孔安国等的意思,认为孔子之见南子,乃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欲因而说灵公使行治道”。“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个比较合乎常情的解释。朱熹《集注》所言“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引来清初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的反驳,他说:“古并无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遍考诸《礼》文及汉晋唐诸儒言礼者,亦并无此说,惊怪甚久。及观《大全》载朱氏《或问》,竟自言是于《礼》无所见,则明白杜撰矣。”但朱熹用一“盖”字,有推测之意,不可作定论。而陈德调的意思是,对于孔子之见南子一事,应与子见弥子一事作同样看待,且二者之间还有联系。他认为子见南子一事乃因弥子引起,弥子假南子以要之,南子又挟君命以先之,孔子不得不见。既是不得不见,则与合礼或不合礼无涉,故不必于礼外求礼。言下之意,子路不悦者,其实是凭己之力来衡量圣人的“道大德宏”,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要之,这其实不就是朱熹所谓“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吗?当然,陈德调最终要表达的是,朱熹完全用不着虚构一个合乎古礼来为孔子开脱,因为圣人怎么着都是有其道理的。
(五)对《论语集注》道学之论提出异议
《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朱子《集注》云:“尹氏曰:‘用舍无与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颜子几于圣人,故亦能之。’”陈德调曰:
不是用则行,舍则藏。不是用我则行,舍我则藏。两“之”字,俱有真实经济。以颜子言之,定是四代礼乐言用之,则把许多经济一齐展布出去而行之,不是空行。舍之,则把许多经济敛藏有待而藏之,不是空藏。这个本领,惟我许尔有是夫。与,犹许也。惟之为言独也。独我许尔,言他人不能知也。子路疑颜子文事有余而武备不足,故以行军为问。岂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正惟颜子优为。乃知平日所藏,无所不有也。前后三“与”字,一气相应。
自来对“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解释,认为惟孔子和颜渊可以做到,而能做到者便是圣人。圣人的标准是知进退存亡,乐天知命。但陈德调则立足于两“之”字内涵分析,认为“俱有真实经济”,不是空行,也不是空藏,即是说圣人也有真本领,而非只会玩假动作。前者解释是心性之学范畴,后者则是事功之学了。所以,接下来针对朱熹引谢氏语,陈德调更是以事功之学直接来驳心性之学了。
《论语·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朱子《集注》曰:“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谢氏曰:‘圣人于行藏之间,无意无必。其行非贪位,其藏非独善也。若有欲心,则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颜子可以与于此。子路虽非有欲心者,然未能无固必也,至以行三军为问,则其论益卑矣。’”而陈德调曰:
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呜呼!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子论政,足食兼以足兵;朝廷设官司徒,不废司马;禹敷文命,而有三苗之征;惟师尚父,而膺燮伐之任,岂尽卑耶?且孔子不与子路,则所与者,必仍属颜子。岂颜子亦卑耶?嗟乎!南宋之蹙,已甚矣!忠贞百战者,斧锧一时;高谈游食者,俎豆千古,则其谓之卑也,亦宜。
朱熹引“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陈德调举南宋困厄之例,反问“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并将谢氏之论斥之为“高谈游食”之言。关于此章的解释,概括而言,也有三种意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心性派,二是以毛奇龄为代表的事功派,三是以周宗建为代表的折中派。毛奇龄说:“行三军非细事,自神农伐补遂,黄帝伐蚩尤而后,行军皆圣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于《师卦》曰:‘开国承家。’又曰:‘可以王矣。’未尝卑也。况临事而惧,正夫子慎战之意。好谋而成,正夫子我战则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语,并不贬抑,而读其书者反从而鄙夷之,可乎?”显然,陈德调的意见是从毛奇龄而来。第三种折中派意见,周宗建《论语商》云:“大抵圣贤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不作两橛,故以此出处则舒卷无心,绝不著些豪意见。以此任事,则锋镝消除,绝不露一豪气。子路三军一问,色相炽然,故夫子把经世大机局点化之,亦正欲其体认到里面去也。临事二语,此是千古圣人兢兢业业之心肠。”如此看来,周宗建是能把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综合加以解说的学者。
《论语·先进》“莫春者”至末节,朱子《集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乎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者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陈德调曰:
此节内外,《注》直说到天地同流、尧舜气象上去。窃以为,圣学不空言气象也。且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点盖谓三子各有用世之撰矣,既究竟知我何人,用我何日,点则不预言,撰亦并不待人知。现在春服可服则服之,童冠可与则与之,舞雩沂水可风浴则风浴之。倘异日知我有人,亦且再作理会,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然已不觉将夫子不怨不尤心事信口道破,故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若夫以泉石啸傲为清高,贤劳鞅掌为多事,此西晋祖尚玄虚之习,为吾儒所痛疾者,岂圣人所乐与哉?又以为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迥不侔矣,尤所未晓。……说此章者,能将开首“不吾知也”及“如或知尔”句,眼光牢注,便是善读书人。点虽狂士,既受夫子之裁,何至一味空狂毫无实际。“不吾知也”,自必数点于诸贤之中;“如或知尔”,岂能推点于诸贤之外?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首节记诸贤之侍坐,如许多才而使之邱壑终老,为诸贤惜,正为自身惜也。“则何以哉”,不是忧其无具,正欲把各色珍宝大家展玩一番。吾故谓此章,头一个悲者夫子,第二个悲者曾点,第三个悲者子路。
《论语·先进》此章,历来解释基本上也是两种意见。一是以朱熹《集注》为代表,从圣人气象上去说。当然,朱熹《集注》实际上也是承皇《疏》、韩愈、程子而来,并有所取。二是以黄震、杨慎为代表,从“答问之正”角度去说。黄震《黄氏日抄》云:“三子言为国之事,皆答问之正也。曾皙,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之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归咏之言,若有触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晳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黄震还批评有些学者过度诠释孔子的意思,他说:“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以曾晳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晳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谈禅”已经是很严重的用词了。明代杨慎《升庵全集》也说:“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语,《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后来陈澧《东塾读书记》亦云:“此则程、朱之说亦有未安。”顺着黄震的思路,而陈德调甚至干脆说:“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但他说曾点之言,“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则又多少有些误解了。可是,他从心理学角度说:“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仍为体贴之言。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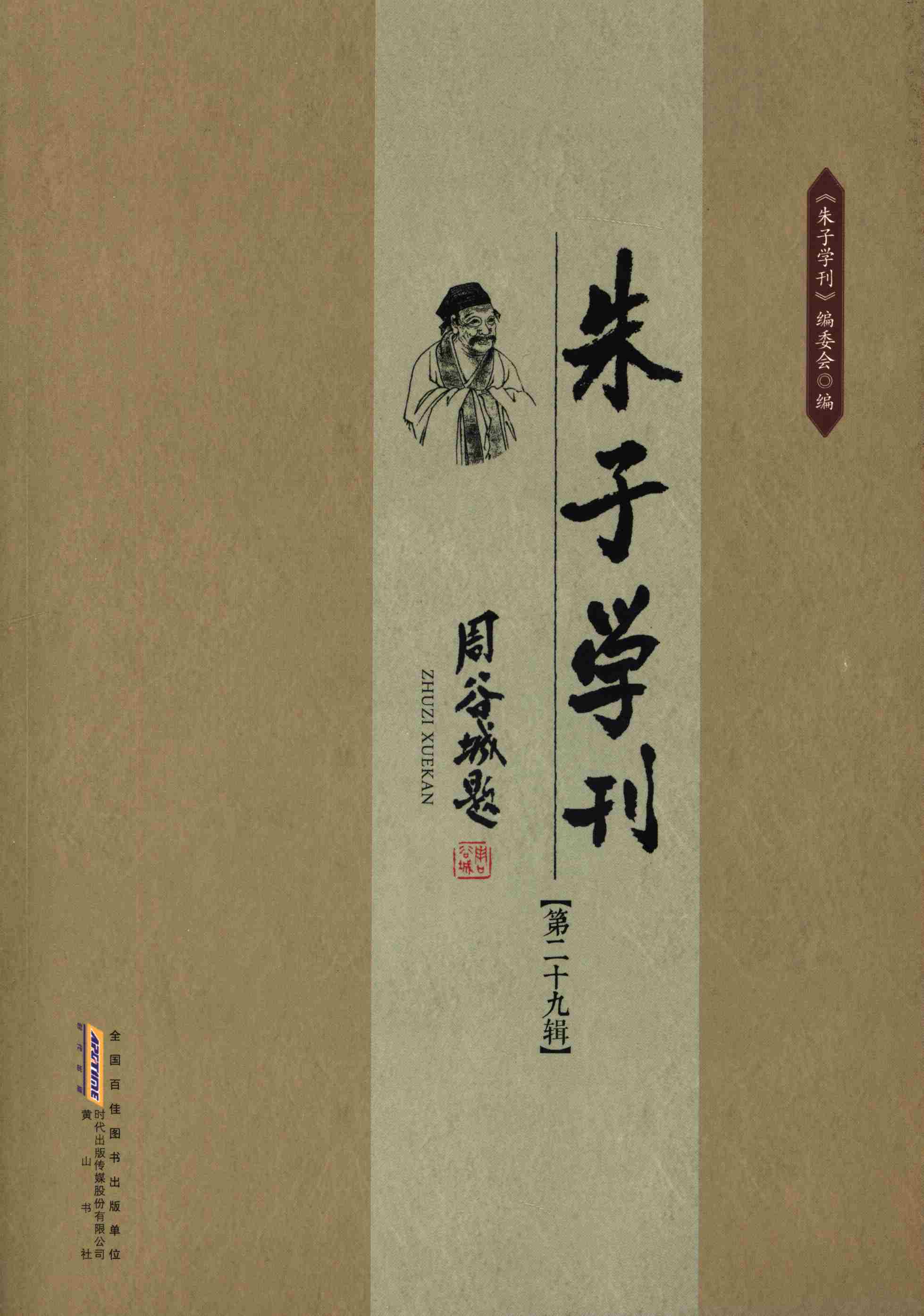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程继红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