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陈德调《我疑录》质疑朱子《论语集注》述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91 |
| 颗粒名称: | 清代陈德调《我疑录》质疑朱子《论语集注》述评 |
| 其他题名: | 兼述其《读古本大学》的知行观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19 |
| 页码: | 161-179 |
| 摘要: | 清代浙江理学的总形势,呈现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交叉发展态势。陈德调作为清中期基层学者,其《我疑录》虽然与毛奇龄的攻朱入王没有直接的学术承继关系,但仍可看出他对朱子学所表现出的个性张扬,从而映现浙东基层理学界的思想活力。随着浙江历代朱子学文献的不断被挖掘,一批原来未曾纳入研究视野的相关论著逐渐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当时基层理学界的“弱势力”,是如何企图刷新权威见解,从而无意间促成了理学界强弱之间对话结构的形成。未来朱子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历史上数量众多的基层学者思想成果,以及层次丰富的朱子学生态史的各个立面与细节。 |
| 关键词: | 清代 陈德调 基层学者 |
内容
浙江理学在清代初期引领了尊朱辟王思潮,为程朱理学在清代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浙江毕竟是王学故地,随着尊朱辟王思潮的推衍,浙江理学同时又出现了攻朱入王的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在清嘉道时期浙东理学人士陈德调那里产生了回响。陈德调,字鼎梅,号燮堂。义乌人。清嘉庆辛未(1811)进士,癸酉(1813)改教官,道光壬午(1822)补授衢州府学教谕,与门弟子讲学,重实行,撤空言。官衢州二十余载,家益贫,门人怜其遇,为置负郭田数顷为养老计。殁,即葬于衢州城南三里许千囊畈。著有《我疑录》1卷、《读古本大学》1卷、《存悔堂诗草》1卷。陈德调虽然是一位地方学者,影响有限,但他在朱子学完全被官方话语所掌控的背景下,却能主动与朱子进行质疑式对话。这种立足于学术的自觉意识,折射出理学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文化力量。
一、清代浙江朱子学形势与陈德调的出现
清代理学的兴盛发展主要体现在清初和晚清。倘就清代初期理学发端而言,它的起步应该在浙江,其中张履祥和陆陇其这两位浙江学者贡献尤著。而浙江理学的总形势,无疑又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呈现交叉发展的态势,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理学阵营。
我们先看浙江尊朱辟王的理学情况。清初的理学转向与建树,是以尊朱辟王为路径的。为吸取明亡的历史教训,思想界出现一股检讨王学的风气,程朱理学在经历明代中晚期以来的削弱之后,此时迎来复兴的局面。在程朱理学复兴的过程中,明遗民起的作用很大。梁启超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内中也有对于王学加以修正者)。”①清初,浙江是明遗民的集中地,这为清初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人才储备。因此,清初程、朱理学复兴局面的开拓,基本上得力于浙江理学界学者们的努力。这段时间形成的尊朱辟王思潮,先导人物就是张履祥。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桐乡人。居杨园,学者称杨园先生。杨园之学,特征有三:居敬穷理,宗法考亭;知行并进,践履笃实;伏处衡茅,系怀民物。《清儒学案》立“杨园学案”,列弟子9人,交游13人,而此前《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张履祥弟子55人,著录弟子多为浙籍人士②。可见这是一个庞大的朱子理学集团。借此,张履祥成为清初理学转向的最早推动者之一,故梁启超说他是“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③。因为这个缘故,张履祥极受后来朱子学家们的推崇,认为他得道学正统。梁启超的评价虽然是对张氏一人而言,其实已经点明了浙江学者对于清初朱子学的贡献所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曾说:“稼书为有清一代正学宗师,持尊朱黜王之见益坚。……然稼书之学,实自吕晚村;晚村得之张杨园。……然杨园以苦节隐,晚村以放言败,而稼书独以俯仰得高誉。”④钱穆为我们理出了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的主线,并将浙江这三位学者接力棒式的努力及其对清初理学转向的贡献作了复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当时的历史真相。吕留良通过与张履祥的交游,使他尊朱批王之论更加尖锐。最终,清初尊朱辟王的理学思潮,在深受张履祥、吕留良影响的理学名臣陆陇其那里得到发扬光大,而这股思潮也终于由民间走向庙堂①。
我们再看清初浙江攻朱入王的理学情况。浙东为王学故地,黄宗羲对于王学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面对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梁启超说他“始终不非王学,但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②。黄宗羲后来的思想着力点主要不在理学本身,而是通过史学来抒发其思想,在思想界留下无人能及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在清初为理学界带来尊朱辟王思潮的主要是浙江学者,构成尊朱的强大阵营;而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理学界也出现了攻朱入王的另一个阵营,这便是以毛奇龄为代表的理学阵营。毛奇龄的理学要点在于:攻驳朱学,修正王学。其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有关“四书”的诸多著作中,如他深刻认同王学关于古本《大学》的诠释,后作《大学正文》《大学知本图说》等文,标明王学立场,攻驳朱学。他攻驳朱子《四书集注》所撰的《四书改错》,认为朱注无一不错。分人、天、地、物、官师、朝庙、邑里、宫室、器用、衣服、饮食、井田、学校、郊社、禘尝、丧祭、礼乐、刑政、典制、故事、记述、章节、句读、引书、据书、改经、改注、添补经文、自造典礼、小诂大诂、抄变词例、贬抑圣门等三十二门,列四百五十一条,每条之下,先列朱注,再予辩驳纠错,可谓振聋发聩。如果说陆陇其是浙江学者将朱学推向庙堂的官方代表,而毛奇龄则是浙江学者中攻朱入王的民间领袖。毛奇龄的意义不仅仅在理学界完成攻朱入王的阵营构建,关键在他所使用的实证方法,促成了清初学风的转向,这也使他成为继顾炎武之后乾嘉汉学重要的先驱人物之一。
自清乾嘉以来,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兴盛局面不再,理学退潮甚至遭到排斥。潘德舆描述说:
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中宗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吻合乎圣人,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诚不为无见。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学有所不备,而其德行、言语、政事,荤荤大者,固孔孟以后必不可无之。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也。①
潘德舆曾将晚清社会危机之发生与社会风气之沉沦的责任,归罪于乾嘉考据之学,虽然过于简单化,但他对于学者溺于考据而丢掉社会责任的忧思,则反映了晚清以来知识界的群体性心态。那么挽大厦之将倾的思想力量来自何方呢?晚清士人群体的目光注意力不约而同地又集中到了程朱理学。于是潘德舆开出济世药方,其云:“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②而能担当此重任之所谓“学术”,即程朱理学,对此李元春解释:
吾儒之学亦且分党而角立,指其名则有记涌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良知之学,今日又有考据之学,而皆不可语于圣贤义理之学。汉儒,记涌之学也;六朝及唐,词章之学也;良知之学,窃圣贤之学而失之过者也;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顾横诋之亦大可感矣。③
由于只有程朱理学属于正学,故才能担当“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之重任。知识界对于理学诉求的呼声日涨,引起朝廷的重视。当然,嘉道两朝对抬升理学地位,也采取了一些直接有效的措施。如朝廷经筵进讲,恢复程、朱理学内容;又如在文庙从祀中增加理学名臣名额。由此,嘉道两朝的理学遂在朝廷和知识界的互动中开始复苏。而至咸同时期,终于呈现了中兴局面。当然,咸同的理学中兴,一方面乃时运使然;另一方面也由于具有湖湘学背景的理学家曾国藩在政治上的快速崛起,使朝廷对于理学的信心大增。这样理学与朝廷的又一次合作,又给理学中兴以深厚的政治基础。理学中兴的最重要体现,便是在晚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学家④。这些理学家从籍贯的地理分布上看,形成了几大带有地域色彩的理学集团,分别为陕西理学集团、河南理学集团、湖湘理学集团、安徽理学集团和浙江理学集团等。
清后期浙江理学集团,代表性学者主要有宗稷辰、邵懿辰、高钧儒、伊尧乐、应宝时、黄方庆、陈居宽、朱一新等。与清初比较,这时候在浙江理学集团内部,出现了两个方向的融合趋势:一是,对于朱、王的界限分别已经不再执着。如会稽学者宗稷辰尝言:“朱子之学,由闽而递传于浙。吾道之昌于越,自尹子证人之学始,至刘子而证人之学成。故尹犹大春也,刘犹大冬也。若紫阳则博文而道舒,姚江则守约而道敛,犹之夏发荣而秋落实焉。至于冬,而天地之性于是乎毕见,万物之理于是乎备昭,学统之全,与岁功等。”①宗稷辰将自己的家塾命名为四贤堂,就已经看出他融合朱王的学术趋向。二是,对于汉宋的判鉴已经趋于调和。汉宋兼采无论在经学领域,还是在理学内部,都成为浙江学术的主潮;前者以定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为代表,后者成绩最为突出的就是义乌朱一新。
陈德调一生处于清代中期,虽然理学不兴,但当时朝廷功令,则仍然隆重朱子,凡试以四书五经命题、所课制艺,俱以朱注为准绳。而陈德调讲经传,多与朱子不合,闻者骇走。黄侗评价《我疑录》说:“考其所言,征引详确,实有为朱子所不逮者。尝语人曰:‘圣学贵实践,宋儒托空谈,吾不忍媚古人于一时,误后学于万世也。’其不为苟同每如此。”②陈德调作为清代嘉道时期非主流的理学学者,他的《我疑录》其实是承清初浙江攻朱入王的理学阵营而来。毛奇龄《四书改错》是思想史上批评《四书集注》最为严重的著作之一,而陈德调《我疑录》中许多观点亦与毛奇龄相似。虽然他与毛奇龄没有直接的学术传承关系,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在清代官方崇尚朱子学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于朱子学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的个性张扬。同时,倘对嘉道时期思想界形势稍作分析,就会发现陈德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王学在清代中期已呈一定的复苏局面,不仅体现在思想界,尤其体现在文学界;不仅体现在主流思想界,还体现在基层思想界。
二、《我疑录》质疑《论语集注》述评
《我疑录》一卷,所疑者唯朱熹《论语集注》,书中针对朱熹关于“贤贤易色”“退而省其私”“哀公问社章”“君子怀德(四句)”“孟武伯问子路章”“伯夷叔齐不念旧恶”“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井有人焉章”“子见南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子行三军则谁与”“三以天下让”“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季氏富于周公章”“同也其庶乎屡空”“子畏于匡章(注阳虎曾暴于匡故匡人围之)”“莫春者至末节”“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樊迟请学稼”“宪问耻节”“晋文公谲而不正章”“如其仁如其仁”“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道不同不相为谋”“师冕见”“有攸不为臣东征(周公无诛管蔡之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节”等29条的解释,逐一质疑,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论语集注》断句提出异议
《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朱子《集注》云:“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坏也。憾,恨也。”①陈德调曰:
按:此句读之错也。以“与朋友共”成句,“敝之而无憾”成句。敝之属友,则憾字自应改作恨字。不知无憾是自快然心慰,与“愤”“恨”字全不相假,且如此亦不过一豪侠行径耳,与圣贤心事何与?愚意当读“与朋友共敝之”成句,“而无憾”成句。言愿有此车马、轻裘与朋友久共直至敝之,而此心始快然无憾。敝之,不属己,亦不属友,极言其志同道合,愿与久处,以辅吾仁。②
关于《论语》此章的断句,历来有两种意见。其中朱熹《集注》的断句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是“敝之”前属。后一种断句,最早见于《白虎通·纲纪篇》引《论语》子路云:“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张载《论语说》:“仲由乐善,故车马衣裘与贤者共敝。从‘愿’字至‘敝之’字为句。”③陈德调认为,朱熹《集注》断句所表达的意思,充其量不过一豪侠行径,而后者断句则表示未敝之时已有共敝之意,语意直接,尤得圣贤气象。比较而言,陈德调的意见似更能体现仲由本意。唐宋人诗歌中,亦多取“共敝之”之意,如唐马戴《边馆逢贺秀才诗》云“鹿裘共敝同为客”,张文昌《赠殷山人诗》云“同袍还共敝”,苏轼《戏周正儒坠马诗》“故人共敝亦常情”,可见“共敝”是一种为大家普遍认同且具有圣贤气象的解释。
(二)对《论语集注》释义提出异议
《论语·里仁》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集注》云:“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陈德调则曰:
圣人下字,各有攸当,非若文士之变易求新也。如他处言怀居,此变易怀土。他处言放利喻利,此变言怀惠。夫怀土非怀居比也,怀居者有纵逸自安之意,土则人之所赖以生。先王别五土之宜以利民,故曰“厥心臧”,惟土物爱,怀之不为过分。怀惠又非贪利比也,贪利者有非分争夺之思,惠则人自与我,或出于君上之恩施,或出于朋友之馈遗,怀之,岂尽丧廉?且变惠言利,而以为小人怀利可也,若变怀言贪,而以为君子贪刑,不大笑话乎?盖此君子小人以分位言,犹如士农之别。言君子当怀德,不可如小人之仅怀土也。君子当怀刑,不可如小人之仅怀惠也。德与土皆我之所固有者,刑与惠皆人之加诸我者,故相对成文。①
比较而言,朱熹《论语集注》简洁明了,释义到位,而陈德调的解说似乎透进一层,也更细腻,但未必够得上疑朱,其实是对朱熹诠释的一种引申,起到丰富、补充与发挥作用。
《论语·颜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朱子《集注》:“言文质等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②陈德调曰:
文质两件,自是对待物事可以相胜言,不可以轻重本末言。大抵文一而已,而质有三样:一是质直之质。主内心而言,文质之所从出者也。此是大本,非此不但文有伪,即质亦有伪,《记》所谓“忠信之人可与学礼”是也。一是质干之质。主植基于事先者而言,文质之所由附者也。一是质朴之质。主措施于事物者而言,虽亦从大本而出,然可与文对言,不可与末对言者也。假以一人之身为质干,而文质二者从此附焉。有不衫不履者,有整齐修饰者,不可以不衫不履者为本,整齐修饰者为末也。又以画之粉地为质干,而文质二者从此附焉。有轻描淡写者,有着色渲染者,不可以轻描淡写者为本,着色渲染者为末也。草野之间多简略,冠裳之会盛繁华,不可以草野之间为本,冠裳之会为末也。礼或多之为贵、少之为贵,不可谓少者为本,多者为末也。又有同是礼文之中,而又质之为贵、文之为贵,不可谓贵本而贵末也。以两朝之规模气象言,商尚质,周尚文,不可谓商尚本,周尚末也。以一朝之规模气象言,郁郁乎文哉,不可谓郁郁乎末哉也。其轻重之说,亦即仿是。至若在天为云霞,在地为草木,在人物为须发毛羽,此天然之文质,又是一种。
文质先后之分则有之,而后者较重于前。草衣卉服,衣之始也,今人可以供曳娄乎?茹毛饮血,食之始也,今人可以给饔飱乎?至于明堂清庙之间,太羹玄酒,大辂越席,不过略存一二,以昭原始,其它冠裳带舄、尊斝笾豆、羽籥琴瑟,非极情致文不足以将诚敬而鬼神亦不之享,由此观之,文重乎,质重乎?①
陈德调此论,仍是从毛奇龄而来。《四书改错》云:“《礼》凡言文质,只是质朴与文饰两相对待之辞,并无曰质是本,文是末者。……向使质是忠信,则文不当胜忠信;文是礼,则质又不当胜礼。相胜且不可,何况相去?朱氏既引杨说,于《质胜章》疑为质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错,而此竟直称质为本,文为末,则错认假逢丑父为真齐顷公矣。”②陈德调说:“文质两件,自是对待物事可以相胜言,不可以轻重本末言。”这显然是对毛奇龄的继承,但他通过对“质有三样”的类型分析,然后再来谈文质之关系,却是《论语》诠释史上能够把这个老问题讲清楚的人。
《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朱熹《集注》云:“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盖圣人于此,非作意而为之,但尽其道而已。尹氏曰:‘圣人处己为人,其心一致,无不尽其诚故也。有志于学者,求圣人之心,于斯亦可见矣。’范氏曰:‘圣人不侮鳏寡,不虐无告,可见于此。推之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矣。’”陈德调曰:
师冕,瞽者,非能贸贸然升夫子之阶,登夫子之席也。其自未入门以前,一路便有相者,何待升阶入席而始赖夫子之告?如谓相者告之,夫子又从而告之,则一堂嘈杂,成何体统。抑知瞽目之人,每到一处,惴惴然惟恐其失仪,夫子曲体之,故于其及阶也,不待相者之告而遽告之,曰:“阶也。”其及席也,不待相者之告而遽告之,曰:“席也。”其一片肫诚,俱在无意中流出。迨闻子张问,又不便明言其故,姑应之曰:“固相师之道也。”然而斯道也,非夫子则莫能尽矣。
陈德调的理解,相对而言更能设身处地,还原当时实际情景。尤其是说孔子每到一处,抢在相者之前而遽告之,这等诚敬之心,自然让人感慕于千载之上。当子张问起“与师言之道与”?孔子不过轻描淡写回以“固相师之道也”。其平常自然如此。陈德调对此章的体味,既合乎人之常情,又贴近圣人之心,较之前注,可谓略胜一层。
(三)对《论语集注》古今人物评价提出异议
《论语·公冶长》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朱熹《集注》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称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其介如此,宜若无所容矣;然其所恶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①陈德调则曰:
此当与孟子之言参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其言皆从恶恶正面极力形容。圣人却把他不见有恶时翻转一看,觉更清到极处。“怨是用希”,为不善学夷、齐者进一良方,其实夷、齐意中一概不计。“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窃谓群圣皆可以量言,惟夷、齐不可以量言。盖夷、齐心头譬如一面实镜,本无尘滓,自然些子难容,及既脱去,仍是一片空明,含容宽恕,概无所用。②
朱熹对《孟子》的引用,重在一个“介”字,但即使如夷、齐有如此之介,仍对所恶之人,保持适度的宽容,因此别人对他们也“怨是用希”。朱熹对“怨是用希”的解释,立足于他人对夷、齐之态度与评价,着眼于日常层面,从人之常情道来。而陈德调对《孟子》的引用,则重在一个“清”字,立足于圣人的自我完善,意若对旧恶,一概不计,则我之心中自无怨恨可言。陈德调此处发明,其实是对明代林希元之说的发挥。旧恶,就是夙怨。不念旧恶,就是不念旧仇。林希元《四书存疑》中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盖所恶者,恶其恶也,非恶其人也。因其自取,非出于有心也。若恶其人而出于有心,则追念不忘矣。”①陈德调所谓“夷、齐心头譬如一面实镜”,与林希元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似乎相同,所不同者陈德调比林希元对圣人明心见性的发挥更为彻底。林希元的圣人心如明镜止水,其恶虽出于无心,但仍是有恶的;而陈德调的圣人之心“本无尘滓,自然些子难容,及既脱去,仍是一片空明,含容宽恕,概无所用”。本来无怨,何生怨心?干净彻底,不落一点尘埃。
《论语·宪问》:“如其仁,如其仁。”朱子《集注》:“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②陈德调曰:
按:夫子满口许管仲之仁。《注》言:“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则是在外者一仁,而在内者又一仁也。然则有大不仁者于此曰:“吾虽无仁人之事,而固有仁人之心矣。”可乎?③
照陈德调理解,仁无分内外,故不可将仁心与事功折解。如果说管仲未得为仁人,则其事功就未必合乎仁道。管仲为霸者之佐,自始至终事业不过以力借仁而已。孔子所言“如其仁”可能就不是朱熹《集注》说的“深许之”之意了。《论语》其他地方涉及管仲,孔子但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按陈德调的意思,《集注》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与事功为二,这是很容易产生逻辑上漏洞的。
(四)对《论语集注》释礼提出异议
《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朱子《集注》云:“南子,卫灵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卫,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故不悦。矢,誓也。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谓不合于礼,不由其道也。厌,弃绝也。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①陈德调曰:
《注》:“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毛西河谓其于礼文无据,而究未明子路所以不说之故。盖此与主颜仇由为一时事。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孔子曰:“有命。”进以礼,退以义。今又去见南子,则仍是非礼之进,与主弥子何异?故子路不说,而非谓小君无可见之礼也。“否”字,亦跟弥子来,盖主弥子,夫子之所否者。今见南子,人亦疑夫子为否,故誓言以明之。“予所否者”,古者誓词多用所字打头,如“所不与舅氏者”之类。“天厌之,天厌之”,言若予所否者,则天应早绝我,复何能行道于天下哉?从古宵小多托名流以自重。弥子不得于已则假南子以要之,南子之请见,亦必挟君命先之,故不得不见。要之,圣人道大德宏,其所见者即是圣人之礼,何必于礼外求礼哉?②
在《论语》里,子见南子是一件很令后儒困惑的事情,也是《论语》里获得注释最多的章节之一。前人注释归纳起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子见南子是否合礼,二是子路为何不悦,三是孔子解释表达了什么。朱熹之前,何晏《集解》综合孔安国等的意思,认为孔子之见南子,乃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欲因而说灵公使行治道”。“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个比较合乎常情的解释。朱熹《集注》所言“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引来清初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的反驳,他说:“古并无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遍考诸《礼》文及汉晋唐诸儒言礼者,亦并无此说,惊怪甚久。及观《大全》载朱氏《或问》,竟自言是于《礼》无所见,则明白杜撰矣。”③但朱熹用一“盖”字,有推测之意,不可作定论。而陈德调的意思是,对于孔子之见南子一事,应与子见弥子一事作同样看待,且二者之间还有联系。他认为子见南子一事乃因弥子引起,弥子假南子以要之,南子又挟君命以先之,孔子不得不见。既是不得不见,则与合礼或不合礼无涉,故不必于礼外求礼。言下之意,子路不悦者,其实是凭己之力来衡量圣人的“道大德宏”,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要之,这其实不就是朱熹所谓“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吗?当然,陈德调最终要表达的是,朱熹完全用不着虚构一个合乎古礼来为孔子开脱,因为圣人怎么着都是有其道理的。
(五)对《论语集注》道学之论提出异议
《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朱子《集注》云:“尹氏曰:‘用舍无与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颜子几于圣人,故亦能之。’”①陈德调曰:
不是用则行,舍则藏。不是用我则行,舍我则藏。两“之”字,俱有真实经济。以颜子言之,定是四代礼乐言用之,则把许多经济一齐展布出去而行之,不是空行。舍之,则把许多经济敛藏有待而藏之,不是空藏。这个本领,惟我许尔有是夫。与,犹许也。惟之为言独也。独我许尔,言他人不能知也。子路疑颜子文事有余而武备不足,故以行军为问。岂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正惟颜子优为。乃知平日所藏,无所不有也。前后三“与”字,一气相应。②
自来对“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解释,认为惟孔子和颜渊可以做到,而能做到者便是圣人。圣人的标准是知进退存亡,乐天知命。但陈德调则立足于两“之”字内涵分析,认为“俱有真实经济”,不是空行,也不是空藏,即是说圣人也有真本领,而非只会玩假动作。前者解释是心性之学范畴,后者则是事功之学了。所以,接下来针对朱熹引谢氏语,陈德调更是以事功之学直接来驳心性之学了。
《论语·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朱子《集注》曰:“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谢氏曰:‘圣人于行藏之间,无意无必。其行非贪位,其藏非独善也。若有欲心,则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颜子可以与于此。子路虽非有欲心者,然未能无固必也,至以行三军为问,则其论益卑矣。’”①而陈德调曰:
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呜呼!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子论政,足食兼以足兵;朝廷设官司徒,不废司马;禹敷文命,而有三苗之征;惟师尚父,而膺燮伐之任,岂尽卑耶?且孔子不与子路,则所与者,必仍属颜子。岂颜子亦卑耶?嗟乎!南宋之蹙,已甚矣!忠贞百战者,斧锧一时;高谈游食者,俎豆千古,则其谓之卑也,亦宜。②
朱熹引“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陈德调举南宋困厄之例,反问“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并将谢氏之论斥之为“高谈游食”之言。关于此章的解释,概括而言,也有三种意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心性派,二是以毛奇龄为代表的事功派,三是以周宗建为代表的折中派。毛奇龄说:“行三军非细事,自神农伐补遂,黄帝伐蚩尤而后,行军皆圣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于《师卦》曰:‘开国承家。’又曰:‘可以王矣。’未尝卑也。况临事而惧,正夫子慎战之意。好谋而成,正夫子我战则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语,并不贬抑,而读其书者反从而鄙夷之,可乎?”③显然,陈德调的意见是从毛奇龄而来。第三种折中派意见,周宗建《论语商》云:“大抵圣贤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不作两橛,故以此出处则舒卷无心,绝不著些豪意见。以此任事,则锋镝消除,绝不露一豪气。子路三军一问,色相炽然,故夫子把经世大机局点化之,亦正欲其体认到里面去也。临事二语,此是千古圣人兢兢业业之心肠。”④如此看来,周宗建是能把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综合加以解说的学者。
《论语·先进》“莫春者”至末节,朱子《集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乎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者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①陈德调曰:
此节内外,《注》直说到天地同流、尧舜气象上去。窃以为,圣学不空言气象也。且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点盖谓三子各有用世之撰矣,既究竟知我何人,用我何日,点则不预言,撰亦并不待人知。现在春服可服则服之,童冠可与则与之,舞雩沂水可风浴则风浴之。倘异日知我有人,亦且再作理会,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然已不觉将夫子不怨不尤心事信口道破,故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若夫以泉石啸傲为清高,贤劳鞅掌为多事,此西晋祖尚玄虚之习,为吾儒所痛疾者,岂圣人所乐与哉?又以为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迥不侔矣,尤所未晓。……说此章者,能将开首“不吾知也”及“如或知尔”句,眼光牢注,便是善读书人。点虽狂士,既受夫子之裁,何至一味空狂毫无实际。“不吾知也”,自必数点于诸贤之中;“如或知尔”,岂能推点于诸贤之外?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首节记诸贤之侍坐,如许多才而使之邱壑终老,为诸贤惜,正为自身惜也。“则何以哉”,不是忧其无具,正欲把各色珍宝大家展玩一番。吾故谓此章,头一个悲者夫子,第二个悲者曾点,第三个悲者子路。②
《论语·先进》此章,历来解释基本上也是两种意见。一是以朱熹《集注》为代表,从圣人气象上去说。当然,朱熹《集注》实际上也是承皇《疏》、韩愈、程子而来,并有所取。二是以黄震、杨慎为代表,从“答问之正”角度去说。黄震《黄氏日抄》云:“三子言为国之事,皆答问之正也。曾皙,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之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归咏之言,若有触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晳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黄震还批评有些学者过度诠释孔子的意思,他说:“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以曾晳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晳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①“谈禅”已经是很严重的用词了。明代杨慎《升庵全集》也说:“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语,《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后来陈澧《东塾读书记》亦云:“此则程、朱之说亦有未安。”②顺着黄震的思路,而陈德调甚至干脆说:“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但他说曾点之言,“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则又多少有些误解了。可是,他从心理学角度说:“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仍为体贴之言。
三、陈德调《读古本大学》的即知即行说
陈德调还有《读古本大学》一卷。古本《大学》其实是王阳明所提倡的,朱熹在为《大学》做集注时,有感于《大学》脱简,做了补文,引起后世很多的议论。这里陈德调标明读的是古本《大学》,其意当然是要区分朱熹的补本《大学》。
陈德调的思想里本来重视经济事功,因此他读古本《大学》一开始就希望找到“力行之事”安在?他说:
圣学最重力行,今观《大学》一书,八条目,十大传,概无及于行者,格致只是考究功夫,心意都在腔子里,修身功夫便在格致诚正上,齐治平不过举而措之之事。朱子又云:“自致而诚而正至治平,皆从一知,直推到底。”然则《大学》力行之事,究竟安在?及吾读“物有本末”注,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而经文“自天子至于庶人”节,则又以修身为本,齐治平为末,意窃疑之。又读“明明德于天下”节,自致治以上皆以先后言,独于格物事不曰“先”而曰“在”,意又疑之。后读古本《大学》疏:“明明德者,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乃知明德之事,即在修身上见。又经文于“其本乱”节下,即紧接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始恍然曰:“《大学》力行之事有在矣,格物是也。”①
陈德调认为,格物即由行以得知,而非空言穷理。他把人之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天然自得之知,即孩提知爱,少长知敬之类;二是先事而求之知,即博稽古今、参考异同、研求事理、殚精极微的穷理,这虽属于圣学之开途,但其功却尚属虚位;三是及之而知之知,此则是知之至者,如人欲为忠,必向臣道上亲切去做而忠之理始明;欲为孝,必向子道上亲切去做而孝之理始出。但对这三种知的获得,必须通过格物这一路径。他说:“格,至也,来也。”(古本《大学》训格为来)谓即其物之来至我的面前,然后躬亲其境,躬践其事,如此方可究事物之理。其云:
譬之适千里者,良知者生而东西南北知所方向;穷理者详考舆地经、道里志,询之往来素熟,纵极周到究之,仍属恍恍;格物者束装裹粮,启行戒道,行十里知十里,行百里知百里,及其既至,而一切所历之山川景物,关津险隘,按之舆经地志、人物传说者,一一信其不谬焉,此物格而后知至之说也。②
一个人倘若要行千里之路,如果凭借良知在先,他也许本能地知道大的方向;如果凭借穷理得到的文献知识,即使周到细致,仍然不免与现实隔膜;但如果采取格物者的姿态,且行且知,便是知行合一了。但这样一来,便有人提出知行的先后问题,陈德调如何解释呢?
或曰:学者先知而后行。子之说,不先行而后知乎?曰:吾固言之矣。穷理者,学问思辨之事,圣学之开途也。格物者,笃行之事,造道之实功也。功实,斯知亦实矣。且夫圣人之教人也,其自弟子之入孝出悌,信言谨行,莫非真切从事,而学文游艺,亲师近友,随时随地而考证焉。即行即知,即知即行,岂若后世之判分两事哉。①
传统观点是将知行判分两事,拆开来讲,陈德调则合起来了。既然知行不可拆解,那么内外、心身也就同样不能分作两开。看他如何解释:
又曰:《大学》由知、由意、由心而次以及于身事,皆自内以及外。子之说,不几自外而及内乎?曰:是不然也。理从内出,功从外入,且人自把许多条目看得七头八脑耳。自内言之,为知、为意、为心,其实只是一个心;自外言之,为身、为家、为国、为天下,其实只重一个身。合心与身而言之,为内、为外,其实只完得一个身。身即是物,修只是格,故孔子言躬行君子,孟子言修身立命,而《中庸》《九经》亦起于修身而不必更及于心者,言身则心、意、知并运乎其中,而不能把内与外划然分作两开也。②
儒者之所以要严别内外的同时还要重内轻外,是因为内不可假,而外则可假。但在陈德调看来恰好相反,倘若外假,人人得见;而内假则诚伪,便滑入二氏之学。
且儒者之所重内而轻外者,以为外可假,而内不可假耳。吾谓内可假,而外不可假,外则行迹显著,无从遮饰,彼假于声音笑貌之间者,仍是假其内耳。然其内自假,而其声音笑貌则仍然不假也。据其实在之声音笑貌而悉心印证之,斯其人之诚伪可得而见,此物格知至之说也。虚摹一声音笑貌之象于意中,谓可得其人之诚伪者,是刻舟求剑,即今之所谓即物穷理者也。然则以探幽索渺为致知,闭门枯坐为慎独,凭空把持为正心,又以为心坎头光光然亮亮然,怀着个明德在内者,是所谓如光灿灿如圆陀陀,二氏之学非吾儒之学也。夫二氏之学,假之大者也。③
即行即知,内外无别,照这个逻辑,则明、修亦可相通了。因此,修身之事自然就是明德之事,不必一番功夫分两番做,其云:
明德之事,只在修身上见。古注可据,而人或骇为创闻。窃意人生有个身,便有一个心,心为五官之一本,一气相通者也。内心具个德,本来自明者也。特德不自明,必接于身而后明,犹火不自明,必接于薪而后明,非不知薪之明由火之明也,而非薪则无以丽其明矣。又如一株树,德存乎根本而明见乎枝叶,非不知枝叶之明由根本之明也,而非枝叶则无以验其明矣。盖枝叶者,即根本之菁华也。是以《大学》自格致诚正以下,但言修身之事,而不复言明德之事,显知明与修之初非两事也。若既格致诚正以修其身,又复格致诚正以明其德,不特一番功夫分两番做,八条目不增九乎?①
按照行即知、内即外、明即修的推理一路下去,很显然身、家、国、天下也是一理,能够打通这四者,在陈德调看来便是“格物致知之极也”。其云:
身与家、国、天下虽然只是一理,要必就自身之物深造至极,则身之知至而其道可通于家,就自家之物深造至极,则家之知至而其道可通于国与天下。然所云可通者,谓知不虚知,则可由此以达彼,而仍不能执此以为彼也。又须到有国与天下之责,然后能格,然后能致焉,何则?身家者,一人之身家;国与天下者,合国与天下之身家以为身家也。夫合国与天下之身家以为身家,则合国与天下之物以为格,自必合国与天下之知以为致。(平天下章实是最重用人)陈殷置辅,大纲小纪,一人端冕于上,百司承职于下,公好恶,存忠信,有先慎乎德之修,无以财发身之患,夫是以重离继照,旁烛无疆,臻治平之有象也。此格物致知之极也。②
即行即知等观点,并不是陈德调的发明,此前王守仁就已经提出来过。黄宗羲说王守仁讲“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①。但据陈德调自述,这些见解其实是他自悟得来,只是与王守仁暗合。他说:
今戊戌(继按:道光戊戌,1838年)春,读王阳明先生集,有知行并进之说,自维鄙见颇觉相似。又其言格物则必兼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尝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其言亦与鄙见稍异而大同。②
照陈德调的自述,他对阳明学的接触,其实是很晚的事情。因此,他的即知即行观完全是自悟得来,恰好与阳明合辙,实属不易。故黄侗慨叹“梅鼎先生朝餐苜蓿,夕拥青氈,以冷官终其身”,“所言即知即行之旨,与姚江不谋而合,则其有功于圣门或亦不在阳明下欤”③。这便是历代无数基层学者的一个典型写照。
综上,陈德调虽不是知名学者,但其敢于疑朱的精神却与清初毛奇龄相接;而即知即行见解的提出,又与王阳明暗合,透过他可以了解当时浙东理学界基层学者的思想活力。与主流学者相比,陈德调《我疑录》和《读古本大学》的存在,仿佛朱子学史上的一个“民间故事”,但这绝非个案。随着笔者对浙江历代朱子学文献的不断挖掘,一批原来未曾纳入研究视野的相关论著逐渐浮出水面,细读之后,发现它们大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这些著述遗存,让我们看到当时基层理学界所谓的“弱势力”,是如何企图刷新权威见解,从而无意间促成了理学界强弱之间对话结构的形成、主流与非主流互动图景的诞生。我们认为,未来朱子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历史上那些基层学者的思想成果,以及层次丰富的朱子学生态史的各个立面与细节。
一、清代浙江朱子学形势与陈德调的出现
清代理学的兴盛发展主要体现在清初和晚清。倘就清代初期理学发端而言,它的起步应该在浙江,其中张履祥和陆陇其这两位浙江学者贡献尤著。而浙江理学的总形势,无疑又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呈现交叉发展的态势,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理学阵营。
我们先看浙江尊朱辟王的理学情况。清初的理学转向与建树,是以尊朱辟王为路径的。为吸取明亡的历史教训,思想界出现一股检讨王学的风气,程朱理学在经历明代中晚期以来的削弱之后,此时迎来复兴的局面。在程朱理学复兴的过程中,明遗民起的作用很大。梁启超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内中也有对于王学加以修正者)。”①清初,浙江是明遗民的集中地,这为清初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人才储备。因此,清初程、朱理学复兴局面的开拓,基本上得力于浙江理学界学者们的努力。这段时间形成的尊朱辟王思潮,先导人物就是张履祥。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桐乡人。居杨园,学者称杨园先生。杨园之学,特征有三:居敬穷理,宗法考亭;知行并进,践履笃实;伏处衡茅,系怀民物。《清儒学案》立“杨园学案”,列弟子9人,交游13人,而此前《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张履祥弟子55人,著录弟子多为浙籍人士②。可见这是一个庞大的朱子理学集团。借此,张履祥成为清初理学转向的最早推动者之一,故梁启超说他是“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③。因为这个缘故,张履祥极受后来朱子学家们的推崇,认为他得道学正统。梁启超的评价虽然是对张氏一人而言,其实已经点明了浙江学者对于清初朱子学的贡献所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曾说:“稼书为有清一代正学宗师,持尊朱黜王之见益坚。……然稼书之学,实自吕晚村;晚村得之张杨园。……然杨园以苦节隐,晚村以放言败,而稼书独以俯仰得高誉。”④钱穆为我们理出了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的主线,并将浙江这三位学者接力棒式的努力及其对清初理学转向的贡献作了复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当时的历史真相。吕留良通过与张履祥的交游,使他尊朱批王之论更加尖锐。最终,清初尊朱辟王的理学思潮,在深受张履祥、吕留良影响的理学名臣陆陇其那里得到发扬光大,而这股思潮也终于由民间走向庙堂①。
我们再看清初浙江攻朱入王的理学情况。浙东为王学故地,黄宗羲对于王学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面对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梁启超说他“始终不非王学,但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②。黄宗羲后来的思想着力点主要不在理学本身,而是通过史学来抒发其思想,在思想界留下无人能及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在清初为理学界带来尊朱辟王思潮的主要是浙江学者,构成尊朱的强大阵营;而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理学界也出现了攻朱入王的另一个阵营,这便是以毛奇龄为代表的理学阵营。毛奇龄的理学要点在于:攻驳朱学,修正王学。其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有关“四书”的诸多著作中,如他深刻认同王学关于古本《大学》的诠释,后作《大学正文》《大学知本图说》等文,标明王学立场,攻驳朱学。他攻驳朱子《四书集注》所撰的《四书改错》,认为朱注无一不错。分人、天、地、物、官师、朝庙、邑里、宫室、器用、衣服、饮食、井田、学校、郊社、禘尝、丧祭、礼乐、刑政、典制、故事、记述、章节、句读、引书、据书、改经、改注、添补经文、自造典礼、小诂大诂、抄变词例、贬抑圣门等三十二门,列四百五十一条,每条之下,先列朱注,再予辩驳纠错,可谓振聋发聩。如果说陆陇其是浙江学者将朱学推向庙堂的官方代表,而毛奇龄则是浙江学者中攻朱入王的民间领袖。毛奇龄的意义不仅仅在理学界完成攻朱入王的阵营构建,关键在他所使用的实证方法,促成了清初学风的转向,这也使他成为继顾炎武之后乾嘉汉学重要的先驱人物之一。
自清乾嘉以来,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兴盛局面不再,理学退潮甚至遭到排斥。潘德舆描述说:
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中宗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吻合乎圣人,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诚不为无见。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学有所不备,而其德行、言语、政事,荤荤大者,固孔孟以后必不可无之。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也。①
潘德舆曾将晚清社会危机之发生与社会风气之沉沦的责任,归罪于乾嘉考据之学,虽然过于简单化,但他对于学者溺于考据而丢掉社会责任的忧思,则反映了晚清以来知识界的群体性心态。那么挽大厦之将倾的思想力量来自何方呢?晚清士人群体的目光注意力不约而同地又集中到了程朱理学。于是潘德舆开出济世药方,其云:“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②而能担当此重任之所谓“学术”,即程朱理学,对此李元春解释:
吾儒之学亦且分党而角立,指其名则有记涌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良知之学,今日又有考据之学,而皆不可语于圣贤义理之学。汉儒,记涌之学也;六朝及唐,词章之学也;良知之学,窃圣贤之学而失之过者也;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顾横诋之亦大可感矣。③
由于只有程朱理学属于正学,故才能担当“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之重任。知识界对于理学诉求的呼声日涨,引起朝廷的重视。当然,嘉道两朝对抬升理学地位,也采取了一些直接有效的措施。如朝廷经筵进讲,恢复程、朱理学内容;又如在文庙从祀中增加理学名臣名额。由此,嘉道两朝的理学遂在朝廷和知识界的互动中开始复苏。而至咸同时期,终于呈现了中兴局面。当然,咸同的理学中兴,一方面乃时运使然;另一方面也由于具有湖湘学背景的理学家曾国藩在政治上的快速崛起,使朝廷对于理学的信心大增。这样理学与朝廷的又一次合作,又给理学中兴以深厚的政治基础。理学中兴的最重要体现,便是在晚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学家④。这些理学家从籍贯的地理分布上看,形成了几大带有地域色彩的理学集团,分别为陕西理学集团、河南理学集团、湖湘理学集团、安徽理学集团和浙江理学集团等。
清后期浙江理学集团,代表性学者主要有宗稷辰、邵懿辰、高钧儒、伊尧乐、应宝时、黄方庆、陈居宽、朱一新等。与清初比较,这时候在浙江理学集团内部,出现了两个方向的融合趋势:一是,对于朱、王的界限分别已经不再执着。如会稽学者宗稷辰尝言:“朱子之学,由闽而递传于浙。吾道之昌于越,自尹子证人之学始,至刘子而证人之学成。故尹犹大春也,刘犹大冬也。若紫阳则博文而道舒,姚江则守约而道敛,犹之夏发荣而秋落实焉。至于冬,而天地之性于是乎毕见,万物之理于是乎备昭,学统之全,与岁功等。”①宗稷辰将自己的家塾命名为四贤堂,就已经看出他融合朱王的学术趋向。二是,对于汉宋的判鉴已经趋于调和。汉宋兼采无论在经学领域,还是在理学内部,都成为浙江学术的主潮;前者以定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为代表,后者成绩最为突出的就是义乌朱一新。
陈德调一生处于清代中期,虽然理学不兴,但当时朝廷功令,则仍然隆重朱子,凡试以四书五经命题、所课制艺,俱以朱注为准绳。而陈德调讲经传,多与朱子不合,闻者骇走。黄侗评价《我疑录》说:“考其所言,征引详确,实有为朱子所不逮者。尝语人曰:‘圣学贵实践,宋儒托空谈,吾不忍媚古人于一时,误后学于万世也。’其不为苟同每如此。”②陈德调作为清代嘉道时期非主流的理学学者,他的《我疑录》其实是承清初浙江攻朱入王的理学阵营而来。毛奇龄《四书改错》是思想史上批评《四书集注》最为严重的著作之一,而陈德调《我疑录》中许多观点亦与毛奇龄相似。虽然他与毛奇龄没有直接的学术传承关系,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在清代官方崇尚朱子学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于朱子学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的个性张扬。同时,倘对嘉道时期思想界形势稍作分析,就会发现陈德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王学在清代中期已呈一定的复苏局面,不仅体现在思想界,尤其体现在文学界;不仅体现在主流思想界,还体现在基层思想界。
二、《我疑录》质疑《论语集注》述评
《我疑录》一卷,所疑者唯朱熹《论语集注》,书中针对朱熹关于“贤贤易色”“退而省其私”“哀公问社章”“君子怀德(四句)”“孟武伯问子路章”“伯夷叔齐不念旧恶”“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井有人焉章”“子见南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子行三军则谁与”“三以天下让”“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季氏富于周公章”“同也其庶乎屡空”“子畏于匡章(注阳虎曾暴于匡故匡人围之)”“莫春者至末节”“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樊迟请学稼”“宪问耻节”“晋文公谲而不正章”“如其仁如其仁”“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道不同不相为谋”“师冕见”“有攸不为臣东征(周公无诛管蔡之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节”等29条的解释,逐一质疑,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论语集注》断句提出异议
《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朱子《集注》云:“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坏也。憾,恨也。”①陈德调曰:
按:此句读之错也。以“与朋友共”成句,“敝之而无憾”成句。敝之属友,则憾字自应改作恨字。不知无憾是自快然心慰,与“愤”“恨”字全不相假,且如此亦不过一豪侠行径耳,与圣贤心事何与?愚意当读“与朋友共敝之”成句,“而无憾”成句。言愿有此车马、轻裘与朋友久共直至敝之,而此心始快然无憾。敝之,不属己,亦不属友,极言其志同道合,愿与久处,以辅吾仁。②
关于《论语》此章的断句,历来有两种意见。其中朱熹《集注》的断句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是“敝之”前属。后一种断句,最早见于《白虎通·纲纪篇》引《论语》子路云:“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张载《论语说》:“仲由乐善,故车马衣裘与贤者共敝。从‘愿’字至‘敝之’字为句。”③陈德调认为,朱熹《集注》断句所表达的意思,充其量不过一豪侠行径,而后者断句则表示未敝之时已有共敝之意,语意直接,尤得圣贤气象。比较而言,陈德调的意见似更能体现仲由本意。唐宋人诗歌中,亦多取“共敝之”之意,如唐马戴《边馆逢贺秀才诗》云“鹿裘共敝同为客”,张文昌《赠殷山人诗》云“同袍还共敝”,苏轼《戏周正儒坠马诗》“故人共敝亦常情”,可见“共敝”是一种为大家普遍认同且具有圣贤气象的解释。
(二)对《论语集注》释义提出异议
《论语·里仁》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集注》云:“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陈德调则曰:
圣人下字,各有攸当,非若文士之变易求新也。如他处言怀居,此变易怀土。他处言放利喻利,此变言怀惠。夫怀土非怀居比也,怀居者有纵逸自安之意,土则人之所赖以生。先王别五土之宜以利民,故曰“厥心臧”,惟土物爱,怀之不为过分。怀惠又非贪利比也,贪利者有非分争夺之思,惠则人自与我,或出于君上之恩施,或出于朋友之馈遗,怀之,岂尽丧廉?且变惠言利,而以为小人怀利可也,若变怀言贪,而以为君子贪刑,不大笑话乎?盖此君子小人以分位言,犹如士农之别。言君子当怀德,不可如小人之仅怀土也。君子当怀刑,不可如小人之仅怀惠也。德与土皆我之所固有者,刑与惠皆人之加诸我者,故相对成文。①
比较而言,朱熹《论语集注》简洁明了,释义到位,而陈德调的解说似乎透进一层,也更细腻,但未必够得上疑朱,其实是对朱熹诠释的一种引申,起到丰富、补充与发挥作用。
《论语·颜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朱子《集注》:“言文质等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②陈德调曰:
文质两件,自是对待物事可以相胜言,不可以轻重本末言。大抵文一而已,而质有三样:一是质直之质。主内心而言,文质之所从出者也。此是大本,非此不但文有伪,即质亦有伪,《记》所谓“忠信之人可与学礼”是也。一是质干之质。主植基于事先者而言,文质之所由附者也。一是质朴之质。主措施于事物者而言,虽亦从大本而出,然可与文对言,不可与末对言者也。假以一人之身为质干,而文质二者从此附焉。有不衫不履者,有整齐修饰者,不可以不衫不履者为本,整齐修饰者为末也。又以画之粉地为质干,而文质二者从此附焉。有轻描淡写者,有着色渲染者,不可以轻描淡写者为本,着色渲染者为末也。草野之间多简略,冠裳之会盛繁华,不可以草野之间为本,冠裳之会为末也。礼或多之为贵、少之为贵,不可谓少者为本,多者为末也。又有同是礼文之中,而又质之为贵、文之为贵,不可谓贵本而贵末也。以两朝之规模气象言,商尚质,周尚文,不可谓商尚本,周尚末也。以一朝之规模气象言,郁郁乎文哉,不可谓郁郁乎末哉也。其轻重之说,亦即仿是。至若在天为云霞,在地为草木,在人物为须发毛羽,此天然之文质,又是一种。
文质先后之分则有之,而后者较重于前。草衣卉服,衣之始也,今人可以供曳娄乎?茹毛饮血,食之始也,今人可以给饔飱乎?至于明堂清庙之间,太羹玄酒,大辂越席,不过略存一二,以昭原始,其它冠裳带舄、尊斝笾豆、羽籥琴瑟,非极情致文不足以将诚敬而鬼神亦不之享,由此观之,文重乎,质重乎?①
陈德调此论,仍是从毛奇龄而来。《四书改错》云:“《礼》凡言文质,只是质朴与文饰两相对待之辞,并无曰质是本,文是末者。……向使质是忠信,则文不当胜忠信;文是礼,则质又不当胜礼。相胜且不可,何况相去?朱氏既引杨说,于《质胜章》疑为质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错,而此竟直称质为本,文为末,则错认假逢丑父为真齐顷公矣。”②陈德调说:“文质两件,自是对待物事可以相胜言,不可以轻重本末言。”这显然是对毛奇龄的继承,但他通过对“质有三样”的类型分析,然后再来谈文质之关系,却是《论语》诠释史上能够把这个老问题讲清楚的人。
《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朱熹《集注》云:“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盖圣人于此,非作意而为之,但尽其道而已。尹氏曰:‘圣人处己为人,其心一致,无不尽其诚故也。有志于学者,求圣人之心,于斯亦可见矣。’范氏曰:‘圣人不侮鳏寡,不虐无告,可见于此。推之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矣。’”陈德调曰:
师冕,瞽者,非能贸贸然升夫子之阶,登夫子之席也。其自未入门以前,一路便有相者,何待升阶入席而始赖夫子之告?如谓相者告之,夫子又从而告之,则一堂嘈杂,成何体统。抑知瞽目之人,每到一处,惴惴然惟恐其失仪,夫子曲体之,故于其及阶也,不待相者之告而遽告之,曰:“阶也。”其及席也,不待相者之告而遽告之,曰:“席也。”其一片肫诚,俱在无意中流出。迨闻子张问,又不便明言其故,姑应之曰:“固相师之道也。”然而斯道也,非夫子则莫能尽矣。
陈德调的理解,相对而言更能设身处地,还原当时实际情景。尤其是说孔子每到一处,抢在相者之前而遽告之,这等诚敬之心,自然让人感慕于千载之上。当子张问起“与师言之道与”?孔子不过轻描淡写回以“固相师之道也”。其平常自然如此。陈德调对此章的体味,既合乎人之常情,又贴近圣人之心,较之前注,可谓略胜一层。
(三)对《论语集注》古今人物评价提出异议
《论语·公冶长》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朱熹《集注》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称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其介如此,宜若无所容矣;然其所恶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①陈德调则曰:
此当与孟子之言参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其言皆从恶恶正面极力形容。圣人却把他不见有恶时翻转一看,觉更清到极处。“怨是用希”,为不善学夷、齐者进一良方,其实夷、齐意中一概不计。“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窃谓群圣皆可以量言,惟夷、齐不可以量言。盖夷、齐心头譬如一面实镜,本无尘滓,自然些子难容,及既脱去,仍是一片空明,含容宽恕,概无所用。②
朱熹对《孟子》的引用,重在一个“介”字,但即使如夷、齐有如此之介,仍对所恶之人,保持适度的宽容,因此别人对他们也“怨是用希”。朱熹对“怨是用希”的解释,立足于他人对夷、齐之态度与评价,着眼于日常层面,从人之常情道来。而陈德调对《孟子》的引用,则重在一个“清”字,立足于圣人的自我完善,意若对旧恶,一概不计,则我之心中自无怨恨可言。陈德调此处发明,其实是对明代林希元之说的发挥。旧恶,就是夙怨。不念旧恶,就是不念旧仇。林希元《四书存疑》中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盖所恶者,恶其恶也,非恶其人也。因其自取,非出于有心也。若恶其人而出于有心,则追念不忘矣。”①陈德调所谓“夷、齐心头譬如一面实镜”,与林希元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似乎相同,所不同者陈德调比林希元对圣人明心见性的发挥更为彻底。林希元的圣人心如明镜止水,其恶虽出于无心,但仍是有恶的;而陈德调的圣人之心“本无尘滓,自然些子难容,及既脱去,仍是一片空明,含容宽恕,概无所用”。本来无怨,何生怨心?干净彻底,不落一点尘埃。
《论语·宪问》:“如其仁,如其仁。”朱子《集注》:“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②陈德调曰:
按:夫子满口许管仲之仁。《注》言:“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则是在外者一仁,而在内者又一仁也。然则有大不仁者于此曰:“吾虽无仁人之事,而固有仁人之心矣。”可乎?③
照陈德调理解,仁无分内外,故不可将仁心与事功折解。如果说管仲未得为仁人,则其事功就未必合乎仁道。管仲为霸者之佐,自始至终事业不过以力借仁而已。孔子所言“如其仁”可能就不是朱熹《集注》说的“深许之”之意了。《论语》其他地方涉及管仲,孔子但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按陈德调的意思,《集注》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与事功为二,这是很容易产生逻辑上漏洞的。
(四)对《论语集注》释礼提出异议
《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朱子《集注》云:“南子,卫灵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卫,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故不悦。矢,誓也。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谓不合于礼,不由其道也。厌,弃绝也。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①陈德调曰:
《注》:“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毛西河谓其于礼文无据,而究未明子路所以不说之故。盖此与主颜仇由为一时事。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孔子曰:“有命。”进以礼,退以义。今又去见南子,则仍是非礼之进,与主弥子何异?故子路不说,而非谓小君无可见之礼也。“否”字,亦跟弥子来,盖主弥子,夫子之所否者。今见南子,人亦疑夫子为否,故誓言以明之。“予所否者”,古者誓词多用所字打头,如“所不与舅氏者”之类。“天厌之,天厌之”,言若予所否者,则天应早绝我,复何能行道于天下哉?从古宵小多托名流以自重。弥子不得于已则假南子以要之,南子之请见,亦必挟君命先之,故不得不见。要之,圣人道大德宏,其所见者即是圣人之礼,何必于礼外求礼哉?②
在《论语》里,子见南子是一件很令后儒困惑的事情,也是《论语》里获得注释最多的章节之一。前人注释归纳起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子见南子是否合礼,二是子路为何不悦,三是孔子解释表达了什么。朱熹之前,何晏《集解》综合孔安国等的意思,认为孔子之见南子,乃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欲因而说灵公使行治道”。“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个比较合乎常情的解释。朱熹《集注》所言“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引来清初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的反驳,他说:“古并无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遍考诸《礼》文及汉晋唐诸儒言礼者,亦并无此说,惊怪甚久。及观《大全》载朱氏《或问》,竟自言是于《礼》无所见,则明白杜撰矣。”③但朱熹用一“盖”字,有推测之意,不可作定论。而陈德调的意思是,对于孔子之见南子一事,应与子见弥子一事作同样看待,且二者之间还有联系。他认为子见南子一事乃因弥子引起,弥子假南子以要之,南子又挟君命以先之,孔子不得不见。既是不得不见,则与合礼或不合礼无涉,故不必于礼外求礼。言下之意,子路不悦者,其实是凭己之力来衡量圣人的“道大德宏”,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要之,这其实不就是朱熹所谓“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吗?当然,陈德调最终要表达的是,朱熹完全用不着虚构一个合乎古礼来为孔子开脱,因为圣人怎么着都是有其道理的。
(五)对《论语集注》道学之论提出异议
《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朱子《集注》云:“尹氏曰:‘用舍无与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颜子几于圣人,故亦能之。’”①陈德调曰:
不是用则行,舍则藏。不是用我则行,舍我则藏。两“之”字,俱有真实经济。以颜子言之,定是四代礼乐言用之,则把许多经济一齐展布出去而行之,不是空行。舍之,则把许多经济敛藏有待而藏之,不是空藏。这个本领,惟我许尔有是夫。与,犹许也。惟之为言独也。独我许尔,言他人不能知也。子路疑颜子文事有余而武备不足,故以行军为问。岂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正惟颜子优为。乃知平日所藏,无所不有也。前后三“与”字,一气相应。②
自来对“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解释,认为惟孔子和颜渊可以做到,而能做到者便是圣人。圣人的标准是知进退存亡,乐天知命。但陈德调则立足于两“之”字内涵分析,认为“俱有真实经济”,不是空行,也不是空藏,即是说圣人也有真本领,而非只会玩假动作。前者解释是心性之学范畴,后者则是事功之学了。所以,接下来针对朱熹引谢氏语,陈德调更是以事功之学直接来驳心性之学了。
《论语·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朱子《集注》曰:“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谢氏曰:‘圣人于行藏之间,无意无必。其行非贪位,其藏非独善也。若有欲心,则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颜子可以与于此。子路虽非有欲心者,然未能无固必也,至以行三军为问,则其论益卑矣。’”①而陈德调曰:
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呜呼!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子论政,足食兼以足兵;朝廷设官司徒,不废司马;禹敷文命,而有三苗之征;惟师尚父,而膺燮伐之任,岂尽卑耶?且孔子不与子路,则所与者,必仍属颜子。岂颜子亦卑耶?嗟乎!南宋之蹙,已甚矣!忠贞百战者,斧锧一时;高谈游食者,俎豆千古,则其谓之卑也,亦宜。②
朱熹引“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陈德调举南宋困厄之例,反问“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并将谢氏之论斥之为“高谈游食”之言。关于此章的解释,概括而言,也有三种意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心性派,二是以毛奇龄为代表的事功派,三是以周宗建为代表的折中派。毛奇龄说:“行三军非细事,自神农伐补遂,黄帝伐蚩尤而后,行军皆圣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于《师卦》曰:‘开国承家。’又曰:‘可以王矣。’未尝卑也。况临事而惧,正夫子慎战之意。好谋而成,正夫子我战则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语,并不贬抑,而读其书者反从而鄙夷之,可乎?”③显然,陈德调的意见是从毛奇龄而来。第三种折中派意见,周宗建《论语商》云:“大抵圣贤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不作两橛,故以此出处则舒卷无心,绝不著些豪意见。以此任事,则锋镝消除,绝不露一豪气。子路三军一问,色相炽然,故夫子把经世大机局点化之,亦正欲其体认到里面去也。临事二语,此是千古圣人兢兢业业之心肠。”④如此看来,周宗建是能把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综合加以解说的学者。
《论语·先进》“莫春者”至末节,朱子《集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乎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者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①陈德调曰:
此节内外,《注》直说到天地同流、尧舜气象上去。窃以为,圣学不空言气象也。且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点盖谓三子各有用世之撰矣,既究竟知我何人,用我何日,点则不预言,撰亦并不待人知。现在春服可服则服之,童冠可与则与之,舞雩沂水可风浴则风浴之。倘异日知我有人,亦且再作理会,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然已不觉将夫子不怨不尤心事信口道破,故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若夫以泉石啸傲为清高,贤劳鞅掌为多事,此西晋祖尚玄虚之习,为吾儒所痛疾者,岂圣人所乐与哉?又以为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迥不侔矣,尤所未晓。……说此章者,能将开首“不吾知也”及“如或知尔”句,眼光牢注,便是善读书人。点虽狂士,既受夫子之裁,何至一味空狂毫无实际。“不吾知也”,自必数点于诸贤之中;“如或知尔”,岂能推点于诸贤之外?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首节记诸贤之侍坐,如许多才而使之邱壑终老,为诸贤惜,正为自身惜也。“则何以哉”,不是忧其无具,正欲把各色珍宝大家展玩一番。吾故谓此章,头一个悲者夫子,第二个悲者曾点,第三个悲者子路。②
《论语·先进》此章,历来解释基本上也是两种意见。一是以朱熹《集注》为代表,从圣人气象上去说。当然,朱熹《集注》实际上也是承皇《疏》、韩愈、程子而来,并有所取。二是以黄震、杨慎为代表,从“答问之正”角度去说。黄震《黄氏日抄》云:“三子言为国之事,皆答问之正也。曾皙,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之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归咏之言,若有触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晳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黄震还批评有些学者过度诠释孔子的意思,他说:“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以曾晳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晳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①“谈禅”已经是很严重的用词了。明代杨慎《升庵全集》也说:“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语,《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后来陈澧《东塾读书记》亦云:“此则程、朱之说亦有未安。”②顺着黄震的思路,而陈德调甚至干脆说:“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但他说曾点之言,“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则又多少有些误解了。可是,他从心理学角度说:“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仍为体贴之言。
三、陈德调《读古本大学》的即知即行说
陈德调还有《读古本大学》一卷。古本《大学》其实是王阳明所提倡的,朱熹在为《大学》做集注时,有感于《大学》脱简,做了补文,引起后世很多的议论。这里陈德调标明读的是古本《大学》,其意当然是要区分朱熹的补本《大学》。
陈德调的思想里本来重视经济事功,因此他读古本《大学》一开始就希望找到“力行之事”安在?他说:
圣学最重力行,今观《大学》一书,八条目,十大传,概无及于行者,格致只是考究功夫,心意都在腔子里,修身功夫便在格致诚正上,齐治平不过举而措之之事。朱子又云:“自致而诚而正至治平,皆从一知,直推到底。”然则《大学》力行之事,究竟安在?及吾读“物有本末”注,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而经文“自天子至于庶人”节,则又以修身为本,齐治平为末,意窃疑之。又读“明明德于天下”节,自致治以上皆以先后言,独于格物事不曰“先”而曰“在”,意又疑之。后读古本《大学》疏:“明明德者,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乃知明德之事,即在修身上见。又经文于“其本乱”节下,即紧接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始恍然曰:“《大学》力行之事有在矣,格物是也。”①
陈德调认为,格物即由行以得知,而非空言穷理。他把人之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天然自得之知,即孩提知爱,少长知敬之类;二是先事而求之知,即博稽古今、参考异同、研求事理、殚精极微的穷理,这虽属于圣学之开途,但其功却尚属虚位;三是及之而知之知,此则是知之至者,如人欲为忠,必向臣道上亲切去做而忠之理始明;欲为孝,必向子道上亲切去做而孝之理始出。但对这三种知的获得,必须通过格物这一路径。他说:“格,至也,来也。”(古本《大学》训格为来)谓即其物之来至我的面前,然后躬亲其境,躬践其事,如此方可究事物之理。其云:
譬之适千里者,良知者生而东西南北知所方向;穷理者详考舆地经、道里志,询之往来素熟,纵极周到究之,仍属恍恍;格物者束装裹粮,启行戒道,行十里知十里,行百里知百里,及其既至,而一切所历之山川景物,关津险隘,按之舆经地志、人物传说者,一一信其不谬焉,此物格而后知至之说也。②
一个人倘若要行千里之路,如果凭借良知在先,他也许本能地知道大的方向;如果凭借穷理得到的文献知识,即使周到细致,仍然不免与现实隔膜;但如果采取格物者的姿态,且行且知,便是知行合一了。但这样一来,便有人提出知行的先后问题,陈德调如何解释呢?
或曰:学者先知而后行。子之说,不先行而后知乎?曰:吾固言之矣。穷理者,学问思辨之事,圣学之开途也。格物者,笃行之事,造道之实功也。功实,斯知亦实矣。且夫圣人之教人也,其自弟子之入孝出悌,信言谨行,莫非真切从事,而学文游艺,亲师近友,随时随地而考证焉。即行即知,即知即行,岂若后世之判分两事哉。①
传统观点是将知行判分两事,拆开来讲,陈德调则合起来了。既然知行不可拆解,那么内外、心身也就同样不能分作两开。看他如何解释:
又曰:《大学》由知、由意、由心而次以及于身事,皆自内以及外。子之说,不几自外而及内乎?曰:是不然也。理从内出,功从外入,且人自把许多条目看得七头八脑耳。自内言之,为知、为意、为心,其实只是一个心;自外言之,为身、为家、为国、为天下,其实只重一个身。合心与身而言之,为内、为外,其实只完得一个身。身即是物,修只是格,故孔子言躬行君子,孟子言修身立命,而《中庸》《九经》亦起于修身而不必更及于心者,言身则心、意、知并运乎其中,而不能把内与外划然分作两开也。②
儒者之所以要严别内外的同时还要重内轻外,是因为内不可假,而外则可假。但在陈德调看来恰好相反,倘若外假,人人得见;而内假则诚伪,便滑入二氏之学。
且儒者之所重内而轻外者,以为外可假,而内不可假耳。吾谓内可假,而外不可假,外则行迹显著,无从遮饰,彼假于声音笑貌之间者,仍是假其内耳。然其内自假,而其声音笑貌则仍然不假也。据其实在之声音笑貌而悉心印证之,斯其人之诚伪可得而见,此物格知至之说也。虚摹一声音笑貌之象于意中,谓可得其人之诚伪者,是刻舟求剑,即今之所谓即物穷理者也。然则以探幽索渺为致知,闭门枯坐为慎独,凭空把持为正心,又以为心坎头光光然亮亮然,怀着个明德在内者,是所谓如光灿灿如圆陀陀,二氏之学非吾儒之学也。夫二氏之学,假之大者也。③
即行即知,内外无别,照这个逻辑,则明、修亦可相通了。因此,修身之事自然就是明德之事,不必一番功夫分两番做,其云:
明德之事,只在修身上见。古注可据,而人或骇为创闻。窃意人生有个身,便有一个心,心为五官之一本,一气相通者也。内心具个德,本来自明者也。特德不自明,必接于身而后明,犹火不自明,必接于薪而后明,非不知薪之明由火之明也,而非薪则无以丽其明矣。又如一株树,德存乎根本而明见乎枝叶,非不知枝叶之明由根本之明也,而非枝叶则无以验其明矣。盖枝叶者,即根本之菁华也。是以《大学》自格致诚正以下,但言修身之事,而不复言明德之事,显知明与修之初非两事也。若既格致诚正以修其身,又复格致诚正以明其德,不特一番功夫分两番做,八条目不增九乎?①
按照行即知、内即外、明即修的推理一路下去,很显然身、家、国、天下也是一理,能够打通这四者,在陈德调看来便是“格物致知之极也”。其云:
身与家、国、天下虽然只是一理,要必就自身之物深造至极,则身之知至而其道可通于家,就自家之物深造至极,则家之知至而其道可通于国与天下。然所云可通者,谓知不虚知,则可由此以达彼,而仍不能执此以为彼也。又须到有国与天下之责,然后能格,然后能致焉,何则?身家者,一人之身家;国与天下者,合国与天下之身家以为身家也。夫合国与天下之身家以为身家,则合国与天下之物以为格,自必合国与天下之知以为致。(平天下章实是最重用人)陈殷置辅,大纲小纪,一人端冕于上,百司承职于下,公好恶,存忠信,有先慎乎德之修,无以财发身之患,夫是以重离继照,旁烛无疆,臻治平之有象也。此格物致知之极也。②
即行即知等观点,并不是陈德调的发明,此前王守仁就已经提出来过。黄宗羲说王守仁讲“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①。但据陈德调自述,这些见解其实是他自悟得来,只是与王守仁暗合。他说:
今戊戌(继按:道光戊戌,1838年)春,读王阳明先生集,有知行并进之说,自维鄙见颇觉相似。又其言格物则必兼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尝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其言亦与鄙见稍异而大同。②
照陈德调的自述,他对阳明学的接触,其实是很晚的事情。因此,他的即知即行观完全是自悟得来,恰好与阳明合辙,实属不易。故黄侗慨叹“梅鼎先生朝餐苜蓿,夕拥青氈,以冷官终其身”,“所言即知即行之旨,与姚江不谋而合,则其有功于圣门或亦不在阳明下欤”③。这便是历代无数基层学者的一个典型写照。
综上,陈德调虽不是知名学者,但其敢于疑朱的精神却与清初毛奇龄相接;而即知即行见解的提出,又与王阳明暗合,透过他可以了解当时浙东理学界基层学者的思想活力。与主流学者相比,陈德调《我疑录》和《读古本大学》的存在,仿佛朱子学史上的一个“民间故事”,但这绝非个案。随着笔者对浙江历代朱子学文献的不断挖掘,一批原来未曾纳入研究视野的相关论著逐渐浮出水面,细读之后,发现它们大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这些著述遗存,让我们看到当时基层理学界所谓的“弱势力”,是如何企图刷新权威见解,从而无意间促成了理学界强弱之间对话结构的形成、主流与非主流互动图景的诞生。我们认为,未来朱子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历史上那些基层学者的思想成果,以及层次丰富的朱子学生态史的各个立面与细节。
附注
*作者简介:程继红,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②严辰:《(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三,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85页。
①参见张杰、肖永明:《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载《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2期。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①潘德舆:《养一斋集》卷十八《任东涧先生集序》,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②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③李元春:《时斋文集初刻》卷二《学术是非论》,清道光四年刻本。
④晚清理学复兴原因,参考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第一章“晚清理学兴衰概述”,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9页。
①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二百三《诸儒学案》九《宗先生稷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876页。
②参见黄侗《陈德调小传》,载《我疑录》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
①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公冶长第五》,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②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2—3页。
③《白虎通》与张载之说,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公冶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4页。
①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1页。
②朱熹:《论语集注》卷六《颜渊第十二》,《朱子全书》第6册,第171页。
①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9—10页。
②毛奇龄:《四书改错》驳朱熹之说,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四《颜渊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4页。
①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公冶长第五》,《朱子全书》第6册,第106页。
②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2页。
①林希元:《四书存疑》之说,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公冶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6页。
②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宪问第十四》,《朱子全书》第6册,第192页。
③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11页。
①朱熹:《论语集注》卷三《雍也第六》,《朱子全书》第6册,第117页。
②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3—4页。
③毛奇龄:《四书改错》驳朱熹之说,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二《雍也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4页。
①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第七》,《朱子全书》第6册,第122页。
②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4页。
①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第七》,《朱子全书》第6册,第122—123页。
②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4页。
③毛奇龄:《四书改错》驳朱熹之说,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二《雍也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3页。
④周宗建:《论语商》,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二《雍也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2页。
①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先进第十一》,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66页。
②陈德调:《我疑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8—9页。
①黄震:《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张伟等主编《黄震全集》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②杨慎、陈澧等说,俱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三《先进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12—813页。
①陈德调:《读古本大学·自述》,《读古本大学》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1页。
②陈德调:《读古本大学·自述》,《读古本大学》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1页。
①陈德调:《读古本大学·自述》,《读古本大学》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2页。
②陈德调:《读古本大学·自述》,《读古本大学》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2页。
③陈德调:《读古本大学·自述》,《读古本大学》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2页。
①陈德调:《读古本大学·自述》,《读古本大学》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2—3页。
②陈德调:《读古本大学·自述》,《读古本大学》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1—2页。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王阳明守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页。
②陈德调:《读古本大学·自述》,《读古本大学》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第3页。
③黄侗:《我疑录序》,载《我疑录》卷首,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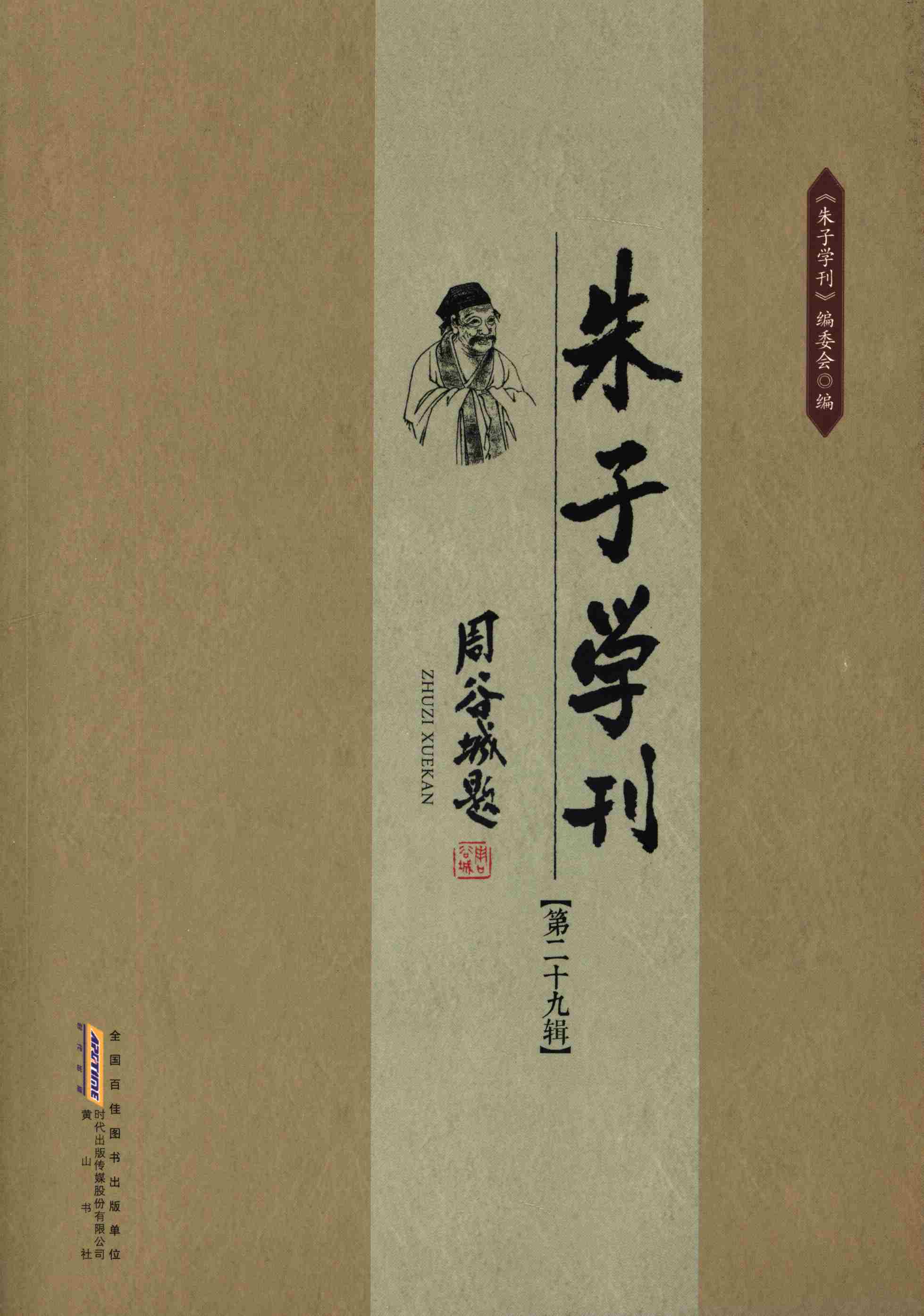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